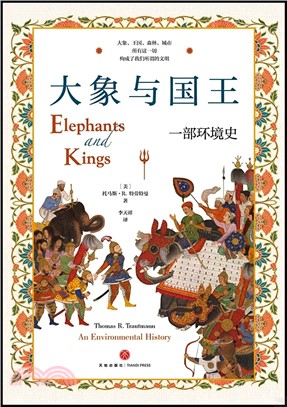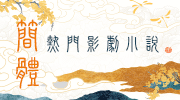大象與國王:一部環境史(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545576726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作者:(美)托馬斯‧特勞特曼
出版日:2023/11/01
裝訂/頁數:精裝/420頁
規格:21cm*14.5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大象龐大而莊嚴,從王權誕生之日起就是國王無法抗拒的尊貴象徵。各個早期文明已存在馴養大象的現象,如埃及、亞述、美索不達米亞、中國,以及印度河流域。在這些地方,大象的主要用途是王室祭品和狩獵物件。然而,托馬斯·特勞特曼在南亞次大陸發現了特殊的用象制度,這一制度保護了它們的棲息地和種群數量:那就是戰象。
以恒河流域為起點,戰象的足跡逐漸遍布南亞,同時向西傳播至波斯、敘利亞、埃及、迦太基、希臘和羅馬,向東傳播至中南半島、爪哇島和印度尼西亞的其他地區。托馬斯·特勞特曼追溯了戰象的緣起、傳播路徑和文化遺存,描繪了一幅跨越了3000年的文化圖景。
為了維持這個獨特的制度,國王必須保護野生大象免受獵人的覬覦,也要保護大象棲息的森林不被砍伐,還要維護與森林民族的關係。因此,國王與大象的關係,實際上是國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間的四角關係——這是一個豐富且複雜的關係網。所有這一切,構成了我們所謂的文明。
19世紀,隨著英國人到來並統治南亞的絕大部分地區,人口數量暴增,獵象成為一項運動。戰象制度退出歷史舞臺,大象的分布範圍隨之縮小,種群數量也急劇減少。這一切都在時刻提醒著:我們需要找到方法來保護自己的未來,並在此過程中保護與我們共存的生物的未來。
作者簡介
托馬斯·R.特勞特曼(Thomas R.Trautmann),美國歷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密歇根大學歷史與人類學榮休教授,曾任密歇根大學歷史系主任和南亞研究中心主任。1997-2006年擔任《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主編。著有《印度次大陸:文明五千年》《語言與國家》《雅利安人與英屬印度》。
特勞特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印度歷史、人類學史和其他相關學科,尤其專精古印度梵語論典。他還撰寫了有關印度達羅毗荼人親屬關係和美國印第安人親屬關係的大部頭著作。特勞特曼常年在密歇根大學為本科生開設印度文明史通識課、專題課,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擅長用通俗淺顯的方式講授印度文明史專業知識。
名人/編輯推薦
托馬斯·特勞特曼是著名的印度學家和世界歷史學家。他在堅實的印度學基礎上開辟了世界環境歷史的新視野。李天祥把這本重要學術著作用通俗優雅的譯文介紹給中文讀者,使得讀者思考象這個雄偉的動物和人類社會特別是統治者交往的過程。戰象和戰馬在世界的政治軍事史上不可或缺。而象在被役使的同時,由於人類的開發和自然環境的變化,被迫節節讓出自己的生存空間。這本書的出版會使中文讀者對南亞以及世界的歷史進程感到耳目一新。
——劉欣如 美國新澤西大學歷史系教授
《大象與國王》一書以宏觀視角探討大象在南亞、東南亞、東亞、西亞、北非以及部分歐洲地區被利用的歷史,將涉及大象的自然史與人類史有機地融合起來,剖析了國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間的多重關係,體現了環境史上下求索的創新精神,值得重視。
——梅雪芹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象的退卻》譯者
★一段跨越3000年、橫跨亞非歐的戰象制度文明
戰象制度開始於公元前1000年的北印度,終結於英國人在印度建立殖民統治的18世紀。以恒河流域為起點,戰象的足跡逐漸遍布南亞,同時向西傳播至波斯、敘利亞、埃及、迦太基、希臘和羅馬,向東傳播至中南半島、爪哇島和印度尼西亞其他地區。亞歷山大大帝曾在印度與戰象搏斗,漢尼拔也曾驅趕戰象跨越阿爾卑斯山。
★密歇根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文化史力作,運用豐富的文獻史料與文物遺存
盡管已經消亡,但戰象形象仍以史詩、國際象棋、節日慶典等難以察覺的方式,活躍在我們身邊。作者托馬斯·特勞特曼,依據豐富的文獻史料與文物遺存,結合其專精的漢語、梵語等古代文獻,分析戰象的文化史意義。本書內附大量文物圖片與示意地圖,無論對歷史學者還是普通大眾都極具參考價值與閱讀趣味。
★中國獨特的大象文化記憶
中國從戰國時期就在戰場上遭遇戰象,到了明朝也依然有來自越南進貢的戰象,但中國從未形成戰象文化。在我們的文化體系中,大象有著怎樣的位置?甲骨文和青銅器上的象是什麼形態?舜帝、周公、孫武和大象有著怎樣的故事?諸多問題等待著發現與解答。
★文明之問:動物如何與人類共存
時至今日,人象矛盾仍然不時出現在新聞中。本書作者指出,人口數量的增長是一個長期問題: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取得了災難性的成功。我們需要找到方法保護自己的未來,並在此過程中保護與我們共存的生物的未來。
序
序 言
西蒙·迪格比(Simon Digby,1971)的著作《德裡蘇丹國的戰馬與大象:軍用物資研究》(War-Horse and Eelephant in the Dehli Sultanate:A Study of Military Supplies)是我的最愛,也是學生們的最愛。他們從我這裡借閱副本後都忘了歸還。誰又能責怪他們呢?畢竟,這部著作有令人手不釋卷的力量。
這部不朽的著作展示了德裡蘇丹國在恒河谷和印度河谷之間占據的戰略位置,以及其歷代國王對馬匹東進和大象西出所擁有的控制能力——這正是北印度其他王國的劣勢。這部書使我了解到印度諸國王在軍事供給制度上的長遠構建。根據迪格比書中所述,此一制度可向前追溯至兩千年前,延續至大約公元1000年,此時制度已發展得更為完善。在迪格比完成他眾多著作中的這部《德裡蘇丹國的戰馬與大象:軍用物資研究》後,我才意識到麥加斯梯尼(Megasthenes)相關記述的重要性:孔雀王朝的皇帝壟斷著馬匹、大象和軍隊。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裡,我都未注意到這一點。這一點與吠陀時代截然不同——可以很確定,在吠陀時期,馬匹、大象和軍隊屬於武士階層私人所有。這種對比表明,孔雀王朝軍隊的力量和制度創新超過當時印度的其他邦國,正因如此,它成功地創建了第一個印度帝國。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正確理解斯特拉博(Strabo)的記述。斯特拉博說,那些記述印度的希臘作家都是騙子,因為他們所記述的內容互相矛盾。麥加斯梯尼對孔雀王朝的記述就與尼阿庫斯(Nearchus)的說法相左。在尼阿庫斯有關印度的記述中,大象和馬匹為私人所有,並且人們會從事一些與役畜或動物馱運相關的工作。斯特拉博沒有認識到,麥加斯梯尼所描述的是以恒河谷為中心的孔雀王朝東部區域,在該區域實行著與別處相異的政策,即國家壟斷戰爭資源;而尼阿庫斯記述的,則是一種存在於吠陀時代晚期的實行私人所有制的政權,這種古老的制度產生於印度西北地區,即印度河谷一帶。我相信,只要人們認識到這一點,有關印度的不同記述之間的矛盾就會消失。我的這一觀點已經發表在《大象和孔雀王朝》(Elephants and the Mauryas,1982)一文中。
可以肯定,這篇文章並不是結束,關於大象和馬還有很多可論述的內容——特別是大象和印度王權之間的關係。我一直收集著自己偶然發現的資料,如有關象學的梵語文稿、英屬印度時期關於大象管理和保護的文獻、阿爾曼迪(Armandi)的早期著作《大象的戰爭史》(Histoire militaire des éléphant,1974),以及斯卡拉德(Scullard)的《希臘羅馬世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在這篇文章中,斯卡拉德做出了重要且嚴謹的記述。我曾有幸參加已故的著名大象生物學家杰斯克爾·紹沙尼(Jeheskel Shoshani)舉辦的一日研討會,當時他還在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任教。我加入了美國哺乳動物協會的大象權益組織,方便獲得杰斯克爾·紹沙尼編輯的刊物。我一直想撰寫一部關於大象與王權以及大象作為軍用物資問題的作品。該書構思良久,並帶有一種深刻的、始終吸引著我的歷史觀。
多年來我一直忙於其他事務,如今這本關於大象的書終於被提上日程,成為首要的工作。就在那一刻,我無意中發現了文煥然(Wen Huanran)的著作。該書論述了中國野生大象和其他動物的分布,以及從古至今中國文獻中這些動物消退和滅絕各階段的記錄。而我了解到文煥然的這部著作,則得益於另一位作家伊懋可(Mark Elvin)的著作《大象的退卻》(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2004)。這是一部優秀的中國環境史著作。該書認為,大象生存範圍之所以縮小,是因為中國王權勢力和農業範圍在不斷擴大。這兩部著作向我揭示了這樣一個觀點:雖然我所論述的主題只是軍需問題的一方面,但是卻具有環境史的深刻背景。根據伊懋可和文煥然的觀點,我確定了本書的研究方向:印度王權與森林及其中“居民”的關係,尤其是與生活在森林中的人和大象之間的關係。很顯然,在土地使用和動物馴化方面將中國與印度進行比較,能夠說明印度王權與森林之間的獨特關係。
書的著成受益於以下的文獻。拉曼·蘇庫馬爾(Raman Sukumar)的著作有力地推動了本書的完成。拉曼·蘇庫馬爾一生致力於研究亞洲象的生理、環境和行為,他也因此成為該領域的首席專家。其處女作《亞洲象:生態與管理》(The Asian Elephant:Ecology and Management,1989)是他以南印度的田野工作為基礎撰寫的專題著作。這部著作極大拓展了人們對野生大象的認識。同時,殖民時代的相關著作也提供了相關知識。另外,蘇庫馬爾的最新著作《亞洲大象的歷史》(The Story of Asia’s Elephants,2011),將人類歷史中有關亞洲象的內容進行了大量概述。《亞洲象:生態與管理》是我撰寫野生大象生理和行為的標桿與參考。而《亞洲大象的歷史》對相關問題已經作了全面探討,使得我能夠進行更為專門的研究,可以聚焦問題的核心,而無須處理次要的枝節。
本書的問世還得益於很多朋友的幫助。
羅賓斯·比爾林(Robbins Burling)是我的第一位讀者,他跟我一樣都相信:在出版前直言不諱的批評能夠體現真摯的友誼。
因為本書的主題與我擅長的領域相去甚遠,所以我很樂於從我所了解並欽佩的學者那裡獲取相關的專業知識。這些學者包括:約翰·貝恩斯(John Baines)、雅內特·裡卡茲(Janet Richards)和薩利馬·依克拉姆(Salima Ikram)有關古埃及的研究;彼得·米哈沃夫斯基(Piotr Michalowsky)有關亞述帝國和兩河流域的研究;邁克爾·哈撒韋(Michael Hathaway,他向我介紹了伊懋可的書)和查爾斯·桑夫特(Charles Sanft)有關中國的研究;央·莫耶(Ian Moyer)和帕特·惠特利(Pat Wheatley)有關亞歷山大和希臘化時代的研究;羅賓斯·比爾林、約翰·惠特莫爾(John Whitmore)、維克托·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和羅伯特·麥金利(Robert McKinley)有關東南亞的研究;拉曼·蘇庫馬爾、蘇倫德拉·瓦爾馬(Surendra Varma)、凱瑟琳·莫裡森(Kathleen Morrison)和素密·古哈(Sumit Guha)有關環境和生態學的研究;蘇倫德拉·瓦爾馬有關圈養大象和象夫的研究;丹尼爾·費希爾(Daniel Fisher)有關大象歷史的研究。我要感謝尤蓬德· 辛格(Upinder Singh)、瓦爾米克·塔帕(Valmik Thapar)、迪維亞巴哈努辛·查夫達
(Divyabhanusinh Chavda)、維波德·帕塔薩拉蒂(Vibodh Parthasarathi)、伊克巴爾·汗(Iqbal Khan)、庫什拉發(Kushlav)和塔拉(Tara)、肯尼斯·霍爾(Kenneth Hall)、吉恩·特勞特曼(Gene Trautmann)在印度和柬埔寨田野考察期間為我提供的幫助。我無法用語言表達對他們所有人的深切感謝。還有我的好朋友西奧多·巴斯卡蘭(Theodore Baskaran)和蒂拉卡(Thilaka),他們一直以來慷慨地幫助我,鼓勵我。
本書的某些部分最初是根據演講報告嘗試寫作而成。這些報告會議由以下大學和機構舉辦:位於班加羅爾的印度理工學院生態科學中心(the Centre for Ecological Sciences,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Bangalore)、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的環境歷史組(Environmental History Group,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德裡大學歷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Delhi University)、密歇根大學南亞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outh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奧塔戈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tago)、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市的坎特伯雷大學人類-大象關係研討會(the Symposium on Human-Elephant Relations,University of Canterbury,Christchurch NZ)、威斯康星大學南亞協會(the South Asia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Wisconsin)。非常感謝這些機構,感謝拉曼·蘇庫馬爾、R.德蘇扎(R. D’Souza)、尤蓬德·辛格、法裡納·米爾(Farina Mir)、威爾·斯威特曼(Will Sweetman)、皮爾斯·洛克(Piers Locke)的盛情邀請,讓我獲得發言的機會。
我由衷感謝麗貝卡·格雷普芬(Rebecca Grapevine)。作為我的研究助理,她工作嚴謹,還教會我如何使用電子設備。我特別欣賞麗貝卡在製作“使用大象進行野戰和攻城戰的戰場分布地圖”(見圖6.1)時建立數據庫的工作,這項工作本身就是一場艱難的野戰和持久的攻城戰。妮科爾·朔爾茨(Nicole Scholtz)不吝時間,以專業的知識繪製出4幅地圖的電子版本(見圖1.5、1.6、1.7、6.1)。伊麗莎白·佩馬爾(Elisabeth Paymal)繪製了所有地圖的最終版本。
我的研究由梅隆基金會資助。作為梅隆基金會的名譽研究員,我獲得了來自密歇根大學文學、科學和藝術學院的配套基金,對此我甚為感激。歷史系教工和時任主席杰夫·埃利(Geoff Eley)對我助益尤甚。感謝他們所有人。
我遇到很多幸運之事,其中就包括《永遠的黑色》(Permanent Black)一書的作者魯昆·阿德瓦尼(Rukun Advani)。他以精湛的編輯能力、友好的待人接物方式給予我寶貴的幫助。該項目還得到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戴維·布蘭德(David Brend)的關照,我的幸運也因此翻了一番。
部分情況下我會對引用的古代資料進行轉述,以便更好地表達自己的理解;原始資料可參見《參考文獻》。
目次
導 論
第一章 大象的退卻與留存
印度與中國//004
大象和馬//013
亞洲象//024
問題//047
大象與印度王權
第二章 戰象
理想的戰象//056
國王與大象//073
戰象的發明//100
戰象和森林民族//107
第三章 用途構成:四軍、王室坐騎、作戰陣形
四軍//116
王室坐騎//129
作戰陣形//140
第四章 關於大象的知識
實用性知識//152
象學//155
《政事論》//165
《阿克巴則例》//183
戰象習俗的傳播
第五章 北印度、南印度和斯裡蘭卡
摩揭陀的崛起//198
十六雄國//200
難陀王朝與同時代的情況//204
大象和孔雀王朝//210
南印度//216
斯裡蘭卡//221
第六章 近東、北非和歐洲
阿契美尼德帝國和亞述帝國//234
亞歷山大帝國//240
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244
迦太基//259
希臘和羅馬//263
薩珊王朝//267
伽色尼王朝//274
第七章 東南亞
印度教化的國家、印度化王國、進行印度化的王國//282
進行印度化的王國和大象//286
東南亞的印度史詩//292
神話中的軍隊和現實中的軍隊//298
印度模式的巔峰、終結和來生//309
大象的未來
第八章 維持平衡,展望未來
中國//315
印度和中國的土地倫理//321
戰象時代//329
運木象的短暫盛行//334
大象和民族國家//344
可能的未來//348
注 釋//354
參考文獻//390
譯後記//417
書摘/試閱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世界上野生大象的數量銳減。大象的生存狀況也令人擔憂。
統計野生動物的數量本就十分困難,尤其是大象這樣龐大的動物。而且,統計結果還會受大量不確定因素影響。但是,我們現有的信息十分確定:非洲象的數量依舊是亞洲象的10倍,據估計分別為50萬頭和5萬頭。然而,雖然非洲象的數量遠多於亞洲象,但是因為國際象牙市場的需求刺激了偷獵行為,非洲象的數量也在迅速下降。雖然亞洲象受到當地政府更好的保護,甚至在一些地方,其數量還有所增長,但是高昂的象牙價格仍然威脅著亞洲象的生存。非洲象和亞洲象的未來依賴制度上的持續性舉措,以保護大象免受各種人為因素引起的破壞威脅。野生大象的生存狀況並不確定,這就需要政府采取持續、堅決且有效的措施。現在,野生大象的生存狀況已受到國家的監護。
鑒於這種威脅,盡可能了解大象退卻的原因是很有幫助的。面對將大象推向滅絕的力量,了解大象能夠留存下來的原因可能對我們更有幫助。本書致力於闡述印度地區大象與人類之間的關係,著重論述印度的王權,以及受到印度宮廷用象文化影響的地區,包括北非、西班牙至印度尼西亞,還有這種文化對環境的影響。除此以外,本書還分析了大象當前的處境在過去五千年中是如何形成的。
印度與中國
當討論印度的象文化何時傳播至北非時,非洲象是論述的重點。但我的著眼點在印度,所以本書重點討論亞洲象。首先我們總體概述近代以來亞洲象的數量。不同國家中,大象數量的區間範圍按最高估算數字排序可列表如下(見表1.1)。
目前,印度擁有的亞洲象數量最多,約為3萬頭,而全世界亞洲象總數約為5萬頭。南印度擁有的大象數量最多,主要集中在西高止山(the Western Ghats)的森林中,即泰米爾納德(Tamilnadu)、卡納塔克(Karnataka)和喀拉拉(Kerala)這三個相鄰邦的交界地帶。第二個大象數量集中的區域位於印度東北部一帶,即阿薩姆邦(Assam)和梅加拉亞邦(Meghalaya)。印度大象總數中約有3 500頭是馴化的大象。在南亞,印度的鄰國也擁有一定數量的大象。其中斯裡蘭卡數量最多,不丹、孟加拉國和尼泊爾僅有少量。我們沒有巴基斯坦的報告,但其大象數量如今已微不足道。當然,野生大象沒有國界線的概念,只要地形合適,它們會反復大規模地遷徙。
東南亞各國也存在數量眾多的大象,主要是那些中南半島上的國家,例如緬甸、泰國、馬來西亞、老撾(曾被稱為“南掌”,意思是“萬象之國”)、柬埔寨和越南。人們在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上發現了野生大象,但是有歷史記錄以來爪哇島是否有過野生大象,仍屬未知。在加裡曼丹島 、馬來西亞的沙巴州(Sabah)和印度尼西亞的加裡曼丹省(Kalimantan)也曾發現過野生大象。我們了解到,為了滿足東南亞王國統治者“進行印度化”的需求,中世紀和近代曾經存在過以馴化大象為商品的大規模海上貿易;一直到伊斯蘭教傳入時期,東南亞諸國國王仍對大象采取印度式的使用方式。特別是在1750年,東印度公司向蘇祿(Sulu)國王提供大象,這可能是現在該地區野生大象種群的來源。然而,我們很難將源自海上貿易的野象和當地遙遠歷史中幸存下來的野象區分開來。加裡曼丹島的個案仍有爭議。但是,人們一致同意,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雨林中的大象源自印度,這些大象是馴化大象的野生後代。這些馴服的大象因用於工廠做工而被引入該地,直到1962年這些工廠被廢棄。它們的後代則成為野生大象。
中國在這個名單上十分靠後,擁有200至250頭野生大象。中國的大象主要分布在與緬甸毗鄰的西南山區——云南省;換言之,這裡的大象棲息環境類似於東南亞。中國擁有的大象數量太少了,似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這樣做並不可行,因為有歷史記載以來,整個中國都或多或少發現過野生大象。此外,云南已經成為中國環保主義的中心,率先對大象采取了保護措施。
文煥然將過去七千多年時間裡中國野生大象的分布情況做了詳細記錄,也記錄了大象退卻至云南地區的過程。伊懋可在其論述中國環境史長期情況的權威著作《大象的退卻》(2004)一書中,引用了文煥然的研究成果。這兩部著作對於目前的研究都很重要,因為它們建立了與印度進行比較的參照點。
文煥然這部關於大象的著作從屬於一項更加巨大的工程,即追蹤歷史記載中某些動植物種類的分布變化。他的觀點是,20世紀30年代,人們在河南安陽殷墟中發現大象殘骸,當時認為這些都是引進自東南亞的馴化大象。那時,人們還不知道野生大象曾分布於整個中國。明朝的歷史文獻中有記載,一些來自東南亞諸國王的馴化大象曾被當作貢物敬獻給中國皇帝。這大概就是20世紀30年代人們如此推測的根據。7直到後來,在古生物學和中國古代歷史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前文提及的大象曾在中國分布廣泛的觀點才建立起來。由此,人們才認識到,在過去的幾千年中,野生大象在除云南外的中國各省被逐漸捕殺或驅趕。該事實已然得到充分認可,但還不為中國以外的世界所知曉。
文煥然繪製了中國部分地區大象分布圖。該地圖標注了90個地區的數據點,來表示該地發現了大象遺骸、活象記錄或者兩者兼有(見圖1.1)。根據這些數據點的年代模式,文煥然在地圖上添加了特定時間內野象分布極北區域的邊界線(見圖1.2)。
文煥然還在地圖中用線條簡單呈現了不同時期的大象分布情況;同時也完整地呈現出,直至今日,野生大象都在持續向中國的西南方向退卻,僅有數百頭大象留存在云南一隅。中國的野生大象曾漫步於北緯19°至北緯40°的大地上,但現在其分布範圍的極北值約為北緯25°。
如何解釋大象在中國的退卻?文煥然認為,氣候是首要因素,人類活動也強化了該趨勢,包括毀林耕種和獵取象牙。根據文煥然的觀點,亞洲象進化出了一種特性,它們對周圍環境的變化特別敏感;這主要是因為它們體形龐大,對食物和水有著巨大的需求,但是大象的生殖循環很慢(兩年妊娠期、獨胎、生育間隔較長),並且不耐寒冷。大象的外形極為特殊,它擁有長鼻子、特殊的牙齒結構(其門齒衍變成長牙,且牙齒數量減少,還形成了四顆大型的臼齒)。同時,大象對溫度、陽光、水、食物的要求較高,其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卻相對較低。依據文煥然的研究,雖然可能存在短暫的逆轉期,但是在過去七千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中國氣候變化的總體趨勢是從較溫暖變為寒冷。
這種氣候變遷模式符合野生大象生活範圍的最北值逐漸南移的趨勢。在這個總體南移的大趨勢中,最北值有時會因為一些微小的逆轉而出現波動。從相當長時間跨度的自然史角度看,文煥然將大象在中國退卻的首要原因歸結為氣候變化。然而,人類活動的重要程度僅次於氣候變化,生態破壞導致大象現在處於瀕危狀態。文煥然認為,有史記載以來,無節制的捕捉和獵殺對大象來說是致命的災難。
伊懋可認同這一觀點,同時也認同野生大象在環境史中的特殊地位相當於“礦工的金絲雀” (the miner’s canary)。在其著作開篇,伊懋可就轉載了文煥然繪製的地圖。同時,除了對氣候變化給予了應有的重視,伊懋可更關注人類造成的環境破壞。因此,文煥然的研究指向自然史,伊懋可則更傾向於人類史。
伊懋可聚焦於森林破壞和耕地擴張。他通過豐富的中文資料(包括典籍文獻和官方檔案),極其詳細地追溯了森林破壞和耕地擴張的歷史情況。他分析認為,人類對大象發動了長達三千年的戰爭,而大象是這場戰爭的失敗者。在中國古典文明中,周朝文化中就存在著“普遍針對野生動物的戰爭”。這種觀點過分嗎?查爾斯·桑夫特分析了從秦朝至西漢的法律,其中便有季節性地限制捕捉野生動物、禁止獵殺處於生長期的動物(尤其是在春夏兩季)、在休耕期允許捕獵行為的記載。捕捉小馬駒、幼獸和孕期中的動物,捕食蛋卵,破壞魚鳥巢穴,砍伐樹木,通過放火焚燒草地進行捕獵,這些行為都被禁止。雖然伊懋可清晰地指出,這些管控措施未能有效防止自然被破壞,但是查爾斯·桑夫特認為,它們顯示了保護自然的意圖。這一發現修正了伊懋可的觀點——這場“戰爭”是人類尤其是王室蓄意為之。但是,這並沒有改變伊懋可的總體觀點——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了影響。
在伊懋可的論述中,大象可以充當自然環境總體惡化程度的晴雨表。他從一開始就強調要認清大象退卻的事實。大象是伊懋可整個研究主題的首要物件:自然環境作為一個整體,在中華文明面前處於衰落的狀態。該書將大象的退卻作為論據,進而論證了:人類及其活動造成了中國野生動物普遍面臨生存困境,大象是其中的典型性物種。與大象的戰爭分為三條戰線:第一,砍伐森林用於耕種;第二,消滅或捕捉大象以保護農民的莊稼;第三,狩獵大象以獲得象牙和象肉(象肉被美食家所推崇)、從事戰爭、參與運輸以及舉行典禮儀式。就我閱讀的涉及中國君王與大象關係的證據資料看,使用大象作戰的情況非常少見,似乎只在非漢族群體中有此案例。與印度成熟的戰象文化不同,戰象從未在中國成為一種習俗。
伊懋可查閱了中國歷史、哲學、文學和宗教領域中涉及環境的豐富資料,在其著作中用三個章節來論述這些史料中蘊含的自然觀點和原始環保主義的態度。他的結論是,雖然在中國歷史上卷帙浩繁的文獻記載中,有關環境史的信息資料非常龐大,但其中對自然的敬畏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起到相應的保護作用。這是一個重要且影響廣泛的觀點,值得詳細引用:
最後,本書概述的價值與觀念史顯露出一個問題,不僅影響了我們對中國歷史的理解,而且影響我們對中國環境史的理解。前文考察和翻譯的宗教、哲學、文學和歷史資料,一直都是我們描述、觀察甚至產生靈感的豐富源泉。但是那些主導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彼此之間常常相互矛盾,對於中國的環境實際發生的情況似乎沒有多少解釋力。個別案例確實可以解釋得通,例如:佛教有助於保護寺院周圍的樹木;執法帶來的神秘性籠罩著清皇陵,使周圍環境絲毫沒有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但從總體來看,解釋不通的情況更多。撇開一些細節不談,似乎沒有理由認為,中國的人為環境是由中國人特有的信仰經過三千多年的長期發展和維持所形成的。或者說,中國在自然世界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與權力、利益追求造成的巨大影響,以及在二者互動中產生的技術,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因此,特有的信仰和觀念對中國環境史的影響微乎其微。伊懋可有力地證明了,環境變遷的真正動力是人們對權力和利益的追逐,而這一觀點對研究印度的歷史學者來說有深遠的影響。這些歷史學者參閱的文獻資料大多是由宗教學者著述的。也就是說,如伊懋可的書中所述,把中國的土地使用模式同法國或者書中所說的印度模式相比較,中國的模式看起來就不僅僅在單純地追求權力和利益。如何根據各種需求分配土地似乎才是根本性的選擇或優先考慮的因素;我稱其為土地倫理,它本身是一種占據主導的觀念,盡管文獻中可能呈現出相反的觀點。
我認為,中國和印度在土地倫理問題上最顯著的差異並不是在文學、哲學或宗教觀念上,而是在君王與大象的關係上。具體說來,印度諸王國和東南亞進行印度化的各王國都會捕捉野象,訓練它們作戰,然而使用大象作戰的制度卻從未扎根於中國。實際情況是,雖然中國的君王曾經接觸過運用大象的戰爭,但是他們拒絕將其作為戰爭手段。就此問題對中國和印度進行比較需要考察諸多差異;例如,中國的種植農業極度依賴大量勞動力,而印度的農業則依賴於家養馴化動物和放牧畜牧動物。我們可以用戰象的歷史進一步解釋中印之間的不同:一方面,大象在中國大規模地退卻;另一方面,近代以來印度和東南亞的野象盡管也在大規模地退卻,但卻留存了下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