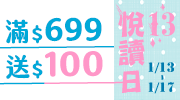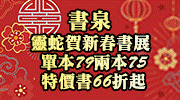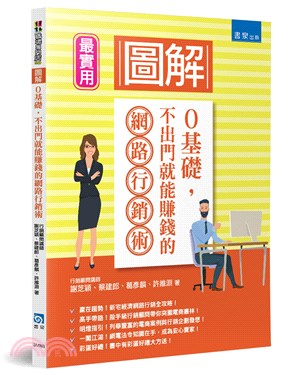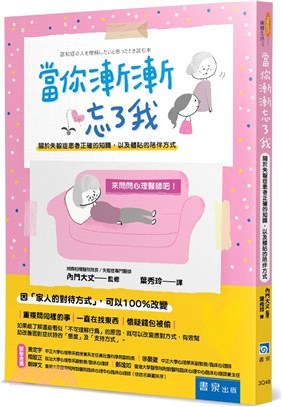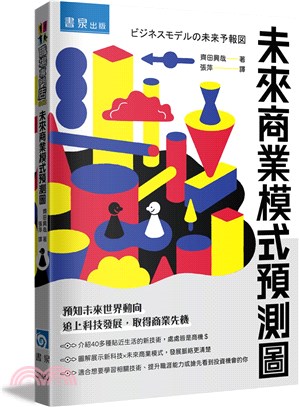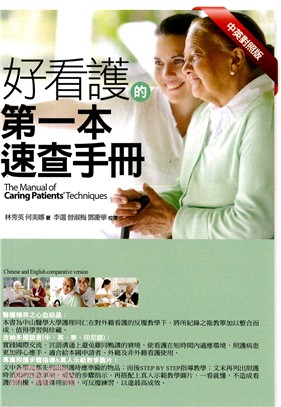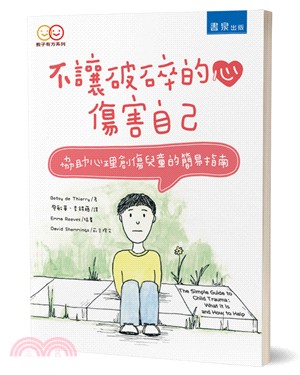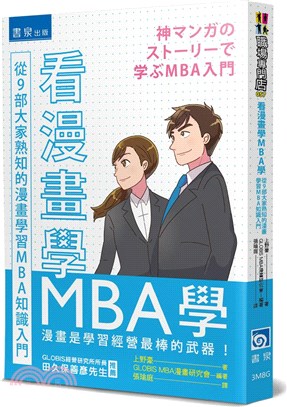念人憶事(電子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他雖曾為文談赤足之美,但他絕不赤足穿拖鞋或穿睡衣來接見客人的。而他當時要作這樣的振作,也已經是一種很大的負擔了。我自從慶祝他八十歲壽辰後,就沒有見過他。一直到在報上見到他病逝的消息,才打電話去問,以後在殯儀館裡對他致最後的敬禮,我心中除了悲傷以外,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觸。──〈追思林語堂先生〉
§ 海派文學宗師,徐訏經典重現
§ 收錄鬼才徐訏26篇念故人、憶舊事的短篇散文
§ 觀察深刻入微、筆法精闢理性,帶領讀者認識不同角度的民國名人
富有「文壇鬼才」美譽的徐訏,以愛情為題材、深入剖析人性的小說最為人所熟知,然而文學界對其散文與論文亦有不錯的評價,盛讚他的文章理性而深刻,充分展現本身深厚的哲學底蘊。本書收錄徐訏26篇念故人、憶舊事的短篇散文,按記述對象的出生年份排序,與徐訏的關係或疏或親,如胡適、汪敬熙、林語堂、老舍等,其中也不乏哀悼篇章。通篇言辭懇切直率,留下精闢的人物觀察紀實。
作者簡介
目次
導言 徬徨覺醒:徐訏的文學道路/陳智德
【念人憶事】
魯迅先生的墨寶與良言
知堂老人的回憶錄
張君勱先生
劉復(半農)
胡適之先生
悼念張雪門先生
賽珍珠
追思林語堂先生
楊震文(丙辰)
我認識的丁文淵先生
悼念詩人伍叔儻先生
張道藩先生
汪敬熙先生
舒舍予先生
悼曹聚仁先生
陸小曼女士
追念余又蓀
悼唐君毅先生與他的文化運動
姚雪垠
錢鍾書
其偉──其人‧其畫‧其事
盛澄華
從《金性堯的席上》說起
悼徐誠斌主教
我所知道的《西風》
悼吉錚
書摘/試閱
【胡適之先生】
胡適之先生的明澈清朗,光耀文化界的聲譽,大家都承認的,但是他不能在哲學、文學方面有真正的建樹,也正如同他的成功方面一樣,是時代所限,也是他個性所限。五四運動的號兵裡,胡適之是最幸運的一個。李大釗、陳獨秀所遭遇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但是這也許在個性上就含有這悲劇的因素。在一九一七年胡適之、陳獨秀提倡「新文學」之時,胡適之給陳獨秀的信,是這樣寫的: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但是陳獨秀的回信則是如此: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的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討論之餘地,必以吾人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裡可以看出胡適之性格的沖和、寬大與平正,陳獨秀性格之凌厲、獨斷與偏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胡適之性格上之矛盾性與妥協性,他的一方面說「不容退縮」一方面又要「容他人之匡正」,實是具有矛盾與妥協的傾向。我想這與以後胡、陳兩個人生命發展的不同是極有關係的。但在白話文運動勝利以後,堅守這個勝利的信仰的,胡適之似乎比誰都澈底。諸凡周作人、周樹人、錢玄同、劉半農等等,好像以後都寫過文言文與哼過舊詩,陳獨秀最後著作是有關文字學,記得也是用文言文寫的,獨獨胡適之,他始終不再寫文言文,也不再寫文言詩。他為傅作義寫陣亡將士碑,是白話文寫的,恐怕也是第一篇以白話文寫碑文的文章。他在抗戰時寄周作人的那首詩也是白話文。胡適之的白話文同他的字一樣,也同他的人一樣,「明澈清朗」正是他的特色,而他似乎也始終以這個「明澈清朗」為白話文的標準。
我碰見胡適之很晚,是他跟蔣夢麟第二次回到北大的時候,那大概是民國十九年或二十年吧。他在北大第二院講幾句話,好像是說,過去許多人想把學術做「姨太太」,這次他與蔣校長回北大,想把學術恢復獨立的地位。這話很普通,當時上海文壇上左派思想很時興,他所指的學術之做「姨太太」,就是做政治的「姨太太」。不過「姨太太」這字眼,在胡適之是一種幽默,可是學生們聽來很不新鮮。
那年胡適之在哲學系開了一課「中古思想史」,這原是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續編的材料。我同幾個朋友去聽過他一堂。哲學系的功課向來是很少人聽講,如陳寅恪、金岳霖、陳大齊諸位教授所授的課,每班不過十幾個人或七八個人,講的談的都是很專門的問題。可是胡適之那天的課則在二院的大禮堂上,聽講的人不但擠滿了課堂,而窗外也站滿了人,許多都是外來的人以及孔德中學的學生。胡適之用很活潑的口才,講佛教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他講了兩個佛經裡有趣的故事,就下課了。我覺得這像是公共演講,內容很通俗,不像是哲學系的功課,當時使我想到唐朝的和尚的俗講。俗講本來是和尚講經,可是後來為吸引聽眾,向通俗有趣吸引聽眾方面發展,所以我沒有選他的課。
胡適之的《中國思想史》(中卷)後來脫稿了,油印本出來,大概贈送給一些友好,可是一直沒有看到正式出版,所以沒有機會讀到。胡適之後來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也開「中國思想史」,許多北大老同學去捧場,那時恰巧我在紐約,也去湊熱鬧。那天課室中大概有二十幾個人,除了七八個北大同學外,聽講的多是上了年紀的女性。我想美國老年人的選點「漢學」聽聽,大概同上禮拜堂聽道一樣,是一種消磨時間的辦法。那時候,漢學與中文在歐美沒有像現在這樣吃香,講中國思想實是對牛彈琴之舉。當時我想到,在美國教書,還是教「人手足刀尺」好,因為這至少還有真正想學的學生。那些捧場的北大同學,自然人各有事,聽一堂,也就不再去了,而那些上了年紀的女性大概有耐心聽下去的人也不多,胡適之在半年以後也就不再開課了。這是我所聽的兩次,一共兩個鐘點的,胡適之的講學。
在紐約時期,有好幾次北大同學的聚餐,胡適之被請為嘉賓。有一次,有一位同學不知怎麼同胡適之談到林語堂的一本新出的書,問胡先生有沒有看過。胡適之當時就說他翻過,發覺裡面多是英國人早就說過的話,林語堂不過是拾英國人的牙慧……。我當時沒有太注意這些,可是席散以後,我同一個同學出來,他說:「胡先生這種地方就不夠風度,沒有幽默。」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胡適之雖常常愛說幽默話,如上面所說的「姨太太」之類,實際上他是缺少幽默感的人。除了幽默感,他還缺少神祕感。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的人物,如陳獨秀、錢玄同,以及文藝作家如魯迅、周作人等似乎都缺少這種神祕感。以後有許多現實主義作家出來,也多數沒有這種神祕感,這大概是啟蒙時期的時代使然。而神祕感與幽默感往往是作為一個偉大文藝作家很大的一個條件。
胡適之為人的大處出入,都見他有過人的風骨,其處世立身,都比他儕輩有明決與果斷。如不競選總統,不接受南洋大學校長之聘,不滯戀美國而到台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如退卸《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之責……都是有先見之明之舉。我覺得在動亂的半世紀中國中,人才濟濟,但有的被風暴所淹沒,有的為時流所浸染,有的在私欲中失節,有的為宣傳所愚弄。這一方面是個性使然,另一方面則正是命運的播弄。這裡面,有三個完全不同的人物,可是細想起來有其完全相同的機運的,則是:胡適之、杜月笙與梅蘭芳。這是人物!這是時代!這也是值得我們細想的所謂一個人的個性與命運的契機。
───
【舒舍予先生】
有一位在哈佛教中國現代史的印度人浮拉先生R. B. Vohra到香港來,因為他正在寫一篇關於老舍的博士論文,想要同我談談,並且希望我拾他一點資料。見面以後,我知道他是於一九五幾年在北京讀書,與老舍見過多次,但當時沒有打算寫論文,所以沒有問他個人的歷史。我很慚愧的告訴他,我雖然也可算認識老舍,但對於他個人歷史,則真是一無所知。
這裡所記的也只是老舍同我的幾次接觸,以及他留給我的印象。
老舍在倫敦教中文,在《小說月報》上發表〈老張的哲學〉的小說時,我剛剛進大學。我有一位朋友李正驤對我說,他正在讀一位新作家的小說,非常喜歡。我當時很想找來看看,但因為忙於功課,迄未實行。他從英國回國後在哪裡做事或教書,我都不知道。等我到上海寫稿賣文時,在《論語》半月刊上投稿,才常讀到老舍為寫給《論語》半月刊的那些幽默文章。那時他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歷史。大概是他於假期中來上海,在《論語》半月刊請客的席上,我第一次碰見他。那時《論語》半月刊主編是林語堂,編輯是陶亢德。隔兩天林語堂先生在家裡請吃飯,林先生住在滬西億定盤路,相當遠,陶亢德接了我,又一同去接老舍,再去林家。
林先生億定盤路的房子是一所很漂亮的花園洋房,老舍一進門就同我說:
「這派頭我們就不能比了。」
林語堂很喜歡老舍在文章上運用道地的北京話。老舍是旗人,北京話說得俏皮,那是不必說了,但我不很喜歡他那種有時故意「耍俏皮」的地方,因為這就跡近油滑,北京話所謂「貧嘴」了。
在談到運用北京話時,老舍有一句給我印象很深的話是:「徐志摩最喜歡用『壓根兒』這句話,但沒有一處是用對的。」
這以後,在他留在上海期間,我們常有見面,也一同看過幾次電影,總是陶亢德約我們在一起的。那時,老舍給我的印象倒不失唯一個誠懇而有風趣的作家。我們自然也偶而談到文藝界的種種。
他對他自己的小說非常自負,談到魯迅,他認為只有雜感可稱首屈一指,小說,則「氣派太小」。至於別人,當然不在他眼裡。那時我很少寫小說。我的寫稿賣文當時也是暫時的客串,我正計畫著要到歐洲去讀哲學或心理學。但是他倒鼓勵我多寫點小說。
以後他回濟南,我與陶亢德還在上海幫林語堂編《人間世》。老舍稿子來往,都由亢德回信,他們倆聯絡得很接近,以後陶亢德就為老舍出書,第一本好像是《櫻海集》,出版者記得就叫亢德書房。
老舍雖早已寫作,但只有到《論語》時代他的文名才比較響亮。這因為當時文藝刊物很少,只有一個施蟄存編的《現代》,而《現代》是門戶之見很深的刊物,對老舍也不怎麼重視。《論語》與《人間世》對老舍宣揚甚力。《人間世》以後,才有傅東華編的《文學》出版,《現代》也就無法繼續存在。後來陶亢德辦《宇宙風》,老舍也是一個主將。
在《人間世》停刊後不久,我就去歐洲讀書;抗戰後,我無法繼續留學,回到孤島的上海,沒有辦法,又繼續過賣文生活,大概這時候我才開始甘心從事寫作。那時陶亢德在上海編《天下事》。老舍已經轉到後方,亢德同他有信札往還,老舍曾叫亢德進去主持出版事宜。
珍珠港事變後,我預備去後方,同亢德談起。亢德叫我到重慶後,與老舍聯繫,希望可以對他作一個安排。我到內地,在桂林躭了幾個月,到重慶已是半年以後的事,我寫了一封信給老舍。記得那時他住在鄉下,一星期進城幾次。他回我一封信,約定一個地方去看他。
那時老舍大概已是全國抗戰文藝協會的理事或會長,或者已經正式的加入左聯了。他同我們在上海往還的時候完全不同,非常虛驕做作。我從上海到重慶,也拜會過國民黨的官貴,後來也把晤到左翼作家中如茅盾,夏衍等,但沒有一個像老舍這樣虛驕而不誠懇的。他既沒有問我淪陷的上海情況,也沒有問我一路來的際遇。一味是淡漠的敷衍,有時還逗著旁邊的一隻小貓。我很疑心他是防備我會求他幫助,所以一談到我情形時,我告訴他我在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有一個小事。他也許因此而較為安心。最後我談到了陶亢德託我轉達的事。他忽然變淡漠的態度興奮起來,大聲地說:「陶亢德……我有什麼辦法!現在有什麼辦法,寫作出版都不自由。當初他的《宇宙風》……那時候,有我與郭鼎堂,自然可以成功,全靠我與鼎堂……」
他當時的態度實在很出我意外,因為我並不是來替亢德要債,也不是向他交涉什麼。我記得,只是說:「亢德也很想進內地來,上次你曾經寫信給他提起過什麼事,現在你是不是可以替他想想辦法。」之類的意思。
老舍說「沒有什麼辦法」也沒有什麼,扯到寫作出版不自由,實是文不對題。再後面,說陶亢德的《宇宙風》全靠他與郭鼎堂,那真是很奇怪的笑話。陶亢德是一個上好的編輯,他辦刊物從拉稿到發行以及和書販打交道,一個人都可以做,可說是一個全能的人才。我一生遇見過好的編輯很多,但像亢德這樣全能的人才則沒有第二個。我不敢說,郭鼎堂與老舍的稿子於《宇宙風》沒有影響,(事實上,哪一個作家都可以自己這麼說!)
但如果沒有他們兩人的稿子,亢德一定可以拉到同分量的作家與文稿。而他以後所辦的《天下事》之成功就是一個證明。其次,如果老舍為亢德寫稿完全是義務的,沒有受過稿費,老舍還有資格說這句話,而亢德所以能請老舍寫稿,是有使老舍滿意的稿酬的,這種買賣性質的交易,是彼此合適的事。老舍這種話引起我很大的反感。我當時笑笑說:「那我就回他一封信好了。」
那時的老舍的確與以前完全是兩個人。當時他可說真是一個共產黨的外圍作家,共產黨把他捧得「飄飄然」,他自以為真是左聯及文協的真正領導人物了。捧一個外圍的人物來做表面的領袖供他們利用,原是共產黨的普通手法,而老舍那時這付嘴臉,正是反映這種角色。我可以說當時真正左翼的人如茅盾、胡風,夏衍都沒有這種飛揚跋扈的神情。老舍以外,有這種嘴臉的,以後我見之於一些被共產黨所爭取而灼灼捧紅的一些年輕的作家與戲劇界電影界的人士。
一九四六年老舍去美國時,我也在美國,那時有好幾個請老舍的場合也請了我,我都沒有參加。這倒沒有故意避他的意思,而是那時已經勝利,我一方面歸心如箭,另一方面我當時正患嚴重的失眠症,應酬就不想參加了。以後我再沒有會見過老舍。
到香港後,從大陸的許多文藝界風波中,我看到老舍在清算胡風時的發言,知道胡風曾經對老舍作過極嚴厲的批評。後來還知道老舍寫了一個劇本,是採用一個共產黨幹部招搖推撞騙的實事。在發表時,他特別提出來說是羅瑞卿鼓勵他寫的,這種花腔正是老舍愛玩的小手段。對社會主義的社會「暴露黑暗」,是反黨的行為。但因為是羅瑞卿所鼓勵,所以也就沒有人對他指摘。以後羅瑞卿被判為反革命走資派,老舍面對紅衛兵,恐怕也很難解說了。馬思聰的文章中說老舍被紅衛兵鬥死了,我心裡感慨很多。他在這個政權下,已經是盡其聰敏與能力來効勞了。我讀過一篇記載在莫斯科參加什麼節日的文章,他真是用盡力量來歌頌蘇聯要人與大陸頂峯人物在台上出現的情形。我總以為像他那樣總一定可以得「榮歸」「壽終」之喜了,不意仍難免於「身」敗「名」裂,亦可見「政治」之不易「伺候」了。
要知道老舍的生平與作品,自有浮拉先生一類的博士論文可讀,我這裡不過紀錄我的一點印象罷了。
一九六九、九。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