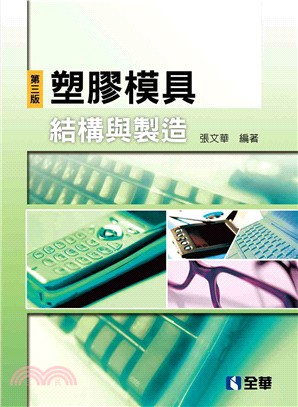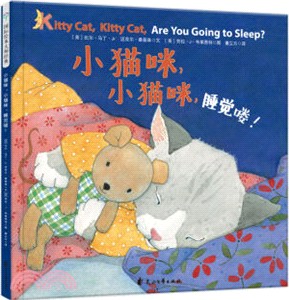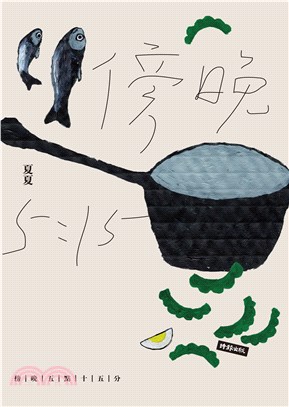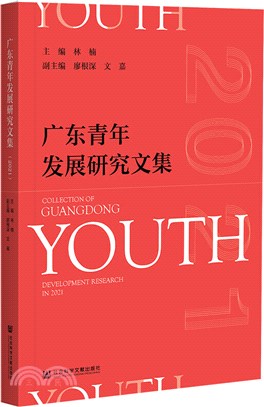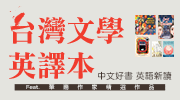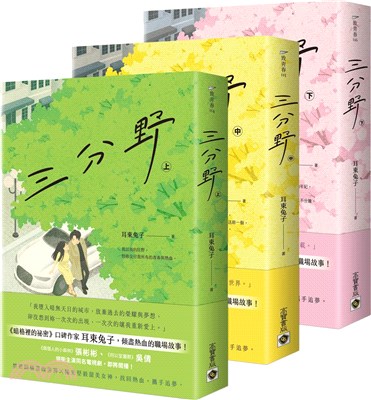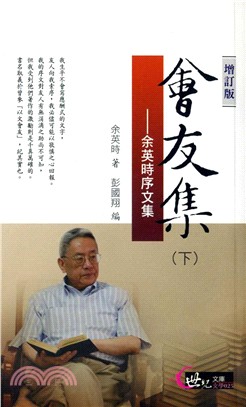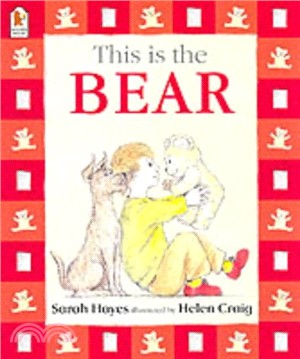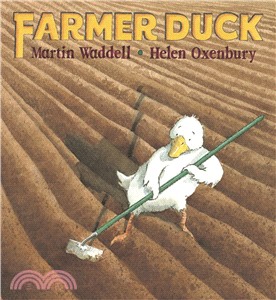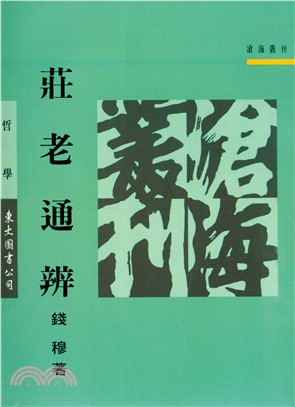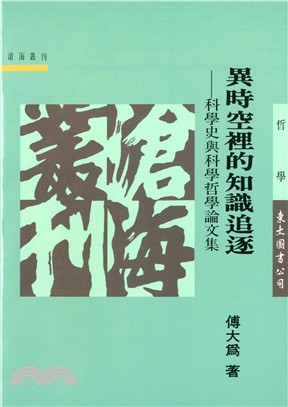毛澤東特務的叛逃: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電子書)
商品資訊
定價
:NT$ 360 元優惠價
:70 折 252 元
閱讀器:書紐電子書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7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而我怎樣當了毛澤東的特務?說來是在半嚇半騙下被迫成的……」
陳寒波,一個共產黨員,一個掌握中共秘密資料的特務,為何展開反共之路?
1950年,中共建政後的一年,上海警察醫院裡三名曾對共產黨懷抱理想與期望的青年,李華、姚宜瑛、榮斌此刻卻同病相憐,身為特務的他們切身體會中共政權下的慘無人道與黑暗面,密謀在眾多共特監視下逃離紅色鐵幕……
21歲的紅色女間諜姚宜瑛,幾經滄桑、蹂躪,終於逃離迫良為特的共產黨迫害,臨別前,寫下這首為「民主自由而歌」的詩,傾訴她痛不欲生的經歷,以及反共的決心:「在血淋淋的五星旗覆蓋下,只要你張開眼睛,空著耳朵,哪兒沒有兇惡的皮鞭在笞撻著人民,哪兒沒有罪惡的枷鎖在壓著人民……我要反抗罪惡的毛澤東匪幫的統治喲!我要擎起槍桿,投身於反共戰場!」
作者陳寒波為前中共特務,而本書是他現身說法之寫實傑作,亦是他遇害前最後見世的著作。
陳寒波,一個共產黨員,一個掌握中共秘密資料的特務,為何展開反共之路?
1950年,中共建政後的一年,上海警察醫院裡三名曾對共產黨懷抱理想與期望的青年,李華、姚宜瑛、榮斌此刻卻同病相憐,身為特務的他們切身體會中共政權下的慘無人道與黑暗面,密謀在眾多共特監視下逃離紅色鐵幕……
21歲的紅色女間諜姚宜瑛,幾經滄桑、蹂躪,終於逃離迫良為特的共產黨迫害,臨別前,寫下這首為「民主自由而歌」的詩,傾訴她痛不欲生的經歷,以及反共的決心:「在血淋淋的五星旗覆蓋下,只要你張開眼睛,空著耳朵,哪兒沒有兇惡的皮鞭在笞撻著人民,哪兒沒有罪惡的枷鎖在壓著人民……我要反抗罪惡的毛澤東匪幫的統治喲!我要擎起槍桿,投身於反共戰場!」
作者陳寒波為前中共特務,而本書是他現身說法之寫實傑作,亦是他遇害前最後見世的著作。
作者簡介
陳寒波
出生於廣東省台山縣,學名晉唐,其父陳壁光為在美經商華僑,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正式成為共產黨員。在中共要求下投考中央軍校,自此展開地下工作,然而隨著對中共治理方式的失望,終於1950年8月逃至香港,為文發表《今日北平》、《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等著作。1952年1月16日,30餘歲的陳寒波在香港遭暗殺。
出生於廣東省台山縣,學名晉唐,其父陳壁光為在美經商華僑,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正式成為共產黨員。在中共要求下投考中央軍校,自此展開地下工作,然而隨著對中共治理方式的失望,終於1950年8月逃至香港,為文發表《今日北平》、《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等著作。1952年1月16日,30餘歲的陳寒波在香港遭暗殺。
目次
【導讀】慘遭暗殺的陳寒波其人其書/蔡登山
《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陳寒波
一、警察醫院重逢
二、侮辱與迫害
三、﹁聯絡部﹂女間諜
四、神女生涯
五、渡江前後
六、如此「副所長」
七、走向反共的新生之路
《地下火》(五幕劇)/陳寒波
時‧地‧人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陳寒波之死》/張公道
一、陳寒波這個人
二、輿論的憤慨
三、陳寒波筆下的共產黨
四、陳寒波筆下的反共理論
五、陳寒波之死對於社會的影響
六、自由世界的溫暖
七、寫在後面
《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陳寒波
一、警察醫院重逢
二、侮辱與迫害
三、﹁聯絡部﹂女間諜
四、神女生涯
五、渡江前後
六、如此「副所長」
七、走向反共的新生之路
《地下火》(五幕劇)/陳寒波
時‧地‧人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陳寒波之死》/張公道
一、陳寒波這個人
二、輿論的憤慨
三、陳寒波筆下的共產黨
四、陳寒波筆下的反共理論
五、陳寒波之死對於社會的影響
六、自由世界的溫暖
七、寫在後面
書摘/試閱
一、警察醫院重逢
在一九五○年的上海,在舟山群島「解放」前,我正在因害著風濕性的關節炎而躺在提籃橋的警察醫院裡。
這是一所海上有名的公立醫院,在租界時代,工部局和總巡捕房曾給它鉅額的開辦費和經常費,建築著七層大廈,規模龐大,病床數百,儀器醫藥設備都很講究。由租界時代,到國民黨統治時代,警官、警察和他們的眷屬,都可以免費住院醫療,可是,到了「解放」時代,警察和他們的眷屬,能獲准住院治療,卻是不容易了,給他們在門診部多診視幾次,已是天大的人情。因為,「解放」後,它已不是警界們所專有了。規模龐大,人員眾多的中共華東局社會部底幹部和眷屬,經常佔滿了病床,為了「保密」,他們是不方便住在市立醫院或其他公立醫院的,一部分可憐的「偽警」們,只好被拒門外了。
像社會部的其他部門一樣,在這醫院裡,也充滿了陰森森的氣氛,絲毫沒有普通醫院的溫暖氣息。王軍事代表是個陰險狠毒的老牌共特,當他有時偶然的巡視病房時,有點心事的病人總是忐忑不安,害怕不測之災會突然的降臨。一個個表面熱情、溫柔、可愛的女看護,不曉得那一個會在「幹訓班」受過特務訓練,不曉得那一個是受「FF室」的領導的,這個特務中的特務組織的觸角,這個專門用來監視社會部的幹部的核心情報網,像其他的情報網一樣,是伸向每個角落去的,因而,每個病人仍是異常小心、謹慎地生活著,除非早經熟識,都不敢輕易深談,跟平時在機關裡一樣,對任何問題,都不敢輕易表示意見。
當我住進五樓的一間雙人小病房的翌日,一個共黨中的老同志榮斌也跟著不約而同地搬進來,和我同住在一個病房裡,他除了正害著跟我一樣的關節炎外,還有其他的毛病,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給疾病和無邊的心事折磨的憔悴不堪了。他年紀比我小,長得短小精幹、機警靈敏,人們都喜歡叫他做小榮。他於去年被遠調到寧波去,面向著舟山群島的軍統機構面秘密鬥爭著。最近因病重,寧波醫藥設備不週,才獲准回滬療養。
「這回我們可不再寂寞了」!他一進房,瞥見我躺在床上,喜出望外地說著。
「哦,你也來了,正好!我們這一回可以優閒地暢談往事了」。我也同樣高興地報給他喜悅的微笑。
從此,我們便在沒有第三者在房中時,低聲的暢談著,大家病狀好轉後,談得更起勁。我參加組織的時間是比他長的,可是,命運的折磨,大家都被人稱過叛徒,大家今天都被人歧視,大家都好像看不見光明和長遠的前途。兩個同病相憐的老友,常常自撫著過去十多年來纍纍的創痕,悽然相對追訴往事,常常情不自禁地潸然下淚。有一次,他正淚痕滿面、傷感異常時,突然,王軍事代表來了,他除了是部長的親信外,而且是醫院方面「FF」的最高負責長,那怕你是高級幹部,只要你在他管下,你的情緒、言行、思想動態,他都有權給你每天送報告上去的,若報告查而屬實,那麼,是少不免受批評和受處分的。
「榮同志因病痛或別的不如意事,而傷感、流淚,這是不對的,傷感是動搖主義、失敗主義的源泉,我們革命者,只有戰鬥、流血!沒有傷感、流淚!你以為對嗎?」
「對對……」小榮臉色轉青,「但我傷感的是不能早日病癒回寧波去獻身為解放舟山而工作!」
「這也沒有意義,為了這個而傷感也是不正確!」他一言一語儘是斬釘截鐵般毫無情感。
「……」小榮呆若木鷄,趕快用手帕揩著淚痕。
「再見!」
「再見!」
望著他的背影,我們不約而同地吁了一口氣。
從此,我們為防止情緒的衝動,避免不必要的批評,大家儘量減少互訴衷曲,除了閱讀組織分配來的輕病同志學習文件外,有時扶著手杖向走廊或其他空曠處散散步。一天,他獨自自出去,卻換了一個也穿著病號衣服的漂亮的女同志進來,興奮地對著我和她說:「你們大約已碰過面吧?但現在在這裡,我應該更親切地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我十年前的老同志,共生死患難多時的李華同志,(他喜歡喚我組織內的用名)是現在我們部裡的『情委』。她就是我曾說過的沒有被批准的愛人……」他忍不住地哭了,兩眼盯著她烏溜溜的眼珠,她兩頰泛起微紅。
「呵,不用介紹了,雖然我們只曾在跳舞晚會見過一兩次面,但犧牲一切,為黨鬥爭的姚同志,在我的印象裡是異常深刻的。」
「不敢當,不敢當!我是勞而無功的,我的理論水準和鬥爭技術太差了,須要向您多多學習!」
「現在,『國際招待所』情況好麼?業務易應付麼?」我無意中說出這一句話,馬上覺得是失言了。
「唉!一言難盡……」她黯然神傷地低垂下臉。
「半年多了!」小榮見到這情況,機巧地把話扭轉,「自從我倆奉批不准結婚,將我遠調外省、不准跟您通訊、不准隨便回滬、不准我倆再發生愛情,否則,以違反紀律及妨礙工作論處,自從離開了您,我一天天感到人生的乏味了,假如不是在這裡偶然的碰見您,我病癒後是沒有勇氣去拜訪您的。」
「你們談談,我要出去買點水果和鷄蛋回來,姚同志就在我們這裡開飯,讓我加點小菜請客。」我瞧瞧手錶,正是下午二時,我覺得,我是應該借機走開的,讓他們好好的細敘別情的。
我走出來,向值日護士打過招呼,托勤務員去買東西,自己到別個病房去聊天,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見到他倆都眼皮哭紅了,淚珠雖揩過,但斑斑淚痕猶在,可見他倆剛才是如何悽慘地悲慟了一場,用過飯後,姚辭去,我問他怎麼樣,他蒙上被頭只答了我一聲:「一切都完了!」
從此,他倆謹慎地,祕密地接觸著,若她白天到來,我多借機讓開,若她半夜裡偷偷的溜進來,連電燈也不開亮地挨在床上絮絮細語,我就乾脆裝睡,故作鼾聲大響。當她不在我們的病房裡時,小榮跟我的談笑,一天比一天地減少了,但情況很明顯,他不是完全害怕我靠不住,而是傷心過度、痛不欲言。因而,我為了使他獲得更多一點的安寧,我也儘量避免因多談多問的關係,致加強他的刺激。反而,我為了使他倆避免掉院中「FF」們的注意,我還幫助他倆向院方進行減少注意的週旋,這樣很快度過了半個月。
「李華同志!我現在當您是我的親哥哥一樣,向您請教一下我蘊藏在心深處一個難於裁決的問題,請您幫助我考慮一下……」在一個夜闌人靜的午夜裡,小榮突然把我從夢中推醒,顫抖地、興奮過度地緊握著我的右腕,嘴巴挨近我的耳朵。「可是,您會批評我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復發嗎?您會不會十多年的交情,像那些死硬份子一樣,翻臉不認得人,而站著所謂堅決的『組織立場』向組織檢舉我麼?向組織出賣我邀功嗎?您會……。」
他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沈、越顫抖,最後好像懊悔不該吐出前面的話來。
「老弟!我們是同病相憐的呵,你一切顧慮都是不必要的,您只管說吧,我可以幫助您考慮,幫助您裁決。」我不等他的話說完,便以最誠懇的語氣迎接上去。
「……」他張開嘴吧,但過分的猶豫,使他的話吐不出來。時計一秒一秒的過去,我有點不耐煩了。他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卻又鼓不起勇氣吐出內心深處的話來,最後兜轉屁股,從他枕床上邊拿來一張照片―一張姚宜瑛前天才送給他的近影。
「您想不到像她這樣聰明,漂亮的女同志,到今天還過著地獄不如的生活,欲生不能、欲死不得,連愛上她的我,也被牽累,也被拖進地獄,她五年來,受盡了折磨,她最近,常常想到自殺!」
「何必要自殺呢?她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困難,她五年來怎樣的不好過?」我對他倆的戀愛故事,只是微有所聞,我對姚宜瑛的過程更是不了解的,只曾聽說過,解放前,他在上海幹地下工作,為掩護工作,曾當過舞女、進過妓院。她現在的「國際招待所」工作,是受部長副部長直接領導的,和我們「情委會」,沒有什麼橫的聯繫,而任何人沒有得到部長的特許,是不准踏進「國際招待所」的,該所中住的「國際友人」,我也只曾正式會過一次商,那是自稱為蘇聯格柏島(G.P.U.)特務組織的密碼專家的俄國大鼻子阿華夫斯基,那是組織通知他到我們這單位中,給我們解決一點所謂帝國主義間諜案中的密碼疑難,但結果證明他的見解也並不高明,有些同志背著竊笑他是「洋飯桶」。而她擔任這招待所的副所長,到底有什麼痛苦,我也不大深悉的。
「唉,正所謂一言難盡,慢慢再談吧,這裡有解放前她幹地下工作的日記的片斷,請先看看。」
小榮為人是異常小心謹慎的,現在,他已把他剛才推醒我時的一股衝動的情感壓下去大半了,他打算一次全盤托出的話,現在是吞下大半了,他只好逐步試探我的反應。
第二天早晨,給我轉遞與「公事」無關的信件的密友黃君,帶了一點水果西點來探我的病,還給我帶來了一封由香港寄他商店轉我的信,拆開一閱,是我堂弟弟答覆我,給我經過詳細調查由滬赴港的一般手續,和入境方法的詳函,黃君告辭後,我便劃火柴要把它燒掉,小榮趁我不當心,一手搶過去,笑著:「情書留下來,我不看您的,但不要燒掉!」
我冷靜靜地搖搖頭:「我是沒有這種心情了,這封信是要燒掉的,不過,我們是同病相憐,我相信您,您是可以看看的―也許看過後,對您有點益處。」
於是,他仔細地研閱著,翻覆看了兩遍,才長吁一聲交還給我,我立刻把它燒掉。
「您為什麼調查往香港的手續和方法?您也想逃亡嗎?」
「不用說,您會猜得著的。同病相憐的心情還不清楚麼?」
他聽著我的話,不斷作會意的點點頭,他現在已深切的領會到,我正跟他作著同樣的打算,憑過去的私誼,和目前的客觀情況,決定了我是絕不會出賣像他這樣的老同志的,他在這一剎那,已把他昨夜的顧慮和猶豫完全掃除了:
「專制、殘忍的統制,把我和您都迫上梁山了!荒淫與無恥的迫害,使我和姚宜瑛不反抗、不逃亡,便只有發瘋或自殺!宜瑛過去為了她母親,不願她母親和妹妹死於非命,五年來受盡了污辱和折磨,到頭來母女三人還是得不到絲毫的幸福,反而更殘酷地遭受著蹂躪、淫辱和宰割!現在,她也覺得再不能顧到她母親的安危,決定跟我投到太湖游擊區去了,我們今後,要用血來寫爭自由的歷史,再不能用血淚來寫被侮辱與迫害的歷史了,你以為對嗎?」
「你聽,李華同志!廿一歲的姚宜瑛,五年來的經歷,是這樣用血淚來寫的!」
在一九五○年的上海,在舟山群島「解放」前,我正在因害著風濕性的關節炎而躺在提籃橋的警察醫院裡。
這是一所海上有名的公立醫院,在租界時代,工部局和總巡捕房曾給它鉅額的開辦費和經常費,建築著七層大廈,規模龐大,病床數百,儀器醫藥設備都很講究。由租界時代,到國民黨統治時代,警官、警察和他們的眷屬,都可以免費住院醫療,可是,到了「解放」時代,警察和他們的眷屬,能獲准住院治療,卻是不容易了,給他們在門診部多診視幾次,已是天大的人情。因為,「解放」後,它已不是警界們所專有了。規模龐大,人員眾多的中共華東局社會部底幹部和眷屬,經常佔滿了病床,為了「保密」,他們是不方便住在市立醫院或其他公立醫院的,一部分可憐的「偽警」們,只好被拒門外了。
像社會部的其他部門一樣,在這醫院裡,也充滿了陰森森的氣氛,絲毫沒有普通醫院的溫暖氣息。王軍事代表是個陰險狠毒的老牌共特,當他有時偶然的巡視病房時,有點心事的病人總是忐忑不安,害怕不測之災會突然的降臨。一個個表面熱情、溫柔、可愛的女看護,不曉得那一個會在「幹訓班」受過特務訓練,不曉得那一個是受「FF室」的領導的,這個特務中的特務組織的觸角,這個專門用來監視社會部的幹部的核心情報網,像其他的情報網一樣,是伸向每個角落去的,因而,每個病人仍是異常小心、謹慎地生活著,除非早經熟識,都不敢輕易深談,跟平時在機關裡一樣,對任何問題,都不敢輕易表示意見。
當我住進五樓的一間雙人小病房的翌日,一個共黨中的老同志榮斌也跟著不約而同地搬進來,和我同住在一個病房裡,他除了正害著跟我一樣的關節炎外,還有其他的毛病,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給疾病和無邊的心事折磨的憔悴不堪了。他年紀比我小,長得短小精幹、機警靈敏,人們都喜歡叫他做小榮。他於去年被遠調到寧波去,面向著舟山群島的軍統機構面秘密鬥爭著。最近因病重,寧波醫藥設備不週,才獲准回滬療養。
「這回我們可不再寂寞了」!他一進房,瞥見我躺在床上,喜出望外地說著。
「哦,你也來了,正好!我們這一回可以優閒地暢談往事了」。我也同樣高興地報給他喜悅的微笑。
從此,我們便在沒有第三者在房中時,低聲的暢談著,大家病狀好轉後,談得更起勁。我參加組織的時間是比他長的,可是,命運的折磨,大家都被人稱過叛徒,大家今天都被人歧視,大家都好像看不見光明和長遠的前途。兩個同病相憐的老友,常常自撫著過去十多年來纍纍的創痕,悽然相對追訴往事,常常情不自禁地潸然下淚。有一次,他正淚痕滿面、傷感異常時,突然,王軍事代表來了,他除了是部長的親信外,而且是醫院方面「FF」的最高負責長,那怕你是高級幹部,只要你在他管下,你的情緒、言行、思想動態,他都有權給你每天送報告上去的,若報告查而屬實,那麼,是少不免受批評和受處分的。
「榮同志因病痛或別的不如意事,而傷感、流淚,這是不對的,傷感是動搖主義、失敗主義的源泉,我們革命者,只有戰鬥、流血!沒有傷感、流淚!你以為對嗎?」
「對對……」小榮臉色轉青,「但我傷感的是不能早日病癒回寧波去獻身為解放舟山而工作!」
「這也沒有意義,為了這個而傷感也是不正確!」他一言一語儘是斬釘截鐵般毫無情感。
「……」小榮呆若木鷄,趕快用手帕揩著淚痕。
「再見!」
「再見!」
望著他的背影,我們不約而同地吁了一口氣。
從此,我們為防止情緒的衝動,避免不必要的批評,大家儘量減少互訴衷曲,除了閱讀組織分配來的輕病同志學習文件外,有時扶著手杖向走廊或其他空曠處散散步。一天,他獨自自出去,卻換了一個也穿著病號衣服的漂亮的女同志進來,興奮地對著我和她說:「你們大約已碰過面吧?但現在在這裡,我應該更親切地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我十年前的老同志,共生死患難多時的李華同志,(他喜歡喚我組織內的用名)是現在我們部裡的『情委』。她就是我曾說過的沒有被批准的愛人……」他忍不住地哭了,兩眼盯著她烏溜溜的眼珠,她兩頰泛起微紅。
「呵,不用介紹了,雖然我們只曾在跳舞晚會見過一兩次面,但犧牲一切,為黨鬥爭的姚同志,在我的印象裡是異常深刻的。」
「不敢當,不敢當!我是勞而無功的,我的理論水準和鬥爭技術太差了,須要向您多多學習!」
「現在,『國際招待所』情況好麼?業務易應付麼?」我無意中說出這一句話,馬上覺得是失言了。
「唉!一言難盡……」她黯然神傷地低垂下臉。
「半年多了!」小榮見到這情況,機巧地把話扭轉,「自從我倆奉批不准結婚,將我遠調外省、不准跟您通訊、不准隨便回滬、不准我倆再發生愛情,否則,以違反紀律及妨礙工作論處,自從離開了您,我一天天感到人生的乏味了,假如不是在這裡偶然的碰見您,我病癒後是沒有勇氣去拜訪您的。」
「你們談談,我要出去買點水果和鷄蛋回來,姚同志就在我們這裡開飯,讓我加點小菜請客。」我瞧瞧手錶,正是下午二時,我覺得,我是應該借機走開的,讓他們好好的細敘別情的。
我走出來,向值日護士打過招呼,托勤務員去買東西,自己到別個病房去聊天,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見到他倆都眼皮哭紅了,淚珠雖揩過,但斑斑淚痕猶在,可見他倆剛才是如何悽慘地悲慟了一場,用過飯後,姚辭去,我問他怎麼樣,他蒙上被頭只答了我一聲:「一切都完了!」
從此,他倆謹慎地,祕密地接觸著,若她白天到來,我多借機讓開,若她半夜裡偷偷的溜進來,連電燈也不開亮地挨在床上絮絮細語,我就乾脆裝睡,故作鼾聲大響。當她不在我們的病房裡時,小榮跟我的談笑,一天比一天地減少了,但情況很明顯,他不是完全害怕我靠不住,而是傷心過度、痛不欲言。因而,我為了使他獲得更多一點的安寧,我也儘量避免因多談多問的關係,致加強他的刺激。反而,我為了使他倆避免掉院中「FF」們的注意,我還幫助他倆向院方進行減少注意的週旋,這樣很快度過了半個月。
「李華同志!我現在當您是我的親哥哥一樣,向您請教一下我蘊藏在心深處一個難於裁決的問題,請您幫助我考慮一下……」在一個夜闌人靜的午夜裡,小榮突然把我從夢中推醒,顫抖地、興奮過度地緊握著我的右腕,嘴巴挨近我的耳朵。「可是,您會批評我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復發嗎?您會不會十多年的交情,像那些死硬份子一樣,翻臉不認得人,而站著所謂堅決的『組織立場』向組織檢舉我麼?向組織出賣我邀功嗎?您會……。」
他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沈、越顫抖,最後好像懊悔不該吐出前面的話來。
「老弟!我們是同病相憐的呵,你一切顧慮都是不必要的,您只管說吧,我可以幫助您考慮,幫助您裁決。」我不等他的話說完,便以最誠懇的語氣迎接上去。
「……」他張開嘴吧,但過分的猶豫,使他的話吐不出來。時計一秒一秒的過去,我有點不耐煩了。他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卻又鼓不起勇氣吐出內心深處的話來,最後兜轉屁股,從他枕床上邊拿來一張照片―一張姚宜瑛前天才送給他的近影。
「您想不到像她這樣聰明,漂亮的女同志,到今天還過著地獄不如的生活,欲生不能、欲死不得,連愛上她的我,也被牽累,也被拖進地獄,她五年來,受盡了折磨,她最近,常常想到自殺!」
「何必要自殺呢?她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困難,她五年來怎樣的不好過?」我對他倆的戀愛故事,只是微有所聞,我對姚宜瑛的過程更是不了解的,只曾聽說過,解放前,他在上海幹地下工作,為掩護工作,曾當過舞女、進過妓院。她現在的「國際招待所」工作,是受部長副部長直接領導的,和我們「情委會」,沒有什麼橫的聯繫,而任何人沒有得到部長的特許,是不准踏進「國際招待所」的,該所中住的「國際友人」,我也只曾正式會過一次商,那是自稱為蘇聯格柏島(G.P.U.)特務組織的密碼專家的俄國大鼻子阿華夫斯基,那是組織通知他到我們這單位中,給我們解決一點所謂帝國主義間諜案中的密碼疑難,但結果證明他的見解也並不高明,有些同志背著竊笑他是「洋飯桶」。而她擔任這招待所的副所長,到底有什麼痛苦,我也不大深悉的。
「唉,正所謂一言難盡,慢慢再談吧,這裡有解放前她幹地下工作的日記的片斷,請先看看。」
小榮為人是異常小心謹慎的,現在,他已把他剛才推醒我時的一股衝動的情感壓下去大半了,他打算一次全盤托出的話,現在是吞下大半了,他只好逐步試探我的反應。
第二天早晨,給我轉遞與「公事」無關的信件的密友黃君,帶了一點水果西點來探我的病,還給我帶來了一封由香港寄他商店轉我的信,拆開一閱,是我堂弟弟答覆我,給我經過詳細調查由滬赴港的一般手續,和入境方法的詳函,黃君告辭後,我便劃火柴要把它燒掉,小榮趁我不當心,一手搶過去,笑著:「情書留下來,我不看您的,但不要燒掉!」
我冷靜靜地搖搖頭:「我是沒有這種心情了,這封信是要燒掉的,不過,我們是同病相憐,我相信您,您是可以看看的―也許看過後,對您有點益處。」
於是,他仔細地研閱著,翻覆看了兩遍,才長吁一聲交還給我,我立刻把它燒掉。
「您為什麼調查往香港的手續和方法?您也想逃亡嗎?」
「不用說,您會猜得著的。同病相憐的心情還不清楚麼?」
他聽著我的話,不斷作會意的點點頭,他現在已深切的領會到,我正跟他作著同樣的打算,憑過去的私誼,和目前的客觀情況,決定了我是絕不會出賣像他這樣的老同志的,他在這一剎那,已把他昨夜的顧慮和猶豫完全掃除了:
「專制、殘忍的統制,把我和您都迫上梁山了!荒淫與無恥的迫害,使我和姚宜瑛不反抗、不逃亡,便只有發瘋或自殺!宜瑛過去為了她母親,不願她母親和妹妹死於非命,五年來受盡了污辱和折磨,到頭來母女三人還是得不到絲毫的幸福,反而更殘酷地遭受著蹂躪、淫辱和宰割!現在,她也覺得再不能顧到她母親的安危,決定跟我投到太湖游擊區去了,我們今後,要用血來寫爭自由的歷史,再不能用血淚來寫被侮辱與迫害的歷史了,你以為對嗎?」
「你聽,李華同志!廿一歲的姚宜瑛,五年來的經歷,是這樣用血淚來寫的!」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