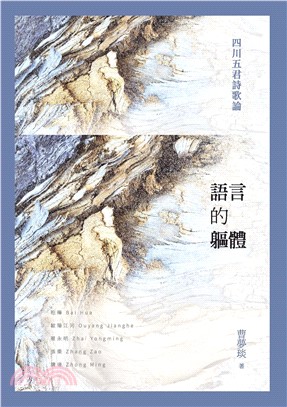語言的軀體:四川五君詩歌論(電子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本書以「四川五君」柏樺、歐陽江河、翟永明、張棗、鐘鳴的詩歌作為切入點,探討寫作中身體的在場、偏移、僵化、缺席、迷失,以及詩人們在展示出富有魅力的語言時,如何流露出語言的恍惚、矯飾,甚至虛假,即語言和身體的錯位。在五位詩人這裡,身體的在場與缺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什麼是對詩歌來說最重要的事?作者認為:「應該是真實,身體的真實。真實、盡可能的真實,這是詩歌需要的。與此同時,錯位的與缺席的身體,對詩人和詩歌來說,是一種缺陷,卻也是另外一種真實,它昭示出困境與局限。也許,更重要的東西在於,如何抗拒不真實而去抵達那個遙不可及的真實,如何對那個時刻準備逃逸的身體警醒著、戒備著。」
作者簡介
序
【後記】
這本書的初稿完成於2011年4月,作為我的碩士論文。在出版前重新閱讀和校對它,勾起了一些對過去時間的記憶。我試圖完善某個觀點,改變若干詞句的寫法。一個日漸成熟,甚至衰老的自己,給那還算年輕的人提出一點意見。這隔著時空的交流,其實蠻有趣。那些任性而散漫的句子,那些認真而幼稚的句子……讓我頭痛、忍俊不禁,甚至陷入慚愧。然而內心是恍然大悟的:它們隱現著我此刻的說話方式。重新打標點,去掉贅詞,縮短長句子換氣:調整之後,她有點像現在的我,即使還不夠成熟。修改有時令我疲憊,有時則了然,索性放任詞句在過去的時間中,其實那幼稚的堅持並不特別討厭。有時,我必須順著她,她有她的想法。我皺眉頭考慮怎麼改,卻逐漸被她的行文感染,開始認同她,甚或驚奇地發現,那樣寫更好。她也讓我崩潰過,但我們最終能夠平靜地商討,也表達出對彼此的認可和遺憾。時間,怎能讓人不遺憾。情緒化的我,記憶著情緒化的時刻,連同那些時刻一起到來的文字。我也在抵禦我,並且這一過程是耗費的,時常讓生活與表達陷入窘迫。
三十歲開始,過於激烈的情緒和生活都消褪了。一切慢慢發生著,卻在某個時刻讓人驚覺改變,知覺永遠是惰性的。到上海大半年之後,某天騎自行車過馬路,陷入恍惚,有點困惑自己怎麼在這兒。也不知從何時開始,我格外留意表達中的細節,每個人的語癖。該如何表達?糾纏彼此的生活和詞,它們撲朔著,鬱鬱落下。什麼東西呼之欲出?呼之欲出……是歌唱。縈繞於心之鬱結的,是歌唱的影子。黃昏影,斜長,好像有溫度,又很絕望。真正的歌唱能否被燃發?就是那種感覺,近乎不可能。
2016年6月2日,上海同濟北苑
目次
目錄
導言╱詩人和他的時代
柏樺--向左傾斜的身體
歐陽江河--扼殺呼吸的美杜莎之首
翟永明--身體的秘密痕跡
張棗--迷失的身體
鐘鳴--恍惚與界限之間的身體
結論
後記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
【導言╱詩人和他的時代】
2010年8月,我來到成都,一個陰霾的城市。曾有人說過,待在四川唯一的不好處是天氣陰沉,偶爾有太陽出來,人們彷彿過節一樣。即使如此,他迷戀那裡,迷戀這座城市的腐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是一種可以延伸到最底層、延伸到每一個人的腐朽。一位化名為「老威」的四川詩人曾寫出一部訪談錄,涉及形形色色、龍蛇混雜的人:棄妻為名利的詩人、放棄寫詩整天打麻將的詩人、「土皇帝」、被判死刑的貪污者……有關腐朽,也有太多可說的:私欲的過度膨脹?抑或僅僅是在「火鍋與茶館的指引下」消磨一個下午,饕餮、神侃?甚至,在離自己死期不遠的囚禁生活中,拼死地爭奪胡豆,還能冒出頗有方言天然幽默感的話。或者,腐朽同時意味著一種語言的腐朽。鐘鳴一再強調北人好經世之想,而南人「喜歡精緻的事物,熱衷神秘主義和革命,好私蓄」、「多愁善感,實際而好幻想」、「生活頹靡本能,卻追求精神崇高」。不同於北方詩人,南方詩人們更多地在詩歌中流露出對語言的享樂情結。「朦朧詩」之後,四川幾乎成為新一代詩歌的中心地帶,各種名號與用心之下的詩派、詩歌宣言紛紜而起。鐘鳴在談到南方詩歌時說:「人人都是理想主義者。只有這樣,彷彿才對得起浪費的歲月。」他用了「浪費」一詞,它標識著無用而感傷的歲月。就講求生活的有效性而言,詩歌確實是一種浪費,一種腐朽。1980年代的詩人們曾沉湎其間,鐘鳴的《旁觀者》其中有一節名為「恍惚及贅詞」。有如本雅明筆下的「遊蕩者」,在人群中,他們是恍惚的;對於人群而言,他們同樣是不合時宜的贅詞。1980年代的詩人們,誇張著寫作、生活、甚至苦難。他們的真實性,可能在於心懷理想,那消失得太快的理想。詩人萬夏曾宣稱:「僅我腐朽的一面╱就夠你享用一生」。(《本質》)然而,一生還是太長了點兒吧?或者太短了點兒呢?
1
「我們本來就是╱腰間掛著詩篇的豪豬」,(李亞偉《硬漢們》)1980年代速速逝去,詩人和他們的詩句留在層次不齊的選本中,偶爾也鐫刻在某些人心中的某些地方,某些時刻被激起,讓他們聊發一下少年狂。然而很快,豪豬們的詩篇,再也無法逼迫女子們「掏出藏得死死的愛情」。( 李亞偉《硬漢們》)時代和詩人的愛情結束得太快,抑或從未開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漢語詩歌所構造的諸多語境,都有某種掙脫事境引力以求失重飛升的欲望。」詩人們滿懷著對飛翔的熱情與自信,站在高處,張開雙臂……然後,跌落?暫停!卡通片中,最經典的一幕是:「一隻鎮定自若地走在懸崖上的貓,只是在朝下看、發現自己是懸空時才墜落。」張開雙臂飛翔的詩人們,在看到他們腳底的深淵之前,並沒有跌落。或者說,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死亡,在「飛翔」的時候。齊澤克(Slavoj Zizek)從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那裡得出「精神的無聲編織」,即「關鍵意識總是來得太遲,它總是在傳染病已經控制整個領域之後,才知道自己已經無立足之地。」對1980年代的諸多詩人來說,情形的確如此。
張棗談到多年前女友離開自己和一個做生意的人好,他當時還很不屑。只有在多年後,在越來越實際的世界中,詩歌的虛弱再無立足之地,詩人和他們的詩歌才迎來第二次死亡:意識到懸崖,意識到第一次早已發生的死亡。該如何看待那已踩空的懸崖、閉著眼睛的飛翔,那在兩次死亡之間短暫而虛幻的歡愉?卡通片中,這一切引人開懷大笑。在現實中,也許是以肉體的死亡,來祭奠那早已死去、卻遲遲未被察覺的理想之死,這是極端。更多的可能是,人們依然像看卡通片一樣來看待這場聲勢浩大的、荒謬的飛翔,包括那些曾參與其中的人:「晚間新聞在深夜又重播了一遍,╱其中有一則訃告:死者是第二次╱死去。」(歐陽江河《晚餐》)。死亡本身是悲劇,宣告,且一再重複的宣告,則是一次次的消解。悲劇到來時人們未曾察覺,還陶醉於死的舞臺中上演生;那麼當他們意識到悲劇時,究竟該為悲劇而悲傷,還是為自己曾經對悲劇的毫無意識而感到荒誕呢?多年後,當年的「莽漢」之一,遠在海外的胡冬如是寫道:
詩,本是在牢籠中創造大雁。
哪裡!生活是老虎,詩才是籠子。
一夥人爭執著,踅向自我的舞臺,
穿的是小丑的紈褲,或鶉結的囚衣
(胡冬《給任何人》四)
1988年徐敬亞主編的《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裡,有名無實或有實無名的各色詩歌團體,被呈現於眾。有些人們還記得,或者在各類文學史中被一筆帶過:「朦朧」、「非非」、「莽漢」、「他們」……還有一些,幾乎被時間所淹。翻開目錄,一些奇特的名稱躍然紙上:「男性獨白」、「悲憤詩人」、「特種兵」、「闡釋俱樂部」……瑪律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在《流放者歸來》中,談到被稱為「迷惘的一代」的藝術家們,他這樣評價他們和他們所信奉的個人主義教條:「個人主義生活方式甚至產生不出具有個性的人。藝術家們在逃避社會上的千篇一律時,很可能採取千篇一律的逃避途徑並按照自己小集團的常規辦事;甚至他們的反常舉止也屬於固定的類型;甚至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所患的精神病也都合乎既定的模式。」青春的力比多讓詩人們個性張揚,爭執著表現自己,詩歌淪為他們自身的牢籠。詩人們用「莽漢」的高音或「非非」的異調,發出自由的呼聲,卻不過是牢籠中誇張的表演。嚮往個性與自由的詩歌,最後成為千篇一律的語言牢籠。那些已經被時間淹沒、或正在被時間淹沒的東西,實際上早已死亡,在它們踅向所謂個性的舞臺之時。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寫作正是一種自由和記憶之間的妥協物,它就是這種有記憶的自由,即只是在選擇的狀態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續過程中已經不再是自由的了。」人們習慣於把1980年代稱為理想主義的年代,它的終結被看作理想主義的死亡。就像自由的語言成為束縛自身的牢籠後,還慣性地維護自己作為自由化身的身份;理想主義也早已死亡,在人們意識到之前,它還在慣性的維持中:
有關大雁塔
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麼
有很多人從遠方趕來
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還來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
也有有種的往下跳
在臺階上開一朵紅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當代英雄
(韓東《有關大雁塔》)
或者為早已死去的理想而殉死,成為「當代英雄」,即使這樣,仍不免被誤讀;或者消解理想,消解記憶中的崇高。有關1980年代的軼聞很多,詩歌的噱頭、詩人的噱頭,甚至苦難和死亡也不免淪為噱頭。海子之死、顧城之死被賦予了多少意義或無意義?人們總是想闡釋,然後生成意義,而不僅僅是敘述。在談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因為邊防官拒不承認通邊簽證而自殺時,阿倫特(Hannah Arendt)寫道:「早一天本雅明就能輕易地通過;晚一天馬賽的美國官員就會得知難民暫時還無法穿過西班牙。不早不晚偏偏在那一天災難才可能發生。」僅僅是敘述,這個一生讓駝背小人盯上、無法擺脫厄運之人的悲劇就悄無聲息地呈現了,沒有煽情,卻讓人震撼。顧城去世之前,在發表過的一篇演講中說:「殺與被殺都是一種禪的境界」,於是有了某些人「故作高深,大談什麼詩人之死是入禪得道,是驚世駭俗的殉美之舉」,死亡還要被賦予多少更可怕的東西?苦難也同樣被作噱頭。貴州詩人黃翔最傳奇的故事是:把詩藏在蠟燭裡。鐘鳴說:「貴州『朦朧詩』,後來令人痛心地,而無法挽回地毀於困獸鬥,也毀於缺乏同一性―還有啟蒙主義的激進,好鬥。」誇大苦難,誇大自己抗爭的細節:
我是一隻被追捕的野獸
我是一隻剛捕獲的野獸
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
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
(黃翔《野獸》)
鐘鳴稱之為「虛假意識形態的人格化」,世界和「我」在絕對的敵意與對立中。且不論將詩稿藏在蠟燭裡有多少可信度,人們去推崇與迷信這個故事,就在轉化與消解苦難。弄些「擢升為時疫的辭令」,(胡冬《筮書》)不過是為了推銷苦難。柏樺的《鐘斯敦》曾讓太多人狂熱地感染「時疫」:「這革命的一夜╱來世的一夜╱人民聖殿的一夜」。多年後在一次訪談中,鐘鳴談到柏樺和他的詩歌,提到「錯裂」一詞。語言與身體的分裂。當「革命」煽動讀者,甚至詩人自己的情緒時,「革命」包含多少真實性,又包含多少修辭成份?在被言說的苦難與真實的苦難之間,有多大的距離?齊澤克所謂的「美麗心靈」不正是如此嗎?「不停地為世界的殘酷而難過,它自己也深受其害,因為世界的殘酷使它的好意無法實現」。然而「美麗心靈」也是造成自己所抱怨世界的幫兇:「我必須失敗,必須受到沉重打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表明我有理由控訴我的敵人」。為了控訴,或者裝飾:「當初,╱對成份談虎色變,現在,祖先的忌諱成為了╱墊壓,像黑人轎車裡的豹紋坐套」。(胡冬《給任何人》八)在2010年新版《畜界•人界》序言裡,鐘鳴說:「要論詩歌的進步,除了『詞』的勝利,就人性方面,我看是非常晦暗的,有如骨鯁在喉。」在荊軻那裡,「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是一種完全身體化的語言,他的行為完成了詩意。「美麗心靈」們的詞彙,則在被害妄想症或受虐狂心態中,離人們本該身體力行去實現的「美麗世界」越來越遠……
(下略)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