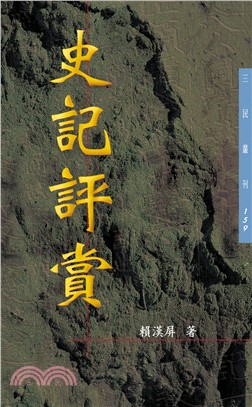九月殘陽:往事記憶三部曲最終章(電子書)
商品資訊
定價
:NT$ 340 元優惠價
:70 折 238 元
閱讀器:書紐電子書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7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武漢,從來沒一日平靜
黃雙林好不容易回到武漢,成為鋼鐵廠工人,結果不僅身陷險境,更目睹周圍一個個工人在苦悶又危險的日常中掙扎――將自己「睡」進武漢鋼鐵的壞女人;嗅聞妻子內褲判斷是否戴綠帽的工段長;為添補家用幫人組裝收音機,卻收聽到臺灣電臺而被批判、被老婆暴打的工人;為改善家計娶了臉上有胎記的長官獨女,雖一路騰達,卻婚外情不斷;因乾兒子發現同志戀情、公然因「雞姦罪」被批鬥,而上吊的男人――這些往事記憶,沾染塵世煙雨,而擁有了靈魂……
往事記憶三部曲最終篇
出身於武漢工人村的中學生,在文化大革命初始成為紅衛兵,經歷上山下鄉的知青,終於返回武漢並成為鋼鐵廠工人,直面底層百姓的悲歡,寫下文革十年的荒誕荒謬荒唐。
黃雙林好不容易回到武漢,成為鋼鐵廠工人,結果不僅身陷險境,更目睹周圍一個個工人在苦悶又危險的日常中掙扎――將自己「睡」進武漢鋼鐵的壞女人;嗅聞妻子內褲判斷是否戴綠帽的工段長;為添補家用幫人組裝收音機,卻收聽到臺灣電臺而被批判、被老婆暴打的工人;為改善家計娶了臉上有胎記的長官獨女,雖一路騰達,卻婚外情不斷;因乾兒子發現同志戀情、公然因「雞姦罪」被批鬥,而上吊的男人――這些往事記憶,沾染塵世煙雨,而擁有了靈魂……
往事記憶三部曲最終篇
出身於武漢工人村的中學生,在文化大革命初始成為紅衛兵,經歷上山下鄉的知青,終於返回武漢並成為鋼鐵廠工人,直面底層百姓的悲歡,寫下文革十年的荒誕荒謬荒唐。
作者簡介
王繼
前三十多年一直生活在武漢,後遷居重慶,在重慶生活也已近三十年了。蹉跎中,年近古稀。
上世紀六○年代在鄂西大山裡做了幾年知青,七○年代初,招工到武漢鋼鐵公司煉鐵廠做了八年的一線鋼鐵工人。雖是初中畢業,學生時代基本沒讀過書。或許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八○年代末,考入武漢大學作家班。
上世紀七、八○年代出版發表長篇中篇短篇小說若干,按字數計應在百萬以上。但羞於提到這些小說,因很大一部分是爲「稻梁謀」的利益之作。雖然其中也有略可一讀的《我就是第三者――也是愛情的故事》(長篇小說)和《六個古怪的世界》(中篇小說)。
停筆二十幾年後,受野夫蠱惑,重拾舊業。二○一七年,台灣南方家園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小說《八月欲望》、《六月悲風》和這部《九月殘陽》,才覺得終於掙脫了利益、心靈的羈絆,寫出了令自己比較滿意,也不會受良心良知折磨的長篇小說。
前三十多年一直生活在武漢,後遷居重慶,在重慶生活也已近三十年了。蹉跎中,年近古稀。
上世紀六○年代在鄂西大山裡做了幾年知青,七○年代初,招工到武漢鋼鐵公司煉鐵廠做了八年的一線鋼鐵工人。雖是初中畢業,學生時代基本沒讀過書。或許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八○年代末,考入武漢大學作家班。
上世紀七、八○年代出版發表長篇中篇短篇小說若干,按字數計應在百萬以上。但羞於提到這些小說,因很大一部分是爲「稻梁謀」的利益之作。雖然其中也有略可一讀的《我就是第三者――也是愛情的故事》(長篇小說)和《六個古怪的世界》(中篇小說)。
停筆二十幾年後,受野夫蠱惑,重拾舊業。二○一七年,台灣南方家園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小說《八月欲望》、《六月悲風》和這部《九月殘陽》,才覺得終於掙脫了利益、心靈的羈絆,寫出了令自己比較滿意,也不會受良心良知折磨的長篇小說。
序
王繼先生的《九月殘陽》,以其親歷,揭示了中國産業工人在一九七○年代的存在本相。這既非傳統左翼普羅文學的敘事,亦非現代企業生態之描摹。他是在回顧中審視他那一代所謂的「工人階級」的命運――名譽上的領導階級,實際上的底層勞工的卑微生活。華語文壇已經很久無人紀錄這類題材,更已荒疏了對那一時代的記憶。而本書正好填補了這一缺失,讓我們得以深刻瞭解那些埋沒於煙塵礦渣後的工人歷史……
─作家 野夫
王繼的小說,帶著觸感。彷彿那些沸騰的鐵漿,那熱血而寂寞的青春的盲動,那狂躁吶喊的理想,都是人性最底層的湧動。那湧動的觸感,就是王繼的文學之心。
─作家 楊渡
王繼將工業這部大機器作為上演人生悲喜劇的舞臺。這個舞臺冷漠、恢弘,不可控制,而且在工業機器本身龐大之外,他顯然更加明確地知道,恢弘的高爐以及沒完沒了的工作,看上去有著它們自己的生命和運作邏輯,但意識形態才是這部機器唯一的靈魂(……)王繼斜眼觀察著在這個無比壓抑、有著濃重暗調的舞臺上,那些被機器無情拖曳的生靈和被意識形態隨意拋擲的生命,他們既受控於工業生產的一系列嚴密機械化編制,人人被固定於一個崗位或一個工種,又受控於廣播喇叭裡隨時傳出的批鬥命令或開會通知,還受控於拮据的經濟和貧困乏味的生活。
─文學評論家 唐雲
人們在沾沾自喜於當今權貴劃分蛋糕遺漏的粉沫時,似乎早已遺忘了那段肉體被毀滅、精神被蹂躪的苦難經歷。其實,死亡和蹂躪離我們並不遙遠,作家王繼還記憶猶新,八年武鋼工人生活的一幕幕圖像,隨著歲月的磨洗,變得愈來愈清晰。他一邊回望,一邊書寫,用浸染血淚的文字,記錄著武鋼工人黃雙林和他的同事們,慘遭身心蹂躪的真實鏡像,以及他們在困頓境遇中的愛情糾葛、婚姻瑣碎和喜怒哀樂。
─文學評論家、作家 黃自華
─作家 野夫
王繼的小說,帶著觸感。彷彿那些沸騰的鐵漿,那熱血而寂寞的青春的盲動,那狂躁吶喊的理想,都是人性最底層的湧動。那湧動的觸感,就是王繼的文學之心。
─作家 楊渡
王繼將工業這部大機器作為上演人生悲喜劇的舞臺。這個舞臺冷漠、恢弘,不可控制,而且在工業機器本身龐大之外,他顯然更加明確地知道,恢弘的高爐以及沒完沒了的工作,看上去有著它們自己的生命和運作邏輯,但意識形態才是這部機器唯一的靈魂(……)王繼斜眼觀察著在這個無比壓抑、有著濃重暗調的舞臺上,那些被機器無情拖曳的生靈和被意識形態隨意拋擲的生命,他們既受控於工業生產的一系列嚴密機械化編制,人人被固定於一個崗位或一個工種,又受控於廣播喇叭裡隨時傳出的批鬥命令或開會通知,還受控於拮据的經濟和貧困乏味的生活。
─文學評論家 唐雲
人們在沾沾自喜於當今權貴劃分蛋糕遺漏的粉沫時,似乎早已遺忘了那段肉體被毀滅、精神被蹂躪的苦難經歷。其實,死亡和蹂躪離我們並不遙遠,作家王繼還記憶猶新,八年武鋼工人生活的一幕幕圖像,隨著歲月的磨洗,變得愈來愈清晰。他一邊回望,一邊書寫,用浸染血淚的文字,記錄著武鋼工人黃雙林和他的同事們,慘遭身心蹂躪的真實鏡像,以及他們在困頓境遇中的愛情糾葛、婚姻瑣碎和喜怒哀樂。
─文學評論家、作家 黃自華
目次
推薦序 唐雲
隨時隨地的誰……――序《九月殘陽》兼論王繼的整體敘事
正文
九月殘陽
跋 黃自華
在歷史的廢墟上,祭奠被碾壓的亡靈――讀王繼長篇小說《九月殘陽》
跋 任樹德
作家王繼
後記
隨時隨地的誰……――序《九月殘陽》兼論王繼的整體敘事
正文
九月殘陽
跋 黃自華
在歷史的廢墟上,祭奠被碾壓的亡靈――讀王繼長篇小說《九月殘陽》
跋 任樹德
作家王繼
後記
書摘/試閱
溫寧靜望著我,很真誠也很天真地對我說:「我真的很認命,真的。」她說她的霉運,似乎與生俱來,躲是躲不脫的。她撩起兩鬢的短髮讓我看:「夾的。你看嘛,我媽生我時難產,是醫生用產鉗強行把我夾了出來。」我對女人生孩子、對產鉗都毫無概念,而且對她的話我有些愕然,有些不太適應。不過,我還是順著她的意思,朝她撩起短髮後的兩鬢看去,她的兩鬢有種人為的很均衡的平整,頭髮撩起後,頭的上部也因此顯得有點方正。她放下短髮,繼續說道:「看過食堂夾包子的夾子吧?產鉗就像那種夾子。我就是被醫生用這種東西從我媽子宮裡硬扯出來的。我媽因生我差點死了,後來他們又擔心我被產鉗夾成了傻子……」食堂夾包子饅頭的夾子,我當然見過,一塊竹片從中間烤彎後形成的夾子。她語氣語調平緩平淡,毫無起伏跌宕,把一個應該有點緊張有點揪心還有點畫面感的故事,敘說得寡然無味。僅僅在她說到「子宮」二字時,我抬頭看了她一眼,她也不解地回看了我一眼。難道她不知道,除了在專業場合,沒人會隨意說出這兩個字。如果不是「子宮」,如果不是她撩起短髮讓我看她的兩鬢,又伸出食指和中指做了夾鉗樣,又告訴我產鉗就像食堂夾包子饅頭的竹夾子,或許我對這個故事、對她的霉運說不會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我一直都沒明白,就在我要離開一號皮帶運輸機、溫寧靜即將頂崗的前幾天,下了白班的我和溫寧靜順著小路回單身宿舍時,她為什麼要停下腳步,站在鐵軌中間的枕木上,給了我說這麼多話?我們後來的交往中,我發現她並不愛說話,甚至可以說是寡言少語。她也極少談及她的父母、她的家人。我的記憶和印象中,溫寧靜一次說了這麽多話,透露出她與她母親的這麽多信息,應該是個意外。
溫寧靜是作為原料車間工人,招進煉鐵廠的,但她一進廠就被借調到廠廣播站了,沒在原料車間幹過一天活。雖然她比我早進廠幾個月,但又比我晚了近一年才回到原料車間。如果軍代表不走,溫寧靜還應該是廠廣播站的播音員。不認識她以前,只要到廠食堂吃飯,就能聽見她播音。她的普通話還算標準,偶爾讀到「樓」、「綠」、「六」、「路」這類字眼時,如果對讀音比較敏感的話,能察覺到她是武漢人,而且是家住漢口的武漢人。她的音域比較窄,肺活量似乎也不足,聲音就顯得尖細,尾音尖細到從喇叭裡傳出來時,人們會擔心風把這顫巍巍的聲音給吹折了。她不是一個合格的播音員,大家也知道她不是一個合格的播音員,就連馬軍代表,也明白她不是個好播音員,凡是廠裡召開大會和批判大會,領呼口號的,一定是另一個男播音員。不具備一個播音員的條件而成了播音員,似乎就坐實了她是跟軍代表睡覺睡成播音員的傳言。這種傳言畢竟離我比較遠,我興趣不大,她成了播音員是睡來的還是別的方式得來的,好像跟我沒啥關係。再者說,我也不太適應別人說軍代表的壞話,我能進煉鐵廠當工人,不也是因為吳軍代表的幾句話麼?
一九七二年年初,林彪事件發生幾個月以後,軍宣隊和軍代表們陸續撤出了煉鐵廠。軍代表大規模撤離前,馬軍代表就已離開了煉鐵廠,他被他隨軍的老婆捉姦在床,提前調回了部隊,未久,脫下軍裝,轉業去了地方上工作。消息傳來,煉鐵廠上下一遍唏噓,一個戰鬥英雄,就這樣倒在壞女人的胯下。軍代表們離廠,我能立即感覺到的變化是,我們業餘時間的軍訓和拉練沒了、各種軍事化稱謂變了,一高爐是一高爐,不再是一連了,原料車間也不再是八連,仍叫原料車間。廠長不再是團長,車間主任也就不再是連長,工段長也不是排長了。去廠食堂吃飯,如果不是有人提醒,我沒注意到廠播音員換了人。這應該也算是一個變化。駐足認真聽了一下,這新女播音員好像並不比溫寧靜高明多少。這一切與我無關的變化,讓我想到樣板戲《沙家濱》裡的唱詞:人一走,茶就涼。萬萬沒想到,當田班長把溫寧靜領到棧橋我工作的一號皮帶運輸機旁時,這變化竟與我有了直接關係。濃煙塵霧中,皮帶運輸機的「哢哢」和「嗡嗡」的嘈雜運轉聲音中,田班長摘下豬八戒面罩式的防塵口罩,提高嗓門,吼著對我說:「黃雙林,溫寧靜就交給你來帶了……」這消息來得突兀,讓我發懵。但班長的話還沒說完,就聽到不遠處傳來野蠻霸道充滿侵略性的「砰」的一聲巨響,把田班長的話截斷了,三個面對面的人,霎時就看不見對方了,從頭頂房梁鋼梁上震落下來的各種粉塵,形成了一道道塵幔,好不容易睜開眼睛,我們眼前依然只是淡褐色比麵粉還細密的燒結礦粉塵。
塵埃終於落定,田班長邊「呸呸」吐著口中的粉塵,邊繼續對我說:「黃雙林,這是車間安排的,小溫交給你帶,小溫能頂崗了,你就到棧橋下面開稱量車去。」我的耳朵仍嗡嗡響著,我要去開稱量車了,而接替我的還是溫寧靜?我興奮得不知說什麼好,就一個勁地朝田班長猛點頭。田班長甩甩豬八戒面罩似的口罩,抖著上面的粉塵,開口罵了一句:「我操!連他媽的一九五八年的粉塵都給震下來了。」罵完,戴上口罩,走了。一九五八年是一高爐出第一爐鐵水的日子,也是整個煉鐵廠正式開工生產的日子。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十四年了,溫寧靜回到原料車間正式上崗的第一天,就沐浴在十四個年頭積攢下來的礦石粉塵中。這注定不是她的幸運日,卻是我的幸運日。她的到來,我離開一號皮帶運輸機就開始倒數計時了。
皮帶工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工種,稱為熟練工。雖然說師傅要帶一個月,我才能獨立操作,但僅僅一週,我就開始獨立操作,能熟練地操縱卸料機把皮帶運輸機運來的焦炭裝進焦炭倉裡。熟練工的壞處是,幹一輩子也沒掌握任何技藝;好處是,三個月的實習期一過,就是月領三十七塊多錢的一級工,一年後,就是四十二塊多錢的二級工。然後,很多年裡就一直是二級工。我離開煉鐵廠時,仍舊還是個二級工。我想,溫寧靜再笨,一、二十天足可以操控一號皮帶和裝卸機了。
溫寧靜嶄新的細白帆布工作服工作帽上,落滿了淡棕色的燒結礦粉塵,一個豬八戒面罩似的防塵口罩遮住大半個臉,她不說話,很難發現她是個女人。田班長剛走,她摘下口罩,邊用手去拂臉上的粉塵,邊問我:「黃師傅,是哪裡發生了爆炸?」我有點奇怪,你不關心詢問我怎麼安排你的工作,卻來關心那聲巨響?工作在萬千機械聲響匯聚的鼎沸中,每天聽幾聲巨響,真不算一個事。我不由瞥了她一眼,這是我正式看她的第一眼。我一直不太好意思看她,我聽到的傳言議論,溫寧靜雖然長得狐狸精似的漂亮,但道德敗壞,為了被招工,睡了她下鄉插隊的公社書記,為了當廠廣播員,又睡了馬軍代表,害得馬軍代表轉業,是個壞女人。溫寧靜沒經驗,剛才用手而沒用圍在脖頸上的毛巾去擦臉,臉被手抹得黑一塊灰一塊,我看不出她的本來面目,也就無法判斷她長得像不像個狐狸精。她那雙不大也不小、細長的黑幽幽眼睛,也並不飛轉流動、顧盼生輝,竟和她的名字一樣,有點寧靜。這很出乎我的意料。她的牙很白,但這並不稀奇,原料車間的人上班時摘了口罩,沒幾個牙不白的。這和黑人顯得牙齒特別白,是一個道理。
不知道為什麼,雖然我詫異,甚至不瞭然溫寧靜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詢問那一聲爆炸來自哪裡,我還是在吃午飯時,把事情的原委弄得清清楚楚,並且馬上講給她聽。是二高爐的那個大火炬,也就是發散閥爆炸發出的巨響,原因麼,可能是粉塵太多太密集引起的爆炸。她沒說話,黑幽幽的眼睛望著我,點了點頭,似乎是感謝的意思。壞女人,肯定和「地富反壞右」的敵我矛盾有區別,應該算人民內部矛盾。領導沒有交待,我也拿捏不準應對溫寧靜這個壞女人的分寸。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子,實在有些討好她的嫌疑。我也想做出副冷淡厭棄她的姿態,甚至我也努力了,不知為什麼就是做不到。一則,因為我要帶她儘快掌握工作流程,我也好儘快離開;二則麼,就因為她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喜歡漂亮的女子,是我性格上最大的缺陷和弱點。原料車間三百多人,加上溫寧靜也就五個女工,其中三個還是調度員,調度員跟廣播員相似,守著電話、麥克風,調度協調著棧橋上下的生產。全車間只有兩個女皮帶工,曾丁丁是主動要上生產一線,而溫寧靜做皮帶工,自然是作為懲罰。高爐比原料車間更慘,四座高爐,幾百號爐前工,就從來沒有過一個女爐前工。壞女人也畢竟是女人。
我跟唐小妖說,只一眼,我就喜歡上了溫寧靜那雙眼睛,那眼睛,黑幽幽的清澈。唐小妖撇撇嘴,罵我道:「你就是個大騷貨!黑幽幽、黑幽幽,那是個無底洞,小心掉進去,爬都爬不出來。」
我一直都沒明白,就在我要離開一號皮帶運輸機、溫寧靜即將頂崗的前幾天,下了白班的我和溫寧靜順著小路回單身宿舍時,她為什麼要停下腳步,站在鐵軌中間的枕木上,給了我說這麼多話?我們後來的交往中,我發現她並不愛說話,甚至可以說是寡言少語。她也極少談及她的父母、她的家人。我的記憶和印象中,溫寧靜一次說了這麽多話,透露出她與她母親的這麽多信息,應該是個意外。
溫寧靜是作為原料車間工人,招進煉鐵廠的,但她一進廠就被借調到廠廣播站了,沒在原料車間幹過一天活。雖然她比我早進廠幾個月,但又比我晚了近一年才回到原料車間。如果軍代表不走,溫寧靜還應該是廠廣播站的播音員。不認識她以前,只要到廠食堂吃飯,就能聽見她播音。她的普通話還算標準,偶爾讀到「樓」、「綠」、「六」、「路」這類字眼時,如果對讀音比較敏感的話,能察覺到她是武漢人,而且是家住漢口的武漢人。她的音域比較窄,肺活量似乎也不足,聲音就顯得尖細,尾音尖細到從喇叭裡傳出來時,人們會擔心風把這顫巍巍的聲音給吹折了。她不是一個合格的播音員,大家也知道她不是一個合格的播音員,就連馬軍代表,也明白她不是個好播音員,凡是廠裡召開大會和批判大會,領呼口號的,一定是另一個男播音員。不具備一個播音員的條件而成了播音員,似乎就坐實了她是跟軍代表睡覺睡成播音員的傳言。這種傳言畢竟離我比較遠,我興趣不大,她成了播音員是睡來的還是別的方式得來的,好像跟我沒啥關係。再者說,我也不太適應別人說軍代表的壞話,我能進煉鐵廠當工人,不也是因為吳軍代表的幾句話麼?
一九七二年年初,林彪事件發生幾個月以後,軍宣隊和軍代表們陸續撤出了煉鐵廠。軍代表大規模撤離前,馬軍代表就已離開了煉鐵廠,他被他隨軍的老婆捉姦在床,提前調回了部隊,未久,脫下軍裝,轉業去了地方上工作。消息傳來,煉鐵廠上下一遍唏噓,一個戰鬥英雄,就這樣倒在壞女人的胯下。軍代表們離廠,我能立即感覺到的變化是,我們業餘時間的軍訓和拉練沒了、各種軍事化稱謂變了,一高爐是一高爐,不再是一連了,原料車間也不再是八連,仍叫原料車間。廠長不再是團長,車間主任也就不再是連長,工段長也不是排長了。去廠食堂吃飯,如果不是有人提醒,我沒注意到廠播音員換了人。這應該也算是一個變化。駐足認真聽了一下,這新女播音員好像並不比溫寧靜高明多少。這一切與我無關的變化,讓我想到樣板戲《沙家濱》裡的唱詞:人一走,茶就涼。萬萬沒想到,當田班長把溫寧靜領到棧橋我工作的一號皮帶運輸機旁時,這變化竟與我有了直接關係。濃煙塵霧中,皮帶運輸機的「哢哢」和「嗡嗡」的嘈雜運轉聲音中,田班長摘下豬八戒面罩式的防塵口罩,提高嗓門,吼著對我說:「黃雙林,溫寧靜就交給你來帶了……」這消息來得突兀,讓我發懵。但班長的話還沒說完,就聽到不遠處傳來野蠻霸道充滿侵略性的「砰」的一聲巨響,把田班長的話截斷了,三個面對面的人,霎時就看不見對方了,從頭頂房梁鋼梁上震落下來的各種粉塵,形成了一道道塵幔,好不容易睜開眼睛,我們眼前依然只是淡褐色比麵粉還細密的燒結礦粉塵。
塵埃終於落定,田班長邊「呸呸」吐著口中的粉塵,邊繼續對我說:「黃雙林,這是車間安排的,小溫交給你帶,小溫能頂崗了,你就到棧橋下面開稱量車去。」我的耳朵仍嗡嗡響著,我要去開稱量車了,而接替我的還是溫寧靜?我興奮得不知說什麼好,就一個勁地朝田班長猛點頭。田班長甩甩豬八戒面罩似的口罩,抖著上面的粉塵,開口罵了一句:「我操!連他媽的一九五八年的粉塵都給震下來了。」罵完,戴上口罩,走了。一九五八年是一高爐出第一爐鐵水的日子,也是整個煉鐵廠正式開工生產的日子。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十四年了,溫寧靜回到原料車間正式上崗的第一天,就沐浴在十四個年頭積攢下來的礦石粉塵中。這注定不是她的幸運日,卻是我的幸運日。她的到來,我離開一號皮帶運輸機就開始倒數計時了。
皮帶工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工種,稱為熟練工。雖然說師傅要帶一個月,我才能獨立操作,但僅僅一週,我就開始獨立操作,能熟練地操縱卸料機把皮帶運輸機運來的焦炭裝進焦炭倉裡。熟練工的壞處是,幹一輩子也沒掌握任何技藝;好處是,三個月的實習期一過,就是月領三十七塊多錢的一級工,一年後,就是四十二塊多錢的二級工。然後,很多年裡就一直是二級工。我離開煉鐵廠時,仍舊還是個二級工。我想,溫寧靜再笨,一、二十天足可以操控一號皮帶和裝卸機了。
溫寧靜嶄新的細白帆布工作服工作帽上,落滿了淡棕色的燒結礦粉塵,一個豬八戒面罩似的防塵口罩遮住大半個臉,她不說話,很難發現她是個女人。田班長剛走,她摘下口罩,邊用手去拂臉上的粉塵,邊問我:「黃師傅,是哪裡發生了爆炸?」我有點奇怪,你不關心詢問我怎麼安排你的工作,卻來關心那聲巨響?工作在萬千機械聲響匯聚的鼎沸中,每天聽幾聲巨響,真不算一個事。我不由瞥了她一眼,這是我正式看她的第一眼。我一直不太好意思看她,我聽到的傳言議論,溫寧靜雖然長得狐狸精似的漂亮,但道德敗壞,為了被招工,睡了她下鄉插隊的公社書記,為了當廠廣播員,又睡了馬軍代表,害得馬軍代表轉業,是個壞女人。溫寧靜沒經驗,剛才用手而沒用圍在脖頸上的毛巾去擦臉,臉被手抹得黑一塊灰一塊,我看不出她的本來面目,也就無法判斷她長得像不像個狐狸精。她那雙不大也不小、細長的黑幽幽眼睛,也並不飛轉流動、顧盼生輝,竟和她的名字一樣,有點寧靜。這很出乎我的意料。她的牙很白,但這並不稀奇,原料車間的人上班時摘了口罩,沒幾個牙不白的。這和黑人顯得牙齒特別白,是一個道理。
不知道為什麼,雖然我詫異,甚至不瞭然溫寧靜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詢問那一聲爆炸來自哪裡,我還是在吃午飯時,把事情的原委弄得清清楚楚,並且馬上講給她聽。是二高爐的那個大火炬,也就是發散閥爆炸發出的巨響,原因麼,可能是粉塵太多太密集引起的爆炸。她沒說話,黑幽幽的眼睛望著我,點了點頭,似乎是感謝的意思。壞女人,肯定和「地富反壞右」的敵我矛盾有區別,應該算人民內部矛盾。領導沒有交待,我也拿捏不準應對溫寧靜這個壞女人的分寸。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子,實在有些討好她的嫌疑。我也想做出副冷淡厭棄她的姿態,甚至我也努力了,不知為什麼就是做不到。一則,因為我要帶她儘快掌握工作流程,我也好儘快離開;二則麼,就因為她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喜歡漂亮的女子,是我性格上最大的缺陷和弱點。原料車間三百多人,加上溫寧靜也就五個女工,其中三個還是調度員,調度員跟廣播員相似,守著電話、麥克風,調度協調著棧橋上下的生產。全車間只有兩個女皮帶工,曾丁丁是主動要上生產一線,而溫寧靜做皮帶工,自然是作為懲罰。高爐比原料車間更慘,四座高爐,幾百號爐前工,就從來沒有過一個女爐前工。壞女人也畢竟是女人。
我跟唐小妖說,只一眼,我就喜歡上了溫寧靜那雙眼睛,那眼睛,黑幽幽的清澈。唐小妖撇撇嘴,罵我道:「你就是個大騷貨!黑幽幽、黑幽幽,那是個無底洞,小心掉進去,爬都爬不出來。」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