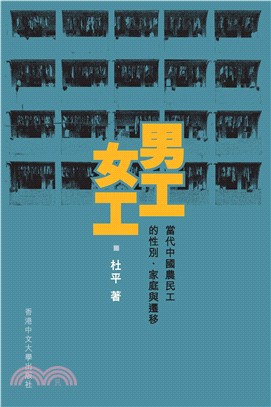男工‧女工: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性別、家庭與遷移(電子書)
商品資訊
定價
:NT$ 540 元優惠價
:
70 折 378 元
閱讀器:書紐電子書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1 點
商品簡介
商品簡介
農民工的興起,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具影響力的社會變革之一。本書與以往的農民工研究不同,作者基於對其群體分化與差異的認識,打破將之視為鐵板一塊的研究取向,不止停留在對女性工廠經驗的關注上,而是進一步從性別的角度分別探討男工與女工在工廠內外的生活,並且檢視他們在城鄉遷徙過程中性別身份與家庭身份的變化。作者對農民工生活處境進行了深入的民族誌研究。他們的故事,揭示了個體所體驗的緊張與憂戚,承載著家庭渴望改變命運的訴求和努力,也透視出社會轉型和結構變遷中深層次的矛盾。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