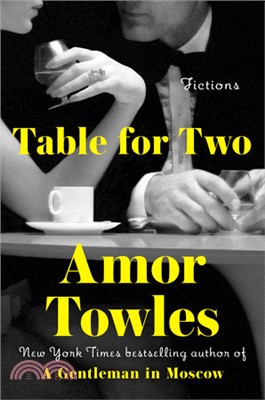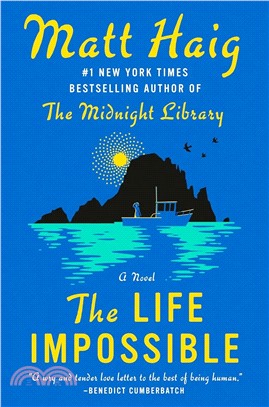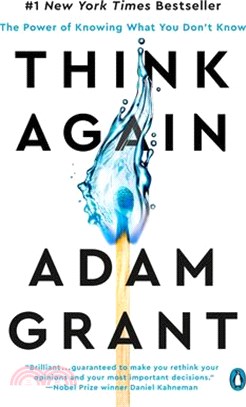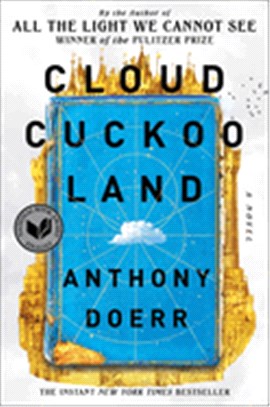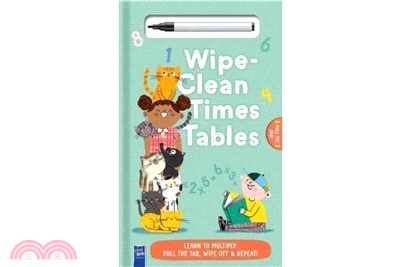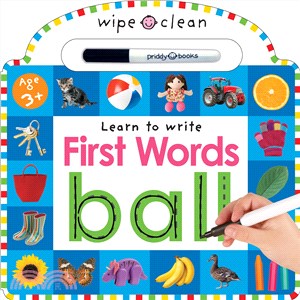商品簡介
這些故事,都是台灣文化的縮影……
躁動、創新,無法維持現狀,卻也不斷前進──
台灣的每一代人都覺得台灣要完蛋了。
但是沒有,經歷戰亂、殖民、產業外移,政治邊陲化等,台灣存活下來。
走過殖民時期的南投鹿谷小村,到近代的富足科技島,
即使年代不同,每一代的台灣人卻都同樣經歷恐慌狀態──
日本殖民時期,以為會被殺或被奴役;光復後,擔憂共軍血洗台灣;
歷經中美斷交、被趕出聯合國,移民潮大舉;
千禧年憂慮被邊陲化,並成為人人口中的「鬼島」。
但,在這些巨大的轉變中,肯定也有許多英雄存在,
只是人們從未多加留意。
本書從鹿谷山村中的林家談起,藉由山中小村落的家族歷史,牽起流傳在漢族社會的諸多傳說,有暗中進行的反動運動,戰火下的戀情與逃難,以及漫長且持續的族群撕裂。但無論時間變遷,或世代如何更迭,還有一群人,低調而努力、精采且忙碌的活著,並在亂世中,呼應神奇的召喚,走向未知的旅程,找到一絲生活的樂趣與尊嚴。
--
林宜敬本人經歷了七○年代的少棒與青少棒熱潮、搖滾樂與嬉皮、巴布迪倫、民歌時代、八○年代學生運動,最後出國留學成為電腦科技業專家。書中所記述的丁家與林家親族三代人的故事,無異是台灣近百年歷史的縮影。
──陳翠蓮|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宜敬董事長,不,政務次長的文筆太迷人了。真高興這樣一位多聞睿智的人才,能在入閣時出版這本好看又有價值的書。他的家族史真是迷人。這幾年,中研院台史所很重視台灣老家族的歷史研究,宜敬家族的鹿谷林家和鹿港丁家真是好題材。他的豐富經驗與邏輯思維更是厲害,台灣的百年糾葛,科技的繁複深奧,他可以三言兩語快刀斬亂麻道出台灣的價值,讓讀者進入AI的世界。他是台灣的包可華,且更廣更寬更深。
──陳耀昌|作家
林博士的文章,乍看平鋪直述,卻往往蕩氣迴腸。
丁韻仙在他健筆下,再現那段精彩而押韻的人生。
林博士的出身以及往來對象,多為仕紳,鮮有土豪。
他的筆下總能呈現一個又一個沒有說教味的故事,讓人聽完一個就想敲破一個碗,只因故事太精彩,讀者太入戲、太興奮、太讚嘆!
林博士能寫還能講。
我聽過無數博士演講,他們在演講台上,就像「屎放袂出來」的人,他們煎熬,台下更如坐牢。
林博士是異類,他的演講魅力,跟寫作實力五五拉鋸!!
──楊斯棓|《要有一個人》作者、醫師
作者簡介
林宜敬
1987年畢業於台大資訊工程系,1995年取得美國布朗大學電腦科學博士學位。曾任台大棒球隊三壘手、美國IBM華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趨勢科技新產品研發部協理、艾爾科技(MyET)創辦人暨執行長。目前則是擔任數位發展部政務次長。作品有:《流寇與創新者》
序
自序
幸福的鬼島
台灣的每一代人都覺得台灣要完蛋了。我的祖父祖母年輕的時候,日本人來了,他們以為所有的台灣人都要被殺或是被奴役,但是沒有,台灣反而因此躲過了中國在清末民初的所有戰亂。
我的父母親小時候,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既不算中國人也不算日本人,是亞細亞的孤兒,是大日本帝國中的二等公民,他們那一輩人看不到前途。但是後來二次大戰爆發,日本跟中國死傷慘重,而台灣孤懸海外,反而逃過了一劫。
我在一九六五年出生,在我小時候,我的父母那一輩都擔心共軍隨時會打過來,血洗台灣,台灣就要完蛋了。但是沒有,台灣不但躲過了中國的大躍進跟文化大革命,而且經濟也起飛了,大家的生活過得越來越好。
小學操場上的大合唱
記得一九七一年的十月十日是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週年的國慶日,台中市的市中心區到處設立了牌樓,掛滿了國旗,到處都有慶祝活動,而我當時六歲,是台中師專附小一年級的新生。我們學校舉辦了一場非常盛大的運動會,然後到了晚上,我媽媽帶我台中市中心的街上,在那略顯昏暗的街燈下看遊行,看初中生的鼓號樂隊,看高中女生的樂儀隊,看高中男生們舉火把,然後看著我那已經在讀初中的大姊跟她的同學們抬著蔣總統的照片,踏著整齊的步伐列隊而過。
接著在十月三十一日蔣中正總統的生日的那一天,我們學校將大禮堂布置成了壽堂,在講台正中央放了一幅很大的蔣總統玉照,擺了一堆像小山般的粉紅色壽桃。然後我們各個班級列隊而入,在大禮堂裡整齊劃一、莊嚴肅穆地面向講台行三鞠躬禮。
但是當那年的冬天來臨的時候,學校的氣氛忽然改變了。每天朝會升旗之後,訓導主任把全校所有一千多名的小學生留在操場上,在寒風當中學唱幾首新的愛國歌曲,一唱就是一個小時。我還記得其中一首歌的歌詞是:
領袖!領袖!偉大的領袖!
你是大革命的導師,你是大時代的舵手,
讓我們服從你的領導,讓我們團結在你的四周。
……
領袖萬歲!領袖萬歲!
我們永遠跟你走!我們永遠跟你走!
而另一首歌的歌詞是:
姑息逆流激盪,世界風雲劇變,我們要沉著,我們要堅定。
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黑暗盡頭,就是光明!
……
我們在操場上唱得慷慨激昂。但是一直要到很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那年的冬天發生了什麼事。就在那一年的十月二十五日,國慶日之後的兩個禮拜,中華民國台灣被趕出了聯合國,當時社會上人心浮動,許多有錢人覺得共產黨就要打過來了,紛紛把房子賣掉,移民美國,結果造成了房地產大跌。
當時學校把我們這些小學生們留在操場上唱愛國歌曲,然後政府在台灣的大街小巷貼滿了「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標語,其實就是急著要穩定那浮動的人心。
但是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們哪裡知道這些?我那時候只擔心自己的功課沒寫完,考試沒有考好,然後放學之後要去哪裡玩而已。還有,雖然我在操場上站得很累,但是我覺得那幾首歌都很好聽,而且蔣總統真的很偉大,他是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
防空洞上我和我的狗
一九七五年,我十歲,跟父母以及兩個姊姊住在台中市南區彰化銀行的宿舍裡。那是一間很漂亮的日本式平房,有前院,有後院,有草坪,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榻榻米房間,有許多剪裁得宜的漂亮榕樹。然後在我們家後院還有一間小倉庫,裡面住著我們家那隻黑白相間的小狗波姬。
四月六日那天是個禮拜天,吃早餐的時候,我的爸爸媽媽問我,昨天晚上睡得還好嗎?有沒有被大雷雨嚇到?我說我睡得很好,根本不知道下雨了。而我的爸爸媽媽則是跟我說,他們過了大半輩子,還沒有遇過像前一天晚上那樣的天象,雷電交加,狂風大作,好像天地就要毀滅一樣。
我當時也不以為意,吃完早餐後就帶著波姬到我家後門外面的防空洞去玩了。將近中午的時候,我的二姊突然打開了後門叫我,她跟我說:「你知道蔣總統死了嗎?你怎麼還在這邊玩?」語氣中帶著一股濃濃的訓斥意味。
我跟我的狗站在高高的防空洞上,向下望著我的姊姊,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我覺得我好像應該痛哭,好像應該感到非常的悲傷,但是卻一點感覺都沒有。這讓我覺得非常不愛國,非常的愧疚。
慌忙逃走的有錢人
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台灣斷絕外交關係,當時我讀初中二年級,那幾天晚上看電視新聞的時候,我們看到美國的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搭飛機來到台北的松山機場,跟台灣的政府官員們商定斷交事宜。電視新聞裡,台灣群情激憤,台北的大學生們在教官的帶領之下,示威抗議,群起圍攻克里斯多福的坐車,潑漆、丟雞蛋、砸爛了克里斯多福轎車上的玻璃。
當時我兩個姊姊已經在台大念書,而我的父母親坐在台中日式宿舍榻榻米上的藤椅裡,看著電視,表情凝重,不發一語。許久之後,我的母親轉頭過來跟我說:「你先不要擔心這些事情,去把書讀好吧。」
其實那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也沒有在擔心什麼,反倒是他們兩人凝重的神情讓我印象深刻,至今難忘。
同樣是要到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台灣又陷入了一波的恐慌當中,又有許多有錢人賣掉了台灣的房子,舉家移民美國,結果造成了台灣房地產的崩跌。而那些慌忙從台灣逃走的有錢人當中,有一些是我父母親的朋友。不知道他們臨走之前,有沒有跟我們的父母親道別?道別的時候,他們說了什麼?心裡又在想些什麼?而我的父母親看著他們的朋友驚慌逃走,心裡又在想什麼?
鬼島上的一家人
我的父母親帶著我跟我兩個姊姊,還有我們家的狗波姬留在台灣,日子就這樣一天又一天的過著。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我大學畢業剛退伍的時候,台灣的工廠大量外移,許多人覺得產業空洞化,所有人都要失業,台灣就要完蛋了。但是後來好像也沒有,台灣的產業居然成功升級了,電子業跟化工業成了台灣產業界的兩大支柱,人民的收入也大幅提高了。
然後在西元二○○○年之後,又有許多的台灣人覺得台灣要完蛋了,因為正當中國大陸的經濟迅速崛起,跨步前進的時候,台灣在政治上只有藍綠永無休止的惡鬥,而在經濟上,台灣又從華人經濟圈的中心變成了邊陲,整個國家幾乎都要停擺了。於是許多的台灣人都說,台灣是一個鬼島。
結果台灣完蛋了嗎?好像也沒有。在二○一九年之後,台灣不但在美中貿易戰當中存活了下來,經濟大幅成長,同時也在新冠肺炎的全球疫情當中表現亮眼。一時之間,台灣成了世界先進民主國家的模範生,這反而讓許多台灣人在心理上無法調適。
台灣真是個幸福的鬼島。
目次
推薦序
一本保存台灣家族歷史與五年級生記憶之書 陳翠蓮
自序
幸福的鬼島
輯一 幸福的鬼島
鹿谷山村中的台灣史
兩個經典到有些陳腐的鹿港愛情故事
水沙連故事集
一個回教家族吃豬肉的故事
一個台灣本土家族的二戰史
林家兄弟在日本逃難的故事
一個台灣小孩在青島成長的故事
一九四五,一個殖民地青年的中國夢
丁韻仙的故事
錢德拉之死
一個本省家庭對白色恐怖的回憶
山東流亡學生與威格納教授
台灣富豪的家庭故事
我們這個時代的千面英雄
輯二 我們的時代
台北是如何成為美食之都的?
野人咖啡與台灣的六○年代
文青的夢魘
我的同學蔡藍欽
台大棒球隊的國手學長們
註記我們這個世代的一支全壘打
三個中南半島的逃難故事
我的傾城之戀
造反者的青春回憶
民主關鍵年代下的軍旅生涯
重看霸王別姬
台灣人的時光機器
後記
我跟九十一歲父親的對話
書摘/試閱
輯一 幸福的鬼島
鹿谷山村中的台灣史
天地會與戴潮春
我們林家世居於台灣南投縣鹿谷鄉的坪仔頂村,那是一個在濁水溪南岸叢山之間的小村落,據說至今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一八六二年,戴潮春率領天地會的旁支八卦會的會眾在台灣中部造反。他在起事之前, 經常派人到各個村子裡「會香」,在大清早設置香案,上面放寶劍一柄、雞一隻。戴潮春會先率領村民們對著香案拈香,然後再由他用寶劍將雞斬成肉泥,同時要求村民們對著香案發誓:「盡忠盡義做國公,不忠不義刀下亡。」
會後,戴潮春順勢組織群眾,每一百個人設立一個「會頭」,由他賜予「烏令」一支。
戴潮春起事之後,很快地就攻下了大墩與彰化縣城。數年之內,叛軍北至大甲,南到嘉義,與清軍互有勝負。而戰亂也很快地蔓延到了南投叢山之中的坪仔頂村。
當時造反的天地會用的是紅旗,而清朝官兵用的是白旗。所以天地會的叛軍來了,坪仔頂村的村民們就插上了紅旗,同時解開辮子在前額留上頭髮,表示效忠於明朝;而官兵來了,村民們就又換上了白旗,同時剃光了前額綁上辮子,表示歸順於清朝。
坪仔頂村的兩大家族是張家跟林家。兩家表面上都效忠於清廷,平時都在家門口掛上了白旗,但是張家卻在暗地裡與天地會的紅旗軍聯絡。
有一天黎明,張家的人突然帶領著紅旗軍殺入村子,放一把火把燒掉了林家的大宅院,於是林家的人只好倉皇逃命。
但是幾天之後,林家的人跟著朝廷的白旗軍反攻殺入坪仔頂,這次換張家人落荒而逃了,他們的房子被搜刮一空。從此之後,坪仔頂的最大地主就只有我們林家,而沒有張家。
戴潮春事件是台灣清治時期三大民變之一,到了一八六五年,清政府靠著霧峰林家的協助,才徹底擊敗戴潮春所帶領的八卦會,而台灣中部也恢復了一時的平靜。
日本人來了
但是到了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台灣被割讓給了日本,而台灣又陷入了混亂。
當時我的祖母只有九歲,據她說,當日本人來的時候,坪仔頂的村民們驚慌失措,紛紛逃進了附近的深山裡。但是她當時並不覺得特別的害怕,只記得家裡的大人做了竹筒飯給她吃。那是她第一次吃到竹筒飯,感覺非常好吃。
又過了幾年,日本的殖民者陸續在台灣建立了各級的政府組織,然後就決定要幫坪仔頂村的所有村民們接種天花疫苗,也就是俗稱的牛痘。
而由於當時秀峰村的村長是我祖父的堂哥,所以接種疫苗的地點就設在我們林家的廳堂裡。村民們魚貫而入,人人都抱著必死的決心,因為傳說那是日本人的毒針,日本的殖民者想要害死所有的村民。
於是好心的村長太太偷偷地在林家的廳堂後面準備了一大缸的清水,當村民們打完疫苗從後面離開的時候,大家都圍在那缸水旁邊,拚命的刷洗自己的手臂,希望能來得及把毒刷掉,保住自己的一條小命。
在甲午戰爭之前,林家的子弟們上的都是私塾,讀得都是漢文書,他們寄望於有一天能去考科舉,求得一官半職。但是日本人來了,國家的官方文字突然從中文變成了日文,結果林家的子弟們都從書生變成了文盲,所以也只好棄文從商。
麻竹與棺木
林家的子弟在鹿谷的深山中砍下了一千多根大麻竹,結成了許多的大型竹筏,然後順著濁水溪而下,一直到台灣海峽出海,然後又沿著海岸南下,划到屏東的東港。
他們所乘坐的竹筏就是他們的商品,他們將竹筏拆解,在本身不產麻竹的東港高價出售,然後步行回家,獲取了豐厚的利潤。
其中幾位林家的男丁們也在東港當地結識了美麗的女子,與她們結婚,並將她們帶回了南投的深山之中的坪仔頂村。我父親說,他們小時候都叫那幾位從東港來的伯母跟嬸嬸們「外地嬤」。
到了一九一九年,也就是大正八年的時候,林家得到了日本殖民政府的特許,成立了一家「羌仔寮材木商會」,去開發杉林溪跟東京帝大溪頭實驗林的林業資源。
而剛好那一年西班牙流感在全球大爆發,台灣也死傷慘重,棺木熱銷。結果商會一年賣出了三千多副的棺材,發了一筆災難財。但是隔年流感不再流行,棺木的銷售業績一落千丈,再加上庫存太多,所以林家的商會就破產了。
到東京的火車票
在日治時期,坪仔頂村的村民們如果要到城裡,必須先搭乘「輕便車」,也就是用人力推動的鐵道車到濁水溪的南岸,然後再乘坐流籠到達濁水溪對岸的集集鎮,對外的交通非常不方便。
但是村民一旦抵達集集火車站之後,就可以在車站購買直達日本東京的車票。用同樣那一張聯票,旅行者可以搭乘集集線的火車到彰化二水,在二水換乘縱貫線的火車到基隆港,然後乘船到日本九州,上岸後,再轉搭火車到東京。
我聽了之後覺得不可思議。但是我的父親跟我說,其實那沒什麼,當時台灣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從集集搭火車到東京,也不過是國內的旅行而已。
山村中的台灣史
以上的這些故事,有些是我的父親跟我說的,有些則是我祖父的堂哥林邦光先生在他的自傳中所寫的。林邦光先生生於一八七四年,卒於一九四九年,他在日治時期曾經擔任坪仔頂村的村長以及竹山鎮羌仔寮區的區長,也就相當於現在鹿谷鄉的鄉長。他的漢文底子深厚,晚年用毛筆字寫下了一篇文言文的自傳。
但是在接下來的六十多年當中,林家子弟看得懂文言文的人不多,而讀過林邦光先生自傳的人更少。因為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先是日本殖民政府希望台灣人盡快忘掉中文以及中國的歷史,然後是國民政府希望台灣人盡快忘記日文以及台灣日治時期的歷史。台灣的官方語言變來變去,歷史課本也變來變去,結果搞到好像台灣從來都沒有歷史一樣。
事實上,台灣不但有歷史,而且非常的精采。即使是在鹿谷叢山之中的一個小村落,也曾經有那麼一群人精采而忙碌地活著。
兩個經典到有些陳腐的鹿港愛情故事
秀才、小姐與丫鬟
我媽媽的曾祖父丁壽泉先生是彰化鹿港人,他從小讀漢文參加科舉,一路從童試、鄉試、會試往上考,最後在清朝光緒六年,也就是西元一八八○年的時候,他遠赴北京的紫禁城,跪在皇帝面前參加殿試,考取了進士。現在鹿港著名的觀光景點「丁進士宅」,就是丁壽泉先生的住宅,也是我媽媽她小時候的家。
丁進士生了一個兒子,那個兒子從小被送到彰化北斗一位林老師家的私塾上課,而且後來也順利考上了秀才,成了丁秀才。故老相傳,在丁秀才金榜題名的那一天,他坐上了轎子,讓眾人抬著他在北斗鎮上遊街慶祝。最後大家把他抬到了林老師家裡,讓丁秀才跪在地上向林老師行謝師禮。
就在這時候,林老師的閨女從簾幕後面看到了正在磕頭的丁秀才。她覺得丁秀才儀表非凡,心中暗暗喜歡,從此飯不思茶不飲,得了相思病。林老師跟他的太太察覺有異,幾次詢問閨女,閨女卻總是不說。
後來林小姐的丫鬟跟林小姐說:「這件事情既然你不敢跟老爺和夫人說,那就讓我去說吧,但是萬一老爺跟夫人不高興,他們說不定會把我打死。所以妳必須先答應我,如果事情成了,我要一起嫁過去,當個姨太太,而不再是個丫鬟。」
林小姐答應了,林家的丫鬟也真的去跟老爺和夫人說了,結果林老爺跟林太太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覺得十分的高興又好笑,說:「這事情還不簡單?我們去跟丁進士他們家講一下不就好了?」於是丁秀才真的跟林小姐結婚了,而林小姐也信守承諾,帶著丫鬟一起嫁過去,丫鬟成了姨太太。
當然,丁秀才就是我媽媽的祖父,林小姐就是我媽媽的祖母。
小學老師與富家小姐
丁秀才跟林小姐結婚之後,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日本人占領了台灣,丁秀才沒有繼續去考科舉,改行當漢醫,然後他跟林小姐也生了一個兒子。
時代變了,丁秀才的兒子長大之後不再讀漢文,不再讀四書五經,他上的是日本人辦的學校,受的是西式的現代化教育。他考上了台南師範學校,畢業之後回到鹿港的鹿港女子公學校任教,成了丁老師。
丁老師在他任教的班上,注意到一位年紀比其他同學大了幾歲,但是天資聰穎,而且長得十分美麗的女學生。原來,在一八九五年日本人占領台灣之前,台灣富有人家的男孩子上的是私塾,而女孩子家中再怎麼富有,也不會被送去上學,也大多不識字。但是日本人來了之後,總督府積極推廣基礎教育,除了要求男孩子要去公學校上學之外,也另外設立了女子公學校,積極的鼓勵女孩子上學。當時鹿港大街上有一位施姓富商,家中的女兒已經十歲,還沒有上過學。於是在鹿港女子公學校的校長與老師們的積極遊說之下,施姓富商送了他女兒去讀書。而丁老師在班上看到的那位聰明美麗的女學生,就是那位施姓富商家的小姐。
施小姐在鹿港女子公學校讀了幾年的書,畢業的時候,年紀也已經有十六歲了。鹿港女子公學校的日本人校長乾脆積極做媒,讓丁老師跟施小姐結婚,讓師生關係變成了夫妻關係。
當然,丁老師就是我的外公,施小姐就是我的外婆。
白髮蒼蒼的情侶
在我年紀還很小,還沒有上幼稚園的時候,我的外公跟外婆就已經是頭髮稀疏灰白的老人了,我從來不曾將他們兩人跟戀愛這回事聯想在一起。我只記得我外公每天早上會帶我去台中公園散步做早操,而我的外婆會幫我們縫衣服,會煮好很吃的東西給我們吃。
當時他們兩人總是不斷的鬥嘴,尤其我外公在台灣光復之後重新學中文,迷上了做唐詩,每天都為了平仄押韻的事情魂不守舍的,惹得我外婆十分生氣。我記得在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次聽到我外婆用鹿港腔的台語罵我的外公:「汝啊,做事就是輕狂,好似那魏延踢翻了孔明的七星燈一樣!」我聽了先是一愣,接著忍不住笑了出來。鹿港的書香世家果然非同小可,連吵架都要引經據典的。
一直到他們兩人過世幾年之後,我才從我媽媽那裡聽到丁老師跟施小姐的戀愛故事,也才聽到丁秀才跟林小姐的戀愛故事。想來在那個民風保守,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戀愛是一種禁忌,所以當事人都不願意多說,但也正因為禁忌,所以回憶起來應該是格外的甜美吧?
而最近我又聽說,所謂日本人校長做媒,撮合我的外公外婆結婚的事情,恐怕也只是我外公跟外婆的「官方說法」而已。據我外婆的妹妹,也就是我姨婆的說法,當時我外婆是鹿港出名的美女,他跟我外公師生戀的事情,早就在鹿港街上傳得沸沸揚揚的,雖然我的外婆總是矢口否認她在談戀愛。但是等到人家來做媒,我的外婆卻又馬上答應了。
所以其實我們的祖先們也都曾經浪漫過,他們不只是祖宗祠堂牆上的幾張黑白照片而已。
山東流亡學生與威格納教授
生活在一起的陌生人
一九七○年代我讀小學的時候,我們家住台中,我就讀於台中師專附小。後來在一九八○年,我十五歲的時候,我們舉家遷居到台北,我先後就讀於懷生國中、建國中學、台灣大學。在我的生活圈裡,一直有許多的外省人第二代,也就是那些在一九四九年隨著國軍撤退來台灣的中國各省人士的後代。
我跟那些外省同學們平常一起念書、一起打球,週末一起到西門町去看電影,我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但其實像我這樣的本省人,並不知道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那些外省同學的父母親在中國大陸經歷了什麼。而那些外省同學們,也同樣的不知道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我的本省人父母親在台灣又經歷了什麼。我們都只讀過在歷史課本裡面的,那些以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為主角的中國近代史。我們只知道那些偉人們經歷了什麼、成就了什麼、在想些什麼。
因為在威權時代的台灣,談論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歷史往往是個禁忌。一方面,國民政府希望台灣本省人忘記日據時期發生在台灣的歷史;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也希望外省人忘記那些在國共內戰期間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不光彩歷史。因此,我們所有這些本省人、外省人們,就這麼陌生而又親密地一起在台灣島上生活著。
大江大海的故事
族群的融合,要從相互了解開始。所以在十多年前,當龍應台寫了《大江大海1949》的時候,我馬上去買了一本。結果看了之後覺得要吐血,因為我實在受不了那個假掰的文藝腔。
後來李敖針對龍應台寫了一本《大江大海騙了你》。我在書店看到了,如獲至寶,想說李敖的看法居然跟我一樣,我應該是他的知音。沒想到回家一讀,發覺李敖東拉西扯,胡言謾罵,寫的比龍應台還糟。所以我被《大江大海》騙了一次,又被《大江大海騙了你》騙了一次。人生之悲慘,莫此為甚。
還好,後來我的好朋友蔡律師介紹我看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一套四本,而那才是真正精采又深刻的、大江大海的故事。
王鼎鈞一九二五年出生於中國山東省的地主家庭,在抗日戰爭中打過游擊,在國共內戰中擔任過國軍的憲兵與補給官,還被共軍俘虜過。他對中國的造假文化、國民黨的失敗,以及共產黨的崛起,都有著非常深刻的觀察。
澎湖的流亡學生
依照王鼎鈞先生回憶錄的說法,國共內戰期間,雙方往來拉鋸,殺戮最為慘重的地方就是在山東。當時只要共軍占領了一個城鎮,就會組織鬥爭大會,把當地的地主們都拉去殺掉,然後等到國軍奪回那個城鎮,地主家庭的子弟們又會組織「還鄉團」,憑藉武力搜捕之前帶頭鬥地主的農民領袖們,把他們通通抓起來殺掉。
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徐蚌會戰結束之後,國軍全面潰敗。山東地主家庭的子弟們就只能加入山東各地所成立的三十二所流亡中學,跟著國軍不斷地往南逃亡。他們從山東逃到江蘇,從江蘇逃到湖南,從湖南逃到了廣州,最後又從廣州逃到了澎湖。
原本那三十二所流亡中學的學生有三萬人之眾,但是其中有些人病了,有些人不想再逃了,人數越來越少,而各個山東流亡中學也不斷地合併。所以當他們逃到澎湖的時候,就只剩下了一所「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總共八千多名學生。
然後一九四九年七月在澎湖就發生了「山東流亡中學事件」。當時駐紮在澎湖的國軍強逼年輕的山東流亡學生們從軍,學生們不肯,於是軍隊在學校操場上用刺刀刺傷了兩名學生,接著又開槍打傷了幾名。
當時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的校長張敏之想要保護學生,四處陳情營救,結果不但他自己被誣指為匪諜,被抓去槍斃,而且還讓數百名學生遭受牽連。許多學生再逼供的過程中被電刑、掌嘴、吊刑、鞭打,或強行灌水,甚至被私下槍斃或是拋入海中淹死。
被遺忘的悲劇
依照王鼎鈞先生的說法,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逃來台,原本民心潰散,政府毫無威信。後來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是靠著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其中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而另一件山東煙台聯合中學冤案則是懾伏了外省人。
但是在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之後,台灣的本省人族群不斷地去挖掘整理二二八慘案的歷史,甚至讓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成為一個國定假日。而相對的,外省人族群卻很少去關心山東流亡學生事件,目前大部分的台灣人對澎湖的山東流亡中學事件也所知甚少。
不但如此,當時被強徵入伍或是受到迫害的山東流亡學生們,後來還有許多人進入了國民黨政府,成為了國民黨的堅定支持者與捍衛者。像是前國防部副部長王文燮、前警政署長顏世錫、前陸軍總司令李楨林、前台大校長孫震等等。
對於這樣的狀況,我原本完全無法理解。一直到二○一六年,我讀了威格納教授的傳記。
被自己綁架的狂熱分子
彼得‧威格納教授(Professor Peter Wegner)是我在布朗大學讀博士的時候,我的論文指導委員之一。他在學術界非常有名,對我十分照顧,經常會講一些跟英語雙關語有關的笑話給我聽,讓身為外國留學生的我聽得一愣一愣的。但是我只知道他是在英國長大的猶太人,對他的成長歷程並不是很清楚。
一直到威格納教授在二○一六年過世,我看到了他的訃聞,才知道他的父母來自奧地利,原本是維也納當地相當活躍而且知名的社會主義分子。威格納教授的父母親在一九三一年結婚之後,隨即移民到蘇聯的列寧格勒,並在隔年一九三二年生下了彼得‧威格納。
威格納教授的父母當時之所以會移民到蘇聯,是因為他們相信蘇聯的共產黨將會給猶太人一個更好的生活。但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某一天,當威格納教授才五歲的時候,兩個蘇聯的秘密警察到他們家帶走了威格納教授的爸爸,從此他的爸爸就失蹤了,再也沒有回來。
於是威格納教授的媽媽帶著他逃回了維也納,然後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納粹德國併吞奧地利之後,威格納教授媽媽又趕緊越野滑雪通過邊界,逃到了瑞士,然後再輾轉逃到了英國。而當時才七歲的威格納教授則是在英國貴格教派與紅十字會的協助之下,搭上了一班特殊的逃命列車,經過荷蘭也逃到了英國,與他的媽媽會合。
後來他們在英國,每當別人問起威格納爸爸在哪裡時,威格納媽媽總是說,她的先生之前加入了志願軍,到西班牙去跟佛朗哥將軍的法西斯政府戰鬥,死在西班牙。
威格納教授長大之後才理解,他的媽媽不願意承認她的先生是死在蘇聯秘密警察的手裡,因為如果承認了,就是否定了蘇聯,就是否定了她一生信奉的社會主義與共產制度,也就是否定了她自己的一生。
威格納太太是一個被她自己的意識形態所綁架的政治狂熱分子。
時代悲劇下的逃亡者
對二次大戰前夕的歐陸猶太人來說,蘇聯的共產黨是一個惡,但是德國的納粹黨是一個更大的惡。雖然蘇聯的共產黨殺害了威格納爸爸,但是他們至少留下了威格納媽媽與小威格納的性命。而相對的,如果威格納一家人落入了納粹德國的手中,那他們一家三口必死無疑。所以,當不得已必須做出選擇的時候,威格納媽媽還是會為那個殺害了她先生的蘇聯共產黨辯護。
同樣的,對於山東地主家庭的子弟們來說,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惡,但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更大的惡。雖然國民黨對山東流亡學生們不好,甚至殺害或是監禁了他們的同學,但如果山東流亡學生們落入了中國共產黨的手中,那他們的下場肯定更為悽慘。所以,當不得已必須做出選擇的時候,山東流亡學生們還是會站在中國國民黨的那一邊。
我們甚至可以說,山東流亡學生們的命運,早已跟國民黨政府緊緊的綁在一起,如果他們否定了國民黨,也就否定了他們自己的一生。
幸福的島嶼
王鼎鈞先生出生於一九二五年,我的父親出生於一九二九年,威格納教授出生於一九三二年,他們都是同一個世代的人。而幾年前讀完王鼎鈞的回憶錄之後,我才陸續得知,我大學時期有幾個最要好的同學都跟王鼎鈞一樣,出身於山東的地主家庭。其中張同學的外祖父曾經是山東流亡中學的老師,龔同學的父親曾經是山東流亡中學的職員,而李同學的父親也來自於山東。
但是由於白色恐怖時期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遭遇的恐怖經歷,張同學、龔同學,以及李同學的父母對於那段歷史也都諱莫如深,從來不曾跟他們提起過。
那應該是一個大時代的悲劇吧。我們應該覺得很慶幸,現在台灣已經完全的民主化,在這個時代生活在台灣島上,我跟張同學、龔同學,以及李同學都不需要在兩個惡之間做出選擇,就像威格納教授跟他媽媽逃到了民主的島嶼英國之後,就再也不用在蘇聯共產黨與德國納粹黨之間做出選擇一樣。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