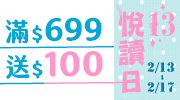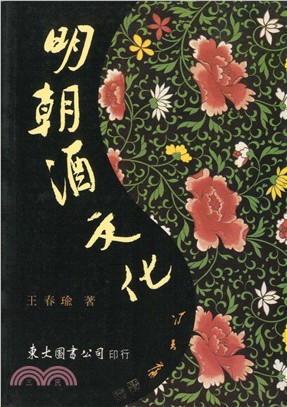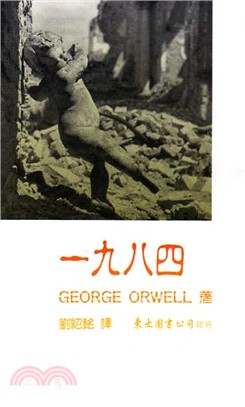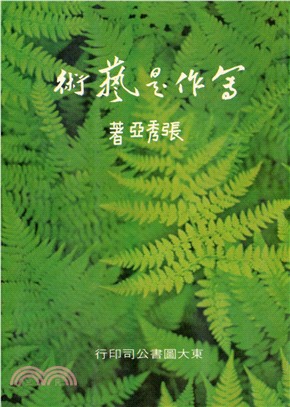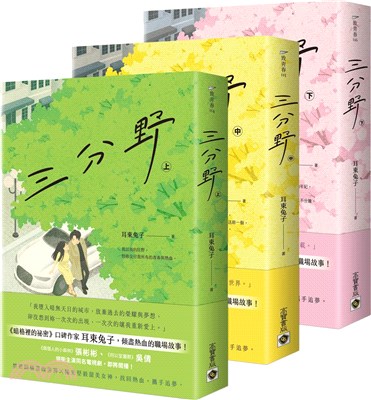嚴家祺序
歷史是不可磨滅的記憶——重返法蘭西
1989年是中國和世界歷史的大轉折,六四大屠殺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至今沒有結束,六四也導致了蘇聯帝國的解體和20世紀兩極世界的消失。六四的許多流亡者來到了法國,這本書多篇文章記述了六四流亡者和六四後中國國內知識分子的抗爭,這也是歷史。
在這本書裡安琪說:「當時流亡者中的許多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留在法國」,「這讓法國方面非常惱火。據說,時任法國駐香港副總領事的孟飛龍,聽說我(安琪)已收到美國某大學的邀請函和某報社的工作機會,有可能去美國時,他激動地將手中的打火機扔向天花板。」我也提出去美國,幫助我們在法國定居的艾麗斯協會的一位成員對我說,我們把你們一個個都安排在法國,你們一個個都到美國去了,你不要走了。於是,我就留在法國。幾年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請我擔任訪問學者。這樣,我還是離開了法國,到了美國。
我經歷了三次人生大轉折,第一次是1989年六四後逃亡香港並到法國,第二次是在華盛頓一週內三次全身麻醉下的心臟手術,第三次就是最近重返法蘭西。這三次大轉折,不是自主行為,而是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驅動的。
人類不同於動物,在於人有高度的理性和深厚的情感。理性賦予人以想像力,使人可以認識宇宙中的規律,創造出有益於人類而自然界中沒有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理性也可以製造罪惡,發動戰爭,危害人類和世界。對人來說,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如何行為,而情感決定人行為的方向和道路。
2023年10月31日,我與妻子高皋乘法蘭西航空公司AF55從美國回到巴黎。我一家七口,有法國人、中國人、美國人。「一家三國」,這一天終於團聚。我82年人生經歷了許多事,一件一件都沒有受到多少困難都過去了,重返法蘭西,是遇到最多困難、也得到很多幫助,最後平安實現。
安琪是香港《前哨》特約記者,巴黎「自由談」沙龍主持人。這本書收集了她在香港《前哨》月刊和其他報刊的多篇文章,書名來自於她十年前在香港《前哨》月刊上寫的一篇紀念法國外交家燕保羅的文章。題目是:〈天若有情天亦老——「黃雀行動」與燕保羅的人道情懷及其他〉。我也是《前哨》月刊的作者,有幾年,幾乎每期都有我的文章。十年前,我讀安琪這篇文章時,才具體地知道,經燕保羅接納安置的中國「六四」流亡者有兩百多名。燕保羅和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馬騰、法國駐香港副總領事夢飛龍,為法國接納六四流亡者作出了巨大努力。回憶起1989年多次見到燕保羅的情景,感到他對我們這些來到法國的流亡者十分關懷和友好。我不知道他的父親也是「流亡者」,更沒有聯想起,從香港來到法國,我的登機證上的英文名字YIPPAUL就是燕保羅。當時我改名為「朱豐」,而不是「保羅」。由於YIP與PAUL之間沒有分開,我想不到YIP是燕字,多年中不知道YIPPAUL就是燕保羅。
讀這篇文章的當時,我給安琪回信說她這篇文章,「不是舊聞,而是新聞,是不可磨滅的記憶」。1989年,我保存了這張登機證,記錄了當時的逃亡過程。
在地球上,物理物體不能記憶。在浩瀚的宇宙中,星球、星系不能記憶。只有動物和人類能夠記憶。對動物與人類來說,許多行為沒有經過大腦,是自主神經系統(又稱「植物神經系統」)的「自律(自主)行為」,如心跳、呼吸、消化、新陳代謝。記憶是動物和人作為「個體」的自主行為的基礎和指南,但動物的記憶轉瞬即逝,只有人類的記憶可以長期保存、不可磨滅。歷史就是不可磨滅的記憶。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證明,理性只是一種「演算法」,而機器人只能按預定程序模擬人類的情感,不能「創造情感」。
1989年6月19日,香港友人林道群、李志華把我與妻子高皋、以及社科院的甘陽,安排快艇從廣東穿越大亞灣飛馳到香港。我們到香港的第四天,6月22日,香港《明報》頭版頭條刊出了〈喬石李鵬覬覦總書記,楊李力主處死嚴家其〉的報導。這一天上午10時,一位中文名叫方文森的法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把我們三位「偷渡客」帶到港英政治處的一個機構。我們被告知,不得在香港再停留下去,因為我們是「非法入境」,必須到其他國家去,法國政府歡迎我們三人去法國。
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在港英政治處,當時就照他們的安排,我們三人改了姓名,我改名為「朱豐」,換上了一身他們要我們穿的衣服。港英政治處的警察將帶著我們三個「假警察」在機場「執勤」,我們每人手裡拿一個「對講機」,做四處巡視的樣子。經過一個單向轉動門、一個鐵門,就到了機場。所謂「執勤」,不過是從港英政治處去機場登機前的路上,如果有人詢問或要檢查,要求我們擺出的姿態。實際上,一路十分順利,我們並沒有扮演警察。
安琪的這部新出版的書,除了燕保羅外,還寫了二十多位大家都熟悉的人,從法國總統密特朗、中國總理趙紫陽、達賴喇嘛、趙無極、高行健、程映湘、余英時,到英國的戴安娜、緬甸的溫丁,許多內容,都會留在人們的長期記憶中。
安琪的這本書,在許多地方談到自由問題。一個人有沒有自由,不僅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而且與他有沒有自主行為意向和努力有關。當一個人有強烈信仰時,他的被迫行為,就成了自主行為。宗教是一種信仰,虔誠的宗教信徒可以把信仰作為自主行為的指南。意識形態也是一種信仰,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意識形態信仰。作為中華文明基礎的儒家,不是宗教,可以說是一種廣義的意識形態信仰。除了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信仰外,世界觀也是一種信仰。人類社會中還有一種根深柢固的信仰,這就是迷信。自由出創造,為了爭取思想自由、創作自由,這本書談到吳國光、劉賓雁、蔣彥永、高行健、章詒和、趙無極、司徒立、劉達文等人,在不同環境中,為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以各自特有的方式追尋自由的艱難歷程。
讀這本書,使我想到,人類的各種文明實際上是幾千年中形成的思想文化、行為習慣、像「印刻」一樣,只能以千百年為尺度非常緩慢地改變,而經濟制度,可以在十年、幾十年中發生改變,政治則是轉瞬即逝的行為,可以在幾月、幾年內發生重大變革。這是千年、百年、十年不同「數量級」的現象。一個國家,關心政治的人愈多,這個國家政治問題就愈大;政治愈好的國家,關心政治的人愈少。在一個國家大變革的前夕,人人都關心政治。戰爭把所有人捲入政治。政治不是行政,不是管理,而是用智慧、用妥協的方法消除戰爭和大規模暴力的國家行為。國際關係不是人際關係,全球化有助於消除全球戰爭,全球化是全球性的政治經濟變革,是21世紀、22世紀以至整個第三千紀的大趨勢。最近幾年,出現全球化的局部倒退,只是短期波折。「全球化」,就是一步一步地用幾年、幾十年時間,按照經濟發展的共同路徑,按照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逐步改變一個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為改變經濟結構,在保留各國貨幣基礎上建立全球單一貨幣或全球總帳本;在政治結構上,在保留國家的基礎上,建立全球聯邦。全球化,就是在這一經濟政治變革下的全球各種文明和平共存的偉大歷程。
嚴家祺 2023-12-15寫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