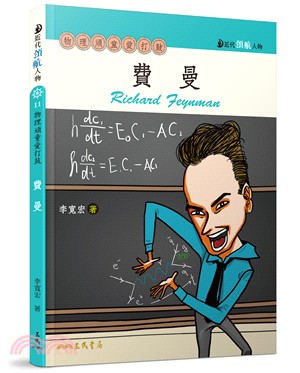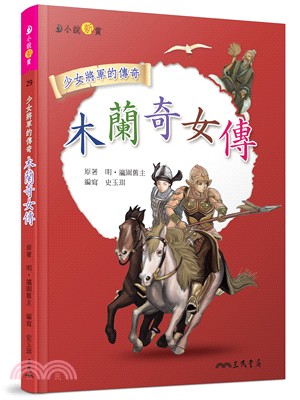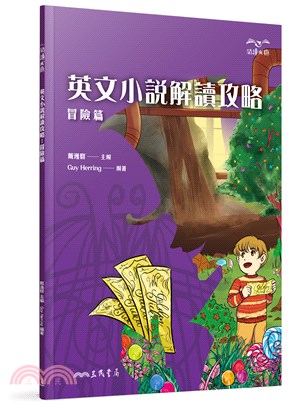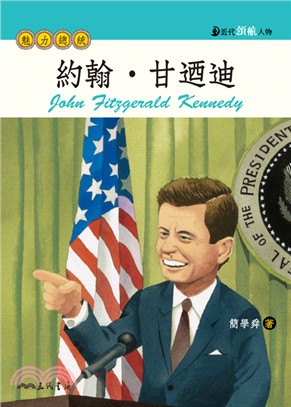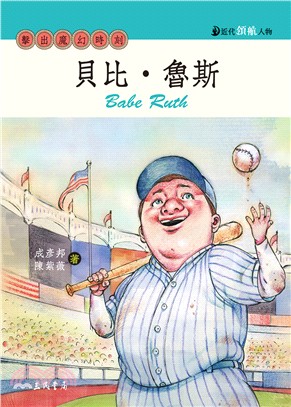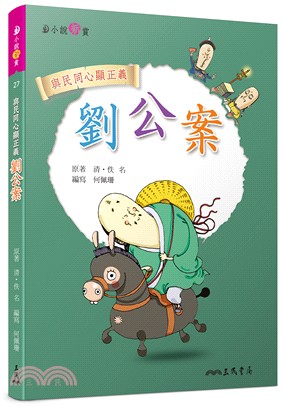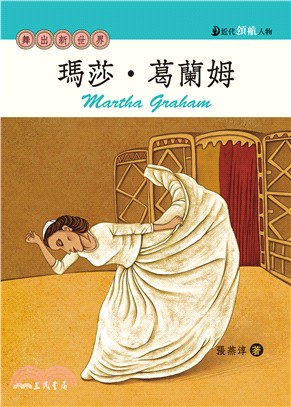聽我胸中的烈火:余光中教授紀念文集(電子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超過一甲子的文學志業,余光中出入東方與西方,在傳統與現代間悠游自得。詩與散文享譽文壇,雙璧爭輝,影響不只一代的後學者;他創作與評論左右開弓,降下五四的半旗,升起現代文藝的大旌,開啟台灣現代主義的新頁;更以信雅達兼具的譯筆引進西方的藝術與文學,成為許多當代藝術工作者的啟蒙書。
他深情注目所處的環境,以詩文和實際行動回應時代社會對他的呼喚,形成群聚效應,因此,台北廈門街是一道文學風景,香港沙田一時之間彷彿成派,高雄西子灣的海天之間有文字的精靈四處躍動,兩岸開放後,成為彼岸文藝界必訪的文學勝景。
余光中既是文壇公認的大師,也是杏壇上孜孜不倦的教師,直到八十七歲高齡仍在教室授課。大師遽逝,各界同悲,有華文處必有文字追懷。李瑞騰教授特精選來自全球各地五十多篇追思文章集結成冊,有作家王文興、陳芳明、張曉風、黃維樑、王洞、羅青、何懷碩、馮亦同等細述文學因緣,藝術家楊世彭、劉國松等素描大師在文學之外對戲劇,美術的推動與影響力,還有學生鍾玲、單德興、樊善標、黃秀蓮等素描老師的厚愛與提攜,後輩張輝誠、辛金順、徐國能等述及余先生作品對他們的影響。一篇篇文章是一道道文學長河裡不同的景致,既彰顯大師的文學高度,更有許多文壇佚事、不為人所知的小故事,讓人見識到離開書桌、下了講堂的余光中。
本書特色
★ 適逢余光中先生逝世周年,特邀李瑞騰教授擔任主編,精選懷念余光中先生紀念文章,包含台灣作家王文興、張曉風、羅青、向明、黃碧端、張輝誠等,香港樊善標、黃維樑等各地作家。
作者簡介
台灣南投人,一九五二年生。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院長。二○一○年二月一日起,由中央大學借調至國立台灣文學館擔任館長四年;二○一四年二月一日歸建,專任中文系教授,現為文學院院長(二○一六年六月起)。著有文學論著《台灣文學風貌》、《文學關懷》、《文學尖端對話》、《文學的出路》、《文化理想的追尋》、《老殘夢與愛》、《新詩學》、《詩心與詩史》等,及散文集《有風就要停》、詩集《在中央》等。
目次
主編序:聽我胸中的烈火 李瑞騰
卷一 余先生的後院
向明 藍星的精神領袖:余光中
劉國松 懷念余光中:一生知音.一世情誼
楊世彭 悼念光中
王文興 余先生的後院
張曉風 偶逢之處
何懷碩 在光中走進詩史
季季 向前看,向後望──余光中先生的三幅畫像
彭鏡禧 遲到的祈請譯詩一首敬悼余光中先生
鍾玲 余光中老師的多重面貌
黃碧端 我和光中先生的中山因緣
陳芳明 詩的志業──悼念余光中
羅青 百年文學一光中──懷余光中先生
賴聲羽 我所認識的余光中
高天恩 「雙宿雙飛」的日子
卷二 日落西子灣
蘇其康 典範譯詩的余光中
白靈 詩壇的賽車手和指揮家——我與余光中接觸的幾種方式
陳幸蕙 忠於自我,無愧於繆思的馬拉松作家
陳義芝 在高寒的天頂:余光中的文學地位與現實處境
單德興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
陳素芳 當夜色降臨,星光升起
張錦忠 在西灣斜陽的余光中
須文蔚 沒有人伴他遠行.追憶余光中先生在台港文學的貢獻
唐捐 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
沈政男 余光中與我
鍾怡雯 左手的謬誤
徐國能 你就在歌裡、風裡
張輝誠 因為在光中
熊婷惠 遇見那來自古老國度的旅人
卷三 飛鵝山上文星輝永
金聖華 一斛晶瑩念詩翁
朱國能 不廢江河萬古流—敬悼恩師余光中教授
李默 嶺逶迤騰細浪
黃維樑 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
鄭培凱 悼念余光中老師
林沛理 懷念余光中──任何英文可以做的事情,中文定可以做得更好
胡燕青 敬悼余光中老師
黃秀蓮 異材秀出千林表──我是余光中學生
陶傑 文星輝永余光中
樊善標 飛鵝山上──敬悼余光中
廖偉棠 孑立在中華民國的餘光之中
卷四 鄉愁已遠
王蒙 余光中永在
王洞 敬悼余光中
馮亦同 日落西子灣——懷念余光中先生
張鳳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追憶余光中先生
楊欣儒 余光中和母親
喻大翔 西子湾畔访余光中
許鈞 余光中的翻譯活動
何龍 死亡,你把余光中摘去做什麼?
曉亞 鄉愁已遠行──記與余光中先生洛城文學因緣
辛金順 天涯此時同一哭:哀悼詩人
周梁泉 十二月十四日中午
龔剛 夢堂詩話:余光中蓋棺芻議
梁白瑜 我恨那摇丧钟的海神
孫茜 「與永恆拔河,還沒有輸定」——追憶余光中
書摘/試閱
聽我胸中的烈火 李瑞騰
我最早討論余光中是一九八○年,來約稿的是神州詩社的黃昏星和周清嘯,指定我談余光中,將刊於《青年中國》;我於是寫了一篇長文〈詩人的時空感知——論余光中近十年來的詩藝表現〉。大約是我交稿後不久,神州的帶頭大哥溫瑞安和方娥真就出事了,先是被捕入獄,然後遣送出境回大馬。神州瓦解,雜誌停刊,我的稿子另交《幼獅文藝》,發表於五十三卷二期(一九八一年二月)。
大陸文革結束之後,海內外華文文壇變化很大,余先生人在香港,感受必然深刻;1970年代末,余先生推薦給聯合報副刊的金兆小說陸續刊出,那時我對巨變後大陸新時期文學興趣正濃,寫了一篇〈鸞鳳伏竄,鴟梟遨翔〉的讀後感,寄到聯副給瘂弦先生,幸蒙刊出(一九八○年九月四日)。稍後,我接到余先生來信,說他從香港回來了,聯副將舉辦金兆小說的座談會,邀我參與,想來是配合金兆小說集《芒果的滋味》的出版(聯經,一九八○年七月),我欣然赴會,一起參與座談的除余先生和瘂弦,另有林海音、朱炎、張默、余玉照和羅青,記錄刊於隔年一月三十日到二月四日的聯副。
那時候,我一邊讀博士班,一邊在出版社當編輯,已發表過一些現代詩的評論。我愛詩,但不願侷限在個別文類,多方摸索觸探,余先生邀約我參與聯副座談,和前輩同席,對我而言是開眼界,文壇關係的擴大;特別是瘂弦,那時他已刊出我兩篇詩文評論,爾後多年,我在聯副發過百餘篇文章,和這最早的因緣息息相關。
就現有資料看來,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已出現在台北市廈門街余宅,一張我和余先生、黃維樑在門口拍的照片可為明證。那應該是維樑從香港來台,約我在余宅會面;我在一九七八年因沈謙約稿,在他主編的《幼獅月刊》發表〈黃維樑的詩論〉(四十七卷五期),結了文字緣,往後的八十年代,我參加幾次和香港有關的活動,或多或少都和維樑有關,包括接手《文訊》編務以後很快製作的《香港文學特輯》(二十期,一九八五年十月)。
一九八二年,好友向陽負責《陽光小集》和《自立晚報‧自立副刊》的編務,請我專訪余光中,訪問稿〈聽我胸中的烈火:夜訪詩人余光中〉刊於《陽光小集》第十期(1982年秋季號),也一併刊於《自立副刊》上。時間是七月十三日,這是我第二次拜訪余先生的書房,留下一組今猶珍藏的黑白照片,我做足功課而來,年輕氣盛,提問直接而尖銳;余先生當晚和永春同鄉餐敘,帶著酒意歸來,談興不錯,極有耐心地回應我的問題。
我三十歲之前和余先生結此善緣,終其一生良性互動,一九八四年他榮獲吳三連散文獎,主辦單位邀我寫評定書;九歌出版社兩度出版大系(一九八九、二○○三),余先生總其編事,兩次我都主編評論卷;二○一三年,我在台文館館長任上,邀請王心心用南管譜唱余先生作品,演唱會敬邀余先生伉儷到台南聆賞;大約同時,余先生賜電邀我擔任中山大學余光中人文講座的諮詢委員;二○一四年余先生榮獲行政院文化獎,余先生邀我在贈獎典禮上擔任引言,介紹他的文學表現。最後是在他的告別式上,我談他的全方位表現;在台北的追思會上,我談他在文學編輯上的獨到之處;在高雄中山大學的紀念追思會上,用台音朗誦他的〈洛陽橋〉。
余先生原籍福建永春,出生於南京,從大學時代開始寫作,終其一生,在詩、散文、評論和翻譯各方面都有精彩表現;一九四九年他由廈門到香港,一九五○年到台北,開始他在台灣漫長歲月的文學實踐。此其間,他曾赴美留學、赴港講學,在台居所也從台北移居高雄西子灣,每到一處,他都深情注目所處的環境,以詩文和實際行動回應時代社會對他的呼喚,形成群聚效應,因此,台北廈門街是一道文學風景,香港沙田一時之間彷彿成派,高雄西子灣的海天之間有文字的精靈四處躍動,和他結緣的文學俊彥都能感受到余先生的溫度和風範。
九歌出版社將為余先生出版紀念文集,囑我編選,我在近百篇的紀念文章中選了大約一半結集成書,想到余先生在台港發光發熱,作品在大陸頗受歡迎,在海外華人社會影響深遠,特以區域分輯,台灣文章較多,分成兩輯,其次香港、大陸及海外地區,作者們從不同的位置抒發他們的哀感,也側寫了他們眼中的余先生,其中也不乏理性的評騭。我讀著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前塵往事都一一浮現出來。
前此在編《九歌四十》之際,余先生病中寫了稿子寄來,筆力仍然遒勁;而今為他編此紀念文集,憶想三十幾年前夜訪廈門街,從他那時的近作〈五十歲以後〉拈出「聽我胸中的烈火」為題,我決定再用一次,想到這裡,余先生的詩句竟如鐘聲鏗鏗然傳來:
莫指望我會訴老,我不會
海拔到此已足夠自豪
路遙,正是測馬力的時候
自命老驥就不該伏櫪
問我的馬力幾何?
且附過耳來,聽我胸中的烈火
聽雪峰之下內燃著火山
聽低嘯的內燃機運轉不息
幾乎煞不住的馬力
踢踏千里,還有四百匹
——〈五十歲以後〉(錄後半)
附件3內文試閱
余先生的後院 王文興
余先生走了。雖是高齡先逝,亦覺愴惋,但我愴惋中亦有平靜,人生更迭,當如是也。我們尊稱他為先生,當年習慣如此,如梁實秋、英千里、台靜農,皆謂先生。
這兩日我常想到他家居台北的一段時間。心中不時的出現他廈門街寓所的印象。那是一座日式住宅,前方是一小院。他的書房面對此一前院。他寫讀,會客,都在這書房中。我有幸得知他住宅背後還有一座後院。有天,蒙他和余太太(太太也是尊稱,即今的師母或夫人)引領,面識了這一後院。
後院是此住院大走廊的所對,面積比前院要大五六倍。想來日間,此一大廊的玻璃門是拉開的,活動時裡外都可以通行。我那日去的時候,正當春日溫和的季節,只見此院草地初綠,園內稀稀落落有一些曬衣架繩,陽光正金黃地照亮在此院內。我們就坐在玻璃門開處,這走廊的地板上,腳踩廊下的台階,面對此園,小談片刻。
這幾日我常想到此園。今感覺此園恐甚像我們對余先生的回憶;他的一生,他留給人的回憶,正像此一後園,幽靜,優美,春日的陽光普照,正如他一生的文學成就。
余光中這個名字,將永垂不朽。他無疑是華文現代文學的第一功臣。這是肯定的。他不僅是吾人現代文學的開山始祖,他甚至促進了我們現代繪畫、現代音樂的誕生。他的名字將永垂青史。
九十是人生的高齡。寄望余太太和余府的眾位小姐節哀。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在光中走進詩史 何懷碩
十四日午前在中廣播音中得知光中先生仙逝的消息,百感交集。自從今年八月他在信中說「目疾為患」之後,我一直想去高雄探望他。八月太熱,想等秋涼,我却又應邀去了一趟杭州及上海。又有一趟北海道之行。因見余老十月下旬九十大壽慶生會堅持站著說話,顯示健康難關已過,百壽可期。便感不急,正想十二月下旬南下,豈料遲了一步而愧悔不已!趕快寫封信慰問咪咪大姊,我說今天頓覺人生好空虛,好荒謬。文豪走了,舉目四望,還有誰?
余老一生優美的詩文,文學界與友生已有許多透徹深入的研究與評論。他的成就有許多方面,最令人難忘的是語言的運用,充分表現了天才的機鋒,是罕遇的奇葩。大概只有蘭姆或王爾德等巨匠才能相提並論罷。這裡面絕不是頭腦機靈,口才便給而已,其人須博古通今,書讀得多,又博聞彊記,還要識趣幽默,通達開朗,口齒清爽,語調親切動聽。聽其言如沐春風,如打通任督二脈,而遍體舒暢。
余老的講演,或幾個文人老友相聚時他的談吐,才子的機鋒,令人如飲甘醇,如夏天喝冰可樂,難以忘懷。因為余老七○年代中去香港教書十多年,一九八五遷高雄教書三十多年,雖偶爾有機會晤面,畢竟不像早年在台北時期。不過,我還不忘記他創「雅不可耐」等新成語。幾十年前有一次在余府(廈門街)作客,余老的尊翁匆匆外出時神采奕奕跟我們打招呼。余老對我說:他老人家每天「閒裏偷忙」。真是溫馨又詼諧。余老的諧趣散文,如「給莎士比亞的回信」;「我是余光中的祕書」;「戲孔三題」等等,讀者可自去品嚐,以拜讀余老詩文來敬悼老詩人吧!
去年十一月,余老寄《粉絲與知音》一書相贈。今年八月,我十多年前《給未來的藝術家》一書出增訂版,遂寄剛收到的第一本給余老,他給我回信,這是最後收到的光中先生的一封信。信末說他為目疾所苦,寫作不方便,而有「長壽則多難,令人難堪,奈何!」之語。我讀後很難過。一位大作家,不太能讀寫,是多麼痛苦。記得一九七五年我在紐約唐人街中國書店買到《知堂回想錄》(知堂老人一九六七年五月逝世。六十年代初寫回想錄,寫完已是文革前夕。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知堂大難難逃,翌年突然去世,八十三歲),它的「緣起」及「後序」都提及古人「壽則多辱」這四個字。他說:「從前聖王帝堯曾對華封人說道,壽則多辱,這雖是一時對祝頌的謙抑的回答,其實是不錯的。人多活一年,便多有些錯誤以及恥辱,這在唐堯且是如此,何況我們呢?」
死於文革可怕的時代,知堂借古人「壽則多辱」來自況,有許多隱藏不便明言之苦痛。光中先生生活在榮光中,在溫暖的家園中,在千萬讀者的仰慕中,但因老病而有「長壽則多難」之嘆。十四日當我一知道詩人駕鶴飛升,立時想到他的「多難」與知堂的「多辱」;兩個處境與成就完全相異的文豪其老年人生的慨歎如此,都令人感慨哀悼。
我不知余老有沒有對其他人透露人生長壽則多難的感慨,他最後這信上的字迹,雖稍遜健康時的挺拔清麗,也還是他自己典型的風格。
一個鄉愁的時代隨著結束了,他在光中走進詩史。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七日《聯合報》
因為在光中──懷念余光中老師 張輝誠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二○一六年十月三十日,我趁南下高雄演講學思達之便,特地到余老師家中探訪。當時余老師和余師母剛從醫院返家休養,氣色很好,心情亦佳,我們一起在客廳聊了一個半小時。
余師母說近幾個月,先是她身體微恙,遍查不出原因,住進加護病房,女兒怕余老師擔心,瞞著余老師;後來余老師獨自外出公園散步,返回大樓門口忽往後跌了一跤,後腦勺著地,外傷出血,幸好有人發現,緊急送醫治療,也住進加護病房,女兒怕余師母擔心,同樣瞞著余師母。後來兩人病情好轉,轉入普通病房,同住一室,這才知道彼此狀況,夫妻重逢,恍如隔世。
我聽余師母這樣說,腦海先想起余老師的詩〈紅燭〉,余老師曾用紅燭譬喻他們夫妻倆,「迄今仍然並排地燃燒著/仍然相互眷戀地照著/照著我們的來路,去路」,只是當時是年輕的洞房,如今卻移到年老的病房。忽然間,我心裡湧起了很多的心疼和不捨,也感受到余老師和余師母難以言喻的鶼鰈情深。當我還停留在各種情緒,余老師倒是先對跌倒一事說了他的看法:「年紀大了,連土地公都喜歡來捉弄,扯人後腿。」這是余老師一貫的幽默、樂觀與純真。
我自從和李崇建老師學習美國心理學家薩提爾的溝通模式,常嘗試著用平和的姿態和語調與人連結,我想表達出內心最深的感受,我對余老師說:「老師您真的很愛師母。」余老師忽改冷面笑匠神情,說:「我們兩個是相依為命啊!」這是深情的余老師。
余師母問起我兒子最近甚麼樣?問我最近在忙甚麼?好像很少在聯合報副刊看到我寫新文章了。──余師母和余老師都喜歡我兒子張小嚕,他們每次遇見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張小嚕來了嗎?」「張小嚕最近好不好?」我一直覺得老人家最大的開心就是看到嬰兒,以及和嬰兒玩,老少之間最美好的連結就是完全不需要透過言語溝通,單純透過撫摸和笑容,這兩者同樣都充滿著無比的善意。張小嚕曾在六個月大、一歲大時兩次到余老師家,第一次乖巧躺在余師母懷裡,余老師緊靠著余師母,對張小嚕說:「在你後面是一個倒著的人喔!」第二次張小嚕在余家客廳滿地爬,鑽進鑽出余老師的座椅底下,余老師低頭對他說:「嚕嚕正在過山洞喔!」還有一次,余老師在台北又再見到白白胖胖的張小嚕,直說:「嚕嚕現在是:內容超過形式。形式是小令,內容卻是長調。」這是心裡住著一個小孩,童心未泯的余老師。
我向余師母說,這兩三年都在忙著推廣學思達,嘗試看看能否改變台灣填鴨教育,幾乎無暇寫作。余老師很感興趣,問我甚麼是學思達?我仔細地向余老師說明,彷彿平日演講一般,余老師專注聽著,聽完後,他表示贊同,最後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不管教學方式怎樣改變,千萬都不能忘記自己的國家、不能忘記自己的祖先。」我點了點頭,旋即想起毓老師以前上課經常說的話:「我告訴你們,數典忘祖,就是忘本。」余老師是這樣、毓老師是這樣、我的父親也是這樣,那是曾經親歷過戰亂、遭遇過國家風雨飄搖危盪之後留存的深切憂患感。
聊完天,我還要趕回台北,余老師即使步履緩慢(看得出他大病初癒,身子還很虛弱,跌倒後元氣大不如前),但他依然慎重、堅持送我到電梯口,余老師伸出手和我握別,我很是感動,雙手緊緊握著余老師。老師忽然說:「你有沒有和周夢蝶握過手?」我說有,在楊昌年老師家中,楊老師宴請周公時。余老師說:「周夢蝶手勁很大,我跟他握手,手好像被鉗子夾住一樣。」余老師還是一如往常幽默,我很平和地對余老師說:「老師,謝謝您,謝謝您對我的提攜與愛護,謝謝您。」
余老師的〈鄉愁〉和〈鄉愁四韻〉是我小時候的文學啟蒙,我對這兩首詩有很深的感動,它讓我終於可以理解不擅言辭的老兵父親,深藏在他內心深處難以言說的悲傷與懷念,他想念他的母親(而且終生再也見不到了)、他的家人、他的故鄉,這首詩幾幾乎成為當時戰亂流離、有家歸不得的共同時代心聲(當然它的流傳與宣揚似乎同時也不經意壓抑了沒有相同感受的另一群人,例如我的阿母、阿公、外戚親族,他們已經在台灣住了幾百年,他們的鄉愁已經是不相同了)。所以當我看到陳芳明老師編選《余光中六十年詩選》,我曾不解地問余老師,為什麼懷鄉題材的詩歌幾乎都沒選了?余老師說:「芳明是在幫我。」我才恍然大悟,時過境遷,價值觀開始轉變,抉擇詩歌的標準也開始轉變了,不同地域、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認同,各取所需、各擇所好。──我忽然想起余老師曾對我說的一段話:「別人寫作可能是專賣店,我的則是百貨公司,應有盡有。」這是余老師的自信,他的作品不怕被挑選,即使像台灣鄉土題材,他也有〈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台東〉、〈霧社〉、〈車過枋寮〉、〈西螺大橋〉等等傑作。
知道余老師過世消息,我心情非常難過。同時也在網路上看到認識的、不認識的朋友開始重新翻出余老師少數幾篇詩文而大加評議,我自學了薩提爾就比較能夠平和面對,甚至開始正向好奇這些評議者寫作時的各種不同感受、觀點和期待,以前過往的種種成長經驗與教養(無論他們可能意識到或者沒意識到),也就充滿同理之情。倘若如此,我也許也就能夠同理余先生在那個時代,他做為一個聲望崇隆的作家,他有他自己的價值觀、認同、深情與追求,每一個時勢的轉變,他都需要作出艱難的抉擇,每做一個抉擇就必須為做出的抉擇,負責與承擔。
我認為余老師的文學成就必定名留青史,他的文學地位也就不會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評定就評定了。──我博士論文寫蘇東坡,我喜歡東坡這個人,喜歡他的作品,有一回我跟余老師說:「老師,我常常感覺您就是當代的蘇東坡,我能認識您,彷彿跨越時空認識了蘇東坡。」余老師一如往常幽默回應:「我的字沒有東坡好,但東坡的英文沒有我好。」我感覺余老師對自己的作品充滿信心,他的傑作和東坡相比亦毫不遜色。我講蘇東坡,一般人也許不太知道東坡過世時,他的名字還刻在〈元祐黨籍碑〉,被視為奸黨(大詩人李白晚年更慘,不但因政治獲罪還被流放夜郎、沉淪漂泊、孤終於江南),但隨著時過境遷,歷史又開始還給東坡更多客觀評價,我相信余老師也是如此,何況余老師目前幾乎沒有東坡或李白剛過世後不久的極端評斷。
我很喜歡陳芳明老師講的兩句話:「政治使人對立,文學讓人和解。」他曾因政治見解不同和余老師決裂,後來又因為文學之故和余老師和解。──毓老師上課經常對學生說:「勘破世情驚破膽,萬般不與政治同。我的祖先是努爾哈赤次子,可以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親手殺了自己的兒子和孫子。我告訴你們,這就是政治!」我每回想起這段話,總是不寒而慄,人世間難道只因為觀點不同、價值觀不同,就一定要對立,沒有和解的機會了嗎?──芳明老師和余老師的和解,正好為大家做了最好的示範。「寬容比愛更強悍」,這也是陳芳明老師的句子。
因為懂得彼此的艱難,懂得了體諒,或許就能夠看見彼此之間的渴望,感受到了愛與被愛,感受到價值、感受到接納,因而慈悲起來。
余老師的〈紅燭〉最後寫著:「燭啊愈燒愈短/夜啊愈熬愈長/最後的一陣黑風吹過/哪一根會先熄滅,曳著白煙/剩下另一根流著熱淚/獨自去抵抗四周的夜寒/最好是一口氣同時吹熄/讓兩股輕煙綢繆成一股/同時化入夜色的空無」,這樣珍惜、疼惜夫妻間的愛與深情,余老師是那樣深深記掛著余師母,余師母又是那樣堅強與勇敢,繼續挺立、繼續燃燒。
余老師先行熄滅,但他確實如同一根蠟燭,曾經在人世間散發出溫暖的光芒,照亮過許許多多人幽微難言、隱晦難宣的心曲。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