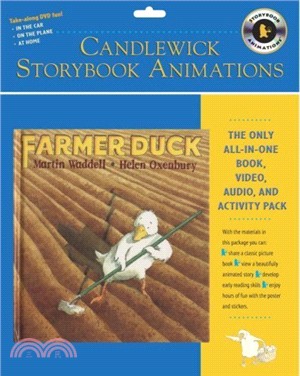春花忘錄(電子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轉動歲月最深情的旋律
重現屬於「老台北」的花樣年華。
陳芳明 主編撰序
作家 房慧真、夏瑞紅 專文推薦 (按姓氏筆劃排序)
作家 王美霞、王盛弘、楊佳嫻、楊富閔、劉梓潔 懷舊推薦 (按姓氏筆劃排序)
她的文字,代表了開放時代的風格,一方面嫁接古典的記憶,一方面探索全新的經驗,終於鍛鑄了夏樹體的散文。──陳芳明
如今來到面前,直見性命的,是經年累月打磨成一本書的夏樹,文字手藝活於她,自由寬廣,任性而為,卻也鎮重以待,特別能讓我想起,寫作的初心。──房慧真
大稻埕街頭巷尾的生活氣味、母語裡的人情世故,還有歲月裡那些人來人往、悲歡離合,密密織成一位深情女子的前半生,也是一個漸漸淡出的時代珍貴的紀念物。──夏瑞紅
本書特色
◎陳芳明主編,新時代散文書系──「Essay時代」第二波重磅推薦。
◎作者透過熾熱情感、庶民語言,創作出俗世舞台上的生旦淨末丑,共同傳唱台北老城最優美的古韻今調,成就灼熱動人的新時代散文佳作。
本書內容
因為有想像的觀眾,假設的舞台,最好的時光,心就還是熱的,我才能不斷掇忘采錄,古早大稻埕,生我養我,兒時商店街的「舊情綿綿」。更在多年混跡,江湖走老之後,膽子不小,把骨子裡那一仙「漂浪之女」的形影搬弄出來。以及,念念想想,「牽你的手」,讓我此身完全不一樣的,那些老人們。——夏樹
最壞的時候浮想連翩著最好的時光,
老人、老街、老樹、老房子、老社區、老故事,
越是黑暗,底層的珍珠才會閃著動人的光。
當走馬燈亮起,曲盤流淌數十年離合悲歡,
麵茶,爆米香,點阿膠,戲棚下純手工「凸糖」,水煙瀰漫的切仔麵攤;
時間恍如童年雞蛋冰,滴閃甜蜜滋味,
為來自大稻埕的漂浪之女,留下真摯的溫柔。
長大後她走進獨居老人家屋,擁抱阿公阿嬤們的皺褶身軀,
當阿嬤回應一聲「乖」,像母親憐愛著自己小孩。
她動也不敢動;最怕一開口,那種說不出的溫情就會陷落……
看夏樹的散文,像是她正在耳邊細語,用親切庶民語言說著迷人的老故事。她刻下童年大稻埕圖景、與年長者相伴的社工生涯,溫暖書寫搭上一首首台語老歌,迴盪大時代的舊情綿綿,彷彿喚出人們記憶裡的一蕊春花,以及湮沒在人事滄桑中、被遺忘的深深眷戀。
本書共分三輯,「舊情綿綿」從童年記憶談大稻埕的環境變遷、生命情態;「漂浪之女」則書寫生活感懷與所遭遇的形色風景、文藝少女的多樣閱讀心靈;「牽阮的手」則深入描繪參與老人照護工作的點滴歲月,勾勒年長者生命缺口及長伴左右的深刻體悟。作者坦言,這個特殊經驗,致使原本性情執拗、孤癖、脾氣壞的她,學會的第一件事,不是社工助人專業,而是擁抱。
作者簡介
古早時代,伊是「大稻埕ㄟ查某囝」;春去秋來,長大成了「大橋頭一蕊花」。輔大歷史系畢業,治史無方,學商不成,誤入社工領域,成為老人服務界的苦海女神龍「大姊頭仔」。寫作完全是雲端上的情與慾,老台北、老故事、老靈魂,雖然白雲蒼狗,但也因此,有了一片樹林。
目次
推薦序/大稻埕的光影──序《春花忘錄》 陳芳明
推薦序/文字手藝人 房慧真
自序/盛夏的春花
輯一 「舊情綿綿」
商店街
燈的星河往事
大光明˙放光明
那一段太平永樂的歲月
寂寞的煙花特別美
紅豆詞
捏麵人
戲棚下
流動車
圓環頂
大稻埕ㄟ查某囝
我城˙小鋪
輯二 「漂浪之女」
講台詞
台妹浮浪貢
外婆的青花瓷
病房記
時光剪
如晤
動物誌
借物少女
輯三 「牽阮的手」
一生一次
來去南機場
底層的珍珠
貓奶奶
老曲盤
神隱老少女
城南老故事
河圖
孤嶺街
記憶的河
跨年
穿過縣境長長的隧道
說故事的人
書摘/試閱
大光明˙放光明
打開時報出版的《台北老街》,極大篇幅,作者莊永明先生,用「台北人寫台北事」的溫柔筆觸,撫今追昔,重新打造出舊日台北「城外」延平北路的一段「太平」歲月。從「延平北路頭」一路走到「台北橋腳」,商家雲集,風月無邊。「江山樓」前,車如水馬如龍,「媽祖宮」裡,有燒香有保庇;直的大街處處興隆,縱的小路條條通達,一下子是「生生皮鞋」、「狗標服裝行」的如今安在,一下子又是「波麗路」、「法主公廟」的輝煌過去,每一段講古都似歷史掌中戲,搬演著那一代台北人繁華如夢的時空傳奇,也像極了張愛玲筆下,上海弄堂那三十年前的老月亮,有著年華已沉可是故事永遠完不了的一爐香。
「延平北路的精華在二段」,《台北老街》裡是這樣講的:
二段的六十一巷,走二、三十步有一家老戲院「大光明戲院」,日據時代稱為「第三世界館」,在台北市「古老」電影院排行榜中,是在前幾名的。這家戲院是台灣人的「專屬電影院」,所以在默片時代是用閩南語旁白的。
這裡的二段六十一巷,就是我小時候住的那條燈火明燦的商店街。
我出生後第一個十年,就住在這巷仔內。六十一巷不很長,但連接了那個年代極重要繁榮的兩條台北大街,從我家,向左走,向右走,幾乎數同樣步伐,你會抵達太陽的西邊延平北路口,以及月亮的東邊重慶北路上。
依照莊永明先生的台北老街地圖,我的童年,離那家古早台灣人專屬戲院「大光明」,也只有二、三十步之遙了。
通常是下午,背著書包放學了,天色尚亮,吃飯嫌早,又不急著寫國語或是算術的功課,我這個小鬼頭,賊頭賊腦現身「大光明戲院」售票廣場。早已忘了身邊玩伴是誰,只記得當時左鄰右舍孩童中,沒哪一個查某囡仔像我,頭毛剪短短,身軀瘦卑巴,穿條小裙褲,三兩下就爬上,購票窗口兩邊的鐵欄杆。其實,那欄杆根本不必費勁去爬,只要雙手往上撐,兩腿用力蹬,空中挺腰轉身,下一秒鐘小屁股就斜坐在欄杆上兩腳晃啊盪,瞇起眼睛,一邊看誰來買票,一邊看電影櫥窗海報。
那是很遙遠的畫面了,黑白劇照下,圖說著三兩句台詞劇情對白,有文有戲,連環張貼,一場看過一場,從預告看到下檔,吸引我讀著,編織著,眼睛茫啊茫,心跳踢踏踩,故事開始了而我就在這裡呢。「大光明戲院」雖然位於巷仔內,但一天放映下來,戲院門口總有那麼多沒事幹的流動人口,跟我一樣貪看櫥窗海報的,圍著「卡打車」用彈珠台打煙腸的,一肩兩擔賣醃漬水果的,等著排隊買票、散場後流連不去、路過、來這「消涼」的……。隨著天色愈來愈暗,出沒的閒雜人等也愈來愈多,那時就差不多該停止張看回家了。
戲院名曰「大光明」,印象中那裡永遠陰陰暗暗,頂頭看板油彩著大花臉的男女主角,沒有霓虹閃爍,看不到明明天光,只屋簷上櫥窗前,點著幾燭光的白色燈管,映著水泥地板坑坑疤疤。住在一條擁有一間老戲院的巷仔內,對一個自小就喜歡東張西望、看圖念字的小孩來說,是一件幸福的事。幸福就是,你不了解這世界,可內心單純的喜樂與滿足,如火苗一樣溫暖光明。於是,巷口大光明,巷內放光明,紅牆綠瓦,烏衣藍衫,一戶一戶都像電影裡既熟悉又陌生的後街人家,那裡面有故事,我從小就知道。
戲院廣場前廝混的時光,有幾次,大人也會帶我進場看電影,當小孩的好處就是看電影免票,沒座位站著也好,還可以跑來跑去。記得大光明戲院觀眾席是會往後仰的木椅,硬梆梆,坐起來吚歪吚歪叫,這沒什麼好挑剔,也沒空管這些,因為戲院很大,所以銀幕更大,影中人直逼眼前,動不動就會蹦出來嚇你一跳。
電影未開演,大銀幕一律垂著紅絲絨布,上面繡貼「黑松汽水」斗大四字,入座後人聲嘈雜如汽水冒泡此起彼落,大家都在等,等那新娘喜幛般的紅布,緩緩從中間往兩邊拉開。先是「松」跟「汽」不見了,再來是「黑」與「水」,拉到最後,一片布簾變成兩根紅柱子立在銀幕邊側。噓~放電影了。我那單純的小腦袋沒懷疑過為什麼,一道光束投曳到前面就會有人有聲有影,感覺是走進了時光隧道,恍恍惚惚,半睡半醒,等到重現光明,布幕也慢慢拉上,明明白白告訴你這一切就要戲終人散。
大光明,放光明、老電影,老情人。我懷念這種放電影前動態的「開場白」,那幕後有人,手動拉開電影序幕的古意與可愛。
記得「紅與白」的銀幕,卻記不起來看了哪些片子。印象中勞萊哈台王哥柳哥等都沒看過,武俠片似乎有,但說不出什麼特別的。畢竟當時年紀小。我對黃梅調也沒風靡過,應該是沒趕上「梁兄哥」熱潮。古裝片、時裝片有看沒有懂的倒是不少,腦海裡偶爾會跑出來一齣歌仔戲天王楊麗花小姐反串的戲,片名不記得,劇情也早忘了,亂七八糟就只記住一幕激情戲。那時,楊麗花還沒後來那麼家喻戶曉,她演一個小廝,被家裡主母看上,兩人相擁雙腿交纏倒在木床,鏡頭一帶,反串的楊麗花小姐下面穿的男人褲管被一雙細白腳丫子慢慢勾動漸漸捲起、捲起,露出一雙赤裸小腿,再下一個鏡頭,就這樣雨收雲散,成其好事了。
電影影響人生,我至今對男人小腿仍然懷有無限遐想。
所有老街,都自有一頁回不去的滄桑,古老戲院領得了一時風騷,卻爭不過百年的浪奔浪流。大光明戲院那一爐香點得人薰薰欲醉,終究還是隨著三十年前的老月亮沉落在淡水河的淺灘。如果沒有記錯,未搬離那條商店街前,戲院就因環境變遷,生意不佳,改為「大光明歌廳」。少了電影海報,多了酒色財氣,廣場不再可愛,沒有「黑松汽水」的帷幕,不見排排坐的觀眾影迷。再後來,歌廳也經營不下去了,大光明就這樣,比繁華落盡還更早一步,黯淡殞落,永遠失去了光明。
外婆的青花瓷
關於外婆我最久遠的記憶是哭喊的我被她抱著。
小時常跟姊姊住在外婆家,爸媽都忙,一間小工廠要養家活口,我不是被放在家門口自己玩耍,就是被託給外婆照顧。姊姊更是被家族親友戲稱,是外婆最小的女兒。有一次媽媽把我帶到外婆家,要離開時我大哭,外婆抱著我、哄著我,我更是冥頑大鬧,手一揮,掃倒了客廳裡擺設的青花瓷瓶。
那只青花瓷,現在只能在牆上我外曾祖母的遺像中看到。年輕的外曾祖母,端坐舊式木製硬椅,素袍髮髻,神態靜美,一旁擺放的,就是這只被我一把掃碎的傳家老古董花瓶。古早相片,昏黃斑駁看不太見花色瓷地,但確實是圓身細頸青瑩釉花。這青花瓷瓶哪來的呢?相傳我外公家上上幾代祖先中出過秀才,大約是那時書香門第傳下的。
外婆從沒當面念過我這件事,倒是常聽大人們指手畫腳說起那只青花瓷。彷彿所有人都在場目睹,我如何頑劣,如何哭鬧,如何在外婆懷中掙扎,如何一個粗暴動作,瞬間毀了一樣美麗的東西。也許這畫面並不是我真正腦海裡躍岀的記憶,只因為不斷被談及、引述、倒敘,以致我,彷彿自己也親眼看見了,愛哭彆扭的童年,那只青花瓷,緩緩落下、跌成一片、一片、就此不復存在的殘念。
我父系與母系家族各有不同技能,爸爸這一族的才幹在人際商場、舌燦應對,媽媽這一支的特質在美術書畫、手藝靈巧。外公是音樂老師,彈一手好琴,寫一手好字,晚年更究學命理風水,儼然「半仙」。外婆雖不識字,但擁有一身好工藝,種花蒔草、修水電、做木工、塗水泥,居家鄙事,完全難不倒她。小學勞作課,幾乎所有要交的手作品都是外婆幫我做的,其他童玩類,沙包、毽子、摺紙、燈籠等,也都是外婆推陳出新做給我玩的。媽媽傳承了外婆「工匠」手藝,水電土木油漆園藝爬上爬下,全部「以母為範」樣樣行。世上不肖子孫多有,父系的「能」,母系的「藝」,凡此種種,在我身上,完全都看不到。
遺傳給我的,可能都是風風火火的硬脾氣吧,這一項,我阿嬤固執好勇,外婆堅忍頑強,無分上下。
我出世前阿嬤就過世了,但外婆的刻苦堅毅,我是從小目睹。家裡東西壞了,外婆會釘釘打打,繼續讓它能用;書架矮凳壁櫃,何必去買,自己做就有了;日曆紙背面,得用來習字算數記流水帳。外婆家有一台踏板縫衣機,用這台古早裁縫車,外婆做過小洋裝車過麻質內衣給我穿,她身上所有衣物,都是自己裁成缝就的,也常縫縫補補新衣變舊舊衣改小其餘作抹布。她最有名的事蹟是,節儉到一顆大紅豆要切成三等分用來配稀飯,我就吃過,這三分之一顆的大紅豆。
可知我打破了外婆家祖傳青花瓷,省吃儉用的她,有多麼惋惜不捨。
從小打破過很多東西,故意的、不小心,可以修復、無可彌補,貴重、輕易,甚至,無形的像別人的心、渺小的像自己的志氣……外婆的青花瓷是我打破的第一樣東西,也是最珍貴奇特,糾纏我最深最久的。長大後才懂得悲憫,許多東西,像歲月逝去,都是成住壞空不會再回來了。
這個夏天悶熱異常,所有人都擔心著,已經九十六歲的外婆過不了這樣酷烈的夏。一入夏,外婆就急速退化,之前,她已經臥床不能吃東西只能灌食了,有時較清醒,更多時候不太認得人,原本就瘦弱的她老人家,蜷縮在床上,像一個無助孩童。我跟姊姊回去看她,忍著淚握住她的手跟她說話,我們都知道,這或許是最後一次了,可以像小時候一樣,親親叫她一聲──阿嬤。
外婆離世那天,台北正創下七月溫高新紀錄,她走得很快,我們都來不及趕回去,只知道她過去得很安詳,沒什麼痛苦。連日熱氣蒸騰,外婆身後簡單莊嚴,停靈所在,正是我極小極小時候,摔碎青花瓷的那個廳室,我知道,外婆走了,以後再沒人會記得我打破青花瓷這一件事了。
二十年前一個寒冷冬夜,我們全都回去外婆家,那一晚外公彌留,小小客廳佛音敬頌: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外公自己會看「時」,半坐躺在廳頭,閉著眼睛喘大氣,用微弱如絲的聲音說著:「還袂輪到、擱排無班。」
夜裡兩點多,舅舅們再一次詢問,「歐多桑,麥躺落未。」外公微微頜首。
只見外婆跑去後壁灶腳,拿了一個粗白瓷碗出來,眾子孫團團跪下,外婆站立,手拿瓷碗高舉,在外公徐徐躺下過氣的同時,驚心一喊:「你返去了!」將瓷碗,重重往地上摔去。
底層的珍珠
記得,那些年南機場的陽光很好,總是斜斜昏昏,一塊一塊打在牆壁地面鎏金酥黃,轉角樓梯口,污漬斑彩如老照片日子停格,水泥破陷似舊電影歲月傾城;亂停的中古機車,腳踏車東倒西歪,鐵門繡蝕,木窗玻璃烏閃閃的瞳。日光無私,照著城裡的豪門大戶也照著這裡的平宅矮屋,被風遺忘的廢棄家具,隨地鋁罐踢過來踢過去,垃圾包起來依然發臭。門裡邊常躲著手抱小孩的花布衫外籍新娘,打赤膊的中年漢子叼著菸蒂當街瞪人……這個時候,陽光那麼好,挽著一個滿臉老人斑的爺爺,輕咳兩聲,走樓梯下來了。
千萬不要在背後叫他,老爺爺九十二歲了,重聽到你用高分貝音量在他耳邊大吼他也不會回頭。家裡電話永遠沒人接,得切換成傳真,寫字告訴他。門鈴一摁,屋內自有警報燈亮啊閃,爺爺才會知道要來開門。在這個家裡,還住著一個九十三歲重度失智的老奶奶,爺爺獨力照顧她。
剛開始奶奶還會從房間裡走出來讓我握著她的手聊天,重複講我說過的每一句話。我說今天星期二,她笑嘻嘻的也跟著說星期二。我問奶奶吃飯了沒,她就歪著頭看你,笑著說吃飯吃飯。我老愛問她,奶奶妳叫什麼名字,這時候就像有微微靈光閃過,奶奶會突然清醒,正確說出自己的名字然後得意地呵呵大笑。一旁的爺爺開始講故事了:「妳不知道啊,她們家是很有名望的,都是優秀的人才,不得了啊,她很聰明,當年還是全中國第一位女子學校的校長,真是了不起啊。」
每次去每次講,我怎會不知道,爺爺自尊心很強,領著低收入戶津貼的兩老,唯有在昔日榮光下才能找回一點點尊嚴。我尊敬這兩位老人家,九十二歲重聽老爺爺照顧九十三歲失智老奶奶,他們,是頑強的生命鬥士,斷垣殘壁下壓不扁的小花。
那幾年的工作經驗讓我知道,失智症是上帝對我們開的最大玩笑了。奶奶尿失禁大小便也是,需整日包尿布,爺爺不知道要常換,有幾次我去,一打開尿布,奶奶拉的稀都變乾了。開爐火不會關,差點燒到房子。出門買東西錢包的錢都被拿光了什麼都沒帶回來。明明剛吃過飯,隔不到十分鐘又去下米煮飯說她肚子餓。晚上不睡覺以為是白天不時要出去玩。大門上中下三道鎖,一點都沒用,她還是有辦法打開跑不見了。結果是外縣市警察局打電話給里長,說奶奶被送到這裡請爺爺趕快去領回她。爺爺總是苦笑,出去時,緊緊牽著奶奶的手,不肯將奶奶送去安養院說要自己照顧她。
除了不斷回憶家族輝煌,唉嘆過去歲月榮光,我沒聽過爺爺罵過老天爺怨過時代恨過命運氣過任何人。偶爾爺爺會說,照顧奶奶很辛苦啊。一缺錢用他就拿出一包一看就知道是玻璃鍍金的假珠寶請我想辦法賣了它,我只能苦笑著說會幫忙問看看;老是從散發酸臭味的冰箱端出濃濁一杯透著黴菌般螢光綠,自己打的,不知道放多久的蔬果汁要給我喝。慚愧的是,從來,我一推再辭找無數理由說什麼也不敢喝一口。
總覺得自己做太少,送尿布麥片等物資,帶他們去看醫生,有時在爺爺出門辦事時到家守護奶奶,安排義工陪奶奶做一小段肢體活動希望減緩她退化。撐了幾年,奶奶幾乎全臥床了,想辦法說服爺爺接受居家服務週一到週五每日三小時。又過了一年,奶奶功能退化到被強制送護理安養,每月,我們能做的就只是,開車接爺爺到安養院去看奶奶了。
在那個日曆永遠沒有撕,光陰靜止,幾乎無聲的小房間,陽光像個頑皮小孩,躲樓梯間,藏屋簷下,在窗外張看,任憑你熱情招手就是不肯進來。我不怪他,生命的缺口,時時會卡進幽暗深谷,陷入闇然山洞,忽明忽滅無可遁逃,只能仰望眼前一絲小小星光。最壞的時候浮想聯翩著最好的時光,老人,老街,老樹,老房子,老社區,老故事,愈是黑暗,底層的珍珠才會閃著動人的光。
河圖
二○○一年,我被老天爺丟在老南邊的河堤,沒背景,沒經驗,也沒有想太多,傻傻的,混在一群專業社工裡,渺小膽怯,生疏呆板,完全是走錯地方的怪咖小蒙童。他們說,接下來你要做的是「社區工作」。那時並不曉得,我的未來,就是一張生命河圖的描走,那麼豐沛,如此激越,改變了我前半生,情感流域平淡緩慢的走向。
是的,往事並不如煙,往事只如河。
從乾旱到雨季,大河蜿蜒到支流汨汨,一去不回到細水長流,河的暢快,河的嗚咽,河的喧譁,河的悲切,河的上下,河的清醒眠夢,河的趕,河的泅,河的前世今生,我就像個河道勘察員,巡過市區里鄰大大小小水路,記下每一段河道湖泊,沙洲漩渦,每一個水邊人家,岸上走卒,這裡,那裡,花了近十年時間,手繪出,只有我才知道的城南河圖誌。
有河就有人。人的溫度,人的百態,人的流動,逝者如斯,我就這樣,向著滄海眾生的方向隨波而去。
她,二十幾歲,是蘆洲一間幼稚園的園長。二○○二年春天,我走河涉水,外表無事,內心惶恐,她等在那裡,是無怨無償的到宅服務義工,比我還早,比我還遠,從淡水河下游左岸,溯河而上,過橋城南,帶著我,跟著我,一起看老人。
美麗的她,性子極好,年輕善良,同時擔任許多單位的義工,慈濟、救難協會、流浪動物……在我們這裡,除了幫忙打問安電話跟老人家聊天,推輪椅帶永春街的阿婆去三總看醫生我找她,汀州街雙眼全盲的阿伯要送餐我找她,詔安街有阿嬤憂鬱症發作了需陪伴安慰我找她,金門街胖伯伯得去拿處方箋取藥我找她,水源路外省伯伯失聯好幾天了趕去破門我找她,安排帶牯嶺街舊書店伯伯出來參加活動我也找她。一個月幾次,我們會一起上寶藏巖訪視羊腸石階上的老爺爺,或是,跑遍整個城南,溯源巷弄水路,送年節關懷物資給每一個等候的獨居老人。
母親節到了,她教自己幼稚園孩童畫母親節賀卡。那卡片,一張張可愛極了,小朋友用斗大歪斜的字或注音,寫著:祝親愛的奶奶永遠青春美麗健康母親節快樂。童稚趣味的筆觸,畫著一個個可愛的老奶奶喜樂的臉。嗯,我們可以再細心一點,每一張畫,要長得像每一個拿到卡片的老奶奶喔,她如此貼心地說。然後,花一整個週末,陪著我,到所有獨居奶奶家中,送卡片,陪她們過母親節。
永遠記得那一年小年夜,送年菜給獨居長輩,那晚,雨勢極大,我跟她,手裡拿著大包小包,冒著大雨就這樣一邊找著地址一邊冷得發抖,快十點了我們才將最後一份年菜送到寶藏巖伯伯家中,伯伯嚇了一跳,那麼晚那麼冷雨那麼大你們怎麼來了。我們相視一笑,滿心歡喜,走著黑黑彎彎的山路下來,身體都溼了,可是心好幸福好溫暖。
那幾年,她把愛,給了許多需要幫助的人,也從未婚到變成人妻,生了一個小女孩。她的女兒很乖,從小就跟著媽媽一起做義工,抱在手上,蹣跚走路,可以幫忙拿東西,小女孩長大了,跟媽媽一樣,體貼溫柔,獲得每個人喜愛。
我們很能聊,她說我,天生就是適合做老人服務,那麼多爺爺奶奶,「怎麼每個人都愛你呢!」
我也常念她,明明那麼多人追怎麼會嫁給這個老公。她的婚姻並不幸福,嫁的人,吃喝嫖賭樣樣來,常常伸手要錢,並不疼惜,如此良善溫暖的她。
終於,她努力撐了十一年的婚姻在一次家暴事件中忍無可忍破局了。報警驗傷通報家暴中心,分居協議對簿公堂打離婚官司爭女兒撫養權,她帶著女兒搬出來,賣了蘆洲的房子,沿著水岸遷徙到八里。開了家小小燒烤店母女倆相依爲命過日子。
天氣已寒未涼的十月,我回頭過河,擺渡西岸,去了她的店。
四五個桌子的小店,居酒屋風情的深夜食堂,一盤盤串燒,羊肉烤魚炸物,大杯生啤酒。浮一大白,我們對飲著這幾年來的人世變化、肝膽相照,她的好,她的痛,她的未來,也聊著那些訪視過,如今大多已不在了的老人家。聽她講,女兒的懂事,那人的卑劣,她到現在,還被勒索著大筆金錢才能從婚姻中脫身。離婚官司仍然沒完沒了。
她有個好女兒。小五的女孩,什麼都看到了,也什麼都懂,告訴媽媽要勇敢通報家暴中心,陪媽媽出庭作證,看到爸爸就趕快轉角躲起來。堅持跟媽媽,下課後在店裡幫忙招呼客人送菜端盤子結帳累了才到後面沙發睡覺等媽媽午夜關店後一起回家,忍受同學異樣眼光。一切努力,只爲了有一個小小遮風避雨的家可以安心睡覺。在自己臉書上PO文:外公,今天是你的忌日,我跟媽媽來看你。媽媽說她累了,如果你要將媽媽帶去照顧,請記得要把我也一起帶去,還有阿嗚跟魯蛋。
阿嗚跟魯蛋,是小女孩領養的二隻流浪狗。
她說,或許是從小跟著我們去做服務,知道許多社會底層,老爺爺老奶奶的艱難,女兒有著異於同齡小孩的懂事成熟,讓人心疼,也讓人感謝,那樣的柔軟沉靜,可以支撐著她們,走過這段日子的苦,與生命繼續周旋。
心酸酸,眼也酸,是的,爲了小孩,大人要更勇敢,去保護自己最重要的人。
十年多來所有浪花的拍擊,湧上了心頭,拿起筆,我在店裡牆上,簽名寫下了:
愛妳。
那是我河圖誌上最真心感謝的一筆。
寂寞的煙花特別美
從前每天我和娟娟在五月花下了班,總是兩個人一塊兒回家的。有時候夏天夜晚,我們便叫一輛三輪車,慢慢盪回我們金華街那間小公寓去。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常常一個人先回去,在家裡弄好宵夜,等著娟娟,有時候一等便等到天亮……
這是白先勇經典小說〈孤戀花〉一開始,像暗裡點起了一根菸,紅光明滅中,這樣寂寞的「我」,平平淡淡說著一段不堪回首的煙花故事。雖是小說開始,卻有一個關於「從前」,而且是「每天」的結束。一夜繁華已盡,尋歡的街道夜歸的三輪車上,坐著從五月花下了班的「我和娟娟」,慢慢盪回自己的家。晚風裡酒氣已殘菸味銷然,樓台下霓虹燈滅胭脂淚乾,唯有這首〈孤戀花〉的台語老歌,還在曲終人散後被細細顫顫地哼唱,我們累了倦了不想再唱,也許,會有那麼幾個不曉事的女孩家,一唱就到天亮。
這些不曉事女孩家裡,肯定是有我一個的。小時候,住在舊日台北城夜生活最絢燦的地段,延平北路上走一回,一回就夠了,那條人文薈萃、商機無限的馬路,宛如大運河般日夜閃爍著五光十色的海上花,過眼如走馬。「做生理」的商賈店家、「攢吃人」的販夫走卒、「走酒家」的風月場合,還有許多無法歸類的人情百態,浪裡浮生舟楫過往。不只是延平北路如運河通南北,整個大稻埕一帶流金鑠鑠,吃喝玩樂的迷糜風光直如十里洋場,日間升斗營生,夜裡聲色犬馬,買進賣出向上提升的同時,也向下沉淪著人來人往的世間遊戲。繁華兩字如此多嬌,但對我而言,家在延平巷弄的童年時光,卻是運河上的清明圖樣,單純過日子努力長大,小孩子該懂的我懂了,小孩子不該懂的我也是似懂非懂,就因為外面世界如此動盪喧囂,我從小面對人群,隱隱總有著門外即天涯的蒼涼。
「五月花」不開在太陽下,就開在我家巷口不遠處,是一高朋雲集,引領風騷的銷金窟,同個地段上,還有一間「黑美人」大酒家,同樣是客來如雲、紙醉金迷。不知道白先勇寫下「從前每天我和娟娟在五月花下了班」這些文字時我幾歲了,我猜想是牙牙學語或蹣跚學步的時候吧。
這些酒家都會把花與人的店名,閃成大面板霓虹燈,層層點亮,再慢慢滅掉,等上一二秒,馬上「五月花」、「黑美人」幾個斗大的字全景一閃如煙花散落,遠遠就看見,但也立刻落入黑夜中,一次又一次,煙花的美麗與哀愁在燈光變幻中重新來過。一個娟娟是一朵煙花,一個夜晚是一樹煙火,煙花們有著自己寂寞的歌,絕不單單只是一曲「青春叢誰人愛,變成落葉相思栽」。
我是有印象的,家前面巷子裡就住著幾個「上班小姐」,她們也許是麗麗還是曉萍,蘭妮或是夢娜,我不知道,她們過她們送往迎來的生活我們有自己勞動階級的脈動。有時,白天不小心經過「黑美人」,暗色玻璃門前,只見一個擦皮鞋小販的鐵灰架踏板,等著今夜哪個老闆意氣風發地「走腳到」,空氣中還凋萎著一縷香氣,那是昨夜那卡西小歌女早熟也早夭的可憐戀花。僅有的一次,在晚上被大人牽著走過「五月花」,就那麼剛好,我看到了,酒家外幾個男子醉得東倒西歪,摟著風情萬千的女人大聲譁笑,不是要進去,也還不準備離開,就占著騎樓搬演一場風塵惡的戲碼。我訝異極了,問大人,他們在做什麼啊。人生有很多問題是要不到答案的,別人就算知道也不會跟你說,可那一幕燈紅酒綠、男歡女愛的金粉畫面,卻提前讓一個小女孩預知了一個「真亦假來假亦真」的世界。那個古早年代不見得有多麼了不起,然而,唯有看過舊時月色才會照見自己內在温溫潤潤的光。
商場與官場文化,過去現在都流行在酒家談生意,大概有粉味的地方應酬起來特別對味,乾杯時候,言語分外投機。大稻埕這個商賈之地,龍蛇雜居,黑白縱橫,有錢有勢的,「走酒家」如「走灶腳」,就連尋常百姓,辛苦做自己,偶爾也要體會不同的人生滋味。有一年尾牙,爸爸宴請「辛勞」(夥計),席設某大歌廳,疏疏落落也是一桌,幼小的我竟然跟了去。舞台上,不時有濃妝歌女獻唱動感舞曲,紅燈綠光閃耀迴旋,平日規規矩矩的小伙子幾杯下肚,眼神就開始迷離。那一餐吃很久,外面夜色深重了,歌廳氣氛愈來愈是火熱。
我乖乖坐了一整夜,正有點睏,冷不防燈火全暗,快板舞曲一下子變得糜糜膩膩,所有人都站起來,往舞台靠攏,鼓譟,吹口哨,後面的人就站在椅子上。我呆住了,拉了拉身旁的爸爸大喊我看不到啊,爸爸笑著彎腰問我妳要看嗎,我都快哭出來了,直説要看,你們都站起來我都看不到啊。只那麼一剎那,爸爸把我扛上了肩頭,就那麼一眼,燈光昏暗,越過眾人頭頂我看到,台上一個身披薄紗的曼妙女子正把一塊綾羅花布從胸前掀去,扭了幾下。我嚇住了,張大口不哭了。就在這時候,我們那桌唯一坐在椅子上的媽媽一把從爸爸肩上扯了我下來,罵道:「夭壽喔,給囡仔看這脫乳舞。」
什麼都看不見了。但在我小小心靈,同樣有一個「他們在做什麼」的疑問,就這樣跟著我長大。
知道飲食男女在做什麼,這可要等到小學快畢業的時候。一天下課,跟同年級幾個小男生晃去歸綏街吃巷弄小吃燒麻糬。那是一個夏日憊懶午後,陽光乾淨刺眼,每個人的影子直直踩在腳下,不識路隨便亂走,忽然看到兩旁房舍,一間間屋子亮著一般人家不會有的青紅燈,幾個女子低胸短裙,翹腿坐在門口。我們馬上知道闖進了一個不該來的地方,每個人都低下頭只想快步通過,背脊發涼中,一個尖細女聲喊道:「少年ㄟ,入來坐。」男同學羞紅了臉,開始往前跑,所有人跟著跑,那段路很長,不時還聽見背後,幾個女人浪蕊浮花,野冶挑逗的笑。
這一切,多像在拍電影。前幾年雙十國慶心血來潮到水門外看「放煙火」,很久沒回到這個地方了,不是為了要看煙火我大概也不會走過這條舊日大街。金秋十月,空氣漓涼喧譁,夜空如晝,火樹銀花迸迸裂裂,在靜黑河面上旋開旋落,引起陣陣驚嘆。巧匠的手開光點睛了紅塵的眼,我忽然覺得寂寞,想起了很多事,幼時「五月花」霓虹燈下我問的那句「他們在做什麼啊」,更小時候歌舞廳中媽媽罵的「夭壽喔,給囡仔看這脫乳舞」,以及那一句讓我們落荒而逃的「少年ㄟ,入來坐」……。寂寞的煙花特別美,我知道,當最美的一朵煙花燃燒了以後,所有沉埋於生命底層的瓦礫與珍珠,都將隨著舊時月色落入人間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