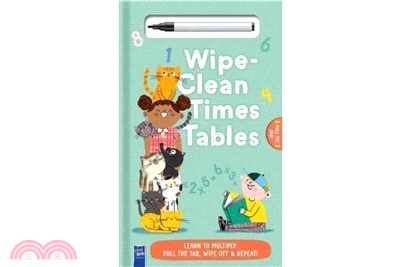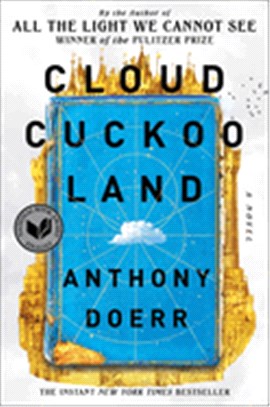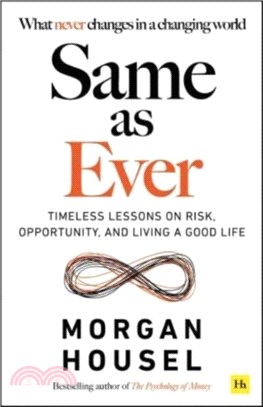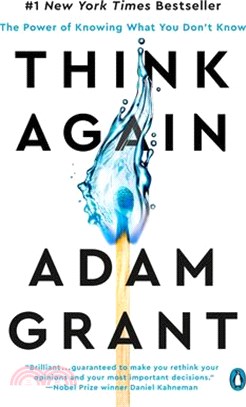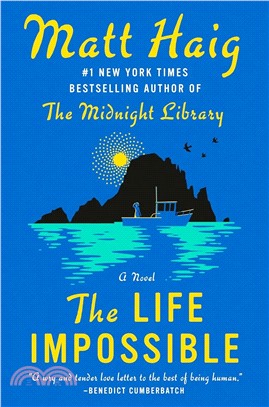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代理經銷 白象文化
《台灣新郎》以「觀念藝術」理念,藉由在原來景緻前再添加物件-「出口到美國的布袋戲人偶」,拍照之後,再將照片送回「物件」原產地展示的「編導式攝影」形式,表述了異國文化對大眾及個人的相關議題。在各個特定的環境中擺置一件特殊物象。
《台灣新郎》系列,內容本質上是作者內在「心智影像」的家庭照片,是個人多年以來和美國文化互動的感觸,以及身處家人分居兩地的沉痛。影像形式上,編導式的《台灣新郎》,著重「紀錄攝影」的文化議題與內容,豐富的影像語彙,融合了「形式主義」、「表現主義」及「觀念攝影」等多元特質為一。本章經由創作的原始動機、內容特質分析、形式理念與相關技藝、藝術特質等幾個章節,細密地論述其中的藝術思維。
《台灣新郎》以「觀念藝術」理念,藉由在原來景緻前再添加物件-「出口到美國的布袋戲人偶」,拍照之後,再將照片送回「物件」原產地展示的「編導式攝影」形式,表述了異國文化對大眾及個人的相關議題。在各個特定的環境中擺置一件特殊物象。
《台灣新郎》系列,內容本質上是作者內在「心智影像」的家庭照片,是個人多年以來和美國文化互動的感觸,以及身處家人分居兩地的沉痛。影像形式上,編導式的《台灣新郎》,著重「紀錄攝影」的文化議題與內容,豐富的影像語彙,融合了「形式主義」、「表現主義」及「觀念攝影」等多元特質為一。本章經由創作的原始動機、內容特質分析、形式理念與相關技藝、藝術特質等幾個章節,細密地論述其中的藝術思維。
作者簡介
◎游本寬,1956 年生,美國俄亥俄大學 MA(藝術教育碩士)、 MFA(美術攝影碩士),現任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教授。 在大專院校從事影像傳播與美學教育逾 30 年,退休前擔任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專任教授、特聘教授(2009-12),退休後往返美國、台灣持續教學、創作,作品曾被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等機構典藏。
專書出版
2021《招.術》
2020《口罩風景》
2019《超越影像「此曾在」的二次死亡》
2017《「編導式攝影」中的記錄思維》
2015《五九老爸的相簿》
2014《鏡話 ‧ 臺詞》,我的「限制級」照片
2012《游潛兼巡露──「攝影鏡像」的內觀哲理與並置藝術》
2011《臺灣公共藝術──地標篇》(政大學術研究出版補助)
2009《臺灣美術系列──「紀錄攝影」中的文化觀》/ 國立臺灣美術館
2003《美術攝影論思》「藝術論叢」80 / 臺北市立美術館(政大八十週年百本好書)
2002《臺灣新郎──「編導式攝影」中的記錄思維》
2001《真假之間,游本寬閱讀臺灣系列之一》/ 交通大學(政大八十週年百本好書)
1995《論超現實攝影──歷史形構與影像應用》/ 臺北 / 遠流
1990《游本寬影像構成》
個展選錄
2018《動 ‧ 風景》照片裝置 / 2018 台北國際攝影節,台北中正紀念堂
2017 <老闆!老闆?摩鐵——>照片裝置 / 華山藝文特區
2016《黑白攝影》/ 2016 台北國際攝影節「師輩秀」,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2015《五九老爸的相簿》,2015 台北藝術攝影博覽會,華山藝文特區
2014《鏡話 ‧ 臺詞》,我的「限制級」照片,2014 台北藝術攝影博覽會,華山藝文特區
2013《台灣水塔》/《臺北聲音 ‧ 臺北故事:聲音藝術家的回顧》音樂會暨影像裝置展,台灣音樂館
2013《遮公掩音》游本寬個展,臺北,大趨勢畫廊
2011《東看 ‧ 西想──游本寬「編導式攝影」》,上海師範大學藝廊
2011《潛 ‧ 露── 2011 游本寬個展》,臺北,大趨勢畫廊
2010《真假之間──「永續寶島」》,臺北,台灣攝影博物館(預備館)
2009《真假之間──「信仰篇」》影像裝置,國立臺灣美術館、北京,中國美術館
2008《台灣百貨店》/《亞洲視覺設計大觀》,藝術博物館,臺灣藝術大學
2008《台灣水塔》/《平遙國際攝影大展》,山西
2008《台灣圍牆》影像裝置 / 《不設防城市──建築與藝術展》,臺北市立美術館
2008《台灣公共藝術──地標篇》影像裝置 /《非 20℃──台灣當代藝術中的『常溫』影像展》,國立臺灣美術館
2007《台灣房子──色彩篇》/《築 ‧ 影》攝影名家四聯展
2003《私人展覽》觀念藝術活動
2002《臺灣房子──民宅系列》/《臺灣辛美學》,臺北,觀想藝廊、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2002《臺灣新郎》/《跨文化視野》,美國,賓州 Southern Alleghenies Museum of Art
2002《法國椅子在台灣》,美國,費城,彭畫廊
2001《閱讀台灣,1212》,新竹,交通大學藝文中心
2000《台灣房子在柏林》影像裝置,德國柏林 Forderkoje 藝術空間
1999《法國椅子在台灣》影像裝置,臺北,伊通公園
1990《影像構成》,臺北市立美術館、臺中,省立美術館
1984《游本寬首次攝影個展》,臺北,美國文化中心
作品典藏
《潛 ‧ 露》系列十件,國家攝影文化中心、《遮公掩音》系列三件,私人典藏、《潛 ‧ 露》系列五件,臺北市立美術館、《東看 ‧ 西想》系列八件,上海師範大學、《台灣新郎》系列十件,國立臺灣美術館、《臺灣水塔》系列十件, 福建泉州華光攝影藝術學院「郎靜山攝影藝術館」、《法國椅子在臺灣》、《臺灣新郎》,紐約州水牛城的第六及七 屆《CEPA 藝廊攝影藝術拍賣雙年展》、<芝加哥地圖 C-5 >,國立臺灣美術館、《台灣房子在柏林》衣櫥系列,德國 柏林 Forderkoje 藝術空間、<有關於高更>、<蘇珊的日記第三十六頁>及<紅色染料 #5 >,臺北市立美術館
專書出版
2021《招.術》
2020《口罩風景》
2019《超越影像「此曾在」的二次死亡》
2017《「編導式攝影」中的記錄思維》
2015《五九老爸的相簿》
2014《鏡話 ‧ 臺詞》,我的「限制級」照片
2012《游潛兼巡露──「攝影鏡像」的內觀哲理與並置藝術》
2011《臺灣公共藝術──地標篇》(政大學術研究出版補助)
2009《臺灣美術系列──「紀錄攝影」中的文化觀》/ 國立臺灣美術館
2003《美術攝影論思》「藝術論叢」80 / 臺北市立美術館(政大八十週年百本好書)
2002《臺灣新郎──「編導式攝影」中的記錄思維》
2001《真假之間,游本寬閱讀臺灣系列之一》/ 交通大學(政大八十週年百本好書)
1995《論超現實攝影──歷史形構與影像應用》/ 臺北 / 遠流
1990《游本寬影像構成》
個展選錄
2018《動 ‧ 風景》照片裝置 / 2018 台北國際攝影節,台北中正紀念堂
2017 <老闆!老闆?摩鐵——>照片裝置 / 華山藝文特區
2016《黑白攝影》/ 2016 台北國際攝影節「師輩秀」,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2015《五九老爸的相簿》,2015 台北藝術攝影博覽會,華山藝文特區
2014《鏡話 ‧ 臺詞》,我的「限制級」照片,2014 台北藝術攝影博覽會,華山藝文特區
2013《台灣水塔》/《臺北聲音 ‧ 臺北故事:聲音藝術家的回顧》音樂會暨影像裝置展,台灣音樂館
2013《遮公掩音》游本寬個展,臺北,大趨勢畫廊
2011《東看 ‧ 西想──游本寬「編導式攝影」》,上海師範大學藝廊
2011《潛 ‧ 露── 2011 游本寬個展》,臺北,大趨勢畫廊
2010《真假之間──「永續寶島」》,臺北,台灣攝影博物館(預備館)
2009《真假之間──「信仰篇」》影像裝置,國立臺灣美術館、北京,中國美術館
2008《台灣百貨店》/《亞洲視覺設計大觀》,藝術博物館,臺灣藝術大學
2008《台灣水塔》/《平遙國際攝影大展》,山西
2008《台灣圍牆》影像裝置 / 《不設防城市──建築與藝術展》,臺北市立美術館
2008《台灣公共藝術──地標篇》影像裝置 /《非 20℃──台灣當代藝術中的『常溫』影像展》,國立臺灣美術館
2007《台灣房子──色彩篇》/《築 ‧ 影》攝影名家四聯展
2003《私人展覽》觀念藝術活動
2002《臺灣房子──民宅系列》/《臺灣辛美學》,臺北,觀想藝廊、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2002《臺灣新郎》/《跨文化視野》,美國,賓州 Southern Alleghenies Museum of Art
2002《法國椅子在台灣》,美國,費城,彭畫廊
2001《閱讀台灣,1212》,新竹,交通大學藝文中心
2000《台灣房子在柏林》影像裝置,德國柏林 Forderkoje 藝術空間
1999《法國椅子在台灣》影像裝置,臺北,伊通公園
1990《影像構成》,臺北市立美術館、臺中,省立美術館
1984《游本寬首次攝影個展》,臺北,美國文化中心
作品典藏
《潛 ‧ 露》系列十件,國家攝影文化中心、《遮公掩音》系列三件,私人典藏、《潛 ‧ 露》系列五件,臺北市立美術館、《東看 ‧ 西想》系列八件,上海師範大學、《台灣新郎》系列十件,國立臺灣美術館、《臺灣水塔》系列十件, 福建泉州華光攝影藝術學院「郎靜山攝影藝術館」、《法國椅子在臺灣》、《臺灣新郎》,紐約州水牛城的第六及七 屆《CEPA 藝廊攝影藝術拍賣雙年展》、<芝加哥地圖 C-5 >,國立臺灣美術館、《台灣房子在柏林》衣櫥系列,德國 柏林 Forderkoje 藝術空間、<有關於高更>、<蘇珊的日記第三十六頁>及<紅色染料 #5 >,臺北市立美術館
名人/編輯推薦
◎A Multiplicity of Experience
With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in Taipei and a family in State College, Pennsylvania, Ben Yu maintains residences in both countries. His large-scale color photographs, from the series entitled The Puppet Bridegroom, relate broadly to the complexities that arise from living in two different cultures.
A hand puppet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bridegroom's clothing is the central motif of his work. The puppet is photographed at places Ben believes embody American culture, such as a brewery, a suburban housing development, and a monumental roadside crucifix. Inspired partly by conceptual artist Eleanor Antin's postcard series 100 Boots (1971-73), in which she photographed one-hundred empty rubber boots at various locations as they travele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ultimately landed in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the nomadic puppet wanders from place to place, dwarfed by the enormity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 With an admirable consistency of vision, Ben mindfully considers the land, signs, highways, buildings and shops, and, with even more awareness, color. Vibrant greens, reds, and yellows abound in the images, shaping the commonplace into the exceptional.
Ben attended graduate school at the height of Post-modernism, during the mid-1980s when theorists proclaimed that "'reality' as a consequence could be understood as socially constructed" (Madeleine Grynsztejn, Carnegie International 99/ 00: VO, p. 116). The ubiquitous nature of photography led to a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 by many artists at this time, and Ben was no exception. Photographs, for all their perceived "truthfulness," are fiction because they are disconnected from the time continuum of reality. Like much of the artwork created during this period, Ben's photography rests between the real and its referent, reflecting a belief i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uppet as it assumes life-like gestures and positions at odds with its surroundings. Indeed, he has transferred his persona onto the puppet with an ambivalence arising from foreign status, albeit compromised by marriage to an American. In each of the images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exist between fiction and documentary, and fabrication and nature.
His decision to insert the puppet into the landscape creates a complex reading culturally and formally. Bridegroom translates from Mandarin as new person, and Ben's work comments on the challenges of living in a foreign land where one is perpetually "new" and never fully assimilated. Creating compositions that at times fluctuate between what is perceived as real and what has been manipulated by the photographer, the distance between pho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is deliberately confused within the frame. The puppet's placement acts as a barrier forcing a confrontation prior to entering the scene. Frequently, it is positioned at critical intersections such as a bend in the road, or an entrance way, furthering an outward visual push toward the exterior of the print. In Boalsburg (2001), for example, the puppet stands in a stark wooded environment defiantly dressed in brilliant red clothing. The few wooded forests that remain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are now protected as national parks, whereas much of Taiwan's natural beauty has succumbed to housing because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limited space, and a shift from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one based in technology. By isolating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association, Boalsburg is emblematic of Ben's ambivalence toward America.
To assert that Ben documents icons of middle-class American culture is far too simplistic. By utilizing popular forms of photography such as the snapshot and vacation pictures, he notices the unnoticeable, seeing details and configurations of signs, colors, and shapes that inhabitants may not, while looking for minute details of the American scene. Trailer parks, a soccer game, cornfields, and drive-ins are associated strongly with American culture but also beg the question "Are the places he chooses to photograph 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if so, whose?" Do the images belong to an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n Hispanic culture, and an Asian American culture equally along with the majority? Do images of Pennsylvania resonate with Southern culture or that of the Western states? The photographs hang silently, offering no answers only a glimpse into the eyes of the other.
Interpreting content is complicated further by the many years I lived as a foreigner in Taipei. After returning home and having to reexamine the familiar along with a multiplicity of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re-entering society, Ben's photographs of Pennsylvania evoked a doubling of cultural associations for me. He was portraying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outsider augmented by our relationship. Images depicting a row of storage sheds, a stone house with beautiful flower gardens in an affluent neighborhood, school busses parked for the summer, and an empty baseball field all quietly disclose a society of abundance and excess. Viewed as a series, the photographs are reminiscent of a desire I had as a photographer in Taiwan to seek out familiar spaces in the unfamiliar. Ultimately, our individual efforts to photographically scrutinize the middle classes of American and Taiwanese societies had become metaphors for pers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alienation. As Italo Calvino writes, an image may appear "like a sheet of paper, with a figure on either side, which can neither be separated nor look at each other."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p.105).
In his mature work that encompasses three photographic series - Between Real and Unreal (1986 ~), French Chair in Taiwan (1997-1999), and The Puppet Bridegroom (1999-2002), Ben has created a strong sense of the essential textures and character of place, whether in Taiwan or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satire or idealism, the images that comprise The Puppet Bridegroom, in particular, delineate the myth of America, imagined by both natives and foreigners, of self-expression, ownership, reinvention, and limitless opportunity. The work speaks to a universality of experience beyond personal references, and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changing fac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Karen Serago
September 2002
With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in Taipei and a family in State College, Pennsylvania, Ben Yu maintains residences in both countries. His large-scale color photographs, from the series entitled The Puppet Bridegroom, relate broadly to the complexities that arise from living in two different cultures.
A hand puppet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bridegroom's clothing is the central motif of his work. The puppet is photographed at places Ben believes embody American culture, such as a brewery, a suburban housing development, and a monumental roadside crucifix. Inspired partly by conceptual artist Eleanor Antin's postcard series 100 Boots (1971-73), in which she photographed one-hundred empty rubber boots at various locations as they travele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ultimately landed in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the nomadic puppet wanders from place to place, dwarfed by the enormity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 With an admirable consistency of vision, Ben mindfully considers the land, signs, highways, buildings and shops, and, with even more awareness, color. Vibrant greens, reds, and yellows abound in the images, shaping the commonplace into the exceptional.
Ben attended graduate school at the height of Post-modernism, during the mid-1980s when theorists proclaimed that "'reality' as a consequence could be understood as socially constructed" (Madeleine Grynsztejn, Carnegie International 99/ 00: VO, p. 116). The ubiquitous nature of photography led to a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 by many artists at this time, and Ben was no exception. Photographs, for all their perceived "truthfulness," are fiction because they are disconnected from the time continuum of reality. Like much of the artwork created during this period, Ben's photography rests between the real and its referent, reflecting a belief i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uppet as it assumes life-like gestures and positions at odds with its surroundings. Indeed, he has transferred his persona onto the puppet with an ambivalence arising from foreign status, albeit compromised by marriage to an American. In each of the images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exist between fiction and documentary, and fabrication and nature.
His decision to insert the puppet into the landscape creates a complex reading culturally and formally. Bridegroom translates from Mandarin as new person, and Ben's work comments on the challenges of living in a foreign land where one is perpetually "new" and never fully assimilated. Creating compositions that at times fluctuate between what is perceived as real and what has been manipulated by the photographer, the distance between pho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is deliberately confused within the frame. The puppet's placement acts as a barrier forcing a confrontation prior to entering the scene. Frequently, it is positioned at critical intersections such as a bend in the road, or an entrance way, furthering an outward visual push toward the exterior of the print. In Boalsburg (2001), for example, the puppet stands in a stark wooded environment defiantly dressed in brilliant red clothing. The few wooded forests that remain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are now protected as national parks, whereas much of Taiwan's natural beauty has succumbed to housing because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limited space, and a shift from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one based in technology. By isolating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association, Boalsburg is emblematic of Ben's ambivalence toward America.
To assert that Ben documents icons of middle-class American culture is far too simplistic. By utilizing popular forms of photography such as the snapshot and vacation pictures, he notices the unnoticeable, seeing details and configurations of signs, colors, and shapes that inhabitants may not, while looking for minute details of the American scene. Trailer parks, a soccer game, cornfields, and drive-ins are associated strongly with American culture but also beg the question "Are the places he chooses to photograph 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if so, whose?" Do the images belong to an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n Hispanic culture, and an Asian American culture equally along with the majority? Do images of Pennsylvania resonate with Southern culture or that of the Western states? The photographs hang silently, offering no answers only a glimpse into the eyes of the other.
Interpreting content is complicated further by the many years I lived as a foreigner in Taipei. After returning home and having to reexamine the familiar along with a multiplicity of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re-entering society, Ben's photographs of Pennsylvania evoked a doubling of cultural associations for me. He was portraying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outsider augmented by our relationship. Images depicting a row of storage sheds, a stone house with beautiful flower gardens in an affluent neighborhood, school busses parked for the summer, and an empty baseball field all quietly disclose a society of abundance and excess. Viewed as a series, the photographs are reminiscent of a desire I had as a photographer in Taiwan to seek out familiar spaces in the unfamiliar. Ultimately, our individual efforts to photographically scrutinize the middle classes of American and Taiwanese societies had become metaphors for pers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alienation. As Italo Calvino writes, an image may appear "like a sheet of paper, with a figure on either side, which can neither be separated nor look at each other."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p.105).
In his mature work that encompasses three photographic series - Between Real and Unreal (1986 ~), French Chair in Taiwan (1997-1999), and The Puppet Bridegroom (1999-2002), Ben has created a strong sense of the essential textures and character of place, whether in Taiwan or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satire or idealism, the images that comprise The Puppet Bridegroom, in particular, delineate the myth of America, imagined by both natives and foreigners, of self-expression, ownership, reinvention, and limitless opportunity. The work speaks to a universality of experience beyond personal references, and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changing fac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Karen Serago
September 2002
序
◎出版前言
十多年前自美返國,沒有回到美術界教職,反而進了比較注重文字思考和論述的傳播學領域。新環境裡,有形的學術氣圍讓文字表述的機會大烏增加,1986年春出版了生平的第一本文字書《論超現實攝影》。幾年下來,倒驚訝的發現,字裏行間的推敲與琢磨,不但能讓模糊的藝術概念得到沈澱,文字論述中的通輯訓練,更對創作的自理有異曲同工的效益。更重要的是,白紙黑字成了創作自省的最佳指標。於是,只要有機會,便常和學生分享這和圖、文並進的創作形式。 話雖如此,總覺得自己在藝術創作實體上一直未會太使勁。
1996年的「台北雙年展」,隔年中、獻藝術家的《你聽•我說》展,在和國內、外當代藝術家的互動過程中讓自己陷人人生規劃的長思:要繼續爬格子?還是走出研究去創作?原地踱步的原因也許和在職環境尚未能接受藝術家升退有關。
是生計考量?還是對自己劍作能力的疑慮?
模糊的日子卻已日復一日的度過。
已不記得是哪年的夏天,和政大現任鄧瑞成校長(當時的傳播學院院長)開聯人生觀時,讓自己類悟應該將中年生涯(重新)定位在藝術創作,大膽的以一位「藝術家教師」走在沒有藝術系的校關裡。
指南山下孤寂的藝術環境,倒是讓自己想出如何將教學活動和創作實體整合的生活態度:創作不再只是媒材玩耍,而可以是精神和生活的實踐。日子開始雙得有些忙碌,創造的腦筋時時都在運轉。此時,文字論述的內容多已調整成如何將“不可明言”的藝術創作,用自己的體驗試加以解說。
如果描述面對藝術當時是某種點的接觸,之後其他形式的討論便是和作品撞擊產生的線。接著,如果能再將討論内容予以文字化,更成面的形式。
藝術創作的起點,如果未能延長成線,再織成了面,點很快就會隨著時間而越來越模糊。
羅蘭.巴特認爲現代人有一種無需用手執筆的新書寫方法,雖然用身體的哪一部份來書寫也許還說不清楚。不過,即使是以機器代勞,總還得用眼睛看:人的身體依然經由視覺與書寫關聯在一起。因此,任何書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原始的閱讀;如同古代的書法家一般,把文字看成身體的一種神秘投影。
2002秋,能出版《台灣新郎》一「編導式攝影」中的記錄思維,除了要感謝家人和周邊所有的朋友之外,更應感謝賜給我頻繁生活變化及挑戰的上天。生活實質的多方體驗,搭架出這些文字和影像的對話。
游本寬
2002年 / 秋 / 政大
十多年前自美返國,沒有回到美術界教職,反而進了比較注重文字思考和論述的傳播學領域。新環境裡,有形的學術氣圍讓文字表述的機會大烏增加,1986年春出版了生平的第一本文字書《論超現實攝影》。幾年下來,倒驚訝的發現,字裏行間的推敲與琢磨,不但能讓模糊的藝術概念得到沈澱,文字論述中的通輯訓練,更對創作的自理有異曲同工的效益。更重要的是,白紙黑字成了創作自省的最佳指標。於是,只要有機會,便常和學生分享這和圖、文並進的創作形式。 話雖如此,總覺得自己在藝術創作實體上一直未會太使勁。
1996年的「台北雙年展」,隔年中、獻藝術家的《你聽•我說》展,在和國內、外當代藝術家的互動過程中讓自己陷人人生規劃的長思:要繼續爬格子?還是走出研究去創作?原地踱步的原因也許和在職環境尚未能接受藝術家升退有關。
是生計考量?還是對自己劍作能力的疑慮?
模糊的日子卻已日復一日的度過。
已不記得是哪年的夏天,和政大現任鄧瑞成校長(當時的傳播學院院長)開聯人生觀時,讓自己類悟應該將中年生涯(重新)定位在藝術創作,大膽的以一位「藝術家教師」走在沒有藝術系的校關裡。
指南山下孤寂的藝術環境,倒是讓自己想出如何將教學活動和創作實體整合的生活態度:創作不再只是媒材玩耍,而可以是精神和生活的實踐。日子開始雙得有些忙碌,創造的腦筋時時都在運轉。此時,文字論述的內容多已調整成如何將“不可明言”的藝術創作,用自己的體驗試加以解說。
如果描述面對藝術當時是某種點的接觸,之後其他形式的討論便是和作品撞擊產生的線。接著,如果能再將討論内容予以文字化,更成面的形式。
藝術創作的起點,如果未能延長成線,再織成了面,點很快就會隨著時間而越來越模糊。
羅蘭.巴特認爲現代人有一種無需用手執筆的新書寫方法,雖然用身體的哪一部份來書寫也許還說不清楚。不過,即使是以機器代勞,總還得用眼睛看:人的身體依然經由視覺與書寫關聯在一起。因此,任何書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原始的閱讀;如同古代的書法家一般,把文字看成身體的一種神秘投影。
2002秋,能出版《台灣新郎》一「編導式攝影」中的記錄思維,除了要感謝家人和周邊所有的朋友之外,更應感謝賜給我頻繁生活變化及挑戰的上天。生活實質的多方體驗,搭架出這些文字和影像的對話。
游本寬
2002年 / 秋 / 政大
目次
◎
A Multiplicity of Experience / Karen Serago
出版前言
導論
壹.面對照片
‧照片是什麼?
‧照片中的藝術性為何?
貳.早期「現代攝影」的純粹「鏡像」觀
‧「現代藝術」
‧「現代攝影」的「純粹攝影」觀
‧「形式主義」的攝影觀
‧史蒂格力茲和美國「現代攝影」
參.「鏡像式表現攝影」的心智視野
‧「心智影像」(mental image)的探索
‧「表現攝影」和「抽象表現繪畫」的對話
肆.拍照記錄
‧「紀錄攝影」的操作定義
‧「紀錄攝影」的社會角色
‧「紀錄攝影」的閱讀場域
伍.個私「鏡像」的記錄藝術
‧「鏡像」紀實與藝術創造間的拉拒
‧「普普藝術」與個私的「紀錄攝影」觀
‧個人、私有化的記錄影像觀
‧渥克.艾文斯的「普普」紀錄影像觀
‧「新地誌型攝影」的紀錄美學
陸.拍照邁向「觀念攝影」
‧「鏡像」在「觀念藝術」中的角色
‧拍照記錄個人的藝術觀
‧照片作為藝術中的實際元素
‧近代「觀念藝術」中的「鏡像」觀念化
柒.再論「編導式攝影」中的影像議題
‧「矯飾攝影」的創造觀
‧「編導式攝影」的特質分析
捌.結論:《台灣新郎》影像賦形的思維
‧創作動機
‧影像內容分析
‧形式理念與相關技藝
‧藝術特質總論
註解
參考書目
作品索引
A Multiplicity of Experience / Karen Serago
出版前言
導論
壹.面對照片
‧照片是什麼?
‧照片中的藝術性為何?
貳.早期「現代攝影」的純粹「鏡像」觀
‧「現代藝術」
‧「現代攝影」的「純粹攝影」觀
‧「形式主義」的攝影觀
‧史蒂格力茲和美國「現代攝影」
參.「鏡像式表現攝影」的心智視野
‧「心智影像」(mental image)的探索
‧「表現攝影」和「抽象表現繪畫」的對話
肆.拍照記錄
‧「紀錄攝影」的操作定義
‧「紀錄攝影」的社會角色
‧「紀錄攝影」的閱讀場域
伍.個私「鏡像」的記錄藝術
‧「鏡像」紀實與藝術創造間的拉拒
‧「普普藝術」與個私的「紀錄攝影」觀
‧個人、私有化的記錄影像觀
‧渥克.艾文斯的「普普」紀錄影像觀
‧「新地誌型攝影」的紀錄美學
陸.拍照邁向「觀念攝影」
‧「鏡像」在「觀念藝術」中的角色
‧拍照記錄個人的藝術觀
‧照片作為藝術中的實際元素
‧近代「觀念藝術」中的「鏡像」觀念化
柒.再論「編導式攝影」中的影像議題
‧「矯飾攝影」的創造觀
‧「編導式攝影」的特質分析
捌.結論:《台灣新郎》影像賦形的思維
‧創作動機
‧影像內容分析
‧形式理念與相關技藝
‧藝術特質總論
註解
參考書目
作品索引
書摘/試閱
◎
建構「觀念攝影」一辭
「觀念藝術」的精神不是以探究媒介和形式而區異的活動,而是藝術家藉由不同的藝術媒介質問什麼是藝術本質?其中在藝術認知方面,如果早先的藝術是讓觀眾在模糊意象中延伸無限的想像空間,那麼「觀念藝術」則是要求觀眾從科學中尋找資料,試探明確、清晰的意義。資深的藝廊策劃人安渚.柯拉(Andrea Miller-Keller)曾歸納出某些觀念藝術家在藝術的操作方面的共同興趣是:使用重複法則;使用真實時、地、比例和過程;認知本質的探索;自我描述;不完整或疏漏,和以非常極限的動作來看藝術(the very act of looking at art)。安渚的論述,尤其是“不完整或疏漏的特質”,難免引人再思,「觀念藝術」放棄形式本身完整的概念,是否只是一種刻意的藝術史策略?而以非常極限的動作來看藝術,是否只是一種標新立異的操作手法?姑且先不去過問這些議題的結果為何,深究的焦點應該放置在:觀念本身是否真的具有藝術價值?
「觀念藝術」從藝術生態觀點來看,在傳統藝廊系統外給予藝術新的意義,成了後現代藝術當中重要的指標。回顧過去三、四十年來,攝影術在「觀念藝術」中扮演質疑藝術本質的角色,形式方面從「極限藝術」的格狀脫穎而出,結合為身體、地景等「觀念藝術」的影像紀錄,其中,當代的“新觀念藝術”攝影大都不是用來對鏡頭前原有物象的特質或內涵的再修飾。相對地,照片如同語言扮演訊息的傳遞者,只是一種記號或形體的標示。然而,對「觀念藝術」中的「鏡像」角色被稱之為“影像訊息”一事,即使《時代》雜誌的藝術編輯羅伯特‧曉斯悔很不以為然,但是,當觀念藝術家愛伶納.安町(Eleanor Antin)的作品<陷落:一件傳統的雕塑>(Caving: A Traditional Scuplture,1972)是在特定期間內,每天早上拍攝自己身體前、後、左、右的四個面向,然後再猶如醫學研究般的順序展現148張照片。整組影像中,藝術家的身體非但不具專業模特兒的吸引力,胸部或臀部反而得在標題〈陷落〉指引下,才讓觀者會特別去比較。(只可惜,其結果也沒有任何明顯的差異)在此可見的事實是:愛伶納如此直接、純粹的影像形式,完全挑戰了早先「現代攝影」的美學。照片的確如同訊息般的冷漠,或純標誌性的表象。總括拍照在邁向觀念化的過程中,至少有下列幾個顯著的特質:
1.以照片來記錄「表演藝術」、「過程藝術」、「地景藝術」等;
2.成功地應用通俗、業餘影像基模於藝術創作之中;
3.另類非單一、定格式的照片呈現觀;
4.以新影像科技挑戰視網膜、大腦對影像記憶力的極限;
5.在鏡頭前虛構故事、自創劇場,讓拍照為一種影像創造與想像;
6.在「應用影像」的範疇中,藉由影像來刺探媒體紀錄能力方面的瑕疵;
7.打被傳統圖、文間的旨徵關係,藉由文字延伸影像的旨意;
8.「標誌性」影像訊息
格雷哥利‧白特考克(Gregory Battcock)認為「觀念藝術」不是一種大眾藝術,而上述諸多特殊的照片內容或形式,乍看之下都不是藝術,對大眾而言甚至是醜陋、無聊的。正也因為有這些顯著的特質,從「觀念藝術」中精化出的「觀念攝影」才得以相異於前期的「畫意攝影」、「形式主義攝影」、「超現實攝影」及「表現主義攝影」。雖然「只聽到有更多的攝影家希望能變成藝術家;卻不見得有藝術家要變成攝影家」(John Baldessan),加上攝影術和生活的緊密性有點類似工藝的範疇,但二十世紀中期之後,「觀念攝影家」卻應用了很多的拍照專業知識及美學,使單純的藝術紀錄或喬塞夫‧科舒的「攝影式觀念主義」得以再獨立為另一個藝術的專業語彙─「觀念攝影」,進而牽引其他藝術運動的動向。
◎
《台灣新郎》以編導影像手法將一座台灣製造,身著中國豔紅新郎古裝的布袋戲人偶,擺置在美國賓州各個場景前拍照,表現個人身處家人分居兩國的沉痛。照片中,人偶的造形、肢體語言皆與所擺置的大自然或人工場景成強烈對比。進層的個人象徵與文化意義在藝術表現中的角色為何?以下本節從「新郎人偶」的符號義,以及它所處的環境內涵與特質分別加以分析。
一、「新郎人偶」的符號釋義
圖象家用圖象來呈現意象,
圖象學家則研究意象所能表達的其他事物。
繪畫經由題材、形式轉變,將一個視覺系統轉換成另一個視覺系統。相照之下,「鏡像」是拍照者經由光線、鏡頭對環境的書寫;猶如留在沙上的足印般;描述著某些事物“曾在此”的遺跡。閱讀繪畫和「鏡像」中的圖象、符號有何異同?探討這個議題之前,不得不先省思「照片論述」中的符號問題。
在社會科學或傳播領域裡,論述、言說(discourse),指的是藉由具體形式,如符號系統(通常又是指語言)等,來顯示內容的方式。語言,附屬在社會架構之下,有論述事物、溝通意見、表達情感或傳播信仰等功能,以一般使用的情況來看,是傳播者和參與者呈現一種持續互動的關係。因此,論述,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是一種語言和社會、文化和傳播間的互動概念。
承續上面的認知,細思照片是否是一種語言,或「照片論述」的可行性時,就常要使人卻步難行。從嚴格的意義來看,藝術圖象中的許多事物並不屬於符號學範圍,因為,不同的圖象既要求不同的表意系統、意義配置,也要求不同的品味介入。其結果就如同羅蘭.巴特所說的,符號學之所以不能掌握藝術的關鍵在於:藝術創作並不能夠被縮減為一個系統。加上,藝術中有眾多的因素都無法被規格化、無法達到溝通標準。因此,符號學者達密便定論的說:「藝術符號學將會只是屬於對照性。」(黃斑雜誌,Macula,1978)。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佩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曾將符號分為三類:「肖似性符號」 (iconic sign),例如:圖表、雕像和語言中的擬聲字;有因果連帶關係的「指涉性符號」(indexical sign),例如: 溫度計、風向儀和密佈的濃煙;以及從符號到釋義間有完整約定俗成的「象徵性符號」(symolic sign),例如:語言符號等。來自現實環境的「鏡像」,從佩爾斯的理念來看,就如同一般圖象,是一種「肖似性符號」,但由於它又和真實的世界有因果性,所以也是一種「指涉性符號」。即使如此,「鏡像」仍難成為如同生活語言般的「象徵性符號」,只能是藉由各種視覺形式(形態、色彩、階調等)所構成的「直觀符號語言」。
“直觀式”的「鏡像」由於未曾經過社會的制約,精確與互動性不夠穩定。由此可知,所謂的「攝影語言」,實際上是專指影像創作過程中,個人審美經驗客觀化,以及景物與抽象概念符號化的結果。嚴格地說,這種專業語言比較像是,拍照家族用來詮釋個人意念的圖象工具。
因此,以此論點進層來分析「台灣新郎」的符號意涵,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
1.新郎人偶的符號意涵—來自台灣、陌生與新手
《台灣新郎》的人偶,借自我美國的岳母,是幾年前她到台灣遊歷時所帶回的飾品,在家裡擺置了好幾年。1999年,當個人面對家庭即將分離兩地的悲情時,心有所感,才將它轉化成影像創作的實體。相較於許多留美的學生,個人對美國文化的接觸經驗算是多的,但文化畢竟是一種與生俱來,或長時間生活的共識,接觸不一樣的文化並不代表就能接受其中的差異;如同了解酸黃瓜在漢堡中的作用,但不見得人人都會喜歡這樣子的組合;“超甜”的美式點心,也未必對得上台灣人的口味等等。有感於文化碰觸過程中,永遠都會有未知的世界,因此,一種如同“新人”般的心態便造就了“台灣新郎”的角色;如同作者的境遇一般,真人、假人都是來自台灣並身處異域。最後再將「新郎」釋義出“陌生”與“新手”的進層意涵。
2.新郎人偶的肢體語言—無奈、隨遇而安、自由冥想的人形風箏
台灣新郎白皙的臉面,表情冷漠,好像任何外在的環境變化它都有應對的準備。特殊的影像氛圍,不像是講求背景擬真和表演者融入的現代式舞台劇,《台灣新郎》有它獨特舞台劇的誇張精神。舞台上,人偶唯一的肢體語言就是“平舉的雙手”。對此,西方肢體語言的解讀是︰對正在發生的事物表示無奈。但是平舉的雙手和頂直下服的整體造形,更像是人形的風箏,意味著無論環境如何的不順,它(他)都可以隨風飄向另一個臆想的場域。
3.新郎人偶的面向語言—排斥與妥協
背對著主環境的人偶,肢體語言上是排斥的表徵。初期,背向環境代表個人心理的強烈抗拒;無法面對突發奇來家人分離的情勢。中期,待慢慢能夠接受家分兩地的實情之後,肢體語言軟化為一種默認與承受。近期,隨著心態上的調整與時空的自我治療,新郎逐漸地褪除畏懼,走出消沉;以平靜的心態,站立在新環境之前,嘗試多去了解、接受新的事物。《台灣新郎》系列影像,新郎人偶三個不同“背向環境”的層次,時序上也並沒有絕對的精確關係;錯綜交替的紛亂和當事者即時的心情有關。因此,台灣新郎有時雖然到此一遊,卻沒有融入當地的情境,而顯現出一種不妥協的美感。除此之外,經常站在照片中明亮處的人偶,也暗示了它面對環境的信心。
二、人偶所處的環境內涵與特質
《台灣新郎》影像核心是個人身處和家人分居兩國痛處的實體感受與反應。象徵個人「新郎人偶」背後的戶外景緻,不是一般的美國風景照片,而是是構成作者創作該系列契因的最原始場域—賓州。其中的自然與人文風貌,猶如文學故事中的背景,是影像故事的主角︰出口到美國的「新郎」演出個人心境的場所。
在地理位置上,賓州居全美中部偏東,屬於「中大西洋區」(Mid - Atlantic),面積比台灣還大。台灣人對它的了解除了早已停產的鋼鐵大城匹茲堡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任何具體的印象。賓州當然不可能代表所有美國的中產階級,但至少不會是大眾傳播中的印象再版。由於《台灣新郎》並不是報導攝影,只是在影像創作中透露出相關的文化訊息。因此,其論述的架構也不依循一般「攝影論文」(The photo-Essay)的規劃;相對地,作者以“普普文化” 的觀察,加上個人即興的感觸,作為啟動快門重要的契因。《台灣新郎》創造的過程即使如此的“藝術”,但新郎背後眾多的影像,仍有幾個顯見的方向,例如:追隨早先美國重要「紀錄攝影」大師的步影,像沃克.艾文斯等人的主題;青蔥翠綠,典型的賓州自然景觀;以及一般中產階級的生活環境、民宅、店鋪等,還有更多無法細加分類的文化景緻。以下僅就人偶所處的環境意涵與特質分述如下:
1.追隨大師步影的沉思與共舞
新郎人偶在賓州的背景與環境選擇上,某些部分是緬懷美國早先「紀錄攝影」大師的影子。意圖藉由親身體驗,再次深思這些題材的意義。例如:戶外看板,不但具有擴大告知的商業效應,和周圍環境的共存關係也是一種“地景藝術”」。而雪景中,「新郎」背景所站立的“教堂戶外看板”,雖然不如攝影大師艾文斯成功地將“美夢”廣告詞和「經濟大恐慌」的現實作強烈的諷刺,但也表現了個人對宗教的廣告與行銷概念的贊嘆。其他如滿佈英文和亮麗圖案的大看板,在光影和環境造形間,則顯示出一種賓州寧靜生活之美。
除此之外,艾文斯對傳統商店外觀的長期紀錄,也是一項頗令後人羨慕的成就。透過老照片,即使是外國人也能夠體會這些店家老闆,將最新商品的廣告傳單、貼紙等,直覺地擺置在最顯眼位置,這種滿溢著真實生活脈動之美的店面設計美學。兼具雜貨店的加油站一直是在地文化的傳統特色之一,艾文斯的老照片中,除了可以看到早期加油筒精簡的「形式主義」風格之外,後頭店面外觀滿佈標籤與廣告,也不停地向觀眾述說了一個時代的美學,閱讀這些照片讓人有尋寶般的心境。現在老照片中的舊式加油筒,如今已不再具有服務功能,但在賓州少數的觀光小鎮,仍被當地人小心地保養以做為重要地標。台灣新郎有幸經過這些地方,也在前面拍照留念,表達對普羅大眾生活觀的認同。
「露天電影院」(Drive-in)如同台灣迎神廟會的野台戲或街頭電影院。相關影像曾經出現在個私「鏡像」紀錄攝影家葛力.溫格葛蘭等人,以及「新地誌型攝影家」羅伯.亞當斯(Robert Adams)作品裏,是美國二十世紀中期通俗文化的要角之一。電影院的營運方式是︰付錢後,將自己的車子開進一個特殊的電影播放廣場,面對大螢幕,觀眾再透過車上調頻收音機,或車旁站立的喇叭來收聽影片中的音效。某些「露天電影院」在電影播放之前,還會有其他表演活動以吸引更多的觀眾。六○年代左右,「露天電影院」不但是年輕人幽會的重要場所,更是家人夏季聚集共享爆米花、冰棒的據點,帶給當今許多中、老年美國人美好的回憶。台灣新郎因此特別拜訪了在賓州僅存的少數者之一。
以美國國旗為主要封面設計的「紀錄攝影」經典作品集:《美國人》(The Americans,1956),原籍瑞士的作者羅伯.福蘭克(Robert Frank)以一個外國人旁觀的心態,在五○年代就注意到國旗普遍出現在當地日常生活的情形。事實上,溫格葛蘭六○年代的作品,也涵蓋相當分量的國旗影像,從辦公室到大街小巷、餐館等。美國在「911」大災難之後,全國上下懸掛國旗的意識高漲,即使不是節慶的日子,也可以看到一般家庭在窗戶上、車庫前、前庭院中佈置國旗,其他公共場所舉目可見的情況更不在話下。2001年九月十一日以後,美國國旗成為該國文化景觀中最顯著的標幟。也因此,即使《台灣新郎》並沒有刻意以它為單一主題,但系列中人偶背後出現國旗的概率仍是偏高。
近代攝影史中,以戶外人工建物,尤其是水塔為對象者,應屬於德國的貝克夫婦。透過他們特殊的影像安排,歐洲的水塔照片系列顯露了當地特有的造形觀。賓州一帶五、六層樓高的戶外水塔為數不少,造形也都未盡相同,有些甚至類似科技電影中的飛碟。特殊的水塔造形原本是一項深具地方觀光價值的地景,但它們在賓州卻只有淡藍、灰白兩色。換句話說,不讓聳立的水塔太過於醒目,也算是當地人在美學上的共識。
2.單純、知性的戶外生活形貌紀錄
《台灣新郎》所有的影像都在戶外進行的主要原因,除了在影像藝術上,意圖表現結合“觀察”與“創作”的特質之外,在操作實務經驗中個人還警覺到︰一旦人偶進到室內,那種來自生活經驗的認知馬上讓它成為飾品;這將使「新郎」又恢復本身的玩具身分,因而在環境的拍攝選擇上,特意捨室內而就戶外。
台灣新郎在賓州見証資本主義型的文化例子是︰典型中產階級最主要的全美連鎖大賣場WAL-MART,這也是以前美國民眾透過「Made in Taiwan」商標認識「台灣」的重要場合,如今聲勢已被「Made in China」所取代。WAL-MART以中低價位為主的低質商品文化,和幾近於即用即丟的中產消費氣息,甚至從停車場中的車輛都可探知一二。
美國幅員廣闊,一般家庭的修繕工資昂貴,多少促成當地人自己動手的傳統,而「工具舍」(tool shed)便是由此延伸的景觀特色。美國經濟富裕,實施週休二日甚早,加上拓荒精神,對當地人而言,擁有一塊自己的土地,在上面種植花木、鋪設草坪是相當悠久的傳統。尤其是退休、獨處的美國夫婦,花時間經營前後兩塊綠地的精神,絕不亞於伴隨的寵物。典型後院「工具舍」內所放置的物品,從割草機到中、大型的電動工具等,種類和數量之多令人嘆為觀止。對於住在地小、人口擁擠的台灣人而言,即使有一塊自己的小院子,也不會想在空地上蓋一間小房舍,專門用來堆放工具之用。因此,這對「台灣新郎」來說,也是一種難以想像的生活體驗。
庭院中除了“大人的玩具屋”之外,「遊戲屋」(play house)則是為小孩子專門設計的戶外建物;經常和周遭的鞦韆、滑梯及散落一地的玩具,形成美國家庭“後院文化”的特殊景觀。「玩具屋」的材質和大小非常地懸殊,富裕人家「遊戲屋」的精緻程度令人瞠目結舌。
資本主義的特質之一便是貧富懸殊,賓州鄉鎮中,民房的結構幾乎只有富裕與中產兩級之分。有錢人家房子的外觀,使用全石材或磚塊堆積而成,前院花草繽紛,後院樹高蔭密。反觀絕大部分中產的上班族,夫婦兩人都必須出外工作,所以小孩大都整天託付給育嬰中心。對於中產階級的夫婦而言,貸款三十年買一棟外觀由化纖材料所鋪蓋的房子,是很典型的置產方式。也因此,外車開進中產階級的社區時,類同、單調的環境規劃,不看路標猶如深入迷宮之中。類似的影像題材,早先七○年代「新地誌攝影家」討論的非常多。
「活動房屋」(trailer)基本上是一種流動性民舍,專門提供給那些沒有經濟能力購置房屋的人們。這些外表極單調的房子,夏天也許沒有冷氣,冬天卻依照法令規定得安裝暖氣。各地政府為了管理便利,都會劃定特別區域將「活動房屋」集中在trailer park。久而久之,有些人也將這種臨時性的棲身之處,變成終身財產。也因此,對這些窮困的居民而言,即使房舍的外觀非常簡陋,也會在僅有的狹小空間中,發揮個人創意,佈置最好的家園。
「美式足球」(soccer)對很多負笈美國的外國學生而言,也許是票價太高了,往往只能隔著電視螢幕,無緣親臨現場參觀。再加上,美式足球總會讓人主觀地認為是人高馬大族群的特種運動;穿戴盔甲的相互衝撞,是一種現代人假運動之名所作的獸性拼鬥。但「台灣新郎」倒觀察到看足球以外的文化。例如︰在球賽開始的前一個晚上,場外就會有遠來的球迷紮營。白天,即使是附近球迷的車子,也會在車身旁準備了餐桌椅,藉著足球賽的日子,一家人或朋友順便享受戶外陽光和家庭聚會的樂趣。尤其當開賽,年輕人入場去觀看時,年長者坐在場外享受溫和陽光的情景,穿梭在車群和戶外的餐桌間,特殊“美式足球文化”的一角發人省思。很多英國“紳士”一提到美式足球就覺得是一種次級的運動。但是,美式足球的愛好者,在儀表上卻不分年齡,大家都會把看足球賽當成蠻正式的一種戶外活動,從底鞋到上裝間都十分整潔。並且雖然陽光很大,也少見有人會如同在海邊曬太陽般的裸露上身。
3.色彩的文化性探究
《台灣新郎》多年的觀察內容甚至曾縮小到“在地色彩”議題;試探究色彩的文化性。這樣的藝術理念深受近代色彩攝影家大衛.葛文(David Graham)的影響;在亮麗的形式中顯示具有“美國色彩”的文化特質。例子可見於為數不少的城市景觀,店面外觀造形、配色等賓州一帶民間色彩美學的例証。在台北,看到「台北美國學校」黃色的校車駛過大街時,個人都會為它特殊造形留下印象。畢竟,四方方的長條形車體,無法在台灣當地找到任何設計的源流。到賓州之後,才發現這樣子的造形其實是非常“美國式”;幾乎全國中、小學都開黃色的校車。黃色校車或計程車即使如同「麥當勞」、「柯達底片」般的規格化,甚至全球性,顯露了資本主義的惡夢。但是「黃色」的過去、現在或未來都會是美國標誌性文化產物中的重要代表。也許心有所悟,所以每當經過一大片金黃色的玉米田時,自然會把兩者的關係作串連。
具有文化特質的顏色中,一種調和“豬肝紅”和咖啡色而成的「馬房紅」(barnred)也是令人注目的對象之一。「馬房紅」使用的場合,可見於一般小家具到戶外建物。許多稍具年代的木造房子,甚至將外觀全都漆成這個顏色。沉穩的「馬房紅」當然大不同於中國傳統的朱紅,也和加州一帶明亮、鮮豔的用色觀成強烈對比,至於它是否和早期拓荒的毅力、冒險精神有相關,則又是另一個顏色與文化研究的議題。
4. 普普攝影觀進入心智影像
早先「法國椅子」作品中的台灣景色是強烈的在地文化影像,一系列虛擬觀光客所造訪的角落,都不是絢麗的官方版本,而是深具台灣當代文化的深度觀察。「台灣新郎」站立地點的選擇考量上承續這個的理念,藉由人偶所站立的景觀表現出“個人、私有化的「鏡像」紀錄藝術”。換句話說,從藝術操作層面來看,一旦將人偶從照片中去除之後,《台灣新郎》系列就是個人的「鏡像」紀錄觀︰一種試圖從單純、知性的大眾生活中,表現出“普普攝影觀”精神。
因此,和「法國椅子」一般,《台灣新郎》刻意避開一般外國人對於美國的刻板印象;一些來自大眾媒體的堆砌︰舊金山大橋、紐約時代廣場、華盛頓白宮、大峽谷等,即使人不到美國腦裡都很熟悉的“明信片印象”。台灣新郎在小國百姓的卑微心理下,想探究的是一般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型態為何?難道美國少女都該長得像螢光幕上的碧眼、金髮、身材窈窕,而男生個個身材魁梧、英俊熱情嗎?於是,台灣新郎以在地的外國人身分,用心去體會與觀察這塊容身之地的異域,試圖從瞭解中為自己心中的缺口找到一個平衡點。
建構「觀念攝影」一辭
「觀念藝術」的精神不是以探究媒介和形式而區異的活動,而是藝術家藉由不同的藝術媒介質問什麼是藝術本質?其中在藝術認知方面,如果早先的藝術是讓觀眾在模糊意象中延伸無限的想像空間,那麼「觀念藝術」則是要求觀眾從科學中尋找資料,試探明確、清晰的意義。資深的藝廊策劃人安渚.柯拉(Andrea Miller-Keller)曾歸納出某些觀念藝術家在藝術的操作方面的共同興趣是:使用重複法則;使用真實時、地、比例和過程;認知本質的探索;自我描述;不完整或疏漏,和以非常極限的動作來看藝術(the very act of looking at art)。安渚的論述,尤其是“不完整或疏漏的特質”,難免引人再思,「觀念藝術」放棄形式本身完整的概念,是否只是一種刻意的藝術史策略?而以非常極限的動作來看藝術,是否只是一種標新立異的操作手法?姑且先不去過問這些議題的結果為何,深究的焦點應該放置在:觀念本身是否真的具有藝術價值?
「觀念藝術」從藝術生態觀點來看,在傳統藝廊系統外給予藝術新的意義,成了後現代藝術當中重要的指標。回顧過去三、四十年來,攝影術在「觀念藝術」中扮演質疑藝術本質的角色,形式方面從「極限藝術」的格狀脫穎而出,結合為身體、地景等「觀念藝術」的影像紀錄,其中,當代的“新觀念藝術”攝影大都不是用來對鏡頭前原有物象的特質或內涵的再修飾。相對地,照片如同語言扮演訊息的傳遞者,只是一種記號或形體的標示。然而,對「觀念藝術」中的「鏡像」角色被稱之為“影像訊息”一事,即使《時代》雜誌的藝術編輯羅伯特‧曉斯悔很不以為然,但是,當觀念藝術家愛伶納.安町(Eleanor Antin)的作品<陷落:一件傳統的雕塑>(Caving: A Traditional Scuplture,1972)是在特定期間內,每天早上拍攝自己身體前、後、左、右的四個面向,然後再猶如醫學研究般的順序展現148張照片。整組影像中,藝術家的身體非但不具專業模特兒的吸引力,胸部或臀部反而得在標題〈陷落〉指引下,才讓觀者會特別去比較。(只可惜,其結果也沒有任何明顯的差異)在此可見的事實是:愛伶納如此直接、純粹的影像形式,完全挑戰了早先「現代攝影」的美學。照片的確如同訊息般的冷漠,或純標誌性的表象。總括拍照在邁向觀念化的過程中,至少有下列幾個顯著的特質:
1.以照片來記錄「表演藝術」、「過程藝術」、「地景藝術」等;
2.成功地應用通俗、業餘影像基模於藝術創作之中;
3.另類非單一、定格式的照片呈現觀;
4.以新影像科技挑戰視網膜、大腦對影像記憶力的極限;
5.在鏡頭前虛構故事、自創劇場,讓拍照為一種影像創造與想像;
6.在「應用影像」的範疇中,藉由影像來刺探媒體紀錄能力方面的瑕疵;
7.打被傳統圖、文間的旨徵關係,藉由文字延伸影像的旨意;
8.「標誌性」影像訊息
格雷哥利‧白特考克(Gregory Battcock)認為「觀念藝術」不是一種大眾藝術,而上述諸多特殊的照片內容或形式,乍看之下都不是藝術,對大眾而言甚至是醜陋、無聊的。正也因為有這些顯著的特質,從「觀念藝術」中精化出的「觀念攝影」才得以相異於前期的「畫意攝影」、「形式主義攝影」、「超現實攝影」及「表現主義攝影」。雖然「只聽到有更多的攝影家希望能變成藝術家;卻不見得有藝術家要變成攝影家」(John Baldessan),加上攝影術和生活的緊密性有點類似工藝的範疇,但二十世紀中期之後,「觀念攝影家」卻應用了很多的拍照專業知識及美學,使單純的藝術紀錄或喬塞夫‧科舒的「攝影式觀念主義」得以再獨立為另一個藝術的專業語彙─「觀念攝影」,進而牽引其他藝術運動的動向。
◎
《台灣新郎》以編導影像手法將一座台灣製造,身著中國豔紅新郎古裝的布袋戲人偶,擺置在美國賓州各個場景前拍照,表現個人身處家人分居兩國的沉痛。照片中,人偶的造形、肢體語言皆與所擺置的大自然或人工場景成強烈對比。進層的個人象徵與文化意義在藝術表現中的角色為何?以下本節從「新郎人偶」的符號義,以及它所處的環境內涵與特質分別加以分析。
一、「新郎人偶」的符號釋義
圖象家用圖象來呈現意象,
圖象學家則研究意象所能表達的其他事物。
繪畫經由題材、形式轉變,將一個視覺系統轉換成另一個視覺系統。相照之下,「鏡像」是拍照者經由光線、鏡頭對環境的書寫;猶如留在沙上的足印般;描述著某些事物“曾在此”的遺跡。閱讀繪畫和「鏡像」中的圖象、符號有何異同?探討這個議題之前,不得不先省思「照片論述」中的符號問題。
在社會科學或傳播領域裡,論述、言說(discourse),指的是藉由具體形式,如符號系統(通常又是指語言)等,來顯示內容的方式。語言,附屬在社會架構之下,有論述事物、溝通意見、表達情感或傳播信仰等功能,以一般使用的情況來看,是傳播者和參與者呈現一種持續互動的關係。因此,論述,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是一種語言和社會、文化和傳播間的互動概念。
承續上面的認知,細思照片是否是一種語言,或「照片論述」的可行性時,就常要使人卻步難行。從嚴格的意義來看,藝術圖象中的許多事物並不屬於符號學範圍,因為,不同的圖象既要求不同的表意系統、意義配置,也要求不同的品味介入。其結果就如同羅蘭.巴特所說的,符號學之所以不能掌握藝術的關鍵在於:藝術創作並不能夠被縮減為一個系統。加上,藝術中有眾多的因素都無法被規格化、無法達到溝通標準。因此,符號學者達密便定論的說:「藝術符號學將會只是屬於對照性。」(黃斑雜誌,Macula,1978)。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佩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曾將符號分為三類:「肖似性符號」 (iconic sign),例如:圖表、雕像和語言中的擬聲字;有因果連帶關係的「指涉性符號」(indexical sign),例如: 溫度計、風向儀和密佈的濃煙;以及從符號到釋義間有完整約定俗成的「象徵性符號」(symolic sign),例如:語言符號等。來自現實環境的「鏡像」,從佩爾斯的理念來看,就如同一般圖象,是一種「肖似性符號」,但由於它又和真實的世界有因果性,所以也是一種「指涉性符號」。即使如此,「鏡像」仍難成為如同生活語言般的「象徵性符號」,只能是藉由各種視覺形式(形態、色彩、階調等)所構成的「直觀符號語言」。
“直觀式”的「鏡像」由於未曾經過社會的制約,精確與互動性不夠穩定。由此可知,所謂的「攝影語言」,實際上是專指影像創作過程中,個人審美經驗客觀化,以及景物與抽象概念符號化的結果。嚴格地說,這種專業語言比較像是,拍照家族用來詮釋個人意念的圖象工具。
因此,以此論點進層來分析「台灣新郎」的符號意涵,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
1.新郎人偶的符號意涵—來自台灣、陌生與新手
《台灣新郎》的人偶,借自我美國的岳母,是幾年前她到台灣遊歷時所帶回的飾品,在家裡擺置了好幾年。1999年,當個人面對家庭即將分離兩地的悲情時,心有所感,才將它轉化成影像創作的實體。相較於許多留美的學生,個人對美國文化的接觸經驗算是多的,但文化畢竟是一種與生俱來,或長時間生活的共識,接觸不一樣的文化並不代表就能接受其中的差異;如同了解酸黃瓜在漢堡中的作用,但不見得人人都會喜歡這樣子的組合;“超甜”的美式點心,也未必對得上台灣人的口味等等。有感於文化碰觸過程中,永遠都會有未知的世界,因此,一種如同“新人”般的心態便造就了“台灣新郎”的角色;如同作者的境遇一般,真人、假人都是來自台灣並身處異域。最後再將「新郎」釋義出“陌生”與“新手”的進層意涵。
2.新郎人偶的肢體語言—無奈、隨遇而安、自由冥想的人形風箏
台灣新郎白皙的臉面,表情冷漠,好像任何外在的環境變化它都有應對的準備。特殊的影像氛圍,不像是講求背景擬真和表演者融入的現代式舞台劇,《台灣新郎》有它獨特舞台劇的誇張精神。舞台上,人偶唯一的肢體語言就是“平舉的雙手”。對此,西方肢體語言的解讀是︰對正在發生的事物表示無奈。但是平舉的雙手和頂直下服的整體造形,更像是人形的風箏,意味著無論環境如何的不順,它(他)都可以隨風飄向另一個臆想的場域。
3.新郎人偶的面向語言—排斥與妥協
背對著主環境的人偶,肢體語言上是排斥的表徵。初期,背向環境代表個人心理的強烈抗拒;無法面對突發奇來家人分離的情勢。中期,待慢慢能夠接受家分兩地的實情之後,肢體語言軟化為一種默認與承受。近期,隨著心態上的調整與時空的自我治療,新郎逐漸地褪除畏懼,走出消沉;以平靜的心態,站立在新環境之前,嘗試多去了解、接受新的事物。《台灣新郎》系列影像,新郎人偶三個不同“背向環境”的層次,時序上也並沒有絕對的精確關係;錯綜交替的紛亂和當事者即時的心情有關。因此,台灣新郎有時雖然到此一遊,卻沒有融入當地的情境,而顯現出一種不妥協的美感。除此之外,經常站在照片中明亮處的人偶,也暗示了它面對環境的信心。
二、人偶所處的環境內涵與特質
《台灣新郎》影像核心是個人身處和家人分居兩國痛處的實體感受與反應。象徵個人「新郎人偶」背後的戶外景緻,不是一般的美國風景照片,而是是構成作者創作該系列契因的最原始場域—賓州。其中的自然與人文風貌,猶如文學故事中的背景,是影像故事的主角︰出口到美國的「新郎」演出個人心境的場所。
在地理位置上,賓州居全美中部偏東,屬於「中大西洋區」(Mid - Atlantic),面積比台灣還大。台灣人對它的了解除了早已停產的鋼鐵大城匹茲堡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任何具體的印象。賓州當然不可能代表所有美國的中產階級,但至少不會是大眾傳播中的印象再版。由於《台灣新郎》並不是報導攝影,只是在影像創作中透露出相關的文化訊息。因此,其論述的架構也不依循一般「攝影論文」(The photo-Essay)的規劃;相對地,作者以“普普文化” 的觀察,加上個人即興的感觸,作為啟動快門重要的契因。《台灣新郎》創造的過程即使如此的“藝術”,但新郎背後眾多的影像,仍有幾個顯見的方向,例如:追隨早先美國重要「紀錄攝影」大師的步影,像沃克.艾文斯等人的主題;青蔥翠綠,典型的賓州自然景觀;以及一般中產階級的生活環境、民宅、店鋪等,還有更多無法細加分類的文化景緻。以下僅就人偶所處的環境意涵與特質分述如下:
1.追隨大師步影的沉思與共舞
新郎人偶在賓州的背景與環境選擇上,某些部分是緬懷美國早先「紀錄攝影」大師的影子。意圖藉由親身體驗,再次深思這些題材的意義。例如:戶外看板,不但具有擴大告知的商業效應,和周圍環境的共存關係也是一種“地景藝術”」。而雪景中,「新郎」背景所站立的“教堂戶外看板”,雖然不如攝影大師艾文斯成功地將“美夢”廣告詞和「經濟大恐慌」的現實作強烈的諷刺,但也表現了個人對宗教的廣告與行銷概念的贊嘆。其他如滿佈英文和亮麗圖案的大看板,在光影和環境造形間,則顯示出一種賓州寧靜生活之美。
除此之外,艾文斯對傳統商店外觀的長期紀錄,也是一項頗令後人羨慕的成就。透過老照片,即使是外國人也能夠體會這些店家老闆,將最新商品的廣告傳單、貼紙等,直覺地擺置在最顯眼位置,這種滿溢著真實生活脈動之美的店面設計美學。兼具雜貨店的加油站一直是在地文化的傳統特色之一,艾文斯的老照片中,除了可以看到早期加油筒精簡的「形式主義」風格之外,後頭店面外觀滿佈標籤與廣告,也不停地向觀眾述說了一個時代的美學,閱讀這些照片讓人有尋寶般的心境。現在老照片中的舊式加油筒,如今已不再具有服務功能,但在賓州少數的觀光小鎮,仍被當地人小心地保養以做為重要地標。台灣新郎有幸經過這些地方,也在前面拍照留念,表達對普羅大眾生活觀的認同。
「露天電影院」(Drive-in)如同台灣迎神廟會的野台戲或街頭電影院。相關影像曾經出現在個私「鏡像」紀錄攝影家葛力.溫格葛蘭等人,以及「新地誌型攝影家」羅伯.亞當斯(Robert Adams)作品裏,是美國二十世紀中期通俗文化的要角之一。電影院的營運方式是︰付錢後,將自己的車子開進一個特殊的電影播放廣場,面對大螢幕,觀眾再透過車上調頻收音機,或車旁站立的喇叭來收聽影片中的音效。某些「露天電影院」在電影播放之前,還會有其他表演活動以吸引更多的觀眾。六○年代左右,「露天電影院」不但是年輕人幽會的重要場所,更是家人夏季聚集共享爆米花、冰棒的據點,帶給當今許多中、老年美國人美好的回憶。台灣新郎因此特別拜訪了在賓州僅存的少數者之一。
以美國國旗為主要封面設計的「紀錄攝影」經典作品集:《美國人》(The Americans,1956),原籍瑞士的作者羅伯.福蘭克(Robert Frank)以一個外國人旁觀的心態,在五○年代就注意到國旗普遍出現在當地日常生活的情形。事實上,溫格葛蘭六○年代的作品,也涵蓋相當分量的國旗影像,從辦公室到大街小巷、餐館等。美國在「911」大災難之後,全國上下懸掛國旗的意識高漲,即使不是節慶的日子,也可以看到一般家庭在窗戶上、車庫前、前庭院中佈置國旗,其他公共場所舉目可見的情況更不在話下。2001年九月十一日以後,美國國旗成為該國文化景觀中最顯著的標幟。也因此,即使《台灣新郎》並沒有刻意以它為單一主題,但系列中人偶背後出現國旗的概率仍是偏高。
近代攝影史中,以戶外人工建物,尤其是水塔為對象者,應屬於德國的貝克夫婦。透過他們特殊的影像安排,歐洲的水塔照片系列顯露了當地特有的造形觀。賓州一帶五、六層樓高的戶外水塔為數不少,造形也都未盡相同,有些甚至類似科技電影中的飛碟。特殊的水塔造形原本是一項深具地方觀光價值的地景,但它們在賓州卻只有淡藍、灰白兩色。換句話說,不讓聳立的水塔太過於醒目,也算是當地人在美學上的共識。
2.單純、知性的戶外生活形貌紀錄
《台灣新郎》所有的影像都在戶外進行的主要原因,除了在影像藝術上,意圖表現結合“觀察”與“創作”的特質之外,在操作實務經驗中個人還警覺到︰一旦人偶進到室內,那種來自生活經驗的認知馬上讓它成為飾品;這將使「新郎」又恢復本身的玩具身分,因而在環境的拍攝選擇上,特意捨室內而就戶外。
台灣新郎在賓州見証資本主義型的文化例子是︰典型中產階級最主要的全美連鎖大賣場WAL-MART,這也是以前美國民眾透過「Made in Taiwan」商標認識「台灣」的重要場合,如今聲勢已被「Made in China」所取代。WAL-MART以中低價位為主的低質商品文化,和幾近於即用即丟的中產消費氣息,甚至從停車場中的車輛都可探知一二。
美國幅員廣闊,一般家庭的修繕工資昂貴,多少促成當地人自己動手的傳統,而「工具舍」(tool shed)便是由此延伸的景觀特色。美國經濟富裕,實施週休二日甚早,加上拓荒精神,對當地人而言,擁有一塊自己的土地,在上面種植花木、鋪設草坪是相當悠久的傳統。尤其是退休、獨處的美國夫婦,花時間經營前後兩塊綠地的精神,絕不亞於伴隨的寵物。典型後院「工具舍」內所放置的物品,從割草機到中、大型的電動工具等,種類和數量之多令人嘆為觀止。對於住在地小、人口擁擠的台灣人而言,即使有一塊自己的小院子,也不會想在空地上蓋一間小房舍,專門用來堆放工具之用。因此,這對「台灣新郎」來說,也是一種難以想像的生活體驗。
庭院中除了“大人的玩具屋”之外,「遊戲屋」(play house)則是為小孩子專門設計的戶外建物;經常和周遭的鞦韆、滑梯及散落一地的玩具,形成美國家庭“後院文化”的特殊景觀。「玩具屋」的材質和大小非常地懸殊,富裕人家「遊戲屋」的精緻程度令人瞠目結舌。
資本主義的特質之一便是貧富懸殊,賓州鄉鎮中,民房的結構幾乎只有富裕與中產兩級之分。有錢人家房子的外觀,使用全石材或磚塊堆積而成,前院花草繽紛,後院樹高蔭密。反觀絕大部分中產的上班族,夫婦兩人都必須出外工作,所以小孩大都整天託付給育嬰中心。對於中產階級的夫婦而言,貸款三十年買一棟外觀由化纖材料所鋪蓋的房子,是很典型的置產方式。也因此,外車開進中產階級的社區時,類同、單調的環境規劃,不看路標猶如深入迷宮之中。類似的影像題材,早先七○年代「新地誌攝影家」討論的非常多。
「活動房屋」(trailer)基本上是一種流動性民舍,專門提供給那些沒有經濟能力購置房屋的人們。這些外表極單調的房子,夏天也許沒有冷氣,冬天卻依照法令規定得安裝暖氣。各地政府為了管理便利,都會劃定特別區域將「活動房屋」集中在trailer park。久而久之,有些人也將這種臨時性的棲身之處,變成終身財產。也因此,對這些窮困的居民而言,即使房舍的外觀非常簡陋,也會在僅有的狹小空間中,發揮個人創意,佈置最好的家園。
「美式足球」(soccer)對很多負笈美國的外國學生而言,也許是票價太高了,往往只能隔著電視螢幕,無緣親臨現場參觀。再加上,美式足球總會讓人主觀地認為是人高馬大族群的特種運動;穿戴盔甲的相互衝撞,是一種現代人假運動之名所作的獸性拼鬥。但「台灣新郎」倒觀察到看足球以外的文化。例如︰在球賽開始的前一個晚上,場外就會有遠來的球迷紮營。白天,即使是附近球迷的車子,也會在車身旁準備了餐桌椅,藉著足球賽的日子,一家人或朋友順便享受戶外陽光和家庭聚會的樂趣。尤其當開賽,年輕人入場去觀看時,年長者坐在場外享受溫和陽光的情景,穿梭在車群和戶外的餐桌間,特殊“美式足球文化”的一角發人省思。很多英國“紳士”一提到美式足球就覺得是一種次級的運動。但是,美式足球的愛好者,在儀表上卻不分年齡,大家都會把看足球賽當成蠻正式的一種戶外活動,從底鞋到上裝間都十分整潔。並且雖然陽光很大,也少見有人會如同在海邊曬太陽般的裸露上身。
3.色彩的文化性探究
《台灣新郎》多年的觀察內容甚至曾縮小到“在地色彩”議題;試探究色彩的文化性。這樣的藝術理念深受近代色彩攝影家大衛.葛文(David Graham)的影響;在亮麗的形式中顯示具有“美國色彩”的文化特質。例子可見於為數不少的城市景觀,店面外觀造形、配色等賓州一帶民間色彩美學的例証。在台北,看到「台北美國學校」黃色的校車駛過大街時,個人都會為它特殊造形留下印象。畢竟,四方方的長條形車體,無法在台灣當地找到任何設計的源流。到賓州之後,才發現這樣子的造形其實是非常“美國式”;幾乎全國中、小學都開黃色的校車。黃色校車或計程車即使如同「麥當勞」、「柯達底片」般的規格化,甚至全球性,顯露了資本主義的惡夢。但是「黃色」的過去、現在或未來都會是美國標誌性文化產物中的重要代表。也許心有所悟,所以每當經過一大片金黃色的玉米田時,自然會把兩者的關係作串連。
具有文化特質的顏色中,一種調和“豬肝紅”和咖啡色而成的「馬房紅」(barnred)也是令人注目的對象之一。「馬房紅」使用的場合,可見於一般小家具到戶外建物。許多稍具年代的木造房子,甚至將外觀全都漆成這個顏色。沉穩的「馬房紅」當然大不同於中國傳統的朱紅,也和加州一帶明亮、鮮豔的用色觀成強烈對比,至於它是否和早期拓荒的毅力、冒險精神有相關,則又是另一個顏色與文化研究的議題。
4. 普普攝影觀進入心智影像
早先「法國椅子」作品中的台灣景色是強烈的在地文化影像,一系列虛擬觀光客所造訪的角落,都不是絢麗的官方版本,而是深具台灣當代文化的深度觀察。「台灣新郎」站立地點的選擇考量上承續這個的理念,藉由人偶所站立的景觀表現出“個人、私有化的「鏡像」紀錄藝術”。換句話說,從藝術操作層面來看,一旦將人偶從照片中去除之後,《台灣新郎》系列就是個人的「鏡像」紀錄觀︰一種試圖從單純、知性的大眾生活中,表現出“普普攝影觀”精神。
因此,和「法國椅子」一般,《台灣新郎》刻意避開一般外國人對於美國的刻板印象;一些來自大眾媒體的堆砌︰舊金山大橋、紐約時代廣場、華盛頓白宮、大峽谷等,即使人不到美國腦裡都很熟悉的“明信片印象”。台灣新郎在小國百姓的卑微心理下,想探究的是一般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型態為何?難道美國少女都該長得像螢光幕上的碧眼、金髮、身材窈窕,而男生個個身材魁梧、英俊熱情嗎?於是,台灣新郎以在地的外國人身分,用心去體會與觀察這塊容身之地的異域,試圖從瞭解中為自己心中的缺口找到一個平衡點。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