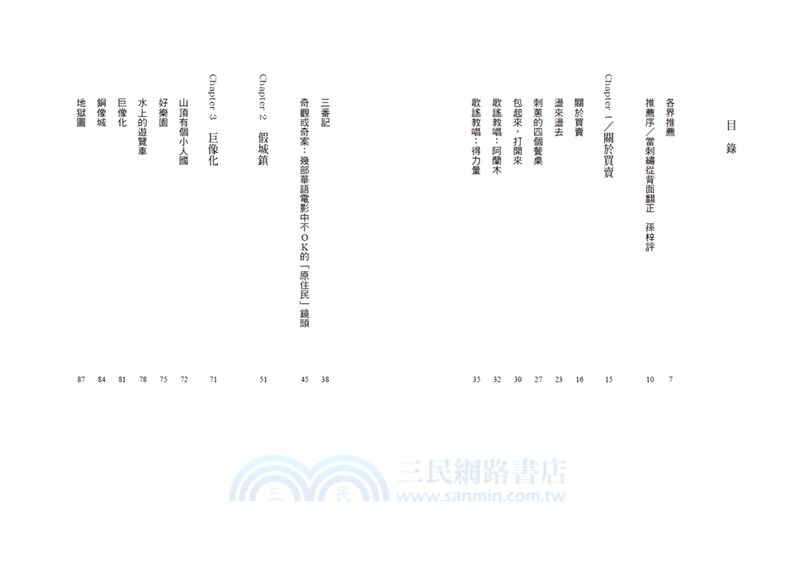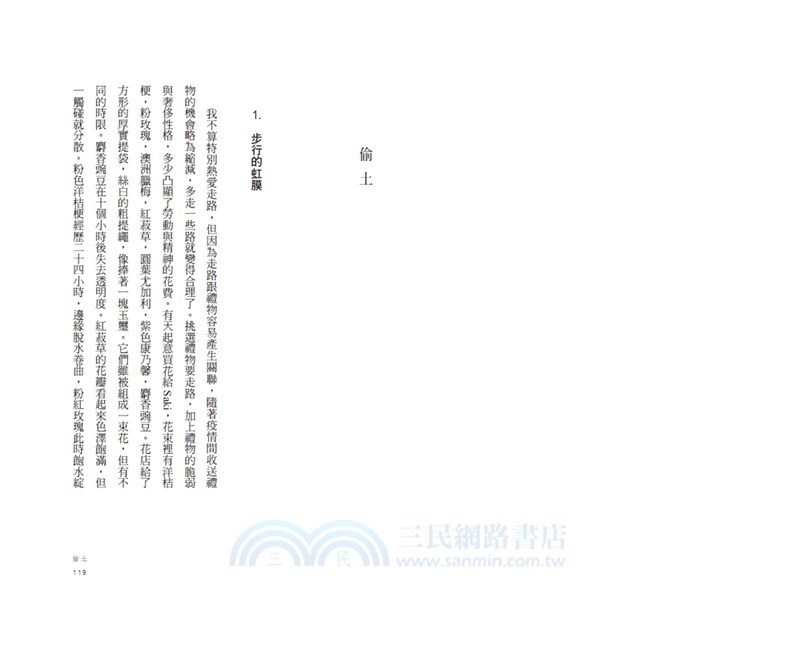假城鎮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本書榮獲2025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
「兩假相逢,必有一真。」
「夜哨間會有一次查哨,如果遇見兩次——很抱歉,其中一次可能不是活人。你也不知從何確認起。」
樓中樓、城中城、畫中畫、鬼中鬼。
B級景點專出甲種戀人,時代的眼淚還要逆再生。
虛實寶島的導覽手冊,外部落酷兒的求生之書。
英語世界中有一個詞:波坦金村莊(The Potemkin Village),意指徒具外觀,用以妝點、掩蓋的建設。典故來自俄國陸軍元帥波坦金,為了取悅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其出巡途經聶伯河的路線上,以高大華麗的繪板與假扮的村民,打造虛假的繁華村落。現代社會中這樣的波坦金村莊也存在,但各自演化出不同的用途:軍事演練、城市美化、娛樂旅遊、企業測試⋯⋯。
馬翊航從軍旅期間遭遇的「假城鎮」經驗展開思考,走筆生命中奇異、令人錯愕的場地與場景——族語內外的傳統與非傳統領域、地方吉祥物、銅像群、都市安全島、八卦山下的十八層地獄、流行金曲裡的情感空間。使向外的軍事觀測,轉為向內的心靈搜索。
本書以八個章節,來回探勘不同定義與尺度的景點/景觀、媒介記憶、身分/身體。「關於買賣」一輯記述接觸卑南語世界後的體感與心緒;「假城鎮」、「巨像化」、「寶島八景」、「棄捐」四輯穿插地理與記憶的B級景觀,物/體的雜音與破片;「偷土」在都市空間,捉摸幽微的非傳統領域;「臺灣點歌王」以流行歌曲為代幣,刮開時代的密碼。「淑女忘記了什麼」回顧參演《豔光四射歌舞團》的經歷,這部「台灣第一部變裝皇后主題劇情片」,今年適逢上映二十周年。
男同志(gay)很「假」(ké)嗎?未出櫃時的假裝是假,但同志生活中需不需要假裝?寫作是求得某種「假期」,還是為了特定目的虛飾的「假動作」?——假借同志(或更多身分),散文能否換得比真/假之論更多的東西?從《山地話/珊蒂化》至《假城鎮》,近似主題的書寫變異,也可說是從古典的電影銀幕進展至VR眼鏡的技術突破:彷彿刻意拒絕某些傷懷的誘惑,更冷調、更沉浸、更自主,卻也詭譎地異化了「在場的我」。
《假城鎮》自強不息地製造、模擬,顧盼臺灣的複雜文化景觀帶來的震顫,以「假」為重重景觀「場勘」、「導覽」、「加框」。這些「城鎮」不單是視覺體驗,也是臺語歌中的「臺北」、手機APP中的路徑、同志交友軟體上的地圖、語言與威權管理下的聲音牆——如今我們手中握有這本導覽手冊、求生之書,引人在日常政治的可疑處遊弋與演習。為了走出來。為了走進去。
孫梓評 作家 專文導讀
張小虹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假全球化》作者
張文薰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柯裕棻 作家
ZERO周美玲 電影導演
賴蔚炅《豔光四射歌舞團》服裝設計
曾啟芃 毀容姐妹會 主唱
倪瑞宏 藝術家
登曼波 藝術家
推薦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馬翊航
臺東卑南族人,池上成長,父親來自Kasavakan建和部落。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幼獅文藝》主編。著有個人詩集《細軟》、散文集《山地話/珊蒂化》,合著有《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百年降生:1900-2000台灣文學故事》等。曾獲民國八十四年台東縣原住民族歌唱比賽國中組冠軍。2004年演出周美玲導演電影《豔光四射歌舞團》,演唱電影主題曲〈流水豔光〉榮獲第四十一屆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
名人/編輯推薦
ZERO周美玲 (電影導演):
記得,當時總共有79名扮裝皇后來試鏡,而台大三名妖精果然成為電影「艷光四射歌舞團」的要角之一,包括本書作者馬翊航。
當年,當金馬獎舞台上唸出「得獎者:豔光四射歌舞團」時,她們放肆歡呼、踩著高跟鞋、用她們最妖嬌的裝扮、最不可一世的歡樂姿態,上台領取「金馬獎最佳電影歌曲」、「年度最佳台灣電影獎」時,她們直接把國人來不及反應的訝異,遠遠拋到浪花般的裙擺之後,浪漫而狂放,掀起陣陣漣漪。還記得李安導演也不禁笑嘆:只有台灣能這樣吧!我微笑回答:是啊,我好愛她們,以她們為榮。
賴蔚炅(《豔光四射歌舞團》服裝設計):
之前我本來以為馬翊航只寫詩,像是文藝美少女都擅長的那樣。
讀「假城鎮」的時候才發現是散文。
某些閱讀的片刻,我竟然在沒有意識之下融進那個青春單純、族語不夠好、思路分岔比榕樹的枝椏更細密繁雜的原住民小孩的人生,而他在未知的世界裡,知道又不知道的活著,把註解也活成了本文。
開始讀的時候本來只想著要節錄一些風景。讀完之後,訝異於他把我沒想過是什麼的那些什麼寫得異常清楚。馬翊航誠實的出租了風格別具的人生片刻。
不看不知道的那一種。
曾啟芃(毀容姐妹會 主唱):
《假城鎮》是沒有連貫文章的一本雜記,卻能死死綁在一起往下走,字裡行間儼然濃縮小時成長帶至生活連結,字裡行間跳之又跳,從流行音樂到母語的說文解字,帶來最單純自我展現。文字的意義跟論述似乎都是大人給我們的,《假城鎮》卻神奇譜出每個人心底私密的單純,從認真的族語教學,到個人迷因後才懂的惡趣味笑話,不只讓人會心一笑,甚至凸顯不需咬文嚼字加上文化搓揉的惡趣味,讀完非但會心一笑,也是釋然的笑,或許我們可能也都經歷過諸如此
類好笑、不好笑,有難過有悲傷的事情,語境不同,本質上似乎一樣吧?不過,要跟我說你沒看過《假城鎮》,別說你好笑。
倪瑞宏(藝術家):
我像搭上了假城鎮的遊園觀光列車,穿梭在台東與台北之間來回環島,路上風景時間交錯,不時有卡拉ok伴唱帶哀愁回音迴盪,瑟縮在老舊公寓角落的單人床,想起吃下整顆刺蔥水餃的滋味,有時絢麗,有時心有不甘,但還不至於在城鎮迷航,卻又覺得自己正在離地飄浮,怕被發現正掛在新店溪上頭,沒關係兩假相逢,必有一真!
目次
附件1目錄
各界推薦
推薦序/當刺繡從背面翻正 孫梓評
Chapter 1 關於買賣
關於買賣
盪來盪去
刺蔥的四個餐桌
包起來,打開來
歌謠教唱:阿蘭木
歌謠教唱:得力量
三番記
奇觀或奇案:幾部華語電影中「不OK」的原住民鏡頭
Chapter 2 假城鎮
Chapter 3 巨像化
山頂有個小人國
好樂園
水上的遊覽車
巨像化
銅像城
地獄圖
高空觀景臺:小說家電影
高空觀景臺:虛空呼喚
假定位
最早的寫生與最晚的馬戲
Chapter 4 偷土
地下層
虛擬地址
擇偶的程序
馬馬馬
身體的階段
偷土
夢遊會
Chapter 5 臺灣點歌王
Chapter 6 棄捐
爸來臺北
破片
我曾見過鍾台妹
棄捐
Chapter 7 淑女忘記了什麼
Chapter 8 寶島八景
花蓮.豐濱月洞
高雄.春秋閣
花蓮.美崙工業區
馬祖.東引
彰化.八卦山
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臺北.蘋果直營店
臺北.間隔與旋轉的裝置
書摘/試閱
〈偷土〉
①步行的虹膜
我不算特別熱愛走路,但因為走路跟禮物容易產生關聯,隨著收送禮物的機會略為縮減,多走一些路就變得合理了。挑選禮物要走路,加上禮物的脆弱與奢侈性格,多少凸顯了勞動與精神的花費。有天起意買花給Saki,花束裡有洋桔梗,粉玫瑰,澳洲臘梅,紅菽草,圓葉尤加利,紫色康乃馨,麝香豌豆。花店給了方形的厚實提袋,絲白的粗提繩,像捧著一塊玉璽。它們雖被組成一束花,但有不同的時限。麝香豌豆在十個小時後失去透明度。紅菽草的花瓣看起來色澤飽滿,但一觸碰就分散。粉色洋桔梗經歷二十四小時,邊緣脫水卷曲,粉紅玫瑰此時飽水綻開。澳洲臘梅於三十六小時之後脫落線型細葉,像剪下的指甲片。我從網路得知,若要延長切花的壽命,可在瓶水加入糖粉,甚至可將莖切處浸入滾水以收縮傷口。重要的是把虛弱的花與強壯的花分開,避免乙烯擴散沾染。一束花,此時又各自隔離在小瓶子,像沉默的天才。
Saki怕毛蟲。他能領會盆地邊緣郊山步道的可親,只是半空中常懸吊半透明的絲線,總引起他緊張地問,「是蜘蛛還是蟲?」一起走福州山步道,觀景平台遇見叔叔阿姨健行團拉起紅布條,毛楷體熱熱鬧鬧。眼前相思樹垂下小蟲,逆光成為剪影。他躲得遠遠,我拿手機拍牠含著看不見的絲,扭動像黑筆在空中謄寫S,C,U。S,C,U。近平台處,一片油綠的劍形長葉中,一朵一朵紫心白花複製貼上。是鳶尾?對,但好像又有點不像——植物辨識軟體解答,原來是巴西鳶尾。下山沿路巴西鳶尾盛開,我邊走邊Google,「巴西鳶尾花朵的壽命只有一天。」鳶尾一現,我們跟叔叔阿姨一樣幸運嗎?回家繼續查詢才知道,巴西鳶尾的花朵確實當日開謝,但花莖頂端會冒出新苗,花莖被重量壓彎,就向前著地生根,英文叫做walking iris,走路的鳶尾。
房間小水瓶裡,頑強留到最後的是紫色康乃馨。細毛在花瓣上反射,像碾碎的雲母粉。我也為它留下一張照片:白牆與深紫,無名水域裡漂浮的黑水母。
②植物認識我
因為想要讓自己植物辨識的能力再好一些,借到了一本潘富俊老師的植物辨識參考書《植物認識我》,但書名總是讓我想到舊時代的冷笑話:「你認識張惠妹嗎?」「當然啊,我認識張惠妹——她不認識我而已。」
從前安裝手機內的植物辨識軟體「形色」,辨識能力雖不差,還附上植物詩詞典故,但終究是中國開發的應用程式,有時不免出現異名、異種的混淆。後來隨著Google的拍照搜尋功能提升,臺北市郊植物大概透過相機也慢慢認識我了。臺北文學季在剝皮寮的特展五月中結束,展間主題之一,請我在內的一群寫作者選擇兩本書,並在書上做閱讀筆記,有如與觀展讀者共讀。為了想讓這兩本書之間有點小默契,我挑了陳育虹的《霞光及其他》、鍾明哲的《都會野花野草圖鑑》。但因為跨不過去「在書上寫字」的心理門檻,決定在植物圖鑑裡放上自己拍的花草相片,在相片背後寫字,再把花草照安插在屬於它的那頁。
我用手機拍下最常見的車前、紫花酢漿、莠狗尾,返家後把照片同步餵給Google與圖鑑。Google頗快地辨認出酢漿草,但車前草的穗狀花序,因為特寫的關係,Google不斷將它辨識成蚜蟲或某種淡青色尺蛾的幼蟲。另外一株極矮小野草,在矮灌木底開著菊型、小如鉛筆橡擦頭的花。Google卻比我翻遍圖鑑來得快:類雛菊飛蓬,是2009才確認的新歸化種,繁殖力非常的強。即使是最平常的植物,認得它們,似乎也不見得就是理所當然的。
從圓山站一路搭車一路拍,拍到大安森林公園站,拍到六張犁站。後來我把詩集《霞光及其他》也當成一種植物,種在我日常的路線。走路時候,意識近來日子又煩亂又委屈,這拍照兼返家的兩小時,已經是逍遙。我想起另一本詩集,《在植物與幽靈之間》,理解人造物有它們的鬆軟失調,植物有時還緊守著自己的秩序。我出門前已經懷抱任務,先把陳育虹的詩框起來了,只是還沒有框風景:「這海灣我們必定走過/岸邊的板凳這時/空著(等待著……)」快到家的最後一站,敦化南路最末段的安全島下午兩點,隔著八線道遙望平常走過的騎樓上,是連續三間診所的招牌:牙的,精神的,骨骼的。葉托,花粉,假莖。陳育虹這首叫〈英吉利灣〉的詩,在眼前的車道製造一彎巨大的弧。拍照,留步,也都得仰賴那般的認識。
③偷土
五月之後,疫情不出門的日子,我試著種種子,讓可以活的東西活起來。一起了這樣的念頭,日常的果實眾,就變得喧騰,咬牙切齒:憑什麼是它,而不是我?
第一個被挑中的是西瓜。
西瓜籽從濕紙巾與水皿之中發芽後,換我開始為其未來擔憂。土從哪裡來?我住的巷子有鳳凰木、大王椰子,它們腳下不就是土嗎?不然,敦化南路安全島上也滿滿是土,踏踏實實。我從廚房裡起出夾鏈袋與鐵湯匙,雙指鉗住夾腳拖,啪嗒啪嗒地從四樓向下走,像一位鋌而走險的母親。Saki跟在我後頭,以他一貫縝密守序的風格思考,直到二樓後對我說,土應該不能偷吧?每個人都像你這樣拿一點土,島上就沒有土了。一瞬間,我還以為他說的島是指臺灣。
缺錢的時候我會想起,哆拉A夢有個道具是集塵器,可以從世界搜刮各種事物的碎片,聚合巨大銅鑼燒,移植茂密毛髮之類。若使用在臺北市,沒有人會發現自己少了一塊錢,我則會多出兩百五十九萬七千元(的銅板)。但此刻,我心心念念的甚至不是錢,只希望可以從四方土地集合一點土,以不被察覺的量。一時之間,我沒有辦法釐清土的自然與歸屬,只好先把夾鏈袋與鐵湯匙擱回廚房。看著抽長的西瓜芽,像一群要去球場,卻少件球衣的少年。
我竟然沒想到網購。設計品網購平台上,輕鬆搜尋到以小包販售的有機土壤。德國有機黑炭土,黑色貼標,白色手寫商標字,小小一包像咖啡渣、芝麻粉。品牌主軸精神,在城市小陽台也可以進行有機栽種的理想,玫瑰萵苣、薄荷、百里香一應俱全,只是賣家註明,疫情期間不配送活的植物。我不完全確定原因,但活體與接觸,在這段期間內畢竟是敏感詞。我只好在購物車裡加上一口軍綠色的長型塑料盆,使我看起來像個負責任的家長。兩週後,盆內又陸續住進了檸檬苗,芒果苗,火龍果苗。本來應該是四種雜亂,四種因果,如今它們齊聚一盆,在有限空間裡,循線摸索未來的動態。
以買土取代偷土的念頭後,我誕生另一種理想。警戒降級,我預計回臺東短居兩個月。臨行前打包,最煩惱的是盆內水果孤兒,與其他盆栽如成熟秀雅的蝴蝶蘭,金邊吊蘭,鳳尾竹。雖然不難托付給室友們,但讓室友無端要承擔草本生死……如果不偷土,那可以在安全島上偷偷種植嗎?我記得雙子星式建築的企業大樓正對面的安全島上,住著一大叢龜背芋(不知道使用「部落」、「家庭」還是「個人」的概念來理解會比較適當),兇悍而悠閒。若在它(們)的葉影下,悄悄挖下小坑,寄託這些小苗。城市多雨,路島行人稀少,當我返回,也許它們會形成另一種邦聯。聽完我的規劃,Saki靜靜地看著我——看來我又觸及了一個敏感詞:擴散。
最後還是將植物託給室友了,我懷抱著關於土的懸念回到臺東。某日下午,約好請Cokim姑姑教學植物與相關族語詞彙。「我們在部落裡面走一走,就很多植物了。」姑姑輕鬆帶我走入隔壁的mumu家,從地縫裡的兔耳草,紫背草,山萵苣,水管邊的海金沙,牆邊的假酸漿,抬頭的食茱萸,黃荊,香椿,毛柿,我的眼睛耳朵手機淋著綠色的雨。mumu隨意指向一株火筒樹,「這個不是我種的,是鳥帶來的。」後來我們見到了一株血桐,姑姑說:「血桐叫uvuv,因為砍它會流血,族語裡面,給傷口惜惜的時候,也是uvuv、uvuv這樣。」我傻傻看著那三公尺高的血桐,就像一個高大、性成熟,且魯莽、脆弱的少年。在如此被植物與土包圍的視野裡,實在不知道如何回顧檢討,上一季我關於偷土的一番事業。
「好想要一個菜園喔。」結束下午的植物課,我反覆向Saki唸著,他可能知道我又想偷土(或者用集塵機,向鄉親們收集一平方公分的地)。手機裡有一張照片,在我和懸月之間,是那塊安全島——並非無主之地。Saki在生活裡反覆提示我,偷跟幻想都是不完備的。我思考人生下一個階段,或許要尋找更務實與自由的手法,在城市裡掛載菜園的雛形。
〈高空觀景臺:小說家電影〉
風景區投幣式望遠鏡的祕密,說穿了雖是:「願意投錢的人看得多,不願意投錢的人看得少。」但同樣十塊錢,投幣式望遠鏡可能是比魚飼料販賣機更奢侈的。投幣買「得到」的飼料,手中顆粒散發著腥腥藻氣;相較之下,望遠鏡真的看得到比較多嗎?例如臺東加路蘭海岸休憩區的投幣望遠鏡,原本肉眼可以看見一整片藍,鏡頭內只能看見一整圈藍。且此類望眼鏡,不知為何總是對焦困難,眼前風景水平地解散集合,解散集合。偶爾掃描到一艘白色小漁船,像驗光機遠方的小房子,使人疑心表象之下的動靜。
北海道函館的五稜郭公園,有座一百零七米的高塔。我與當時的旅伴刻意挑了傍晚前往,在閉館前環視市景的交接時刻:遠方纜車線消失於黃昏,白路燈將古城廓與河川的臉染成一種缺乏決心的綠。城內城外的千張屋頂一起種著黑暗,遠看公寓牆如餅薄,手指就可以扳碎。居高臨下望遠鏡的強勢,使我幾乎看見陽台的白枕套,計程車內疲累的人,販賣機紅燈:売切れ。我拿相機對著目鏡,想要它們彼此適配,強於我的雙眼。風景,風景,我要更多的風景。後來(如我所願地?)意外看得更多,當晚颱風21號暴風圈籠罩,異國的新聞畫面標題是「接近の北日本は不安な夜」。我知道五稜塔上的落地玻璃是不可能透風的,但生命的風波在眼睛的後面。以至於回想那片風景,總要伴隨著搖搖欲墜的感覺。
洪常秀電影裡,常出現變焦拉近的鏡頭,使靜止的日常突然移動,顯現新的框架。當鏡頭「離開」人物,觀者也不得不留心「他們」與四周的牽連,即使電影裡有這麼多的無端。他的第二十七部長片《小說家電影》,依然有這樣的鏡頭,但卻是加強版的:在一座配有望遠鏡的高空觀景臺上。在一場不無尷尬的偶遇之後,鏡頭像一隻可以無盡延長的手,抵達遠方黑白色的路邊秋草。原本穩定的鏡頭,也因為極端的拉近,產生細微、但無法忽略的晃動。角色們離開觀景臺,抵達其他的空間,執行他們預期與不可預期的任務,但我卻一直無法忘記那望遠又望遠的畫面。也許它明確地提醒了我:「清晰」以外的願望與無望。
〈高空觀景臺:虛空呼喚〉
幾年前購入一本名為《情緒之書》的書,乍聽好像是協助導引情緒,其實副標是「156種情緒考古學,探索人類情感的本質、歷史、演化與表現方式」。一百五十六種?不只列不出來,我甚至不確定這一百五十六種情感,是否都經歷過。其中一個條目是「虛空呼喚」,好像可以直接作為小說書名或某種寶可夢技能(這種情緒在法文中叫l'appel du vide,的確有書有歌都以此為名)。虛空呼喚指的是人在懸崖、高樓時幽幽浮現,縱身一躍的衝動。讀到這筆條目,我多想拿紅筆在標題上打勾,加上括弧。
(象鼻岩那裡,鹿野高台那裡,九樓宿舍那裡。)
「馬翊航使出了虛空呼喚——」在名古屋二百二十公尺高的Sky Promenade展望臺時候,我多想帥氣地這樣叫喊,但其實是我被虛空呼喚束縛了。要抵達四十六層觀景,得搭乘每分鐘抬升三百六十公尺的高速透明電梯,那歷程使人領悟,虛空不只從下向你呼喚,而是另一個高處。玻璃百尺外是二百四十七公尺的JR雙塔,此與彼兩點連結起來,我的幻影懸掛在名駅通之上,不在任何一個平面上。目前人類建築虛空呼喚的上限是八百二十八公尺的杜拜哈里發塔,它未來的幾位對手仍在成長中。
◆
五月第一個週末看了舞台劇《愛情生活》:有穩定對象與不錯住處的男同志狗,與屏東北上求職(或尋愛)的貓一夜情。貓成為第三者,但他允諾只需要在狗的日常中分一點小小的愛。誰都知道,愛怎麼會只是一點點的東西。貓難以得到的東西之一是旅行。北海道不行,碧潭也不行。他決心在這段委屈的感情裡面來次出走,於是去了韓國。舞台上方多功能的細長橫幅螢幕,此刻顯現自機上俯瞰的視角,與首爾塔夜景。預料外的提示之一是,從飛機向下看,可能因為超越日常尺度,與牢不可破的隔離,虛空呼喚似乎不復存在。
《愛情生活》的賣點之一,是十二場次三位演員兩個角色的攻受排列組合。我在有限的戀愛史裡曾像狗,曾像貓,也曾像狗(戲中未曾現身的)男友。蔡依林有一首歌〈第三人稱〉,以簡單的後設概念,表達了情感關係中自我敘述的功能。《愛情生活》也是這樣的,狗有時戀他正在戀的愛,狗有時敘述他不知道為何而戀的愛。我的戀魂邊看戲邊漂浮,想應該召喚哪一段關係來入座。這狀態讓人聯想到風景區人頭挖空的畫板(2003年的烏來雲仙樂園就有一片)。頭伸進去微笑、吐舌頭、手在板外比YA,拍照像斷了頭。
當機窗與夜景在戲劇裡極短暫地停留,戀愛與虛空呼喚卻同時,推了一下我的肩頭。我在我自己的上方,如果向下墜的話,也許就可以重新結合了吧。戀愛是求全的犯險,還是致災的誘惑?在那些奇異的地平線上,我幾乎什麼都沒有想充足。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