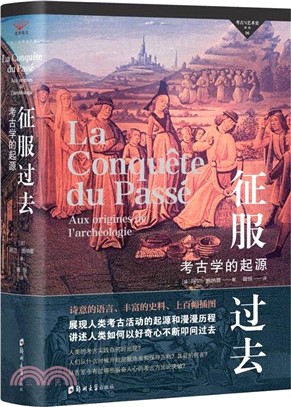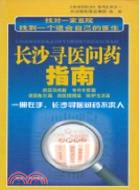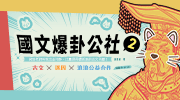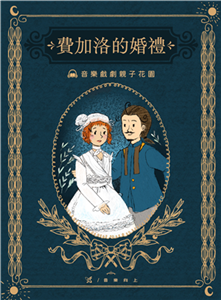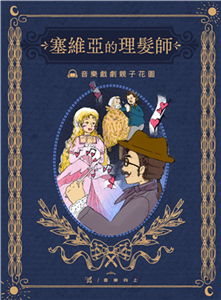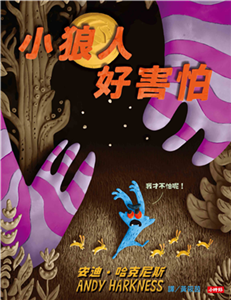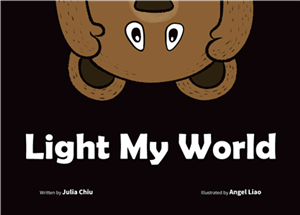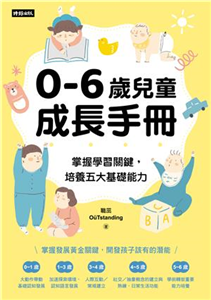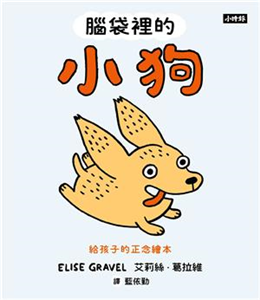商品簡介
在現代考古學於19世紀誕生之前,人類的“準”考古實踐已經源遠流長。至少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對遺跡的好奇就成為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中得到展開。若將考古理解為對遺跡的探究,那麼它並不是文藝復興時期才發明的。
本書從源頭開始,對人類探求過去的種種知識做了一次深入調查,可謂一部豐富多彩的考古學“史前史”。從巴比倫國王到中國古代的皇帝,從古埃及的祭司到美索不達米亞的書吏,從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的世界再到現代歐洲,在這漫長的時光裡,人類與過去的對話一直延伸到考古學的建立,至今仍在進行中。
作者簡介
阿蘭·施納普(Alain Schnapp),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巴黎第一大學考古學名譽教授。曾在歐洲和美國的多所大學任教,並擔任法國國家藝術史研究所(INHA)首任所長。曾參與法國考古學的改革以及法國國家預防性考古研究所(INRAP)的創立。
其研究方向為希臘城市的考古學、圖像學以及考古學的歷史。著有《征服過去:考古學的起源》、《獵人與城市:古希臘的狩獵與情色》(Le Chasseur et la cité: chasse et érotique dans la Grèce ancienne)、《世界廢墟史:從起源到啟蒙運動》(Une histoire universelle des ruines: Des origines aux Lumières)等多部作品,並發表過許多關於希臘世界的圖像學,以及拉歐斯遺址(卡拉布裡亞)、埃萊夫瑟納和伊塔諾斯遺址(克裡特島)的發掘等專業研究成果。
名人/編輯推薦
以詩意的語言、豐富的史料、上百幅插圖
展現人類考古活動的起源和漫漫歷程,
講述人類如何以好奇心不斷叩問過去。
人類的考古實踐自何時出現?
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挖掘地面和保存古物?其目的何在?
從古至今都發生過哪些振奮人心的考古方法論突破?
這部如萬花筒般精彩紛呈的書,將為你講述包含但不限於以下的故事——
·柏拉圖心目中的“考古學”是怎樣的?
·盧克萊修如何描述人類的起源?
·羅馬人為何訂立保護古建築的法令?
·人們圍繞巨石陣進行過哪些考古活動?
·熱爾貝如何發現屋大維的寶藏?
·傳說中“地裡長出的陶罐”是何物?
·“閃電石”是自然形成的嗎?
·古物學家的“珍奇屋”裡都有什麼?
·考古地層學是如何出現的?
·收藏家和考古學家的區別在哪裡?
·考古學何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序
新版前言 過去的侵蝕
這本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著作到了21世紀是否仍值得關注?這個問題只能由讀者來回答了。但我感覺,近年來那些我們認為已經翻篇了的危機和過時的習俗仍影響著考古學。柬埔寨和哥倫比亞考古遺址遭到野蠻挖掘時我們腦海中產生了不祥預感,隨著巴米揚大佛被炸毀、伊拉克和敘利亞巴爾米拉的博物館被洗劫,這預感已然成為現實。考古學旨在揭示世界的狀況,然而在社會不平等、存在戰爭風險或戰爭已經爆發的地區是無法開展考古研究的,甚至無法確保公眾能夠參觀當地的古代遺跡。當年美索不達米亞的君主們在軍事大捷後會將對手信奉的神明“囚禁”起來;亞述學家們在巴比倫的宮殿裡發現了一批雕像和碑文,都是那些來自遠方被征服國度的戰利品。萬幸的是這些東西沒被毀掉!不過我們仍要保持謹慎,被夷為平地的寺廟、被梟首的雕像、被錘爛的銘文在世界各地依然屢見不鮮,盡管世界各民族的侵略者們常常在摧毀和存放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態度之間搖擺。這兩種行為方式只不過是間歇性出現的歷史錯誤,在任何地方、任何文明中都會存在。沒有文化可以保存一切;為了生存,就必須翻新、建造、覆蓋。那些使用稻草、磚塊或木頭等短時性材料的人不會因為清理和重建而感到為難;而那些巨石建築或金字塔的建造者,則不得不忍受這些使他們不堪重負但又啟發著他們的遺跡。因此,我們無法逃避過去。無論我們試圖忘記它還是貶低它,試圖恢復它還是頌揚它,都必須對它做點什麼。過去是所發生事情的一個片段,印度人會說這是“債務”,它將現在的人與他們的先輩聯繫在一起,盡管人們並不總是知道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沒有過去的社會,就像沒有記憶的人一樣,是不存在的。當這本書出版時,保護考古遺產的共識和承諾似乎觸手可及。但不幸的是,情況又發生了變化。我們已經意識到,籠罩在遺址甚至博物館上的威脅越來越大。考古學家與人種學家一樣,面臨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峻的情況,他們的研究物件在逐漸被侵蝕,他們與自然主義者一起,意圖保護考古遺址及其環境。為此,必須制定保護遺跡的新策略。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率先在20世紀上半葉制定了能夠應對工業化和經濟擴張挑戰的考古政策。它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多地保護遺址,並強制在領土整治中對所有主要的土地利用規劃作業進行初步挖掘。這一決定得益於傳統。自17世紀以來,在丹麥和瑞典就有一個考古服務機構,它既能保護古物,又具備科學和文化能力,使發現能夠與公眾分享。“搶救性考古”的觀念,以及之後的“預防性考古”的想法,在20世紀下半葉盛行,先是在英國、德國和美國得到應用,之後影響到義大利、希臘和法國,直到1992年被歐洲理事會認定為普遍性要求。預防性考古是保護隱藏的遺跡的主要手段之一。全球化的經濟影響已經觸及迄今為止還未被工業化和集約化農業影響的地區,面對這一情況,考古學是抵抗遺址被侵蝕的唯一壁壘。遺憾的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許多國家,公共資源的不足使有效的預防性政策得不到保證。在經常遭受種族間緊張局勢和戰爭衝突的地區,文化遺產的保護受到了威脅,甚至有時會成為故意破壞的物件,就如我們在阿富汗、敘利亞和伊拉克看到的,那裡的考古遺址和博物館遭到了多次攻擊。總的來說,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現在,考古學的手段和方法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無論是勘探過程、挖掘和分析技術,還是在信息處理方面。它既屬於人文科學,也屬於自然科學,然而這些進步正受到傳統生活方式的消失和衝突的加劇的威脅,衝突帶來了人口流動和暴力的連串問題。這意味著考古學使用的倫理道德維度是其未來的基本要求,需要我們對該學科的實踐和目標進行集體反思。
古物學和考古學
這本書是對探索過去的技術的反思,是對考古學史前史的一次嘗試,它優先考慮了過去的物質證據,而並不排除書面來源。有些社會沒有文字,相反有些社會則完美地支配著文字知識,而這種掌握隨著世紀的流逝變得如此豐富,以至於我們幾乎無法相信可以存在沒有文字的歷史。然而,從最熱的沙漠地帶到最冷的冰原,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惡劣條件下的人們,也能夠傳遞故事、建造遺跡、使用可以作為記憶媒介的工具。當然,此處的記憶不是希臘人或者中國人以各自方式賦予的“歷史”,但故事是歷史的組成部分,是將過去和現在聯繫起來,建立必要的社會聯繫的方式之一。《人與物質》(L’Homme et la Matière)是我這一代許多考古學家的床頭書,書中安德烈·勒羅伊-古爾漢(André Leroi-Gourhan)討論了人類從自然界獲取所需之物的無數技術。在寫這篇文章時,我首先試圖為我的學生們回顧現代考古實踐的起源,目的是讓我們目前的知識去經受歷史批判的考驗:我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挖掘地面?從什麼時候開始保存古物?出於何種目的?這些問題又引出了關於古物(或被我們認為是古代的物品)的挖掘、保護、修復和解釋的一系列知識性問題。考古學的歷史,如此一來便成為對過去進行探索實踐的歷史。從現代考古學出發,與古物學實踐對比,這些實踐與人類意識一樣普遍。對我來說,這些實踐和考古學之間的張力顯而易見,但也很微妙。也許我的這本書需要以本來只在結論中出現的定義來開頭。現代考古學有一個出生證明,它誕生於1830年至1860年間一場積極的革命背景下,革命首次試圖破除自然歷史與人類歷史之間的障礙。在這30年之前,世上只有古物學家。他們可能會挖掘地面,巧妙地分類一些未知的物體,甚至堅決地依賴技術史,但據我所知,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將過去的科學提升為一種包含這三個方面的古物學實踐的普遍知識。這就是為什麼我相信,無論多麼博學的古物學家,與我們今天所說的考古學家之間都存在著深刻的結構性差異。英戈·赫克洛茨(Ingo Herklotz)於1999年出版的總結完全更新了我們對啟蒙時代之前的古物學家的了解,並進一步強調了他們與考古學家的區別。
現代考古學家視自己為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的同行;他們認為他們的學科毋庸置疑是普遍知識的一個分支。我們將會看到,古物學家們正是缺乏這種普遍性,即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如卡西亞諾·達爾·波佐(Cassiano dal Pozzo)、約翰·奧布裡(John Aubrey)或凱呂斯伯爵,已經嘗試過面對它。所以,我並不打算在提出關於考古學起源的研究時,把古埃及的祭司、美索不達米亞的書吏、古代中國的文人、大洋洲的吟遊詩人當作現代考古學的先驅。我試圖展示對過去的追求,可以定義為博物學,與人類的好奇心一樣普遍。有一個共同的遺產,將古物學家與考古學家拉近了,同時,也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將他們分開。考古學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柏拉圖在《大希庇阿斯》中賦予它的意義,即對過去的追求,是關於各種起源的討論,從定義上說是局部的;另一個來自現代常識,將其定義為一門探索過去物質遺跡的通用學科。這兩個術語相交,但不相混淆;我在本書中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建立這些差異。在此過程中,我引入了福柯提出的第三個意義:區分構成知識構建物質的層次。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重新發現了勒羅伊-古爾漢的觀點,他指出:人類知識可以總結為不同文化中以不同方式組織的組合,但這些都涉及對物質規律的適應。對過去的處理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否定過去,通過歌謠或神話來美化它,用“不朽”的作品來延長它,用精細的構造和重建設施來改造它,但我們無法逃脫它。你必須接受過去,為了做到這一點,人類社會有成千上萬種經營管理和協商的技巧。那麼,為什麼要審視考古學的過去,而不是試圖勾勒出它未來的輪廓呢?正是因為對未來的任何探索都需要批判性的評估和回顧性的方法,試圖理解為什麼所有社會,無論其性質如何,都需要過去。
因此,這本書並不是一部考古學的歷史,而是對其上至遙遠起源、下至19世紀上半葉被實證科學接納為一門合格的自主學科的研究。然而,在此希望避免一種目的論的方法,把收集古物、挖掘或研究建築物等早期活動視為學科的誕生。好奇心文化在史前和原始社會就已經存在。安德烈·勒羅伊-古爾漢在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阿爾西-蘇爾-居爾(Arcy-sur-Cure)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一系列化石,它們無疑是因為其奇特性而被收集起來的,構成我們觀察到的最早的收藏品。然而,在沒有文字的社會中,對過去的興趣並不局限於此,而是采取了與景觀密切聯繫的形式,其特點為伴隨著社區生活的故事和神話提供了支持。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出色地詮釋了澳大利亞中部土著阿蘭達人(Arandas)的習俗。阿蘭達人與他們的領土之間建立了深遠的歷史聯繫。這需要一種不同尋常的能力來識別出他們的起源故事中所必需的地點和遺跡。在這個社會中,有一些被稱為“楚林加”(churingas)的橢圓形木頭和石頭,被視作祖先的身體,並歸屬於一個被認為是其後裔的在世者。它們被精心維護並存放在一些天然避難所裡。阿蘭達人沒有固定的庇護所,他們沒有宗教建築,但他們有記憶的物品,這些物品使過去成為現實。因此,人類的記憶常常與物體或空間的布局有關,這賦予了它具體的形式。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巨石為我們提供了其他集體記憶的證據: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樣,建造它們所需的巨大勞動力不僅僅是為了當時。它們在空間中留下的是向子孫後代發出的信息。它們是一種意圖的證明,使它們成為真正的“紀念碑”(monumenta),其物質性來自拉丁語“monere”,意為警告和示意。
正如我們看到的,至少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對遺跡的好奇心、對見證過去的各種跡象的關注,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這種好奇心催生了古物學,在古代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已經是一種發達的智力實踐。對於為這些帝國統治者服務的文人和學者來說,對過去的了解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和宗教工具。因此,正是這些早在古希臘-羅馬之前的文明發明了一種探索時間的方法。他們復制、翻譯、解釋古代銘文,他們收集物品,他們觀察,有時甚至還挖掘地面。當這些實踐在希臘和羅馬發展起來時,一種新的、更具概念性的敘述過去的方法被發明出來了。希臘人和羅馬人沒有上述偉大帝國裡的博學的古物學家,因為他們不具有他們前輩手中那樣古老和豐富的檔案,但他們引入了一種獨立的研究,他們稱之為“歷史學”(historia)的研究方法。從那時起,歷史學家與古物學家共存,根據各自的好奇心來利用對方的信息。古物學家從痕跡、遺跡、紀念碑、習俗開始,並試圖確定它們的意義和用途;歷史學家努力重建事件以及跨越不同社會的社會經濟機制。這個議程至少從希羅多德(Hérodote)開始就已經存在,並且它仍然滲透在我們的當代知識體系中。
然而,盡管歷史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並被我們現代科學的成就所豐富,但它仍然符合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Thucydide)所賦予的那種定義。古物學和考古學之間的本質區別在於,古物學家在一個地點、一個區域或一個國家的框架內工作,而考古學家(甚至更多是史前史學家)服務於一種普遍的方法。他在特定地點和時間觀察到的東西是時間和空間機制的一部分,這種機制更普遍地參與了所謂的人類進化。概念框架的普遍性與類型學、古代技術分析和地層學的實踐相結合,這些是現代考古學定義的核心。一些古物學家已經預見到了這些做法,但他們並沒有將它們統一成一個知識體系,而這恰恰是考古學的特點。
因此,這本書是對考古學之前知識的調查。我們將看到對過去的好奇心的歷史在不同的文化中展開。在這本書中,我探索了一條漫長的道路,這條道路在19世紀考古學建立之前,引導人們與過去對話。這場對話仍在進行中。我希望寫下這個歷史,從我能發現的最古老的文獻開始,從古代東方到現代歐洲,試圖闡明對過去的“愛好者”的種種策略和行為。這項調查不能說是詳盡無遺的,但卻是可以擴展的。我仍有信心繼續探索,通過不同的文明,我認為這是一種馴服時間的方式,一種維護自己子孫後代的方式。有人在地裡藏下銘文,就像往海裡扔瓶子一樣,其他人在秘密而奇妙的房間裡收藏銘文和珍稀物品,還有人建造起土墩或金字塔:
當一些人擔心他們的墳墓時,其中有人小心翼翼地拒絕承認它們:他們哪怕虛榮心再洶涌,也不敢承認自己的墳墓。
生活在17世紀英格蘭的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在這裡給出了關於現代人與過去之間關係的最深奧的哲學思考。此外,博爾赫斯(Borges),作為比任何現代作家都更深入思考記憶侵蝕概念的人,為托馬斯·布朗於1643年出版的代表作[《醫生的信仰》(Religio Medici)]寫了一首詩:
……保護我免受自己的傷害。布朗和蒙田,
還有某個不知名的西班牙人都說過:
那麼多金子我的眼睛卻只保留了這少許,
在陰影到達它們之前。
饒恕我那急躁和痛苦,
想要被遺忘,成為大理石和塵土;
還想最後一次成為無法修復的自我。
不用劍也不用紅色長矛:
主啊,保佑我,不再抱有希望。
探索過去可能源於對知識的渴望、自我提升的激情,甚至塑造未來的欲望,它總是涉及個人的投入和關注自我的焦慮,這在某種程度上引導著人們走向虛無的感覺,以及時間消逝和世代更迭的主題。我通過發現的故事,介紹了這個歷史的一些階段。另一條道路會引導我去探索詩歌創作中與過去相遇的主題。面對布朗和博爾赫斯的斯多葛式命令,塞費裡斯(Séféris)提醒我們需要馴服古代作品:
確實,廢墟
並非雕像:殘骸,那就是你自己。
它們以一種奇特的純粹性追逐著你,
在家裡、辦公室和大型宴會上,
在對長眠的無法言說的恐懼中,
它們講述你希望未曾經歷過的事情。
阿蘭·施納普
2020年5月
目次
導 言 考古學與過去的存在 1
第一章 古代與中世紀的材料
帝國與考古學 39
希臘-羅馬世界與考古學 60
中世紀面對古代遺跡 85
第二章 古物學家們的歐洲
歷史之都——羅馬 130
遺失的高盧古代史 140
英國旅行學者和德國探索者 148
斯堪的納維亞人 168
第三章 從古物學家到考古學家
大地是一部歷史書 197
系統描述的時代 226
第四章 對人類自然歷史的否定
古代的人和世界 246
考古學的建立 261
第五章 考古學的創立
對人類上古時期的推測 309
將考古學視為一門自然科學 342
總 結 古物學家的三大矛盾 356
注 釋 366
附 錄 374
索 引 431
參考書目 450
圖 錄 473
圖片來源 485
書摘/試閱
德國探索者。尼古拉·馬夏克
挖掘本身並不是一種需要任何特殊技能或技巧的行為,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古人在某些情況下認為,可以通過挖掘回答一些文化、技術甚至歷史方面的問題。根據埃及、亞述或中國的文獻記載,除了古已有之的尋寶活動,還有探尋信息的行動,中世紀部分編年史也提到過;然而對如奧格蘭德這樣的創新者自發完成的考古行動知之甚少。根據資料可以判斷,來自圖林根的尼古拉·馬夏克(Nicolaus Marschalk,1460/1470—1525)似乎是第一位通過挖掘用人文主義文化解決歷史問題的學者。他研究了石陣與古墓之間的區別。而且他由於對拉丁文資料中關於日耳曼人的記載非常熟悉,曾試圖確定石陣的建造者是赫魯利人(Hérules),墳冢的挖掘者是奧博特人(Obetrites)。不滿足於研究遺跡的他還注意到墳墓附近發現的骨灰甕,他認為這些甕中裝的是埋在墳冢中的首領仆從的骨灰:“有些人任憑被燒死,骨灰直接裝入地上的甕中。”
與“閃電石”(燧石)、石陣和墓冢一樣,由骨灰甕構成的史前墓地也是中世紀和現代歐洲“古景觀”包含的一個要素。但在中歐平原上出現的巨大“甕場”確實讓人好奇。這些大多出於偶然的發現,在大人物的見證下有了特殊的意義。1529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訪問托爾高教堂時,人們向他介紹了新發現的甕。大家的結論是:“以前那裡肯定是一片墓地。”類似的情況還有1544年,布雷斯勞(弗羅茨瓦夫)居民喬治·烏伯(Georg Uber)在施普雷森林的呂本發現陶罐後,寫信給一位朋友:
我相信這裡曾經是一個葬禮儀式的現場。他們沒有合適的骨灰甕,就用陶罐來代替。為了表示虔誠,他們將骨灰和器具殘骸裝在這些陶器中。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接受這一觀點。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在同年出版的著作《宇宙志》中重提“地上長出陶罐”的古老神話,但當時很多人不買帳。面對一些人的質疑,薩克森的安娜(Anne de Saxe)公主下令展開調查,十年後,薩克森選帝侯(prince électeur de Saxe)對這些陶罐的發現表示祝賀:“很可能古代異教徒有焚燒逝者的習俗,所以才會有埋在那裡(甕場)的陶罐。”像閃電石一樣,這些骨灰甕(現在被認定為史前盧薩蒂亞文化之物)被認為是適合收藏在皇家珍奇屋中的奇物。這些珍貴的物品經常被美化以迎合當時的審美;法蘭克福和漢堡的博物館至今還保存著兩個罐子,配有錫制蓋子的那個源於盧薩蒂亞文化,另一個日耳曼-羅馬時期的(黑陶)帶有銀質裝飾。
陪葬的陶罐和其他器物成為16世紀中歐古物學家爭論最多的話題之一。由於王公貴族的欣賞,這些物件很快變得價值連城,人們對其趨之若鶩,當然學者們也被要求給出解釋。有些解釋是超現實的(地下矮人的“杰作”),有些解釋則是自然的[揚·德烏戈什(Jan Dlugosz)按照波蘭傳統認為是地熱造成的],當然也不乏考古學角度的解釋。但考古學的觀點雖然從15世紀末就被提出,但至少在18世紀初之前都未入主流。不過格奧爾格·阿格裡科拉(Georg Agricola)在他的名著《礦石的性質》中對此問題做出了精彩總結:
薩克森和下盧薩蒂亞的無知群眾認為這些器皿是在地下生長的,圖林根人則認為它們是曾經居住在西貝爾格山洞中的猿人使用過的器物。經過分析,這些是古代日耳曼人的骨灰甕,這些異教徒將死者的骨灰存放在甕中。
原史時期的骨灰甕讓16世紀的學者為難,不僅是因為他們的知識與群眾的信仰相悖,還由於骨灰甕顯然與常規的喪葬習俗不符。什勒斯維希公爵(duc de Schleswig)的朋友保盧斯·塞浦拉烏斯(Paulus Cypraeus)描述了1588年在修路過程中發現的一處遺跡:
[骨灰甕的數量是如此之多],只需用腳踩踏其上或將鏟子輕插入土就可以看到陶罐和骨頭的殘骸。
這些土裡面堆積的奇怪器皿與當時的習俗相去甚遠,1562年一位名叫約翰內斯·馬塞修斯(Johannes Mathesius)的路德宗牧師給出了一種有邏輯的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甕的外形多樣且各不相同,埋在地下的甕像水中的珊瑚一樣柔軟,暴露在空氣中才會變乾燥。……據說那裡曾經有一座墓,裡面有死者的骨灰,就像一個老舊的骨灰盒一樣。……這些器物到了五月才被挖出,在埋藏它們的地方隆起了一座小丘,就像大地母親的孕肚(指引找尋他們的人)。我認為它們來源於大自然而非人造,是由上帝和自然創造的。
牧師的這段奇妙文字比理性學者們的評論透露了更多信息,因為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發現的背景。收藏家們追捧這些古物並通過某種方式對其進行交易。這些古物學家實地考察時觀察到,在特定氣候條件下勘探工作會更容易,並總結出了發現古物最有效的實操方法。地下古物的“收獲期”常在5月,這可能是因為那時植物的快速生長讓人們更容易觀察到異常情況(植物密集較高或土壤顏色變化)。不是土地將古物顯露出來,而是新的觀察方法讓人們能夠更容易發現遺跡。雖然以現代考古學的觀點來看,牧師的理論十分荒謬,實則不然,他提出了一個考古學認識論的基本問題。觀察者覺察到土壤的異常——顏色變化,凸起明顯,植被覆蓋,瓦礫、碎片或燧石的出現,並根據推斷出的考古結果將它們命名為遺址、墳墓或定居地。但這些形跡是原始的(古人直接安置)還是次生的(由於土壤侵蝕或土壤移動)?是否應該將氣候因素(春季發現的罐子最多)與地表指數的變化(現代假設)或土壤內部成分的變化聯繫起來?馬塞修斯的想法雖被證明是錯的,但仍具有不小的影響。
獵奇者、王公貴族和學者一直對骨灰甕保持著濃厚的興趣,這是16世紀考古學界的主旋律。人們發現了多處遺址,最著名的是位於西裡西亞地區的馬斯洛和格裡茲切。1546年,斐迪南一世皇帝(Ferdinand I)向馬斯洛派遣調查組;1577年,魯道夫二世(Rodolphe II)在格裡茲切組織進行了研究。魯道夫對發現的骨灰甕感到高興,並令人在現場豎立一根木樁以示紀念。這種興趣當然與古物陳列室的發展和功能有關,而古物陳列室也能夠展示古物品位從古至今的變化歷程。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