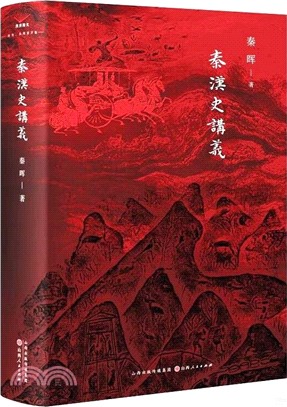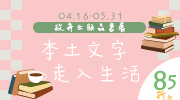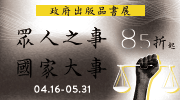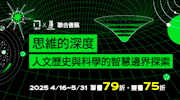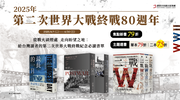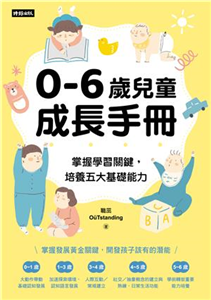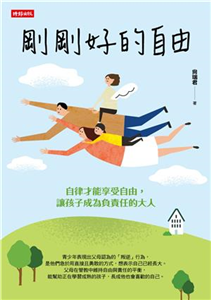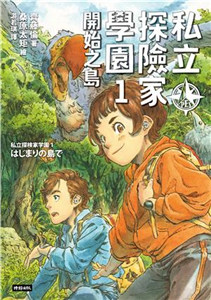商品簡介
本書以秦暉在清華大學講授“秦漢史”課程為藍本,增加了近年來不斷發現的考古資料,幾經整理修改而成。
不同於最初的課堂錄音,此次成書比錄音記錄多出近一倍內容。而且,不同於傳統的斷代史著述,本書略於政治史,而從縱(時間上的周秦、漢唐對比)橫(空間上的秦漢與羅馬帝國對比)兩個維度來探討秦漢帝國那套政治經濟制度和觀念的由來,以及它們在秦漢以後的影響,高屋建瓴,對於當下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已榮休),博士生導師。著有《南非的啟示》《共同的底線》《田園詩與狂想曲》《傳統十論》等。
名人/編輯推薦
◎為什麼說中國三千年歷史上發生的最深刻變化是“周秦之變”?“周秦之變”何以奠定了中國文明的框架?
◎秦漢帝國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怎麼形成的?包含了哪些主要內容?該制度在運作過程中產生了哪些弊病?這些問題的積累又如何導致了秦漢帝國的解體?
◎為什麼歷史上對秦漢的評價會有巨大的差異?矛盾的關鍵點在哪裡?能帶來怎樣的啟示?
◎“漢魏之變”又該如何理解?為什麼它不如“周秦之變”重要?為什麼它沒能跳出秦漢奠定的格局?
◎唐宋與秦漢相比又如何?盛唐超越了漢代的“古典商品經濟”高峰嗎?
◎為什麼漢代與古羅馬在經濟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實質含義會大相徑庭?這說明了什麼?
這本書講透了秦漢,也講透了中國歷史和精神文化中最深層的一些東西。
序
從“周秦之變”到“漢魏之變”:我的秦漢史教研
1995年我經張豈之先生介紹,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授。清華歷史學本來名氣很大,但1952年院系調整後變成蘇聯式的工科大學,這門學科在清華就中斷了。我到清華時,該系恢復創設未久,主要人員都是原社科系中國革命史和近現代史基礎課教師。所以,那時系裡搞過中國古代史教研的,基本就我一人。當時歷史系還沒有招收本科生,我除了帶過兩屆研究生外,主要是開設全校性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和農民史選修課。到了世紀初歷史系開始招收本科生,上面也要求開設“成套的”歷史系專業課,包括中國古代史的各個斷代史專業課。當時歷史系已經有了唐宋明清的教師,但仍然沒有秦漢這一“斷代”的專家,所以上面就要求我來“補缺”,開設秦漢史專業課。這樣一直到2009年侯旭東教授入職清華、我向他交棒為止,我在清華大約教授了七八年的秦漢史課程。這本講義的雛形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
在中國傳統史學的“二級學科”分類中,我是屬於“專史”而非“斷代史”出身的。研究生時期跟隨趙儷生先生治土地制度史和農民戰爭史,當時的重點也放在明清這一時段。20世紀90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農民史和農村改革問題。秦漢史本不是我的專業方向,但是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曾經多次“聽從組織安排”去從事並非我“專長”的工作,比如參加陜西通史項目承擔宋元卷和這次去教授秦漢史,這倒也並不全是出於“集體主義”或“團隊精神”的考慮。因為我本身興趣比較廣泛,而且在專史研究中也涉及過這些時段,覺得還是有一得之愚可以貢獻,或者更不客氣地說,對該“專業”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見,所以還是“義不容辭”或者說是“趣不容辭”地接受了。
我們這一代史學工作者是從所謂“五朵金花”的時代過來的。由向達先生首創的“五朵金花”之說,指1949年後中國史學界集中討論的五個問題:古史分期、土地制度、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和民族融合。這些討論具有眾所周知的意識形態背景,但即使在這個範圍內也未必一直能夠自由討論,在“文革”時期一度萬馬齊喑、“金花”凋零之後,改革初年又重新綻放,並且發展到最高潮。而隨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金花”討論就已經不再是史學研究的主流。但是如今回頭看,這種史學作為五四以後傳入的“新史學”中最有影響的一支,在其演變成經學化、神學化的“官史學”之前,曾經確實帶來了中國史學的一大進步。至少在兩個方面,它的突破和後繼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第一,它把中國歷史納入了全球化的視野,突破了傳統史學除了大中華就只有“四夷傳”的狹隘眼界。第二,它打破了單純敘述王朝興衰、鋪陳人事,而不作制度分析的模式,尤其是打破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的傳統“斷代史”格局,而把制度邏輯、社會演變作為歷史的主線。我以為,我們的思想解放,在摒棄經學化、神學化、官學化的同時,當然不應該再回到“二十四姓家譜”的模式去。如果考慮到當年“新史學”還可以出現“十批判書”這樣的作品,“官史學”就一度只能歌頌“千古一帝”,即便後來學界“告別革命”而回歸“保守”,淡化意識形態而轉趨西方“學術前沿”,還是盛行“子路頌秦王”與新瓶裝舊酒,就能夠感到一種深深的遺憾。
我早年所治的土地制度和農民戰爭史屬於典型的“金花”史學,而在這派史學無法回避的“古史分期”問題上,我當時持明確的“魏晉封建論”觀點,視秦漢為“前封建”的“古典”社會(我從不用當時流行的“奴隸社會”概念),因此發表過若干以秦漢橫向比較羅馬、縱向比較隋唐的考證著述。在調入清華前,我在陜西師範大學還開過“古代社會形態學”和“封建社會形態學”兩門選修課。即便20世紀90年代以後,“世道與心路”都已發生重大改變,我現在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金花”模式,也不再以社會形態的概念分析周秦、漢魏之別,但至少在上述兩個方面,當年新史學的影響是不會消滅的。我後來使用的“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等概念,也明顯帶有當年新史學的烙印。所以在清華開設秦漢史課時,這些學術經歷便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的秦漢史課程與一般“斷代秦漢史”有很大區別。
我假設學習秦漢史專業的學生應該具備通史階段的秦漢史知識,沒有必要花時間再講一遍這四個王朝(我認為前後漢完全是兩個王朝,中間的新朝亦非“僭逆”,加上秦應為四個朝代)的興衰概要,所以絕大部分課時都用來討論這四朝的制度和觀念演變。尤其是分析“周秦之變”和“漢魏之變”。前者要講清楚中國是何以從“三代”走進帝制的,這對此後的中國產生了怎樣的深層次影響。而後者則要說明這一由四個王朝組成的“第一帝國”如何發生了不同於一般王朝更替的深刻危機,導致秦制後來發生了不同於一般所謂“合久必分”的長時段紊亂,但周制卻復興無望,最終在經歷數百年“中間期”後又走向了秦制框架下的第二帝國。換句話說,我不想花時間給學生講一套“四姓之興亡”的故事,只想在有限時間內梳理一下中華第一帝國時期的“世道與心路”,以給今人提供進一步思考的津梁。我一向認為,中華文明數千年,最深刻的變化就是走進帝制的“周秦之變”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變”。而且對兩者的認識緊密相關。對前者認識的深淺,關係到後者的成敗;對後者的體驗亦能加深對前者的理解。而在這兩者之間次一等的變化,就是所謂的漢魏之變了。如果本書能夠促進人們對這些變化的討論,我的願望就達到了。
我在清華講授秦漢史雖然年頭不算很長,但當時“超星圖書館”做了全程視頻錄像,據說流傳甚廣,至今海內外仍有不少受眾。當時只是做了課程PPT,並沒有成書的講義。後來我不再講授這門課,也沒有想到要出版講義。但是,近年來好幾位有心的讀者卻分別根據課程錄像,整理成幾個不同版本的全文本惠寄給我,並與書界的朋友一起,極力鼓動我出版。浙江財經大學的劉志先生還花了大量時間校對引文,去除語病,劃分章節。他們的熱心和奉獻令人感動,也使我覺得出這本書不僅有它的價值,也還要對得起學生、讀者和聽眾朋友們的厚愛。
當然,從我過去寫的秦漢相關論文,到課程開設期間乃至視頻傳播中,各種評價也都存在。讚同的聲音就不說了,批評的意見林林總總,常見的就是說我的秦漢史不合常規,有“以論代史”的色彩。對此我這裡做一點響應:
過去我們的史學界有過“論從史出”還是“以論帶史”的爭論。改革時期由於對過去史學官學化的不滿,“論從史出”受到肯定,而“以論帶史”則被譏為“以論代史”。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上,那時用以“代史”的“論”其實只是一些由“信仰”支持而未經論證的理論教條,而把中國歷史削足適履地塞進教條編織的框框裡,還要不斷根據上面的需要而改變敘事(比如因“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指示而對嬴政先生從大批到大贊),這固然不是合格的“史”,但難道這能叫“論”?其實這種思維不改變,即便換了一套意識形態氛圍,比如不再講“五種社會形態”而改為追隨“國際學術前沿”的“後現代理論”,或者從“反傳統”變成“頌傳統”的“保守主義史學”,那種“教條多而論證少”的弊病也還是存在的。
我們講“史”和“論”的關係,其實就是史料和史論的關係,更一般地說其實就是論據與論證的關係。不光是史學,任何一種實證研究,即既非文藝創作也非單純的價值弘揚,而是一種以事實判斷和邏輯推斷為基礎、講究知識增量的研究,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都是論據和論證的結合。無據而論,固然是不著邊際的空言,有據無論,也會變成不知所云的廢話。有人說“史料就是史學”、“有幾分史料說幾分話”,我是不同意這些說法的。史料不等於史學,就像數據不等於數學、實驗室不等於科學家一樣。但要強調的是:論證是一種自己的合乎邏輯的思維,它不等於引述理論。我們看過去“金花”時代的某些著述,往往看起來也是旁征博引,不僅史料要“掉書袋”,理論更要“掉書袋”。一篇文章幾十個注,史料引證不多,“經典作家語錄”引證倒是不少。有人說這是“以論帶史”,有人嘲曰“以論代史”。其實這並不是“論”多了,而恰恰是“論”極其貧乏的表現。史學不是神學,也不是經學。離開經典作家,你就不會思考了?
說實話,我受“經典作家”影響也很深。但是除了某些事關知識產權的前人具論外,我是不主張理論上掉書袋的。我的論證主要是自己的思考,當然思考並非憑空,接受各種啟發非常重要。除了“經典作家”的啟發,我認為現實生活的啟發其實是不可少的。例如本書中關於商鞅“壞井田”究竟是國有化還是私有化的問題,關於“鄉舉裡選”是怎麼回事的問題,等等,我的一些新見其實都來自生活經歷。看到青川秦《田律》,就使我想起親身經歷過的“山水林田路綜合治理”。而我關於小共同體具有“溫情的等級制”的看法,除了“經典作家”的啟發,其實也來自常識。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問題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麼複雜,而是“大人物忽視常識卻迷信教條”造成的。當然常識不一定對,“證偽常識”往往是重大科學發現的突破口,哥白尼就是把“太陽東升西降,顯然圍著地球轉”的常識證偽,而開創了近代天文學。但是常識可以證偽,卻不能無視。實證研究者哥白尼和一個無視常識而高叫“太陽就是從西邊升起”的妄人,根本區別就在於此。
當然,研究歷史要靠史料,史料的書袋必須得掉。但是秦漢史在這一點上也不同於其他“斷代”,因為這一時期存世文獻較宋明以後要少得多,沒那麼多書袋可掉。這一時期的研究比近古時期更加倚重考古,但考古資料與文獻相比恰恰是“不自明”的,其意義更加有賴於論證。再就是秦漢史既然很難發現新史料,對前人研究推陳出新就更重要,而與“多一分史料多一分話”相比,對前人研究無論推陳還是出新,也更需要論證。所以秦漢史研究相對於宋元明清而言,其實就是一個論據相對有限、而更倚重論證的領域。當然,作為一個並非治“斷代史”出身的學人,我在秦漢史方面的論證對不對,還是要敬請方家賜正。
這本書在朋友們的催促和鞭策下,以劉志先生整理的《秦漢史》課程實錄視頻文稿為基礎寫成。但從課程錄制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大約近20年,期間秦漢史研究,尤其是考古資料又有了長足的進展。尤其是張家山竹簡《漢律》的發表、裡耶秦簡的發現,以及隴東秦西早秦遺址的發掘,都有重大價值,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我當年授課時這些都還沒有。我歷來主張舊作再版一般不修改,以保存寫作的“時代坐標”。但是這本書不同。一是它過去未出版過,是作為新書出版的。二是當初作為講義是面對學生,現在可能也有這方面的讀者,對學生我應該給他們以與時俱進的知識,而不是提供一個“時代斷面”而已。當年授課時,我的講義是每年都要修改的,現在出書也應該如此。所以這次成書我做了較大的修改補充,篇幅也比視頻記錄稿多了近一倍,至於成效,就期待讀者的批評了。
目次
緒 論 中國文明史上的秦漢時代
第一節 秦漢:中國第一帝國 3
第二節 秦漢史授課的重點 5
第三節 秦漢史的史料 6
第四節 秦漢時代的重要性 12
第一章
周秦之變:從族群社會到編戶齊民(上)
——小共同體本位的周制與儒家思想
第一節 對周秦之變的評價 27
第二節 周秦之變何以名之 36
第三節 周制的特徵 41
第四節 周制的經濟基礎 66
第五節 儒家與周制的價值體系 72
第六節 周制的危機 91
第二章
周秦之變:從族群社會到編戶齊民(下)
——法家的興起與“百代都行秦政制”
第一節 法家的興起及其主張 107
第二節 法家改革瓦解小共同體本位的周制 129
第三節 “百代都行秦政制”——秦制的主要特徵 150
第四節 秦制的危機 157
第三章 法道互補:“儒表法裡”之下的強權與犬儒
第一節
從“儒道互補”到“法道互補”:漢初的黃老
之術 165
第二節 儒表法裡的形成 186
第三節 “周表秦裡”:由漢武帝到王莽 217
第四章 鹽鐵論戰:帝國經濟中的“干預”與“放任”
第一節 “大夫”與“賢良文學”爭什麼? 242
第二節 鹽鐵論戰與北宋的“王馬黨爭” 252
第五章 強國弱民:秦漢帝國的政治制度
第一節 秦漢的鄉裡制 261
第二節
“五口百畝之家”與“閭裡什伍之制”:規定與
現實 274
第三節 唯上、弄權、枉法的酷吏與循吏及豪強 282
第四節 連續的歷史,循環的怪圈 298
第六章 漢魏之變:儒表法裡中的“儒裡化”階段
第一節 東漢以後宗法復興 325
第二節 以禮入法:法律的儒家化 330
第三節 官員選拔標準的道德化 338
第四節 社會組織變化:小共同體的復興 348
第五節 政治邏輯變化 358
第六節 經濟現象的變化 361
第七節 漢魏之變不如周秦之變深刻 372
第七章 秦漢經濟:中國古代第一次商品經濟高潮
第一節 集約農業的起源 405
第二節 秦漢的水利工程 414
第三節 秦漢“名田宅”制度 423
第四節 賤商制度下的“偽市場經濟” 431
第五節 千古奇文“貨殖列傳” 440
第六節 漢唐商品經濟之比較 446
第七節
漢代的古典借貸關係——兼與古希臘-羅馬的
比較 463
第八節 古典租佃制——漢代與羅馬的比較 482
余 論 505
書摘/試閱
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同樣的事實判斷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同樣的價值判斷,也可以依據好像是截然相反的事實。但是我們可以想一下這些截然不同的東西,是不是背後也有一些共同性呢?講得簡單一點,康有為說秦始皇開創了一個自由平等的時代,而譚嗣同說秦始皇開創的是一個暴力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強盜的時代。這兩者是不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呢?我們可以設想在先秦所謂封建時代,它的主要特徵就是社會上有很多主人或者說是領主、封建主,或者說是“小邦君”。每個主人都有自己的一批依附者,顯然這個主人是貴的,依附者是賤的,這個時候是有等級制的,是有尊卑之分的。而秦制的確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領主都給消滅了(至少理論上如此),把領主制變成了官僚制。
從秦始皇以後,可以這樣講,貴族和平民的差異性縮小。即使不能說完全消失,但至少是貴族下降了,以後的貴族也不是原來意義上那種貴族。所有人都成了皇帝的奴才,奴才有時甚至成了一種資格。比如像清朝,在現存清宮檔案中有大量的奏折,誰能夠對皇帝自稱“奴才”,這是要有規定的。一般的漢族大臣向皇帝上奏,只能說“臣某某”,比如林則徐,他就要說“臣林則徐啟奏皇帝陛下”,只有滿族親貴琦善、穆彰阿這些人,他們給皇帝上奏才可以說“奴才琦善啟奏皇帝陛下”,“奴才穆彰阿啟奏皇帝陛下”,敢稱“家奴”者一定是滿人而且是關係很親密的人,不是誰想當奴才都可以當上的。如果不是滿族親貴,哪怕像林則徐那樣官至正二品,即使是頗受重視,也頗有權力的人,也不配當“奴才”。能夠當奴才,那要有一定的資格。不是滿族人,要當奴才,人家還不認,你只能當臣。的確可以說,從皇帝之下皆奴才這一點講,是平等了。
秦漢以後的制度基本上就是以官僚制取代了貴族制,這一點是比較明顯的。把周代所謂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語出《左傳·昭公七年》)那樣一種貴賤分層的制度變成了一種“爾等皆為奴”這樣的制度。從這個角度講,說實現了一種“平等”,至少相對而言比以前毫無疑問是平等了。雖然彼是一個宰相,爾是一個引車賣漿者流,至少在一點上是平等的,那就是皇帝要殺你和殺他是一樣的,想殺就殺了,沒有什麼兩樣。皇帝要提拔誰也沒有人能阻攔,比如百裡奚、呂蒙正,皇上一旦看重,就可以做到“布衣卿相”。
但是這樣的一種平等,是使大家都變成貴族了,還是使大家都變成附庸了呢?答案應該是明擺著的。我覺得康有為的說法最大的問題,大概就在於這一點。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平等,是秦始皇治下那個樣子的平等嗎?是追求皇帝不管對宰相還是引車賣漿者流都想殺就殺,想賞就賞的這種平等嗎?當然不是。秦始皇所要追求的無非就是把所有的人都變成他的奴才,在這一點上是沒有貴賤之分的。秦制使人無尊卑,都隸屬於“大盜”,在這一點上講,是很“平等”的。
可以說秦制的成功也在這裡,如果沒有這樣的“平等”,它就不可能有強大的對人力、物力的動員能力,先秦時代哪一個領主能夠做到?每一個領主只能調動依附於自己很少的人,可是秦始皇就不同了。最直觀的,就是周王陵與秦始皇陵相差懸殊。周王陵規模小到難以辨認,而始皇陵僅一個兵馬俑坑就號稱“世界第八奇跡”。統一至秦亡不過十余年,長城、始皇陵、阿房宮這些重點工程一個接一個,動輒70萬人、50萬人齊上陣,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這的確是前無古人的本事。
在諸侯時代,小領主和自己的附庸往往是有直接的人際關係,是互相認識的,有直接交往的,甚至是有血緣關係的。比如河北出土的一件兵器上刻有一個家族世系,一共四代20人的名字被記錄在上面。它毫無疑問是個熟人社會,主人和自己的附庸之間是一種小共同體的依附關係。可是到了秦始皇時代就不是這樣。
西周時期,按照周制,即所謂封建制,雖然周天子不認識下面一班臣民,實際上他也管不到下面的一班臣民,下面的一班臣民有自己的領主,領主又有上一級的領主。庶人之上有士,士之上有大夫,大夫之上有諸侯,諸侯之上是周天子,是一種身份性的即固定的等級關係,下兩層的人是不可能越級與上面的人發生聯繫的。
周天子當然不可能認識庶人,但至少在理論上,他應該是認得諸侯的,因為這些諸侯,從理論上來講,都是西周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和小宗之間的關係,相當於一個大家庭內的嫡長子和其他兄弟,或者類似於父子這樣的關係。同理,諸侯一般都是認得卿大夫的,一直下來,每個人和他的主人之間都有一種比較固定的附庸關係。
可是秦始皇他怎麼能認得全國人民呢?他也沒有辦法直接管理全國幾千萬臣民。因此所謂的秦制,它和封建制真正的區別在哪裡呢?封建制是很多的主人各自管束著自己的屬下附庸,而且附庸至少在理論上是固定的,是一種長時期相對穩定的人際關係。而秦始皇有無數的附庸,他根本認不得也管不過來,因此他只能用一些他看中(提拔)的奴才去管理其他奴才。理論上講,這些人都是秦始皇的奴才,從宰相到農民,對於皇帝而言都是臣下之奴,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只不過宰相受寵,皇帝給他很大的權力。
秦制的“好處”就是通過這樣一種辦法,可以實現中央集權,可以有很強的對人力、物力的調配能力。但是,我們通常從人之常情講,受寵的奴才管理不受寵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親自管理奴才更糟糕,對奴才的憐惜和照顧的程度恐怕要更差。因為道理很簡單,就算奴才不具人格只被視為財產,而個人的奴才不管怎麼樣,“產權明晰”是你自己的,這個所有權是很清楚的。比如你有一匹馬,這一匹馬既然是你的,你總不會無緣無故把它虐待死,殺了它對你有什麼好處?你的“財產”不就損失了嗎?大家都知道“兔子不吃窩邊草”這個道理,那是因為窩邊草是它自己的,它更願意去吃別人的草。
但是受寵的奴才不太可能對不受寵的奴才產生一種“己物”愛惜照顧之心。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陌生人,沒有什麼依附關係,這些人不是他自己的人,而是皇帝的人,他本人也是皇帝的人。對於他來講,最重要的是怎麼能夠鞏固皇帝對自己的寵愛,而不是怎麼爭取更多的人依附於自己——像我們經常講的招降納叛,吸引更多的人來投奔自己——在秦制下這可是大忌,要殺頭的。
秦以前不是這樣的,秦以前每個領主都要標榜他對下面很不錯,然後才會有“良好口碑”,使很多人投奔他。所謂“毛遂自薦”“馮諼彈鋏”就是這種口碑。因為,首先他們處於熟人社會;其次,持久依附關係要考慮長期性;第三,隸屬關係邊界比較明確。如果反之,那就會造成一種現象,受寵的奴才整不受寵的奴才往往比主人整奴才還要兇狠,他們有狐假虎威之橫暴,而無損及己物之顧惜。這種現象應該說是人之常情,即使在官僚制內部也有這樣的現象。
在秦以後的歷史中,被士大夫最痛恨的是什麼人?就是宦官。為什麼宦官最遭痛恨?因為宦官是皇帝身邊的人,的確是比一般的官僚更可能得寵的奴才。皇帝與宦官接觸最多,往往很信任宦官,所以他們最得寵,或者說最容易得寵,最有機會得寵。而皇帝如果給宦官賦予很大的權力,讓他去管理他人,宦官的殘暴往往比朝官更甚。
這是因為與朝官相比,他更是名副其實的受寵奴才。取得皇帝的寵信是他唯一的目標。如果說朝官還略微顧及考慮一些別的因素,宦官因自身的條件限制除了“爭寵”沒有其他了。宦官用以前階級分析的方法可以說基本上都是出身“苦大仇深的老貧農”,絕不可能是貴族出身——哪一個貴族會願意“凈身”自宮為奴?秦始皇寵信的趙高,現在有人考證說他不是閹奴,至少沒被閹凈。但是他出身“世世卑賤”是史有明載,從無爭議的。
然而無論出身如何卑賤,宦官一旦被皇帝寵信,權傾一時,就常常會忘乎所以,做出一些糟糕透頂的事。對此,當然不能用“階級分析”說事:因為他們是窮苦出身,就會為窮人維權。宦官如此,朝官亦然,程度不同而已。“布衣卿相”絕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從常識判斷,皇權爪牙對無緣皇寵的百姓(“布衣卿相”對一般的“布衣”),比貴族對自己的附庸更無情,這不說是規律,也應是大概率現象。
我們可以說,譚嗣同講的暴力或者說是“大盜”之制,和康有為講的“平等”,用官僚制取代貴族制後的這樣一種結構,也就是說用受寵的奴才管理不受寵的奴才這樣一種制度——就是同一事物的兩面。皇權之下,大家都是奴才,“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好的說法;“朝為座上賓,暮成階下囚”,這是壞的說法。朝賤暮貴者有之,朝不保夕者有之。但是兩者都一樣,個人的命運是完全托之於皇權的,不像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包括先秦時代的那些貴族,甚至也不像我國歷史上漢族以外少數民族地區的那些世襲土司,官僚群體沒有自己的領地、屬民和其他獨立依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平等”與“大盜”,都是這麼一回事。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