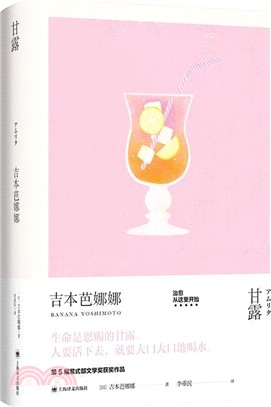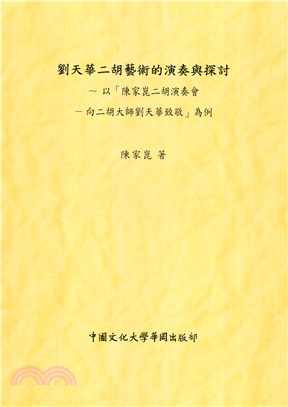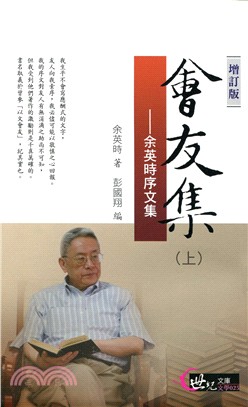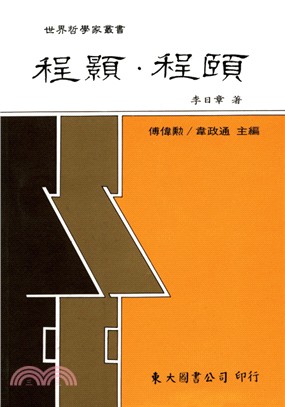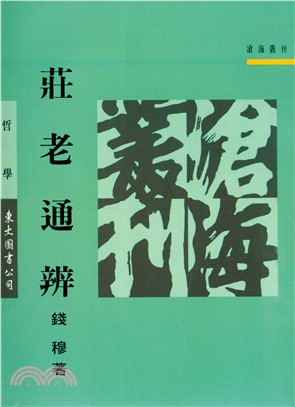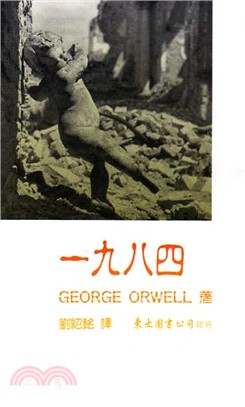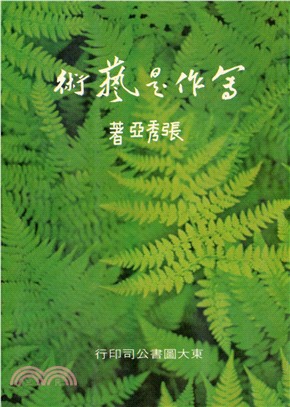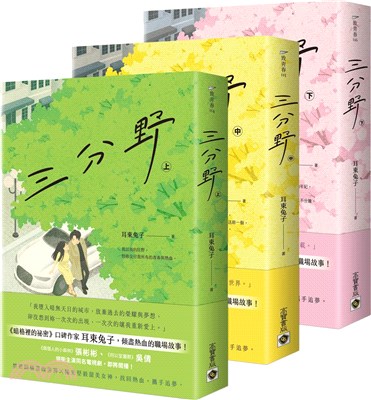商品簡介
女主角朔美的父親因腦血栓突然去世,妹妹真由在服用安眠藥後醉駕發生車禍不幸身亡。因此,她與母親、同母異父的弟弟由男、表妹幹子以及母親童年時的摯友純子組成了一個奇異的新家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某天,朔美在去打工的路上撞傷頭部,失去了一部分記憶。之後,她開始與妹妹生前的男友龍一郎交往,而對妹妹真由的懷念始終縈繞在兩個人的周圍。與此同時,弟弟由男不知何故開始逃學,母親有了新的男友,很久未見的學生時代的好友榮子突然闖入生活……雖然哀傷無可避免,但朔美漸漸發現,時光就像甘露一樣美麗。
作者簡介
吉本芭娜娜(よしもとばなな)1964年在日本東京出生,畢業於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文藝學科。1987年憑借《廚房》獲得海燕新人文學獎。主要作品還有《哀愁的預感》《甘露》《N?P》《虹》等。2000年憑借《不倫與南美》榮獲義大利多瑪格文學獎。與日本著名藝術家奈良美智合作推出《無情?厄運》《阿根廷婆婆》《雛菊人生》三部作品。在歐美和亞洲各國享有盛譽。
名人/編輯推薦
◆ 治癒,從這裡開始。
∽ ∽ ∽
◆生命是恩賜的甘露。人要活下去,就要大口大口地喝水。
∽ ∽ ∽
◆第5屆紫式部文學獎獲獎作品。吉本芭娜娜裡程碑式長篇小說。
目次
憂鬱
甘露
什麼也沒有變
單行本後記
文庫本後記
書摘/試閱
我是一個典型的夜貓子,一般總要到天快亮時才上床,而且一上午都酣暢大睡,過了中午才會醒來。
因此,那天真是例外之中的例外。說"那天",就是第一次收到龍一郎寄來的快件的那天。
我的弟弟還很小。對了,那天早晨,弟弟突然撞開我的房門,衝進來將我搖醒。
"快起來!阿朔姐,有人寄郵包來了!"
我昏昏沉沉地探起身子。
"什麼事?"我問。
"有人寄給你一個大郵包!"
他歡鬧著又蹦又跳,如果我不理他又要睡下去的話,他眼看就會跳上床來,騎在我的身上。我只好醒了醒頭腦,起床下樓去看個究竟。弟弟也纏著我一起跟下樓去。
我推開廚房的門,看見正母親坐在餐桌邊吃麵包。咖啡的馨香撲鼻而來。
"你早。"我向母親問候道。
"你早。今天怎麼起得這麼早啊?" 母親一臉驚詫地望著我。
"被阿由硬拖起來的。這孩子今天怎麼沒有去幼兒園?"
"我有些發燒啊。" 弟弟"撲通"一下跳上椅子,邊說著邊伸手取麵包。
"所以才樂得靜不下來了?" 我這才算明白弟弟為什麼如此歡快。
"你小時候也是這樣啊,看見你又蹦又跳的,心想什麼事情讓你樂成這樣,原來在發燒。"母親說道。
"其他人呢?"
"還在睡覺呢。"
"是啊。還只有九點半呢。"我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睡下時已經五點,突然被弟弟喊醒,腦袋還迷迷糊糊的。
"阿朔,你要不要也來喝一杯咖啡?"
"好吧。" 我在椅子上坐下。陽光從正面的窗戶直射進來,暖洋洋地滲透到我的體內。我已經很久沒有享受過朝陽的溫馨了。母親清晨在廚房裡忙碌著的嬌小身影,看上去仿佛是正在做新婚遊戲的高中生。
其實母親還很年輕。她在十九歲時生下我,在我這樣的年齡時已經是有著兩個孩子的母親了。我覺得真恐怖。
"呃,咖啡來了。要不要來點麵包?"
母親端著咖啡杯的手也很漂亮,怎麼也想不到那是一雙已經做了二十多年家務的手。我喜歡母親那副嬌弱的樣子,又有些發怵,總覺得她暗中在做著什麼狡猾的事情,所以才顯得比別人年輕。
長得並不風韻絕致,卻清秀而又妖艷,在年長男性面前頗有人緣的女孩子,班級裡至少總會有一個。看來母親以前就是這種類型的人。她十九歲時結婚,那時父親四十歲。在母親生下我和妹妹真由以後,父親因腦溢血猝然死去。
六年前母親第二次結婚,生下弟弟,一年前離了婚。
自從失去丈夫、妻子、孩子這一穩定的家庭形式之後,我們家成了供食宿的"旅館"。
如今住在這家裡的,除了母親、我和弟弟之外,還有吃住都在我家的表妹幹子,和因為某種原因而住在我家的純子,共五個人。純子是母親的孩提之交。
家裡有著一種奇怪的融洽,像女兒國一般相處得非常和諧,我覺得自己很喜歡這樣的形式。弟弟還年幼,簡直是個寵物,能使家裡充滿歡樂,讓大家的心聚在一起,其樂融融。
母親這次很稀罕地找了一個年齡比她小的戀人,但弟弟還太小,加上母親害怕在婚姻上重蹈舊轍,所以眼下還不打算結婚。那位戀人常常來我家玩,和弟弟十分投緣,我覺得他以後也許會和我們住在一起。這種感覺古怪的平衡,也許會持續到母親再婚的那一天。
大家生活在一起,卻毫無幹系,沒有血緣之類的關聯。
第二個父親住到我家的時候,我就有過這樣的想法。他性格內向待人隨和,所以他離開了這個家,我甚至感到落寞。那種有一個人離開家以後留下的特有的無可言狀的憂鬱和沉悶,我怎麼也不能從中擺脫出來。
因此,我開始覺得,在某位人物出現而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時,如果有一個人(在我們家是母親)能在一定的成員之間保持平衡,那麼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的人,就會不知不覺地變成一家人。
然而,還有另一種可能。
如果不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長久,即使有血緣上的關聯,那個人也會作為令人懷戀的風景之一而漸漸遠去。
就如妹妹真由那樣。
我喝著咖啡,啃著有些發硬的麵包,腦袋裡如此胡思亂想著。
我想,是餐桌與晨靄的組合,才令我對家庭想入非非起來。
"呃,阿由,你再去睡一會兒吧。不好好休息,感冒會越來越嚴重的!" 母親將弟弟往房間裡推。
"慢著!你說的快件,真的來了?"我問。
"我倒忘了。在大門邊。" 母親關上弟弟的房門,回過頭來回答。
我站起身,向大門走去。
陽光照在白木地板上,地上聳立著一個縱長的大型紙箱,像白色的雕塑一樣。
起初我還以為是花。
我試著提了提紙箱,沉甸甸的。寄件人寫著是"山崎龍一郎",寄出地址是千葉的一家旅館。是龍一郎在旅途中寄來的。
是什麼呀!我忍不住當即就麻利地打開了紙箱。
裡面沒有附信。
紙箱裡出現了一只用塑料袋裹得嚴嚴實實的維克托狗,顯得很沉。即使隔著塑料袋,看上去也令人不由感到一陣陣喜歡。
我小心翼翼地將塑料袋一層一層剝去,裡面的狗就像從大海裡浮現出來一樣躍入我的眼簾,光滑而古雅的色彩,以悵然的角度歪斜著脖子。
"哇!好可愛啊!"我驚呼道。
我把維克托狗在一堆破爛的塑料袋和紙箱中間,睡眼惺忪地站立在那裡,久久地望著它。
在晨藹和塵埃的氣息中,維克托狗如置身於雪景中一樣潔凈。
我不知道龍一郎為什麼會寄來維克托狗。但是,我仿佛真切地感受到了龍一郎在旅途中的懷念之情。可以想象,龍一郎在舊家具店的店鋪櫥窗裡一發現它便愛不釋手了。
而且,寄來維克托狗,這顯然是在訴說著什麼。
這正是我渴望聽懂的某種含義。
我像維克托狗那樣歪斜著脖子側耳細聽,卻一無所獲。
龍一郎是妹妹真由的戀人。
真由已經死去。
半年前,真由駕駛著汽車撞在電線桿上死了。她是酒後駕車,而且還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
真由天生一副如花的容貌,既不像父母,也不像我。這並不是說我們長得就特別難看,但不知為什麼,惟獨她一個人絲毫也沒有我們三人共通的說得好聽些是"酷"、說得不好聽是不懷好意的味道,孩提時簡直像天使木偶一般可愛。
她的姿色令她不可能順利地走一條普通的人生道路,她在還懵懵懂懂的時候就被人搜羅去當兒童模特兒,在電視劇裡當配角,成人以後當上了電影女演員。因為這些經歷,真由很早就離開了家,生活在演藝圈,在演藝圈裡長大。
因此,平時她工作繁忙,我們很少與她見面。她患神經衰弱症突然引退的時候,我們都大吃了一驚。因為此前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她流露出工作不順利的神情,每次見到她,她也總是快快樂樂的。
少女處在成長期的時候,演藝圈給少女造成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在引退以前,真由的打扮還很古怪,容貌、身段、化妝、服飾等女人的外形,簡直好像是凝聚著單身男人的癡心妄想。
在演藝圈裡無論混多久,很多人都不會變成那副模樣,所以我想真由也許原本就不適合幹那一行。她現炒現賣,臨時抱佛腳,不斷地掩飾自己的弱點,形成了東拼西湊的自我。神經衰弱是她生命力的吶喊。
引退以後,真由與所有的男朋友中斷了關係,突然與龍一郎同居。這時我想,真由是打算重新策劃自己的人生了。
龍一郎是作家,聽說和真由認識時還是電影劇本的改稿人。真由喜歡龍一郎寫的劇本。無論他在為誰改稿,真由都能找到他。因此,兩人的關係密切起來。
說是作家,其實他只在三年前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以後再沒有出過書。但令人稱奇的是,這一本書對某種人來說簡直是經典之作,至今還在不聲不響地暢銷著。
那部小說極度抽象,內容精致,描寫一群玩世不恭的年輕人。在見到作家本人之前,真由推薦我讀這本書。讀過以後,我覺得這樣的人很可怕,我不想與他認識。我懷疑他是一個瘋子。
但是,見面以後我才發現,他是一位極其普通的青年。而且我心裡在想,這個人能夠編織出如此精致的小說,他的大腦一定經常在進行著時間的整合和濃縮。他竟然會有那樣的才華。
真由引退後沒有固定的職業,和龍一郎住在一起,同是打打工。他們同居的時間持續得太長了,以致我和母親甚至忘了他們還沒有結婚。我經常去他們居住的公寓裡玩,他們也常常回家來玩,而且總是一副快快樂樂的樣子,說實話,我們並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陷入在酗酒、服藥的泥沼裡不可自撥。
她因為睡不著覺而喝酒、服藥,或者在陽光燦爛的下午從冰箱裡取出啤酒,我們絲毫也沒有覺察到她那樣的舉動是一種反常。但是,聽說她有這樣的習慣以後,我們才覺得她確實經常在服用那樣的東西。因為太自然了,以致我們都沒有察覺。
如今,我回想起真由幼年時那天使般的睡容,緊鎖著的長長的睫毛,潔白嬌嫩得難以呵護的皮膚,覺得她在進入演藝圈之前,在和龍一郎邂逅之前,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有了今天之所以這樣的征兆。
但是,實際上沒有人能夠知道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起因於哪裡,今後會怎麼樣。她自己還是談笑自若,惟獨心靈卻非常貧匱,正漸漸地腐蝕著。
"會不會只是服錯藥吧。" 真由被送到醫院裡時,在醫院的走廊裡,龍一郎說道。她已經沒救了。
"是啊,她還那麼年輕......"我附和著答道。
但是,我和龍一郎以及在邊上聽著我們交談的母親,其實都不相信真由會服錯藥。這是明擺著的,我們誰也不會冒冒失失地講出口來。
她真的會服錯藥嗎?
真由平時做事非常細致,出門旅遊總是將常用藥按每天服用的量分別裝在不同的小袋子裡。這樣的人難道會服錯藥?
何況,那時她已經顯得比實際年齡蒼老了許多,好像風燭殘年一般,雖然人還年輕,卻已經不可能看見未來和希望了。
不要搶救了,她自己也不會希望醫生搶救她的──
我們都是她的親人,都愛著她,然而這樣的想法卻籠罩在我們坐等著的冰冷的沙發周圍,大聲叫嚷似地撞擊著我們的內心,回響在醫院裡那清冷而蒼白的墻壁上。
很長一段時間,母親幾乎每天都哭紅眼睛,然而我卻不曾好好哭過。
我為妹妹的死只哭過一次。
那是維克托狗送來幾天後的一個夜裡,弟弟陪同表妹幹子去錄像帶店租回一盤名為"隔壁的托托洛"的錄像帶。
兩人來我的房間拉我一起看,於是我走下樓去。他們沒有絲毫的惡意,而且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錄像。我將雙腳伸進溫暖的被爐,和他們兩人一起觀看錄像。被爐上已經備好了小甜餅幹和茶水。
播放了約有五分鐘,我感到不妙。
那是一部描述一對姐妹生活的影片,極其普通的形象,卻勾起了我內心裡所有的懷念。那種懷念超越了個人的經歷,恍然大悟的感覺像波浪一樣不斷地衝擊著我的胸膛。影片原原本本地描繪出姐妹兩人在短暫的童稚年代看到的風和光,那是無比幸福的生活。
其實,那時我壓根兒就沒有想起真由。
幼年一家三人去高原玩,躲在蚊帳裡講著鬼怪故事、害怕得擠在一起睡著了,真由那褐色的纖發散發著嬰兒一般的乳香味......我絕不會在頭腦裡具體描繪出這樣的情景。但是,我沉浸在這些情景所擁有的、簡直像強力衝擊鉆一樣的懷念裡不可自撥,我的思緒偏離了錄像,感到眼前漸漸地暗淡下來。
當然,有著如此感受的,只有我一個人。
弟弟全神貫注地盯視著畫面不說話,幹子一邊寫著報告,一邊用眼角橫過來看,還不時用漫不經心的口吻攀談著。
"呃,阿朔姐,系井重裡演的那個父親的角色,很差勁啊。"
"是啊。但是,不是演得恰到好處嗎?"
"你說對了,這就是'味'啊!"
弟弟冷不防插進話來。
因此,盡管我們是三個人在一起觀看同一部電影,東拉西扯地交談著,當時卻惟獨我一人體會到一種奇異的感覺,我感到自己離開了他們,正在孤獨地朝著超現實主義的虛幻空間漸漸走去。
那種感覺在視覺上非常明晰,而不是情緒上的憂悶。我想這一定是和家人在一起觀看,而不是我獨自觀看的緣故。
錄像結束以後,我走出房間去衛生間。剛開始時的感動已經消失,我一邊打開衛生間的門,一邊極其平常地想著:"這是一部好電影啊。"
維克托狗就放在衛生間裡,我的房間裡已經沒地方放東西了,所以一樓的衛生間成了我存放東西的地方。
我坐在馬桶上,望著維克托狗的脖子那悵然地傾斜著的角度,忽然忍不住想哭。等到我回過神來,我已經在流淚。事情發生得很突然,最多不超過五分鐘。但是,我哀切地痛哭著,哭得無緣無故,哭得昏天黑地。那是一種悲痛欲絕的感覺。我幽幽地哭著。 真由平時總是喝得醉醺醺的,要不就是懶懶散散的,連喜怒哀樂都麻木了,到後來整天都塗抹著濃厚的化妝。我不是為真由哭的,而是為了這世上所有的姐妹失去的年華。
我從衛生間裡出來,回到被爐邊。
"阿朔姐,你怎麼去了這麼長時間,在拉屎吧?"弟弟問我。
"是啊,不行嗎?"我沒好氣地回答。
幹子笑了。
總算哭了個痛快,就這麼一次,從此我再也沒有哭過。
難道這就是維克托狗向我的傾訴?
在龍一郎出門去旅行之前,我只和他見過一次。
那是臨近春天的一個夜晚。
我原來一直在做辦公室小姐,但不久前與上司發生爭執被解雇了,所以暫時先在一家我常去的老酒吧裡打工,每周上班五天。
那是一個神秘而漫長的夜晚。漫長得可以分割成幾塊,整體上卻又始終有一種氛圍連貫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眼看就要上班遲到了。天已近夕,我甚至來不及打扮,在黃昏的街道上急急地朝打工的酒吧趕去。雨後的站前廣場如同黑夜的水濱一樣流光四溢。我匆匆地走著,地上反射出來的耀眼的光亮,不斷地刺激著我的眼眸。
路邊不斷有人截住過路人,拼命詢問"你認為幸福是什麼",我也被攔住了好幾次。我不耐煩地回答說"我不知道",那些人便很優雅地向後退去。
但是,因為他們的提問,有關幸福的殘影在我焦急的內心裡驟然曳出一條長長的繽紛的思緒。我仿佛覺得,幾首歌唱幸福的名曲的旋律,不斷地在我內心裡流淌著。
但是,我陷入了沉思。
在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有一個更強烈的、金碧輝煌的圖像。我仿佛覺得那才是人們真正希望得到的。那是一個比匯集著所有的希望或光芒更加令人心醉的圖像。
當車站前有人詢問何謂幸福時,那個圖像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當喝酒喝得醉薰薰時,它便陡然浮現在眼前,好像唾手可得。
難怪如此吧,我幡然醒悟。這麼說起來,真由是對幸福貪得無厭,懶惰,一事無成,虛偽,稟性受到了扭曲。
令人稱奇之處,只有一個。
能讓人忘掉一切肅然起敬的才能,就是她的笑臉。
她的笑臉已經變形,完全成為一種職業性的笑,但當她冷不防流露出天真無邪的笑容時,她的笑臉能夠打動別人的心,掩蓋她所有的缺點。
那張燦爛甜美的笑臉,在唇角上翹、眼角溫柔地搭拉下來的一瞬間,同時會猛然撥開云霧,映現出藍天和陽光。
那是一張健康而天然的笑臉,清純奪目,讓人難受得想哭。
即使肝臟全部損壞,臉色憔悴,皮膚變得極其粗糙,她的笑臉的威力也依然不會受到任何損傷。
她已經把自己的笑臉帶進了墳墓裡。
我感到後悔。在她還活著的時候,每次看到她那張笑臉時,我應該把自己內心裡的感動告訴她的。能夠說出來就好了,而不是屏息望著她。
我拼命地趕到打工的酒吧裡,卻連一個客人也沒有。柜臺裡,老闆和另一名打工的女孩正在百無聊賴地埋頭挑選著音樂。酒吧一旦沒有了音樂,簡直就像海底一樣靜寂,講話聲顯得特別刺耳。
"怎麼會這樣冷清?今天是星期五?" 我感到意外。
"因為剛下過雨吧。"老闆滿不在乎地說道。
於是,我戴起圍裙和他們一起瞎忙乎起來。我在來這裡打工之前,作為客人也很喜歡來這家酒吧。
總之,燈光黯淡,足以讓人靜得下心來。黑咕隆咚的,簡直看不見自己的手。天已傍晚,酒店裡卻好像故意不打開燈在等候著客人的光顧一樣。即使沒有客人,空閑著時也是很有情趣的。形狀各異的桌子和椅子隨意地擺放著,每一個都散發著古雅的情趣。像從前中學教室那樣散發著油漆味的木地板,以茶褐色為基調的古典式的裝潢,不小心靠上去時會發出"吱嘎"響聲的柜臺。
酒吧裡人多嘈雜的時候,和像現在這樣閑靜的時候,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非常神奇。我茫然地打量著酒店的店堂。
突然,店門"砰"地一下打開。
"嘿!" 龍一郎大步地走進店裡。我們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我怔怔地愣了老半天,才向他打著招呼: "歡迎光臨"。
"怎麼回事,你們這家酒店,有客人上門反而會感到很吃驚?" 龍一郎開著玩笑在吧臺邊坐下。
"大家都以為今天不會有人來了呢。"我回答。
"這麼寬敞的店鋪,太可惜了吧。"龍一郎環顧著店內。
"偶爾也會客滿的,而且這裡人一多,就沒有情趣了。"我笑著。
"你可以到柜臺外面來,等來了客人再進去嘛。"老闆說道。
老闆是一位不到四十歲的性情中人,他最喜歡店裡的清閑,那樣可以不停地播放自己喜歡的音樂。
我走出吧臺,把圍裙放在邊上,做出隨時都能夠捧場的模樣(結果那天夜裡再也沒有客人來過)。
總之,那天夜裡,我就是用那種懶散的感覺開始喝酒,一邊沒完沒了地聽著同一首爵士音樂。
在閑聊著時,龍一郎忽然問我:"幸福,究竟是什麼呢?"
這也是我們閑聊中的一句笑話,但我一瞬間愣住了。
"今天晚上,你也在車站廣場前被人攔下詢問了?"我問。
"我問你,它是什麼?"
"'幸福'這個詞,人們不是經常使用嗎?"我回答。
杯子裡,冰塊的冷色調透過清澈的茶水,在緩緩地融化著。
我默默著凝視著冰塊。有的時候,夜晚的氣氛很奇妙,心中的聚焦能夠與任何事物都吻合。那天夜裡就是這樣。我已經有了醉意,但心中的聚焦卻絲毫也沒有散亂的跡象。幽暗的店堂,和像腳步聲一般鏗鏘有力地從遠處傳來的鋼琴的旋律,更加快了那樣的吻合。
"我覺得你們姐妹倆使用這個詞的頻率比普通人高。"龍一郎說道,"你到我們那裡去的時候,你們兩人總是把頭湊在一起,像小鳥似地吱嘎吱嘎盡說一些與幸福有關的事情啊。"
"不虧是一個作家,講起話來也是作家的表現。"我說道。
"首先,你們家現在的組合已經像美國的電影裡那樣了,年輕的母親,加上年幼的弟弟,還有表妹?還有誰?"
"是媽媽的朋友。"
"我沒有說錯吧。看來你們考慮幸福的機會比別人多嘛。到了這樣的年齡,有一個在幼兒園裡的弟弟,真是太難得了。"
"可是家裡有一個孩子是很快樂的,大家都會變得年輕啊。盡管很煩人,但每天看著他一點點長大,是很有意思的呀!"
"他的周圍整天圍著上了年紀的女人,長大後會變成一個古怪的男人啊。"
"男孩子只要長得英俊就行,如果長得英俊,到了讀高中的時候......我嘛,要有三十多歲了?好討厭!不過,到了那時,我要穿著高跟鞋,戴著太陽眼鏡,一副充滿青春活力的樣子去與他約會,讓年輕的女孩子吃吃醋。"
"那不行。那樣的人長大後會成為奶油小生,沒有出息。"
"不管怎麼樣,總是有盼頭的。小孩子真好。小孩子本身就代表著一種可能性呀!"
"是啊!回想起來,一切都還沒有開始呢。入學儀式,初戀,情竇初開,修學旅行......"
"修學旅行?"
"你感到奇怪?我在讀高中時因為發高燒錯過了去旅行的機會,一直都耿耿於懷。"
"你不出去旅行?"我問。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問出這樣的話,只是將浮動在內心裡的話冷不防脫口說了出來。
"旅行?......是啊,隨時都可以去吧。"
龍一郎一副非常向往的神情,仿佛在玩味著一個自出生以後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甜蜜的詞語。
"現在旅行,可以不用像以前那樣勒緊腰帶了。"
"勒緊腰帶旅行,持續幾個月,身體會垮的。"
我心不在焉地點著頭。龍一郎好像忽然發現什麼,變得興致盎然。
"我因為工作關係,常常去九州、關西這些地方。比如,打工寫遊記,就是和編輯、攝影記者一起出去的。一般都是工作上的伙伴,彼此之間哼哼哈哈,敷衍一下。不過,這和一個人獨自漫無目的地出去旅行完全不一樣,一邊旅行一邊收集數據、寫筆記,這樣連續旅行幾天,頭腦就會變得非常清醒,連家也不想回了。奇怪的是,內心裡會真正地覺得,應該一直這樣走下去。既不需要承擔什麼責任,房租費之類的花費又無論從什麼地方都可以匯寄過去。要證明自己的身份,還隨身帶著護照,所以必要時甚至還能去國外。存款又不缺。在回家的飛機上或新幹線列車裡,內心裡充滿著期待,怎麼也平靜不下來,真想就這樣一直乘坐下去,如果在某個地方再換乘交通工具,就可以遠走高飛。那時我會產生一種感覺,一個全新的人生將要從這裡開始。添置必需的用品,可以在旅館的浴室裡洗衣物,稿子可以用傳真發送。如此說來,人的想象力也會變得越來越細膩,比如誰說過某個地方哪裡最棒啦,或者某座城市裡的節日是什麼時候啦......我心想,既然如此快樂,為什麼不出去旅行?一路上還不斷地責怪著自己,卻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家門口。還是想要回家吧。"
"是因為真由在家裡?"
"現在沒有了呀!"
"是啊。"
當時,我忽然感到嗒然若失,仿佛在為一個即將遠行、從此不會再見面的人開歡送會。地點是在我平時打工的酒吧裡。酒吧裡漂蕩著一抹令人魂不守舍的昏暗。
我害怕氣氛會變得沉悶或悲傷起來,於是打量著柜臺裡面,猶豫著是否要向他們求助,老闆和打工的女孩子已經在認真交談了,不太可能以調侃的口氣加入到我們的談話裡。
"提起真由,她是一個飄泊的人。"龍一郎冷不防說道。
這是這天夜裡他第一次主動提起真由。
"你說飄泊?這是什麼意思?是作家使用的形容詞嗎?" 我笑了。
"接下來我會解釋得更清楚。" 龍一郎也笑了,"我是說,這孩子離開工作以後對一切都相當冷漠,但她非常清純。她的清純就是古怪,古怪得讓人琢磨不透。這也是她的魅力所在......旅行這東西的確很神秘......不過,我不是指'人生似旅途'、'旅途中的伴侶'之類的話,和同一伙人搭檔一起旅行幾天,盡管沒有男女之別也沒有工作的拖累,也許是疲憊的緣故,人會變得自以為是吧?在回家的列車裡,大家難舍難分,興高采烈歡鬧不停,說什麼話都感到很趣,眉飛色舞,快樂得忘乎所以,以為這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 就著那樣的興頭,即使回到家裡,旅伴的形象也會像殘片一樣伴隨在自己的身邊,第二天早晨獨自醒來時,還迷迷糊糊地想:怎麼了?那些人到哪裡去了?在晨曦下悵然若失。不過,成熟的人就會將它當作過眼流云,只是刻骨銘心地記著它的美麗。難道不是嗎?真由就不同。她有時很幼稚,那樣的感覺哪怕只經歷過一次,就認定自己有責任將它保持下去。而且她認為在所有的好感之中,惟獨那樣的感覺才是真正的戀情。我沒有固定的職業,她為我操心,以致把很多心思都放在與外界打交道上,她認為這就是戀愛。是不是結婚,或者兩人今後打算做些什麼,這些與將來有關的盤算,從來就沒有提起過。對她來說沒有將來,只有旅行。這反而讓人感到可怕......她的生活模式好像是長生不老的,連我自己都覺得好像已經卷進她的生活模式裡了。"
"那是因為真由當過電影女演員呀。"我說道。
關於這一類事情,在真由死去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得很多了。
"導演、攝制人員、演員,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期,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大家天天都相處在一起吧?不分晝夜地工作,累得筋疲力盡,大家聚在一起,比家人、戀人的關係更深沉更親密。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時間上,都是那樣的。 不過,那種聚合是為了拍攝一個電影劇本,拍攝完畢,大家各奔東西,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裡。最後存在記憶裡的,只是那段日子裡的殘片和映像。只有在試片的時候,面對著那一個個場景的時候,才會追憶起那些共同度過的日子。但是,那段時光決不會再有第二次。想必那是人生的縮影吧,如果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就不會有那樣的多愁善感。真由不會是因為喝酒或吃藥才中毒的,是那種悲歡離合帶給她的強烈感受才使她不能自拔的。"
"是嗎?你們這對姐妹對中毒很有研究啊。"龍一郎笑了。
"我可不一樣。"我連忙說道,"我還沒有相信到要尋死的地步。"
"真的嗎?看起來真是如此。你們兩人的類型相差得很遠啊。"他說道。
但是,我卻陷入了沉思。
我真的能斷言自己與真由不一樣嗎?
我真的不是那種將松糕蘸著紅茶吃、自以為沉浸在無比的幸福裡不能自拔的人嗎?
我真的沒有把眼前的生活當作是一種短途旅行,沒有把那些住在一起的人當作萍水相逢的短途旅伴嗎?
不過,我不很清楚。我覺得想要弄清楚是危險的。我害怕。
如果弄得太清楚,我和別人也許都會變成真由。
到凌晨二點,酒吧關門,我們打掃完以後離開了酒吧。
雨已經完全停了,星星在天空中閃爍,那是一個寒意料峭的夜晚,天空中微微地飄蕩著春天的氣息。溫馨的夜風透過大衣纖薄的布料,包容著我的身體。
辛苦了──
大家相互打著招呼分手以後,只剩下龍一郎和我兩個人。
我問他:"坐出租車回去?"
"只能這樣了吧。"
"那麼,你帶我一段吧。"
"行啊,是順道......對了,你們哪裡有沒有我的書?"
"什麼書?"
"我昨天就在尋找了,但沒有找到。我突然想讀那本書,去附近的書店裡找過,但沒有買到。我記得一定是混在真由的書裡送到你們那裡去了,書的標題是《警察說:半夜飄泊的眼淚》,是菲力浦K?笛克寫的。是文庫本,所以有沒有也無關緊要。不過,如果在你們那裡的話,我能不能現在就去取一趟?"
"......你能把故事情節告訴我嗎?"我吃驚地問。
黑夜,街道化作一個剪影沉寂在黑暗裡,出租車宛如一條光的河流描繪著弧形飛馳而去。晦冥之中沉澱著季節變化時特有的清新,吸入肺腑的空氣裡滿溢著夢境一般的芳香。
出乎我的意料,龍一郎的回答很乾脆: "我已經記不得了,那本書很早以前讀過,記憶中和他的其他作品混在一起了。你知道情節嗎?"
"我不知道啊。"我說道。
他說了聲"是啊",攔住一輛出租車。
家裡一片漆黑。我帶著龍一郎躡手躡腳地登上樓梯,徑直去我的房間。
真由的書暫時全都放在我這裡,還沒有經過整理。文庫本都集中在床邊上,壘成四堆,幾乎都有書套。
"你等一下,我要把它徹底地翻一遍。"
"需要我幫忙吧。"
"不用了,你在那邊坐著。"
我轉過身去,把背對著龍一郎,面對著堆積如山的書。
"可以聽聽什麼音樂嗎?"
"行啊,CD片和磁帶都堆在那裡,你自己挑選吧。"
"OK。"
他在我的身後大模大樣地開始挑選音樂。我靜下心來,開始一本本翻開書套尋找著。
其實我讀過那本書,它的故事情節我還記得很清楚,但我也不想說。
那本書裡說一位警察有個長得很漂亮的妹妹,因為藥物中毒而服用了不明來歷的藥品,結果出了事故,死得很悲慘。書中的人物形象與真由一模一樣。
他如果不是故意佯裝不知(我知道他不是這樣),那一定是想哭。
我心裡思忖著。
他是想哭卻哭不出來,於是在下意識地尋找和挑選著能夠痛哭一場的機會。
多麼心酸啊。
因為那本書的內容十分露骨,我心裡很不舒服,尋思著是不是該把那本書找出來給他。我正這樣煩惱著的時候,身後的擴音器裡突然傳出喧鬧聲。
合著琴弦的聲響,人們的嘈雜聲,跑了調的背景音樂,玻璃杯的碰撞聲。
"這是什麼?" 我一邊找書,一邊大聲問他。
他漫不經心地讀著錄音帶盒上的標題。
"嗯......上面只是寫著'88年4月,公共馬車樂隊'呀。是現場錄音吧?那次我很想去,結果有事沒去成,那次演奏會以後不久,這支樂隊就解散了。我很喜歡這支樂隊,它叫......"
他東拉西扯地說著,但我這時陡然沉浸到一個感慨裡,已經聽不見他的說話聲。
??讚同,或者是領會了──
這時候,磁帶仍在不停地轉動著,我內心裡慌亂的聲音將我胸膛裡的疑問不斷地膨脹起來。為什麼?怎麼會找到的?家裡有這樣的磁帶,連我自己都已經忘得一幹二凈。
我不知道該如何表現接下來在我內心裡產生的巨大波瀾。千思萬縷,我不知道該怎樣選擇,頭腦裡出現了瞬間的空白。在我眾多的磁帶中,這樣的磁帶碰巧只有一盤。
不行!如果現在馬上停止播放,還能夠掩飾過去......
無論是尋找那本書也好,還是從那麼多的磁帶中特地選中這一盤也好,如果能讓他發泄潛伏在內心深處的感慨的話,也許真的應該讓他聽聽......
躊躇,像閃電一樣咀嚼著我的內心。
我心亂如麻,既充滿著溫情,又想耍弄他一下。內心裡更幽深的溫情和挑逗,通俗劇和紀錄片,各種事物糾合在一起,難以取舍,令我感到茫然,無處適從。感情是浪漫的情愫,使我的思緒朝著讓他聽聽的方向傾斜。
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決斷,就好像在天上俯視著一對情侶將要結束生命的聖母馬利亞一樣。
那盤磁帶開始播放沒多久,在嘈雜聲中突然冒出一個熟悉的聲音。
"姐姐,這東西怎麼弄才能錄音啊?這樣可以嗎?"
是真由的聲音。
那天真由突然喊我出去,說龍一郎原本應該來的,但他有事沒有來,要向我借錄音機。我沒有辦法,只好跟著她去演出現場。兩年前真由還很活躍,至少她還希望把自己喜歡的音樂錄下來。而且,那是惟一一盤錄入真由的聲音的磁帶。
開演前那一刻,真由這樣和我嘮著話。場子裡的照明黯淡下來,燈光將舞臺照得通亮。人們低聲說著話,一邊等著開演。
接著,是我的聲音。
"可以了,錄音的紅燈不是亮了嗎?讓它亮著。"
"亮著呢,多虧你啊。"真由說道。
令人懷念的聲音,高亢而清脆,余音繚繞,頗為珍貴。
"姐姐,磁帶真的在轉?"
"沒關係,你不要再去碰它了呀。"
"我不放心呢。"
真由低下頭望著磁帶微微一笑。她的面容在昏暗中已經成為一個剪影,但我知道她那笑臉正因為是微笑,所以變得特別燦爛。
"你這麼容易擔心,是母親遺傳給你的吧。"我說道。
真由依然低伏著臉。
"媽媽最近身體怎麼樣?"她問。
突然響起一陣劇烈的掌聲和歡呼聲。
"哇!要開始了!"
當時,真由抬著頭如癡如醉地望著舞臺,顯得非常寧靜。
她的抬頭角度比以前出演任何一部電影時都動人。
只有她的臉在黑暗中浮現出來,就像沐浴著陽光的月亮一樣,泛著蒼白的光芒,她的瞳子像在夢境中似地瞪得溜圓,兩邊的鬢發披著銀光,尖尖的小耳朵豎起著,充滿著期盼,好像想要聽清所有的聲音......
不久,音樂響起,我猛然回過神來。
龍一郎說道:"竟然能聽到她的聲音。"
我回過頭去,他沒有哭,只是瞇著眼睛溫情地苦笑。
"我不知道啊!"
那天夜裡,這是我說的第二次謊話。於是,心中的緊張情緒霍然化解,時間的流逝回到了老地方。我又轉過身去,開始找書。
那天夜裡,他獨自一人的時候,會不會痛哭呢?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