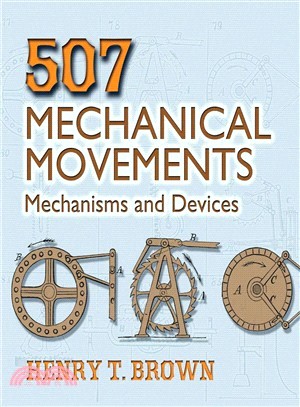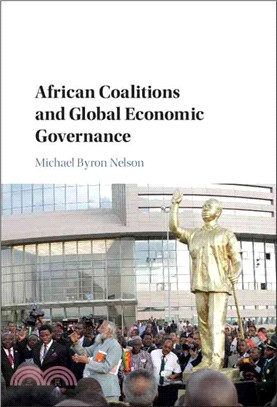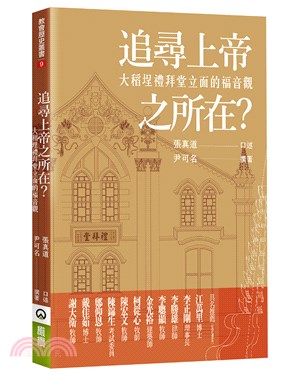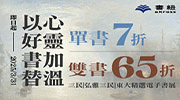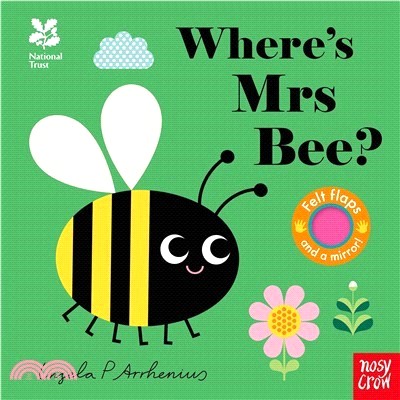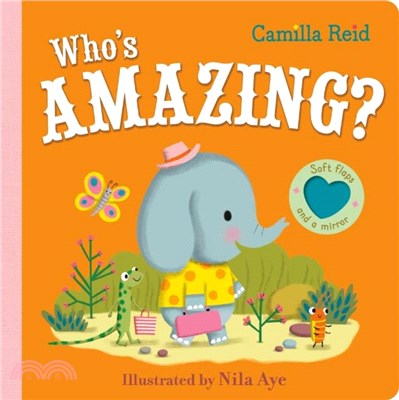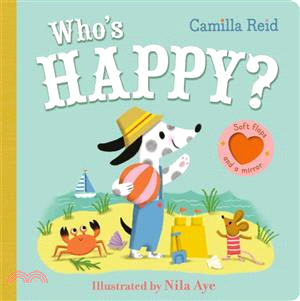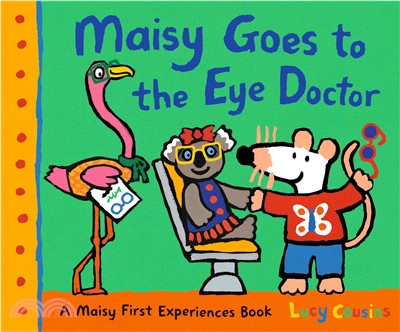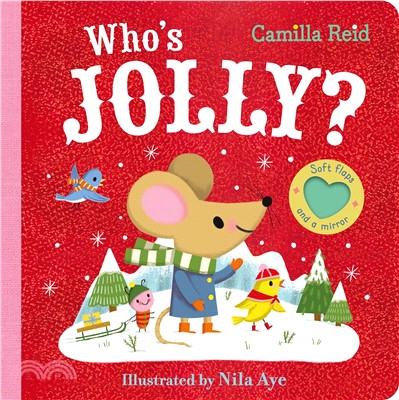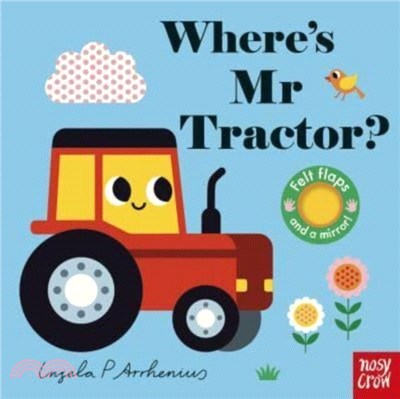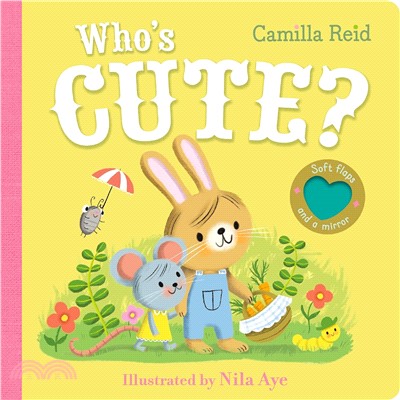庫存:3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0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鍾肇政唯一未出版之長篇通俗小說《夕暮大稻埕》!
在那五光十色的繁華大稻埕,電影辯士兼導演吳臨風在此邂逅了他心中的最佳女主角。命運作弄人的是彩玉、彩雲、彩霞三人相繼出現在他生命之中,到底誰才是他真正的第一女主角呢?
就讓我們隨著淡水河的長流娓娓道來。
作者簡介
鍾肇政
(一九二五年—二○二○年),作家,台灣桃園龍潭人。作品以長篇小說見長,著有《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被認為是台灣大河小說之濫觴。兩套三部曲藉由個人成長經歷,及家族歷史映照時代㜤遞、政權更替下台灣斯土斯民的抵抗、尊嚴與民族情懷,建構壯闊的國族書寫。除大河小說外,另有長、短篇小說、論述、隨筆等,皆收錄於《新編鍾肇政全集》,計45冊47本,凡2千萬字,著作等身。
(一九二五年—二○二○年),作家,台灣桃園龍潭人。作品以長篇小說見長,著有《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被認為是台灣大河小說之濫觴。兩套三部曲藉由個人成長經歷,及家族歷史映照時代㜤遞、政權更替下台灣斯土斯民的抵抗、尊嚴與民族情懷,建構壯闊的國族書寫。除大河小說外,另有長、短篇小說、論述、隨筆等,皆收錄於《新編鍾肇政全集》,計45冊47本,凡2千萬字,著作等身。
序
代序-大稻埕憶舊(節錄)
遙遠的記憶
立意要寫寫大稻埕,不知起於何年何月,該有好一段歲月了。
原因很簡單,只是因為我幼小時曾經在那裡住過幾年。那也幾乎是我開始有記憶的日子──那以前的記憶是更少更少,即使是大稻埕的這一段,也還是那麼少那麼少。
儘管少,可是有幾樁印在腦海裡的,卻那麼鮮明。例如大水的記憶。那一條「港町」──該是日本人來了以後才取的名字,顧名思義,正是港口邊的一條街路──路窄窄的,兩邊住家高出路面該有四五尺吧,我若站在路面,屋基比我還高出許多。那樁大水的記憶裡,這條街路全是水,有人在路上撐船──只是一塊門板樣的木板,也有小販站在那種門板上面沿街叫賣。可以想見,把屋基墊得那麼高是為了出水時避免屋裡淹水。
我就站在石階上頭,像常見的那種「亭仔腳」上看著滾滾大水,和偶而路過的那種木板船。我也還記得,有時到屋後大水門邊去看看從那關緊的巨大鐵門下及門縫湧進來的翻滾的水。可以想像這時後的河水必定氾濫著,一片排水倒海而過的濁濁洪水。當然,只要我爬到那面防水巨牆上,便可以看到那種壯闊的景象,可是一個學齡前的小孩,自然不會被允許上去一賭究竟。
記憶裡屬於那裡的事情不多,大抵都是生活上的若干細節。那時似乎是大稻埕很繁華的昇平年代,台北也開始有自己的流行歌曲,大陸電影常在大稻埕幾家電影院上映。「烏貓」「烏狗」成了流行語,意思應是「摩登女人」「摩登男子」吧。阿姨抱養的表弟不知怎麼學來的,常常唱一支流行歌曲,我也不知不覺學會了。那是叫〈月夜愁〉的一首流行歌,該是作曲家鄧雨賢紅透半邊天的年代。至於電影,我好像常常去看。例如阿姨就有過不少次,塞給我一顆「五選」(五分)的鎳幣說:「阿政,去看影戲」。有一次,一家人走在街路上,我竟然讀出了街角一塊板子上的電影海報的三個字「三姊妹」,使大人們嚇了一跳,嘖嘖稱奇之餘,把我誇讚了一番,八成是因為我還在學齡前的緣故吧。
不過我倒更喜歡日本的「チャンバラ」(劍鬥片),而來自大陸的《火嬈紅蓮寺》,自然也成了使我深深入迷的片子。記憶裡,此片好像分成好幾十集,雖然無法全部看,幾個驚心動魄的鏡頭,在六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清晰地印在腦海裡。幾個名「辯士」(在銀幕旁為觀衆說明劇情的人)的名字,我也耳熟能詳。永樂町的「永樂座」,太平町(今延平北路)的「台灣第一劇場」「太平館」等影院都是我常光顧的地方。另外,「裏驛」(後車站)的「大舞台」是專演歌仔戲的,是母親與阿姨常去的地方,我也被帶去過幾次。
華屋瓦礫 人世滄桑
那年,我決定要寫大稻埕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到故地去做一番巡禮。其實,在成年以後的歲月裡,無端地興起懷舊之思也不知凡幾,甚至有了機會我總會去看看。光是「港町」這個名稱,就已夠使我心中萌生一種含有浪漫意味的念舊情懷了。可惜歲月匆匆,倏忽間人也垂垂老矣,實際重履斯地的機會,除了戰後初期曾經有過幾次之外,竟然是一片空白。直到七○年代末期,我得機在台北擔任了一項編報紙副刊的工作,每周上北兩次,這才有了張羅一點時間的機會。我確曾利用那樣的時間,命豪兒開車陪我去過。第一次,記憶裡的「石橋仔頭」,和那兒的一所派出所,以及從派出所繞進去出到永樂町、永樂座的路已經面目全非了,遍尋不著。第二次雖然出到改稱為迪化街的永樂町,以及城隍廟、永樂市場等地,也從那條古色古香卻依然繁華的狹窄街道穿過去,還是未能找到「港町」,僅發現到城牆早已拆毁,變成一條河邊大道,遠非昔日景觀了。
幸好有了也是港町人的老友莊永明,願為我當嚮導,而另一位老友文經社的吳榮斌也表示願意相陪,於是我多年宿願終究獲償。我們來到了港町,也找到昔日我們一家人住過的舊房子──嚴密地說,那是猷舍住的前面部分──雖然港町依舊那麼窄,屋基也還是高出路面許多,斜對面的陳天來宅更將舊日風華保存著,然而大體而言,仍然只能說一聲面目全非了。左鄰的怡和行成了一座方塊型巨廈,對面曾是一大群女士撿茶的矮陋瓦屋也消失無踪,換成了樓房,一切的一切,硬是把印象裡矗立雲表的陳宅給比下去了!
我不敢聲張,但内心裡翻滾不能自已。面臨人間滄桑,白雲蒼狗,只能偷偷地長嘆一聲「逝者如斯」而已。可是這還只是一個開頭。我們沿街往北走,很快地來到李春生大宅。心裡早有面對人世無常的準備,但是李宅所給予我的,只能用「衝擊」兩字來形容。永明帶著我踩進故宅裡的巷道,牆頹屋陷,瓦礫處處,根本已不僅僅是面目全非的景況而已!
怎麼會這樣呢?
在瓦礫堆裡穿行之際,我們看到了一紙告示貼在一面牆上。大意說:房子要改建,正在拆除中,請勿接近,以免危險云云。屈指一算,這是一九八三年秋間的事,已有八、九年那麼久,新廈應該早就蓋起來了。那以後我未再有機會前往一探究竟,然而可以想見,縱能找到那所新廈及舊居,昔年風貌必是無從追尋的了。
幾句題外話
在劇忙中斷斷續續地寫這篇蕪文,不知不覺成了我的生命史中的一頁,而且似乎拉拉雜雜的。但是,執筆寫「夕暮大稻埕」的心理、生活背景大體就是這個樣子,也就顧不得又臭又長了。
本書的時代背景,應是一九二○年代,但我未作明確交代。這個年代也正是日據時代中期,以抗日意識為凝聚點的「文化協會」(一九二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抗爭活動的時代。港町也曾是那些抗日志士、文化鬥士活動的中心之一。永明即為我指出,文協常用來充作集會或辦演講會的房屋舊址所在,它與我們一家人住過的屋子不過一箭之距。在本書中穿插這些志士及他們的活動,是極為輕而易舉之事,但是我沒有這麼做,甚至諸多人物中連一個日本人也沒有,並且情節還採取較通俗的方式。
其所以如此,自然有原因。由於有人認為我只能寫那種日據時代與抗日意識的作品,甚至還有人不憚於認定我是藉此來取悅、討好當道的!
如果說,我太在意這種近乎曲解或者說攻訐的外界說法,那也不算太離譜,不過我原先倒以為沒有那些志士、鬥士,照樣可以表現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然而,到頭來我仍然不得不承認,如此一來對於歷史脈動的掌握方面,便不免有所欠缺了。
──這些,說來還只是題外話罷了,多說無益,縱然不無若干遺憾在心,也只好如此了。
趁這引出一些記憶之便,我還要再附帶一筆。本書是去舊地巡禮後於次年(一九八四)執筆的。記得那一天我們去港町之後(也許之前)還到博物館去看了剛出土的「卑南出土文物展」。我被那些形形色色的土器、飾物之類狠狠地敲動了心絃,異想天開地竟萌生了撰寫以卑南考古為背景的作品,這便是我繼本書之後有「卑南平原」一書執筆的張本,當然,這些更是「題外之外」的話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
遙遠的記憶
立意要寫寫大稻埕,不知起於何年何月,該有好一段歲月了。
原因很簡單,只是因為我幼小時曾經在那裡住過幾年。那也幾乎是我開始有記憶的日子──那以前的記憶是更少更少,即使是大稻埕的這一段,也還是那麼少那麼少。
儘管少,可是有幾樁印在腦海裡的,卻那麼鮮明。例如大水的記憶。那一條「港町」──該是日本人來了以後才取的名字,顧名思義,正是港口邊的一條街路──路窄窄的,兩邊住家高出路面該有四五尺吧,我若站在路面,屋基比我還高出許多。那樁大水的記憶裡,這條街路全是水,有人在路上撐船──只是一塊門板樣的木板,也有小販站在那種門板上面沿街叫賣。可以想見,把屋基墊得那麼高是為了出水時避免屋裡淹水。
我就站在石階上頭,像常見的那種「亭仔腳」上看著滾滾大水,和偶而路過的那種木板船。我也還記得,有時到屋後大水門邊去看看從那關緊的巨大鐵門下及門縫湧進來的翻滾的水。可以想像這時後的河水必定氾濫著,一片排水倒海而過的濁濁洪水。當然,只要我爬到那面防水巨牆上,便可以看到那種壯闊的景象,可是一個學齡前的小孩,自然不會被允許上去一賭究竟。
記憶裡屬於那裡的事情不多,大抵都是生活上的若干細節。那時似乎是大稻埕很繁華的昇平年代,台北也開始有自己的流行歌曲,大陸電影常在大稻埕幾家電影院上映。「烏貓」「烏狗」成了流行語,意思應是「摩登女人」「摩登男子」吧。阿姨抱養的表弟不知怎麼學來的,常常唱一支流行歌曲,我也不知不覺學會了。那是叫〈月夜愁〉的一首流行歌,該是作曲家鄧雨賢紅透半邊天的年代。至於電影,我好像常常去看。例如阿姨就有過不少次,塞給我一顆「五選」(五分)的鎳幣說:「阿政,去看影戲」。有一次,一家人走在街路上,我竟然讀出了街角一塊板子上的電影海報的三個字「三姊妹」,使大人們嚇了一跳,嘖嘖稱奇之餘,把我誇讚了一番,八成是因為我還在學齡前的緣故吧。
不過我倒更喜歡日本的「チャンバラ」(劍鬥片),而來自大陸的《火嬈紅蓮寺》,自然也成了使我深深入迷的片子。記憶裡,此片好像分成好幾十集,雖然無法全部看,幾個驚心動魄的鏡頭,在六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清晰地印在腦海裡。幾個名「辯士」(在銀幕旁為觀衆說明劇情的人)的名字,我也耳熟能詳。永樂町的「永樂座」,太平町(今延平北路)的「台灣第一劇場」「太平館」等影院都是我常光顧的地方。另外,「裏驛」(後車站)的「大舞台」是專演歌仔戲的,是母親與阿姨常去的地方,我也被帶去過幾次。
華屋瓦礫 人世滄桑
那年,我決定要寫大稻埕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到故地去做一番巡禮。其實,在成年以後的歲月裡,無端地興起懷舊之思也不知凡幾,甚至有了機會我總會去看看。光是「港町」這個名稱,就已夠使我心中萌生一種含有浪漫意味的念舊情懷了。可惜歲月匆匆,倏忽間人也垂垂老矣,實際重履斯地的機會,除了戰後初期曾經有過幾次之外,竟然是一片空白。直到七○年代末期,我得機在台北擔任了一項編報紙副刊的工作,每周上北兩次,這才有了張羅一點時間的機會。我確曾利用那樣的時間,命豪兒開車陪我去過。第一次,記憶裡的「石橋仔頭」,和那兒的一所派出所,以及從派出所繞進去出到永樂町、永樂座的路已經面目全非了,遍尋不著。第二次雖然出到改稱為迪化街的永樂町,以及城隍廟、永樂市場等地,也從那條古色古香卻依然繁華的狹窄街道穿過去,還是未能找到「港町」,僅發現到城牆早已拆毁,變成一條河邊大道,遠非昔日景觀了。
幸好有了也是港町人的老友莊永明,願為我當嚮導,而另一位老友文經社的吳榮斌也表示願意相陪,於是我多年宿願終究獲償。我們來到了港町,也找到昔日我們一家人住過的舊房子──嚴密地說,那是猷舍住的前面部分──雖然港町依舊那麼窄,屋基也還是高出路面許多,斜對面的陳天來宅更將舊日風華保存著,然而大體而言,仍然只能說一聲面目全非了。左鄰的怡和行成了一座方塊型巨廈,對面曾是一大群女士撿茶的矮陋瓦屋也消失無踪,換成了樓房,一切的一切,硬是把印象裡矗立雲表的陳宅給比下去了!
我不敢聲張,但内心裡翻滾不能自已。面臨人間滄桑,白雲蒼狗,只能偷偷地長嘆一聲「逝者如斯」而已。可是這還只是一個開頭。我們沿街往北走,很快地來到李春生大宅。心裡早有面對人世無常的準備,但是李宅所給予我的,只能用「衝擊」兩字來形容。永明帶著我踩進故宅裡的巷道,牆頹屋陷,瓦礫處處,根本已不僅僅是面目全非的景況而已!
怎麼會這樣呢?
在瓦礫堆裡穿行之際,我們看到了一紙告示貼在一面牆上。大意說:房子要改建,正在拆除中,請勿接近,以免危險云云。屈指一算,這是一九八三年秋間的事,已有八、九年那麼久,新廈應該早就蓋起來了。那以後我未再有機會前往一探究竟,然而可以想見,縱能找到那所新廈及舊居,昔年風貌必是無從追尋的了。
幾句題外話
在劇忙中斷斷續續地寫這篇蕪文,不知不覺成了我的生命史中的一頁,而且似乎拉拉雜雜的。但是,執筆寫「夕暮大稻埕」的心理、生活背景大體就是這個樣子,也就顧不得又臭又長了。
本書的時代背景,應是一九二○年代,但我未作明確交代。這個年代也正是日據時代中期,以抗日意識為凝聚點的「文化協會」(一九二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抗爭活動的時代。港町也曾是那些抗日志士、文化鬥士活動的中心之一。永明即為我指出,文協常用來充作集會或辦演講會的房屋舊址所在,它與我們一家人住過的屋子不過一箭之距。在本書中穿插這些志士及他們的活動,是極為輕而易舉之事,但是我沒有這麼做,甚至諸多人物中連一個日本人也沒有,並且情節還採取較通俗的方式。
其所以如此,自然有原因。由於有人認為我只能寫那種日據時代與抗日意識的作品,甚至還有人不憚於認定我是藉此來取悅、討好當道的!
如果說,我太在意這種近乎曲解或者說攻訐的外界說法,那也不算太離譜,不過我原先倒以為沒有那些志士、鬥士,照樣可以表現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然而,到頭來我仍然不得不承認,如此一來對於歷史脈動的掌握方面,便不免有所欠缺了。
──這些,說來還只是題外話罷了,多說無益,縱然不無若干遺憾在心,也只好如此了。
趁這引出一些記憶之便,我還要再附帶一筆。本書是去舊地巡禮後於次年(一九八四)執筆的。記得那一天我們去港町之後(也許之前)還到博物館去看了剛出土的「卑南出土文物展」。我被那些形形色色的土器、飾物之類狠狠地敲動了心絃,異想天開地竟萌生了撰寫以卑南考古為背景的作品,這便是我繼本書之後有「卑南平原」一書執筆的張本,當然,這些更是「題外之外」的話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
目次
代序-大稻埕憶舊(節錄)
觀音山落日
淡水河的嗚咽
一百萬的查某
彩玉和彩雲
臨風和娜娜
港町大水之夜
九間仔街的激情
五月十三迎城隍
魂斷台北橋
愛的旅途
啊,青春只有一次
肉彈三勇士的震撼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尾聲
觀音山落日
淡水河的嗚咽
一百萬的查某
彩玉和彩雲
臨風和娜娜
港町大水之夜
九間仔街的激情
五月十三迎城隍
魂斷台北橋
愛的旅途
啊,青春只有一次
肉彈三勇士的震撼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尾聲
書摘/試閱
最後一場戲,無疑也是整個拍片過程當中,最艱鉅的階段。
在別墅裡,那位頭家展開了一場對彩雲的猙獰的撲襲,非把她弄到手不肯罷休。
彩雲原來已看開了。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就要那樣決定了。她當然是心有未甘,但也懂得自己無力抗拒。
她的一份極為勉強的諦念,壓抑了自己的本性。
她甚至也漸漸地有了順從命運的自棄。不為什麼,只因從家破人亡以來的淒苦境遇,使她體會了人力的渺小。再加上將近一年的學藝的囝仔藝旦生涯,使她耳聞目睹了太多太多相似的沉淪經過。無謂的掙扎,對一個像她那樣的弱者,反倒更可能造成傷害,使她陷入更悲慘的境地。而如果她能順應潮流,從中覓取一條路,很多的時候,這條路倒是較為平坦易行的。「反正我們都是苦命人,在苦命裡,圖個小小的舒服,也是應該的……」阿姨的這一類話聽多了,卻也教人覺得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彩雲也許太年輕,也許年紀太大;也可能她本性裡的一付倔強脾氣太強了些,結果在面臨最後關頭的當兒,一反自己的決心,發而為強烈的抗拒。
強烈的抗拒,更搧動了猛撲者的慾念。
當撲襲加上了這麼一股兇狠時,抗拒變成了拚命。
一撲一拒,相激相盪,步步昇高,終至一發不可收拾了。
彩雲忘了自我,所有的諦念,所有的對命運的屈從,最後終於離她而去。
剩下的只有保護自己的本能。
她的刁蠻與倔強,壓倒了一切世俗的見解。
她覓得了一個縫隙,逃離了虎口。
處女的尊嚴,得到了勝利。
這是上一場的主戲。
接下來,是她狂奔而出後的奔逃鏡頭。
夜裡的幾個街角,幾條僻徑。
一個無助的、狂亂的孤寂身影。
連在街頭彳亍的狗都避開她。
她來到大橋頭。
──這就是最後一場戲了。
夜空裡,一弓一弓的橋,像黝黑的虹。
水聲輕咽。
幾縷燈光的倒映閃爍不定,益增淒涼之色。
奔至橋中,她這才首次發現置身何處。
也許她早已意識到這個地點,一路奔馳過來的。
也可能冥冥中有什麼引導著她。
彷彿到了這裡,她總算有了喘一口氣的清醒。
她激烈地喘著氣息,回頭察看。
有驚悸,但也漸有驚魂甫定的放鬆。
她回顧。總於確定了自己身在何處。
逃離虎口的喜悅,早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徬徨,以及對身世飄零的痛苦與絕望。
也許,她祈望有什麼人在這當兒忽從天降。那是她的救星。瘦長個子的年輕人。她知道他愛她,她也愛他。他是她這一刻所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救她的人。可是,她也分明知道他沒有這力量。他曾在一個緊要關頭爽了約。要不是五月十三大祭典,在那一場昏天黑地的熱鬧裡,體會到人世間一切不可靠,她說不定不會到別墅去挨受屈辱。嗯,世間人沒有一個可靠的。
即令城隍爺也……
她在下決心。
決心既定。她就哭起來。
她還得顧慮兩方動靜。這邊,大橋頭;那邊,三重埔。隨時可能有人或車過來的。
終於,她要行動了。
爬上橋欄,縱身一躍。
──鏡頭捕捉住了墜落的稻草人。
戲還沒完哩!
鏡頭還要載浮載沉的生命掙扎的戲。
一行人移到稍北的河岸淺灘。
娜娜泡在水裡,聽監督的命令做戲。
遠處有二三漁火。
她雙手猛划猛划。
她沉下又浮起。
她喝水。
監督的要求好嚴格。拍戲徹夜進行。
娜娜真地會淹死哩。
然後,她失去掙扎力氣,順流而下。
陳大塊總算在監督劉太陽的情商下,為這最後一場戲,準備了一輛烏頭仔車。
娜娜在車裡屈身更衣,然後被載回九間仔街。
唯一知道她受了風寒的是吳臨風。
烏頭車要開走時,大塊叔和監督他們都圍在車旁送她。陳大塊還說要同車送她回去。可是她堅決表示很好,不願意勞煩人家。臨風看到娜娜用一條毯子裹住身子,臉上雖然裝著笑,可是在一盞昏黃的小車燈下,她蒼白著臉,還好像在使勁地忍著牙齒碰撞。即使時當大熱天,但從凌晨時分起,足足在河水裡泡了三個小時水。像娜娜那樣的嬌軀,怎麼忍受得了。
臨風和大家一塊回到永樂座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臨風本來與工作人員無關,可是自從永樂座改演正音的這些日子以來,他在戲院裡沒有事做,所以一直陪著大家跑,有時需要人手,便主動湊上一腳去幫幫忙,否則便做壁上觀。回到永樂座,他也應該可以告退的,但幫著收拾些用具,成了他慣常的工作。
忙了一陣子,大夥也就要散了。這個時候,人人都已是累極倦極,可是臨風儘管累得一身都像棉絮似的,一點勁兒也沒有,但心裡卻有一份無法壓抑的擔憂與期待。他的一顆心,可以說早已飛到彩霞那兒去了。她一定病了。她不可能絲毫不受影響。也許,她這一刻非常需要人陪她,照顧她。
然而,臨風就是沒敢大大方方地先告退。好不容易地才忙完,跟著大家走出了地下室,走向大門口。
「劉的。」開麥拉張明光好像有滿肚子的氣。「這樣就散了?」
「嗯,先睡個覺吧。」監督劉太陽有氣無力地。
「可是……哎哎,天馬兄不應該不露臉啊。真懂得享受。」張明光終究挑明了。
「人家忙。」監督安撫地答。
「忙?哼哼,我們累死了,他還不知道呢。忙!」張明光悻悻地說:「大塊的也不應該一聲不響,半路上就溜了。這些人,實在不是東西。」
「明光,抱怨也沒用啦,人家是頭家啊。」
「什麼頭家。大家都是為了一個理想合作的,怎麼可以分頭家和夥計。」
「不是啦,我不是說他們這麼分了。喂喂,你今天怎麼亂發脾氣?事情都完了,我們也盡力了,天下泰平了,可以好好休息了,你就少說幾句吧。」
「……」開麥拉總算不響了。
「這樣吧。」監督想起了似地回過頭看了一眼說:「對啦,拜託臨風兄吧。」
「我……」臨風微微一驚。
「是啦。拜託你到天馬兄那裡說一聲,戲都拍完了。我們等他的消息。」
「好的。」臨風只好一口承擔下來。
天早已大亮了,不過時候還早,街道上人影寥寥,都是一些挑賣的小販之類。出到永樂町,很快地就來到城隍廟口了。
有杏仁茶的叫賣聲。那微微的杏仁香味,和油車粿的香味,在鼻腔裡混在一塊。肚子猛地咕嚕咕嚕起來。
還是快一點去吧。這份臨時落到頭上來的差使,使他有些不高興,不過仔細一想,卻也正是他應該負起來的一份責任。他要打斷強大的引誘般地加快了步子。
他很快地就來到許天馬在太平町的寓所。
果不其然,這位大稻埕第一號辯士,這時剛剛起床,正在漱洗呢。不過聽到臨風來到,倒也很快地就出來客廳了。
臨風向馬內遮報告了監督的交代,約略地說明了一夜來的拍片情形。許天馬點燃了一支雪茄說:
「真是太辛苦了。他們埋怨我,是難怪的。可是臨風,你也知道我目前的忙亂情形。」
「我相信他們會諒解的。」
「其實,我昨晚戲散後,本來也想趕去大橋頭的,偏偏昨晚出了一點事,回到家都快三點了,實在支持不下去。一方面也想,有陳大塊在場,應該不會有事,所以就沒去了。沒想到他也先走。」
「是戲拍完,回來時才離開,先回家去了的。」
「難得陳大塊這次還這麼熱心。好吧。我明白了。晚上先來個慶功宴吧。唔,七點好了,就在江山樓。我會叫人去通知他們。你也來。」
「我也要嗎?」
「當然要。還有男女主角柯非光,娜娜,所有工作人員通通要。對啦,剛剛你說娜娜浸在河裡,足足有三點鐘那麼久是嗎?她還好吧?」
「我不知道。大概……」
「你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呢?」
「臨風,你的事,我可都知道呢。」
「我?」
臨風心口一震。他看到馬內遮眼睛裡有一抹非同尋常的光。而它正穿透著他的胸口。他分明感到自己的臉在漲,在燒,心口也突然跳動起來了。
「嘿嘿,別以為瞞得過我的眼光。」
「馬內遮,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的事,是什麼事呢?」
「咦,你想賴?我說的是你和娜娜的事啊。」
「我,我,沒有啊。」
「你看,臉都紅了。你還是這麼純情。你這樣,還想瞞得住啊?哈哈哈……。你的童貞,都獻給她了吧?」
「馬內遮,我真的……」
「不用說了。」許天馬打斷了臨風說:「我是很嫉妒,說不出的滋味,不過情場如戰場,有人勝利,有人敗北,還有什麼話呢?很意外,也不意外,你還不懂的,不過這都沒關係啦。你可要提防一下陳大塊。」
「他?」
「別會錯意,他也搶不過你的,這一點可以放心。我說的是……他可不像我這麼放得開呢。」
在別墅裡,那位頭家展開了一場對彩雲的猙獰的撲襲,非把她弄到手不肯罷休。
彩雲原來已看開了。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就要那樣決定了。她當然是心有未甘,但也懂得自己無力抗拒。
她的一份極為勉強的諦念,壓抑了自己的本性。
她甚至也漸漸地有了順從命運的自棄。不為什麼,只因從家破人亡以來的淒苦境遇,使她體會了人力的渺小。再加上將近一年的學藝的囝仔藝旦生涯,使她耳聞目睹了太多太多相似的沉淪經過。無謂的掙扎,對一個像她那樣的弱者,反倒更可能造成傷害,使她陷入更悲慘的境地。而如果她能順應潮流,從中覓取一條路,很多的時候,這條路倒是較為平坦易行的。「反正我們都是苦命人,在苦命裡,圖個小小的舒服,也是應該的……」阿姨的這一類話聽多了,卻也教人覺得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彩雲也許太年輕,也許年紀太大;也可能她本性裡的一付倔強脾氣太強了些,結果在面臨最後關頭的當兒,一反自己的決心,發而為強烈的抗拒。
強烈的抗拒,更搧動了猛撲者的慾念。
當撲襲加上了這麼一股兇狠時,抗拒變成了拚命。
一撲一拒,相激相盪,步步昇高,終至一發不可收拾了。
彩雲忘了自我,所有的諦念,所有的對命運的屈從,最後終於離她而去。
剩下的只有保護自己的本能。
她的刁蠻與倔強,壓倒了一切世俗的見解。
她覓得了一個縫隙,逃離了虎口。
處女的尊嚴,得到了勝利。
這是上一場的主戲。
接下來,是她狂奔而出後的奔逃鏡頭。
夜裡的幾個街角,幾條僻徑。
一個無助的、狂亂的孤寂身影。
連在街頭彳亍的狗都避開她。
她來到大橋頭。
──這就是最後一場戲了。
夜空裡,一弓一弓的橋,像黝黑的虹。
水聲輕咽。
幾縷燈光的倒映閃爍不定,益增淒涼之色。
奔至橋中,她這才首次發現置身何處。
也許她早已意識到這個地點,一路奔馳過來的。
也可能冥冥中有什麼引導著她。
彷彿到了這裡,她總算有了喘一口氣的清醒。
她激烈地喘著氣息,回頭察看。
有驚悸,但也漸有驚魂甫定的放鬆。
她回顧。總於確定了自己身在何處。
逃離虎口的喜悅,早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徬徨,以及對身世飄零的痛苦與絕望。
也許,她祈望有什麼人在這當兒忽從天降。那是她的救星。瘦長個子的年輕人。她知道他愛她,她也愛他。他是她這一刻所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救她的人。可是,她也分明知道他沒有這力量。他曾在一個緊要關頭爽了約。要不是五月十三大祭典,在那一場昏天黑地的熱鬧裡,體會到人世間一切不可靠,她說不定不會到別墅去挨受屈辱。嗯,世間人沒有一個可靠的。
即令城隍爺也……
她在下決心。
決心既定。她就哭起來。
她還得顧慮兩方動靜。這邊,大橋頭;那邊,三重埔。隨時可能有人或車過來的。
終於,她要行動了。
爬上橋欄,縱身一躍。
──鏡頭捕捉住了墜落的稻草人。
戲還沒完哩!
鏡頭還要載浮載沉的生命掙扎的戲。
一行人移到稍北的河岸淺灘。
娜娜泡在水裡,聽監督的命令做戲。
遠處有二三漁火。
她雙手猛划猛划。
她沉下又浮起。
她喝水。
監督的要求好嚴格。拍戲徹夜進行。
娜娜真地會淹死哩。
然後,她失去掙扎力氣,順流而下。
陳大塊總算在監督劉太陽的情商下,為這最後一場戲,準備了一輛烏頭仔車。
娜娜在車裡屈身更衣,然後被載回九間仔街。
唯一知道她受了風寒的是吳臨風。
烏頭車要開走時,大塊叔和監督他們都圍在車旁送她。陳大塊還說要同車送她回去。可是她堅決表示很好,不願意勞煩人家。臨風看到娜娜用一條毯子裹住身子,臉上雖然裝著笑,可是在一盞昏黃的小車燈下,她蒼白著臉,還好像在使勁地忍著牙齒碰撞。即使時當大熱天,但從凌晨時分起,足足在河水裡泡了三個小時水。像娜娜那樣的嬌軀,怎麼忍受得了。
臨風和大家一塊回到永樂座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臨風本來與工作人員無關,可是自從永樂座改演正音的這些日子以來,他在戲院裡沒有事做,所以一直陪著大家跑,有時需要人手,便主動湊上一腳去幫幫忙,否則便做壁上觀。回到永樂座,他也應該可以告退的,但幫著收拾些用具,成了他慣常的工作。
忙了一陣子,大夥也就要散了。這個時候,人人都已是累極倦極,可是臨風儘管累得一身都像棉絮似的,一點勁兒也沒有,但心裡卻有一份無法壓抑的擔憂與期待。他的一顆心,可以說早已飛到彩霞那兒去了。她一定病了。她不可能絲毫不受影響。也許,她這一刻非常需要人陪她,照顧她。
然而,臨風就是沒敢大大方方地先告退。好不容易地才忙完,跟著大家走出了地下室,走向大門口。
「劉的。」開麥拉張明光好像有滿肚子的氣。「這樣就散了?」
「嗯,先睡個覺吧。」監督劉太陽有氣無力地。
「可是……哎哎,天馬兄不應該不露臉啊。真懂得享受。」張明光終究挑明了。
「人家忙。」監督安撫地答。
「忙?哼哼,我們累死了,他還不知道呢。忙!」張明光悻悻地說:「大塊的也不應該一聲不響,半路上就溜了。這些人,實在不是東西。」
「明光,抱怨也沒用啦,人家是頭家啊。」
「什麼頭家。大家都是為了一個理想合作的,怎麼可以分頭家和夥計。」
「不是啦,我不是說他們這麼分了。喂喂,你今天怎麼亂發脾氣?事情都完了,我們也盡力了,天下泰平了,可以好好休息了,你就少說幾句吧。」
「……」開麥拉總算不響了。
「這樣吧。」監督想起了似地回過頭看了一眼說:「對啦,拜託臨風兄吧。」
「我……」臨風微微一驚。
「是啦。拜託你到天馬兄那裡說一聲,戲都拍完了。我們等他的消息。」
「好的。」臨風只好一口承擔下來。
天早已大亮了,不過時候還早,街道上人影寥寥,都是一些挑賣的小販之類。出到永樂町,很快地就來到城隍廟口了。
有杏仁茶的叫賣聲。那微微的杏仁香味,和油車粿的香味,在鼻腔裡混在一塊。肚子猛地咕嚕咕嚕起來。
還是快一點去吧。這份臨時落到頭上來的差使,使他有些不高興,不過仔細一想,卻也正是他應該負起來的一份責任。他要打斷強大的引誘般地加快了步子。
他很快地就來到許天馬在太平町的寓所。
果不其然,這位大稻埕第一號辯士,這時剛剛起床,正在漱洗呢。不過聽到臨風來到,倒也很快地就出來客廳了。
臨風向馬內遮報告了監督的交代,約略地說明了一夜來的拍片情形。許天馬點燃了一支雪茄說:
「真是太辛苦了。他們埋怨我,是難怪的。可是臨風,你也知道我目前的忙亂情形。」
「我相信他們會諒解的。」
「其實,我昨晚戲散後,本來也想趕去大橋頭的,偏偏昨晚出了一點事,回到家都快三點了,實在支持不下去。一方面也想,有陳大塊在場,應該不會有事,所以就沒去了。沒想到他也先走。」
「是戲拍完,回來時才離開,先回家去了的。」
「難得陳大塊這次還這麼熱心。好吧。我明白了。晚上先來個慶功宴吧。唔,七點好了,就在江山樓。我會叫人去通知他們。你也來。」
「我也要嗎?」
「當然要。還有男女主角柯非光,娜娜,所有工作人員通通要。對啦,剛剛你說娜娜浸在河裡,足足有三點鐘那麼久是嗎?她還好吧?」
「我不知道。大概……」
「你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呢?」
「臨風,你的事,我可都知道呢。」
「我?」
臨風心口一震。他看到馬內遮眼睛裡有一抹非同尋常的光。而它正穿透著他的胸口。他分明感到自己的臉在漲,在燒,心口也突然跳動起來了。
「嘿嘿,別以為瞞得過我的眼光。」
「馬內遮,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的事,是什麼事呢?」
「咦,你想賴?我說的是你和娜娜的事啊。」
「我,我,沒有啊。」
「你看,臉都紅了。你還是這麼純情。你這樣,還想瞞得住啊?哈哈哈……。你的童貞,都獻給她了吧?」
「馬內遮,我真的……」
「不用說了。」許天馬打斷了臨風說:「我是很嫉妒,說不出的滋味,不過情場如戰場,有人勝利,有人敗北,還有什麼話呢?很意外,也不意外,你還不懂的,不過這都沒關係啦。你可要提防一下陳大塊。」
「他?」
「別會錯意,他也搶不過你的,這一點可以放心。我說的是……他可不像我這麼放得開呢。」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