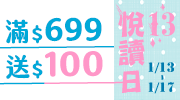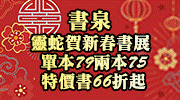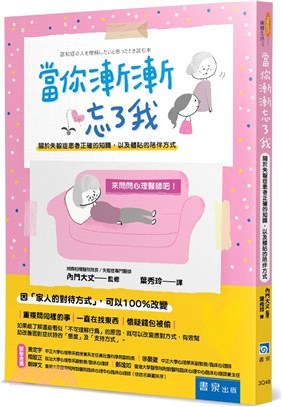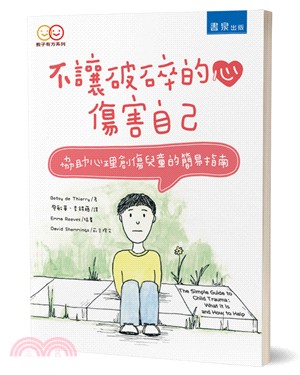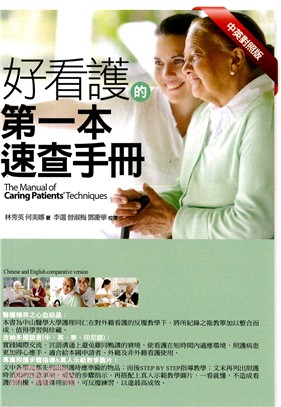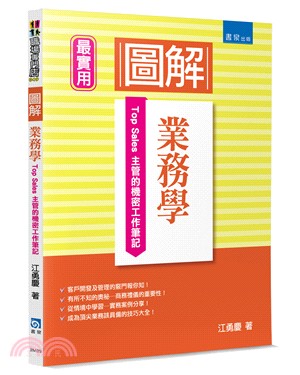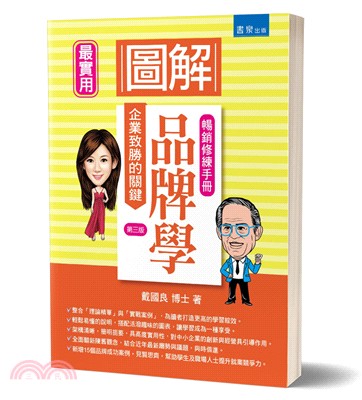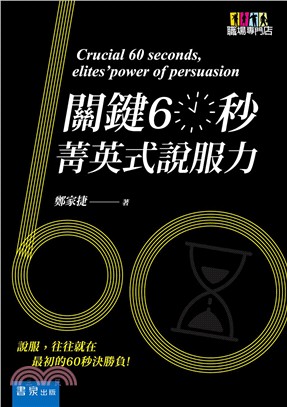城北舊事(電子書)
商品資訊
定價
:NT$ 380 元優惠價
:79 折 300 元
閱讀器:書紐電子書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9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山海交織的賦格曲,街頭燃燒的一切,
青春是魍魍也惘惘的迷途,
卻有一道尋夢成長的路徑:一路向北……
「我經常在那一大片荒草之中奔跑,
如今夢中依然,醒來只是悵惘。」
★郝譽翔獻給永恆的故鄉――「北投」最柔情的地誌書寫
★記下狂飆的九○年代,解嚴後野百合,生命故事的起點
「北投」之名源自於平埔族語ki-pataw,「女巫」的意思。如同巫者的形象,此處終年飄散山嵐和硫磺煙霧,淡水河流經、座落關渡平原、觀音山腳下,這片陸地送來海洋鹹濕的氣息,莽莽養育著一股野性的召喚。
郝譽翔以散文書寫年幼自高雄北上搬遷至北投的經驗,在上個世紀末,那非典型的台北邊陲小城,沒有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反倒像是大自然的野性搖籃,讓郝譽翔成長於斯,患夢於此。她乘坐北淡線列車晃遊,著迷坂本龍一的追星時刻,沒有明天般地夜騎於深夜的陽金公路……她的桀驁與不馴,彷若是特異地域生養的狂奔一人。
她因著這股「野」,在大學青年的九〇年代,經歷解嚴後的台灣、野百合學運的動盪時光,觀看街頭運動如嘉年華般狂癲,股票上萬點眾人的浮動與狂躁,彷彿是過於漫長的夏日激情,把所有人推到時代的浪尖……她想要逃,離開憂鬱的母親,恐怖的情人,決裂的閨密……逃到美國沙漠小鎮,最終在三十歲落腳島嶼東部。北投已然從生命中消失了,但山與海卻仍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在花蓮,她告別青春。
二十多年後,郝譽翔以文字永恆捕捉那些鬱動而光燦的瞬間,巫女般喚起那段神魔的城北歲月。
「那是山與海混沌的交界,夜與夢的黑洞,
我生命中最初讀到的一首詩,句句都是命運的隱喻,
讓我不禁悠然神往,卻又每每悵然若失於它是如此的晦澀不可解。」――郝譽翔
【名家推薦】
郝譽翔的這本散文集(其實更像一本詩意的小說)的基底不外是抒情。但感傷中不斷纏繞頸項的糾結與困頓,及不時迸出腦頂的暴烈與絕望,比起一般的青春紀事殘酷許多。她是以一種近乎披肝瀝膽的細膩,無畏地呈現青春萌芽時期的苦楚與躁動。」――廖咸浩|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外文系特聘教授――專文推薦
純淨做為綱本,冷靜帶來心碎,筆觸幽靜神祕,面似散文但有小說滲透。童貞不曾離去,一個手勢、氣味都是轉角,瀕臨了便如躲貓貓,「原來就在這裡」。細流、巨流擁有共同發源,《城北舊事》為成長與地誌書寫,完成最佳範本。
――吳鈞堯|作家
譽翔文學二十年,先小說後散文,確定且雋實地相信:學術另一面,她是這一代才情獨具的好作家!北投的少女回眸青春,不風花雪月,慧眼淨心,秀緻文字虔真寫就人生悲歡、正是:郝譽翔風格最深切的塵世風景。
――林文義|作家
從回憶出發的書寫經常沾染上魔幻的色彩,郝譽翔筆下的北投、城北居所,不僅是神魔之地,也是年少狂放的縮影;帶我們回到青春現場,不安定的,不受拘束的,像是被什麼驅動而朝不明的方向往地平邊際追索,卻從未有人逃脫……。
――邱坤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
我羨慕、欽佩譽翔有著這麼觀察入微的眼睛、這麼鉅細靡遺的記憶,以及這麼生動細膩的文筆。這本書不只是地景人文的書寫,更活生生勾勒出一個時代早已逝去的樣貌。
――施昇輝|暢銷斜槓作家
哪怕已在好看極了的《幽冥物語》和《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寫過北投,《城北舊事》沒有停止記憶的定點挖掘,且盡情擴充回憶的面積,使一去不返的青春與一九八○台灣,俱能在沛然的傾訴中,鮮豔重塑。
――孫梓評|作家
作者生命中所有的詩意,盡在疏離和不馴之間流連。她就是一個存在的夢,文字敘述亦如夢的延伸,忽而真實、忽而迷幻,照見你我曾經騷動的青春。
――鄭如晴|作家、前世新大學教授
我搭著通往城北的捷運,讀女孩揚起青春之筆寫盡城北舊事,一站一站,如一艘回憶之船;原來,神魔也好,狂野也罷,這樣那樣的記憶皆是城北點滴。她以靈動的文字輕輕激起的成長漣漪,與時代緊緊相連,從此,城南有林海音,城北有郝譽翔。
――盧美杏|《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蔡素芬|作家
蔡詩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劉維公|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
韓良憶|作家
――追憶推薦(按姓名筆畫排序)
青春是魍魍也惘惘的迷途,
卻有一道尋夢成長的路徑:一路向北……
「我經常在那一大片荒草之中奔跑,
如今夢中依然,醒來只是悵惘。」
★郝譽翔獻給永恆的故鄉――「北投」最柔情的地誌書寫
★記下狂飆的九○年代,解嚴後野百合,生命故事的起點
「北投」之名源自於平埔族語ki-pataw,「女巫」的意思。如同巫者的形象,此處終年飄散山嵐和硫磺煙霧,淡水河流經、座落關渡平原、觀音山腳下,這片陸地送來海洋鹹濕的氣息,莽莽養育著一股野性的召喚。
郝譽翔以散文書寫年幼自高雄北上搬遷至北投的經驗,在上個世紀末,那非典型的台北邊陲小城,沒有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反倒像是大自然的野性搖籃,讓郝譽翔成長於斯,患夢於此。她乘坐北淡線列車晃遊,著迷坂本龍一的追星時刻,沒有明天般地夜騎於深夜的陽金公路……她的桀驁與不馴,彷若是特異地域生養的狂奔一人。
她因著這股「野」,在大學青年的九〇年代,經歷解嚴後的台灣、野百合學運的動盪時光,觀看街頭運動如嘉年華般狂癲,股票上萬點眾人的浮動與狂躁,彷彿是過於漫長的夏日激情,把所有人推到時代的浪尖……她想要逃,離開憂鬱的母親,恐怖的情人,決裂的閨密……逃到美國沙漠小鎮,最終在三十歲落腳島嶼東部。北投已然從生命中消失了,但山與海卻仍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在花蓮,她告別青春。
二十多年後,郝譽翔以文字永恆捕捉那些鬱動而光燦的瞬間,巫女般喚起那段神魔的城北歲月。
「那是山與海混沌的交界,夜與夢的黑洞,
我生命中最初讀到的一首詩,句句都是命運的隱喻,
讓我不禁悠然神往,卻又每每悵然若失於它是如此的晦澀不可解。」――郝譽翔
【名家推薦】
郝譽翔的這本散文集(其實更像一本詩意的小說)的基底不外是抒情。但感傷中不斷纏繞頸項的糾結與困頓,及不時迸出腦頂的暴烈與絕望,比起一般的青春紀事殘酷許多。她是以一種近乎披肝瀝膽的細膩,無畏地呈現青春萌芽時期的苦楚與躁動。」――廖咸浩|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外文系特聘教授――專文推薦
純淨做為綱本,冷靜帶來心碎,筆觸幽靜神祕,面似散文但有小說滲透。童貞不曾離去,一個手勢、氣味都是轉角,瀕臨了便如躲貓貓,「原來就在這裡」。細流、巨流擁有共同發源,《城北舊事》為成長與地誌書寫,完成最佳範本。
――吳鈞堯|作家
譽翔文學二十年,先小說後散文,確定且雋實地相信:學術另一面,她是這一代才情獨具的好作家!北投的少女回眸青春,不風花雪月,慧眼淨心,秀緻文字虔真寫就人生悲歡、正是:郝譽翔風格最深切的塵世風景。
――林文義|作家
從回憶出發的書寫經常沾染上魔幻的色彩,郝譽翔筆下的北投、城北居所,不僅是神魔之地,也是年少狂放的縮影;帶我們回到青春現場,不安定的,不受拘束的,像是被什麼驅動而朝不明的方向往地平邊際追索,卻從未有人逃脫……。
――邱坤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
我羨慕、欽佩譽翔有著這麼觀察入微的眼睛、這麼鉅細靡遺的記憶,以及這麼生動細膩的文筆。這本書不只是地景人文的書寫,更活生生勾勒出一個時代早已逝去的樣貌。
――施昇輝|暢銷斜槓作家
哪怕已在好看極了的《幽冥物語》和《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寫過北投,《城北舊事》沒有停止記憶的定點挖掘,且盡情擴充回憶的面積,使一去不返的青春與一九八○台灣,俱能在沛然的傾訴中,鮮豔重塑。
――孫梓評|作家
作者生命中所有的詩意,盡在疏離和不馴之間流連。她就是一個存在的夢,文字敘述亦如夢的延伸,忽而真實、忽而迷幻,照見你我曾經騷動的青春。
――鄭如晴|作家、前世新大學教授
我搭著通往城北的捷運,讀女孩揚起青春之筆寫盡城北舊事,一站一站,如一艘回憶之船;原來,神魔也好,狂野也罷,這樣那樣的記憶皆是城北點滴。她以靈動的文字輕輕激起的成長漣漪,與時代緊緊相連,從此,城南有林海音,城北有郝譽翔。
――盧美杏|《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蔡素芬|作家
蔡詩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劉維公|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
韓良憶|作家
――追憶推薦(按姓名筆畫排序)
作者簡介
郝譽翔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北教育大學語創系教授,熱愛旅行、潛水和帆船,並且多次將旅行、海洋和島嶼等化成為個人創作的主題。曾獲得金鼎獎、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獎、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及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獎等重要獎項。
著有小說《幽冥物語》《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初戀安妮》《逆旅》《洗》;散文《回來以後》《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一瞬之夢:我的中國紀行》《衣櫃裡的秘密旅行》;電影劇本《松鼠自殺事件》;學術論著《大虛構時代――當代台灣文學論》《情慾世紀末――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論 》等。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北教育大學語創系教授,熱愛旅行、潛水和帆船,並且多次將旅行、海洋和島嶼等化成為個人創作的主題。曾獲得金鼎獎、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獎、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及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獎等重要獎項。
著有小說《幽冥物語》《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初戀安妮》《逆旅》《洗》;散文《回來以後》《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一瞬之夢:我的中國紀行》《衣櫃裡的秘密旅行》;電影劇本《松鼠自殺事件》;學術論著《大虛構時代――當代台灣文學論》《情慾世紀末――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論 》等。
序
【推薦序】
長溝流月的那些夏天
◎廖咸浩(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外文系特聘教授)
要為一本寫北投的書寫序,好像應該並不難,因為你在北投待過三年。然而,卻正是因為這三年的經驗,讓你在看這本書的過程中,對你的「北投」經驗產生了始料未及的沉思。
你不能說你對北投很熟悉,因為你在北投「只」待過三年。但話又說了回來,這三年是你的青春期的開始,而讓你覺得北投似乎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人生的開始。
你與北投是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情況下結的緣。你分明在萬里這個漁村出生並念完小學,理所當然的,基隆才應該是你青春期躁動的所在。然而一件很微小的一件事改變了你與整個北海岸的關係,十二歲那年從向東遠眺(去基隆的路上你總是暈車甚至嘔吐,而覺得旅程極遠)轉向了西偏西南,然後再經過一個大轉彎,而來到了北投。
事情起因於父親已預知將自萬里調動到其他城鎮而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為你報考了一所未來任職所在地的縣中。當你知悉之後氣急敗壞地拒絕了父親的安排。因為十二歲行將小學畢業的你,心中念茲在茲就是要考上省立基隆中學;縣中是無法想像的降格以求。你氣急敗壞地在報紙上無頭蒼蠅般地尋找,竟在各地聯招都已經截止報名的情況下,發現北投區聯招延長報名一天,而且更重要的是,參與聯招的中學竟有一所省中!因為你是長子,父親恐是因為第一個孩子考初中而不敢大意,甚至可能覺得他有所閃失過意不去,竟順從了你的執拗,並且立刻帶著你從萬里直奔北投――但萬萬沒想到的是該區聯招的第一志願竟是縣立北投初中!
經過這番周折而最終念的還是縣中,不能不說你跟北投是有著什麼不可解說的緣分,讓父親在這麼重大的決定上竟接受了你近乎無厘頭的要求,也讓你自己決定了自己的未來。
因此,你向來認為,北投對你而言不是一個意外,而是你自己的選擇。
到北投報名那天,父親帶著你經基隆到台北,再從台北轉北淡線去北投。里爾克曾說過,你來到一座城市的路徑決定了你對它的好惡。當年的北投固然從各方面來看都是個迷人的地方,但你是坐著北淡線火車來到北投,而對北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印象。
那時候的北淡線彷彿是一條走入歷史之外的祕密路徑,特別是淡水到石牌的這一段。那天,火車過了一條河不久,你就在窗上愈加扶疏的樹影中睡著了。醒來時火車剛好停在石牌站。窗外意外的沒有一絲蟬聲、沒有一抹人跡,只有樹影參差錯落,火車好像是停在一個靜止的夢境邊緣。遠處的水田中,一隻白鷺鷥單腳站立著,彷彿是夢境的守衛者,又宛如某種隱喻……這是你對廣義的北投的第一個印象。
一個月後來北投考試的前一晚,父親帶著你先到北投投宿。他特意選擇了在新北投火車站旁的「大屯旅館」,以便到考場方便。那是你第一次住旅店。從小和全家人睡在一大片硬榻榻米上,這是你第一次睡在旅店中過於柔軟的床上,聞著隱約的薰香氣息,竟覺得有如天堂的美好。第二天一早又在附近禪寺令人心安的誦經聲中悠悠醒來……你對北投的印象便如此定調了。
三年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每天早晨五點半就要從淡水的林子出發,到淡水轉火車,在舊北投下車後,再步行到溫泉路高處的校區。冬天常在凜凜的寒風中困頓推進。夏日早晨公路上又因遍布著壓死的蛇,腳踏車必須在新舊蛇屍中不斷迂迴轉進。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對當時的你而言,北投就是地球的中心。相較於你成長的漁村,或你當時居住的山村,在北投一切都在發生中。
但友誼、功課、藝術、運動等等能轉移青春期躁動的主題,都遠不如試圖填補一種莫名的渴望來得讓人神魂專注。你不知道在渴望什麼,但在任何孤獨的時刻,你卻是那麼強烈地感受到從某個深淵中汩汩升起的渴望。一直到第一次親手接過別人轉來的女生的信。你心中狂跳不止,且在拆開那封摺成方形的信時,手也在發抖,你才漸漸曉事。
然後,你發現了眷村,並短暫跟削薄了髮綹的留級生有些來往。但那一刻的來臨才是最終的啟示:你在一個長著鳳眼的旗手臉上,看到耀眼而眩目的光,從此你停止了盲目無緒的尋找,而在擔任升旗司儀的時候,因她在前方升旗,且身後樂隊的男生在談論她,而心中充塞著一種必須分享的飽滿……。你遂開始寫作。偶爾你還會特意坐新北投支線到北投站,不過是為了朝鐵路局宿舍多望幾眼……。
然而,北投是不屬於你的。每天你都必須再長途跋涉回到山村的居所,途中還要經過一個墓園。一回到家便有一種被拋出恆星軌道外的清冷。總覺得得之不易的光會會隨著長日將盡而熄滅。
在那三年之中,你雖然從來沒有和光源有真正的接觸,但經由光與暗不斷地反覆交替著,你覺得那已是長長的一生了。
雖然你深知人與地方的關係絕不只一種型態,也預期了任何人的北投經驗都會與你的甚為不同,但你一直認為你對北投的印象有一定的普世意義。因此,讀到郝譽翔寫的北投,書中那種你極不熟悉的反差,讓你對於經驗這類哲學議題必須重新思考。
郝譽翔的這本散文集(其實更像一本詩意的小說)的基底不外是抒情。但感傷中不斷纏繞頸項的糾結與困頓,及不時迸出腦頂的暴烈與絕望,比起一般的青春紀事殘酷許多。她是以一種近乎披肝瀝膽的細膩,無畏地呈現青春萌芽時期的苦楚與躁動。在其根基處的處境是:父親長期缺席卻又隔時帶來幸福的暗示,母親倉皇持家育女反成為女兒必須馱載的重負。這種交織互迫的情緒所造就的抒情,便是因少女的應然無處得尋而產生。
但貫穿其間不絕如縷的鬼魅氣氛又特別引人躑躅紙面。不只是家附近的暗巷中賣麵的婦人,或遠處奔馳而過的列車,就連她參與群眾運動時親見的政治人物,不論被眾人歡樂抬起的青壯輩,或是空蕩著一支袖子的前行者,也都不免沾上了鬼氣。
然而,她筆下的鬼魅並不讓人畏懼,反而有一種特別的風情,既有聊齋的纏綿也有赫塞的惆悵。鬼即是人,甚至人不如鬼。因此,鬼魅之氣更可能是一種對峙於人不如鬼的演出,一種對平庸現實的報復。窮困是一種平庸,富裕也是一種平庸,唱歌五音不全是一種平庸,繪畫比賽得獎也是一種平庸。追根究柢如何才能臻至不平庸? 因此在書中鬼魅之氣其實另有一種渡河逃世的絕美之姿。
顯然,對郝譽翔而言,北投彷彿是一個巨大的囚籠,她必須以時而乖張時而自傷的暴虐敲打籠子的鋼欄,彷彿敲得夠大聲,就能脫困。這樣艱困的成長,在近半百時回顧,卻仍是那麼蒼白慘綠,且對於失落的青春是否曾播下什麼種子,亦未有明確主張。似乎,只有不時出現的山與海才算座落在囚籠之外。
然而,囚籠的鬼魅之氣並無法掩蓋全書的另一種既交織又逆向於前者的日常想望,雖然只是很罕見地在賣臭豆腐的退伍老兵身上看到:「他總是笑得燦爛,把生氣帶進了這一座死氣沉沉的小城,就像是在理直氣壯地說乾坤朗朗,歲月靜好,所以能在這兒賣上一鍋熱氣騰騰的臭豆腐,也是人生難得的福氣。」連老兵姓顏都覺得「未免太好,一如他明亮的笑臉」。但即使這麼接近一種簡單的幸福感,郝譽翔仍然逞強似地以吃大辣來確保幸福不會中止。吃大辣或許只是為了老顏一句像父親般縱容的驚嘆。
那種辣是在傷口上設法加料改造的企圖吧?顯然時間也無法讓嗜辣者的汗水慢慢止息,因為時間只藏在每個人的心中,而且可能是多重並行的。如作是觀,寫作這本書或許就是一種對嗜辣的告別?對心中時間的某條伏流的告別?
但同樣是青春的體悟,何以你對北投的明亮卻感覺如此強烈?也許不只是因為第一次的北投經驗發生在夏天,而更可能是你所來自的漁村處處都有著鬼魅的蹤跡。竹林子裡每根竹子都是鬼。只要是大石頭後面必藏著鬼。河對岸的墓園更是鬼影幢幢;偶爾有人家的爸爸不知是喝醉了還是其他原因在大聲囈語著,旁邊圍觀的人也要強調他是被「彼邊港」的魔神仔煞
到。而那些在林投樹之間拿著劍圍著篝火跳躍的道士就更是為了驅鬼了。鬼魅至極的則是從市街上小布爾喬亞商家鋪天蓋地而來的日本演歌;那種長期困在土俗情調中的鬼魅曲風,則讓你幾近窒息。由是,北淡線,特別是北投石牌一帶終於讓你喘了一口氣。因為這裡是如此的明亮安靜。
因此,於你有驅鬼意義的北投,在她筆下竟是鬼魅湧現的所在。然而你也很難說你自己的體悟不夠真實,只是遇見北投的方式不同吧。或更進一步地說,北投從來也沒有不變的存在;它只存在於每個人與特定時間點的它交會的剎那,事後的殘留消失得更快,馴至了無痕跡。你好奇的是,在那交會的剎那,到底是你們各自選擇了北投,還是北投撞見了你們?
恐龍的滅絕據說是因為太陽撞上一片薄薄的暗物質,而造成了地球的大災難。在從的里雅斯特去威尼斯的火車上,你讀到這段文字。你抬頭不經意地看了看對面座位上閉目養神的女子。她與你坐得這麼近,但卻可以與你或這段文字無關。然而是否也可能因為與暗物質的偶然擦身,而在那一刻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宇宙尺度的變化?因此不同的北投經驗會不會都是諸如暗物質造成的,而可能只是純粹的機遇? 當然一切也可能都緣於某種宇宙尺度的全像投影?甚至都已寫定在阿卡西紀錄中?如此,表面的機遇便只是命定的軌跡?
這種純後設的想像讓不少人安心,但也讓少數人覺得沮喪,特別是作家。作家的意義何在? 只是訊息的發現者,或應是訊息的實現者?你分明認為是自己主動地選擇了北投,難道這只是假象?時間只是一種一切都已命定而產生的幻覺?
你寧相信(且有所本)人在特定的時刻(如坐忘)是與宇宙完全相連的,因此,每個人的確都如全像投影理論的認知,擁有全宇宙的資訊。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切都已有定數,而是處於等待實現的潛勢。如此,人就不存在於時間中,而是不斷在創造時間。故最終客觀獨立的時間並不存在,一切都儲存於一個過去、現在與未來同時並存的平面。但所有的可能性都隱而未顯地在一個巨大而周行不止的變化(或曰「大化」)中鵠候,等待可能或不可能的實現。也許只有作家(及藝術家)願意嘗試,所謂嘔心瀝血吧。然而,最終作家能做的或只是一個微弱的動作,微弱卻依然可能有著宇宙尺度的影響。正如書中所言:「攀住了一個字,緊接著是下一個字,就像是在渡河。」雖然險惡,但也許在下一刻就到了捨舟登岸的時刻,也未可知。
因此,誰也不曾擁有北投,不但不曾擁有北投的時間,甚至難說曾擁有個別的北投事件。只有個人因為對那交會的剎那深入骨髓的銘刻有所不能割捨(不論那是愛或悲傷),所企圖進行的記憶建構,或更精確地說,時間的建構。做為作家,企圖建構的時間絕對不會是俗成的時間,而是前所未有的時間。不論是魑魅魍魎或無法直視的光都只是一個渡河的工具。一個從傷口中幻化成蝶的蛹。蝶遂因迷而誤入純粹時間而終不迷。
這麼說來,每個人都是有傷口的,或大或小,或深或淺。你也是帶著某種無名的傷口來到北投尋找光,而郝譽翔則是在北投被迫讓傷口擴大蔓延,馴至在黑暗中浮浮沉沉。
但有傷口是幸運的,尤其是一個近乎無法彌縫的傷口。因為傷口,才有記憶的捕捉與時間的創造。當那位在書中幾乎不存在的父親無端出現、給予了短暫而虛幻的幸福感後、忽而又棄她而去並「轉進一條小巷弄」消失無蹤的那一剎那,彼處或正有一扇卡夫卡的窄門突然打開。這時候就看郝譽翔用什麼角度看進窄門。找對角度,看到的就會是亞列夫,並在那微小的亮點上欣見整個宇宙。人世的一切便都可以原諒,也可以一再地重新開始。幽暗與明亮的輪替互生(chiaroscuro),從來也不會止息,更是生之頌歌的基調。
這篇序接近完成的時候,很意外夢見了初中時暗戀但卻從未說過話的少女旗手。她是來道別的,但夢中的道別覺得沒有感傷只有溫馨。依稀她對你說你已經不需要再藉助對她的想像掙脫那原初的傷口……。醒來時意識到自己已是獨自的一個人。
【後記】
收錄在這本散文集中的作品,大多原為《自由時報》副刊的專欄而寫,雖然成書之時經過全盤的修改,但若非當初素芬姊的邀稿,以及每兩週一次來自梓評的催促和鼓勵,否則我不會啟動這場回憶的文字之旅,故有此書的誕生都要感謝他們。
專欄名為「城北舊事」,乃因「北」之於我一直是憧憬與嚮往的方向,童年時代由高雄移居台北,乃至於落腳在北投,又可以說是台北城市之「北」,而那是一道青春的尋夢成長路徑:一路向北。
然而北投卻又非典型的台北。那是一座山與海所環繞的盆地邊陲小城,尤其在上個世紀的七〇和八〇年代,更像是大自然的野性搖籃,而非城市資本主義現代文明,這或許也造就了我的桀驁不馴。
我特別喜歡「桀驁不馴」這四個字,在城北生活多年下來,不知不覺中就長成了如此,也不知道是出於自己的本性呢? 還是來自於環境的薰陶?但我每每無事或憂傷之時,確實習慣性地就要逃入陽明山和淡海的懷抱,一如女巫被放逐於荒野。
書中也特別記錄了我曾瘋狂崇拜的偶像坂本龍一。最近看了他的紀錄片《終章》,卻半途按下了停止鍵不忍再看。白髮的他依然十分瀟灑優雅,然而見到他為病體所折磨之時,我卻不禁感到自己的青春也一併被蛀蝕崩毀了,淪為千瘡百孔的廢墟,而天人五衰,花冠頓萎。
也因此這本書於我意義更為深遠,唯有文字,才能夠永恆捕捉那些純潔而光燦的瞬間。我的城北歲月,一首由山與海交織而成的賦格曲。
我也特別喜歡「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這句話,出於我最愛的導演北野武的電影。我十四歲時看電影《俘虜》只注意坂本龍一,完全忘了還有北野武的存在,即使他才是真正貫穿全片的要角,直到十多年後我才發現,大有相見恨晚的遺憾。
早在台灣尚未引進北野武的電影前,我就透過重慶南路的錄影帶攤「秋海棠」,看了盜版的《花火》和《奏鳴曲》,深深被電影中反覆出現的海洋所吸引。後來也是在「秋海棠」買了《那年夏天,寧靜的海》,回家一看卻沒有字幕,於是又氣呼呼跑回重慶南路找老闆理論。
但老闆卻酷酷的,連頭也不抬,慢條斯理繼續整理著攤上的錄影帶,說:「為什麼需要字幕呢? 電影裡的男女主角都是啞巴啊,根本就沒開口說話。」
想想也對。在《那年夏天,寧靜的海》中說話的,都是一些不相干的路過之人,想必那些對白也不重要吧。後來有機會看了正版的DVD,果然真如老闆所言。
原來這就是我們真實的生活。無聲的動作,回憶的默片,為陽光所一點一滴推移,靜悄悄地在我們的眼前流逝,而其中藏匿著最深沉的哭泣、歡笑與耳語,也唯有自己才能夠聽見。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於台北
長溝流月的那些夏天
◎廖咸浩(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外文系特聘教授)
要為一本寫北投的書寫序,好像應該並不難,因為你在北投待過三年。然而,卻正是因為這三年的經驗,讓你在看這本書的過程中,對你的「北投」經驗產生了始料未及的沉思。
你不能說你對北投很熟悉,因為你在北投「只」待過三年。但話又說了回來,這三年是你的青春期的開始,而讓你覺得北投似乎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人生的開始。
你與北投是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情況下結的緣。你分明在萬里這個漁村出生並念完小學,理所當然的,基隆才應該是你青春期躁動的所在。然而一件很微小的一件事改變了你與整個北海岸的關係,十二歲那年從向東遠眺(去基隆的路上你總是暈車甚至嘔吐,而覺得旅程極遠)轉向了西偏西南,然後再經過一個大轉彎,而來到了北投。
事情起因於父親已預知將自萬里調動到其他城鎮而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為你報考了一所未來任職所在地的縣中。當你知悉之後氣急敗壞地拒絕了父親的安排。因為十二歲行將小學畢業的你,心中念茲在茲就是要考上省立基隆中學;縣中是無法想像的降格以求。你氣急敗壞地在報紙上無頭蒼蠅般地尋找,竟在各地聯招都已經截止報名的情況下,發現北投區聯招延長報名一天,而且更重要的是,參與聯招的中學竟有一所省中!因為你是長子,父親恐是因為第一個孩子考初中而不敢大意,甚至可能覺得他有所閃失過意不去,竟順從了你的執拗,並且立刻帶著你從萬里直奔北投――但萬萬沒想到的是該區聯招的第一志願竟是縣立北投初中!
經過這番周折而最終念的還是縣中,不能不說你跟北投是有著什麼不可解說的緣分,讓父親在這麼重大的決定上竟接受了你近乎無厘頭的要求,也讓你自己決定了自己的未來。
因此,你向來認為,北投對你而言不是一個意外,而是你自己的選擇。
到北投報名那天,父親帶著你經基隆到台北,再從台北轉北淡線去北投。里爾克曾說過,你來到一座城市的路徑決定了你對它的好惡。當年的北投固然從各方面來看都是個迷人的地方,但你是坐著北淡線火車來到北投,而對北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印象。
那時候的北淡線彷彿是一條走入歷史之外的祕密路徑,特別是淡水到石牌的這一段。那天,火車過了一條河不久,你就在窗上愈加扶疏的樹影中睡著了。醒來時火車剛好停在石牌站。窗外意外的沒有一絲蟬聲、沒有一抹人跡,只有樹影參差錯落,火車好像是停在一個靜止的夢境邊緣。遠處的水田中,一隻白鷺鷥單腳站立著,彷彿是夢境的守衛者,又宛如某種隱喻……這是你對廣義的北投的第一個印象。
一個月後來北投考試的前一晚,父親帶著你先到北投投宿。他特意選擇了在新北投火車站旁的「大屯旅館」,以便到考場方便。那是你第一次住旅店。從小和全家人睡在一大片硬榻榻米上,這是你第一次睡在旅店中過於柔軟的床上,聞著隱約的薰香氣息,竟覺得有如天堂的美好。第二天一早又在附近禪寺令人心安的誦經聲中悠悠醒來……你對北投的印象便如此定調了。
三年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每天早晨五點半就要從淡水的林子出發,到淡水轉火車,在舊北投下車後,再步行到溫泉路高處的校區。冬天常在凜凜的寒風中困頓推進。夏日早晨公路上又因遍布著壓死的蛇,腳踏車必須在新舊蛇屍中不斷迂迴轉進。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對當時的你而言,北投就是地球的中心。相較於你成長的漁村,或你當時居住的山村,在北投一切都在發生中。
但友誼、功課、藝術、運動等等能轉移青春期躁動的主題,都遠不如試圖填補一種莫名的渴望來得讓人神魂專注。你不知道在渴望什麼,但在任何孤獨的時刻,你卻是那麼強烈地感受到從某個深淵中汩汩升起的渴望。一直到第一次親手接過別人轉來的女生的信。你心中狂跳不止,且在拆開那封摺成方形的信時,手也在發抖,你才漸漸曉事。
然後,你發現了眷村,並短暫跟削薄了髮綹的留級生有些來往。但那一刻的來臨才是最終的啟示:你在一個長著鳳眼的旗手臉上,看到耀眼而眩目的光,從此你停止了盲目無緒的尋找,而在擔任升旗司儀的時候,因她在前方升旗,且身後樂隊的男生在談論她,而心中充塞著一種必須分享的飽滿……。你遂開始寫作。偶爾你還會特意坐新北投支線到北投站,不過是為了朝鐵路局宿舍多望幾眼……。
然而,北投是不屬於你的。每天你都必須再長途跋涉回到山村的居所,途中還要經過一個墓園。一回到家便有一種被拋出恆星軌道外的清冷。總覺得得之不易的光會會隨著長日將盡而熄滅。
在那三年之中,你雖然從來沒有和光源有真正的接觸,但經由光與暗不斷地反覆交替著,你覺得那已是長長的一生了。
雖然你深知人與地方的關係絕不只一種型態,也預期了任何人的北投經驗都會與你的甚為不同,但你一直認為你對北投的印象有一定的普世意義。因此,讀到郝譽翔寫的北投,書中那種你極不熟悉的反差,讓你對於經驗這類哲學議題必須重新思考。
郝譽翔的這本散文集(其實更像一本詩意的小說)的基底不外是抒情。但感傷中不斷纏繞頸項的糾結與困頓,及不時迸出腦頂的暴烈與絕望,比起一般的青春紀事殘酷許多。她是以一種近乎披肝瀝膽的細膩,無畏地呈現青春萌芽時期的苦楚與躁動。在其根基處的處境是:父親長期缺席卻又隔時帶來幸福的暗示,母親倉皇持家育女反成為女兒必須馱載的重負。這種交織互迫的情緒所造就的抒情,便是因少女的應然無處得尋而產生。
但貫穿其間不絕如縷的鬼魅氣氛又特別引人躑躅紙面。不只是家附近的暗巷中賣麵的婦人,或遠處奔馳而過的列車,就連她參與群眾運動時親見的政治人物,不論被眾人歡樂抬起的青壯輩,或是空蕩著一支袖子的前行者,也都不免沾上了鬼氣。
然而,她筆下的鬼魅並不讓人畏懼,反而有一種特別的風情,既有聊齋的纏綿也有赫塞的惆悵。鬼即是人,甚至人不如鬼。因此,鬼魅之氣更可能是一種對峙於人不如鬼的演出,一種對平庸現實的報復。窮困是一種平庸,富裕也是一種平庸,唱歌五音不全是一種平庸,繪畫比賽得獎也是一種平庸。追根究柢如何才能臻至不平庸? 因此在書中鬼魅之氣其實另有一種渡河逃世的絕美之姿。
顯然,對郝譽翔而言,北投彷彿是一個巨大的囚籠,她必須以時而乖張時而自傷的暴虐敲打籠子的鋼欄,彷彿敲得夠大聲,就能脫困。這樣艱困的成長,在近半百時回顧,卻仍是那麼蒼白慘綠,且對於失落的青春是否曾播下什麼種子,亦未有明確主張。似乎,只有不時出現的山與海才算座落在囚籠之外。
然而,囚籠的鬼魅之氣並無法掩蓋全書的另一種既交織又逆向於前者的日常想望,雖然只是很罕見地在賣臭豆腐的退伍老兵身上看到:「他總是笑得燦爛,把生氣帶進了這一座死氣沉沉的小城,就像是在理直氣壯地說乾坤朗朗,歲月靜好,所以能在這兒賣上一鍋熱氣騰騰的臭豆腐,也是人生難得的福氣。」連老兵姓顏都覺得「未免太好,一如他明亮的笑臉」。但即使這麼接近一種簡單的幸福感,郝譽翔仍然逞強似地以吃大辣來確保幸福不會中止。吃大辣或許只是為了老顏一句像父親般縱容的驚嘆。
那種辣是在傷口上設法加料改造的企圖吧?顯然時間也無法讓嗜辣者的汗水慢慢止息,因為時間只藏在每個人的心中,而且可能是多重並行的。如作是觀,寫作這本書或許就是一種對嗜辣的告別?對心中時間的某條伏流的告別?
但同樣是青春的體悟,何以你對北投的明亮卻感覺如此強烈?也許不只是因為第一次的北投經驗發生在夏天,而更可能是你所來自的漁村處處都有著鬼魅的蹤跡。竹林子裡每根竹子都是鬼。只要是大石頭後面必藏著鬼。河對岸的墓園更是鬼影幢幢;偶爾有人家的爸爸不知是喝醉了還是其他原因在大聲囈語著,旁邊圍觀的人也要強調他是被「彼邊港」的魔神仔煞
到。而那些在林投樹之間拿著劍圍著篝火跳躍的道士就更是為了驅鬼了。鬼魅至極的則是從市街上小布爾喬亞商家鋪天蓋地而來的日本演歌;那種長期困在土俗情調中的鬼魅曲風,則讓你幾近窒息。由是,北淡線,特別是北投石牌一帶終於讓你喘了一口氣。因為這裡是如此的明亮安靜。
因此,於你有驅鬼意義的北投,在她筆下竟是鬼魅湧現的所在。然而你也很難說你自己的體悟不夠真實,只是遇見北投的方式不同吧。或更進一步地說,北投從來也沒有不變的存在;它只存在於每個人與特定時間點的它交會的剎那,事後的殘留消失得更快,馴至了無痕跡。你好奇的是,在那交會的剎那,到底是你們各自選擇了北投,還是北投撞見了你們?
恐龍的滅絕據說是因為太陽撞上一片薄薄的暗物質,而造成了地球的大災難。在從的里雅斯特去威尼斯的火車上,你讀到這段文字。你抬頭不經意地看了看對面座位上閉目養神的女子。她與你坐得這麼近,但卻可以與你或這段文字無關。然而是否也可能因為與暗物質的偶然擦身,而在那一刻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宇宙尺度的變化?因此不同的北投經驗會不會都是諸如暗物質造成的,而可能只是純粹的機遇? 當然一切也可能都緣於某種宇宙尺度的全像投影?甚至都已寫定在阿卡西紀錄中?如此,表面的機遇便只是命定的軌跡?
這種純後設的想像讓不少人安心,但也讓少數人覺得沮喪,特別是作家。作家的意義何在? 只是訊息的發現者,或應是訊息的實現者?你分明認為是自己主動地選擇了北投,難道這只是假象?時間只是一種一切都已命定而產生的幻覺?
你寧相信(且有所本)人在特定的時刻(如坐忘)是與宇宙完全相連的,因此,每個人的確都如全像投影理論的認知,擁有全宇宙的資訊。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切都已有定數,而是處於等待實現的潛勢。如此,人就不存在於時間中,而是不斷在創造時間。故最終客觀獨立的時間並不存在,一切都儲存於一個過去、現在與未來同時並存的平面。但所有的可能性都隱而未顯地在一個巨大而周行不止的變化(或曰「大化」)中鵠候,等待可能或不可能的實現。也許只有作家(及藝術家)願意嘗試,所謂嘔心瀝血吧。然而,最終作家能做的或只是一個微弱的動作,微弱卻依然可能有著宇宙尺度的影響。正如書中所言:「攀住了一個字,緊接著是下一個字,就像是在渡河。」雖然險惡,但也許在下一刻就到了捨舟登岸的時刻,也未可知。
因此,誰也不曾擁有北投,不但不曾擁有北投的時間,甚至難說曾擁有個別的北投事件。只有個人因為對那交會的剎那深入骨髓的銘刻有所不能割捨(不論那是愛或悲傷),所企圖進行的記憶建構,或更精確地說,時間的建構。做為作家,企圖建構的時間絕對不會是俗成的時間,而是前所未有的時間。不論是魑魅魍魎或無法直視的光都只是一個渡河的工具。一個從傷口中幻化成蝶的蛹。蝶遂因迷而誤入純粹時間而終不迷。
這麼說來,每個人都是有傷口的,或大或小,或深或淺。你也是帶著某種無名的傷口來到北投尋找光,而郝譽翔則是在北投被迫讓傷口擴大蔓延,馴至在黑暗中浮浮沉沉。
但有傷口是幸運的,尤其是一個近乎無法彌縫的傷口。因為傷口,才有記憶的捕捉與時間的創造。當那位在書中幾乎不存在的父親無端出現、給予了短暫而虛幻的幸福感後、忽而又棄她而去並「轉進一條小巷弄」消失無蹤的那一剎那,彼處或正有一扇卡夫卡的窄門突然打開。這時候就看郝譽翔用什麼角度看進窄門。找對角度,看到的就會是亞列夫,並在那微小的亮點上欣見整個宇宙。人世的一切便都可以原諒,也可以一再地重新開始。幽暗與明亮的輪替互生(chiaroscuro),從來也不會止息,更是生之頌歌的基調。
這篇序接近完成的時候,很意外夢見了初中時暗戀但卻從未說過話的少女旗手。她是來道別的,但夢中的道別覺得沒有感傷只有溫馨。依稀她對你說你已經不需要再藉助對她的想像掙脫那原初的傷口……。醒來時意識到自己已是獨自的一個人。
【後記】
收錄在這本散文集中的作品,大多原為《自由時報》副刊的專欄而寫,雖然成書之時經過全盤的修改,但若非當初素芬姊的邀稿,以及每兩週一次來自梓評的催促和鼓勵,否則我不會啟動這場回憶的文字之旅,故有此書的誕生都要感謝他們。
專欄名為「城北舊事」,乃因「北」之於我一直是憧憬與嚮往的方向,童年時代由高雄移居台北,乃至於落腳在北投,又可以說是台北城市之「北」,而那是一道青春的尋夢成長路徑:一路向北。
然而北投卻又非典型的台北。那是一座山與海所環繞的盆地邊陲小城,尤其在上個世紀的七〇和八〇年代,更像是大自然的野性搖籃,而非城市資本主義現代文明,這或許也造就了我的桀驁不馴。
我特別喜歡「桀驁不馴」這四個字,在城北生活多年下來,不知不覺中就長成了如此,也不知道是出於自己的本性呢? 還是來自於環境的薰陶?但我每每無事或憂傷之時,確實習慣性地就要逃入陽明山和淡海的懷抱,一如女巫被放逐於荒野。
書中也特別記錄了我曾瘋狂崇拜的偶像坂本龍一。最近看了他的紀錄片《終章》,卻半途按下了停止鍵不忍再看。白髮的他依然十分瀟灑優雅,然而見到他為病體所折磨之時,我卻不禁感到自己的青春也一併被蛀蝕崩毀了,淪為千瘡百孔的廢墟,而天人五衰,花冠頓萎。
也因此這本書於我意義更為深遠,唯有文字,才能夠永恆捕捉那些純潔而光燦的瞬間。我的城北歲月,一首由山與海交織而成的賦格曲。
我也特別喜歡「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這句話,出於我最愛的導演北野武的電影。我十四歲時看電影《俘虜》只注意坂本龍一,完全忘了還有北野武的存在,即使他才是真正貫穿全片的要角,直到十多年後我才發現,大有相見恨晚的遺憾。
早在台灣尚未引進北野武的電影前,我就透過重慶南路的錄影帶攤「秋海棠」,看了盜版的《花火》和《奏鳴曲》,深深被電影中反覆出現的海洋所吸引。後來也是在「秋海棠」買了《那年夏天,寧靜的海》,回家一看卻沒有字幕,於是又氣呼呼跑回重慶南路找老闆理論。
但老闆卻酷酷的,連頭也不抬,慢條斯理繼續整理著攤上的錄影帶,說:「為什麼需要字幕呢? 電影裡的男女主角都是啞巴啊,根本就沒開口說話。」
想想也對。在《那年夏天,寧靜的海》中說話的,都是一些不相干的路過之人,想必那些對白也不重要吧。後來有機會看了正版的DVD,果然真如老闆所言。
原來這就是我們真實的生活。無聲的動作,回憶的默片,為陽光所一點一滴推移,靜悄悄地在我們的眼前流逝,而其中藏匿著最深沉的哭泣、歡笑與耳語,也唯有自己才能夠聽見。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於台北
目次
推薦序 長溝流月的那些夏天◎廖咸浩
推薦語 ◎吳鈞堯、林文義、邱坤良、施昇輝、孫梓評、鄭如晴、盧美杏
在山與海的交界
野性水城
山上有靈
故事的端倪
遙遠的國度
那條彎彎曲曲的鐵路
非我族類
深夜裡的廣播劇
無辣不歡
外面的世界
青春惘惘
暴雨將至
桀驁不馴
那正在街頭燃燒的一切
衝浪般的狂歡
神魔之地
一個人的椰林大道
一九九一年之夏
二十四歲離家遠行
著魔的月圓之夜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後記
推薦語 ◎吳鈞堯、林文義、邱坤良、施昇輝、孫梓評、鄭如晴、盧美杏
在山與海的交界
野性水城
山上有靈
故事的端倪
遙遠的國度
那條彎彎曲曲的鐵路
非我族類
深夜裡的廣播劇
無辣不歡
外面的世界
青春惘惘
暴雨將至
桀驁不馴
那正在街頭燃燒的一切
衝浪般的狂歡
神魔之地
一個人的椰林大道
一九九一年之夏
二十四歲離家遠行
著魔的月圓之夜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後記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一】
在山與海的交界
早晨一睜開雙眼,所見到的竟全是山,峰與峰之間錯落相連,直到天邊。
但山巒的顏色並不翠綠,就像是被誰兜頭潑了一盆冷水似的,淋漓灰青,又像是淚水幽幽滲出了紙端,教人看了只是莫名地一怔。
所以這哪裡能算得上是城市呢? 或許因為如此,我總是堅持說自己是「北投人」,而不是「台北人」。
也或許是,北投原來就不屬於台北。
清朝時,北投歸於淡水廳的管轄,日治時期又以大屯山系的最高峰「七星山」為名,劃入了七星郡。這一帶向來就是山高水遠,自成一處化外之地,我因此愛淡水和七星之名,遠遠勝過於台北。
♦
北投正式被納入台北市的範圍,竟是遲至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的事了。
但即使如此,當一九七五年我們全家人從高雄北上,落腳在北投之時,住家的附近卻仍然多是一派農村的恬淡氛圍,而日常生活中所慣見到的風景,也大多是蒼茫無邊的淡水河以及關渡平原,總是讓我不禁聯想到「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之類的詩句,和現代化的城市根本沾不上邊。
也或許我只是不明白,所謂的城市究竟應該是什麼模樣?
來到北投的那一年我才七歲,先前只是一個懞懂的孩子,回憶起來,在高雄的日子唯有窗外周而復始的日升日落,歲月無聲無息地滑過,就像是一部靜默的黑白電影,竟想不出有什麼悲哀和歡喜可言。
但來到北投以後世界卻大不相同了。陌生的異鄉忽然跳出了顏色、聲音和氣味,強烈的光影不安地閃爍著,躁動著,讓我驚怯睜大了眼,惶惶不知所措。我開始懷念起高雄那份明亮到過分純粹的陽光了,乾燥無雨的天氣,空中總是白雲朗朗,以及左營鄉下外婆家的磨石子地面,即便是在炎炎的夏日赤腳踩上去,也是傳來一股透澈心肺的冰涼。
然而這一切全都消失無蹤了。
就連高雄鄰居皮鞋店和我同年紀的小女孩,天天一起結伴上學玩耍,我卻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和長相了,只剩下一團朦朧的黑影。反倒是她家店門口擺在玻璃櫃中的一排黑色男鞋,始終令我印象深刻。在無人的午後陽光籠罩之下,它們顯得既無助又徬徨,彷彿困惑著不知道下一步該要走向何方?
那些皮鞋還在玻璃櫃中等待著未知的主人,但我卻已經提早一步先行離開了。搬家那天,我坐上了載滿舊家具的卡車,準備一路搖搖晃晃地北上。鄰居小女孩就坐在皮鞋店前的小圓凳上,望著我,遲疑地揮了揮手。
那是道別的手勢,從此不復得見。
我想我必然是哭了。遷徙是啟蒙的開始,我的生命將要退回到一片空白的原點,重新來過一遍。我沉默地抵抗著,為注定即將失去的一切流下了絕望的淚水。但這有什麼用呢? 又有誰會覺得孩子的眼淚是珍貴的?
♦
接近傍晚的時分,搬家卡車終於來到了尊賢街,那是我們在北投的第一個住家。夕陽昏黃的餘暉鋪滿了巷子兩側的公寓,映襯得一樓鐵門的朱紅油漆更加斑駁,像是誤闖入一齣未老先衰的夢境,黯然得教人心驚。
後來,我們多半把那一帶稱之為「石牌」,而認為更往北走越過公館路以後才能夠算是北投。但「石牌」這兩個字總是讓我覺得又硬又冷,像是鐫刻著某種權威話語的石碑,神聖而不可侵犯,並不存在一絲一毫可以妥協的柔軟空間。
果然那附近也大多是些道德意味濃厚的街名,從「尊賢」、「實踐」、「明德」、「自強」到「立農」,再再向我們訓示著一種理想崇高的人格。
這些街名雖然取得堂皇,卻也多是些狹窄的尋常巷弄罷了,以柏油瀝青鋪成,縱橫交錯,切割出來一大片六〇年代以後才在台北街頭大量湧現,清一色是灰色洗石子牆的四層樓公寓。它們的造型方正,中規中矩,一如居住在其中的也大多是些勤勉樸實而面容拘謹的軍公教人員。
我們在尊賢街只住不到短短的兩年,又改搬到實踐街去。就像蒼蠅飛起在空中盤旋數圈之後,總會固執地又要落回原點,日後我們就在這些巷弄之間搬來搬去的,而新舊的住處往往不出三百公尺遠。
也是要等到多年以後,我才恍然大悟「實踐」之名的源頭,竟是因為街尾有一座國民黨專門訓練高階軍官的「實踐學社」,前身還是日本帝國陸軍的軍事顧問組織「白團」。
我從未意識到,原來住家的附近就隱藏著一個如此神祕的軍事組織?只知道實踐街口確實終年瀰漫著一股令人敬畏的氣息。那是四棟中央社的宿舍,同樣是低調的灰色公寓,我每天上學放學都必定會打門口經過,得以窺見出入在其中的社員。他們大多身穿白襯衫手提黑色的公事包,低著頭行色匆匆,彷彿包裡裝的全是一些不可洩漏的天機。
這就是我所認知的石牌。
至於北投,還要落在更遠之處,那朝向地平線盡頭綿延的大屯山脈,終年飄散著青白的山嵐和硫磺煙霧,以及更遠的淡水,日復一日向這片陸地送來海洋鹹濕的氣息,彷彿以一個更加遼闊而美的世界在殷殷召喚著我。
那是山與海混沌的交界,夜與夢的黑洞,我生命中最初讀到的一首詩,句句都是命運的隱喻,讓我不禁悠然神往,卻又每每悵然若失於它是如此的晦澀不可解。
【內文試閱二】
那正在街頭燃燒的一切
關於八〇年代,我特別記得的就是一九八七年,並不是因為台灣解嚴──我還沒有如此巨大的歷史感,而是那一年我恰好高三,畢業前夕教官突然在朝會上宣布:因為解嚴,學校的髮禁也一併宣告解除,從現在起你們可以把頭髮留長了。
雖然搞不清楚戒嚴和髮禁究竟有什麼關係?但對於十八歲的女孩而言,頭髮之事非同小可,念茲在茲,操場上爆出歡聲雷動,大家感動得相擁幾乎掉下熱淚。只可惜畢業在即,頭髮又不能在一瞬之間留長,我們只好跑到美容院去把頭髮削得更薄更短,一種當時最流行的羽毛剪,也算是以頭髮來宣告了解嚴之後的自主權。
所以解嚴是從自己的身體開始的,接下來才輪到了大腦。
七月揮汗如雨考完了聯考,我把高中三年下來累積的教科書一頁頁撕開,本來想放一把火將它們燒得精光,才算是壯烈,後來又嫌麻煩,乾脆全扔給垃圾車運走,不但毫無留戀之情,還有如釋重負的快樂,卻又不免詫異著自己居然可以痛恨知識到這種地步。
於是就這樣稀里糊塗畢了業,我從聯考的桎梏中解脫,也脫下高中三年身上那襲一陳不變的白衣黑裙,從此青春的小鳥拍拍翅膀飛出牢籠,自由自在海闊天空,哪裡還有時間回顧?
只記得為高中生涯劃下句點的,不是畢業典禮,而是體育老師帶我們去石門水庫露營。他是台灣赤足滑水的國手,特地要在我們這群女孩前大顯一番身手,只見他光著雙腳被一艘白色快艇拖著,輕功水上飄似的快速從藍綠色的湖水上掠過,濺出了一道道驚人的水花,現出繽紛而迷離的七彩虹暈,彷彿是我們一場告別青春的成年禮。
就在那天傍晚我和K共划一艘木舟,一直划入石門水庫的最深處。K是我高中三年最要好的同學,相較於我的急躁粗心,她總是溫柔而嫻靜。黃昏時分環湖四周的林蔭幽幽,我一不小心手一滑,木槳居然掉落水中,沒幾秒就直直沉到湖底。
沒了槳,要如何把船划回岸去?我只好急著向碼頭上的同學招手求救,也不知道她們到底有沒有看見?夕陽西下,山裡的天色迅速轉暗,只見岸上遙遙的燈光閃爍,傳來隱約的笑語,卻都被湖水一一吞沒,而四下靜悄悄地只聽得見我和K的呼吸。
百年修得同船渡。所以我和K真是有緣,但不知是緣深還是緣淺?當時的我們渾然不知十多年過後,K會喪生於高速公路上的一場客運大火。
我卻始終清晰地記得,那天石門水庫所蕩漾著夢幻般的紫藍色光影,映照她一雙深邃又烏黑的大眼,而我在K的眼裡看見了自己:同樣是十八歲,同樣對於即將迎來的大學生涯充滿了樂觀期待。我們於是忘了對未來本該有的忐忑與不安,就在那一年的九月分手,迫不及待飛往了各自的校園。
♦
日後屬於我的這一世代經常被稱之為「學運世代」。
這個標籤難免以偏概全,卻也多少具有某種程度的準確,因為就算我們不是學運中的一分子,也必定是一個旁觀者或是路過之人,而在有意無意之中對於運動有了深淺不一的涉入。
尤其我讀的又是台大政治系,這是我在大學聯考填下的第一志願,如今回頭再看這個選擇未免有點古怪,卻都該歸咎於八〇年代成功的黨國教育,使我到了十八歲卻依然懷抱著一種天真到近乎愚騃的理想,以為一個有志的青年就該從政報效國家。
當我果真如願以償進入了政治系,所經歷到的第一次震撼洗禮就是學生會長選舉,如火如荼在校園中展開。那其實也不過是一場學生級的選舉罷了,但兩位候選人的背後卻有不同的政黨在支持,彼此之間廝殺激烈,謠言耳語不斷,黑函和黑金滿天飛,儼然已經是一個社會選舉的小小雛形。
才剛從漫長威權年代之中掙脫出來的我們,形同是一群民主的新生兒,還停留在牙牙學語的階段,又如何能夠懂得文明的規範? 於是選舉時一拚鬥起來,就不免原形畢露,全淪為了一隻隻齜牙咧嘴的野獸。
我這才發現自己是何等的幼稚和愚蠢,原來政治不是青年報效國家的浪漫理想,而是血淋淋的權力運作。大一的必修課是政治學,教授在黑板上寫得密密麻麻,我拚命地抄著筆記,卻都是紙上談兵。一整年的課堂下來我只記得一句話:「政治就是眾人的利益分配」,而其餘全都還給了教授忘得一乾二淨。
♦
原來說到底,政治無關個人的理想和犧牲奉獻,而是眾人的利益分配。
我腦筋卻一時運轉不過來,就這樣茫茫然度過了新鮮人的一年,聽學長姊說社團才是大學的必修學分,便嘗試去造訪一些頗為活躍的學運社團如大新社、大陸社和大傳社,卻多半是躲在角落,默默聆聽那些嘴裡叼著香菸、腳趿藍白拖的社團老骨頭們口沫橫飛。
後來又在同學的慫恿下參加了一些服務性社團,這是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的產物,來到八〇年代在台大的校園仍屬主流。但我依然不免懷疑上山下海走入偏鄉,除了造就一個熱情滿滿的暑假之外,究竟是在服務自己?還是服務別人?
當年流行學者從政,政治系有幾位留學歸國的年輕老師投入選舉,我也自告奮勇到競選總部幫忙,成為學生助選員之一,沒日沒夜站在街頭發傳單,綁布條,插旗子。我還在學長的指導下模仿海德公園的「演說之角」(Speakers' Corner),也搬了一張小圓凳拿起擴音器,就站在北投的黃昏市場前拉票演說。
但我一站上去才發現凳子居然有這麼高? 眼見底下一大片黑壓壓的頭顱洶湧,雙腿就忍不住發抖,聽到自己的聲音從擴音器中傳出來,更是尖銳刺耳得陌生,反倒能聽得一清二楚的,是從夜市傳來人們吃吃的嘲笑聲。
一個大學生究竟是否知道得比一個賣菜的攤販還多? 我連自己都沒辦法說服了,更何況是他人? 我成了一個徹底的懷疑論者,對於那些堂而皇之的宣言或口號,不管是來自哪一方的,我都懷疑。
想像之中的浪漫青年,來到現實竟成了一個行動上的侏儒。
原來我根本不適合吃政治和選舉這行飯,相較於站在舞台上,我更喜歡當一個台下的觀眾,隱身於茫茫的人海之中,只在一旁觀察,而不會輕易地站起身來介入。
幸好八〇年代末的台北街頭,尤其是我居住的北投更是黨外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幾乎天天都在上演集會遊行和大大小小的政見發表會,到處都是可以湊熱鬧的政治嘉年華,而那才是活生生的教室,比起大學課堂不知有趣幾百倍。
這時對岸也恰好爆發六四天安門學運,我們每天一進教室,就和同學熱切傳閱報紙上的新聞,以為這正是二十世紀關鍵性的一刻,而歷史即將就要全盤改寫。但年輕的我們又怎麼能夠預知,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場運動卻幾乎被人遺忘消失?
然而我仍記得當時因蓬萊島案坐牢而出獄的陳水扁,在北投走進某間中學操場的政見發表會時,被民眾高高扛在肩頭上,有如神降人世一般穿過人群,接受成千上萬民眾膜拜歡呼的光榮,讓整個夜都因此熊熊地燃燒沸騰。
我甚至有好幾次走到政見會的台前,以最虔誠而且神聖的心,掏出一個大學生口袋中僅有的紙鈔,鄭重地把它們投入捐款箱。
我甚至握過台獨教父的手,而他的另一隻手在二次大戰中被炸斷,始終藏在西裝褲的口袋中。
我家附近也常有封街演講,人潮塞滿了整條巷子幾乎見不到盡頭。我擠在隊伍中拚命踮起腳尖,才勉強瞧見以美麗島事件辯護而聞名的律師,正站在木板臨時搭出來的簡陋講台上,用激動的語氣搭配誇張的手勢演說。
我已經完全忘了他說些什麼?但那似乎不重要,反而是街道兩旁高高懸起的昏黃燈泡,照耀著不安蠕動的人們,有如黑夜的大海暗潮洶湧卻又金波蕩漾。那是星星點點的革命之火,正在翻滾醞釀著,只等待風起,火勢就足以一路延燒燎原。
在山與海的交界
早晨一睜開雙眼,所見到的竟全是山,峰與峰之間錯落相連,直到天邊。
但山巒的顏色並不翠綠,就像是被誰兜頭潑了一盆冷水似的,淋漓灰青,又像是淚水幽幽滲出了紙端,教人看了只是莫名地一怔。
所以這哪裡能算得上是城市呢? 或許因為如此,我總是堅持說自己是「北投人」,而不是「台北人」。
也或許是,北投原來就不屬於台北。
清朝時,北投歸於淡水廳的管轄,日治時期又以大屯山系的最高峰「七星山」為名,劃入了七星郡。這一帶向來就是山高水遠,自成一處化外之地,我因此愛淡水和七星之名,遠遠勝過於台北。
♦
北投正式被納入台北市的範圍,竟是遲至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的事了。
但即使如此,當一九七五年我們全家人從高雄北上,落腳在北投之時,住家的附近卻仍然多是一派農村的恬淡氛圍,而日常生活中所慣見到的風景,也大多是蒼茫無邊的淡水河以及關渡平原,總是讓我不禁聯想到「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之類的詩句,和現代化的城市根本沾不上邊。
也或許我只是不明白,所謂的城市究竟應該是什麼模樣?
來到北投的那一年我才七歲,先前只是一個懞懂的孩子,回憶起來,在高雄的日子唯有窗外周而復始的日升日落,歲月無聲無息地滑過,就像是一部靜默的黑白電影,竟想不出有什麼悲哀和歡喜可言。
但來到北投以後世界卻大不相同了。陌生的異鄉忽然跳出了顏色、聲音和氣味,強烈的光影不安地閃爍著,躁動著,讓我驚怯睜大了眼,惶惶不知所措。我開始懷念起高雄那份明亮到過分純粹的陽光了,乾燥無雨的天氣,空中總是白雲朗朗,以及左營鄉下外婆家的磨石子地面,即便是在炎炎的夏日赤腳踩上去,也是傳來一股透澈心肺的冰涼。
然而這一切全都消失無蹤了。
就連高雄鄰居皮鞋店和我同年紀的小女孩,天天一起結伴上學玩耍,我卻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和長相了,只剩下一團朦朧的黑影。反倒是她家店門口擺在玻璃櫃中的一排黑色男鞋,始終令我印象深刻。在無人的午後陽光籠罩之下,它們顯得既無助又徬徨,彷彿困惑著不知道下一步該要走向何方?
那些皮鞋還在玻璃櫃中等待著未知的主人,但我卻已經提早一步先行離開了。搬家那天,我坐上了載滿舊家具的卡車,準備一路搖搖晃晃地北上。鄰居小女孩就坐在皮鞋店前的小圓凳上,望著我,遲疑地揮了揮手。
那是道別的手勢,從此不復得見。
我想我必然是哭了。遷徙是啟蒙的開始,我的生命將要退回到一片空白的原點,重新來過一遍。我沉默地抵抗著,為注定即將失去的一切流下了絕望的淚水。但這有什麼用呢? 又有誰會覺得孩子的眼淚是珍貴的?
♦
接近傍晚的時分,搬家卡車終於來到了尊賢街,那是我們在北投的第一個住家。夕陽昏黃的餘暉鋪滿了巷子兩側的公寓,映襯得一樓鐵門的朱紅油漆更加斑駁,像是誤闖入一齣未老先衰的夢境,黯然得教人心驚。
後來,我們多半把那一帶稱之為「石牌」,而認為更往北走越過公館路以後才能夠算是北投。但「石牌」這兩個字總是讓我覺得又硬又冷,像是鐫刻著某種權威話語的石碑,神聖而不可侵犯,並不存在一絲一毫可以妥協的柔軟空間。
果然那附近也大多是些道德意味濃厚的街名,從「尊賢」、「實踐」、「明德」、「自強」到「立農」,再再向我們訓示著一種理想崇高的人格。
這些街名雖然取得堂皇,卻也多是些狹窄的尋常巷弄罷了,以柏油瀝青鋪成,縱橫交錯,切割出來一大片六〇年代以後才在台北街頭大量湧現,清一色是灰色洗石子牆的四層樓公寓。它們的造型方正,中規中矩,一如居住在其中的也大多是些勤勉樸實而面容拘謹的軍公教人員。
我們在尊賢街只住不到短短的兩年,又改搬到實踐街去。就像蒼蠅飛起在空中盤旋數圈之後,總會固執地又要落回原點,日後我們就在這些巷弄之間搬來搬去的,而新舊的住處往往不出三百公尺遠。
也是要等到多年以後,我才恍然大悟「實踐」之名的源頭,竟是因為街尾有一座國民黨專門訓練高階軍官的「實踐學社」,前身還是日本帝國陸軍的軍事顧問組織「白團」。
我從未意識到,原來住家的附近就隱藏著一個如此神祕的軍事組織?只知道實踐街口確實終年瀰漫著一股令人敬畏的氣息。那是四棟中央社的宿舍,同樣是低調的灰色公寓,我每天上學放學都必定會打門口經過,得以窺見出入在其中的社員。他們大多身穿白襯衫手提黑色的公事包,低著頭行色匆匆,彷彿包裡裝的全是一些不可洩漏的天機。
這就是我所認知的石牌。
至於北投,還要落在更遠之處,那朝向地平線盡頭綿延的大屯山脈,終年飄散著青白的山嵐和硫磺煙霧,以及更遠的淡水,日復一日向這片陸地送來海洋鹹濕的氣息,彷彿以一個更加遼闊而美的世界在殷殷召喚著我。
那是山與海混沌的交界,夜與夢的黑洞,我生命中最初讀到的一首詩,句句都是命運的隱喻,讓我不禁悠然神往,卻又每每悵然若失於它是如此的晦澀不可解。
【內文試閱二】
那正在街頭燃燒的一切
關於八〇年代,我特別記得的就是一九八七年,並不是因為台灣解嚴──我還沒有如此巨大的歷史感,而是那一年我恰好高三,畢業前夕教官突然在朝會上宣布:因為解嚴,學校的髮禁也一併宣告解除,從現在起你們可以把頭髮留長了。
雖然搞不清楚戒嚴和髮禁究竟有什麼關係?但對於十八歲的女孩而言,頭髮之事非同小可,念茲在茲,操場上爆出歡聲雷動,大家感動得相擁幾乎掉下熱淚。只可惜畢業在即,頭髮又不能在一瞬之間留長,我們只好跑到美容院去把頭髮削得更薄更短,一種當時最流行的羽毛剪,也算是以頭髮來宣告了解嚴之後的自主權。
所以解嚴是從自己的身體開始的,接下來才輪到了大腦。
七月揮汗如雨考完了聯考,我把高中三年下來累積的教科書一頁頁撕開,本來想放一把火將它們燒得精光,才算是壯烈,後來又嫌麻煩,乾脆全扔給垃圾車運走,不但毫無留戀之情,還有如釋重負的快樂,卻又不免詫異著自己居然可以痛恨知識到這種地步。
於是就這樣稀里糊塗畢了業,我從聯考的桎梏中解脫,也脫下高中三年身上那襲一陳不變的白衣黑裙,從此青春的小鳥拍拍翅膀飛出牢籠,自由自在海闊天空,哪裡還有時間回顧?
只記得為高中生涯劃下句點的,不是畢業典禮,而是體育老師帶我們去石門水庫露營。他是台灣赤足滑水的國手,特地要在我們這群女孩前大顯一番身手,只見他光著雙腳被一艘白色快艇拖著,輕功水上飄似的快速從藍綠色的湖水上掠過,濺出了一道道驚人的水花,現出繽紛而迷離的七彩虹暈,彷彿是我們一場告別青春的成年禮。
就在那天傍晚我和K共划一艘木舟,一直划入石門水庫的最深處。K是我高中三年最要好的同學,相較於我的急躁粗心,她總是溫柔而嫻靜。黃昏時分環湖四周的林蔭幽幽,我一不小心手一滑,木槳居然掉落水中,沒幾秒就直直沉到湖底。
沒了槳,要如何把船划回岸去?我只好急著向碼頭上的同學招手求救,也不知道她們到底有沒有看見?夕陽西下,山裡的天色迅速轉暗,只見岸上遙遙的燈光閃爍,傳來隱約的笑語,卻都被湖水一一吞沒,而四下靜悄悄地只聽得見我和K的呼吸。
百年修得同船渡。所以我和K真是有緣,但不知是緣深還是緣淺?當時的我們渾然不知十多年過後,K會喪生於高速公路上的一場客運大火。
我卻始終清晰地記得,那天石門水庫所蕩漾著夢幻般的紫藍色光影,映照她一雙深邃又烏黑的大眼,而我在K的眼裡看見了自己:同樣是十八歲,同樣對於即將迎來的大學生涯充滿了樂觀期待。我們於是忘了對未來本該有的忐忑與不安,就在那一年的九月分手,迫不及待飛往了各自的校園。
♦
日後屬於我的這一世代經常被稱之為「學運世代」。
這個標籤難免以偏概全,卻也多少具有某種程度的準確,因為就算我們不是學運中的一分子,也必定是一個旁觀者或是路過之人,而在有意無意之中對於運動有了深淺不一的涉入。
尤其我讀的又是台大政治系,這是我在大學聯考填下的第一志願,如今回頭再看這個選擇未免有點古怪,卻都該歸咎於八〇年代成功的黨國教育,使我到了十八歲卻依然懷抱著一種天真到近乎愚騃的理想,以為一個有志的青年就該從政報效國家。
當我果真如願以償進入了政治系,所經歷到的第一次震撼洗禮就是學生會長選舉,如火如荼在校園中展開。那其實也不過是一場學生級的選舉罷了,但兩位候選人的背後卻有不同的政黨在支持,彼此之間廝殺激烈,謠言耳語不斷,黑函和黑金滿天飛,儼然已經是一個社會選舉的小小雛形。
才剛從漫長威權年代之中掙脫出來的我們,形同是一群民主的新生兒,還停留在牙牙學語的階段,又如何能夠懂得文明的規範? 於是選舉時一拚鬥起來,就不免原形畢露,全淪為了一隻隻齜牙咧嘴的野獸。
我這才發現自己是何等的幼稚和愚蠢,原來政治不是青年報效國家的浪漫理想,而是血淋淋的權力運作。大一的必修課是政治學,教授在黑板上寫得密密麻麻,我拚命地抄著筆記,卻都是紙上談兵。一整年的課堂下來我只記得一句話:「政治就是眾人的利益分配」,而其餘全都還給了教授忘得一乾二淨。
♦
原來說到底,政治無關個人的理想和犧牲奉獻,而是眾人的利益分配。
我腦筋卻一時運轉不過來,就這樣茫茫然度過了新鮮人的一年,聽學長姊說社團才是大學的必修學分,便嘗試去造訪一些頗為活躍的學運社團如大新社、大陸社和大傳社,卻多半是躲在角落,默默聆聽那些嘴裡叼著香菸、腳趿藍白拖的社團老骨頭們口沫橫飛。
後來又在同學的慫恿下參加了一些服務性社團,這是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的產物,來到八〇年代在台大的校園仍屬主流。但我依然不免懷疑上山下海走入偏鄉,除了造就一個熱情滿滿的暑假之外,究竟是在服務自己?還是服務別人?
當年流行學者從政,政治系有幾位留學歸國的年輕老師投入選舉,我也自告奮勇到競選總部幫忙,成為學生助選員之一,沒日沒夜站在街頭發傳單,綁布條,插旗子。我還在學長的指導下模仿海德公園的「演說之角」(Speakers' Corner),也搬了一張小圓凳拿起擴音器,就站在北投的黃昏市場前拉票演說。
但我一站上去才發現凳子居然有這麼高? 眼見底下一大片黑壓壓的頭顱洶湧,雙腿就忍不住發抖,聽到自己的聲音從擴音器中傳出來,更是尖銳刺耳得陌生,反倒能聽得一清二楚的,是從夜市傳來人們吃吃的嘲笑聲。
一個大學生究竟是否知道得比一個賣菜的攤販還多? 我連自己都沒辦法說服了,更何況是他人? 我成了一個徹底的懷疑論者,對於那些堂而皇之的宣言或口號,不管是來自哪一方的,我都懷疑。
想像之中的浪漫青年,來到現實竟成了一個行動上的侏儒。
原來我根本不適合吃政治和選舉這行飯,相較於站在舞台上,我更喜歡當一個台下的觀眾,隱身於茫茫的人海之中,只在一旁觀察,而不會輕易地站起身來介入。
幸好八〇年代末的台北街頭,尤其是我居住的北投更是黨外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幾乎天天都在上演集會遊行和大大小小的政見發表會,到處都是可以湊熱鬧的政治嘉年華,而那才是活生生的教室,比起大學課堂不知有趣幾百倍。
這時對岸也恰好爆發六四天安門學運,我們每天一進教室,就和同學熱切傳閱報紙上的新聞,以為這正是二十世紀關鍵性的一刻,而歷史即將就要全盤改寫。但年輕的我們又怎麼能夠預知,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場運動卻幾乎被人遺忘消失?
然而我仍記得當時因蓬萊島案坐牢而出獄的陳水扁,在北投走進某間中學操場的政見發表會時,被民眾高高扛在肩頭上,有如神降人世一般穿過人群,接受成千上萬民眾膜拜歡呼的光榮,讓整個夜都因此熊熊地燃燒沸騰。
我甚至有好幾次走到政見會的台前,以最虔誠而且神聖的心,掏出一個大學生口袋中僅有的紙鈔,鄭重地把它們投入捐款箱。
我甚至握過台獨教父的手,而他的另一隻手在二次大戰中被炸斷,始終藏在西裝褲的口袋中。
我家附近也常有封街演講,人潮塞滿了整條巷子幾乎見不到盡頭。我擠在隊伍中拚命踮起腳尖,才勉強瞧見以美麗島事件辯護而聞名的律師,正站在木板臨時搭出來的簡陋講台上,用激動的語氣搭配誇張的手勢演說。
我已經完全忘了他說些什麼?但那似乎不重要,反而是街道兩旁高高懸起的昏黃燈泡,照耀著不安蠕動的人們,有如黑夜的大海暗潮洶湧卻又金波蕩漾。那是星星點點的革命之火,正在翻滾醞釀著,只等待風起,火勢就足以一路延燒燎原。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