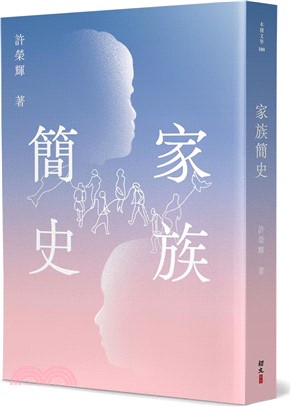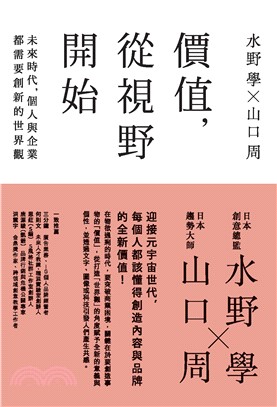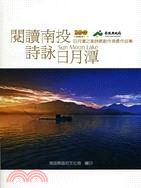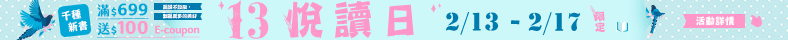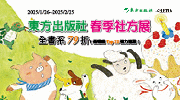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以戲劇中「幕」的概念和絮語的形式,將人物想像成舞台上出場的角色,並通過若干個角色的自我敘述她們記憶中的畫面、場景,揭示一個家族四代人的經歷,反映出社會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況。
【生於鄉間的蔡烏願,被命運掌控】
「我總覺得,我們母親那一代的女子,是帶著『宿命』來到這個世界的,她們的命運都早已安排好了的。」
身為第一代的女性代表蔡烏願,生於鄉間,堅守傳統的鄉土規範,婚姻大事由不得她控制。為了能與丈夫相見,她必須冒險前往,在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攀越過崎嶇的山頭,藏在偷渡船的船艙裏,渡過黑海。這段艱辛的路程,展現了蔡烏願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和堅忍的特質。
【每個人都「搵食艱難」】
作者從四代人身上,到他們所遇到的人身上,充分展現了「人生是苦的」的真理。通過母親因病無法返工的事實,呈現出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下,卑微的人改變不了的不人道現象。而在施秀美的童年時期曾遇到的女小販淑姨,發現她在做生意的過程中,給人一種拒人千里的感覺,讓人不禁思索她背後所受的苦難和經歷。
這部作品不僅是一本家族史,更是社會底層生活的真實寫照,引人深思。
好評推薦:
「對於這樣的寫作人來説,書寫只是一種記錄,諦聽內心的聲音,訴説自己的故事。我想,許榮輝就是其中一位。讀畢他的這本遺著《家族簡史》,一個最大的感受是,由心而發的聲音不會走調。他完成了人生最後的訴説,也為自己的文學生涯劃下了一個完滿的句號。」——蔡益懷
「從我到家族,由世紀至簡史,許榮輝先生都是一邊刻畫人物角色片段零散的生活情節,一邊站在故事之外以敘述者的角度去評點、引申到現實香港的時代狀況。因此,不少論者說過許先生的作品『散文化』,這當然是受到他最推崇的小說家,契訶夫的影響。所以,他的寫作信念,由第一本小說《我的世紀》,到臨終的《家族簡史》,都是從生活出發,卻不止於單純的客觀呈現、寫實、照像,而是透過故事,去說心中的話。」——黎漢傑
【生於鄉間的蔡烏願,被命運掌控】
「我總覺得,我們母親那一代的女子,是帶著『宿命』來到這個世界的,她們的命運都早已安排好了的。」
身為第一代的女性代表蔡烏願,生於鄉間,堅守傳統的鄉土規範,婚姻大事由不得她控制。為了能與丈夫相見,她必須冒險前往,在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攀越過崎嶇的山頭,藏在偷渡船的船艙裏,渡過黑海。這段艱辛的路程,展現了蔡烏願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和堅忍的特質。
【每個人都「搵食艱難」】
作者從四代人身上,到他們所遇到的人身上,充分展現了「人生是苦的」的真理。通過母親因病無法返工的事實,呈現出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下,卑微的人改變不了的不人道現象。而在施秀美的童年時期曾遇到的女小販淑姨,發現她在做生意的過程中,給人一種拒人千里的感覺,讓人不禁思索她背後所受的苦難和經歷。
這部作品不僅是一本家族史,更是社會底層生活的真實寫照,引人深思。
好評推薦:
「對於這樣的寫作人來説,書寫只是一種記錄,諦聽內心的聲音,訴説自己的故事。我想,許榮輝就是其中一位。讀畢他的這本遺著《家族簡史》,一個最大的感受是,由心而發的聲音不會走調。他完成了人生最後的訴説,也為自己的文學生涯劃下了一個完滿的句號。」——蔡益懷
「從我到家族,由世紀至簡史,許榮輝先生都是一邊刻畫人物角色片段零散的生活情節,一邊站在故事之外以敘述者的角度去評點、引申到現實香港的時代狀況。因此,不少論者說過許先生的作品『散文化』,這當然是受到他最推崇的小說家,契訶夫的影響。所以,他的寫作信念,由第一本小說《我的世紀》,到臨終的《家族簡史》,都是從生活出發,卻不止於單純的客觀呈現、寫實、照像,而是透過故事,去說心中的話。」——黎漢傑
作者簡介
許榮輝(1949-2024)
曾在香港新聞界長期擔任新聞翻譯工作,作品入選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著作有小說集《我的世紀》、《石龜島傳說》、《對照細說》。其中《我的世紀》獲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首獎。
曾在香港新聞界長期擔任新聞翻譯工作,作品入選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著作有小說集《我的世紀》、《石龜島傳說》、《對照細說》。其中《我的世紀》獲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首獎。
序
我看許榮輝的文字因緣
二〇二四年二月一日,我收到許榮輝先生手機傳來久違的信息。當時還以為是許先生又看到什麼好書或者文章,想和我分享討論,畢竟大家認識已經好多年,知道他的性格,話題永遠圍繞談文說藝,不會閑聊或者說八卦。豈料,一看,赫然卻是令人悲痛的噩耗:
黎先生,您好!
我是許榮輝太太,我先生於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五日因病離世,喪禮已於昨日舉行。
許生有個遺願,拜託黎先生出版他的小說,不知是否可行。
我真的想不到,兩個月前還和許先生電郵往還,商討一本短篇小說集的內容,準備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書稿到今日還在我手,但先生卻已經不在了。
近年因病,記憶不十分清晰,認識許先生的詳細經過,印象模糊。依稀記得,是在《城市文藝》偶然讀到他的短篇小說,繼而在劉以鬯前輩主編《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追看他的成名作〈鼠〉。這才知道原來我們有這麼一位優秀的小說家,驚喜之餘,卻也覺得可惜。他的作品既多且精,卻為何完全沒有作品結集出版過?當時,自己初創出版社,凡事敢於嘗試,為求出版好書,不怕尷尬,因此致函梅子先生,請他代為引薦。梅子先生一向樂於助人,很爽快就答應了。就是這樣,我和許先生開始了這些年的文字因緣。
二〇一八年,我們合作的第一本小說集《我的世紀》出版,並獲得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首獎。一般來說,作者奪得獎項,高興之餘總會到場領獎,感受會場的氣氛以及大眾的祝賀,多少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心。這當然是正常不過的事,尤其是像許先生那樣,默默筆耕數十年,到了頭髮斑白才得獎,更可以說是遲來的掌聲。不過,許先生非常謙厚,並沒親身出席活動,反而是邀請我以出版人的身份去領獎。相比社交應酬,他更喜歡一個人靜靜的閲讀、寫作。
是的,許先生是一個純粹的寫作人,你不會在大大小小的展覽、活動、發佈會看到他的身影。即便是我,和他合作出版過《我的世紀》(2018)、《石龜島傳說》(2020)、《對照細說》(2022)三本小說集,也只是和他有數面之緣。其中一次,是《我的世紀》得獎之後,許先生相約梅子先生與我,在北角茶聚,算是慶功宴吧。其餘幾次都是在速食店、咖啡店匆匆交談,不過地點還是在北角。那時,我一直困惑,為何許先生對北角情有獨鍾,直至收到許太電郵傳來他的長篇小說遺作《家族簡史》,我才知道,原來他就像小說的那些主人公,在這個地方成長、生活,甚至打工。縱使後來遷居他處,年長一輩如他還是對故居念念不忘。
文學評論都將許先生歸類為現實主義、寫實派的作家,但因為他甚少露面,也從不作自我宣傳,所以一般人不會太清楚他的寫作歷程,以及風格形成的因由。其實,若果仔細爬梳他寫過的散文與評論文章,倒能拾到一鱗半爪。他曾在〈只有真善美,才有大愛〉一文自言,寫作路上影響他最大的,外國的是契訶夫,本地的是張初:
我認識張初先生,是開始於閱讀他的文學作品。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我讀了他的一篇叫做〈廠長〉的報道文學,其實也是一篇相當出色的短篇小說。
……
這篇小說叫我當時讀了震撼,並不僅僅因為我也生活其中,在那段歲月也做過家庭手工,而是一直想著,小說怎麼可以寫得這麼精彩,把時代脈搏捕捉得那麼準確!我們如何把我們生活的時代某種最普遍的生活畫面捕捉,然後以特別的角度切入,寫得深刻而動人,哪裏是容易的事。照我看來,這個經典短篇,像我喜歡的契訶夫短篇那樣的精緻、深刻、動人。
許先生固然是出身基層,所以寫他熟悉的底下階層生活,是順理成章。但是,他的本意是希望透過呈現這些生活畫面,去把握時代的脈搏,換言之,就是以小見大。
回頭看他兩部書的書名,起點的《我的世紀》,以及終點的《家族簡史》,都是以一己的「我的」、「家族」,去刻畫一個社會的「世紀」、「簡史」。《我的世紀》是短篇小說集,目錄是許生親自編排,以時代劃分,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紀初以及二十一世紀一十年代,涵蓋的範圍正好是他開始移居香港,直至當下,所以題目曰:「我的」,理由在此。《我的世紀》是以時間作歸納,敘述的角度是垂直的,至於《家族簡史》則是四代人的獨白為中心,作橫切的鋪陳。他以這一豎一橫,去把握這個城市的時代脈搏。
《家族簡史》講述的是一家四代人的生活,起自移民南下的蔡烏願,終於他鄉漂泊的陳芳雨。故事以多幕劇的形式,讓每一篇的主人公現身臺前,獨白自己的所看、所思、所言、所行。這種運用多人的限知視角敘述,結構類近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的「複調小說」(Polyphonic Novel),「在一部作品中能夠並行不悖地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語言,各自都得到鮮明的表現而絕不劃一,這一點是小說、散文最為重要的特點之一。」(巴赫金著、白春仁、顧亞鈴譯《巴赫金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卷5,頁266)正好切合開首言明的口述歷史設定:
大家聽了這個提議都高興得不得了,都很興奮。
若秀説:「家族簡史,口述的?到底是誰想出了這樣好的主意?」
……
秀美説:「芳雨説,只要跟家族有關的,都可以憶述,可以是關於自己的事情,關於家族裏的人與事,就算是一條街道,一件物品,只要與家族有關,都可以用來口述一番,不受限制。」
若秀説:「生個孩子,也可以拿來憶述一番。」
李芳紅笑著説:「那是當然了。就家史來説,其實是大事。」
口述家族的生活片段,看似零碎散亂、不成系統,實則作者是希望構成一幅反映戰後香港小市民的浮世繪。
家族第一代蔡烏願因已去世,所以她的故事由女兒施秀美代為憶述。開篇即在她的名字「烏」上做文章:「讓人想到的都是不好的東西,烏雲密佈,烏鴉,要是讓我慢慢想的話,還有很多。」名字,對蔡烏願那一代女性,不是一種個人的標記,而是一個族群的代號:
王慶是這樣説的,在家鄉,母親一輩(也許還有更上幾輩,這一點,我就不大確知了),名字裏都有個「烏」字。我母親的名字裏,當然也有個「烏」字。
小時候,生活在那麼多名字裏都有個「烏」字的女子中,覺得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從古早就傳下來的儀式,有怎麼的規矩都得遵守。就如這個「烏」字,大家都有,你怎麼可以沒有呢?
這種具體而微的觀察,確實是當時南下香港那一代大部分女性的形象:從農村出來,信守的是傳統鄉土的規範,整齊劃一,共同體比個人重要。為了家族,她們可以默默付出,甚至勇於犧牲,蔡烏願的婚姻正是其中一個例子,丈夫的年紀比自己大好多,雙方結合,都是出自盲婚啞嫁,事先沒有感情基礎,只是信從長輩的安排,就成為夫妻。而丈夫娶妻,幸福片刻,又再遠渡南洋謀生活。但是,蔡烏願雖然年少,但比丈夫更刻苦、更能忍耐:「一個傳統女子依在丈夫身邊露出甜美的笑容,既是含蓄卻明顯又是十分高興、樂意」,「一對患難夫妻,妻子對丈夫完全沒有怨恨」,生活雖然艱難,卻從沒有失去熱情。
蔡烏願雖然在故事裏缺席,沒有親自登場,但卻是最重要的。她的後代,全部都遺傳了她的特質:堅忍。對生活、對人事、對未來,都不放棄。蔡烏願的女兒施秀美經歷過一次失敗的婚姻,仍然能夠挺過來,重新開創事業,再次收穫愛情。施秀美第一次婚姻出生的女兒洪若秀年少時父母離異,導致性格叛逆,人生曾經跌入穀底,但環境再惡劣,仍然默默守護女兒陳芳雨。陳芳雨自幼聰明好學,獨立自強,繼承了蔡烏願的頑強鬥志。至於施秀美第二次婚姻出生的女兒宋若美,則擁有蔡烏願溫柔、善良的特質。面對同母異父的姐姐,她主動攀談親近,及至協助調解母親與姐姐多年的心結,促成家庭的大團圓,實在居功至偉。
蔡烏願的故事,有女兒施秀美,以及孫女洪若秀的追憶,補充遺失的家族拼圖。而施秀美兩次婚姻的轉折,兩個同母異父的姐妹洪若秀與宋若美,以及宋若美與姨甥女陳芳雨的互動,則透過施秀美好友李芳紅的視角敘述。因此,李芳紅主要出現在第七、八幕,以另一種敘述的視角,補寫家族幾位女性的生活片段。如此,則讓一家人的眾聲喧嘩以外,增添一個冷靜、客觀的聲音。
從我到家族,由世紀至簡史,許榮輝先生都是一邊刻畫人物角色片段零散的生活情節,一邊站在故事之外以敘述者的角度去評點、引申到現實香港的時代狀況。因此,不少論者說過許先生的作品「散文化」,這當然是受到他最推崇的小說家,契訶夫的影響。所謂「小說散文化」,老前輩汪曾祺在〈小說的散文化〉講得最簡潔。要言之,就是這類小說「一般不寫重大題材」、「他們所關注的往往是小事」、「不過分地刻畫人物」、「大都不是心理小說」、「不去挖掘人的心理深層結構」以及「好像完全不考慮結構,寫得輕輕鬆鬆,隨隨便便,瀟瀟灑灑」。回頭看《家族簡史》,每個人物獨白的只是人生幾個片段,敘述也不按時序鋪陳,可以說,是以作者的意念為中心,故事的情節只是服從的配角。因此,本書會在第一幕先安排蔡烏願的孫女宋若美先敘述外婆最愛講述「喜鵲報喜」的故事,時序在後:
有一晚,我跟母親閒談,母親笑著説,若美,你想不到吧,你外婆也會講故事給我聽哩。
……
母親説:「你外婆太喜歡講這個故事了,每一次講都用同一種口吻,一種愉悅的口吻,對她自己講的故事內容充滿了熱愛。……」
之後第二幕才輪到蔡烏願的女兒施秀美追記童年時與母親居住的是板間房奇景,時序在前:
從我稍為懂事起,記憶裏,我們母女經常搬家,居無定所。無論搬到哪裏,住的都是板間房,而且無論住到哪裏,同一居所裏的總有女子。
……
我大概可以這樣補充説,這些女子,年紀跟我母親相仿,鄉音未改,單身的多,常常喜歡兩、三個單身女子合租一間板間房。這樣生活負擔就輕得多。
雖然講的是蔡烏願的生活,但並沒有對她的心理活動作直接描寫,只是透過她女兒的評價來推敲她本人的所思所想:「對她自己講的故事內容充滿了熱愛」、「後來我就知道,母親喜歡選擇這樣的地方居住。」而這些回憶之所以被敘述,其實是為了讓作者順利說出以下對當時世代的觀察:
生於貧窮年代,當外婆聽了這個故事,並且知道故事意義的時候,外婆的心靈是會很有感受的吧,上天對人間是好的,只不過是喜鵲報錯了喜而已。以這樣的方式來認識人生,日子是不是就會好過了些?都是命運使然。
我的母親一定也是一樣,大概是某個親戚,帶著剛從蛇頭那裏贖回來的母親,站在車水馬龍的街頭,一副驚慌失措的、不知如何過馬路的無助樣子。
徬徨的心是需要安頓的,這樣一種聚居的情況,很自然地發展了出來,經過輾轉介紹,一個大單位裏的幾個板間房,往往住的都是這些來港與夫會面的女子。
所以,他的寫作信念,由第一本小說《我的世紀》,到臨終的《家族簡史》,都是從生活出發,卻不止於單純的客觀呈現、寫實、照像,而是透過故事,去說心中的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黎漢傑
二〇二四年二月一日,我收到許榮輝先生手機傳來久違的信息。當時還以為是許先生又看到什麼好書或者文章,想和我分享討論,畢竟大家認識已經好多年,知道他的性格,話題永遠圍繞談文說藝,不會閑聊或者說八卦。豈料,一看,赫然卻是令人悲痛的噩耗:
黎先生,您好!
我是許榮輝太太,我先生於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五日因病離世,喪禮已於昨日舉行。
許生有個遺願,拜託黎先生出版他的小說,不知是否可行。
我真的想不到,兩個月前還和許先生電郵往還,商討一本短篇小說集的內容,準備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書稿到今日還在我手,但先生卻已經不在了。
近年因病,記憶不十分清晰,認識許先生的詳細經過,印象模糊。依稀記得,是在《城市文藝》偶然讀到他的短篇小說,繼而在劉以鬯前輩主編《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追看他的成名作〈鼠〉。這才知道原來我們有這麼一位優秀的小說家,驚喜之餘,卻也覺得可惜。他的作品既多且精,卻為何完全沒有作品結集出版過?當時,自己初創出版社,凡事敢於嘗試,為求出版好書,不怕尷尬,因此致函梅子先生,請他代為引薦。梅子先生一向樂於助人,很爽快就答應了。就是這樣,我和許先生開始了這些年的文字因緣。
二〇一八年,我們合作的第一本小說集《我的世紀》出版,並獲得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首獎。一般來說,作者奪得獎項,高興之餘總會到場領獎,感受會場的氣氛以及大眾的祝賀,多少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心。這當然是正常不過的事,尤其是像許先生那樣,默默筆耕數十年,到了頭髮斑白才得獎,更可以說是遲來的掌聲。不過,許先生非常謙厚,並沒親身出席活動,反而是邀請我以出版人的身份去領獎。相比社交應酬,他更喜歡一個人靜靜的閲讀、寫作。
是的,許先生是一個純粹的寫作人,你不會在大大小小的展覽、活動、發佈會看到他的身影。即便是我,和他合作出版過《我的世紀》(2018)、《石龜島傳說》(2020)、《對照細說》(2022)三本小說集,也只是和他有數面之緣。其中一次,是《我的世紀》得獎之後,許先生相約梅子先生與我,在北角茶聚,算是慶功宴吧。其餘幾次都是在速食店、咖啡店匆匆交談,不過地點還是在北角。那時,我一直困惑,為何許先生對北角情有獨鍾,直至收到許太電郵傳來他的長篇小說遺作《家族簡史》,我才知道,原來他就像小說的那些主人公,在這個地方成長、生活,甚至打工。縱使後來遷居他處,年長一輩如他還是對故居念念不忘。
文學評論都將許先生歸類為現實主義、寫實派的作家,但因為他甚少露面,也從不作自我宣傳,所以一般人不會太清楚他的寫作歷程,以及風格形成的因由。其實,若果仔細爬梳他寫過的散文與評論文章,倒能拾到一鱗半爪。他曾在〈只有真善美,才有大愛〉一文自言,寫作路上影響他最大的,外國的是契訶夫,本地的是張初:
我認識張初先生,是開始於閱讀他的文學作品。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我讀了他的一篇叫做〈廠長〉的報道文學,其實也是一篇相當出色的短篇小說。
……
這篇小說叫我當時讀了震撼,並不僅僅因為我也生活其中,在那段歲月也做過家庭手工,而是一直想著,小說怎麼可以寫得這麼精彩,把時代脈搏捕捉得那麼準確!我們如何把我們生活的時代某種最普遍的生活畫面捕捉,然後以特別的角度切入,寫得深刻而動人,哪裏是容易的事。照我看來,這個經典短篇,像我喜歡的契訶夫短篇那樣的精緻、深刻、動人。
許先生固然是出身基層,所以寫他熟悉的底下階層生活,是順理成章。但是,他的本意是希望透過呈現這些生活畫面,去把握時代的脈搏,換言之,就是以小見大。
回頭看他兩部書的書名,起點的《我的世紀》,以及終點的《家族簡史》,都是以一己的「我的」、「家族」,去刻畫一個社會的「世紀」、「簡史」。《我的世紀》是短篇小說集,目錄是許生親自編排,以時代劃分,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紀初以及二十一世紀一十年代,涵蓋的範圍正好是他開始移居香港,直至當下,所以題目曰:「我的」,理由在此。《我的世紀》是以時間作歸納,敘述的角度是垂直的,至於《家族簡史》則是四代人的獨白為中心,作橫切的鋪陳。他以這一豎一橫,去把握這個城市的時代脈搏。
《家族簡史》講述的是一家四代人的生活,起自移民南下的蔡烏願,終於他鄉漂泊的陳芳雨。故事以多幕劇的形式,讓每一篇的主人公現身臺前,獨白自己的所看、所思、所言、所行。這種運用多人的限知視角敘述,結構類近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的「複調小說」(Polyphonic Novel),「在一部作品中能夠並行不悖地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語言,各自都得到鮮明的表現而絕不劃一,這一點是小說、散文最為重要的特點之一。」(巴赫金著、白春仁、顧亞鈴譯《巴赫金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卷5,頁266)正好切合開首言明的口述歷史設定:
大家聽了這個提議都高興得不得了,都很興奮。
若秀説:「家族簡史,口述的?到底是誰想出了這樣好的主意?」
……
秀美説:「芳雨説,只要跟家族有關的,都可以憶述,可以是關於自己的事情,關於家族裏的人與事,就算是一條街道,一件物品,只要與家族有關,都可以用來口述一番,不受限制。」
若秀説:「生個孩子,也可以拿來憶述一番。」
李芳紅笑著説:「那是當然了。就家史來説,其實是大事。」
口述家族的生活片段,看似零碎散亂、不成系統,實則作者是希望構成一幅反映戰後香港小市民的浮世繪。
家族第一代蔡烏願因已去世,所以她的故事由女兒施秀美代為憶述。開篇即在她的名字「烏」上做文章:「讓人想到的都是不好的東西,烏雲密佈,烏鴉,要是讓我慢慢想的話,還有很多。」名字,對蔡烏願那一代女性,不是一種個人的標記,而是一個族群的代號:
王慶是這樣説的,在家鄉,母親一輩(也許還有更上幾輩,這一點,我就不大確知了),名字裏都有個「烏」字。我母親的名字裏,當然也有個「烏」字。
小時候,生活在那麼多名字裏都有個「烏」字的女子中,覺得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從古早就傳下來的儀式,有怎麼的規矩都得遵守。就如這個「烏」字,大家都有,你怎麼可以沒有呢?
這種具體而微的觀察,確實是當時南下香港那一代大部分女性的形象:從農村出來,信守的是傳統鄉土的規範,整齊劃一,共同體比個人重要。為了家族,她們可以默默付出,甚至勇於犧牲,蔡烏願的婚姻正是其中一個例子,丈夫的年紀比自己大好多,雙方結合,都是出自盲婚啞嫁,事先沒有感情基礎,只是信從長輩的安排,就成為夫妻。而丈夫娶妻,幸福片刻,又再遠渡南洋謀生活。但是,蔡烏願雖然年少,但比丈夫更刻苦、更能忍耐:「一個傳統女子依在丈夫身邊露出甜美的笑容,既是含蓄卻明顯又是十分高興、樂意」,「一對患難夫妻,妻子對丈夫完全沒有怨恨」,生活雖然艱難,卻從沒有失去熱情。
蔡烏願雖然在故事裏缺席,沒有親自登場,但卻是最重要的。她的後代,全部都遺傳了她的特質:堅忍。對生活、對人事、對未來,都不放棄。蔡烏願的女兒施秀美經歷過一次失敗的婚姻,仍然能夠挺過來,重新開創事業,再次收穫愛情。施秀美第一次婚姻出生的女兒洪若秀年少時父母離異,導致性格叛逆,人生曾經跌入穀底,但環境再惡劣,仍然默默守護女兒陳芳雨。陳芳雨自幼聰明好學,獨立自強,繼承了蔡烏願的頑強鬥志。至於施秀美第二次婚姻出生的女兒宋若美,則擁有蔡烏願溫柔、善良的特質。面對同母異父的姐姐,她主動攀談親近,及至協助調解母親與姐姐多年的心結,促成家庭的大團圓,實在居功至偉。
蔡烏願的故事,有女兒施秀美,以及孫女洪若秀的追憶,補充遺失的家族拼圖。而施秀美兩次婚姻的轉折,兩個同母異父的姐妹洪若秀與宋若美,以及宋若美與姨甥女陳芳雨的互動,則透過施秀美好友李芳紅的視角敘述。因此,李芳紅主要出現在第七、八幕,以另一種敘述的視角,補寫家族幾位女性的生活片段。如此,則讓一家人的眾聲喧嘩以外,增添一個冷靜、客觀的聲音。
從我到家族,由世紀至簡史,許榮輝先生都是一邊刻畫人物角色片段零散的生活情節,一邊站在故事之外以敘述者的角度去評點、引申到現實香港的時代狀況。因此,不少論者說過許先生的作品「散文化」,這當然是受到他最推崇的小說家,契訶夫的影響。所謂「小說散文化」,老前輩汪曾祺在〈小說的散文化〉講得最簡潔。要言之,就是這類小說「一般不寫重大題材」、「他們所關注的往往是小事」、「不過分地刻畫人物」、「大都不是心理小說」、「不去挖掘人的心理深層結構」以及「好像完全不考慮結構,寫得輕輕鬆鬆,隨隨便便,瀟瀟灑灑」。回頭看《家族簡史》,每個人物獨白的只是人生幾個片段,敘述也不按時序鋪陳,可以說,是以作者的意念為中心,故事的情節只是服從的配角。因此,本書會在第一幕先安排蔡烏願的孫女宋若美先敘述外婆最愛講述「喜鵲報喜」的故事,時序在後:
有一晚,我跟母親閒談,母親笑著説,若美,你想不到吧,你外婆也會講故事給我聽哩。
……
母親説:「你外婆太喜歡講這個故事了,每一次講都用同一種口吻,一種愉悅的口吻,對她自己講的故事內容充滿了熱愛。……」
之後第二幕才輪到蔡烏願的女兒施秀美追記童年時與母親居住的是板間房奇景,時序在前:
從我稍為懂事起,記憶裏,我們母女經常搬家,居無定所。無論搬到哪裏,住的都是板間房,而且無論住到哪裏,同一居所裏的總有女子。
……
我大概可以這樣補充説,這些女子,年紀跟我母親相仿,鄉音未改,單身的多,常常喜歡兩、三個單身女子合租一間板間房。這樣生活負擔就輕得多。
雖然講的是蔡烏願的生活,但並沒有對她的心理活動作直接描寫,只是透過她女兒的評價來推敲她本人的所思所想:「對她自己講的故事內容充滿了熱愛」、「後來我就知道,母親喜歡選擇這樣的地方居住。」而這些回憶之所以被敘述,其實是為了讓作者順利說出以下對當時世代的觀察:
生於貧窮年代,當外婆聽了這個故事,並且知道故事意義的時候,外婆的心靈是會很有感受的吧,上天對人間是好的,只不過是喜鵲報錯了喜而已。以這樣的方式來認識人生,日子是不是就會好過了些?都是命運使然。
我的母親一定也是一樣,大概是某個親戚,帶著剛從蛇頭那裏贖回來的母親,站在車水馬龍的街頭,一副驚慌失措的、不知如何過馬路的無助樣子。
徬徨的心是需要安頓的,這樣一種聚居的情況,很自然地發展了出來,經過輾轉介紹,一個大單位裏的幾個板間房,往往住的都是這些來港與夫會面的女子。
所以,他的寫作信念,由第一本小說《我的世紀》,到臨終的《家族簡史》,都是從生活出發,卻不止於單純的客觀呈現、寫實、照像,而是透過故事,去說心中的話。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黎漢傑
目次
由心而發的聲音不會走調——許榮輝遺著《家族簡史》/蔡益懷
我看許榮輝的文字因緣/黎漢傑
序幕1
序幕2
第一幕
1、施秀美(1)•名字
2、施秀美(2)•名字
3、施秀美(3)•相片
4、施秀美(4)•相片
5、施秀美(5)•探親
6、宋若美(1)•移民
7、宋若美(2)•喜鵲
第二幕
8、施秀美(6)•居住
9、施秀美(7)•儀式
10、施秀美(8)•相處之道
11、李芳紅(1)•原罪
12、施秀美(9)•番客
13、李芳紅(2)•族群圈子
14、施秀美(10)•母親的眼神
第三幕
15、陳芳雨(1)•春秧街
16 、陳芳雨(2)•市井味
17、施秀美(11)•我的童年
18、施秀美(12)•分離
19、施秀美 (13) •老闆娘
20、施秀美(14)•再次分離
21、施秀美(15)•淑姨
22、施秀美(16)•美食小店
第四幕
23、洪若秀(1)•風雨
24、洪若秀(2)•搖籃
25、洪若秀(3)•靜好時光
26、洪若秀(4)•瞳仁
27、洪若秀(5)•配角,或臨記
28、洪若秀(6)•買女裝的男人
第五幕
29、洪若秀(7)•男人的妻子
30、洪若秀(8)•生活的變遷
31、洪若秀(9)•父親來了
32、洪若秀(10)•撫摸我的頭的手
33、洪若秀(11)•寶貝
34、洪若秀(12)•父親做生意手法
第六幕
35、洪若秀(13)•父親處世之道
36、陳芳雨(3)•母女關係
37、陳芳雨(4)•母親的心靈創傷
38、宋若美(3)•父女偶遇
39 、宋若美(4)•無邊的落寞
第七幕
40、李芳紅(3)•我和秀美的結緣
41、李芳紅(4)•廚師阿海
42、李芳紅(5)•一個關鍵性人物
43、李芳紅(6)•宋平與秀美的邂逅
44、李芳紅(7)•婦唱夫隨
45、李芳紅(8)•淒厲絕望叫聲
46、李芳紅(9)•普通人的真愛
第八幕
47、李芳紅(10)•人生的絕境
48、李芳紅(11)•生活也會好起來
49、李芳紅(12)•璀璨的煙花
50、李芳紅(13)•大哥洪這個人
51、李芳紅(14)•愛情憧憬破滅
52、陳芳雨(5)•慈祥的外公
第九幕
53、陳芳雨(6)•母親的痛哭
54、陳芳雨 (7) •愛情價值觀
55、宋若美(5)•母女的笑紋
56、宋若美(6)•充滿親情的保溫壺
57、宋若美(7)•美味食物
58、宋若美(8)•廣告牌和酒味
59、宋若美(9)•集體美味早餐
第十幕
60、陳芳雨(8)•我心裏的親情
61、陳芳雨(9)•機場送別
62、陳芳雨(10)•母親的歡顏
63、陳芳雨(11)•世紀疫情
64、陳芳雨(12)•外曾祖母的形象
65、陳芳雨(13)•人生之路
66、陳芳雨(14)•結語
我看許榮輝的文字因緣/黎漢傑
序幕1
序幕2
第一幕
1、施秀美(1)•名字
2、施秀美(2)•名字
3、施秀美(3)•相片
4、施秀美(4)•相片
5、施秀美(5)•探親
6、宋若美(1)•移民
7、宋若美(2)•喜鵲
第二幕
8、施秀美(6)•居住
9、施秀美(7)•儀式
10、施秀美(8)•相處之道
11、李芳紅(1)•原罪
12、施秀美(9)•番客
13、李芳紅(2)•族群圈子
14、施秀美(10)•母親的眼神
第三幕
15、陳芳雨(1)•春秧街
16 、陳芳雨(2)•市井味
17、施秀美(11)•我的童年
18、施秀美(12)•分離
19、施秀美 (13) •老闆娘
20、施秀美(14)•再次分離
21、施秀美(15)•淑姨
22、施秀美(16)•美食小店
第四幕
23、洪若秀(1)•風雨
24、洪若秀(2)•搖籃
25、洪若秀(3)•靜好時光
26、洪若秀(4)•瞳仁
27、洪若秀(5)•配角,或臨記
28、洪若秀(6)•買女裝的男人
第五幕
29、洪若秀(7)•男人的妻子
30、洪若秀(8)•生活的變遷
31、洪若秀(9)•父親來了
32、洪若秀(10)•撫摸我的頭的手
33、洪若秀(11)•寶貝
34、洪若秀(12)•父親做生意手法
第六幕
35、洪若秀(13)•父親處世之道
36、陳芳雨(3)•母女關係
37、陳芳雨(4)•母親的心靈創傷
38、宋若美(3)•父女偶遇
39 、宋若美(4)•無邊的落寞
第七幕
40、李芳紅(3)•我和秀美的結緣
41、李芳紅(4)•廚師阿海
42、李芳紅(5)•一個關鍵性人物
43、李芳紅(6)•宋平與秀美的邂逅
44、李芳紅(7)•婦唱夫隨
45、李芳紅(8)•淒厲絕望叫聲
46、李芳紅(9)•普通人的真愛
第八幕
47、李芳紅(10)•人生的絕境
48、李芳紅(11)•生活也會好起來
49、李芳紅(12)•璀璨的煙花
50、李芳紅(13)•大哥洪這個人
51、李芳紅(14)•愛情憧憬破滅
52、陳芳雨(5)•慈祥的外公
第九幕
53、陳芳雨(6)•母親的痛哭
54、陳芳雨 (7) •愛情價值觀
55、宋若美(5)•母女的笑紋
56、宋若美(6)•充滿親情的保溫壺
57、宋若美(7)•美味食物
58、宋若美(8)•廣告牌和酒味
59、宋若美(9)•集體美味早餐
第十幕
60、陳芳雨(8)•我心裏的親情
61、陳芳雨(9)•機場送別
62、陳芳雨(10)•母親的歡顏
63、陳芳雨(11)•世紀疫情
64、陳芳雨(12)•外曾祖母的形象
65、陳芳雨(13)•人生之路
66、陳芳雨(14)•結語
書摘/試閱
四十歲以後
四十歲時你在哪裡?回想十多歲那時的我,想告別慘綠的年代,自滿得以為自己到了二十多歲。到了二十多歲,事業正開始,陽光灑滿地,開心得以為自己到了三十多歲。到了三十多歲的年紀,前途未蔔,但什麼都似乎在掌握之中,恍似無憂無慮。到了四十多歲,告別香港,在悉尼重新開始,一切彷彿又回到從前。現在回頭看看四十多歲的當時,原來已經十多年以後。確是昨日匆匆。一步一步的走過來,我的步伐竟然如此沉重。如今對別人說:該走便要走,我反而有點遲疑,不敢說對或不對。每個人有自己的腳步,也有自己的盤算和考慮。離開家園是很個人的選擇,只有自己才知道路是怎麼走,也絕對沒有對或錯。即使生活在澳洲十多年了,要搬到另外一個州居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決定。四十多歲這個年紀,的確過了半生,如果你還沒有擁有一大筆財富足夠退休,還要繼續工作,就要謹慎的走下去。
一個最近的調查發現,四十五到五十四歲這個階段澳洲人,原來是最不幸的一代。許多僱主眼中,這一代的人最不能接受新事物,例如科技改變,所以很不願意聘用他們。全國四十五到五十四歲的人佔了二百九十萬,今年三月失業大軍有十八萬多人,佔百分之六點二。失業的數字從何得知?因為他們仍在積極的尋找工作。放棄找工作的人,不在計算失業率之列。僱主這種不公平的看法,稱之為年齡歧視絕不為過。男人又比女人更難找得工作。在年齡和性別兩種歧視之下,果然是舉步為艱,前途黯淡。加上疫情影響,許多商鋪停業,不少人甚至找一份臨時工也十分困難。
澳洲政府容許海外學生每週工作不多於二十小時。一般情況下,大學的碩士或博士研究生可能在校內找到一份導師的工作。以每小時約三十五澳元計算,尚可幫補一般生活開支。不過三月開始封關以來,就讀的海外學生減少,導師的工作也多少受到影響。其他就讀大學本科的學生,本來也可以到咖啡館或餐廳兼職。不過現在市中心上班的人比正常的少很多,商鋪多關上大門。勉強經營下去的話,也不會輕易聘請兼職。於是老闆在店裡身兼數職,節省開支算了。媒體不時報導,不少海外學生失去兼職,三餐不繼。有些同鄉經營的食肆,曾經免費送贈飯盒作為支持。電視畫面所見,不少人在門外輪候。專為貧窮人士提供食物的foodbank,也多了很多人光顧。但我問來到我們部門實習的一個海外學生,她反而說沒有聽過有同學有如此境況。這個來自中美洲千里達的女孩,可能經濟情況不比尋常。她的本科就讀美國賓州費城,捨近圖遠來到悉尼讀碩士,跟其他經濟不俗的海外學生一樣,有強力的父母作背後支援,根本不用為三餐煩惱。至於畢業後,能否找到工作,倒是不用擔心。
另外一份報導指出,澳洲的工作,目前有一半是屬於短期、臨時或合約制。四五十歲的人士,除了難找到工作外,也難於找到長期固定的工作。短期的可是數天或是數星期,工作完成拜拜,大家兩不相欠。不少人也不討厭這樣的工作,因為有彈性,習慣的話看看可否繼續,不習慣的話也重新出發,或許可以停下來,去一趟旅行。我的一個朋友接受了大學自願退休的邀請,結束了十一年賓主之情,得到差不多一年的離職補償。我問他為什麼如此大膽。他說升職無望,做下去沒有什麼意思,倒不如出外碰碰運氣。他現在六十一歲,還想幹到六十四歲。結果憑他的資歷,來到我們這𥚃接受五星期短期合約的工作。大家碰面,我當然驚訝,但合作起來,他還是那麼積極。所以求職的難與易,有時不是單純從年紀看。僱主也不是白癡。如果沒有好的推薦,恐怕也沒有那麼容易成事。但找工作愈來愈難,應該還是事實。尤其是和年輕的一輩爭奪相同的職位,你會選擇一個最燦爛年華的年輕人,還是一個在職場已經工作了三十年的中年人?
四十歲時你在哪裡?回想十多歲那時的我,想告別慘綠的年代,自滿得以為自己到了二十多歲。到了二十多歲,事業正開始,陽光灑滿地,開心得以為自己到了三十多歲。到了三十多歲的年紀,前途未蔔,但什麼都似乎在掌握之中,恍似無憂無慮。到了四十多歲,告別香港,在悉尼重新開始,一切彷彿又回到從前。現在回頭看看四十多歲的當時,原來已經十多年以後。確是昨日匆匆。一步一步的走過來,我的步伐竟然如此沉重。如今對別人說:該走便要走,我反而有點遲疑,不敢說對或不對。每個人有自己的腳步,也有自己的盤算和考慮。離開家園是很個人的選擇,只有自己才知道路是怎麼走,也絕對沒有對或錯。即使生活在澳洲十多年了,要搬到另外一個州居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決定。四十多歲這個年紀,的確過了半生,如果你還沒有擁有一大筆財富足夠退休,還要繼續工作,就要謹慎的走下去。
一個最近的調查發現,四十五到五十四歲這個階段澳洲人,原來是最不幸的一代。許多僱主眼中,這一代的人最不能接受新事物,例如科技改變,所以很不願意聘用他們。全國四十五到五十四歲的人佔了二百九十萬,今年三月失業大軍有十八萬多人,佔百分之六點二。失業的數字從何得知?因為他們仍在積極的尋找工作。放棄找工作的人,不在計算失業率之列。僱主這種不公平的看法,稱之為年齡歧視絕不為過。男人又比女人更難找得工作。在年齡和性別兩種歧視之下,果然是舉步為艱,前途黯淡。加上疫情影響,許多商鋪停業,不少人甚至找一份臨時工也十分困難。
澳洲政府容許海外學生每週工作不多於二十小時。一般情況下,大學的碩士或博士研究生可能在校內找到一份導師的工作。以每小時約三十五澳元計算,尚可幫補一般生活開支。不過三月開始封關以來,就讀的海外學生減少,導師的工作也多少受到影響。其他就讀大學本科的學生,本來也可以到咖啡館或餐廳兼職。不過現在市中心上班的人比正常的少很多,商鋪多關上大門。勉強經營下去的話,也不會輕易聘請兼職。於是老闆在店裡身兼數職,節省開支算了。媒體不時報導,不少海外學生失去兼職,三餐不繼。有些同鄉經營的食肆,曾經免費送贈飯盒作為支持。電視畫面所見,不少人在門外輪候。專為貧窮人士提供食物的foodbank,也多了很多人光顧。但我問來到我們部門實習的一個海外學生,她反而說沒有聽過有同學有如此境況。這個來自中美洲千里達的女孩,可能經濟情況不比尋常。她的本科就讀美國賓州費城,捨近圖遠來到悉尼讀碩士,跟其他經濟不俗的海外學生一樣,有強力的父母作背後支援,根本不用為三餐煩惱。至於畢業後,能否找到工作,倒是不用擔心。
另外一份報導指出,澳洲的工作,目前有一半是屬於短期、臨時或合約制。四五十歲的人士,除了難找到工作外,也難於找到長期固定的工作。短期的可是數天或是數星期,工作完成拜拜,大家兩不相欠。不少人也不討厭這樣的工作,因為有彈性,習慣的話看看可否繼續,不習慣的話也重新出發,或許可以停下來,去一趟旅行。我的一個朋友接受了大學自願退休的邀請,結束了十一年賓主之情,得到差不多一年的離職補償。我問他為什麼如此大膽。他說升職無望,做下去沒有什麼意思,倒不如出外碰碰運氣。他現在六十一歲,還想幹到六十四歲。結果憑他的資歷,來到我們這𥚃接受五星期短期合約的工作。大家碰面,我當然驚訝,但合作起來,他還是那麼積極。所以求職的難與易,有時不是單純從年紀看。僱主也不是白癡。如果沒有好的推薦,恐怕也沒有那麼容易成事。但找工作愈來愈難,應該還是事實。尤其是和年輕的一輩爭奪相同的職位,你會選擇一個最燦爛年華的年輕人,還是一個在職場已經工作了三十年的中年人?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