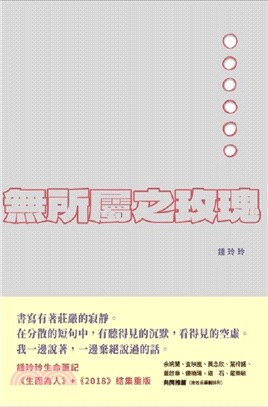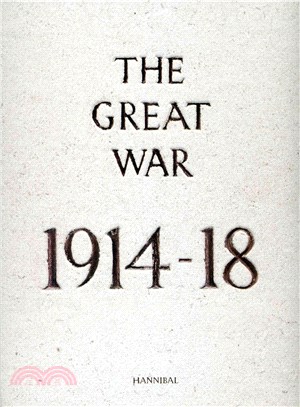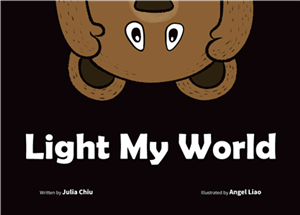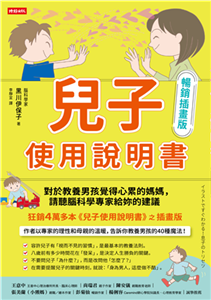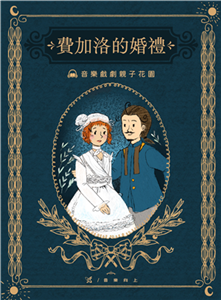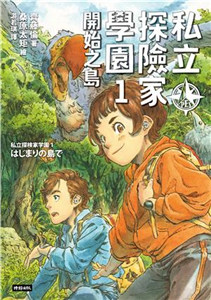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書寫有著莊嚴的寂靜。在分散的短句中,有聽得見的沉默,看得見的空虛。我一邊說著,一邊棄絕說過的話。」
鍾玲玲生命筆記.《生而為人》+《2018》結集重版
《無所屬之玫瑰》結集鍾玲玲分別於2014及2018年隨文學雜誌《字花》附送的《生而為人》及《玫瑰念珠2018》(本為沒有名字的書)。《無所屬之玫瑰》思考生命、愛、家族與命運等命題。全書分為三部份,分別是寫於2008年的〈自由的幻影〉;2014年的〈生而為人〉;及2018年的〈A君的來信〉、〈愛菲愛上帝愛到死〉、〈那深深的腥紅〉及〈無所屬無所屬之玫瑰〉。
「一九四八年秋,我出生了。但生而為人這個事實,卻不是由我決定的。事實是每個人的出生,都是身不由己的。這一年的秋天,我便六十四歲了。人活到這個年紀難免會感慨萬千,思想著到底該慶幸能夠到這世上一回呢,還是慨嘆著說,要是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現在我是這樣想的,要是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
「那麼,該重新開始呢,還是就此結束呢。據說自敘事宣告無效以後,我們步入的是新的抒情年代。在這兒重要的不再是弄明白,而是活著吧。」
「安娜知道她的存在不過是自由的幻影。她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奔赴這個世界的。」
「在越出自身界限的神魂顛倒中仿似置身和聲的中心,並真心相信,即便愛的對象是虛幻的,但愛的感覺是真實的。這充實的感覺在不敘述、不描繪、不論證的情況下得以體現情感的特徵,因而情感的語言不是書面的,而是全面的。」
鍾玲玲生命筆記.《生而為人》+《2018》結集重版
《無所屬之玫瑰》結集鍾玲玲分別於2014及2018年隨文學雜誌《字花》附送的《生而為人》及《玫瑰念珠2018》(本為沒有名字的書)。《無所屬之玫瑰》思考生命、愛、家族與命運等命題。全書分為三部份,分別是寫於2008年的〈自由的幻影〉;2014年的〈生而為人〉;及2018年的〈A君的來信〉、〈愛菲愛上帝愛到死〉、〈那深深的腥紅〉及〈無所屬無所屬之玫瑰〉。
「一九四八年秋,我出生了。但生而為人這個事實,卻不是由我決定的。事實是每個人的出生,都是身不由己的。這一年的秋天,我便六十四歲了。人活到這個年紀難免會感慨萬千,思想著到底該慶幸能夠到這世上一回呢,還是慨嘆著說,要是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現在我是這樣想的,要是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
「那麼,該重新開始呢,還是就此結束呢。據說自敘事宣告無效以後,我們步入的是新的抒情年代。在這兒重要的不再是弄明白,而是活著吧。」
「安娜知道她的存在不過是自由的幻影。她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奔赴這個世界的。」
「在越出自身界限的神魂顛倒中仿似置身和聲的中心,並真心相信,即便愛的對象是虛幻的,但愛的感覺是真實的。這充實的感覺在不敘述、不描繪、不論證的情況下得以體現情感的特徵,因而情感的語言不是書面的,而是全面的。」
作者簡介
鍾玲玲,出生於湖南衡陽,後移居香港。「創建實驗學院」詩作坊成員,《大拇指周報》、《素葉文學》雜誌早期編輯作家。曾獲第一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獎。出版有小說《愛人》(1987)、《愛蓮說》(1991)、《玫瑰念珠》(1997)、《2018》(2018),詩、散文合集《我的燦爛》(1979),散文集《我不燦爛》(1988)、《解咒的人》(1989)、《生而為人》(2014),與鍾曉陽合著《雲雀與夜鶯》(2023)。
目次
007 自由的幻影 2008
025 生而為人 2014
075 2018
025 生而為人 2014
075 2018
書摘/試閱
自由的幻影
你的自由,不過是自由的幻影而已。
——布纽爾——
從前曾經。如今依然。
一九六七年秋,波赫士在一場演講中說了這樣的話——「我已經快要七十歲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份貢獻給文學,不過我能夠告訴你的,僅困惑已。」。儘管話中的準確含意就只有說話者最清楚了,但我不禁猜想,倘若他的寫作及為此付出的全部努力不過是同一事物的雙重幻影,那麼在始終堅持的執念中必然存在設想不到的底蘊,或許是因為在這兒有那麼多的愛,或許是因為在別的地方從未如此深愛過。是這樣嗎?正如貝克特說的,只能如此。只能如此,因為除此以外,再也想不起,曾經有過的,非寫不可的理由。
我寫作,當然是因為有話要說,但亦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了。由於反覆說著的始終是同一句話,因此被禁錮於生存和寫作的同一性中,僅僅意味著有這麼一個人,坐在桌子的面前,並一再追問,「看我幹了甚麼。」。無用的重複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動機,那就是重要的不是說些甚麼,只是說著。只是說著。在被捲入、被束縛的困境中,偶爾難免會想,當初受到的誘惑是甚麼。就彷彿在這兒曾經有過那麼多的愛,愛天上的白雲,掠過的飛鳥,路邊的小花,街角的樹木,夏天的女孩和遇見的每一個人。因為熱愛文學,就是熱愛生命。它既是時代付與的,亦是與生俱來的。記憶中好像曾經經歷一個較有朝氣的創造時期,在同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彷彿一切都是得宜的。但正如馬克思說到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人們不得不直面生活的真實狀況,並且不得不直面相互間的真實關係。或許根本沒有同路人這回事,並最終成為不合時宜的。曾經付與的期望跟所有事情一樣,終須為無力抵抗的誘惑,付出沉重的代價。
但到底是怎樣的誘惑呢。契訶夫是絕望的歌唱家,他的絕望可以總結為以下的道白,一個問,「你在寫些甚麼?」,一個回答,「並沒有甚麼重要的。」。絕望的杜哈絲仍然堅持寫作,並一再追問,是怎樣的絕望呵。帕斯困惑的是——如果這白皙的燈光是真的,這寫字的手是真的,那注視著文字的眼睛是否也是真的。我一再猜想,倘若注視著的眼睛跟進行中的寫作全是真的,那就得問,哦,這個人,坐在桌子的面前幹甚麼。要是俯身向前,他在寫些甚麼。要是靠著椅背,他在想些甚麼。要是臉向窗戶,他在看些甚麼。要是甚麼也看不見,在他空洞眸子裡的是甚麼。他最深的深處到底穿越何種途徑,才能把與生俱來的及後來學會的化作文字。他的書寫到底通過何種語言,才能成為反覆閱讀、不斷回味的文學。他是否終於可以說,這就是我渴望的,我曉得渴望著的是甚麼。
欲望來自躁動的大海,隨著高舉的浪花,成為白色的泡沫。我們欲望的對象是悲壯的幻象,從年輕到年老,總是無力地被誘惑、不斷地被考驗、嚴酷地被耗盡。作者臉對中空的白紙,就仿似撿拾海嘯過後海岸遺留的殘餘物,既追問知道的根據,又追問相信的理由。因而卡夫卡在一封書信中說——「我寫的和我說的不一樣,我說的和我想的不一樣,我想的和我應該想的不一樣,因而最終陷入最深沉的黑暗中。」。大江健三郎在《小說家的生與死》提到——「我心裡常害怕對方這樣問我,你相信自己有小說家的才能嗎?」
我相信自己有寫作的才能嗎?倘若使欲望得以永存的唯一方式便是重新回到最初的起點,那麼我寫作無非是因為在這裡有我值得一過的生活,我願意為最初的誘惑付出沉重的代價。儘管並不曉得愛著的是甚麼,但卻充分體驗,在別的任何地方,從未如此深愛過。是這樣嗎?由於說著的始終是無法說清的各種狀態的交匯地,因而在遺忘與復歸中響起的滴嗒聲彷彿得自神諭。一下問,「你仍在嗎?」,一下回應,「我在。」
我閱讀,為的就是⋯⋯
據說依目的的不同,寫作同一個故事有五百萬種方式,那麼依目的的不同,閱讀同一個故事是否也有不同的體會呢。一些讀者追問故事的內容,一些讀者追問敘事的形式,一些讀者反覆地解讀,就彷彿閱讀中的故事不是有限的,而是無限的。利奧塔認為,再沒有較學習閱讀更沒完沒了、更緩慢、更艱辛、更無利可圖的了。我不禁一再猜想,這會是怎樣的一種閱讀呵。
我閱讀,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儘管當中曾經有過重重的誤解,但終於明白,必然是自農夫的心事開始的。據說農夫對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毫無領悟,但卻慨嘆著說,「要是能操他那份心便好了。」。我對閱讀過的書從未有過深刻的領悟,但也慨嘆著說,「要是能操他那份心便好了。」。因此閱讀對我來講,始終是、仍然是、我追問的不過是,那驅使我自無動於中的虛無中驚醒的是甚麼。
就跟只能在簡單的顫抖中發現音樂那樣,我只能在簡單的短句中發現文學。那驅使我自無動於中的虛無中驚醒的不是故事的內容,不是敘事的形式,不是反覆的解讀,而是得以體現的情感。「她就在這兒。」,既包含一切意思,又沒有明確的含意。「騎士決意不再在有限意義上關心公主,從此踏上不知所終的旅程。」,當然人生就是旅程,他總是要踏上的。他躂躂的馬蹄已經去得夠遠了嗎?再也看不見她了嗎?或許根本沒有公主。騎士在不知所終的旅途上,痛苦地體驗到時光中的別離和空間中的距離。好幾次停住腳步,疑心也沒有騎士這個人。但這樣的閱讀是毫無益處的嗎?為甚麼我從未學會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或許我唯一學會的不過是辨別多樣的情感。在越出自身界限的神魂顛倒中仿似置身和聲的中心,並真心相信,即便愛的對象是虛幻的,但愛的感覺是真實的。這充實的感覺在不敘述、不描繪、不論證的情況下得以體現情感的特徵,因而情感的語言不是書面的,而是全面的。
因此對一顆熾熱的心來講,無論那一種說法仍然是非常膚淺的。學者認為從面對死亡到探討復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是從簡單的短句開始的,並且在同一個起點結束的。這不是很奇怪嗎?一八六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筆記中寫下這樣的句子——「瑪莎躺在桌子上。我還能不能再看見她。」,我反覆閱讀並一再思忖,這簡單的句子是如何上升為文學的。就彷彿桌上躺著的她不在別處,就在這裡,儘管已經死了,但我仍是以凝視活人的目光看見她的,只要我仍能以凝視活人的目光看見她,那麼死去的她就跟仍然活著一樣。但我還能不能再看見她。要是死亡便是再也看見不到,那麼唯一的指望便是從死中復活,因為過度的愛不是通過肉體,而是通過精神完成的。我自讀到的句子中既發現一個開端,又捲入一段旅程。但必須待多年以後才明白,並沒有該去的更遙遠的地方。
布朗肖認為閱讀就是呼喊死者的名字——「拉撒路,到外面來。」。就一切事物都應當一去不返這一點來講,我們自閱讀中得以重遇的必然是曾經的欲望。因為我們閱讀為的就是盼望這樣的重遇。因為我們曉得,當我們死了以後,便再沒有充實的感覺了。
是這樣嗎?我自貢布里希的《藝術與科學》中讀到這樣的、短短的一行標題——「你是否仍然記得這時候的維也納?」。讀到時就彷彿真有那麼一個我生於一九〇九年的維也納,並待在那兒,度過我的青年時代。在那兒我曾經學習過、生活過。那時候的維也納對我來講,就是從前幸福的時候、被愛的時候。我自看到的相片中讀到短短的一行說明——「和波普爾一起討論問題」。看到時就彷彿白髮蒼蒼的那個我不在別處,就在這裡。但誰個和我討論問題呢?還要理解甚麼呢?萬事俱休的我清楚曉得從前是怎個樣子的,現在又是怎個樣子的。在懷疑的自願終止中同時體味到生存的甜蜜和苦澀。因而不禁熱淚盈眶,因為得以重遇的,是從前的明月。
你的自由,不過是自由的幻影而已。
——布纽爾——
從前曾經。如今依然。
一九六七年秋,波赫士在一場演講中說了這樣的話——「我已經快要七十歲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份貢獻給文學,不過我能夠告訴你的,僅困惑已。」。儘管話中的準確含意就只有說話者最清楚了,但我不禁猜想,倘若他的寫作及為此付出的全部努力不過是同一事物的雙重幻影,那麼在始終堅持的執念中必然存在設想不到的底蘊,或許是因為在這兒有那麼多的愛,或許是因為在別的地方從未如此深愛過。是這樣嗎?正如貝克特說的,只能如此。只能如此,因為除此以外,再也想不起,曾經有過的,非寫不可的理由。
我寫作,當然是因為有話要說,但亦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了。由於反覆說著的始終是同一句話,因此被禁錮於生存和寫作的同一性中,僅僅意味著有這麼一個人,坐在桌子的面前,並一再追問,「看我幹了甚麼。」。無用的重複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動機,那就是重要的不是說些甚麼,只是說著。只是說著。在被捲入、被束縛的困境中,偶爾難免會想,當初受到的誘惑是甚麼。就彷彿在這兒曾經有過那麼多的愛,愛天上的白雲,掠過的飛鳥,路邊的小花,街角的樹木,夏天的女孩和遇見的每一個人。因為熱愛文學,就是熱愛生命。它既是時代付與的,亦是與生俱來的。記憶中好像曾經經歷一個較有朝氣的創造時期,在同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彷彿一切都是得宜的。但正如馬克思說到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人們不得不直面生活的真實狀況,並且不得不直面相互間的真實關係。或許根本沒有同路人這回事,並最終成為不合時宜的。曾經付與的期望跟所有事情一樣,終須為無力抵抗的誘惑,付出沉重的代價。
但到底是怎樣的誘惑呢。契訶夫是絕望的歌唱家,他的絕望可以總結為以下的道白,一個問,「你在寫些甚麼?」,一個回答,「並沒有甚麼重要的。」。絕望的杜哈絲仍然堅持寫作,並一再追問,是怎樣的絕望呵。帕斯困惑的是——如果這白皙的燈光是真的,這寫字的手是真的,那注視著文字的眼睛是否也是真的。我一再猜想,倘若注視著的眼睛跟進行中的寫作全是真的,那就得問,哦,這個人,坐在桌子的面前幹甚麼。要是俯身向前,他在寫些甚麼。要是靠著椅背,他在想些甚麼。要是臉向窗戶,他在看些甚麼。要是甚麼也看不見,在他空洞眸子裡的是甚麼。他最深的深處到底穿越何種途徑,才能把與生俱來的及後來學會的化作文字。他的書寫到底通過何種語言,才能成為反覆閱讀、不斷回味的文學。他是否終於可以說,這就是我渴望的,我曉得渴望著的是甚麼。
欲望來自躁動的大海,隨著高舉的浪花,成為白色的泡沫。我們欲望的對象是悲壯的幻象,從年輕到年老,總是無力地被誘惑、不斷地被考驗、嚴酷地被耗盡。作者臉對中空的白紙,就仿似撿拾海嘯過後海岸遺留的殘餘物,既追問知道的根據,又追問相信的理由。因而卡夫卡在一封書信中說——「我寫的和我說的不一樣,我說的和我想的不一樣,我想的和我應該想的不一樣,因而最終陷入最深沉的黑暗中。」。大江健三郎在《小說家的生與死》提到——「我心裡常害怕對方這樣問我,你相信自己有小說家的才能嗎?」
我相信自己有寫作的才能嗎?倘若使欲望得以永存的唯一方式便是重新回到最初的起點,那麼我寫作無非是因為在這裡有我值得一過的生活,我願意為最初的誘惑付出沉重的代價。儘管並不曉得愛著的是甚麼,但卻充分體驗,在別的任何地方,從未如此深愛過。是這樣嗎?由於說著的始終是無法說清的各種狀態的交匯地,因而在遺忘與復歸中響起的滴嗒聲彷彿得自神諭。一下問,「你仍在嗎?」,一下回應,「我在。」
我閱讀,為的就是⋯⋯
據說依目的的不同,寫作同一個故事有五百萬種方式,那麼依目的的不同,閱讀同一個故事是否也有不同的體會呢。一些讀者追問故事的內容,一些讀者追問敘事的形式,一些讀者反覆地解讀,就彷彿閱讀中的故事不是有限的,而是無限的。利奧塔認為,再沒有較學習閱讀更沒完沒了、更緩慢、更艱辛、更無利可圖的了。我不禁一再猜想,這會是怎樣的一種閱讀呵。
我閱讀,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儘管當中曾經有過重重的誤解,但終於明白,必然是自農夫的心事開始的。據說農夫對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毫無領悟,但卻慨嘆著說,「要是能操他那份心便好了。」。我對閱讀過的書從未有過深刻的領悟,但也慨嘆著說,「要是能操他那份心便好了。」。因此閱讀對我來講,始終是、仍然是、我追問的不過是,那驅使我自無動於中的虛無中驚醒的是甚麼。
就跟只能在簡單的顫抖中發現音樂那樣,我只能在簡單的短句中發現文學。那驅使我自無動於中的虛無中驚醒的不是故事的內容,不是敘事的形式,不是反覆的解讀,而是得以體現的情感。「她就在這兒。」,既包含一切意思,又沒有明確的含意。「騎士決意不再在有限意義上關心公主,從此踏上不知所終的旅程。」,當然人生就是旅程,他總是要踏上的。他躂躂的馬蹄已經去得夠遠了嗎?再也看不見她了嗎?或許根本沒有公主。騎士在不知所終的旅途上,痛苦地體驗到時光中的別離和空間中的距離。好幾次停住腳步,疑心也沒有騎士這個人。但這樣的閱讀是毫無益處的嗎?為甚麼我從未學會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或許我唯一學會的不過是辨別多樣的情感。在越出自身界限的神魂顛倒中仿似置身和聲的中心,並真心相信,即便愛的對象是虛幻的,但愛的感覺是真實的。這充實的感覺在不敘述、不描繪、不論證的情況下得以體現情感的特徵,因而情感的語言不是書面的,而是全面的。
因此對一顆熾熱的心來講,無論那一種說法仍然是非常膚淺的。學者認為從面對死亡到探討復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是從簡單的短句開始的,並且在同一個起點結束的。這不是很奇怪嗎?一八六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筆記中寫下這樣的句子——「瑪莎躺在桌子上。我還能不能再看見她。」,我反覆閱讀並一再思忖,這簡單的句子是如何上升為文學的。就彷彿桌上躺著的她不在別處,就在這裡,儘管已經死了,但我仍是以凝視活人的目光看見她的,只要我仍能以凝視活人的目光看見她,那麼死去的她就跟仍然活著一樣。但我還能不能再看見她。要是死亡便是再也看見不到,那麼唯一的指望便是從死中復活,因為過度的愛不是通過肉體,而是通過精神完成的。我自讀到的句子中既發現一個開端,又捲入一段旅程。但必須待多年以後才明白,並沒有該去的更遙遠的地方。
布朗肖認為閱讀就是呼喊死者的名字——「拉撒路,到外面來。」。就一切事物都應當一去不返這一點來講,我們自閱讀中得以重遇的必然是曾經的欲望。因為我們閱讀為的就是盼望這樣的重遇。因為我們曉得,當我們死了以後,便再沒有充實的感覺了。
是這樣嗎?我自貢布里希的《藝術與科學》中讀到這樣的、短短的一行標題——「你是否仍然記得這時候的維也納?」。讀到時就彷彿真有那麼一個我生於一九〇九年的維也納,並待在那兒,度過我的青年時代。在那兒我曾經學習過、生活過。那時候的維也納對我來講,就是從前幸福的時候、被愛的時候。我自看到的相片中讀到短短的一行說明——「和波普爾一起討論問題」。看到時就彷彿白髮蒼蒼的那個我不在別處,就在這裡。但誰個和我討論問題呢?還要理解甚麼呢?萬事俱休的我清楚曉得從前是怎個樣子的,現在又是怎個樣子的。在懷疑的自願終止中同時體味到生存的甜蜜和苦澀。因而不禁熱淚盈眶,因為得以重遇的,是從前的明月。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