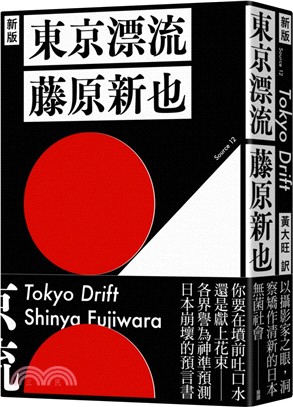商品簡介
一本各界譽為「神準預測日本崩壞」的預言書
「二十年後,我結束旅程,回頭看到的日本,已經呈現一片《我在你的墳上吐口水》般的世界觀。日本人固有的『慈悲』血液,現在不都已經變成了『憎恨』的血液?街上的行人都張著憎恨的弓箭,有時會一齊射向選定的犧牲者,變成一場有益身心的血祭。
為什麼他們的恨意這麼重?
而我只想仔細探究『慈悲』變成『憎恨』的二十年間,日本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慈悲』能改變一個人,
『憎恨』的話語則無法改變一個人。
你要在墳前吐口水,
還是獻上花束?」
--摘自本書後記
日本當代攝影大師 藤原新也
以攝影家之眼洞察矯作清新的日本無菌社會
以近乎私家偵探辦案般解謎的挖掘
令我們窺見繁榮背後的巨大空洞
平面設計師 王志弘 /選書.設計 藝文評論家 張世倫/ 推薦
「對藤原新也而言,在恆河親眼目睹的死亡,沒有看不見的暴力可怕。而他筆下喧囂灼熱的東京,在高度科技化、商業化、快速代謝、大量生產、大量製造垃圾之餘,由於所有的汙穢、負面情緒、黑暗都被排除、阻絕,繁榮背後那種看不見的空洞也跟著日益增大。
生活變成從一個密室,移動到另一個密室的過程。十分鐘前在車站前廣場向過往行人募款的愛心家庭,十分鐘後已經在連鎖餐廳排排坐好,用午後三點的下午茶,犒賞自己對非洲飢民的無私付出。習慣電視節目脫口秀表演的小孩,眼神中已經帶有(電視劇中常見)大人的狡詐。失去船的船夫,在商店街沿路殺了幾個幸福家庭的主婦,然後衝進附近的中國餐館,上了樓上強姦老闆娘。重考生拿著可能是以考試成績換來的球棒,打爆有屋階級爸媽的頭。滿臉幸福的新世紀思想導師,侵吞公款插翅高飛。
這本書裡有一張照片,最能顯現出藤原新也對於這個世界與人生的看法:恆河邊兩隻野狗分食一具泡水屍體。他按下快門的當下是否猶豫,我們不得而知。這樣的照片在日本即使是當成藝術作品,裱框掛在藝廊一角,不難想像還是會引發爭議。追求藝術品味優越的買家,寧可去收藏森山大道、荒木經惟或是藝術掮客村上隆認證的數位輸出作品,不會把這樣的照片放在豪宅的客廳。這張照片,以及他的名言『人就像被狗吃掉一樣自由』,在《印度放浪》之後,仍然不斷以各種形式出現於其他的文字作品之中。」
--摘自本書譯者序
作者藤原新也自1969年起,以亞洲國家為主,遍遊歐亞13年。回國之初,日本發生一連串的冷血逆倫刑案與無差別殺人事件,使作者驚然發現日本社會已有巨大改變,和他記憶中的故鄉大不相同。
日本家庭的中心從「神壇」轉變化「電視機」,「人對土地故鄉的執著」也轉變為「個人對個人的執著」;社會普遍的物質需求心態,從「對欲望的克制」,演變為「鼓勵消費」。
他比較了自己出國前所認識的「60~70年代的日本」,和回國後所見的「70~80年代」的日本,以旁觀者的警醒眼光,針對當下的社會問題提出批判,對當局者迷的日本國民做出提醒。
最後兩章收錄了作者在雜誌《FOCUS》連載的爭議文章,以及後續引發的風波。
篇章摘要
〈莉卡娃娃奉經〉
一九八八至八九年,一位名叫宮崎勤的青年,連續虐殺三名四至七歲女童,並姦屍、食用、分屍後遺棄。凶嫌再三反覆自己的犯案動機,至其被處死時仍無定論。這起事件成為當時日本媒體渲染犯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豬要在晚上載走〉
作者描寫自己公寓四周的人事風景──作者居住在東京芝浦,該地倉庫、廢棄工廠林立,惡臭運河穿梭,是東京少數不以人做主角的無人地帶。就連河裡游魚都死氣沉沉,小孩無精打采。
夜裡馬路上不時傳來尖銳聲響,作者一直以為那是飆車族的車輪摩擦聲,直到一天的深夜散步,他才發現那聲響竟是出自一車準備前往屠宰場的豬隻的嘶鳴。政府雖無明文禁止在白晝運送豬隻,但會散發惡臭的東西,就得在日常生活之外悄悄處理,這早已是都市人的潛規則……
惡臭瀰漫的污水處理場的屋頂,竟有一座無人知曉的巨大公園,宛如都市裡難得的荒涼草原,是海市蜃樓,成為作者沉澱思緒的休憩所。一天傍晚,作者第一次在公園裡見到遊人──一名五、六歲的女童,卻有著老婦的苛薄眉頭,她衝著作者直嚷:「討厭,小優自己一個人玩得正開心……大叔你的家在哪裡!快給我回家去!」作者不禁納悶,究竟是什麼樣的父母,會養出一個這麼彆扭的小孩……
〈兩種十誡〉
因應60-80年代日本社會經濟高度成長,凡事講求效率的時代潮流,日本的家屋形式也產生巨變,家庭的中心從「神桌」轉變化「電視機」;佛祖勸人「克制欲望」的教誨,變成不斷高呼「努力吧!買東西吧!」的電視廣告,社會價值觀出現根本性的變革。佛教的十善戒不再是市民的信仰了,他們改信從欲望做出發點、鼓勵消費的「新十誡」。
〈旅程的冰點〉
日本家屋形態改變之前,日式屋宅多是獨門獨棟,是附有後門、簷廊,與鄰人互動頻繁的開放性建築。但在講求效率的新時代潮流運作下,日本人的屋宅主流漸漸轉為仿照英國監獄或日本兵舍、以使用率為第一考量的國宅形式封閉性建築。
作者認為此為母體與土地價值崩壞的一種呈現,日本人對鄉里的執著漸漸淡化。作者一家原經營日式旅館,但因應都市改革計畫,旅館遭拆除,一家人被迫遷離故里。自此,作者再無鄉愁,選擇離開日本,出國流浪。同時期,亦有大批青年選擇離開日本,他認為自己的行動並非個例,而是時代潮流的產物。
〈小小的黑魔術〉
回到睽違十三年的故土,作者發現儘管日本國民看似健康明朗,市街清潔,生活便利富饒,但和他旅行過的東南亞國家比起來,人民的臉上卻缺乏生氣,少見喜怒哀樂,人民的情感被某種力量封印起來,轉而在某些地下活動發洩。
作者將那些活動稱做「密室」。不同世代有各自不同的「密室」,八○年代初期盛行的「密室」行為是「搞笑藝人秀」和「卡拉OK」。在此之前,則有「學生運動」、「摔角」、「異端宗教」等。在完善的管理社會的水面下,人們各自大笑、歡唱、怒吼……,找地方發洩。然而各自的社群之間往往並無交流,人心也變得更加孤立。作者在本章分析了各社群的共通點與相異處,以及行動背後的成因。
〈行善風潮〉
回到日本,作者發現社會已然巨變,一時無法適應,他擔心自己永遠會像個異鄉人,自覺像個失憶症患者。但他發現,得了失憶症的人不只是他,八○年代的日本人可說全都等同患了失憶症。
作者在本章對他出國前(60~70年代)和回國後(70~80年代)所見的日本,做了整理比較,並預言了下一波的時代潮流──行善和文化活動。
作者舉出1982年5月的三件事──「日本國憲法成為暢銷書」、「全民反核運動」、「義工活動的普及」──為例,並在下一章闡述他的所見與觀感。
〈青天白日〉
出版業的餐會酒席上,一位編輯將自己負責的新書校樣交給眾人傳閱,那本書便是後來成為暢銷書的《日本國憲法》。內容除了條文內容,還搭配了日本豐綠的田園山村風景照,作者不禁感到一絲諷刺,因為他只覺得看到了日本的昔日幻影。書中照片顯然是將「反戰」的訴求視覺化,這或許是正確的做法,不容異議,但仍令作者心生無奈之感……
作者接到攝影師同業的一通電話,要他捐款支持反核運動,他回答「我參加,但這不是因為我『贊同』這個活動,而是因為『我不反對』」。反核,任誰看來都是絕對正確的舉動。但這「絕對善」的壓力,卻也令作者感到無所適從……
這天是母親節,作者打算去享用一頓遲來的午餐,但一走出車站,他突然感覺到幾道帶著「殺氣」的視線,原來是來自現已司空見慣的募款集團。但這回的募款人是一群家庭主婦帶著幼子,在太陽底下為非洲的饑童募款,場面十分溫馨。這「過度開朗的殺氣」令作者心生不解。自己無法理解的事情,就用相機拍下吧。作者匆匆返家取相機,離家前他瞥了一眼時鐘,三點七分,他腦中閃過一絲不安,「三點是吃點心時間……這活動該不會在三點結束吧」。當他趕到現場,果然早已人去樓空……
〈飢渴前線〉
本章對照了三種「密室」──卡拉OK、摔角表演、搞笑藝人秀,與三種「善行」──日本憲法的暢銷、反核、義工活動,發現這些行為的背後,其實都是源自於對正義的傾倒。
但,捨棄了鼓吹良善的「舊十誡」二十年,人們的良心為何會在八○年代初期重新抬頭?作者認為,人們之所以渴望良善,是因為經過二十年「惡十誡」的洗禮,大家都得了良心飢渴症。人們之所以行善、無償付出,其實是為了得到另一種型態的回報──安撫良心的餌食。
不過,在印度的旅行經驗,也使作者體會到:善行的「施與」,是比「接受」更需要謹慎看待的事,因為過剩的愛也可能害人。許多善行名義上是為了拯救他人,卻往往淪為用來拯救自己的偽善。而日本便是個對善行意識尚未成熟的社會。
〈狂熱〉
在本章,作者分享了他在印度旅行的私人經歷,進一步說明何謂「成熟的善行」。
〈漫長的喜劇〉
日本戰後二十年是經濟高度成長期,時代風氣鼓勵消費,人們以「性惡說」為本,一味追求名利,努力賺錢,好獲得「三種神器」(黑白電視、洗衣機、冰箱),帶動大環境經濟發展。這可說是一齣在浪費主義社會上演的幻想「喜劇」。
然而喜劇也會演到盡頭,當人們飽食終日,三種神器的取得不再是難事,人們突然喪失了消費意欲,內需減低的結果是經濟的不景氣。在1952年的美國亦曾發生類似情況,當時不只是經濟亮紅燈,人們也喪生了工作的意欲,當時美國的解決之道為軍事產業的發展。日本無法靠同樣的辦法解套,但所幸,儘管內需衰退,日本國民仍未喪失工作意欲,依然積極工作,因為他們猶在追求「最終神器」──獨門獨棟的家。日本的這場「喜劇」因此硬是比美國多演了幾年。
然而,1981年11月發生的幾起事件,終於讓這場「喜劇」正式變「悲劇」──王貞治的退休、山口百惠息影、一柳展也以金屬球棒毆殺父母的天倫血案。
一柳家是典型的中產階級、「新日本家庭」的代表,他們得到了「最終神器」,但代價卻是「家庭的崩壞」,最後只能悲劇收場。
〈蘋果派家庭的家規〉
二十年來,日本父親汲汲營營地賺取金錢,終於買下自己的家。看似美夢成真,但此時一家人卻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家族精神的蕩然無存、親情的疏離。
中產階級的家訓從「長輩的人生智慧、舊十誡」,轉變為「增加收入→擴大生產與需求(新十誡)→獲得三種神器→蓋自己的房子」,但當最後的目標達成,一家人頓失目標,此時日本父親也不再有能耐帶領家人,家族精神陷入了真空狀態。
在此情勢下,日本父母選擇了最簡單的辦法──把對「絕對善」盲目的信仰,對「絕對惡」盲目的排斥,當做新家訓。親子之間,除了餐桌上非洲難民兒童的照片,已經沒有共通的話題。
對「物質」的追求已無法滿足人心,人們轉而追求「精神」(文化),在1982年5月發展出新的時代潮流──行善文化。
不成熟的善行為何有害?因為未經思考的善行是種慠慢,導致對惡的認定也會變得短淺、偏狹,因此孕生出新的暴力,在社會上引起新一波的「魔女狩獵」──將自己不習慣的人事物都視為異端,予以排除。
〈東京漂流〉
1981年7月22日,日本關東一帶雷電大作,都內水患頻傳。像這種大自然發威的日子,作者稱做「自然之日」。在大自然的威嚴面前,文明社會破綻百出,洪水一過,平日試圖掩藏的腐敗臟腑再也隱瞞不住,袒露在外,惡臭撲鼻。
眼見這一幕,作者心想:自己或許也有能力扮演一種類似「大自然」的角色,揭開都市生活裡的腐敗真相……
作者淺談與雜誌《FOCUS》合作的緣由經過。
〈FOCUS〉
收錄作者在雜誌《FOCUS》的連載文章五篇。每篇都會交代案件經過、輿論反應、作者對該事件的看法,以及刊登照片背景、拍攝動機與手法等等。
連載一、偽作‧深川街頭隨機殺人事件
連載二、鋁棒弒親事件
連載三、東京最後一隻野狗‧有明菲利塔之死
(連載三於本書最後刊出。)
連載四、阿南達瑪迦協會瑜珈老師失蹤事件考
連載五、美國淵賞楓行‧車掌小姐情殺案棄屍現場
連載六、幻之城‧絲綢之路
〈人就像被狗吃掉一樣自由〉
針對《FOCUS》第六回連載內容的迴響,作者做出回應。由於三得利的偽廣告事件,觸犯媒體禁忌,該回的連載文章遭到編輯部大幅改寫,作者因此決定中斷雙方合作。本章刊出編輯部竄改過的文章全文。
〈東京漂流〉THE DAY AFTER(專訪)
作者接受雜誌專訪,細數自《FOCUS》連載,至《朝日新聞》「丸龜日記」專欄的書寫,眼見宮崎事件、鋁棒弒親案、深川街頭隨機殺人事件一樁一樁發生,內心種種無力茫然的心情。
作者簡介
1944年出生於福岡縣門司港。 在東京藝術大學就讀時,決定離開大學校門,度過了十幾年的流浪各國的生活。 80年代所著《東京漂流》,作為優秀的批判文明類書籍成為了最暢銷書。 著作中有《印度放浪》《全東洋街道》《美國》《巴黎的水滴》《合起沒有任何願望的手》等。獲 得過木村伊兵衛獎,每日藝術獎等。
目次
莉卡娃娃奉經
豬要在晚上載走 魚影 車輪 狐狸般的火 海市蜃樓 小女孩
兩個十誡 老象 力保美達 轉位
旅程的冰點 家貓 逆旅
小小的黑魔術 旅途上帶回的草 密室 拼圖 加州 「後記」
行善風潮 基因 巫女 八二年五月革命
青天白日 日本國憲法 核武 家庭
飢渴前線 晴天幻想 誘餌 牛奶
狂熱 霍亂 枕經
漫長的喜劇 劇本 BUY AND HAPPY 田園調布 八○年十一月
蘋果派家庭的家規 法國麵包 女巫
東京漂流 熱界雷 生蠔 碼頭 斷罪 陽具 惡靈
FOCUS 連作 攝影 不動產照片 方舟
人就像被狗吃掉一樣自由 地獄極樂 嬰靈 十字架
«東京漂流»THE DAY AFTER(專訪)
後記
書摘/試閱
首先,我要說明本次刊登的狗吃人照片。
這是我以前拍的照片,也收錄在過去出版的印度攝影集裡。我並不喜歡拘泥於自己過去的工作內容。雖說有些攝影師,會把自己的作品送進銀行保險箱保存,但對我來說是難以置信的事。過去的工作於我,就像是一條條破舊的抹布。所以我過去留下的底片,總是積滿灰塵,也有很多根本已經發霉而無法印成照片。
但是只有這張「狗吃人」的照片,跟其他的照片不一樣。這張狗啃咬人類死屍的圖,既是記憶猶新的事實,到了現在還是構成我世界觀的潛在規則。
此外,不同於六○年代的蓬頭垢面、埋頭苦幹,經過七○年代至八○年代,累積了一定程度的財富,並進入安定經濟成長時期的日本人,也比過去更注重周遭的清潔。所以所有不見容於中產階級社會中的穢物、異物、危險品或等同物品,都被巧妙地封印並且抹殺殆盡。
但是在我看來,當人類企圖消滅體內的病原體時,同時也會誤殺維持身體健康不可或缺的益菌。在這種意義上,社會正在不斷朝著自我破壞前進。
我並不喜歡激進派的思想,但是這樣的社會為了保持它真實的意義,我還是主張一定要有人出來散播一定劑量的毒素與細菌,以保障大眾的健全。
所以這張「狗吃人」的照片,在這個步步走向自毀的時代進程中,被我當成一種益菌看待,也成為我無法割捨的一個事實存在。我不辭辛勞從印度拍回這樣的現實讓各位讀者看,所以我不會把這張照片當成普通的「攝影作品」,掛在無聊的空間裡,而更想把這兩隻狗放到這個社會裡,讓牠們實際去咬個什麼東西來看看。
這張「狗吃人」的照片自從完成以來,一向乏人問津。當我從印度帶回這張照片時,我曾在一份畫刊上有一個叫〈印度行腳〉的連載專欄。這個連載的最後一回,我本來想以跨頁刊登這張照片,最後沒有被採用。我對於他們撤回請求的判斷標準沒有意見,但是如果以另一種判斷標準來看,則會變成這樣:
幾年前,我記得大概是越戰快要結束的時候。同一份畫刊上刊登了一幅引發轟動的照片。一個前線的美軍士兵,像檢枯枝一般玩弄著一個被炸彈炸死的「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士兵的殘骸。這張照片引起日本社會的大肆批判,也在雜誌社內引起很大的爭議。所以面對我所拍的這張狗與屍體的照片,編輯部的考量即使跟刊登那張越戰照片時一樣,在我來說也是理所當然。
但可能是因為編輯部也注意到,越共的屍體照與印度人的屍體照,其實具有不同的意義:單純說來,前者是異常心理,後者是自然死亡。即使只是兩具死屍,竟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義。
越南的屍體照有什麼異常不用多加說明,我覺得不需要浪費太多篇幅;在此我還是要為不熟悉印度日常習俗的讀者說明,為什麼印度的屍體照就顯得正常。
眾所周知,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簡單來說,佛教就是「自然主義」的宗教。自然主義所指的並不是放任什麼都順其自然,而是順應天地萬物內在的道德規律,參加社會生活的方法。既是所謂的「他力本願」,也不是一套強制性的主義。
躋身工業先進國的日本,現在幾乎已經越來越難以這種佛教的方式過生活了;在自然影響力仍強大的印度,還是以這種方式生活。人做為滄海一粟,生命與狗、昆蟲與其他的生命平等,並未因為生而為人而特別尊貴。
有一起事件可以充分表現印度人的生死觀。大約十年前,日航的客機在印度一個農村墜機,造成幾位農民罹難時,印度人要求的賠償金額非常低,反而造成日航方面的困擾。即使印度的生活水準僅及日本的十分之一,賠償金額還是少了兩位數。日本媒體對此大感驚訝,但在印度好幾年的我早已見怪不怪,因為我知道人命並沒有那麼值錢。人,也不過是生物的一種。
所以,如果其他的生命死後沒有墳墓,印度人也不需要。他們死後不是火化灑進河川大海裡,就是鳥葬或直接丟進河裡。死後重歸自然。
即使被一群野狗啃食,也極為自然。
也就是說,人類是如同被狗吃掉一樣自由的生物。
對此現象,我甚至覺得感動,認為是很美的場面。印度果然是世界強國。如同拍攝綻放的野花一樣,我對著路邊按下了快門。
當時我拍下了一個正正式式的宗教場面。
但是在日本的報導攝影媒介上,這種真正的宗教照片被禁止刊登。這件事剛好也發生在一九七三年。當時的日本社會,如同我在先前所說,由於經濟的停滯,人們開始清掃周圍的環境。我觀察到這種如同「益菌」的照片,與越共的屍體一起被當成異物與穢物被清掃一空。
而我覺得讓持有無常觀的日本民眾看這樣的寫實照,並不抵觸日本人的審美觀或傳統價值。在中世紀的日本,狗啖食人的死屍是繪畫中常見的自然風景,也常有僧侶透過連日「白骨觀」等觀想法得到開悟。如果把這張照片當成現在的「白骨觀」,早已不被日本社會架構當做正常的死亡看待。
我看到這個社會,正在透過一連串的隱蔽,企圖將死亡這種嚴肅的事實抽離人生藍圖。
這種穢物、異物的隱蔽作業,不僅是由國家或地方行政體系執行,連住在團地的家庭主婦,都有組織地雷厲風行,但是在他們的頭上,還有一個更巨大的組織在刻意推進這種排除運動。
那就是商業手法的世界。
商業手法已經主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環境。這種日常生活思想,正在企圖單方向地向大眾不斷宣傳人類或世界的存在方式,極為可怕。
在商業手法的世界裡,人與生活的負面要素全被排除在外。商業手法的世界觀要大眾歡樂,所以人類與生俱來的憤怒心必須被去除。有歡樂,不能有悲傷。所以商業手法的世界裡,欠缺怒與哀的喜樂之人如洪水般氾濫。所以渡邊貞夫之類的名人,上了廣告也只會爽朗地笑而已。
身而為人都想過得快樂,這不是一件壞事。然而只有喜樂而無怒與哀的人,只能說他們心智不成熟。商業手法的策略,就是在我們的周遭圍滿了這樣的不成熟者,人格育成會產生偏差也是理所當然。
很久以前,曾經有人說過:設計之中不應該有哀愁,而最近的廣告之中,只有極少數會出現「哀愁」的成分,使整個廣告有點人味,至於「憤怒」還是完全缺席,所以當然不會出現以死亡或瘋狂做為主題的廣告。就如同現代社會如何對健全的大眾隱瞞死亡的事實……或說在這個更講求商業效益的社會之中,死亡、屍臭與死亡的氣息正被完整地密封起來。我甚至認為,商業化環境對人的物質化管理,已經超過了行政體系的影響力。
很早開始,我就有一股很激進的衝動,想試著把「會吃屍體的狗」丟進這種廣告化的環境裡,並靜觀其反應。如果有機會與廣告界的朋友見面喝個兩杯,我一定會半開玩笑地問他,有沒有可能讓我拍一支這樣的廣告?當然他們也不可能找來真的屍體,所以根本是小孩子玩笑一樣的空話,說了也是白說。即使是玩笑甚至是挑釁,我都有幾分認真。
這次我更認真,索性自己在文章裡弄了個假廣告。
事實上在排版的時候,我幾乎沒有花時間考慮狗應該放在什麼位子。因為是絲路上的狗,放回絲路是理所當然的事。提到絲路,我又想到了最近瘋狂流行的偉大NHK〈絲綢之路〉電視節目,以及偉大三得利酒廠的〈絲綢之路〉陳年威士忌廣告引發的「冒牌絲綢之路事件」。
為什麼我會說他們是冒牌的?因為他們採取了跟廣告世界中一模一樣的手法,把人世間的哀、怒、死亡、瘋狂穢物異物什麼的全部排除在外。他們不惜成本,千里迢迢來到絲路上,為的就是用日本文化的手法強拍他們理想中的絲綢之路,並且將其中的哀怒死亡、宗教污穢異物全部剔除,讓那些懷著中產階級意識的觀眾,可以在電視機前一邊喝著泡好的即溶咖啡,一邊聽著電子音樂的飄渺音色,一邊享受盆栽般的「夢之城」奇觀。這種絲綢之路,既是矯枉過正的「夢之城」,也是海市蜃樓般的幻象。
製作三得利陳年威士忌「夢之城」篇的創意總監、文案與廣告導演,剛好都是我認識的朋友。以前我曾在酒席上裝瘋賣傻,答應他們合作一支三得利的廣告。
事實上,我本來打算把這張「狗吃人」的負片交給他們,請他們做出一個仿作廣告;結果打電話去廣告公司一問,有兩個不在,一個藉機偷溜。
從有人藉機偷溜,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個尖酸刻薄的人。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執行我的計畫,並且看看讀者有何反應。
人就像被狗吃掉一樣自由
〈東京漂流〉連載第六回的主旨,並不在於否定商業手法或是廣告宣傳的存在。
即使在共產國家或走社會主義路線的國家,仍然存在著廣告。「宣傳」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存在已經相當明顯,而我們每天被迫處在這個環境裡。在商業國家,商業手法更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不管是街角的鰻魚專賣店,在七月二十日掛起了印有「土用鰻魚熱賣中」的紙條,還是巨大企業耗資幾億促銷商品,不僅是商業手法,也是廣告宣傳。
在連載第六回發表之後,部分讀者看過我的文章後,嚴詞攻擊我完全否定商業手法。如果你仔細看我的文章,一定可以看出我的意思,我並不否定商業手法的存在。我既不如過去那些完全否定資本主義的學生運動人士一樣懦弱,也不再年輕。
我立論的前提本來是,商業手法是構成我們生活環境的一部分。我以此探討現代商業手法的型態,以及商業手法創造價值扭曲精神土壤將帶來的危險性。
為了說明這種危險性,我要重新提出我的問題。
「為什麼六○年代後的日本社會,會集體管理民眾,並且排除一切穢物義務或前近代的人性化生活呢?」
對此我的看法如下:
將產能、產量與擴張視為至高無上價值的現代型商業手法,將人與人性化生活做為生產的功能看待。
為了提升生產效率,將每個人都當做一顆螺絲釘或符號,更方便他們的管理。
所以影響產能的「感情或感性行為」便成了生產力的障礙。
日本生活文化特有的前近代型人際關係或社會構造,也成了產能的絆腳石。
也就是說,世界上那些妨礙生產、擴張與產能的負面元素,在此都成了穢物異物;現代商業手法的宿命之一,就是要盡力排除這些元素。
我們是否應該依照這種現代商業手法的特性,考察六○年代以後的大眾生活樣式,以及設施的齊全化?如果以這種商業手法的特性去看廣告宣傳,發現其中擁有一樣的方法論,也是極為自然的事。
現今中產階級心目中的前近代大眾價值,或是潔癖式的排除性,都是商業手法傳遞給大眾的訊息,並且是大眾模仿廣告中的價值觀產生的一種生活意識。
商業手法透過影音感化大眾,並傳遞訊息的特點,與傳教活動相似。現代商業手法下的商業手法,已經成為像宗教般左右人的生存方式與價值觀,一個最大的「傳道」。
但是這種傳道之中,暗藏著一種殺意。這種殺意將人與事物明暗兩面中的光明面無限擴大,並且將生存、存在整體的另一面向完全抹殺。宗教的傳道中包括了類似「地獄思想」、「極樂思想」,或說「生」與「死」,也就是生命中光明與黑暗的整體性;現代商業手法下的傳道,則帶有一種偏執於「極樂」或「生」,而消滅其他極端的宿命。
一九六○年後出生的嬰兒,從三歲起便必須接受極端計算且具效果,視聽覺以及言語的「傳道」餵養。孩子們欠缺掌握人與人際生活全體形象的能力,在無知的環境中矇蔽自己,並且被教育成只在乎自己的生理性以及個人情操,最後養育出一個一個的肉體。在「生命總體像」被抹消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失去了掌握生命全像的能力,漸漸失去對商業價值以外其他價值的理解,並開始對「不可理解」的事物懷有敵意,並極有可能將之滅絕。
例如:
「人味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爺爺變髒了。」
童言無忌中,確實表現出這種傾向。
在法國或西德等西歐國家,對於商業化的環境有各式各樣的限制,並使廣告商形成生存思想;在日本完全沒有這種先進國的思想。
缺乏這種思想的結果,就是八○年代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情緒中顯著地出現一種叫做「安樂症」(euphoria)的精神症狀。我主張這種症狀應該列入八○年代的精神分析用語。「安樂症」做為學術用語,在描述上缺乏精準性,所以我稱之為
「幸福過多症候群」。
這種「幸福過多症候群」的患者,心理上欠缺的部分與商業化訊息的一樣,具有嚴重的精神障礙。他們身上感受世界最遠端的感官知覺已經開始退化,取而代之的是對未知事物不加理解便加以排除的歇斯底里性神經知覺肥大。
這種八○年代的「幸福感過多症候群」,從各種蛛絲馬跡來看,都可以確定是「幸福感過多性廣告文案」長期滲透下養成的精神障礙。
這種症候群的危險性,在於排除侵襲自己幸福感的一切外在因素。患者會因為聽見隔壁鄰居的聲音,覺得自己的幸福感被侵犯,而藉故動手殺人。更因為「死亡的意義」在這種商業化的環境被抹殺,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世代,也極端缺乏對人生必經「死亡的意義」之認知。
在某種程度上,住在商業化島國的民眾,會自行模仿廣告中的形象。進入八○年代,只要民眾欠缺覺醒性,想必還是繼續成為模仿者。這種「廣告訊息」做為八○年代的神諭,在這個商品文化充斥的八○年代,使我感受到它正面臨二十年來最大的危險邊緣。
在高度成長的六○年代,廣告訊息都還是以眾所周知的「商品」消費慾望為訴求,並且不斷高呼品牌的口號。七○年代,人際關係的疏離深化,並開始出現冷淡與寂寞的時候,廣告便轉而訴求「愛」、「親密」與「溫柔」的基本調性。
八○年代的廣告訊息,更因應時下的「商品文化至上主義」思潮,開始玩弄商業化的文化(商品文化),也就是所謂的「世界觀」。
換言之,現代的神諭已開始從過去的刺激購買慾,轉變成現在對「思想」的窺探。但是這種「思想」仍然是一種廣告訊息的宿命:缺乏生命與生存整體像的空殼子。
八○年代的廣告訊息,對於無知者來說,正轉變成披著商品文化外衣的一種麻煩。
我在〈東京漂流〉第六回中,引用了最能做為八○年代廣告典型的三得利促銷廣告為例子。
因應操弄假絲綢之路文化的廣告手法,我使用了長久以來在亞洲旅程上習以為常、有別於世界觀的亞洲形象與之對抗,也是我引用三得利促銷廣告的理由之一。
我以此為舞台,將商業手法下傳出的訊息中永遠被排除的典型之一──「死亡的意義」是否仍有存在必要,以一句廣告文案對商業化的環境提出我的疑問。
人就像被狗吃掉一樣自由
我以這句文案與一張照片,做出一篇表現出「商品文化時代」共通的思想廣告。
我想這句文案與這張照片,在當下已經超越商業化批判的領域。這是我依據自己的簡短歷史,向「文明」這個巨大體系發表的一則自我宣傳「思想廣告」。
然而很不幸地,我在F週刊上已經連續六回的連載,卻因此被迫腰斬。但這也不至於造成太誇張的問題,在這樣的社會上,這種狀況我已經習以為常。
看似自由的社會體系底下,根深柢固的「禁忌」其實比以往更多。即使現在社會對於性表現幾乎可說是完全解放,背負對政治、重大新聞或宗教團體批評使命的大眾傳播媒體,也能像追求自我淨化一樣,每天播報類似的新聞。在另一方面,對於社群歧視問題、天皇問題與商業手法批判等話題的禁忌,也隨著時間逐漸擴大與硬化。
我的連載〈東京漂流〉被腰斬,便是因為我的文字與視覺牴觸了「批判商業手法」的禁忌。然而我無意以扒糞或感情用事的水平,描寫整個事件的過程。如果我只執著於誰如何阻止我再寫下去之類的描述,不僅會減輕事態的重要性,還會白費我這本書一開頭的宗旨。
但是我還是希望各位讀者明白,這並不只是於現代的某家特定出版社或某家公司才有的特殊狀況。應該保有言論自由的媒體,現在也漸漸成為巨大商業勢力的爪牙。這起事件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為了避免自己發生不測,所以我特別在此做這樣的聲明。
如同我剛才的商業化論述所說,商業化時代的思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就跟政治一樣重要,也是身處商業大國的我們全體都應該重視的問題。
希望我們不再把現代文明背負的問題當做禁忌,商業化體系與大眾傳播媒體也應該具備允許自由討論的度量與決斷力。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