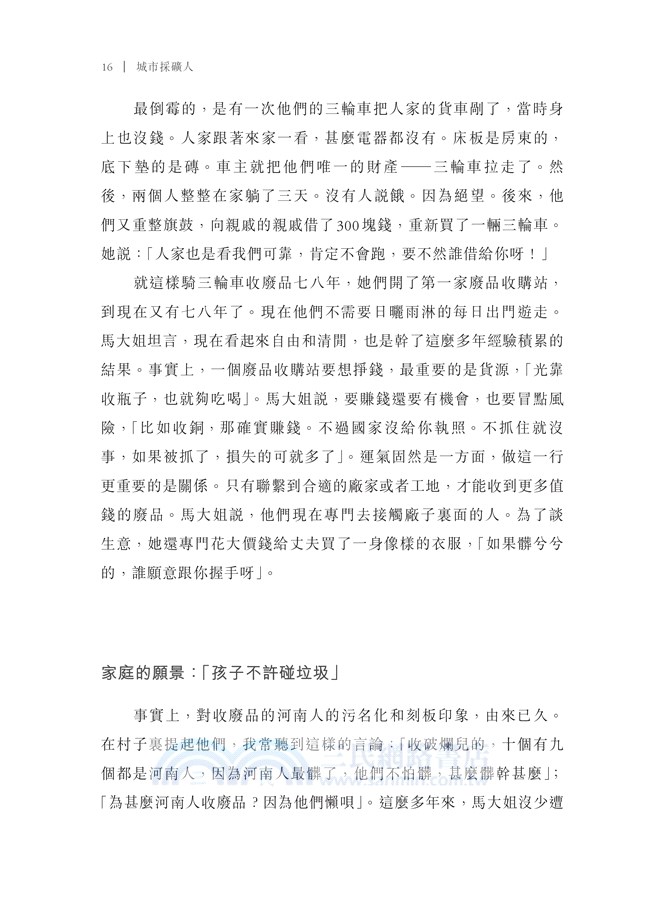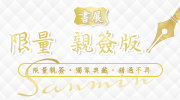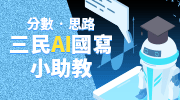商品簡介
——陳冠中(作家)
「收廢品的人」是都市生活中的「隱形人」。人們天天看見他們,但又似乎從來看不見他們。《廢品生活》引領我們去端詳凝視這些人——不僅僅是去發掘他們的卑微與掙扎,更是去發現他們如何在卑微與掙扎中構建自尊和「意義」,以此捍衛人之為人的完整。富有同情但不煽情,好看但不失學理,是一部理解當代中國的人類學力作。
——劉瑜(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買買買,也是丟丟丟。嘉明與劼穎的《廢品生活》是一部描繪廢品與人的民族誌,也是一幅「人類世」(anthropocene)的山水畫,揭示垃圾並非中國經濟奇跡的廢渣或副產品,反而是現代生產方式的核心,所謂垃圾圍城,垃圾就是當代生活的隱喻。作者以人類學家的眼光,以物觀我,以微知著,從廢品出發,觀照中國的盛世背後,社會的建構重組,空間的流轉變幻,百姓的得失尋覓。
——盧思騁(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總幹事)
在香港做垃圾研究,對象除了消費者、賣力的清潔工,還有經常被遺忘的拾荒者。拾荒大軍有多浩蕩?說不準三萬、四萬都有人說過;他們究竟是誰,過問的人不多,只留下僂背彎腰的長者和弱勢者的綜合印象。拾荒者把半隻腳踏進堆填墳場的可回收物拯救出來,是名副其實的環保先鋒,他們往往成就了功勳卻無人記起。感謝作者,為這些減廢朋友填補一筆空白。
——朱漢強(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
作者簡介
張劼穎,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研究領域為環境人類學、廢棄物、社會運動和科學技術社會研究(STS)。碩士畢業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曾發表出版物包括《搖滾節》、《垃圾從業者的工作、生活和主體性》、《中國高速城市化和消費社會背景下的垃圾問題》;譯作《如何做質性研究》。
目次
導言:廢品的政治與文化 / vii
第一部分 城市採礦人:廢品回收作為非正式經濟 / 3
1. 回首跌宕京漂路:一個女收廢品人的口述創業史 / 13
2. 低端企業家:北京收垃圾,老家拾尊嚴 / 23
3. 底層的生存策略:從「超生游擊隊」到「黑心小作坊」 / 31
第二部分 垃圾場上的家園:拾荒社群的組裝家庭和想像的老家 / 43
4. 拾荒父子:離愁與創業夢 / 55
5. 年輕的母親:垃圾場上育兒的苦與樂 / 67
6. 拾荒第二代:垃圾大院「回娘家」 / 75
7. 「這就叫自由」:拾荒者的老北京 / 85
第三部分 廢品的空間:城鄉交合區 / 97
8. 冷水村的引路人:接駁城鄉的黑車師傅 / 111
9. 老鄉鄰居交錯相逢:裝修父子的教育夢 / 123
10. 垃圾場上的高跟鞋:時尚、尊嚴與母愛 / 133
結語:廢品生活 / 141
參考文獻 / 145
書摘/試閱
導言 廢品的政治與文化
「垃圾圍城」
沒有人喜歡垃圾。垃圾骯髒,而且是「沒用」的!不是嗎?沒有人喜歡骯髒而且沒用的東西。城市生活處處光鮮亮麗,整潔如新。在公司、學校、住宅樓、大商場裏面流連,清潔工會隨時掃去髒東西,把垃圾丟藏在最隱蔽處。其實,我們在城市裏大量消費,大量丟棄,不但消費會帶來快感,扔掉東西也是種樂趣。拆開新的商品,把包裝扔掉。吃不完的飯菜,可以倒掉。東西多了、舊了、不想要了,可以丟掉。現代都市人,誰不能領會「喜新厭舊」的要義?這種種消費的增長,同時導致垃圾以爆炸性的速度激增。
中國過去二三十年迅速發展,造就了驚人的經濟奇跡,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雙重作用,使得城市擴張及其人口膨脹;城鎮居民急速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物質主義,衣食住行日新月異,消費品不斷推陳出新,耐用品也大大減短了產品壽命。在「保八」(保持國民經濟生產在8%增長率)、「電器下鄉」(把電器消費品推廣到農村)、結婚要有房又有車等夢想口號下,更多的消費品被生產出來,拋棄更多為了消費更多,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一個不可逆轉的現象。同時,這過程也催生了大量的廢棄物。各地政府儘管不斷加建垃圾處理設施,卻始終追不上不斷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造成「垃圾圍城」之局面。為了應對這個困局,多地政府提出興建垃圾焚化爐,又遭遇民眾激烈反對,環境維權的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簡而言之,當代中國在享受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已經泥足深陷於垃圾之戰。
在正規的垃圾處理體系之外,每個城市還有一些群體,天天與廢品或垃圾打交道。他們寄居在城市的邊緣,垃圾成了他們的生產原材料,成了他們在城市建立生活、獲取收入的資源。這些就是人們常說的拾荒者、廢品收購者,或者是「收破爛的」、「撿破爛的」、「收買佬」。他們在城市似乎既是無處不在的,又是「隱形」的──我們習慣了他們在城市的角落,隱約知道他們在垃圾或廢品中勞作,但幾乎對這個群體一無所知,我們不想瞭解他們,甚至有意地忽略他們。
本書研究的目的,是瞭解這個每天幫助城市排廢、卻不受關注的群體,從廢品經濟和空間的角度,重新看中國城市化。本書所研究的冷水村,是個位於北京六環外的一個「城鄉交合區」(這空間會在本書第三部分詳細解釋),裏面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收廢品大院,這些大院即是儲存、處理廢品的場所,同時是廢品從業者的家園、廚房、休閒場所,以及他們小孩的遊樂場。冷水村只是當今盛世中國的龐大垃圾經濟的冰山一角,但非常具有代表性──城市垃圾被運往城鄉交合區處理,污染物被盡量外移;政府無力應對龐大的垃圾量,容讓廢品回收群體以自己的方法處理、再循環,也容讓這群體在城市邊緣謀生。
收廢品者在當代中國是一種雙重的污染符號──他們不但是城市的外來人口、農民工,同時又很髒,有點神秘甚至危險。因為每天與垃圾這種骯髒的物質打交道,他們被再度污名化。可以說,如果農民工是城市居民的「他者」,廢品從業者便是所有現代城市人的「雙重他者」。研究當代中國的收廢品群體,不但讓我們瞭解這個在城市化過程裏一直維持著「非農非城」的邊緣性身份的群體,也瞭解我們每天的消費行為和這個群體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廢品生活》這本書希望把這個社會建構的自我和他者重新聯繫在一起。通過審視廢品、廢品經濟、收廢品人,我們嘗試重新看待這個城市的消費與浪費,重新理解廢品回收經濟和空間如何與我們息息相關。與其說我們對所謂「邊緣的」、「貧窮的」撿破爛人群感興趣,不如說我們希望解構這些二元的建構,透過瞭解廢品從業者的工作和生存空間,進一步認識我們的城市成員、城市化,以及中國特有的現代性問題。
反思廢品的文化意義與物質性
垃圾──在通常的理解當中,完全是死物、廢物,無用的。但如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早在1960年代的著作《純潔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指出,不潔物(dirt)在每個社會,不論現代還是原始,都是相對性的,而且是相當重要的社會文化符號。她指出人們認知不潔物,不在於它本質上就是骯髒的,而在於它的曖昧、不可界定、不確定,也在於它安排和界定一個社會中甚麼是對與錯,甚麼是神聖(sacred),甚麼是凡俗(profane)……有研究者指出,垃圾處於一個「被抽乾意義的異化的物的世界」,而正是社會和文化賦予其「可被丟棄的」、沒有意義和價值的屬性(Kennedy 2007)。 從這個意義上,審視污染物(pollution)的社會意義不在於研究它的內在性,而在於它的曖昧性(ambiguity),它與我們社會系統中其他物的關聯;在於研究我們如何追求一套新的衛生標準,如何追求在一個用完即棄的社會(disposable society)對待本來「有用」之物(Harvey 1991)。
文化理論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稱垃圾處理者為「現代社會裏的無名英雄,日復一日地更新和突出正常與病態,健康和治病,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接受的和丟棄的,應該的和不應該的,人類宇宙空間的內在和外在的邊界。」(2006: 21–22)換言之,垃圾處理者每天的勞動不但是幫我們的城市「排污」,減少我們堆填區的負擔和垃圾焚燒所排出的污染物;他們主要的貢獻,是防止因為有用和沒用的界限模糊而可能產生的混亂。試想,如果垃圾在我們的住宅區堆積如山,如果廢棄物讓本來光鮮潔淨的消費場所臭氣薰天,將會是怎樣令人難以忍受的場景?在這個意義上,收廢品者和清潔工人為社會生活的正常運作作出貢獻,日復一日地維護著日常生活中物的秩序,默默地拿走不正常的、病態的、不想要的物質,維持一個社會的「正常規範」(social norms),也就是一個社會「應該有的樣子」,它是如此正常,以至於我們以為事情本該如此。在當代中國,正是這些背負著雙重污名的收廢品人,為資源回收再用和環保做了莫大的貢獻。也可以說,他們直接維持中國現代性的光潔的那一面,不讓垃圾充斥和呈現在我們的視野,不讓我們哪怕有一刻懷疑經濟發展,看見骯髒、浪費的那一面。
中文的文獻當中,對來自農村的拾荒者的研究,大多是視之為當今中國城市化過程當中,城市管理所面臨的一個「社會問題」;換句話說,將這個群體視為難以有效納入管理的一群人(張登國2007;趙澤洪等2005)。這個角度跟國外的研究不謀而合。中國以外關於收廢品人的研究,同樣側重發展中國家裏都市管理面對的問題:城市的高速發展,遠遠超過原來的政府廢品處理承受力,大量的都市廢品產出和處理需求,又吸引人口眾多但沒有特別技能的農民轉移至城市。這些城市農民工透過撿收和轉售垃圾,脫離農村和進入城市謀生。結果是收廢品成為一個主要的非正式經濟圈,不但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也同時提供謀生工作機會給巨大的農民工人口(Wilson, Veils and Cheesman 2006)。在部分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收廢品人甚至佔總體人口的2%,而且廢品經濟也是非正式經濟活動之中最重要的項目(Medina 2007)。但這個沒有政府規管的非正式經濟,也同時衍生很多環境衛生、工作安全、社會歧視、貧民窟,甚至童工的問題。事實上,收廢品人的工作和居住環境惡劣,經常要處理醫藥廢品和工業產生尖銳的廢品,廢品所流出來的污水,又是他們的生活一部分(Sasaki et al. 2014)。
很多發展研究都帶著同情的眼光,強調這個群體的「邊緣性」,探討這個群體在所移居的城市當中的底層、邊緣、弱勢、草根的地位,與當地居民的衝突性關係,呼籲一種對他們的尊重和生活工作條件的改善(陳岳鵬、劉開明2007;孟祥遠、吳煒2012;張上翔2007)。也有研究傾向確認這個群體的工作,認為從環境保護、資源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這個群體作出了貢獻,尤其是他們的回收行為,產生了未曾預料但不容忽視的經濟貢獻(葛蓓蓓2010;郭素榮、陳宗團2000;陶友之2007;周燕芳、熊惠波2011)。國內外的研究都承認,收廢品是一個農民工在城市謀生的策略,但未必能讓他們在城市裏脫貧。而且,無論在中國、印尼、菲律賓、印度或南美,收廢品人的性別、年齡、老鄉地方、種姓、種族差別,都在他們之間構成層層的僱傭等級、權力關係,甚至矛盾衝突,使他們難以團結,也難以把他們納入常規經濟(Adama 2014; Hayami et al. 2006; Sasaki and Araki 2013)。在巴西也有研究發現,婦女收廢品人透過組織合作社,來申明她們的工人和公民身份,教育公眾有關收廢品人的社會(Machado-Borges 2010)。
此外,國內外的社會學家已經對拾荒人和收廢品者作出很多細膩複雜的書寫,探索社區內部的生活以及複雜的關係網絡,尤其是這個群體的「社群性」問題。申恆勝(2013)注意到這個外界看起來封閉的社會世界內部,具有多重複雜的關係,包括老鄉之間的「幫帶」關係,以及同行之間對資源的競爭關係。陳偉東和李雪萍(2002)觀察到,在湖北的一個拾荒群體,具有自發的秩序,形成了一種具有多重契約關係的「自治共同體」,為了更好地跟外部的政府機構和所在社區互動,甚至成立了「破爛王黨支部」。周大鳴和李翠玲分析了拾荒者的主要工作內容和收入組成,指出工傷和病痛在拾荒者當中十分常見,無論是拾荒者還是其子女,社會資源都非常匱乏(2008)。他們還觀察到,廣州的拾荒者一方面把鄉村的網絡關係以及生活方式,帶到了新移入城市當中的拾荒聚落;另一方面,這個聚落又兼具城市生活的各種特徵;此外,這個聚落還維持著相對活躍的公共生活(2007b)。垃圾場具有一種「空間政治」,在其中有多重的「關係叢」發生著作用,這些關係包括國家、老闆、拾荒者,以及所在地村民等多種行動者的複雜關係(
《廢品生活》跟這些社會學研究的取向類同,都強調進入拾荒社群的內部,而不僅僅是從外部或自上而下的,把這個群體簡單地當成是麻煩的製造者或者同情的對象。但我們側重的,不但是都市發展產生的社會不公義、經濟不平等。因為這個角度還是把「垃圾」或「廢品」當作一種底層農民工的經濟生產資料。我們的研究重要之處在於重新審視廢品,除了是一種具有衍生經濟價值的物質之外,還是一種不斷生產文化價值、定義社會邊界,甚至是身份政治的、有能動性的物質。帶著這個不一樣的問題出發點,我們的研究更多探討收廢品人與垃圾糾纏不清的關係,並因此帶出來的收廢品人主體性的建構,和一個更動態的拾荒聚落網絡。
本書試圖切入廢品的社會文化意義。雖然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樣是收廢品人,我們講述的不但是他們與廢品的經濟關係,更是他們與廢品建立的文化社會關係。我們想要提出的是,廢品其實不斷在建構人和環境的關係、人和他人的關係,也在參與建構一套新的價值觀,甚至如既有的研究所言,建構一套新的道德觀(Hawkins 2005)。 研究文化與廢品的著名學者Gay Hawkins就指出,在近年興起的「減廢減排」的話語裏,廢品已經不再像以往只剩下負面的價值,廢品的回收已經與環保新生活、中產消費和可持續發展等後工業價值開始聯繫起來。他認為,廢品甚至逐漸形成一個倫理力量(ethical force)。事實上,廢品不斷地影響我們每天的身體實踐和日常習慣:比如我們開始為垃圾分類;外出帶環保袋,甚至自己的餐具和飯盒;把廢紙、鐵罐、塑料瓶挑出、壓平、累積售賣或丟棄;把廚餘和一般垃圾分開處理等等。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提倡環境保護的社會運動和政府宣傳都在呼籲減廢減排,開拓回收經濟。在發達國家,垃圾回收已經與一種新的綠色公民主體(green citizen subject position)和環境道德掛鈎,而且得到非常廣泛的社會支持。簡單來說,在今天的環保話語抬頭後,廢品和垃圾已經開始超越以前只被認為是死物、無用的概念,其社會文化意義也越來越值得研究(Hawkins and Muecke 2003)。
在發展中國家,從廢品經濟引申出來的文化意義、主體性和身體實踐和道德,還是一塊沒有很多討論的空白。本書正是要重新認識廢品在轉型中國的物質性(materiality)──除了是一個底層的生產資料以外,還怎樣介入城鄉斷裂的底層生活、移民家庭的建構,以至城鄉交合區的空間。
廢品在北京
本書以《廢品生活》為名,是希望將「廢品」作為理解今天城市化的一種重要的分析範疇(analytical category)。首先,廢品這概念指涉作為垃圾被丟棄,或被回收的廢棄物。所以在本書中,我們有時候用「垃圾」,有時候用「廢品」,兩者的意義有共通之處。進一步地,以「廢品」作為一種分析範疇,我們希望探討的是廢品這種物質的流動,如何構成當代城市生活、社會動態和權力關係。在這個分析層面,廢品不單單是被回收的垃圾,而是作為一種社會、經濟、文化現象,它涉及到回收行業、拾荒行為,以及所牽連成千上萬的消費物質和城鄉個體的流動,和兩者形成的獨特貿易及社會網絡。在本書中,將廢品作為一個分析範疇,我們希望讀者不只讀到底層人民如何透過拾荒來到建構他們的城市生活,更讀到廢品如何構成今天重要的城鄉經濟,瞭解廢品如何刻劃新的城市空間,也體會到廢品其實就是我們作為消費者的生活,是我們城市生活中經常被忽略抹殺的重要社會文化。所以說,「廢品生活」不僅是收廢品人的生活,更是指我們所有人的、和廢品息息相關的社會生活。
以廢品的回收再用來理解社會文化,並不是我們獨創。書寫Republic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y(2003)(被翻譯為《民國北京市》)的歷史學家董玥(Madeleine Yue Dong)就指出,舊物回收(recycling and reuse)是民國時期大部分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一種獨特的城市文化,能透視當時非法夜市場的形態,能讓人理解參與舊書舊物買賣的一種古董文化認同,甚至提供一種理解民國商品現代性和城市公民權的視角。無獨有偶,Susan Strasser(1999)則透過廢品交易的歷史,書寫英、美兩國城市經濟社會生活的變遷,指出人們有關廢品的生活習慣的改變,隨著城市化的過程、新能源和交通工具的應用、商品交易市場的變遷,以及人們的衛生觀念而發生轉變。回收、廢物再用、修補破舊之物,曾經是家庭生活中男男女女必備的技能。然而隨著一套方便、衛生、更新換代的文化興起,人們才逐步習慣於丟棄,而不是循環利用。
事實上,從北京這座大都市看廢品,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歷史上在北京,廢品從來就不是垃圾那麼簡單,它與城市文化、公民界限,甚至國家意識形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Joshua Goldstein在“e Remains of the Everyday: One Hundred Years of Recycling in Beijing”(2006)這篇文章,就寫到共產黨政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成功把人數將近7,000的個體回收貿易人,組織為一個叫「北京市廢品回收公司」的國營單位。隨著計劃經濟的興起,回收的舊物開始轉變,報紙和政府單位的宣傳印刷品成為重要的回收品。每個家屬院設有小型回收站,給送來廢紙鐵罐的居民幾分錢的回饋,對當時在配給經濟下現金缺乏的居民來說,有莫大的吸引力。
當然,毛澤東時代的廢品回收並不是為了修補翻新舊物,讓它們再流入夜市二手轉售,而是為了把它們納入到大型的工業製造,成為煥然一新的產品。Goldstein認為,廢品的「工業回收」在毛澤東時代正式揭幕。從1966年開始,廢品回收成為一個奉獻國家工業的行為,是一種新社會主義下的公民責任,號稱能把每人每天節省回收的點滴,融入整個工業製造的機械裏;而在當時「大躍進」期間,工業發展「超英趕美」的意識形態語境下,廢品回收被勾連為「光榮建國服務」的一種日常實踐(Goldstein 2006: 270–273)。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不只意味著往後三十多年以市場為主導的政治經濟,更是一種新社會文化的來臨──「丟棄文化」(culture of disposability)。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論說,丟棄文化是一種歐洲與美國在七八十年代的「後現代的文化形式」,使用和丟棄一次性物品,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的習慣和性格。我們不但丟棄一次性的餐具和飯盒,還丟棄太多一次性的衣服鞋襪。丟棄文化甚至蔓延到我們的社會關係,比如極速的婚姻結合和離散(1991: 284–308)。如今,這種丟棄文化也已經滲透到了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2000年後的全民消費,進一步加劇「消費就是為了丟棄」的邏輯。同時,市場經濟所來的通脹,讓只值一分幾毛的回收行為變得可笑。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後來改名為「北京物資回收公司」的國營回收單位,也逐漸把本來駐紮社區的回收站,變成地產開發點和出租車公司項目,令原來全市兩千多個回收站降為後來的幾個,也順理成章地把單位的老員工分配到新的業務上(Goldstein 2006: 278–280)。結果是,國營回收單位的業務靠著壟斷重型金屬的工業回收而繼續,另一方面則開始轉型,開發其他業務。其薪水福利好的國企工人,不願意也不需要在全市迅速增長的小區生產的垃圾堆裏尋找、分揀、跨城運送可回收物品。這種勞動力成本和投入都超高的工序,在這二三十年由十幾萬農民工一力承擔。北京物資回收公司也嘗試吸納零散的農民工到其管轄區域內工作,嘗試管理他們,給他們穩定工資、制服、規定工作時間等等,但是這種嘗試大都失敗收場,收廢品人根本不願被收編到體制裏。事實上直到今天,國企「收編」的努力一直在繼續,而大量「散兵游勇」的收廢品人和正式的廢品回收企業並存的局面,也持續存在。
一言以蔽之,國營回收單位逐漸遠離了廢品回收的一線,隨之冒起的現象是飲食旅館、小區百貨、商場等直接跟收廢品群體交易,垃圾成為一種可售賣的商品,而收廢品人則爭相以高價買下這些「垃圾源頭地盤」,以開拓他們的廢品轉售生意。
《廢品生活》所關注的,就是這個十幾萬人的收廢品人群體──他們的生活,以及廢品和收廢品人所編織的城市化空間和實踐。事實上,廢品現象並不局限於北京,而是充斥在全國各層的城鄉空間。這使得廢品的在當代中國研究尤其重要,因為它標示著社會經濟文化、階級界限、國民行為和身份,都在劇烈轉變。如果廢品在民國和毛澤東時代都標誌著那麼獨特的國家城市文化和現代性,今天從廢品看盛世中國,可以展開更複雜的有關城鄉關係、空間和城市化過程的分析。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無庫存之港版書籍,將需向海外調貨,平均作業時間約3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縮短等待時間,建議您將港書與一般繁體書籍分開下單,以獲得最快的取貨速度。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