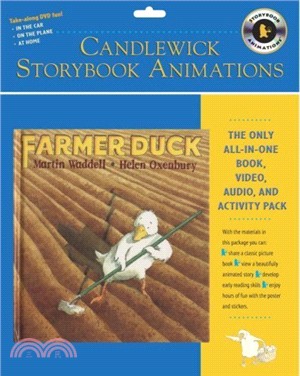社群媒體前兩千年
商品資訊
ISBN13:9789869253987
替代書名:Writing on the wall : Social Media - the first two thousand years
出版社:行人
作者:湯姆.斯丹迪奇
譯者:林華
出版日:2016/07/01
裝訂/頁數:平裝/416頁
規格:21cm*14.8cm*2.2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古羅馬最偉大的政治家西塞羅其實每天都在上網。
他的瀏覽器是莎草紙,他的頻寬是奴隸的腳。他發表一篇「動態」,這則「動態」便會在他的人際網絡中開始流傳,其他人順勢寫下心得、發表新聞,或者「轉推」抄寫到另一張莎草紙。在羅馬城內,回覆一個問題約需兩小時。奴隸們交替往來,於是各種最新消息、政治謀略與八卦,遍傳遍了羅馬。
如果我們把「技術」抽開,從歷史中尋找能擔任「社群媒體」的相同角色,便會發現:每個歷史階段,其實都有這樣密集人際互動、資訊交換的相應機制。在古羅馬我們找到奔波的莎草紙;在十六世紀我們找到不斷傳遞散布、引發革命的印刷小冊;在啟蒙時代我們找到川流不息的咖啡館。這些臉書出現之前的社群媒體,雖然速度慢一點,但卻有現在臉書、推特的全部特性。
一旦把現代網路建立起來的「社群媒體」與之前兩千年的歷史連上,許多現在的疑惑或許就變得清晰許多:臉書之於阿拉伯之春到底扮演什麼角色?論述言論的庸俗化會對文化有何影響?今日社群媒體真正新穎的地方在哪裡?
作者湯姆.斯丹迪奇是個非傳統的歷史作家,出身科技圈,長期為Wired雜誌、紐約時報等媒體撰寫重點文章。他總能用新穎的角度,重新找到理解歷史或科技的線索。他之前的幾本著作《歷史六瓶裝》、《歷史大口吃》不但精彩好看,更是引起眾多討論。
在這本書中,作者自由穿梭於各個時代,利用細膩的歷史線索,構築出一支「臉書出現之前的社群媒體歷史」。讓我們因而能撥開「社群媒體是當代產物」、「社群媒體因為科技才可能」的種種迷霧,看清眼前發生的真相。
作者簡介
作者 / 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
擁有牛津大學工程與電腦科學學位,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數位編輯,也是經濟學人網站Economist.com的總編輯。他也為多家知名報紙章雜誌撰寫文章,包括《連線》(Wired)、《衛報》(Guardian)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等。曾著有《歷史大口吃》、《歷史六瓶裝》(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ix Glasses)、《維多利亞時代的網路》(The Victorian Internet)、《土耳其人》(The Turk)和《海王星檔案》(The Neptune File)。目前與妻女住在倫敦,可參考他的網頁:www.tomstandage.com.
譯者 / 林華
聯合國高級翻譯,在聯合國總部工作30餘年,現為同聲傳譯中文組負責人。主要譯著包括《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北京中信出版社)《斷裂的年代: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戰爭史》等,合譯有《論中國》《世界秩序》《強權與鐵腕:普京傳》(以上皆為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等著作。
名人/編輯推薦
【按讚推薦】
廖健苡/哲學星期五策劃人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好評推薦】
「潛回歷史,細看新聞媒體、八卦報導、電子郵件、社群網站的原型,機智風趣且具啓發性。」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從斯丹迪奇的《維多莉亞的網際網路》這本書開始,我就是他的忠實讀者。那本書是關於電報的興起,一方面讓我們弄清網路科技與電報的關係,一方面讀來饒富興味。這次也是如此。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紐約時報
斯丹迪奇再一次展現他過人天賦,把過往歷史銜接到現在的爭論與科技。《社群媒體前兩千年》一書做出好看而且極有說服力的主張。
——史蒂文•强生(Steven Johnson),Future Perfect以及《好主意從哪來》作者
這本書將會改變你對社群媒體的看法。它揭露:今日科技只是幫我搔我們喜愛分享與連接的癢。
——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網景及Andreessen Horowitz之共同創辦人。
湯姆.斯丹迪奇讓我們了解,在文化的自然進程中,我們過去身處的「大眾媒體時代」其實是長達兩世紀的反常狀態。媒體原本就是屬於社群的,而現在只是再度加強。
——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長尾效應》、《免費》及《自造者時代》作者
序
【引言】西塞羅的網路
不了解過去就永遠處於孩提狀態。不利用往昔的成果,世界必定永遠只是混屯初開。
——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
西元前五十一年七月,古羅馬政治家兼演說家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來到現今土耳其東南部的西里西亞(Cilicia)就任總督,即地區行政官。在繁忙紛攘的羅馬,西塞羅是政治生活中各種明爭暗鬥的中心人物,他十分不情願地離開羅馬,打算一有可能就馬上回去。當時令他憂心如焚的問題是,軍隊統帥凱撒(Julius Caesar)是否會自西揮師羅馬,奪取權力。西塞羅一生致力捍衛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制度,維護它精心規定的權力分配和對個人權威的嚴格限制,防止凱撒之類的人集中把持權力。但是,按新通過的一項反貪腐法的要求,西塞羅和其他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必須到各行省去擔任總督。好在即使在遙遠的西里西亞,西塞羅仍然有辦法掌握羅馬的情況——因為羅馬的統治階層發展出一套傳播訊息的完整制度。
那時,既沒有印刷機,也沒有紙張,傳播訊息靠的是信件和其他文件的交流。人們把這些信件和文件抄錄在莎草紙卷上,寫下自己的評論,然後與別人分享。《西塞羅書信集》是那一時期保存下來的、他與別人的通信集。內容顯示西塞羅經常寫信給各地的朋友,通知他們最新的政治謀劃,轉達他從別人那裡聽來的新聞,也發表自己的評論和意見。有些信的收件人不只一個,是供當眾朗讀的,或張貼在公共場所以饗大眾。
西塞羅或別的政治家作了一篇出色的演講後,會把演講詞的抄本分贈給身邊的密友,這些人讀了演講詞後再傳給別人。這樣,除了演講當時的聽眾外,還會有更多的人讀到演講的內容。書籍流傳的方法大同小異,也是一卷卷莎草紙從一個人手中傳給下一個人。誰若想保留某篇演講或某本書,就必須在傳給別人之前讓抄寫員謄錄一份。《每日紀事》(Acta diurna,即國家新聞公報)也是以副本的形式在人群中流傳,正本則每天張貼在羅馬公共廣場的公告板上,內容有政治辯論的簡要總結、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節日的日期,以及其他的官方新聞。西塞羅啟程去西里西亞時,讓馬庫斯.凱利烏斯.魯弗斯(Marcus Caelius Rufus)(他的朋友兼門生)寫信給他時,也把每天的《每日紀事》抄本送給他。不過,那只是西塞羅的訊息來源之一。他寫道:「其他人也會寫信給我,很多人會提供新聞給我,哪怕是謠言,我也能從中聽到不少消息。」
這種眾口相傳的非正式傳播系統,使得訊息能在至多幾個星期的時間內,就能到達最遙遠的省分。羅馬的新聞到達西邊的不列顛需約五週的時間,到達東邊的敘利亞約七週。遠方的商人、士兵和官員,把羅馬共和國中心的消息傳播給自己社群圈子裡的人,與朋友分享信件、演講詞或《每日紀事》的摘要,並把邊疆地區的新聞和傳言傳給他們在羅馬的關係人。沒有正式的郵政服務,所以只能由信使遞送,或交給往合適地方的朋友、行腳商或旅行者。西塞羅和羅馬精英階層的其他成員,就這樣靠由他們社群圈子的成員組成的關係網保持消息靈通,大家都收集訊息,過濾後互相交換。
在現代人看來,這一切給予人一種奇怪的似曾相識的感覺。用今天網際網路的行話來說,西塞羅參加的是一個「社群媒體」系統:在這個社群媒體環境中,訊息沿社會關係網在人們當中流傳,四面八方的人來參加同一場討論,組成分散的群體。羅馬人靠莎草紙卷和信使傳遞消息,今天的幾億人利用臉書、Twitter、博客和其他的網際網路工具,聯繫起來快得多,也容易得多。所用的技術很不一樣,但這兩種相隔兩千年的社群媒體,在基礎結構和發展態勢等許多方面是相同的:兩者都是雙向的交談環境,訊息沿著社群關係網從一個人橫向傳給另一個人,而不是由一個非人的中心來源縱向傳播。
西塞羅的網絡不過是今天社群媒體在歷史上的眾多先例之一。其他的重要例子包括,早期基督教教眾間流傳信件和其他文件;16世紀宗教改革發動時印刷小冊子的洪流席捲德意志;都鐸王朝(Tudor)和斯圖亞特王朝(Stuart)的宮廷中,交流和抄錄滿紙流言的詩作;英國內戰期間,保王派和議會派為爭取公共輿論的支持,發表針鋒相對的小冊子;啟蒙時期,人們在咖啡館閱讀大量新聞報告和小冊子;第一批科學刊物和通訊學會,使相隔遙遠的科學家能夠討論、並進一步發展彼此的研究;各種小冊子和地方報紙大聲疾呼,動員民眾支持美國獨立;還有大革命前的法國利用手抄詩作和新聞稿,把各種傳言從巴黎散布到全國。這樣的社群媒體系統層出不窮,因為在大部分人類歷史的時間內,社群關係網是新思想和新訊息傳播的主要手段,無論是以口頭的形式還是書面的形式。多少世紀以來,這些社群媒體系統的力量、傳播範圍和包容性,一直在穩步增長。
但後來,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一切都變了。蒸氣印刷機的出現,加上20世紀收音機和電視的發明,產生了我們現在所謂的「大眾媒體」。這些新的大眾傳播技術能夠以空前的速度和效率,把訊息直接供應給大批受眾,但它們的高昂費用意味著,對訊息流的控制集中到了少數人的手中。訊息的傳遞於是採取了一種單向、集中、廣播的方式,壓倒了過去雙向、交流、社會化傳遞的傳統。大眾傳媒技術催生了龐大的傳媒帝國,也培育了一種國家認同感,並使專制政府的宣傳如虎添翼。
然而,過去十年間,媒體的社會性質大張旗鼓地重新呈現。網際網路使各種易於使用的發表工具得以百花齊放,使社群媒體的觸及範圍和規模有了空前的擴大,得以走到前臺,和廣播媒體一較高下。臉書、twitter、Youtube以及其他的社群平臺,成了大眾傳媒公司的勁敵。更重要的是,它們對社會和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社群媒體挾數位網絡的巨大威力重新出現,這不僅代表著媒體領域,而且是整個社會的深刻轉變。
它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難題。社群媒體的新形式是否導致了瑣碎與粗鄙的公共討論?當權者面對社群媒體的批評該如何回應?社群媒體是否必然會促進自由和民主?社群媒體在引發社會變革方面有沒有作用?有什麼樣的作用?它是否只是無謂的浪費時間,使人們不能專注於有益的工作?既然社群媒體意味著線上聯繫取代了真實世界的互動,那麼是否骨子裡是批評社會的?社群媒體是否只是一時時髦,不必理會,很快即成為明日黃花?
歷史上不同時期和地點產生的社群媒體,形形色色,但它們都由一條共同的線連在一起,即它們都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分享訊息的基礎之上。本書將對這些社群媒體進行思考,以尋求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早期的社群媒體參與了歷史上許多偉大的革命。關於公共討論瑣碎化的擔心,和認為新形式的媒體會嚴重影響人的專注的觀點,在幾世紀以前即已存在,關於是否應管控社群媒體系統以及社群媒體,是否會導致社會和政治變化的辯論也早已有之。透過對今日數位社群媒體模擬前人的審視,我們可以在瞭解歷史的基礎上,對今日的辯論提出新的看法。與此同時,我們今天使用社群媒體的經驗又能使我們以新的眼光看待過去。我們發現,包括聖保羅(Saint Paul)、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內的一些歷史人物,對社群媒體系統的運用特別純熟,所產生的後果一直延續至今。
使用網際網路的現代人對此一定大感驚訝,他們也許以為今天的社群媒體環境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但即使在網際網路時代,我們分享、消費、使用訊息的許多手法都是建立在幾百年前就有的習慣和傳統的基礎上。今天社群媒體的用戶不自覺地繼承了一個有著驚人歷史淵源的豐富系統。發掘這些古老的前身,追溯過去兩千年社群媒體興起、衰落和重生的故事,提供了一個我們看待西方媒體的歷史大有啟發的新視角。它顯示,社群媒體不只是把我們聯結在一起,還聯結著我們和過去。
目次
引言 西塞羅的網路
社群媒體早在兩千年前就出現,這個理解不但有助於看清現在的媒體發展,也讓我們能反過來用新角度看待這兩千年的媒體發展。
第一章 社群媒體遠古的基石:人類為何生來熱衷分享?
社會性大腦、語言的傳播和書寫的發明,這三件式建立起社群媒體的基石,讓人類足以成為社群動物。
第二章 羅馬媒體:第一個社群媒體生態系統
西元前一世紀,奴隸是羅馬時期的寬頻網路。送信的奴隸、謄稿的奴隸,讓身處偏遠的西塞羅,不但能獲知羅馬城內最新消息,也能讓人知道他的最新狀況。
第三章 馬丁路德的病毒行銷:社群媒體在革命中的角色(一)
十六世紀,在宗教改革時期的第一個十年間,一共出版了六百萬本小冊子,其中三分之一是馬丁.路德所寫的。那時候,作者沒有版稅可拿,分享、推薦、翻印這些事,就是「按讚」的一種模式。
第四章 流動的詩篇:用於自我表現與自我推銷的社群媒體
德文郡手稿是一群年輕廷臣交換詩歌、短籤的一本冊子。這本冊子保留了十九個人在五年間,閱讀詩歌、評論時事、表達感情的紀錄與討論。換言之,就是一個隱密的社群空間。
第五章 讓真理與謬誤抓對廝殺:管制社群媒體的困難
十六世紀期間,整個歐洲對印刷品的內容以及印刷商的控制日趨嚴厲。彌爾頓寫下《論出版自由》,反對任何形式的內容審查,而這些思想激勵了十八世紀法國跟美國的革命思想。
第六章 到咖啡館去:社群媒體促進創新
十七世紀,阿拉伯的咖啡館傳入歐洲,在巴黎跟倫敦都大受歡迎。但各種疑慮便蜂擁而至。許多人認為,咖啡館讓大家分心,讓大家終日與朋友討論各種無謂的小事。
第七章 印刷的自由:社群媒體在革命中的角色(二)
潘恩《常識》一書的成功改變了人們對獨立的態度。過去,許多人對獨立連談都不願意談,更遑論支持了。因此有人說:在實現美國的獨立中,筆與印刷機和劍同樣功不可沒。
第八章 人民的哨兵:暴政、樂觀者以及社群媒體
審查制度甫一放鬆,小冊子即如潮水般洶湧而至。截至一七
八九年五月,一年內印刷的小冊子總冊數可能超過一千萬冊。這造成了空前的全國性大辯論。不久之後,人民攻進巴士底獄。
第九章 大眾媒體的興起:中央化的開始
報紙到了十九世紀已經全然不同了,報紙上的文章由專業記者撰 寫,資金主要來自廣告商。跟十八世紀的報紙相比,社群的互動性消失了,讀與寫的距離從未如此遙遠。
第十章 社交媒體的反面:無線電的黃金時代
BBC有皇家的認可,又有政府部門的地位,對聽眾採取的是一種家長式居高臨下的態度。它不只給聽眾提供娛樂,還想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素質。這成為歐洲國家廣播事業的典範。
第十一章 社群媒體的重生:從 ARPANET 到臉書
有一百五十年的時間,人對人的媒體被集中化大眾媒體所湮沒,現在鐘擺又蕩了回來。流行幾世紀之久,基於分享、抄送和個人推薦的社群形式的媒體如今借網際網路的東風強勢回歸。
結語 歷史「轉推」自己
不管將來社群媒體採取何種形式,有一點是清楚的:它不會消失。如本書所述,社群媒體並非新事物,它已經存在了好幾個世紀。在跨越歷史的共享平台上,思想在人與人之間不斷傳送。
註解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基督教和社群媒體
對羅馬的社群媒體系統運用得最成功的是,公元一世紀初一位富有魅力的猶太傳教士的追隨者。他們努力利用共享媒體,在他教誨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早期基督教與希臘-羅馬世界的其他宗教不同,除了講道,還高度依賴書面文件傳播教義,指導信徒,開展辯論,解決爭端。從公元一世紀中期開始,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教會之間,就開始不斷地交流信件和其他文件。《新約》的二十七篇中有二十一篇是信件(使徒書信),剩下的六篇中的兩篇裡含有書信。總算起來,自古以來基督教徒寫的書信流傳到後世,約有九千封。雖然基督教徒有時被稱為「信書之人」,但是說早期教會是一群通信之人組成的團體更加準確。
這些信中最出名的是大數城的保羅(Paul of Tarsus),這位早期教會的重要領導人寫的使徒書信。保羅曾多次前往希臘和小亞細亞傳教,希望在那裡建立基督徒社區。旅行期間,他與所創立的教會和計劃訪問的教會保持聯繫的方式就是寫信。《新約》所載的二十一篇使徒書信中,據說有十四篇出自保羅之手(雖然現代學者對其中七篇的出處提出了質疑)。保羅的書信都是具體寫給具教會的。比如,《羅馬書》是寫給羅馬教會的,《哥林多書(前、後)》是寫給科林斯(Corinth)教會的。但顯然也是為了向更廣泛的受眾傳播教義。這些書信在收信的教會朗讀給教徒們聽,這是第一波分享;正如保羅在寫給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帖撒羅尼迦前書》)中所說:「我因主誓求你們,向眾兄弟朗讀這封書信。」但他也要求收信的教會,把他的信抄給附近的其他教會。他給科林斯教會的第二封信(《哥林多後書》)針對的是「哥林多的天主教會和全亞該亞(Achaia,科林斯所在的省)的眾位聖徒」;《加拉太書》(Galatians)寫給加拉提亞(安納托利亞中部的一個地區)的各個教會;給歌羅西(Colossae)教會的《歌羅西書》(Colossians)指示收信人:「你們宣讀了這封信,務要使這封信也在勞迪西亞(Laodicea,即老底嘉。譯注)人的教會內宣讀;至於那由勞迪西亞轉來的信,你們也要宣讀。」(老底嘉城離歌羅西十一英里。)保羅寫信就是為了供人抄寫和分享,他的信也確實廣為流傳。朗讀他的書信成了基督徒禮拜儀式的一部分,早期教會把他的書信視為聖書經文,納入《新約》。
基督教書信的流傳建立在希臘-羅馬世界現有習慣的基礎之上。寫出基督教最早文件的人是早期教會中識字的人,或者是在皈依基督教的富人家中勞作的奴隸。保羅按羅馬慣常的方法口授信件。比如,他口授《羅馬書》時,記錄的抄寫員名叫特爾提烏斯(Tertius,在信尾處,他問候了他在羅馬的朋友,並表明了自己的信仰:「我,寫下此信的特爾提烏斯,歡迎你們來到主的懷抱。」)。信交由旅行的人從一個教會帶給另一個教會,有時則派人專程送信。到公元一世紀中葉,羅馬帝國四通八達的道路網和方便的海上交通,使旅行更加快捷、安全,也使得羅馬帝國內各地之間的聯繫,達到了空前的緊密程度。因此人們更願意旅行,無論是為了經商,還是為了參加宗教節日慶祝或運動會,或者是去外地探親訪友。保羅不在旅途中的時候,會住在科林斯或以弗所(Ephesus)這樣海陸交通都十分便捷的城巿,以方便發收信件。
保羅借書信來管理他建立的教會網,並在教眾中培養起一種大家同屬更大的基督徒群體的歸屬感。在信中,他多次把作為某信收信方的教會,和其他教會以及更廣泛的基督教運動聯繫起來。比如,在《帖橵羅尼迦前書》中,他把被其他希臘人迫害的教徒的苦難,等同於同樣在朱迪亞(Judea)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的苦難:「因為你們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們受了猶太人的苦害一樣。」他告訴科林斯人,他要求加拉提亞的各教會籌錢幫助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並說他期望科林斯人也伸出手。他還強調,他創立的教會與使徒彼得創立的教會,和詹姆斯(James)在耶路撒冷領導的其他教會,親如一家。在基督教創建伊始,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的日子裡,感覺到自己歸屬於一場更大的運動讓人安心。教會的教眾想瞭解別的教會的狀況,也想知道他們求援的祈禱是否得到了回應。
教會間分享和傳播的並不只有保羅寫的信。比如,同樣載於《新約》的彼得的第一封信(《彼得前書》),是寫給小亞細亞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的(「散居在本都、加拉提亞、卡帕多西亞、亞細亞和比提尼亞的選民」)。克雷芒(Clement)在公元一世紀末寫的第一封信,由羅馬教會的長老送給科林斯教會,為的是解決解職芋些教職人員而引發的糾紛。信中提到了保羅的書信,這意味著羅馬和科林斯教會,都存有保羅書信的抄本;也許,那時保羅的書信已經匯集起來,成為基督教的經典經文。克雷芒的使徒書信顯示了書信如何確立了教會長老的權威,被用來解決早期教會成員之間,就教義和遵教行為的爭辯和異議。自保羅以降的各位教會長老的書信,常被用作論據來支持某個神學論點。這方面的例證包括亞歷山大里亞的狄奧尼西(Dionysius of Alexandria)的書信,他的信傳播於地中海地區各個教會,還有安提阿的噥納爵(Ignatius of Antioch)的書信。
確實,公元一世紀末任安提阿城主教的依納爵的書信傳播,表明了基督教用來分享訊息的社會網路連結的運作。對基督教這個新宗教,羅馬人的態度往好裡說是心懷疑慮,往壞裡說就是充滿敵意,隔沒多久,就發動一次對基督徒的迫害。在這樣一次陣發性的迫害中,依納爵被逮捕。他拒絕放棄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被判處武裝監押,去羅馬接受懲罰,預計會被扔到圓形劇場(Colossum)裡餵獅子。依納爵帶著鐐銬,被十名士兵牽著從安提阿前往羅馬,途中他受到來自小亞細亞許多城鎮的基督徒代表團的歡迎。他寫信給以弗斯、馬格尼西亞(Magnesia)和特拉雷斯(Trailes)的教會,感謝他們的支持,號召他們堅定信仰,避免異端邪說,並服從他們的主教。他還給羅馬的朋友寫信,告訴他們他要到了。
他在特洛阿(Troas)的愛琴港等船的時候,聽到消息:安提阿教會的內部爭端得到了解決。依納爵大喜,寫信給附近費拉德爾菲亞(Philadelphia)和士麥拿(Smyrna)的教會,請它們給安提阿去信祝賀。依納爵還寫信給士麥拿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讓他通知小亞細亞所有的教會,寫信給安提阿表示祝賀。途經希臘城巿菲利比(Philippi)時,依納爵請那裡的教會給安提阿寫信。菲利比人把信送給士麥拿的主教波利卡普,請他把他們的信和小亞細亞各教會的信,一併轉給安提阿。菲利比人在寫給波利卡普的信中,還要求得到所能拿到的依納爵書信的抄本。波利卡普回信說:「應貴處要求,茲送上我們手上所有的依納爵書信,有專門寫給我們的,也有他的其他書信。現在全部附於此信之後,定會使貴方受益良多。」這說明了依納爵的信寫出之後,幾週內即傳播開來,因此,一位學者把這一文件分享的系統,稱為「神聖網際網路」。
今日,我們有時甚至能知道寫下、抄錄和重抄這些文件的抄寫員的名字,因為文件中提到他們的名字,或在文件結尾處署名。在波利卡普遭到了逮捕和處決後,安提阿附近的菲洛梅里厄姆(Philomelium)教會,請士麥拿教會給它一份波利卡普生前及殉道事蹟錄。於是,蓋烏斯根據波利卡普的追隨者艾雷尼厄斯(Irenaeus)的記錄,匯編了一份事跡錄,由一位名叫尤拉埃斯圖斯(Euraestus)的抄寫員寫出來。這封送給菲洛梅里厄姆的信,現今名為「波利卡普殉難記」(The Martyrdom of Polycarp),其中載有如下指示:「你們聽完這些事蹟之後,把信轉給遠方的兄弟們,讓他們也讚美主。」後來,此信的抄本署名,表明了它確實經過了抄錄和流傳:「此事蹟錄是蓋烏斯從波利卡普的門徒艾雷尼厄斯的文件抄來的。波利卡普曾和艾雷尼厄斯一起生活。科林斯的伊索克雷特斯(Isocrates)把蓋烏斯的抄本抄錄下來。願他們都得主恩典。我,皮翁尼烏斯(Pionius),受聖波利卡普的啓示尋找這份抄本,找到時它已年代久遠而破爛不堪,現在我又把它抄寫下來。」一九四五年,在埃及找到了一批存在陶罐裡的四世紀基督教文件,其中有一組叫「納傑哈馬迪藏書卷六」(Nag HammadicodexⅥ,納傑哈馬迪是埃及地名,是這裡所說的基督教文件的發現地 譯注)。書尾題署也證明了當時抄錄和流傳的做法:「我抄了這一份論文⋯⋯其實我接到了很多論文。我沒有抄寫那些,因為我想您也接到了。我連抄寫都會猶豫,因為您可能已經拿到了。」
納傑哈馬迪的文件像公元二世紀以來所有的基督教文件一樣,是手本,即寫在一張張莎草紙或羊皮紙上,沿一邊裝訂起來,像現代的書一樣,不像希臘-羅馬時代常用的捲軸。雖然深得基督教徒的喜愛,卻不是他們發明的:羅馬人和埃及人都使用手本形式的小筆記本,因為它們比捲軸體積小,便於攜帶。羅馬的蠟版也經常以手本的形式疊放在一起。似乎這種筆記本和蠟版,主要用於筆記、或記錄其他需要馬上記下來的訊息;正式文件則用莎草紙捲,直到三世紀中期,莎草紙捲仍較受青睞。公元一世紀末的羅馬詩人馬提雅爾(Martial),向讀者推薦手本,因為一隻手就可以掌握,而且旅行很方便。儘管他熱情推薦此種模式,響應者卻寥寥無幾,只有新興的基督教團體是重要的例外。到了二世紀初,幾乎所有的基督教文件都採用了手本的形式,相比之下,非基督教的文件只有不到百分之五是手本形式。
到底為什麼基督徒要捨捲軸而取手本,原因至今尚不清楚。一個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份重要文件(或者是馬可福音,或者是保羅的使徒書信集)採用了手本形式,隨著文件的抄錄和流通,這種形式也就得到了確定。另一個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書寫人和抄錄員大多是識字的普通人,不是專業的抄寫員,因此他們樂意摒棄傳統的觀念,即手本是用來記筆記的,真正的文件應寫在捲軸上。這種猜測有一個事實為依據:基督教的文件從一開始就有其特有的形式。希臘-羅馬的文件採用傳統的「文字之河」的形式,沒有標點符號,沒有分段,也沒有文字間隔。基督教的文件則每段開頭以大字標明,另外還有把字隔開的標記、標點符號、分部符號和頁數。這些讓普通人(而不是專業朗讀者)在朗讀基督教文件時,來得容易得多。所以,從捲軸到手本的轉變,可能僅是對希臘-羅馬文學習慣,更廣泛的摒棄的一個方面。一俟基督教在四世紀早期成為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手本取代捲軸即成定局。埃及乾燥的氣候條件利於莎草紙的保存,在那裡發現的所有希臘文件中,二世紀寫成的,有百分之九十八寫在莎草紙捲上,三世紀時,這個比例降到了百分之八十一,四世紀和五世紀比例更低,各降為百分之二十六和百分之十一。(在電腦時代,我們又恢復了滾動看文件的傳統,不過我們現在是自上而下滾動,不像羅馬人自右而左滾動。)
基督教的創立借助於媒體,從莎草紙捲轉向手本形式,是早期教會大力利用媒體的又一項長期遺產。作為那個時代對社群媒體最傑岀的使用者,保羅是古代最有影響的書信作者,甚至超過了西塞羅。基督教早期有一些不同的派別互相競爭,就基督訓誡的含義以及訓誡對誰而發,各執己見。保羅利用社群媒體普及了他的觀點,確定了基督教會不僅接受猶太人,而且對所有人都敞開大門的原則。他的影響如此之大,時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堂中仍在朗讀他的書信──這有力地證明了,抄錄文件、並在社群關係網內傳播的做法強大的威力。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