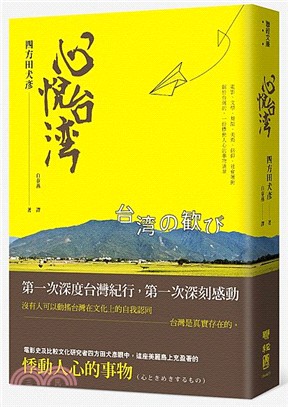定價
:NT$ 380 元優惠價
:90 折 342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內容簡介
第一次深度台灣紀行,第一次深刻感動
沒有人可以動搖台灣在文化上的自我認同
── 台灣是真實存在的。
電影史及文化比較研究人四方田犬彥眼中,這座美麗島上充盈著的
悸動人心的事物(心ときめかすもの)
周遊地球幾趟下來,能夠吸引我的,只有平凡而已。
── 電影編劇 Chris Marker
與其說是「平凡」,不如說是「家常」吧,對於日本重量級文化學者四方田犬彥而言,台灣的歷史,以及歷史積累型塑而成的社會現況,讓他這個異國人剛下飛機踏上這片土地的瞬間,就失去了防備心,真是令人困惑啊。
接下來,他感受到一種召喚,他被要求去認知那個橫亙其中的鄉愁和喪失感的混合物。然而,那是真實的嗎?這個鄉愁是屬於怎樣的意識形態呢?
台灣的植物讓人震撼,在路旁的盆栽裡、即將傾頹的廢屋庭院裡、大學校園裡,植物一逕地繁枝茂葉,誇示其旺盛的生命力。人被這一片濃綠所魅惑,有時竟覺得喘不過氣來。
然後他去到另一個海島。在叫做哈瓦那的城市裡,面前攤開好幾冊筆記本,這是他在台灣的所見所聞,裡面的素材召喚著他,去製作一份「悸動人心的事物」的清單。
最後,就是這本《心悅台灣》。
目次
序言
第一部 台北
名為台北的都市
最古老的城市 萬華
在日本統治的陰影下 大稻埕和西門町
布袋戲的結束
現代台灣人的三種父親形象 吳念真、王童、陳映真
神話回歸與廢墟 林懷民與宋澤萊
回憶楊德昌
阿爾發城的詩人 鴻鴻
粉紅色噪音的翻譯 夏宇
魏德聖與日本
太陽花學運 大學生占領立法院
第二部 尋找黑面女神
黑面女神 媽祖
進香日記
第三部 台南
台南印象
府城文士林瑞明
從民權路到大天后宮
失去的水道 水仔尾
剪黏與夜市
最早的台語電影
終章
後記
序言
你正在哈瓦那,眺望著波浪拍打岩壁高高濺起的飛沫,想起前一陣子待在台灣的日子。令人害怕的暑熱,每次外出回來,非得沖澡不可。窗外廣袤的藍天像要穿透似的,遠處隱約傳來練習康加鼓的聲音。
台灣和古巴有一點相似,也有一些不同。
兩地都是位於亞熱帶的小島,植物一逕茂盛地生長著。來到鄉下,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甘蔗田,黃昏時大王椰子搖曳著美麗的剪影。人們發揮著棒球及電影方面的才能,各自在屬於中文及西班牙的巨大語言圈,創造出風格獨特的文學。這兩個社會,距離單一民族的幻想甚遠,數個族群和文化共存混融著。在古巴,西班牙人消滅了原住民,召來了黑人和漢人;在台灣,原住民存活下來,不少人與漢人殖民者混血同化。兩地都信奉執掌航海的處女神,在加勒比海是瑪利亞,在台灣海峽則是媽祖。從地緣政治學來看,兩國皆為軍事據點,在冷戰體制下與鄰近大國曾經有過軍事上的緊張關係。不過兩國現在都跟美國沒有邦交,因此不像日本那樣成為美軍駐紮的基地。
若要說台灣和古巴的不同之處,倒是有一點,那就是古巴仍維持一黨獨裁政治,而台灣長期以來雖未形成多黨制政黨體制,但民主主義政體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已經軟著陸了。
你正在哈瓦那,想起前一陣子待在台灣的日子。
電影編劇家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在《日月無光》(Sans Soleil)說:「周遊地球幾趟下來,能夠吸引我的,只有平凡而已。」
那是你自幼累積至今、關於台灣的印象。
那美麗的、宛如出生自藍色海洋的蝴蝶標本。不知是誰當作伴手禮帶來的鳳梨酥。有著甜膩旋律的〈雨夜花〉黑膠唱片。寫著「大陸難胞奔向自由」的深藍色郵票(穿著粗布衣裳、瘦骨嶙峋的女人拿著手帕掩面哭泣)。伸出長長的舌頭、瞪大雙眼昂首濶步的巨大神像(不知在哪本書上看到的)。巨大的鍬形蟲。南部寺廟屋頂以美麗的形狀往上翹起的燕尾。發出響亮音色的銅鑼和嗩吶。插著蓮花的水瓶裡來回游動的小魚。
因此,當你在台北下飛機之後,第一站便直奔成功高中校園內的昆蟲館。在台灣,有兩件事讓你感到困惑,那是歷史和自然。
當人們知道你是日本人之後,會向你談起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的現代化、衛生和教育,甘蔗品種改良及土地灌溉的事情。台灣街頭充斥著日文,台灣人在日本三一一大地震時捐贈了巨額善款。這是你無法預期的情況(你最初到韓國留學的時候,日本卻是他們極力想要隱蔽的對象。當你開始關注民族主義者高聲提倡的那種複雜的日本觀時,一切就開始了)。
有那麼一瞬間,台灣讓你變得亳無防備。接著,你被要求去認知那個橫亙其中的鄉愁和喪失感的混合物。然而,那是真實的嗎?這個鄉愁是屬於怎樣的意識形態呢?
然而,最讓你感到震撼的卻是植物。
油棕櫚樹披覆著大量新芽,細長柔軟的枝條像麵線般向四面八方展開。馬氏射葉椰子的樹幹分出了數不清的枝條。錦屏藤有著無數的氣根,從莖節的地方長出,大量懸掛而下。大王椰子的老株在樹幹上長出粗大的瘤刺,大片的葉子叢生在樹頂上。姑婆芋和小芭蕉聚生在這椰子樹下方。紫檀的樹幹上長滿了厚重的苔蘚。台灣海棗的樹幹上有著明顯的刻痕,長得像酋長頭的巨葉正在與強風對抗著。檳榔樹有著像竹子般細長的樹幹。榕樹的樹根像章魚腳往四方伸出,粗大的樹幹互相糾纏,形成無法解讀的圖案。鳳凰木的細葉在高處搖曳著。荔枝樹彎曲的樹幹不斷分岔,果實不斷大量地掉落地面……
在路旁的盆栽裡、即將傾頹的廢屋庭院裡、大學校園裡,植物一逕地繁枝茂葉,誇示其旺盛的生命力。你被這一片濃綠所魅惑,有時竟覺得喘不過氣來。
現在,你在桌上擺著好幾冊的筆記本,仔細地反覆閱讀著。讓你感動的到底是什麼?究竟是什麼讓你感到驚奇和喜悅?你打算製作你的「悸動人心的事物」清單,如同一千年前京都的女散文家那樣地。(譯注:「悸動人心的事物」(心ときめきするもの)出自清少納言《枕草子》)
內文選摘(節錄)
名為台北的城市
若要介紹台灣,就必須先從台北捷運的廣播說起。
台北捷運在廣播站名時會以不同的語言重複四次。以「永春」為例,會以「Yonchun」、「Yinchun」、「Yentsun」、「Yonchun Station」的順序廣播,依序是國語(北京話)、台語(閩南語)、客語、英語。若在鄉下搭公車,最後廣播的有時不是英語,而是當地原住民的語言。
在台灣二千三百二十三萬人口(二○一一年調查)當中,南島語族的原住民人口約占二%、也就是五十一萬人(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增訂本)》,濱島敦俊、石川豪等譯,平凡社,二○一三)。若依一般的分類法,他們是由已經漢化的平埔族十族及政府認定的高山族十六族所構成,擁有各自的語言、信仰及習俗。南島語族以太平洋及印度洋全域為居住範圍,西邊以馬達加斯加島為界,中間有印尼、菲律賓,東邊則達夏威夷島、復活節島、紐西蘭。有些學者認為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發祥地,但還未能成為定論。
台灣現在已經不用「先住民」這個詞了,因為「先」這個字有強烈的「已經滅絕」的詞義,因此在一九九四年第三次修憲時,正式將他們稱為「台灣原住民」。不管如何,在交通廣播用語和行政當局的立場是:在台灣使用的所有語言都是平等的。我居住的公寓由一個老人和年輕女性負責打掃,一開始他們就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是阿美族人。老人頗能說日語,但不甚流暢。老人告訴我,小時候他家附近有一個日本人,在戰後確定要回日本時,那日本人在海邊擁抱他,向他道別。老人還說,台灣的棒球是很強的,當然日本也很強啦。
幾乎沒有例外地,台灣人從小就接觸多種語言,會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語種。在這個比日本九州還小的島嶼上,至少有十七種語言並存交雜。對於信奉單一語言幻想的日本人與韓國人而言,這種複雜的語言環境是無法想像的,但台灣人就生活其中。台灣人對於自己該選擇用哪種語言說話,與自己的出身背景、歷史及意識形態有關,不過他們也習於像雜耍遊戲般地操弄數種語言。例如,一九九○年代以降的搖滾樂,就流行將客家語和原住民語放進歌詞裡,作家宋澤萊則將相同內容的小說用台語和國語各寫一遍,而在楊德昌的電影《獨立時代》(在日本發行時的名稱是《エドワード‧ヤンの恋愛時代》)裡,就有一場是一對男女在搭計程車時同時以中文和台語進行漫長的交談。
再把話題拉回站名的廣播,雖然同一個地名在不同語種裡有不同的發音,但是寫成漢字的表現方法只有一種,所以在標示上不會有繁雜的問題。只要能寫出正確的漢字,任何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文化傳統來發音。台灣社會是由複數文化和語言形成的這個概念,已是現在台灣人的基本認知。台灣政治體制對於文字的理念是:漢字絕對不可以簡化,即使是複雜難寫的文字,也必須正確寫出。全世界現在只有香港和台灣仍然保存漢字原樣,繼續使用著。越南已禁用漢字;韓國則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將漢字推至教育體制邊緣;日本在美軍占領下推行漢字簡化運動;中國原本以廢除漢字為最終目標,但中途受挫而改推漢字簡化。因此,台灣在文化史上是極具意義的。
我在台灣的大學裡學到了一個基本知識,那就是在課堂上對於中國的稱呼。眾所周知,蔣介石率領的中國國民黨敗給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之後,在一九四九年逃到台灣。台灣從此受到「中華民國」的統治,而中國大陸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雙方自彼時反目到現在。在台灣內部,有一派人主張台灣獨立,欲取得世界的承認,也有一派人積極尋求與中國統一。如果你是以「台灣」、「大陸」來稱呼,就會被視為統一派;而如果你以「台灣」、「中國」來稱呼,表示你承認兩地各為一國,強調台灣具有不同於中國的獨立性。在日本人看來或許是瑣碎的事,但對台灣人卻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牽涉到自己對政治及文化認同的立場。即使是細微的用語差異,也會成為這個人所依歸、所自我認同的佐證,必須加以留意。一位教授如此告訴我: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附庸國。台灣吸收了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不偏向任何一方,汲取島內各種文化的多樣性而形成獨特的社會形態。台灣雖然與美國、日本、中國沒有正式邦交,也無法在聯合國取得席位,但沒有人可以動搖台灣在文化上的自我認同。台灣是真實存在的。
我以電影史研究者的身分進行演講及授課的主題有:日本紀錄片在三一一大地震之後的變化、與李香蘭有關的性別(Gender)問題、日本電影裡的沖繩表象、滿洲國「啟民電影」(宣傳片)分析等。聽眾為一般學生、研究者、教授等,他們都很認真地回應我的談論。尤其是我到一九九九年大地震受災嚴重的台灣中部幾所大學演講時,我們針對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及核災相關拍攝行為的道德標準問題,進行了誠懇深刻的交流討論。
在授課和演講的空檔,我常到台北電影資料館觀賞館方收藏的台語電影。這不是國民黨政權以中文製作的大型反共電影,而是運用台灣民間資金拍攝的小規模電影、是以台語製作的B級娛樂電影。就我所知,除了台灣人之外,關心這個議題的只有一位摩洛哥的女性研究者。
此次並非我第一次來台灣。其實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只要有機會我就往台北跑。但不知為何,每次的訪問行程總是來去匆匆。就我造訪全世界都市的次數而言,排在巴黎、首爾、香港、紐約之後的,應該就是台北了。但每次造訪的幾天都住在飯店,訪問目的是參加學會發表或訪問電影導演拍攝的新片,根本沒有時間以某一處為據點,用較長的時間與人們接觸,或者參加民間宗教巡禮活動。我一直被這個不充足的感受困擾著。就這一點而言,我在韓國的時候,相對地幸運多了。我無法創造一個能夠跨越電影評論這個狹窄領域、直接面對台灣文化的機會。
在我滿六十歲時,我下了一個決心,並且實踐了。我辭去日本多年的大學工作,打算專心從事寫作。當此事實現後,我馬上想到的,便是長期居留台灣。我已經從無聊的授課和教授會議中解放出來,開始走向實踐多年來的夢想之路。
回憶楊德昌
對於楊德昌(Edward Yang)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東京國際影展上映,我至今仍記憶猶新。那天是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影展對於這部電影的歸屬傷透腦筋。中國大使館事先提出警告,如果官方使用「中華民國」或「台灣」名稱的話,本次影展的所有中國電影會全部撤掉,而且今後不再參展。
影展不得已只好偽造《牯嶺街》的出身地,以「日本美國合作電影」這個根本不存在的曖昧名稱上映。而這部電影仍然獲得評審團特別大獎。
在影展最後一天的頒獎典禮上,楊德昌站在台上對著麥克風沉默了一段時間,接著,像是要反擊之前所受的屈辱似地,他以簡潔的英語堂堂正正地說:「我是來自台灣的導演,而且這是一部台灣電影。」整個會場瞬間響起歡呼聲,我對他(當時)的太太蔡琴道了一聲恭喜。會場上很多的台灣人、以及知曉這部電影上映前曲折過程的少數日本人,都拚命地鼓掌。
我第一次觀賞楊德昌的《恐怖分子》,是在拍攝後隔年的一九八七年。當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沒有做任何準備功課,就在曼哈頓中國城的新都戲院看了這部具有歷史意義的電影。
這是一部從片頭開始就充滿張力的電影。一個以攝影師為志願、年輕的資產階級男子和他的女友裸身在床上,女友正讀著一本散文集。化驗師與女小說家滿臉倦怠,以冷淡、沒有愛意的口氣交談著。一把槍從公寓窗口伸出,房間裡傳來嗚咽的哭聲。
警車鳴笛來到現場,戴黑眼鏡的警長指揮逮捕犯人。但是,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或許是受到強烈的直覺督促,那位資產階級青年趕到現場。在槍擊戰當中,一位混血少女企圖逃走。她未及深思地從樓上往下跳,導致腳部骨折。青年情不自禁地連續拍下她的姿態,悄悄地將她送往醫院……同一時間點在不同場所發生的四起事件,每個鏡頭沒有因果關係地串連起來,故事一直進行下去。不知所云。在美國的電影學校,一定會教導學生說這是絕對不允許的「錯誤串接方式」。非但如此,為電影故事賦予基礎性的時空整合性,在電影一開始就整個地瓦解了。
影像的殘缺片段像是兩道謎題互相拉扯、纏繞著。青年不願等候徵兵通知而四處遊蕩。痛恨母親的混血少女逃脫軟禁狀態,在街頭青澀地模仿妓女的模樣。女小說家正陷入極度消沉的情緒裡,以為丈夫有外遇而開始分居。少女拿著電話簿隨機亂打電話,這個契機讓女作家寫出一部出色的長篇推理小說。有一天,少女突然想要去看看以前住過的公寓。那裡整面牆上貼滿了少女的相片。她與那位攝影師青年有了一夜情之後,便像小鳥似地飛走了。青年回到自己富裕的家中,徵兵通知寄到了。就像模仿自己創造的小說情節那樣地,小說家被自己的丈夫射殺了。
我想要試著說明《恐怖分子》的情節,卻很不順利。其實本當如此,因為這部電影完全無視於一般電影必須流暢地講述故事的這個要求。每個鏡頭都讓觀眾置身於截然不同的空間所發生的事件裡,而且在所有事件還未結束時,又被帶往後面的鏡頭。好幾條分出去的故事線終於纏在一起,一個虛構的臉龐於焉浮現。那是一張名為台北的都市之臉,一個突然進入高度消費的社會、必須面臨軍事不穩定狀態的都市之臉。真是一部很棒的電影。我告訴自己,為了接受這部電影,我必須忘記原本建構好的關於電影的所有體驗,才能夠對這部電影做出評價。
進香日記
從開始進香那個瞬間起包圍住我的,是一種壓倒性的時空意識改變。我明白自已已從原本熟悉的、世俗性的時間概念中脫離出來,將自己委身於一個完全未知的、另一種不同的時間秩序裡。鎮瀾宮華麗的起駕儀式結束之後,大批的信徒追隨神轎出發了。留在這裡的,是深深的黑暗。當我面對這片黑暗時,感受到的便是這種印象。剛才還一起參與慶典的大量人潮都被這個黑暗所吞噬,而我自己也將走入其中。
沒有方向感,也沒有距離感,只能在這個微亮的空間裡,依稀辨識著忽而出現的先行者的身影,跟在他們後面走著。出發時間嚴格規定為凌晨零時,一旦開始進香,這裡就不再有時間感,眼前可見的只有無止盡擴散開來的黑暗。
我參加的進香團遞給我的並不是地圖,而只是一張紙,上面記載著神轎到達奉天宮之前沿路參訪的廟名及預定抵達的時間。開始進香徒步不久,我就知道預定抵達時間完全不具有任何意義。神轎總是不以為意地遲到,有時晚到兩小時,甚至還曾慢五小時。進香團的移動時機完全依照坐鎮於神轎內的媽祖的意思,絕對不可以發出責難之聲。時間沒有嚴格分段,就像軟糖那樣可伸可縮,跟我們平日習慣的線性移動大異其趣。
隨著時間意識的變化所產生的是空間意識的變化。
信徒必須身心清淨才能參加進香。同樣地,神轎通過的空間也必須事先清淨才行。隊伍最前面的滑稽眾神偶及報馬仔的工作,便是將媽祖即將到來的消息告知村民,要他們開始準備以改變空間。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和白煙的目的,便是要將世俗的空間加以淨化,以火牆將空間阻絕,在媽祖出現之時,短暫建構出一個神聖的結界。媽祖之所以能夠無視於現實法則進行遊戲式的移動,是因為祂隨時能夠置身於這個世俗雜物全都排除的清淨空間。
神轎總是挑移動效率差的路線行進。有時會在同一個地點打轉,有時繞了很遠的路,總是不斷無意義地偏離路線。開車或搭遊覽車的人,勢必選擇已舖好的馬路行進,無法跟隨這個無效率的路線。媽祖這個方向定位乍看是恣意而為,但若是從頭到尾都以步行進香的話,就能夠了解其真意。一天平均睡眠三到四小時,全程以徒步方式走完全程的人,最後腳底長出水泡。待水泡破掉之後,仍必須拖著這個痛苦繼續走下去。無止盡的疲勞感持續增加,真是壯烈的苦行啊。但是,在這個痛苦的媒介下,他們漸漸地從個人式的、人稱式的狀態脫離出來,轉化為匿名的「走動著的存在」。
進香到底是怎樣的行為呢?雖然長時間的歲月流逝之後會產生若干變化,但是從大甲到彰化、西螺的這條路線,在清朝時期就已存在。進香者意識到自己現在走的這條路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路,因此他們會發現,他們現在所處的時間已經超越「現在」這個被框限的時間。這讓他們眼前所見的水田和魚池,看起來都像是永恆不變的。借用宗教史學家伊利亞德的說法,這是對於循環式的時間意識的發現,而這是一種曾經支配農耕社會的時間意識。這個發現讓人們從個體抽離出來,被定位成祖型重複的主體。在強烈陽光的照射下,腦袋無法思考,只是日復一日不斷地走著。這個單純又無止盡的重複行為讓「香客」(進香客)去除雜念,拉升到異常興奮的情緒。
這種興奮的情緒在經過某個時間點之後會轉變成恍惚感:我正在走著,我之前有走過,我接下來要開始走。在進香途中,參加者如此地與神轎裡的媽祖進行神祕的交流。他們感受到是,媽祖的靈力讓自己有走下去的力量,也促成自己變得與媽祖一樣的神聖化。
最早的台語電影
聽說台灣第一部台語片已被找到的事,是我來到台灣一個月之後。那時我在新竹清華大學演講結束,與主辦單位的教授們一起吃午餐時,得知這個消息。其中一位教授專門研究台灣電影,他以激動的口吻告訴我,《薛平貴與王寶釧》在兩個月前終於被找到,現在正在台南修復中。
對於一個電影史研究者而言,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若以天文學家做比喻的話,就等於是在太陽系發現新的行星,意義相當重大。我確信,當台灣的電影人聽到這個消息時,一定會有某種感動的。《薛平貴與王寶釧》是拍攝於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釐米電影,是台灣第一部台語片。當初上映時非常轟動,但後來一直以為永遠佚失了,至少我手頭上的幾本台灣電影書籍都是這麼記載的。不只是電影研究者,對於慣用台語的大多數台灣人而言,這個遺憾得以補足,具有極大的意義。
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戰敗,台灣被中華民國接收,原本在台灣長期上映的電影無法再播放了,好萊塢電影和來自上海的中國電影填補了這個空隙。不久之後,台灣的新支配者國民黨也開始製作政治宣傳電影,台灣有三家電影公司負責這個工作。但是,這些電影全以國語發音,一般台灣人聽不慣國語,就像聽到外國話一樣,觀看這樣的電影是不會產生共鳴的。
一九四九年,香港製作的廈語片(以廈門話發音的電影)在台灣極受歡迎,台灣立即興起廈語片的流行風潮。我在香港電影節看過幾部當時的廈語片,除了口白的音調較高之外,整體感覺廈門話和台語極為相近。比起國家強迫的國語,大多數的台灣人反而更喜歡能夠輕鬆聽懂的廈門話,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隔年一九五○年,日本片開放進口,而廈語片仍然非常流行,甚至打上「正宗台語片」、「台語片王牌」等宣傳字眼。這意味著,企圖要以廈門話來充當台語。香港的粵語片(以廣東話發音的電影)也以廈門話配音後在台灣上映。國民黨政府雖然致力推廣國語電影,但一直不見效果。
廈語片受歡迎的理由之一是,大部分的電影改編自民間戲劇歌仔戲(台語發音是Koahi)的故事,並且借用這些演員拍攝而成。歌仔戲在日本時代被視為亡國調」而沒有公演的機會。到了戰後,在大陸演員及歌手來台的助力下,開始流行起來,於一九五○年達到全盛。全台的歌仔戲團像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聽說總數超過四百家,其中尤以女性劇團受歡迎的程度最令人驚奇。這其實是當時東亞地區極具特色的現象,就像日本寶塚少女歌劇團、香港少女劇團,也分別在當地大受歡迎。這個現象有待研究者從大眾表演史及電影史兩方面來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台灣人開始製作自己的台語片,是在一九五○年代後半期。他們厭倦粗製濫造的廈語片,找來受歡迎的歌仔戲團演員拍攝電影。一九五六年,第一部台語片《六才子西廂記》以十六釐米拍攝而成。但是由於拍攝技術仍屬幼稚階段,上映幾天後就停播了。在這之後,導演何基明拍出了《薛平貴與王寶釧》。這部三十五釐米的電影,不管是演員演技或排場效果都相當優秀,新春一月四日在台北的中央、大觀、美都麗三家劇院上映,立即大獲好評。何基明利用該片賺到的錢成立了一家小小的電影公司,馬上著手拍攝續集及第三集。在《薛平貴與王寶釧》受歡迎的刺激之下,台灣各地開始拍攝台語電影。次年一九五七年,台語片的數量已超過廈語片。
但諷刺的是,歌仔戲電影的流行卻造成歌仔戲舞台表演的凋零。在數年之內,大部分的劇團都倒閉了。相較於以國家為後盾的大公司拍攝的國語片,拍攝台語片的製作公司資金有限,只能以低預算快速拍成。台語片在一九六○年代起起落落,到了八○年代一度完全消失。後來侯孝賢等新浪潮導演出現,讓出場人物在電影裡講台語或客家話。一路發展至今,現在的新春賀歲片都以台語發音,這是另一種脈絡下產生的回歸現象。
雖說如此,當今日台灣已經能夠積極採用多語言、多元文化主義時,重新討論台語片就成了必要的課題。這是為了讓台灣文化認同定調的工作,也能夠為台語片的電影史定位照映出新的發展方向。
第一次深度台灣紀行,第一次深刻感動
沒有人可以動搖台灣在文化上的自我認同
── 台灣是真實存在的。
電影史及文化比較研究人四方田犬彥眼中,這座美麗島上充盈著的
悸動人心的事物(心ときめかすもの)
周遊地球幾趟下來,能夠吸引我的,只有平凡而已。
── 電影編劇 Chris Marker
與其說是「平凡」,不如說是「家常」吧,對於日本重量級文化學者四方田犬彥而言,台灣的歷史,以及歷史積累型塑而成的社會現況,讓他這個異國人剛下飛機踏上這片土地的瞬間,就失去了防備心,真是令人困惑啊。
接下來,他感受到一種召喚,他被要求去認知那個橫亙其中的鄉愁和喪失感的混合物。然而,那是真實的嗎?這個鄉愁是屬於怎樣的意識形態呢?
台灣的植物讓人震撼,在路旁的盆栽裡、即將傾頹的廢屋庭院裡、大學校園裡,植物一逕地繁枝茂葉,誇示其旺盛的生命力。人被這一片濃綠所魅惑,有時竟覺得喘不過氣來。
然後他去到另一個海島。在叫做哈瓦那的城市裡,面前攤開好幾冊筆記本,這是他在台灣的所見所聞,裡面的素材召喚著他,去製作一份「悸動人心的事物」的清單。
最後,就是這本《心悅台灣》。
目次
序言
第一部 台北
名為台北的都市
最古老的城市 萬華
在日本統治的陰影下 大稻埕和西門町
布袋戲的結束
現代台灣人的三種父親形象 吳念真、王童、陳映真
神話回歸與廢墟 林懷民與宋澤萊
回憶楊德昌
阿爾發城的詩人 鴻鴻
粉紅色噪音的翻譯 夏宇
魏德聖與日本
太陽花學運 大學生占領立法院
第二部 尋找黑面女神
黑面女神 媽祖
進香日記
第三部 台南
台南印象
府城文士林瑞明
從民權路到大天后宮
失去的水道 水仔尾
剪黏與夜市
最早的台語電影
終章
後記
序言
你正在哈瓦那,眺望著波浪拍打岩壁高高濺起的飛沫,想起前一陣子待在台灣的日子。令人害怕的暑熱,每次外出回來,非得沖澡不可。窗外廣袤的藍天像要穿透似的,遠處隱約傳來練習康加鼓的聲音。
台灣和古巴有一點相似,也有一些不同。
兩地都是位於亞熱帶的小島,植物一逕茂盛地生長著。來到鄉下,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甘蔗田,黃昏時大王椰子搖曳著美麗的剪影。人們發揮著棒球及電影方面的才能,各自在屬於中文及西班牙的巨大語言圈,創造出風格獨特的文學。這兩個社會,距離單一民族的幻想甚遠,數個族群和文化共存混融著。在古巴,西班牙人消滅了原住民,召來了黑人和漢人;在台灣,原住民存活下來,不少人與漢人殖民者混血同化。兩地都信奉執掌航海的處女神,在加勒比海是瑪利亞,在台灣海峽則是媽祖。從地緣政治學來看,兩國皆為軍事據點,在冷戰體制下與鄰近大國曾經有過軍事上的緊張關係。不過兩國現在都跟美國沒有邦交,因此不像日本那樣成為美軍駐紮的基地。
若要說台灣和古巴的不同之處,倒是有一點,那就是古巴仍維持一黨獨裁政治,而台灣長期以來雖未形成多黨制政黨體制,但民主主義政體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已經軟著陸了。
你正在哈瓦那,想起前一陣子待在台灣的日子。
電影編劇家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在《日月無光》(Sans Soleil)說:「周遊地球幾趟下來,能夠吸引我的,只有平凡而已。」
那是你自幼累積至今、關於台灣的印象。
那美麗的、宛如出生自藍色海洋的蝴蝶標本。不知是誰當作伴手禮帶來的鳳梨酥。有著甜膩旋律的〈雨夜花〉黑膠唱片。寫著「大陸難胞奔向自由」的深藍色郵票(穿著粗布衣裳、瘦骨嶙峋的女人拿著手帕掩面哭泣)。伸出長長的舌頭、瞪大雙眼昂首濶步的巨大神像(不知在哪本書上看到的)。巨大的鍬形蟲。南部寺廟屋頂以美麗的形狀往上翹起的燕尾。發出響亮音色的銅鑼和嗩吶。插著蓮花的水瓶裡來回游動的小魚。
因此,當你在台北下飛機之後,第一站便直奔成功高中校園內的昆蟲館。在台灣,有兩件事讓你感到困惑,那是歷史和自然。
當人們知道你是日本人之後,會向你談起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的現代化、衛生和教育,甘蔗品種改良及土地灌溉的事情。台灣街頭充斥著日文,台灣人在日本三一一大地震時捐贈了巨額善款。這是你無法預期的情況(你最初到韓國留學的時候,日本卻是他們極力想要隱蔽的對象。當你開始關注民族主義者高聲提倡的那種複雜的日本觀時,一切就開始了)。
有那麼一瞬間,台灣讓你變得亳無防備。接著,你被要求去認知那個橫亙其中的鄉愁和喪失感的混合物。然而,那是真實的嗎?這個鄉愁是屬於怎樣的意識形態呢?
然而,最讓你感到震撼的卻是植物。
油棕櫚樹披覆著大量新芽,細長柔軟的枝條像麵線般向四面八方展開。馬氏射葉椰子的樹幹分出了數不清的枝條。錦屏藤有著無數的氣根,從莖節的地方長出,大量懸掛而下。大王椰子的老株在樹幹上長出粗大的瘤刺,大片的葉子叢生在樹頂上。姑婆芋和小芭蕉聚生在這椰子樹下方。紫檀的樹幹上長滿了厚重的苔蘚。台灣海棗的樹幹上有著明顯的刻痕,長得像酋長頭的巨葉正在與強風對抗著。檳榔樹有著像竹子般細長的樹幹。榕樹的樹根像章魚腳往四方伸出,粗大的樹幹互相糾纏,形成無法解讀的圖案。鳳凰木的細葉在高處搖曳著。荔枝樹彎曲的樹幹不斷分岔,果實不斷大量地掉落地面……
在路旁的盆栽裡、即將傾頹的廢屋庭院裡、大學校園裡,植物一逕地繁枝茂葉,誇示其旺盛的生命力。你被這一片濃綠所魅惑,有時竟覺得喘不過氣來。
現在,你在桌上擺著好幾冊的筆記本,仔細地反覆閱讀著。讓你感動的到底是什麼?究竟是什麼讓你感到驚奇和喜悅?你打算製作你的「悸動人心的事物」清單,如同一千年前京都的女散文家那樣地。(譯注:「悸動人心的事物」(心ときめきするもの)出自清少納言《枕草子》)
內文選摘(節錄)
名為台北的城市
若要介紹台灣,就必須先從台北捷運的廣播說起。
台北捷運在廣播站名時會以不同的語言重複四次。以「永春」為例,會以「Yonchun」、「Yinchun」、「Yentsun」、「Yonchun Station」的順序廣播,依序是國語(北京話)、台語(閩南語)、客語、英語。若在鄉下搭公車,最後廣播的有時不是英語,而是當地原住民的語言。
在台灣二千三百二十三萬人口(二○一一年調查)當中,南島語族的原住民人口約占二%、也就是五十一萬人(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增訂本)》,濱島敦俊、石川豪等譯,平凡社,二○一三)。若依一般的分類法,他們是由已經漢化的平埔族十族及政府認定的高山族十六族所構成,擁有各自的語言、信仰及習俗。南島語族以太平洋及印度洋全域為居住範圍,西邊以馬達加斯加島為界,中間有印尼、菲律賓,東邊則達夏威夷島、復活節島、紐西蘭。有些學者認為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發祥地,但還未能成為定論。
台灣現在已經不用「先住民」這個詞了,因為「先」這個字有強烈的「已經滅絕」的詞義,因此在一九九四年第三次修憲時,正式將他們稱為「台灣原住民」。不管如何,在交通廣播用語和行政當局的立場是:在台灣使用的所有語言都是平等的。我居住的公寓由一個老人和年輕女性負責打掃,一開始他們就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是阿美族人。老人頗能說日語,但不甚流暢。老人告訴我,小時候他家附近有一個日本人,在戰後確定要回日本時,那日本人在海邊擁抱他,向他道別。老人還說,台灣的棒球是很強的,當然日本也很強啦。
幾乎沒有例外地,台灣人從小就接觸多種語言,會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語種。在這個比日本九州還小的島嶼上,至少有十七種語言並存交雜。對於信奉單一語言幻想的日本人與韓國人而言,這種複雜的語言環境是無法想像的,但台灣人就生活其中。台灣人對於自己該選擇用哪種語言說話,與自己的出身背景、歷史及意識形態有關,不過他們也習於像雜耍遊戲般地操弄數種語言。例如,一九九○年代以降的搖滾樂,就流行將客家語和原住民語放進歌詞裡,作家宋澤萊則將相同內容的小說用台語和國語各寫一遍,而在楊德昌的電影《獨立時代》(在日本發行時的名稱是《エドワード‧ヤンの恋愛時代》)裡,就有一場是一對男女在搭計程車時同時以中文和台語進行漫長的交談。
再把話題拉回站名的廣播,雖然同一個地名在不同語種裡有不同的發音,但是寫成漢字的表現方法只有一種,所以在標示上不會有繁雜的問題。只要能寫出正確的漢字,任何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文化傳統來發音。台灣社會是由複數文化和語言形成的這個概念,已是現在台灣人的基本認知。台灣政治體制對於文字的理念是:漢字絕對不可以簡化,即使是複雜難寫的文字,也必須正確寫出。全世界現在只有香港和台灣仍然保存漢字原樣,繼續使用著。越南已禁用漢字;韓國則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將漢字推至教育體制邊緣;日本在美軍占領下推行漢字簡化運動;中國原本以廢除漢字為最終目標,但中途受挫而改推漢字簡化。因此,台灣在文化史上是極具意義的。
我在台灣的大學裡學到了一個基本知識,那就是在課堂上對於中國的稱呼。眾所周知,蔣介石率領的中國國民黨敗給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之後,在一九四九年逃到台灣。台灣從此受到「中華民國」的統治,而中國大陸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雙方自彼時反目到現在。在台灣內部,有一派人主張台灣獨立,欲取得世界的承認,也有一派人積極尋求與中國統一。如果你是以「台灣」、「大陸」來稱呼,就會被視為統一派;而如果你以「台灣」、「中國」來稱呼,表示你承認兩地各為一國,強調台灣具有不同於中國的獨立性。在日本人看來或許是瑣碎的事,但對台灣人卻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牽涉到自己對政治及文化認同的立場。即使是細微的用語差異,也會成為這個人所依歸、所自我認同的佐證,必須加以留意。一位教授如此告訴我: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附庸國。台灣吸收了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不偏向任何一方,汲取島內各種文化的多樣性而形成獨特的社會形態。台灣雖然與美國、日本、中國沒有正式邦交,也無法在聯合國取得席位,但沒有人可以動搖台灣在文化上的自我認同。台灣是真實存在的。
我以電影史研究者的身分進行演講及授課的主題有:日本紀錄片在三一一大地震之後的變化、與李香蘭有關的性別(Gender)問題、日本電影裡的沖繩表象、滿洲國「啟民電影」(宣傳片)分析等。聽眾為一般學生、研究者、教授等,他們都很認真地回應我的談論。尤其是我到一九九九年大地震受災嚴重的台灣中部幾所大學演講時,我們針對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及核災相關拍攝行為的道德標準問題,進行了誠懇深刻的交流討論。
在授課和演講的空檔,我常到台北電影資料館觀賞館方收藏的台語電影。這不是國民黨政權以中文製作的大型反共電影,而是運用台灣民間資金拍攝的小規模電影、是以台語製作的B級娛樂電影。就我所知,除了台灣人之外,關心這個議題的只有一位摩洛哥的女性研究者。
此次並非我第一次來台灣。其實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只要有機會我就往台北跑。但不知為何,每次的訪問行程總是來去匆匆。就我造訪全世界都市的次數而言,排在巴黎、首爾、香港、紐約之後的,應該就是台北了。但每次造訪的幾天都住在飯店,訪問目的是參加學會發表或訪問電影導演拍攝的新片,根本沒有時間以某一處為據點,用較長的時間與人們接觸,或者參加民間宗教巡禮活動。我一直被這個不充足的感受困擾著。就這一點而言,我在韓國的時候,相對地幸運多了。我無法創造一個能夠跨越電影評論這個狹窄領域、直接面對台灣文化的機會。
在我滿六十歲時,我下了一個決心,並且實踐了。我辭去日本多年的大學工作,打算專心從事寫作。當此事實現後,我馬上想到的,便是長期居留台灣。我已經從無聊的授課和教授會議中解放出來,開始走向實踐多年來的夢想之路。
回憶楊德昌
對於楊德昌(Edward Yang)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東京國際影展上映,我至今仍記憶猶新。那天是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影展對於這部電影的歸屬傷透腦筋。中國大使館事先提出警告,如果官方使用「中華民國」或「台灣」名稱的話,本次影展的所有中國電影會全部撤掉,而且今後不再參展。
影展不得已只好偽造《牯嶺街》的出身地,以「日本美國合作電影」這個根本不存在的曖昧名稱上映。而這部電影仍然獲得評審團特別大獎。
在影展最後一天的頒獎典禮上,楊德昌站在台上對著麥克風沉默了一段時間,接著,像是要反擊之前所受的屈辱似地,他以簡潔的英語堂堂正正地說:「我是來自台灣的導演,而且這是一部台灣電影。」整個會場瞬間響起歡呼聲,我對他(當時)的太太蔡琴道了一聲恭喜。會場上很多的台灣人、以及知曉這部電影上映前曲折過程的少數日本人,都拚命地鼓掌。
我第一次觀賞楊德昌的《恐怖分子》,是在拍攝後隔年的一九八七年。當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沒有做任何準備功課,就在曼哈頓中國城的新都戲院看了這部具有歷史意義的電影。
這是一部從片頭開始就充滿張力的電影。一個以攝影師為志願、年輕的資產階級男子和他的女友裸身在床上,女友正讀著一本散文集。化驗師與女小說家滿臉倦怠,以冷淡、沒有愛意的口氣交談著。一把槍從公寓窗口伸出,房間裡傳來嗚咽的哭聲。
警車鳴笛來到現場,戴黑眼鏡的警長指揮逮捕犯人。但是,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或許是受到強烈的直覺督促,那位資產階級青年趕到現場。在槍擊戰當中,一位混血少女企圖逃走。她未及深思地從樓上往下跳,導致腳部骨折。青年情不自禁地連續拍下她的姿態,悄悄地將她送往醫院……同一時間點在不同場所發生的四起事件,每個鏡頭沒有因果關係地串連起來,故事一直進行下去。不知所云。在美國的電影學校,一定會教導學生說這是絕對不允許的「錯誤串接方式」。非但如此,為電影故事賦予基礎性的時空整合性,在電影一開始就整個地瓦解了。
影像的殘缺片段像是兩道謎題互相拉扯、纏繞著。青年不願等候徵兵通知而四處遊蕩。痛恨母親的混血少女逃脫軟禁狀態,在街頭青澀地模仿妓女的模樣。女小說家正陷入極度消沉的情緒裡,以為丈夫有外遇而開始分居。少女拿著電話簿隨機亂打電話,這個契機讓女作家寫出一部出色的長篇推理小說。有一天,少女突然想要去看看以前住過的公寓。那裡整面牆上貼滿了少女的相片。她與那位攝影師青年有了一夜情之後,便像小鳥似地飛走了。青年回到自己富裕的家中,徵兵通知寄到了。就像模仿自己創造的小說情節那樣地,小說家被自己的丈夫射殺了。
我想要試著說明《恐怖分子》的情節,卻很不順利。其實本當如此,因為這部電影完全無視於一般電影必須流暢地講述故事的這個要求。每個鏡頭都讓觀眾置身於截然不同的空間所發生的事件裡,而且在所有事件還未結束時,又被帶往後面的鏡頭。好幾條分出去的故事線終於纏在一起,一個虛構的臉龐於焉浮現。那是一張名為台北的都市之臉,一個突然進入高度消費的社會、必須面臨軍事不穩定狀態的都市之臉。真是一部很棒的電影。我告訴自己,為了接受這部電影,我必須忘記原本建構好的關於電影的所有體驗,才能夠對這部電影做出評價。
進香日記
從開始進香那個瞬間起包圍住我的,是一種壓倒性的時空意識改變。我明白自已已從原本熟悉的、世俗性的時間概念中脫離出來,將自己委身於一個完全未知的、另一種不同的時間秩序裡。鎮瀾宮華麗的起駕儀式結束之後,大批的信徒追隨神轎出發了。留在這裡的,是深深的黑暗。當我面對這片黑暗時,感受到的便是這種印象。剛才還一起參與慶典的大量人潮都被這個黑暗所吞噬,而我自己也將走入其中。
沒有方向感,也沒有距離感,只能在這個微亮的空間裡,依稀辨識著忽而出現的先行者的身影,跟在他們後面走著。出發時間嚴格規定為凌晨零時,一旦開始進香,這裡就不再有時間感,眼前可見的只有無止盡擴散開來的黑暗。
我參加的進香團遞給我的並不是地圖,而只是一張紙,上面記載著神轎到達奉天宮之前沿路參訪的廟名及預定抵達的時間。開始進香徒步不久,我就知道預定抵達時間完全不具有任何意義。神轎總是不以為意地遲到,有時晚到兩小時,甚至還曾慢五小時。進香團的移動時機完全依照坐鎮於神轎內的媽祖的意思,絕對不可以發出責難之聲。時間沒有嚴格分段,就像軟糖那樣可伸可縮,跟我們平日習慣的線性移動大異其趣。
隨著時間意識的變化所產生的是空間意識的變化。
信徒必須身心清淨才能參加進香。同樣地,神轎通過的空間也必須事先清淨才行。隊伍最前面的滑稽眾神偶及報馬仔的工作,便是將媽祖即將到來的消息告知村民,要他們開始準備以改變空間。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和白煙的目的,便是要將世俗的空間加以淨化,以火牆將空間阻絕,在媽祖出現之時,短暫建構出一個神聖的結界。媽祖之所以能夠無視於現實法則進行遊戲式的移動,是因為祂隨時能夠置身於這個世俗雜物全都排除的清淨空間。
神轎總是挑移動效率差的路線行進。有時會在同一個地點打轉,有時繞了很遠的路,總是不斷無意義地偏離路線。開車或搭遊覽車的人,勢必選擇已舖好的馬路行進,無法跟隨這個無效率的路線。媽祖這個方向定位乍看是恣意而為,但若是從頭到尾都以步行進香的話,就能夠了解其真意。一天平均睡眠三到四小時,全程以徒步方式走完全程的人,最後腳底長出水泡。待水泡破掉之後,仍必須拖著這個痛苦繼續走下去。無止盡的疲勞感持續增加,真是壯烈的苦行啊。但是,在這個痛苦的媒介下,他們漸漸地從個人式的、人稱式的狀態脫離出來,轉化為匿名的「走動著的存在」。
進香到底是怎樣的行為呢?雖然長時間的歲月流逝之後會產生若干變化,但是從大甲到彰化、西螺的這條路線,在清朝時期就已存在。進香者意識到自己現在走的這條路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路,因此他們會發現,他們現在所處的時間已經超越「現在」這個被框限的時間。這讓他們眼前所見的水田和魚池,看起來都像是永恆不變的。借用宗教史學家伊利亞德的說法,這是對於循環式的時間意識的發現,而這是一種曾經支配農耕社會的時間意識。這個發現讓人們從個體抽離出來,被定位成祖型重複的主體。在強烈陽光的照射下,腦袋無法思考,只是日復一日不斷地走著。這個單純又無止盡的重複行為讓「香客」(進香客)去除雜念,拉升到異常興奮的情緒。
這種興奮的情緒在經過某個時間點之後會轉變成恍惚感:我正在走著,我之前有走過,我接下來要開始走。在進香途中,參加者如此地與神轎裡的媽祖進行神祕的交流。他們感受到是,媽祖的靈力讓自己有走下去的力量,也促成自己變得與媽祖一樣的神聖化。
最早的台語電影
聽說台灣第一部台語片已被找到的事,是我來到台灣一個月之後。那時我在新竹清華大學演講結束,與主辦單位的教授們一起吃午餐時,得知這個消息。其中一位教授專門研究台灣電影,他以激動的口吻告訴我,《薛平貴與王寶釧》在兩個月前終於被找到,現在正在台南修復中。
對於一個電影史研究者而言,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若以天文學家做比喻的話,就等於是在太陽系發現新的行星,意義相當重大。我確信,當台灣的電影人聽到這個消息時,一定會有某種感動的。《薛平貴與王寶釧》是拍攝於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釐米電影,是台灣第一部台語片。當初上映時非常轟動,但後來一直以為永遠佚失了,至少我手頭上的幾本台灣電影書籍都是這麼記載的。不只是電影研究者,對於慣用台語的大多數台灣人而言,這個遺憾得以補足,具有極大的意義。
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戰敗,台灣被中華民國接收,原本在台灣長期上映的電影無法再播放了,好萊塢電影和來自上海的中國電影填補了這個空隙。不久之後,台灣的新支配者國民黨也開始製作政治宣傳電影,台灣有三家電影公司負責這個工作。但是,這些電影全以國語發音,一般台灣人聽不慣國語,就像聽到外國話一樣,觀看這樣的電影是不會產生共鳴的。
一九四九年,香港製作的廈語片(以廈門話發音的電影)在台灣極受歡迎,台灣立即興起廈語片的流行風潮。我在香港電影節看過幾部當時的廈語片,除了口白的音調較高之外,整體感覺廈門話和台語極為相近。比起國家強迫的國語,大多數的台灣人反而更喜歡能夠輕鬆聽懂的廈門話,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隔年一九五○年,日本片開放進口,而廈語片仍然非常流行,甚至打上「正宗台語片」、「台語片王牌」等宣傳字眼。這意味著,企圖要以廈門話來充當台語。香港的粵語片(以廣東話發音的電影)也以廈門話配音後在台灣上映。國民黨政府雖然致力推廣國語電影,但一直不見效果。
廈語片受歡迎的理由之一是,大部分的電影改編自民間戲劇歌仔戲(台語發音是Koahi)的故事,並且借用這些演員拍攝而成。歌仔戲在日本時代被視為亡國調」而沒有公演的機會。到了戰後,在大陸演員及歌手來台的助力下,開始流行起來,於一九五○年達到全盛。全台的歌仔戲團像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聽說總數超過四百家,其中尤以女性劇團受歡迎的程度最令人驚奇。這其實是當時東亞地區極具特色的現象,就像日本寶塚少女歌劇團、香港少女劇團,也分別在當地大受歡迎。這個現象有待研究者從大眾表演史及電影史兩方面來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台灣人開始製作自己的台語片,是在一九五○年代後半期。他們厭倦粗製濫造的廈語片,找來受歡迎的歌仔戲團演員拍攝電影。一九五六年,第一部台語片《六才子西廂記》以十六釐米拍攝而成。但是由於拍攝技術仍屬幼稚階段,上映幾天後就停播了。在這之後,導演何基明拍出了《薛平貴與王寶釧》。這部三十五釐米的電影,不管是演員演技或排場效果都相當優秀,新春一月四日在台北的中央、大觀、美都麗三家劇院上映,立即大獲好評。何基明利用該片賺到的錢成立了一家小小的電影公司,馬上著手拍攝續集及第三集。在《薛平貴與王寶釧》受歡迎的刺激之下,台灣各地開始拍攝台語電影。次年一九五七年,台語片的數量已超過廈語片。
但諷刺的是,歌仔戲電影的流行卻造成歌仔戲舞台表演的凋零。在數年之內,大部分的劇團都倒閉了。相較於以國家為後盾的大公司拍攝的國語片,拍攝台語片的製作公司資金有限,只能以低預算快速拍成。台語片在一九六○年代起起落落,到了八○年代一度完全消失。後來侯孝賢等新浪潮導演出現,讓出場人物在電影裡講台語或客家話。一路發展至今,現在的新春賀歲片都以台語發音,這是另一種脈絡下產生的回歸現象。
雖說如此,當今日台灣已經能夠積極採用多語言、多元文化主義時,重新討論台語片就成了必要的課題。這是為了讓台灣文化認同定調的工作,也能夠為台語片的電影史定位照映出新的發展方向。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四方田犬彥
1953年出生於大阪,東京大學攻讀宗教學,東大研究所攻讀比較文學,長年擔任明治學院教授,主要講授電影史課程。於韓國建國大學、韓國中央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台拉維夫台拉維夫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擔任客座教授及研究員。目前主要研究及書寫領域是以影像與文學為主的文化現象。亞洲相關著作有:《對我們而言的「他者」韓國》、《首爾風景》、《香港-東京往復書簡:守望香港》(合著)、《亞洲全方位》、《電影風雲》、《亞洲電影的大眾想像力》、《李小龍》等。譯有愛德華‧薩伊德《回到巴勒斯坦》、《帕索里尼詩集》。詩集有《人生的乞食》、《我的煉獄》。曾獲SUNTORY學藝獎、桑原武夫學藝獎、伊藤整文學獎、藝術選獎等。最近一次獲獎紀錄是2014年第64屆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賞。已翻譯為中文的著作包括《守望香港》、《日本電影與戰後的神話》、《可愛力量大》、《亞洲背景下的日本電影》、《日本電影100年》、《旅行之王─旅之王樣》。
譯者簡介
白春燕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淡江大學日文系、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研究所畢業。曾任《國際魯迅研究》、《國際村上春樹研究》翻譯編委。研究範圍涵蓋日治時期中國、日本、台灣的文學交流、左翼文藝理論流布。已出版著作《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1930年代台日普羅文學思潮之越境交流》。
四方田犬彥
1953年出生於大阪,東京大學攻讀宗教學,東大研究所攻讀比較文學,長年擔任明治學院教授,主要講授電影史課程。於韓國建國大學、韓國中央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台拉維夫台拉維夫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擔任客座教授及研究員。目前主要研究及書寫領域是以影像與文學為主的文化現象。亞洲相關著作有:《對我們而言的「他者」韓國》、《首爾風景》、《香港-東京往復書簡:守望香港》(合著)、《亞洲全方位》、《電影風雲》、《亞洲電影的大眾想像力》、《李小龍》等。譯有愛德華‧薩伊德《回到巴勒斯坦》、《帕索里尼詩集》。詩集有《人生的乞食》、《我的煉獄》。曾獲SUNTORY學藝獎、桑原武夫學藝獎、伊藤整文學獎、藝術選獎等。最近一次獲獎紀錄是2014年第64屆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賞。已翻譯為中文的著作包括《守望香港》、《日本電影與戰後的神話》、《可愛力量大》、《亞洲背景下的日本電影》、《日本電影100年》、《旅行之王─旅之王樣》。
譯者簡介
白春燕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淡江大學日文系、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研究所畢業。曾任《國際魯迅研究》、《國際村上春樹研究》翻譯編委。研究範圍涵蓋日治時期中國、日本、台灣的文學交流、左翼文藝理論流布。已出版著作《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1930年代台日普羅文學思潮之越境交流》。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