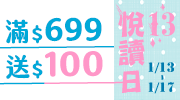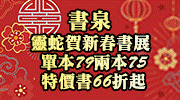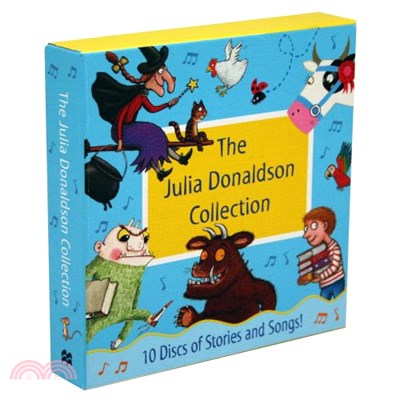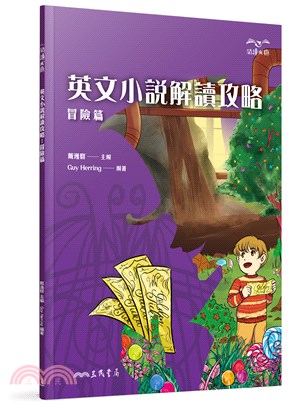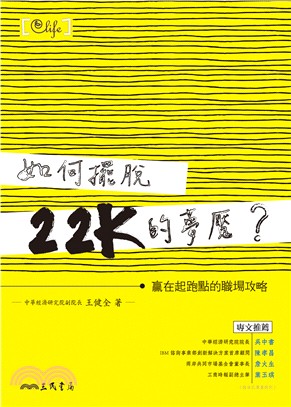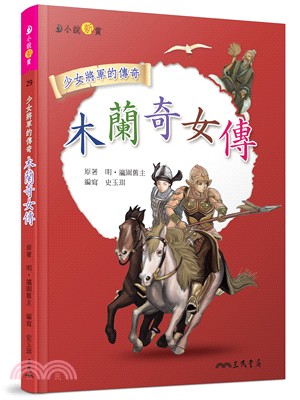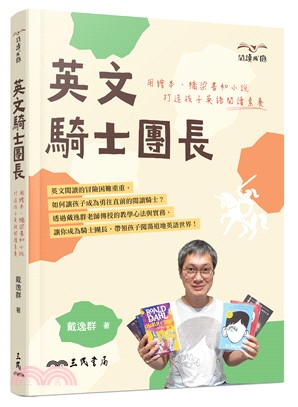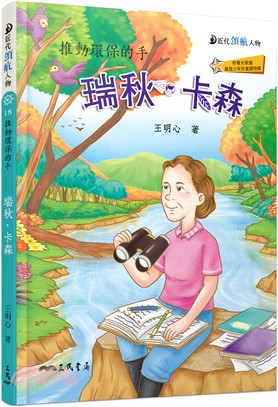好品味,壞品味?:一場拆解音樂品味的聆賞實驗
商品資訊
系列名:common
ISBN13:9789869577526
替代書名:Let's Talk About Love: A Journey to The End of Taste
出版社:大家
作者:卡爾‧威爾森
譯者:陳信宏
出版日:2018/02/07
裝訂/頁數:平裝/256頁
規格:22cm*17cm*2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沒多久,你發現作者是在打臉菁英品味,
最後明白,其實每個人都被婊了!
一本在音樂圈、世界各地大學的英文及文化研究系所,還有部落格與podcast,
甚至電視談話節目中,引爆品味辯論的評論經典!
有人喜歡藍色風景畫,有人喜歡黑色抽象畫;有人喜歡席琳.狄翁,有人喜歡巴布.狄倫。品味戰爭,每天都在我們的世界開打。而音樂可能比任何型式的嗜好更能標記個人認同,更能表現出你想讓別人認識的表象人格。音樂的品味戰爭,其實是「身分認同」的戰爭!
但是,我們會如何討論「喜愛」,或者更精確說,我們會如何討論「厭惡」?藉著仔細檢視我們在音樂上的恐懼和厭惡,檢視我們認定的「壞品味」,可能會讓我們看出許多隱藏的真相,以及你所不認識的自己。
本書作者卡爾‧威爾森身為靠「品味」吃飯的專業樂評人,他逐漸對「品味」感到好奇:品味如何形成?如何運作?為何大眾品味似乎與所謂「文化菁英」間存在巨大的差異?為了解答這些問題,卡爾決定進行一項實驗:認真聆聽一部廣受大眾喜愛,卻令他厭惡的音樂作品,並深入研究其表演者,看看他是否會因此愛上這部作品,並開始欣賞他原本厭惡的這名音樂人,從而動搖他的「品味」根基。
魁北克出身的卡爾選擇了他最知名的同鄉,在當地具有民族英雄地位的天后歌手席琳‧狄翁。
在本書中,讀者將隨著卡爾的研究取徑前進,對品味展開研究與反思。他先是檢視流行樂評史上的翻案紀錄,包括金屬、迪斯可、異國沙發音樂乃至前衛搖滾等,藉此質疑評論者的威信。再從席琳的法語背景切入美國流行音樂的種族地圖,觀察黑人與白人音樂如何畫地分界,及模糊地帶如何變動;藉由席琳打入日本市場的過程展示跨國唱片公司的全球在地化策略;更從席琳充滿爆發力的演唱方式分析流行音樂的表演美學與角色塑造。卡爾也實際拜訪了幾位席琳歌迷,驗證樂評人想像中的壞品味大眾樣貌究竟有幾分為真,這些歌迷的音樂品味又如何反映他們的人生經歷。
接著,他從席琳的音樂類型歷史談到雅俗分界的起始點、階級品味的成形,並爬梳布迪厄的思想,探討品味如何扮演策略性工具的角色,一方面用來區隔社會階層低於我們的人,另一方面也用來追求我們認為自己應得的地位。品味因而是一種區辨我們和別人的手段,也是對於差別的追求。最後,卡爾將重新聆聽席琳的《說愛》專輯,並寫下一篇完整的評論文章,作為實驗的總結。
本書於2007年出版後引起不少討論,作者也因此受邀上了知名的深夜諷刺電視節目《科爾伯特報告》。許多教師在美學哲學、批評、流行音樂與文化研究的課堂上使用本書,例如小說家強納森‧列瑟在哥倫比亞大學開設的非虛構文類寫作課程(知名演員詹姆斯‧法蘭科更因爲這門課而對本書愛不釋手,甚至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中對娛樂記者聊起本書)。2014年,卡爾為本書的再版召集了一場文字雞尾酒派對,邀請藝人、思想家與評論家等各界人物發表他們對本書的回應。其中某些人直接回應本書議題,某些人則把本書當成跳板,提出自己的論述與分析,使得本書成為更多思考與對話的起點――而這正是我們對藝術評論的諸多期望之一。
作者簡介
出身加拿大魁北克的文化評論家。為網路雜誌《頁岩》(Slate)撰寫音樂評論,也為《紐約時報》《環球郵報》及《大西洋》、《Hazlitt》等報章雜誌撰稿。
他於2007年在Continuum出版社「33 1/3轉」系列中出版本書,不久即好評四起,許多評論家都立即將本書列為該系列中最喜歡的作品。但本書引發的激烈品味辯論不僅限於音樂寫作圈,也包括世界各地大學的英文和文化研究系所,還有部落格與podcast,甚至電視談話節目。於是作者在2014年推出擴充版。除了原先內容,也收錄著名作家如尼克.宏比、樂手如Nirvana前貝斯手Krist Novoselic與文化批評家如Sukhdev Sandhu針對本書主題所寫的回應,以深化並充實「談論喜愛」一事的意義。
譯者簡介 陳信宏
專職譯者,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翻譯獎項,並以《好思辯的印度人》(先覺出版)入圍第33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譯作包括《令人著迷的生與死》《宗教的慰藉》《新聞的騷動》(先覺出版)等。
目次
第1章 ▎來談談厭惡
第2章 ▎來談談流行音樂(以及流行音樂的批判者)
第3章 ▎來用法語談談
第4章 ▎來談談征服世界
第5章 ▎來談談濫情
第6章 ▎來大聲唱歌
第7章 ▎來談談品味
第8章 ▎來談談誰的品味差
第9章 ▎找些歌迷來談談
第10章 ▎來唱首龐克版本的〈愛無止盡〉(或者來談談我們的感受)
第11章 ▎來談談《說愛》
第12章 ▎來談談喜愛
【第二部 隨筆:當我們說愛,我們在說些什麼】
序――卡爾‧威爾森
我們值得這樣的藝術家――尼克.宏比
把燈開著,就不會那麼無用――克里斯特.諾弗塞利克(前Nirvana樂團貝斯手)
如果女孩全都被送到北海以外――安.鮑爾絲
最容易忘記的事情――瑪麗.蓋茨基爾
跟什麼相比?――傑森.金恩
來談談黛安娜.羅絲――達芙妮.布魯克斯
深陷其中――德魯.丹尼爾
老套之子――蘇克德夫.桑杜
情境脈絡以內與以外的表演――詹姆斯.法蘭科
太多社會學――馬可.羅斯與《n+1》雜誌編輯
捨棄對於好品味的捨棄――強納森.斯特恩
回家――歐文.帕雷特
歌單:來聆聽愛――希拉.海蒂
第三部 後記
來談談後續――卡爾.威爾森
書摘/試閱
第二章 ▎來談談流行音樂(以及流行音樂的評論者)
我討厭席琳.狄翁,不只是因為艾略特.史密斯。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她的音樂是把單調乏味強化到令人反感的程度——雖是節奏藍調,卻把性愛與狡黠的元素切除一空;雖是法國香頌,卻把機鋒與靈魂剜除殆盡。她的作品是歐普拉認同的消費主義心靈雞湯,無窮無盡地強調自我肯定,卻對社會衝突與社會脈絡視而不見。以名人來說,她就是無趣至極的加拿大乖寶寶,連搞出像話的個人醜聞都辦不到,唯一的例外是一件令人作嘔的舊聞:她嫁給從她十二歲就開始代理她的經紀人,對方年紀比她大了一倍。
就我所知,我連一個喜歡席琳.狄翁的人也沒遇過。
我離開席琳.狄翁的大本營蒙特婁之後,對她的鄙夷還是沒有消退,即便我已不那麼沈迷於「地下」文化戒律,開始欣賞較為主流的音樂之後,也還是一樣。我對音樂的態度轉變稱不上是什麼創舉,僅是跟整個音樂評論界的步調一致,只有最牛脾氣的老頑固以及莽撞浮躁的年輕小伙子才不受影響。這種轉變的速度快得驚人。一個新世代在音樂評論界獲致了影響力,其中許多人比較關注嘻哈、電子音樂或拉丁音樂,而不是搖滾樂——不管是不是主流搖滾。這群人發起全面的批判,批評以搖滾文化的準則衡量所有流行音樂的毛病,也就是所謂的「搖滾主義」,而與此相對的則是「流行主義」(popism)或「流行樂觀主義」(poptimism)。線上音樂部落格與討論區加速了這類意見趨勢的傳播。網路摒棄密集聆聽整張專輯的做法,轉而偏好零散挑選單曲下載聆聽,新奇的流行音樂作品因此有更多機會出頭。此外,下載音樂的方式也打破唱片公司對於音樂發行近乎獨占性的掌控,反抗大眾文化音樂巨獸的行為由是顯得多此一舉。
另一方面,當時正好有一些絕佳的流行音樂作品推出,成為所有人的討論話題。一九九九年,在多倫多的一家書店裡,一個傑出的年輕實驗音樂吉他手出乎我意料地問我有沒有聽過少女天后艾莉亞的暢銷單區〈你是那個人嗎〉(Are You That Somebody)。我當時還沒聽過,但不久之後就聽到了。那是一首節奏繁複的節奏藍調,製作人提摩西.莫斯利(Timothy Mosley)又叫提姆巴蘭,他與同儕把流行榜變成樣態多元的遊樂場。在提姆巴蘭之後,流行樂界天翻地覆,即便是備受鄙夷的青少年流行音樂,樂評家也注意到同出一脈的創意表現。到了二○○七年,在《紐約時報》這類地位崇高的出版品和高傲的老牌雜誌《紐約客》上,讚揚一曲成名的節奏藍調歌手及「商場龐克」青少年樂團 的文章之多,並不下於稱譽布魯斯.史普林斯汀或U2合唱團的篇幅。
這是多次修正主義所帶來的結果:聲稱某件遭到眾人嚴詞批判的音樂作品其實是天才之作,這樣的言論常能為樂評家引來注意。多年來,這種做法也確實「挽救」了金屬、迪斯可、異國沙發音樂乃至前衛搖滾等音樂類型,以及從阿巴合唱團到機車頭樂團的許多藝人。儘管先前提過《滾石》雜誌的譏評,但現在頑童合唱團在樂評界的地位卻與吉米.罕醉克斯不相上下。就連南北戰爭以前的黑面歌舞音樂 也獲得新評價,樂評家發現其中的旋律及種族歧視病理都是美國流行歌曲扭曲根基的一部分。
這股省思浪潮讓樂評家的鄙斥顯得不太可信,畢竟,既然一九七○年代的樂評家對迪斯可的看法大錯特錯,那麼他們現在對小甜甜布蘭妮的惡評不也可能有問題?流行音樂為什麼一定要變成陳年舊物才能獲得公平待遇?流行音樂為什麼一定是「不入流」的喜好?流行音樂評論的出錯紀錄一旦累積得夠長,那麼不論是大眾或樂評家的共識,看起來也就都不再是可靠的指引。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忠於自己的喜好?當今的論點認為,除非你喜歡白人至上歌曲,否則絕對沒有理由要為自己喜歡的音樂感到內疚或羞愧。我同意這樣的看法。但奇特的是,樂評家的「個人喜好」仍然經常引領所有人走上同一條道路。
這種集體的路線調整也是一種市場修正。經過一九九○年代初期的騷亂之後——當時「地下音樂」獲得主流的矚目,但立刻又遭到揚棄——許多樂評家與「地下音樂」的樂迷因此陷入憤世嫉俗的情緒。樂評家與一般大眾之間揮之不去的品味落差,恐將演變為死守陣地的戰爭,以致喜歡艾略特.史密斯這類「樂評寵兒」跟喜歡流行歌星成了互斥的兩件事。不過,這種現象並不持久。學者也許能夠對大眾品味徹底嗤之以鼻,而偏好怪異艱澀的音樂作品,但現職的流行音樂評論家如果這麼做,長期下來不免會丟掉工作(而且是咎由自取)。況且,所謂的「地下音樂」也已逐漸陷入泥沼。
不過,叫好與叫座之間的代溝不論怎麼縮減,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每到年底,當樂評家列出年度最佳專輯,電台司令(Radiohead)、鬼臉煞星(Ghostface)或巴布.狄倫總是會勝過大多數的排行榜贏家(儘管排行榜贏家不再全軍覆滅)。在影評人的最佳電影名單上,暑期賣座巨片同樣只能讓位給票房侏儒,包括令人喘不過氣的家庭劇情片、「獨立製片」的黑色喜劇,以及亨利.詹姆斯小說的改編電影。這種分歧一再出現,以致顯得相當天然。一般人常說這只不過是因為評論家受過美學教育,接觸的作品也遠比大眾來得多。不過,這樣的說法似乎暗示了評論家的評價比較客觀也比較持久,但紀錄卻顯示事實並非如此。
歸根究底,如果喜好沒有對錯之分,而各式各樣的流行音樂也能夠滿足大眾形形色色的需求,那麼我和許多評論者對於席琳.狄翁的厭惡到底有什麼實質根據?
儘管如此,英國樂評家暨社會學家佛瑞茲(Simon Frith)在二○○二年接受rockcritics.com訪問時卻說得一點也沒錯,席琳.狄翁「可能是我記憶裡最受厭憎的超級巨星,至少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不喜歡她,不只是樂評家,甚至連我岳母也是一樣」。他接著指出:「我不認為她有可能像阿巴合唱團那樣獲得平反,大家好像都覺得她就是芭樂到不行。」
而且,佛瑞茲還是席琳.狄翁的歌迷。
***
音樂次文化之所以存在,原因是我們的本能反應告訴我們特定種類的音樂適合特定種類的人。隱藏在其中的密碼不一定清楚可見。歌曲的節奏、前衛性、溫情、獨特表現,或是歌手身上某種難以言喻的特質,都會吸引我們。我們也會聽聽朋友或者文化領袖所推薦的音樂。不過,我們很難不注意到這類程序如何反映以及造就我們的自我定義,也很難不注意到表象人格(persona)與音樂品味經常帶有相當高的一致性。這種現象雖然在堪稱認同戰爭的高中階段最是露骨,但在人生的其他階段,音樂也一樣標記了個人認同。藉著脫口而出的鄙夷語句,像是「小女生的歌」、「只有嬉皮才會喜歡那個樂團」、「聽起來像是約會強姦犯愛聽的歌」,我們把自己不想被歸入其中的群體遠遠推開。精神分析一定會說,比起顯意識當中的渴望,我們厭惡的對象其實更能夠揭露有哪些東西在我們不情願的狀況下仍然吸引了我們。藉著仔細檢視我們在音樂上的恐懼和厭惡,檢視我們認定的「壞品味」,有可能讓我們得知哪些不愉快的真相呢?
一九九九年,英國《獨立週日報》(Independent on Sunday)的「他們為什麼有名?」系列專欄以痛快公然的菁英主義姿態描繪了席琳.狄翁的歌迷在許多非歌迷想像中的樣貌:「必定有一群歌迷被夾在反胃作嘔與漫不在乎的態度之間,那是我們其他人根本不會注意到的一些平凡溫吞的中間英格蘭人物(譯註:中間英格蘭(Middle England)是一種社會政治用詞,指的是英國中下層階級抱持保守或右翼思想的人口。)。想必都是些老奶奶、身穿晚禮服的人士、體重過重的兒童、手機銷售員以及購物中心愛好者之輩。」
讀到這段文字,我不禁同情起那些人來。他們也許身穿不合時宜的晚禮服,也許是過胖的小朋友,卻只因為喜愛那個嗓音傲視全世界的美豔女士所唱的情歌,就遭到這樣的惡意謾罵。而且,比起我對席琳.狄翁的憎厭,我更痛恨《獨立週日報》這個不知名的撰稿人。不過,他其實也只是明確表達出我們的偏見。例如我說「歐普拉認證」,其中隱含的不就是他描述的這種形象嗎?他對於席琳.狄翁歌迷的描寫如果正確無誤,那麼其中的成員在鐵達尼號上想必主要都是三等艙的乘客。我對她的不屑如果也延伸到他們身上,那麼我是不是打算剝奪他們搭上救生船的權利?
《獨立週日報》的惡毒言語顯示了評價低落的音樂為什麼通常只在全盛期過後多年才會平反。現在,異國沙發音樂聽起來不再像是阿諛奉承的保險業務員用來營造氛圍以引誘顧客上鉤的可悲工具,而是開始帶有陌生的魅力,遵循一套因為遺失而顯得迷人的音樂規範。當音樂仍屬於現在式時,由於潛藏的社會敵意以及擔心自己被視為「俗氣」的蠢蛋,我們也就不那麽樂於接納——把席琳.狄翁當成歷史來聽,也許才會真正聽到她。
***
本書是一項品味的實驗,刻意跳脫個人的美學。這項實驗涉及社會認同與敵意,也涉及藝術與藝術鑑賞如何能夠減緩或加重這些感受。在這個藝術的目的與意義已經變得一片模糊的時代,這麼一項實驗也許能夠打開幾扇窗。不過,主要的問題在於人的品味是否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而我首先要檢視的就是我自己的品味。
我想,有個條件是,我們厭惡的對象必定有某些特性和我們切身相關。任意的目標不可能引起那麼強烈的厭惡。我對史詩流行情歌雖然通常敬而遠之,但由於席琳.狄翁是加拿大人,因此比麥可.波頓更令我無法忍受──她受到的批評,都不免殃及我的國家,例如《南方四賤客》的電影主題曲〈都怪加拿大〉(Blame Canada)就是這麼唱的:「等到加拿大消失無蹤∕世界上就不再有席琳.狄翁。」我覺得自己也受到了牽累,想要提出抗議:「等等,我們比你們還早開始討厭她!」
我的測試案例將會是《談愛》,也就是收錄了〈愛無止盡〉的那張專輯。這張專輯不是她最暢銷的作品(她最暢銷的專輯是一九九六年發行的《真愛》[Falling Into You)),也不是她的歌迷最推崇的作品。不過,這張專輯的銷售量還是非常驚人,而且是在狄翁的名氣和我對她的憎恨都達到頂點之際推出。況且,對於一部研究文化熱情與反感的著作而言,這不正是最恰當的書名嗎?
我除了要讓自己埋首於這張專輯之外,也會像檢視我感興趣的任何藝人一樣,深入檢視席琳.狄翁,包括她的背景、事業生涯與影響、她所屬的音樂類型,以及她傳達了什麼樣的感性。不過,我也會檢視品味本身,包括品味所受到的談論、品味在美學理論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品味所受到的研究,包括科學研究與不那麼科學的研究。我會不會因此發現潛藏在我內心深處的席琳.狄翁歌迷?我的目標不是在歡樂圓滿的氣氛中結束本書。我如果因為這項實驗而喜歡上她的音樂,我們自可從中學到一課;但如果沒有,我們也可能學到其他的東西。
為了表達善意,且讓我直接稱呼她的名字,就像她的歌迷一樣:嗨,席琳,妳好。
這項實驗距離我平常的批評傾向,其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遠。我一向偏好比較不容易親近的音樂,例如藝術搖滾、迷幻民謠、後龐克、自由爵士,或者鐵克諾與嘻哈音樂當中較為抽象的作品。我撰文評介這類音樂,原因是我認為「艱澀」的音樂有助於撼動我們的觀點,把我們推出習慣的範圍之外。如同佛瑞茲在《表演儀式》(Performing Rites)這本書中所寫的,艱澀的聆聽體驗帶有些微的「烏托邦式衝動,以及對於日常生活的否定」,並且為我們開啟了一條通道,通往「另一個世界,一個[艱澀]會變得『容易』的世界」。對我而言,席琳.狄翁的音樂實際上不是比任何後現代聲響拼貼都來得「艱澀」嗎?至少聽起來一定比較不舒服。聆聽她的音樂,說不定會比我視為理所當然的那種「艱澀」更加令我迷惑。
畢竟,不論席琳有什麼優點,總之不會是聲響創新、語言創意、社會批評、暴烈的激昂、情慾的火花,或是我和許多樂評家在音樂中尋求的其他特質。她的歌迷一定聽到了某些東西。那些東西是什麼,又能夠以什麼樣的語言加以探討?儘管很不願意承認,但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可能埋在音樂的平庸性質當中。我多年來一再追逐的那些音樂,其「艱澀性」都帶有「另一個世界」的暗示,也以聲響預測未來的轉變。不過,我在這樣的追逐過程中也不免開始納悶,比較「容易」的音樂是不是帶有另一種暗示,有助於調解我們和自己早已置身其中的這個世界?這種音樂所處理的問題也許不需要發揮高度的想像力,卻需要付出其他心力,例如耐心或者妥協。其中可能也有否定,但不是我習慣的那一種。
另一方面,妥協正是我所擔心的事情:也許我跳入了一個相對論的兔子洞。如果連席琳都可以平反,那麼品味是不是根本沒有好壞之別,藝術也沒有優劣之分?如果我決定不再譴責席琳.狄翁那種花哨的音樂,那麼我對於玻璃雕刻家奇胡利(Dale Chihuly)那種欠缺深度的裝飾作品,或是「繪光大師」金凱德(Thomas Kinkade)的俗氣畫作,是不是也都應該重新評價?金凱德是我們這個時代在商業上最成功的畫家,筆下的純淨風景充滿懷舊氣氛,絲毫不見煩惱、幽默或挖苦。他在藝術圈外擁有許多支持者,一幅作品可以賣上幾十萬美元。此外,平庸的書籍或是保守派意見領袖那種含糊其詞的發言,又該怎麼說呢?你如果沒有自己的立場,也許就不免被人牽著鼻子走。
討厭席琳.狄翁如果是錯的,那麼說不定我根本不想站在對的一方。
且不論風險為何,我發現自己竟有個出乎意料的盟友。
***
在重溫一九九八年奧斯卡頒獎典禮的過程中,我無意間發現一則以前沒看過的報導:艾略特.史密斯對小型音樂雜誌《微笑相伴》(Comes with a Smile)坦承,他那天晚上抵達典禮會場,「原本打算離席琳.狄翁遠遠的。我以為她會在保鏢的簇擁下降臨,對所有人擺出怪異的超級巨星姿態,可是她完全不是那個模樣。」
他在另一場訪談裡指出:「她人非常好,以致我再也沒有辦法討厭她。我雖然忍受不了她的音樂——我無意冒犯,可是我實在一點都不喜歡,但她本人卻非常非常親切。她問我會不會緊張,我說:『會啊。』她接著說:『很好,這樣你會比較激動,唱起歌來會更好聽。你那首歌很美。』然後,她緊緊抱了我一下。我抵擋不了。我實在沒有辦法只因為覺得她的音樂很平庸,就推開那股溫暖。」
史密斯的朋友斯萬森(Marc Swanson)是視覺藝術家,他向史密斯的傳記作家紐根特描述了後來的發展:「在這[之後],我們常會遇到有人向他搭訕,不認識他的人。他們會說:『你好,我看到了你在奧斯卡的演出,感覺怎麼樣?』然後,[他們會]說些貶損席琳.狄翁的話。每次聽到他們這麼說,我就不禁倒抽一口氣,他的眼裡也會冒出怒火,向對方說:『你知道嗎,她其實是很好的人。』這時候他們總是會畏縮起來,說道:『哦,我不是那個意思,我相信她一定是很好的人。』……我覺得那就是他可愛的地方,他總是為席琳.狄翁辯護。」
而且史密斯只見過席琳一次。想想看,我們要是逗留久一點,說不定也能夠在她的音樂裡發現令人不忍推開的溫暖。
第二部 ▎我們值得這樣的藝術家——尼克.宏比
英國作家尼克.宏比大概是當代小說家當中最深入探討流行音樂與流行樂迷文化的一位。他偶爾撰寫音樂評論,也不時在《信徒》雜誌(The Believer)談書,近年更發表散文集《多洗澡,少說話》(More Baths, Less Talking),但他的作品中,最能提升我們對聆聽與品味的思考的,卻是小說。舉個例,在《失戀排行榜》這部小說及改編電影裡,擔當主要角色的幾個音樂宅男一開始只著重美學選擇的正確或錯誤,藉著列出十大優秀作品榜單來詮釋自己的人生,卻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連結。這個鮮活豐富的故事無法化約為單純的道德指令,但如果真的這麼做,那麼其中所教導的將會相當近似《好品味,壞品味?》所探討的內容。——卡爾.威爾森
我最近聽了電視合唱團(Television)的許多現場專輯,並想著我的媽媽。這種聯想並不常見,實際上,在我記憶中從未有過。但讀過卡爾.威爾森這本書的人,大概就能理解,我們免不了會遇上某些出乎意料甚至不討喜的並置。
我在二〇〇九年結識威爾森。他在多倫多一場活動的舞台上,針對小說《赤裸的茱麗葉》(Juliet, Naked)訪問我,事後提及他寫了一本討論席琳.狄翁的書。我立刻興奮不已,因為我明白他一定會談及我過去十年花了許多時間思索的一些議題:誰能夠決定一件藝術作品算是「好」作品?藝術作品的愛好者與評論家是以什麼基礎做出這些決定?他們可以信賴嗎?就某部分而言,我寫作《赤裸的茱麗葉》正是試圖探究這些問題,但我選擇創造一名作品顯然會受到老面孔(也就是搖滾樂評以及網路音樂宅)喜愛的音樂人。威爾森的書則更大膽。我們這些熱愛音樂的人,我指的是真正像樣的音樂,像是巴布.狄倫、尼爾.楊、邁爾士.戴維斯、非法利益合唱團(The Velvet Underground),當然還有電視合唱團,我們有多少人面對席琳時除了譏笑,還有其他反應?然而,就我所知,威爾森卻願意為了她剖析自我以及自己的品味。他打算#敞開心胸#思考她。哇!
藝術批評(還有我對於藝術批評的閱讀、體驗以及貢獻)有一點讓我覺得愈來愈不安,那就是開放的心胸極為罕見。相反的,評論家把完全未經檢驗的好品味當成武器,用來鞭笞無知的大眾。而假使你開始懷疑那些無知的大眾其實住在大城市之外,沒有機會接受一流大學的藝術教育,或是已經過了退休年齡,或是不看自由派的報紙,那麼,你會不安也是正常的。看到《獨立週日報》那位不知名的記者把狄翁的歌迷貶抑為「老奶奶、身穿禮服的人士、體重過重的兒童、手機銷售員以及購物中心愛好者之輩」,就知道威爾森的驚駭不是沒有理由的。較老舊、奢華的藝術形式在評論文章中往往遭受憤世嫉俗的惡毒批評,而遭到痛斥的不只是《達文西密碼》,也包括這部小說的讀者,評論家蘇瑟蘭(John Sutherland)就稱他們為「粗俗的大眾」。文學評論家布魯姆(Harold Bloom)曾經公然斥責全球上億個喜愛《哈利波特》的孩童(他們就是「錯」了)。《衛報》的藝評瓊斯(Jonathan Jones)宣稱英國最受喜愛的畫家維特里安諾(Jack Vettriano)「根本連藝術家都算不上」(維特里安諾要是知道了,肯定要納悶自己每天都在做些什麼)。「他只是恰好受到購買複製畫的『普通人』喜愛而已。」瓊斯還在文末沮喪地指出,維特里安諾是「符合我們水準的藝術家」,從而把一項無害的國民愛好轉變為號召全國集體自殺的理由。
就像丹.布朗、J.K.羅琳與傑克.維特里安諾的廣大吸引力一樣,席琳.狄翁的高人氣也令所有幸運到能擁有自認為的高雅品味的人驚恐不已又百思不得其解。不過,吐到狄翁臉上的口水似乎吐錯地方了,因為她演唱的是流行音樂。流行音樂的重點(此處所謂的「流行音樂」大概涵蓋了一切不屬於古典音樂的音樂)不就在於自由平等嗎?流行音樂最令人振奮的地方,不正是這種音樂可以由任何人創作(至少是任何髮型夠酷的人),也可以為任何人而創作,即便是體重過重以及沒有朋友的人,即便是喜歡逛購物中心的人,即便是音樂部落客也不例外?我之所以喜愛流行音樂,就是因為這種音樂的包容與親和。
關於文學作品的力量,有許多奇特的論述指稱傑出的文學作品能夠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而且極力強調這點,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順帶一提,實際上沒有這樣的效果。許多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與英文教授都在不經意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類觀點正當化了攻訐窮苦老百姓的惡毒言論:要是他們閱讀一些像樣的作品,這個崩壞的社會就有救了。畢竟,搶匪不會讀吳爾芙的著作,如果他們讀了,便會受她影響而奉獻自己的人生去做些有益的事情。不過,有沒有人曾經認真主張過,聆聽流行音樂,像是雷蒙斯合唱團的第一張專輯,能夠提升我們的道德?雷蒙斯合唱團帶來的音樂樂趣,與其說能夠遏止暴動,倒不如說可能引發暴動。既然如此,為什麼有那麼多搖滾樂評希望粗俗的大眾不再聆聽席琳,改聽雷蒙斯合唱團?他們為什麼這麼在意?席琳有什麼不好?她會對我們造成什麼傷害?
我這輩子都在聽流行音樂,現在也還聽。我聽新音樂,也聽舊音樂,包括熟悉與不熟悉的。當你的年齡走過三字頭、四字頭與五字頭,如果你仍然認真對待某種形式的流行文化,那麽你不免要承受別人故作包容的同情及輕蔑——至今仍是如此!接下來,我將花十秒鐘在網路上找個高雅文化評論家所寫的文字,證明我的論點。以下這段就行,出自古典樂評萊布列希(Norman Lebrecht):
更糟的是,跨界音樂消費者並不年輕,也不輕易受人影響。根據業界內部調查,大多數跨界音樂消費者都是中年人,他們逃離了搖頭甩腦、滿口髒話的搖滾樂,卻無法成熟地轉而聆聽西方文明的經典作品。至於他們為什麼做不到,只有天知道。也許他們聽硬式搖滾聽壞了耳朵,以致聽不出樂音的細膩精妙。
沒錯,他說的就是我。如同世界上大多數人,我也沒辦法達到成熟的轉型。
在《藝術有什麼用》(What Good Are The Arts?)這本出色的文集當中,英文評論家暨學者凱里(John Carey)以冷靜的邏輯思維探究偉大藝術的倡導者所提出的那些異想天開、盤根錯節,偶爾充滿笑果的主張。閱讀他的論述不但讓我鬆了一口氣,也使我感覺獲得平反與理解。畢竟,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的「成熟轉型」,而且所謂西方文明的經典作品,終究也只是情人眼裡出西施。
「這件作品算不算藝術?」的問題,如今只能得到這樣的回答:「你認為是就是,認為不是就不是。」如果這似乎將我們推入相對主義的深淵,那麼我只能說我們實際上一直都在這深淵裡,如果那真是一道深淵的話。
我非常喜歡凱里的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打臉了許多我想看到被打臉的人。不過,直到讀了威爾森的書,我才瞭解凱里其實也打了我的臉。我的品味、偏見、信念、喜愛與厭惡,其實也和高雅文化的愛好者一樣站不住腳。我是否曾批判品味難以理解的人?當然有。可是因為我基本上是平民主義者,反對裝模作樣,支持親和、簡單與趣味,所以我一直認定自己的立場穩固無虞。我才拿起《好品味,壞品味?》讀幾分鐘,就感受到這立場開始動搖,而在我讀完全書之前,就已土崩瓦解。我確實落入了深淵。過去我評判流行音樂所倚仗的機制,其實也毫無彈性、未經檢驗而且充滿階級心態,絲毫不遜於最目中無人的高雅文化評論家。
說到這裡,就必須回頭談我媽和電視合唱團。赫爾墨斯(Will Hermes)的《愛上著火的建築》(Love Goes To Buildings On Fire)是一本出色的著作,探討了七○年代中期的紐約市音樂,我因為這本書而回頭聽了電視合唱團的現場專輯《爆炸》(The Blow-Up)。聽著〈小強尼珠寶〉(Little Johnny Jewel)這首歌裡又長又刺耳的吉他獨奏,心裡想著《好品味,壞品味?》的內容,我於是開始思考這首歌的自傳元素,這首歌之所以令人興奮、感同身受,正是因為這些元素。畢竟,湯姆.魏爾倫(Tom Verlaine)用吉他彈奏的反覆樂句及猛然迸出的一大串音符,在別人(例如我母親)耳中聽來恐怕會是一片噪音,而約翰.柯川的薩克斯風獨奏有時候在我耳中聽來也是如此。但我之所以聽得懂魏爾倫,覺得他的音樂就像在對我講故事,是有原因的。
舉個例,在電視合唱團推出第一張專輯的一九七六年,我十九歲,正在大學修讀英文學位。也就是說,我當時的年紀正適合接受那個時期冒出頭的種種新音樂,而另一項同等重要的因素,則是我當時有用不完的時間可以聽那些音樂,不論是在我的房間裡,還是去表演現場。我本來已經知道有個法國象徵派詩人保爾.魏爾倫(Paul Verlaine),因此得知有人借用他的姓氏,就不禁大感興趣。我出生於一九五○年代末期,所以成長過程完全沈浸在搖滾的歷史中。我已花了多年時間細細聆聽罕醉克斯、杜恩.歐曼(Duane Allman)與吉米.佩奇(Jimmy Page)的吉他獨奏。(只不過魏爾倫的吉他和他的樂團專屬於我,就像歐曼兄弟合唱團和罕醉克斯屬於我朋友的哥哥。)在一九七六年,我對《新音樂快遞》雜誌(New Musical Express)中的一字一句都深信不疑,而《新音樂快遞》的肯特(Nick Kent)針對電視合唱團首張專輯《華蓋之月》(Marquee Moon)寫了一篇洋溢迷戀之情的長篇樂評,當時我的朋友和我都飢渴地拜讀了。那時的我認為紐約市是全世界最令人興奮的地方。我可以找到無盡的理由說明自己為什麼永遠都會深愛電視合唱團,以及為什麼現在還是深愛他們。
凱里提及克萊特勒夫婦(Hans and Shulamith Kreitler)內容詳盡的《藝術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Arts),其中指稱不同人對同一件藝術作品產生不同反應的原因「涉及多不勝數的變數,不僅包括感官、認知、情緒及其他人格特質,還有生平閱歷、獨特的個人經驗、過去接觸藝術的經驗,以及個人的聯想」。換句話說:不必浪費時間解析原因。
肯特在《新音樂快遞》的樂評裡寫道:「《華蓋之月》是一張適合所有人的專輯,不論他們的音樂信仰以及(或者)癖好為何。」可是當然實際上並非如此。這張專輯不適合我母親,也可能不適合你。我不禁納悶肯特當初撰寫這篇樂評的時候,究竟認為「所有人」涵蓋了哪些對象?
在我的理想世界裡,世人隨時都在閱讀、聆聽音樂及觀賞電影,並且深深喜愛他們所接觸的那些藝術。評斷這些人或者他們喜愛的作品,不論是席琳.狄翁還是舒伯特的交響曲,即是以徹底無益的方式破壞他們與文化的關係。卡爾.威爾森這本充滿洞見、挑戰性以及人性的小書相當重要,因為只要我們願意聆聽這本書提出的意見,那麼我理想中的那個世界就會多那麼一點點實現的可能。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