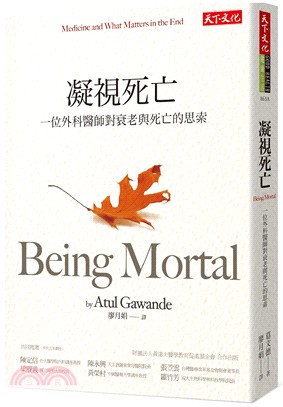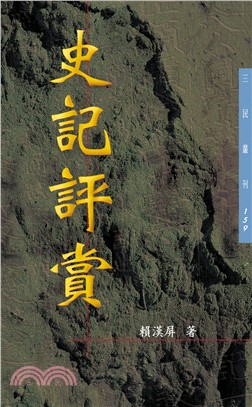凝視死亡: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
商品資訊
系列名:健康生活系列
ISBN13:4713510945575
替代書名: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出版社:天下文化
作者:葛文德
譯者:廖月娟
出版日:2018/08/15
裝訂/頁數:平裝/368頁
規格:21cm*14.8cm (高/寬)
重量:498克
商品簡介
你願意人生最後一里路,是眼神空洞的坐在輪椅上滑行嗎?
你希望至愛親人的餘生,是靈魂被禁錮在病床上的軀體裡?
現代醫學已經扭轉了嬰兒死亡率和傷病致死率,
但是面對衰老和死亡,醫學能做的還是很有限。
葛文德透過自己家庭和病人的故事,
描述了衰老、死亡過程中的困擾、痛苦與無奈。
醫師該如何與病人討論死亡?如何提供適度而不浪費資源的療法?
如何協助病人在虛幻的期望與有品質的臨終生活之間,做出抉擇?
這些不僅是醫學院很少會教的課,也是許多人避諱不敢面對的生命課題。
葛文德毫無畏懼的迎向這個禁忌話題,
以誠懇的態度、溫暖的筆觸,敘述老人安養、臨終照護的種種面向,
揭示人生的終極目標可不是「好好的死」,
而是「好好的活、有尊嚴的活過每一分鐘」。
作者簡介
著名外科醫師、哈佛醫學院外科教授、暢銷書作家、非營利組織領導人。
美國波士頓布里根婦女醫院一般外科和內分泌外科醫師、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管理學系教授、哈佛大學醫學院外科「提爾(Samuel O. Thier)講座」教授、阿里亞尼醫藥創新中心(Ariadne Labs)執行長、非營利組織Lifebox的會長(Lifebox致力於提升全球各地的外科手術安全)。
自1988年起擔任《紐約客》主筆,著有《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開刀房裡的沉思》、《檢查表:不犯錯的祕密武器》、《凝視死亡》四本書,皆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兩度獲頒美國國家雜誌獎,亦獲得美國醫療服務研究協會(AcademyHealth)最具影響力獎、麥克阿瑟研究獎、以及路易士.湯瑪斯科學寫作獎。
譯者:廖月娟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屢獲翻譯獎,譯作等身。
1966年生,。曾獲誠品好讀報告2006年度最佳翻譯人、2007年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2008年吳大猷科普翻譯銀籤獎。譯作包括《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醫療抉擇》、《賈伯斯傳》、《成為賈伯斯》、《文明的代價》、《告別之前》、《狼廳》、《雅各的千秋之年》、《我的焦慮歲月》等數十冊。
名人/編輯推薦
各界推薦
這是一本應該強制每個人都要閱讀的書……
如何讓晚年生活有意義,《凝視死亡》提供了有用的指引。
——《時代》雜誌
葛文德探索了醫學的斷層帶,
《凝視死亡》關注的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
——《芝加哥論壇報》
葛文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醫師作家之一,
《凝視死亡》不只深深打動人心,更是充滿洞見。
—— 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名作家紐約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教授
這是葛文德最新、最棒的一本書……
他以感人的故事、清晰的見解,帶我們凝視衰老和死亡的課題。
——《紐約時報書評》
葛文德以睿智和勇氣,提出了我們不太願意思考、面對的問題。
—— 英國《週日泰晤士報》
讀罷《凝視死亡》,令人潸然淚下,
一整個星期都無法停止談論書裡提到的故事和觀點……
這是很罕見的一本書,竟能夠激盪出這麼多思緒的火花。
——《自然》期刊
葛文德的書如此令人印象深刻,這應當能改變醫學界的走向……
期待更多人閱讀和消化這本《凝視死亡》。
—— 英國《金融時報》
當社會怯於碰觸衰老和死亡的議題,
這本書有如暮鼓晨鐘,警示我們哪裡走岔了,如何改弦易轍。
——《舊金山紀事報》
序
前 言
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
葛文德
雖然我在醫學院學到了很多東西,可從來沒有人教我如何面對死亡。儘管在第一個學期,為了學習人體解剖學,我分到了一具乾癟、皮膚像皮革般的屍體,但教科書幾乎沒提到衰老或瀕臨死亡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不了解死亡過程,對臨終經驗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死亡又會如何影響到周遭的人。就我們所見,醫學訓練的目的就是教我們如何救治病人,而非照顧臨終病人,讓他們安然離去。
記得醫學院曾舉行為期一週的病醫關係研討會,以讓我們成為更圓融、更有愛心的醫師。在那個星期,我們花了一個小時討論托爾斯泰的經典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另外也有幾個星期我們曾練習身體檢查的禮節,學習避免不當的肢體接觸;還有幾週則探討社會經濟學與種族對健康的影響。一天下午,我們一起思索伊凡.伊里奇的境況——他得了某種無以名之的不治之症,一天比一天嚴重,最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伊凡.伊里奇年四十五歲,是聖彼得堡中級法官,畢生為了社會地位汲汲營營。一天,他從梯子上摔了下來,腰部撞到窗框,感覺有點疼痛。幾天後,非但沒好,還更加疼痛,甚至不能上班。他本來「聰明過人、風度翩翩、充滿活力,而且討人喜歡」,然而因病痛而陷入沮喪,身體也愈來愈虛弱。朋友和同事都當他是瘟神,避之唯恐不及。他太太請了多位名醫來幫他診治,花了不少錢,但還是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麼病。那些醫師的診斷各有不同,給他的治療也都沒有效果。伊里奇就這麼活在痛苦當中,心中充滿怒氣,怨恨老天為什麼要這麼折磨他。
托爾斯泰寫道:「其實,折磨伊里奇最甚的是欺騙、謊言。他周遭的人都說,他只是病了,只要好好靜養,接受治療,就能康復,不願面對他即將死亡的事實。」伊凡.伊里奇曾抱著一絲希望,心想,也許不久他就會好轉,但他日漸虛弱、消瘦,自知來日不多。他活在極度的痛苦之中,深深恐懼死亡。但他最難過的,則是他的醫師、朋友和家人都不承認他快死了。
托爾斯泰寫道:「他非常希望有人能同情他這個垂死之人,然而就是沒有人可憐他。在漫長的折磨之後,他真的希望大家能同情他,就像同情一個生病的孩子(可他怎麼好意思這麼說?)。他渴望別人的憐愛與安慰。他知道自己是政府要員,德高望重,鬍子都花白了,因此不可能有人會來憐憫他,但他還是如此渴望。」
在我們這些醫學生看來,伊凡.伊里奇得不到任何安慰,也沒有人承認他快死亡,這是主人翁個性與俄國文化的問題。托爾斯泰筆下那個十九世紀末的俄國似乎殘酷而原始。那個社會相信伊凡.伊里奇只要接受治療,必然能夠好起來。但我們又何嘗不是?不管伊里奇得的是什麼病,我們認為現代醫學必然能夠治好他的病,只不過我們也相信誠實和親切是現代醫師的基本責任。要是我們碰到像伊里奇這樣的病人,必然會懷著同情心醫治他。
我們擔心的是知識不足。雖然我們知道如何同情病人,但沒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能正確診斷出來,並給病人妥善的治療。我們付了高昂的學費進了醫學院,為的是了解身體內部的運作、疾病的機轉,以及利用長期累積下來的發現和技術來遏止疾病。至於其他的,就沒想那麼多了。所以我們把伊凡.伊里奇所受的折磨拋在腦後。
幾年後,我開始接受外科訓練、展開行醫生涯,我接觸到的一些病人使我不得不直視身體衰敗與人終將死亡的現實。不久,我就發現自己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麼幫助這樣的病人。
接近生命終點之時,什麼是最重要的?
我在擔任外科住院醫師之初開始寫作,最早寫下的文章中有一篇是約瑟夫.拉札洛夫的故事。拉札洛夫是在市政府服務的老公務員,他太太在幾年前罹患肺癌先他而去。此時,六十出頭的拉札洛夫因前列腺癌廣泛轉移,腹水嚴重,鼠蹊部和雙腿也都出現水腫,那陣子已瘦了二十幾公斤。一天,他在家醒來,右腿動彈不得,加上大小便失禁,於是住院治療。當時,我是實習醫師,正在神經外科部門學習。我在拉札洛夫開刀的前一天去病房看他。我們發現,癌細胞已擴散到他的胸脊,壓迫到他的脊髓。癌症進展至此,已無治癒的可能,但我們還是盡力為他治療。由於緊急放射線治療沒能使腫瘤縮小,神經外科醫師給他兩個選擇:緩和醫療或是切除壓迫到脊髓的腫瘤。拉札洛夫決定接受手術。我的任務就是拿同意書讓他簽字,代表他明白手術的風險,願意接受手術。
我站在病房外,拿著病歷,手心冒汗,一直在想,到底怎麼談到這個話題才好。我們希望藉由手術使他的脊椎不再遭到進一步的損傷。然而,手術無法使他痊癒,不能使他擺脫癱瘓重新站起,也不能讓他回復原來的生活。不管我們怎麼努力,頂多只能讓他多活幾個月,而且手術本身風險很高。我們必須切開他的胸腔,取出一根肋骨,塌陷他的肺葉,才能看到脊椎。失血量一定不少,復原更是艱辛。由於他已經很虛弱,術後必然面臨併發症的嚴重考驗。手術可說是兩面刃,雖然可能改善他的病情,但也可能帶來更大的威脅,使他喪命。神經外科醫師已經跟拉札洛夫提過這些風險,但他堅定表達想要開刀的意願。現在,我必須進去,完成文件的簽署。
躺在床上的拉札洛夫面如死灰,形銷骨立。我自我介紹說,我是實習醫師,要請他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確保他知道手術的風險。我說,手術可去除他脊椎上的腫瘤,但可能會有嚴重的併發症如全身癱瘓或中風,甚至可能致命。那時,他兒子也在病房內,問道,這麼做會不會太逞強了?拉札洛夫不高興兒子扯他的後腿。
他說:「別放棄我,給我活下去的機會吧。」他簽好同意書,我走出病房,他兒子也跟著出來,把我拉到一邊,說他母親之前在加護病房躺了很久,靠呼吸器苟延殘喘,直到過世。當時,他父親曾說,他絕不要這樣,現在卻一意孤行,再危險都不顧。
當時我認為拉札洛夫先生堅持開刀實在是不智之舉,現在依然這麼想。他真是失算,但不是因為手術風險太高,而是因為手術並不能讓他得到他真正想要的,也就是重拾健康人生。手術再怎麼成功,他依然羸弱,一樣需要有人替他把屎把尿。他追求的只是一個幻想,卻可能因此踏上一條漫長而痛苦的死亡之路——事實正是如此。
從技術層面來看,這次的手術可說無懈可擊。開刀房團隊總計花了八個半小時切除侵犯到脊椎的腫瘤,然後以樹脂骨泥填塞脊椎被侵蝕的缺口。手術終於解除了脊髓的壓迫。但拉札洛夫一直沒能恢復,在加護病房出現呼吸衰竭、全身性感染、血栓等問題。我們給他抗凝血劑以對付血栓,他卻因此出血。每天我們都有節節敗退之感,最後不得不承認,他已經回天乏術。術後第十四天,他兒子請我們住手。
主治醫師要我為他拔除呼吸管——他賴以為生的管線。我查看含有嗎啡的點滴,看流速是否已調到最大,他才不會有吸不到氣的痛苦。我想,他說不定還有聽覺,於是彎下腰,在他耳邊輕輕說,我就要幫他拔除呼吸管。管子拔出之際,他咳了兩、三下,一度張開眼睛,很快再閉上。他的呼吸愈來愈費力,不久就停了。我把聽診器放在他胸口上。他的心跳聲愈來愈弱,終於停止。
自從我寫下拉札洛夫先生的故事,至今已過了十多個年頭。我最深的感觸並非他的決定有多糟,而是我們沒能誠懇的把所有選項都攤在他面對,跟他討論。我們很會跟病人解釋每一種療法所具有的危險,但我們不曾真正碰觸疾病的現實。幾個月治療下來,拉札洛夫的腫瘤科醫師、放射科醫師、外科醫師等,無一不知他不可能痊癒,但還是眼睜睜看他受盡折磨。我們不曾使他看清事實的全貌,沒坦承自己的能力終究有限,更別提跟他討論在接近生命的終點之時,什麼對他而言是最重要的。如果說他在追逐幻想,我們又何嘗不是?他躺在醫院裡,癌細胞已擴散到全身,致使身體部分癱瘓,要使他回復到幾星期以前的狀況,機率可說是零。而我們似乎無法承認這樣的事實,幫他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沒能面對現實,沒能給他安慰,也沒能引導他,告訴他要怎麼做。我們只是給他一種又一種的治療,騙自己相信,說不定會有奇蹟出現。
我們並不比十九世紀那些為伊凡.伊里奇診治的醫師來得高明。有鑑於病人受到種種有如酷刑的肉體折磨,說實在的,我們恐怕比那些古早時代的醫師更糟。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你不得不懷疑:莫非我們才比較原始?
面對死亡,你必須謙遜
現代科學使人類的生命歷程有了很大的轉變。現代人可以活得更久,也過得更好,這是以前的人無法享有的。然而,科學進展也使我們在衰老和瀕臨死亡的過程中,大抵仰賴醫療專業人士的照顧,只是身在醫學界的我們還沒準備好承擔這樣的責任。
這個事實被隱藏得很好,因為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生命末期的真實境況。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一般人大抵在自己家中去世,但到了一九八○年代,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如此——那些在家中過世的人通常是因為猝死,來不及送醫,例如心肌梗塞、中風、受到嚴重創傷,或者住的地方過於偏遠,人煙稀少,附近無醫療院所。不只美國這樣,整個工業世界都是如此。衰老與死亡總離不開醫院和養老院。
雖然我父母都是醫師,從小耳濡目染,但等我自己當上醫師,才發覺自己對醫學世界還很陌生。以前,我不曾看過任何人死亡,因此在我親眼目睹死亡那一刻,著實震撼。我並不是聯想到自己也會有這麼一天,即使死者跟我年紀相仿,我也沒有那念頭。我身穿白袍,病人穿著住院袍。我還無法想像自己會從醫師變成病人。然而,我可以想像我家人被死亡的陰影籠罩,畢竟我曾經看過我太太、父母和我的孩子歷經重病威脅,命在旦夕。儘管情況不樂觀,醫學還是把他們從鬼門關口拉了回來。因此,對我而言,最大的震撼就是,醫學竟然沒能把人都搶救回來。當然,我知道理論上來說,病人有可能會死亡。然而,我們還是屢屢衝破難關,似乎規則總能被打破。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競技,但我們每次都能贏得勝利。
每一位剛站上崗位的醫師和護理師,都曾面對死亡或是眼睜睜看著病人走向死神懷抱。最初面對這樣的生死衝擊,有人哭了,有人則像強迫關機一樣,把自己的感覺切斷,還有些人似乎不以為意。我最初目睹死亡的時候,內心的防衛機制使我得以忍住淚水。但我常夢見死者。我經常做惡夢,夢見病人的屍體出現在我家裡,甚至在我床上。
我萬分恐慌,不解的問:「這個人怎麼會在這裡?」
我知道我麻煩大了,說不定已捲入命案。我得趕快悄悄把屍體送回醫院,別讓任何人發現。我想把屍體抬進後車廂,但是太重了,根本抬不起來。或者,我已設法把屍體放進後車廂,但血像黑黑的汽油不斷滲出,淹沒了整個後車廂。又或者,我把屍體送到醫院,搬上推床,推過一條又一條的走廊,就是找不到死者原來住的那間病房。「嘿!」有人對我大叫。我拔腿就跑,那人緊追不捨。我嚇醒了。四周漆黑,我太太在我身邊酣睡,我直冒冷汗,心臟狂跳。我以為那些人就是死在我手裡。我失敗了。
當然,死亡不代表誰失敗了。死亡是正常的。死亡也許是敵人,但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我知道這些抽象的真理,但不曾面對死亡的真面目。是的,人終將一死,每一個人都不例外,包括我眼前這個人,我負責照顧的這個病人。
已故外科前輩努蘭(Sherwin Nuland)在經典之作《死亡的臉》(How We Die)感嘆:「大自然終將獲得勝利,在我們之前的世世代代都接受這樣的命運。在大自然之前,醫師願意認輸、謙遜。」然而,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接受扎實的訓練,擁有最先進的科技,說實在的,並不怎麼了解謙遜的意義。
你選擇走上行醫這條路,想像自己從中獲得莫大的成就感,於是你對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這種成就感就像木匠修復破損的古董木櫃,或科學教師用精闢的解說讓五年級的學童恍然大悟,了解什麼是原子。有一部分的成就感來自能夠助人,另一部分則來自利用精熟的技術解決難纏、複雜的問題。你的能力讓你獲得自我肯定。因此,對臨床醫師而言,最大的威脅莫過於覺得自己無能為力,無法解決病人的問題。
打從出生那一刻開始,我們每天都在變老——這是人生無可避免的悲劇。這是我們可以了解、也能接受的事實。瀕死與死去的病人以後再也沒出現在我的夢裡,但這並不代表我已知道如何面對無法修補的一切。醫學這個行業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修補人體的缺損。如果你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我們自然知道怎麼做。如果無法解決呢?於是,我們變得茫然、冷漠,而病人只能受苦,覺得活得沒尊嚴。
試著把死亡的處置納入醫療過程,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我們的經驗還很粗淺。而證據顯示,現今的做法大有問題。
坦然面對衰老與垂死的歷程
這本書要談的是死亡的現代經驗,包括衰老、死亡的感覺是如何;醫學如何改變這樣的經驗,以及有哪些是改變不了的;還有,我們想要面對生命的有限,卻因不了解現實而出錯。在外科行醫十年來,我自己也步入中年。我發現我自己和我的病人都認為現況已到了教人忍無可忍的地步。應該怎麼做呢?我們不只不知道確切的答案,甚至不知道是否可能找到詳盡的答案。然而,基於作家與科學研究者的信念,我相信藉由揭開面紗、貼近觀察,我們可以從困惑、怪異和混亂之中理出些頭緒。
你不必待在老人或疾病末期的人身邊,就可了解醫學常常只是讓人承受無謂的痛苦。在即將走到人生的盡頭之時,我們常為了一丁點的機會,不惜用藥物讓自己大腦昏沉,耗盡所有體力。我們住在養老院或加護病房,接受制式的常規治療,不再能擁有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如果我們不願坦然面對衰老與垂死的經驗,必然會活在痛苦中,無法得到基本的慰藉。要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善終,那就只能讓醫學、科技和陌生人來操控自己的命運。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要了解這一切。我們對死亡仍有太多的誤解。有些人一看到醫師論到每一個人難逃衰老和死亡,就不由得驚懼起來。即使醫師仔細分析、用心推敲,這個社會似乎仍有很多人仗著自己年輕體壯,冷眼旁觀,無視老人、病人遭到犧牲。有生就有死,生命週期就是這麼殘酷。如果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就只能在痛苦裡輪迴,無法解脫。
如何面對死亡?眼下說不定就有更好的做法,只是我們視而不見。
目次
推薦序 可憐身是眼中人 侯文詠
前 言 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
第一章 獨立的自我
第二章 肉身解體
第三章 依賴
第四章 一個老人的生活願景
第五章 值得活的人生
第六章 放手
第七章 生死問答
第八章 勇氣
結 語 幫助病人完成更大的人生目標
資料來源
誌謝
讀後感 韓良誠
書摘/試閱
第三章 依賴
不知當我們衰老、病痛纏身、凡事都得依賴他人之時,
要如何才會覺得人生是值得活的。
老人說,他們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死前的種種——失聰、喪失記憶、失去摯友,以及不再能夠像以前一樣獨立過活。正如席佛史東告訴我的:「年老是一連串的失落。」菲立普.羅斯(Philip Roth)在描述男性肉體衰老的小說《凡人》中,論道:「年老不是一場戰役,而是屠殺。」
如果運氣好加上講究健康(注意營養、運動、控制血壓,必要時去看醫生),通常還是能活得長久,而且過得不錯。然而,我們身體的損壞日積月累,終有一天不管身體或心智都難以應付每日生活所需。儘管很少人突然遭逢意外死亡或猝死,大多數的人到了老年,總會衰退到無法獨立生活。
我們不喜歡去想這件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沒有預作準備。若非身體已經衰退到非要別人照顧不可了,幾乎都不願正視問題,然而這時再來盤算,為時已晚。席佛史東來到這個十字路口的時候,出問題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妻子貝拉。貝拉的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席佛史東儘管已經九十幾歲了,健康狀況還好得出奇。他沒生什麼重病,依然每週上健身房運動,繼續為宗教研究的學生上課,教授老年醫學課程,也在果園灣的健康委員會服務,甚至還在開車。但貝拉的情況很糟,她已完全失明,耳朵也不好,記憶也退化得厲害。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席佛史東必須一再跟她說,我就坐在她對面。
雖然貝拉和席佛史東為他們失去的青春和健康感傷,但也為自己還擁有的欣喜。貝拉或許不記得我和許多她不太熟的人,但很喜歡跟我們一起聊天。此外,她和席佛史東結縭數十年,總有說不完的悄悄話。席佛史東從照顧貝拉,找到人生的目的,而貝拉也發現自己對席佛史東意義重大,因為他們倆是相依為命的生命伴侶,只要能看到對方,就覺得安心。席佛史東幫她穿衣,幫她洗澡,餵她吃飯。兩人出門散步,總是手牽著手。夜晚,他們在床上相擁,然後慢慢進入夢鄉。席佛史東說,這些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是他們生命中最寶貴的。儘管他們已共同生活將近七十年,但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知、相愛。
然而有一天,他們才了解:這樣的生活如何不堪一擊。貝拉感冒了,中耳積水,鼓膜破裂,導致失聰。她本已完全失明,記憶退化,和席佛史東的溝通完全倚賴話語,現在聽不到了,她只能活在一個人的黑暗世界。席佛史東在她掌中寫字母,但她無法辨識他在寫什麼。就算簡單如穿衣服這樣的事,她也完全搞不清楚。她失去了感覺定位,也不知時間。她陷入精神錯亂,有時還會出現幻覺,焦躁不安。席佛史東因壓力和睡眠不足,心力交瘁,無法繼續照顧貝拉。
席佛史東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養老社區的人建議:把貝拉送到社區照護中心,接受專業照護。他無法接受這樣的安排。他說,絕對不行,她得跟他一起住在家裡。
幸好,不到二十天,貝拉的右耳鼓膜復原了,雖然左耳聽力已完全喪失,至少右耳能聽。
席佛史東說:「我們溝通比以前困難,但至少還能溝通。」
我問,如果貝拉的右耳又聽不到了,或者再碰到類似打擊,他會怎麼做?他說,他不知道。「我很害怕自己有一天會無法照顧她,我只能盡量不去想未來。甚至明年會如何,我也不敢想。太令人沮喪了!我只能想下星期的事。」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每個人處在這樣的景況,也只能如此。但世事無常,他們深深恐懼的打擊還是來了。一天,兩人一起散步時,貝拉突然跌倒。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路很平,他攙扶著她慢慢走,但貝拉還是摔了一跤,兩條腿的腓骨(小腿骨外側,從膝蓋到足踝的細長骨)都斷了。急診醫師為貝拉雙腿打上石膏,直到膝蓋上方。席佛史東最害怕的事發生了。他已經九十幾歲,像貝拉這樣的情況,他哪照顧得了?貝拉不得不住進社區照護中心,由看護和護理師二十四小時輪班照顧。
你或許會以為,如此一來,貝拉和席佛史東都可鬆一口氣,不必再承擔照護的重擔。其實,情況要比我們想的來得複雜。從一方面來看,照護人員能提供的真的只有「專業照護」,其他的都沒有。他們承接席佛史東長久以來背負的重擔——幫貝拉洗澡、如廁、穿衣等,因應她的日常生活所需;席佛史東因此可以喘息。但席佛史東和貝拉發現,照護員常讓他們生氣。有些照護員只把貝拉當成病人,而不是一個人。例如,她有自己喜歡的梳頭方式,但是沒有人問她頭髮希望怎麼整理,也沒興趣了解。席佛史東總是幫貝拉把食物切得剛好,讓她比較好吞下,知道要怎麼扶她,她才會比較舒服,也知道她喜歡的穿衣方式。但他怎麼跟照護員解釋,他們就是抓不到要領。有時,在氣急敗壞之下,他索性放棄,不管他們已經做了什麼,乾脆自己再做一次,因此造成衝突和怨懟。
「他們覺得我礙手礙腳,我則認為他們愈幫愈忙,」席佛史東說。
他也擔心這陌生的環境會讓貝拉精神更加錯亂。幾天後,他想出新的辦法,決定帶貝拉回家,自己照顧。
他們的公寓離照護中心只有一個樓層。儘管只是一層之隔,感覺卻天差地遠。然而席佛史東畢竟無力自行擔起照顧之責,還是請了幾位護理師,二十四小時輪班幫忙照顧貝拉。雖然一個半月後貝拉才能拆石膏,還有一段辛苦的日子要過,但席佛史東總算能放心了。他和貝拉都覺得這樣比較自在。她可以住在自己家、睡在自己的床,而且與親愛的丈夫同枕共眠。幸好他們及早搬回家住。因為就在貝拉拆下石膏、能再度走路的四天後,她就過世了。
那時,他們正在吃午餐。貝拉轉頭,對席佛史東說「我不舒服」,便頹然倒下。救護車很快把她送到當地醫院。席佛史東不想拖慢救護人員,就讓他們先走,開車尾隨於後。貝拉被送到醫院後,沒等到席佛史東趕到,就斷氣了。
三個月後,我見到席佛史東。他還沉浸在喪妻之痛。他告訴我:「我覺得自己的身體少了一部分,好像被肢解似的。」他聲音沙啞,眼眶泛紅。幸好,他還有一大安慰:貝拉在過世前沒有受苦,而且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仍待在自己的家,跟摯愛的先生在一起,而不是在冷冰冰的照護中心死去,惶惶不安,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愛麗絲搬進長木屋之後
我太太的祖母愛麗絲一樣非常害怕離家。家讓她有歸屬感,並覺得自己還有能力掌控生活。但是在她被壞人恐嚇取財之後,顯然不能再一個人住了。我岳父吉姆物色了幾家養老院想帶她去看,儘管她一點興趣都沒有,最後還是妥協。岳父下定決心要找到一個她會喜歡的地方,讓她在那裡安享晚年。然而事與願違。看著這一連串事件的發展,我慢慢了解癥結何在,也才發現,我們這個社會給老人和殘障者的照護制度仍然有許多問題。
吉姆希望能在離他們家不遠的地方找到合適的地方,方便日後開車去探望,並希望費用是愛麗絲賣掉房子後可以負擔的。他也想找一個可提供永續照護的養老社區,就像席佛史東和貝拉住的果園灣,有自己的公寓,獨立生活,將來失去自理能力後,也有醫護人員能就近提供二十四小時的照顧。他列出好幾個可以去參觀的地方,有的近、有的遠;有的是營利機構、也有非營利組織。
愛麗絲最後選擇了一棟專供老人住的複合住宅大樓,姑且稱之為長木屋。這是隸屬聖公會的非營利機構。她有些教會朋友已經住在那裡。吉姆從家裡開車過去,幾乎不用十分鐘。這個社區很熱鬧,有不少活動。對愛麗絲和她的家人來說,簡直太理想了。
「其他地方都太商業化了,」吉姆說。
愛麗絲在一九九二年秋天搬進去。她住的是一房一廳的獨立公寓,比我想的要來得寬敞。這公寓還有完備的廚房,有足夠的收納空間放她的餐具,光線也很不錯。我岳母南恩要求管理人員將這公寓重新粉刷,也找了以前曾為愛麗絲裝潢房子的設計師,來幫她擺放家具、掛畫。
南恩說:「愛麗絲一搬進來的時候,發現老家的家具都在這裡,已經擺好了,原本使用的餐具也都在這裡的廚房抽屜,就會有家的感覺。」
愛麗絲搬進長木屋幾個星期後,我去看她,發現她似乎悶悶不樂。她不是喜歡抱怨的人,也沒說任何生氣、哀傷的話,更沒表示什麼不滿。她變得退縮了——我以前從來沒看過她這樣子。雖然她外表和過去差不多,但眼神已失去往日的神采。
起初,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她再也不能開車的緣故。沒有車子,行動自由就受到限制。她剛搬進長木屋,也把她的車開來了,希望能繼續開。但是就在搬進去的第一天,她開車出去買東西,她的車就不見了。她報警說車被偷。警察來了,做了筆錄,答應說他們會好好調查。不久,吉姆也趕到,他根據自己的預感,朝向隔壁的巨碩食品商場停車場看了一下。愛麗絲的車就在那裡。她糊塗了,把車停在另一家店的停車場,才會找不到車。她在羞愧之下,決定以後再也不開車。就在這一天,愛麗絲不但失去了她的老家,也失去了她的車子。
但她的失落與憂傷不止於此。她的新公寓有廚房,但她完全不煮,和大夥兒一起在長木屋的食堂吃飯,但她吃得很少,變瘦了,而且不喜歡與人交往。她也不參加團體活動。她以前喜歡去教會參加裁縫班、讀書會,也上健身房或是跟大家一起去林肯中心,現在都不去了。如果你不想參加已有的活動,也可以籌組自己喜歡的活動。然而,她不管做什麼都興趣缺缺,老是一個人。我們猜想,她或許有憂鬱症。於是吉姆和南恩帶她去看醫生,醫師也開了藥給她吃。但依然沒有幫助。儘管她原來住的綠堡街和長木屋相距只有十一公里,但從老家搬到長木屋之後,她的人生必然起了很大的變化。她不喜歡現況,但也莫可奈何。
這裡不是我真正的家
長木屋似乎是養老最理想的所在。那裡設備新穎,不但安全,照護品質也是一流的。愛麗絲住的公寓就像她的老家一樣舒適,而且更安全,生活也更便利。她能住進長木屋,子女和家人都鬆了一口氣。只是這不是愛麗絲喜歡的地方。她一直覺得不習慣或是難以接受。儘管家人和長木屋的照護員已盡全力,她還是鬱鬱寡歡。
我問她,為什麼她會這麼不開心。她無法指出到底是哪裡有問題。我從社區其他住戶口中得知,愛麗絲最常抱怨的就是:「這裡不是我的家。」對愛麗絲而言,長木屋只是家的複製品,不是真正的家。只有住在真正的家,才會讓人有如魚得水之感。
幾年前,我讀到一篇文章,講述杜魯曼(Harry Truman)的故事。杜魯曼住在華盛頓州奧林匹亞附近聖海倫火山的山腳下。一九八○年三月,火山開始噴煙,蠢蠢欲動,附近居民都撤離了,但高齡八十三歲的杜魯曼拒絕離開。他年輕時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擔任飛行員,退役後曾在禁酒時代釀造私酒。他已擁有這棟座落於靈湖畔的屋子,長達五十年以上。五年前,他太太死了,留下他一個人、十六隻貓和火山腳下一塊面積廣達十八甲的土地。三年前,因屋頂積雪,他爬上去鏟雪,摔斷了一條腿。醫師說,他一大把年紀還爬這麼高,真是個無可救藥的大傻瓜。
「媽的!」杜魯曼反駁道:「老子已經八十歲了,八十歲的人有權自己作主,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由於火山即將噴發,當局下令火山腳一帶的居民都得撤離。但是杜魯曼決定死守家園。火山口的煙冒了兩個多月。當局再次警告火山周圍十幾公里範圍內的居民,要他們趕快離開,杜魯曼依然不肯走。他說,那些科學家既無法提出斬釘截鐵的報告,而且多有矛盾。他擔心有人闖入他家,洗劫財物,住在靈湖畔的另一個居民就遭到這樣的慘事。對杜魯曼來說,他的家就跟他的命一樣。
他說:「如果我的家保不住,我就同歸於盡。反正,萬一這個家沒了,我也活不到一個星期。」他直言無諱,頭戴一頂強鹿農業機具公司的綠色鴨舌帽,手上拿了個高腳杯,裡面是波本酒加可樂——在記者眼中,這人實在很有意思。為了他的人身安全,當地警察考慮過乾脆把他逮捕。繼而想到他年事已高,加上這種手段會引來非議,後來還是作罷。他們對杜魯曼說,如果火山爆發,他們會盡力把他救出來。然而,杜魯曼毫不領情。他跟朋友說:「如果我明天死了,這一生也算了無遺憾。能做的,我都做了。我想做的每一件事,也都完成了。」
一九八○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八點四十分,聖海倫火山果然爆發了,威力相當於五百枚廣島原子彈爆炸。岩漿吞噬了整個靈湖,杜魯曼、他的愛貓和他的家都無法倖免。杜魯曼在災難過後成了偶像——他因不惜一死、堅守家園,受到很多人景仰。岩堡居民甚至在城鎮入口為杜魯曼建了一座紀念碑,至今依然屹立。翌年,有人把這個災難事件改編成電影「聖海倫火山」,由老牌明星卡尼(Art Carney)飾演杜魯曼。
雖然愛麗絲不住在火山腳下,但她似乎和杜魯曼一樣戀家。出售她在綠堡街的房子,住進養老院,等於是要她放棄經營數十年頭的生活。儘管長木屋比較安全,生活也便利得多,但她就是不習慣。雖然她在長木屋過著所謂「獨立自主」的生活,然而還是活在管理員和照護人員的監管之下。照護員會注意她吃什麼,吃太多或吃太少,而護理師也會密切注意她的健康狀況。他們發現她的步履愈來愈不穩,因此要她使用助行器。
愛麗絲住進養老院,雖然她的家人會比較放心,但她不喜歡被人照顧或控制。她年紀漸增,生活上的限制也就愈來愈多。照護員擔心她不吃藥或忘記服藥,於是要求她每日兩次到護理站,讓護理師盯著她吞下藥物。如果她不願這麼做,就不能繼續住在獨立生活的公寓,必須搬到院裡附設的照護中心。於是,吉姆和南恩為她請了個名叫瑪麗的看護,一方面確保她會確實服藥,另一方面也可跟她做伴,好讓她繼續待在公寓。愛麗絲雖然挺喜歡瑪麗,但不喜歡瑪麗一天到晚在她身邊打轉,又沒什麼事做。這樣的安排反而使她更不快樂。
愛麗絲或許覺得,住進養老院像一條不歸路,一旦踏入這個陌生的國度,就再也無法離開了。儘管邊界的守衛很和善,答應她會有個舒適的地方可住,她也會被照顧得很好;但她不喜歡別人來照顧她,只想一個人過。可是守衛已拿走了她的鑰匙和護照。如果是在老家,她就覺得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世人視死守家園的杜魯曼為英雄。對靈湖畔的杜魯曼來說,長木屋那樣的地方根本就不是家。對維吉尼亞州的愛麗絲而言,未嘗不是如此。
這個世界是怎麼了?為什麼我們晚年不是必須把所有的控制權交出來,就是只能自生自滅,就像與家園同歸於盡的杜魯曼?
得獎作品
亞馬遜暢銷書總榜第5名、社會科學暢銷書榜第1名、
亞馬遜公衛政策暢銷書榜第1名、死亡議題暢銷書榜第1名
美國《華盛頓郵報》2014年度十大好書
美國《紐約時報》非文學類暢銷書榜第1名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書榜第1名
美國獨立書店2015年非文學類大獎,銷售量超過五十五萬冊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