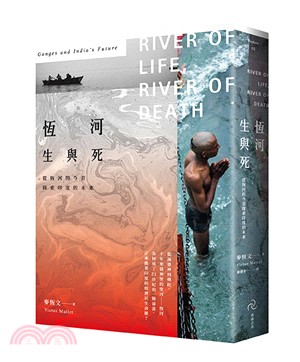恆河生與死:從恆河的今昔探索印度的未來
商品資訊
系列名:EXPLORE
ISBN13:9789869695855
替代書名:River of Life, River of Death: Ganges and India’s Future
出版社:自由之丘
作者:麥恆文
譯者:謝濱安
出版日:2019/04/17
裝訂/頁數:平裝/416頁
規格:21cm*15cm*2.5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748【高於十二年級】
商品簡介
為何成了21世紀的一條毒流,正牽動著印度的經濟民生命脈?
恆河生,印度生;恆河亡,印度亡
印度正在扼殺著恆河,而恆河也正回過頭來扼殺印度……三十多年新聞採訪經歷的作者馬凱,從源頭一路至出海口、溯至遠古一路至今日,追索著這條印度人的女神之河、被尊為「恆河之母」的聖河,同時發現到挽救這條甚至可說是世界上最重要河流的奮戰絕不會失敗……
幾千年來,比地球上任何一條河都哺育了更多人口的恆河,更被印度人視為是流淌著神聖之水的恆河女神。然而今日,大量的工業毒廢物的污染、民生垃圾等等,印度正在無以復加地毒害著這條河,而恆河也回過頭來造成了印度極大的危害。作者派駐印度的四年來,透過親身採訪來的第一手報導,以及詳盡的史料及科學文獻,試圖調查釐清這些威脅著印度甚至世界的人類及動物健康的污染。
作者從恆河位於喜馬拉雅山的源頭開始了他的旅程,主河流及重要支流一路流經多個聖城:瑞詩凱詩、馬圖拉、阿格拉、泰姬瑪哈陵、安拉阿巴德、瓦拉納西、帕特納……,以及政經大城:德里、坎普爾、加爾各答……,最後流到了恆河三角洲這個有著大批老虎出沒的紅樹林沼澤區,並於孟加拉灣出海。沿途中,有悲劇,也有成功的喜悅,他遇到了那些敬畏恆河的朝聖者,也遇到了依靠恆河維生的農民及商人,更遇到了那些排放汙水及有毒廢棄物扼殺著這條河的企業家及居民,當然還有那些企圖挽救她於毒手的人。
書中深入鑽研恆河在宗教、歷史及生態方面的諸多神祕謎團,不斷叩問為何印度人能夠同時敬拜並虐殺著他們的國家之河?而同時期地球上成功挽救了泰晤士河、萊因河以及芝加哥河這些重要大河的河流淨化顯著案例,又是否能在恆河身上再次印證?
作者簡介
新聞工作者及作家。1981年取得牛津大學英文學士,從事新聞採訪超過三十年,先後服務於路透社(Reuters)及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負責亞洲、非洲、中東及歐洲的報導寫作。二〇一二至二〇一六年,派駐印度新德里,出任金融時報的南亞分社社長,現擔任金融時報巴黎分社社長。一九九九年他寫了《老虎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Tigers, HarperCollins)一書,描寫東南亞的工業革命以及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出版後極受好評。他曾兩度贏得亞洲出版人協會(SOPA)的年度新聞評論獎項,也以恆河的命運故事以及印度總理莫迪的掘起特別報導,兩度獲得了印度知名的拉摩納葛印卡(Ramnath Goenka)傑出外國記者獎。
謝濱安
台大經濟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編輯。譯作有《女性面對的戰爭》、《魯賓遜漂流記》、《自由:我生命中遲來的第一次……》。
名人/編輯推薦
國外好評:
將歷史、地理、環境、政治、宗教及其他許多面向,以傑出且引人的方式結合在一起。這條河流在世界上占有無比的重要地位,它的整個流動及生命軌跡溯自喜馬拉雅山並一路直至孟加拉灣。
──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經濟學帕特爾講座教授 尼可拉斯.史登(Nicholas Stern)
企圖藉由一條河來探尋印度這個國家的驚奇之舉及愚昧之行,這是莫大的抱負⋯⋯作者成功完成了它!
──印度專欄作家及評論家 古沙蘭.達斯(Gurcharan Das)
本書文筆如主題般的樂觀且流暢,作者透過了時空的變換興衰及人性的自大,在這本書中描繪了恆河的整個流程,這也是北印度在靈性及物質上的一條生命線。詳實豐富的描述,顯露出這位訓練有素的觀察者充滿靈光的洞察力,他的整個敍事讓人閱讀起來深受著迷且啟發人心。
──印度國會議員及政治作家 夏希.塔魯爾(Shashi Tharoor)
熟練地結合了極其引人的歷史及對印度今日的精準觀察,本書在其主要論題上聰明地切中要旨──恆河所面對的威脅──從汙染、人口過多、氣候變遷,以及常有的惡劣政策──其實也正是印度往前邁進時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作者有時極為嚴厲地面對快速改善的這種不實期待,但又熱切地關注希望最終能獲致成功。這讓他成就了一本傑出且重要的著作。
──經濟學家及實業家、英國金融局前主席 阿戴爾.特納(Adair Turner)
作者生動地描述了為什麼印度一定要掌握住抗生素抗藥性這個巨大挑戰⋯⋯我希望莫迪總理的政策顧問都能讀到他有力的詮釋。
──創造「金磚四國」一詞的高盛前首席經濟學家吉姆.歐尼爾(Jim O’Neill)
作者是極少數不只是熱愛並且也瞭解印度的國外記者,然而他也有能力看見它的缺失並且不帶偏頗地評斷為了改正缺失所付出的努力。這代表了他對印度的報導極有見地且發人深省。
──印度電視節目主持人、新聞評論人 卡倫.塔巴(Karan Thapar)
序
前言
寫這本書是個意外。二〇一二年,我和家人在雨季期間到德里定居,抵達的頭兩天,我在車門邊的地圖集裡發現了一張令人困惑又著迷的圖:地圖上的亞穆納河旁邊,也就是位於北印度心臟地帶的此地,有個紅色的圓形小圖示裡頭畫有一艘帆船——它是代表遊艇碼頭或帆船俱樂部的通用符號。我很喜歡船,但難以相信在距離海洋如此遙遠,又飽受污染黑名的河流上有辦法享受乘帆船出航的樂趣——非但如此,這條流經現代德里的河流幾乎被廣大的居民所忽視。
就某方面而言,我的感受是對的。我在德里遇到的每個人都不曉得船的事情,然而,一張轉載刊於《印度斯坦報》(Hindustan Times)上的一九七〇年代的老照片進一步激起了我的興趣,照片中有艘小艇在週末航行於亞穆納河河上。幾個月後,我終於來到地圖上標示的地點——那條帶領我深入德里南部的歐克拉(OKhla)工業區的道路現在仍叫「帆船俱樂部路」——那裡有個「國防部帆船俱樂部」,建築物與花園都維持在良好的狀態,令我相當訝異。穿過草坪,幾艘帆船小艇整齊擱置在面河的船架上。這是一幅令人哀愁的景象,顯然這些船鮮少有使用機會(或許完全沒機會)。該地的管理員證實了我這個想法。
原因直接呈現在俱樂部的門前:這坨臭氣熏天、充滿黑色泡沫的污穢物,原本是一條河流。亞穆納河是恆河的一大支流,無論在印度神話或繪畫中,或者在歷史記憶裡頭,它都是一座充滿百合花、烏龜和魚類的大自然天堂。河岸邊,歡愉之神克里希納吹笛,身旁環繞著側耳傾聽的牧牛女子。若是在今天,這位藍皮膚的神一定會選擇避開此地。德里上游處,整條亞穆納的河水幾乎都被截流灌溉或供應首都所需。在乾季,河流往下游依序經過馬圖拉、阿格拉,以及泰姬瑪哈陵(十七世紀由蒙兀兒帝王沙賈汗為紀念他鍾愛的妻子穆塔芝所建的知名陵墓),水中充斥德里兩千五百萬居民製造的未經處理的污水和工業廢料。
歐克拉是亞穆納河在德里地區的下游終點,此處狀況尤其惡劣。剩餘的河水衝過水堰時激起成堆的泡沫。清晨時分,這些超現實的白泡沫在橘色的晨曦中閃耀,宛如許多小冰山遍布在油膩漆黑的河面上。狀況最糟時,在人類穢物污染嚴重的歐克拉區段河水中,糞便型大腸桿菌的含量超過印度沐浴標準將近五十萬倍。
我心想,假如這條河會流入恆河,那恆河本身的狀況又是如何?我是一個剛抵達印度不久的英國人,連我都知道恆河是一條聖河,一條深受歷史與文學讚頌的河流。即便在今天,恆河(Ganges)——或唸「根迦」(Ganga),絕大多數的印度語系都如此發音——在印度的信仰、社會、經濟與政治上,地位都比亞穆納河來得重要。恆河是母親之神,她獨特純淨的河水能帶來救贖,數億印度教徒都將恆河的水供奉於壺罐中崇拜。懷抱虔敬的心,印度教徒總希望自己死後能在恆河岸邊接受火化,並讓遺骨隨流水漂散。即便是世俗派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後的首任總理——都希望自己死後能有部份骨灰交付予恆河,他說:「恆河象徵印度世世代代的文化與文明,不斷地變化,不斷地流動,她永遠不會是相同的恆河。」印度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他在二〇一四年以壓倒性的差距勝選為印度教民族主義人民黨(BJP,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黨魁——也刻意選擇恆河邊的古城瓦拉納西(貝拿勒斯)做為他的國會議區。莫迪將這條河稱頌為母親——恆河母(Ma Ganga)——並立即承諾淨化河水的計畫,同時將相關部門改名為「水資源、河川發展與恆河復興部」(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 River Development & Ganga Rejuvenation)。
恆河的重要性甚至超出到印度的海岸線以外。正在書寫這些文句的我剛從斯里蘭卡回來,我在可倫坡意外造訪了一座佛寺,除了佛陀之外,裡頭也布滿象神、毗濕奴等印度教神明的神像。原來這座佛寺名叫「根迦拉瑪耶」(Gangaramaya),據回答我問題的那位僧侶所言,它是這條巨河在北方三千公里之外的一條分流。「當地有座湖泊裡頭充滿了,」他說道,「恆河之水。」
即便在遙遠的英國,恆河也擁有精神上的神聖地位。在調查期間,我意外發現一段趣事。一九六四年,恆河的水在愛丁堡公爵菲利浦親王面前儀式性地注入一座村莊的水井中。親王來到此地是為了促進印度與英國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是這座位於雷丁(Reading)附近斯托克街(Stoke Row)上的水井的建成百年紀念,此水井由十九世紀一位慷慨的印度王侯下令開鑿,一直保存到現在。據說,當時有一位任職於聯合省(United Province,包含今日印度人口數量最多的北方邦在內的一個幅員廣闊的地區)的英國政府官員名叫愛德華.安德森.里德(Edward Anderson Reade),他在一場舉辦於貝拿勒斯王侯宮殿的晚宴中談及當時重創奇爾特恩丘陵(Chiltern Hills)的一場旱災。王侯在知道一位男孩因爲喝下加諸最後一滴水而被母親毒打的事件後,決定出資建造這座深井,至今依舊被稱為「王侯之井」。其實,王侯早在三十年前就曾聽聞里德曾融資在印度建設水井的事蹟,這無疑對此次的支援有所幫助。
當時我為了替《金融時報》尋找題材來回奔波於印度和南亞之間,從選舉、工業自動化、氣候變遷到宗教衝突,幾乎無所不包。突然我理解到,若從源頭往出海口的方向書寫恆河,或許能窺見一點這個極度複雜卻又令人感到興奮的當代印度的狀況。在見證坎普爾的工業污水、瓦拉納西的家庭廢水,以及帕特納與加爾各答的垃圾之後,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一條在印度文化歷史上如此重要,象徵印度教信仰的河流,會遭受如此草率的對待?我想知道,這條印度最偉大的河流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該怎麼做才能拯救它。
有些朋友建議我應該寫一本談論莫迪的書。我曾經面對面採訪過他,他也在這本談論河流的書中佔據一角;然而,他是個已經出頭的政治家,總有一天也會像過去的其他人一樣下台。另外有人把我說的「恆河」(Ganges)錯聽成「甘地」(Gandhis),以為我想寫的是尼赫魯的後裔,目前代表人物為桑妮雅.甘地與她兒子拉胡爾的那個政治家族;由兩人領導的國民大會黨在二〇一四年被莫迪與人民黨擊敗。不過,我發現蜿蜒曲折的恆河在今日依然是條交織纏繞在印度身上的細線,甚至比尼赫魯-甘地的時代更能演繹當前的狀況。正如溫斯頓.邱吉爾針對泰晤士河與英國之間所描述的關係一樣,恆河正是印度歷史的那條「金線」。恆河沿岸有許多偉大的城市,有些依然存活,其他衰敗遺棄,都已經存在數千年之久,在那個時代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比中國或者羅馬帝國都還大,幅員甚至是西歐的三倍之多。
因此,為何受到如此大量印度人崇拜的恆河,同時卻也遭受同一群人的傷害?為何印度人和他們的政府有辦法忍受(即便只有一週)過量建設於聖河上的灌溉水壩——有時候甚至出現完全缺水的狀況——以及人類污染物與工業毒物的毒害?印度教徒堅信純淨的恆河不會受到這些污染影響,這是真的嗎?這條河還有得救的可能嗎?
在本書中,我將解釋印度人如何以污染扼殺恆河,恆河又如何反過頭來扼殺印度人。但故事並非毫無希望。書寫過程中,我逐漸了解到所有發生在印度的對與錯,也開始相信印度人能像歐洲人與美國人成功拯救泰晤士河、萊茵河與芝加哥河一樣拯救恆河。同時,我也意識到(有愈來愈多憂慮的印度人跟我一樣)虔誠印度教徒在心中將恆河實體上的污濁與其精神上的純潔區分開來,假裝物理世界無法侵犯精神領域,這件事是多麽荒謬。談及亞穆納河時,有位聖人曾經說過,河流本身才是「真正的神」,而非那些遙不可及的精神象徵。正是如此,恆河如此重要,首先就是因為它的物理性為人們供給了生命所需的水源與沃土,才以大自然之靈的姿態受到崇敬,最後演變為印度教眾神中一位豐腴的女神。
我不是印度教徒,大概永遠也不會像數億名印度人那樣充滿熱忱地崇敬恆河,但我對這條河的愛就跟我愛其他所有偉大的河一樣多——或許更多,因為我還嘗試著去了解它——我很關心它的未來。外國人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懷抱環保理念的一群)很容易遭指控為偽君子,他們抗議道:「你們為了追求經濟成長破壞了自己的環境,現在卻想阻止我們發展。」或者「以前泰晤士河那麼醜陋,你們卻說我們這些污染的河流讓你震驚。」我過去在中國與南亞也曾遭受類似批判,令人吃驚的是,鮮少有印度人會因西方媒體對聖河的描述與報導出的問題憤恨發怒。我想這是因為絕大多數人知道這些問題都是真的。
本書大致以順流而下的方向進行,起始於恆河位於喜馬拉雅山麓的源頭,終止在孟加拉灣的入海口。有些朋友堅稱這是悲觀處理此一主題的方式,因為河流源自於冰凍純淨的山區,愈往下游經過愈多城市就變得更髒,污染程度更嚴重,但我不這麼看。我喜愛恆河上游潔淨的空氣與水,但也同樣享受著航行於河上、擺脫沿岸大城那些無序的歡愉等過程,尤其遼闊海洋給我帶來了無限可能的感受。此外,恆河水隨著流程增加逐漸變髒這個說法也是錯的;大自然的多變,諸多支流注入新水量——最知名的就是發源自西藏的布拉瑪普特拉河(雅魯藏布江),以及沿途不斷發生的沉積與汙染物的擴散,都讓一切變得比想像中複雜許多。
隨著章節前進,我們將順著恆河一路往下走,沿途有悲劇,有成功的喜悅,有古代與現代印度的諸多神祕謎團,以及演出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朝聖者、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農民、畫家,還有探險家——最後結束在孟加拉灣恆河三角洲的紅樹林沼澤。
目次
2. 聖牛之口:喜馬拉雅山上的源頭
3. 聖水
4. 建造一座巨型城市――同時拯救恆河
5. 瓦拉納西:印度的一日首都
6. 瓦拉納西:破碎的諾言
7. 毒物之河
8. 超級細菌之河
9. 恆河豚、鱷魚與老虎
10. 人口壓力:為何人口成長並非紅利?
11. 水與井:水龍頭為何乾涸?
12. 水壩與乾旱:整治恆河
13. 寶萊塢之星:電影中的恆河
14. 充滿異國風情的河:恆河上的外國人
15. 風暴與沙岸:恆河上的船隻
16. 貿易重鎮不再:加爾各答與孟加拉
17. 不可能的任務:如何淨化恆河?
18. 美麗的森林:恆河入海之地
書摘/試閱
瓦拉納西——打破承諾
為了更詳實評估恆河在瓦拉納西的狀況,我與在瓦拉納西接待我的主人實地走了一趟尼薩德拉賈(Nishadraj)神廟與河壇;該命名來自傳說中的船族部落之王,他住在這條河上,曾應羅摩神的請求,助他過河拯救妻子希塔(Sita),而這座神廟就是船族的大本營。帶我們來這裡的是穿著體面的德文德拉.米斯拉(Devendra Misra),他是當地的藥廠業務員。他領著我們沿著河岸前進,到處都是垃圾,經過了歷來眾多王公建造的神廟,以及一座標示著「引水作業」的巨大抽水站;它為這座城鎮抽出河水,並形成了一道小型渦流——就在上游大約四百呎處髒汙的亞西水渠,直接將未經處理的汙水排放到恆河。
我們一面步行經過了正在進行修繕的老舊木划船以及一座小型的濕婆林伽神壇,米斯拉一面跟我說莫迪已經做了他辦得到的事情——他指著垃圾桶說道,現在甚至連垃圾桶都有了——並將恆河的問題歸咎於一般人民。「人們在公共場所一直沒有什麼衛生習慣,他們沒有屬於國家的精神,」他說,「莫迪先生已經竭盡所能了。而且傷害這條河的不止當地居民,還有來自村落的那些人,他們帶來一堆東西,最後都丟棄在河壇上。」不過我們抵達尼沙德拉吉古哈河壇後,他也附和其他瓦拉納西居民一同抱怨河流水量不夠,並感嘆那「透明清澈」到可以用來淨身的水已經不見了。「如今,我甚至不想把恆河的水含在嘴裡,我現在會有遲疑。」(「但他必須這麼做,他是婆羅門,」我的同事低聲說道,「他每天早上都會來河壇。」)
神廟最近剛重新粉刷成明亮的紅色與土耳其藍(他們跟我說現在我們欣賞到的古希臘神廟、神像雖然都是蜂蜜色的石材,但在古時候其實也都被塗成俗豔的色彩),我們仔細端詳了尼沙德.拉吉本身的肖像,還蓄著精美的鬍鬚。我第一個接觸的船夫是七十歲的米泰.拉爾(Mithai Lal),最初他不願意開口,但後來同意與我們談談恆河與他的營生。他的家族擁有兩艘木船,其中一艘裝有引擎,另一艘則需要用划的。我問船夫們是否記得恆河上曾經有過帆船,沒人給我回應,但米斯拉說以前確實有一些帆船用來載運六十至七十噸的火葬用木柴。拉爾頭髮花白,鬍子沒刮,骯髒的白色T恤下挺著啤酒肚以及藍格紋兜提。「我們從曾祖父一輩就定居在這裡,」他嚴肅地說道,「這裡發生了很多改變。河流現在變得很小,都快要沒有了,它現在狀況很糟,沒什麼水。他們建造許多水壩,把水都取走留給水壩用。」
要維持一個二十人大家庭的生計並不容易,部分原因是本來可能的遊客與朝聖者因為汙染不再前來,另一方面則因為政府下令禁止在此河段釣魚(「當然,人們會違法在夜間釣魚。」他承認道)。「汙染太嚴重了,恆河實在髒到人們不再來了,人們不想來這裡。我們還是一直喝恆河的水,因為不得不。」
同樣地,他姑且選擇相信莫迪,而譴責當時的北方邦首席部長阿基勒許.亞達夫(Akhilesh Yadav);亞達夫家族領導社會黨(Samajwadi Party)對抗莫迪與印人黨。(由莫迪領導的印人黨接下來在二〇一七年三月贏得北方邦的選舉,把亞達夫趕下台,並指定激進派的印度教祭司阿蒂提亞納特瑜伽士〔Yogi Adityanath〕接任。)「莫迪先生是團隊的領導人,為了解決問題他已經投入資金,該把事情做好的人是阿基勒許,但他什麼都沒做。」甚至在雨季來臨的前幾週的這個時候,水位破例地低,拉爾指著遠遠岸邊的沙岸及其延伸而出約兩百公尺遠的一片綠地說:「河水原本會在那片綠地的高度。我們家族的人都在河裡洗澡。我們家裡有水龍頭,但如果不供水時,我們就喝河水。恆河之母永遠純淨,她從未給我們帶來麻煩。」
我們與拉爾談論著恆河的同時,我注意到神廟的露天平台上有另外一位戴眼鏡的男人正在修補漁網,根據網眼的巨大尺寸,我推斷他應該是想捉一些大型的鯰魚。六十七歲的羅姆.拉坎.普拉薩德(Ram Lakhan Prasad)跟拉爾一樣對恆河的現況已經不抱幻想了,「恆河的所有支流都建了水壩,所以這裡才會沒水。因為有她,我才得以長大,得以受教育。」——他對著河流致意——「但現在一切都沒了,連這條河都成了臭水溝。至少還要再等六個星期(雨季才會到來),目前水位卻這麼低,難以想像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基本上,裡頭全是從工廠排放出來的化學藥劑和汙水。有些人說:『別在河裡洗你的牛。』但我們以前一直都這麼做,向來沒什麼問題。」我同意他最後的埋怨——認為在河裡洗牛會造成嚴重的河水汙染是荒謬的——然後我問他,真正的問題是否跟人口成長以及他們帶來的汙水排放沒有關係?「我同意這會給河流帶來壓力,」他回答道,「但你有看見她被折騰得多糟糕吧?他們到處蓋水壩,請他們放過這條河吧!」他的手絕望地指向遠處河岸成堆的垃圾山。
我們決定往上游去調查亞西水渠,在那裡我們看到了岸邊有一大棟混凝土造的垃圾處理場和抽水站。我們聽說這個場站約在十年前蓋好,但它悄無聲息棄置在那裡,顯然已經多年沒有營運。豬隻與乳豬將鼻子探入垃圾堆中翻找,上方則是一座平台支撐著一具大型柴油發電機用來應付瓦拉納西頻繁的斷電狀況。我們穿過掛鎖都已經生鏽的大門,進入建物內部,看見了一些外表價值不低但已經布滿灰塵的控制面板,還有成堆的麻布袋以及鬆脫的機器的一些部分。亞西水渠可說是瓦拉納西最大也最髒的排水管之一,暢通無阻地流動著。我看見一只保麗龍盒被湍急的水流沖下,最後才卡在河岸邊的舊塑膠袋堆中與其他垃圾上。我們在附近的小屋找到看守的達曼.傑伊.辛格(Dhaman Jay Singh),他向我們保證修復工作正著手進行中──儘管我們沒看到任何標示。他說,發電機和抽水設備四年前曾經測試過,但當時抽出的水淹沒了上游的一處村落,測試只得中止。
隔日破曉前,我們出發前往河壇火葬場,在那裡工人的責任是焚燒屍體,他們是在瓦拉納西過世的人以及那些死後才送來這裡以求骨灰能夠託付給恆河。無所不在的牛群仍然在商店街的走廊上睡覺,唯一一個接近我們的小販推銷著供奉用的花朵,以及剛從樹上折下用來潔牙的苦楝樹枝。就連身穿橘袍的沙度都還在河邊的長凳上睡著。我們來到了達薩斯瓦梅朵河壇(Dashashwamedh Ghat),這裡是十匹馬犧牲的河壇(傳說梵天在火祭中奉獻了十匹馬),以及拉金德拉.普拉薩德博士河壇(Dr. Rajendra Prasad Ghat,普拉薩德博士是印度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是在這裡,一九八六年拉吉夫.甘地發起了第一次但命運不佳的「恆河行動計畫」。一座巨大的警察局突出地立於河岸邊,而正對面遠遠的岸邊乾涸的河床沙灘上是成堆的垃圾──估計是違法傾倒。隨著橘色的太陽穿透灰塵升起,來自奧里薩邦(Orissa)的一家人正在河邊用塑膠容器盛裝河水,打算帶回去家鄉的濕婆神廟,沐浴中的父親浮出水面──河面散布著塑膠,偶爾還會浮起宗教供奉用的燈──連忙用手拉好自己的內褲。
迪帕克.馬吉(Deepak Maji),一位六十歲的船夫,他的家族幾個世代以來都在河上工作。無論是莫迪為了淨化恆河付出的努力,或者河岸附近那些新廁所,都沒有給他什麼好印象。當我問他恆河是否有任何改變時,他以粗啞的聲音回道:「沒有,還是一樣,除了汙染沒有任何改變。現在莫迪坐在那邊粉刷這些房子,但還有什麼改變了呢?人們還是一樣在這裡拉屎、撒尿,有誰能夠阻止他們?只要你一跟他們說,他們就會反擊。有誰能要求其他人做任何事?」就在他說這些話的同時,一個蹲坐在母親身邊的孩子拉了一地腹瀉在河岸上。我們決定雇用一個比較年輕的船夫,三十五歲的馬丹.馬基(Madan Maji),帶我們前往不遠處的火葬場。在他剛用槳把船划離河壇後,我看到幾位船夫把船就綁在警察局正下方的岸邊,正拉上一張漁網,儘管藏在警察看不到的地方,網子上也沒有半條魚。我問他,這裡到底允不允許在河裡釣魚?他的回答讓我感到相當有趣,它微妙地說明了印度人看待法律的那種彈性態度:「在亞西河壇和拉迦河壇大橋(Raj Ghat Bridge)之間這一段『比較』不被允許。」他不需要告訴我我們現在就正位於這兩個地點之間。
在我們前往下游的馬尼卡尼卡河壇(Manikarnika Ghat)(大概是這裡最知名的火葬場)途中,他指著一幢俯視河流的大房子,兩邊角落的欄杆上各有一座上了漆的老虎雕像,那是「多姆之王」(Dom Raja)──多姆公會(喪葬業公會)的現任首腦──的房子。理論上他的身分屬於賤民,但據說他極為富裕,因為印度教的有錢人很願意付錢給守護聖火的多姆,由他們來執行印度教的喪禮儀式這個由他們包攬的事物。稍晚,我們在回程的途中爬上面河一側陡直的戶外階梯,不抱希望地敲著一扇上鎖的門,最後終於從朝著陸地的那一側找到了入口,一邊經過了一隻鬥牛犬和一頭牛,結果發現多姆之王正在睡覺,怎麼也叫不醒。正在露台上享用早餐的他的家人告訴我們,他剛在清晨五點結束工作。那些為他工作的人表示,其實他不太需要做事,因為他已經很有錢了根本不需要工作。然而曾在二○一五年與多姆之王碰過面的一位記者將這座宮殿形容成「大型雜物間」,他還發現這位本名桑吉特(Sanjit)的多姆之王是個矮小黝黑的男人,看起來「衰老又可憐」,每天都要喝下幾瓶威士忌,幫助他忘卻那些腐爛屍體散發出來的惡臭。他的胸口與手上滿是燒傷的疤痕,但多姆之王說,那是六年前在一場婚禮上因為瓦斯罐爆炸造成的,與火葬無關。
馬尼卡尼卡河壇的火葬場上,幾具木柴灰燼中的殘骸仍在晨光照射下冒著煙。近處有幾堆木柴在等待下一位客人,以及一些用來秤木柴重量的藍色磅秤。幾條狗在河壇上打架,兩個男人在河邊臨時搭建的休息區看電視,他們表示每天要處理八十到一百五十具屍體。不管如何,印度人似乎都以一種就事論事的方式面對死亡,而對虔誠的印度教徒而言,死亡在聖城瓦拉納西這裡不僅可以接受,甚至還是受歡迎的。「天氣很好,不太熱也不太冷,所以沒有很多要過世的人。」蘇倫德拉.普拉薩德(Surendra Prasad)說道,他在白天時負責紗麗設計的工作,但自願每天清晨到這個河壇及其三處彌留安寧所工作四小時。畢竟,瓦拉納西常被說是擁有「一萬個寡婦」的城市,但這些通常因為失去依靠而暫時藏身於此的女人,現在真正的數量可能將近四萬人。「這是我的業報(karma)工作,我在為了來世累積善業。我們照顧他們,提供食物、藥給他們,幫他們按摩,當他們走了,我們火化他們。」
要火化一個人視體型約需要兩百到三百六十公斤的木柴,且通常得耗費兩個半小時才能完成。我詢問這些木頭哪裡來的?他說是從南邊的中央邦(Madhya Pradesh)一大片森林那裡,北方邦的木頭早就用盡了。穿著白色背心與兜提的普拉薩德一邊和我走在狗群、牛群、羊群到處晃蕩的河壇上,一邊解釋儀式的流程。親人會打開死者嘴巴,將恆河的水倒進去三次;長子或丈夫要去理髮師那裡刮掉鬍子並穿上白色衣服;親人為那永恆之焰購買木材——普拉薩德強調,至少要兩百公斤——並付錢給河壇,然後把木材交給他們,讓他們用乾草引火來點燃柴堆。屍體會被搬運到柴堆上開始焚燒,燒到只剩下骨盆或頭骨等大塊骨頭時,親人便要到恆河盛水回來澆熄火焰,總共要五次。(以下這些他沒說到,頭骨要不是在燃燒的火焰中爆裂,就是由長子或火葬場工人拿棍棒將它敲碎,用以釋放死者的靈魂前往天堂。)重覆五次的儀式反映著人體的五種元素,普拉薩德說道:地、水、火、風以及「以太」(或說「空」)。「骨灰冷卻之後,死者便安息。」到恆河上盛水第五次的儀式結束後,親人會拿陶罐砸在他們肩膀上,罐子會被砸破,這代表「你進天堂,我回家鄉。」之後,骨灰放入河水中,然後工人會潛下水去取回鼻環或其他珠寶。
這個河壇是個沉靜、講求實效的地方。我看到一幅卡莉女神戴著骷髏項鍊的畫像,還檢視了那個長方形石坑裡俯視著恆河的永恆之焰。一個戴眼鏡的男人坐在旁邊的墊子上,拿著一本記錄費用的手寫帳冊。河壇焚燒屍體的區域其中一處平面上,柴堆仍然冒著煙、炙熱的燒著,不過頭骨已經碎裂,遺體也僅剩骨頭與灰燼。整個環境相當隨意,四周散布著一些垃圾:塑膠袋、舊水瓶、牛糞、幾塊碎布,以及盛裝線香的空紙盒。安靜地流過河壇的恆河,對於印度教最莊嚴的火葬場之一的馬尼卡尼卡河壇來說,是很重要的。離開時,我從另一個面向看見了印度教徒的生與死是如何與恆河緊密的交織在一起。馬尼卡尼卡的原意是「耳環」,而有一些傳說說到了濕婆神之妻這位代表愛與豐饒的女神帕瓦蒂(Pravati),是如何在此地遺失她的耳環——也可能是她故意藏起來要捉弄她的丈夫濕婆。幸運的是,我正巧在帕瓦蒂女神的節慶當天來到河壇,她的神像展示在粉刷過的河壇水池中央,四周裝飾著鮮花。普拉薩德向我保證,水池中的水絕對是直接取自高穆克的「聖牛之口」,也就是恆河位於喜馬拉雅冰河的源頭。當水池中的水全部流入恆河時,他說,能從底部看見一頭牛的面孔。
在這趟瓦拉納西之旅的最後,我拜訪了另一位關心恆河命運的婆羅門,卡米什瓦.烏帕亞(Kameshwar Upadhyay)是一位梵文學者,他的宗教資歷使他自然成了莫迪和印人黨的盟友——他說他是印人黨第一位總理阿塔爾.比哈里.瓦巴伊(Atal Bihari Vajpayee)的星象師──然而印人黨政府跟世俗派的國大黨一樣,都讓他感到失望。他在二〇〇三年從貝拿勒斯印度大學退休後,創立「學者議會」著手復興梵文研究與吠陀傳統,並撰寫一本書說明真正的印度教徒該如何生活。烏帕亞說他在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七年間,發起了一項淨化恆河的運動,因為效果太好而遭到多個非政府組織、世界印度人理事會(Vishva Hindu Parishad)以及部分國民志願服務者聯盟(右翼印度教團體)的攻擊。我問為什麼?「因為我們擊中了(恆河問題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我到處去跟人們說,這就像一個孩子無法阻止母親在生理期過後去見父親一樣,沒人有權利在河流上建水壩,你不能限制她,不能阻止她流動……正如女人藉由生理期獲得淨化,這條河藉由流動而淨化。」隨著我們針對河流性別的討論(大多是女性,只有梵天之子布拉馬普特拉河與印度河是例外),我發現無論是烏帕亞還是在瓦拉納西發起的其他恆河活動,他們關心的重點都在於從河裡取出做為灌溉之用的河水,而非施加於河裡的汙染。
從科學來說,這確實有些道理,因為水流量增加會有稀釋效果,從而減低汙染造成的傷害程度,儘管仍無法完全消除問題,不過烏帕亞對於宗教層面的關注和實際層面一樣多。他引述傳統及經典,聲稱即使化學物無法改變一條河,我們仍不應該阻礙水的流動,因為那真的會殺死一條河流。「拉吉夫.甘地政府和阿塔爾.比哈里.瓦巴伊政府在河流上蓋這些水壩用來發電,他們截斷了整條河流。」他說,「根據印度的傳統,你可以限制海洋,但不能阻擋河流。」他繼續說道,甘地和瓦巴伊都犯下了「罪」、違反一九一六年的協議。這項協議由當時英國政權與恆河沿岸共一一九位王公共同訂下,並由貝拿勒斯印度大學的創辦人馬丹.莫漢.馬拉維亞(Madan Mohan Malviya)居間安排,內容提到「恆河必須在開闊的天空下自然地且永恆地流動」。(事實上這項現今依然納在政府法規裡的協議,變成是個相當技術面的公文及折衷方案,套用在赫爾德瓦爾的水壩建造上就是要求必須確保一定流量——精確來說就是每秒一千立方呎──流過赫爾德瓦爾的河壇。)
「我本來是瓦巴伊的星象師,但我對這些事情相當不滿所以逐漸遠離他。」他說道。我問他,莫迪是否改變了什麼?「沒有,我從一九九八年觀察到現在,他們持續在談汙染的控制。只是問題不在汙染,你都不把水留在河裡了,那才是問題……當一頭牛提供你乳汁,你就只要餵養牠就好,而不是讓牠流血。」對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徒而言,這是相當強烈的控訴。當我問到為什麼莫迪無法帶來改變,他把怒火轉移到烏瑪.巴蒂這位負責水利與恆河修復工程的內閣閣員身上,「有個很好的理由,負責的政府部門及領導它的部長沒有任何遠見、沒有聖哲的思維。她一直說人們不可以再把屍體丟進河裡,但這就是上天賜予我們恆河的唯一理由啊!人類身體裡頭的東西怎麼可能汙染恆河?」烏帕亞說,這是扼殺恆河的陰謀詭計。這不是關於需要砸下多麽大筆的預算,重點在於水流量。「我們現在無法再像傳統一直以來的那樣,直接喝下恆河的水了。」他說,「下一個世代,那些出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人,甚至不會知道恆河曾經有過那樣的水質。我從二〇〇一年開始就不再去恆河了,它的狀態令我難過……只要莫迪先生的畫押,就能拯救恆河,我們需要的不是兩萬克羅(三十億美元)的資金,只要讓恆河自然流動就行了。」
在瓦拉納西聽了這麼多關於恆河命運沮喪的言論之後,我離開市區來到上游不遠處的丘納爾堡(Chunar Fort),看見恆河仍然安穩地流動著讓人感到慰藉。原本往東流的恆河在此處大轉彎向北流過瓦拉納西。現在是雨季之前的炎熱乾季,衰退的河流使得大片沙岸露出。河邊殘破失修的英國墓地旁,農夫們正在照料一小塊田裡的小米與名叫南瓦(nenua)的一種小黃瓜。從堡壘的高牆上,我望見了木舟上幾名漁夫,鸛鳥和鴴鳥在淺灘覓食,而沙岸邊河水較為湍急的地方,有兩隻恆河豚正在捕魚。儘管我這趟旅程的目的是為了調查毒害印度這條聖河的汙染本質及嚴重程度,看見這一幕總是讓人感到振奮了起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