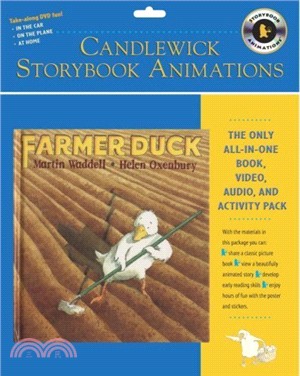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本書從生命開端寫起,全書十章,以「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點題,細說生命倫理的近世與現代故事。今天人類已經可以「扮演上帝」,科技還在攀登更高的山峰。在最高峰處,倫理學試圖提醒:小心腳步,也要回望來路。
本書說故事,也澄清觀念、分析問題,邀請讀者同來思考。生命倫理問題往往不能只憑理性辯論做抉擇,底下還有關懷、同情,以及對人和生命尊嚴的敬意。
作者簡介
從事人文及倫理寫作,其中《當中醫遇上西醫――歷史與省思》(2004)獲國家文津圖書獎。近年出版著作有:《醫院筆記:時代與人》(2016)、《有詩的時候》(2017)、《當我用心寫――一個醫生的十年記》(2017),以及《如何走下去――倫理與醫療》(陳浩文、區結成編著,2018)。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中,區醫生通過一環接一環的小故事,向讀者娓娓道來平常人都有可能會面對到的各類生命倫理相關的問題。全書深入淺出、筆精墨妙, 我會向所有對生命倫理學有興趣的讀者推薦本書。」前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鄭維健博士
「區結成醫生在公營醫院服務了三十年,退休了,但我覺得他其實沒有真的退休。放下醫生袍,拿起筆,他以區聞海的身份繼續行醫,不是在某一所醫院,而是為了整個社會。他以個人經驗結合醫學知識,啟發大眾讀者,面對不可測的未來。」香港作家、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淑嫻
「曾經,荃灣有四幢分別喚作春明、夏雨、秋趣和冬隱的大廈,為千百居民提供遮陽擋雨的家園。區聞海醫生在秋趣樓住了六年,練就一顆清心一雙慧眼,寬容看待世事變幻,不忘醫療本業,同時旁徵博引,抽絲剝繭,交出滿有趣味的倫理觀察。」專欄作家陶囍
====================================================================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邵鵬柱教授、香港醫院管理局策略發展總監李夏茵醫生、電影及劇場編導演賴恩慈為本書撰序
目次
第一章「生」 生之波瀾:避孕、體外受孕
第二章「命」 性命攸關的抉擇
第三章「誠」 生物醫學研究的誠與信
第四章「可」 可與否:墮胎的爭端
第五章「貴」 昂貴稀有的醫療
第六章「自」 個人自主:知情同意、自主
第七章「由」 眾人自由:公共衛生與社會規範
第八章「價」 價值觀、存異
第九章「更」 更強的生物科技
第十章「高」 高峰,高處不勝寒?
書摘/試閱
醫學科技和倫理問題有孿生關係。人工生殖科技的出現觸動了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觀,尤其是基督教。而且,科技開啟了許多新的門口,衍生一圈又一圈的生命倫理課題。
這些問題離開大眾的生活也許比較遠,畢竟需要為人工生殖科技的問題費思量的人並不多;這一章談生命另一端的課題,就與每個人有關。
27.
醫療上的決定,當牽涉到與性命攸關的抉擇,往往有些沉重。這兒從一則安靜從容的新聞寫起。動筆寫這一章的時候,讀到新聞報道,92歲的美國前總統夫人芭芭拉.布殊(Barbara Bush)病情惡化,決定放棄接受「額外的醫療救治」(ad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前總統辦公室在2018年4月15日發表聲明說,布殊夫人已返回家中靜養,接受舒緩照顧和家居護理。她在兩天後逝世。
芭芭拉.布殊受國民愛戴和尊重,稱為「人民祖母」。傳媒沒有過分挖掘暴露她晚期醫療的細節。據CNN報道,她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及充血性心臟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CHF),晚年多次出入醫院。之前她的病史還包括格里夫氏症(Grave’s disease,一種由自體免疫力引起的甲狀腺機能亢進症)、胃穿孔(進行了手術)、心瓣膜嚴重狹窄(也動了手術)。2018年她因呼吸困難入院,4月上旬出院後不久,病情反覆再入院,我猜想或是肺炎未能清除。
眾人眼中積極堅強的芭芭拉曾在自傳中透露,中年時代,她曾經歷長時期的抑鬱症,最壞的時候每晚在其時主管中央情報局的丈夫臂彎裡飲泣,無法自拔。她還回想起,有時會在公路一側停下車來,因為忽然冒起輕生念頭,恐怕自己禁不住會故意撞上一棵樹或迎面而來的車。後來她全情投入義務工作,捱過難關。
筆者早年是老人科醫生,對這樣長長的病史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從病史可以頗為肯定地推斷,芭芭拉.布殊拒絕的「額外醫療救治」,包括不接受「心肺復甦術」(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也應該包括拒絕使用人工呼吸機器(artificial ventilator)延續性命。這兩樣救命的法寶是在六十年代才興起的新事物,根本地改變了人類死亡的過程。
說「死亡的過程」聽來有些奇怪。救命的發明,不是為了戰勝死亡嗎?為什麼說「改變了死亡的過程」? 因為雖有不少人得益被救活,但也有不少——可能是多數——病人是被動地接受了CPR。末期病人在生命最後一程用呼吸機器續命,有時只是苟延殘喘。
世上像芭芭拉.布殊一樣,嘗過許多哀榮苦樂和病痛的老人很多,多數沒有這前總統夫人那般有福氣,能夠及時和有意識地抉擇如何去世、在什麼地方去世。
我的意思不是說年老病人,或者患有末期器官衰竭的病人,只配使用保守「省事」的醫療方式。相反,我覺得他們應該得到更細心的照顧,才有機會像芭芭拉那樣,可以依意願作選擇。
28.
心肺復甦術是五、六十年代的發明,先是在1956年發明了「口對口人工呼吸」,其後加上「體外心臟按壓」(external cardiac massage,俗稱「心外壓」),發展為一套現代的基本心肺復甦術。
美國心臟協會在1963 年正式認可心肺復甦術。1972 年,全球第一個大規模心肺復甦培訓項目在西雅圖成立,頭兩年就有超過十萬人通過培訓,CPR從此成為普及的基本急救術。
心肺復甦術在七十年代與多種醫學介入手段相結合,成為一套醫療人員使用的高級心肺復甦術。這包括以插管(intubation)通氣,使用心電圖監控、靜脈注射急救藥物、心臟除顫(cardiac defibrillation)電擊等。
CPR本來是用來搶救意外和突發事故,例如溺水、觸電、中風、急性中毒或心臟病突發,漸漸就變成了對醫院病人的標準急救作業程式,幾乎每一個住院病人心臟停止跳動,都會想也不想地搶救一番。
問題或者就在這裡:CPR對病人,尤其是老人,不是沒有傷害的,即便是看似簡單的插管動作,使用喉鏡撐開口腔插管時,遇上齒齦鬆動的長者,可能會壓斷他們的門牙。體外心臟按壓可引致胸骨壓斷、內臟破裂出血等併發症,本身有骨質疏鬆症的病人特別容易因CPR而受傷。
或者問,救命是千鈞一髮的事,哪還顧得上胸骨會不會折、門牙會不會斷落?那麼我們就要退一步問:不假思索的「套餐式」搶救到底有多少效用?病人有沒有拒絕CPR的權利?
CPR並不是對所有病人都有用。在不少末期病患,CPR恢復心跳的機率低於百分之一,即使心跳恢復,病人被接駁人口呼吸器,再施以深切治療,也可能只是延長走向死亡的最後過程。而且,如果病人並非即時被發現心臟或呼吸停頓,從開始CPR至恢復心跳之間,病人可能已有一段時間缺氧,令腦部受損。有些病人會變成依靠儀器維生的植物人。
早在1974年,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已注意到 CPR 有被誤用和濫用的趨勢,醫學會在制訂指引時提醒,CPR 的主要目的在防止未預期的突發死亡,不應用於無法復元的末期瀕死病患身上。
病人有拒絕CPR的權利。在本身病情和神志許可下,應給病人機會選擇。若是不予討論,眾人沉默,等到病人失去自主能力就去例行搶救,對病人並不公平,亦不尊重。
29.
同是在1974年,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認同了美國醫學會的指引,提醒CPR不可一刀切用於所有病人,要考慮現實情境,留空間允許病人自然死亡。AHA進而倡議,在不應勉強嘗試CPR的病例,如果得到病人或代理人同意,醫生應當把do not resuscitate(DNR)的指示清晰寫在病人的醫療紀錄上面,以免其他醫生不適當地施行搶救。
這是打破禁忌的一步。在此之前,當然不少醫生也會在專業上避免濫施搶救,在某些臨終病人,醫護人員有時是以同情而隱晦的默契「收手」,容許病人自然死亡。即使來到八十年代,我還見過病人的醫療紀錄上面隱晦地寫上「TLC」三個有如密碼的字母。TLC是tender loving care的縮寫,這是指示,基本的愛心護理便好了,不要給病人「搶救套餐」。從昔日只可意會不可直言,到今天有清晰指示,這當然是打破了禁忌。
Do not resuscitate三個字簡潔,DNR三個字更容易上口,但意思有欠準確。直譯為「不作復甦」,彷彿說病人明明可以復甦康復也給指令不予搶救。實際上,DNR是用於那些病人表明不想接受CPR,或是病況不適宜勉強進行CPR的個案。美國醫學界後來以DNAR(do not attempt resuscitation)取代了DNR的叫法。Do not attempt的意思是指示不要嘗試進行CPR急救。
英國的醫學界認為DNAR的叫法還是有欠準確,因為對resuscitation一字可以有寬緊不同的理解,他們採用更嚴謹一點的名稱:DNACPR(do not attempt CPR),要準確地表明,病人不想接受或不宜接受包括插喉管和心外壓等的CPR程式,但不是叫醫護人員一律終止其他有需要的維生治療,例如氧氣。在香港公立醫院的倫理指引也採納DNACPR這個名稱,中譯作「不作心肺復甦術」,口語化一些就是指示「不要施行CPR」。
我長時間參與醫院管理局臨床倫理委員會(Clinical Ethics Committee)的工作,認識了不少有心人,他們特別關心病人在生命後期不應被機械式地搶救。臨床倫理委員會製作了一些指引,供前線人員參考。這些屬於內部使用,但也有一份頗為詳盡的小冊子〈「預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 不作「心肺復甦術」?〉,是醫護人員齊心合力寫給公眾的。
儘管有指引,對於病者和家人,甚至醫護人員,DNACPR的決定並不是都是順理成章地沒有掙扎的。畢竟有些觀念深入人心:不施行CPR,是不是等同完全放棄?作為家人,不是應該支持病人,堅持「對抗病魔」、勇敢「戰鬥到底」嗎?
30.
2018年,香港消防處在社區推廣急救,為提升市民的關注,設計了一段短片,宣傳心肺復甦術和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片中有一個藍色人物「任何仁」(諧音「任何人」)與長青女藝人羅蘭合作,拯救一名心臟驟停的市民。藍色「任何仁」一炮而紅,變成消防處推廣CPR的吉祥物。
但醫院裡面的CPR和社區拯救是不同的。哈佛大學醫學院附設麻省總醫院有一位駐院醫生Dr. Khullar為《紐約時報》寫網誌,有一篇題為「The CPR We Don’t See on TV」。他說,大多數電視劇集中的CPR常能起死回生,心外壓和電擊之下,病人甦醒過來;但現實中病房裡的CPR並非如此有神效。
Dr. Khullar不是潑冷水,他只是把病房所見如實道來:醫院病人的病況,與社區遇上的心臟驟停(cardiac arrest)個案,並不相似。
我第一次見到接受心肺復甦術的病人,那經歷並不是我所預計的。
當然,我預計了她看起來會有不適。畢竟,她的心臟剛才曾停止跳動。但我沒有為眼前的場景做好心理準備:這個 8 0多歲的體弱女子,幾乎沒有了意識,她嘔吐過,肋骨骨折,肺部挫傷。她的胃因充氣而腫脹,胸部有血跡。我心裡想,她看起來更像是從心肺復甦術的關頭倖存,而不是從自己的心臟病活過來。幾天後,她去世時,我不禁暗問,當初她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將會接受什麼的步驟。
往下是他的觀察反思:
在我與病人的談話中,(提到接受CPR與否時)我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反應。一個病人——年輕而健康的——淚流滿面,以為我是因為他即將死亡而提出建議不做CPR。一些人迴避談論,他們認為不可能有需要預先考慮,也許是不想認知有遇上需要CPR的可能。大多數病人即使能平心靜氣地處理這個話題,但幾乎沒有例外地,往往不明白CPR到底是為何要用,它的風險和好處是什麼。
Dr. Khullar引述一些文獻,表明在醫院經歷心臟驟停後接受心肺復甦術的患者中, 不到兩成者能存活出院。研究又發現病患者大大高估了成功率,八成人以為他們在接受CPR後能出院的機會超過一半, 近四分之一的人更以為出院機會超過九成。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電視節目裡面接受CPR的病者角色,有四分之三立即被救活過來,有三分之二能長期活著。這或者只是劇情所需,但整體上卻給予公眾錯誤的樂觀想像。
31.
Dr. Khullar的文章可以拿來與香港本地的一篇文章對著讀。這是一位醫學生在醫院的實錄,很有本地的現場感。
這個醫學生與同學如常上病房,尋找研究學習的病例。他們遇上病房人員在處理遺體:
……(我們)經過四周拉上窗簾的床位:從簾間瞥見病人臉容安詳,只是睡著覺的樣子,他連接著的cardiac monitor還一下一下地顯示著他的維生指數;床邊圍滿了訪客,想必是病人的親屬。在我們眼中,這只是一個療養中的個案,在病房內同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然後我們就沒有多事,徑直向隔鄰的病人問症。其間沒有儀器檢測到讀數異常的響聲,一堆醫生護士趕往病床急救的混亂場景。無聲無息地,無知的我們沒有察覺到身旁一條生命的消逝。
三個職員邊閒談邊推著「病床」進來……我們趕忙讓開。但這張「病床」非常特別,上面沒有床鋪,兩側也沒有床欄;只是一塊下面裝了輪子的鐵板。
我還在納悶之際,職員走到窗簾仍然合上的病床前叫喚:「我們幫你過床了。」
我們在外面沒聽到病人的回應,只聽有一下拉鏈拉上的聲音。我們面面相覷。
那三個職員在一下子就抬起了銀色的大袋子,移到鐵板上。這大袋子我們熟悉不過,因為在兩年前的解剖課上,我們每星期就要打開這袋子的拉鏈一次,所以再見到它,也會對其背後的意義毫不陌生。話雖如此,在解剖室以外看見它,也會心生怪異的感覺。搬好身體後,職員升起鐵板三邊的圍板,變成一個可移送的盒狀車子,再在談笑間推走車子離開。
作者接著想:
醫學診斷是一門靠結果推斷起因的藝術;而如果我要就剛才的死神到訪事件推測前因後果,我猜測病人生前應該簽訂了DNACPR(不作心肺復甦術),所以才可有機會在醫院靜靜地離世。相比起其他病人去世前,仍要接受重複的胸口按壓,留下一大片瘀傷,這樣好好死去也是一種幸福。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