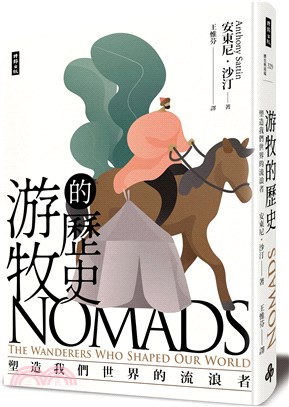游牧的歷史:塑造我們世界的流浪者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紐約時報》《泰晤士報》專文推薦
「游牧民族沒有歷史,他們只有地理。」
──德勒茲(Gilles Deleuze),法國哲學家
游牧民族,這個詞貫穿了人類的故事。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個詞充滿浪漫的懷舊情懷,但很多時候,它帶有一種含蓄的判斷,意指流浪者、漂泊者、移民者、逃亡者、居無定所的人,或是無家可歸的人。他們都是不為人知的人。
在這個愈來愈多人旅行的時代,有許多人都曾有過這種「不為人知」的異地經驗,我們需要認識那些過著移動生活之人的歷史,因為少了這些,就無法理解人類的流浪旅程是如何塑造我們現在的樣貌。
本書追溯移居者和定居者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將他們多樣分歧的非凡故事聯繫起來。這些故事發生在世界上一些最極端的景觀中,時間序列跨越一萬兩千年,從新石器革命到21世紀,從羅馬帝國的強盛到衰亡、阿拉伯與蒙古的偉大游牧帝國,再到蒙兀兒帝國,以及絲路的發展,游牧族群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
游牧民族的歷史常遭到蔑視與拋棄,因為那些和城牆、紀念碑一起生活的人,以及寫下大部分歷史的人,未能體認和找到那些生活在界限之外,過著較為雜亂無章之人的生命中,更為輕盈和流動的意義或價值。我們需要留下更輕盈的腳步,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與世界產生連結,超越城市的界線,在我們了解自己是誰、可以成為什麼之前,需要知道我們曾經是誰。
這本書能幫助讀者理解,我們和游牧民族之間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也不是定居或移居的問題,無論我們是否承認,無論喜歡與否,游牧民族至少占了人類歷史的一半,並為許多歷史學家傳統上稱之為文明的進展,做出重要貢獻。
作者簡介
安東尼‧沙汀(Anthony Sattin)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成員、新聞記者、播音員,也是備受讚譽的歷史與旅行書籍作家,現在倫敦與中東兩地生活。
譯者簡介
王惟芬
臺大動物系、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科技醫療史碩士。日前在巴黎半工半讀,一邊於索邦法式文明課程修習法文,一邊翻譯寫作,偶爾還兼中文家教。曾經謀生處:中研院動物所與生物多樣性中心、葉子咖啡店、總統府、臺大海洋所與臺大醫學院。譯著以科普、科學史、藝術史、環境科學及傳記文學為主。
目次
序言:在伊朗扎格羅斯山脈
第一部:平衡的行動
第二部:帝國的行動
第三部:恢復的行動
謝辭
著作版權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一個年輕人向我走來,肩上扛著一根棍子,腳下跟著一群羊。羊群分散在他前方、旁邊和身後,就像附近溪流中的融水一樣亂竄,牠們像一群吵鬧的孩子,在團團簇擁下把少年擠到小路。在他身後跟著一個年長的男人,左肩掛著一支步槍,這個老男人雖然飽經風霜,但仍然很健壯。他咂舌鼓動,要羊群繼續前進。在他後頭有兩個騎驢的女人,一個比另一個年長,我猜她們是他的妻子和女兒。她們看起來很堅強,但在扎格羅斯山脈的碎片山峰下,生活可是相當艱難。其他驢子則背負著他們的財物,這些都包在婦女編織的銹褐色厚重布包裡,當帳篷搭好後,這些布包很快就會有新用途,可以當作門襟。
在這個海拔高度,樹木稀少,但雪已經融化,山谷中迸放著目不暇給的美麗,鳶尾花、侏儒鬱金香和其他春季時節的花朵覆蓋著上好的牧草。這家人一邊笑著一邊趕羊,帶著他們的綿羊和灰白相間的山羊沿著遍布岩石的小徑向我走來,公羊頂起牠們雄偉的後掠角。我也和他們一起微笑起來,想到巴赫蒂亞里(Bakhtiari)部落每年會從平原遷移到山區,尋找夏季牧場,就讓我興奮不已。
我已經花了幾天時間照顧其他一些移民。西亞維希(Siyavash)和他的家人在山谷的斜坡上用黑色的山羊毛搭起帳篷,並為他們的羊群搭建一個圍欄,還準備一個大型的開放式帳篷來接待鄰居和客人。我的帳篷搭在對岸,跟他隔著一條由融冰沖刷出來的小溪,從那裡我可以看到一片大景,白雪覆蓋的山峰,鋸齒狀地深入天際,還有遍布野花的山谷。我撿來一段寬大的扁平油管,充當我和游牧民族間的橋樑,這座便橋也讓我想起在中東地區第一次石油開採,一號井就是在巴赫蒂亞里附近開挖,是在一九○八年的時候。
這裡美景處處。如果我是一名攝影師,我會去捕捉午後移動的陰影和傾斜的陽光,它們將雪山染成一片粉紅色,並在溪流表面投下燦爛的金光。如果我是一位作曲家,我會把隆隆水聲與流經河床石塊的撞擊聲、蜜蜂的嗡嗡聲、鈴鐺的叮噹聲,以及夜間招呼羊群的哨聲和呼喊聲調融合譜曲。美存在於這裡的一切。但我只是位光著腳曬得有點黝黑的作家,我掏出一支鉛筆來記錄藍天中純粹的光質,呈色的方式,尤其是乍現在綠色山谷中的黃色,以及在太陽下山後突然降臨的寒意。那天深夜,游牧民族的帳篷在河對岸發著光,宛如餘燼,月光則在山脊上照耀著,我一邊準備入睡,一邊想著當初拜倫是怎麼知道「早期波斯人沒有白費/他的祭壇是高地和山峰⋯⋯在那裡尋求精神⋯⋯」在那高處,我的精神高漲,感到深深的喜悅。
在接下來的幾天,西亞維希和他的家人向我介紹他們的山谷和人民。他們還供我餐點,我們吃飯的時候,他們談論他們的生活、他們認識的土地、他們穿越這片土地的旅程、他們飼養的動物、他們擔心的孩子——該把他們送到州立寄宿學校接受教育嗎?——還有許多在二十一世紀要在扎格羅斯山脈過著游牧生活所面臨的其他挑戰。他們告訴我,山谷裡的植物、在我們頭頂上掠過的猛禽,以及那些生活在山坡更高處的其他動物。他們認識在那裡可以生長的一切,知道該鼓動什麼,害怕什麼。他們談到從炎熱的低地進入山區的旅程,以及當他們腳下的土地開始結冰時又要如何再度走回去,這是他們的祖先在過去走過的旅程,早在有人開始記錄之前很久就已經有的路徑。我從北非和中東的貝都因人(Bedouin)和柏柏爾人(Berbers)那裡也聽過類似的故事,我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那裡度過,從廷巴克圖(Timbuktu)的泥房和圖書館外的圖阿雷格人(Tuareg)和沃達貝人(Wodaabe)那裡,從東非紅色灌木叢中宛如橙色閃光穿梭而過的敏捷年輕馬賽人(Maasai)那裡,從印度塔爾沙漠(Thar Desert)邊緣的游牧民族那裡,從安達曼海的船隻,在吉爾吉斯斯坦的高地,還有亞洲其他地方。無論是柏柏爾人、貝都因人、高喬人(gaucho)還是莫肯人(Moken),他們的言談似乎總是圍繞著同樣的主題,不外乎是傳承、驕傲的歸屬感、與周圍環境的和諧相處、尊重大自然提供的一切,以及政府希望他們這些游牧生活者定居下來時所遭遇的種種困難。
這些人全都讓我聯想到一份崇高的和諧感,是與自然世界並存的那種和諧。他們是透過與自然萬物平等生活來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而不是透過治理掌控,這是基於一份認知,體認到人類生活仰賴我們的環境,而這一點是我們這些生活在城鎮和都市中的人很容易忘記的。巴赫蒂亞里人聽得懂他們牛群的叫聲,理解當中每個音調的意義,知道牠們何時吃飽喝足、飢餓或受到威脅,也聽得出何時會有生離死別的降臨,就像他們知道要如何解讀雲層,翻譯風中攜帶的氣味一樣。這樣的事蹟我聽聞的越多,就越發體會到我們曾經都過著這樣的生活——而且就在不久前,在宏大的人類歷史框架中。
一個家庭帶著他們的牲畜和所有財物搬家,這樣的景象讓我們當中的一些人興奮不已,但也會讓另一些人感到恐懼、厭惡或蔑視。
他們從哪裡來?
他們為什麼來這裡?
他們什麼時候要離去?
他們如何生存?
他們是誰?
游牧民族(Nomad)。這個詞的根源貫穿了人類故事,從我們身處的時代可以一路回溯到非常早期的印歐文字「nomos」。這個字彙具有多種含義,可以翻譯為「固定或有界限的區域」,也可以翻譯成「牧場」。從這個字根衍生出「nomas」,意思是「一個流浪的放牧部落的成員」,並隱含「在尋找牧場的人」的意味,不過也包含「一個有合法權利放牧的地方」,而這些包含有游牧的、定居的,以及搬出去定居的。後來,這個字根分裂,隨著人類開始建立城鎮,有更多的人定居下來,最後成為「nomad」這個單字,用來形容一批生活在沒有圍牆,界限之外的人。定居者現在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使用「nomad/游牧民族」一詞。對於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來說,這個詞充滿浪漫的懷舊感,但很多時候,它帶有一種含蓄的判斷,這是指流浪者、漂泊者、移民、居無定所的人、逃亡者,以及無家可歸的人。他們是不為人知的人。
在這個有越來越多人旅行的時代,我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曾有過這樣一種「不為人知」的異地經驗,「nomad」這個字彙顯然需要更為寬廣慷慨的解釋,尤其是在我們目前所談論的,所提出的想法,以及各種小工具和商品中,有許多都與流動性和移動有關。正因為如此,隨著本書的進展,在我筆下「游牧民族/nomad」的意涵也會發生演變。在本書的開端,我是用它來代表狩獵採集者,但很快也包含那些為尋找牧場而放牧的人。到了最後,它還包括所有流浪漂泊的人。不僅是因為這些人就像游牧民族一樣,被迫過著輕盈不著痕跡的生活,也還有那些刻意選擇過這種生活的人,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描述自己時不再使用「無家可歸」(homeless)一詞,而是「居無定所」(houseless),許多現代游牧民族生活在他們所謂的「車輪莊園」(wheel estate)中。作家布魯斯・查特溫(Bruce Chatwin)在他原創十足的小說《歌之版圖》(The Songlines)中可說是側寫了這種生活方式的早期版本,書中描述一位英國推銷員如何只靠著一只手提箱在非洲飛行,度過他的生活。在推銷員生活中,唯一的固定點,一個代表他家的地方,就是在倫敦的一個上鎖的行李櫃。在行李櫃裡放有一個紙箱,裡面裝滿了他的家人和他過去的照片和其他紀念品。如果他想再增加一些新的寶物,他需要丟棄舊的才能騰出空間。在查特溫和我看來,這位四處旅行的推銷員的生活型態,散發出一種非常現代的游牧形式。
推銷員沒有給世界增加任何東西,就像他沒有給他的盒子增加任何東西一樣,這點讓人很輕易地對推銷員產生蔑視。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大多數游牧民族的歷史一直遭到蔑視和拋棄——因為那些和牆壁、紀念碑一起生活的人,以及寫下大部分歷史的人,未能體認和找到那些生活在界限之外,那些過著較為雜亂無章的人的生命中,更為輕盈和流動的意義或價值。我們現在正活在一個由理性時代和啟蒙運動塑造,由工業和技術革命推動的世界——但「我們的」世界腳步正變得步履蹣跚。社會契約正在破裂,社群正在崩解。我們的世界所依賴的原物料和自然資源變得越來越稀少,而我們在地球上的作為與行動所產生的後果,如今在景觀、氣候和我們的生活結構都大量反應出來。除了要開發回收水和發電的新方法外,如今還有一份迫切的需要,需要對我們的生活型態以及身而為人的意義進行新的思考。需要改變。我們需要留下更輕盈的腳步,而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和世界產生連結,超越城市的界線。但在我們了解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可能成為什麼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曾經是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我也是」(#MeToo),以及其他社會運動正在建議我們翻過高牆,超越那些舊的根深柢固的假設、結構和偏見來講述歷史,不僅是以白人男性為主的歷史,還要講述BAME(黑人、亞裔及其他少數族裔)、女性和原住民的歷史。我們現在還需要認識那些過著移動生活的人的歷史,因為少了這些,我們就無法理解人類的流浪旅程是如何塑造出我們現在的樣貌。
本書追溯了移居者和定居者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我將他們多樣分歧的非凡故事聯繫起來。這些故事發生在世界上一些最極端的景觀中,時間序列跨越一萬兩千年。這條線始於我們現在公認的紀念性建築的開端,大約是在公元前九千五百年,結束於我們自己的時代。還有其他方法可以理解這些故事,當然也還有許多其他途徑可以穿越這個時空,但這是我選擇依循的一條,從該隱和亞伯通向今日的你我。故事開始時,全人類生活在一個移動的世界中,唯一的邊界是森林、河流、山脈和沙漠等自然的障礙,以及人類用樹枝和荊棘所打造的人工路障。在本書的結尾,流浪者必須在一個被分割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道路,這世界已然由各種邊界、高速公路和城牆,以及由民族國家制定的國際協議所切割。
這個對流浪生命的挖掘一共分為三個行動。第一個行動讓我們回到早期的歷史,當定居者和游牧者從狩獵採集轉向農業和放牧的生活型態時,他們大多同居和合作。我會描述史上第一批紀念碑的建造,這些建物的規模令人吃驚,而且建造的年代出人意料的古早,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幾條大河、尼羅河和印度河沿岸的那些非凡的城邦和帝國崛起前就已經建造起來,並且提出為什麼早期的定居者對於在他們邊界之外的移動世界──一個曾經屬於他們的世界──備感威脅的原因。
在進入帝國的第二行動中,會聚焦在一種更複雜的游牧形式,並追踪那些仍然過著流動生活的人群所創造的一些偉大帝國的興衰起迭。在西方,這一時期始於羅馬帝國的衰落,通常又稱為黑暗時代。但對於匈奴和阿拉伯人、蒙古人、中國的元朝和許多其他游牧民族來說,無論是在近東還是從現在中國的長城延伸出來,一直到匈牙利的廣闊草原帶,這都是一個充滿輝煌成就的時代。透過十四世紀阿拉伯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等人的記錄和著作,可以看到游牧民族對歐洲文藝復興的貢獻有多大,以及他們對我們現代世界的影響有多深遠。
第三個行動是以現代的誕生為開端,西方學者堅持認為白人必須主宰自然世界,就像他們努力主宰人類世界一樣。在這個競爭和衝突的時代,游牧民族就這樣從歐洲的視野中完全消失,再也看不出其相關性,以至於在英文中的「nomad/游牧民族」一字,因其通行程度太低而無法收錄在英文字典。但這也正是有人感覺到某些重要的東西正在流失,並展開恢復行動的時刻。在這一點上,就跟本書所遭遇的困難一樣,由於缺乏游牧者的史料迫使我們得透過定居者的眼睛來觀察,因此本書最後部分的大半內容,追溯的是定居者對游牧者的反應。接著最為關鍵的一點,世人逐漸體認到合作比競爭更有價值,游牧者對我們這些定居者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正如同他們對我們了解自身的重要性一樣。
這些故事是經過多年的研究和討論而積累出來的,儘管這是一部歷史敘述,但它不是學術著作,也不是關於游牧民族的權威歷史。我懷疑,對這樣一批生活得如此輕盈,而且大多數是透過口述傳統來保存他們的故事的人來說,我們永遠不會寫出一部關於他們的明確歷史。相反地,我希望展現出游牧民族長期以來是如何受限於我們作家和歷史,根據軼事和事後思考的方式來呈現,證實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觀察,即「游牧民族沒有歷史,他們只有地理」。這句話可能看似太簡化,但當我第一次讀到時,它確實解釋了我心中的許多懸念,說明為什麼在我們的歷史中很少有關於游牧民族的篇章。這種遺漏有誤導之虞,也意味著我們錯過了許多讓他們非常自豪的寶貴歷史。我希望這本書能達到的一個目標是幫助讀者理解,我們和他們之間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也不是定居或移居的問題,因為無論我們是否承認,無論我們喜歡與否,一直以來游牧民族至少占了人類歷史的一半,並為許多歷史學家傳統上稱之為文明的進展,做出重要貢獻。
儘管我們將他們的故事視為我們故事的陰暗面,但游牧民族的故事,不論是精采程度,還是重要性都不比我們的歷史遜色。例如,在公元前二世紀,就在羅馬共和國擊敗迦太基,主掌地中海後,當中國在漢武帝的統治下蓬勃發展,在黃河和歐洲之間的貿易活動沿著新生的絲路緩慢發展時,匈奴的游牧勢力從滿洲延伸到哈薩克斯坦,包括西伯利亞、蒙古和現在中國新疆省的部分地區。與此同時,史基泰(Scythian)游牧民族及其盟友,在哈薩克斯坦控制了黑海和阿爾泰山脈之間的大部分土地。總體來說,這些游牧民族的領土比羅馬帝國或漢帝國都來得大,而且也更為強大。這與一般普遍認為這些移居者是原始而孤立的說法大相徑庭,我們從墓葬文物中得知,他們的領袖身著飾有獵豹皮毛的中國絲綢長袍,坐在波斯地毯上,使用羅馬玻璃,並且十分鍾愛希臘的金銀珠寶。所有這些都彰顯出一個可能性,即這些游牧民族主宰著從東海延伸到大西洋的這個相互連結的貿易世界。
這不是西方對通常被稱為羅馬或漢朝世界的傳統看法,就像西方歷史傾向於聚焦在蒙古可汗所殺的人數,而不是和平的蒙古人(pax Mongoliana)所造就的進步和他們所取得的優勢一樣。
游牧故事中另一個常被忽視的層面是人類與自然世界間不斷變化的關係。這些關係因為城市的發展、農業發展,以及晚近的工業化和科技進步而轉型。這些變化使得許多定居者日益遠離周遭的自然環境,但游牧民族則繼續培養他們與自然世界的關係。他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做——他們也不得不如此——因為他們早已體認到,一切都是相互關聯,萬物都是相互依存。他們知道關心周圍的環境符合他們的利益…(摘自序言)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