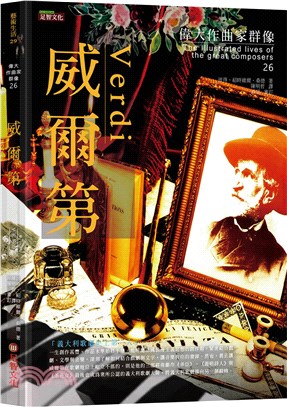偉大作曲家群像26:威爾第
商品資訊
系列名:藝術生活
ISBN13:9789865569822
出版社: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作者:彼得.紹時維爾.桑德
譯者:陳明哲
出版日:2022/12/09
裝訂/頁數:平裝/210頁
規格:24.5cm*17.5cm*1.5cm (高/寬/厚)
重量:536克
版次:1
定價
:NT$ 380 元優惠價
:
90 折 342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0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飛吧!讓思念乘著歌聲的翅膀。」――威爾第《那布果》
朱瑟培‧威爾第是旅店經理之子,誕生於義大利,從小就展露出對音樂的喜愛。他的正規教育在十四歲那年因超齡被米蘭音樂院拒收之後,便告終止;但他一生的音樂創作仍能明顯的反映時代異動與社會變遷。早期作品反應出社會運動與民主思潮,他的第三部歌劇《那布果》,創作之初只因對其中一段文句特別心有所感︰「飛吧!讓思念乘著歌聲的翅膀」,演出之後竟然讓長期飽受奧國虐政的義大利同胞發自內心的認同與壓抑許久的情感得以釋放。這股民主思潮也一發不可收拾,從此全義大利人民對威爾第的期待除情緒的宣洩外,也暗藏民主運動的傳播。
威爾第被許為義大利歌劇史上的第一人,一生創作甚豐,作品水準始終不墜。他呼應法國浪漫主義思想的創作期,緊密結合戲劇、文學與音樂,深刻了解如何結合戲劇與文字,讓音樂自由的發揮。然而,真正讓威爾第在歌劇地位上屹立不搖的,則是他的三部經典劇作──《弄臣》、《遊唱詩人》與《茶花女》。尤其是他最受世人鍾愛的《茶花女》,就連原作家小仲馬看過之後也說:「或許五十年後,沒有人記得我的小說,但威爾第卻讓她變成不朽」。後來也成為眾所公認的義大利歌劇大師,將義大利歌劇推向另一個巔峰。除了歌劇以外,威爾第的《安魂彌撒曲》,也被認為是偉大的聖詠管弦樂傑作之一,可與莫札特的《安魂曲》及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互相媲美。
可是對他的同胞而言,威爾第在統一義大利的復興運動中,是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重要人物。在這本書裏,作者描寫了威爾第一生中幾個擾攘不安的時期,闡述它們如何影響了他的音樂。文中穿插當時的油畫、蝕雕作品和照片多幀,還有複製的樂譜手稿、舞台和服裝設計圖樣,以及宣傳威爾第歌劇首演的傳單,是一本專為經常上歌劇院欣賞歌劇的愛樂者和學生們所編的精彩傳記。
朱瑟培‧威爾第是旅店經理之子,誕生於義大利,從小就展露出對音樂的喜愛。他的正規教育在十四歲那年因超齡被米蘭音樂院拒收之後,便告終止;但他一生的音樂創作仍能明顯的反映時代異動與社會變遷。早期作品反應出社會運動與民主思潮,他的第三部歌劇《那布果》,創作之初只因對其中一段文句特別心有所感︰「飛吧!讓思念乘著歌聲的翅膀」,演出之後竟然讓長期飽受奧國虐政的義大利同胞發自內心的認同與壓抑許久的情感得以釋放。這股民主思潮也一發不可收拾,從此全義大利人民對威爾第的期待除情緒的宣洩外,也暗藏民主運動的傳播。
威爾第被許為義大利歌劇史上的第一人,一生創作甚豐,作品水準始終不墜。他呼應法國浪漫主義思想的創作期,緊密結合戲劇、文學與音樂,深刻了解如何結合戲劇與文字,讓音樂自由的發揮。然而,真正讓威爾第在歌劇地位上屹立不搖的,則是他的三部經典劇作──《弄臣》、《遊唱詩人》與《茶花女》。尤其是他最受世人鍾愛的《茶花女》,就連原作家小仲馬看過之後也說:「或許五十年後,沒有人記得我的小說,但威爾第卻讓她變成不朽」。後來也成為眾所公認的義大利歌劇大師,將義大利歌劇推向另一個巔峰。除了歌劇以外,威爾第的《安魂彌撒曲》,也被認為是偉大的聖詠管弦樂傑作之一,可與莫札特的《安魂曲》及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互相媲美。
可是對他的同胞而言,威爾第在統一義大利的復興運動中,是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重要人物。在這本書裏,作者描寫了威爾第一生中幾個擾攘不安的時期,闡述它們如何影響了他的音樂。文中穿插當時的油畫、蝕雕作品和照片多幀,還有複製的樂譜手稿、舞台和服裝設計圖樣,以及宣傳威爾第歌劇首演的傳單,是一本專為經常上歌劇院欣賞歌劇的愛樂者和學生們所編的精彩傳記。
作者簡介
彼得.紹時維爾.桑德(Peter Southwell Sander)
出身音樂家庭,曾於劍橋開尤斯學院(Caius College)專攻英國語文,對歌劇的喜愛終生不渝。這是他第一本介紹主要歌劇們家的著作。
出身音樂家庭,曾於劍橋開尤斯學院(Caius College)專攻英國語文,對歌劇的喜愛終生不渝。這是他第一本介紹主要歌劇們家的著作。
序
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
導讀
飛吧!讓思念乘著歌聲的翅膀
在1820年代末期,巴黎成為浪漫主義運動的重要戰場,在戲劇與歌劇的創作上,一種新的戲劇性語言及新型態的角色人物塑造正逐漸形成中。……
1827年,戲劇史上最偉大的莎士比亞演員之一,查爾斯‧坎博(Charles Komble)在巴黎演出造成轟動。他讓巴黎重新認識戲劇角色裏蘊藏的強力心理衝擊,與發揮出來無與倫比的感染力。也在這年,一向推崇莎士比亞的雨果在《克倫威爾》新書出版的序文中,提出對浪漫主義的宣言,他認為法國的新古典戲劇作品裏,角色的塑造缺乏觀眾認識的人性,因此應多加入正反、善惡的對比性;於是克倫威爾除了英雄氣質的描寫外,多了詼諧的一面;他同時極力主張廢除只為效果而寫的誇飾演說與台詞。1829年,法文版的《奧泰羅》搬上巴黎舞台,羅西尼難得譜寫的一部嚴肅歌劇《威廉泰爾》也在巴黎歌劇院上演。1830年,雨果的《艾納尼》(Hernani)在法蘭西喜劇院上演,這齣描寫一個熱情的罪犯、一個冷酷老頭兒和國王查理五世一起追求一個妓女的故事,在連環套的劇情安排下,贏得滿堂采,也換來當局的「特別關注」。……
1840年,義大利作曲家董尼才悌、白利尼、梅爾卡丹特(S. Mercadante),威爾第等人爭相仿效雨果所帶動的浪漫主義創作風格,類似《艾納尼》的交叉式劇情,串串套結隨著歌曲一首首的發展,不到高潮的結局看不出結果。音樂與戲劇緊密的結合(dramma per musica),並大玩心理遊戲,已不是華格納的「樂劇」形式所能涵蓋。
十九世紀前半葉的義大利是受法、奧皇室控制的分裂城邦封國,法國的民主運動、文化發展對她一直有相當的影響力。不僅高階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緊跟著法國的流行風潮,就連市井小民,如沒見過多少世面的威爾第父親,都懂得跑到鄰近大城給威爾第登記一個法國名字。這,就是出生於1813年的威爾第成長的大環境。
威爾第的正規教育在十四歲那年因超齡被米蘭音樂院拒收之後,便告終止;但他一生的音樂創作仍能明顯的反映時代異動與社會變遷。1840年至1850年的早期作品反應出社會運動與民主思潮,他的第三部歌劇(也是第一次引起廣大迴響的)《那布果》,創作之初只因對其中一段文句特別心有所感︰「飛吧!讓思念乘著歌聲的翅膀」,演出之後竟讓飽受奧國虐政的義大利同胞發自內心的認同與壓抑許久的情感得以釋放。這股民主思潮一發不可收拾,從此全義大利人民對威爾第的期待除情緒的宣洩外,也暗藏民主運動的傳播。接下來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倫巴底人》、《兩個佛斯卡里》、《貞德》、《馬克白》等都是愛國的威爾第藉異國故事談政治迫害與政爭。威爾第在這十年間名利雙收,卻是他口中的「船奴般的歲月」。有著還不完的稿債與人情,幾乎每六個月到一年便得交出一件歌劇作品。最後落得醫生開出「不得再寫曲子」的處方,各界歌劇經紀人、譜商才罷休。
第二個十年,1850年至1860年代,是威爾第呼應法國浪漫主義思想的創作期,緊密結合戲劇、文學與音樂,也是作曲技巧臻於成熟的時期。這段時間裏他只為自已喜好的作品寫音樂,從與當代文學作家、劇作家們的通信中發現,威爾第的確深讀不少文學與戲劇作品,他深刻的了解如何結合戲劇與文字,讓音樂自由的發揮。這十年中的作品至今仍上演不輟︰《丑角》、《遊唱詩人》、《荼花女》、《假面舞會》、《命運之力》等;然而這些歌劇竟不約而同是「謀殺」、「死亡」、「復仇」等的晦暗主題,或許仍與威爾第心繫當時義大利到處發生的流血獨立運動有關。
從1862年的《命運之力量》後,威爾第刻意規避所有與音樂有關的事,除不准朋友提到創作,就連家中鋼琴也故意以走音破壞。從此時到1901年去世前,威爾第的興趣在務農和積極入世的從事慈善事業(如對地方建設的回饋、晚年蓋醫院、籌建音樂家退休後之收養院),後期的幾齣歌劇都是在「不經意」間寫下的,有向自己、向前輦羅西尼挑戰的《奧泰羅》,有為愉悅自己而寫下的《法斯塔夫》,當然也對過去幾件作品做修訂。
在十九世紀封建時代,要從低下的窮苦人家逐漸成就自我,到晚年成為舉足輕重,並為義大利全國人民所景仰,實非易事,威爾第終其一生以人道關懷,正直誠懇待人,他所成就的不只是個音樂家,還是一個偉大人物。莎士比亞是他心中的神,在創作歌劇時,常惦記莎翁劇作的精髓;文學作家曼佐尼是他心底的聖人,對人誠懇對事敬業,是聖人給他的典範;而他的敵人是偽善、平庸、自負與僧侶!威爾第也絕不是完人,他對歌手要求嚴苛、不假言辭,對樂譜商不吝辭色──甚至比商人更計較錙銖;但,他仍是個可敬的人。
傳記的寫法很多種,在歌劇作曲家傳記中較常見的兩種,一是按歌劇劇目的風格演變依年代探訪;二為編年曆的方式談音樂家生平。前者提供充分的音樂資訊,較權威的音樂理論及對音樂家系統性的認識;後者側重「人」的本質,從平凡認識作曲家,也順道淺嚐樂曲風格的成形背景。彼得‧紹時維爾─桑德(Peter Southwell-SandSander)的《威爾第》著筆手法屬於後者,提供愛樂者以最有效、最吸引人的方式了解威爾第和他的時代背景,藉由各地方名人到義大利及法奧的遊記柬段,讓讀者神遊十九世紀的義大利古城、感受法國七月革命的巷戰,也摘錄威爾第的書簡,讓讀者從威爾第的親筆文中認識威爾第真摯的人性與音樂創作觀。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音樂系、伊利諾大學戲劇系雙博士
邱瑗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
導讀
飛吧!讓思念乘著歌聲的翅膀
在1820年代末期,巴黎成為浪漫主義運動的重要戰場,在戲劇與歌劇的創作上,一種新的戲劇性語言及新型態的角色人物塑造正逐漸形成中。……
1827年,戲劇史上最偉大的莎士比亞演員之一,查爾斯‧坎博(Charles Komble)在巴黎演出造成轟動。他讓巴黎重新認識戲劇角色裏蘊藏的強力心理衝擊,與發揮出來無與倫比的感染力。也在這年,一向推崇莎士比亞的雨果在《克倫威爾》新書出版的序文中,提出對浪漫主義的宣言,他認為法國的新古典戲劇作品裏,角色的塑造缺乏觀眾認識的人性,因此應多加入正反、善惡的對比性;於是克倫威爾除了英雄氣質的描寫外,多了詼諧的一面;他同時極力主張廢除只為效果而寫的誇飾演說與台詞。1829年,法文版的《奧泰羅》搬上巴黎舞台,羅西尼難得譜寫的一部嚴肅歌劇《威廉泰爾》也在巴黎歌劇院上演。1830年,雨果的《艾納尼》(Hernani)在法蘭西喜劇院上演,這齣描寫一個熱情的罪犯、一個冷酷老頭兒和國王查理五世一起追求一個妓女的故事,在連環套的劇情安排下,贏得滿堂采,也換來當局的「特別關注」。……
1840年,義大利作曲家董尼才悌、白利尼、梅爾卡丹特(S. Mercadante),威爾第等人爭相仿效雨果所帶動的浪漫主義創作風格,類似《艾納尼》的交叉式劇情,串串套結隨著歌曲一首首的發展,不到高潮的結局看不出結果。音樂與戲劇緊密的結合(dramma per musica),並大玩心理遊戲,已不是華格納的「樂劇」形式所能涵蓋。
十九世紀前半葉的義大利是受法、奧皇室控制的分裂城邦封國,法國的民主運動、文化發展對她一直有相當的影響力。不僅高階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緊跟著法國的流行風潮,就連市井小民,如沒見過多少世面的威爾第父親,都懂得跑到鄰近大城給威爾第登記一個法國名字。這,就是出生於1813年的威爾第成長的大環境。
威爾第的正規教育在十四歲那年因超齡被米蘭音樂院拒收之後,便告終止;但他一生的音樂創作仍能明顯的反映時代異動與社會變遷。1840年至1850年的早期作品反應出社會運動與民主思潮,他的第三部歌劇(也是第一次引起廣大迴響的)《那布果》,創作之初只因對其中一段文句特別心有所感︰「飛吧!讓思念乘著歌聲的翅膀」,演出之後竟讓飽受奧國虐政的義大利同胞發自內心的認同與壓抑許久的情感得以釋放。這股民主思潮一發不可收拾,從此全義大利人民對威爾第的期待除情緒的宣洩外,也暗藏民主運動的傳播。接下來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倫巴底人》、《兩個佛斯卡里》、《貞德》、《馬克白》等都是愛國的威爾第藉異國故事談政治迫害與政爭。威爾第在這十年間名利雙收,卻是他口中的「船奴般的歲月」。有著還不完的稿債與人情,幾乎每六個月到一年便得交出一件歌劇作品。最後落得醫生開出「不得再寫曲子」的處方,各界歌劇經紀人、譜商才罷休。
第二個十年,1850年至1860年代,是威爾第呼應法國浪漫主義思想的創作期,緊密結合戲劇、文學與音樂,也是作曲技巧臻於成熟的時期。這段時間裏他只為自已喜好的作品寫音樂,從與當代文學作家、劇作家們的通信中發現,威爾第的確深讀不少文學與戲劇作品,他深刻的了解如何結合戲劇與文字,讓音樂自由的發揮。這十年中的作品至今仍上演不輟︰《丑角》、《遊唱詩人》、《荼花女》、《假面舞會》、《命運之力》等;然而這些歌劇竟不約而同是「謀殺」、「死亡」、「復仇」等的晦暗主題,或許仍與威爾第心繫當時義大利到處發生的流血獨立運動有關。
從1862年的《命運之力量》後,威爾第刻意規避所有與音樂有關的事,除不准朋友提到創作,就連家中鋼琴也故意以走音破壞。從此時到1901年去世前,威爾第的興趣在務農和積極入世的從事慈善事業(如對地方建設的回饋、晚年蓋醫院、籌建音樂家退休後之收養院),後期的幾齣歌劇都是在「不經意」間寫下的,有向自己、向前輦羅西尼挑戰的《奧泰羅》,有為愉悅自己而寫下的《法斯塔夫》,當然也對過去幾件作品做修訂。
在十九世紀封建時代,要從低下的窮苦人家逐漸成就自我,到晚年成為舉足輕重,並為義大利全國人民所景仰,實非易事,威爾第終其一生以人道關懷,正直誠懇待人,他所成就的不只是個音樂家,還是一個偉大人物。莎士比亞是他心中的神,在創作歌劇時,常惦記莎翁劇作的精髓;文學作家曼佐尼是他心底的聖人,對人誠懇對事敬業,是聖人給他的典範;而他的敵人是偽善、平庸、自負與僧侶!威爾第也絕不是完人,他對歌手要求嚴苛、不假言辭,對樂譜商不吝辭色──甚至比商人更計較錙銖;但,他仍是個可敬的人。
傳記的寫法很多種,在歌劇作曲家傳記中較常見的兩種,一是按歌劇劇目的風格演變依年代探訪;二為編年曆的方式談音樂家生平。前者提供充分的音樂資訊,較權威的音樂理論及對音樂家系統性的認識;後者側重「人」的本質,從平凡認識作曲家,也順道淺嚐樂曲風格的成形背景。彼得‧紹時維爾─桑德(Peter Southwell-SandSander)的《威爾第》著筆手法屬於後者,提供愛樂者以最有效、最吸引人的方式了解威爾第和他的時代背景,藉由各地方名人到義大利及法奧的遊記柬段,讓讀者神遊十九世紀的義大利古城、感受法國七月革命的巷戰,也摘錄威爾第的書簡,讓讀者從威爾第的親筆文中認識威爾第真摯的人性與音樂創作觀。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音樂系、伊利諾大學戲劇系雙博士
邱瑗
目次
前言
原著致謝詞
總序
導讀 飛吧!讓思念乘著歌聲的翅膀
1. 崛起
2. 功成名就
3. 關鍵時期
4. 「船奴般的歲月」
5. 寫悲劇連連大捷
6. 義大利萬歲!
7. 命運之力量
8. 公共的榮耀與私人的悲苦
9. 兩部經典之作
10. 安魂曲
譯名對照表
原著致謝詞
總序
導讀 飛吧!讓思念乘著歌聲的翅膀
1. 崛起
2. 功成名就
3. 關鍵時期
4. 「船奴般的歲月」
5. 寫悲劇連連大捷
6. 義大利萬歲!
7. 命運之力量
8. 公共的榮耀與私人的悲苦
9. 兩部經典之作
10. 安魂曲
譯名對照表
書摘/試閱
1 崛起
「藝術是宇宙性的……
其創作卻是出於個人之手」
――威爾第
西元1857年,正當歌劇《遊唱詩人》(Il trovatore)和《荼花女》(La traviata)在義大利首演之後不過五年光景,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的一位記者羅素(W. H. Russell)被派到印度去採訪暴亂的新聞,走訪了英國文官眷屬避暑的辛姆拉(Simla)和其他幾個山村度假據點。他發現「許多英國式的洋房在大門上漆著充滿懷鄉情調的名字,像『拉奔罕小屋』(Laburnham Lodge)、『展望』(Prospect)、『榆木之居』(The Elms)等等。從它們敞開的窗戶流瀉出鋼琴和歌曲的聲音,顯示《荼花女》的音樂已經流傳到了此間,而《遊唱詩人》的樂譜更可以在此地的每個音樂書攤上買得到。」從這一則報導,便可窺見威爾第這兩齣最成功的歌劇,是如何地在短短幾年間聞名遐邇。
然而在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裡,英國學術界和評論界並未加入喜愛這兩齣歌劇的狂熱裡。他們幾乎眾口同聲,只對威爾第的《奧泰羅》(Otello)和《法斯塔夫》(Falstaff)的成就給予肯定,而認為演出他的另外四、五部歌劇,只不過可以賺錢罷了。「聽歌劇的人,多半沒有什麼音樂素養。」胡伯‧派律(Huber Parry)爵士傲慢地說。他和整個英國音樂界都認為,與居於全世界主流地位的德國音樂──尤其是德國歌劇──相比,義大利音樂自羅西尼(Rossini)到浦契尼(Puccini)一脈,不過是一股微不足道的逆流罷了。
這和十七、十入世紀的情勢簡直有天壤之別。當時義大利音樂席捲全歐,莫札特(Mozart)和海頓(Haydn)都發現,他們在爭取音樂總監一職時,多少都遭遇到一些困難,因為幾乎每一個歐洲王室都希望聘請一位義大利「樂長」(Kapellmeister);他們都曾經被要求寫作「義大利式」歌劇;而且也都覺得,前往義大利遊學是他們音樂學習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儘管海頓和貝多芬(Beethoven)一樣,始終末能達成這個心願。
由於義大利音樂到了威爾第時代已不再有那麼顯赫的地位,所以他必須從自己的本鄉本土崛起,以贏得實至名歸的世界性地位。對義大利人而言,他一直是眾所公認的「大師」(II Maestro),因為他的音樂不只是能夠激起國人心靈深處的共嗚,同時也表達了大家對「復興運動」(Risorgimento,這個運動的宗旨,是要建立一個自由團結的義大利)的期望。同時代的義大利人都知道,威爾第和他的音樂不是只屬於義大利,不過他在義大利音樂和歷史上的地位卻是非常重要。在他誕生一百週年的1913年,也是他逝世後的第十二年,「義大利披濟報」(Italo Pizzi)寫道︰
朱瑟培,威爾第(Giuseppe Verdi)是整個義大利的一部分,也是全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用曼佐尼(Manzoni)讚美荷馬(Homer)的話來形容他︰「他的音樂除蒼穹之外,別無故鄉。」
然而這位「義大利歌劇宗匠」的出身卻十分寒微。他的家鄉是義大利北部隆可列(Le Roncole)地方的一個小村落,出生地是一間簡陋的客棧。這家客棧的地板和天花板都是用粗糙的木料鋪成,一片斜長的屋頂直拉下來,連帶蓋住了側面的一圈馬廄;牆上開著窗,從木板釘成的窗櫺望出去,是單調平坦的帕瑪平原(Parma)。這棟建築現今仍舊存在,並由義大利政府設置為國家古蹟,加以保護。
威爾第在晚年曾經寫道︰「天哪!出生於窮鄉僻壤的貧苦人家,我根本無從接受教育。他們張羅了一架殘破的立式鋼琴,擺在我的雙手下,過了不久後,我就開始寫下音符……,一個接著一個的音符……,我就是這樣開始作曲的。」早期的傳記作家顯然受到這段敘述的影響,都說威爾第的父母是不識字的貧農。事實上,他的雙親都是小地主、旅店店東和雜貨店家庭出身,嚴格說都不能算是農民。晚近的研究更發現,威爾第的父親卡羅(Carlo Verdi)曾經在隆可列的聖‧米凱雷‧阿堪傑羅(St Michele Arcangelo),當了十五年的財務卿,因此他根本不可能是文盲。他們家族在聖阿葛塔(Sant' Agata)居住了六代之久;到了卡羅的父親,也就是威爾第的祖父這一代,才搬到隆可列。卡羅在這裡出生,並且經營一家鄉村旅店。
卡羅在1805年1月3日和皮雅成查(Piacenza)一位酒店主人的女兒露基亞‧烏提尼(Luigia Uttini)結婚。1813年10月10日,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朱瑟培‧佛吐尼諾‧法蘭契斯可(Giuseppe Fortunino Francesco)。這一年也是文藝出版上相當重要的一年──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和雪萊(Shelley)的《夢的仙后》(Queen Mab)相繼問世;舒伯特(Schubert)完成了他的第一首交響曲;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在維也納首演;羅西尼的歌劇《唐克雷第》(Tancredi)和《阿爾及利亞的義大利女郎》(L’Italiana in Algeri)也首度演出成功。同時這一年也正處於社會劇變的邊緣,史蒂文生(Stevenson)製造成功的第一具蒸汽火車頭在隔年(1814年)啟用;到了1820年,用鋼鐵打造的蒸汽船和橫渡大西洋的輪船也相繼問世。
威爾第出生次日,便在教區教堂受洗,並用拉丁文登記名字。她母親誤將他的生日記成10月9日,所以他總是在這一天慶生,甚至到六十三歲發現了真相之後,他還是一直將錯就錯。由於拿破崙的軍隊從十九世紀初便占領了義大利北部地區,因此威爾第的父親卡羅還得步行到鄰鎮布瑟托(Busseto),用法文辦理出生登記;上面登載威爾第的法文名字是「約瑟夫‧佛吐尼‧法蘭斯華」(Joseph Fortunin Francois)。
威爾第未滿週歲之前,拿破崙在楓丹白露(Fontainbleau)宣布遜位,奧地利和俄羅斯聯軍也乘勢將法國軍隊逐出義大利。關於威爾第在戰亂期間的遭遇,一向有不少玄奇的軼聞,許多穿鑿附會的說法更是明顯地不真實。不過我們多少有理由相信他的第二任太太向朋友所描述的若干情節,從中可以歸納出至少威爾第本人深信不疑的經過︰當時有若干俄羅斯士兵經過隆可列,一路燒殺擄掠,姦淫婦女;威爾第的母親抱著襁褓中的他躲在教堂鐘樓裡,才得以倖免。除了這位作曲家兒子之外,卡羅和露基亞還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為朱瑟琶‧法蘭契斯卡(Giuseppa Francesca Verdi)。她比威爾第小兩歲半,由於罹患腦膜炎之故而智能不足,在1833年她十七歲的時候,逝世於隆可列。
村裡的聖母教堂(Madonna dei Prati)是對威爾第童年影響最深的地方。但是,感染他的是音樂,而不是天主教的信仰。最後一位為他編寫劇本,同時也是最偉大的劇作家阿里哥‧波伊多(Arrigo Boito),有一段文字描寫威爾第,說「他和我們大家一樣,很早就放棄信仰。但是,終其一生對這件事抱著愧疚,悔恨之情似乎遠甚於我等。」威爾第是由當地的一位修士啟蒙,教他讀書寫字;至於音樂上的啟發,則是受教於村裡的一位管風琴師皮耶妥‧拜斯托洛齊(Pietro Baistrocchi)。他在音樂上顯然很早就展露才華,所以在八歲這一年,他父親便為他買了一架小型古鋼琴(spinet)。這架琴最早的狀況,大概不至於像他後來保存時那麼地「殘破」。這架鋼琴曾經由一位叫做史提法諾‧卡瓦列提(Stefano Cavaletti)的鄰居免費幫忙維修,他說,「看著小小年紀的威爾第耐心地練習彈奏那架鋼琴,我就感到心滿意足。」威爾第一直珍藏著這架琴,如今保存在史卡拉歌劇院博物館(La Scala Musuem)裡。
不久之後,修士與管風琴師相繼過世,朱瑟培‧威爾第也在十歲這年進入設在布瑟托的文科學校(ginnasio)就讀。他寄宿在當地一位補鞋匠家裡,每逢週日和節日便步行三哩路回隆可列在教堂裡司琴,賺取三十六里拉的年薪(十三年後,他拒絕了孟札〔Monza〕地方的一所教堂以八倍年薪聘請他擔任風琴師的機會)。他在往返學校和老家之間的路上,總是把靴子脫下來拎在手上,生怕穿壞。有一回在聖誕節早晨,他不小心掉進路旁積水很深的排水溝裡,幸虧有個農夫正好路過,將他救起,他才免於淪為波臣。
……
「藝術是宇宙性的……
其創作卻是出於個人之手」
――威爾第
西元1857年,正當歌劇《遊唱詩人》(Il trovatore)和《荼花女》(La traviata)在義大利首演之後不過五年光景,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的一位記者羅素(W. H. Russell)被派到印度去採訪暴亂的新聞,走訪了英國文官眷屬避暑的辛姆拉(Simla)和其他幾個山村度假據點。他發現「許多英國式的洋房在大門上漆著充滿懷鄉情調的名字,像『拉奔罕小屋』(Laburnham Lodge)、『展望』(Prospect)、『榆木之居』(The Elms)等等。從它們敞開的窗戶流瀉出鋼琴和歌曲的聲音,顯示《荼花女》的音樂已經流傳到了此間,而《遊唱詩人》的樂譜更可以在此地的每個音樂書攤上買得到。」從這一則報導,便可窺見威爾第這兩齣最成功的歌劇,是如何地在短短幾年間聞名遐邇。
然而在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裡,英國學術界和評論界並未加入喜愛這兩齣歌劇的狂熱裡。他們幾乎眾口同聲,只對威爾第的《奧泰羅》(Otello)和《法斯塔夫》(Falstaff)的成就給予肯定,而認為演出他的另外四、五部歌劇,只不過可以賺錢罷了。「聽歌劇的人,多半沒有什麼音樂素養。」胡伯‧派律(Huber Parry)爵士傲慢地說。他和整個英國音樂界都認為,與居於全世界主流地位的德國音樂──尤其是德國歌劇──相比,義大利音樂自羅西尼(Rossini)到浦契尼(Puccini)一脈,不過是一股微不足道的逆流罷了。
這和十七、十入世紀的情勢簡直有天壤之別。當時義大利音樂席捲全歐,莫札特(Mozart)和海頓(Haydn)都發現,他們在爭取音樂總監一職時,多少都遭遇到一些困難,因為幾乎每一個歐洲王室都希望聘請一位義大利「樂長」(Kapellmeister);他們都曾經被要求寫作「義大利式」歌劇;而且也都覺得,前往義大利遊學是他們音樂學習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儘管海頓和貝多芬(Beethoven)一樣,始終末能達成這個心願。
由於義大利音樂到了威爾第時代已不再有那麼顯赫的地位,所以他必須從自己的本鄉本土崛起,以贏得實至名歸的世界性地位。對義大利人而言,他一直是眾所公認的「大師」(II Maestro),因為他的音樂不只是能夠激起國人心靈深處的共嗚,同時也表達了大家對「復興運動」(Risorgimento,這個運動的宗旨,是要建立一個自由團結的義大利)的期望。同時代的義大利人都知道,威爾第和他的音樂不是只屬於義大利,不過他在義大利音樂和歷史上的地位卻是非常重要。在他誕生一百週年的1913年,也是他逝世後的第十二年,「義大利披濟報」(Italo Pizzi)寫道︰
朱瑟培,威爾第(Giuseppe Verdi)是整個義大利的一部分,也是全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用曼佐尼(Manzoni)讚美荷馬(Homer)的話來形容他︰「他的音樂除蒼穹之外,別無故鄉。」
然而這位「義大利歌劇宗匠」的出身卻十分寒微。他的家鄉是義大利北部隆可列(Le Roncole)地方的一個小村落,出生地是一間簡陋的客棧。這家客棧的地板和天花板都是用粗糙的木料鋪成,一片斜長的屋頂直拉下來,連帶蓋住了側面的一圈馬廄;牆上開著窗,從木板釘成的窗櫺望出去,是單調平坦的帕瑪平原(Parma)。這棟建築現今仍舊存在,並由義大利政府設置為國家古蹟,加以保護。
威爾第在晚年曾經寫道︰「天哪!出生於窮鄉僻壤的貧苦人家,我根本無從接受教育。他們張羅了一架殘破的立式鋼琴,擺在我的雙手下,過了不久後,我就開始寫下音符……,一個接著一個的音符……,我就是這樣開始作曲的。」早期的傳記作家顯然受到這段敘述的影響,都說威爾第的父母是不識字的貧農。事實上,他的雙親都是小地主、旅店店東和雜貨店家庭出身,嚴格說都不能算是農民。晚近的研究更發現,威爾第的父親卡羅(Carlo Verdi)曾經在隆可列的聖‧米凱雷‧阿堪傑羅(St Michele Arcangelo),當了十五年的財務卿,因此他根本不可能是文盲。他們家族在聖阿葛塔(Sant' Agata)居住了六代之久;到了卡羅的父親,也就是威爾第的祖父這一代,才搬到隆可列。卡羅在這裡出生,並且經營一家鄉村旅店。
卡羅在1805年1月3日和皮雅成查(Piacenza)一位酒店主人的女兒露基亞‧烏提尼(Luigia Uttini)結婚。1813年10月10日,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朱瑟培‧佛吐尼諾‧法蘭契斯可(Giuseppe Fortunino Francesco)。這一年也是文藝出版上相當重要的一年──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和雪萊(Shelley)的《夢的仙后》(Queen Mab)相繼問世;舒伯特(Schubert)完成了他的第一首交響曲;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在維也納首演;羅西尼的歌劇《唐克雷第》(Tancredi)和《阿爾及利亞的義大利女郎》(L’Italiana in Algeri)也首度演出成功。同時這一年也正處於社會劇變的邊緣,史蒂文生(Stevenson)製造成功的第一具蒸汽火車頭在隔年(1814年)啟用;到了1820年,用鋼鐵打造的蒸汽船和橫渡大西洋的輪船也相繼問世。
威爾第出生次日,便在教區教堂受洗,並用拉丁文登記名字。她母親誤將他的生日記成10月9日,所以他總是在這一天慶生,甚至到六十三歲發現了真相之後,他還是一直將錯就錯。由於拿破崙的軍隊從十九世紀初便占領了義大利北部地區,因此威爾第的父親卡羅還得步行到鄰鎮布瑟托(Busseto),用法文辦理出生登記;上面登載威爾第的法文名字是「約瑟夫‧佛吐尼‧法蘭斯華」(Joseph Fortunin Francois)。
威爾第未滿週歲之前,拿破崙在楓丹白露(Fontainbleau)宣布遜位,奧地利和俄羅斯聯軍也乘勢將法國軍隊逐出義大利。關於威爾第在戰亂期間的遭遇,一向有不少玄奇的軼聞,許多穿鑿附會的說法更是明顯地不真實。不過我們多少有理由相信他的第二任太太向朋友所描述的若干情節,從中可以歸納出至少威爾第本人深信不疑的經過︰當時有若干俄羅斯士兵經過隆可列,一路燒殺擄掠,姦淫婦女;威爾第的母親抱著襁褓中的他躲在教堂鐘樓裡,才得以倖免。除了這位作曲家兒子之外,卡羅和露基亞還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為朱瑟琶‧法蘭契斯卡(Giuseppa Francesca Verdi)。她比威爾第小兩歲半,由於罹患腦膜炎之故而智能不足,在1833年她十七歲的時候,逝世於隆可列。
村裡的聖母教堂(Madonna dei Prati)是對威爾第童年影響最深的地方。但是,感染他的是音樂,而不是天主教的信仰。最後一位為他編寫劇本,同時也是最偉大的劇作家阿里哥‧波伊多(Arrigo Boito),有一段文字描寫威爾第,說「他和我們大家一樣,很早就放棄信仰。但是,終其一生對這件事抱著愧疚,悔恨之情似乎遠甚於我等。」威爾第是由當地的一位修士啟蒙,教他讀書寫字;至於音樂上的啟發,則是受教於村裡的一位管風琴師皮耶妥‧拜斯托洛齊(Pietro Baistrocchi)。他在音樂上顯然很早就展露才華,所以在八歲這一年,他父親便為他買了一架小型古鋼琴(spinet)。這架琴最早的狀況,大概不至於像他後來保存時那麼地「殘破」。這架鋼琴曾經由一位叫做史提法諾‧卡瓦列提(Stefano Cavaletti)的鄰居免費幫忙維修,他說,「看著小小年紀的威爾第耐心地練習彈奏那架鋼琴,我就感到心滿意足。」威爾第一直珍藏著這架琴,如今保存在史卡拉歌劇院博物館(La Scala Musuem)裡。
不久之後,修士與管風琴師相繼過世,朱瑟培‧威爾第也在十歲這年進入設在布瑟托的文科學校(ginnasio)就讀。他寄宿在當地一位補鞋匠家裡,每逢週日和節日便步行三哩路回隆可列在教堂裡司琴,賺取三十六里拉的年薪(十三年後,他拒絕了孟札〔Monza〕地方的一所教堂以八倍年薪聘請他擔任風琴師的機會)。他在往返學校和老家之間的路上,總是把靴子脫下來拎在手上,生怕穿壞。有一回在聖誕節早晨,他不小心掉進路旁積水很深的排水溝裡,幸虧有個農夫正好路過,將他救起,他才免於淪為波臣。
……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