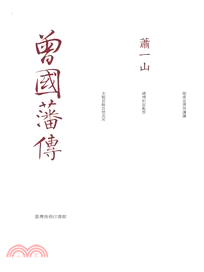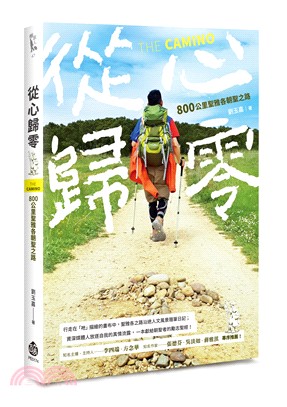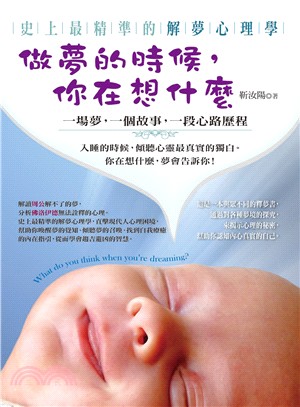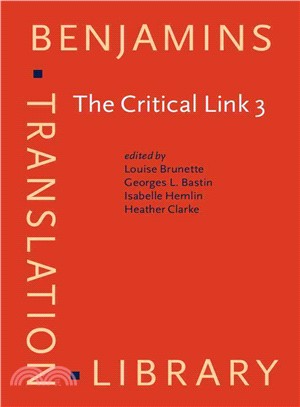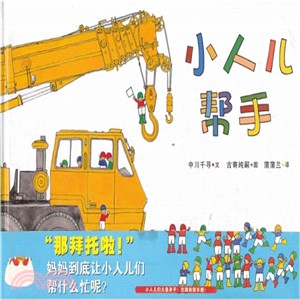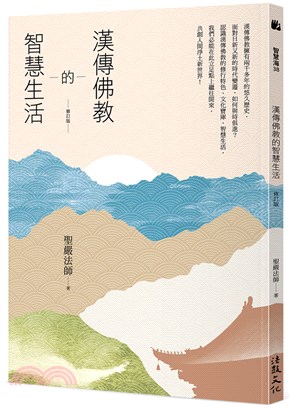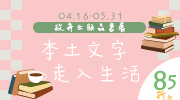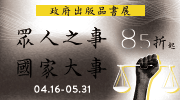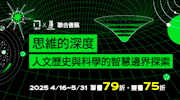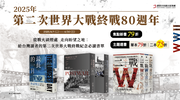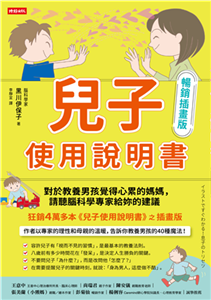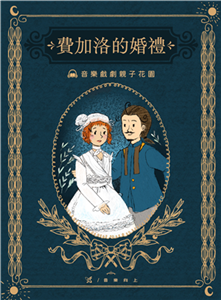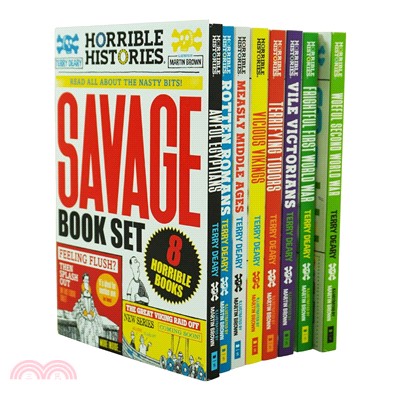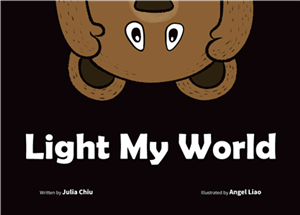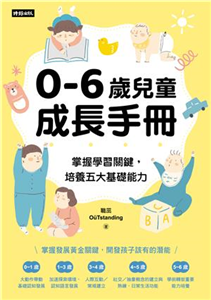曾國藩傳
商品資訊
定價
:NT$ 250 元優惠價
:79 折 197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曾國藩畢生以「禮學」為本,奉行「中庸」精神,剛柔互用,謹慎自持,力行以身化人。為官則致力經世之學,以天下百姓為念,講求「公」、「誠」的精神教育,以儒家治軍,使湘軍成為「有主義的軍隊」,威震天下。他的眼光以世界為格局,守舊與革新並行,既倡導傳統禮教,同時開辦洋務,帶領中國走出順應世界潮流的第一步。他的人格風範與修身治國之道,啟發後代無數能人志士,從梁啟超、黃興到毛澤東、蔣介石,無不受其影響。
本書特色
山縣寒儒守一經,出山姓氏各芳馨,
要令天下銷兵氣,爭說湘中聚德星。
舊雨三年精化碧,孤鐙五夜眼常清,
書生自有平成量,地脈何曾獨效靈。
曾國藩(1811-1872年)為晚清至近代史上,影響中國至深的人物。其一生與湘軍的淵源極深。處於歷史上內憂外患最急遽的時代,卻器識過人。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其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面對長期的內戰及如海鯨波山洶洶而來的帝國主義,他處變不驚,堅忍卓絕。不論在京官時期或辦團時代,都是強矯一流的人物。他的生平修養皆由學問而來。本書從曾國藩之詩文、書牘、日記、奏諭等「真實的讀本」裡,將其一生學業之典型、救世圖國之宏願,在文墨紙卷間一一細說重頭,紹其徽志。
處世的智慧―敬、恕、公、誠
以敬恕為養心之要,以公誠為處世之訣。對於軟熟和同不黑不白的寬厚論說,痛恨刺骨。
中庸思想,剛柔並濟
其思想一宗孔子的中庸之道,經世之學,合道文而為一,剛柔並濟,老墨並用。
本書特色
山縣寒儒守一經,出山姓氏各芳馨,
要令天下銷兵氣,爭說湘中聚德星。
舊雨三年精化碧,孤鐙五夜眼常清,
書生自有平成量,地脈何曾獨效靈。
曾國藩(1811-1872年)為晚清至近代史上,影響中國至深的人物。其一生與湘軍的淵源極深。處於歷史上內憂外患最急遽的時代,卻器識過人。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其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面對長期的內戰及如海鯨波山洶洶而來的帝國主義,他處變不驚,堅忍卓絕。不論在京官時期或辦團時代,都是強矯一流的人物。他的生平修養皆由學問而來。本書從曾國藩之詩文、書牘、日記、奏諭等「真實的讀本」裡,將其一生學業之典型、救世圖國之宏願,在文墨紙卷間一一細說重頭,紹其徽志。
處世的智慧―敬、恕、公、誠
以敬恕為養心之要,以公誠為處世之訣。對於軟熟和同不黑不白的寬厚論說,痛恨刺骨。
中庸思想,剛柔並濟
其思想一宗孔子的中庸之道,經世之學,合道文而為一,剛柔並濟,老墨並用。
作者簡介
蕭ㄧ山(1902-1978)
江蘇銅山人,原名桂森,號非宇。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有清史研究第一人之稱。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教授;中央大學、河南大學、東北大學、西北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大會代表等。1948年來臺後,任教於臺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語所研究員,監察委員。著有:《清代通史》《清代史》《清史》《太平天國叢書》《近代祕密社會史料》《太平天國詔諭》《太平天國書翰》《民族文化概論》《非宇館文存》等書。
江蘇銅山人,原名桂森,號非宇。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有清史研究第一人之稱。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教授;中央大學、河南大學、東北大學、西北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大會代表等。1948年來臺後,任教於臺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語所研究員,監察委員。著有:《清代通史》《清代史》《清史》《太平天國叢書》《近代祕密社會史料》《太平天國詔諭》《太平天國書翰》《民族文化概論》《非宇館文存》等書。
目次
引 子
第一章 家庭環境
第二章 經世之禮學
第三章 學術背景
第四章 思想體系
第五章 天才與志氣
第六章 京官時代的政論
第七章 湘軍編練及其特點
第八章 太平天國的平定
第九章 改造舊社會與建設新事業
第十章 湘淮軍代興的關係
第一章 家庭環境
第二章 經世之禮學
第三章 學術背景
第四章 思想體系
第五章 天才與志氣
第六章 京官時代的政論
第七章 湘軍編練及其特點
第八章 太平天國的平定
第九章 改造舊社會與建設新事業
第十章 湘淮軍代興的關係
書摘/試閱
引 子
上相南征策眾材,軍容十萬轉風雷,
書生卻進安民策,盜弄潢池事可哀!
這是我國近代一位偉大的人物―曾國藩送唐鏡海先生之詩,其實這首詩不啻為他自己的寫照,唐鏡海哪有這樣的功業呢?說起曾國藩來,一般人總要聯想到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承襲天地會的餘緒,啟發民族革命的偉業,為社會主義作先導,當然不能算「盜弄潢池」,但是清朝人都稱他作長毛賊,而十五年的天國,居然被一個書生打平了,這不是很可哀的事嗎?清末民初的革命黨人,繼洪楊而倡排滿運動,建民國而復皇漢聲威,不免就要唾罵曾文正公了。
章炳麟是當時激烈派的代表,他曾經說過:「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要其天資,亟功名善變人也。始在翰林,豔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稍游諸公名卿間,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詞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於歷試,亦有群率張其羽翮,非深根寧極,舉而措之為事業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既振旅,始為王而農行遺書,可謂知悔過矣。其功實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癬疥如蛇蚹,其徵也。凡有成勳長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唐人謂鄭畋之生,妊于死母,其誇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見《檢論》雜誌)。
以民族罪人加諸曾國藩而託之於其子孫之口,真是他的「魂魄猶有餘羞」嗎?可是章炳麟又以英雄許之,說:「曾左之倫,起儒衣韋帶間,驅鄉里服耒之民,以破強敵,宗棠又能將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則上度皇甫規嵩,下不失為王鐸鄭畋,命以英雄誠不虛」(《檢論‧對二宋》)。更推論他們的為人治蹟,說道:「湘軍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撻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聞,又橫張神教以軼干之。
曾國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過群保鄉邑,非敢贊清也。當是時駱秉章向榮獨知向義,……湘人雖蔑易秉章,又甚惡向榮為人,卒不能干正義,故其檄書不稱討叛,獨以異教愆禮數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豈弟,是以沒世不免惡名。然其行事猶足以愜人心者,蓋亦多矣。……曾左知失民不可與共危難,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數為長吏牽掣,是以所至延進耆秀,與共地治,而殺官司之威。
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終身衣不過大紬,食不過一肉,時時與人圍棋宴遊,或具酒肴,雜以茶茆,言談時及載籍,文辭恢啁間之,其山澤之儀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於姦,初政十年,吏道為清矣。……夫此諸將帥者,倨讓不同,寬猛亦從其性也,而皆體任自然,不好苛禮,不擾四民,不徇汙吏,不畏強死。群校所推,以曾左為主。雖下未齒王導謝安之流,誠令監視一國,輔以知遠,而軌以法程,亦可以垂統矣!」(《檢論‧近思》)。
可見就是怪僻的章炳麟除民族大義一點外,也不能不佩服曾文正公,「行事足愜人心」,共治伸張民權,「體任自然」,「吏道為清」,是一個「可以垂統」的人物哩!要說他「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豈弟」,就是他「沒世不免惡名」的原因,那更有點冤枉!章先生既知道他「不敢贊清」,而以「異教愆禮」數洪楊,足徵國藩是為文化而戰爭,為宗教而戰爭,自不能以民族大義責之!據傳說:彭玉麟始終不願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異族之義,並曾勸國藩自主東南;英人戈登也勸過李鴻章,他們為什麼都不敢作呢?我們試一看左宗棠的性格,那樣豪邁不羈,他曾見過洪秀全,勸以仍用孔孟學說,秀全不聽。
後來他立功邊徼,氣凌朝右,尚不免懍殿陛之森嚴,以天威為可畏,就可以知道在幾千年君主專制政體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曾國藩又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輕舉妄動呢?後來剿捻匪,辦教案二事,均為盛名所累,不得國人諒解,一轉眼間,鐘銘世勳,聖相威嚴,卻變為謗譏紛紛,舉國欲殺,可見舊社會的潛勢力之大。
如果他做些狐埋狐搰的勾當,難道就能成功嗎?事後論人,自己不免忘掉時代環境了!他們在實際上確把滿清的政權轉移於漢人,無形中又增加了會黨的勢力,替民族革命隱隱做了下驅除難的工作,就在這一點來講,也算功可補過吧!況且他們的眼光,已著重在全世界上,帝國主義者乘方張之勢,壓迫欺陵我們,漢滿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無的,為整個中華民族謀出路,計劃出一種復興的方案,守舊維新,安內攘外,雖然沒有達到救國救世的目的,畢竟是個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們稱贊啊!
梁任公以史學家的眼光,批評曾國藩說:「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使曾文正公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謹嚴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同事業之成,有所以字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見《飲冰室文集》論私德)。
又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 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堅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鈔》序)。
這把曾國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而為「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的由來說得很明白,見解非常平允,可謂曾文正公一個知己。但梁先生還不曉得曾文正公之所以偉大,因為他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曾公同時之新學家容閎,及今人郭斌龢氏對於此點頗有所見,容氏說:「曾文正公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謂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舊教育中之特產人物」(見《西學東漸記》)。
郭氏說:「我國過去教育目的,不在養成狹隘之專門人才,而在養成有高尚品格多方發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之教育理想,與此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下所產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備,文武兼資。有宗教家之信仰,而無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篤實,而無其迂腐;有藝術家之文采,而無其浮華;有哲學家之深思,而無其鑿空;有科學家之條理,而無其支離;有政治家之手腕,而無其權詐;有軍事家之韜略,而無其殘忍。
西洋歷史上之人物中,造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發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與文正相比者,實不數數覯。而文正之在中國,則雖極偉大,要不過為中國正統人物中之一人。嗚呼!斯真中國教育之特色,中國文化之特色也」(見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曾文正公與中國文化〉一文)。容郭二氏均以曾國藩的「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為我國教育文化之特色,較之梁先生的評論深刻多了。
然而他們仍未能說明我國之教育理想,就是「內聖外王」「明體達用」的經世之學,曾國藩所謂「經世之禮」也。不錯,禮學是孔子的教人之道,也是中國文化的正統,但如曾國藩其人者,在中國歷史上,依然「不數數覯」,非僅其中之一人而已。為什麼呢?因孔子沒後,二千年來,「春秋經世」之義,甚少解人,有成就的更不用說了。
考據詞章義理三種學問的發展,致陷人於「狹隘之專門人才」一途,如荀子所譏為俗儒陋儒者。故曾國藩對他們均有所菲薄,而欲以深與博之功力,兼綜三者之長,以恢復固有文化的特色。其成就之恢宏,遠非一般號稱「正統人物」者所能相比。倘不了解這種意境,則曾國藩豈不變成一個萬能的天神了嗎?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昔人之所以詠張江陵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了。當時他的朋僚歌功誦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徵引,只看一個朋友而兼「政敵」的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宗棠寄其子孝威書云:「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輓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
見何小宋(璟)代懇恩卹一疏,於侯心事,頗道得著,闡發不遺餘力,知劼剛亦能言父實際,可謂無忝矣。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咨送,可謂鉏去陵谷,絕無城府。至玆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
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直一哂耶」。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揚揄,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宗棠之進用,亦由國藩所薦,乃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利之爭,故皆能持大體。以「撰語自誇,務壓二公」(指曾胡)的左宗棠,早有「曾侯觥觥,當世所宗,公與上下,如雲如龍」(祭胡文忠公文)之言,又不僅俟蓋棺以後始云:「自愧不如元輔」了。即此可知曾國藩為一代冠冕,絕不是偶然的。
曾國藩的事業之成就,完全由學問而來,無關乎命運,今昔人的議論都是一致的。就是撰湘軍志的王闓運,對曾公時露不滿之意,他說:「湘軍兵威之盛,豈天數耶?一二人謀力之所致也」。國藩自己也說過:「山縣寒儒守一經,出山姓氏各芳馨。要令天下銷兵氣,爭說湘中聚德星。舊雨三年精化碧,孤鐙五夜眼常青。書生自有平成量,地脈何曾獨效靈?」(次韻何廉昉太守感懷述事詩)。
這是老實話,至於他在金陵軍營官軍昭忠祠記裏說:「時未可為,雖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所謂「天」「時」是指太平軍初起「代興迭盛,橫行一時」的朝氣;或指將衰「權分勢散,廣封騃豎」的暮氣。其家書亦嘗歸功於天,乃謙讓不矜之意,萬不可體會有失。
最有趣味的是他告訴門人俞樾的話說:「李少荃(鴻章)拚命做官,俞蔭甫(樾)拚命著書,吾皆不為也」(見《春在堂隨筆》)。究竟他拚命幹些什麼事呢?豈僅「上相南征策眾材,軍容十萬轉風雷」嗎?也不是的。假如讀者要知道這位「書生自有平成量」的「聖相」是如何造成,請讓我把他的生平一一仔細道來!
上相南征策眾材,軍容十萬轉風雷,
書生卻進安民策,盜弄潢池事可哀!
這是我國近代一位偉大的人物―曾國藩送唐鏡海先生之詩,其實這首詩不啻為他自己的寫照,唐鏡海哪有這樣的功業呢?說起曾國藩來,一般人總要聯想到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承襲天地會的餘緒,啟發民族革命的偉業,為社會主義作先導,當然不能算「盜弄潢池」,但是清朝人都稱他作長毛賊,而十五年的天國,居然被一個書生打平了,這不是很可哀的事嗎?清末民初的革命黨人,繼洪楊而倡排滿運動,建民國而復皇漢聲威,不免就要唾罵曾文正公了。
章炳麟是當時激烈派的代表,他曾經說過:「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要其天資,亟功名善變人也。始在翰林,豔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稍游諸公名卿間,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詞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於歷試,亦有群率張其羽翮,非深根寧極,舉而措之為事業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既振旅,始為王而農行遺書,可謂知悔過矣。其功實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癬疥如蛇蚹,其徵也。凡有成勳長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唐人謂鄭畋之生,妊于死母,其誇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見《檢論》雜誌)。
以民族罪人加諸曾國藩而託之於其子孫之口,真是他的「魂魄猶有餘羞」嗎?可是章炳麟又以英雄許之,說:「曾左之倫,起儒衣韋帶間,驅鄉里服耒之民,以破強敵,宗棠又能將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則上度皇甫規嵩,下不失為王鐸鄭畋,命以英雄誠不虛」(《檢論‧對二宋》)。更推論他們的為人治蹟,說道:「湘軍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撻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聞,又橫張神教以軼干之。
曾國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過群保鄉邑,非敢贊清也。當是時駱秉章向榮獨知向義,……湘人雖蔑易秉章,又甚惡向榮為人,卒不能干正義,故其檄書不稱討叛,獨以異教愆禮數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豈弟,是以沒世不免惡名。然其行事猶足以愜人心者,蓋亦多矣。……曾左知失民不可與共危難,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數為長吏牽掣,是以所至延進耆秀,與共地治,而殺官司之威。
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終身衣不過大紬,食不過一肉,時時與人圍棋宴遊,或具酒肴,雜以茶茆,言談時及載籍,文辭恢啁間之,其山澤之儀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於姦,初政十年,吏道為清矣。……夫此諸將帥者,倨讓不同,寬猛亦從其性也,而皆體任自然,不好苛禮,不擾四民,不徇汙吏,不畏強死。群校所推,以曾左為主。雖下未齒王導謝安之流,誠令監視一國,輔以知遠,而軌以法程,亦可以垂統矣!」(《檢論‧近思》)。
可見就是怪僻的章炳麟除民族大義一點外,也不能不佩服曾文正公,「行事足愜人心」,共治伸張民權,「體任自然」,「吏道為清」,是一個「可以垂統」的人物哩!要說他「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豈弟」,就是他「沒世不免惡名」的原因,那更有點冤枉!章先生既知道他「不敢贊清」,而以「異教愆禮」數洪楊,足徵國藩是為文化而戰爭,為宗教而戰爭,自不能以民族大義責之!據傳說:彭玉麟始終不願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異族之義,並曾勸國藩自主東南;英人戈登也勸過李鴻章,他們為什麼都不敢作呢?我們試一看左宗棠的性格,那樣豪邁不羈,他曾見過洪秀全,勸以仍用孔孟學說,秀全不聽。
後來他立功邊徼,氣凌朝右,尚不免懍殿陛之森嚴,以天威為可畏,就可以知道在幾千年君主專制政體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曾國藩又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輕舉妄動呢?後來剿捻匪,辦教案二事,均為盛名所累,不得國人諒解,一轉眼間,鐘銘世勳,聖相威嚴,卻變為謗譏紛紛,舉國欲殺,可見舊社會的潛勢力之大。
如果他做些狐埋狐搰的勾當,難道就能成功嗎?事後論人,自己不免忘掉時代環境了!他們在實際上確把滿清的政權轉移於漢人,無形中又增加了會黨的勢力,替民族革命隱隱做了下驅除難的工作,就在這一點來講,也算功可補過吧!況且他們的眼光,已著重在全世界上,帝國主義者乘方張之勢,壓迫欺陵我們,漢滿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無的,為整個中華民族謀出路,計劃出一種復興的方案,守舊維新,安內攘外,雖然沒有達到救國救世的目的,畢竟是個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們稱贊啊!
梁任公以史學家的眼光,批評曾國藩說:「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使曾文正公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謹嚴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同事業之成,有所以字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見《飲冰室文集》論私德)。
又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 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堅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鈔》序)。
這把曾國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而為「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的由來說得很明白,見解非常平允,可謂曾文正公一個知己。但梁先生還不曉得曾文正公之所以偉大,因為他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曾公同時之新學家容閎,及今人郭斌龢氏對於此點頗有所見,容氏說:「曾文正公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謂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舊教育中之特產人物」(見《西學東漸記》)。
郭氏說:「我國過去教育目的,不在養成狹隘之專門人才,而在養成有高尚品格多方發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之教育理想,與此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下所產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備,文武兼資。有宗教家之信仰,而無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篤實,而無其迂腐;有藝術家之文采,而無其浮華;有哲學家之深思,而無其鑿空;有科學家之條理,而無其支離;有政治家之手腕,而無其權詐;有軍事家之韜略,而無其殘忍。
西洋歷史上之人物中,造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發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與文正相比者,實不數數覯。而文正之在中國,則雖極偉大,要不過為中國正統人物中之一人。嗚呼!斯真中國教育之特色,中國文化之特色也」(見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曾文正公與中國文化〉一文)。容郭二氏均以曾國藩的「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為我國教育文化之特色,較之梁先生的評論深刻多了。
然而他們仍未能說明我國之教育理想,就是「內聖外王」「明體達用」的經世之學,曾國藩所謂「經世之禮」也。不錯,禮學是孔子的教人之道,也是中國文化的正統,但如曾國藩其人者,在中國歷史上,依然「不數數覯」,非僅其中之一人而已。為什麼呢?因孔子沒後,二千年來,「春秋經世」之義,甚少解人,有成就的更不用說了。
考據詞章義理三種學問的發展,致陷人於「狹隘之專門人才」一途,如荀子所譏為俗儒陋儒者。故曾國藩對他們均有所菲薄,而欲以深與博之功力,兼綜三者之長,以恢復固有文化的特色。其成就之恢宏,遠非一般號稱「正統人物」者所能相比。倘不了解這種意境,則曾國藩豈不變成一個萬能的天神了嗎?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昔人之所以詠張江陵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了。當時他的朋僚歌功誦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徵引,只看一個朋友而兼「政敵」的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宗棠寄其子孝威書云:「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輓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
見何小宋(璟)代懇恩卹一疏,於侯心事,頗道得著,闡發不遺餘力,知劼剛亦能言父實際,可謂無忝矣。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咨送,可謂鉏去陵谷,絕無城府。至玆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
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直一哂耶」。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揚揄,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宗棠之進用,亦由國藩所薦,乃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利之爭,故皆能持大體。以「撰語自誇,務壓二公」(指曾胡)的左宗棠,早有「曾侯觥觥,當世所宗,公與上下,如雲如龍」(祭胡文忠公文)之言,又不僅俟蓋棺以後始云:「自愧不如元輔」了。即此可知曾國藩為一代冠冕,絕不是偶然的。
曾國藩的事業之成就,完全由學問而來,無關乎命運,今昔人的議論都是一致的。就是撰湘軍志的王闓運,對曾公時露不滿之意,他說:「湘軍兵威之盛,豈天數耶?一二人謀力之所致也」。國藩自己也說過:「山縣寒儒守一經,出山姓氏各芳馨。要令天下銷兵氣,爭說湘中聚德星。舊雨三年精化碧,孤鐙五夜眼常青。書生自有平成量,地脈何曾獨效靈?」(次韻何廉昉太守感懷述事詩)。
這是老實話,至於他在金陵軍營官軍昭忠祠記裏說:「時未可為,雖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所謂「天」「時」是指太平軍初起「代興迭盛,橫行一時」的朝氣;或指將衰「權分勢散,廣封騃豎」的暮氣。其家書亦嘗歸功於天,乃謙讓不矜之意,萬不可體會有失。
最有趣味的是他告訴門人俞樾的話說:「李少荃(鴻章)拚命做官,俞蔭甫(樾)拚命著書,吾皆不為也」(見《春在堂隨筆》)。究竟他拚命幹些什麼事呢?豈僅「上相南征策眾材,軍容十萬轉風雷」嗎?也不是的。假如讀者要知道這位「書生自有平成量」的「聖相」是如何造成,請讓我把他的生平一一仔細道來!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