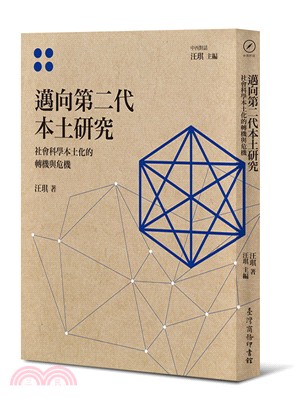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轉機與危機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在反思本土學術的同時,也挑戰西方典範的有效性。
★書中檢討與評論的目的不在否定或抹煞,而是對話與討論。
★以一種較「本土化」視野更為寬廣的思維,來推展本土學術可長可久的發展。
內容說明
多年來,華人學界對於本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反省與批評始終不斷;「理論上盲目追隨西方」、與「實務上疏離本土需求」是兩個經常被提出來的缺失。許多人認為「本土化程度不足」是問題的關鍵。然而就像是慶典的煙火,「本土化」議題雖然不時出現、卻也不曾帶來根本的改變。截至目前為止,本土化的終極目標為與途徑為何?甚至何謂「本土化」都仍然沒有定論。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過去討論本土化,大多限制在研究過程本身,例如研究主題、觀察與分析角度是否貼近本土、文獻探討是否涵蓋本土論述等。然而本土化所牽涉的並不僅只是研究執行層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隱藏在執行面背後的、思考方式與歷史文化所造成的典範衝突。
本書因此採取更宏觀的角度,在典範衝突之下找尋可能兼顧「立足本土」與「國際對話」的方案。論述由解析「本土化」概念的意涵開始,進而深入歷史文化脈絡,由社會科學的特質、西學引入中國的時代背景、以及華人治學與歐洲思辯傳統等三方面,分析影響今天本土學術表現的關鍵因素。在剖析各種本土化取徑的優劣之後,並提出以達成「共通性」來取代社會科學所追求的「共同性」為目標的學術發展策略。
作者簡介
作者的研究興趣主要在文化與傳播,近年則聚焦於社會科學本土化議題,並以此為主題發表多種中英文著作,包括2011年編輯出版的英文專書《傳播研究去西方化》(Routledge出版)以及《亞洲傳播學刊》專刊 等。她曾經多次獲得學術殊榮,包括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亞洲傳播獎」(AMIC, Asian Communication Award),與「星雲新聞傳播教育貢獻獎」。
序
序
或許是自己的生長環境與經歷,文化議題始終讓我著迷;但是會把文化差異帶進學術研究本身來看「本土化」,卻是經年累月在「問」、「被問」、「反問」與我所得到、以及沒有得到的答案之間發酵、沈澱而來的。
十多年前,在巴黎一次以全球化為題的演講結束後,一位白髮蒼蒼的教授來問:「為什麼妳不講『你(們)的』理論」?面對這樣一個從未想過的問題,我只能回說:「全球化理論就是這樣」;「但東方有很深刻的思想傳統」,他顯然不滿意我的答覆,說完轉身離去。又一次和一位被我認為是「狂熱馬克思主義者」、「思想不轉彎」的朋友閒聊,無意間說出自己的疑惑:「為什麼新舊馬克思主義論述總把自由主義經濟與文化視為對立的兩個極端」?本以為這問題會觸發對方熱辣的反駁,不料這位德國學者竟回說:「有道理;問得好」!這答覆同樣讓我出乎意表。巴黎老教授的問題讓我開始思索「我」、和「我的文化傳統」與我所瞭解的理論之間的關連;而終生以馬克思研究為職志的老友,則讓我不得不認真面對「理論未必有效」、以及「所以又怎樣」的問題。
問題引導思考,但有時沒有問題,也同樣逼人思考。一段時日後,,我觀察到這類對答 絕少在本土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界出現----這又是為什麼?問到理論,我當年給法國老教授的答覆:「人家理論就是這樣」是常見的回應;也有更熱心的學者建議:「先回去把它弄懂再問」。但就只有「沒弄懂」才會有問題嗎?在西方的思辯傳統,問題是科學發現與知識建構的起點。常常是:有問題就沒問題、沒問題倒會有問題。或說華人不習慣發問與質疑,但重「體悟」與「轉化」。問題是,我們的研究中展現了多少體悟的淬鍊與轉化的智慧?如果我們覺得不應該安於本土學術的現狀,未來的路又要怎麼走?
對於許多學者,「本土化」是問題的答案;它也是一個學術自主的問題。「主體性」淪喪所造成的現象令人不安,由這個角度切入 本土化議題十分自然。但是本土化概念有其含混之處;對我而言,今天華人學術發展所面對的也絕不只是一個學術帝國主義的問題, 而是學術典範、教育體制與政策問題,更是歷史文化問題──是一個關乎整體、而非只是「本土」或非西方學界的問題。文化是關鍵,、也是所有上述因素背後的根源;它不是一個冰冷遙遠的研究題材,也是研究的本身。我們要進入西方所建構的現代學術領域,無時無刻不在面對跨文化互動所可能出現的問題。脫離文化脈絡去講「主體性」,不但很容易讓我們落入「文化中心主義」的陷阱,許多無解的問題也隨之而來。
本書是根據作者於2011年編輯出版的英文著作:<<傳播研究去西方:不同的問題與框架>>(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tering Frameworks and Changing Questions)中,自己執筆的三章發展而成。這本書的付梓, 也是一連串因緣際會的產物。2007年我由香港回到台北執教,當時一個有關傳播研究本土化的「頂尖大學研究計畫」主持人出缺,給了我一個重拾此一研究議題的機會。說「重拾」,是因為1998年起,我已經開始了這一主題的跨學門計畫,但是在舉辦了幾次工作坊、以及初步資料蒐集之後,始終沒能在工作的轉換中, 得到進一步開展的機會。2007年的「頂大計畫」提供了一個平台----兩年期間由工作坊發展出國際學術會議,會議論文再分別由《亞洲傳播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與勞特利其出版社 ( Routledge ) 出版,至此告一段落。同一時間,國立政治大學提供的「講座研究費」, 讓我得以開啟了一個頗為浪漫的「中西對話系列叢書」計畫,希望能藉由深入歷史文化脈絡去討論各學門的關鍵概念,為未來建構本土論述鋪路。然而系列專書第一、二本所得到的反應讓我了解,對大部份學界人士,「本土化」的意義、作法與牽涉的因素,,還是相當陌生與模糊。困心含慮的推敲, 使我興起了撰寫本書、以及調整系列叢書方向的念頭。
由文化角度來看本土學術有助於拓展視野,但也令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是「本土化」所牽涉的議題, 逼使我遠遠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傳播研究,進入許多頗為陌生的領域----包括哲學、詮釋學、甚至中東、以及南亞近代史。這其中的每一個領域 都足以令人傾畢生之力去鑽研;而我只是一名過客、一名粗暴的掠奪者,貪心地各處尋找可以灌溉本土議題的活水泉源。書寫過程中的另一挑戰,是我提出的論述, 是否能夠通過自己所定立的標準、達到自己期許他人的目標?每一支射向別人的箭,都有兩支對準自己。但不論顧慮有多少,在學術的領域,態度可以謙虛,但在「表述看法」方面, 却需要「(野人)獻曝」的勇氣。學術思想的衍展, 貴在我們檢驗別人主張的同時,別人也檢驗我們的主張----包括我們對別人主張的檢驗。在這樣的思維之下,我不揣淺漏、提出自己的看法,準備接受批評與檢驗;本書中對於第一代本土化論述的檢討與評論,也是在這樣的思維下展開的。
檢討與評論的目的不在否定或抹煞,而是對話與討論─這也是本書的目的。事實上,由人類歷史來看,無論中國、歐洲或其他文明的傳統,缺少了這一環,思想都趨向停滯。歐洲中古時期與中國在近兩千年科舉盛行時期,都出現思想的停滯現象。如果三百年前歐洲在拋棄神權時,一併拋棄了希臘傳統,則今天的歐洲會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歐洲嗎?如果文藝復興讓歐洲的思想再度蓬勃發展,則華人學界何不能換個角度審去視「傳統」?西方有一句諺語:「(替嬰兒洗完 澡)不要把嬰兒連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師法西方不必全盤否定自我;科舉式思考不足取,何不回到中國歷史上 思想發展最蓬勃的春秋戰國時期去尋找答案?諸子學說的論述方法與取徑, 難道沒有值得我們參考借鏡之處?這部份我們了解了多少?
經過近兩千年思想上的限縮與百餘年的自我否定,如今要求華人學界融合中西、啟動一次學術上的「浴火重生」, 絕非易事;但若今天我們不往前走,,未來將益發地擧步維艱。本土學術發展是一場接力賽;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把棒子丟掉、自我放棄。
本書大部份書稿是在退休之後寫就的。我謝謝兩岸四地在不同階段給我寶貴意見的學界朋友。多年來他們給我的回應與鼓勵,讓我瞭解本土學術發展議題在不同華人學術社群的意義。唯一令我遺憾與感傷的,是在本土議題上一路相互激勵的好友、香港浸會大學講座教授張佩瑤,未及看到本書便已辭世。另方面,青年學者──包括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班、以及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新聞史論青年師資特訓班同窗會的成員──對於本土學術發展的關懷,令我對未來充滿期待。我也謝謝在整個書寫過程當中擔任助理的紀金慶。金慶一手總攬所有的「後勤任務」。他對於我各種「非典型」文獻搜尋與分析指令的回應,是我思索問題很大的助力。而本書以及「中西對話系列叢書」書稿能夠問世,更要感謝北京大學出版社以及臺北商務印書館拋開利潤考量、全力支持簡、正體字版的出版,和北大出版社謝佳麗女士的熱心協助。
最後, 我謝謝我的女兒肇華和外子彭家發教授多年來的體諒與支持。當我離家遠去新加坡與紐西蘭閉門寫作,老伴與家中老狗相伴;一天兩餐便當度日。為了這本他口中的「天書」,到處幫我找資料、在夜晚燈下一字一句地耐心替我校訂書稿。這些點點滴滴留在心頭,豐富了四十年婚姻生活的色彩。
母親任永温女士是我一生的精神支柱,而父親公紀先生則是我的啟蒙老師。現在回想起來,自己也是外交官子女的父母親,給我的教育其實蘊含了相當多元的文化思維。童年時期 我曾因氣喘病而休學,父母親特地帶我上阿里山調養身體。每天早上七點,父親便把我叫醒,牽起我的手,在漫天晨霧的山中健走。蛛網一樣的山徑向四面八方延展;父親往往不走熟路, 卻慫恿我去探尋未知的景色。他經常玩的一個把戲,是兩手一攤,說:「迷路了」。此時八歲的我, 就會豪氣干雲地帶領父親找路。不知道為什麼,當年的我,對於「找到路」總是充滿信心。近六十年後的今天,撰寫本書的經歷很巧妙地牽連著兒時在山中找路的記憶。
謹以此書獻給先父母,以及所有為本土學術發展努力不懈的有心人。
2013年9月15日於基督城寒舍
目次
導讀
序
第一章 「本土化」:錯誤的答案
一、「在地化」與一片迷霧中的「本土化」
二、真假本土研究
三、在「本土」談學術:問題在哪裡?
第二章 自己的敵人:「西方主義」
一、遭遇西方
二、「西方主義」與「東方主義」論述
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四、「西用」擴張
五、對於「中體」信心的崩潰:自我與他者衝突的高潮
六、二十一世紀的「西方主義」
七、全盤接收主流西方所發展的方法與理論
八、跟著西方貶抑自己
第三章 「治學」與「思辯」(dialectic):道不同,可相為謀?
一、文獻性質:「學問」與「知識」
二、研究取徑:「治學」與「求知」
三、春秋戰國論述典範與西方的「不可共量」與「可共量」特質
第四章 找路
一、回歸本土的兩種取徑與目的
二、關鍵與弔詭:普世性與「一」「多」的論爭
第五章 學術的巴貝爾高塔倒塌之後
一、理解、詮釋、與翻譯
二、對於詮釋的挑戰
三、「不可共量性」的種類
四、共同性、相容性與可共量性(Commonlity, Compatibility and Commensurality)
五、「共量性」與「不可共量性」的相依相隨
六、由「普世」到「不可共量性」
七、「不可共量性」到「可共量性」
八、超越「歐洲中心主義」與「普世性」:可共量性/共通性
第六章 實戰手冊:找回主體性、面對異質文化
一、典範錯置與主體性
二、超越「西方主義」,面對異質文化的挑戰
三、代結論
概念索引
人名索引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本土化」:錯誤的答案
距今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在遭逢殖民侵略、現代化與民主化多重衝擊的同時,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思想典範轉移。在號稱「普世」的科學價值洗禮之下,中國知識份子把兩千年來被視為「國學」的典籍鎖進「中國文史」的小箱子,開始走上一條「學術現代化」的不歸路。
然而這條「擁抱普世」的路,卻並非走得無怨無悔、也絕不是全然地義無反顧。由民國初年到文革,儘管中國文化傳統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種運動中被「自己人」所否定、撻伐,但「本土」的焦土之下,種子卻沒有腐化、消失;一股不安的躁動情緒,隱身在「西化」/「國際化」/「全球化」的表象之下,伺機而動。由一九三六年,無論是社會學家楊開道對於「中國社會科學……只用外國的材料」的批評,到潘菽和吳文藻有關「學術中國化」3的呼籲,以至於今天華人學界有關「本土化」的檢討,都可以說是反映了同一種對於現狀的不滿,以及對於現代學術「普世性質」、以及自身角色的疑問與惶惑。問題是,「解藥」在哪裡?
截至目前為止,許多華人以及亞非學界人士都將「本土化」視為答案;多年來,「本土化」或多或少也都曾經引起一些有關學術上「自我」與「他者」的反省。但各個華人社會的學術發展路徑與學門特質不同,「本土化」被重視的程度也有差別。香港與新加坡受惠於其特殊的歷史經驗與貿易地位,研究國際化程度和壓力一向較高。台灣由七○年代開始經濟起飛,留學生回流,積極引入國外的理論與方法。一九八○年代,學界面臨全球化挑戰,楊國樞等學者發起「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之後,開始討論社會與行為科學「中國化」的問題,港、台才陸續出現了有關本土化的學術討論與著作。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牽連,起步較晚。但改革開放後社會科學重建;面對西方文獻大量快速引入,學界也陸續出現了本土化、中國化的討論。
在八○年之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國際學術環境已經與一九三○年代大不相同,然而對於未來發展方向的疑惑不但仍然沒有解開,學術環境在「追求國際競爭力」的壓力之下,似乎更加沒有多元發展的空間。有關本土化的討論,整體而言在深度和廣度上也始終沒有太大突破。就如同傳播學者黃旦所描述的,這些所謂「本土化」「爭論」其實是「有爭無論」;一些「非黑即白非白即黑式的你來我往」論題既然從未曾展開,也就難怪「轅門外三聲砲響」,但引起的不過是星點煙火;四周仍然是「一片死寂」。而這種沉默,黃旦警告說,比爭論本身更值得警惕和重視。
「本土化」的議題未能撼動人心有許多原因;或是政治與民族情緒的參雜滲透、或是欠缺切實可行的方法與途徑,都使得討論無以為繼。然則「下一步」邁不出去,其實隱含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就是概念本身。就以學術「本土化」的進展而言,有學者認為台灣已經由「研究現象本土化」逐漸進展到「研究概念本土化」、以至於「研究典範本土化」。然而同樣看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也有人認為不可樂觀;社會學者葉啟政就認為,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不但成績稱不上耀眼,甚至遭遇瓶頸、後繼乏力。觀察結論如此不同,是否因為判斷標準不一、或者根本對於「本土化」的內涵有不同的認識?「本土化」究竟指的是什麼?如果意義不清楚,「本土化」是方是圓人人理解不同,我們又怎麼知道如何去觀察、判斷,應該贊成或反對、又如何去實踐?
一、「在地化」與一片迷霧中的「本土化」
意義的含混與矛盾,常使討論陷入泥沼;然而要澄清「本土化」概念,還得先處理「本土」與「在地」之間的差異。文獻中對「全球化」的討論不少,但有關「本土」的則非常有限。在英文裡,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化」一般被解釋為「本土」(indigenous)或 「在地」(local)。兩者的意義都被它們的相反詞所制約:非「外來」的,便是「本土」;而非「全球」的,便是「在地」。「本土」和「在地」最主要的差別,是前者還有「原生(於一地)」的意思,例如「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而「在地」的拉丁字源「locus」的意思其實是「地方」(place), 因此「在地」也和「地方」脫不了關係:然而這個「地方」卻未必是一個「地理」的概念,而是人和他所居住、生活的土地之間的連結;它牽涉到人如何去「熟悉與瞭解自己居住的地方與社區」、尤其牽涉到人「對地方的情感」、一個讓人真正覺得「有歸屬感的地方」。換言之,「在地」是由「人」與「地方」之間的聯繫與思考習慣所形塑的。 「在地」的世界可能是流動不拘的,然而人與「地方」的聯繫與習慣卻不輕易動搖;正如哈維(David Harvey)所指出的,世界的變動愈大,我們愈像一條航行五湖四海的船,不能沒有一個可以下錨的地方。由上述解釋,我們可以確定「在地」,其實並不一定有很清楚的時間、或空間的指涉;它存在每個人心中、未必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
「在地」的意義已經如此抽象、流動,使得問題更複雜的,是目前中文文獻談論「本土化」概念,有時候是在「本土」(indigenous)的意義之下去談的,但是也有些是在「在地」(local)的意義之下去談的。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這兩者經常被交替使用、甚至翻譯上也未必有所區分,但是如果要從全球化的理論脈絡來看,則「本土化」與「在地化」卻有微妙但關鍵性的差異。「在地化」對應「全球化」,而全球化論述所注意的,是現代自由經濟體制進一步向全球擴張時所出現的各種現象,因此在這個脈絡下談「在地化」,出發點與觀察角度其實是「全球如何進入在地」。以廣告文案為例,過去麥當勞廣告裡歡欣鼓舞吃漢堡的可能都是西方人,然而「在地化」之後,同樣是一個在搖籃裡看到麥當勞招牌就會開心歡笑的娃娃,非洲觀眾看到的是黑膚色娃娃、亞洲觀眾看到的是黃膚色娃娃;觀眾覺得親切,美國漢堡薯條也賣得更好。「理論上」所有地區的商品都可以用這種方式銷到其他地區去,就如同宏碁電腦在國外的廣告通常也不會只出現黃皮膚演員;但這並不是「全球化」論述的走向。它的觀察角度反映的其實是西方─甚至是西方的跨國企業。也因此「在地化」的本意並不是要讓「在地人」回心轉意,重新認識水餃的美味,而是要更多吃水餃的人去吃漢堡。在學術上,「在地化」所隱含的,因此不過是靈活運用源自西方的理論,增強它的適用性與有效性。
除此之外,「全球化」/「在地化」的論述裡面,有另外一個通常被忽略的涵義:如果一個地區並沒有可供外銷的產品,那麼談談外來產品的「在地化」就可以了;至於「在地」如何發展產業的競爭力、積極加入國際貿易活動就更不是論述所關心的議題。用上述漢堡與水餃的例子來說,「在地化」並不是要讓水餃在美國賣得更好。但是對於非西方學界而言,如何發展學術研究、積極加入國際對話卻正是最迫切的問題。上述分析顯示,在「全球化」的脈絡之下談「在地化」,其觀察角度與關懷主旨都並非出自「在地」或「本土」、也不能涵蓋目前非西方學界所關心的許多議題。由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如此非西方仍然是研究中的「他者」或「客體」,不但沒有成為研究的主體、也沒有平等對話的空間。
與「在地化」一詞相比,使用「本土化」概念無須掛心上述問題,但卻容易走入「文化本質主義」(cultural essentialism)的死角。一旦被冠上「本土」的稱號,「文化」立刻被「典型化」,成為一種口號性的用詞;無論贊成或反對都充滿情緒反應、甚至落入愛國/愛鄉情懷或意識型態的漩渦。在中國大陸,有人認為「本土化」反科學、反全球化,因此是「大逆不道」的;又或者認為「本土化」不是傳統化、台港化,而是中國化,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研究」。在台灣,日本殖民與國民黨統治的經驗同樣使「本土化」概念無可避免地牽扯上族群情結,最後引發「中國化」是否等同「本土化」的爭議。但事實上,這些爭議的本身就已經明白揭示將「本土」「典型化」或「木乃伊化」,是忽略了文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與「改變中有存續、存續中有改變」的特質。
就上述這些說法來看,「本土化」往往隱藏著十分複雜的內涵,無怪乎阿拉塔司(Syed Farid Alatas)將之定義為一個「無定型」(amorphous)的詞彙、一個定義鬆散的類目。
這個類目包含了許多不同學門、不同作者的著作,只不過是這些作者都關懷外來理論與本土文化及本土現實「不搭」的問題、以及是否有可能發展另類的科學傳統。而中文文獻中有關「本土化」的解釋,正巧反映了阿拉塔司的觀察─意涵十分「多元」:它可以是一種建立本土知識體系的「過程」、「活動」,也可以是知識上的自覺、反省與批判;還有更多人認為「本土化」是一種手段或策略,它包含了所有學術社群功能的自主與自立。16整體而言,華人社會科學界在討論「本土化」時,大多將之視為一種努力或手段。或更貼切的說,「本土化」是:透過自省以使研究貼近心目中的「本土」的努力、手段、或策略;目的一方面要使研究彰顯本土的語言、社會、文化特質17與主體性以服務本土18,另方面也強調要發展理論論述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簡言之,「本土化」主要的意義在將根基放置在本土,而不再透過西方的出發點、觀察角度與關懷主旨來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上述的定義方式雖然揭櫫了本土化努力的大方向,但在方法與實踐的層面仍然留下不少模糊地帶;其中一個經常和這個問題纏雜在一起的,就是很多人對於「本土化」雖然有一些瞭解,但是對於「什麼才算是『本土』研究」卻並不很清楚。有不少人認為自己、以及自己所問的問題、所研究的人、現象、以及收集的資料既然都是「本土」的,這樣的研究自然是「本土研究」,又何需刻意區分本土或非本土?如果這樣還不算本土,那還可能如何加強?
二、本土研究的陷阱
確實,儘管我們已經盡量釐清「本土」、以及「本土化」概念的意涵,落實到執行層面,「研究」、甚至「理論」、「概念」、「典範」是否就可以清楚區分「本土」或「非本土」,甚或「假本土」或「真本土」,仍然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換言之,我們似乎可以在進行研究的時候使用「本土化」這個手段,使研究更貼近我們心目中的「本土」,但是具體說,這「手段」如何落實、又是否可以保證「成果」?正如同一個傻徒弟可以按照師傅教他的手法去雕刻一尊觀音像,但這並不能保證最後的成品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觀音像」──「他」可能太胖、或眼睛太大、或姿態放縱,以致於我們已經無法確定這成品刻畫的究竟是不是觀音、或是真觀音或假觀音。然則誰又能說出一尊「觀音像」的客觀評判準則和「充要條件」?還是說:只要徒弟有心想要雕的是觀音像、那就是觀音像?
話雖如此,很多時候我們在討論本土化的時候,依然常常預設了「本土研究」的存在。多年前,心理學者楊中芳認為,要繼續深化本土化研究,心理學者必需要對幾個問題形成共識:
1. 怎樣作才算「本土」心理學研究?
2. 什麼樣的研究「本土化程度」才算高?
3. 如何把歷史/文化放在研究的思考架構中─挖掘老古董、研究傳統概念與方法就是本土研究嗎?
4. 要怎樣分工才能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本土」心理學?
楊中芳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怎樣的研究才算『本土』研究?」就預設了「我們是可以明白劃分『本土研究』與『非本土研究』的;只是我們對於劃分的標準不很清楚、沒有共識。」而她的第二個問題:「什麼樣的研究本土化程度才算『高』」還預設了一個「本土」的性質,就是它不僅僅是「是」或「不是」的問題、而還是程度的問題。楊國樞就曾批評一些國外學者對於邊陲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契合性」不足,這表示我們可以有很「本土」的研究─也就是「本土契合性」很足夠的本土研究,也可以有「不大本土」、或「契合性很差」的本土研究。為幫助讀者瞭解他所稱的「本土契合性」,楊國樞特別整理了一套「契合性」的影響因素;將研究以「特有」或「非特有」現象、「被研究者」或「研究者」觀點、以及「單文化」或「跨文化」研究作區分,最後歸納出「以研究者觀點探討特有現象的單文化研究」為「本土契合性」最高的研究。
楊國樞所歸納的研究類別讓我們瞭解在實際操作的層面如何去落實「本土契合性」;然而這些要件仍然有其侷限。翟學偉在評論「本土契合性」的概念時就指出,楊國樞其實並沒有改變研究視角和西化立場23;葉啟政則認為概念之中預設了實證主義的立場。不但如此,許多套用外國理論的「複製型研究」,倒有不少是符合要件的。甚至有人因為「契合性」要件中有「特有現象」,因此誤以為「本土化」要突顯本地特色,就只能關注華人或華人社會特有的信念、價值或現象,例如「緣分」、「面子」、「報」、或網路世界的「人肉搜索」等等。這些題目自有其研究價值,只是如果過度強調「特殊性」(particularity),將使得理論的開展十分困難。
與一項研究的「本土成分」高低有關的,是一項研究究竟「因何而起」、「為誰而作」。目前文獻中有一種經常可見的本土研究,是回到傳統典籍或本土文獻中「指認」其中符合社會科學概念或理論的部分。換言之,這種研究嘗試證明「西方有的、我們也有」。包括傳播學在內的許多社會科學界人士在剛開始思索本土化議題的時候,走的都是這條路;直到今天,類似的例子依然俯拾皆是。亞非地區許多有關「公共論域」(public sphere)概念26的研究,其實不過就在努力證明這樣的現象「也可以在本地社會找到」。另外一個被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則是一位印度史學家及科學哲學家南達(Meera Nanda)的主張27。她宣稱透過古典印度文本所得來的吠陀梵語(Vedic)28知識是「科學的」。米羅︵Walter Mignolo︶ 不客氣地批評這種研究其實是不偏不倚地掉入了西方基本教義的陷阱;因為它所改變的只是西方學界主張的內容、而非內容背後所依循的邏輯。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更認為這種「照著西方藥單到自己的傳統(或社會文化)去抓藥」的研究,不過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化身─也就是由西方人眼裡看自己的「虛幻角色」(avatars)。它代表著邊陲學者嘗試恢復自信、與西方建立平等對話的努力;但也反映出他們在急於連結本土與主流西方文獻之餘,忽略了其中潛藏的價值與世界觀的重要差異。同樣的,一些學者把「陰陽」歸到西方「二元對立」的傳統模式之下,完全忽略了兩者反映的世界觀在根本上是不相同的。這種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幫助「歐洲中心」論述證明歐洲確是「普世」與「全球」的;即使不是「助紂為虐」,也不能超越既有框架、發展由本土觀點出發的論述。
另外還有一種研究,表面上可能具有所有「本土研究」的形式要件,但是因為這種研究所反映的不是本土、而是西方、甚至資本主義者的需求,因此在本質上與十八、 十九世紀殖民主為殖民所需而作的研究同樣都是「木馬屠城記」中的「木馬」。一九八○年西方學界對於中國組織機構當中「關係」突如其來的興趣,顯然和大陸市場開放之後,西方投資者與中國官僚體系打交道的挫折經驗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這個觀察角度下,所謂「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不過是資本主義進入各地市場的工具而已。 這種研究代表了非西方學界對於研究問題與觀察角度欠缺自主性,以至於那些有權力、影響力的一方就決定了他們所應該從事的研究、以及如何進行這些研究。
由上述分析來看,一項研究是否「真本土」、或「足夠本土」,很難以單純的「是」、或「否」來回答。過去不少學者提出「本土研究」的要件;但是一項具備所有這些要件的研究是否必然就是「真本土」、或「高本土性」研究?似乎又不盡然。這個問題不但牽涉到「本土」與「本土化」的含混定義、資料與研究方法的應用、學術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更牽涉到異質文化的差異是否妥善處理、以及「主體性」的根本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在後面的章節會有更深入的討論,但是由以上的分析來看,經由「本土化」來推展本土學術發展不僅很容易使我們陷入死角,而且「本土化」原來的詞義也仍然是「令外來的事物更適用/適應本土」,其實並不帶有將「本土」轉為行動主體的意思。那麼發展本土學術我們真的不談「本土化」不行嗎?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所有困難,真的是「不夠本土」所造成的、抑或還有其他的問題存在?我們是否陷入了「本土」的泥沼、卻忽略了問題真正的關鍵?換言之,如果我們跳出「本土/外來」的框框去看本土學術發展的瓶頸,可能看到什麼?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