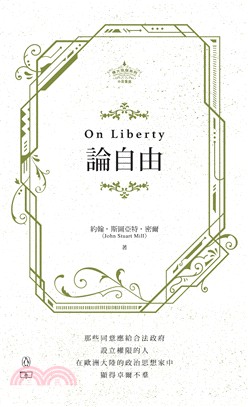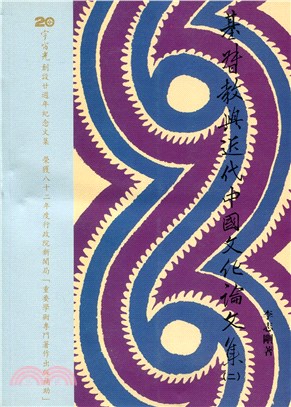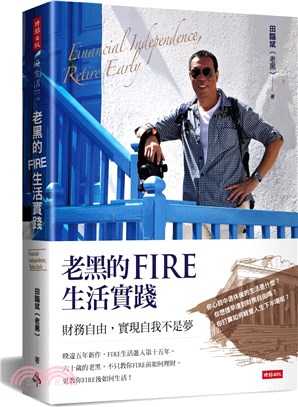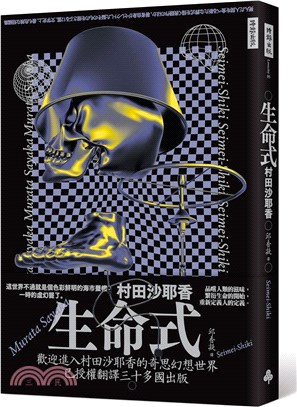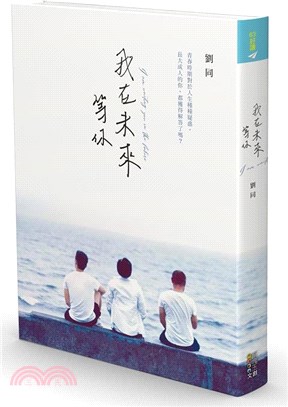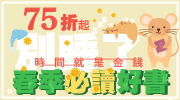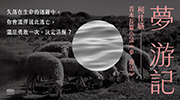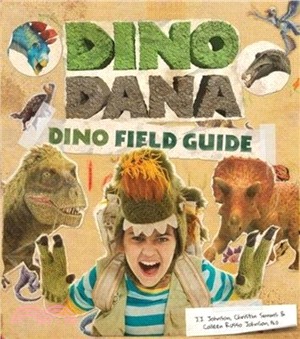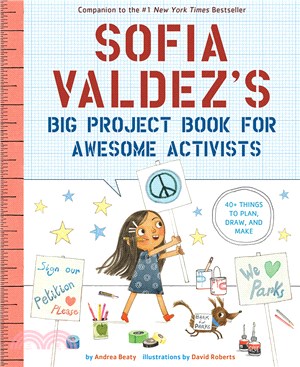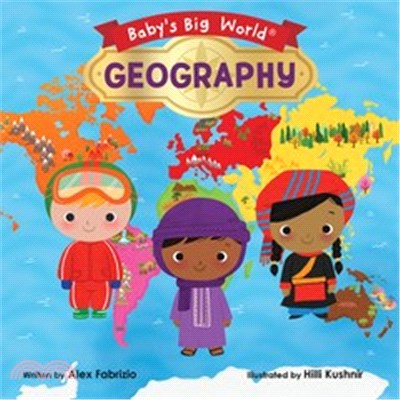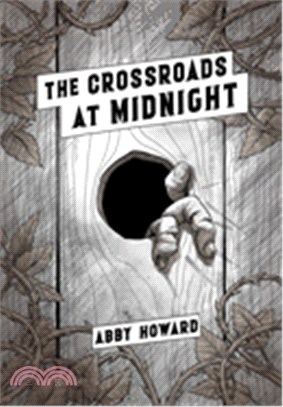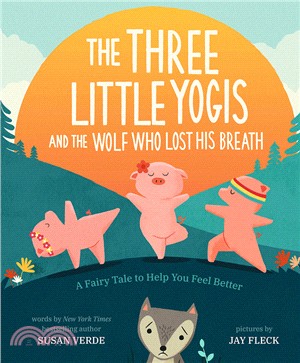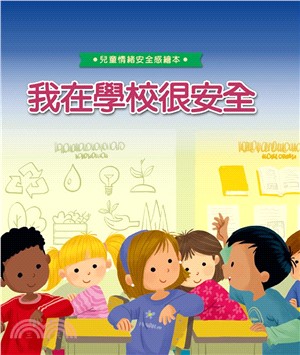論自由 On Liberty(中英對照)
商品資訊
系列名:偉大思想系列
ISBN13:9789620757358
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
作者:[英]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
譯者:牛雲平
出版日:2017/09/15
裝訂/頁數:平裝/325頁
商品簡介
縱觀歷史,有些書能改變世界,這些著作扭轉了我們對自身和他人的看法,甚至引發爭論、產生異見,挑起戰爭,催化革命。這些著作發人深省,激發憤懣,鼓動情緒,提供慰藉。它們使我們的生命變得豐盛,卻同時帶來破壞。
“偉大思想家系列”叢書精挑細選了偉大思想家、先驅、激進分子和夢想家的經典著作,當中的思想曾經撼動世界,也塑造了讀者的人生。
《論自由》討論個人在宗教信仰、思想、言論、個性等方面的自由,研究社會對個人可行使權力的性質和界限,明確提出了“多數人暴政”這一名言,以及“人類無論作為個人或集體,只有出於自衛這唯一目的時,才能干預任何人或人群的行動自由”這個鮮明論點。
作者簡介
序
“偉大思想系列”中文版序
企鵝“偉大思想系列”2004年開始出版。美國出版的叢書規模略小,德國的同類叢書規模更小一些。叢書銷量已遠遠超過200萬冊,在全球很多人中間,尤其是學生當中,普及了哲學和政治學。中文版“偉大思想系列”的推出,邁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歡欣鼓舞。
推出這套叢書的目的是讓讀者再次與一些偉大的非小說類經典著作面對面地交流。太長時間以來,確定版本依據這樣一個假設──讀者在教室裏學習這些著作,因此需要導讀、詳盡的註釋、參考書目等。此類版本無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夠重建托馬斯‧潘恩《常識》或約翰‧羅斯金《藝術與人生》初版時的環境,重新營造更具親和力的氛圍,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當時,讀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沒有其他參照。
這樣做有一定的缺點:每個作者的話難免有難解或不可解之處,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識會缺失。例如,讀者對亨利‧梭羅創作時的情況毫無頭緒,也不了解該書的接受情況及影響。不過,這樣做的優點也很明顯。最突出的優點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變得重要起來──托馬斯‧潘恩的憤怒、查爾斯‧達爾文的靈光、塞內加的隱逸。這些作家在那麼多國家影響了那麼多人的生活,其影響不可估量,有的長達幾個世紀,讀他們書的樂趣罕有匹敵。沒有亞當‧斯密或阿圖爾‧叔本華,難以想像我們今天的世界。這些小書的創作年代已很久遠,但其中的話已徹底改變了我們的政治學、經濟學、智力生活、社會規劃和宗教信仰。
“偉大思想系列”一直求新求變。地區不同,收錄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國或美國,一些作家更受歡迎。英國“偉大思想系列”收錄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則默默無聞。稱其為“偉大思想”,我們亦慎之又慎。思想之偉大,在於其影響之深遠,而不意味着這些思想是“好”的,實際上一些書可列入“壞”思想之列。叢書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叢書其他作家的很大影響,例如,馬塞爾‧普魯斯特承認受約翰‧羅斯金影響很大,米歇爾‧德‧蒙田也承認深受塞內加影響,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發現他們被收入同一叢書,一定會氣憤難平。不過,讀者可自行決定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們衷心希望,您能在閱讀這些傑作中得到樂趣。
“偉大思想系列”出版人
西蒙‧溫德爾
目次
譯者導讀 / vi
一 序言 / 3
二 論思想與討論自由 / 20
三 論個性自由──人類幸福的因素之一 / 76
四 論社會對個人的管制權限 / 103
五 論自由原則之應用 / 133
書摘/試閱
一 序言
本文所論並非所謂的“意志自由”──那個不幸與誤稱為“哲學必然性”的學說相對立的學說,而是“公民或社會自由”,即:社會以何種性質、在何種限度內對個人實施權力才算正當。關於這一問題,尚無人概述及或浮泛而論,但其隱性存在卻深深影響着當前的種種現實論爭,並將很可能迅速成為未來的關鍵問題。這一問題絕非新生事物,在某種意義上,人類幾乎自誕生之初就被它分裂為不同羣體。然而,人類中相對文明的羣體如今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新階段、新形勢下,公民自由問題浮現而出,需要人類提出更具實質性的新對策。
自由與威權的鬥爭是我們熟悉的某些歷史階段的最顯著特徵,在古希臘、古羅馬和英國歷史上尤其如此。不過,古代的鬥爭是臣民或臣民中某些階層與政府之間的鬥爭。自由意味着受到保護,免遭政治統治者的暴政之害。統治者們(古希臘某些平民政府中的統治者除外)被認為與其治下的民眾必然相互對立。他們或是居於統治地位的個人,或是一個部族或階級;其威權或由繼承而得,或借征服獲取。他們的權柄絕非民眾可任意予奪,只要有可防範其強權鎮壓的法子,民眾便不會冒險或許也並不願去爭奪他們的尊位。統治者的權力被視為不可或缺但也極其危險之物,是一種既可用以對抗外敵亦可毫不猶豫地對抗臣民的武器。若要防止鷲羣中的弱小成員慘遭眾禿鷲捕殺,則需委派一隻最為強悍的禿鷲做首領,以制伏其他禿鷲。然而,禿鷲王之嗜好劫掠鷲羣,絕不亞於那些勁量略小的兇鷲,所以必須永遠警惕其尖喙與利爪。故此,那時愛國志士的目標就是為統治者設定權限,防止其對民眾濫施權力;這種設限行為就是他們意謂的自由。設限方式有兩種:第一,獲得統治者對某些名為政治自由或政治權利的承認。統治者若侵犯這些自由或權利就是瀆職,他若果真悍然侵犯,那麼民眾進行某種抵制甚或全民造反就屬合理合法。第二,建立憲法作為制約手段。總體而言,這一方式發生較晚。據此,統治者若想採取某些較為重要的行動,必須先徵得民眾或被認為代表着民眾利益的某個組織的同意。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統治者都或多或少地被迫服從於第一種設限方式,但並未服從第二種方式。使第二種方式奏效,或者在其已部分奏效的情況下使其完全奏效,就成為各國自由愛好者的主要目標。只要人類滿足於靠一個敵人對抗另一個敵人,滿足於接受某個主人的統治──前提是他多少可以有效地保證不對他們實施暴政,他們便別無祈望。
但是,在人類事務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這樣一刻:人們意識到,由與自己利益對立的他者充當統治者,並非天然法則。他們感到,更好的辦法是,應該讓國家的各種官員充當他們的租戶或代表,他們可以隨意解約,遣散這些官員。似乎惟有如此,才能絕對確保政府權力不被濫用,他們的利益才不會受損。漸漸地,不論何處,只要存在平民政黨,這種靠選舉產生臨時統治者就會提出新的需求,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前限定統治者權力的做法,成為該政黨的主要奮鬥目標;他們力圖使統治者產生於被統治者的周期性選舉。發展到後來,一些人開始感到,以前太看重限定權力本身這件事了。當統治者利益與民眾利益對立時,限定其權力(似乎)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現在所需要的是,讓統治者認同民眾,讓統治者的利益和意志與全體國民的利益和意志合一。國家不必防範自己的意志,不必擔憂其會對自己實行暴政。讓統治者完全向全體國民負責,國民可以隨時罷免他們,因為國民可自主決定權力的用途,所以可放心將權力託付給他們。統治者的權力正是全體國民自身的權力,這種權力高度集中,便於行使。這種想法或感覺,曾普遍出現於上一代歐洲自由主義者之中,並在今天的歐陸自由主義者中仍佔主流地位。那些同意給政府──他們認為非法的政府除外──設立權限的人,在歐陸的政治思想家中顯得卓爾不羣。我國的形勢也一度鼓舞了與這些自由主義者想法類似的論調,倘若後來情勢未改,這種論調如今可能已甚囂塵上。
然而,與人生經歷一樣,在政治和哲學學說中,失敗可能會掩藏各種缺陷與弱點,而成功則會暴露它們。當平民政體僅存於夢想或遠古歷史的傳聞之中時,人們無需限定自己對自己行使的權力,這種觀念似乎不爭自明。法國大革命之類的暫時性社會騷亂也全然沒有動搖這一觀念。在此觀念中,那些最糟糕的騷亂乃是少數篡奪者造成的;它與大眾機構的常規運作方式毫無關係,而是反對國王獨裁和貴族專制的突發事件。但是,後來一個民主共和國佔據了巨幅的國土,且竟然躋身世界強國之列;這一重大事實使人們開始關注和評論選舉制、責任制政體。此時,世人方才意識到,“自治”、“人民對自我行使的權力”等詞語並未表達事情的實相。行使權力的“人民”與作為權力行使對象的人民並不總是同一羣體;所謂“自治”並非每個人自我管治,而是一切別人對他進行管治。而且,“人民的意志”實際上意味着人民當中人數最多或最活躍的羣體──即多數派,或那些成功將自己打造為多數派的人──的意志。於是,人民可能會有壓迫自己當中部分羣體的意願。這種情況同其他形式的權力濫用一樣,都需嚴加防範。因此,即便掌權者要定期對全民──即其中的最強大派──負責,限定政府對個人的權力仍然至關緊要。上述主張不僅受到思想家們的支持,也獲得了歐洲社會中重要階層的青睞──因為民主政體會損害其實際利益或假定利益,順利成為了主流觀點。現在,各種政治理論已普遍將“多數人的暴政”列為社會需警惕的罪惡之一。
如同其他暴政一樣,多數人的暴政主要是通過公權機構的行為實施的,從其誕生至今,令人恐懼不已。但富有思想的人們意識到,倘若社會這一集體本身即是凌駕於其每一單個成員之上的暴君,那麼其暴虐手段之豐富,將絕不限於它通過其官吏所實施的那些行為。社會有能力也確實執行着它自己的種種命令:如果發出的命令並非正確的,或者竟對無權插手的事情濫發號令,那麼它就是在實行比許多其他政治壓迫更可怕的社會暴政。這是因為,它雖然通常不以極刑威懾單個成員,卻能更深刻地滲透到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束縛住個體的靈魂,令其無可逃遁。因此,保護人們免遭官員的暴政並不足夠,還需保護他們免遭主流意見和大眾感覺的暴政,免遭社會的暴政:社會傾向於用民事處罰之外的手段,將自己的主張和做法當作行為規範強加於那些持異議者身上;它傾向於束縛任何與己相左個性的發展、儘可能防止這種個性的形成,並迫使所有的性格特點以社會自身為模型進行自我塑造。所以,集體意見對個人獨立性的合法干預是有界限的。發現這一界限,並保護它免遭侵越,同保護人們免遭政治獨裁之害一樣,對維護人類事務的健康狀態而言不可或缺。
然而,一般說來,雖然上述主張通常不太可能遭到反對,但把這一界限設在哪裏──如何在個人自主與社會管控之間進行恰當調整,卻幾乎是個毫無頭緒的全新問題。所有人們珍視的生存價值,都有賴於對他人行動的切實約束。因此,必須要強制實行某些行為規範;其手段首先是法律,在許多法律不適用的事項上則要借助輿論。這些行為規範應該是甚麼呢?這一點就成為人類事務中的重大問題。而倘若我們排除少數最顯著的例子,就會發現,它乃是人類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沒有哪個時代、哪個國家對其解決方案與其他時代、其他國家雷同;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對它的判定會令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國家大為震驚。然而,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人們全渾然不覺其解決之難,似乎人類歷來對其看法並無二致。在他們心目中,自己所建立的規程是不言而喻更自證自明的。這種幾乎普遍存在的錯覺便是一個例證,足以證明習俗之神奇影響。習俗不僅是諺語所說的第二天性,還屢屢被錯當成了第一天性。在防止人類對彼此強加的種種行為準則產生疑慮方面,習俗的效果格外徹底。那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在這一問題上,無論人與人之間,還是個人,都不需講甚麼理由。人們已習慣於相信,也因為受那些嚮往哲學家風範的人鼓動而相信,在這類問題上,他們的感覺比推理更重要,所以推理毫無用處。指導他們形成人類行為規則的實用原則就是每個人心中的感覺:所有人都必須像他或他贊成的人所希望的那樣行動。事實上,誰都不肯向自己承認,他的判斷標準只是個人偏好;一個毫無理據的、衡量某個行為的主張,只能算是個人偏好;就算他明瞭理由,倘若這些理由僅僅是喚起其他人感覺中的類似偏好,那也仍然只是許多人的個人偏好罷了。不過,對普通人而言,他獲得別人支持的個人偏好不僅僅是一個完美無瑕的理由,而且是他用以判斷自己所有的道義觀、趣味觀或得體觀的唯一依據,甚至也是理解自己宗教信條的總指南,儘管他的道德觀、趣味觀或得體觀都並未明確寫入其宗教信條當中。相應地,人們對甚麼值得讚美、甚麼值得譴責的看法,是受到一切五花八門動機影響的。那些動機繁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對他人行為的期望;而他們關於任何其他事物的願望,同樣受到數不勝數的誘因的影響。這些動機有時是他們的理智,有時又是某些偏見或迷信,經常是對社羣的喜愛之情,也經常是對社羣的厭惡之情──羨慕或嫉妒、傲慢或輕蔑,但最通常是他們自己的各種慾求或畏懼──即他們那合法或非法的一己私利。無論哪國,只要存在某個佔據支配地位的階級,該國的道德觀就會源於此階級的階級利益以及階級優越感。斯巴達人與其奴隸之間、種植園主與黑奴之間、王侯與臣民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道德準則,多半就是階級利益和階級優越感的產物。由此產生的種種是非觀念又作用於該權勢階級內部成員的道德觀,影響着他們彼此的關係。反觀之,無論哪國,只要存在一個喪失了支配地位或其支配地位已不得人心的權勢階級,該國盛行的道德觀念便往往帶有對優越感不耐煩甚至厭惡的痕跡。對於已被法律或輿論強加的各種將行和緩行的行為規範,還有一大決定性原則:人類會想像其俗世主人或天上神靈之好惡,並屈己以從。人類這種奴性雖然本質上是自利的,但並不虛偽;它產生的是十足真誠的憎惡之情,驅使人們燒死了巫師和異教徒。許多惡劣因素都會影響道德觀念的走勢,社會那些普遍且顯著的利益無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大因素。然而,與其說這些社會利益本身是道德觀念的產生原因,不如說它們是道德觀念派生的喜惡之情所造就的結果。原本與社會利益無關的人類喜惡之情,在道德觀念的建立過程中赫然突顯,威力驚人。
這樣,社會之好惡,或其中某強勢羣體之好惡,乃是實際決定道德規範的主要事物。全體成員都要遵循那些規則,否則便會遭到法律或輿論的懲罰。總體而言,那些思想和情感超前於社會的人原則上都會對此情形聽之任之,但在某些枝節問題上可能與之發生牴牾。他們忙於探尋社會應對哪些事物產生好惡,而不是質疑社會之好惡應否成為個人必須遵守的法律。他們更樂意努力改變人類對他們持有異見的具體事項的看法,而不願與其他異端分子一起,共同致力於捍衛自由。只在一件事上,他們不再單打獨鬥,而是依理佔據了制高點且堅守始終;這件事就是宗教信仰。做此事有很多益處,尤其是它極為醒目地表明,所謂道德感是多麼不可靠:一個頑固者心中“神學家之間的憎恨”是道德感表現最直白的事例之一。第一批打破自詡為“普世教會”組織之枷鎖的人,通常與該教會一樣,不願容忍異己的宗教主張。而一旦衝突結束,哪一方都沒有獲得完勝,每個教派都會被弱化,各教派都會把期望值降低到能夠維持既有的地盤就行;少數派發現沒有機會變成多數派,只得懇求那些他們無法改變其信仰的人,允許他們持有不同宗教主張。這樣,幾乎僅僅在宗教信仰的戰場上,才存在個人有權利反對社會原則的理據,才能公開駁斥社會有權管轄異見分子的說法。那些給世界帶來了宗教自由的偉大作者大都堅稱:良心自由是一項不可廢除的權利,並徹底否定了“個人有義務向他者解釋自己宗教信仰”的觀點。然而,人類天生對自己真正關心的一切不容異議;除了個別宗教觀念淡漠的地方,人們因厭煩神學爭論而贊成宗教自由之外,宗教自由在任何國度都沒有真正實現過。幾乎所有宗教信仰者心中,對信仰自由義務的承認都是暗自有所保留的;即便在那些最寬容的國家,情況也是如此。有人會做到容忍教政問題上的異見,但不會容忍教義問題上的異見;有人能寬容任何人,卻不能寬容天主教徒或唯一神論者;有人則能寬容任何人,卻不能寬容天啟教信徒;有些人的寬容度稍大,但不能容忍對任何神靈和來世的信仰。無論何處,只要大多數人的宗教情感仍然真誠而熱烈,要求全員遵從宗教的呼聲就高漲不退。
相比其他歐洲國家,英國政治歷史情形特殊,所以其法律的枷鎖較輕,而輿論的枷鎖較重。英國人對立法或執法當局明目張膽干預私人行為的事情十分戒備。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維護個人獨立的公正考慮,而是出於將政府視為公眾利益對立面的思維習慣。大部分英國人都尚未感覺到政府的權力就是他們自己的權力,或政府的主張就是他們自己的主張。他們若果真感覺如此,個人自由就很可能像遭到輿論侵犯那樣,面臨政府侵犯的威脅。然而,直至今日,他們仍有一股強烈的情感,可以隨時喚起:抵制法律在它以前未曾管轄過的事情上對個人進行管制的任何企圖;可他們在這種情感升騰時,卻毫不分辨所涉事項是否屬於法律管制的範疇。因此,此種情感雖然總體而言十分有益,但很可能在具體事例的處理上對錯參半。事實上,並不存在一種公認的原則可常規衡量種種政府干預是否正當;人們的判斷依據就是其個人好惡罷了。有些人不管發現有善事需實行,抑或有惡事需矯正,都很樂意鼓動政府採取行動;而其他人則寧願承受幾乎所有的社會弊病,卻不肯增加一項允許政府管控的新事物,使人類受益。在任一具體事例中,人們是屬於前一羣體或後一羣體,要看他們大體懷有哪種感覺;倘若那件事被提議由政府作為,就要看他們對此事的興趣度如何,或者看他們是否相信政府會按他們的意願作為。判斷他們屬於哪一類羣體,不要看他們對政府適合做甚麼是否持有始終如一的意見。在我看來,缺乏公認衡量原則或規則的後果是,這一派與那一派同樣常常出錯,他們錯誤調用和錯誤譴責政府干預的頻率大體相當。
本文旨在宣明一條十分簡單的原則,以完全監管社會強迫以及控制個人的方式,無論是法律刑罰的肉體暴力或公共輿論的精神威壓。該原則就是,人類無論作為個人或集體,只有出於自衛這唯一目的時,才能干預任何人或人羣的行動自由。違反其意志,對一位文明社會的成員正當行使權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傷害他人。個人的物質或精神利益不足以作為對其行使權力的正當藉口。“那樣做是為了他好”、“那樣做會使他更幸福”、“在別人看來那樣做很明智甚或非常正確”,這些都不是強迫接受或忍受管制的正當理由。我們可以提出許多充足的理由抗議、與之理論、說服或懇求,但沒有充足理由逼迫或告知,他如若不然必將自吞惡果。要證明這一做法的正當性,必須估算出,要阻止其從事的那一行為會對他人產生何種惡果。任何人需要對社會負責的那些行為都必須是關聯他人的;對那些只與個人有關的行為,他都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個人是自己身體和精神的君主。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