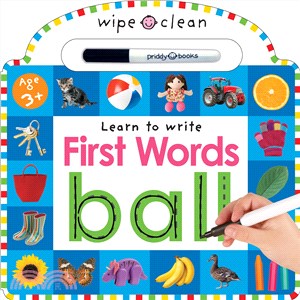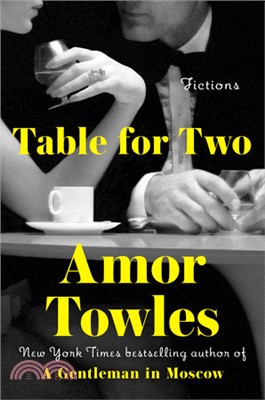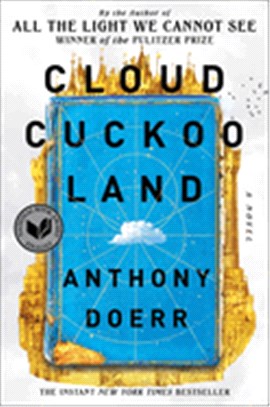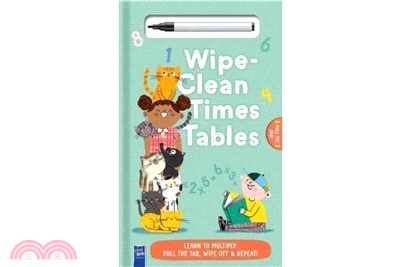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本書聚焦大眾教育中的“平等―效率”困境。如今的很多教育研究將目光投向教育改革,人們期待那些改革能關注平等機會這個問題。西方國家的學校也探索了許多替代方案,諸如去分層化、更靈活的課程、重視子女的自我觀感勝過重視他們的學業成績、通過測試來確保沒有子女掉隊,以及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選擇。本書研究者收集到的證據表明,儘管展現了一些進步的可能通道,他們仍然對於很多學校所採取的激進的改變機會結構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根據目前所知,人們不宜期望短期能出現奇跡。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一個高效的教育體系來挑戰每位受教育者,讓他們都實現自己的潛力。在那個意義上,一個高效的教育體系也有助於實現平等。
作者簡介
Ludger Woessmann 是德國慕尼黑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著名教育經濟學專家,教育經濟信息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他因其在教育的基礎效應方面的重要研究獲得 Gossen Prize獎,2017年獲得 Gustav Stolper Prize獎。
Paul E. Peterson 哈佛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教育改革領域的先鋒學者。
譯者杜振東,講師,碩士導師,研究方向:英漢口筆譯研究;有若干譯作出版
Paul E. Peterson 哈佛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教育改革領域的先鋒學者。
譯者杜振東,講師,碩士導師,研究方向:英漢口筆譯研究;有若干譯作出版
名人/編輯推薦
在尋求平等的過程中,人們忽視了教育效率和平等的互補性。在我們龐大的學校體系中,如果能實現效率的最大化,這對於公平的貢獻很可能將遠遠大於現在正在實施的許多改革。
目次
目 錄
叢書序言1
鳴謝1
第一部分問題所在
1引言: 學校與平等機會問題
Paul E. Peterson和Ludger Woessmann
2英國的教育擴張與代際流動
Stephen Machin
3教育和終生收入: 來自瑞典的年齡-收入概況縱向追蹤調查
Sofia Sandgren
第二部分解決方案A: 改變同伴群體?
4北卡羅來納州公立學校的同伴效應
Jacob Vigdor和Thomas Nechyba
5英國中等學校選拔的非均勻效應
Fernando Galindo-Rueda和Anna Vignoles
6學校分層教育的最佳時間: 一個以德國為例的一般模型
Giorgio Brunello, Massimo Giannini和Kenn Ariga
第三部分解決方案B: 重新聚焦資源?
7美國如何改變教育成果的分佈
Eric A. Hanushek
8荷蘭人力資本政策對弱勢群體的有效性
Edwin Leuven和Hessel Oosterbeek
9通過教育-財政改革為美國的種族和社會經濟群體提供平等機會
Julian R. Betts和John E. Roemer
第四部分解決問題還是惡化問題?標準與選擇
10美國教育改革與弱勢群體學生
John H. Bishop和Ferran Mane
11英國中學教育中擇校對于學生基於能力與社會經濟因素分流影響的研究
Simon Burgess, Brendon McConnell, Carol Propper和Deborah Wilson
12意大利公眾對公立學校印象質量對私立學校選擇的影響
Daniele Checchi和Tullio Jappelli
叢書序言1
鳴謝1
第一部分問題所在
1引言: 學校與平等機會問題
Paul E. Peterson和Ludger Woessmann
2英國的教育擴張與代際流動
Stephen Machin
3教育和終生收入: 來自瑞典的年齡-收入概況縱向追蹤調查
Sofia Sandgren
第二部分解決方案A: 改變同伴群體?
4北卡羅來納州公立學校的同伴效應
Jacob Vigdor和Thomas Nechyba
5英國中等學校選拔的非均勻效應
Fernando Galindo-Rueda和Anna Vignoles
6學校分層教育的最佳時間: 一個以德國為例的一般模型
Giorgio Brunello, Massimo Giannini和Kenn Ariga
第三部分解決方案B: 重新聚焦資源?
7美國如何改變教育成果的分佈
Eric A. Hanushek
8荷蘭人力資本政策對弱勢群體的有效性
Edwin Leuven和Hessel Oosterbeek
9通過教育-財政改革為美國的種族和社會經濟群體提供平等機會
Julian R. Betts和John E. Roemer
第四部分解決問題還是惡化問題?標準與選擇
10美國教育改革與弱勢群體學生
John H. Bishop和Ferran Mane
11英國中學教育中擇校對于學生基於能力與社會經濟因素分流影響的研究
Simon Burgess, Brendon McConnell, Carol Propper和Deborah Wilson
12意大利公眾對公立學校印象質量對私立學校選擇的影響
Daniele Checchi和Tullio Jappelli
書摘/試閱
1引言: 學校與平等機會問題
Paul E. Peterson和Ludger Woessmann
杜振東譯
作為一個教育目標,平等機會是個新鮮事物。自1763年從普魯士開始,到19世紀末,基本上所有西歐國家以及美國都實施了由國家出資的大規模初等義務教育1。但是直到近幾十年,大眾教育的主要目的,正如那些代表大眾教育而為之奔走呼號的人們所表述的那樣,既不是為了促進社會流動性,也不是為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是為了挽救靈魂、培養忠誠的公民,以及促進經濟生產力(Peterson 1985; Gradstein, Justman和Meier 2005)。任何平等主義的後果都只是意外而已。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社會主義黨派走上歐洲的政治舞臺,對於平等教育機會的要求得到了強化,多數國家對幾乎所有的年輕人打開了學校之門,至少到16歲。中等教育在美國開展得甚至比歐洲還要早,儘管不是沖著同樣的平等機會的理念去的。但是這一點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而發生了變化,因為民權運動的領導者堅持教育必須既取消種族隔離,又是平等主義的。隨著這些事件的深入,研究的議程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James Coleman的先驅性著作之後(比如可參見Coleman等1966)。他的著作引領了隨後的大部分學術研究議程――包括在本卷發表的這些論文。
如今很多教育研究仍然聚焦於那些改革,人們期待那些改革能關注平等機會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倡導者的期望值非常高。延長受教育的年限,即貫穿青春期,乃至成人期的早期,人們預期這樣會讓下一代更加平等。向下延長受教育年限,讓入學年齡變得更小,人們預期這樣可以給缺失足夠的家庭激勵以補償。
人們期望通過將財政資源集中在貧困人口的教育上,也能達到類似的目的。
將能力和背景迥異的學生混合在一起教育也大行其道,人們希望這樣一來,那些處於較劣勢地位的學生可以向其他人學習。人們也實施了問責制度,確保教育能夠面向所有學生,甚至那些起點較低的學生。同樣,人們通常也認為,通過擇校,貧窮家庭有可能獲得只有富裕家庭才能享受得到的教育機會。
本卷收錄的各篇論文,最初是2004年9月在德國慕尼黑舉辦的一次國際會議上宣讀的論文。這些論文探討了在發達工業社會裡,上述以及其他旨在實現平等教育機會的學校改革的結果,主要聚集歐洲和北美國家。該次會議由CESifo和哈佛大學的“教育政策和治理項目”聯合主辦。
1.1為何學校未能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 平等機會的雙重含義
儘管人們對此主題興趣濃厚,然而對於平等教育機會的含義卻莫衷一是。一些人認為,平等的教育機會僅僅意味著在學校建制之內所有人獲得相同的待遇,而且每個人得到與其能力相匹配的教育,這樣一來,所有人都獲得了同樣的機會來增強他們入學時所具有的不同能力。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平等的教育機會要求學校彌補一些孩子入學時的能力不足,這樣下一代的哪些成員可以在未來社會平步青雲,就完全是由隨機因素來決定的。
對於持第二種觀點的人來說,本書收錄的這些論文可能會讓他們失望。總體來說,這些論文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人們提出的很多學校改革,都很難指望切實改變一個社會的機會結構。讀完本論文集,讀者難免會得出與George Counts曾經得出過的大同小異的結論。此人是一個激進的悲觀主義者。在大蕭條期間,他寫了《學校敢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嗎?》(1932)一書,對書名提出的問題他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從George Counts的那本書面世到現在,情況似乎沒有發生多大的改變。
但是,人們應不應該就此極度悲觀,卻取決於他們如何去理解平等教育機會。
大多數學校官員,或者說實際上人們中的大多數,即使在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美國的民權運動之後,仍然不指望學校可以深刻地改變社會結構。很少有人同意那種中規中矩的言論,即“學校應該讓每一代人的機會平等化”,事實上是,“人們自然而然地希望給自己的子女某種優勢”(Hochschild和Scovronick 2003,2)。他們反而希望學校對學生的一切全盤接受,無須去改變學生身上深受家庭影響而形成的各種品質。
的確,大多數人希望是家庭溫暖的懷抱,而不是國家提供的冷漠的教育,去承擔確保其下一代長期福利的主要責任。大多數家長奉獻出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財力來增進他們子女的福祉。父母雙全對於子女來說比單親家庭要好。部分原因在於,如果家庭能有更多的財力用於教育,孩子也許會學習得更好。但是,儘管財力也許很重要,父親也的確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母親付出的時間和才華,卻證明具有最重要的意義。母親的才華可以通過她的稟賦和所受的教育來獲得最好的測度(White 1982; Meyer 1996; Jencks和Phillips 1998; Rothstein 2004)。在絕大多數家庭,母親的關懷、談話和教導起了主要作用。
這必然會導致不平等。家庭的質量各不相同,也許如今比過去更加不同,至少在美國是這樣。有些父母擁有巨大的個人和職業資源用來奉獻給他們子女的福祉。而有些父母則自顧不暇,更談不上顧及子女了。現代社會的兩大變化也許在凸顯家庭之間的差異。一方面,婚姻伴侶日益從稟賦類似的人群中選擇,特別是當女方成為養家糊口者之後更是如此(Oppenheimer 1988; Mare 1991)。另一方面,占比日益增多的子女是單親家庭撫養長大的。這些趨勢也許將加劇教育的不平等。雙收入家庭,相比單親家庭,更能給他們子女的教育奉獻更多的時間、才華和財力資本(Jencks 1979; McLanahan和Sandefur 1994; Neal 2006)2。
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潛力至關重要,而學校能做的貢獻必然是很有限的。各國學生在校的時間不同,孩子在校的時間大約為每日6個小時,每週5天,占一年中四分之三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內,他們處於老師的照看之下,但老師通常負責照看的並非1到3個孩子,而是大概10到30個。即使極具敬業精神的專業教師,論及對孩子的付出,相比起父母而言也無法等量齊觀。父母天生會深切關注子女的幸福。正如一些最好的教師常常解釋的那樣,家庭為子女的成長提供方向,教師在改變其軌跡方面能力非常有限。
家庭是所有社會化機構中最強有力者,對此古人也十分了然。希臘哲學家柏拉圖(1992)對家庭的影響力就心知肚明。他建議,未來國家的保護者,應該很小的時候就從家庭中脫離出來,被安置在一個高度結構化的教育環境中撫養,以確保他所謂的哲學家國王能夠獲得所需要的綜合素質。現代的柏拉圖主義者諸如Hochschild和Skovronek(2003,如上所引),為了實現他們的平等主義夢想,可能會不得不建造一個綜合的義務性的大眾住讀教育體系,在該體系內,不僅國家的未來保護者必須要儘早被帶離家庭,而且所有的孩子都要這樣,以便脫離高度多樣化的家庭的影響。
所以如果認為平等機會意味著義務教育結束之時學生的成績是同等的,那麼可以相當確定的一點是,那種平等主義的理想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倘若這種觀念付諸實施,大多數人都會加以抵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如此。試想我們告訴那些執著的父母們,那些孜孜以求致力於子女教育的父母們,因為他們這種做法,他們的子女將會被安置到一個不利的學校環境中去。只有這樣,其他得不到父母足夠支持的孩子們才可以趕上來。很難設想有哪個社會會沿著這樣的思路進行組織。
然而,平等教育機會也許可以更加狹義地進行構想。如果所有走進校門的孩子被給予了相同的機會來增進他們剛入校時的稟賦,那麼也可以說是學校機會平等。有了這樣一個對平等機會的解釋,那麼人們就不會再指望什麼結果平等,而是會滿足於除了學校干預發生以前就存在的之外,不再有額外的不平等。公共提供的機會將是平等主義的,因為學校提供的附加值對於所有孩子都將是相似的。在這樣一個世界裡,社會不公平仍將存在,但是公共學校體制將不用對這種不公平的加劇和永存負責。
1.2不同國家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影響
正是這第二種更加局限的對於平等機會的理解,似乎在大部分現今教育中大行其道。在大多數發達工業社會裡,學校似乎沒有做多少工作來試圖改變機會結構的發展方向(Anderson 1961)。在教育系統得到巨大擴張的社會裡,家庭背景的影響仍然十分強大。比如,近期由第三次“國際數學和科學評測”(TIMSS)從國際測試成績數據中獲取的證據表明,家庭背景對於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十分巨大,所有參加測評的國家概莫能外。而且歐洲家庭的平均影響值與美國的十分接近(Woessmann 2004)。
在表1.1中,我們報告了來自一個更加新近的國際測試的相似證據。此測試即2000年舉辦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主辦,針對各國具有代表性的15歲學生樣本群體進行測評。平均而言,在這個測試中,10年級學生比9年級學生的成績高出了30分。測評結果還顯示,在歐洲最大的三個國家(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學生的學業成績都與下列家庭背景特徵強相關: 父母的職業、就業狀況、原住國、家庭狀況,以及家中藏書數量。
出於好幾個原因,家中藏書的數量可以被理解成學生家庭在教育、社會和經濟背景方面的一個強大的、無所不包的代表,在社會學研究中經常被提及和用到(例如De Graaf 1988; Esping-Andersen 2004)。總的來說,大量藏書意味著一個高度重視教育、推動子女取得學業成就的家庭環境(參見Mullis等2004),代表了父母的社會背景,並且是經濟實力的寫照,因為書是需要用錢買來的。家中藏書的數量一再成為國際學業成就測試中學生成績的最重要的預測指標。此外,Schütz, Ursprung和Woessmann(2005)通過另一組不同的數據研究表明(至少對數量有限的幾個擁有該統計數據的國家而言),家庭收入(PISA中未收集)和家庭藏書量之間的相關性在這幾個國家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
鑒於家庭收入也許是家庭背景“理想的”測度,因此至少從經濟的角度,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強了將家庭藏書量作為進行跨國比較分析時全面代表家庭背景量度的有效性。相較而言,其他的家庭背景(比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代表指標的跨國可比性可能有限,比如各國之間特定的教育項目的含義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如果用家庭藏書量來作為反映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有助於學生學習的家庭特徵的國際可比性指標,那麼會發現家庭藏書在500本以上的15歲學生,其PISA測試的成績相比家中藏書不足10本的學生,要高出2到3個學年的水平(表1.1)。家庭背景的影響不僅在這四個國家中表現很明顯,而且其大小在德國和美國十分接近。對英國學生的影響只是略小一些。如果假定高中學習成績對未來取得經濟成功影響很大――正如許多研究表明的那樣(比如Bishop 1992; Murnane, Willett和Levy 1995; Neal和Johnson 1996; Currie和Thomas 2001),那麼會發現在這三個國家中,學校教育體系似乎並沒有帶來特別高的社會流動率。必須承認,家庭藏書量對學習成績的影響在法國似乎要輕一些,但即使在這個國家,家中藏書超過500本的學生相比家中藏書不到10本的孩子,其成績也要好出兩個學年的水平。
在這四個國家中,家庭背景對於學生的成績都有著重大影響,然而很可能法國教育體制中的某些特徵緩和了這種衝擊。法國因其“幼兒學校”而著名。該體制為來自一切背景的孩子提供廣泛的學前課程。近期Schütz等人(2005)提供的國際比較證據表明,學前課程(以及綜合教育)的普及的確與各國更高的社會流動性之間具有系統性關聯。而很多其他的教育政策則與之關聯性不大。這一發現也與本書中(第8章)Edwin Leuven和Hessel Oosterbeek提供的對荷蘭的研究成果相一致。他們的研究顯示,降低義務教育入學年齡,並在標準年齡以前實現普及教育,的確是五種教育干預當中唯一能夠改善劣勢學生群體教育成績的那一種。
同時,其他國家的教育體制可能會強化家庭的影響。比如,德國強調在人生早期就為某個特定的職業做準備,這也許會將學生置於與其父母類似的社會角色。在美國,由於學校政策制定的去中心化,加上廣泛的因種族與收入因素導致的居住區隔離,可能會強化現有的社會模式。Steve Machin在其關於英國高等教育擴張的論文(第2章)中指出,英國高等教育的擴張強化並增進而不是緩解了社會差別。富裕家庭的子女相比工人階級家庭的子女,更加傾向於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因為高等教育受到政府的大幅補貼,所以其淨效應是一種強化社會差別的有組織的安排,這與平等主義者對教育擴張的期待背道而馳。
1.3學校教育的最初目的
一旦人們明白所謂平等主義原則在西方大眾教育史中僅僅發揮了微乎其微的作用,就不會詫異於教育擴張有時會強化而不是緩和社會不公平。而英語中“學校”(school)這個詞本身其實是從希臘語“休閒”(leisure)派生而來的,因為在古雅典,只有那些可以將自己從體力勞動的義務中解脫出來的人,才有能力享受教育(Drucker 1961)。在後來學習僅僅局限於修道院內的幾百年裡,情況也沒有發生改變。對大眾而言,在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閱讀簡直是不可能的。古騰堡的活字印刷術在16世紀早期得到廣泛傳播,實現了將話語迅速印製成文字,並讓王宮、城堡和修道院之外的人們獲益。
宗教改革者們,無論是披著路德派還是加爾文派的外衣,都極力利用這個新發明所帶來的各種可能性,敦促信眾閱讀《聖經》,而不是依賴牧師的訓誡、教堂的繁文縟節,或者僧侶的想像(Pelikan 2005)。由於個人需要而閱讀《聖經》,於是讀寫能力迅速擴散,特別是在歐洲北部大部分地區,以及後來北美大陸的北部大部分地區,因為新教在上述地區紮下了根。即使到今天,上述地區仍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區。
如果說教化的初衷是宗教,那麼其後果卻是經濟,因為教化的擴張促進了財富的產生。馬克斯·韋伯(2001)將新教國家擁有更快的經濟增速歸因於這些國家擁有更高的儲蓄率,因為這些地方有一個要求信徒延遲滿足需求的信仰體系。但是資本主義在新教國家成了氣候,更可能的原因是,旨在閱讀《聖經》的教育催生了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人力資本6。一個類似的觀點認為,人力資本驅動取得經濟成功起源於宗教,乃是因為自8世紀以來,猶太人選擇了城市熟練手工業者和商人作為其職業。Botticini和Eckstein(2005a, 2005b)從人為資本的角度來解讀猶太人的歷史,指出經商的猶太人取得經濟成功,根源在於一個傳承數個世紀的猶太人戒律,該戒律要求猶太男子必須能在會堂中閱讀《律法書》(《舊約》前五卷的總稱,譯者注)並教其兒子們閱讀《律法書》。
在歐洲,因為宗教狂熱的衰退,政治考量異軍突起。一旦一個大規模的教育系統對民族國家的增強作用明顯不亞于一支公民軍隊,政治領袖們就會看在眼裡。儘管公共學校起源于荷蘭,但對公立教育和國家建設之間的關係理解得最透徹的卻是俾斯麥,這導致產生了一句警句:“在創造了德意志帝國的1870年普法戰爭中,普魯士的小學校長打敗了法國”(Drucker 1961,21)。儘管德國的鐵路也許跟那場戰爭的結局關係更大,而不是其學校,但那句警句的確是有真理的成分。面對統一那些雖然語言相通,但方言無數的各個政治轄區的重任,俾斯麥利用學校來打造共同語和國家意識(Lamberti 1989; Gradstein, Justman和Meier 2005, ch. 2)。他的成功啟發歐洲的鄰國紛紛效仿。
在大西洋彼岸,政治目標也沒有小到哪裡去。在美國,所需要的不是合併以前分崩離析的政治區劃,而是接納一波又一波湧入的移民,這些移民語言各異、禱告的方式也不同。對於Horace Mann和其他打造了共同學校的人而言,歐洲南部和東部過來的移民,其文化遺產不一樣,因此“需要道德提高”以及用英語語言進行教導,而這兩者他們都認為可以通過國家開辦的、新教控制的公共學校來實現(Kaestle 1983; Glenn 1987)。
然而,關於學校可以成為經濟增長引擎的觀念在當時仍然沒有得到確立。對於很多工商界人士,學校只不過是一項高成本的公共開支罷了,浪費了本來可以用於更有效的用途上的資源。
如果公共學校可以略微出類拔萃,那麼它們應該致力於為具體行業或者職業培養學生,他們才是工業經濟的中流砥柱。Peter Drucker(1961,15)記錄了一個鮮活的例子:
一位現在是美國最大的企業之一的首席執行官的人,在1916年找他的第一份工作的時候,不敢承認自己擁有經濟學的高級學位。“我告訴雇我的人,我從14歲起就在鐵路上做文員,”他說,“否則我的申請就會被打回,因為對於一個企業界的職位來說,我受教育太高了。”即使到了20世紀20年代晚期,當我自己開始工作時(德魯克繼續說),英格蘭或者歐洲大陸的商業公司仍然會在雇傭一個讀完中學的人做低級文員的時候猶豫不決。
對於勞工團體而言,學校常常被看作一個抬高成年體力勞動者價格,同時保護兒童不受工作場所虐待的方法(Peterson 1985, ch. 3)。有關實施義務教育法和童工法的運動往往並駕齊驅。思想更加深邃的勞工領袖和勞動群體中很多更加有志向的人們認識到,接受教育是一種逃脫農場和工廠辛苦勞作的方式。但即使在那時,學校仍然被看作少數人的逃生艙口,而不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改變社會流動模式的一種方式。即使像W.E.B. DuBois這樣的激進而才華橫溢的黑人領袖,也沒有倡導全民平等教育,而是僅僅呼籲“有才華的十分之一”享受平等教育,以便將其人民帶到應許之地(DuBois 1953,52,54; Cremin 1988,121-122)。
相形之下,普通公民將中等教育乃至更高教育看作一個獲得發展的機會。他們對中等教育的需求,最早在美國得到了表達,也許是因為在美國,地方就可以做決定,特別是學區,而不需要在該問題上達成全國性一致意見(Peterson 1985, ch. 3; Goldin 2001)。某個社區建造一所中學,其相鄰社區會注意到。儘管這種做法迅速擴散,但即使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等教育雖日益廣為傳播,卻遠遠未能普及。事實上,在美國國內,中等教育增長最快的十年是在大蕭條期間。這並非因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或者地方學校董事會具有平等機會的願景,而是因為工作機會太有限,年輕人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學校董事會焦頭爛額,因為教室太擁擠,教師收入微薄,有時候他們收到的是白條而不是現金,比如在芝加哥(Peterson 1985, ch. 9)。儘管如此,教育系統仍然無法切斷這種自下而上的需求。
所以美國中等教育的擴散是偶然發生的,其驅動力是個人的決定以及外部經濟力量,而不是任何廣泛的政策性決策。然而,這並不妨礙該美國模式在“二戰”末被理想化。勝利者獲得的不是戰利品就是展示其當仁不讓的智慧。歐洲社會主義政黨起死回生,他們倡導的“全民中等教育”深孚眾望,保守黨人無力抵抗。在眾人還不明就裡之際,一個共識已經達成。從五六歲或者七歲到大概十五六歲,全民享受的公立學校教育很快成為義務制,而且誰想再繼續讀下去也有機會。人們辯論的不是這件事該不該辦,而是由何種機構來辦――教堂還是國家。對於後面這部分問題,每個國家給出的答案不同,取決於每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之間的角力。
芝加哥大學的一群經濟學家,其中最知名的有Theodore Schultz(1961)和Gary Becker(1964),他們通過提出一套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理論幫助鞏固了這一共識。增加一個國家的財富,不僅僅取決於這個國家有多少工廠,或者其儲蓄率,還取決於其勞動力素質,儘管人們長期以來認為前兩條才是關鍵。這種觀點一旦以理論的形式提出來,實驗者馬上就跟進了,他們證明一個人在校讀書的年數越多,他踏入社會後的收入就越高(例如Becker 1964; Mincer 1974; Card 1999),甚至在整個成年期都如此,Sofia Sandgren對一組瑞典成年男子的調查研究(第3章)明確地證實了這一點。換言之,教育投資如同商業投資,也會產生回報率。令人稱奇的是,教育投資回報率往往大大超過傳統的資本投資。
在所謂的人力資本理論剛剛問世之時,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平等和效率兩者之間潛在的妥協問題。人們指望給全民更多的教育以便為大眾帶來新機會,同時提升勞動力素質。勞工、企業還有政見各異的各黨派,都將學校當成出路。儘管教育者總是在索要比納稅人願意出讓的更多的資源,但國家資助的學校在戰後大部分時間仍然是一個活力四射的增長板塊。學校的方方面面都在增長: 數量、規模、招生、所服務學生的年齡段、資金支持,以及教師和管理者所獲得的專業資質。人們不僅將全民中等教育視為當然,高等教育系統(大學、高級研究所,以及繼續教育)也接近呈指數級增長。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學者們開始意識到,一切並非都那麼簡單(一個預警報告請見Anderson 1961)。的確,人力資本的個人投資回報率至今仍然很強勁,也許如今比任何時期都更加強勁;的確,如果想要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的持續提高是重中之重。但是教育的擴張,其本身不一定是增進人力資本的最有效的途徑;並且教育擴張也不能保證社會流動性。如果大家都完成中等教育學業,大家仍將處於自己的稟賦和家庭支持可以讓自己到達的境界,除非學校裡能發生不同尋常的事情。簡而言之,人們可以在人力資本方面獲得長足發展是真的,但在機會結構方面無法獲得可觀的遷移也是真的。
1.4學校開支和班級規模的削減
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對於“布朗起訴學校董事會”(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的判決而激發的民權運動,將注意力集中在平等機會問題上,這比美國任何其他孤立的政治事件給予該問題的關注都要多。1896年的一個法庭裁決認為,在《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之下,根據種族而隔離運作的學校,只要擁有平等的設施,則是可以接受的。通過推翻這一裁決,布朗宣稱,實施種族隔離的學校本質上是不平等的,儘管其設施可能平等。借助布朗案裁決的機會,民權運動達到了其最高點,在1964年推動《民權法案》獲得通過。該法案加速了美國南部學校的去種族隔離化過程,並將公共生活各個層面的種族歧視定為非法。
而這些事件對學術會話的影響也非同一般。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權法案》要求美國國家教育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Education)對美國的學校實施一項全國性調查,以便統計美國黑人和白人所擁有的教育資源之間的任何差異。
詹姆斯·科爾曼受命領銜該調查,他收集了大量關於學校和學生特點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他委託開展了首次全國性大規模學生成績調查。15該調查報告發佈於1966年,按照現今的標準,其數據分析還很粗糙(Coleman等1966;為增進可讀性,此處僅參考了Coleman的文本)。然而,該研究的很多發現對以後在歐洲和美國實施更加精細的調查極有幫助。
一個結果曾被廣泛地預見到,那就是,平均而言,黑人學生的考試成績遠遠落後于其白人同學。還有一點大家也毫不意外,那就是學習也深受其他人口統計學特徵的影響,包括母親的受教育程度、父親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很多其他人口統計學特徵(上述調查結果的更多細節,請參考Coleman等1966)。雖然該報告的調查結果精確定義了平等機會這個問題的量級,但它同樣也掀起了一場在很大程度上是毫無意義的關於遺傳或者環境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決定性因素的辯論(Herrnstein和Murray 1994; Goldberger和Manski 1995; Heckman 1995; Rothstein 2004;更加深刻的綜合分析和闡釋,請參考Jencks和Phillips 1998)。
意義重大的是,科爾曼同樣發現,學校在改善該問題方面幾乎無所作為,無論是在種族群體內部還是跨群體之間。科爾曼的研究實際上顯示,剔除區域或者城市―農村差異之後,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平均而言,所在學校擁有近似的生均開支和相似的師生比、教師資質,以及絕大多數反映其他物質特徵的指標值也近似。更令人詫異的是,一旦考慮到人口統計學特徵,學校方面的特徵對於學生成績的影響就顯得微乎其微,這是一個完全出乎意料的發現,而且至今仍影響深遠。更高的開支未能帶來更高的學生考試成績。學校的其他物質特徵對學生的影響也可忽略不計。平均而言,學生似乎不會因為以下因素而學到更多東西: 其教師的資質更好或者工資更高;其所在班級規模更小,或者教學樓設施更完善、更加現代化,或者圖書館藏書更多;或者在很多其他物質方面更加寬裕。這些研究成果如此讓人不安,以至於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組織了一個持續多年的研討會,專門致力於對上述調查的仔細覆核。該研討會由知名的統計學家Frederick Mosteller和後來的紐約州參議員Daniel P. Moynihan領導。經過數據分析,研討會成員認定,科爾曼和他的團隊的研究不存在問題(Mosteller和Moynihan 1972)。
自那時起的很多研究,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做的,無論使用的是科爾曼時期的簡單方法還是現如今的先進手段,一再證實科爾曼當年的結論(Hanushek 2002; Neal 2006; Woessmann 2005a以及其中的參考資料)。本書中有三章內容將彼時的文獻與現今的平等機會問題研究銜接起來,考察重新關注為弱勢群體提供額外物質資源,可以在何種程度上改變教育結果的分佈。Julian R. Betts和Paul E. Roemer(第9章)發現,如果單純依賴額外增加開支作為唯一的干預策略來實現種族群體間的平等,那麼學校將需要在黑人學生身上花費相當於白人學生8倍到10倍的金錢。類似地,Eric A. Hanushek(第7章)發現,為弱勢群體平均化標準師資投入或者削減班級規模對於消除得克薩斯州種族群體間的現有不公平無濟於事。對歐洲來說,Leuven和Oosterbeek(第8章)同樣證明,荷蘭若干項再次將資源向弱勢學生群體傾斜的政策(削減班級規模、額外增加人員資源、額外增加計算機資源,以及延長義務教育時間等)未能改善平等機會問題。
在科爾曼進行的所有與物質資源有關的調查結果中,至今仍然極具爭議的一條發現與班級規模有關,班級規模亦即一個學校的學生與教師的人數比例。科爾曼和很多其他學者發現,從各方面看,無論規模大小都沒有什麼影響(Hanushek 1996; Hoxby 2000)。很多普通教師、家長和學生都認為這個結果難以置信。田納西州的一項大型實驗研究證明,班級規模的縮小對於學生成績有正面影響,這對這種常識般的觀點給予了支持(Mosteller 1995; Krueger 1999)。近年來,一項關於班級規模的國際研究發現,班級規模的影響十分有限,除了兩個國家例外,在這兩個國家裡,教師收入低、教師資質也特別低。這似乎說明,班級規模的縮小可能在教師資質低的情況下是一條提高學生成績的有用辦法(Woessmann和West 2005)。這些結果可能與前述的荷蘭在班級規模方面的准實驗研究相一致,Leuven和Oosterbeek(第8章)對此做了報告。他們發現,縮小班級規模的影響微乎其微,這個結果在擁有一支收入頗豐的教師隊伍的國家裡完全可以預見。但可以確定的是,關於這個主題仍將持續開展多年的研究。
1.5同伴群體與學校分層教育
科爾曼的第二個頗具爭議的發現是,學生在學校的同伴群體的素質,是影響其學習成績最重要的與學校相關的因素之一。黑人學生如果與白人一起上學則學得更好。更籠統地講,處於社會劣勢地位的學生如果能和更加佔據社會優勢地位的學生一起上學,他們的學習成績會更好。但反之並不成立。白人學生的學習成績並沒有因為黑人孩子的存在而受到負面影響。
這些研究結果極大地鼓勵了那些反學校種族隔離運動的領導者們。此外,這些研究結果也與一個年深日久按學生能力將學生分開的教學實踐背道而馳。這種做法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的基礎之上的: 學生和與其學習成績相近的同伴在一起可以學到最多。在很多歐洲國家,處於青春期早期的學生過去乃至現在仍然被送往不同的中學讀書。能力更強的學生被分配到更加學術性的課程中去,而那些能力欠佳的學生則被送往一個課程內容更加籠統或者職業教育的學校中去。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學生過去和現在都上一樣的綜合性中學,但是被分配到不同的課程軌道上去――學術、普通,或者職業“軌道”。如今採納綜合學校模式的很多歐洲國家通常都採取了類似的分層做法。
在科爾曼研究結果的指導下,許多學校改革者開始廢止雙重學校制度或者校內分層教育。如果能力弱的學生可以得到幫助而且不會對學習成績更好的學生造成負面影響,那麼這個政策將既促進平等機會,也可以促進整體人力資本提升。但這仍然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在本書中,學者們給予了各種回答。在本書第4章,Jacob Vigdor和Thomas Nechyba發現,使用如科爾曼調查和其他調查中所使用的標準方法來評估的同伴群體影響未能反映真正的因果關係。他們使用的是高級計量經濟學方法以及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廣泛的面板數據來區分相關性與因果關係。他們指出,傳統方法無法輕易測量能力;那些因為測量不准而顯得能力較高的個人被分配到明顯能力更強的同伴群體中;此類分層將導致同伴影響失准,除非該分析能將分層過程的因素考慮在內。同樣,Hanushek(第7章)使用了來自得克薩斯的面板數據,研究顯示同伴群體的能力或者社會經濟狀況對學生的表現幾乎沒有影響。這些調查表明,曾一度被認為已經有了定論的同伴效應問題,現在卻又回到了研究日程的頂部。
在第5章裡,這項研究得到更深入的討論。為了瞭解混合班級的效應,Fernando Galindo-Rueda與Anna Vignoles使用了英國一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數據。當時,不同的地方教學機構,分快慢班制度與不分快慢班制度並存。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將不同能力學生混合的做法的唯一影響,大概就是降低了能力最高的學生的表現。因此,儘管學習結果上的不平等得到了消減,但是強迫尖子生降低其水平絕不是人們期望用來解決平等機會問題的辦法。需要注意的是,這也許意味著存在非線性同伴效應,因為混班以後,只是尖子生遭受了損失,卻沒有贏家。然而,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普遍適用於其他情景的程度仍不明了。社會和學業能力混合的最直接效應也許與其長期效應十分不同。學校重構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學生從一個學校轉往另一個學校,可以壓抑學生的學業表現,這是Hanushek在第7章要闡述的內容。
短期與長期結果的區別,也許有助於協調第5章Galindo-Rueda和Vignoles的研究結果。他們借助於Hanushek與Woessmann(2006)的跨國證據表明,從長期來看,混班教學可以消減學業表現上的不平等,同時既不會傷及平均學業表現,也不會傷及尖子生的學業表現。儘管這些研究仍將莫衷一是,Giorgio Brunello、Massimo Giannini以及Kenn Ariga在第6章所提出的理論模型卻十分難能可貴。該研究考慮到了一些決定實施篩選式教育最佳年齡的關鍵經濟要素。
1.6以結果為導向及成績標準
也許與其說科爾曼最偉大的貢獻是他取得的具體的研究成果,不如說是他所開拓的思路。至少在一個方面,他將公眾的注意力引向了教育的輸出(即學生學到了多少),而不僅僅是輸入(教育年限、支出、班級大小、教師工資,以及教師資質),而後者曾一度被視為學校質量的首要指標。
1969年,就在科爾曼報告發佈後不久,美國諸州教育委員會(U.S.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發起了國家教育進步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稱NAEP)。這是一個全國性抽查考試,受試對象為9歲、13歲和17歲的學生,旨在獲取他們在學習表現方面的信息。通過週期性舉行該抽考,人們期望NAEP可以記錄學生表現隨時間推移而取得的進步。幾乎在同時,國際上一群學者成立了國際教育成就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該協會隨即啟動了首次對於許多發達工業國家中學生的數學和科學學業成就可比數據的系統化採集。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國際化評估得以週期性舉辦,最終演化成為定期舉辦的“國際數學與科學學習趨勢”(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評估,其最近一次考試發生在2003年。TIMSS評估始於2000年,後來的PISA調查對其是一個補充。關於PISA我們前面有所提及7。
NAEP、TIMSS、PISA,以及其他類似調查得到的結果,都要比科爾曼的許多研究成果更加令人眼界大開。其中,NAEP本來要研究美國教育的“進步”,結果卻揭示了教育的停滯――2005年中學畢業生的表現並沒有比1970年的好多少(美國教育部2005; Peterson 2006)。同時,TIMSS和PISA的調查發現,日本和其他亞洲學生,而不是歐洲或北美學生在數學和科學方面的成就最大(例如: Mullis等2004,以及許多其他早期研究)。工業化世界的後來者是如何如此迅速地達到教育的頂層位置,仍然是一個謎團,分析家對其謎底仍在孜孜以求。對於上述各類國際測試的多個分析,都強調了盛行于亞洲的綜合性畢業考試(參照Bishop 2006和Woessmann 2005b)。這些考試往往在中學教育的最後一年舉行。其內容充實,學生取得的考試成績千差萬別,大學和用人單位往往極為重視。通過確定清晰的目標並提供不同的完成層次,這類考試往往能夠激勵學生、教師和家長朝著較高表現水平而努力。本卷中由John H. Bishop與Ferran Mane完成的這一章(第10章)對此進行了討論。該章通過美國的證據表明了畢業考試和較高畢業要求的正面效果。
1.7學校的選擇
最後,永遠對新點子保持開放態度,且無論自己的發現有多麼驚人都永不滿足的科爾曼,通過又一項研究開闢了新的研究空間。這篇論文的題目為《公立和私立學校: 中學分析及其他》,也是由美國教育部委託完成的(Coleman, Hoffer和Kilgore 1981,1982; Coleman和Hoffer 1987)。在這項研究中,他們收集了學生表現及其背景特徵,以及公立和私立中學的多種學校特徵。當研究結果公佈的時候,公眾非常震驚。他們瞭解到,學生在天主教學校能學到更多,而這些學校此前被認為是那些出於宗教而不是教育目的的家庭送子女去的、低成本、下等的學校。然而,與以前一樣,他的研究結果在使用更加精細的研究方法就不同的數據組而進行的其他調查面前,仍舊展現了較強的穩健性(例如: Neal 1997;最新近的文獻綜述請見Neal 2002; Wolf 2006)。然而,後續研究卻揭示出了一個科爾曼報告中原有的、此前未被關注的觀點,即天主教教育的好處,對於少數族裔,特別是對於非洲裔美國人的好處,要大於對白人學生的好處。
科爾曼的這篇論文導致了大量旨在促進學校選擇的政策性干預,既包括公立學校之間的學校選擇,也包括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的選擇。研究人員才剛剛開始梳理歐洲和美國嘗試過的多種擇校干預行動的影響(參見Howell和Peterson 2002和Hoxby 2003對美國的研究;Bradley和Taylor 2002, Leva ic' 2004,以及Sandstrm和Bergstrm 2005提供的歐洲的例子)。本卷包括了參與此話題討論的兩篇頗有價值的論文。在第11章裡,Simon Burgess、Bredon McConnell、Carol Propper以及Deborah Wilson使用了廣泛的英國學生管理數據。他們的研究表明,只要學生擁有可以住宿的選擇,則附近學校的選擇組的大小與住校後學生依照能力和社會經濟地位所展現的跨校分層正相關。本卷中關於學校選擇的另外一章由Daniele Checchi與Tullio Jappelli(第12章)完成,呈現了意大利的例子。來自意大利的證據表明,將子女送往私立學校的家長,對於他們當地公立學校質量的評價要比那些將子女送往公立學校的家長低一些。這表明,當家長面臨低品質公立學校的時候,往往會逃往私立學校。
1.8結論: 教育效率是不是通往教育公平的最佳道路?
許多關於學校對平等教育機會問題影響的話題,都是由科爾曼的研究工作提出的。但也許他的影響最深遠的遺產(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卻在誘發人們對於教育機會平等的意義感知的變化方面(參見Coleman 1968)。在科爾曼報告發佈以前,平等教育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傳統方式闡釋的: 學校應該為所有學生提供平等服務。但是當科爾曼的報告表明平等的資源――包括平等的開支、平等的設施、資質平等的師資等――未能帶來平等的結果,於是平等機會的定義開始發生了巨變,提出了超出資源平等化的要求: 對於弱勢群體應當實施集中額外資源的補償性教育。通過確認和拓展科爾曼的初期研究結果,本卷來自美國和歐洲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弱勢群體上花費大量區別性開支,也不見得能獲得結果的平等。
鑒於平等機會問題可以歸因於可度量的、物質性的學校特徵的程度如此之小,人們要求學校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學校也探索了許多替代方案,諸如去分層化、更靈活的課程、重視孩子的自我感受勝過重視他們的學業成績、通過測試來確保沒有孩子掉隊,以及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選擇。去分層化以及很多其他措施的效果嚴重依賴于同伴效應的準確性質,而這一點至今仍未有較好的理解。在推進我們理解的同時,本卷中呈現的美國和歐洲的證據,亦未能對同伴效應提供準確無誤的答案,儘管美國和歐洲的研究人員提醒人們,任何隨意的同伴效應很有可能哪怕存在也是微乎其微的。有些研究呈現的結果表明,較高的表現標準――如果能恰當實施――則有望降低不平等的情況。精准選擇項目也可能幫助被困在低品質學校的弱勢群體學生,但是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項目的設計,而其長期效果仍然是未知數。有鑑於此,本卷中收集到的這些證據,儘管展現了一些取得進步的可能途經,但它們仍然對很多學校所採取的激進的改變機會結構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
根據目前所知,人們不宜期望短期內就能出現奇跡。當人們將平等機會定義為輸出平等的時候,學校將難免捉襟見肘,儘管誰也不能指責學校竭盡所能幫助那些弱勢群體。學生從別處學得太多,家庭各不相同,孩子千差萬別,我們也不能對學校期望過高。但如果人們接受的是一個更陳舊的、更加廣泛認同的關於機會平等的定義,那麼這個問題就好辦多了。學校可以也應該挑戰學生潛力的極限。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一個高效的教育體系來挑戰每個孩子,讓他們都實現自己的潛力。在那個意義上,一個高效的教育體系也有助於實現平等。正如Theodore Schultz(1981,88)在25年前說的:“在尋求平等的過程中,人們忽視了教育效率和平等的互補性。在我們龐大的學校體系中,如果能實現效率的最大化,這對於公平的貢獻很可能將遠遠大於現在正在實施的許多改革。”
注釋
Paul E. Peterson和Ludger Woessmann
杜振東譯
作為一個教育目標,平等機會是個新鮮事物。自1763年從普魯士開始,到19世紀末,基本上所有西歐國家以及美國都實施了由國家出資的大規模初等義務教育1。但是直到近幾十年,大眾教育的主要目的,正如那些代表大眾教育而為之奔走呼號的人們所表述的那樣,既不是為了促進社會流動性,也不是為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是為了挽救靈魂、培養忠誠的公民,以及促進經濟生產力(Peterson 1985; Gradstein, Justman和Meier 2005)。任何平等主義的後果都只是意外而已。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社會主義黨派走上歐洲的政治舞臺,對於平等教育機會的要求得到了強化,多數國家對幾乎所有的年輕人打開了學校之門,至少到16歲。中等教育在美國開展得甚至比歐洲還要早,儘管不是沖著同樣的平等機會的理念去的。但是這一點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而發生了變化,因為民權運動的領導者堅持教育必須既取消種族隔離,又是平等主義的。隨著這些事件的深入,研究的議程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James Coleman的先驅性著作之後(比如可參見Coleman等1966)。他的著作引領了隨後的大部分學術研究議程――包括在本卷發表的這些論文。
如今很多教育研究仍然聚焦於那些改革,人們期待那些改革能關注平等機會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倡導者的期望值非常高。延長受教育的年限,即貫穿青春期,乃至成人期的早期,人們預期這樣會讓下一代更加平等。向下延長受教育年限,讓入學年齡變得更小,人們預期這樣可以給缺失足夠的家庭激勵以補償。
人們期望通過將財政資源集中在貧困人口的教育上,也能達到類似的目的。
將能力和背景迥異的學生混合在一起教育也大行其道,人們希望這樣一來,那些處於較劣勢地位的學生可以向其他人學習。人們也實施了問責制度,確保教育能夠面向所有學生,甚至那些起點較低的學生。同樣,人們通常也認為,通過擇校,貧窮家庭有可能獲得只有富裕家庭才能享受得到的教育機會。
本卷收錄的各篇論文,最初是2004年9月在德國慕尼黑舉辦的一次國際會議上宣讀的論文。這些論文探討了在發達工業社會裡,上述以及其他旨在實現平等教育機會的學校改革的結果,主要聚集歐洲和北美國家。該次會議由CESifo和哈佛大學的“教育政策和治理項目”聯合主辦。
1.1為何學校未能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 平等機會的雙重含義
儘管人們對此主題興趣濃厚,然而對於平等教育機會的含義卻莫衷一是。一些人認為,平等的教育機會僅僅意味著在學校建制之內所有人獲得相同的待遇,而且每個人得到與其能力相匹配的教育,這樣一來,所有人都獲得了同樣的機會來增強他們入學時所具有的不同能力。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平等的教育機會要求學校彌補一些孩子入學時的能力不足,這樣下一代的哪些成員可以在未來社會平步青雲,就完全是由隨機因素來決定的。
對於持第二種觀點的人來說,本書收錄的這些論文可能會讓他們失望。總體來說,這些論文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人們提出的很多學校改革,都很難指望切實改變一個社會的機會結構。讀完本論文集,讀者難免會得出與George Counts曾經得出過的大同小異的結論。此人是一個激進的悲觀主義者。在大蕭條期間,他寫了《學校敢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嗎?》(1932)一書,對書名提出的問題他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從George Counts的那本書面世到現在,情況似乎沒有發生多大的改變。
但是,人們應不應該就此極度悲觀,卻取決於他們如何去理解平等教育機會。
大多數學校官員,或者說實際上人們中的大多數,即使在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美國的民權運動之後,仍然不指望學校可以深刻地改變社會結構。很少有人同意那種中規中矩的言論,即“學校應該讓每一代人的機會平等化”,事實上是,“人們自然而然地希望給自己的子女某種優勢”(Hochschild和Scovronick 2003,2)。他們反而希望學校對學生的一切全盤接受,無須去改變學生身上深受家庭影響而形成的各種品質。
的確,大多數人希望是家庭溫暖的懷抱,而不是國家提供的冷漠的教育,去承擔確保其下一代長期福利的主要責任。大多數家長奉獻出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財力來增進他們子女的福祉。父母雙全對於子女來說比單親家庭要好。部分原因在於,如果家庭能有更多的財力用於教育,孩子也許會學習得更好。但是,儘管財力也許很重要,父親也的確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母親付出的時間和才華,卻證明具有最重要的意義。母親的才華可以通過她的稟賦和所受的教育來獲得最好的測度(White 1982; Meyer 1996; Jencks和Phillips 1998; Rothstein 2004)。在絕大多數家庭,母親的關懷、談話和教導起了主要作用。
這必然會導致不平等。家庭的質量各不相同,也許如今比過去更加不同,至少在美國是這樣。有些父母擁有巨大的個人和職業資源用來奉獻給他們子女的福祉。而有些父母則自顧不暇,更談不上顧及子女了。現代社會的兩大變化也許在凸顯家庭之間的差異。一方面,婚姻伴侶日益從稟賦類似的人群中選擇,特別是當女方成為養家糊口者之後更是如此(Oppenheimer 1988; Mare 1991)。另一方面,占比日益增多的子女是單親家庭撫養長大的。這些趨勢也許將加劇教育的不平等。雙收入家庭,相比單親家庭,更能給他們子女的教育奉獻更多的時間、才華和財力資本(Jencks 1979; McLanahan和Sandefur 1994; Neal 2006)2。
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潛力至關重要,而學校能做的貢獻必然是很有限的。各國學生在校的時間不同,孩子在校的時間大約為每日6個小時,每週5天,占一年中四分之三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內,他們處於老師的照看之下,但老師通常負責照看的並非1到3個孩子,而是大概10到30個。即使極具敬業精神的專業教師,論及對孩子的付出,相比起父母而言也無法等量齊觀。父母天生會深切關注子女的幸福。正如一些最好的教師常常解釋的那樣,家庭為子女的成長提供方向,教師在改變其軌跡方面能力非常有限。
家庭是所有社會化機構中最強有力者,對此古人也十分了然。希臘哲學家柏拉圖(1992)對家庭的影響力就心知肚明。他建議,未來國家的保護者,應該很小的時候就從家庭中脫離出來,被安置在一個高度結構化的教育環境中撫養,以確保他所謂的哲學家國王能夠獲得所需要的綜合素質。現代的柏拉圖主義者諸如Hochschild和Skovronek(2003,如上所引),為了實現他們的平等主義夢想,可能會不得不建造一個綜合的義務性的大眾住讀教育體系,在該體系內,不僅國家的未來保護者必須要儘早被帶離家庭,而且所有的孩子都要這樣,以便脫離高度多樣化的家庭的影響。
所以如果認為平等機會意味著義務教育結束之時學生的成績是同等的,那麼可以相當確定的一點是,那種平等主義的理想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倘若這種觀念付諸實施,大多數人都會加以抵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如此。試想我們告訴那些執著的父母們,那些孜孜以求致力於子女教育的父母們,因為他們這種做法,他們的子女將會被安置到一個不利的學校環境中去。只有這樣,其他得不到父母足夠支持的孩子們才可以趕上來。很難設想有哪個社會會沿著這樣的思路進行組織。
然而,平等教育機會也許可以更加狹義地進行構想。如果所有走進校門的孩子被給予了相同的機會來增進他們剛入校時的稟賦,那麼也可以說是學校機會平等。有了這樣一個對平等機會的解釋,那麼人們就不會再指望什麼結果平等,而是會滿足於除了學校干預發生以前就存在的之外,不再有額外的不平等。公共提供的機會將是平等主義的,因為學校提供的附加值對於所有孩子都將是相似的。在這樣一個世界裡,社會不公平仍將存在,但是公共學校體制將不用對這種不公平的加劇和永存負責。
1.2不同國家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影響
正是這第二種更加局限的對於平等機會的理解,似乎在大部分現今教育中大行其道。在大多數發達工業社會裡,學校似乎沒有做多少工作來試圖改變機會結構的發展方向(Anderson 1961)。在教育系統得到巨大擴張的社會裡,家庭背景的影響仍然十分強大。比如,近期由第三次“國際數學和科學評測”(TIMSS)從國際測試成績數據中獲取的證據表明,家庭背景對於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十分巨大,所有參加測評的國家概莫能外。而且歐洲家庭的平均影響值與美國的十分接近(Woessmann 2004)。
在表1.1中,我們報告了來自一個更加新近的國際測試的相似證據。此測試即2000年舉辦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主辦,針對各國具有代表性的15歲學生樣本群體進行測評。平均而言,在這個測試中,10年級學生比9年級學生的成績高出了30分。測評結果還顯示,在歐洲最大的三個國家(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學生的學業成績都與下列家庭背景特徵強相關: 父母的職業、就業狀況、原住國、家庭狀況,以及家中藏書數量。
出於好幾個原因,家中藏書的數量可以被理解成學生家庭在教育、社會和經濟背景方面的一個強大的、無所不包的代表,在社會學研究中經常被提及和用到(例如De Graaf 1988; Esping-Andersen 2004)。總的來說,大量藏書意味著一個高度重視教育、推動子女取得學業成就的家庭環境(參見Mullis等2004),代表了父母的社會背景,並且是經濟實力的寫照,因為書是需要用錢買來的。家中藏書的數量一再成為國際學業成就測試中學生成績的最重要的預測指標。此外,Schütz, Ursprung和Woessmann(2005)通過另一組不同的數據研究表明(至少對數量有限的幾個擁有該統計數據的國家而言),家庭收入(PISA中未收集)和家庭藏書量之間的相關性在這幾個國家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
鑒於家庭收入也許是家庭背景“理想的”測度,因此至少從經濟的角度,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強了將家庭藏書量作為進行跨國比較分析時全面代表家庭背景量度的有效性。相較而言,其他的家庭背景(比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代表指標的跨國可比性可能有限,比如各國之間特定的教育項目的含義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如果用家庭藏書量來作為反映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有助於學生學習的家庭特徵的國際可比性指標,那麼會發現家庭藏書在500本以上的15歲學生,其PISA測試的成績相比家中藏書不足10本的學生,要高出2到3個學年的水平(表1.1)。家庭背景的影響不僅在這四個國家中表現很明顯,而且其大小在德國和美國十分接近。對英國學生的影響只是略小一些。如果假定高中學習成績對未來取得經濟成功影響很大――正如許多研究表明的那樣(比如Bishop 1992; Murnane, Willett和Levy 1995; Neal和Johnson 1996; Currie和Thomas 2001),那麼會發現在這三個國家中,學校教育體系似乎並沒有帶來特別高的社會流動率。必須承認,家庭藏書量對學習成績的影響在法國似乎要輕一些,但即使在這個國家,家中藏書超過500本的學生相比家中藏書不到10本的孩子,其成績也要好出兩個學年的水平。
在這四個國家中,家庭背景對於學生的成績都有著重大影響,然而很可能法國教育體制中的某些特徵緩和了這種衝擊。法國因其“幼兒學校”而著名。該體制為來自一切背景的孩子提供廣泛的學前課程。近期Schütz等人(2005)提供的國際比較證據表明,學前課程(以及綜合教育)的普及的確與各國更高的社會流動性之間具有系統性關聯。而很多其他的教育政策則與之關聯性不大。這一發現也與本書中(第8章)Edwin Leuven和Hessel Oosterbeek提供的對荷蘭的研究成果相一致。他們的研究顯示,降低義務教育入學年齡,並在標準年齡以前實現普及教育,的確是五種教育干預當中唯一能夠改善劣勢學生群體教育成績的那一種。
同時,其他國家的教育體制可能會強化家庭的影響。比如,德國強調在人生早期就為某個特定的職業做準備,這也許會將學生置於與其父母類似的社會角色。在美國,由於學校政策制定的去中心化,加上廣泛的因種族與收入因素導致的居住區隔離,可能會強化現有的社會模式。Steve Machin在其關於英國高等教育擴張的論文(第2章)中指出,英國高等教育的擴張強化並增進而不是緩解了社會差別。富裕家庭的子女相比工人階級家庭的子女,更加傾向於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因為高等教育受到政府的大幅補貼,所以其淨效應是一種強化社會差別的有組織的安排,這與平等主義者對教育擴張的期待背道而馳。
1.3學校教育的最初目的
一旦人們明白所謂平等主義原則在西方大眾教育史中僅僅發揮了微乎其微的作用,就不會詫異於教育擴張有時會強化而不是緩和社會不公平。而英語中“學校”(school)這個詞本身其實是從希臘語“休閒”(leisure)派生而來的,因為在古雅典,只有那些可以將自己從體力勞動的義務中解脫出來的人,才有能力享受教育(Drucker 1961)。在後來學習僅僅局限於修道院內的幾百年裡,情況也沒有發生改變。對大眾而言,在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閱讀簡直是不可能的。古騰堡的活字印刷術在16世紀早期得到廣泛傳播,實現了將話語迅速印製成文字,並讓王宮、城堡和修道院之外的人們獲益。
宗教改革者們,無論是披著路德派還是加爾文派的外衣,都極力利用這個新發明所帶來的各種可能性,敦促信眾閱讀《聖經》,而不是依賴牧師的訓誡、教堂的繁文縟節,或者僧侶的想像(Pelikan 2005)。由於個人需要而閱讀《聖經》,於是讀寫能力迅速擴散,特別是在歐洲北部大部分地區,以及後來北美大陸的北部大部分地區,因為新教在上述地區紮下了根。即使到今天,上述地區仍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區。
如果說教化的初衷是宗教,那麼其後果卻是經濟,因為教化的擴張促進了財富的產生。馬克斯·韋伯(2001)將新教國家擁有更快的經濟增速歸因於這些國家擁有更高的儲蓄率,因為這些地方有一個要求信徒延遲滿足需求的信仰體系。但是資本主義在新教國家成了氣候,更可能的原因是,旨在閱讀《聖經》的教育催生了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人力資本6。一個類似的觀點認為,人力資本驅動取得經濟成功起源於宗教,乃是因為自8世紀以來,猶太人選擇了城市熟練手工業者和商人作為其職業。Botticini和Eckstein(2005a, 2005b)從人為資本的角度來解讀猶太人的歷史,指出經商的猶太人取得經濟成功,根源在於一個傳承數個世紀的猶太人戒律,該戒律要求猶太男子必須能在會堂中閱讀《律法書》(《舊約》前五卷的總稱,譯者注)並教其兒子們閱讀《律法書》。
在歐洲,因為宗教狂熱的衰退,政治考量異軍突起。一旦一個大規模的教育系統對民族國家的增強作用明顯不亞于一支公民軍隊,政治領袖們就會看在眼裡。儘管公共學校起源于荷蘭,但對公立教育和國家建設之間的關係理解得最透徹的卻是俾斯麥,這導致產生了一句警句:“在創造了德意志帝國的1870年普法戰爭中,普魯士的小學校長打敗了法國”(Drucker 1961,21)。儘管德國的鐵路也許跟那場戰爭的結局關係更大,而不是其學校,但那句警句的確是有真理的成分。面對統一那些雖然語言相通,但方言無數的各個政治轄區的重任,俾斯麥利用學校來打造共同語和國家意識(Lamberti 1989; Gradstein, Justman和Meier 2005, ch. 2)。他的成功啟發歐洲的鄰國紛紛效仿。
在大西洋彼岸,政治目標也沒有小到哪裡去。在美國,所需要的不是合併以前分崩離析的政治區劃,而是接納一波又一波湧入的移民,這些移民語言各異、禱告的方式也不同。對於Horace Mann和其他打造了共同學校的人而言,歐洲南部和東部過來的移民,其文化遺產不一樣,因此“需要道德提高”以及用英語語言進行教導,而這兩者他們都認為可以通過國家開辦的、新教控制的公共學校來實現(Kaestle 1983; Glenn 1987)。
然而,關於學校可以成為經濟增長引擎的觀念在當時仍然沒有得到確立。對於很多工商界人士,學校只不過是一項高成本的公共開支罷了,浪費了本來可以用於更有效的用途上的資源。
如果公共學校可以略微出類拔萃,那麼它們應該致力於為具體行業或者職業培養學生,他們才是工業經濟的中流砥柱。Peter Drucker(1961,15)記錄了一個鮮活的例子:
一位現在是美國最大的企業之一的首席執行官的人,在1916年找他的第一份工作的時候,不敢承認自己擁有經濟學的高級學位。“我告訴雇我的人,我從14歲起就在鐵路上做文員,”他說,“否則我的申請就會被打回,因為對於一個企業界的職位來說,我受教育太高了。”即使到了20世紀20年代晚期,當我自己開始工作時(德魯克繼續說),英格蘭或者歐洲大陸的商業公司仍然會在雇傭一個讀完中學的人做低級文員的時候猶豫不決。
對於勞工團體而言,學校常常被看作一個抬高成年體力勞動者價格,同時保護兒童不受工作場所虐待的方法(Peterson 1985, ch. 3)。有關實施義務教育法和童工法的運動往往並駕齊驅。思想更加深邃的勞工領袖和勞動群體中很多更加有志向的人們認識到,接受教育是一種逃脫農場和工廠辛苦勞作的方式。但即使在那時,學校仍然被看作少數人的逃生艙口,而不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改變社會流動模式的一種方式。即使像W.E.B. DuBois這樣的激進而才華橫溢的黑人領袖,也沒有倡導全民平等教育,而是僅僅呼籲“有才華的十分之一”享受平等教育,以便將其人民帶到應許之地(DuBois 1953,52,54; Cremin 1988,121-122)。
相形之下,普通公民將中等教育乃至更高教育看作一個獲得發展的機會。他們對中等教育的需求,最早在美國得到了表達,也許是因為在美國,地方就可以做決定,特別是學區,而不需要在該問題上達成全國性一致意見(Peterson 1985, ch. 3; Goldin 2001)。某個社區建造一所中學,其相鄰社區會注意到。儘管這種做法迅速擴散,但即使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等教育雖日益廣為傳播,卻遠遠未能普及。事實上,在美國國內,中等教育增長最快的十年是在大蕭條期間。這並非因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或者地方學校董事會具有平等機會的願景,而是因為工作機會太有限,年輕人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學校董事會焦頭爛額,因為教室太擁擠,教師收入微薄,有時候他們收到的是白條而不是現金,比如在芝加哥(Peterson 1985, ch. 9)。儘管如此,教育系統仍然無法切斷這種自下而上的需求。
所以美國中等教育的擴散是偶然發生的,其驅動力是個人的決定以及外部經濟力量,而不是任何廣泛的政策性決策。然而,這並不妨礙該美國模式在“二戰”末被理想化。勝利者獲得的不是戰利品就是展示其當仁不讓的智慧。歐洲社會主義政黨起死回生,他們倡導的“全民中等教育”深孚眾望,保守黨人無力抵抗。在眾人還不明就裡之際,一個共識已經達成。從五六歲或者七歲到大概十五六歲,全民享受的公立學校教育很快成為義務制,而且誰想再繼續讀下去也有機會。人們辯論的不是這件事該不該辦,而是由何種機構來辦――教堂還是國家。對於後面這部分問題,每個國家給出的答案不同,取決於每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之間的角力。
芝加哥大學的一群經濟學家,其中最知名的有Theodore Schultz(1961)和Gary Becker(1964),他們通過提出一套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理論幫助鞏固了這一共識。增加一個國家的財富,不僅僅取決於這個國家有多少工廠,或者其儲蓄率,還取決於其勞動力素質,儘管人們長期以來認為前兩條才是關鍵。這種觀點一旦以理論的形式提出來,實驗者馬上就跟進了,他們證明一個人在校讀書的年數越多,他踏入社會後的收入就越高(例如Becker 1964; Mincer 1974; Card 1999),甚至在整個成年期都如此,Sofia Sandgren對一組瑞典成年男子的調查研究(第3章)明確地證實了這一點。換言之,教育投資如同商業投資,也會產生回報率。令人稱奇的是,教育投資回報率往往大大超過傳統的資本投資。
在所謂的人力資本理論剛剛問世之時,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平等和效率兩者之間潛在的妥協問題。人們指望給全民更多的教育以便為大眾帶來新機會,同時提升勞動力素質。勞工、企業還有政見各異的各黨派,都將學校當成出路。儘管教育者總是在索要比納稅人願意出讓的更多的資源,但國家資助的學校在戰後大部分時間仍然是一個活力四射的增長板塊。學校的方方面面都在增長: 數量、規模、招生、所服務學生的年齡段、資金支持,以及教師和管理者所獲得的專業資質。人們不僅將全民中等教育視為當然,高等教育系統(大學、高級研究所,以及繼續教育)也接近呈指數級增長。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學者們開始意識到,一切並非都那麼簡單(一個預警報告請見Anderson 1961)。的確,人力資本的個人投資回報率至今仍然很強勁,也許如今比任何時期都更加強勁;的確,如果想要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的持續提高是重中之重。但是教育的擴張,其本身不一定是增進人力資本的最有效的途徑;並且教育擴張也不能保證社會流動性。如果大家都完成中等教育學業,大家仍將處於自己的稟賦和家庭支持可以讓自己到達的境界,除非學校裡能發生不同尋常的事情。簡而言之,人們可以在人力資本方面獲得長足發展是真的,但在機會結構方面無法獲得可觀的遷移也是真的。
1.4學校開支和班級規模的削減
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對於“布朗起訴學校董事會”(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的判決而激發的民權運動,將注意力集中在平等機會問題上,這比美國任何其他孤立的政治事件給予該問題的關注都要多。1896年的一個法庭裁決認為,在《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之下,根據種族而隔離運作的學校,只要擁有平等的設施,則是可以接受的。通過推翻這一裁決,布朗宣稱,實施種族隔離的學校本質上是不平等的,儘管其設施可能平等。借助布朗案裁決的機會,民權運動達到了其最高點,在1964年推動《民權法案》獲得通過。該法案加速了美國南部學校的去種族隔離化過程,並將公共生活各個層面的種族歧視定為非法。
而這些事件對學術會話的影響也非同一般。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權法案》要求美國國家教育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Education)對美國的學校實施一項全國性調查,以便統計美國黑人和白人所擁有的教育資源之間的任何差異。
詹姆斯·科爾曼受命領銜該調查,他收集了大量關於學校和學生特點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他委託開展了首次全國性大規模學生成績調查。15該調查報告發佈於1966年,按照現今的標準,其數據分析還很粗糙(Coleman等1966;為增進可讀性,此處僅參考了Coleman的文本)。然而,該研究的很多發現對以後在歐洲和美國實施更加精細的調查極有幫助。
一個結果曾被廣泛地預見到,那就是,平均而言,黑人學生的考試成績遠遠落後于其白人同學。還有一點大家也毫不意外,那就是學習也深受其他人口統計學特徵的影響,包括母親的受教育程度、父親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很多其他人口統計學特徵(上述調查結果的更多細節,請參考Coleman等1966)。雖然該報告的調查結果精確定義了平等機會這個問題的量級,但它同樣也掀起了一場在很大程度上是毫無意義的關於遺傳或者環境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決定性因素的辯論(Herrnstein和Murray 1994; Goldberger和Manski 1995; Heckman 1995; Rothstein 2004;更加深刻的綜合分析和闡釋,請參考Jencks和Phillips 1998)。
意義重大的是,科爾曼同樣發現,學校在改善該問題方面幾乎無所作為,無論是在種族群體內部還是跨群體之間。科爾曼的研究實際上顯示,剔除區域或者城市―農村差異之後,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平均而言,所在學校擁有近似的生均開支和相似的師生比、教師資質,以及絕大多數反映其他物質特徵的指標值也近似。更令人詫異的是,一旦考慮到人口統計學特徵,學校方面的特徵對於學生成績的影響就顯得微乎其微,這是一個完全出乎意料的發現,而且至今仍影響深遠。更高的開支未能帶來更高的學生考試成績。學校的其他物質特徵對學生的影響也可忽略不計。平均而言,學生似乎不會因為以下因素而學到更多東西: 其教師的資質更好或者工資更高;其所在班級規模更小,或者教學樓設施更完善、更加現代化,或者圖書館藏書更多;或者在很多其他物質方面更加寬裕。這些研究成果如此讓人不安,以至於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組織了一個持續多年的研討會,專門致力於對上述調查的仔細覆核。該研討會由知名的統計學家Frederick Mosteller和後來的紐約州參議員Daniel P. Moynihan領導。經過數據分析,研討會成員認定,科爾曼和他的團隊的研究不存在問題(Mosteller和Moynihan 1972)。
自那時起的很多研究,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做的,無論使用的是科爾曼時期的簡單方法還是現如今的先進手段,一再證實科爾曼當年的結論(Hanushek 2002; Neal 2006; Woessmann 2005a以及其中的參考資料)。本書中有三章內容將彼時的文獻與現今的平等機會問題研究銜接起來,考察重新關注為弱勢群體提供額外物質資源,可以在何種程度上改變教育結果的分佈。Julian R. Betts和Paul E. Roemer(第9章)發現,如果單純依賴額外增加開支作為唯一的干預策略來實現種族群體間的平等,那麼學校將需要在黑人學生身上花費相當於白人學生8倍到10倍的金錢。類似地,Eric A. Hanushek(第7章)發現,為弱勢群體平均化標準師資投入或者削減班級規模對於消除得克薩斯州種族群體間的現有不公平無濟於事。對歐洲來說,Leuven和Oosterbeek(第8章)同樣證明,荷蘭若干項再次將資源向弱勢學生群體傾斜的政策(削減班級規模、額外增加人員資源、額外增加計算機資源,以及延長義務教育時間等)未能改善平等機會問題。
在科爾曼進行的所有與物質資源有關的調查結果中,至今仍然極具爭議的一條發現與班級規模有關,班級規模亦即一個學校的學生與教師的人數比例。科爾曼和很多其他學者發現,從各方面看,無論規模大小都沒有什麼影響(Hanushek 1996; Hoxby 2000)。很多普通教師、家長和學生都認為這個結果難以置信。田納西州的一項大型實驗研究證明,班級規模的縮小對於學生成績有正面影響,這對這種常識般的觀點給予了支持(Mosteller 1995; Krueger 1999)。近年來,一項關於班級規模的國際研究發現,班級規模的影響十分有限,除了兩個國家例外,在這兩個國家裡,教師收入低、教師資質也特別低。這似乎說明,班級規模的縮小可能在教師資質低的情況下是一條提高學生成績的有用辦法(Woessmann和West 2005)。這些結果可能與前述的荷蘭在班級規模方面的准實驗研究相一致,Leuven和Oosterbeek(第8章)對此做了報告。他們發現,縮小班級規模的影響微乎其微,這個結果在擁有一支收入頗豐的教師隊伍的國家裡完全可以預見。但可以確定的是,關於這個主題仍將持續開展多年的研究。
1.5同伴群體與學校分層教育
科爾曼的第二個頗具爭議的發現是,學生在學校的同伴群體的素質,是影響其學習成績最重要的與學校相關的因素之一。黑人學生如果與白人一起上學則學得更好。更籠統地講,處於社會劣勢地位的學生如果能和更加佔據社會優勢地位的學生一起上學,他們的學習成績會更好。但反之並不成立。白人學生的學習成績並沒有因為黑人孩子的存在而受到負面影響。
這些研究結果極大地鼓勵了那些反學校種族隔離運動的領導者們。此外,這些研究結果也與一個年深日久按學生能力將學生分開的教學實踐背道而馳。這種做法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的基礎之上的: 學生和與其學習成績相近的同伴在一起可以學到最多。在很多歐洲國家,處於青春期早期的學生過去乃至現在仍然被送往不同的中學讀書。能力更強的學生被分配到更加學術性的課程中去,而那些能力欠佳的學生則被送往一個課程內容更加籠統或者職業教育的學校中去。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學生過去和現在都上一樣的綜合性中學,但是被分配到不同的課程軌道上去――學術、普通,或者職業“軌道”。如今採納綜合學校模式的很多歐洲國家通常都採取了類似的分層做法。
在科爾曼研究結果的指導下,許多學校改革者開始廢止雙重學校制度或者校內分層教育。如果能力弱的學生可以得到幫助而且不會對學習成績更好的學生造成負面影響,那麼這個政策將既促進平等機會,也可以促進整體人力資本提升。但這仍然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在本書中,學者們給予了各種回答。在本書第4章,Jacob Vigdor和Thomas Nechyba發現,使用如科爾曼調查和其他調查中所使用的標準方法來評估的同伴群體影響未能反映真正的因果關係。他們使用的是高級計量經濟學方法以及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廣泛的面板數據來區分相關性與因果關係。他們指出,傳統方法無法輕易測量能力;那些因為測量不准而顯得能力較高的個人被分配到明顯能力更強的同伴群體中;此類分層將導致同伴影響失准,除非該分析能將分層過程的因素考慮在內。同樣,Hanushek(第7章)使用了來自得克薩斯的面板數據,研究顯示同伴群體的能力或者社會經濟狀況對學生的表現幾乎沒有影響。這些調查表明,曾一度被認為已經有了定論的同伴效應問題,現在卻又回到了研究日程的頂部。
在第5章裡,這項研究得到更深入的討論。為了瞭解混合班級的效應,Fernando Galindo-Rueda與Anna Vignoles使用了英國一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數據。當時,不同的地方教學機構,分快慢班制度與不分快慢班制度並存。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將不同能力學生混合的做法的唯一影響,大概就是降低了能力最高的學生的表現。因此,儘管學習結果上的不平等得到了消減,但是強迫尖子生降低其水平絕不是人們期望用來解決平等機會問題的辦法。需要注意的是,這也許意味著存在非線性同伴效應,因為混班以後,只是尖子生遭受了損失,卻沒有贏家。然而,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普遍適用於其他情景的程度仍不明了。社會和學業能力混合的最直接效應也許與其長期效應十分不同。學校重構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學生從一個學校轉往另一個學校,可以壓抑學生的學業表現,這是Hanushek在第7章要闡述的內容。
短期與長期結果的區別,也許有助於協調第5章Galindo-Rueda和Vignoles的研究結果。他們借助於Hanushek與Woessmann(2006)的跨國證據表明,從長期來看,混班教學可以消減學業表現上的不平等,同時既不會傷及平均學業表現,也不會傷及尖子生的學業表現。儘管這些研究仍將莫衷一是,Giorgio Brunello、Massimo Giannini以及Kenn Ariga在第6章所提出的理論模型卻十分難能可貴。該研究考慮到了一些決定實施篩選式教育最佳年齡的關鍵經濟要素。
1.6以結果為導向及成績標準
也許與其說科爾曼最偉大的貢獻是他取得的具體的研究成果,不如說是他所開拓的思路。至少在一個方面,他將公眾的注意力引向了教育的輸出(即學生學到了多少),而不僅僅是輸入(教育年限、支出、班級大小、教師工資,以及教師資質),而後者曾一度被視為學校質量的首要指標。
1969年,就在科爾曼報告發佈後不久,美國諸州教育委員會(U.S.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發起了國家教育進步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稱NAEP)。這是一個全國性抽查考試,受試對象為9歲、13歲和17歲的學生,旨在獲取他們在學習表現方面的信息。通過週期性舉行該抽考,人們期望NAEP可以記錄學生表現隨時間推移而取得的進步。幾乎在同時,國際上一群學者成立了國際教育成就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該協會隨即啟動了首次對於許多發達工業國家中學生的數學和科學學業成就可比數據的系統化採集。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國際化評估得以週期性舉辦,最終演化成為定期舉辦的“國際數學與科學學習趨勢”(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評估,其最近一次考試發生在2003年。TIMSS評估始於2000年,後來的PISA調查對其是一個補充。關於PISA我們前面有所提及7。
NAEP、TIMSS、PISA,以及其他類似調查得到的結果,都要比科爾曼的許多研究成果更加令人眼界大開。其中,NAEP本來要研究美國教育的“進步”,結果卻揭示了教育的停滯――2005年中學畢業生的表現並沒有比1970年的好多少(美國教育部2005; Peterson 2006)。同時,TIMSS和PISA的調查發現,日本和其他亞洲學生,而不是歐洲或北美學生在數學和科學方面的成就最大(例如: Mullis等2004,以及許多其他早期研究)。工業化世界的後來者是如何如此迅速地達到教育的頂層位置,仍然是一個謎團,分析家對其謎底仍在孜孜以求。對於上述各類國際測試的多個分析,都強調了盛行于亞洲的綜合性畢業考試(參照Bishop 2006和Woessmann 2005b)。這些考試往往在中學教育的最後一年舉行。其內容充實,學生取得的考試成績千差萬別,大學和用人單位往往極為重視。通過確定清晰的目標並提供不同的完成層次,這類考試往往能夠激勵學生、教師和家長朝著較高表現水平而努力。本卷中由John H. Bishop與Ferran Mane完成的這一章(第10章)對此進行了討論。該章通過美國的證據表明了畢業考試和較高畢業要求的正面效果。
1.7學校的選擇
最後,永遠對新點子保持開放態度,且無論自己的發現有多麼驚人都永不滿足的科爾曼,通過又一項研究開闢了新的研究空間。這篇論文的題目為《公立和私立學校: 中學分析及其他》,也是由美國教育部委託完成的(Coleman, Hoffer和Kilgore 1981,1982; Coleman和Hoffer 1987)。在這項研究中,他們收集了學生表現及其背景特徵,以及公立和私立中學的多種學校特徵。當研究結果公佈的時候,公眾非常震驚。他們瞭解到,學生在天主教學校能學到更多,而這些學校此前被認為是那些出於宗教而不是教育目的的家庭送子女去的、低成本、下等的學校。然而,與以前一樣,他的研究結果在使用更加精細的研究方法就不同的數據組而進行的其他調查面前,仍舊展現了較強的穩健性(例如: Neal 1997;最新近的文獻綜述請見Neal 2002; Wolf 2006)。然而,後續研究卻揭示出了一個科爾曼報告中原有的、此前未被關注的觀點,即天主教教育的好處,對於少數族裔,特別是對於非洲裔美國人的好處,要大於對白人學生的好處。
科爾曼的這篇論文導致了大量旨在促進學校選擇的政策性干預,既包括公立學校之間的學校選擇,也包括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的選擇。研究人員才剛剛開始梳理歐洲和美國嘗試過的多種擇校干預行動的影響(參見Howell和Peterson 2002和Hoxby 2003對美國的研究;Bradley和Taylor 2002, Leva ic' 2004,以及Sandstrm和Bergstrm 2005提供的歐洲的例子)。本卷包括了參與此話題討論的兩篇頗有價值的論文。在第11章裡,Simon Burgess、Bredon McConnell、Carol Propper以及Deborah Wilson使用了廣泛的英國學生管理數據。他們的研究表明,只要學生擁有可以住宿的選擇,則附近學校的選擇組的大小與住校後學生依照能力和社會經濟地位所展現的跨校分層正相關。本卷中關於學校選擇的另外一章由Daniele Checchi與Tullio Jappelli(第12章)完成,呈現了意大利的例子。來自意大利的證據表明,將子女送往私立學校的家長,對於他們當地公立學校質量的評價要比那些將子女送往公立學校的家長低一些。這表明,當家長面臨低品質公立學校的時候,往往會逃往私立學校。
1.8結論: 教育效率是不是通往教育公平的最佳道路?
許多關於學校對平等教育機會問題影響的話題,都是由科爾曼的研究工作提出的。但也許他的影響最深遠的遺產(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卻在誘發人們對於教育機會平等的意義感知的變化方面(參見Coleman 1968)。在科爾曼報告發佈以前,平等教育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傳統方式闡釋的: 學校應該為所有學生提供平等服務。但是當科爾曼的報告表明平等的資源――包括平等的開支、平等的設施、資質平等的師資等――未能帶來平等的結果,於是平等機會的定義開始發生了巨變,提出了超出資源平等化的要求: 對於弱勢群體應當實施集中額外資源的補償性教育。通過確認和拓展科爾曼的初期研究結果,本卷來自美國和歐洲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弱勢群體上花費大量區別性開支,也不見得能獲得結果的平等。
鑒於平等機會問題可以歸因於可度量的、物質性的學校特徵的程度如此之小,人們要求學校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學校也探索了許多替代方案,諸如去分層化、更靈活的課程、重視孩子的自我感受勝過重視他們的學業成績、通過測試來確保沒有孩子掉隊,以及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選擇。去分層化以及很多其他措施的效果嚴重依賴于同伴效應的準確性質,而這一點至今仍未有較好的理解。在推進我們理解的同時,本卷中呈現的美國和歐洲的證據,亦未能對同伴效應提供準確無誤的答案,儘管美國和歐洲的研究人員提醒人們,任何隨意的同伴效應很有可能哪怕存在也是微乎其微的。有些研究呈現的結果表明,較高的表現標準――如果能恰當實施――則有望降低不平等的情況。精准選擇項目也可能幫助被困在低品質學校的弱勢群體學生,但是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項目的設計,而其長期效果仍然是未知數。有鑑於此,本卷中收集到的這些證據,儘管展現了一些取得進步的可能途經,但它們仍然對很多學校所採取的激進的改變機會結構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
根據目前所知,人們不宜期望短期內就能出現奇跡。當人們將平等機會定義為輸出平等的時候,學校將難免捉襟見肘,儘管誰也不能指責學校竭盡所能幫助那些弱勢群體。學生從別處學得太多,家庭各不相同,孩子千差萬別,我們也不能對學校期望過高。但如果人們接受的是一個更陳舊的、更加廣泛認同的關於機會平等的定義,那麼這個問題就好辦多了。學校可以也應該挑戰學生潛力的極限。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一個高效的教育體系來挑戰每個孩子,讓他們都實現自己的潛力。在那個意義上,一個高效的教育體系也有助於實現平等。正如Theodore Schultz(1981,88)在25年前說的:“在尋求平等的過程中,人們忽視了教育效率和平等的互補性。在我們龐大的學校體系中,如果能實現效率的最大化,這對於公平的貢獻很可能將遠遠大於現在正在實施的許多改革。”
注釋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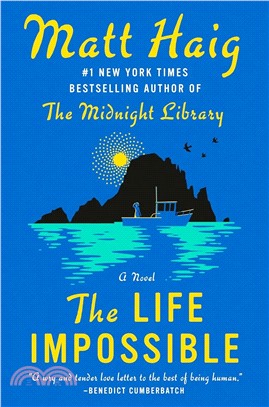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