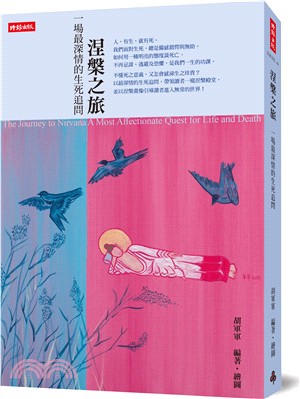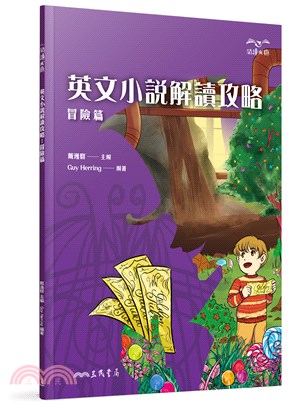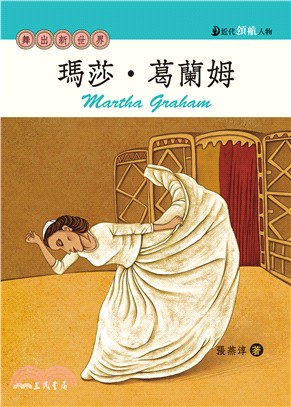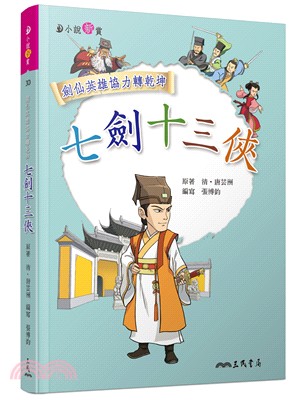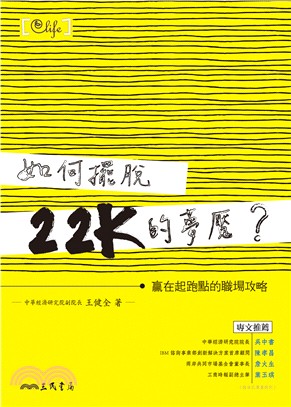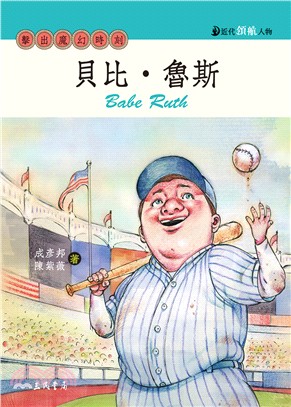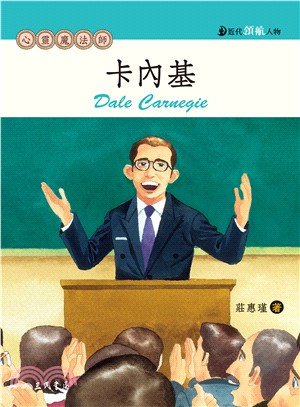涅槃之旅:一場最深情的生死追問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我們面對生死,總是備感錯愕與無助。
如何用一種明亮的態度談死亡,不再忌諱、逃避及恐懼,
是我們一生的功課。
不懂死之意義,又怎會感涕生之珍貴?
以最深情的生死追問,帶領讀者一窺涅槃殿堂,並以涅槃畫像引導讀者進入無常的世界!」
參究生命真相,引領生死開闊
死要死得從容,生要生得雋美
本書由胡軍軍與林谷芳、首愚法師、繼程法師、寬謙法師、鄭振煌、李光弘長老、陳嘉映、詠給‧明就仁波切、林清玄、成慶、濟群法師、柴中建等,分別以採訪、專文形式,與讀者一起探究生死和涅槃的終極意義,以及豐富而細緻的生死思辨。
‧我渴望生命的每一個當下湛然明亮。涅槃之路雖然遙遠,好在有了耕耘的起點。
‧一切的執著終將過去,一切的繁複將歸為簡單,我將不再是我,世界也不再是世界。
‧我竟然與古代的石窟藝術家們心靈相通,似乎回到童年清朗的視線,客塵煩惱褪去一層。
‧一個藝術家的觀念在宇宙萬法裡何其微不足道,一個個體生命的悲喜榮辱更是夢幻泡影。
書末收錄:印順導師《佛教的涅槃觀》與星雲大師《涅槃》專文
作者簡介
1971年生於中國上海,浙江紹興人。90年代混跡北京,從事詩歌繪畫創作,1995年獲劉麗安詩歌獎。1998年移居紐約八年,2006年回上海定居至今。曾舉辦「山外有山」、「常觀無常」、「涅槃本色」、「涅槃天下」等繪畫展覽,並創立「高安基金會」,在教育和佛法推廣方面有廣泛贊助;同時籌備「阿虛博物館Ash Museum」。自2015年起創作《涅槃》系列,以繪製佛像為弘法心願。
序
〈自序〉
涅槃生死等空花──胡軍軍
我向來對生命──生從何來,死往何去,這件事情充滿了迷戀。從身體入手,試著反觀我們這個身體,還有比我們這個身體更能生出各種欲念,領受各種奇妙的感覺的嗎?時而得意忘形,時而悲痛欲絕,時而大夢初醒,時而輾轉難眠;這個身體長袖善舞,口吐蓮花;這個身體,創造了文明,號稱改變了世界。只是這一切,這個身體,當油盡燈枯之時,似乎宇宙戛然而止。死亡,從未對誰網開一面。
中國人向來不愛談死,我不合時宜慣了,也就不在意再多一回。因為各種的因緣際會,從二○一五年起,我選擇了「涅槃」作為繪畫的創作題材,原因可以列上很多,回報佛恩是其中一個;更重要的是,涅槃的境界對我構成了無以復加的吸引,試想誰能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束縛,誰能優游生死的大海,誰能衝破大限,面含微笑掌握離去的時刻,誰能看破放下,誰就是圓滿自在!
我因為畫了「涅槃」,感覺生命有了種無形的能量圍繞左右,老天賦予了我很多方面的「專美」,使我忐忑經常,而不得不絞盡腦汁,能分享點什麼就盡量眾樂樂。此書的緣起正是如此,因為畫「涅槃」的關係,我藉由因緣請益周邊能遇到的善知識,請他們分享他們心中的涅槃觀、生死觀,以及種種來自生命深處的心得體會。他們每一位對我的啟迪,使我今天迫不及待地要整理成冊,與每一位讀者分享他們獨特的人生軌跡,因為我充分地相信,有一天,沒準書中的哪一句話,會點亮黑暗,溫暖孤寂的心靈,撫平我們從未消失的生死恐懼。
首愚和尚,是我今生唯一遇到的一位曾經修持多次「般舟三昧」法門的僧侶,這種修行方法的嚴苛程度對於普通眾生而言,不啻為天方夜譚。單論這種求道的決心,就足以讓人仰視了!修成正果,是要發大心的,也許我們太多人在發心上就怯弱了一大截,更遑論這往後的道業了。弘法幾十載,我眼中的首愚和尚秉持「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精神,行履不止,是真正的佛門楷模。
繼程法師,他的笑容如琉璃般純淨,我對他的採訪在法鼓山的本山舉行。法鼓山於我如同學佛路上的娘家,我二○○三年開始接觸佛法,讀的正是聖嚴法師的書籍。當初在紐約的東初禪寺皈依聖嚴法師,他所賜的法號「常觀」,我特別珍惜沿用至今。而繼程法師,作為聖嚴師父的法子之一,如今是法鼓山備受歡迎的禪修導師,他的著作也是廣受信眾的青睞。他渾身的自在氣場,是對禪修最好的解讀。
此書中的寬謙法師,我與她的因緣最深,也是書中唯一一位女性出家人。寬謙法師延續了天台宗講經說法的脈絡,開創了她獨特的教學風格,啟發了許多人的法身慧命。在當今的佛教界,她的存在難能可貴,她的教法值得被更多人關注。我跟隨寬謙法師有許多次各國佛教遺址的朝聖機會,她的行動無數次在有力地實踐佛陀所教的緣起性空之法。她既然發願生生世世願為女性出家人來福澤娑婆世界,我但願有幸依然有來生的護持機會。
李光弘長老作為基督教義的代表,也是我希望書中提供一個更廣泛、更寬容的角度給讀者來面對生死。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在哪扇窗口遇見最宜人的風景。事實上,在我們的交談過程中,我傾聽的經驗相當愉悅。光弘長老在他的教區受人愛戴,他的佈道散發著神性的魅力,真善美從來不是一種理論口號;當真善美付諸生活的點點滴滴,請相信,宗教是沒有界限的,人和人之間是高度互愛,不分彼此的。
鄭振煌先生曾經翻譯過一本家喻戶曉的書籍《西藏生死書》,他本人也是位修學有成的大居士。他在生死學方面的研究極其深入,而他對生死的態度可謂雲淡風清,讓我想到一句: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記得那晚在他的維鬘學會採訪結束,鄭先生堅持送到電梯口,他送別一位晚輩居然用超過九十度的鞠躬禮,那瞬間我眼眶一熱,他是在親身教導我如何去除我慢啊!
陳嘉映教授是我二十出頭就認識的老友,只是我當年年少輕狂,經常自以為是,那種舍我其誰的青春歲月,嘉映和他周邊的朋友瞭解最多。我一九九八年出國遊歷之後,再見其面,已是十餘年之後,陳嘉映已被稱為「中國最可能接近哲學家稱呼的人」,他的學生已桃李滿天下了。哲學,我始終認為就是圍繞在關於生死的討論,所以此書中,從一個哲學家的角度來探討生死,應是珍貴的一篇了。
明就仁波切的名字,大家熟知他是因為他被西方媒體稱作「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早年我在國外定居時就聽聞過他的名字,後來聽說他放棄一切的一切,身無分文,居無定所,足足在野外生存了四年,中間經歷了最直接、最凌厲的生死考驗。最近幾年,明就仁波切在中西方廣泛教育禪法,無數人得益於他的禪修指導。我專程飛去加德滿都完成對他的採訪,滿足了我一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的好奇心;當然,我尤為看重,仁波切對死亡過程的開示,那是我心中最珍視的部分。
林清玄老師,提到這個名字,我的心中依然有痛楚掠過;就在他逝去的九天前,我在臺北對他作了這場關於涅槃和生死的訪談,雖然他說過「來是偶然,走是必然」,但我們之中,誰真正做好了這場死亡的告別呢?在席間,他強調他是位浪漫的佛弟子,他把浪漫的精神一直貫徹到了此生的最後一刻,也給世間示現了「無常」的根本!
成慶老師,是位在學院執教的青年學者,他對中國佛教史的熟稔和日本禪宗史的深入,可以為當今年輕學子展現一位宗教學者的魅力;畢竟,未來是年輕人的世界,而他們在青年時代所形成的世界觀,需要明亮而溫暖的指引。黃泉路上無老少,誰說年輕人就不需要面對生死呢?理解了生死,才能更強大、更明白活著。
濟群法師在本書中的這篇文章是對涅槃的全面注解。涅槃這個主題,平常少有人關注,要把涅槃說清楚,也非得有一位學識深厚,具真知灼見,具修行經驗的高僧大德才能勝任。說來跟濟群法師的師徒緣分,也有十幾年了,如今他的弟子遍布大江南北,不可勝數,法師卻依然身著一襲發舊的僧袍,初心未改,將佛陀的智慧言傳身教,感化著這一方淨土。
柴中建老師曾經在藏地閉關多年,他精通哲學和佛學,同時涉獵文化藝術領域。宗教和藝術從來都不可分割,對我個人而言,尤其如此。在書中,有這篇評論,是極為恰當的補充。
林谷芳老師,是兩岸三地風光最為清奇的禪者代表,禪門有他,平添不少意趣。本來禪門不說涅槃,就像禪門不立文字,但該說時還得說。蒙老師不棄,為本書作序,也是對眾多行者的拈提之力,涅槃,解脫,頓悟,空性,說了一大堆,最終要見的是般若,而不是執著般若船。
印順導師有「玄奘以來第一人」的美譽,只是他的學說晦澀艱深,其思想高度非常人所能企及。這次搜尋有關「涅槃」的資料,所幸導師留下這篇彌足珍貴的「涅槃」文獻,應該作為當世最為權威的「涅槃」詮釋,在此特向印順文教基金會致敬,感謝願意授予版權在本書中發表。
星雲大師則是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向我們開示了「涅槃」。大師終其一生,用「光照大千」的氣度在全球設立了三百餘個道場,我有幸在最近幾年,多次領略大師的風采,他如同一座須彌山,為當代佛教的復興寫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章,至為可敬可佩!也向佛光山一併致謝,允許使用此篇文獻。
還有太多人為本書的最終呈現功不可沒,雖然我沒有將名字一一列出,相信他們同樣能夠收到我來自內心最誠摯的謝意。常說八萬四千法門,對治八萬四千煩惱,本書並不期待找到一個一致的生死解決之道,而是希望將這些智者的見解一一列出,如能各蒙甘露,實在是令人萬分欣喜之事。
我的涅槃畫作還會繼續,涅槃之道,我走得心甘情願。學佛是生生世世之事,而這一世,我無比珍惜同「涅槃」朝夕相伴。
二○一九年二月 上海
繁華落盡見涅槃——林清玄訪談
胡軍軍:您文學上的成就斐然,好多篇文章被選入了教科書,同時您也是位虔誠的佛弟子。如果現在在卓越的文學才華和佛學上的證悟兩者之間只能選一個,您會選哪個?我的意思一面是鮮花掌聲,一面是一個清冷的小小的證悟。
林清玄:我覺得不能選,原因是這一切的形成都是因緣,有時候是由不得你的。比如說我跟佛學結緣,是我九歲的時候。那一年我們家龍眼生產特別多,我父母親就說,那你背一些到佛光山給師父吃,因為聽說有個師父在那裡開山。從我們家走路到那裡大概半個多小時,我就背著一簍龍眼跑到山上去。到了以後,龍眼放下,我打算要走了。有一個人過來說:「小兄弟,你要不要皈依?」我說:「皈依是幹麼?」他們說:「就是拜師父。」我說:「拜哪個師父?」他們說:「就是前面那個師父。」我一看,是一個年輕的英俊的高大的師父,完全顛覆了我的想像。我說:「好,他看起來滿精神的,應該有資格做我的師父。」我把簍子放下來,我就皈依了星雲大師。
胡軍軍:所以您也沒多想?
林清玄:沒多想,那時候九歲,皈依到現在五十八年,成了佛弟子。因為皈依的佛光山離我媽媽家很近,走路就會到,所以有空就跑過去混混,就跟佛教結緣了。
胡軍軍:那您跟文學是怎麼結緣的?
林清玄:我跟文學結緣也差不多在那個時候,八歲的時候。那時候我就想,我們家歷代都是農夫,我不要做農夫,農夫太辛苦。那有什麼事可以做?想說寫文章給人家看,所以立志要當作家。為了生活的實際需要,就試圖跟文學比較靠近,一直尋找我的出路。後來我就到了城市,到臺北。到臺北在我們那個年代算很遠了,現在當然很近。我跑到臺北找出路,然後因為寫文章的關係就當了記者,然後當了報社的主編,那時三十歲。按一般的定義來講,我算成功比較早,因為我三十歲的時候就做報社的總編輯了。
胡軍軍:很年輕就名滿天下了。
林清玄:所有的重要的文學獎我都得過,我的書已經有很暢銷的了。暢銷書排行榜裡二十本裡面大概有六本到八本是我的書,大家都覺得我很成功。我在電視臺主持一個節目,在廣播電臺主持一個節目,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可是我卻過得很不快樂。我想如果成功是這樣,那就不值得追逐。在三十歲時有一天我讀到一本書,叫做《奧義書》——印度哲學很重要的經典,裡面說一個人到三十歲,要把全部的時間用來覺悟。如果到三十歲不把所有的時間用來覺悟,就是一步一步在走向死亡之路。那一年我正好突破三十歲,我想說要開始走向死亡之路了,我應該找出路,讓自己快樂。所以三十歲那一年我就上山去閉關。帶著我師父的書,就是星雲大師的演講集,還有「人間佛教」的一些著作,在山上待了快三年,完全沉浸在佛教裡面,確立說這個是我這一輩子要尋找的路。
但又想到佛教的思想這麼好,可是知道的人那麼少,應該有人來告訴他們說,它的思想真正的好在哪裡?要怎麼傳播?那時候正在寺廟裡面幫師父燒那個冥紙,看到火光裡面浮出三個字,林清玄,嚇一大跳,這註定是我要做的事。不到一個月我就下山了。下山以後我在想怎麼樣用最快的速度傳播佛法?應該是演講跟寫作,所以我就開始寫佛教的文章,然後找一個地方去演講,當然是要找最大的最有影響力的地方。我計畫要去演講,大家說:「哪有居士在演講?」那時候很保守,不讓我演講。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地方叫菩提講堂,我就說我每個星期來幫你講一場佛教,我都不收費,如果有人捐獻的話,就全部送給那個演講的地方。所以在我演講的地方就擺一個大盆在門口,來聽演講就樂捐。一開始的第一場來聽的才不到二十個人。
胡軍軍:您記得當時講的什麼內容?
林清玄:當時我第一場講的是《心經》。我有一點改革精神,一般佛教的師父講《心經》一講講半年,我說我要在兩個小時裡面講完《心經》,那時候頭腦很好,演講都不用稿子,要講的東西全部在腦子裡面。
胡軍軍:您是從小就特別有演講天賦嗎?
林清玄:不是,完全是自我訓練。後來有人問我:「你怎麼那麼會講?」我說:「很簡單,如果你一年講上一百場演講,連續講十年,肯定是很會講。」因為後來我主持電視跟電臺的節目,大概口才訓練得還不錯,電臺節目是每天直播,一大早六點到七點叫「林清玄時間」,就是上去跟讀者閒聊。因為我很忙,沒時間準備,後來就養成了會講的習慣。
一開始第一場是二十幾個人來聽,聽完以後馬上口碑就傳出去,說我講得真好,一兩個小時就完全知道《心經》是在講什麼。然後聽眾大概每星期都成倍數增長,幾個月之後,每次我演講那幾天,外面的三條街都塞車,沒辦法停車,車也走不動,很多員警來管制交通,來問說到底在幹麼?怎麼塞成這樣?他們就說是林清玄在演講。後來規模愈來愈大,變成每次演講都從四樓,沿著樓梯一直到一樓這樣,塞滿了聽眾,完全沒地方坐。一講講了大概兩年多,那個地方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講堂。
我的演講特色就是在兩個小時裡面把一個題目講完,比如說《維摩詰經》,我就講兩個小時講完了,《金剛經》兩個小時講完了。其實這並不難,關鍵找幾個非常重要的重點,比如說你要講《金剛經》,你就記住,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你把幾個重要的概念記起來,然後就講這幾個重要的概念,讓你知道原來是這樣子,讓你聽完有重重的一擊的感覺。
比如你要講《心經》,你就講觀自在菩薩,講行深,一直走到最深的地方,智慧就開起來,大概很簡單明白的講;比如說有一講我講蓮花,大概聽眾聽完了以後一輩子都不會忘,因為我說蓮花,在佛經裡面說蓮花有五德:清淨、細膩、柔軟、堅韌、芳香,這是蓮花的五種德行。但是一般人記不住,我說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方法來記住蓮花有哪五種德性?清淨,就是台語叫做白泡泡,很潔白,用臺灣話記很容易記住。細膩,就是油密密,柔軟,就是檸信信,堅韌,就是Q堆堆,芳香,就是堂公公。以後他們一下就用台語把這五個德行記下來,就知道蓮花原來有這五德。為什麼佛教用蓮花做象徵?因為蓮花最具有這五德,然後最柔軟。你要知道你有沒有辦法去西方極樂世界?很簡單,找一個蓮花池,找一朵蓮花坐上去,你會發現蓮花馬上扁掉,為什麼?因為你的身心很濁很重,它撐不住。你要練到什麼樣的狀態,可以在蓮花裡面化身?你要身心輕快,然後你有這五種德行,就馬上可以投身極樂世界。那怎麼樣使你的蓮花開啟呢?我就說《心經》最後的寄語是,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就是說你要去彼岸,你要去彼岸,一直努力地去彼岸,祈求內心的蓮花開放。大概如此,我會把整個重點的精神融會貫通。
後來人實在太多了,菩提講堂已經坐不下了,我就開始辦那種大型的公開的演講。曾經辦過一場,在臺灣的桃園巨蛋,五萬人的會場,大概只有兩三個人曾經在那裡演講過,一個是星雲大師,一個就是我。那時候應該是破紀錄的,但是傳出很多謠傳,說我是菩薩來化現的,我演講的時候背面都有佛像,人來了就會先禮拜,大家就說我很驕傲,為什麼人家在禮拜的時候我還是繼續講,視若無睹,我說他們又不是在拜我,他們在拜後面的佛像,可能到後來變成有一點以訛傳訛。
其實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有什麼特殊,我只是不斷地在尋找覺悟之道,然後希望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別人,什麼是覺悟,覺悟要走向哪裡。大概我的基本精神是這樣,可是那時候影響力滿大的,所以有的人就說我影響了整個佛教的復興。因為那時候基本上這些大師都變成我的好朋友了,他們出書的時候都請我幫他們寫序,我幫星雲大師寫過序,幫聖嚴法師寫過序,幫證嚴法師寫過序。很多師父要傳播他們的想法的時候,就找我寫序,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一路走來,我的方向應該是沒有扭曲,一直都還是我原來所要找的方向。
胡軍軍:有一部經典,《大般涅槃經》,我覺得現在被提到的機會很少,我自己也沒聽到過有人專門解說這部經;在您的《菩提系列叢書》裡,您在很多處引用「大般涅槃經」的句子,這是一部怎樣的經典?您是怎麼理解涅槃的?
林清玄:佛教有很多經,一般人比較少機會接觸。當年我在山上的時候,總共讀了大概有兩千部佛經,經律論裡面經的部分讀的特別多。《大般涅槃經》就是講一個人,也就是佛陀,從入胎一直到成佛,在人間的基本的過程。其實我演講講過涅槃。當我們講到涅槃的時候,會從幾個重點來講。當時佛教的翻譯家把梵文翻成中文的時候,對那些特別難懂的東西,不翻譯,比如說涅槃、般若、菩提、菩提心等等,他們不直接翻譯。譬如說般若,我們應該翻成妙智慧,如果用中文。可是他們不翻,為什麼不翻?因為讓你思考,就好像走路踢到石頭一樣,讓你思考什麼是般若?你就開始去研究。你會發現般若很難,因為佛教的《心經》是從《般若經》裡面來,《金剛經》也是從《般若經》裡面來。然後最完整的一部叫《大般若經》,六百卷,大概我看那一部就看了六個月,從頭到尾在看。
涅槃也是。涅槃,什麼是涅槃?涅槃翻成中文就是究竟的止息,最終的止息。為什麼不翻?因為翻了以後你會想說,涅槃就是死了。可是行住坐臥,裡面都有涅槃。佛教裡面說要行如風,要坐如鐘,要立如松,要臥如弓。行住坐臥,都是涅槃的一部分。所以我把涅槃翻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管是行住坐臥,都把你的身口意捏死在盤子裡,大家一聽就懂了,原來是這樣子。你在行住坐臥,你的念頭都止息。這個境界就很高,這就不是只是死掉。就是說你在拜佛的時候,你的意念止息,那你就涅槃了。所以涅槃基本上如果用活潑的態度來講,就是禪心開啟的狀態,你在走路吃飯的時候,禪心都開啟。如果你沒有禪心開啟的狀況,就是你拜佛的時候你的心也不止息,你讀書的時候你的心也不止息。你的心止息了,你就不但很活潑,而且不怕孤單。
我聽到過一句話講得很好,「你要有文化藝術的修養,你就不怕人生的孤寂。」人生很孤寂,找不到可以談話的人,找不到相應的人。可是因為你內在有那種很好的修養,所以你孤獨的時候也很好,不孤獨的時候也很好。涅槃有一點像這樣。有一部電影叫《一個人的武林》,我們說一個人的修行,就是涅槃,你完全活在你的內在的狀態裡面。《大般涅槃經》就是講入胎,經過多少個月,他的成長,在成長的過程裡面意識在裡面怎麼養成,然後直到死亡,其實是蠻人間性的。
胡軍軍:我讀到過一個史料,大約在東晉時期後兩百年左右的時間,當時存在過一個學派叫涅槃學派,當時很多的高僧被稱作涅槃師,他們就這部經典做了很多的討論和爭辯,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這部《涅槃經》的沒落?
林清玄:原因很簡單,佛教是跟著時代在變革的。佛教在中國曾經有八大宗,每一宗派都是很興盛的,像弘一大師修的律宗,玄奘大師創的唯識宗,智者大師的天台宗,還有即使不只在西藏,在中國也有密宗,在唐朝時候都是很盛的。為什麼大部分的宗派都消失?你現在要修唯識你很難找到老師,我以前曾經在寺廟講過唯識。為什麼會沒有老師?因為那一套就很難理解,你就很難進入那個狀況。譬如說律宗很難,你要一條毛巾用到破,然後睡覺的床,一定不能睡高廣大床,你的床要寬度三尺,長度六尺,然後你不能塗香花鬘的,不能用香皂,你一定要去買那種洗衣服的肥皂,反正就是太多規矩,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又譬如密宗的觀想,是特別難,那就會被淘汰。佛教不會淘汰眾生,但是眾生會淘汰佛教。其實這也是末法的特徵,很多很好的宗派像華嚴宗、法華宗都不如從前了。華嚴宗依靠的經典就是《華嚴經》,《華嚴經》是特別美的一部經,因為眾生的心不美,所以華嚴宗就沒有人修行了。《法華經》在日本是很風行的,在中國也很冷清了。所以淘汰到最後,變成禪淨雙修,禪宗跟淨土宗。因為禪宗跟淨土宗的經典是特別簡單,《阿彌陀經》、《六祖壇經》,一般人都讀得懂。你看像《大般涅槃經》、《大般若經》、《楞嚴經》、《楞伽經》那種,一般人大概讀第一章就讀不下去了,門檻很高,「七處征心」,用各種方法阻擋你,不讓你一下就跨進來。眾生都比較懶惰,跨不過去,那就算了,我找別的門進去。後來又有一種說法,每一個法門都可以進入最高的境界,所以那個不能修也沒關係,我們來修別的,到最後就變成最簡單的淨土宗。大家不會去看經典,也找不到老師,就變成這樣。
胡軍軍:這麼多年的學佛經歷,佛法在您身上所發生的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林清玄:應該說是翻轉人生。我以前認為人生反正就是不斷的追求,但是這種追求都是外在的。學佛以後就翻轉了,就變成比較更內在的追求。所以其實佛教是一個內在的革命。我常說,學佛其實很簡單,就是把貪瞋痴慢疑翻轉,轉成悲智行願力,是悲,是慧,力行、願望、力量,這你都有,就是五毒變成五智,這是最大的翻轉。在我的內心裡面,我知道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一般人不知道,一般都是把大部分的時間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
胡軍軍:相信您有很多的讀者是在讀了您的書以後,開始對佛教產生好感,之後慢慢開始學佛的。您是把文學作為載道的工具嗎?
林清玄:其實有幾個階段,一開始是把文學當成傳法的工具,跟我的演講一樣,就是說希望告訴別人佛教有多麼好,但是那時候自己不知道,我已經陷入了那種分別見,分別的心。我舉個例子,怎麼樣打破這個分別見。我那時候喜歡蓮花嘛,有一天要去看蓮花,我跟我媽媽講說,我可能要兩個多小時以後才回來,因為我要去某某地方看蓮花,聽說那裡蓮花正在盛開。我媽媽就說:「不要跑那麼遠去看蓮花,我種的芋頭也開花了,你去田邊看看芋頭開花。」我就跑到田邊去看我們家的芋頭開花,看了以後我嚇一跳,沒想到芋頭的花的美跟蓮花是一樣美,甚至更美。因為那時候正好有夕陽,然後芋頭的花是淺藍色的,我從來沒有看過芋頭開花,那是因為還沒開花,芋頭都已經被吃掉了。所以第一次看到非常震撼,所以就打破了我的分別見,原來世間的一切都是這麼美,不一定只有跟佛教有關的東西。所以從那以後,不管是我的文學或者對佛教的傳播,我想應該是自然的流露,這樣的態度最好。
所以那個階段應該說是繁華落盡見真純,你對繁華的那種見解已經不一樣了,突破了那種表面。所以我從事文學跟佛學,它們對我是貫通的。我寫過一個偈子,叫做「茶味禪味,味味一味,詩心佛心,心心相印」。我說詩人如果寫詩寫到很高的狀態,它就進入禪。像王維、蘇東坡那種詩歌,像白居易就進入禪的那種境界。反過來講,禪師如果開悟,他就自然會寫詩,很奇怪,像六祖慧能大師他不認識字,可是他開悟以後講出來的東西就像詩歌一樣。所以詩的心跟佛的心追求到最後是相通的,就好像老朋友相見,其實就是這麼簡單。但是一開始我們就起了分別心,說文學是怎麼樣?佛學是怎麼樣?比如說臺灣有名的詩人像周夢蝶,他的詩我覺得這是一個開悟者寫的詩,他不講佛教,可是那裡面就讓你覺得這樣的文學詩歌,到了最後的境界大概就是如此。
胡軍軍:上次見到您,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點,說您皈依了一百多個師父。您為什麼會皈依這麼多師父?哪幾位對您產生了重大影響?
林清玄:皈依就是走向清白之路,後來我們明白皈依的實相,應該從這種形式的、表面的皈依回過頭來,找到皈依的真實價值。其實,皈依一個師父,就等於皈依了一切的三寶,也等於皈依了自性的三寶。
第一個皈依的師父當然是星雲大師。青年時期我曾經閉關,我的閉關跟一般的人閉關不一樣,不是說真正關在關房裡面,我的閉關是心的閉關,所以到假日的時候,我會到處去參訪名師。這些名師不管是臺灣的或者西藏的或者日本的,還有國際的有名的出家人,只要來臺灣,我就會去參訪。不只是出家人,像德蕾莎修女,她是位修行很好的人,我聽說她來臺灣,我跑去見她,那時候她快八十歲。
胡軍軍:您是我這一生碰到的唯一一位見過德蕾莎修女本尊的人。您對她有什麼印象?
林清玄:看到她的感覺就跟看到證嚴法師是一樣的,就是當她走路,你即使側耳貼在地上,也聽不到她走路的聲音,是這樣的人,非常安靜,然後移動非常的輕巧。這種輕巧,我叫做「見地唯恐地痛」,走在地上怕地會痛的那種感覺。看到這種人,我就會很自然的禮拜,覺得真的是太厲害了,修行太好了,雖然她跟佛教完全沒有關係。我那時候就是抱持著這樣的心,聽到哪裡有一個大師很厲害,我就會跑去見。
有一次我聽說有一個大師在那裡開示,接見群眾,幫人摩頂,我就排隊排三個多小時去讓他摩頂,摩了以後好像也沒什麼,依然頭髮愈來愈少(哈哈哈)。還聽說有一個師父,你只要看他一眼,你就不會墮入地獄;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就去看一眼,我跑很遠的路去。不過大部分都是假的,但是也有很多很好的修行人。像後來我也皈依印順導師,也皈依聖嚴法師,皈依惟覺法師,很多有名的法師,還皈依過很多法王跟仁波切。我很有興趣找他們去問法,通常問三句就倒了。
胡軍軍:您把人家給問倒了?
林清玄:我沒有把他們問倒,但是他們的答案就是讓我覺得俗,俗人的那種答案,比如說發財什麼那種。要拜多少拜,你就會得到什麼功德那種,我就覺得比較低級了,可能他把我看成是一般人。所以我當時就做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說拜梁皇寶懺,如果一個人自己舉辦一場梁皇寶懺,那會有多大多大的功德,在佛經裡面這樣說的。我真的找了一個師父,一個人辦一場梁皇寶懺,花了一百萬臺幣。那時候一百萬台幣算很多錢的。有位老師父,八十幾歲,他就整個寺廟為我辦了一場梁皇寶懺,七天七夜。那時候我比較有錢,一百萬就拜了一場。反正那時候就有一點好奇寶寶的樣子,然後皈依了很多師父,總共加起來大概超過一百位。
胡軍軍:是啊,上次聽您提到這個,我印象特別深刻。
林清玄:這個過程滿有趣,對各種宗派都有了一些瞭解。比如說我有一個師父叫做懺雲法師,其實是修行很好的,但在臺灣沒有什麼知名度,因為他是修律宗的,他跟弘一法師一樣,自己在山頂上蓋一個小廟,然後律宗修持地很好。我就跑去住他的廟,跟他住在一起。女眾來到他的寺廟大概三十公尺外,他綁了一條線,女眾不能跨過那條線。女眾有事站在紅線外面,敲磬「鈧鈧」響,然後師父就派人出去問什麼事。他連女眾的樣子都不看,反正律宗就是嚴格到這種地步。我是聽到敲磬,就會跑出去,問問什麼事?所以他收留我一陣子,發現我不是這種傳人,不適合學律宗。還有他們過午不食,下午一點後就不能吃了,有時候我餓的要命,我說:「師父,可不可以煮一碗米粉湯來吃?」類似這種。他很欣賞我,可是他覺得我不適合做他的傳人。後來他過世了,他的廟在有次地震的時候整個毀於一旦,完全找不到樁基,我是想將來如果有機會我可以寫出來。反正很多很有趣的因緣。
胡軍軍:那是太有趣的一些佛門故事。聖嚴法師是我的皈依師父,您談談他好嗎?
林清玄:聖嚴師父當時辦一個雜誌叫《人生雜誌》。有一天他上場說:「《人生》,這一次大家都收到了嗎?」我就問旁邊的朋友說:「這麼好!皈依他,還有人參可以拿,你們有收到嗎?」後來才知道是一個雜誌,《人生雜誌》。我曾經常去找他,他的學問很好,對什麼東西都有非常完整的見解。雖然不是我所嚮往的非常犀利的那種,可是他就是非常穩,做什麼都非常穩。我皈依他的時候很特別,我拜下去時就淚流不止,我就知道我跟這位師父應該有特殊的因緣。
胡軍軍: 弘一大師在臨終前寫下的「悲欣交集」,我每次看到那幾個字,總感覺這背後還有千言萬語,您如何解讀弘一大師的這幾個字?
林清玄:我寫過弘一的傳記。我寫過佛教的傳記不多,星雲大師我寫過,弘一大師還有玄奘大師,我寫過傳記。弘一那本傳記的書名叫《呀,弘一》,為什麼叫《呀,弘一》, 因為弘一對我來講就是生命的驚嘆號,看著他的一生這樣,就好像處處都留下驚嘆號,一直到死也是留下驚嘆號。所以他的偉大是來自於他修行的過程給我們的教化。所以「悲欣交集」,那時候我看到也很感動,就是說不清楚,人生修行這件事情說不清楚,所以「悲欣交集」。我也時常會這樣子,就是在最枯竭的時候會覺得人生就是這樣,說不清楚的人生,這個就是「悲欣交集」。從一方面,你好像找到了,就欣了;你好像還沒找到,所以悲。如果透徹了,就沒有悲欣的痛。透澈了就是,總有群星在天上,你在怎麼樣狀況底下都是燈火輝煌。可是因為「悲欣交集」帶給你的,就是還有一些未了的。所以我看到這四個字,我就相信說,弘一還會再來。
「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未嘗多結怨,浩蕩入紅塵。」菩薩在天上本來過得很好,像月光一樣,可是為了解救更多的眾生,所以整裝待發,浩浩蕩蕩再一次進入紅塵。「悲欣交集」給我的感受就是這樣,回去整裝待發了。
胡軍軍:剛才您談到弘一大師,您感覺他是願意再來世間的,聽了讓人驚歎感懷。如果說現在有西方淨土和再來人間兩個選擇的話,您會選擇去哪裡?
林清玄:我深深地相信一個觀點,就是書到今生讀已遲。如果你這一輩子才開始讀佛經,那已經太慢了。你肯定是讀過很多輩子,這一輩子才會碰到佛經。所以我對我自己的理解應該也是這樣子,在某個遙遠的地方,或者某個遙遠的時代,我曾經讀過這一部書,所以我才會歷歷在目,翻過去就有很熟悉的感覺。讀經典,馬上就知道重點在哪裡,然後歷歷如繪,這表示我從前曾經讀過,但是當時可能沒有究竟,所以這生再來。
我認為每世每一輩子你只得一分,如果一百輩子能成佛,下輩子我得兩分,下下輩子我得三分,慢慢成佛。所以我並沒有那麼渴望,說從此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聽鳥唱歌、講經說法,或者說走在黃金鋪地的臺階,這個對我來講還沒有木頭鋪地好,所以我沒有那麼嚮往那種境界。我覺得應該在每一個過程去經歷,所以我有幾本書在大陸還滿受歡迎的,有一本叫做《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光》,還有一本《所有的遺憾都是成全》。我上輩子可能留下很多遺憾,就是要為了成全我這一輩子。然後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光,把現在的時光掌握好,這才是最重要。類似這種其實也是在播下一些種子,其實這些都是佛教的思想,只是用一個很美的狀態把它包裝起來。
胡軍軍:您的文字裡有很多禪宗的故事,您平常會參禪嗎?禪對您意味著什麼?
林清玄:會。參禪,就是一般人認為是打坐,其實我自己是比較不拘形式,我不會說我現在要打坐,大家都不要講話,可能有種情形,大家都在吃飯,但你的心是安住的,那你就是在打坐。所以參禪對我來講,佛教講「戒定慧」,「戒」不是說你要不要喝酒什麼,那種叫「戒」,「戒」就是生命的減法,把那些不需要的去掉,我就在守「戒」;定,就是你的心放在一個地方;那慧就是有特別的見解,特別的體悟。
戒定慧都是參禪,所以基本上我會讀禪宗的公案、禪宗的書,然後我養成一種習慣,就是內心放在一個地方,然後盡量做生命的減法,把你的生命盡量簡單,就是有一個老妻、幾個老友、養一條老狗,類似這種生活就很簡單,簡單就是純粹,純粹就會接近「定」。「定」就是禪宗最重要的。
「禪」這個字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單純的心,右邊是單,左邊是心。你的心一直維持單純,那你就在禪裡。所以我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樣,我在教別人時也是這樣。我說:「好,你每天有八分鐘你的心很單純,這八分鐘你的心就在禪裡,你有八個小時很單純,你這八個小時就在禪裡。」類似這樣其實是一個改革的觀念,我以前常常去打禪七,但是很奇怪,我一打禪七,一坐上蒲團就會睡著!就很好睡,因為環境很安靜,所以每次打禪七,師父都用板子打我,「啪!哎呀,幹麼吵我?我睡得正甜。」睡得很好,也在禪裡。我說硬撐、抹油什麼的把自己撐起來,說我絕對不睡覺,睡覺有什麼關係?坐著閉眼讓你睡覺很舒服,不睡覺也舒服,反正我比較沒有那種框架,所以我說如果跟著我的書去瞭解佛教,佛教是一種樂教——快樂的宗教。如果說讀了林清玄的書,學佛以後變得很苦,那就不是我的徒弟!
胡軍軍:您的文字充滿了悲天憫人的情懷,字裡行間透露出人世間的各種溫度,不過最終喜怒哀樂似乎都化為一縷青煙飄散而去。寫作對您來講一直是一個愉悅的事情嗎?還是說中間也有寫不出來的那些苦惱?
林清玄:一直是一個很開心的事。就好像武俠小說裡面的俠客一樣,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練劍。練劍不一定有敵人,但是要有套路。就是說你要練,為什麼要一直練?因為保持在身心的巔峰狀態。寫作也是一樣。我不斷的寫,就是要保持我的身心在那種巔峰的狀態,所以我寫的東西不一定會發表,但是我一定每天都會寫,變成一種習慣。我覺得其實跟其他的工作一樣,就好像奧運的跳水選手,一天跳八個小時,幹嗎跳那麼多次?是因為他要保持在那個巔峰。高爾夫球選手整天都是打高爾夫球,一般人看起來是很無趣的,可是對他自己是很有趣的。對登山的人,他登得越高越有樂趣,對寫作也是一樣,你達到心、手、口、思想都在一個巔峰的線上,那你可以很開心。寫作對我來講一點都不困難,大家都問我總共寫了多少本書?我總共寫了三百本書。我是怎麼做到的?其實就是每天一直做一直做,它就慢慢變成那麼多。
胡軍軍:生命有許多的苦難,生死輪迴之苦應是其中最大的苦難,您覺得佛法是如何在啟示眾生,看透生死的迷障?
林清玄:我們會害怕生死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未來還有世界,未來還有人生。佛法難聞今已聞,人生難得今已得。人的身體很難得到,現在已經得到,要好好用來修行。如果你知道生跟死之間,就好像你移民去國外,雖然這裡的人看不到你了,可是他們知道你很安好,因為你在國外。如果你相信佛法,就是說你在這裡大家處得很好,有一天你不在,我們不會悲傷,因為知道你去極樂世界,或者你去了琉璃淨土,你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居住。
如果有這樣的高度,其實生跟死沒什麼兩樣,在我看起來就是這樣子,就好像移民或者搬到別的城市去居住,總有相逢之日,這樣一想就會開懷。像今年兩個月前我的哥哥過世,我特別回去奔喪,心裡很難過。可是到了這個年紀,接下來就是可能每一年都要碰到這樣的場面,會有人離開你,然後你的角度就要改變一下。我就想到我哥哥的好,我說我這個哥哥真的很可愛。他住在鄉下,他是我們家唯一的一個農夫。我們十八個兄弟姊妹都沒有人做農夫,只有他做農夫。
胡軍軍:我聽說過您有這麼多兄弟姊妹,您的父親收養了他弟兄的孩子。
林清玄:我排行第十二。每次回到鄉下,我哥哥知道我回去了,他不會特別來打擾我,也不會來看我,因為他知道我可能要工作。只要聽到我回去,他就會去割香蕉,把自己採的一串香蕉,掛在我家門口。我一開大門,就知道三哥今天來過,有一串香蕉掛在門口,要不然就掛兩個鳳梨。他就是這麼可愛的人。但是突然聽說他過世,就會想到他的那種體貼那種好,還有我們家的哥哥姊姊都很幽默,也想到他的幽默。想到他有一天在山上,八十幾歲身體還很好去爬山,爬到一半想上廁所,但是廁所太遠了,他就在草叢蹲下來上廁所,一蹲下來是斜坡,從山頂滾到山下,類似這種超爆笑的事情,我回憶起來,留下很多美好的記憶,大概就把他看成他移民了吧,所以這一點我倒是還滿看得開。
胡軍軍:我自己在學佛的最初幾年,深深感覺到信仰對生命的重要性,甚至我都擔心身邊的朋友,如果沒有信仰,要如何面對無常,如何度過餘生。您如何看待信仰對生命的重要性?一個沒有信仰的生命可能幸福嗎?
林清玄:剛開始學佛的時候,從山上下來時,我是一個滿狂熱的佛教徒。我們家附近有個醫院,我想這些人都沒有聽到佛的教化,不知道念佛可以往生,那太可憐了,應該有一個人來告訴他們。我就跑去醫院做義工,然後碰到快死的人,我就說你要從現在開始念佛,只要後面幾天很專心地念佛,你就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結果很多人聽了很生氣,我都快死了,你還講這些?我有點想不通,這個佛法這麼好,為什麼他們都不聽?後來我懂了,其實一切要講因緣。
以前釋迦摩尼佛就說,該度的我都已經度了,還沒度的我也留下度化的因緣。後來我自己想開了,其實就是因緣決定的。如果你在這一輩子沒有遇到,是因緣還沒有成熟,遇到了,你應該感到歡喜,原來這麼多人裡面可以遇到佛法的並不多。比如說中國大陸有十四億人,如果聽到有人講佛法,那是太了不起了,因為實在機會太少太少。
如果我沒有學佛,可能現在會很悲哀。悲哀就是很世俗,然後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麼。像我以前,大家都認為我很成功,賺很多錢,四十年前我一年的版稅就有一億臺幣,那時候買了很多房子。日本有個設計師叫三宅一生,我就說我早就勝過他,我六宅一生。我有六個房子,他才三宅一生(哈哈哈)。後來學佛了,智慧開了以後,我就做林清玄基金會,建學校,蓋圖書館,所以現在只剩下一宅一生,現在只剩下一個房子。我太太常常警告我,只剩下這一個了,不要再賣掉。我的人生已經完成我講的翻轉,翻轉了就知道什麼是重要,而你現在就走在重要的路上,這多好,多開心。萬一你這輩子都沒有聽到佛法,就這樣死掉了,太可惜了。
胡軍軍:您有許多在各地的演講計畫,並且前不久還旅居大陸各地,每個地方住上幾天,以參訪古蹟為樂。您是在尋找寫作靈感嗎?這樣的生活方式一定其樂無窮吧?
林清玄:其實也不是尋找寫作靈感,就是用佛教的說法叫「人間遊行」,人間各地去遊行。在遊行的過程裡面,隨緣度眾生,就是隨著因緣。最近因緣比較好,有很多機會去千年的古寺,千年的古寺通常會有很好的建築,很美,然後裡面會有幾個修行很好的師父,就到處參訪。然後會碰到一些有緣的人,跟很多人結緣。以前在臺灣,我就經常到處跑,我光是離開臺灣就三百多次。應該很少人跑這麼多,大概星雲大師以前跑得比我厲害,他全世界蓋了四、五百座寺廟,所以我習慣經常在全世界跑,我的人生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在遊行,在中國大陸也是一樣。我在大陸走過三百多個城市,每一次會跟幾千人、幾萬人結緣,埋下一顆種子。這種子不一定馬上就會發芽,但是有一天會發芽。
胡軍軍:您自認為是名精進的佛弟子嗎?
林清玄:我沒有那麼精進,我很怕碰到很精進的。沒有,我可以說我是一個浪漫的佛弟子。我比較不喜歡太精進。
胡軍軍:怎麼個浪漫法?
林清玄:最好一直睡到自然醒,就是說你的心一直保持對人間的那種熱情。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小乘的佛法,因為那種教義會不斷地把你捆綁,綁到你完全不知道你是誰的那種,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小乘佛法。
跟小乘佛法我發生過很多笑話。有一次我接到泰國皇室的邀請,去泰國演講,算是很大的事情,很隆重,皇帝請你去演講。因為他們辦了一個大會,我整裝待發跑到泰國去。一下飛機,看到好多人拿紅布條歡迎我,歡迎林清玄大師蒞臨泰國,蒞臨曼谷。然後我就走過去說:「你們在等林清玄?」「是。」全部都是僧團,都剃光頭。然後我就說:「我是林清玄。」當場好幾個昏倒,因為在泰國,居士是不能說法的!看我穿著西裝跑來泰國說法,結果把我跟皇帝的約會也取消了(哈哈哈),後來不但沒有講,跟皇帝吃飯,還有跟泰國僧王的約會也取消了,統統取消了。結果我就在泰國走來走去走了七天,然後回來了。
胡軍軍:過去幾十年臺灣的佛教道場建設和義工文化開展地非常成熟,成了大陸佛教的楷模,非常令人讚歎。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寺院,您認為大陸佛教應該在哪些方面借鑑臺灣的經驗?
林清玄:臺灣佛教之所以那麼好,是因為裡面的出家人好,並不是寺廟好。跟大陸的寺廟比起來,臺灣都是小孩子,臺灣的寺廟都很年輕,不算什麼。可是因為臺灣有很多修行很好的師父,所以他們就形成一種吸引力;你如果修行的好,自然會吸引那種程度很好的年輕人進入佛教。所以臺灣的佛教之所以值得借鑑,就是因為有很多才俊,有很多修行很好的師父。
大陸也是一樣,大陸如果佛教要復興,要往更好的方向,一定要人才,光是寺廟是不行的。所以我在大陸也經常跟他們這樣講,因為我也經常到大陸的寺廟演講。去年我還去法門寺、少林寺演講,都是一場大概有五、六千人。大家對佛教還是很認可,可是誰講給他們聽?沒有人,或者說講得不好。其實我在大陸講佛教,聽得最開心的是出家人,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講法。我到趙州禪師的柏林禪寺,在河北,講茶禪一味。出家人特別瘋狂,覺得好像聽到一個完全新的東西一樣。所以大陸需要培養很多佛教的人才。
胡軍軍:現代社會憂鬱症氾濫,嚴重影響個人和家庭的健康幸福,有些甚至走上自殺的不歸路。您會如何開導這些患者?
林清玄:我覺得在現在社會每個人都有憂鬱症,只是程度不一樣,有的還沒有,像我有時候也很憂鬱,可是我不會自殺。因為我說人生就像一條多惱河,德國有一個河是多瑙河,很多煩惱的河。很多人到了多瑙河邊是去散步,去尋找人生的浪漫。可是很多人就忍不住要跳下去,因為有一個無形的煩惱在推動他。就好像我們在黃浦江邊散步一樣,我們不會跳下去,因為我們會看到那個美。會跳下去的,是因為你看不到那個美。所以憂鬱症之所以那麼嚴重,是因為我們在成長的過程裡面,沒有看到人生的美,沒有看到追尋的美,沒有這種美來支撐你的人生,所以很快進入黑暗,因為你沒有美支撐。所以我覺得在我們的教育裡面,或者在我們的一般人的思想裡面,應該培養這種美的教育。
佛教其實是一個美的教育,菩薩都很美,然後思想都很美,就是讓你有力量在多惱河邊的時候沒有那麼惱,而是有一些歡喜。
在不如意的時候,應該回來守住自己的心,等待因緣和時機的好轉!不要讓心到處亂跑。善導大師曾說:「息心即是息災」。如果我們要改變不如意的狀態,最快速、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息心」。
胡軍軍:您剛才說您也有憂鬱的時候,您用什麼具體的方法開解自己?
林清玄:你要培養很多正向的東西,這些正向的東西,包括你的思想,你的體會,你的情感,都要訓練自己。我有一本書叫《常想一二》,就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所以要常常想那一兩件快樂的事,每天都有一兩件快樂的事,讓你有接下來要走下去的那種力氣跟勇氣。
胡軍軍:古代的文學家燦若星河,您最喜歡最欣賞哪幾位?
林清玄:中國的文學家裡面我最喜歡是蘇東坡、白居易,李白也喜歡。我喜歡的文學家不只是文學家,還應該是生活家,還應該是思想家。他自己有一套思想,然後他對生活有很好的體驗跟見解。不只是寫作,寫作是最後的一個枝節。如果只會寫作,那就沒什麼好說的,應該也會寫作也會做菜,也會交朋友,然後又有美感等等,其實是很綜合的。西方的就是泰戈爾、卡萊爾‧紀伯倫、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這些也是除了創作還是生活家,也是思想家,不只是會寫文章,會寫詩,還會畫畫,各種東西都會一點的。
我自己也是這樣。我小時候寫書法,練魏碑,大家都笑我:「人家都在寫柳公權,你在寫魏碑。」柳公權字體軟綿綿的,我不喜歡;宋徽宗的瘦金體,看起來就好像隨時要跌倒;那個魏碑多好,大大的,然後有力量。所以我說書法我自己練,練得不錯,然後也畫畫。我看到人家煮出很好的食物美食,我也學烹飪。什麼都去做一點。茶道很好,我也來學茶道,類似這樣。所以陸羽有一句話影響我一輩子,他說:「恥一物不盡其妙!」如果有一件事情我沒有做到最高境界,我就覺得很可恥、很羞愧。雖然每一樣都要做到最好,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那個過程讓你一步一步往前進。我以前聽到人家說:「富有三代才懂得穿衣吃飯。」我說:「很多富有三代不見得懂很多。」反過來想,可不可能這輩子就懂得穿衣吃飯?我要往這個方向努力,把樣樣都做得很好,你想死就沒有那麼容易(哈哈哈)。
胡軍軍:我剛才在聽的過程中看到您女兒一旁用非常崇拜的眼光看著您,聽得非常認真。她是不是一位佛教徒?她會全盤接受您講的這些佛理嗎?
林清玄:她是佛教徒,但不見得聽我的。我帶她去皈依星雲大師,回來以後跟我講什麼話?「爸爸,你以後不要罵我。」我說:「幹麼?」「我是你的師妹。」(哈哈哈)。我記得在她青春時期,我給她寫過一段話:「在十六歲時,你要抓住生活的點。二十歲時,你要畫出思想的線。三十歲時,你要鋪設生活的面。之後,你要創造影響世界全體的面。」我常常告訴她:創作就是生活的呼吸,常常調息,養成自己的節奏,就永遠不會忘記了。她有天賦的才華,有飽滿的愛,這是她最大的資產。
平常在生活裡面我經常跟我女兒聊天,她很有才華,想法很成熟。她自己從小就會煮咖啡、泡茶,廚藝也很好,很會煮菜,從美國回來之前還在宿舍裡面辦一個party,親自做一桌菜請大家吃,把美國人都嚇壞了,這小女孩這麼厲害。應該是各個方面都滿有發展的。我兒子也是一樣,也懂得吃,懂得美好的事物。所以他們在外面我們比較不擔心,因為從小那些好的品質,爸爸媽媽都已經把它養成了。我們和孩子的相處比較像朋友。
胡軍軍:對於我這樣一位以涅槃為題材的藝術家,您有什麼建議嗎?
林清玄:我覺得不要著相。比如說,你有一些畫,畫樹枝和涅槃在一起的,枯枝是涅槃,也是止息的一種狀態。但是我看了以後的疑問就是,為什麼沒有一朵花,沒有一片葉子?如果在這麼枯寂的狀態下,你畫一朵花,寫兩句話:惟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枝頭上還有一朵花,但是我知道明天它就被風吹走,哇,那個就很涅槃!
胡軍軍:現在的新作品裡面有花有鳥,葉子,古琴都有了,把涅槃溶入中國的山水裡面。
林清玄:我覺得涅槃不只是人的一個姿勢,而是萬物推展的過程裡面的一個章節。比如說冬天,冬春之交那是涅槃,涅槃是為了更活潑的未來,更有力量的未來。佛之涅槃,就是要讓你們知道這是人間的教化,所以你們不要害怕,人間的教化就是這樣。生命一定有終極之處,但是佛的教化是沒有止息的;人間有止息,可是佛的思想或者傳承是沒有止息的。如果可以突破那種形,讓別人在看你的畫的時候得到內在的止息,不只是因為這個畫畫得好靜;而是你在靜裡面,還讓別人能感受到那種安頓。涅槃應該就是一種身心安頓煩惱之事。那種安頓,可以更多地表達出來,可能就更好了。
胡軍軍:您曾經經歷一次婚變,當年引起很大的反應,大概也改變了您的人生軌跡,您覺得是別人誤解了您嗎?有什麼話想要說嗎?
林清玄:這很正常,因為你的心不美好,對什麼都有誤解;你的心美好,對什麼都沒有誤解。其實我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就是我只是聽從我的心,聽從我的內在的那種追尋。我以前在大陸作過一個演講,叫做「不怕人生的轉彎」,我說我八歲立志要當作家,大家都說不可能,農家小孩祖先都不認字,你怎麼可能變成一個作家?我十四歲離開家鄉,我說我要為自己踏出一條路,大家都說不可能。我後來學佛,三十歲去閉關,成了當年報紙上的頭條新聞,但是我不說什麼,只是覺得時候到了,我應該要轉彎。
我再婚也是如此,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我的朋友曾對我說:「清玄,你和淳珍的愛情,以後一定會成為美談,那些誹謗你的人,不會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我想起有人問佛陀:「如果你舉得出證據,我就不再擾亂你。」佛陀溫和地舉起右手,指向前方,接觸大地,大音希聲,大象無言,他沉默地接觸大地,是說:「大地就是我的證據,無數的輪迴裡,我所行的一切都在大地留下了證據!」
佛陀修行的證據在大地,我留下的證據就是我的文章。我不斷不斷耕田,信心是我的種子,智慧是我的耕犁,我一直前進不退轉,希望能種出一片無憂的所在。我可以無憾地說:我所走過的路,我的文章都已留下美麗的證據!
二○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臺灣臺北天母
此篇訪談於二○一九年一月十二日在臺北進行,沒想到九天後就傳來林清玄先生過世的消息,未曾想這竟是一場生死的告別。從文中的答案來看,清玄先生並不貪戀淨土世界的安逸,而是還要再來傳播至善至美的人間萬法的。他捨不得錯過這世界的任何一個美,我祈願,他的離去,也如同涅槃一般,清涼寂靜,大美無言。
目次
序言 指月涅槃——林谷芳
自序 涅槃生死等空花
涅槃風光,不生不死——首愚法師訪談
閑裡偷忙話生死——繼程法師訪談
生死無憾,涅槃自在——釋寬謙法師訪談
安息的尊貴——李光弘長老訪談
如此而已,毫無恐懼——鄭振煌訪談
萬般自然,面對生死——陳嘉映訪談
如果今天是你此生的最後一天——詠給‧明就仁波切訪談
繁華落盡見涅槃——林清玄訪談
弱水三千,只取涅槃——胡軍軍訪談
涅槃從不是高高在上——成慶訪談
涅槃之美,不可思議——濟群法師/文
涅槃:唯一結果與無限可能——柴中建/文
附錄
佛教的涅槃觀 ——印順導師/文
涅槃——星雲大師/文
書摘/試閱
〈序言〉
指月涅槃──林谷芳
佛家說「行住坐臥」是身心具現於外的「四威儀」,而其中,行,動而易散;住,立而易疲;臥,躺而易昏。故以坐為上,佛造像主要亦以坐像而立。
坐像之外,亦有立像。坐,是入於一切圓滿,無須外求的「自受用」境界;立,是因於慈悲度世,接於眾生,為佛德之外顯,是能讓六道「他受用」的映現。
而在坐、立之外,也有臥像。
臥像,俗稱臥佛,一般觀念是「躺著的佛」,但事實上,祂不是躺著的佛,不是睡時的佛,祂是「涅槃的佛」。
涅槃,是指佛在這娑婆世界,「所作已辦」,因緣已盡,所以不再受世間諸有,示現的「寂滅」之相。
這寂滅之相,寧靜安詳,原來,世壽已盡,永離塵世也可如此圓滿!就這樣,佛的涅槃像乃為尚浮沉於生死大海的眾生示現了生命最終的可能。
說最終,其實也最根柢。人出生即有不同的聰慧愚劣,條件即有富貧高下,境遇亦有順逆顯隱,但這種種「世間法」的優劣高低,在面對生命的消逝——死亡前,卻就顯得如此地虛浮不實。
死,是必然的結束,且這結束並無法預測,於是芸芸眾生,固孜孜矻矻地構建自己生命的王國,卻又不得不隨時面對這王國主體的消逝,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這是生命根柢的課題——儘管這課題難解,尋常人常只能先將它置於一旁。
但難解、且置,並不代表問題不根柢,更不代表真能如此略過。畢竟,尋常人面臨死生,世緣盡斷,真能不惶恐者幾希!而更有些生命,認為如不在此作根柢觀照,則世間的一切也就如浮沙之塔,了無實義。
這樣的人是哲學家,是宗教行者。
哲學是本質之學,生死的本質何在?它對人生的意義為何?哲學家在此作終極的思索與觀照,提出種種具本質意義的落點與論述,從而讓芸芸眾生在此得到一些憑依,不致只能或渾渾噩噩,或避而不談,或虛無享樂地度其一生。
但哲學的作用儘管如此,哲學家建構的卻仍不離其論理的本質;也就是說,它可以就是,而且也往往就是一種概念論理的完整,而這論理能否真作用於生命,又如何實際作用於生命,則不是我們所能要求於哲學家,哲學家也毋須如此要求自己者。
但同樣在死生作觀照,宗教行者則大大不同於哲學家。
行者,是以生命體踐為本的,一切的義理若不能化歸為生命的踐行就無根柢的意義。談死生,因此不只須窮究死生之本質,還得真正超越於死生。而這超越,並不只具現於實修法門的成立,更須一定程度地直接映現在行者自身。
正如此,宗教的創教者都在死生之際映現了自己一定的證道風光。
證道與死生映現,不僅是一般的相關。原來,看事物,觀萬法,世間的邏輯是「未知生,焉知死」,宗教的邏輯卻是「未知死,焉知生」。正因有死生的天塹,正因欲在此天塹上跨越,所以有宗教。談來生、談彼岸、談輪迴、談天國,是這跨越天塹的義理設定,也是這跨越天塹的實證領悟。在不同的義理與實證下,宗教有著它共同「跨越死生」的原點。正如此,創教者焉能不在此留下實證以昭來茲!
而這樣的死生映現,也必然有它不尋常的風光。
這風光,有以自己血肉之軀換得眾生之救贖者,有以神通異能展現死生之不成障礙者,總之,就因死生的超越太本質、太困難,這樣的風光總須呈現出它非尋常之處,讓後來者既欣羡,卻又不敢多所奢望。
欣羡,是因這樣的解脫之境正是葛藤盡脫的境界;不敢奢望,是因太難,只有聖者乃能如此,我們凡夫也只能就跟隨著聖者的腳步前進。
但釋尊不然,涅槃不然。
釋尊不然,是因為他不似其他宗教的聖者——尤其是創教者般,直接從彼岸而來,他教的創教者或為神子,或有神蹟,總有其彼岸之姿。但釋尊不然,儘管後世多了他許多的本生故事,大乘佛教尤其將「佛」之一字推至極致,甚乃出現「一佛一世界」的國土觀,但歷史的釋迦,從頭至尾,就是以一個尋常生命出現的,這尋常生命與我等凡夫若有不同,只因他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覺者,仍在這娑婆世界行住坐臥,只是呈現了無惱無苦的生命狀態。而這狀態,在面臨死生時又是如何?沒有這根柢的示現,無惱無苦也就缺乏究竟的勘驗。
而這究竟的勘驗,正是佛陀的涅槃。
涅槃是「不受後有」,不造業,也就不在生死大海裡浮沉,「三法印」中用了「涅槃寂靜」說此。寂靜,是不生,但這不生,又非斷滅,因有斷滅,就有恆常,還就是二元分割,還就是有無取捨。
涅槃離此兩端,究竟寂滅,在此連彼岸都已不存,臥佛之所示正是如此。而即便大乘佛教舉無量世界無量諸佛,但真正示現涅槃的,也僅只釋迦這歷史的覺者一佛。從這唯一,從死生的天塹,從宗教「了生死」的本質,涅槃像乃就有它不共的意義,涅槃更就是佛教這覺者的宗教的核心,而學佛,談覺悟,也就繞不開對涅槃的觀照。
所以說,佛,是與我們一般的生命,但所證卻又完全非一般生命所能測度;涅槃,是具現於此岸的解脫,卻又絕非此岸的心識所能度量。
這是佛教,這覺者的宗教最最與他教不同者。
這現前所示是離於相對的無限,看似平常無神蹟的涅槃卻是「諸聖罔及」的超越,連超越都不見的解脫。
但雖諸聖罔及,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可眼前的涅槃相卻又如此真實,對眾生也就形成了最大的吸引:原來離於諸苦的狀態可以如實親證,「彼岸」,再也不只是渺不可及的遠方,也不是想像馳騁的另一個世界。
原來,覺者覺悟的當下就已親證彼岸,但平時身處一如之境的覺者在語默動靜上雖時時示現,卻就不如在這終極天塹上給予眾生的觸動大。「千古艱難唯一死」,歷來的仁人志士在此「超越」的固不乏見,但他們都以「更高」的價值凌越死生,再如何,依然在「對待」的世界中轉,何曾有這「不受後有」的寂靜!而這寂靜卻正是身處火宅的生命最大的嚮往。
正如此,一部涅槃經歷史中,也就成立了一個涅槃宗,面對涅槃的提問,也就從早先的「不受後有」、截斷眾流的回答,轉而成為對此終極之境的描摹。
這描摹,從「苦、空、無、常」的現世舉「常、樂、我、淨」,從「不受後有」的寂滅轉成永遠救贖的慈悲,從個人死生的超越轉為諸佛國土的幻化。這種種,從佛理而言,固是內在理路發展的必然,但若無世尊現世的示現,無涅槃直接的體證,都將缺乏一種如實的信念與基礎。
以此,觀照涅槃乃成為學佛的一種必然,但問題是,涅槃卻又不好觀照。
涅槃是解脫,這解脫是佛教的「彼岸」,但它與諸教的彼岸又有根本的不同。
諸教的「彼岸」,是相對於「此岸」而有,此岸之不足者,在彼岸乃得滿足。所以此岸有苦,彼岸就樂;此岸有死亡,彼岸就永生;此岸有匱乏,彼岸就富饒;此岸有爭鬥,彼岸就和平;此岸有陰暗,彼岸就光明。
這樣的彼岸好想像,由之而起欣羡之心,但涅槃呢?
有相對,就有取捨,有取有愛,就有老死,而涅槃正是究竟寂滅,無有對待,這「無」,正如後世禪家所言:不能作「虛無」會,不能作「有無」會,但如此,活在有無的眾生又如何以有無之心去了知超越有無的涅槃呢?
在「有」的世界談「不受後有」,在言語的世界談「言語道斷」,其本質的侷限與內在的弔詭是必然的,面對此悖論,舉「不二」的《維摩詰經》乃如此說道:「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
而舉不立文字,以免「死於句下」的宗門,更直接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示此言語道斷之境。
談涅槃,於第一義,真「開口便錯」!
但能不談嗎?
釋尊說法四十九年,究竟的覺者當然知道究竟是離於言說的;不立文字的禪宗甚且留下了較諸宗更多的禪籍燈錄;「老子若無為,何留五千言」!無為,是為而不恃,生而不有;禪的「不死句下」,是不為言語所困;所以釋尊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得一句,宗門更直說「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語言文字是指月之指,是載人之舟,學人因指、因舟而得親近彼岸,但不可執指為月,不可以舟為岸,能如此,就得文字般若。
攝受文字的要能不執,講述文字的更得如此。知道自己所言所指,即便再如何圓滿精邃,畢竟非那「照天照地第一月」,更也知種種一切,原都妄心所造,只在此以更多不同向度之參照,示之眾生,一般人在此固可能只如盲人摸象,僅得一端,但有緣者若能會而觀之,亦有更多全相描摹之可能。
誠然,修行之證入,原可直取「向上一路」,原可直搗黃龍,但義學之鋪衍,證量之觀照,亦可使學人不致盲修瞎練,對初機者尤好應緣。而就此,軍軍之有這本訪談錄也就極其必要與自然。
必要與自然,在軍軍,作為一「弱水三千,只取涅槃」這般只畫涅槃的行者,儘管對涅槃之像可以直面全體地領略,由是乃以畫涅槃為終生職志,但「信為能入,智為能度」,在直觀的情性相應外,要將涅槃像更深地現於世人之前,也就只能更廣垠、更深入地在此觀照反芻,於是,從宗長、法師、居士、哲人、學者諸方汲取更多對涅槃的觀照,乃必要而自然。
必要與自然,對佛子,乃至廣大的修行人亦然。涅槃,這現世中直現的圓滿究竟,畢竟是最核心、最貼切的一場覺者示現,前輩與其他行者如何觀照於此,固必深深觸動學人,而由此種種觀照,學人亦就更能勘驗自己在辦道路上的虛實。
觀照反芻、觸動勘驗,正須從各種向度琢磨。於是,訪談者何只有不同身分、不同宗派之行者學人,立言之處,其基點更就從義學到實證,從感性的直領到哲思的辯證。由是,所指雖是第二月,但此第二月,恰如千江之水的千江月,何只能讓你知月的實然存在,在機緣成熟下,你一轉身,一回眸,一抬頭,一望眼,也就得親證親見那「第一月」。
身為禪家,軍軍曾以涅槃提問,我以禪舉不二,所以「說身無常」,卻「不說樂於涅槃」,「說身是苦」卻「不說厭離於身」,因說樂於、厭離,就又落入「二元的顛倒」。所以禪家說涅槃,也就只在無常之中「直顯」涅槃的境界,而非在無常之外,另立一個涅槃,就如此,宗門向來少有涅槃這樣的主題觀照,尤其不在此作義理式的鋪衍。
但如此說,並不代表禪就離涅槃最遠,恰恰相反,於現世中直示超越,正是禪最與涅槃相近之處。世尊的涅槃固以「舍壽」而示「不受後有」,但究竟證道,其實也就無處不是涅槃,只是死生的示現是現世最後一次,也是常人最罣礙之處的示現,這「無餘涅槃」乃有它不可替代的意義。
說死生示現,禪家的風光最接近佛陀的涅槃,在此或大美,或氣概,或遊戲,或平常,不似他教之神異,只以此岸之姿,直啟尋常生命之疑情:原來,可以如此直就解脫!
在此,說氣概,是無學祖元在元軍刀劍臨頸時吟出的:
乾坤無地卓孤笻,喜得人空法亦空。
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裡斬春風。
說遊戲,是妙普性空庵主自做木盆,放流而逝的:
坐脫立亡,不若水葬;
一省柴燒,二省開壙。
撒手便行,不妨快暢;
誰是知音,船子和尚。
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
這是禪家「有無具遣、佛魔同掃」的風光,但禪還有「現前直領、全然即是」的一面。
在此,直領詩意的是天童宏智:
夢幻空華,六十七年;
白鳥淹沒,秋水連天。
平常無事的是比丘尼法海:
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
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
對道人,「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這詩意,這平常,更似佛之涅槃,深體之,觸動猶深。而這觸動,更就以佛之涅槃像世世代代垂諸學人。
談這觸動,近現代亦有如此示現者:弘一的圓寂,吉祥而臥。我自己就曾遇見多位未曾有道心、善於思辨存疑的知識分子,因看到「人,竟可如此!」而幡然轉身。
就如此,釋尊的涅槃雖遠,好在有涅槃像的傳世;歷史的涅槃像雖遠,好在當世還有持續造涅槃像者,持續觀照涅槃實義者。
正因這畫涅槃像,正因這集涅槃觀,禪家之我亦應緣聊充指月之一指耳!
是為之序!
二○一九年一月 臺北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