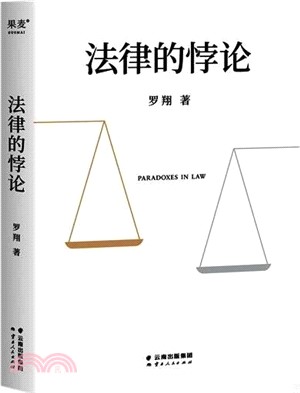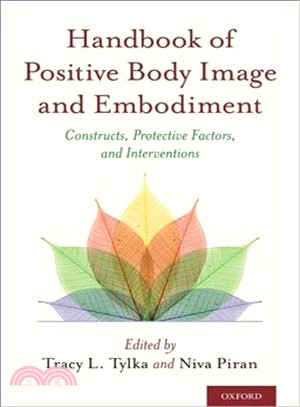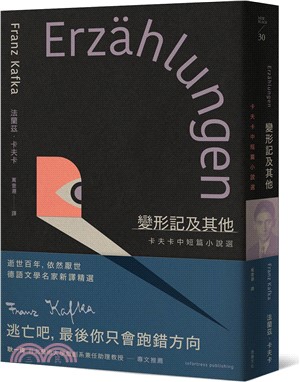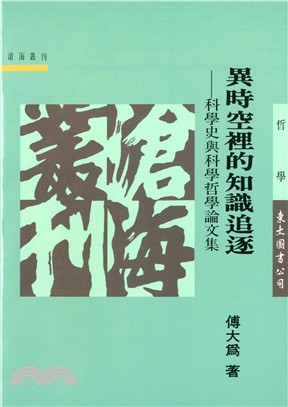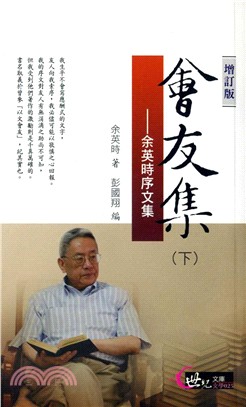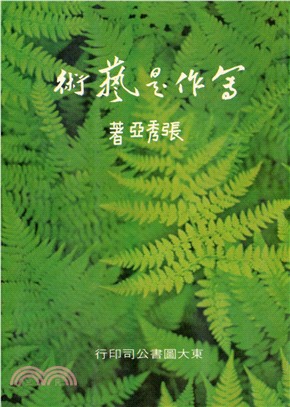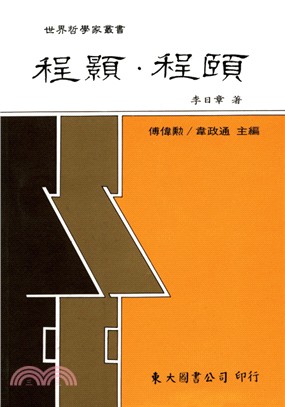商品簡介
序
目次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回歸以來,香港的政治體制到底屬於「行政主導」還是「三權分立」,各方一直存在爭議。特區政府在推行法案及重要政策時,往往未能在立法會取得足夠的支持,不少法案及政策因此而擱置或拖延。政府施政舉步維艱,行政與立法割裂的困局愈趨嚴重。如果局面持續或惡化,將會嚴重阻礙香港的發展。面對上述的局面,我們必須找到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從制度、架構等方面改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本書嘗試比較全球幾種重要的政體,即民主代議制、總統制等之下的行政與立法關係,分析其特點及優劣,作為思考香港情況的基礎。接着從歷史的角度審視港英殖民時期的制度發展、《基本法》的設計原意,以及回歸後政府管治團隊的變化,梳理出行政權與立法權的變遷與發展,從而探討形成現今局面的原因。作者再從立法會的重要職權,包括提案、向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動議辯論等方面,以及立法會內部政黨的政治,闡釋行政與立法雙方的拉鋸情況。本書期望通過以上多方面的討論,引起大眾反思立法會諮詢架構、選舉制度、「無黨派政府」等問題,從而找到一個平衡點,發掘出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的方法,提升香港的管治質素。
序
前言
《基本法》確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以行政為主導,並且行政與立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約。此種政治體制,一般認為是在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上,行政應當處於優先和主導的地位。在一系列的政制發展討論中,中央及特區官員多次強調行政主導的重要性,並將它提升至《基本法》甚至是國家主權的層次來討論。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清楚地指出:「行政主導是特區政體設計的一項重要原則,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重要表徵。任何方案必須鞏固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體制,不能偏離這項設計原則。」《基本法》作如此設計,有其歷史因素和現實政治考慮,中央在1980年代思考香港的管治體制時,認為其以港督為核心的行政主導、立法局和行政局為港督諮詢機構的「行政吸納政治」的體制具有高效、穩定且易於控制的優點。同時,基於香港政制的地方性及延續香港政制與繁榮穩定的實際需要,中央認為行政主導是最易於滿足前述需求的政制形式。
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基本法》設計的行政主導原則並沒有貫徹落實,立法會對政府施政呈現出「配合不足,制約有餘」的特點。儘管《基本法》第74條和分組點票機制等對立法會制衡政府的權力施加了諸多限制,但立法會仍能通過一些制度化甚至非制度化的方式來擴權,例如立法會加緊對政府財政的控制、通過不斷提出修正案的方式來增加政府法案通過的難度(極端表現為「拉布」)、通過不具有約束力的動議辯論和「不信任案」向政府施壓等。同時由於立法會與政府之間缺乏政黨或委員會作為紐帶,政府官員因此無法像西方民主政體般,透過政黨在議會內建立穩定的支持,結果造成行政與立法持續割裂的管治困局。
為什麼一個適應香港需求的行政主導體制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行政長官在憲制文本《基本法》上具有優越地位,但回歸21年來,香港政治卻呈現一副「特首弱勢」的現象,行政主導面臨着名不副實的體制性尷尬。過往的研究往往局限於檢討香港管治的內部體系,比如「特首不黨」原則導致特首無法依賴執政黨及政黨管治聯盟;比如香港公務員沿襲港英舊制,抵制特首及委任官員的支配和調度;比如立法會缺乏「忠誠反對派」,激進泛民主派「逢中央必反」、「逢特首必反」;比如特首由非普選產生,即使是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仍被質疑「認受性不夠」等。其實有多項制度的安排是對行政主導的制度有利,如:立法會採取比例代表制的選舉辦法,再輔以功能組別議席,使得立法會內幾乎不可能出現某個單一政黨控制議會多數議席的情況;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規定特首不得有任何政黨背景,此舉從根本上保證特首不被任何政黨利益「綁架」,因為哪怕是根正苗紅的政團,亦會受本港民情的牽引,不會事事與中央保持一致;如《基本法》的選舉安排讓特首和立法會各自由互不相關的選舉系統產生,進一步降低了特首對政黨的依賴。問題是,儘管有前述鞏固行政主導的制度安排,為何歷任特首還是處處碰壁,施政困難?
為化解香港行政與立法的僵局,2007年12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允許香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增強行政長官的民意認受性,其後實現立法會全體議員的普選,又稱「雙普選」。香港的行政主導沿襲自港英時代的港督制。港督制下的港督合法性來源單一,是基於英國的單方授權。回歸後的行政長官合法性則是複合的,是基於地方選舉與中央任命,此時基於地方性政制的行政主導制仍具有一定的憲制合理性。但普選是否為解決行政立法關係難題的必然選擇?在普選實現之前,《基本法》的政制設計為香港政治的發展變化預留下極為廣闊的空間,行政主導的現狀與民主普選的目標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現有的條件下要如何化解,值得深思。
現存對香港政制的研究大多是將立法會視為行政主導體制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再分析其與行政權力(港府、特首乃至行政會議)的關係,並從在「雙普選」的藍圖下能保證行政主導體制有效性的角度出發,就其存在的問題提出制度或者執行上的建議。大多數研究以法理為經,案例為緯,分析行政和立法關係的應然和實然狀態,認為立法會自九七回歸後所為的制度和行為擴權已是不爭事實。這個過程還未結束,但必須受到《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約束。內地學者普遍認為《基本法》體現了「行政主導模式」的憲政設計,而隨着《基本法》實施進程的推進和香港社會多年來政經力量對比的變化,立法會擴權的趨勢漸漸明顯,香港立法會出現了「對抗吸納制衡」的制度難題。[1]也有學者從政治發展的角度出發,為行政―立法關係的未來走向提供建議,如分析功能界別的發展歷程、特殊功能和政治前景,或者是政府如何利用行政會議和高官任命來調整與立法會的關係等。
另有研究是針對立法會從選舉到立法再到監督過程當中不同行為主體的關係問題,代表性的研究多關注立法會中的政黨政治,即將立法會視為香港政黨政治的主要成長場所,分析立法會中的政黨博弈、不同政黨的實際表現,並對立法會的政治運作前景作出分析、研判。[2]在這一領域中,內地學者和香港學者的研究思路有明顯不同,前者注重梳理和特徵辨別,[3]而後者則注重基於一手資料的選舉策略、議題製造、媒體報道等問題,[4]學界在香港政黨的現狀上有較多共識,認為香港的政黨政治是一種非典型政黨政治,其發展受到「中國因素」(China factor)、行政主導體制、比例代表制選舉、議會內部功能界別和分組點票制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5]儘管存在着多種局限,但是其出現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具有諸多積極作用。[6]在未來,政黨政治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必然選擇,在此期間,如何協調政黨與其他權力主體的關係十分重要,有很多學者都贊同最終取消行政長官的非政黨屬性,並以執政黨或者政黨聯盟形式建立「內閣制」。即使不能實現,至少也需要建立一個以「政黨為基礎的政府」(party-based government),否則可能產生難以調和的衝突。[7]
關於1997年回歸前的立法局,香港的立法機關與西方民主國家相比,一般被認為擁有較小權力,有學者按照其對政策的影響將立法機關分為三種:[8]第一種為政策制訂型立法機關(又稱「積極型立法機關」),不但能改變、撤銷行政機關的措施,還能形成甚至用自己所立的法來取而代之。美國國會為其典型例子;第二種為政策影響型立法機關(又稱「回應型立法機關」),可以修正或者拒絕行政機關的政策,但不能形成或用自己的立法取代。德國和英國議會為典型例子;第三種為僅具備較小的政策影響力或不具備政策影響力的立法機關(又稱「邊緣型立法機關」或「橡皮圖章」),多表現為不能修正或拒絕行政機關的偏好,以前社會主義國家為典型例子。[9]世界範圍內大多數立法機關都表現為第二種或第三種形態,有學者將回歸前的香港立法機關歸為政策影響型,議員可以聯合通過動議辯論、行使提案權、拒絕或者威脅不通過政府的財政開支要求等。[10]回歸後,立法會的提案權受到《基本法》第74條和附件二分組點票規則的進一步限制。
Norman Miners教授在《香港政府與政治》一書中着重分析了1985年後香港立法機關的演進和制度化,指出立法機關承擔的三項主要活動為:立法、財政控制和監督政府。[11]這一傳統分類也與《基本法》授予立法會的權能一致;在另一篇文獻中,Miners教授分析了1970至1994年間香港立法機關功能的轉變,尤其是關注殖民地時期立法局議員,特別是非官守議員如何影響政策制訂,通過私人提案、委員會工作等方式制衡行政部門。[12]研究香港立法機關職能的學者Cheek-Milby,在1995年的專著中將香港立法機關的職能分為代議、政策制訂(立法)、體制維繫三項職能。雖然這並未完全囊括立法會前世今生的所有功能,也沒有按這些功能的重要程度排序,但Cheek-Milby的研究對立法會的歷史演進作了整全的描述,並對立法會的法案、修正案、質詢、動議進行量化分析,還關注了不同時期議員所扮演的角色。[13]其得出以1984年為分野:1984年以前的立法局在議會研究學者Mezey教授的分類下為「最小型立法機關」,1984年以後的立法機關為「邊緣型立法機關」,其得到的公共支持和參與形塑公共政策的能力不斷增強。[14]
除了Mezey教授的類型學外,Norton和Curtis教授的分類也獲學界所採納。Curtis根據強弱程度將立法機關分為四類:服從型(唯命是從)議會、贊成型議會(英國)、對等型議會和對抗型議會。[15]「對等型」議會這個概念後在蔡子強、劉細良的研究中,這一用語又被「議政型」(adversial)議會所取代。他們的研究綜合了Norton和Curtis的分類,構造出新的由弱到強的議會類型:政策宣告型、政策質疑型、政策影響型和政策制訂型。他們認為立法會在1991至1992年這段時間由政策宣告型議會轉變為政策質疑型議會,1992年以後又轉變成政策影響型議會,但亦有可能倒退回政策質疑型(政策質疑型,議會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以議會作為觀點交鋒的場所)。[16]針對殖民地時期立法局的研究,學者多運用類型化的研究方法進行制度分析,因為此時立法局並未發揮實質影響力,直到直選議席的出現,同時在這一時期,又伴隨常務委員會的出現、公開的議事規則的出現,議員逐漸獨立於行政機關,均說明立法會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了。[17]
九七以後對立法會的研究亦多伴隨探討與行政機關的關係。通過比較1995至1997年間與1997年以後立法會的表現,馬嶽認為香港立法會在九七後監督政府和審議方面的角色更為積極,在為特區政府提供合法性方面更為重要,也運用財政監督權對政府財政構成重要限制。[18]同時,馬嶽還提到立法會之所以對政治體制能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包括:民主派議員的委任、公民社會的成長、媒體的監督等。對立法會功能組別最完備的研究是思匯政策研究所2004至2006年的功能組別研究報告,其在經驗研究中提出了兩項假設:功能組別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灌輸了部門利益和維護不同經濟、專業界別所需要的特殊知識。[19]通過分析質詢、動議、議案和法案的數量、議員出席工作會議、委員會會議的表現,思匯政策研究所指出功能組別主要體現的是「界別利益思維」,在公共政策的審議上,其表現不如直選議員積極,[20]並且基於功能組別投票行為的經驗研究得出,功能組別有運用分組點票機制否決直選議席的趨向。為進一步揭示功能組別的行為方式,他們又分別對功能組別在法案和政策審議過程中的表現進行深入研究。其所得出的說法―功能組別代表着部門利益―是非常狹隘的。當政策事宜與部門利益無關時,功能組別通常會缺席審議,或者跟隨政黨利益來投票,或者根據政府利益來投票,而此時關於功能組別的兩項原始假設因缺乏足夠證據並不成立。[21]
前述大部分文獻是基於《基本法》對香港立法會啟動性權能的憲制限制,對立法會在九七回歸以後的政治影響多持悲觀態度,[22]甚至曾認為香港立法會具有積極性的學者也在九七後承認立法會面臨「政策影響力削弱」這一制度性變化。[23]如香港學者雷競璇認為,在回歸後的政治實踐中,《基本法》規定的分組點票機制大大限制了立法會的立法、議政和監督能力,使之比起香港回歸前的立法局猶有不如。[24]馬嶽認為,《基本法》對立法會的限制還造成政黨和議員政策影響力的下降,政黨沒有實質貢獻,只會站定立場相互攻訐。[25]《基本法》第74條對立法會提案權限制的影響不言而喻,如私人提案銳減、立法會不再主導議程設置等。由此帶來的後果始料不及,可能導致立法會議員將工作重心轉移至對政府的監督職能及委員會的工作,尤其是法案委員會和法案審議小組。
其實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如顧瑜認為雖自殖民地時期,香港就被稱為是擁有一個行政主導體制的政府,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行政首長相比,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擁有的權力是比較大的,但從《基本法》所賦予立法會的職權中可以看到,除了議員的提案權受到很大限制外,立法會擁有世界上其他議會通常都擁有的權力,例如通過法案、預算案及其他財政建議的權力。此外,還有相當部分是監察行政機關的權力。儘管《基本法》第48條規定的立法會職權條款、第74條對立法會提案權施加限制、附件二的分組點票機制等很明顯削弱了立法會的權力,造成立法會「有代表性卻無權力」,但行政長官強大的憲法權力與現實中是否強勢卻是兩回事。比如,從2013年開始,一到審議財政預算案的季節,政府就會遭遇立法會裏面的「拉布」。[26]雖然政府擁有提出所有重要建議的權力,卻難以掌握審議這些建議的節奏。政府「有權無票」,而立法會「有票無權」,其實並非一個準確的描述。隨1991年直選議席的引入和政黨政治的發展,1992至1997年間立法局的政策影響不斷增強。雖然大多數政策制訂權仍掌握在行政長官及政府官僚手中,但立法會也能通過制度化的機制影響到政策制訂,主要是通過預算控制和私人提案來實現。就政策制訂的過程而言,立法與行政關係的準確描述應為「主動型行政,回應型立法」,即行政機關就政策制訂而言具有啟動作用,而立法會則對行政機關的啟動作出回應型的審查,而審查的強度由立法會中跨政黨之間的合作程度決定及立法會中黨派與市民之間的關係決定。[27]
綜前所述,內地和香港學者關於《香港基本法》下的立法權與行政權互動關係的研究已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數還是屬於介紹性,或者專門從立法機關、功能組別、行政長官及其管治團隊等特定視角出發來研究,其研究結論也多具有權宜性、對策性的色彩。學界至今仍缺乏對《基本法》下立法權和行政權互動關係的綜合性和系統性的深入研究。因此對此問題仍有待學界進行更專門、更基礎的研究,從而從理論上更好地回應香港社會近年來民主政治的新發展。
現時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根本問題,在於特區政府是按無黨派政府的方式運作,而未有與任何政黨形成緊密的政治聯盟,政府官員因此無法像西方民主政體般,透過政黨在議會建立穩定的支持,結果造成行政與立法持續性割裂的管治困局。在行政立法持續性割裂的管治體制下,由於難以確保政府啟動的法案及重要政策可在立法會取得足夠支持,加之特區政府不善於處理爭議法案、政策(尤其是涉及政制改革和重大的社會公共利益),最終令不少法案及政策被迫擱置或者拖延,留給外界一種印象―《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約又相互配合」的政制設計在實踐中落空,立法會對政府制衡有餘而配合不足。對此,我們有必要有系統地檢視九七回歸前後,香港立法與行政關係的變遷及變遷背後的動因。
九七回歸前,香港沒有民主選舉,卻有一定的公民自由和經濟自由,也有獨立的司法和自由市場,此種現狀也是適應英國殖民統治的政治需要而形成的。除港督外,所有殖民地政府官員皆為公務員。這些公務員擁有極大的決策權,但他們無須對立法機關或市民直接負責。殖民地時期的行政局及立法局皆為港督的「諮詢」架構,其成員都由港督任免,故當時不存在立法制衡行政之說。彭定康政府推行代議制改革後,1995至1997年的立法局是立法機關在法律制訂、財政監督和影響公共政策方面最為積極的時期。從制度化的角度而言,這一時段的立法局也比1997年回歸後的立法會有更大權力,因為回歸後的立法會受制於《基本法》第74條和分組點票機制等諸多限制。總之,因政黨政治興起,又有直選議員加入,出現了正式的委員會制度和其他提高立法會自主性制度,為1985年後立法機關積極制衡政府創造了有利條件。
九七回歸後,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留給立法會的權力十分有限,政黨無法以組閣或者委員會的方式在事前監督上影響政府,所以只能尋求以質詢權等為代表的事後監督。此外,《基本法》承諾了一個「雙普選」式的民主化未來,並由此導致行政主導體制的現狀和民主制度的目標之間出現拉鋸。儘管如此,立法會仍通過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方式擴權,並對行政主導構成一定衝擊。因此在研究香港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時,必須正視一個基本現實―行政與立法之間存在着權力上的競爭關係。當立法會擴權或自主性逐步增強,就不可避免地與行政主導的管治原則相衝突;但當立法會的自主性削弱時,卻不一定出現一個真正強勢的行政主導政府。就香港回歸後近20年的管治經驗來看,立法會自主性屈尊的同時,立法與行政的關係亦常隨着規則與慣例的改變而出現新的變化,例如立法會中原本藉以尋求共識的議事機制失效,無法容納日益激烈的政治鬥爭,導致的結果便是立法會與街頭政治聯動,整個管治系統失靈。
本書的研究思路與論述結構為:第一章會分析行政與立法關係的基本理論,對全球主要幾種政體中的行政與立法關係進行比較研究。第二、三、四章按照時間線索,從整體上梳理港英殖民統治時期及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第五、六、七章分別從立法會的重要職權和其他重要制度設計層面探討立法與行政的關係。第八章承前文內容,進一步對形塑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立法會內部政黨政治進行了研究。第九章總結了九七前後香港立法與行政關係的變遷及變遷背後的動因,並提出了改善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提升香港管治質素的建議。
《基本法》確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以行政為主導,並且行政與立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約。此種政治體制,一般認為是在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上,行政應當處於優先和主導的地位。在一系列的政制發展討論中,中央及特區官員多次強調行政主導的重要性,並將它提升至《基本法》甚至是國家主權的層次來討論。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清楚地指出:「行政主導是特區政體設計的一項重要原則,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重要表徵。任何方案必須鞏固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體制,不能偏離這項設計原則。」《基本法》作如此設計,有其歷史因素和現實政治考慮,中央在1980年代思考香港的管治體制時,認為其以港督為核心的行政主導、立法局和行政局為港督諮詢機構的「行政吸納政治」的體制具有高效、穩定且易於控制的優點。同時,基於香港政制的地方性及延續香港政制與繁榮穩定的實際需要,中央認為行政主導是最易於滿足前述需求的政制形式。
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基本法》設計的行政主導原則並沒有貫徹落實,立法會對政府施政呈現出「配合不足,制約有餘」的特點。儘管《基本法》第74條和分組點票機制等對立法會制衡政府的權力施加了諸多限制,但立法會仍能通過一些制度化甚至非制度化的方式來擴權,例如立法會加緊對政府財政的控制、通過不斷提出修正案的方式來增加政府法案通過的難度(極端表現為「拉布」)、通過不具有約束力的動議辯論和「不信任案」向政府施壓等。同時由於立法會與政府之間缺乏政黨或委員會作為紐帶,政府官員因此無法像西方民主政體般,透過政黨在議會內建立穩定的支持,結果造成行政與立法持續割裂的管治困局。
為什麼一個適應香港需求的行政主導體制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行政長官在憲制文本《基本法》上具有優越地位,但回歸21年來,香港政治卻呈現一副「特首弱勢」的現象,行政主導面臨着名不副實的體制性尷尬。過往的研究往往局限於檢討香港管治的內部體系,比如「特首不黨」原則導致特首無法依賴執政黨及政黨管治聯盟;比如香港公務員沿襲港英舊制,抵制特首及委任官員的支配和調度;比如立法會缺乏「忠誠反對派」,激進泛民主派「逢中央必反」、「逢特首必反」;比如特首由非普選產生,即使是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仍被質疑「認受性不夠」等。其實有多項制度的安排是對行政主導的制度有利,如:立法會採取比例代表制的選舉辦法,再輔以功能組別議席,使得立法會內幾乎不可能出現某個單一政黨控制議會多數議席的情況;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規定特首不得有任何政黨背景,此舉從根本上保證特首不被任何政黨利益「綁架」,因為哪怕是根正苗紅的政團,亦會受本港民情的牽引,不會事事與中央保持一致;如《基本法》的選舉安排讓特首和立法會各自由互不相關的選舉系統產生,進一步降低了特首對政黨的依賴。問題是,儘管有前述鞏固行政主導的制度安排,為何歷任特首還是處處碰壁,施政困難?
為化解香港行政與立法的僵局,2007年12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允許香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增強行政長官的民意認受性,其後實現立法會全體議員的普選,又稱「雙普選」。香港的行政主導沿襲自港英時代的港督制。港督制下的港督合法性來源單一,是基於英國的單方授權。回歸後的行政長官合法性則是複合的,是基於地方選舉與中央任命,此時基於地方性政制的行政主導制仍具有一定的憲制合理性。但普選是否為解決行政立法關係難題的必然選擇?在普選實現之前,《基本法》的政制設計為香港政治的發展變化預留下極為廣闊的空間,行政主導的現狀與民主普選的目標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現有的條件下要如何化解,值得深思。
現存對香港政制的研究大多是將立法會視為行政主導體制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再分析其與行政權力(港府、特首乃至行政會議)的關係,並從在「雙普選」的藍圖下能保證行政主導體制有效性的角度出發,就其存在的問題提出制度或者執行上的建議。大多數研究以法理為經,案例為緯,分析行政和立法關係的應然和實然狀態,認為立法會自九七回歸後所為的制度和行為擴權已是不爭事實。這個過程還未結束,但必須受到《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約束。內地學者普遍認為《基本法》體現了「行政主導模式」的憲政設計,而隨着《基本法》實施進程的推進和香港社會多年來政經力量對比的變化,立法會擴權的趨勢漸漸明顯,香港立法會出現了「對抗吸納制衡」的制度難題。[1]也有學者從政治發展的角度出發,為行政―立法關係的未來走向提供建議,如分析功能界別的發展歷程、特殊功能和政治前景,或者是政府如何利用行政會議和高官任命來調整與立法會的關係等。
另有研究是針對立法會從選舉到立法再到監督過程當中不同行為主體的關係問題,代表性的研究多關注立法會中的政黨政治,即將立法會視為香港政黨政治的主要成長場所,分析立法會中的政黨博弈、不同政黨的實際表現,並對立法會的政治運作前景作出分析、研判。[2]在這一領域中,內地學者和香港學者的研究思路有明顯不同,前者注重梳理和特徵辨別,[3]而後者則注重基於一手資料的選舉策略、議題製造、媒體報道等問題,[4]學界在香港政黨的現狀上有較多共識,認為香港的政黨政治是一種非典型政黨政治,其發展受到「中國因素」(China factor)、行政主導體制、比例代表制選舉、議會內部功能界別和分組點票制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5]儘管存在着多種局限,但是其出現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具有諸多積極作用。[6]在未來,政黨政治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必然選擇,在此期間,如何協調政黨與其他權力主體的關係十分重要,有很多學者都贊同最終取消行政長官的非政黨屬性,並以執政黨或者政黨聯盟形式建立「內閣制」。即使不能實現,至少也需要建立一個以「政黨為基礎的政府」(party-based government),否則可能產生難以調和的衝突。[7]
關於1997年回歸前的立法局,香港的立法機關與西方民主國家相比,一般被認為擁有較小權力,有學者按照其對政策的影響將立法機關分為三種:[8]第一種為政策制訂型立法機關(又稱「積極型立法機關」),不但能改變、撤銷行政機關的措施,還能形成甚至用自己所立的法來取而代之。美國國會為其典型例子;第二種為政策影響型立法機關(又稱「回應型立法機關」),可以修正或者拒絕行政機關的政策,但不能形成或用自己的立法取代。德國和英國議會為典型例子;第三種為僅具備較小的政策影響力或不具備政策影響力的立法機關(又稱「邊緣型立法機關」或「橡皮圖章」),多表現為不能修正或拒絕行政機關的偏好,以前社會主義國家為典型例子。[9]世界範圍內大多數立法機關都表現為第二種或第三種形態,有學者將回歸前的香港立法機關歸為政策影響型,議員可以聯合通過動議辯論、行使提案權、拒絕或者威脅不通過政府的財政開支要求等。[10]回歸後,立法會的提案權受到《基本法》第74條和附件二分組點票規則的進一步限制。
Norman Miners教授在《香港政府與政治》一書中着重分析了1985年後香港立法機關的演進和制度化,指出立法機關承擔的三項主要活動為:立法、財政控制和監督政府。[11]這一傳統分類也與《基本法》授予立法會的權能一致;在另一篇文獻中,Miners教授分析了1970至1994年間香港立法機關功能的轉變,尤其是關注殖民地時期立法局議員,特別是非官守議員如何影響政策制訂,通過私人提案、委員會工作等方式制衡行政部門。[12]研究香港立法機關職能的學者Cheek-Milby,在1995年的專著中將香港立法機關的職能分為代議、政策制訂(立法)、體制維繫三項職能。雖然這並未完全囊括立法會前世今生的所有功能,也沒有按這些功能的重要程度排序,但Cheek-Milby的研究對立法會的歷史演進作了整全的描述,並對立法會的法案、修正案、質詢、動議進行量化分析,還關注了不同時期議員所扮演的角色。[13]其得出以1984年為分野:1984年以前的立法局在議會研究學者Mezey教授的分類下為「最小型立法機關」,1984年以後的立法機關為「邊緣型立法機關」,其得到的公共支持和參與形塑公共政策的能力不斷增強。[14]
除了Mezey教授的類型學外,Norton和Curtis教授的分類也獲學界所採納。Curtis根據強弱程度將立法機關分為四類:服從型(唯命是從)議會、贊成型議會(英國)、對等型議會和對抗型議會。[15]「對等型」議會這個概念後在蔡子強、劉細良的研究中,這一用語又被「議政型」(adversial)議會所取代。他們的研究綜合了Norton和Curtis的分類,構造出新的由弱到強的議會類型:政策宣告型、政策質疑型、政策影響型和政策制訂型。他們認為立法會在1991至1992年這段時間由政策宣告型議會轉變為政策質疑型議會,1992年以後又轉變成政策影響型議會,但亦有可能倒退回政策質疑型(政策質疑型,議會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以議會作為觀點交鋒的場所)。[16]針對殖民地時期立法局的研究,學者多運用類型化的研究方法進行制度分析,因為此時立法局並未發揮實質影響力,直到直選議席的出現,同時在這一時期,又伴隨常務委員會的出現、公開的議事規則的出現,議員逐漸獨立於行政機關,均說明立法會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了。[17]
九七以後對立法會的研究亦多伴隨探討與行政機關的關係。通過比較1995至1997年間與1997年以後立法會的表現,馬嶽認為香港立法會在九七後監督政府和審議方面的角色更為積極,在為特區政府提供合法性方面更為重要,也運用財政監督權對政府財政構成重要限制。[18]同時,馬嶽還提到立法會之所以對政治體制能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包括:民主派議員的委任、公民社會的成長、媒體的監督等。對立法會功能組別最完備的研究是思匯政策研究所2004至2006年的功能組別研究報告,其在經驗研究中提出了兩項假設:功能組別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灌輸了部門利益和維護不同經濟、專業界別所需要的特殊知識。[19]通過分析質詢、動議、議案和法案的數量、議員出席工作會議、委員會會議的表現,思匯政策研究所指出功能組別主要體現的是「界別利益思維」,在公共政策的審議上,其表現不如直選議員積極,[20]並且基於功能組別投票行為的經驗研究得出,功能組別有運用分組點票機制否決直選議席的趨向。為進一步揭示功能組別的行為方式,他們又分別對功能組別在法案和政策審議過程中的表現進行深入研究。其所得出的說法―功能組別代表着部門利益―是非常狹隘的。當政策事宜與部門利益無關時,功能組別通常會缺席審議,或者跟隨政黨利益來投票,或者根據政府利益來投票,而此時關於功能組別的兩項原始假設因缺乏足夠證據並不成立。[21]
前述大部分文獻是基於《基本法》對香港立法會啟動性權能的憲制限制,對立法會在九七回歸以後的政治影響多持悲觀態度,[22]甚至曾認為香港立法會具有積極性的學者也在九七後承認立法會面臨「政策影響力削弱」這一制度性變化。[23]如香港學者雷競璇認為,在回歸後的政治實踐中,《基本法》規定的分組點票機制大大限制了立法會的立法、議政和監督能力,使之比起香港回歸前的立法局猶有不如。[24]馬嶽認為,《基本法》對立法會的限制還造成政黨和議員政策影響力的下降,政黨沒有實質貢獻,只會站定立場相互攻訐。[25]《基本法》第74條對立法會提案權限制的影響不言而喻,如私人提案銳減、立法會不再主導議程設置等。由此帶來的後果始料不及,可能導致立法會議員將工作重心轉移至對政府的監督職能及委員會的工作,尤其是法案委員會和法案審議小組。
其實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如顧瑜認為雖自殖民地時期,香港就被稱為是擁有一個行政主導體制的政府,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行政首長相比,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擁有的權力是比較大的,但從《基本法》所賦予立法會的職權中可以看到,除了議員的提案權受到很大限制外,立法會擁有世界上其他議會通常都擁有的權力,例如通過法案、預算案及其他財政建議的權力。此外,還有相當部分是監察行政機關的權力。儘管《基本法》第48條規定的立法會職權條款、第74條對立法會提案權施加限制、附件二的分組點票機制等很明顯削弱了立法會的權力,造成立法會「有代表性卻無權力」,但行政長官強大的憲法權力與現實中是否強勢卻是兩回事。比如,從2013年開始,一到審議財政預算案的季節,政府就會遭遇立法會裏面的「拉布」。[26]雖然政府擁有提出所有重要建議的權力,卻難以掌握審議這些建議的節奏。政府「有權無票」,而立法會「有票無權」,其實並非一個準確的描述。隨1991年直選議席的引入和政黨政治的發展,1992至1997年間立法局的政策影響不斷增強。雖然大多數政策制訂權仍掌握在行政長官及政府官僚手中,但立法會也能通過制度化的機制影響到政策制訂,主要是通過預算控制和私人提案來實現。就政策制訂的過程而言,立法與行政關係的準確描述應為「主動型行政,回應型立法」,即行政機關就政策制訂而言具有啟動作用,而立法會則對行政機關的啟動作出回應型的審查,而審查的強度由立法會中跨政黨之間的合作程度決定及立法會中黨派與市民之間的關係決定。[27]
綜前所述,內地和香港學者關於《香港基本法》下的立法權與行政權互動關係的研究已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數還是屬於介紹性,或者專門從立法機關、功能組別、行政長官及其管治團隊等特定視角出發來研究,其研究結論也多具有權宜性、對策性的色彩。學界至今仍缺乏對《基本法》下立法權和行政權互動關係的綜合性和系統性的深入研究。因此對此問題仍有待學界進行更專門、更基礎的研究,從而從理論上更好地回應香港社會近年來民主政治的新發展。
現時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根本問題,在於特區政府是按無黨派政府的方式運作,而未有與任何政黨形成緊密的政治聯盟,政府官員因此無法像西方民主政體般,透過政黨在議會建立穩定的支持,結果造成行政與立法持續性割裂的管治困局。在行政立法持續性割裂的管治體制下,由於難以確保政府啟動的法案及重要政策可在立法會取得足夠支持,加之特區政府不善於處理爭議法案、政策(尤其是涉及政制改革和重大的社會公共利益),最終令不少法案及政策被迫擱置或者拖延,留給外界一種印象―《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約又相互配合」的政制設計在實踐中落空,立法會對政府制衡有餘而配合不足。對此,我們有必要有系統地檢視九七回歸前後,香港立法與行政關係的變遷及變遷背後的動因。
九七回歸前,香港沒有民主選舉,卻有一定的公民自由和經濟自由,也有獨立的司法和自由市場,此種現狀也是適應英國殖民統治的政治需要而形成的。除港督外,所有殖民地政府官員皆為公務員。這些公務員擁有極大的決策權,但他們無須對立法機關或市民直接負責。殖民地時期的行政局及立法局皆為港督的「諮詢」架構,其成員都由港督任免,故當時不存在立法制衡行政之說。彭定康政府推行代議制改革後,1995至1997年的立法局是立法機關在法律制訂、財政監督和影響公共政策方面最為積極的時期。從制度化的角度而言,這一時段的立法局也比1997年回歸後的立法會有更大權力,因為回歸後的立法會受制於《基本法》第74條和分組點票機制等諸多限制。總之,因政黨政治興起,又有直選議員加入,出現了正式的委員會制度和其他提高立法會自主性制度,為1985年後立法機關積極制衡政府創造了有利條件。
九七回歸後,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留給立法會的權力十分有限,政黨無法以組閣或者委員會的方式在事前監督上影響政府,所以只能尋求以質詢權等為代表的事後監督。此外,《基本法》承諾了一個「雙普選」式的民主化未來,並由此導致行政主導體制的現狀和民主制度的目標之間出現拉鋸。儘管如此,立法會仍通過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方式擴權,並對行政主導構成一定衝擊。因此在研究香港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時,必須正視一個基本現實―行政與立法之間存在着權力上的競爭關係。當立法會擴權或自主性逐步增強,就不可避免地與行政主導的管治原則相衝突;但當立法會的自主性削弱時,卻不一定出現一個真正強勢的行政主導政府。就香港回歸後近20年的管治經驗來看,立法會自主性屈尊的同時,立法與行政的關係亦常隨着規則與慣例的改變而出現新的變化,例如立法會中原本藉以尋求共識的議事機制失效,無法容納日益激烈的政治鬥爭,導致的結果便是立法會與街頭政治聯動,整個管治系統失靈。
本書的研究思路與論述結構為:第一章會分析行政與立法關係的基本理論,對全球主要幾種政體中的行政與立法關係進行比較研究。第二、三、四章按照時間線索,從整體上梳理港英殖民統治時期及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第五、六、七章分別從立法會的重要職權和其他重要制度設計層面探討立法與行政的關係。第八章承前文內容,進一步對形塑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立法會內部政黨政治進行了研究。第九章總結了九七前後香港立法與行政關係的變遷及變遷背後的動因,並提出了改善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提升香港管治質素的建議。
目次
第一章 行政與立法的一般理論與實踐
第二章 港英時期行政與立法關係的演變
第三章 《基本法》設計下的行政與立法
第四章 《基本法》下的民主與官僚
第五章 立法會提案權與行政―立法關係
第六章 香港立法會動議辯論權與行政―立法關係
第七章 立法與行政關係在其他制度設計中的博弈
第八章 議會政黨政治對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形塑
第九章 總結與建議
第二章 港英時期行政與立法關係的演變
第三章 《基本法》設計下的行政與立法
第四章 《基本法》下的民主與官僚
第五章 立法會提案權與行政―立法關係
第六章 香港立法會動議辯論權與行政―立法關係
第七章 立法與行政關係在其他制度設計中的博弈
第八章 議會政黨政治對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形塑
第九章 總結與建議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BL] 香港特區立法權與行政權關係研究](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962/96293736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