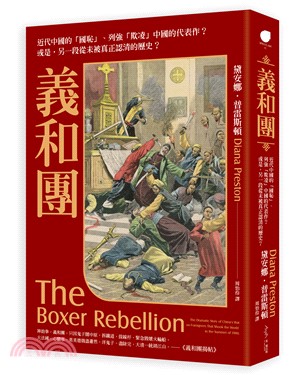義和團:近代中國的「國恥」、列強「欺凌」中國的代表作?或是,另一段從未被真正認清的歷史?
商品資訊
系列名:Speculari
ISBN13:9789869805827
替代書名:The Boxer Rebellion: The Dramatic Story of China's War on Foreigners That Shook the World in the Summer of 1900.
出版社:光現出版
作者:黛安娜‧普雷斯頓
譯者:周怡伶
出版日:2019/10/09
裝訂/頁數:平裝/576頁
規格:21cm*14.8cm*3cm (高/寬/厚)
重量:778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從殺中國人開始。
歷史課本不會有的角度I
從「八國聯軍」的角度,來看義和團事件--
「八國聯軍」一直以來都被視作為中國的國恥,列強侵略的代表作。但為什麼會有「八國聯軍」出現?歷史課本上輕描淡寫地帶過的「天津教案」「庚子拳亂」「德國公使被殺」,實際上是什麼樣的情形?對歐美各國來說,又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本書作者黛安娜•普雷斯頓(Diana Preston)蒐集了來自牛津大學圖書館、大英圖書館、英國國立陸軍博物館、國立海軍博物館;美國胡佛圖書館、美國海軍歷史中心;澳洲的馬歇爾圖書館等重要的研究機構或圖書館所提供,事發當時的外交人員與軍官、眷屬的書信、日記、記錄,從國際事件的角度,還原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的始末。
歷史課本不會有的角度II
「義和團事件」,其實是國際人道、衝突事件?
而透過當時外交人員與軍官、眷屬的書信、日記、記錄,本書不但詳實且生動地還原當時這些外國人遭遇的險惡情況(無分老幼老女與身分被大規模攻擊、殘殺等等)也回顧當時中國的基督徒,基於什麼樣的實際與政治需求被認定「不是中國人」,因而遭到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戮。
我們會發現:中國式的抵禦外侮,就從迫害有了其他選擇的中國人開始。再加上各式各樣政治上的、個人的企圖與私慾,以及歐美各國的錯誤判斷,現代根本無法想像的大規模國際人道、衝突事件,荒謬卻又慘絕人寰地在近代中國上演,進而引發各國雖然互相對立,但被作者界定為「聯合國維安行動雛形」的「八國聯軍」。
歷史課本不會有的角度III
一百二十年後,「義和團事件」真的過去了嗎?
二○二○年將是「義和團事件」的一二○週年。一九○○年時,任職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愛爾蘭人羅伯・赫德(Sir Robert Hart)曾經認為「西元二千年的中國,將會跟一九〇〇年的中國,大不相同!」這會是真的嗎?
事實上,透過作者的梳理與回顧,我們會發現:一九○○年後,義和團仍持續受到多方肯定,其中不但包括中共政府及其重要人物(如周恩來),就連被視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中山也曾公開肯定義和團的「愛國情操」。而這樣的肯定甚至延續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作者雖未提及,但這一次,編輯部請到張國城老師為讀者進行導讀。不但回顧歷史上的義和團事件,也進一步理解「義和團精神」如何被延續到現代,成為當政者的重要資產。
作者簡介
作家、歷史學家,曾在牛津大學修習現代史,獲得學位後,成為英國國家報紙和雜誌的專題和旅遊文章的自由撰稿人,並在BBC和加拿大廣播公司擔任廣播節目主持人,參與多部電視紀錄片的製作。
普雷斯頓在八年前開始進行「歷普」(歷史普及),第一本書是「英俊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的人物傳記《克羅登荒原之路》(The Road to Culloden Moor),最近一本作品《上乘悲劇――史考特船長的北極探險》(First Rate Tragedy, Captain Scott’s Antarctic Expeditions)受到各方讚譽,認為描繪史考特的心理,引人深思。在選擇寫作主題時,普雷斯頓會尋找那些本身就很引人入勝的故事和事件,這也有助於讀者更深入地瞭解過去。她喜歡寫人的經歷──這是讓人們思考和並採取行動的動機──而個人的故事能構成更大的歷史圖景。
不寫作時,普雷斯頓與她的丈夫麥可熱愛旅行。他們一起去過印度、亞洲、非洲和南極洲,並攀登了馬來西亞沙巴州的神山、坦尚尼亞的吉力馬札羅山,和委內瑞拉的羅賴馬山。他們的冒險之旅還包括在薩伊追蹤大猩猩,並在橫越納米比亞沙漠時露營。
黛安娜和麥可‧普雷斯頓目前住在英國倫敦。
周怡伶
台灣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英國約克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廣泛關注社會人文議題,曾任職非營利組織、出版編輯及內容創作,現職書籍翻譯。譯作有《我的阿富汗筆友》、《西奧律師事務所――FBI的追擊》、《貓狗的逆襲――荊棘滿途的公民之路》等十餘本。ilinchou@gmail.com
書摘/試閱
「任何戰爭的事實真相,過去從來沒有被寫出來,將來也不例外⋯⋯」
——新聞記者,喬治・林區(George Lynch)
「太陽完全升起時,剩下那一小群人,全都是歐洲人,站在一起頑強地面對死亡⋯⋯前仆後繼,最後終究不敵壓倒性的多數群眾,剩下這些歐洲人每一個都被以極端殘忍的方式斬殺。」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倫敦《每日郵報》(Daily Mail)刊了一則戲劇化的戰事報導,由該報特派員從上海發出。這則新聞的標題是「北京大屠殺」,內容描述令人毛骨悚然,證實了世界各地的猜測——被圍困在北京外交使館區的好幾百個外國人,遭到謀殺。
這則新聞傳遍世界,增添了恐怖的描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詳盡描繪俄國公使和夫人被丟進滾燙的熱油裡,該報還告訴讀者說,被困的自衛外國人「發了瘋用手槍射死自家婦孺⋯⋯拳匪衝向他們,無論死或傷,見人就砍,斬下首級掛在步槍跑到大街上。」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以悲傷的口吻寫道,「對這個恐怖的真相有所懷疑,是愚昧而且懦弱的」,並且發出「西方世界義憤填膺的復仇之聲」,還打算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一場追思禮拜,也刊出措辭沈重的訃聞。但是,就在這一片悲憤的氣氛中,美國國務院(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收到一則簡短的電報,使眾人暫停下來。這封電報是美國一位資深外交官從北京發來:「我們被圍困在英國大使館已有一個月。唯有獲得迅速馳援才能避免大屠殺」。預定在聖保羅大教堂的追思禮拜連忙取消,報社方面輕描淡寫地表示,之前得到的訊息顯然是錯誤的。
《每日郵報》刊登的那則報導,確實是一則假新聞,而且還扭曲得離譜,這個故事發生在一段奇異的歷史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中國北方的外國人遭到追殺。光是在北京,就有十一個國家的外國人被圍困在外國使館區。這群背景各自相異的外國人,為了求生存而被迫合作。外交官、傳教士、學者、海關官員、軍人、冒險家、旅館老闆、來訪的社會名流、新聞記者、工程師,一起構築防禦工事、堆沙包、滅火、用米和騾肉煮成難吃的大雜燴,心裡想著,最初是為什麼會被捲入這場災禍。據英國首相索斯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多多少少抱著懷疑地表示,甚至連被派遣到北京的各國聯軍也是個「嶄新的實驗」。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當時是在中國工作的採礦工程師,他的夫人璐・胡佛(Lou Hoover)驚奇地說,「有史以來,從未有過這麼多不同國籍的人一起投入軍事行動」。這是國際合作的創舉,是聯合國維安行動的雛形,在當時世界各國緊張敵對的情勢下顯得相當突出。
義和團之亂是一個相當不尋常的事件,既有英雄色彩卻又滑稽可笑,既悲慘震驚卻又生猛荒謬。它引發了各式各樣的傳說。對於使館區的防衛者有各式各樣的描繪,有的說他們是「文明」世界的堅定代表,英勇地把邪惡老太后——「中國的耶希碧 」——底下那些喊打喊殺的野蠻人趕走;有的說這些防衛者其實從來沒有陷於險境,他們只不過是一群膚淺無情、只知牛飲香檳的寄生蟲。真相,在兩者之間。既有勇氣與人性的表現,也有自私自利及極端冷酷的行為。
在這一切之上,它是一個充滿各種人性的故事。存活下來的外國人寫下許多事件描述及後續發展,希望能記錄下曾經發生的事——「在風暴真正來襲之前那種隱隱的恐怖感⋯⋯;一支虛弱的作戰士兵被困在歐洲防線上⋯⋯各國彼此應對的方式奇妙到有時會覺得外交手腕根本就消失了;最後終於抵達的救援聯軍是那麼怪異 ⋯⋯」。有人以當時充滿華麗辭藻的語言風格寫道,他們希望「栩栩如生表現出⋯⋯步槍上膛的咔咔聲;上身赤膊、汗珠閃閃的亡命之徒,野蠻地喊叫;重現令人不寒而慄的嗩吶鳴響;描寫出高聳入雲的烽火」。這些流利的文字描述,充滿意見而且通常是偏見,為這些事件提供引人入勝的洞察觀點。然而,在一九〇〇年那個身心受創的夏天,他們為什麼會產生那樣的感覺,又為什麼會那樣做,我們為了深入理解,就必須先瞭解當時他們世界中的某些事,以及他們既有的成見。
當時,人口數量跟現在非常不同。一九〇〇年出版的懷帖克的歲時曆(Whitaker’s Almanack),摘錄了受到義和團之亂影響的各國人口數目。英國的人口大約是四千萬;而當時佔全球表面積五分之一的大英帝國,人口總數是四億。美國的人口,根據一八九〇年普查,只有六千三百萬左右;到了一九〇〇年普查,由於移民,人口暴增到七千六百萬。義大利有三千一百萬人,法國將近三千九百萬,日本四千三百萬,德國約五千二百萬,俄國則是一億三千萬。而中國的人口,據稱超過三億。懷帖克駁斥了中國人口將近四億的說法,他語帶不遜寫道:「一般認為,中國官員所謂的普查是不可靠的。」
當時,西方國家正處在新世紀的開端,人們還在爭論,到底世紀開始的時間應該是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還是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在英國和美國是從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算,受到英國皇家天文學會的認可。然而,德意志皇帝和德國政府堅持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才對。有些人是樂觀主義者,相信進步和文明將會一直向前而無法抵擋。作家喬治・威爾斯(H.G.Wells)預言一個有飛機、空調以及舒適郊區生活的世界,但是,他也跟別人一樣,預言會有戰爭發生。有些人認為,大規模的國際衝突只是遲早的事。當中國北方的動亂爆發時,他們在想這會不會就是觸媒。有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女傳教人璐耶拉・麥恩兒(Luella Miner),眼光非常清楚,她描述「周遭的氣氛就好像電光火石一觸即發」,並且焦慮地問道,「我們是否來到了一直擔心的歐戰觸發邊緣?」
敵對雙方將在戰場上對決,而達爾文的演化論更進一步支持了這個想法。對某些人來說,至少演化論似乎是正式認可了種族之間以及個人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而且它將社會階級、貧富差距、還有從上到下的各式欺凌剝削,都給正當化了。十九世紀有一位著名的英國新聞記者威廉・湯瑪士・史提得(William Thomas Stead),後來因鐵達尼號失事而遇難,他曾寫道,「演化論可以視為這個世紀的宰制教條。其隱含的影響在生活各層面都可以感覺得到。它深切改變了我們對生命創造的觀念,而且愈來愈影響我們對道德的看法。人們在問,為什麼不趕快把所有的笨蛋、瘋子、以及治不好的病人都送去毒氣室?而且,在更大場域的國際政治上,我們為什麼要對弱國施恩?誰夠力,誰就有理。趕盡殺絕的戰爭,似乎被認可是符合自然的。」
英國和美國都認為,盎格魯薩克遜種族優於其他白人種族,因此,有權統治其他種族。有一位作家認為盎格魯薩克遜人「完美符合現代生活的種種特徵條件」。盎格魯薩克遜注重實務興趣以及物質擁有,因此在全球市場中獲勝,「因為他們是天生的物質發明家,而物質是民主制度裡大眾最為關心的。」這位作家成功以雙韁繩來駕馭自利行為及道德標準,這一點讓他很突出,不過這位作者認為,盎格魯薩克遜具有「優越的心理狀態,無感於這種天生的二元性」,於是沾沾自喜下了結論,「說英語的人和其他人有著一種心理上的差異,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在別人身上顯得偽善的,在他們身上就不會。他們是善感的人;善感的人,並不擅長分析自己的動機和衝動。」
西方人這種自覺的優越感,特別是講英語的西方人,在義和團之亂的英美文獻之中,明顯地佔了絕大多數。他們瞧不起「歐陸人」抽煙喝酒無所事事,而且歐陸人總是避免出力,盎格魯薩克遜人則是苦幹實幹。有一位美國傳教士寫道:「英國和美國的男孩子,就算是穿著斑駁的制服,也能一眼就分辨出來,因為他們的體格就是男子漢。這讓我對自己的種族感到驕傲。」
當「英國的世紀」接近尾聲時,英國把眼光投向美國,這是合理的;而且,英國擔任全球警察、以及龐大帝國的行政官,這種責任實在是難以獨自負荷。英國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向美國發出「負起白人的重擔」這項呼籲。對於他和跟他想法一樣的人來說,白人的重擔,包括了所有不是白人的人。他的訴求帶有無私的高貴氣息,美國人採納了:他們認為,新的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對於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發生在中國的事件正是一個根本性的探問。共和黨的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一八九六年被選為總統,儘管私下有點遲疑,但他是個擴張主義者。當時,夏威夷正要正式被併入美國國土之中。古巴當時是西班牙殖民地,美國和西班牙為了古巴處置問題,雙邊緊張情勢升高。一八九八年二月,一艘配備武器的巡航艦緬因號(USS Maine)在哈瓦那港爆炸沈沒。這艘船爆炸原因可能是大意在火藥室旁儲存易燃煤炭,不過,當時的自然反應卻是怪罪西班牙人。
美國的帝國主義者亞伯特・比佛利奇(Albert Beveridge)曾宣稱:「我們是一個到處征戰的民族,我們必須順從流在我們體內的血,要去佔領新的市場,有必要的話,要佔領新的土地。」大西洋是「我們的真正戰場。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菲律賓建立了島嶼帝國。而美國在太平洋上有一支強有力的艦隊。菲律賓理所當然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宣戰,五天之後,美國海軍中校德威 (Captain Dewey)在馬尼拉灣攻擊一支西班牙艦隊。美國在古巴對西班牙的戰爭,則是結束於聖地牙哥一支西班牙艦隊被擊敗;四天後,夏威夷成為美國屬地的條約正式批准生效。古巴獲得獨立,西班牙因戰敗而割讓波多黎各及關島給美國。
菲律賓方面,問題就比較棘手了。菲律賓獨立運動的領導人阿奎納多(Emilio Aguinaldo)已經跟西班牙人對抗了好幾年,在戰爭中他是站在美國人這一邊。他推崇美國,而且喜歡人家叫他「菲律賓的喬治・華盛頓」,阿奎納多希望菲律賓獨立作為回報。但是他的盼望落空了。在幾番辯論之後,美國把菲律賓納為屬地,阿奎納多發動游擊戰,一直打到一九〇〇年初。最後,美國的死傷人數,是美西戰爭的四倍之多。「因為菲律賓問題,我被大力抨擊,」麥金利總統說,「但是不應該怪到我頭上。說真的,他們是上帝送我們的禮物。」
菲律賓問題並沒有阻擋美國的多數公眾意見,不像歐洲大陸支持波耳人從英屬南非獨立的奮戰。波耳人被視為具有自由身份的白人,經濟獨立,他們對抗的是人數眾多且裝備較精良的敵人。英波戰爭的起因有一部分是為了非波耳人在波耳共和國裡的權利,但是,也許更是為了鑽石礦場的控制權。英國最後獲勝,《生活》(Life)雜誌說得乾脆:「擁有鑽石的小男孩,打不過經驗老到的大強盜。」
英波戰爭在一八九九年十月中旬開戰,一開始是英國人節節落敗。英國軍隊很久沒有打仗了,上一次是四十年前的克里米亞戰爭。年輕的軍官出身於私立貴族學校,在這種學校受到高度尊崇的是英勇氣概而非學業表現,結果證明了他們不如老經驗的波耳指揮官。一八九九年十二月「黑色的一週」,英國打了三次大敗仗,分別在梅傑斯豐坦(Magersfontein)、風暴山(Stormberg)及科倫索(Colenso);一九〇〇年初,慶伯利(Kimberley)、拉迪史密斯(Ladysmith)、梅富根(Mafeking)三個城市被圍。看到英國軍隊的表現這麼差,英國大眾都震驚了。大敗於斯匹恩山(Spion Kop)消息傳來,這絕對不是英國人想要的新年禮物,而且這似乎也證實了他們暗自擔心的事,那就是大英帝國擴張過度而撐不下去,開始走向衰落。
英國的歐陸對手可是幸災樂禍。一八九八年,英法兩國在尼羅河的法秀達(Fashoda)發生衝突,法國在非洲的發展野心因而受到阻礙,此時還懷恨在心。一九〇〇年一月還有英國報紙刊出嚴正的文章表示,法國有可能趁著英國忙著跟波耳人打仗時,發動一支聯軍來轟炸倫敦以示復仇。俄國和英國也是互相猜忌,尤其是在亞洲。這個時期就是所謂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英國跟印度的間諜——就像吉卜林筆下的基姆(Kim)那樣——混跡在中亞高山地區的遊牧民族之中暗暗監視,以防俄國的擴張主義威脅到英屬印度。英國跟德國的關係也很緊張。德國的威廉大帝(Kaiser William)雖然很愛戴他的祖母維多利亞女王,但是他認為,德國的軍事及商業力量正在崛起,所以應該要得到相應的殖民地才對。威廉大帝追求實現他的想法,決心要與英國優越的海軍一爭高下。一九〇〇年新年當天,他承諾要讓德國海軍重生,好讓德國有機會贏得「它尚未得到的位置」。
一八九八年,俄國沙皇尼可拉斯二世(Nicholas II)已然體認到這些大國之間的敵對以及隨之而來的軍備競賽,於是他召集了一個國際會議來辯論這個議題。會議在一八九九年五月於海牙(Hague)召開,會中各國同意一項協議,針對國際爭端提供自願性的仲裁。另外還有一項協議是,定出陸戰的相關規範,包括絕對禁止「交戰國」搶佔私人產業,也就是說,禁止洗劫財物!而且還有一條用心良苦但毫無約束力的解決方案,明列軍事支出以及新種武器的限制,「這對於人類道德與物質利益是相當必要的」。除了英國和美國之外,其他二十四位使節都同意禁止使用達姆彈。然而,發生在中國北方的事件顯示,遵守這條協定還不如乾脆打破協定。
當時外界對日本的了解並不多,不過日本跟中國都有派代表參加海牙會議。自從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日本迅速現代化,把西方科學及工程技術,以及古老的愛國主義價值觀及東方道德觀,結合起來。
一八九四/五年,中國被日本的海軍和陸軍打敗,兩軍在組織及裝備上都是沿循歐洲路線。這場戰爭震驚全世界,因此德意志皇帝創造了這個用詞「die Gelbe Gefahr」——黃禍,這個觀念迅速傳開。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黃禍》(The Yellow Danger),作者席爾(M.P. Shiel)描述中國人跟英國的歐洲敵國共謀,意圖打破英國在遠東的霸權;其實,中國人真正意圖是與日本之間的秘密結盟,以成為歐洲及亞洲的霸主。書中有一個角色這麼說,「如果黃種民族幾億人團結起來,大步朝西前進,那麼歐洲會面臨到什麼命運,實在是無從想像了。」 話雖如此,作者已經把那幅景象描繪出來給讀者看。嘶喊的中國人,在巴黎大街上用斬下的首級及四肢當球打;而且,「東方佬」還會用食人族的手段。「在歐洲,區分黃種人與雜食者的矮籬,真的是非常矮——歐洲人的皮肉不是黃色的,而是粉紅,就像初生幼鼠那樣。飢餓感一來襲,這道矮籬很輕易就被跨越過去了。」
《黃禍》書中用來形容東方角色的詞彙辛辣,例如「對殘忍有著惡魔般的愛」、「窮凶惡極的狡猾」。這種語言也可見於一九〇〇年被困在北京的外國人所寫的書信、日記和國際報紙的文章中,用詞完全一模一樣。《泰晤士報》憤怒譴責假想中的北京大屠殺,文章中警告「全球的黃種人暴動崛起」的危險。外國人在北京被圍困當時,美國某份報紙上刊出一首詩,相當典型:
幾百萬可悲而且怪異的黃色面孔,
帶著恨意把他們團團圍住;
絕望之中,他們以勇氣堅守著斷垣殘壁,
等在外面的是那些暴徒。
達爾文主義更是加強了這種恐懼和偏見,而且鼓勵西方人把東方人看作是比較沒有高度演化的物種,而且受到野蠻的動物本能驅使。一八九七年,在中國北部發行的《先鋒報》(Herald)出版了一篇文章標題是〈達爾文主義和中國〉。文中引述一位荷蘭科學家杜波(Eugene Dubois)的研究,此人宣稱發現了爪哇猿人的形成過程中「失落的連結」,基於這一點,這位匿名的報紙文章作者說,東方人就是不像歐洲人那樣高度演化,任何對此懷疑的人必須去中國的街上走一走:「很多中國人還保有控制雙腳的演化遺存現象,這一點在歐洲人身上已經完全看不見了⋯⋯。觀察那些苦力赤腳踩在潮濕的街道,就足以證明他們腳板的內側從來沒有碰觸到地上⋯⋯」,他接著又說:「⋯⋯人在發怒的時候,就跟野獸沒兩樣」。當中國人暴怒時,他的「類人猿祖先」就回返了,把他變成「一頭憤怒的野獸,眼睛有如噴火,嘴巴吐出泡沫,幾乎就像瘋狗分泌毒液那樣⋯⋯觀察他彎腰後突然挺身、手臂揮舞、手指頭抽動,幾乎無法受控制的樣子⋯⋯活生生就是一個發怒的類人猿。」
作者應該會發現,有一種心態令人完全無法理解。「中國人從來不曾有一絲懷疑,無論拿各種事物來考量,他們認為自己絕對優越,外國人根本不能比,而且他們最後一定會勝利」,牧師提摩西・理查(Timothy Richard)是在山東旅行的威爾斯傳教士,熱切地把這個訊息捎回家鄉,他描述有一個中國人問他打從哪裡來:
「打從青州府來的,」我回答。
「可是,」他說,「你不是中國人呀;你是外國人。」
「沒錯,」我回答,「我出身英格蘭」。
「英格蘭!」他大喊,「就是那個反叛我們的國家⋯⋯」
「不能說英格蘭反叛,」我說,「因為它從來不屬於中國。」
「但是它確實是叛變,」他反駁,「以前英格蘭是對中國朝貢的國家之一⋯⋯後來它造反了,自有天下以來這是最大的叛變。」
大部分外國人根本不認為自己是造反的蠻族,而且他們還瞧不起中國的獨裁及封閉的政府制度,認為這些完全不合時宜。但是,一九〇〇年的歐洲大陸還存在國王和皇帝,只有法國和瑞士是共和國。被派到北京的聯軍組成國家之中,只有美國、英國和法國可以說是民主制度。俄國沙皇、奧匈帝國皇帝、德意志皇帝,可以隨時解雇大臣,就跟中國的皇太后一樣。
或許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時期也是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高峰。持這種想法的哲學家對未來的看法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其中的人可以完全自由,沒有政府、法律、私有財產權,也沒有腐敗的體制。沒有人可以剝削別人的勞動而生活,人類天性會產生自然而然的正義。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烏托邦,必須發動革命,因為統治階級不會自願放棄權力。炸彈和刺客的子彈,就是革命的工具。一八九四年,法國總統卡爾諾(Carnot)被暗殺;一八九七年,西班牙總統卡諾瓦(Canovas)被暗殺;一八九八年奧國女皇伊莉莎白被暗殺。北京使館區被圍困時,義大利人得知他們的國王也被無政府主義者暗殺了。
同時,一八八七年俄國,年輕的烏里亞諾夫(Alexander Ulyanov)連同其他四個學生被絞死,因為他們策劃以炸彈殺掉沙皇亞歷山大三世(Tsar Alexander III)。烏里亞諾夫的兄弟伊里奇(Vladimir Ilyich)誓言復仇。伊里奇被流放西伯利亞三年,一九〇〇年初被釋放後,他前往維也納,繼續策劃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這次要更有盤算、更有組織,而不是像無政府主義者喜歡的隨機暴動。伊里奇得知中國發生的事件之後,他呼籲「被奴役的中國人割斷它的鎖鍊 」,一九〇一年他開始使用化名「列寧」(Lenin)。
無論是否主張革命,社會主義運動得到支持是因為,十九世紀末的西方世界仍然相當不平等。在英國,至少有十五個貴族地主,從土地得到的收益一年超過十萬英鎊。收入懸殊差距非常大。派駐中國的英國公使竇納樂(Sir Claude MacDonald)年薪是五千英鎊。一個海軍副將,例如駐中國的皇家海軍艦隊司令西摩爾中將(Sir Edward Seymour),年薪是一千四百六十英鎊。但是,他的下士水手,一年薪水只有三十二鎊;步兵隊長年薪約二百一十鎊,二等兵年薪不到二十鎊。售貨員、辦公職員及老師,年薪大約是七十五鎊到一百鎊之間。在美國,百分之一的人擁有整個國家總財富的一半。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年薪五千五百美元,陸戰隊上校大約二千美元,陸戰隊士兵大約一百六十六美元。辦公職員薪水是一千三百二十美元,女僕年薪是四百八十美元。(一九〇〇年的匯率大約是一英鎊對四・八美金)。在購買力方面,在英國要購買房子的全副傢俱要花一百五十英鎊。一瓶威士忌價格是三先令又六便士,二十五支雪茄價格是五便士,一份「牛肉及雜碎餐」價格是四便士。在美國,一套品質好的西裝是十一美元,一瓶威士忌大約二美元,一磅醃碎牛肉是八分美元,一份「火雞餐」是二十分。在北京城劫掠那段時期,許多一般士兵和水手很難過的是,他們手邊沒有錢能像長官那樣購買大特價的贓物。
科技也是促使社會轉變的一個因素。十九世紀是蒸汽的時代。路上的鐵路及海上的蒸汽船,大大增加旅行的速度、大量人口移動以及貿易量。從英國到上海,坐蒸汽船不到六星期就能抵達。電報、海底電纜以及新發明的電話,使人們幾乎可以無時差通訊。一八九七年六月,維多利亞女王在白金漢宮的電報室,發了一封登基六十週年的訊息給她治下的帝國臣民。不到兩分鐘,訊息就已經通過伊朗的德黑蘭(Teheran),直奔她帝國的最遠疆界。中國發生暴動時,「所有現代文明的設備」都派上用場來協助被圍困的人。根據其中一位的說法,「電報載著吾等慘況於大海波濤下迅速傳送,全球四方海軍基地和地面營旅因而騷動」。這種裝置發明,大大增加軍隊部署至暴動地點的速度。然而,靠動力的運輸交通還在初期階段,要是鐵路和電報纜線斷掉時,軍隊還是得像中古世紀那樣,靠著馬匹來傳送訊息及馱運行李和槍枝,在中國的各國聯軍就是如此。
槍枝本身也演進得更有威力,能迅速開火,也比較準確。早在一八七九年英國對戰南非的祖魯人(Zulus)就已經使用首批機關槍。也許是預見到這一點,一九〇〇年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上,最大的個展就是施耐德(Schneider-Creusot)的長程大砲,以及維克斯-馬克沁(Vickers-Maxim)的快速擊發機關槍。中國人對這些新式武器非常有興趣,而且投資很多在歐洲軍火製造商。這些武器竟被用來對付供應武器的國家,在中國的戰事還是其中頭一遭。德意志皇帝聽到消息,有一艘德國戰艦在中國遭到最新式的克普大砲攻擊,因此非常生氣地向軍火製造商佛列茲・克普(Fritz Krupp)抱怨,「我派士兵去跟黃皮膚野獸打仗,此等危急情勢可不是發財的時機。」
然而,造訪巴黎萬國博覽會的五千萬訪客,非常驚訝看到其他迅速發展的科技。主展場是電力宮(Palace of Electricity),裝上五千七百顆以電力供應的電燈泡,整座宮殿耀眼輝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造燈光聚在同一處。而且,此時距愛迪生首度向大眾展示電影還不到十年,觀眾已經可以欣賞到由十個同步投影機「循環播放」的影片,只是這些機器不時就故障。博覽會上另一個亮點是蜿蜒在地面上的兩條移動走道(trottoir roulant);還有X光機也展出了,遺憾的是,這個新發明是北京圍困中的醫院很需要的。
除了萬國博覽會以外,巴黎還是不負令名,繼續豐富的夜生活。歐洲紳士來到巴黎,沈醉在本國所無的異國風情煙花界。有一家妓院老闆自傲展示一張椅子,英國王儲、也就是未來的國王愛德華八世,就是坐在這張椅子上挑選共度春宵的女人。紅磨坊裡大跳康康舞。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此時雖然病重,但還是生動地畫出那些娼妓。孱弱的王爾德(Oscar Wilde)在一八九七年出獄之後,流放於巴黎。
如果說巴黎充滿誘惑力,那麼東方的溫榻軟床就更是挑逗了。對西方男人來說,東方女人具有神秘的魅力。根據一個維多利亞時期的人以狂放熱情所寫,一般認為東方女人「完美理解所有的性愛藝術及手法,能夠滿足任何品味,而且臉蛋跟身材賽過世界上任何女人⋯⋯」。有一位被圍困的日記作者描述跟滿族女人的一段遇合,「耳中仍迴盪著狂亂的喊打喊殺時,那就像一劑迷魂藥」。許多男人覺得,當地的床伴,或說是「字典情人」,是一個學習語言的好途徑,而且充滿樂趣。一八九八年美國的《世紀雜誌》(Century Magazine)刊載了一篇故事就描寫到這一點。這篇充滿感傷的傳奇故事,描寫一個年輕日本女子嫁給美國海軍軍官,但是後來被拋棄。這個故事經過戲劇化之後,就是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的靈感來源。
另一方面,出身良好的西方女人是不可以享受性愛的,否則就會被視為天生的娼妓胚子。一八九六年,英國首批「性事大師」之一艾德華・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表達出維多利亞時期的普遍觀點,對於許多女人來說,性不過就是「真正的犧牲,即使是自願的」。寇松勳爵(Lord Curzon)教他的夫人如何行房時說過一句名言,「淑女絕對不可以動」。但是,許多記載顯示,北京的西方人透過頻繁的婚外私通,兩性雙方都表現熱絡。
同時,在北京的西方人不解的是,在這個女性被輕視且被支配的國家中,掌權的顯然是皇太后。而所有牽涉其中的西方各國,除了維多利亞女王為帝國元首之外,沒有一個國家的女性擁有完整的民主權利。就連時任美國總統的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一九〇五年還這樣寫道:「懂事且負責任的女性不會想要投票。在創造我們的文明的過程中,由男人女人分別承擔的職責,很久很久以前就由一位比我們更高的智慧設定好了。」這種說法,跟孔夫子遺訓也差不多;好幾個世紀以前,孔夫子就已經定義了中國女性被支配的地位。
軟弱被視為娘娘腔,在很多方面,白種女性是白種男性的所謂負擔之一,尤其要保護女性名譽,以免被一大群造反的低等種族玷污。這就是為什麼,女性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時,往往引起非教會社群的非議。報紙上還激烈爭辯女性是否應該從事運動。杜賽斯公爵夫人(Duchesse d’Uzes)說,「所有的運動只要不造成太多疲勞都是有益健康的」。諾度醫生(Dr. Max Nordau)認為,「在運動中,即使是最有男性特徵的運動,女性具有不同於男性的其他企圖跟希望。她會在意穿著。她試圖以好本事來取悅人。這是另一種賣弄風情的形式,說到底就是在賣弄風情。」當然,許多女人在保衛使館區時承擔了軍事角色,有一兩位女性駐守防禦工事,出身芝加哥的北京飯店(Hôtel de Pékin)老闆娘,還前去援救改宗信教的中國人。
抽菸是另一個爭議點。根據一九〇〇年二月英國《淑女園地》(Lady’s Realm)雜誌,女性讀者四比一贊成女人抽菸,但是要符合某些條件。「要看煙是怎麼抽,也要看是在哪裡抽;如果可能會冒犯別人,她就不會抽菸⋯⋯要展現自己之前,先學習怎麼抽;不要扭曲你的臉;不要吸進去;避免抽廉價香菸。」至於反對女人抽菸的意見則頗為刻薄,「我認為抽菸的女人很可怕而且一點都沒有女人味⋯⋯,我希望男人不要理睬這種女人,因為她活該:不可能有其他辦法能夠讓她醒悟。」時至一九〇八年,紐約市還頒佈蘇利文條例(Sullivan Ordinance)禁止女人在公眾場合抽菸。但是,在北京使館區被圍那段期間,許多女人抽煙抽得很兇而且還是公開的,有部分原因是放鬆壓力,另外也是為了蓋過身體的臭味。
到了一九〇〇年,女性也有機會受新式教育,學院和大學開出各種科目的學位課程給女性。女性也開始認真思考如何養活自己,不只是經濟上需要,而是為了擁有更大的自由。女性雜誌上有許多找工作的建議;也有些女性進入專業領域。義和團之亂當時,英國的女醫生超過兩百位,而一八八〇年只有二十五位。被包圍在北京使館區內就有五位女醫生,但是很有趣的是,她們毫不猶豫同意擔任男性醫師手下的護士。
這就是一九〇〇年,不幸在北京遭遇圍困的外國人的世界。他們遭遇到的事情,促使許多人以紙筆寫下來,這些不時透露熱情的生動紀錄,描述了一個至今仍有共鳴、超乎尋常的事件。為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報導義和團之亂的愛爾蘭記者喬治・林區寫道,「任何戰爭的事實真相,過去從來沒有被寫出來,將來也不例外。」他是對的;但是,義和團事件之中,那些精彩而充滿人性的經驗,卻精準地躍然紙上。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