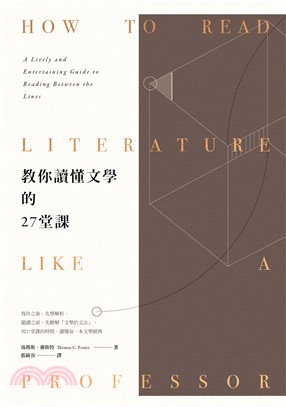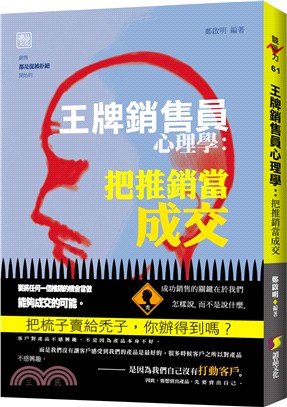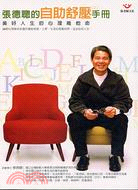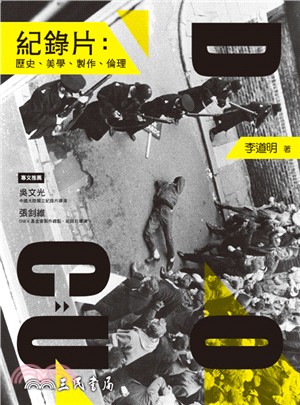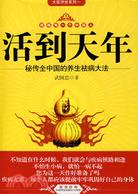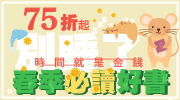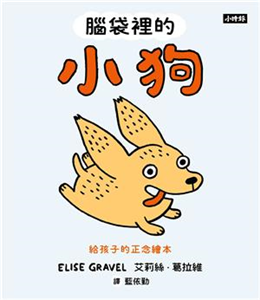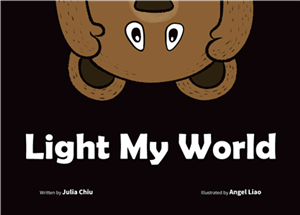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
商品資訊
系列名:木馬文學
ISBN13:9789863597704
替代書名:How to Read Literature Like a Professor
出版社:木馬文化
作者:湯瑪斯‧佛斯特
譯者:張綺容
出版日:2020/03/11
裝訂/頁數:平裝/416頁
規格:21cm*14.8cm*2.7cm (高/寬/厚)
重量:499克
版次:3
商品簡介
27堂紙上文學課,讓你成為非一般讀者
湯瑪斯.佛斯特以超過20年的豐富教學經驗,告訴我們如何閱讀,如何尋找模式與象徵。閱讀是一項極度燒腦的工作,需要靠著直覺與感受,與熟悉文學的文法才能融會貫通,通曉他人看不見的隱藏意涵――
文學名師帶你讀懂世上所有文學經典!
▍踏上旅程後,騎車或騎龍都一樣
魔戒、星際大戰……只要主角被派去某地做某事,十之八九都屬於追尋文學。只要被叫去跑腿,上路出發,並包含追尋五大要素:追尋者、目的地、去那兒的理由(假的)、試煉與挑戰、另一個去那兒的理由(真的)――都算數。
▍世上萬物皆文本,沒有誰高誰下
文學經典是一張大家都假裝不存在的清單。引用荷馬不如引用辛普森家庭,拿出莎士比亞說嘴不如談談安徒生童話。重點不在於你掉的書袋多高貴,而在於你想要傳達什麼,而且讓人看得懂。
▍「神之文本」莎士比亞,忘記他你做不到
重量級名家,名言製造機,迷因與鄉土劇大始祖。莎翁引用一出,必得心領神會的點頭。只要沒有靈感、想不出主角名字、名作引用到膩……莎翁永遠都在你身邊。
▍要看懂西方作品,關鍵就在十字架上的那男人
西方世界最意義深遠的命名工具書,人生在世可能經歷的苦難,《聖經》裡幾乎都有詳細記載。無論是否信教,聖經都是隨講隨通的文本,連魔鬼也引用不綴!
▍世上沒有原創,經典都是抄來的
文學向來從文學中再生文學。當你想讀著某本小說,卻發現怎麼看都有其他作品的影子?你的眼睛沒有問題,因為文本之間原來就互有關連。此外,一部作品好不好看跟有沒有參考其他典故,一點關係都沒有。
☞文學申論題聖經
☞創作人的先修學分
☞給讀者的輕鬆閱讀指南
27堂文學課中還有――
政治歸政治,龜苓龜苓膏?
反諷地獄哏也能安全下莊?
文學中的性愛,是鑰匙和碗?
復活不是重生?吃飯無關吃飯?
身上有疤、長相醜陋是一種表態?
童話故事才是真本事,無腦的人看不懂?
……更多文學手法,翻書見真章!
作者簡介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英文教授,擁有25年教學經驗,教授古典及當代小說、戲劇、詩以及創意寫作。他曾著述多本關於20世紀愛爾蘭及英國小說與詩歌的作品。佛斯特認為,將文人用以創作的符碼引介給讀者,幫助大眾擁有更多瞭解文學的管道,更能做到推廣閱讀的目的。他認為世上其實沒有必讀經典,讀者應該要做的是尋找能激發自身想像力、自我挑戰――或單純只是讓你覺得好看的作品,這才是文學閱讀的真諦。作者現居於美國密西根州東蘭辛市。
張綺容
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現任世新大學英語學系助理教授,曾任中原大學專任助理教授、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著有《中英筆譯》、《英中筆譯》系列二冊、《翻譯進修講堂》、《英譯中基礎練習》,譯作包括《傲慢與偏見》、《大亨小傳》、《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怪奇地圖》等二十餘本書。
名人/編輯推薦
※Amazon長年暢銷書
※美國大學文學系指定閱讀書籍
※200位作家寫作技巧分析,300部文學作品
※譬喻、嘲諷、引用、象徵等文學手法全解析
※應用範圍包含書籍、影視全領域
作家 朱宥勳、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作家 宋怡慧、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黃涵榆、小說家 楊富閔
導讀:追尋一種閱讀與傾聽的生命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黃涵榆
我在英語系教授英美文學課程將近二十年,不管是在課堂或課餘時間,同學們「讀不懂」、「讀文學有什麼用」的反應時有所聞,也有不少學生進英語系或外文系純粹只是為了精進口說的語言能力,並沒有把閱讀文學設定為重要的學習目標。這類的反應其實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台灣學生要克服外語的鴻溝已經不算一件容易的事,更別說是進入到文學作品的內涵,再加上整個社會氛圍總是以「競爭力」衡量一切,文學似乎總被認為產值或CP值不高,許多學生更容易望之卻步。
我並不打算在這裡分析上述的制式反應或刻板印象顯露了對於文學和深刻的語言學習的什麼誤解與抗拒,我也不打算大談文學的「無用之用」。但是我相信,《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How to Read Literature like a Professor)可以帶給中文讀者閱讀文學更強的動力。
《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是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英文系教授湯瑪斯.弗斯特(Thomas C. Foster)的著作。本書在二○○三年出版之後已多次再版,第一部中文譯本在二○一一年上市。除了本書之外,作者弗斯特也寫了好幾本如何閱讀各包括小說、詩歌、電影各類型作品的書籍,推廣大眾識讀和文化啟蒙可謂不遺餘力。
「文學是什麼」也許可以做為讀者開卷的提問。作者提到他對文學的定義很寬鬆,包括小說、戲劇、詩歌、電視、電影甚至廣告和電子傳媒,都可以是文學。如果我們暫時將文學定義為經過巧妙安排的文字與影像作品,本書做為一本導讀,自身就具有高度的文學性,並非一般講究SOP和實際效用的操作手冊。本書的結構仿效一門文學課程的安排,每章就是每週的授課內容,有各自的主題,包含用餐、妖魔、文學典故、天氣意象、暴力、政治、疾病等等,以多部作品為討論的範例,還安排了「期中報告」、「期末報告」和「隨堂測驗」的進度。舉例而言,第二章「你是我的座上賓:有觀聖餐裡的二三事」以亨利.菲爾丁的《湯姆.瓊斯》、瑞蒙.卡佛的《大教堂》、喬伊斯的短篇故事〈死者〉為範例,細膩地討論作品的措辭、敘述觀點和角色互動,用餐的場景如何映照出角色的情慾糾葛、內心衝突或道德兩難。作者也不忘連結到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我們跟誰、為了什麼目的與人共餐,是分享或圖謀不軌。綜觀全書,作者將他多年文學研究與教學經驗,透過風趣慧詰的口吻,設計出饒富戲劇性的情境與引導式的問題,與讀者進行隨興但具啟發性的討論,讓文學閱讀和詮釋變得友善可感。
本書在實質的層次上始於「追尋」(第一章的主題),在譬喻的層次上,全書為讀者開啟的也是一種追尋。為什麼需要像一個文學教授那樣閱讀文學?像和不像教授一樣閱讀文學有何差別?閱讀文學和其他類型的閱讀經驗又有何不同?諸如此類都是作者引導讀者不斷探究的問題。作者一開始就指出,普通讀者閱讀作品的時候大多關心情節、人物的身份和他們做了什麼,更會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故事情境和角色,並將作品類比到自己的生活經驗,隨之經歷喜怒哀樂的起落。文學教授的閱讀不需要也不可能排除情感的投射,但是他們還會關注作品的其他元素,能夠在不同作品之間建立連結,而不是停留在個人的、片段的閱讀。更重要的是,專業的受過訓練的文學閱讀能夠掌握「文學的方法」,也就是掌握作品的創作規則和上下文脈絡,形成對於作品整體發展的推測。小說、詩歌、戲劇各種文學類型有各自的方法,但仍然存在著某些跨文類的共同成規。也許專業與一般的閱讀差別就在於是否能掌握「文學的方法」,也是宏觀與個人、開放與狹隘的差別。「像教授一樣閱讀文學」意謂著深入仔細的分析與理解,需要耐心練習和經驗的累積。
當讀者累積了相當的閱讀經驗,漸漸掌握某些「文學的方法」,自然會在過程中經驗「好像在哪裡見過」的即視感,那也是作者借用加拿大文學評論家弗萊(Northrop Frye)說過的「文學從文學中再生文學」所要闡述的經驗。西方文學某些作品,包括《聖經》、希臘神話、莎士比亞戲劇和一些民間傳說與神話,成了其他作品持續引用的典故,儼然成為「文學原型」或作者說的「神話」,充分體現了「文學從文學中再生文學」這個概念。希臘神話裡乘著父親代達羅斯製造的羽翼飛上天而後墜落死亡的依卡洛斯成了十六世紀荷蘭畫家布勒哲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一五五八年畫作、二十世紀的奧登(W. H. Auden)與威廉.卡洛斯.威廉(William Carols William)詩作的題材。古羅馬詩人奧維德詩作《變形記》為後世的卡夫卡小說和諸多的科幻與恐怖文學裡的「變形」主題開啟先河。英國詩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和喬伊斯賦予荷馬史詩裡的尤里西斯(或稱奧狄修斯)現代文化與心理意涵。造物者對亞當與夏娃的安排則成為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的巨著《失樂園》(Paradise Lost)和瑪麗.雪萊的科幻恐怖經典《科學怪人》(Frankenstein)演繹的題材。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學原型或神話系統,而本書作者所界定的「神話」指的是成為後世作品反覆引用、進行對話或改寫的材料,持續發揮文化影響,為後世注入歷久彌新的力量,形成作者創作和讀者閱讀的座標、集體記憶和世界觀。《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這本書毫無疑問為讀者探索這樣文化資產開啟了一些路徑。
即便作者弗斯特表明他對當代法國文學理論——他並未指明是哪些,不過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是精神分析和後結構主義——沒什麼興趣,讀者不難在他的文學課發現一些理論議題的思辨,但是完全不像一般學術著作堆砌和展演炫奇的理論術語。有關文學典故的討論自然帶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那如同上述的「好像在哪裡見過」的即視感,不同作品之間的連結與迴音,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作者如何匯集、引用、改寫來自各種文化傳統的文本,或延伸,或反諷,或刻意扭曲,形成一個多音的意義系統。再者,我們也從弗斯特的文學課裡接觸到一些詮釋學和現象學的概念,了解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如何設定的「理想的讀者」,如何佈局和鋪陳讀者閱讀的線索,而讀者閱讀的活動無異於解碼的過程。我們也可以跟隨著作者,思辨經典如何牽涉到篩選與排除機制,也就是哪些作品被當作經典,哪些不被列入經典之流,都是十足的政治、種族或性別的議題。同時,作者也表達了他對於所謂的「政治文章」的反感,也就是為政治宣傳而寫的作品,但是他高度肯定「政治文學」(或者也可以說是「文學的政治性」),反映作品創作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現實。我們也從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的閱讀,思考包括瘟疫、梅毒、淋病、AIDS等疾病如何糾結著文化傳統、道德譴責和社會感受,從而連結到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隱喻》,甚至進一步帶入傅柯的瘋癲史或生命政治的探討。這些林林總總的理論種子留待對理論思辨有興趣的讀者繼續灌溉耕耘。
我相信讀者修習「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的過程中,能夠漸漸體會閱讀文學作品也是一種傾聽、思考和創造的過程。如作者弗斯特所言,「教授可以旁徵博引,擴大你的閱讀視野,而你也可以靠自修達到教授的境界」,這當然需要一點耐心演練和經驗累積,在一個無事的午後,一個靜謐的角落,一杯名為孤獨的茶,或在自己的房間。讀完這本書並不真的完成了什麼,而是另一個追尋的開始。讀者不妨(或者不必)依著作者提供的建議書單,規劃接下來的行程。作者弗斯特最後告訴讀者,「閱讀應該是一件快樂的事。大家都說文學是『作品』,但其實文學應該是一種『遊戲』。所以,開心的玩吧!」
所以,各位讀者,跟著這本書開心的玩吧!別忘記我們的生命總是伴隨著聽故事開始與成長,讓《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召喚你那純粹而真實的記憶,給予你追尋的動力吧!
序
前言.他是怎麼辦到的?
林卡爾?那個膽小鬼?
沒錯,就是林卡爾那個膽小鬼。不然你們以為惡魔長怎樣?全身通紅、頭上長角、腳上長蹄、背後還拖著一條尾巴?這樣騙得了誰?
我和課堂上的學生正在討論韓斯貝莉的《陽光下的乾葡萄》,這是美國戲劇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我隨口暗示劇中惡魔的化身就是林卡爾,全班立刻驚呼連連,一如往常般直嚷著「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陽光下的乾葡萄》劇情圍繞著楊華特一家人開展,楊家是非裔美國人,在芝加哥的白人社區置產,頭期款才剛繳清。林卡爾是一位唯唯諾諾的白人,個頭矮小,為人謙懦,白人社區委員會交給他一張支票,派他去跟楊家交涉,要他把楊家的房子買下來。時值楊父過世,楊家剛領到一大筆保險金,經濟上不虞匱乏,主角楊華特一口回絕林卡爾的提議;然而,過了不久,楊華特發現保險金不翼而飛,只剩下三分之一堪用;一夕之間,林卡爾那張令人難堪的支票,頓時成為楊家脫困的救贖。
跟惡魔打交道的故事在西方文化中源遠流長,其中又以《浮士德》傳說最為人所知;《浮士德》故事有各式各樣的版本,惡魔會提議用主角念茲在茲的物品(例如權力、知識、打敗洋基隊的快速球)來交換主角的靈魂;這樣的故事模式在西方文學中屢見不鮮,上至十六世紀克里斯多福.馬婁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劇》,十九世紀歌德的劇作《浮士德》,下至二十世紀史蒂芬.文生.班寧的短篇小說《黑夜煞星》,以及喬治.艾伯和道格拉斯.沃勒的音樂劇《失魂記》。在韓斯貝莉的劇作中,雖然林卡爾提議買下楊宅時並未向一家之主楊華特索求靈魂,但是事實上林卡爾就是在索求楊華特的靈魂,只是林氏本人不知道罷了。楊家的財務危機由楊華特一手造成,楊氏唯一脫困的辦法,就是承認自己不如那些排擠他的白人,承認自己的驕傲、自尊、人格都可以用金錢收買,這還不是出賣靈魂嗎?
韓斯貝莉的劇作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的浮士德傳說,在於楊華特最後成功抗拒撒旦的誘惑。其他浮士德故事的結局或喜或悲,取決於惡魔有無成功取得主角的靈魂。在韓斯貝莉的劇作中,楊華特雖然在心裡跟惡魔達成交易,但是在認清自我並且看清代價之後,終於及時拒絕林卡爾的提議。結尾的神來之筆縱然滿紙悽苦、飽蘸淚水,但是就戲劇架構而言,本劇算是以喜劇收場—楊家在看似淪落之前及時打住,保全了人格與自尊,楊華特也因為打倒心魔和惡魔(林卡爾),從而取得英雄般的崇高地位。
在課堂上意見交流的過程中,教授常常講到一半突然發現,自己的表情跟學生的不一樣:教授的臉上寫著:「什麼?你們看不出來?」學生的臉上則寫著:「看不出來啊,是你自己亂編的吧?」這下好了,雙方產生了溝通障礙。基本上,兩邊閱讀的教材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雙方分析文本的方法。外文系的同學或教授對於上述情況應該能心領神會:就在那瞬間,教授彷彿憑空捏造出一套說法,簡直像在變魔術似的,將文本分析的手法玩弄於股掌之間。
其實教授並非信口胡謅,也不是在玩弄技巧,只是因為閱讀經驗比較豐富,所以經年累月下來熟諳一套「閱讀語言」,而學生在這方面還處於牙牙學語的階段。我所謂的「閱讀語言」指的是「文學的文法」,這套文法自有一套成規和模式、規範和守則,一旦學會之後就能用來閱讀文學作品。語言的文法規定了每句話的用法和意涵,「閱讀語言」也是如此;「閱讀語言」的文法跟語言的文法一樣,或多或少都具有任意性。什麼叫作「任意性」?以「任意」這個詞為例,「任意」這兩個字原本沒有意義,然而大家在過去某個時間點約定成俗,將「任意」的含意確定下來,這個含意只有在中文中才成立,日本人或芬蘭人聽到「任意」,只會認為我們在胡言亂語。不只語言,藝術也具有任意性,例如製造景深的「透視技法」,在古代西方人的眼裡是繪圖的關鍵,這種看法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相當流行,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東西方藝術開始交流,西方人發現日本繪畫根本沒有景深的概念,日本的畫家和賞畫的大眾都不重視「透視技法」 ,也不認為缺乏景深會在構圖上會造成困擾。
同理,文學也自有一套文法,我想不用我說你也知道,就算你本來不知道,讀完上一段之後應該也猜得到。為什麼?因為文章有脈絡可尋,而你也懂得閱讀的技巧,例如知道作文規則、識得文章章法、預測下文脈絡。我在點出文章的主旨(文學的文法)之後,便開始東拉西扯什麼語言、藝術、音樂、馴狗……不管我扯得多遠,你在讀完兩、三個例子之後便識破我的技法,知道我遲早會利用這些例子來說明開篇主旨。看吧!果然我玩的就是這一套把戲,這下子皆大歡喜:作者運用作文規則,讀者識得作文規則;讀者進而遵循脈絡、預測下文,作者最後應驗讀者的推測,文章的高明之處豈不莫過於此?
言歸正傳,我剛剛插這一段話唐突了點,在這之前我提到文學也有一套文法。小說和故事有一套龐雜的規則,包括角色人物、情節推演、篇章結構、觀點限制;詩歌也有一套複雜的規範,包括形式、結構、節奏、押韻;而戲劇又另成體系。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跨文類的文學成規,譬如春天的意象舉世皆然,白雪、黑暗、睡眠的涵義放諸四海皆準,不論詩歌、戲劇或故事提到春天,我們自然就會天馬行空衍生出眾多有關春天的聯想,例如青春、新生、大好前程、初生的羔羊、跳躍的孩童……不勝枚舉;如果我們再往下推敲,這些聯想就會觸發更多抽象的想像,例如死而復生、汰舊換新、生生不息。
好吧,就當你說的都對,世界上真的有一套用來閱讀文學的成規,但是,我要怎麼做才能認識這些成規呢?
就跟那些登上卡內基音樂廳的演奏家一樣:勤加練習。
普通讀者欣賞作品時,都會聽話地將注意力集中在人物和情節發展上,關注的焦點不外乎這些角色是誰?做了什麼事?交上什麼好運?遭遇哪些厄運?他們的反應最初(甚至從頭到尾)表現在情緒上,隨著情節推演大喜大怒、或笑或哭、或喜或憂;換言之,讀者自然而然將感情投入到作品裡,我相信任何一位敲鍵盤或爬格子的作家,在將小說連同祈禱一起寄給出版社時,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這種感染力。然而,一位文學教授在捧讀小說時,雖然也會受到作品感染(狄更斯筆下的小妮爾死掉時,就連鐵漢也會落淚),但是他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小說的其他元素上,例如作者如何營造效果?這個角色在哪裡看過?這個情節好像似曾相識?但丁、喬叟、或者鄉村音樂詩人梅洛.海格,是不是說過類似的話?如果你能捫心自問以上問題、透過文學訓練來閱讀文本,你就能以全新的眼光來閱讀、理解文學,你的閱讀經驗也將因此趣味橫生、收穫更加豐碩。
記憶。象徵。模式。這三點就是文學教授有別於普通讀者的關鍵 。我們這些文學教授簡直像被詛咒一樣,記憶力一個比一個好。每次我拜讀一部新作,腦海裡的旋轉資料架就會默默轉動,找尋該作與他作之間的因果關連,心想這個角色我是不是在哪裡看過?這個主題似乎很眼熟?我想不這麼做都不行!我經常希望自己不要動用這種能力, 無奈大腦卻不聽使喚 。像有一次我去看克林.伊斯威特自導自演的《蒼白騎士》,才看不到半個小時,心裡就冒出一個聲音:懂了,這是艾倫.拉德當年演的《原野奇俠》。從那一刻起,艾倫的面孔就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害我根本無法專心看電影,大大妨礙我享受通俗娛樂的樂趣。
除了記憶力驚人,文學教授的閱讀和思考模式都離不開象徵,除非論點被推翻,否則無處不象徵。我們常常自問自答:這是不是隱喻?那是不是類比?這是在象徵什麼?主修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大學生及碩士生,心思通常都很敏銳,在看事物表象的同時,還能看出其象徵意涵。例如妖魔葛南斗既是中世紀史詩《貝爾武夫》裡面的怪獸,同時也象徵了:一、大自然對人類生存的威逼。(中世紀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經常遭受大自然的威脅。)二、需要高層次性靈才能克服的人性黑暗面。(主角貝爾武夫象徵的就是人類高尚的情操。)文學院的訓練就是在鼓勵學生多運用象徵的聯想力,這種聯想力會愈用愈敏銳,長久訓練下來,原本心思敏銳者當然就更加犀利。
文學教授還有另一項跟聯想力相關的專業閱讀能力—辨認模式。許多主修文學的學生在閱讀時除了能關照細節,還能看出細節背後的模式。辨認模式跟聯想一樣,都必須從故事中抽離,跳脫情節、故事、角色等干擾情緒的文學手法。長年的閱讀經驗告訴這些學生,書本和人生其實大同小異,都有一套模式可循。辨認模式的能力並非文學教授專擅,譬如優秀的技師在將你的愛車送電腦診斷之前,會先利用一套模式來診斷引擎哪裡出了問題:如果是這樣又那樣,就是這裡和那裡出了問題。文學作品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模式,如果你能一邊閱讀一邊抽離,或者在掩卷之後退一步觀看全局,你就能看到那些模式。小小孩學說話的時候總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一點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也要報告,然而,隨著年齡增長,他們開始學習掌握故事梗概,懂得捨去無關痛癢的細節,保留可以讓故事增色的細節。培養閱讀能力的過程也是這樣。初階讀者常常受困在枝微末節裡,例如閱讀俄國作家鮑里斯.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時,初階讀者常常被饒舌的俄國名搞得暈頭轉向,然而,油條的讀者則會迅速吸收細節,或者乾脆不管這些枝枝節節,直接找出故事情節底下的模式、規律和原型。
底下我舉個例子,讓我們看看象徵的聯想力、模式的辨識力和超強的記憶力,如何運用在非文學的領域。假設你正在研究一名男性受試者,他的言談舉止顯示出他對父親懷有敵意,但是對母親卻很依賴、很親近,而且明顯偏愛母親。好啦,就是一個男人而已,沒關係!可是,你卻在乙男子身上發現相同的情況,而且丙男子也是如此,丁男子也是如此……你開始懷疑這會不會是一種行為模式,因此喃喃自語道:「我是不是在哪裡看過類似的案例?」你利用超強的記憶力挖掘過去的經驗,但是你挖到的並非是以往的臨床經驗,而是一齣年少時讀過的戲劇,劇中的主人翁弒父娶母,儘管眼前的案例和戲劇毫無關連,但是你的象徵聯想力賦予你能力,讓你將當下的真實案例和之前的閱讀經驗串連在一起,而你巧妙的命名能力讓你馬上將這種行為模式命名為「伊底帕斯情結」。就像我說的,不是只有文學教授才具備這三種能力,基本上,佛洛依德「閱讀」病患的方法,和學者解讀文本的方式大同小異,他利用想像力來闡述、理解病例,正如我們藉由想像力來闡釋小說、戲劇和詩歌。佛氏將戀母情結和伊底帕斯王聯想在一起的瞬間,是人類思想史大躍進的里程碑,不論在文學界也好、心理分析學界也好,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我在以下章節書寫的內容,跟我在課堂上教授的內容大同小異,我想讓普羅大眾知道文學院的學生如何閱讀文本,並且將文學作品的規範和模式介紹給一般讀者。我不僅希望我的學生能認同我的觀點:沒錯,林卡爾就是魔鬼的化身,他跟楊華特之間的交易就是《浮士德》故事的原型;我更希望我的學生能夠自行得出以上結論。我知道他們一定辦得到,只是需要練習、耐心和適度的指導。同樣的道理,我相信你也辦得到。
目次
第一章 每趟旅程都是追尋(不過凡事總有例外)
第二章 你是我的座上賓:有關聖餐禮的二三事
第三章 你是我的俎上肉:有關吸血鬼的二三事
第四章 凡格局方正者,必為十四行詩
第五章 這個……我好像……在哪裡見過?
第六章 覺得怪怪的嗎?可能是典出莎士比亞喔
第七章 又覺得怪怪的嗎?這次可能典出聖經喔
第八章 糖果屋和糖果巫
第九章 這真是太希臘了
第十章 雨非雨,雪非雪
期中報告 作者真的是這個意思嗎?
第十一章 你以為暴力只會讓你受傷嗎?
第十二章 那是象徵嗎?
第十三章 政治,政治,談來談去都是政治
第十四章 是的,他也是基督的化身
第十五章 想像的翅膀
第十六章 談性不是性
第十七章 不談性才是性
第十八章 如果沒淹死,就是受洗成功
第十九章 讀書,地點很重要
第二十章 讀書,季節也很重要
期末報告 說一個故事
第二十一章 我很醜,我與眾不同
第二十二章 人瞎總是有原因的
第二十三章 心病不只是心病
第二十四章 疾病不一定是疾病
第二十五章 不要只用你的眼睛看
第二十六章 他是認真的嗎?談談反諷
第二十七章 隨堂測驗
後記
索引
推薦書單
書摘/試閱
糖果屋和糖果巫
「文學從文學中再生文學」,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輸你這個觀念;不過我對文學的定義很寬鬆,舉凡小說、戲劇、詩歌、歌劇、短篇故事、電視、電影、廣告,甚至看都沒看過、尚未發明的電子傳媒也包括在內。有了這個觀念,接下來我要你想像自己是一位作家,你想寫一個故事,而且你腦海中已經有初步構想,只是還需要從前人的作品中找尋靈感、擴充內容,這時候,請問你要向哪一部作品求助?
老實說,你能想到《魔鬼剋星》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不過,流行只是一時的,就算是一九八○年代紅遍半邊天的喜劇片,過了一百年之後還會有人記得嗎?機會不大。但是《魔鬼剋星》確實能引起同代的人共鳴。如果你想針對時下的熱門話題激起讀者廣大的迴響,當紅的電視劇和電影都是不錯的選擇,只是事過境遷,影響力畢竟有限。因此,我希望你可以朝比較經典的方向思考。說到「經典」,所謂的「文學經典」是一張大家假裝不存在的清單(注意,不存在的是清單,不是作品),但是大家都明白這張清單的影響力。哪些作品稱得上是經典作品?哪位作家算得上是經典作家?換句話說—現在大學生讀的是哪一位作家的經典名著?這些都是常常引起唇槍舌戰的議題。法國有權威的學術機構專門編列經典書目,但是美國可沒有,我們的經典書目常常是有實無名。在我當學生的時代,側身經典作家之流者以男性白種人居多,吳爾芙可謂萬綠叢中一點紅,是少數躋身大學殿堂的當代英國女作家;然而,現在女性作家出頭天,桃樂斯.理察森、旻娜.洛伊、史黛妃.史密斯 、伊笛絲.思特薇爾E等,都和吳爾芙齊名。隨著歲月遞嬗,所謂的「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也會逐流浮沉。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到原本引經據典的話題吧。
在這條「文學傳統」的長河中,你要向哪一位作家求助呢?荷馬嗎?我想現代人一看到這個名字,腦海裡第一個浮現的恐怕是《辛普森家庭》的一家之主—荷馬.辛普森吧。再說,這個時代還有人在讀《伊里亞德》嗎?住在密西根荷馬村的村民會讀荷馬嗎?住在俄亥俄州特洛伊鎮的鎮民關心特洛伊戰爭誰輸誰贏嗎?如果時光倒回到十八世紀,引用荷馬絕對妥當,雖然大多數人讀的版本都是英文譯本,很少人讀過希臘原文。然而,現在時代變了,如果你希望大家看懂你的典故,千萬不要拿荷馬當賭注。(不過也不能因為沒人認識荷馬就不引用荷馬,只是要有心理準備:能領會其中玄妙的讀者寥寥無幾。)那求助於莎士比亞總行了吧?畢竟說到引用典故,莎士比亞四百年來被引用的次數無人能出其右,至今仍遙遙領先。這種說法固然言之成理,只是如果你要求雅俗共賞,莎士比亞可能會引起一些讀者反感,覺得你這個作家太過於嚴肅;再說,莎士比亞名句就好比單身市場上的曠男怨女:好的都被挑光了。這麼說的話,引用二十世紀的作家總行了?譬如喬伊斯怎麼樣?絕對不行,喬伊斯太諱莫如深了。那艾略特呢?也不行,他自己的作品就是典故大全。現代人對於何謂經典,大家的看法莫衷一是,導致現代作家不知道讀者共同的文學記憶究竟為何。以前人讀的作品大多相去不遠,現在人讀過的作品卻天差地別。這教作家如何是好呢?有沒有哪些文學作品是現代讀者都熟悉的?而且可以讓作家可以從中用典、嘲倣的?
兒童文學。
沒錯!譬如《愛麗絲夢遊仙境》、《金銀島》、《納尼亞傳奇》、《柳林風聲》、《戴帽子的貓》、《月亮晚安》。美國讀者可能不認識薛洛克,但是一定知道蘇斯博士筆下的「凡是俺」。此外,童話故事也是人盡皆知,只不過前提必須是家喻戶曉的童話故事,如果是像一九二○年代被俄國形式主義學者視為稀世珍寶的斯拉夫童話,現在就算丟在肯塔基州帕杜卡市街頭可能都沒人認得。《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的運氣就好多了,多虧了迪士尼,前者從俄羅斯海參崴紅到美國喬治亞州,後者從愛爾蘭紅到美國加州。再者,引用童話的另一個優點,就是童話世界善惡分明、非黑即白,因此容易預測讀者的反應。相較於哈姆雷特對奧菲麗亞始亂終棄,奧菲麗亞的兄長為了替妹妹報仇,在劇終殺死哈姆雷特,這樣的情節使讀者心中五味雜陳,對作品沒有一個定論;然而,對於壞心的繼母、邪惡的小矮人,我們作何感想,大家心裡都有數。再說,誰不憧憬白馬王子?誰不希望眼淚具有神奇療效?
在眾多童話故事中,最受作家青睞的童話非《糖果屋》莫屬(至少在二十世紀末確是如此)。儘管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流行的童話,然而小孩迷路回不了家的故事跨越時空,廣受全球讀者喜愛。在焦慮的二十紀末,「盲信樂團」高唱《找不到回家的路》,在這《粗野少年族》的時代,在這迷失的一代,大家不喜歡《糖果屋》才怪。自從一九六○年代以降,《糖果屋》便以不同面貌出現在不同故事中。羅伯特.庫佛寫過短篇故事《薑餅屋》,其中的創新就是男主角不叫漢賽爾、女主角不叫葛萊德。作者利用我們對原著的了解,寫作時只點到為止,利用符碼來象徵我們熟悉的元素。從主角踏進糖果屋開始,到巫婆被活活燒死為止,當中的來龍去脈讀者一清二楚,所以庫佛索性省略不寫。在情節鋪展的過程中,作者使用換喻的手法,將巫婆轉化成黑色斗篷,讓讀者像用眼角餘光瞄到巫婆。(換喻是一種修辭手段,利用部分代替整體,譬如用「華府」作為美國政府表態的立場。)此外,巫婆沒有直接對孩子下手,而是殺掉吃麵包屑的鴿子。就某個層面而言,宰殺鴿子比殺害孩子更兇殘,因為這等於是在抹殺孩子對歸家之路的記憶。在《薑餅屋》的結尾,小男孩和小女孩走到一間薑餅屋前,看見一件黑色斗篷在微風中翻揚。作者藉此讓我們重新評估自己對《糖果屋》的理解,看看我們是否認為故事會照原本的劇情走下去。庫佛故意讓故事在進入高潮之前戛然而止,讓兩個孩子天真無邪地走入巫婆的地盤,強迫我們審視自己內心的焦慮、緊張和不安,思考這些情緒有多少是源自於對原著的了解。換句話說,他是在暗示我們:看吧,你對《糖果屋》的情節瞭若指掌,不用我來寫結局你也知道,這是引用童話的手法之一,除此之外,作家還可以用讀者熟悉的童話故事來作變調,譬如大肆改寫、顛覆童話世界,安潔拉.卡特的《血窟》就是一個例子;傳統童話多少帶有性別歧視的色彩,而卡特的這本童話選集收錄的是從女性主義視角顛覆的童話故事,包括《藍鬍子》、《穿長筒靴的貓》、《小紅帽》,作者故意讓我們對情節的發展期待落空,藉以彰顯原著故事裡的性別歧視,進而揭露整個西方文化對性別的歧視。
除上所述,賦予老故事新意涵的方式不勝枚舉。羅伯特.庫佛和安潔拉.卡特選擇聚焦在故事情節上,然而大多數的作家則是選擇打撈故事片段,用這些片段撐起全新的故事,不讓讀者把重點擺在《糖果屋》或《長髮公主》上。不如我們假設你是一位作家,現在你筆下有一男一女,他們不一定是小男孩和小女孩,也沒有人說他們是一對兄妹,更沒有人規定他們非得是木匠的孩子。這樣好了,你筆下的角色是一對年輕的戀人,不知道怎麼搞的,這對戀人莫名其妙迷了路,車子在離家很遠的地方拋錨,雖然附近沒有森林,但是卻有國宅林立的都市叢林。他們開著BMW的休旅車,心想八成是剛才開著開著拐錯了彎,才會來到這片窮鄉僻壤。換句話說,他們迷路了,而且身邊沒有手機,唯一的求助對象是一間毒梟寄居的廢棄屋。這則虛擬故事戲劇張力十足,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場景現代、沒有木匠、沒有麵包屑、也沒有薑餅屋。所以到底是為什麼要利用這些老掉牙的童話故事呢?在這麼現代的場景裡,童話元素有什麼意義?
這樣好了,我問你:在這則故事裡,你最想強調的是什麼?對你而言,這對戀人遭遇的困境最能引起你共鳴的地方在哪裡?答案可能是迷失感:小孩獨自離家,沒想到天外飛來橫禍。答案也有可能是誘惑:小孩對著糖果屋垂涎三尺,大人面對毒品魂不守舍。或者,答案也有可能是自力更生的孤獨,失去保護網的無助。
你可以根據你想要強調的部分借用不同的故事(例如《糖果屋》),同時凸顯出該故事跟你的故事之間相互呼應的地方。聽起來好像很難,但寫起來其實很簡單。例如你可以讓男主角心想:「早知道就先在地上留下一行麵包屑,我跟這一帶不熟,如果邊開車邊灑麵包屑,就算拐錯彎至少還能沿原路繞回去。」或者,你可以讓女主角暗自祈求,希望眼前的破屋不是巫婆設下的陷阱。
換言之,你不需要寫出全部的故事,這是作家的一大福音。你可以起個頭,蜻蜓點水似地帶過,無須一五一十地詳細敘述。有什麼不可以呢?又沒有人要你把故事從頭到尾說一遍。我們只是要取材自先前的故事(或說是「先行文本」,從教授的角度來思考,世上萬物都是文本),也許是利用當中的細節、也許是模仿情節發展的模式,藉此讓我們的故事更有質感、更有深度,或者帶出主題、製造反諷、顛覆讀者對故事根深蒂固的認知。用多用少取決在你。老實說,你只要稍微影射一下,馬上就能勾起讀者對整篇故事的記憶。
為什麼會這樣?首先,童話故事跟《聖經》、神話、莎士比亞等口傳故事或書寫故事一樣,都屬於人生這部大故事的一部分;二來,打從我們的爸媽說故事給我們聽開始(或是把我們塞在電視機前面開始),形形色色的童話故事就成了我們的精神糧食,只要你看過迪士尼的經典童話,這些童話元素就會成為你思想的一部份。說實話,一提到格林兄弟,要不想到華納兄弟都難。
這麼說來,不是還滿諷刺的嗎?
一點也沒錯!這就是引用先行文本最棒的地方。反諷的手法儘管千奇百怪,有時明顯,有時微妙,但都是推動小說和詩歌發展的動力。讓我們回到原來的話題吧:這對行徑可疑的戀人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在森林裡迷路的小孩,但是心理年齡可能相差不遠。他們在這一帶無親無故,可能跟迷途羔羊一樣犯了錯,因而深入險境、走上歧途。諷刺的是,無論是他們開的BMW名車、手上戴的勞力士名錶、身上穿的昂貴服飾、口袋裡的美元鈔票,這些權力的象徵非但派不上用場,甚至讓他們的處境更加危險。不管是對這兩個大人而言,還是對《糖果屋》裡的兩個小傢伙來說,避開巫婆和找到回家的路都不輕鬆。但是,這兩個大人不需要把巫婆推進烤箱,也不需要在地上灑麵包屑,更不需要把人家的牆板拆下來吃,而且離天真無邪的歲月更是遠之又遠。只要將非黑即白的童話世界和是非不分的現實世界兩相對照,諷刺意味立刻呼之欲出。
自從存在主義盛行以來,兒童迷失的故事紅透半邊天,羅伯特.庫佛、安潔拉.卡特、約翰.巴斯、提姆.歐布萊恩、路薏絲.厄瑞綺、童妮.摩里森、湯瑪斯.品瓊等人都引用過。不過,你不需要因為《糖果屋》紅極一時(或說是半世紀),就覺得不引用不行,沒有人規定你非得跟隨潮流不可,你還有其他選擇,例如《灰姑娘》就有她的舞台;此外,只要有壞皇后或狠心的繼母,《白雪公主》也有派上用場的時候,甚至《長髮公主》也有用武之地,就連搖滾天團傑.蓋爾樂團都把她編進歌詞裡。那白馬王子怎麼樣呢?可以,但是要禁得起比較,準備好諷刺的衝擊。
雖然我一直假裝你是作家,但其實你我心裡都明白:我們終究只是讀者。所以,要怎麼把這一套道理應用在閱讀裡呢?第一,你要改變看待文本的方式。當你好好坐下來欣賞一本小說,你會關注在角色、劇情、想法等尋常小事上;可是,如果你是教授,你就會開始找尋熟悉的身影,比如說:等等,這我好像在哪裡讀過,喔,是《愛麗絲夢遊仙境》!可是作者為什麼要在這裡用紅皇后的典故呢?等等,這好像是愛麗絲掉進地洞裡面的橋段耶?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為什麼?永遠要問自己:「為什麼?」
我是這樣想的:我們希望故事很新奇,但也希望故事很熟悉;我們都想讀一本從來沒讀過的小說,但是又希望新中有舊,讓我們可以從舊有的閱讀經驗中了解新的文本。如果一則故事能夠新舊共存,就能在故事的主旋律之外譜出和諧的弦外之音,從而帶出深度和厚度,引起更大的迴響和共鳴。這些弦外之音可能來自莎士比亞、但丁、米爾頓、《聖經》,但也可能來自平易近人的文學傳統。
所以,下次到附近書店買小說回家看的時候,別忘了順便複習一下《格林童話》。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