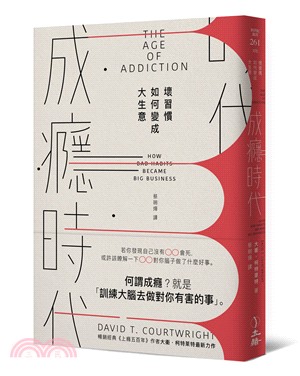成癮時代:壞習慣如何變成大生意
商品資訊
系列名:新世紀叢書
ISBN13:9789863601616
替代書名:The Age of Addiction: How Bad Habits Became Big Business
出版社:立緒文化
作者:大衛‧柯特萊特
譯者:蔡明燁
出版日:2020/09/11
裝訂/頁數:平裝/376頁
規格:23cm*15cm*2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上癮史」標竿著作,全球享樂革命的悠久歷史,
深入研究、高度可讀,最重要而豐富的擴充。
《上癮五百年》作者、美國北佛羅里達大學歷史學教授
大衛.柯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新書
來自一位著名的成癮專家,一個挑釁性的、獨特的權威歷史,講述了複雜的全球企業如何將人類大腦的獎勵中心作為目標,驅使我們上癮,從止痛藥到大麥克,到電玩遊戲到社群軟體,並帶來驚人的社會後果。
我們生活在一個成癮的時代,從強迫性的遊戲、購物到暴飲暴食和藥物濫用,我們能做些什麼,才能抵制那些陰險而刻意纏繞我們大腦的誘惑呢?作者大衛.柯特萊特說,除非我們了解創造和迎合我們壞習慣的全球企業的歷史和特點,否則一切都難以達成。
本書記錄了「邊緣資本主義」的勝利,這是一個不斷增長的競爭性企業網絡,其目標即是針對負責感情、動力和長期記憶的大腦。隨著全球貿易及跨國工業、複雜營銷,甚至在政府同謀和犯罪組織的幫助下,造就了對大腦的誘惑的型式變得廉價而成倍增長。
作者簡介
大衛.柯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
美國北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Florida)歷史學教授,著作包括《暴力之地:從邊境到內地城市的單身男人與社會失序》(Violent Land: Single Men and Social Disorder from the Frontier to the Inner City)、《黑暗樂園:美國鴉片毒癮的歷史》(Dark Paradise : A History of Opiate Addiction in America)等。
蔡明燁
高雄市人,台大圖書館系畢業後,曾任劇場導演、報社記者、電視編劇等職,並於英國里茲大學取得傳播學博士學位,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里茲大學任教多年,曾任歐洲台灣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祕書長(2012–2018),現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以及《台灣研究國際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總編輯。除個人中英文作品外,譯著包括《媒體與政治》(2001年,木棉出版)、《推銷台灣》(2003年,揚智文化)、《英國製造:國家如何維繫經濟命脈》(2017年,立緒出版)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名人推薦】
一本讓人難以釋卷、富可讀性的書籍,講述壞習慣變成了大生意……行文生動活潑,充滿幽默感,Courtwright撰寫了一段令人著迷的歷史,講述我們喜歡什麼以及為什麼喜歡它的經歷,從古代中東啤酒最早的風味,到西維吉尼亞的鴉片類藥物。
——Micah Meadowcroft
一段迷人的歷史,關於美國企業塑造了人們的習慣與慾望。
——Sean Illing,Vox網站
Courtwright的上癮系列不拘一格,令人欽佩,他豐富的知識……與所有上癮一樣,這本書提供了許多樂趣和回報。
——Lennard Davis,《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關於成癮的演變,一段全面、雄心勃勃的報導記述……這種大膽、發人深省的融合,將會吸引《槍炮、病菌與鋼鐵》傳統下的「大歷史」迷。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Courtwright具有開創性的藥物濫用史研究的重要擴充,這項對愉悅「武器化」加劇的研究(以及生物、社會和經濟誘因的過量刺激),對於任何想知道成癮如何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的人來說都是必讀的。深入研究,高度可讀性並清醒地提醒我們,我們對奴役的脆弱,被以解放的形式銷售。
——Deborah Rudacille,《The Riddle of Gender》作者
序
【自序】
前言
二○一○年某個夏日,我在給劍橋大學基督學院(Christ’s College, Cambridge)演講完之後,有個來自瑞典、名叫丹尼爾.伯格(Daniel Berg)的碩士班學生來找我。演講時,我曾不經意地提到網路上癮,伯格告訴我,我其實點出了一個比我想像中更巨大的事實。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 University)裡的許多男同學都已經輟學了,棲身在臨時住處,欲罷不能地玩著《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這些人說的英文行話多於瑞典文,永遠在突襲,永遠如此。
「他們對自己的情況有何感想呢?」我問。
「他們覺得很焦慮。」伯格說。
「但他們還繼續玩下去?」
「是,他們繼續玩下去。」
這種行為確實像是上癮,帶有強迫性,充滿懊悔地追求一種短暫的、對個人及社會有害的嗜好。瑞典男性在電玩遊戲上所付出的個人代價是最高的,誠如伯格所坦承:「在我們經濟史的碩士班裡,我現在是唯一的男生了。」
回到佛羅里達州,我發現數位娛樂對學業注意力的分散,比較沒有性別的區隔,例如在課堂上持智慧手機者,幾乎男女平等,不過當我跟學生們分享伯格告訴我的事時,他們馬上就能認出那一類型的人。有個學生自承,他因為強迫性電腦遊戲,喪失了一年的光陰,他也說自己正在復原當中——只不過從他的學業成績來判斷,恐怕仍岌岌可危。另外有個學生說,他認識的玩家會在電腦旁擺個罐子,這樣可以避免中斷遊戲去上廁所。
於是對我來說,電腦旁的罐子,成為「上癮」定義之改變的一種象徵。直到一九七○年代以前,「上癮」這個詞很少用在強迫性藥物使用外的情境,然而一九七○年代以後的四十年間,「癮」的概念卻已不斷擴大,許多回憶錄作者們都承認自己曾對博奕、性、購物,乃至碳水化合物的各種成癮。德國性治療師把網路色情稱為「誘導性毒品」(gateway drug),誘捕了無數的年輕人。《紐約時報》有篇社論指稱,糖是可以讓人上癮的,「就跟毒品一模一樣」。有位年輕的紐西蘭媽媽,每天要喝上十公升的可樂,牙齒都掉光了,最後當她死於心律不整時,上了頭條新聞。還有一名中國江蘇省的十九歲曠課生,為了治癒對網路的沉迷,砍斷自己的左手,因此見了報。據官方估計,中國有一四%像江蘇這名學生一樣的青少年,都面臨著類似的困境,從而設立了網路成癮康復營,南韓和日本也隨之跟進。台灣的立法委員通過提案,要對放任孩子超時上網的父母們處以罰款,並更新一條禁止未成年人抽菸、喝酒、吸毒、嚼食檳榔的法律條文。這些行為當中,除了最後一項可能對美國人沒有吸引力之外,在二○○○年代初期的每一年間,都有四七%的美國人,對其中至少一項行為或藥物呈現上癮或失調的現象。
通常他們會出現一項以上的徵兆。醫學研究人員發現,藥物和行為上癮的人都會出現雷同的自然病史,也就是說,他們的大腦會有相似的改變,相似的忍受模式,相似的渴求、嗜醉,以及退縮經驗。而且對於相似的性格失調與強迫症,他們也會顯示出相似的基因傾向。躁狂的賭徒和習慣在賭場夜夜買醉的人,差不多就是同一種人。精神病學聖經《心理失調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二○一三年的版本中,對於賭博失調與藥物上癮的描述文字,幾乎難以區分,編輯們將「網路遊戲失調」(internet gaming disorder)一詞列入觀察名單中,指認其為「有待進一步研究的病情」,同時在二○一八年,世界衛生組織(簡稱 WHO)也將「電玩失調」(gaming disorder)正式納入了新版《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之中。
但不是每個人都認同有關成癮的討論,臨床專家就極力避免這樣的字眼,擔心會讓病人受挫或污名化;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不過是缺乏自律的藉口;社會學家認為此一說法有如醫學帝國主義;哲學家嗅出了箇中的模稜兩可,認為用同一個詞彙形容不同的事物會有誤導之嫌。我樂於聆聽所有的批評,但在現階段,我還是選擇用「成癮」的字眼,因為這個詞彙提供了簡明有用、且一般都能理解的方式,來指涉一種強迫性的、有條件的、很容易再犯的、有害的行為模式。本書很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要解釋為什麼此一有害的行為模式,會隨著時間而變本加厲且多樣化起來。
首先,我們可以從對成癮的了解做個回顧。一個癮的形成,有如一趟旅途的開始,往往是不經意的,在消費的光譜中走向有害的終點。這個旅途的過程可能很快,可能很慢,也可能斷斷續續。偶爾的耽溺,即使是像海洛因這種毒品,並不一定都會導致成癮;一旦成癮了,成癮的狀態也不一定就是永久的。上癮的人可以戒掉,或者永遠戒掉,或者戒掉很長一段時間。並非所有的過量使用都必然導致上癮;有些人可能賭博賭得很多很大,但不一定就是強迫性賭徒,就像有些人可能吃得特別多,對體重計造成龐大負擔,但不表示他們就一定是食物成癮。但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經常性的、大量的使用,很容易逐漸導向成癮的結果,好比一個固定的飲酒者,當他對喝酒的慾望加強時,就很容易爆發成一個十足的酒鬼。上癮,就是一個習慣變成了一個很壞的習慣,對個人及他人都變成一種很強烈的、專注的、有害的行為模式。至於是什麼樣的傷害,則端視上癮的藥物及行為本身。強迫性賭徒可能毀了自己學業與婚姻的前景,然而,它們並不會損壞肝臟或肺臟。
上癮的過程是社會性的,也是生理性的。壓力跟同儕的行為,都有可能把一個人推向成癮的深淵,雖然這個過程最終都會顯現在他們的大腦裡面。經常喝酒、吸毒,以及有吸毒般效果的行徑,都會導致神經元的變化,包括改變基因的表現,日積月累,這些改變會出現在中樞神經系統較多且較大的區域,猶如幾滴染料在繃緊的床單上暈散開來。這種改變具有持久性,尤其是仍在發育中的大腦。兒童與青少年越早經驗到成癮物質或嗜好,就越可能保存此一行為所曾經帶給他們快感的強烈記憶,即使曾加以勒戒也難以消除。
成癮的本質——更確切地說,誘惑——對銷售習慣性產物的企業有很大的影響。他們需要鼓勵人們及早且經常消費。從前的酒吧老闆們便深知一個道理:好好招待小男孩,將來他們長大了,口袋裡的鈔票就會進到你的收銀機裡;他們喝得越多,你的利潤就越高。迄今為止,八○%的酒精飲品銷售,都是賣給二○%重度消費的顧客群,此一模式可適用於各種以大腦獎勵為目標的企業。超過一半以上的大麻,全進到了那些醒著時有一半以上時間都處於麻醉狀態者的肺裡和胃裡。無論是對大麻或對其他物質的上癮,格外容易在窮人、邊緣化群體,或基因脆弱者之間發展起來,它們是不平等、不公義,以及疾病的淵藪之一。然而成癮以及它們的前兆——重度消費——則始終是一系列全球化企業的利潤中心。
(未完)
目次
第一章 新興的樂趣
第二章 大眾娛樂
第三章 兼具解放性及奴役性的樂趣
第四章 反惡習的行動主義
第五章 支持惡習的行動主義
第六章 食物成癮
第七章 數位成癮
第八章 反過量
參考文獻
圖片出處
謝誌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新興的樂趣
樂趣、惡習,以及成癮的歷史是互有關聯的。隨著樂趣的種類與強度不斷提高,惡習與成癮也隨之增長。並不是說所有新的樂趣都是邪惡的、會使人上癮的——其實大多數都有益處,而且對社會具有建設性。然而,在樂趣不斷拉長的影子底下,惡習和成癮也就不停孳生。所以,追隨樂趣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擴展,是我們故事追本溯源的起點。
這是一個起步很緩慢,然後腳步加快的故事。樂趣的軌跡呈幾何圖形倍增:開始得極其緩慢且笨拙;從十七、十八世紀起加速;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時,其攀升已達令人頭暈目眩的境地。整個過程從數千年前就開始了,那時人類探索、培養、交換、混合,以及把他們在大自然裡找到的享受——例如甘蔗裡的糖——精緻化且商品化;同時人們也會創造、散布自然界裡找不到的逸趣,例如碰運氣的遊戲等。此外,人們還會創造新的環境,通常是不為人知的都市環境,在其中他們可以用很低的花費,冒社會制裁最少的危險,去享受各種新發現的娛樂。
新樂趣的變革,和所有的變革一樣,帶有幾分偶然性。發明娛樂和消遣的集體經驗,有時腳步會放慢,有時又會加快,不需要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不需要關閉英國劇院,不需要奧古斯特.艾斯科菲耶(Auguste Escoffier),也不需要蜜桃梅爾芭(Peach Melba),因為到頭來,變革是與個人無關的,一旦當它凝聚了足夠的動能時,就能克服行經道路上的一切阻攔,彷彿鬆動的巨石帶來的雪崩。
歷史學家將這種巨石稱為「外生因素」(exogenous causes),也就是說,它們的本質和力量,跟它們所帶動的樂趣之間是彼此獨立的。本章和下一章旨在從遙遠的過去,追溯到最近幾個世紀的工業與都市革命,來探討這些外生因素。雖然這些因素之間有很多時而衝突之處,但最後卻產生了共同的效果,將尋找新樂趣這種曾經是漸進的、附加的,且多半屬於偶然的過程,變成一種快速的、加乘的,且越來越蓄意營造的模式。
發現所帶來的樂趣
世界歷史包含了長時期遷徙帶來的分歧,以及相對上短得多的時間,是以貿易為基礎帶來的整合。人類學家和基因學家一直在爭辯,什麼時候智人(Homo sapiens)這個物種的幾個分支開始從非洲擴散出去;什麼時候抵達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像是歐亞、大洋洲和美洲;以及他們和相近於人類的物種——如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雜交到什麼程度。新的考古發現,包括比原先預期更早的、從非洲被掠奪出土的證據,都讓這些辯論持續暗流湧動,但有三點共識存在:第一、智人的遷徙已經衍生為一種至少長達五、六萬年的全球性離散;第二、數支採獵者,為了適應他們分布的新環境,造成現代人類歷經了不同的文化及生物演化;第三、這種全球性的遷徙,導致了非刻意、但卻碩大無比的動植物尋寶熱,既是為了實用性,也是為了追求愉悅感。
根據《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解釋,樂趣「是一種狀態或感知,受到感覺良好或渴望的經驗或期待誘發而來;一種快樂的滿足感或享受;喜悅、滿足;與痛苦相反。」流動的人類之所以能夠發現許多新的「喜悅」和「滿足」,來自於地球地質史的遺澤。盤古大陸(Panga e a)在將近兩億年前逐漸崩裂,讓植物群和動物群有充分的時間,隨著分離的陸塊漸行漸遠,並演化出不同的屬性。
其結果,是自然界的歡快來源令人眼花撩亂。蜜蜂(Apis mellifera)源自於亞洲,快速分布到非洲和歐洲,而當一群人類擴張到整個非洲,並進入亞洲和歐洲之際,他們狂熱地尋獵蜂蜜,在西班牙、南非和印度出土的岩壁畫裡,歌頌著這些冒險。但當遷移者們更向東去,進入美洲大陸之後,人們就不得不把蜜蜂置之腦後了:那些落腳於北美洲東部的人群,在糖楓的汁液裡找到了替代品;那些前進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則獲得了不同的獎勵:無刺銀蜂(Meliponinae)的群落,提供給他們蜂蜜與蜂蠟。
約在四萬五千至六萬五千年前,當第一批人類抵達澳洲時,他們也享受到無刺蜂帶來的好處,同時還大啖狩獵動物,這可能是澳洲最大型物種滅絕的原因之一。澳洲是地球上面積最小、最平坦、最乾燥、也最荒瘠的宜居大陸,相對缺少生物多樣性,這也意味著,這些人的子孫除了蜂蜜之外,必須接受相對較少的娛樂資源,唯一的例外是尼古丁。土著居民從嚼碎的土生菸葉裡提取出來,和木頭的灰燼混在一起。儘管他們是用火的專家,但他們很少燻葉子。歐洲的日記作者們,把這些人稱為「習慣性的咀嚼者」,很像東印度人嚼檳榔那樣。另外一群發現菸草的中石器時代人類是美洲印地安人,他們會嗅、吸,也會咀嚼這些菸葉植物。
菸草(Nicotiana)提供的是一種複雜的快感,包括幻覺和其他的中毒效果,另外,中美洲原生的好幾種曼陀羅花(Datura)也有相同的功效,還有迷幻草藥死藤水(yagé 或 ayahuasca),這是用亞馬遜盆地卡皮木(Banisteriopsis caapi)樹幹上的藤蔓所煎製的一種飲料。第一批美洲人,怎麼會對這種製造花俏幻覺的苦味植物感到津津有味,或許有點兒令人納悶,但他們的薩滿文化很珍視意識上的改變,認為這是一種與靈的世界交流,療癒身體與靈魂的方法,也是引導年輕人進入聖禮的重要途徑,因此各種令人不舒服的副作用,便都被賦予了良善的目的,比方說,在迷幻仙人掌(peyote)儀式中嘔吐,會被說成是為了淨化身體。
人們開始在傳說有關自己和宇宙的故事背景當中,體驗到新的樂趣。發明故事,並使這些故事流傳下去——現今被稱為「神話」、「社會結構」、「想像的真實」——是一個認知上的決定性突破,使人類的大群體合作及全球性擴張成為可能。這種擴張,加上後來的農業與工業革命,持續創造人們接觸新的精神活躍物質的機會,其效果如何,則是由社會學習來加以形塑。
美國心理學家提摩西.李瑞(Timothy Leary),與精神分析家諾曼.辛伯格(Norman Zinberg),給了這個學習過程一個說法,就是現在最熟知的:藥物、心態與背景。心態指的是使用者的性格與意圖;心態會影響用藥經驗的本質,用藥發生的具體環境和社會背景也會產生影響。雖然李瑞和辛伯格主要的興趣在於使用者對威力強大藥品的反應,如迷幻藥(LSD)及海洛因(heroin),但後來的研究顯示,他們提出的原則有更廣泛的適用性。住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由於新鮮的薄荷茶會帶給他們兒時回憶及家庭儀式的聯想,所以當他們聞到薄荷味時,神經顯現的反應通常會比沒有這種文化背景的非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更加強烈。飲酒者的經驗,無論是不是法國人,通常都取決於背景音樂,《布蘭詩歌》(Carmina Burana)能使一杯卡本內蘇維翁紅葡萄酒(cabernet sauvignon)顯得更強勁濃郁,但《胡桃鉗》(The Nutcracker)的「花之圓舞曲」(Waltz of the Flowers),卻會讓同樣的酒韻顯得微妙而細緻。昂貴的標籤能讓只值五美元的劣酒嚐起來美味不少,此效果在品酒者獎勵電路的核磁共振成像掃描裡,是可以被測量出來的。當參加晚宴的客人以為他們喝的是高級的納帕山谷(Napa)卡本內蘇維翁時,從他們的讚美詞裡也同樣聽得出來。
心態和背景對安慰劑效應有著重要的影響。熟悉的治療儀式,可以刺激病人的大腦釋放神經傳導物質,影響心情,促進免疫系統的反應。因為我們的大腦學會了預期,透過預期,可以激活腦內啡、內源性大麻素、多巴胺,以及其他神經傳導物質系統,這個過程並不需要藉由一種真正的實體,生化性地誘導歡愉或療癒效果。假設早期人類大腦的作用方式跟我們相類似,那麼早期的娛樂史,應該就是意味著和各種動植物的不期而遇,發現它們包含某種分子可以模仿,或者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
催情劑可以為我們提供簡易的示範。某些香料、食材、動物的部分軀體,長期以來便被人類認定能夠增強生殖能力、慾望,以及性功能。有些壯陽劑,例如印度《愛經》(Kama Sutra)裡極推崇的斯瓦揚古塔(swayamgupta)種子甜餅(書中說:「可以跟成千上萬名女子睡覺,到頭來,她們還會個個求饒。」),就會產生一種直接的生理作用。根據有關虎爪豆(Mucuna pruriens)的病例對照研究,斯瓦揚古塔種子的來源,呈現出對睪固酮與精子的機動性都有正面的功效。但是其他食物的壯陽屬性,則多半來自於建議作用,例如酪梨(Avocado),一般都是長成一對懸吊著,Ahuacatl 這個字,即阿茲特克人(Aztecs)所說的果子,也就是「睪丸」的意思,而酪梨橢圓形的厚重果實本身,也就足以讓人們將之當成壯陽藥那樣趨之若鶩了。陽剛氣十足的外型,增添了許多生物的吸引力,像獨角鯨(narwhal)的長牙、香蕉、蘆筍及人參等——人參是一種很常用的中藥,顧名思義,意指「(男)人的根本」。人參有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功效,一方面是它的形狀本身即充滿暗示性,二方面是它飽含植物性雌激素,能夠促進性慾和陰莖的血管舒張。
人參展現了暗示的力量,但無論多麼強大,也不會是人們特別喜歡某種物質或行為的唯一理由。生物構造也在其中扮演一角。當牽涉到填飽肚子的大事時,雖然我們可以學習去享受各式各樣栽種出來的食物,但我們偏愛甜味食物,卻是與生俱來的本能。物競天擇眷顧喜歡甜味食物的個體,因為在自然界裡,甜味食物營養高而毒性少。所有會吃植物的哺乳類動物都有相同的口味偏好,並非偶然;黑猩猩和人類甘冒激怒蜜蜂的危險,只為了取得蜂巢裡的蜂蜜,也是同樣的道理。
對新樂趣的追尋,受到生物線索的指引。無論受到何種社會目的與文化架構的包圍,能夠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產生愉悅、消除疼痛的植物,都更可能受到珍惜、培養及散布;如果效果越強,這個植物就越容易受到注意和喜愛。能被記住的快感(或痛感)的強度,尤其如果是發生在經驗的末端,在大腦做決定的天秤上,會比感受的持久度更具有分量。我們記住的總是樂趣的爆發,這乃是神經科學、行為經濟學、民族植物學,以及行為學的基本原則。動物也會對具有麻醉性的物質狼吞虎嚥,儘管沒有所謂的心態或背景來指導牠們。歷久不衰的「麥田圈」,一度曾讓塔斯馬尼亞(Tasmania)種植罌粟花的農人大感困惑,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只是自我麻醉的小袋鼠們不斷徘徊所留下的印記而已。
人類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各種新樂趣的來源。早期的歐洲人喜歡罌粟花可食用的種子、油脂,以及強力的生物鹼。美洲印地安人用菸草做藥和儀式,治療痙攣、小兒哭鬧、昆蟲與蛇的可可樹,學習製作巧克力——一種富含營養、帶有苦味的刺激性飲品。為了調和苦味,他們加入了木頭的灰燼、辣椒、香草和其他香料。做為皇帝的每日膳食,以及被犧牲受害者的最後一餐,巧克力變成他們文化裡的貴重物品,從而使可可豆被當成一種戰利品、地位的象徵,以及金錢來使用。然而,直到南北半球動植物發生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之前,除了美洲熱帶叢林以外,過去從沒有人能夠取得這種食品藥物資源。
早期的娛樂史,基本上有如巧克力史再加入一些區域性變異。甘蔗本來僅限於南亞和東南亞,因為富含蔗糖,注定成為巧克力最重要的添加物。還有人類狩獵的紅色原雞(red jungle fowl),後來被馴化成了家雞,土著食用牠們的肉和蛋,取牠們的骨頭來占卜、縫紉、紋身、製作樂器,甚至牠們的雄禽還會被用來鬥雞——一種古老的運動和賭博方式。可樂果(cola nut)曾經只生長於西非的森林裡,罌粟花只生於歐洲,大麻只在中亞,茶只在中國西南部,黑胡椒只在南亞,諸如此類。透過農業、文明和遠程貿易的發展,讓這些令人愉悅且有用的物質通行全球,而且經過數世紀的實驗、加工提煉、混合和製造,讓這些物質比當初好奇的人類移民第一次試嚐的時候,有了更加令人滿足的回報。
栽種所帶來的樂趣
在分散的自然樂趣法則之外,有個例外,那就是乙醇,即酒精裡的食品藥物分子。任何一個有成熟的、碰傷的果實之處,就有酒精。酵母菌在空氣中自然飄浮,落在果子上,透過果糖的無氧發酵,就產生了酒精。正如馮內果(Kurt Vonnegut)所辛辣指出的,酒精是酵母的糞便,濃度很高的時候,毒性可以強到殺死原先製造酒精的酵母本身。
發酵中的果實會吸引各式各樣的動物,小至果蠅,大至麋鹿。演化生物學家長久以來都很困惑,為什麼動物會去吃讓牠們生病、思路混淆、舉止笨拙的東西,儘管這個東西也會帶來卡路里、營養和歡愉。由於生病、思路混淆,以及舉止笨拙這三件事,會導致體能降低,按理說,演化原則應該會反對食用酒精的選項才是。
最可能的一個解釋,應該是毒物興奮效應(hormesis)——在酒精和藥物史當中,或者更廣泛地說,在樂趣、惡習和成癮的歷史中,這個生物原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基本概念非常簡單:許多化學合成物,量少時都是有營養或有益處的,一旦過量就變成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很多行為亦復如是,例如博奕,偶一為之是無傷大雅的消遣,但變成習慣性後,就完全是兩回事了。)著名記者戴維.卡爾(David Carr)曾現身說法,解釋酒精毒物興奮效應的後果:「經常喝很多酒,你的內臟會膨脹起來,讓你看起來像個有腿的梨子,如果不是器官衰竭要了你的命,就是你的食道出血,或可能來個沒腦子的一摔,昏過去,臉部朝地栽下,永遠倒地不起。」
卡爾或其他任何酒醉者臉部朝地栽下去的可能性,部分取決於酒精的可取得性,而對於所有會因劑量加大而提高危險性的娛樂物質,這是一個普遍的法則。生物人類學家威廉.麥格魯(William McGrew)指出,毒物興奮效應用來解釋酒精之於酗酒的情況,也可適用於過多鹽分之於高血壓,過多糖分之於糖尿病,或者飽和脂肪之於心血管疾病。「上述這些例子,」麥格魯說:「都是自然界稀有的物質,在不自然的條件之下,變得很容易取得,它們通常都是動植物因農業馴化過程或是工業技術的副產品。人類會開始過量攝取乙醇,是因為我們已經變成了啤酒釀酒人、葡萄酒釀製商,以及烈酒釀造廠了。可以說,原始人類基於文化演化,將我們從葡萄酒帶到了啤酒,然後又帶到了烈酒。」
但也有可能得反過來說——是我們對飲酒的追求,刺激了文化的演進。人類學家始終在爭辯,馴化動植物的零碎過程,早在一萬一千年前就開始了,那麼造成新石器轉型(Neolithic Transition)的真正原因,究竟何在?追根結柢,爭論的焦點在於促動發明的源頭,到底是為了方便?還是為了需求?有些學者強調誘因,例如更大的食物保障,以及給採獵者們更多的便利等,畢竟採獵者為了尋找野生食物,足跡必須踏遍各處採集;另外有些人則著重在推進的因素,例如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以及氣候的日漸惡化。不過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自一九五三年起開始辯論,也就是人類栽種穀類作物,相對上比較少是用來做成澱粉類食物(穀粒、粥和麵包),而更多是用來釀製啤酒,一種富有營養、令人陶醉、無菌的飲料。草類——如大麥——種子裡的碳水化合物,透過浸泡、萌芽、再乾燥的過程,就能被轉化成一種酵母可消化的麥芽糖,而農業便是確保全年都有麥芽可供釀酒的方式之一——有人更認為這是唯一方式。馴化酵母可能也是為了相同的理由。DNA 分析顯示,馴化酵母的菌株和馴化穀粒的菌株一樣古老。
(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