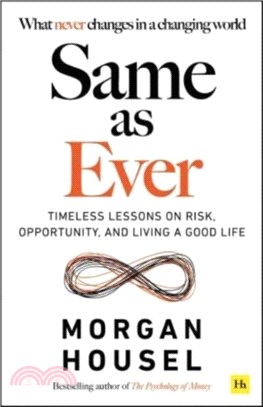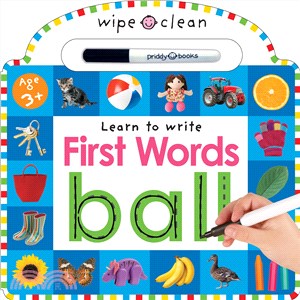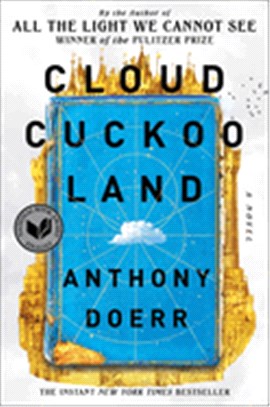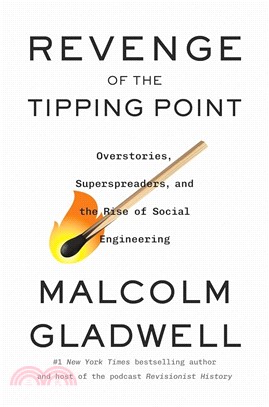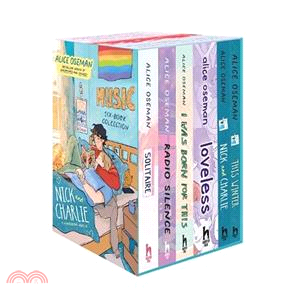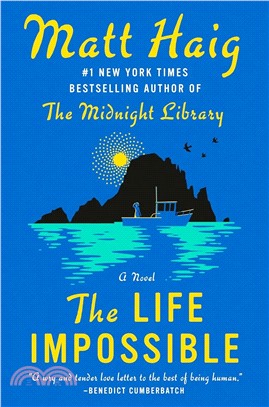商品簡介
▍中研院士王德威稱:「欲知戲的魅力能有多大?請自王安祈始。」
王安祈何許人也?雖非舞臺上頂著明星光環的演員,戲曲圈內卻應無人不識其名,她是打造國光劇團全新劇藝品牌的幕後重要推手,國光劇團的藝術總監,同時也是國內知名教授、劇作家、劇評家、資深戲曲學者;然而在這種種頭銜之中,如若要王安祈自我陳述,她會說:「戲迷,是我唯一的身分。」
▍一切都從「愛戲」的一片癡心開始。
打從娘胎即開始聽戲的王安祈,自幼著迷於戲曲,在她聽遍名角絕唱、看遍經典老戲之餘,這些一再搬演的劇碼漸漸無法滿足她對戲的深層渴望,且隨著時代改變,老觀眾凋零,而年輕人不再以戲曲為日常娛樂,傳統戲曲無疑面臨了難以傳承維繫的危機。如何讓戲曲與當代接軌?傳統之中是否有創新的可能?
正因王安祈是如此的熱愛傳統京劇,她更不忍視其悄然湮沒在時代長河裡,王安祈以戲曲為終身志業,二○○二年起接掌國光劇團藝術總監,致力推動戲曲現代化及文學化。國光劇團創團於一九九五年,於今已走過二十五載,抱持著對培養新生代與傳承技藝的使命,在劇藝的耕耘與開闢上,無不卯足全力。
本書詳細記錄王安祈如何從一個戲迷成為編劇,再成為國光藝術總監,她以怎樣的理念打造出國光新編劇的嶄新面貌,由外而內的挖掘角色人物的人性與情感,也由內而外的將其文學理念透過戲曲傳遞給觀眾。在不同的創作階段中,傳統與創新兩股力量互有拉扯,更有融合與交會的精彩火花。
作者簡介
第九屆國家文藝獎得主。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1985),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退休(2019),現為臺灣大學名譽教授。學術研究獲國科會傑出獎、臺大胡適學術講座等榮譽。2002年起任國光劇團藝術總監,規劃《王熙鳳》,新編《王有道休妻》、《三個人兒兩盞燈》等。新編劇本曾獲新聞局金鼎獎、教育部文藝獎、編劇學會魁星獎、文藝金像獎(連獲四屆),金曲獎最佳作詞獎,1988年因編劇榮獲十大傑出女青年,2005年獲國家文藝獎。2019年獲第卅屆傳藝金曲獎特別獎。
作者/王照璵
生於台南,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碩士班時在王安祈老師的影響下,一頭栽進繽紛的戲曲世界,自此戲曲成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喜愛品味戲曲演出中:伶人、故事、聲腔,交疊映照出的人生況味。碩士論文《清代中後期北京「品優」文化研究》,博士論文《近現代「京劇捧角」文化研究》。
作者/李銘偉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博士候選人。曾任無垢舞蹈劇場資深舞者、臺灣大學「白先勇崑曲之美講座」專任助理、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兼任講師。著有《崑劇表演方法研究:論「演員身體」的構成元素與角色創造上的運用》。
序
情之所鍾,唯戲而已
王德威
(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王安祈教授是當代兩岸戲曲界的靈魂人物之一,她的編劇才華、劇場思维、以及戲劇素養有目共睹;近二十年來更與國光劇團合作,兼顧守成與創新,成果豐碩。未來的戲曲史必有她與國光團隊共創劇藝新美學的一席位置。
王安祈得天獨厚,五歲開始接觸戲曲,對京劇情有獨鍾。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臺灣迎向新潮,西方影音風靡一時。王安祈卻出入傳統舞臺,生旦淨丑、西皮二黃,樂此不疲;二十五歲即擔任三軍劇團競演評審,引來菊壇大老、甚至青衣祭酒顧正秋的矚目。與此同時,她進入研究所,專攻戲曲博士。八十年代以來,王安祈不僅參與軍中劇團的劇本改編或創作,也廁身民間劇團的實驗。雅音小集、當代傳奇劇場、盛蘭劇團等好戲都能見到她的身影。
二○○二年,王安祈加盟國光劇團擔任藝術總監。由學者跨行戲劇工作,這是她個人以及國光傳奇的開始。她的挑戰來自三方面:如何將個人願景灌注於團隊實際演出製作;如何促進傳統舞臺和現代劇場對話;如何詮釋京劇在臺灣落地生根的意義。
京劇遲至十八世紀末始具規模,二十世紀初成為最受歡迎的劇種。譚鑫培之後,余叔岩、梅蘭芳等名角相繼崛起。與此同時文人學者介入菊壇,或協助名伶精進劇藝,或藉由京劇啟蒙大眾。前者的例子首推齊如山與梅蘭芳合作,將梅推向伶界大王的地位;後者則見諸田漢、歐陽予倩等改編創新的成果。無論如何,民國時期的京劇界仍然集中在名角的個人魅力上,劇本為名角量身定制,劇團功能在於眾星拱月。
一九四九年後這樣的生態發生質變。在大陸,私人劇團歸屬國有,從編劇、製作到演出層層組織。儘管政策時鬆時緊,再大的角兒也必須奉「人民的名義」行事。文革樣板戲一網打盡多少菁英,集體為革命高誦讚歌。文人如汪曾祺、吳祖光都曾役於其中。時至今日,劇團作為「單位」,仍然與有形無形的政治角力,創新轉型談何容易?
臺灣京劇的發展也曾經歷一段相似處境。一九四九年,顧正秋率領「顧劇團」來臺,在臺北大稻埕演出將近五年時間,為京劇在臺灣打下基礎。五十年代三軍劇團成立,一方面娛樂渡海而來的數十萬官兵,一方面也搬演「國劇」南渡的好戲。然而時移事往,軍中劇團到了八十年代疲態畢露,市場日益多元,導致觀眾流失。郭小莊的雅音小集、吳興國的當代傳奇此時崛起,標誌著京劇求新求變的努力。
王安祈其生也晚,沒有趕上當年北平、上海名角如雲的黃金時代;但她又何其有幸,在臺灣見證了京劇海外別傳的風雲變幻。京劇到臺灣的人才有限,軍中劇團的政戰包袱難以祛除,但臺灣沒有像大躍進、文革這樣的浩劫,畢竟延續了一脈薪火。當王安祈出入臺北中山堂、國軍活動中心的時代,對岸的同齡人正在《紅燈記》、《沙家浜》旋律中上山下鄉。是在梅尚程荀、余高譚馬傳唱聲中,王安祈一路從寶島四大鬚生聽到徐露、劉玉麟、陳元正、郭小莊等,也開啟她的創作事業。
新世紀初王安祈加入國光,為兩岸京劇生態帶來又一次轉折。眾所周知,國光為三軍劇團解散後的重新編制,是臺灣唯一國家級劇團。但國光創團即面臨定位挑戰。島上政治文化急劇轉變,本土意識甚囂塵上,京劇有了必也正名乎的尷尬。與此同時,強調原汁原味的大陸京劇開始光臨寶島,為臺灣京劇帶來衝擊。
這些衝擊卻為王安祈創造了契機。齊如山與梅蘭芳那樣的捧角時代早已過去,專業劇場興起,任何名角都難以單打獨鬥;另一方面,軍中劇團的管理和演出模式已然鬆動,就算骨子老戲也必須脫胎換骨。臺灣國光雖脫胎於三軍劇團,接受國家資源挹注,卻在種種政治轉型、文化維新的誘因下,有了難得的可塑性。
一切只等待一位能「借東風」的藝術總監融合新舊,創造臺灣京劇品牌。問題是,如何求變求新?早期國光曾積極配合社會脈動,走向民間。「臺灣三部曲」之《媽祖》、《鄭成功與臺灣》及《廖添丁》是為一例。這類演出汲取臺灣本土題材,培養在地觀衆的親和力;不必諱言的是,也有贖回京劇「原罪」的動機。但在政治正確的壓力下,編導演事倍功半,成果與三軍劇團時代的愛國競賽劇目不相上下。
王安祈提出「新世紀,新京劇」的思維。從整編劇本、唱腔、到重構劇場美學,調整觀衆層次,培養演出團隊默契,甚至提升行銷策略,展開全方位挑戰。歸根結底,一切始於劇本的打造。所謂劇本,不應只是敷衍故事、編腔譜曲的腳本,而是一個創造意念的發想,一種表演形式的預設,更重要的,是劇作者和劇團的理想——甚至情感結構——的宣言。
王安祈近年所編寫、改寫、合作或構思的新戯不再斤斤計較忠孝節義的題材,轉而發掘廣義人生的複雜層面,出入古今,頗能引發共鳴。《天地一秀才——閻羅夢》大膽穿越時空、挑戰正義論述,《三個人兒兩盞燈》串聯家國歷史和幽幽情欲,《胡雪巖》反思個人命運與政治鬥爭,都是野心之作。至於《王熙鳳大鬧寧國府》的喧囂與淚水、《金鎖記》的華麗與蒼涼,更是雅俗共賞,成爲國光的招牌好戲。
除此,國光的小劇場《王有道休妻》、《青塚前的對話》,還有與國家交響樂團合作的《快雪時晴》、與國外導演合作的《歐蘭朵》、靈感來自《聊齋》和日本漫畫的《狐仙故事》以及近似清唱劇的《孟小冬》,在在顯示編導演各方越界甚至跨國的勇氣。這類實驗當然有其風險,但絕對是刺激劇團活力的要素。
國光的實驗當然招來不少評者側目,王安祈自有回應之道。京劇其實是近代劇種,源頭駁雜;十八世紀末徽班進京供奉朝廷,因緣機會,促成了京劇興起。自此之後,京劇的演進與改變未嘗稍息。京劇成爲「國粹」則是齊如山等二十世紀的發明。内行人都知道,京劇的聲腔集合了高腔、徽戯、漢調等源頭,所謂的西皮二黃都來自北京以外。二十世紀四大名旦或四大鬚生的唱腔和舞臺風格形成,或從連臺本戲、時裝戯、海派戲、樣板戲的劇場試驗,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臺灣自創品牌,良有以也。
好事者每以大陸京劇為正宗法乳,相形之下,臺灣京劇似乎只是衍生,是擬仿。殊不知大陸京劇歷經卅年動亂,千瘡百孔,何嘗不歷經重重修補改造?臺灣京劇從無到有,又何嘗沒有推陳出新的發明?京劇原本就是兼容並蓄的劇種,落地之後如何生根才是有意義的話題。所謂「正宗」,不妨各表一枝。更重要的是,無論創新守成,編導演是否能夠表露——或者演出——真情實意,才是意義所在。這大約是王安祈對國光劇團最大的抱負了。
※ ※ ※
初識王安祈教授者對她的印象應該是望之「嫣」然,即之也溫,彷彿傳統女性美德化身。但正如國光第一任藝術總監貢敏先生所謂,溫良恭儉之下,王安祈不乏「搞怪」的能量。的確,綜觀國光近二十年的劇目,不論老戲新戲,在在可見她以柔克剛、當仁不讓之處。她與國光劇團聯手打造的劇藝新美學可就以下相互關聯的四點說明:
經典回眸。王安祈是古典的:「我心底最關切的一塊,是京劇傳統老戲。京胡一響,便能觸動我心底最柔軟的一塊。」她浸潤戲曲多年,傳統早成為教養的一部分。但她明白,當代京劇工作者的挑戰不在簡單的維護或放棄傳統,而是體認這一傳統所内蘊的範式規矩以及求新求變的能量,從來就是張力所在。只有正視並且善用這一張力,才能夠激發京劇的創造性轉變。
王安祈的嘗試始於傳統劇本改編,曾迎來不少挑戰。上世紀八十年代她為陸光劇團編修《陸文龍》劇本,為情節和人物動機作合理性改動,曾引起著名鬚生周正榮先生抵制。之後她對名劇《御碑亭》性別位置重作思考,寫出《王有道休妻》,甚至驚動了顧正秋女士。她與兩位菊壇前輩的對話未必只關乎唱腔情節而已,更及於審美範式的移轉。如王安祈所見,以往名伶一段唱腔、一個身段千錘百煉,已足以引起觀眾共鳴。但京劇融為當代表演藝術選項後,觀眾對演出自然產生多元、有機的要求。
面對經典,王安祈一方面強調「溫故知新」, 一方面進行「托古改制」。國光既是傳統戲曲的重鎮,對老戲的演出整編責無旁貸。《四進士》、《四郎探母》、《三堂會審》、《法門寺》、《慶頂珠》等戲不在話下,失傳劇作如《九更天》經過重新修訂後以《未央天》登場,叫好叫座。除此,各種老戲以主題式的串聯重新包裝,每每讓人耳目一新。像以「鬼」、「瘋」,或以「青龍」、「白虎」星座相爭為題的系列公演,都讓新觀衆眼睛一亮,老戲迷會心一笑。二○○六年的「禁戲匯演」、二○○七年的「司法萬歲」與當時環境作出微妙對話,戯裏戯外的互動發揮得淋漓盡致。
抒情凝視。王安祈來自學院,文學根底深厚,她為國光新美學的定位就是人文情懷,抒情向度。傳統京劇的精華也來自臺上臺下的審美交流,但這套模式局限在一、二精彩演唱段或身段、名伶與戲迷心領神會的剎那上。當京劇已經不再是人人哼之唱之的旋律,如此情景交融的可能勢必打了折扣。王安祈追求整體的舞臺藝術,不只演唱,更是性格塑造、結構布局、情節邏輯、節奏掌握、舞臺調度。因此:「抒情應該和戲是緊密扣合、相互推動,情節衝突關鍵應是抒情表演重點」。
王安祈企圖從劇本構思以及唱詞唱腔設計裡提升演出意境——所有演出者,而非一二名角,自覺進入這一意境,從而召喚觀眾一起「入夢」。正所謂「因戲生情,因情入夢。」相對於程式化的腳色行當,她發掘人物、情景的抒情韻味,甚至内心幽微層次。從《三個人兒兩盞燈》到《金鎖記》都是叫好叫座的戯碼。前者想像宮闈之內的女性情慾流轉的可能,甚至及於同性;後者演繹傳統壓力下的女性,走投無路而變態瘋狂。這些都是以往戲曲不可思議的題材,一經國光演出,竟引來無數迴響:「人間多少難言事,但求戲場一點真。」
國光「内向凝視」的風格以往偏向紅顔金粉,難免遮蔽京劇的豐富性。近年王安祈與編劇林建華轉向陽剛歷史,挖掘靈感。《孝莊與多爾袞》、《康熙與鰲拜》、《夢紅樓.乾隆與和珅》演出英雄與時勢的博弈,動人心魄。劇中人即使大開大闔,仍有「内向凝視」的時刻。不論蓋世君王如康熙、乾隆,或位極人臣的鰲拜、和珅、多爾袞,在詭譎的鬥爭之際,陡然發覺身不由己的蒼涼,而有了史詩般的興歎。
跨界實驗。與彼岸京劇相比,國光新戯不僅顯現強烈的人文訴求與抒情特質,也勇於跨界實驗。最特殊的例子包括與美國劇場大師羅勃威爾森(Robert Wilson)合作的《歐蘭朵》(Orlando)、與日本橫濱能樂堂合作的《繡襦夢》。前者取材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同名經典,後者源自唐代傳奇《李娃傳》與日本能劇《松風》、《汐汲》;前者將梅派名旦魏海敏推向反表演的表演,後者則讓京崑小生溫宇航在崑笛、三味線合奏聲中,和能劇偶踊共舞於一臺。這些實驗當然都只能偶一為之,卻顛覆了傳統戲曲自成一家的局限。
國光真正精彩的越界實驗來自對古典資源的活學活用。《青冢前的對話》改寫老戲《文姬歸漢》,讓王昭君、蔡文姬跨越時空對話;《閻羅夢》讓書生進入歷史輪迴,方生方死;《快雪時晴》以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入戲,演繹出千年以來書法與人生的離散;《十八羅漢圖》則探討書畫真僞之辨,遐想情與物、真與幻的翻轉。《定風波》、《天上人間 李後主》分別以蘇軾的詩詞,李後主的詞曲烘托詩人、詞人的生命;《夢紅樓》甚至將古典小說「聖經」《紅樓夢》與盛清宮廷秘史糅合為一。
對國光團隊而言,所謂「越界」,不再是東西藝術、文學交相爨演的橋段,而必須深入媒介流轉最隱微的層次。《快雪時晴》搬演王羲之墨寶如何經過一千六百年時空洗禮,落籍臺灣的經過。 編導利用劇場時空轉換的元素,想像《快雪時晴帖》在東晉、大唐、南宋、大清、「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不同命運。如果《快雪時晴》中王羲之書法只作爲一個超越的藝術聖品存在,《十八羅漢圖》裏的古畫卻是一件真僞難辨的神秘古物,在劇中經歷了修補僞造、鑑定交易,彷彿所有經手的人物,都為這張畫添加了層層人間色彩。
《夢紅樓》更藉曹雪芹小説銘刻禁忌,以及禁忌的本源——欲望。就戲論戲,《夢紅樓》必須在舞臺上呈現戲劇化張力,而非僅作爲人物投射或對話的文本。「看」書就是「看」戯。編導藉著京劇舞臺固有的抽象美學,加上現代劇場重組或切割時空的各種設計,讓乾隆與和珅「遇見」紅樓夢各色人物,甚至有了互動對話。這一穿越式的演出構想,回應了國光早期的《閻羅夢》,而效果尤有過之。
戲劇反思。王安祈與國光所有的創新實驗導向一個大哉問:什麼是戲,什麼是戲曲,什麼是臺灣的國光戲曲?這類反射性的話題在世界戲劇史上其來有自,現代及後現代劇場尤其常見。王安祈將其置於特定的京崑傳統和臺灣時空中,因此有了特別意義。而她所在意的不僅是歷史性的回顧,更是知識性的叩問。
從二○一○年到一三年,國光推出「伶人三部曲」系列,《孟小冬》(二○一○)、《百年戲樓》(二○一一)、《水袖與胭脂》(二○一三)。《孟小冬》演的是傳奇余派坤生孟小冬一生的藝術追尋,《百年戲樓》演的是京劇從民初到文革之後的三代滄桑;《水袖與胭脂》演的是梨園國烏托邦裡,各個角色對自己託身行當的終極對話。這三齣戲各以人、史、戲為軸線,為觀眾訴說戲曲身世,堪稱國光「京劇新美學」代表作。
三齣戲中以《百年戲樓》最易引起觀眾興趣。不但劇中人物似有所本,所穿插的唱段也多為戲迷耳熟能詳的經典。《水袖與胭脂》遙擬戲曲祖師爺唐明皇的前世今生,以及作為行當的生旦淨末丑的現身說法。他們一旦進入角色和劇情,演出愛恨癡嗔,觀照性別、情愛、歷史、以及劇場本身的局限和超越。這兩齣戲都有戲中串戲的妙趣,也大量借重現代劇場媒介,演員輪番上陣,忽真忽幻,極盡視聽之娛。
但王安祈同時叩問,有沒有一種最純粹的戲?《孟小冬》是一齣探討京劇本質的京劇。王安祈不刻意訴諸任何前衛理論,但藉著「冬皇」一生和「聲音」的糾纏,她的劇本已經有了後設的向度。此劇基本以清唱劇形式呈現,舞臺以樂團為背景,以聲腔樂曲的轉換串聯時間和人事的起伏。演員雖然彩妝登場,但理想上並不全身投入,「重現」某一情景,而是保持微妙的心理和時間距離,詮釋當事人的心路歷程。如此出虛入實的表演法貌似時髦,其實暗合京劇表演美學的原理。
王安祈和國光對「戲」的反思以《關公在劇場》達到巔峰。關公戲在梨園有獨特傳統,甚至攸關舞臺儀式的神聖性,輕易不得撼動。王安祈與香港「進念‧二十面體」合作,將以往的重要折子戲如《走麥城》、《青石山》等融會貫通,重新演繹武聖悲壯的生命高潮。演出充滿前衛元素,但核心部分卻回到京劇——甚至戲劇——最古老的源頭。所謂 「戲中有祭、祭中有戲」,表演與儀式相互滲透,在在令人震撼。鬚生唐文華在戲中使出渾身解數,有了突破性表現。大陸知名導演田沁鑫、編劇陳亞先在二○○九年也曾在上海製作《關聖》,演出效果差強人意。古典與現代如何對話,高下立判。
王安祈與國光攜手二十年,臺灣京劇面貌迥然一新,成為彼岸不能忽視的表演團體。自顧正秋劇團渡海而來,七十年倏然已過,國光「劇藝新美學」隱隱成為主流。這一美學是由團隊所共同創造。文化主體,有容乃大,除王安祈外,導演從李小平到戴君芳等,演員從魏海敏、唐文華、到溫宇航以及青年新秀,琴師從李超到馬蘭等,編劇如林建華等,還有無數幕後工作人員,他們來自兩岸,來自傳統與現代劇場,各盡其力,各顯所長。如此的合作模式前所未見。
回首來時路,王安祈或許也不免驚奇:六歲從胡琴聲中初識生命的憂傷,十四歲一個月連跑九場俞大綱先生《繡繻記》演出、只為默記劇本,少女時代買遍「女王」唱片行所有「匪戲」唱片,大學畢業自題小照,「此生誓以戲曲為職志」,結婚條件非戲迷不嫁,初睹杜近芳來臺演出,如遇故人而潸然淚下……,直到新世紀義無反顧,加入國光。情之所鍾,唯戲而已。欲知戲的魅力能有多大?請自王安祈始。
目次
推薦序 情之所鍾,唯戲而已(王德威)
出版序 承繼傳統 開創當代 指向未來(陳濟民)
出版序 幸福的動能:王安祈與國光品牌(張育華)
代 序 什麼是京劇新美學(王安祈)
楔 子 從戲迷到編劇與總監
一、改編裡的創作--向內凝視 靈魂深處
閻羅夢、王熙鳳、李世民與魏徵
二、危險的女性--鏡照詰問 迴波千旋
王有道休妻、三個人兒兩盞燈、金鎖記、狐仙故事
三、英雄的喟嘆--萬仞高岡 天地蒼茫
清宮三部曲、關公在劇場
四、以戲說戲--胭脂舞流紅 心事戲中尋
孟小冬、百年戲樓、水袖與胭脂
五、藉戲論藝--幽情密意在筆鋒
青塚前的對話、十八羅漢圖、李後主
六、跨界,另一種鏡照
歐蘭朵、繡襦夢
七、傳統,最柔軟的一塊
八、不拘一格求人才
探春
九、五倫之外
附錄:國光劇團新編劇目首演紀錄及創作群名單
書摘/試閱
代序
什麼是京劇新美學?(王安祈)
什麼是國光京劇新美學?
什麼是國光京劇新美學?
我總被問到這問題,現代化有沒有界線?國光要把京劇帶到什麼地步?其實我心裡的藍圖,京劇不是起點,念茲在茲的是「創作」,當代的創作。
台灣當代的創作,小說、詩歌、散文、現代戲劇,各展新姿,為什麼不能把京劇納入創作領域?為什麼不能把京劇當主體進行當代的創作?
創作是挑戰、是開新,而非繼承、模擬、複製,誰甘心成為傳承系譜上的一點一線?編導演都想在舞台上建構自我。
挑戰與創新絕對不是推翻傳統,我以學術訓練和劇場經驗為基礎,向內凝視,潛入傳統深處,諦觀反思,提出現代化與文學性為國光發展方向。「向內凝視」是國光新戲的創作態度與過程,也是追求的境界。
開發新情感時,常想穿透悲歡離合的表象,深掘更細膩幽微的情思,捕捉更飄忽迷離的感悟。每個人心底都有連自己都說不清、看不透的欲求,平常隱而不顯,特定時刻乍然湧上心頭,許多人在那一刻才認清自己,國光的新戲很喜歡捕捉這種恍惚難言、瞬間浮現的流蕩心緒,我希望能以古雅的韻文唱詞勾抉幽微,細細梳理、點滴傳遞,使戲不止於抒情,更深化至「心靈書寫」;情調看似浪漫唯美,其實是逼視殘酷真相的自我叩問,叩問的不僅是個人私情,更以整部戲探索:什麼是戲?什麼是藝術?什麼是文學?我們用戲、用文學呈現的人性、建構的歷史,是真實,還是矯飾甚或虛妄?叩問發自內心,戲是心境的投射,所以好幾部戲都在隱喻自身。隱喻,不僅與傳統的虛擬寫意一貫相通,更能使傳統虛擬寫意的內涵更加深厚。
捉摸不透、恍惚難言的感情要如何表現呢?傳統戲慣於以唱「自剖心境」,但難以言說的幽微情愫怎能明白剖析?我有意識的改用「意象化文詞」描摹情境,把內在潛藏的意識,從靈魂深處勾掘而出,展化為形象。劇中人沒說,觀眾卻透過形象約略捕捉;劇中人自己都摸不透的心底潛意識,觀眾卻能透過文詞畫面,猜著幾分。隱微的心緒,通過這些意象投射浮現,任觀眾捕捉感悟,更利用「後設、諧仿、互文、記憶、意識流、蒙太奇」等等文學理論或運鏡技法,從文詞到舞台,共同開發新情意,建立新情觀。這些作法並非炫奇,文學技巧與理論早從現代、後現代無限翻新,京劇既然期待從劇壇挺進文壇,編劇手法自可多元運用,何況它們原即與傳統京劇的「虛擬寫意」一致,原本就內在於傳統,一旦重新提煉,綻放新意,即可內外一體共同打造「時空交錯、虛實疊映」的詩意舞台。
如果用一句話為國光京劇新美學下定義,應該就是:「傳統京劇演員的身體與聲音(唱唸做打舞)與現代文學技法交互融會,共同探索人性歷史文學的虛實真偽」。想追求的不僅是可供演員發揮唱念的表演腳本,更是動態文學創作。為適應當前演劇時間,編織曲折的故事,卻要掌握明快的節奏,但是絕不因戲劇張力和節奏明快而放棄抒情,最終目的是用意象化的文詞,捕捉恍惚難言的流盪心緒,營造靜謐幽獨甚至微茫孤絕的意境。
我們雖然未必有信心能編出精品,卻希望成為當代台灣值得討論的動態文學作品。既然視京劇為當代創作(而非傳統藝術在當代的遺留,甚或殘存),那麼日新月異的文學技法、視覺影像,各式藝術手段都可妥善運用。一旦把起點與終點翻轉,觀念便不受侷限,便不再存在「京劇到底要變成什麼樣子」的問題。因為京劇不會是完成式、過去式,他是現在進行式,更指向未來。
以上先開宗明義試為京劇新美學下定義,接下來將定義裡涉及的「動態文學創作」、「意象化文詞」、「隱喻自身」等關鍵分別展開細說,各自涵融在以下三道問題中:
(一)「動態文學創作」和「表演腳本」有何不同?
(二)如何對古典崑劇與戲曲改革新編戲雙重學習又交叉取樣?
(三)如何隱喻?叩問什麼?
※※※※※※※※※※※※※※※※※※※※※※※※※※※※※※※※
「動態文學創作」和「表演腳本」有何不同?
首先分辨「動態文學創作」和「表演腳本」的不同。這二者看似只有一線之隔,但根據我個人的劇場經驗,可以清楚分辨觀念的不同。
京劇界的傳統是把劇本當表演腳本,即使編新戲,基本的想法也是:編一個新故事,把京劇的唱念做打好好展現一番。主演一拿到劇本,通常先翻看自己有幾個大唱段,迅速估量是西皮還是二黃,能有機會唱一段高撥子或是反二黃嗎?主角也會迅速翻看最後的收場高潮在不在自己身上。曾看到一本岳飛的戲,原來編劇在岳飛死後還有一場,演以牛皋為首的岳家軍,在忠良遭害金兵又來犯時,竟然又接到聖旨要他們出征抗金。牛皋先是憤而扯旨,而後在岳夫人勸說下,終於率岳家軍繼續保國。這場花臉牛皋為主的戲,在保黎民與報君王之間矛盾掙扎,非常動人,也把岳飛精忠報國的精神高度昇華,但這樣的劇本卻和主角的表演形成衝突,我當時一看便知危險,後來果然被改了,最後一場戲硬生生被拿掉,直接結束在風波亭,以主角的壯烈犧牲為收束。其實原劇本的編劇極為有名,地位崇高,但主角對自己的表演高度關注,觀眾也可能覺得主角都死了為何還要拖戲,這樣的觀念很普遍,這不是個案,是常態。其中沒有對錯,只有表演輕重和文學劇本的觀念差異。
即以梅蘭芳的名作《穆桂英掛帥》而論,為了讓梅蘭芳演完〈捧印〉之後有紮靠的時間,安排了一大段楊宗保的唱。楊宗保在劇中無足輕重,楊家接不接帥印這等重要大事,宗保非但沒有表示意見甚至根本不在場上,劇中有很長一大段時間他是消失的,被遺忘的,直到穆桂英決定披掛紮靠,才忽然讓宗保出場,唱一段拖時間。梅蘭芳對劇本是很講究的,但是在舞台生涯回憶的紀錄裡,經常會說這類的話:我唱了一大段,需要有時間休息,讓兵士們練練武吧,或是別的角色行當也可以唱一段表現一下,讓觀眾喚喚耳音。劇本,是提供表演的腳本,在傳統觀念裡天經地義。所以傳統京劇《戰太平》,為了老生紮靠,竟讓妻妾兩位夫人唱上一大段,唱什麼呢?居然是代替丈夫發兵點將,完全不顧劇情是否合理。同樣也是代夫點兵的還有《銀屏公主》,而公主這一大段唱不僅是給丈夫紮靠時間,更是旦行主角的重點唱段。銀屏公主面對的困境是丈夫出征之後兒子闖禍打死太師,但那時的唱不宜用二黃也不宜太慢,所以在前面安排一段二黃慢板,既解決換裝問題,又可使主角的唱腔板式多樣、完整周全,滿足觀眾聽戲的需求,和文學創作是全然不同的思考。
傳統觀念和表演程式緊密結合牢不可破,編新戲時常有許多顧慮。主要人物出場各有不同程式,打引子上、念上場詩或對子上、唱上,無論如何總要是全場焦點,才能得個碰頭彩。而我常希望劇中人直接入戲,盡量減少自報家門,以免拖緩節奏,也怕敘述性沖淡戲劇性,但這就不太合傳統規矩了。有的演員很不喜歡演新戲,因為不是「暗上」就是「溜下」,好在國光演員已有默契,明白「直接入戲」是結構也是節奏,所以自會找到亮相的節骨眼。例如《十八羅漢圖》溫宇航飾演宇青,起先很擔心自己的上場不醒目,因為我是讓他回應著師父(魏海敏)的呼喚端藥出場,直接答話入戲,沒有念上場詩。宇航理解我對結構和節奏的關注,所以自己找到關鍵點,把「宇青在此」念得清晰有力,宇青二字還頓了一頓,像是答應師父,也像是自報家門,效果等同於亮相,果然獲得碰頭好。而我覺得《金鎖記》曹七巧(魏海敏)的報名,編劇之一趙雪君的設定最兩全其美。曹七巧一出場是在幻象中,夢裡一家和樂諧美,丈夫小劉一邊送她玫瑰香粉一邊溫柔的喚著她名字,七巧甜甜的回應著:「你叫我什麼?七巧?我的名字?七巧,我…曹七巧。」既像報名,又像幻象瞬間消散,跌回現實,面對自我。像這樣就是文學創作的思考,而非表演腳本。
有時主角覺得整部戲只有唱念,戲太靜,想要表現一場大動作身段,編劇往往必須順應主角的要求改劇本加戲。像句踐復國後,西施歸越與范蠡重會,不料卻發覺懷了夫差的骨肉,引起句踐疑懼。這劇本衝突性極強,但都是文戲,主演希望增加深山產子,可以發揮激烈的身段。於是編劇新寫一場風雨雷電中避開鄉鄰獨自入山產子的獨角戲,連唱帶歌舞,當年雅音小集這場很精彩,後來國光演出也維持這設定,只是換了唱詞,連帶的身段也重新安排。這是表演有發揮、劇情也有必要的正面例子,但是當長平公主在國破家亡後隱避尼庵,主演也想加一場挑柴走山路的動作戲,這對編劇來說就有些無奈了。同樣的,要表現孔雀東南飛的女主角遭婆母虐待,如果不用夜織寒機,硬要改成雪地挑水,身段動作是增強了,劇情卻未免有些過頭。這些都是因為京劇劇本被當作表演腳本。
角色的分派當然更影響劇本,我在三十年前曾編過京劇《紅樓夢》,有一場寶玉和琪官蔣玉菡的戲,我安排兩個小生對唱。演寶玉的主角很猶豫,覺得蔣玉菡是配角,怎能和我寶玉對唱?哪有兩個小生對唱之理?本想刪掉蔣的唱詞,改為念白,還好後來接受了,還特邀曹復永客串,形成情調獨特的兩個頭牌小生戲。我在劇中還寫了曹雪芹一角,於開場、中場和尾聲三度出場,唱著「好了歌」,看著自己筆下人物的情思繚繞。當時製作人覺得此角唱不多,請演賈政的老生演員兼扮即可,我一聽大驚,曹雪芹豈能與賈政同一人?趕緊奔去解釋,終於獲得同意,隨即我寫信邀請吳興國客串,吳哥當下首肯,這才解決難題。如果按照製作方要求由賈政兼飾,那曹雪芹只能出來頭尾兩次,中場那段好了歌「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必須刪掉,因為緊接著就演到賈政打子,曹雪芹來不及換裝趕回賈政。至今回想,猶覺驚險,衷心感謝製作單位願意聽編劇解釋。
而我為雅音小集編的《再生緣》,後來大陸山西京劇團取得劇本演出,據說就改了角色也增加了唱詞。當時我輾轉收到對方傳話,說全劇沒有花臉行當,要把孟麗君父親改成花臉,增加大段唱,滿足觀眾視聽。但我認為孟父最後在金殿的出現對孟麗君身分懸疑的揭示沒有任何作用,他自己剛剛傷癒還朝還在一片混亂迷糊之中,沒有可表現花臉剛毅性格的機會。何況那場原以雌雄莫辨為主情調,實在沒有增加花臉黃鍾大呂之聲的需要,所以我並未增寫唱詞。但聽說劇團自己加了唱,而且還把風流皇帝由小生改為老生,以免和皇甫少華角色重複。只是因我並未看過正式演出(此劇進京參賽,李勝素獲大獎),不太能確定,但從排練過程中的思考,即可看出對於劇本的要求仍以表演全面發揮為主。
當然我知道,既然是京劇演出,一定和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不同,編劇必須注意演唱段落的輕重分布,人物的上下出入(例如不能才下場緊接著又上,那叫「頂場」),上下半場演出時間要盡可能平均,才能找到關鍵點中場休息,甚至演員有沒有換裝的時間,這些都必須寫劇本時先做設定,不能拋給導演解決。「筆下有人物,胸中有舞台」,才有能力從事動態文學的創作。但這和表演的腳本,仍是不同觀念。例如《十八羅漢圖》中場休息原落在宇青下山,上半場到此即可落大幕,但李小平導演希望有一點點朦朧的「預示」為下半場起懸念。我也不喜歡上半一結束就「找截乾淨」,也希望有短短幾句唱配合畫面,既有餘韻又寓哲思,正適合十八羅漢圖。但是難題來了,唱詞要寫什麼?不能以宇青口吻擔憂往後,也不喜歡用伴唱旁述紅塵紛擾。我想了很久,決定把後半宇青被囚禁時的唱詞,擷取片段修改詞意置於此,利用同中有異,達到重複又對照的作用,似與不似間,前後相關。我自覺這是文學創作的思考,不同於為了紮靠讓夫人點兵,而且因為這一增添,連帶想到下半開場也不宜迅速直入,於是又添了一場師父(魏海敏)念白:「境象者,心象也。一樣的胭脂花紅,低眉、垂首、仰觀、回眸,所見自是不同。尺幅千里,未必盡是山水本色,反為自身眼目。」宇青似在聆聽又似回憶,各色人物環繞四周,虛演羅漢,無形有相,與上半場之收尾若有似無的相呼應。個人覺得這是動態文學的創作手法,與傳統的表演腳本,看似相隔一線,其實卻有是否是創作的一念之別。
※※※※※※※※※※※※※※※※※※※※※※※※※※※※※※※※
如何對古典崑劇與「戲曲改革」新編戲雙重學習又交叉取樣?
接下來談如何對古典崑劇與對岸「戲曲改革」新編戲交叉取樣。
傳統沒有創作嗎?新編戲不是很多嗎?難道國光全數視而不見,非要另立門戶標新立異?當然不是,我的創新全來自傳統,主要學習對象有二,一是古典崑劇的「一曲微茫」意境,二是對岸「戲曲改革」以來新編戲的敘事結構。
我對傳統京劇表演程式、劇場規律很熟,能分辨各行當、各流派的特質,但不是純擁護式一股腦接受,我會認真反省傳統京劇「演員中心」的劇本問題,因而特別喜歡一九五○年代對岸「戲曲改革」(簡稱「戲改」)以來新編戲的戲劇張力,包括組織矛盾糾葛的能力,以及多元又緊湊的敘事結構。而與此相反的,我也著迷於古典崑劇的「抒情內省、內旋深掘」,試圖藉意象化文詞「潛入內心、勾抉幽微」,營造「一曲微茫」的意境。對於崑劇與戲改,我希望能雙重學習,卻必須交叉取樣,因為這兩種特質是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我卻期待能弔詭地融入國光新編京劇。
崑劇和戲改是我在編劇時學習的典範,但我對這兩類劇本並非全面認同。戲改是對岸的國家政策,所以有時情感過於宏大崇高,目的過於明確,我想學習的僅只是敘事結構。對於百戲之母崑劇,我敢直說,敘事結構無法適用於現在的新編戲,目前的戲演出時間不到三小時,傳奇崑劇卻都是長篇,動輒四五十齣,每齣只放出一點點劇情,劇情緩慢推進,事隨人走,最易形成的是對比(例如《琵琶記》京城的蔡伯喈和家鄉的趙五娘,一齣一齣輪番上場,各自單線發展,緩慢形成對比,直到最後才紐合),卻缺少把矛盾糾葛組織成板塊推進的能力。所以對於崑劇,我想學習的只在意象化文詞展示的心緒樣態。
交叉取樣很不容易,因為這兩種特質根本相反,要想融合難度極高,而國光京劇新美學追求的就是:編織曲折的故事,組織矛盾糾葛,卻不被複雜的劇情困住,最終目的是勾抉幽微、潛入內心。在轉折多變化的戲劇性情節裡,用意象化的文詞,捕捉難以言說的流蕩心緒;掌握明快的節奏,卻企圖營造「一曲微茫」的意境。
關於意象化文詞,和傳統的「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不盡相同,傳統京劇常用「實指望、又誰知」直接自剖,陳述心情轉折,這些經典名劇都有動聽的唱腔,但情感很明確,即使也可用「籠中鳥、南來雁」或「一輪明月」等寓情於景,但都分別確指懊悔、無奈、焦慮、悲憤等等,情感可以直接分類、直接明喻,和我想追尋的隱微情愫不太一樣,我想學習的在傳統京劇裡很難找到範本。我試圖改用「意象化文詞」,唱詞曲文不僅是形容、描述、寫景、對話,也不僅是心情告白,它經常像是「靈魂深處的尋幽訪密」。有時整段唱的目的未必是抒情或達意,只是寫出一幅一幅畫面,不是據實寫景,也不只情景交融,經常是在模塑情境、營造意象,讓深不可測的隱微心緒,通過這些意象約略呈現,任觀眾捕捉感悟。自己覺得最有代表性的是《金鎖記》曹七巧兒子結婚那段,導演將婚禮和鴉片兩個看似無關的場景並置,既可跨越空間,又暗示兩個事件之間緊密的關係,這是蒙太奇在寫意舞台上的運用,觀眾大可從視覺畫面上興奮讚賞,但唱詞要怎麼寫?面對「鴉片榻上的婚禮」,我該如何寫唱詞?總不可能讓七巧自剖心境的直接唱出:我要以餵食鴉片和給他娶妻這兩種手段來掌控兒子。我想了很久,這在古典崑劇經典裡都沒有可參考的,崑劇文詞都很美,但也有很多只是浮泛的情意,至少我找不出像這樣不相干卻有關連的兩個畫面並置的前例。於是我放棄直接抒情,改為意象營造:「霧濛濛、氣氤氳,任他是七彩斑斕、光影繽紛,一樣的茫茫迷霧、影朦朧。」我試圖摹塑某種情境,像是抽鴉片的狀態,卻又不限於此。尤其特別的,是在曹七巧的唱腔裡突然插入三爺姜季澤的聲音,三爺的甜言蜜語對七巧來說就像鴉片,挑逗得心頭暖暖的,想要黏上去,竟被扯向無盡深淵。那幾句「飛揚、墜沉,天高、淵深,風輕、水重,逍遙、羈籠」,不是特定人物心聲,也不僅僅指鴉片,而是某種人生的情境樣態。主演唐文華一反老生的蒼勁,用類似費玉清的嗓音,軟綿綿的,唱出頹靡腐朽的樣態。聽著這嗓音,像看見頹靡腐朽正對人伸出手來招搖魅惑,無法抵擋的「惡之風華」浮現在國光舞台上,企圖超越傳統的教化而更逼近文學本質。
《百年戲樓》第三段的主戲是女弟子背叛出賣師父的文革大戲,編劇之一周慧玲用樣板戲《紅燈記》與這段形成互文,掀起高潮。但山雨欲來之際,我們並未讓劇情快速推進,反而瞬間打斷,騰出時空寫了一段內心戲,女弟子的內心戲,卻又不是傳統自剖心境的大段唱腔,因為我想她不是預謀出賣師父,那時她應是驚惶失措,自己也摸不透自己在想什麼、該做什麼,眼前大概只有斷斷續續的恐懼畫面,所以我用意象化的內心獨白,從一雙師父送給她的「蟠龍繞鳳金絲掐紅牡丹重瓣小繡鞋」起意,營造變形意象,寫一陣狂風驟雨之後,「黃土四濺,濺上金絲,蟠龍繞鳳竟成了真的蛇,從四面八方,鑽了過來。」用意象的變形扭曲,暗示著她說不清的恐慌,當然也扣緊貫串全劇的白蛇意象,《白蛇傳》在此並非單純的戲中戲,它隨著劇情進展,點滴成形。這正是「戲劇張力」與「深掘內在、幽獨孤絕」相互交織的例子。
若再往前推,《閻羅夢》在三國故事之後,也沒有立即推動情節,而是在書生第二次判決輪迴之前,突然燈光乍冷、音樂沉靜,轉為關公、曹操各幽靈各自反思自己一生在永恆歷史上的定位。這是我與國光合作的起始,這一段「靈魂的靈魂深處」,似已預告「向內凝視」是往後每一部新戲的創作態度與過程,曲折的劇情與明快的節奏,最終目的是探索幽深的內心。
以上是我對崑劇微茫意境和戲改新戲敘事結構交叉取樣的幾個例子。對於「戲曲改革」我還想多做些說明,因為學界普遍認為戲改是政治對戲曲的干預破壞,那我為何把它當作學習對象之一?
我對戲改新編戲的認識,不是靠書面資料,而是來自戒嚴時期偷聽、偷看對岸新戲的經歷。幼年時先發現台灣的唱片行偷渡出版了一些來路不明的新戲,極為動聽,轟傳於戲迷圈,而後又發現收音機短波可以聽到對岸廣播,於是定時收聽大陸戲曲節目,直到後來錄影機誕生,大陸新戲錄影帶偷渡入台,我在時斷時續模糊雜音和閃爍畫面間,興奮感受這些戲改新戲和傳統老戲的不同。新戲多半劇情曲折,情緒跌宕,敘事結構精煉,矛盾衝突劇烈、唱腔旋律也比傳統老戲新穎多變。因為是直接從聽戲看戲接觸戲改政策,直到後來從事學術研究才補齊了史料,所以我並沒有先入為主的認定戲改是「政治利用戲曲、監控戲曲、改造戲曲」。雖然那時出現了許多僵化政策戲,但經過時間淘洗,爛戲都自動消失,剩下的《白蛇傳》《野豬林(林沖)》《秦香蓮》《趙氏孤兒》《狀元媒》《李慧娘》《楊門女將》《春草闖堂》,可都是結結實實的上等好戲。它們至今仍受演員和觀眾歡迎,已納入傳統,卻仍被稱為新戲,正是因為可明顯感受唱腔和結構不同於傳統。不只京劇,越劇《紅樓夢》《梁祝》,黃梅戲《天仙配》《女駙馬》也都是戲改政策下的新編或改編戲,他們都有政治目的,否則無法符合政策,但編劇演員都是高手,讓政治目的隱藏融入合理動人的劇情之中,形成「看不見的政策」。看《楊門女將》誰不隨著採藥老人言派唱腔而感動?看《春草闖堂》誰不隨著劇情的起伏和春草的機智而歡笑?既已入戲,誰又理會春草揭發了封建醜陋而採藥老人表現了軍民一家親?
如果把當時被政治掌控的劇壇視作一片焦土,那麼我眼裡看到的是焦土上長出的朵朵鮮花。在傑出編劇演員和整個創作群努力之下,突破一切障礙綻放藝術光輝,凸顯了創作的可貴。這是我認識的戲曲改革,這些不是台灣京劇新美學,但是我們的養分。通過聽戲看戲和研究,我能清晰釐清各個層面,長於焦土上的鮮花讓我對創作更加敬畏。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