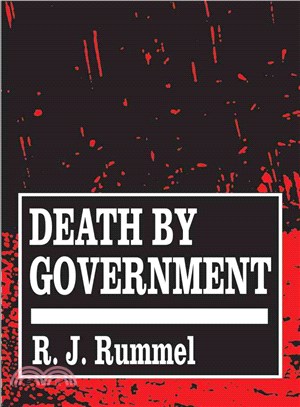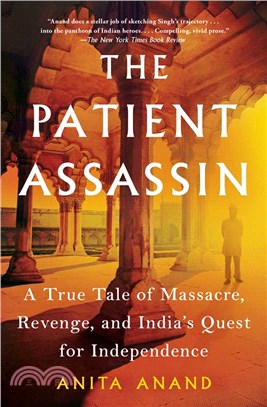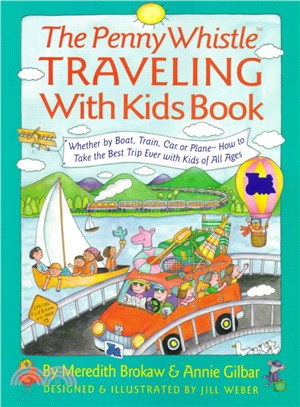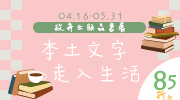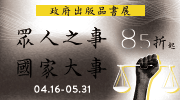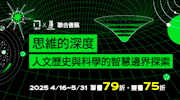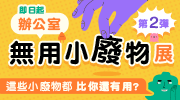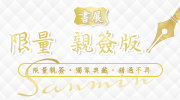西方古典學術史Ⅱ:學術復興至18世紀末(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208170049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英)約翰‧埃德溫‧桑茲
譯者:張治
出版日:2021/10/01
裝訂/頁數:精裝/710頁
規格:21cm*14.5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西方古典學術史》是英國古典學者約翰•愛德溫•桑茲最重要的著作,全書共三卷,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西元前6世紀至19世紀古典學術的發展歷程,細數希臘羅馬學術發展流變,涉及各時期文學、史學、哲學等領域,尤以文獻學、版本學、詞源學、語法學見長,著述極為詳贍淵博,可看作對以往各個時代古典學術成就的總錄。
本書為第二卷,所講述的古典學術史由文藝復興起,至18世紀。全書首先以義大利為中心,講述文藝復興時期對希臘、羅馬著作的研究,接著16,17,18世紀各為一章,每章分國別講述古典學術史。古典學研究的重要地區,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英國、德國,均有詳細的論述。
作者簡介
約翰·愛德溫·桑茲(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英國古典學者,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研究員、導師,劍橋大學校方發言人,不列顛學會會員。曾獲都柏林(三一學院)、愛丁堡、雅典、牛津幾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劍橋大學“終身榮譽發言人”的稱號,被希臘蕞高榮譽級別組織“救世主勳章團”授予司令官徽章。1911年獲爵士頭銜。
主要著作有《西方古典學術史》《西方古典學術簡史》《復活節希臘遊記》《哈佛講演錄:學術復興》等,與人合編有《古典名物詞典》《希臘研究手冊》等。
名人/編輯推薦
跨越百年,數次再版、經久不衰的經典之作
材料之翔實無出其右 古典學脈絡一書盡覽
全面系統闡述前6世紀至中古末期古典學術發展歷程
細數古典學術發展流變,涉及文學、史學、哲學等領域
詳贍淵博,總錄各個時代古典學術成就
序
前言
這部《古典學術史》的第2、3卷出版,便結束了我們自1900年元旦那天開始的工作。第1卷,從西元前6世紀論述至中世紀結束,在1903年10月問世了,當時我有幸在1905年春天受邀在哈佛發表了朗氏Lane系列講座,結果在同年出版,題為《哈佛講演錄:論學術復興》。《學術史》的第1卷在美利堅合眾國受到了友好的接納,如同在英國及歐洲大陸一樣,這促成了1906年10月第二版的刊行。
現在出版的兩卷,始於學術復興運動而止於當下。書中包括了對14—19世紀主要學者生平與著作的考察。各卷下分設的每個時期,開篇都有一部該時代之學者的年序綱目,注明了各自生卒年期,以及在這最後四個世紀中,將他們按照所屬的國別進行群類劃分。在16、17世紀,國家按以下次第排列,——義大利、法國、尼德蘭、英國和日爾曼。不過,在18世紀,如此順序就遭到摒棄,因為本特利在希臘學術上對荷蘭的影響,使得把英國置於尼德蘭之前有歷史上的必要性。也有更為顯著的理由,19世紀需要丟棄上述這個順序,才能說明日爾曼的情況。因此,在第3卷第1部分,日爾曼18世紀的學術史,之後接著敘述同一國家在19世紀的情況。有出色的慣例,論述日爾曼語瑞士時即與日爾曼有關,論述法語瑞士時即與法國有關。西班牙與葡萄牙被我們關注,主要在16世紀;比利時與荷蘭分開論述,是在1830年比利時王國建立之後。在此世紀中,有些篇幅可用以回顧丹麥、挪威以及瑞典、希臘與俄羅斯的古典學術史,也有簡短的論述涉及匈牙利與之相關的命運。19世紀在英國的歷史,直接連接著合眾國,見於此書最後一章。
第2卷所附的書目,展示了在準備第2、3卷時採用的大多數資料來源。或許令人覺得,這部著作有著比實際情形更多的先驅。在哥廷根,厄恩斯特·科耳修斯Ernst Curtius徒勞地試圖勸導紹佩Sauppe以及迪滕貝格Dittenberger寫作一部古典語文學通史,未能如願。關於這個主題簡略而具有提示意義的概述時不時會出現一部,但只有本書嘗試涵蓋整個領域,涉及任何豐富的細節。福格特Voigt那部令人懷有敬意的著作,只涉及了義大利學術復興的第一個世紀。布林西安Bursian具有價值的“德國古典語文學史”,則幾乎專門局限於該國之範圍;盧奇安·穆勒Lucian Müller寫過一小冊關於古典學識在荷蘭的著作;還有勒爾施Roersch,他在一部比利時的百科全書中埋藏了比利時古典學術之命運的簡述。在所有歐洲其他國家的情況下,還有在美利堅合眾國,都沒有一部單獨成書的歷史;因此,本書的所為乃是首次之創舉,這不僅對於英國而言是如此,也同樣可用於義大利、法國、斯堪的納維亞、希臘和俄羅斯,以及合眾國,而對荷蘭、比利時以及德國之學術史的重新研究,也使之延續到當下的情形。在本書中,其生平與著述得到評議的學者,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作古之人。只有非常少數的個案中,完全緘默會顯得不太正常,於是我提及了幾位在世學者的姓名,諸如韋爾Weil與孔帕雷迪Comparetti。
在努力描述自彼特拉克時代至今一長串古典研究代表人物之主要特色的過程中,我不斷地回想起古羅馬人的一個風俗,他們在中庭的壁龕裡按照宗譜支系放置著祖先的彩繪面具。這些肖像被視為家宅的主要裝飾,從不移動;除非偶而家庭成員中有人亡故,這時每個面具都由一位在世的代表戴上,並穿上長袍來摹擬逝者,為其舉行葬禮遊行,至廣場中的講臺處方止。在那裡,“祖先們”從馬車上走下來,就座於顯要席位,最直系的親屬上臺並列數四周環坐者的姓名和功績,最後是那些晚近剛剛去世的人[ 波裡比烏斯,vi 53;普林尼,《博物志》,xxxv 6;蒙森的《羅馬史》,book III,chap. xiii開篇。]。對於今日的學者們,這些篇章提供了一系列他們自己的imagines maiorum【先輩肖像】,每一幅都安置於自己獨特的壁龕中,並按照時、地次序將之分屬於各自的世紀和國家。他們在一支綿延漫長的遊行佇列中先行於我們,本書作者有權走入這世界的中心廣場,向所有聆聽者宣揚每一個人物的姓名與成就。
在此後這兩卷中,有接近六十位學者的肖像被採用製版。有17幅作品的原始版畫或石印本[ Burman, Ernesti, Fabricus, Gronovius, Hemsterhuys, Heyne, Lachmann, Lambinus, Meineke, Montfaucon, K. O. Müller, Muretus, Niebuhr, Ritschl, Ruhnken, Salmasius, Vossius. 以上這些及其他所有肖像的出處,最後可從插圖目錄中獲得。],我得益於古德曼教授,他從前在康奈爾就職,現在則在慕尼克工作,慷慨地將全部藏品贈送與我。皮埃爾·德·諾亞克Pierre de Nolhac先生友好地允準我複製了彼特拉克的肖像,這幅圖構成了他討論“彼特拉克與人文主義運動”的經典著作之扉頁。亨利·奧蒙Henri Omont先生業已同意我重制瓜理諾的肖像,那幅圖首次是由他從英國一份鈔本中公佈於世的。大英博物館的G. F. 希爾先生,饋贈給我薄伽丘的大獎章之鑄模。薩洛芒·雷納克Salomon Reinach先生大行善舉,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選擇了羅貝·艾蒂安、卡索邦、杜康日和馬必雍的肖像版畫,為我拍攝下來,並代為複製布瓦松納德Boissonade的肖像。羅伯茨E. S. Roberts牧師,他是岡維爾與凱斯學院院長,現在是劍橋的副校長,曾將詹·葛魯忒的海德堡肖像的一幅精美相片出借給我。哈特曼教授,現在是萊頓大學的校長,也許我使用他私藏的科貝特所贈肖像的石印副本。萊比錫的托伊布納Teubner諸先生,早已允準複製柏克的某幅肖像,其子向我擔保,在他看來那是最為出色的一幅。範·維拉莫維茨-默倫多夫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教授,蒙森的乘龍快婿,曾借給我一幅他岳父令人敬慕的肖像,由威廉·裡奇蒙德爵士繪製。約翰·穆雷先生曾給我一幅格羅特肖像的精美版畫,並允許我在該史家傳略文字前重新該圖。佛羅倫斯的阿李納理Alinari先生們允準使用吉蘭達約Ghirlandaio所繪費奇諾、蘭迪諾、波利齊亞諾與喀耳孔第勒斯群像的複製版;倫敦的照相師們也同樣授權,使我得以採用伊拉斯謨的肖像,以及後來的理查·耶博爵士之像,而牛津的幾位萊曼Ryman先生,使我得以在清單中添加上蓋斯福德的肖像。最後,紐約的惠勒J. R. Wheeler教授寄給我美利堅雅典學校的大獎章,複製於這部著作的結尾處。
在那些友善地提供我傳記或書目信息的人中,我可以提及的,除了薩洛芒·雷納克先生,還有前駐倫敦希臘公使約翰·真納蒂烏斯John Gennadios先生;聖彼德堡的傑林斯基Zielinski教授,他促成其同儕馬林Maleyn教授為我撰寫了一篇關於俄羅斯國內學術簡短論述;還有米蘭的薩巴迪尼Sabbadini教授;哥本哈根的葛茲教授;烏普薩拉的許克Schück與維德Wide教授,以及該大學圖書館館員畢格登Bygdén博士;根特的圖書館館員範·德·海根V. van der Haeghen博士,以及魯汶的助理圖書館館員維茨J. Wits,他向我提供了同鄉人物許多記錄資料;哈佛的懷特J. W. White教授與摩根M. H. Morgan教授,紐約的西勒爾E. G. Sihler教授,巴爾的摩的馬斯塔德Mustard教授,以及耶魯的已故席默爾Seymour教授;牛津默頓學院研究員艾倫P. S. Allen先生;劍橋國王學院的卡爾·赫爾曼·布羅伊爾Karl Hermann Breul博士,以及伊曼紐爾學院研究員賈爾斯Giles先生。在轉寫俄羅斯姓名方面,我遵從了佈雷Bury教授的建議。涉及斯堪的納維亞學者傳記時所研讀的丹麥文、挪威文及瑞典文原始資料,都是受惠於大學圖書館的馬格努松Magnússon先生,而在修訂有關首刊版的部分編年綱目時,我得到了聖約翰學院文科碩士查理·塞爾Charles Sayle先生的幫助。聖約翰學院研究員史密斯W. F. Smith先生翻譯過拉伯雷,他向我提供了有關那位人文主義者的一條記載。我從未邀請友人們對拙著加以考評,但是當國王學院研究員亞瑟·蒂利Arthur Tilley先生對部分屬於他大作《法國文藝復興時期之文學》Literature of the French Renaissance論述範圍的片段略加垂顧後,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審讀意見。這部著作其他部分的少數被我和大學出版社細心的審讀員們都疏忽了的錯謬,被記錄在《勘誤表》中【譯按,中譯本俱已在原文各處加以修正】。每一卷結尾的索引,都並不局限於當卷的內容。比如特別是第3卷的索引,收入了條目物件的可選擇部分綜合文獻之參考頁碼。
J. E. 桑茲
默頓樓,
劍橋,
1908年7月。
目次
目 錄
中譯本說明 1
前言 4
主要內容概略 9
第一編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與學術史
第一章 引論。彼特拉克與薄伽丘 21
第二章 薩盧塔蒂、赫律索洛拉斯、巴爾齊紮 41
第三章 經典的發現。博喬、奧理斯帕、菲勒爾佛、
雅努斯·剌斯喀理斯 51
第四章 佛羅倫斯的早期梅第奇時代 74
第五章 前期希臘移民 94
第六章 後期希臘移民 112
第七章 佛羅倫斯、那不勒斯和羅馬的學園 120
第八章 古典著作在義大利的出版 138
第九章 自利奧十世時代至羅馬之劫 157
第二編 十六世紀
第十章 伊拉斯謨 185
第十一章 1527—1600 年的義大利 193
第十二章 西班牙與葡萄牙 224
第十三章 1360—1600 年的法國 235
第十四章 尼德蘭,1400—1575 年 293
第十五章 約1370—約1600 年的英格蘭 303
第十六章 1350—1616 年間的德意志 347
第三編 十七世紀
第十七章 17 世紀的義大利 385
第十八章 17 世紀的法蘭西 391
第十九章 1575—1700 年間的尼德蘭 412
第二十章 17 世紀的英國 452
第二十一章 17 世紀的德意志 485
第四編 十八世紀
第二十二章 18 世紀的義大利 505
第二十三章 18 世紀的法國 520
第二十四章 18 世紀的英國 537
第二十五章 18 世紀的尼德蘭 589
圖錄說明 622
參考書目 627
譯名對照表(人、地部分) 647
譯名對照表(著作部分) 671
索引 679
書摘/試閱
第三章 經典的發現。博喬、奧理斯帕、菲勒爾佛、雅努斯·剌斯喀理斯
對經典著作鈔本手稿的尋訪,肇始於彼特拉克[ 上文第7頁。],由薄伽丘[ 上文第14頁以下。]和薩盧塔蒂[ 上文第17頁以下。]承續其餘波,在康士坦茨會議期間(1414-1418)蔓延至義大利疆土以外。那次著名的會議不僅見證了第一位在義大利傳授希臘文的偉大教師之過世,還發現了不在少數的一批古代拉丁經典。尋訪者中最著名的是博喬·布拉喬利尼(1380-1459)[ 參看Voigt,i 235-251,257-2603。]。他出生於阿雷佐附近的特蘭諾沃Terranuovo,在佛羅倫斯受學於喬萬尼·瑪律帕吉尼和赫律索洛拉斯,1403年之後出任教皇秘書,以此身份出席了會議。在“使徒聖座Apostolic See”空缺期間【譯按,此前存在西方教會的分裂狀況,阿維尼翁、比薩、羅馬各有一位教皇,康斯坦茨會議即為解決這一問題而召開,會議期間,三位舊教皇先後離職或被廢黜,最終會議擁立一位新教皇】,即自1415年5月24日至1417年11月11日,教皇秘書無公職在身,其主要的發現即在這一段空檔。這些發現與四次不同的考察有關:(1)1415年夏,往克呂尼,(2)1416年夏,往聖高爾,(3)1417年初,往聖高爾及其他修道院,(4)同年夏,往朗格勒及法蘭西、日爾曼其他地區[ 這4次考察得到Sabbadini的細緻區別,見《拉丁與希臘文鈔本的發現:14、15世紀》(翡冷翠,1905)。]。
(1)在馬孔Mâcon北部的克呂尼[ 博喬,《書信集》,ii 7,ex monasterio Cluniacensi【出自克呂尼修道院】。],博喬發現了一部西塞羅演說詞的古代鈔本,其中包括了《為克倫提烏斯辯》pro Cluentio、《為塞克圖斯·羅斯基烏斯辯》pro Sexto Roscio和《為墨列那辯》[ 《書信集》,ii 26(致尼科利),Orationes meas Cluniacenses potes mittere ... Scribas mihi quae orationes sunt in eo volumine praeter Cluentianam, pro Roscio et Murena.]。近來的研究顯示,其中還有《為米洛辯》和《為凱琉斯辯》pro Caelio[ A. C. Clark,在《牛津遺獻輯刊》,x(1905),《博喬所見克呂尼之文物》The Vetus Cluniacensis of Poggio,p. iii。博喬的鈔本,被鑒定為即12世紀克呂尼書目所著錄的第496號,“Cicero pro Milone et pro Avito et Murena et pro quibusdam aliis【西塞羅為米洛辯及為哈比圖斯(譯按,Avito系Habitus之誤,克倫提烏斯全名為Aulus Cluentius Habitus)、墨列那及其人辯】”。在博喬的鈔本傳入義大利之前,對於該本的校讀,包括了《為米洛辯》和《為凱琉斯辯》,已被抄入聖維克多鈔本中,此本今存於巴黎(拉丁件,14,749)。]。博喬使這些手稿免於損毀,將之寄與佛羅倫斯的友人們,其中弗朗切斯科·巴爾巴羅Francesco Barbaro在對之進行釋讀的過程中遇到極大的困難[ 瓜理諾關於《為塞克圖斯·羅斯基烏斯辯》,§132,見引於Clark的《遺獻》Anecdoton,iii【譯按,當指《牛津遺獻》Anecdota Oxoniensia】。]。已知最早的副本,完成於1416年2月,由“約安內斯·阿雷提努斯Joannes Arretinus”獻給科西莫·德梅第奇Cosimo de’Midici,前者顯然是那位知名的書法家[ Sabbadini,《拉丁與希臘文鈔本的發現》,77,注釋22。關於其他副本,見Clark,xxxix。]。
(2)博喬1416年夏在聖高爾的考察有幾位同伴,一個是巴爾托洛梅奧·達蒙泰普爾恰諾Bartolomeo da Montepulciano,在謄錄新見之拉丁鈔本手稿方面有傑出貢獻;一個是琴喬·魯斯蒂奇Cencio Rustici,他與博喬和蒙泰普爾恰諾一樣,是赫律索洛拉斯的學生,從事於希臘著作的翻譯;還有一個是皮斯托亞的佐米諾(或索佐梅諾Sozomeno)Zomino of Pistoia,他憑藉對於希臘文的知識,以及在語法學和修辭學的興趣,在康斯坦茨及其他地方收集了116種拉丁與希臘鈔本,這些手稿在他臨終前贈給了自己的出生地城市(卒於1458)[ 韋斯帕夏諾,《15世紀名人傳》Vite di uomini illustri del secolo xv,503-5,一篇“皮斯托亞人津比諾Zembino Pistolese”的小傳。他的編年通史部分刊印於Muratori的《義大利史料系年彙編》,xvi 1063。]。這次訪書的熱情如此高漲,即便是路程的險阻惡劣也不能動搖博喬、蒙泰普爾恰諾和琴喬從康斯坦茨出發的決心,他們攀越了綿延約20英裡的陡峭山峰才到達了聖高爾。在這座古代學識的家園,他們見到修道院院長和修士們對於文學毫無興趣,有不少珍貴的手稿便蒙著灰塵,被放置在修道院教堂一座陰暗的塔樓中,那是(據博喬說)一間惡臭的監獄,即使死囚也難以在此羈留[ 博喬,《書信集》,i 5(致瓜理諾,1416年12月15日)。]。琴喬被所見此景大為震動,聲稱若是那些書卷能夠發聲,它們將會呼告:“噢,喜愛拉丁語調的仁人君子們,請讓我們不再受這罪了吧,解救我們出獄吧”[ 琴喬致信在羅馬的弗朗切斯科·達菲亞諾Francesco da Fiano,見於Quirinus(Angelo Maria Querini),《弗朗切斯科·巴爾巴羅來往書劄初編》Diatriba praeliminaris in duas partes divisa ad Francisci Barbari et aliorum ad ipsum epistolas(1741),p. 8。]。在博喬最初的收穫品中,有一部完整的昆體良《演說術原理》[ 《書信集》,i 5,ibi inter confertissman librorum copiam, quos longum est percensere, Quintilianum comperimus adhuc salvum et incolumem, plenum tamen situ et pulvere squalentem ... Repperimus praeterea libros tres primos et dimidiam partem quarti C. Valeri Flacci Argonauticon, et expositiones ... super octo Ciceronis orationes Q. Asconii Pediani ... Haec mea transcripsi, et quidem velociter, ut ea mitterem ad Leonardum Arretinum et Nicolaum Florentinum; qui cum a me huius thesauri adinventionem cognovissent, multis a me verbis Quintilianum per suas litteras quam primum ad eos mitti contenderunt.【此間藏書極為可觀,一時難以盡述,我們在此發現昆體良著作竟完好無損,儘管發黴蒙灰……又覓得瓦勒理烏斯· 弗拉庫斯《阿爾戈傳奇》前三卷及半部第四卷,及八卷阿斯柯尼烏斯· 佩甸努斯的西塞羅演說詞注疏(譯按,見本書第一卷中譯本第211頁)……我親手迅疾地謄錄完畢,將之寄贈萊奧納多·阿雷提努斯(譯按,指布魯尼)和佛羅倫斯的尼古勞斯(譯按,指尼科利),他們一聽聞我所發現的寶物,就寫來長信,敦促我儘快把昆體良著作寄去】。參看布魯尼,《書信集》,iv 5。],這是彼特拉克在殘篇斷簡之外從未見識過的著作[ 上文第8頁。],薩盧塔蒂一直想從法國獲得此書卻未能如願[ 書信,(1)見於Thomas,《約安內斯·德·蒙斯特裡奧洛的生平與著述》De Johannis de Monsteriolo vita et operibus(1883),110;(2)見於薩盧塔蒂的《書劄集》,i 260。],加斯帕理諾•達巴爾齊紮竟然魯莽地應承說要以己作來續補亡佚的部分[ 布隆多斯Blondus【譯按,即下文的弗拉維奧·比翁多】,《義大利遊覽志》Italia illustrata,346。]。博喬立即將這好消息告知在佛羅倫斯的尼科利和布魯尼,將手稿運往康斯坦茨,費時53天,親筆謄錄完畢[ 《宗座虛位錄》Sede Apostolica vacante言及副本之題記,見引於Reifferscheid,《萊茵博物館》,1868,145。布魯尼覆信響應博喬第一次宣佈其發現的日期,是1416年9月13日(《書信集》,iv 5)。]。1495年,其謄錄本顯然仍存於梅第奇圖書館[ 《義大利歷史檔案》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Ser. III,xx 60,今存兩個博喬的謄錄本:Vat. Urbin. 327,及Ambros. B 155 sup.【superlativo,極上品】(Sabbadini,《安布羅斯圖書館拉丁本分析》Spogli Ambrosiani Latini,350)。],加斯帕理諾得到的另一副本,直接源自康斯坦茨[ Sabbadini,《加斯帕理諾•巴爾齊紮關於昆體良與西塞羅的研究》Studi di Gasparino Barzizza su Quintiliano e Cicerone(1886),4。]。
與此同時,博喬還發現了一部瓦勒理烏斯• 弗拉庫斯《阿爾戈傳奇》的鈔本,包括了卷I至IV 317。他抄出一部副本,這成為其他謄抄本的來源,今存於馬德裡的一部手稿即系此本[ x 81(摹本見上文第24頁),其筆跡較乎博喬謄抄的傑羅姆和普洛斯珀更為潦草。這兩種手稿的照片,我得A. C. Clark先生賜覽。]。另一個副本,可能是某個無知的日爾曼抄手為巴爾托洛梅奧所制,藏於牛津的王後學院[ A. C. Clark,在《古典學評論》,xiii 119-130。]。完整的著作鈔本,稍晚時期才得以在義大利出現(約1481)[ Vat. 3277(9世紀);Thilo,引言【譯按,指Thilo所校訂的《阿爾戈傳奇》一書引言】,xl;參看A. C. Clark,前揭,124;Sabbadini,《拉丁與希臘文鈔本的發現》,151。]。
博喬還發現了一部手稿,內容包含阿斯柯尼烏斯注疏的西塞羅五篇演說詞,以及一位不知名注家注疏的一大部分《反維勒斯》諸篇[ 《一反》及《二反》卷i、ii至§35。]。這部手稿在康斯坦茨由巴爾托洛梅奧[ 1416年7月25日。]與佐米諾[ 1417年7月23日。]忠實地予以複製。巴爾托洛梅奧的謄抄本今存於洛倫佐圖書館[ liv. 5。];佐米諾鈔本則在皮斯托亞。博喬也抄寫了一部副本,多有臆度改訂之處,今存於馬德裡,與上文提及瓦勒理烏斯• 弗拉庫斯著作並於同一卷冊之中[ A. C. Clark,在《古典學評論》,x 301-5。]。博喬倉促完成之謄抄本有一種精善副本,成為洛倫佐圖書館[ liv 4。]和萊頓所藏鈔本的原本。博喬以己見做的校訂,在此後一段時期得到所有阿斯柯尼烏斯之整理者的遵從,直到基斯林Kiessling和舍爾Schöll發現了巴爾托洛梅奧與佐米諾的忠實鈔本。
琴喬在告知他人以上三部手稿俱得以謄錄之後[ Quirinus,前揭,horum quidem omnium librorum exempla habemus.【我們已有全部書籍之副本】。],又記錄了新的發現,包括普理西安對維吉爾數行詩篇的注疏[ Partitiones(即“修辭解析parsing”)xii versuum Aeneidos.【《埃涅阿斯紀》之12行詩的修辭解析】。],以及一部維特魯威著作的鈔本。後者並非孤本,因為我們知道萊歇瑙(距康斯坦茨較近)有一鈔本,還有一種存於阿維尼翁的教廷圖書館[ Müntz,《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史》Histoire de l’Art pendant la Renaissance,i 238。]。
(3)第二次考察聖高爾,是在1417年1月的一次寒冬大雪中[ 巴爾托洛梅奧在1月21日致信特拉威薩利(《書信集》,p. 984);在隨後巴爾巴羅寫給博喬的信中提到了vis hyemis【於冬日】與nives【雪】(p. 2),時在1417年7月6日。]。得到了官方的批準,巴爾托洛梅奧與博喬被定為同樣級別與權威的考察員[ 巴爾巴羅,《書信集》,pp. 4,6。這次考察的發起人是樞機主教布蘭達Branda(Sabbadini,《拉丁與希臘文鈔本的發現》,79,注釋33)。]。此次訪察未限於聖高爾一家修道院。其他修道院,巴爾托洛梅奧稱其一為“於阿爾卑斯之中心”,可能是指埃因歇德倫,另外還有三家,可確定包括萊歇瑙那家著名的本篤會隱修院,724年建立於下湖區【譯按,Untersee即屬於康斯坦茨湖,該島即名萊歇瑙,見中譯本第一卷第458頁】的島上,還有康斯坦茨湖北岸不足16英裡處建於稍晚時期的魏恩加滕Weingarten隱修院。在聖高爾他們找到了一部維哲修斯和一部龐貝烏斯·費斯多(實為助祭保羅的摘要),兩者均由巴爾托洛梅奧加以謄抄。維哲修斯存於彼特拉克圖書館,而所謂的“龐貝烏斯·費斯多”則下落不明[ Sabbadini,80,注釋36。]。其他的新發現,有盧克萊修、曼尼琉斯、西利烏斯·伊塔利庫斯、阿米安·馬賽理努斯,以及卡珀爾、攸提珂斯和普洛布斯這幾位語法學家。盧克萊修是在一家“僻遠”的修道院中重見天日的,由博喬命人謄抄副本[ 博喬致信巴爾巴羅,在1418年初,“Lucretius mihi nondum redditus est, cum sit scriptus: locus est satis longinquus, neque unde aliqui veniant【盧克萊修還未返回我手,儘管已經抄完:彼地甚為偏遠,鮮有人來】”。(A. C. Clark,《古典學評論》,xiii 125)。Lehnerdt認為可能是指阿爾薩斯的米爾巴克Murbach im Elsass(《文藝復興時期的盧克萊修》Lucretius in der Renaissance,5),他主張博喬或許是在考察朗格勒期間來此的。]。可能在1418年夏,此副本被寄給了尼科利,由其保存至1434年[ 博喬致信尼科利,《書信集》,ii 26(1425年6月),iv 2(1429年12月;Munro,《盧克萊修》,p. 33;Lehnerdt,5)。],並與此同時製作了一部書法精美的謄錄本,今藏洛倫佐圖書館,乃是盧克萊修著作鈔本整個族系中的祖本。曼尼琉斯著作,今以馬德裡的一部謄錄本為代表[ R. Ellis,在《赫爾墨斯與雅典娜》,viii(1893)261-286,以及《古典學評論》,vii 310,356,406。馬德裡鈔本(M 31)包括了曼尼琉斯和《詩草集》,原本與另外一部有阿斯柯尼烏斯和瓦勒理烏斯• 弗拉庫斯著作的鈔本(X 81)捆紮在一起。在第一部的卷首題錄了全部的內容:Manilii Astronomicon Statii Papinii sylvae et Asconius Pedianus in Ciceronem et Valerii Flacci nonnulla【曼尼琉斯《天文學家》、帕丕尼烏斯· 斯塔提烏斯《詩草集》、阿斯柯尼烏斯· 佩甸努斯之西塞羅注疏、瓦勒理烏斯• 弗拉庫斯著作數卷】;第二部的篇末,見上文第24頁的摹本,又參看Clark,《古典學評論》,xiii 119。],其中包含若干處校讀文字,這不見於冉布盧斯Gembloux的那部最早最完善的手稿之中。關於西利烏斯·伊塔利庫斯的《布匿戰紀》Punica這部為中古人所不知曉的著作,其副本是為了巴爾托洛梅奧與博喬而謄寫的[ Clark,《古典學評論》,xiii 126-9;xv 166。],其文本今日得以傳世,全賴這四個鈔本,其中兩部藏於佛羅倫斯的[ L本(Laur. xxxvii 16)與F本。],可能代表了為博喬而制的副本,另兩部則是為巴爾托洛梅奧而制[ O本(牛津王後學院)與V本(梵蒂岡,Vat. 1652)。]。阿米安·馬賽理努斯著作第14至31卷之鈔本,雖無明證,但可知是來自富爾達,或許是該修道院院長本人帶至康斯坦茨的[ Ziegelbauer(轉引自Urlichs,在《萊茵博物館》,xxvi 638),lectissima de sua bibliotheca exportari volumina iussit, quae magnam vero partem deinceps non sunt restituta.【他要求將圖書館精選之書卷拿去展示,不過大多數原本未能歸還】。博喬,《書信集》,ii p. 375,Ammianum Marcellinum ego latinis musis restitui cum illum eruissem e bibliotecis ne dicam ergastulis Germanorum. Cardinalis de Columna habet eum codicem, quem portavi, litteris antiquis, sed ita mendosum, ut nil corruptius esse possit. Nicolaus Nicolus illum manu sua transcripsit in chartis papyri. Is est in bibliotheca Cosmi.【隨著我從圖書館發掘出這部鈔本,我就要重新建立對阿米安·馬賽理努斯之拉丁文的研究,更不消說日爾曼的工作坊了。科隆納家的樞機主教得我轉贈擁有這部古典文學的鈔本,但是謬誤甚多,簡直無從損壞。尼科洛·尼科利親手將之謄抄於紙上。此本今存於科西莫之書室】。前揭由Clark在《古典學評論》xiii 125所刊印之書信,De Ammiano Marcellino non reperio, qui symbolum conferat【我未尋得誰人能夠對於阿米安·馬賽理努斯加以點校】(“在辨讀或解釋上予以援助”)。]。最終則周轉至梵蒂岡圖書館[ No. 1873,10世紀;摹本見Chatelain,《古典拉丁語的古文書法》,no. 195。]。博喬後來煞費苦心,也未能從赫斯費德獲得該史家著作的另一鈔本[ 《書信集》,ii 7,iii 12(1423-7)。赫斯費德鈔本的文本,刊行於1533年,原本則亡佚了,唯有6頁殘卷,於1876年在瑪律堡重見天日。參看Schanz,§ 809。]。至於普洛布斯(與另兩位語法學家一併被提及)的著作,是指被冠以其名的那部《小學末藝》Ars minor,或作《藝學門徑》Institutio Artium【譯按,即第一卷提及的《組句析文之藝》Instituta Artium】。
(4)1417年夏,或許是在馬恩河畔的朗格勒,博喬發現了《為凱基納辯》pro Caecina[ 《為凱基納辯》題記;hanc orationem ... cum eam ... in silvis Lingonum adinvenisset ...【當我去往朗格勒,在林間發現了這部演說詞】。];他又在法國或德國一家不知名的修道院中,發現了另外七部演說詞,即三篇《論土地權》、兩篇《為剌比理烏斯辯》pro Rabirio,還有《為喜劇演員羅斯基烏斯辯》pro Roscio Comoedo與《斥皮索》[ 《斥皮索》題記;has septem ... orationes ... perquisitis plurimis Galliae Germaniaeque ... bibliothecis cum latentes comperisset【此演說詞七篇,乃高盧與日爾曼所得之大收穫,盡是舉世未聞之書籍】(A. C. Clark,《牛津遺書考》,p. 11;Sabbadini,《拉丁與希臘文鈔本的發現》,81)]。1418年初,在康斯坦茨,博喬仍持有這些演說詞的謄錄本,但他隨後將之寄往威尼斯,由弗朗切斯科·巴爾巴羅保管至1436年[ 書信,轉引自A. C. Clark,《古典學評論》,xiii 125-6。]。惟有通過這個謄錄本及其副本,兩篇《為剌比理烏斯辯》才得以傳諸後世,而博喬第一次考察時發現的克呂尼本之謄錄本,則是《為墨列那辯》及《為塞克圖斯·羅斯基烏斯辯》的絕世之權威來源。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