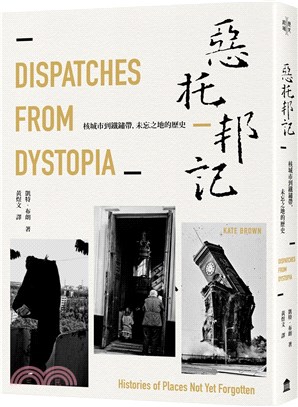惡托邦記:核城市到鐵鏽帶,未忘之地的歷史
商品資訊
系列名:歷史.跨域
ISBN13:9789860601657
替代書名:Dispatches from Dystopia: Histories of Places Not Yet Forgotten
出版社:左岸文化
作者:凱特‧布朗
譯者:黃煜文
出版日:2021/12/28
裝訂/頁數:平裝/256頁
規格:21cm*15cm*2cm (高/寬/厚)
重量:339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來自反烏托邦的報導,充滿哀愁又引人入勝
獲獎無數的歷史學家寫下未忘之地的歷史
◎
《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2016年最佳圖書
「衛兵打開行李箱,往裡頭瞧了瞧,關上行李箱,檢查我們的傳真許可文件,然後揮揮手,讓我們進入車諾比隔離區。我關心車諾比隔離區近十年,卻到了這個時候才得以進入一窺究竟。我想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79年的電影《潛行者》(Stalker)禁區(the Zone)裡的荒涼景象。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及我的想像裡,禁區四處可見生鏽的工廠廠房、倒塌的電話線與被陰暗森林占據的建築物。除了人煙稀少、設下重重障礙與衛兵把守,禁區還散發著一股神祕而致命的力量,威脅要殺害暴露者的子孫,或讓他們出現突變。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裡,潛行者為了賺取一小筆錢,祕密帶領冒險者進入禁區,想揭露其中的謎團。他們在夜色與濃霧的掩護下潛入,在傾頹的工業廢墟間躲避子彈。」
凱特.布朗是一位極富想像力的歷史學家,也是作家與旅行家。她認為,「歷史學家能親自走一趟自己研究的地方,真正體會自己論文的主題,一定能寫出更好的歷史作品。」在《惡托邦記》裡,她進行一場令人驚訝且不尋常的田野之旅,前往遭忽視或抹滅的邊緣地帶,探究這些地方的歷史。
她漫遊車諾比隔離區,先是在網路上,之後親自前往。她想知道現實與虛擬何者才是真正的偽造。她來到西雅圖一家飯店的地下室,檢視1942年日裔美國人被送往監禁營途中存放在地下室的個人物品。在烏克蘭的烏曼,她躲在樹上,觀看只有哈西迪猶太男性才能參加的猶太新年慶典。在俄羅斯烏拉山脈南部,她與克什特姆小鎮居民談話,當地不可見的輻射汙染物正神秘地讓生活陷入困境。最後,她回到出生地,中西部工業鐵鏽帶的伊利諾州埃爾金,考察懷「鏽」情緒的興起與自身的成長經驗,如何開啟她對現代主義荒原的探索。
布朗在本書開頭寫道:「在前往故事發生地旅行的二十年間,我遊遍部分東歐、中亞與美國西部。不知不覺地,我竟成為一名專業的災難觀光客。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我歷經一連串現代主義的荒原,一個比一個惡名遠播,一個比一個孤寂淒涼。」多年來她造訪的地方都不是旅遊勝地,而是所謂的「惡托邦」(dystopia),即被遺忘了的,甚至刻意被遺忘的厭惡之地。
《惡托邦記》帶領讀者來到這些非典型的現場,有力而動人地描述被消音、破壞或汙染的地方歷史。在講述這些過去無人知曉的故事時,布朗也檢視地方的形成與消亡,以及那些仍繼續住在乏人問津、脆弱地貌上人們的生活。
獲獎無數的歷史學家寫下未忘之地的歷史
◎
《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2016年最佳圖書
「衛兵打開行李箱,往裡頭瞧了瞧,關上行李箱,檢查我們的傳真許可文件,然後揮揮手,讓我們進入車諾比隔離區。我關心車諾比隔離區近十年,卻到了這個時候才得以進入一窺究竟。我想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79年的電影《潛行者》(Stalker)禁區(the Zone)裡的荒涼景象。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及我的想像裡,禁區四處可見生鏽的工廠廠房、倒塌的電話線與被陰暗森林占據的建築物。除了人煙稀少、設下重重障礙與衛兵把守,禁區還散發著一股神祕而致命的力量,威脅要殺害暴露者的子孫,或讓他們出現突變。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裡,潛行者為了賺取一小筆錢,祕密帶領冒險者進入禁區,想揭露其中的謎團。他們在夜色與濃霧的掩護下潛入,在傾頹的工業廢墟間躲避子彈。」
凱特.布朗是一位極富想像力的歷史學家,也是作家與旅行家。她認為,「歷史學家能親自走一趟自己研究的地方,真正體會自己論文的主題,一定能寫出更好的歷史作品。」在《惡托邦記》裡,她進行一場令人驚訝且不尋常的田野之旅,前往遭忽視或抹滅的邊緣地帶,探究這些地方的歷史。
她漫遊車諾比隔離區,先是在網路上,之後親自前往。她想知道現實與虛擬何者才是真正的偽造。她來到西雅圖一家飯店的地下室,檢視1942年日裔美國人被送往監禁營途中存放在地下室的個人物品。在烏克蘭的烏曼,她躲在樹上,觀看只有哈西迪猶太男性才能參加的猶太新年慶典。在俄羅斯烏拉山脈南部,她與克什特姆小鎮居民談話,當地不可見的輻射汙染物正神秘地讓生活陷入困境。最後,她回到出生地,中西部工業鐵鏽帶的伊利諾州埃爾金,考察懷「鏽」情緒的興起與自身的成長經驗,如何開啟她對現代主義荒原的探索。
布朗在本書開頭寫道:「在前往故事發生地旅行的二十年間,我遊遍部分東歐、中亞與美國西部。不知不覺地,我竟成為一名專業的災難觀光客。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我歷經一連串現代主義的荒原,一個比一個惡名遠播,一個比一個孤寂淒涼。」多年來她造訪的地方都不是旅遊勝地,而是所謂的「惡托邦」(dystopia),即被遺忘了的,甚至刻意被遺忘的厭惡之地。
《惡托邦記》帶領讀者來到這些非典型的現場,有力而動人地描述被消音、破壞或汙染的地方歷史。在講述這些過去無人知曉的故事時,布朗也檢視地方的形成與消亡,以及那些仍繼續住在乏人問津、脆弱地貌上人們的生活。
作者簡介
凱特.布朗(Kate Brown)
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歷史系教授。著有《惡托邦記:核城市到鐵鏽帶,未忘之地的歷史》(Dispatches from Dystopia: Histories of Places Not Yet Forgotten)、《無名之地的歷史:從種族邊境到蘇聯腹地》(Biography of No Place: From Ethnic Borderland to Soviet Heartland)、《鈽托邦:失去選擇的幸福與核子競賽下的世界墳場》(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等書,其中《鈽托邦》獲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亞伯特貝弗里奇獎(Albert J. Beveridge Award)等獎項。
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歷史系教授。著有《惡托邦記:核城市到鐵鏽帶,未忘之地的歷史》(Dispatches from Dystopia: Histories of Places Not Yet Forgotten)、《無名之地的歷史:從種族邊境到蘇聯腹地》(Biography of No Place: From Ethnic Borderland to Soviet Heartland)、《鈽托邦:失去選擇的幸福與核子競賽下的世界墳場》(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等書,其中《鈽托邦》獲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亞伯特貝弗里奇獎(Albert J. Beveridge Award)等獎項。
名人/編輯推薦
「充滿哀愁卻又引人入勝,布朗前往世界上最偏遠與最脆弱的目的地的旅程,讓我們得以探索地方與記憶的意義,從而微妙地再次發展出探索的技巧。《惡托邦記》是一部打動人心的重要作品。」
──阿拉斯泰爾.邦奈特(Alastair Bonnett),《難以駕馭之地》(Unruly Places: Lost Spaces, Secret Cities, and Other Inscrutable Geographies)作者
「布朗是極富想像力的歷史學家:她是一名學者、作家與旅行家,她迫使我們把極糟糕的狀況視為機會,把空蕩蕩看成是另一種繁榮。對於地方的現代性命運有興趣的人──特別是在一些現代性原本扮演著核心角色的地方──都應該閱讀《惡托邦記》。這本書也是探討意義構成的藝術與科學的一系列論文集:何時該去檔案館與何時該忽略它們,如何凝聽與嗅聞一個地方,為什麼我們在撰寫關於別人過去的故事時,最後卻像是在寫我們自己的故事。」
──查爾斯.金(Charles King),《敖得薩:夢想城市的天才與死亡》(Odessa: Genius and Death in a City of Dreams)作者
「流暢、一針見血、深具說服力且絕無冷場。」
──《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布朗的作品駕輕就熟地跨越個人旅行見聞與學院研究之間的界線。她的論文從被戰爭撕裂的中亞地區一躍來到西雅圖被人遺忘的飯店地下室。布朗認為,歷史學家能親自走一趟自己研究的地方,真正體會自己論文的主題,一定能寫出更好的歷史作品。」
──《書架新訊》(Shelf Awareness)
「布朗是歷史學家,也是旅行者。……對布朗來說,光是研究一個地方、重製已經發表的照片還不夠。身體力行與寫作者親自體會才是貫串全書的主軸。布朗認為歷史不應該局限在印刷紀綠、檔案與官方記載上,她主張歷史學家必須探求那些無法被謄抄校對的歷史。而為了探求這種歷史,歷史學家就必須親臨現場。布朗寫道:『本書的基本前提是,旅行可以是一種協商形式,是對確然無疑之事與信念的闡明,是對過去的重新蒐集。』」
──《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歷史學家花很多時間待在檔案館與圖書館裡。但文獻通常無法呈現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或故事遭到刻意掩蓋的人。為了挖掘這些人的故事,身為歷史學家與災難觀光客的布朗,冒險進入各式各樣的荒原。《惡托邦記》令人信服地記錄那些從過去到現在生活在邊緣的人們。」
──《科學新聞》(Science News)
「《惡托邦記》是一本傑出的作品,這本書不僅介紹了幾個吸引人的地方,也結合了最好的歷史分析與旅行文學。儘管書中帶著一股淡淡的哀愁,但在憂鬱中仍讓人存有願景,這是一本值得大家閱讀的好書。」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歷史學家凱特.布朗《惡托邦記》深刻呈現『廢墟攝影』的美感,記錄這些在文化或經濟急遽變化下遭到遺棄或衰敗的地方。布朗並未埋首圖書館裡仔細研讀第一手的史料文獻,而是親身前往烏克蘭的烏曼、蒙大拿州的比靈斯這些地方探查,反烏托邦的故事就迴盪在那片土地以及居住在上面的人身上……布朗每一篇論文都深具吸引力,彙整起來構成了龐大的故事內容,顯示地方訴說著過去一直未被講述的故事。」
──《流行事》(PopMatters)
──阿拉斯泰爾.邦奈特(Alastair Bonnett),《難以駕馭之地》(Unruly Places: Lost Spaces, Secret Cities, and Other Inscrutable Geographies)作者
「布朗是極富想像力的歷史學家:她是一名學者、作家與旅行家,她迫使我們把極糟糕的狀況視為機會,把空蕩蕩看成是另一種繁榮。對於地方的現代性命運有興趣的人──特別是在一些現代性原本扮演著核心角色的地方──都應該閱讀《惡托邦記》。這本書也是探討意義構成的藝術與科學的一系列論文集:何時該去檔案館與何時該忽略它們,如何凝聽與嗅聞一個地方,為什麼我們在撰寫關於別人過去的故事時,最後卻像是在寫我們自己的故事。」
──查爾斯.金(Charles King),《敖得薩:夢想城市的天才與死亡》(Odessa: Genius and Death in a City of Dreams)作者
「流暢、一針見血、深具說服力且絕無冷場。」
──《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布朗的作品駕輕就熟地跨越個人旅行見聞與學院研究之間的界線。她的論文從被戰爭撕裂的中亞地區一躍來到西雅圖被人遺忘的飯店地下室。布朗認為,歷史學家能親自走一趟自己研究的地方,真正體會自己論文的主題,一定能寫出更好的歷史作品。」
──《書架新訊》(Shelf Awareness)
「布朗是歷史學家,也是旅行者。……對布朗來說,光是研究一個地方、重製已經發表的照片還不夠。身體力行與寫作者親自體會才是貫串全書的主軸。布朗認為歷史不應該局限在印刷紀綠、檔案與官方記載上,她主張歷史學家必須探求那些無法被謄抄校對的歷史。而為了探求這種歷史,歷史學家就必須親臨現場。布朗寫道:『本書的基本前提是,旅行可以是一種協商形式,是對確然無疑之事與信念的闡明,是對過去的重新蒐集。』」
──《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歷史學家花很多時間待在檔案館與圖書館裡。但文獻通常無法呈現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或故事遭到刻意掩蓋的人。為了挖掘這些人的故事,身為歷史學家與災難觀光客的布朗,冒險進入各式各樣的荒原。《惡托邦記》令人信服地記錄那些從過去到現在生活在邊緣的人們。」
──《科學新聞》(Science News)
「《惡托邦記》是一本傑出的作品,這本書不僅介紹了幾個吸引人的地方,也結合了最好的歷史分析與旅行文學。儘管書中帶著一股淡淡的哀愁,但在憂鬱中仍讓人存有願景,這是一本值得大家閱讀的好書。」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歷史學家凱特.布朗《惡托邦記》深刻呈現『廢墟攝影』的美感,記錄這些在文化或經濟急遽變化下遭到遺棄或衰敗的地方。布朗並未埋首圖書館裡仔細研讀第一手的史料文獻,而是親身前往烏克蘭的烏曼、蒙大拿州的比靈斯這些地方探查,反烏托邦的故事就迴盪在那片土地以及居住在上面的人身上……布朗每一篇論文都深具吸引力,彙整起來構成了龐大的故事內容,顯示地方訴說著過去一直未被講述的故事。」
──《流行事》(PopMatters)
目次
導讀 鏽墟裡的點燈人:凱特.布朗的反烏托邦紀事/郭婷(多倫多大學語言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第一章 親臨現場
第二章 巴拿馬飯店,日裔美國人與無法壓抑的過去
第三章 車諾比禁區中(不)可能的歷史
第四章 克什特姆,身體的秘密
第五章 烏曼,受玷花園的神聖空間
第六章 格子狀的生活,為什麼哈薩克和蒙大拿幾乎是相同的地方?
第七章 鐵鏽帶,返鄉憶往
致謝
註釋
參考書目
第一章 親臨現場
第二章 巴拿馬飯店,日裔美國人與無法壓抑的過去
第三章 車諾比禁區中(不)可能的歷史
第四章 克什特姆,身體的秘密
第五章 烏曼,受玷花園的神聖空間
第六章 格子狀的生活,為什麼哈薩克和蒙大拿幾乎是相同的地方?
第七章 鐵鏽帶,返鄉憶往
致謝
註釋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第一章 親臨現場(節錄)
寫作者很少透露隱藏在作品之後的構思歷程。在本書中,我描述當一名研究者猛然闔上筆電,拿起包包,緊張地再次確認護照與機票,然後搭乘飛機飛往幾乎無人知曉的目的地時所發生的事。在前往故事發生地旅行的二十年間,我遊遍部分東歐、中亞與美國西部。不知不覺地,我竟成為一名專業的災難觀光客。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我歷經一連串現代主義的荒原,一個比一個惡名遠播,一個比一個孤寂淒涼。我的冒險經常每況愈下。我罕能找到想尋找的東西。我迷失、犯錯、追尋愚蠢的假定,並且因為對文化缺乏敏感度而失誤連連。面對這些不幸的困境,正如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名句,我有幸仰賴陌生人的好意,提供我食宿,為我指引道路,並且告訴我他們的故事。我遵循卓越而大膽的冒險家傳統,這些冒險家比我更吃苦耐勞且更具勇氣,也比我更確信他們所見的一切。他們隨身帶著標籤,用來製作地圖、目錄清單、百科全書、統計資料與各項法則。但旅行不全然是單方面擴展見聞的行為。本書的基本前提是,旅行可以是一種協商的形式,是對確然無疑之事與信念的闡明、對過去的重新蒐集,而這些全靠陌生人的協助,他們慷慨地打開家門,向我們揭露正在進行中充滿偶然與主觀的歷史。
本書的每一章分別以一個地點為題,探討各地社群與土地的歷史,這些地方的歷史在過去一直遭到噤聲、打壓與汙名化。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我將敘述這些地方的歷史,包括它們的興起與衰微,以及依然在這些被遺忘的地區生活的居民。這種說法看似簡單,但地方鮮少成為非文學類散文的主題。許多作家先入為主地認為行為的發生地是既存的,彷彿地方只是用來承載人類互動交流的中立容器,而非本身具備動力的影響因素。與此相對的是所謂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這個觀念的核心旨在探討空間安排如何形塑人類、自然與動物世界,空間對世界的影響遠不如頒布的律法、市場交易或社會規範的效果來得容易被人察覺,因為人們經常把空間組織當成自然(或既存)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本書的動機是把地方當成某種原始資料,這種資料與檔案館裡建檔的文件一樣豐富、重要、不穩定與不可靠。
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文本與時間要比空間來得重要,他們主張與時間緊密連繫的文件證據具有正當性。但檔案管理人員與歷史學家也知道,文件有可能不精確、曖昧不明且帶有某種目的性,有時根本是錯的,甚至還會故意造假欺騙。歷史學家發現檔案並非死氣沉沉的記錄,而是擁有自身的敘事,這些敘事主動塑造並決定了過去。在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將探討地方做為一種原始資料,它們提供研究者解碼的內容,與檔案文件一樣曖昧不明和充滿挑戰。
本書提到的地方都是我在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與美國擔任研究員時專門研究的對象。有些主題微小,而且有一定的範圍。例如我在某一章探討西雅圖一家飯店的地下室,一九四二年日裔美國人在被送往監禁營途中將個人的財產寄存於此,但他們從此未再返回。有些主題則毫無限制。我先是在網路上漫遊車諾比隔離區(Chernobyl Zone of Exclusion),然後又親自前往當地,我想搞清楚哪一種──現實或虛擬──才是偽造的。在第四章〈克什特姆,身體的祕密〉中,我在俄羅斯南烏拉山脈(southern Urals)小鎮克什特姆(Kyshtym)重新領略十九世紀的「蒸汽」觀念,這個詞被用來描述不可見的二十世紀汙染物,並且說明這些汙染物如何神祕地擊倒身體並阻礙家族的傳承。在第五章〈烏曼,受玷花園的神聖空間〉中,我想參與烏克蘭(Ukraine)烏曼(Uman)哈西迪猶太人(Hasidic Jews)一年一度的猶太新年慶典,卻發現自己只能以乾女兒的身分短暫跨越神聖空間的疆界。二○○○年,我寫下第六章〈格子狀的生活,為什麼哈薩克和蒙大拿幾乎是相同的地方?〉,因為我對於自己眼中所謂「贏得」冷戰的美國之勝利主義深感挫折。為了讓美國人從不同的層面思考美國以及(而非對抗)俄國的歷史,我在冷戰結束後的那幾年試圖說明蒙大拿州(Montana)鐵路城鎮與哈薩克(Kazakhstan)古拉格城鎮的明顯區別,實際上已不存在。如今看來,當時的比較文章有點過頭,但我還是在書裡收錄這篇文章,因為它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最後一章我回到出生地,中西部的工業鐵鏽帶,我考察自己的人生經歷如何啟發自己開啟一段對現代主義荒原的長期探索。
當我進行這項棘手的事務,將這些被猛烈撕扯開來的地域之敘事重新縫補在一起時,我遭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地方與生活在地方上的人說了許多不同而且彼此衝突的過往故事。如何講述這些聲音多元的故事又能維持完整的敘事形式,確實讓我傷透腦筋。更糟的是,如果這些是沒有聲音的故事呢?如果我所追查的歷史,每個記得這段歷史的人要不是不在當地或者早已不在人世了呢?當我抵達某個地方時,我在當地的事實便改變了地方本身,也改變了我講述當地故事的方式。當我承認自己的觀點受到影響,當自己的視角受到當地的束縛與限制時,我講述的故事如何能臻於完善?然而,承認這件事會不會讓我講述的故事變得不夠道地,或者反過來變得更加真實?當我成為故事的一部分時,我又使用什麼聲音寫作?這些問題就像漩渦一樣,讓我受困在歷史的海洋而難以掙脫。在往後各章裡,我分享我所思索的答案,這些答案不算是真正的解答,而是我在面對二十世紀晚期哲學家所提出的主觀性問題時,草率拼湊而成的。
大陸的分界
地理學家羅伯特.薩克(Robert Sack)與馬爾帕斯(J. E. Malpas)寫道:「地方是最基礎的,因為它是我們存在的經驗事實。」如果他們說的是正確的,地方確實是理解人類存在的核心,那麼為什麼當我出現在某地時,我經常無法捕捉到地方的意義?事實上,只要一句有關位置的簡單陳述就能指出問題所在。我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在歐洲或亞洲進行的,這樣一句事實宣告十分簡單,然而一旦你開始質疑為何歐洲與亞洲在地理上是分開的,一切就變得不簡單了。
一七三○年代,歷史學家兼地理學家瓦西里.塔提什謝夫(Vasilii Tatishchev)在地圖上畫了一條線,這條線意義重大,它以烏拉山脈山脊為界,將歐洲與亞洲區分開來。其他的大陸都是以海洋為分界,但塔提什謝夫卻是在龐大的陸塊上畫下歐亞兩洲的界線。在馬匹與車輛可以輕易通行的低矮山脈上畫定大陸分界,這個做法相當大膽。塔提什謝夫為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工作,彼得受人景仰的偉大之處在於,與前幾任沙皇不同,彼得認為歐洲較為優越,因此他致力於讓俄羅斯擺脫他所認為的落後亞洲,設法讓俄羅斯出現在歐洲的地圖上。在塔提什謝夫畫下分界線之前,歐洲地理學家約略以莫斯科以西的頓河(Don River)作為歐洲的東界,這條界線正好將俄羅斯劃入亞洲。彼得希望俄羅斯能成為歐洲的一部分,他也了解所有十八世紀有自尊心的歐洲君主都擁有海外殖民地。將大陸的分界移到東邊的烏拉山脈,不僅讓俄羅斯披上歐洲的大衣,也讓西伯利亞成為俄羅斯的腹地,位於亞洲的西伯利亞瞬間成了俄羅斯的附屬地。塔提什謝夫大筆一揮,一口氣讓俄羅斯成為位於歐洲的宗主國,同時也擁有亞洲殖民地。
在今天,只需要兩條腿與一點想像力,你就能橫跨歐亞大陸分界。在塔提什謝夫重新想像歐洲與亞洲之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二十世紀自然地理學家開始解釋塔提什謝夫分界。他們想像三億年前西伯利亞板塊碰撞歐洲地台東緣,衝擊力抬升了陸塊,造成西伯利亞板塊扭曲變形,沉入歐洲地台下方,在北極與哈薩克沙漠之間形成一道低矮的山脈鏈。烏拉山上的界碑協助造訪者辨識歐亞大陸的分界。二○○七年,我在一個寒冷下雨的六月天與一群人來到此地。從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出發,開車一個小時,我們開上一個長而低矮的斜坡,幾乎沒有人感覺到這是一座山脈,我們最後在路邊一個小餐館停車。這是個渺無人煙的地方,是松樹與樅樹林中的一處空地,我們四周圍繞著樹木,宛如高聳的城牆,看起來難以穿越、潮濕且不宜久留。一名男子在小亭子裡販售香檳給結婚的新人與觀光客。我環顧四周,尋找在此停留的理由。我發現小空地上有一座紅色大理石平台,平台當中有一道白色石頭紋路,這就是歐亞大陸的分界。幾對新人繞著平台,等著輪到自己上去,讓攝影師拍一張新郎、新娘橫跨歐亞兩洲親吻的照片。從丟棄的酒瓶數量不難看出,許多夫婦的結婚相簿裡一定有著類似的照片。我也不能免俗地站到台座上,讓人照了張相。
當我站上區隔歐亞大陸的分界時,一切如此平靜。陰暗的樹林並未傳來漸強的管絃樂,也沒有壯闊的遠景宣示我踏入了亞洲。只有偕行的眾人砰地一聲打開香檳,倒入塑膠杯裡。雖然這道大理石分界是當代重要的分類範疇,將俄羅斯人歸類為歐洲人、哈薩克人歸類為亞洲人,但顯然香檳的氣泡更能吸引眾人的注意。我們舉杯,才一輪敬酒就把香檳喝個精光,然後將空瓶扔進瓶堆,接著便心滿意足地返回溫暖乾燥的巴士,讓車子迅速載我們回到葉卡捷琳堡與亞洲。
這是不可告人的小祕密:通常表面看來充滿意義的地方,乍看之下卻難以描述其歷史與重要性。地方經常讓人失望,這是它受到忽視的一個原因,但對我來說,第二個原因,同時也是比較迫切的原因,在於描述我造訪的地方時等於承認我從這些地方提取的知識是片面且不足取的。地方呈現的只是遺跡與殘骸,遭受破壞、充滿泥濘、凹陷、鏽蝕與受到掠奪。一旦我到了正確的地方,所有的事物卻不在正確的位置上,毫無組織而混亂,就像一箱文件扔到了空中,所有的結構與秩序都被抹滅。我抵達一個地點,對於哪些事物遭到錯置、偷竊、破壞或掩埋一無所知。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寫道:「能見度是許多不透明與不可見的事物所構成的結果。」然而,唯有我抵達之時,那些事物才呈現出這樣的結果。
進行歷史研究的地方通常是檔案館或圖書館。乍看之下,檔案館似乎比過去事件的發生地更為有用而完整。在檔案館裡,文獻經過系統化的整理,文件已經分類與歸檔。檔案人員做了大量不可見的工作,讓事物可見與可理解,他們收集文獻並予以分類,藉此構建知識框架。如此一來,當歷史學家抵達時,就有現成的結構來理解過去。檔案人員透過歸檔與組織,將廣袤的領土擠壓到如地圖般微小的圖樣裡,這比你站在現場觀看地貌,焦急地望著地平線尋找線索,來得更條理分明也更容易判讀。當研究者來到現場,組織性的工作幾乎未曾進行,解讀地方尋求過去的前景總是令人沮喪。學者在試圖釐清過去發生的事件時,通常是形單影隻。歷史學家以批判的眼光鑽研檔案,有些知識經過整理,有些知識則遭到消音,但認識這些問題並不表示歷史學家會放棄這些檔案。檔案依然非常有用。地方也是如此。雖然我想從地方有限的視角觀看過去所需面臨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我不認為這構成了放棄地方的理由。
想想,歷史發生在地方,而不是像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的,歷史是在時間中發生。或者更精確地說,時間與地方透過隱喻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事物,無論過去或現在,都在特定的時空中發生。菲力普.艾辛頓(Philip Ethington)提到,西方文化總是將時間想像成某種空間之物──時間是一條「線」,是一個「框架」,人們即將跨越某個時代的「門檻」。他寫道:「過去在我們身後,未來在我們面前。」時間與空間融合的隱喻,源自於時間是人類行為在空間中的軌跡,而空間本身也是移動的目標。基於這點,地理學家認為人類必須先在某個地方,而後才能創造事物,地方是建構意義與社會的核心條件,除此之外,我認為地方也是建構歷史學、社會學、文學批評與人類學的核心條件。光從檔案資料標繪過去的時間軌跡,這種做法只會讓能見度更加晦暗。地方的闕如在非虛構敘事中造成引人矚目的缺口,讀者在埋怨文字枯燥毫無生命的同時,一定會發現這一點。讀者會感覺到少了什麼。
下落不明
美國能源部官員有一個首字母縮略字MUF,意思是下落不明(missing unaccounted for)。他們用MUF這個字來表示鈽經過能源部處理後卻下落不明。鈽在一九四○年代出現在週期表中,是一種人工合成的元素。鈽也是人類所創造的最不穩定與最具摧毀性的產物。在微量狀況下,人類的感官無法感知它,但如果在某個地點累積足夠的量,鈽就會超越臨界點,產生連鎖反應。下落不明的鈽可能造成嚴重問題,而下落不明一詞也成為學術研究一個恰當的比喻。在非虛構的敘事中經常出現下落不明這四個字。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歷史學家致力於挖掘與呈現國家歷史中長期消失的聲音。一九六○年代暴動後不久,歐美學界出現了新社會史,原本在城市街頭長久下落不明的民眾憤怒情緒,不知從哪裡冒出來,一下子就衝破了臨界值,令那些忽視民眾情緒的人大驚失色。從那時起,勞工、社會與環境史家,以及文化、種族與性向的少數族群史家,都開始研究全新的社群、運動與認同歷史。今日的作家因此可以擷取比過去更為廣泛的聲音與主題。然而,在尋求這些聲音時,社會科學家發現,面對文盲、社會邊緣人或歷史遭到刻意抹煞的人,要透過文字記錄恢復這些人的歷史往往成效不彰。
有些人的生活完全被推土機推倒掩埋(這種說法有些是比喻,有些則確有其事),關於這些人的文獻記載往往非常缺乏且令人挫折,我因此養成了前往過去行為發生的現場探查的習慣。我追隨前現代史家的腳步,他們研究的都是些未留下任何文獻歷史的人物。他們發展了一套解讀地方、地質學、氣候、動植物群落、民間傳說與宗教儀式的方法,試圖尋找解開過去的線索。在本書中,我不斷提到某個地點,這個地點就是哈薩克,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間,這塊土地受到蘇維埃集體化的嚴重侵奪,四百萬名哈薩克人有二百萬人死亡或逃亡。往後十年,數百萬被驅逐者、犯人與流放者被送到了哈薩克。由於這段歷史,我也到了哈薩克。
寫作者很少透露隱藏在作品之後的構思歷程。在本書中,我描述當一名研究者猛然闔上筆電,拿起包包,緊張地再次確認護照與機票,然後搭乘飛機飛往幾乎無人知曉的目的地時所發生的事。在前往故事發生地旅行的二十年間,我遊遍部分東歐、中亞與美國西部。不知不覺地,我竟成為一名專業的災難觀光客。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我歷經一連串現代主義的荒原,一個比一個惡名遠播,一個比一個孤寂淒涼。我的冒險經常每況愈下。我罕能找到想尋找的東西。我迷失、犯錯、追尋愚蠢的假定,並且因為對文化缺乏敏感度而失誤連連。面對這些不幸的困境,正如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名句,我有幸仰賴陌生人的好意,提供我食宿,為我指引道路,並且告訴我他們的故事。我遵循卓越而大膽的冒險家傳統,這些冒險家比我更吃苦耐勞且更具勇氣,也比我更確信他們所見的一切。他們隨身帶著標籤,用來製作地圖、目錄清單、百科全書、統計資料與各項法則。但旅行不全然是單方面擴展見聞的行為。本書的基本前提是,旅行可以是一種協商的形式,是對確然無疑之事與信念的闡明、對過去的重新蒐集,而這些全靠陌生人的協助,他們慷慨地打開家門,向我們揭露正在進行中充滿偶然與主觀的歷史。
本書的每一章分別以一個地點為題,探討各地社群與土地的歷史,這些地方的歷史在過去一直遭到噤聲、打壓與汙名化。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我將敘述這些地方的歷史,包括它們的興起與衰微,以及依然在這些被遺忘的地區生活的居民。這種說法看似簡單,但地方鮮少成為非文學類散文的主題。許多作家先入為主地認為行為的發生地是既存的,彷彿地方只是用來承載人類互動交流的中立容器,而非本身具備動力的影響因素。與此相對的是所謂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這個觀念的核心旨在探討空間安排如何形塑人類、自然與動物世界,空間對世界的影響遠不如頒布的律法、市場交易或社會規範的效果來得容易被人察覺,因為人們經常把空間組織當成自然(或既存)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本書的動機是把地方當成某種原始資料,這種資料與檔案館裡建檔的文件一樣豐富、重要、不穩定與不可靠。
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文本與時間要比空間來得重要,他們主張與時間緊密連繫的文件證據具有正當性。但檔案管理人員與歷史學家也知道,文件有可能不精確、曖昧不明且帶有某種目的性,有時根本是錯的,甚至還會故意造假欺騙。歷史學家發現檔案並非死氣沉沉的記錄,而是擁有自身的敘事,這些敘事主動塑造並決定了過去。在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將探討地方做為一種原始資料,它們提供研究者解碼的內容,與檔案文件一樣曖昧不明和充滿挑戰。
本書提到的地方都是我在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與美國擔任研究員時專門研究的對象。有些主題微小,而且有一定的範圍。例如我在某一章探討西雅圖一家飯店的地下室,一九四二年日裔美國人在被送往監禁營途中將個人的財產寄存於此,但他們從此未再返回。有些主題則毫無限制。我先是在網路上漫遊車諾比隔離區(Chernobyl Zone of Exclusion),然後又親自前往當地,我想搞清楚哪一種──現實或虛擬──才是偽造的。在第四章〈克什特姆,身體的祕密〉中,我在俄羅斯南烏拉山脈(southern Urals)小鎮克什特姆(Kyshtym)重新領略十九世紀的「蒸汽」觀念,這個詞被用來描述不可見的二十世紀汙染物,並且說明這些汙染物如何神祕地擊倒身體並阻礙家族的傳承。在第五章〈烏曼,受玷花園的神聖空間〉中,我想參與烏克蘭(Ukraine)烏曼(Uman)哈西迪猶太人(Hasidic Jews)一年一度的猶太新年慶典,卻發現自己只能以乾女兒的身分短暫跨越神聖空間的疆界。二○○○年,我寫下第六章〈格子狀的生活,為什麼哈薩克和蒙大拿幾乎是相同的地方?〉,因為我對於自己眼中所謂「贏得」冷戰的美國之勝利主義深感挫折。為了讓美國人從不同的層面思考美國以及(而非對抗)俄國的歷史,我在冷戰結束後的那幾年試圖說明蒙大拿州(Montana)鐵路城鎮與哈薩克(Kazakhstan)古拉格城鎮的明顯區別,實際上已不存在。如今看來,當時的比較文章有點過頭,但我還是在書裡收錄這篇文章,因為它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最後一章我回到出生地,中西部的工業鐵鏽帶,我考察自己的人生經歷如何啟發自己開啟一段對現代主義荒原的長期探索。
當我進行這項棘手的事務,將這些被猛烈撕扯開來的地域之敘事重新縫補在一起時,我遭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地方與生活在地方上的人說了許多不同而且彼此衝突的過往故事。如何講述這些聲音多元的故事又能維持完整的敘事形式,確實讓我傷透腦筋。更糟的是,如果這些是沒有聲音的故事呢?如果我所追查的歷史,每個記得這段歷史的人要不是不在當地或者早已不在人世了呢?當我抵達某個地方時,我在當地的事實便改變了地方本身,也改變了我講述當地故事的方式。當我承認自己的觀點受到影響,當自己的視角受到當地的束縛與限制時,我講述的故事如何能臻於完善?然而,承認這件事會不會讓我講述的故事變得不夠道地,或者反過來變得更加真實?當我成為故事的一部分時,我又使用什麼聲音寫作?這些問題就像漩渦一樣,讓我受困在歷史的海洋而難以掙脫。在往後各章裡,我分享我所思索的答案,這些答案不算是真正的解答,而是我在面對二十世紀晚期哲學家所提出的主觀性問題時,草率拼湊而成的。
大陸的分界
地理學家羅伯特.薩克(Robert Sack)與馬爾帕斯(J. E. Malpas)寫道:「地方是最基礎的,因為它是我們存在的經驗事實。」如果他們說的是正確的,地方確實是理解人類存在的核心,那麼為什麼當我出現在某地時,我經常無法捕捉到地方的意義?事實上,只要一句有關位置的簡單陳述就能指出問題所在。我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在歐洲或亞洲進行的,這樣一句事實宣告十分簡單,然而一旦你開始質疑為何歐洲與亞洲在地理上是分開的,一切就變得不簡單了。
一七三○年代,歷史學家兼地理學家瓦西里.塔提什謝夫(Vasilii Tatishchev)在地圖上畫了一條線,這條線意義重大,它以烏拉山脈山脊為界,將歐洲與亞洲區分開來。其他的大陸都是以海洋為分界,但塔提什謝夫卻是在龐大的陸塊上畫下歐亞兩洲的界線。在馬匹與車輛可以輕易通行的低矮山脈上畫定大陸分界,這個做法相當大膽。塔提什謝夫為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工作,彼得受人景仰的偉大之處在於,與前幾任沙皇不同,彼得認為歐洲較為優越,因此他致力於讓俄羅斯擺脫他所認為的落後亞洲,設法讓俄羅斯出現在歐洲的地圖上。在塔提什謝夫畫下分界線之前,歐洲地理學家約略以莫斯科以西的頓河(Don River)作為歐洲的東界,這條界線正好將俄羅斯劃入亞洲。彼得希望俄羅斯能成為歐洲的一部分,他也了解所有十八世紀有自尊心的歐洲君主都擁有海外殖民地。將大陸的分界移到東邊的烏拉山脈,不僅讓俄羅斯披上歐洲的大衣,也讓西伯利亞成為俄羅斯的腹地,位於亞洲的西伯利亞瞬間成了俄羅斯的附屬地。塔提什謝夫大筆一揮,一口氣讓俄羅斯成為位於歐洲的宗主國,同時也擁有亞洲殖民地。
在今天,只需要兩條腿與一點想像力,你就能橫跨歐亞大陸分界。在塔提什謝夫重新想像歐洲與亞洲之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二十世紀自然地理學家開始解釋塔提什謝夫分界。他們想像三億年前西伯利亞板塊碰撞歐洲地台東緣,衝擊力抬升了陸塊,造成西伯利亞板塊扭曲變形,沉入歐洲地台下方,在北極與哈薩克沙漠之間形成一道低矮的山脈鏈。烏拉山上的界碑協助造訪者辨識歐亞大陸的分界。二○○七年,我在一個寒冷下雨的六月天與一群人來到此地。從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出發,開車一個小時,我們開上一個長而低矮的斜坡,幾乎沒有人感覺到這是一座山脈,我們最後在路邊一個小餐館停車。這是個渺無人煙的地方,是松樹與樅樹林中的一處空地,我們四周圍繞著樹木,宛如高聳的城牆,看起來難以穿越、潮濕且不宜久留。一名男子在小亭子裡販售香檳給結婚的新人與觀光客。我環顧四周,尋找在此停留的理由。我發現小空地上有一座紅色大理石平台,平台當中有一道白色石頭紋路,這就是歐亞大陸的分界。幾對新人繞著平台,等著輪到自己上去,讓攝影師拍一張新郎、新娘橫跨歐亞兩洲親吻的照片。從丟棄的酒瓶數量不難看出,許多夫婦的結婚相簿裡一定有著類似的照片。我也不能免俗地站到台座上,讓人照了張相。
當我站上區隔歐亞大陸的分界時,一切如此平靜。陰暗的樹林並未傳來漸強的管絃樂,也沒有壯闊的遠景宣示我踏入了亞洲。只有偕行的眾人砰地一聲打開香檳,倒入塑膠杯裡。雖然這道大理石分界是當代重要的分類範疇,將俄羅斯人歸類為歐洲人、哈薩克人歸類為亞洲人,但顯然香檳的氣泡更能吸引眾人的注意。我們舉杯,才一輪敬酒就把香檳喝個精光,然後將空瓶扔進瓶堆,接著便心滿意足地返回溫暖乾燥的巴士,讓車子迅速載我們回到葉卡捷琳堡與亞洲。
這是不可告人的小祕密:通常表面看來充滿意義的地方,乍看之下卻難以描述其歷史與重要性。地方經常讓人失望,這是它受到忽視的一個原因,但對我來說,第二個原因,同時也是比較迫切的原因,在於描述我造訪的地方時等於承認我從這些地方提取的知識是片面且不足取的。地方呈現的只是遺跡與殘骸,遭受破壞、充滿泥濘、凹陷、鏽蝕與受到掠奪。一旦我到了正確的地方,所有的事物卻不在正確的位置上,毫無組織而混亂,就像一箱文件扔到了空中,所有的結構與秩序都被抹滅。我抵達一個地點,對於哪些事物遭到錯置、偷竊、破壞或掩埋一無所知。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寫道:「能見度是許多不透明與不可見的事物所構成的結果。」然而,唯有我抵達之時,那些事物才呈現出這樣的結果。
進行歷史研究的地方通常是檔案館或圖書館。乍看之下,檔案館似乎比過去事件的發生地更為有用而完整。在檔案館裡,文獻經過系統化的整理,文件已經分類與歸檔。檔案人員做了大量不可見的工作,讓事物可見與可理解,他們收集文獻並予以分類,藉此構建知識框架。如此一來,當歷史學家抵達時,就有現成的結構來理解過去。檔案人員透過歸檔與組織,將廣袤的領土擠壓到如地圖般微小的圖樣裡,這比你站在現場觀看地貌,焦急地望著地平線尋找線索,來得更條理分明也更容易判讀。當研究者來到現場,組織性的工作幾乎未曾進行,解讀地方尋求過去的前景總是令人沮喪。學者在試圖釐清過去發生的事件時,通常是形單影隻。歷史學家以批判的眼光鑽研檔案,有些知識經過整理,有些知識則遭到消音,但認識這些問題並不表示歷史學家會放棄這些檔案。檔案依然非常有用。地方也是如此。雖然我想從地方有限的視角觀看過去所需面臨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我不認為這構成了放棄地方的理由。
想想,歷史發生在地方,而不是像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的,歷史是在時間中發生。或者更精確地說,時間與地方透過隱喻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事物,無論過去或現在,都在特定的時空中發生。菲力普.艾辛頓(Philip Ethington)提到,西方文化總是將時間想像成某種空間之物──時間是一條「線」,是一個「框架」,人們即將跨越某個時代的「門檻」。他寫道:「過去在我們身後,未來在我們面前。」時間與空間融合的隱喻,源自於時間是人類行為在空間中的軌跡,而空間本身也是移動的目標。基於這點,地理學家認為人類必須先在某個地方,而後才能創造事物,地方是建構意義與社會的核心條件,除此之外,我認為地方也是建構歷史學、社會學、文學批評與人類學的核心條件。光從檔案資料標繪過去的時間軌跡,這種做法只會讓能見度更加晦暗。地方的闕如在非虛構敘事中造成引人矚目的缺口,讀者在埋怨文字枯燥毫無生命的同時,一定會發現這一點。讀者會感覺到少了什麼。
下落不明
美國能源部官員有一個首字母縮略字MUF,意思是下落不明(missing unaccounted for)。他們用MUF這個字來表示鈽經過能源部處理後卻下落不明。鈽在一九四○年代出現在週期表中,是一種人工合成的元素。鈽也是人類所創造的最不穩定與最具摧毀性的產物。在微量狀況下,人類的感官無法感知它,但如果在某個地點累積足夠的量,鈽就會超越臨界點,產生連鎖反應。下落不明的鈽可能造成嚴重問題,而下落不明一詞也成為學術研究一個恰當的比喻。在非虛構的敘事中經常出現下落不明這四個字。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歷史學家致力於挖掘與呈現國家歷史中長期消失的聲音。一九六○年代暴動後不久,歐美學界出現了新社會史,原本在城市街頭長久下落不明的民眾憤怒情緒,不知從哪裡冒出來,一下子就衝破了臨界值,令那些忽視民眾情緒的人大驚失色。從那時起,勞工、社會與環境史家,以及文化、種族與性向的少數族群史家,都開始研究全新的社群、運動與認同歷史。今日的作家因此可以擷取比過去更為廣泛的聲音與主題。然而,在尋求這些聲音時,社會科學家發現,面對文盲、社會邊緣人或歷史遭到刻意抹煞的人,要透過文字記錄恢復這些人的歷史往往成效不彰。
有些人的生活完全被推土機推倒掩埋(這種說法有些是比喻,有些則確有其事),關於這些人的文獻記載往往非常缺乏且令人挫折,我因此養成了前往過去行為發生的現場探查的習慣。我追隨前現代史家的腳步,他們研究的都是些未留下任何文獻歷史的人物。他們發展了一套解讀地方、地質學、氣候、動植物群落、民間傳說與宗教儀式的方法,試圖尋找解開過去的線索。在本書中,我不斷提到某個地點,這個地點就是哈薩克,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間,這塊土地受到蘇維埃集體化的嚴重侵奪,四百萬名哈薩克人有二百萬人死亡或逃亡。往後十年,數百萬被驅逐者、犯人與流放者被送到了哈薩克。由於這段歷史,我也到了哈薩克。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