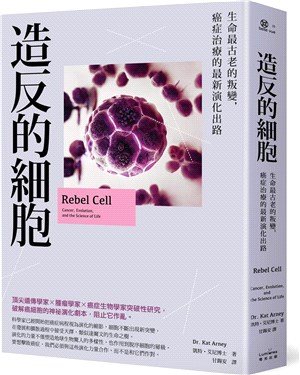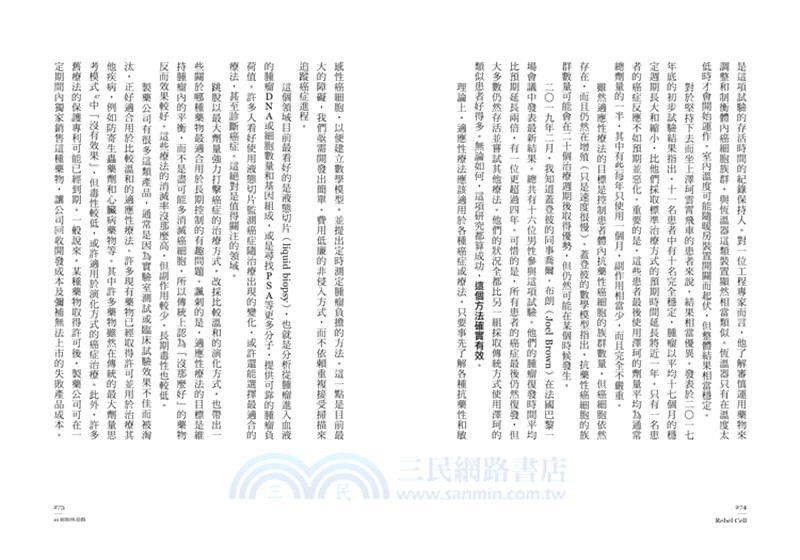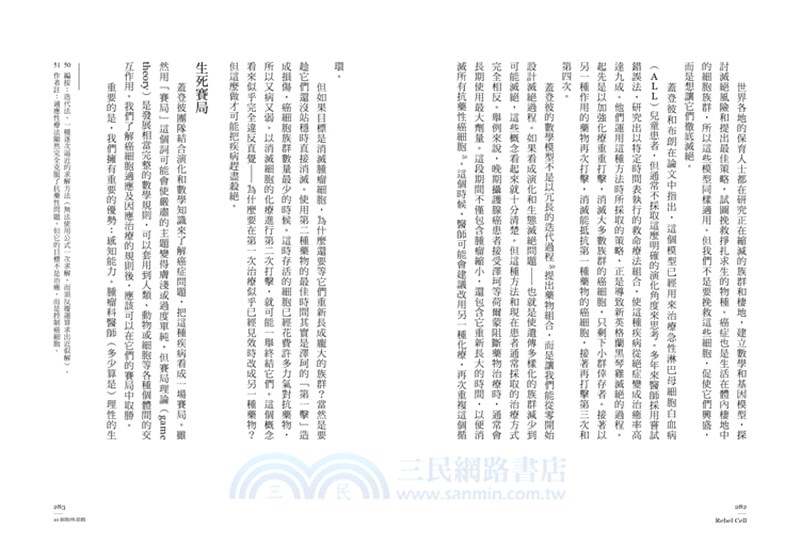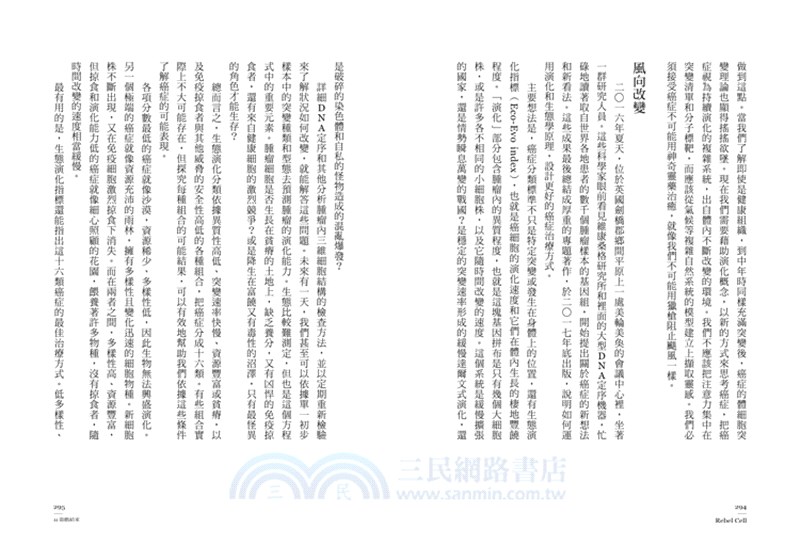造反的細胞:生命最古老的叛變,癌症治療的最新演化出路
商品資訊
系列名:belle vue
ISBN13:9786269584581
替代書名:Rebel Cell: Cancer, Evolution, and the Science of Life
出版社:奇光出版
作者:凱特・艾尼
譯者:甘錫安
出版日:2022/07/06
裝訂/頁數:平裝/352頁
規格:21cm*15cm*2.3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泰晤士報》2020年度最佳書籍★
★2020年Foreword Indie Award健康類獲獎書籍★
生動的癌症研究,內容扎實又深入淺出,腫瘤專家和癌症患者都該一讀!
──《泰晤士報》
頂尖遺傳學家╳腫瘤學家╳癌症生物學家突破性研究,
破解癌細胞的神祕演化劇本,阻止它作亂。
我們迫切需要新的思維來面對癌症的形成,
並且依據演化事實來預防和治療癌症。
◆人類為什麼會罹患癌症?是因為現代飲食和不健康的習慣?環境中的化學物質?不良的基因遺傳?或者純粹只是運氣不佳?答案是都對也都不對。癌症是生命系統本身的缺陷,我們避免不了。
◆揭露醫學最強敵手的諸多奧祕,深入最新研究,探究這些細胞反賊如何在精密的人體社會中造反並掀起大亂。我們正開始破解癌細胞的神祕演化劇本,描繪出這些凶惡細胞生存、興盛或死亡的全貌,並運用這些知識預測及阻絕癌細胞的下一步行動。
◆深度訪談世界知名科學家、癌症專家,包括在遺傳學、腫瘤學、癌症生物學研究上做出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學者專家,如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癌症與演化中心主任馬雷(Carlo Maley)、西班牙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多細胞基因組實驗室主持人路易茲-特里羅(Iñaki Ruiz-Trillo)、英國劍橋維康桑格研究所主任遺傳學家史特拉頓(Mike Stratton)、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懷海德生物醫學研究所癌症研究先驅溫柏格(Robert Weinberg)、英國薩里癌症研究所兒童白血病專家葛里夫斯(Mel Greaves)、英國皇家學會院士腫瘤學家史旺頓(Charles Swanton)、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泌尿學教授皮恩塔(Kenneth Pienta)等癌症研究者領導的頂尖實驗室的卓越研究成果,更為本書增添科學信實佐證。
◆本書是生與死、希望與自滿、先天與後天的故事。探討對於癌症真實樣貌的新思考模式,以及它在人類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它述說癌症從何而來、朝何處去,以及我們應該如何阻止它作亂。
「在這個新世界中,每種癌症在遺傳上都是獨一無二,藉由演化逃脫困境,舊有的藥物開發和臨床試驗模型已經不再適用。它已經成為極度科層化的產業,使用的工具越來越精密,收穫卻越來越少。我們必須大幅進步,才能擊敗如此狡猾的對手。但我們終於開始破解癌症神祕的演化劇本,同時揭露這些脫序細胞生活環境中的生態。我們越來越有希望能運用這些知識預測及阻絕它的下一步,熟練地操縱演化過程本身,控制及塑造腫瘤旺盛的生長。」
──本書作者 凱特・艾尼
科學家已經開始把癌症病程視為演化的縮影,細胞不斷出現新突變,
在發展和擴散過程中接受天擇,類似達爾文的生命之樹。
演化的力量不僅塑造地球生物驚人的多樣性,也作用到脫序細胞的層級。
要想擊敗癌症,我們必須與這些演化力量合作,而不是和它們作對。
癌症是生命系統本身的缺陷
癌症一直伴隨著我們。它殺死我們的原始人類祖先以及史前生物恐龍,腫瘤在寵物和野生動物中生長,即使微小果凍狀的水螅也會罹癌。許多人卻認為癌症是當代殺手,是現代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但事實並非如此。儘管在許多物種中可能很少見,但癌症是潛伏在幾乎所有生物體內的敵人。為什麼?因為癌症是生命系統的一種缺陷。人類罹患癌症是因為我們避免不了。
揭露造反細胞的演化祕密
當細胞反抗,擺脫分子束縛而失控增殖分裂時,癌症就開始了。這就是我們無法避免癌症的原因:因為驅動癌症的基因對生命本身至關重要。革命已經持續了數百萬年,但直到20世紀,醫生和科學家才在了解和治療癌症上取得重大進展,正開始破解癌細胞的神祕演化劇本,描繪出這些凶惡細胞生存、興盛或死亡的全貌,並運用這些知識預測及阻絕癌細胞的下一步行動。
訪談頂尖科學家深入最新研究,解碼癌細胞並阻止它作亂
遺傳學家與獲獎科學作家艾尼一方面解說「我們對癌症所知的一切為什麼都不正確」,一方面以她最具代表性的風趣與明晰帶領讀者深入最新的研究工作,探究這些細胞反賊如何在精細嚴密的人體「社會」中造反並掀起大亂,以及在人類生命中扮演的角色,闡明癌症從何而來、朝何處去,以及我們應該如何阻止它作亂。
★2020年Foreword Indie Award健康類獲獎書籍★
生動的癌症研究,內容扎實又深入淺出,腫瘤專家和癌症患者都該一讀!
──《泰晤士報》
頂尖遺傳學家╳腫瘤學家╳癌症生物學家突破性研究,
破解癌細胞的神祕演化劇本,阻止它作亂。
我們迫切需要新的思維來面對癌症的形成,
並且依據演化事實來預防和治療癌症。
◆人類為什麼會罹患癌症?是因為現代飲食和不健康的習慣?環境中的化學物質?不良的基因遺傳?或者純粹只是運氣不佳?答案是都對也都不對。癌症是生命系統本身的缺陷,我們避免不了。
◆揭露醫學最強敵手的諸多奧祕,深入最新研究,探究這些細胞反賊如何在精密的人體社會中造反並掀起大亂。我們正開始破解癌細胞的神祕演化劇本,描繪出這些凶惡細胞生存、興盛或死亡的全貌,並運用這些知識預測及阻絕癌細胞的下一步行動。
◆深度訪談世界知名科學家、癌症專家,包括在遺傳學、腫瘤學、癌症生物學研究上做出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學者專家,如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癌症與演化中心主任馬雷(Carlo Maley)、西班牙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多細胞基因組實驗室主持人路易茲-特里羅(Iñaki Ruiz-Trillo)、英國劍橋維康桑格研究所主任遺傳學家史特拉頓(Mike Stratton)、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懷海德生物醫學研究所癌症研究先驅溫柏格(Robert Weinberg)、英國薩里癌症研究所兒童白血病專家葛里夫斯(Mel Greaves)、英國皇家學會院士腫瘤學家史旺頓(Charles Swanton)、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泌尿學教授皮恩塔(Kenneth Pienta)等癌症研究者領導的頂尖實驗室的卓越研究成果,更為本書增添科學信實佐證。
◆本書是生與死、希望與自滿、先天與後天的故事。探討對於癌症真實樣貌的新思考模式,以及它在人類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它述說癌症從何而來、朝何處去,以及我們應該如何阻止它作亂。
「在這個新世界中,每種癌症在遺傳上都是獨一無二,藉由演化逃脫困境,舊有的藥物開發和臨床試驗模型已經不再適用。它已經成為極度科層化的產業,使用的工具越來越精密,收穫卻越來越少。我們必須大幅進步,才能擊敗如此狡猾的對手。但我們終於開始破解癌症神祕的演化劇本,同時揭露這些脫序細胞生活環境中的生態。我們越來越有希望能運用這些知識預測及阻絕它的下一步,熟練地操縱演化過程本身,控制及塑造腫瘤旺盛的生長。」
──本書作者 凱特・艾尼
科學家已經開始把癌症病程視為演化的縮影,細胞不斷出現新突變,
在發展和擴散過程中接受天擇,類似達爾文的生命之樹。
演化的力量不僅塑造地球生物驚人的多樣性,也作用到脫序細胞的層級。
要想擊敗癌症,我們必須與這些演化力量合作,而不是和它們作對。
癌症是生命系統本身的缺陷
癌症一直伴隨著我們。它殺死我們的原始人類祖先以及史前生物恐龍,腫瘤在寵物和野生動物中生長,即使微小果凍狀的水螅也會罹癌。許多人卻認為癌症是當代殺手,是現代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但事實並非如此。儘管在許多物種中可能很少見,但癌症是潛伏在幾乎所有生物體內的敵人。為什麼?因為癌症是生命系統的一種缺陷。人類罹患癌症是因為我們避免不了。
揭露造反細胞的演化祕密
當細胞反抗,擺脫分子束縛而失控增殖分裂時,癌症就開始了。這就是我們無法避免癌症的原因:因為驅動癌症的基因對生命本身至關重要。革命已經持續了數百萬年,但直到20世紀,醫生和科學家才在了解和治療癌症上取得重大進展,正開始破解癌細胞的神祕演化劇本,描繪出這些凶惡細胞生存、興盛或死亡的全貌,並運用這些知識預測及阻絕癌細胞的下一步行動。
訪談頂尖科學家深入最新研究,解碼癌細胞並阻止它作亂
遺傳學家與獲獎科學作家艾尼一方面解說「我們對癌症所知的一切為什麼都不正確」,一方面以她最具代表性的風趣與明晰帶領讀者深入最新的研究工作,探究這些細胞反賊如何在精細嚴密的人體「社會」中造反並掀起大亂,以及在人類生命中扮演的角色,闡明癌症從何而來、朝何處去,以及我們應該如何阻止它作亂。
作者簡介
凱特‧艾尼博士(Dr. Kat Arney)
英國首屈一指的科學作家、科學傳播者及講師。擁有劍橋大學自然科學一級學位和發育遺傳學博士學位。2004-2016年在英國癌症研究中心科學傳播團隊擔任要職,參與設立該中心的科學部落格並撰文獲獎,同時擔任中心媒體發言人。作品曾刊載在《連線》(Wired)、《每日郵報》(Daily Mail)、《自然》(Nature)、《馬賽克》(Mosaic)、《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等期刊。也曾參與數個BBC Radio 4科學紀實節目、紀實喜劇《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搞砸了世界嗎?》(Did the Victorians Ruin the World?),以及兩週一次的Podcast節目《遺傳學解密》(Genetics Unzipped)。另著有《海明威的貓:基因如何運作》(Herding Hemingway's Cats: Understanding How Our Genes Work)和《如何設定人類遺傳密碼》(How to Code a Human)。
英國首屈一指的科學作家、科學傳播者及講師。擁有劍橋大學自然科學一級學位和發育遺傳學博士學位。2004-2016年在英國癌症研究中心科學傳播團隊擔任要職,參與設立該中心的科學部落格並撰文獲獎,同時擔任中心媒體發言人。作品曾刊載在《連線》(Wired)、《每日郵報》(Daily Mail)、《自然》(Nature)、《馬賽克》(Mosaic)、《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等期刊。也曾參與數個BBC Radio 4科學紀實節目、紀實喜劇《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搞砸了世界嗎?》(Did the Victorians Ruin the World?),以及兩週一次的Podcast節目《遺傳學解密》(Genetics Unzipped)。另著有《海明威的貓:基因如何運作》(Herding Hemingway's Cats: Understanding How Our Genes Work)和《如何設定人類遺傳密碼》(How to Code a Human)。
名人/編輯推薦
【名家推薦】
◆《泰晤士報》
生動的癌症研究,闡明了癌症是我們為極其複雜的身體所付出的代價。
◆丹尼爾‧戴維斯(Daniel M. Davis)│《絕美靈藥》(The Beautiful Cure)作者
這本書中有滿滿的生物重要概念。每一章都有讓我大感驚奇之處。艾尼在知名癌症基金會工作多年,作品擁有深入又扎實的理解,是絕佳的引路人。
◆查克‧韋納史密斯(Zach Weinersmith)│《拯救或毀滅世界的十種新創科技》作者
本書不只是癌症的歷史或科學發展,艾尼還提出探究癌症時的思考方式。
◆史蒂芬‧麥甘(Stephen McGann)│《呼叫助產士》(Call the Midwife)編劇及演員
艾尼是適合所有讀者的科學作家,她是優秀又有才華的敘事大師。
◆達拉斯‧坎貝爾(Dallas Campbell)│科學傳播者與《Ad Astra》作者
本書通透清晰地再次呈現那個我們聞之色變的病症背後的故事。想深入了解這個對手,一定要讀這本書。它是科普寫作界破解迷思的經典之作。
◆勞倫斯‧赫斯特(Laurence D. Hurst)│米爾納演化中心主任及遺傳學會理事長
世界上沒有神奇子彈和許多人大肆炒作的靈丹妙藥。要提高癌症患者的康復機率,需要革命性的全新思考方式。艾尼強而有力地指出,這個全新的思考方式會隨時間演變。全世界的腫瘤專家都應該一讀這本文字輕鬆、內容扎實又深入淺出的作品。這本書也有力地證明,生物學中任何事物都必須由演化角度思考才能理解,癌症也不例外。
◆馬克‧史蒂文森(Mark Stevenson)│未來學家,著有《重新啟動世界》(We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 Outsiders Rebooting Our World)
凱特‧艾尼再推新作。她把複雜主題變得單純容易,把神祕難解變得容易理解,提出正確的問題,找出令人驚奇的答案,而且呈現方式既幽默又風趣。如果醫療從業人員能和凱特在這本令人手不釋卷的書中表現一樣,懂得如何與大眾以及彼此溝通,對抗癌症的戰爭將會比現在進展更大。
◆《泰晤士報》
生動的癌症研究,闡明了癌症是我們為極其複雜的身體所付出的代價。
◆丹尼爾‧戴維斯(Daniel M. Davis)│《絕美靈藥》(The Beautiful Cure)作者
這本書中有滿滿的生物重要概念。每一章都有讓我大感驚奇之處。艾尼在知名癌症基金會工作多年,作品擁有深入又扎實的理解,是絕佳的引路人。
◆查克‧韋納史密斯(Zach Weinersmith)│《拯救或毀滅世界的十種新創科技》作者
本書不只是癌症的歷史或科學發展,艾尼還提出探究癌症時的思考方式。
◆史蒂芬‧麥甘(Stephen McGann)│《呼叫助產士》(Call the Midwife)編劇及演員
艾尼是適合所有讀者的科學作家,她是優秀又有才華的敘事大師。
◆達拉斯‧坎貝爾(Dallas Campbell)│科學傳播者與《Ad Astra》作者
本書通透清晰地再次呈現那個我們聞之色變的病症背後的故事。想深入了解這個對手,一定要讀這本書。它是科普寫作界破解迷思的經典之作。
◆勞倫斯‧赫斯特(Laurence D. Hurst)│米爾納演化中心主任及遺傳學會理事長
世界上沒有神奇子彈和許多人大肆炒作的靈丹妙藥。要提高癌症患者的康復機率,需要革命性的全新思考方式。艾尼強而有力地指出,這個全新的思考方式會隨時間演變。全世界的腫瘤專家都應該一讀這本文字輕鬆、內容扎實又深入淺出的作品。這本書也有力地證明,生物學中任何事物都必須由演化角度思考才能理解,癌症也不例外。
◆馬克‧史蒂文森(Mark Stevenson)│未來學家,著有《重新啟動世界》(We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 Outsiders Rebooting Our World)
凱特‧艾尼再推新作。她把複雜主題變得單純容易,把神祕難解變得容易理解,提出正確的問題,找出令人驚奇的答案,而且呈現方式既幽默又風趣。如果醫療從業人員能和凱特在這本令人手不釋卷的書中表現一樣,懂得如何與大眾以及彼此溝通,對抗癌症的戰爭將會比現在進展更大。
序
前言
「癌症起於一個細胞出現基因突變並開始失控地增殖。」
我踏入科學寫作領域以來,包括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基金會科學傳播團隊工作的十二年間,不知道以各種方式寫了多少次這個句子。但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句話真正的意義,或是這句話可能根本不對。
癌症是影響全人類的疾病。即使我們自己或鍾愛的人幸運地沒有被癌症找上,這種疾病依然是全球健康問題,每年有數百萬人因而失去生命。幾千年來,科學家和醫師一直在努力發掘它的原因、結果和治療方法,但直到二十世紀後半才算取得重大進展。現在英國的癌症確診患者中,大約有一半可以存活十年以上,這個數字未來應該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對樂觀者而言,這個玻璃杯是半滿的。
我們已經知道如何治療癌症。更正確地說,我們已經知道如何治療某些癌症。最好的方法是盡早發現癌細胞,趁癌細胞還沒擴散到體內各處(稱為轉移〔metastasis〕),就以精密的外科手術摘除。在遏阻乳癌和攝護腺癌方面,如果運用時機正確,放射治療可能有效,荷爾蒙療法的效果可能相當好。化療對許多血液癌症效果非常好,尤其是用在兒童身上;藥物治療甚至連晚期睪丸癌也可完全治癒。新一代免疫療法的成效相當優異,但目前這種療法只對不到五分之一的患者有效。然而,對於大多數已不幸面臨癌症開始在體內肆虐的患者而言,問題就從「我能不能好轉?」變成「我還有多少時間?」。沒有疑問,只是時間問題。
這個狀況相當類似於一九七一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宣告「抗癌戰爭」開始時的狀況。尼克森為了轉移大眾對越戰的注意,同時企圖藉助阿波羅登月任務激發的冒險精神,因而投入數百萬美元,希望在十年內找出治療癌症藥物。然而,正如在遠東地區不幸失利一樣,他低估了對手。一九八六年,統計學家約翰‧貝拉爾(John Bailar)做了計算:儘管有少數病例成功治癒,晚期癌症絕大多數依然無法治癒。依據貝拉爾的說法,這場抗癌戰爭已視為「雖敗猶榮」。
雖然我們對抗某幾種癌症已經取得一些進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可怕的黑色素瘤),但如果仔細觀察現在的統計數字,也可發現相同的模式。越來越多人在早期即診斷出預後良好的癌症,因此大幅提高整體數字。但晚期轉移性癌症的存活時間仍然只能以月或年計算,難以達到數十年以上。
主要問題是外科手術和放射治療等精密工具對擴散的癌症沒有效果,而化療的原理是消滅癌細胞的速度快於癌細胞攻占正常細胞,效果並不佳。即使有效,腫瘤也幾乎一定會復發,可能是幾星期、幾個月或幾年後,而且其後每次治療對健康危害更大,效果則越來越差。這半滿的玻璃杯其實極難裝滿。
二十世紀開始時,剛成立的英國皇家癌症研究基金會的科學家忙著在實驗室培養小鼠癌細胞,希望發掘這類異常增殖的奧祕。研究人員對這些細胞無窮無盡的再生能力大感驚奇,研究總監恩尼斯特‧巴希弗德(Ernest Bashford)一九○五年在基金會的科學報告中指出:「在人工繁殖下,一個小鼠腫瘤生成的組織總量,足以組成體型和聖伯納犬相仿的超大型老鼠。」
現在我們已經比較了解細胞掙脫分子約束的全貌。造反者出現在文明有序的多元細胞社會中,對正常生命發出混雜無章的嘲弄,失控地生長和分裂。一個細胞變成兩個,兩個變成四個,四個變成八個,不斷累積,形成數百萬以上的暴徒。但它們還不滿足。這些造反者侵略破壞周圍的正常組織,讓人體內的警察亦即免疫系統忽視它們。它們偷偷潛入血液,經由血管四處遊走,成立分支和安置潛伏細胞。每個癌細胞都受我們自身脫序的基因驅動――基因是告知細胞何時分裂、發育成什麼,甚至何時死亡的遺傳說明書。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認為,「癌症靈藥」的關鍵是了解腫瘤細胞內出錯的基因和分子。二十世紀的大半時間,有一小群科學家一直在做這項工作,花費的金錢難以估計。研究人員從全世界數千名癌症患者的腫瘤和健康組織樣本提取、判讀和分析DNA,數不清的字母拼寫出生命的說明手冊,其中的錯字被認為是導致癌細胞生長與擴散的原因。但這些資訊沒有提出解答,反而揭露腫瘤內部比以往所知更多的遺傳混亂。
我們能觀察到菸草煙霧或太陽紫外線在基因組中造成的傷害。有證據指出保護細胞的生物防衛機制可能失效,甚至轉而攻擊我們。有些奇怪的痕跡則原因不明,或許有一天能歸因於環境中的有害化學物質或新的分子過程。DNA分析發現了規模或大或小的損傷跡象,有些是少許錯字,有些則是整個染色體打散後重新結合的大規模遺傳災難。更令人困惑的是,現在我們知道即使是完全健康的組織,到我們中年時也會有許多突變細胞,其中有許多可歸類為癌症突變。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研究指出,使一個細胞變成腫瘤的基因改變不一致也不固定。世界上沒有單一的「癌症基因」,所以也沒有單一的「癌症靈藥」。每個人的腫瘤基因組成都有明顯差異,連每一顆腫瘤的微小範圍內的基因錯誤也有變化。每種癌症都是由不同細胞群構成的基因拼布,任何一種都可能帶有阻礙治療效果的基因改變。癌症一旦發展到一定的大小和多樣性,復發將無可避免。
科學家已經開始把癌症病程視為演化的縮影,細胞不斷出現新突變,在發展和擴散過程中接受天擇,類似達爾文的生命之樹。我們在這裡發現癌症另一個令人不安的生物學真相:癌症在我們體內發展時,驅動地球生物演化的過程無可避免地也在發揮作用。
更糟的是,原本用於挽救生命的療法反而成為協助癌症演化的選擇壓力,這些療法消滅對藥物敏感的癌細胞,讓具抗藥性的細胞更加繁盛。不幸的是,沒有殺死癌症的,一定會使它更強大;等它捲土重來,則將勢不可擋。難怪目前的治療方法對如此可怕的怪物束手無策。
我們迫切需要新的思維來面對癌症的形成,並且依據演化事實來預防和治療癌症。我們必須更清楚地了解在腫瘤內演化的脫序細胞,以及它們生活的環境,把它們視為隨時間改變的族群,而不是能以簡單的突變清單描述的固定實體。德國生物學家理查‧戈德施密特(Richard Goldschmidt)提出「有希望的怪物」(hopeful monster)這個名詞來描述寒武紀史前海洋中在極短時間內發展出全新特性的生物。癌細胞則是「自私的怪物」,瘋狂又急速地在患者的生存時間內演化。饑荒或掠食者往往成為塑造物種的選擇壓力,同樣地,癌細胞也會回應選擇,在人體內的生態系中上演演化戲碼。
在這個新世界中,每種癌症在遺傳上都是獨一無二,藉由演化逃脫困境,舊有的藥物開發和臨床試驗模型已經不再適用。它已經成為極度科層化的產業,使用的工具越來越精密,收穫卻越來越少。我們必須大幅進步,才能擊敗如此狡猾的對手。但我們終於開始破解癌症神祕的演化劇本,同時揭露這些脫序細胞生活環境中的生態。我們越來越有希望能運用這些知識預測及阻絕它的下一步,熟練地操縱演化過程本身,控制及塑造腫瘤旺盛的生長。
二〇一九年一月,我正在撰寫本書第一版初稿時,我的推特出現一則消息,一家以色列生技公司開發出能治療各種癌症的藥物,並將於一年內上市。儘管有許多未經驗證的轉推和媒體報導,但這種療法僅在小鼠身上測試過,也沒有臨床資料足以支持,代表這項宣布造福的對象很可能只有公司財務,而不是可預見的將來的癌症患者。可以想見,一年之後,這種「神奇靈藥」仍然還在開發中,而且沒有任何患者接受過治療。
令人氣憤的是,揭穿這類過度吹捧的神奇靈藥和徹底胡扯的文章所得到的點擊通常比原始報導少很多。這個問題由來已久。一九〇四年,倫敦聖巴托羅繆醫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外科醫師達西‧鮑爾爵士(D’Arcy Power)在《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寫了一篇措辭激烈的論文,批評德國的奧圖‧史密特醫師(Otto Schmidt)偽造癌症藥物。他指出,史密特的無效藥物「出乎意料地廣為流行,如同刊載在《每日郵報》上的長摘要」。
我們願意相信世界上有「癌症靈藥」,這個名詞已經深植於我們的文化意識,代表能完全根治這種疾病。我們希望這些時間、金錢、心力、痛苦與失去的生命都能讓我們更接近發現這種靈藥。我們很容易受特效藥、靈丹和奇蹟等話題吸引。改以演化和生態的新方式來思考癌症,需要改變心態――不只從科學和醫學界的觀點,還要從患者和大眾的觀點來看,因為期待已久的解決方案可能會和我們的預期不完全相同。
「癌症起於一個細胞出現基因突變並開始失控地增殖。」
我踏入科學寫作領域以來,包括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基金會科學傳播團隊工作的十二年間,不知道以各種方式寫了多少次這個句子。但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句話真正的意義,或是這句話可能根本不對。
癌症是影響全人類的疾病。即使我們自己或鍾愛的人幸運地沒有被癌症找上,這種疾病依然是全球健康問題,每年有數百萬人因而失去生命。幾千年來,科學家和醫師一直在努力發掘它的原因、結果和治療方法,但直到二十世紀後半才算取得重大進展。現在英國的癌症確診患者中,大約有一半可以存活十年以上,這個數字未來應該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對樂觀者而言,這個玻璃杯是半滿的。
我們已經知道如何治療癌症。更正確地說,我們已經知道如何治療某些癌症。最好的方法是盡早發現癌細胞,趁癌細胞還沒擴散到體內各處(稱為轉移〔metastasis〕),就以精密的外科手術摘除。在遏阻乳癌和攝護腺癌方面,如果運用時機正確,放射治療可能有效,荷爾蒙療法的效果可能相當好。化療對許多血液癌症效果非常好,尤其是用在兒童身上;藥物治療甚至連晚期睪丸癌也可完全治癒。新一代免疫療法的成效相當優異,但目前這種療法只對不到五分之一的患者有效。然而,對於大多數已不幸面臨癌症開始在體內肆虐的患者而言,問題就從「我能不能好轉?」變成「我還有多少時間?」。沒有疑問,只是時間問題。
這個狀況相當類似於一九七一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宣告「抗癌戰爭」開始時的狀況。尼克森為了轉移大眾對越戰的注意,同時企圖藉助阿波羅登月任務激發的冒險精神,因而投入數百萬美元,希望在十年內找出治療癌症藥物。然而,正如在遠東地區不幸失利一樣,他低估了對手。一九八六年,統計學家約翰‧貝拉爾(John Bailar)做了計算:儘管有少數病例成功治癒,晚期癌症絕大多數依然無法治癒。依據貝拉爾的說法,這場抗癌戰爭已視為「雖敗猶榮」。
雖然我們對抗某幾種癌症已經取得一些進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可怕的黑色素瘤),但如果仔細觀察現在的統計數字,也可發現相同的模式。越來越多人在早期即診斷出預後良好的癌症,因此大幅提高整體數字。但晚期轉移性癌症的存活時間仍然只能以月或年計算,難以達到數十年以上。
主要問題是外科手術和放射治療等精密工具對擴散的癌症沒有效果,而化療的原理是消滅癌細胞的速度快於癌細胞攻占正常細胞,效果並不佳。即使有效,腫瘤也幾乎一定會復發,可能是幾星期、幾個月或幾年後,而且其後每次治療對健康危害更大,效果則越來越差。這半滿的玻璃杯其實極難裝滿。
二十世紀開始時,剛成立的英國皇家癌症研究基金會的科學家忙著在實驗室培養小鼠癌細胞,希望發掘這類異常增殖的奧祕。研究人員對這些細胞無窮無盡的再生能力大感驚奇,研究總監恩尼斯特‧巴希弗德(Ernest Bashford)一九○五年在基金會的科學報告中指出:「在人工繁殖下,一個小鼠腫瘤生成的組織總量,足以組成體型和聖伯納犬相仿的超大型老鼠。」
現在我們已經比較了解細胞掙脫分子約束的全貌。造反者出現在文明有序的多元細胞社會中,對正常生命發出混雜無章的嘲弄,失控地生長和分裂。一個細胞變成兩個,兩個變成四個,四個變成八個,不斷累積,形成數百萬以上的暴徒。但它們還不滿足。這些造反者侵略破壞周圍的正常組織,讓人體內的警察亦即免疫系統忽視它們。它們偷偷潛入血液,經由血管四處遊走,成立分支和安置潛伏細胞。每個癌細胞都受我們自身脫序的基因驅動――基因是告知細胞何時分裂、發育成什麼,甚至何時死亡的遺傳說明書。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認為,「癌症靈藥」的關鍵是了解腫瘤細胞內出錯的基因和分子。二十世紀的大半時間,有一小群科學家一直在做這項工作,花費的金錢難以估計。研究人員從全世界數千名癌症患者的腫瘤和健康組織樣本提取、判讀和分析DNA,數不清的字母拼寫出生命的說明手冊,其中的錯字被認為是導致癌細胞生長與擴散的原因。但這些資訊沒有提出解答,反而揭露腫瘤內部比以往所知更多的遺傳混亂。
我們能觀察到菸草煙霧或太陽紫外線在基因組中造成的傷害。有證據指出保護細胞的生物防衛機制可能失效,甚至轉而攻擊我們。有些奇怪的痕跡則原因不明,或許有一天能歸因於環境中的有害化學物質或新的分子過程。DNA分析發現了規模或大或小的損傷跡象,有些是少許錯字,有些則是整個染色體打散後重新結合的大規模遺傳災難。更令人困惑的是,現在我們知道即使是完全健康的組織,到我們中年時也會有許多突變細胞,其中有許多可歸類為癌症突變。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研究指出,使一個細胞變成腫瘤的基因改變不一致也不固定。世界上沒有單一的「癌症基因」,所以也沒有單一的「癌症靈藥」。每個人的腫瘤基因組成都有明顯差異,連每一顆腫瘤的微小範圍內的基因錯誤也有變化。每種癌症都是由不同細胞群構成的基因拼布,任何一種都可能帶有阻礙治療效果的基因改變。癌症一旦發展到一定的大小和多樣性,復發將無可避免。
科學家已經開始把癌症病程視為演化的縮影,細胞不斷出現新突變,在發展和擴散過程中接受天擇,類似達爾文的生命之樹。我們在這裡發現癌症另一個令人不安的生物學真相:癌症在我們體內發展時,驅動地球生物演化的過程無可避免地也在發揮作用。
更糟的是,原本用於挽救生命的療法反而成為協助癌症演化的選擇壓力,這些療法消滅對藥物敏感的癌細胞,讓具抗藥性的細胞更加繁盛。不幸的是,沒有殺死癌症的,一定會使它更強大;等它捲土重來,則將勢不可擋。難怪目前的治療方法對如此可怕的怪物束手無策。
我們迫切需要新的思維來面對癌症的形成,並且依據演化事實來預防和治療癌症。我們必須更清楚地了解在腫瘤內演化的脫序細胞,以及它們生活的環境,把它們視為隨時間改變的族群,而不是能以簡單的突變清單描述的固定實體。德國生物學家理查‧戈德施密特(Richard Goldschmidt)提出「有希望的怪物」(hopeful monster)這個名詞來描述寒武紀史前海洋中在極短時間內發展出全新特性的生物。癌細胞則是「自私的怪物」,瘋狂又急速地在患者的生存時間內演化。饑荒或掠食者往往成為塑造物種的選擇壓力,同樣地,癌細胞也會回應選擇,在人體內的生態系中上演演化戲碼。
在這個新世界中,每種癌症在遺傳上都是獨一無二,藉由演化逃脫困境,舊有的藥物開發和臨床試驗模型已經不再適用。它已經成為極度科層化的產業,使用的工具越來越精密,收穫卻越來越少。我們必須大幅進步,才能擊敗如此狡猾的對手。但我們終於開始破解癌症神祕的演化劇本,同時揭露這些脫序細胞生活環境中的生態。我們越來越有希望能運用這些知識預測及阻絕它的下一步,熟練地操縱演化過程本身,控制及塑造腫瘤旺盛的生長。
二〇一九年一月,我正在撰寫本書第一版初稿時,我的推特出現一則消息,一家以色列生技公司開發出能治療各種癌症的藥物,並將於一年內上市。儘管有許多未經驗證的轉推和媒體報導,但這種療法僅在小鼠身上測試過,也沒有臨床資料足以支持,代表這項宣布造福的對象很可能只有公司財務,而不是可預見的將來的癌症患者。可以想見,一年之後,這種「神奇靈藥」仍然還在開發中,而且沒有任何患者接受過治療。
令人氣憤的是,揭穿這類過度吹捧的神奇靈藥和徹底胡扯的文章所得到的點擊通常比原始報導少很多。這個問題由來已久。一九〇四年,倫敦聖巴托羅繆醫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外科醫師達西‧鮑爾爵士(D’Arcy Power)在《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寫了一篇措辭激烈的論文,批評德國的奧圖‧史密特醫師(Otto Schmidt)偽造癌症藥物。他指出,史密特的無效藥物「出乎意料地廣為流行,如同刊載在《每日郵報》上的長摘要」。
我們願意相信世界上有「癌症靈藥」,這個名詞已經深植於我們的文化意識,代表能完全根治這種疾病。我們希望這些時間、金錢、心力、痛苦與失去的生命都能讓我們更接近發現這種靈藥。我們很容易受特效藥、靈丹和奇蹟等話題吸引。改以演化和生態的新方式來思考癌症,需要改變心態――不只從科學和醫學界的觀點,還要從患者和大眾的觀點來看,因為期待已久的解決方案可能會和我們的預期不完全相同。
目次
Contents
前言
1 細說從頭
2 生命的代價
3 巧取豪奪的細胞
4 找出所有基因
5 好細胞變壞時
6 自私的怪物
7 探索癌症星球
8 怪者生存
9 無用的藥物
10 細胞株遊戲
11 遊戲結束
致謝
名詞解釋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前言
1 細說從頭
2 生命的代價
3 巧取豪奪的細胞
4 找出所有基因
5 好細胞變壞時
6 自私的怪物
7 探索癌症星球
8 怪者生存
9 無用的藥物
10 細胞株遊戲
11 遊戲結束
致謝
名詞解釋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書摘/試閱
9 無用的藥物
二○一五年耶誕節前,英國資訊顧問克里斯潘‧亞戈(Crispian Jago)住院接受手術,準備摘除已經擴散到肝臟的龐大腎臟腫瘤。手術看來相當成功,但第二年夏天復發――這次狀況看來不大樂觀。這類狀況一向很難精確預測,但醫師說他的壽命大概只剩下一年半左右。出乎意料,我聯絡他時他還活著,但從他最初確診已經過了將近四年。不過他多活了這麼久,不是因為現代化基因定序和分子標靶藥物,他從來沒有分析過腫瘤的DNA。相反地,他沒死是因為英國南安普敦大學醫院腫瘤科醫師馬修‧惠特(Matthew Wheater)有根據的猜測。
首先,克里斯潘嘗試服用福退癌(Votrient,學名pazopanib)。這種藥物起初似乎有效,三個月後腫瘤縮小了一成左右。但他的好運沒有維持下去,癌細胞演化出抗藥性。二○一七年夏天,腫瘤持續生長,擴散到體內各處,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
他開始服用新的免疫藥物保疾伏(Opdivo,學名nivolumab),這種藥物對某些患者有效,但不是所有患者都會見效。他剛好不屬於幸運的一群,治療開始僅兩個月,就看得出完全沒有幫助。雖然福退癌只控制癌症一年,這段時間也足以讓他等到新的療法。
惠特醫師放棄保疾伏之後,讓克里斯潘改用剛剛取得英國國民保健署許可的癌必定(Cabometyx,學名cabozantinib)。開始治療不到一星期,他就感到好轉;幾個月內,癌症就消失九十五%。讓醫師驚訝的是,這種藥物似乎控制住了癌症,不過腫瘤相關知識顯示,抗藥性到某個時候一定會出現。即使如此,克里斯潘依然樂觀地認為會有結果。他聳了聳肩說:「我覺得我就站在鬼門關前了,必須盡量活久一點,等下一種藥出現。」我不認為末期癌症患者一定會病懨懨的,而他看來很好又活力十足,很難想像他的身體已經漸漸被這些自私的細胞占據。我留意到的主要改變是他的頭髮和鬍子在一年內從深棕色變成驚人的白色。即使是在盛夏,他也穿著三件式毛呢西裝,忙著買下他找到的所有平佛洛伊德的專輯。如果我這輩子遭遇逆境時能有一點點他這幾年來的積極、堅忍和幽默感,我就很高興了。
他說:「當時他們告訴我癌症已經擴散,沒辦法動手術。我女兒英迪當時念大一,還有兩年才畢業。他們說我還有八個月,所以我想:好吧,我大概看不到了,但至少可以當成目標。」
他不只看到英迪以最高成績畢業,還很有信心能看到小兒子彼得在二○二○年取得學位。當時彼得已經二十一歲,我覺得機會很大。
除了努力活到小孩的畢業典禮,克里斯潘在這期間還有一個目標,就是活得比年老的拉布拉多犬威爾伯特更久。這隻狗的好運很遺憾地結束於二○一八年十月,現在埋在克里斯潘和太太多麗同住的可愛鄉間小屋花園裡。我撰寫這本書時,他覺得身體還算不錯,喜歡跟接替威爾伯特的黑色拉布拉多犬史丹利一起玩。
但是也有些不大好的消息。二○一九年夏天的掃描結果顯示,有個腫瘤長在他的腦部前端。雖然治療讓癌症僅限於頸部以下,但療效無法越過腦部和血液間的屏障,與偷偷摸摸行動的癌細胞不同。這顯然是個大炸彈,但他不擔心為了控制這個不受歡迎的新成員而必須接受放射線治療,反而比較煩惱不能開他心愛的保時捷。
跳脫打地鼠遊戲
一般腫瘤發展到目前技術可以診斷時,可能含有數十億到一兆個細胞,每個細胞可能都含有幾萬個基因突變和改變。它已經是個複雜的生態系,有許多不同的細胞物種在多樣化的微棲地中生活和死亡――有些物種習慣於缺氧的毒性沼澤,有些則喜歡比較舒適的環境。
每個人的癌症都是獨一無二的雪花,取決於原本的基因組成和塑造它的演化過程。它發展到開始擴散的時候,抗藥性和復發基本上已經無可避免。在某個地方,會有一些癌細胞能抵擋我們的醫學攻勢。諷刺的是,藥物目標越明確、越特殊,癌症越容易演化出對抗的方法。
克里斯潘令人驚奇的存活,是一百多年來人類專注研究的親身證言。這類成功經驗溫暖了慈善募款機構的心,也讓製藥公司賺得風生水起。但現代腫瘤醫學已經變成典型的生物領域打地鼠遊戲:先嘗試一種療法、等這種療法失效時再試另一種,如此不斷重複,直到沒有選擇為止。這個結果遲早都會到來,取決於腫瘤種類和可使用的療法而定。
精準腫瘤醫學的概念逐漸成為癌症治療的主流思想。這個概念原本的用意是以癌細胞中特定的錯誤分子為目標,例如基利克的目標是造成白血病的費城染色體,賀癌平(Herceptin,學名trastuzumab)的目標則是具有額外癌症驅動基因HER2的乳癌細胞,並且要先以診斷檢驗判定哪些患者適合採用這種療法。
這個定義有時會擴大到包含所有用於阻斷癌細胞內特定訊號的療法,也包含克里斯潘使用的福退癌和癌必定,這兩種都是酪胺酸激酶抑制劑,可阻斷癌細胞中數種不同的增殖訊號。這類藥物被視為「智慧型」藥物,與「愚笨」的傳統化療藥物不同。
腫瘤科醫師逐漸習慣依據特定的錯誤基因或分子(可行動突變)來選擇療法,而不管腫瘤發生在體內的位置。腫瘤在膀胱、腸道或乳房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這些細胞是否含有能以藥物消滅的突變。在此之前,基因檢測的費用很高,所以這種方式只適用於有限的常見目標。但DNA定序技術速度更快、費用更低之後,定序整個腫瘤基因組,尋找可行動突變將逐漸成為主流。
依據個別患者腫瘤的特定驅動突變而選擇藥物的概念,迅速從幻想化為實際。這種方式令人驚奇又有未來感,而且符合現代想法,認為應該針對每個人的腫瘤精準選擇個人化療法,而不是一體適用的標準化程序。這個精準腫瘤醫學典範已經成為癌症研究領域的信條,清楚證明三十多年來製作癌症基因清單和開發聰明(但十分昂貴的)藥物所投入的心力是值得的。
許多人非常看好這種方式改變晚期轉移性癌症患者存活時間的潛力,然而實際上的表現並不符合期待。目前為止,實際狀況是大多數人的癌症沒有接受檢測或沒有適用的基因改變可讓這些神奇子彈當成目標。
美國奧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腫瘤醫學家維內‧普拉薩德(Vinay Prasad)和同事,研究二○○六年以來美國食品藥物署(FDA)核准搭配患者腫瘤基因檢測使用的三十多種標靶藥物。十二年前在美國診斷出罹患轉移型癌症的五十多萬人中,大約有五%可以使用這類療法。到二○一八年,這個數字只提高八%左右。別忘了,這只是接受癌症檢測後可能適用的患者。有許多人從來沒有接受過腫瘤基因檢測,原因可能是費用和實用性。此外,即使基因檢測指出這些極度昂貴的療法確實有效,也沒辦法保證英國國民保健署或醫療保險會支付這些費用。
更糟的是,它的效益相當有限。普拉薩德估計,適用於基因檢測所選標靶療法的患者本來就少,真正有效益的只有略多於一半,效果平均只能持續兩年半。整體說來,適合使用基因標靶療法的人數每年僅緩步增加○.五%左右。雖然有總比沒有好,但絕對不是媒體形容的癌症療法的「量子躍遷」。
新聞標題拚命講聖杯、重大改變、奇蹟和神奇靈丹。有人說這些新療法是改變現狀的全壘打,終於帶來我們追尋已久的癌症靈藥。但就算不要說得太悲觀或忽視近年來延長存活時間的進展,實際狀況也沒有那麼美好。
在另一項研究中,普拉薩德探討使用這類誇張詞句形容新癌症藥物的新聞報導,發現這些療法有一半尚未取得FDA核准,只有七分之一曾經進行實驗室研究,用在人類患者身上還早得很。這類誇張修辭大多是過度興奮的記者的傑作,但醫師、業界專家、患者和政治人物也有散布過度誇大成功經驗之嫌。
以基因檢測決定療法越來越普遍,但本身也面臨挑戰。二○一七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一個研究團隊把九名癌症患者的腫瘤樣本寄給兩家提供最新DNA定序技術檢測突變的公司。定序結果應該會讓認為這類尖端精準腫瘤技術即將大展身手的人感到憂心。
兩家公司的結果都指出其中一名患者沒有檢測得出的基因改變。至於其餘八名患者,兩家公司從樣本檢測出的基因突變只有五分之一相同。兩家公司依據檢測結果提出建議標靶藥物時,有五名患者的建議療法組合完全不同。排除兩方檢測的技術差異或不一致後,這個結果仍然不令人意外。我們已經知道,一般腫瘤是基因各不相同的細胞株拼布,發現的突變也取決於取得及送檢的樣本。
這個精準醫學典範還有其他問題。舉例來說,在腫瘤中發現可行動的突變,不表示標靶藥物一定有效。研究人員現在發現,以出現在許多癌症中的錯誤基因為目標的藥物對某幾種腫瘤有效,但是有些腫瘤儘管具有「適合」的突變,這些藥物仍然沒有效果。
例如標靶療法招牌藥物日沛樂的目標是阻斷BRAF基因中某個突變造成的增殖訊號過度活化。對於含有這種錯誤基因的惡性黑色素瘤患者而言,這種藥物有助於延長壽命,但對含有相同突變的腸癌患者則沒有幫助。腫瘤細胞能迅速「重接」內部路徑,活化替代訊號,讓它們繼續迅速增殖。
許多人認為現代「智慧型藥物」的副作用較少,所以優於「傷身的化療」。這個觀念源自傳統靜脈注射化療,這類化療每次間隔數星期,某些患者會有幾天不舒服的副作用,接著緩和一陣子。我們或許會想,這類聰明的新療法應該能為患者帶來比較好的生活品質,但其實不一定如此。
有一項研究觀察三十八項新藥物臨床試驗結果,這些試驗涵括將近一萬四千名罹患十二種癌症的患者,但沒有發現存活時間和「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之間有明顯關聯。「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是身體、情緒和社交健康程度,以及對工作或其他事務的影響。整體而言,與接受對照治療的患者相比,新藥物使癌症復發時間平均延後一.九個月。
克里斯潘接受第一次福退癌治療時,副作用嚴重到必須住院。這種狀況不常見但不算前所未聞。此外,現在有許多標靶療法是每天服用藥錠,每天的副作用很快就會消退。比方說,醫師所謂「第三/四級腹瀉」的定義是一天上七次廁所,但臨床試驗認為這種狀況「可接受」。如果服用這種藥物真的能挽救生命,依據上廁所規畫日常生活或許是應該付出的合理代價,但許多這類藥物的存活效用最多只能算是中等。
最後還有一個最大但沒有人真心想討論的問題。新聞標題或許很吸引人,但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這些亮眼新藥並不是靈丹,而且差得很遠。人類雖然相當擅於治療早期癌症,尤其是在比較富裕的國家,但晚期轉移性癌症的存活時間通常仍然只有幾個月或十年內(當然一定有例外)。
二○一四年,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教授提托‧佛荷(Tito Fojo)觀察二○○二到二○○四年間上市的七十多種癌症新藥,這些藥物的費用每年高達數千美元。儘管聲勢驚人,但這些新藥延長的存活時間平均只有兩個月。另一個研究團隊的後續報告把時間拉長到略少於三個半月,但可能過度樂觀,原因是它只看短期臨床試驗結果,不看較長的後續時間。
偶爾也有奇蹟出現。有年輕母親或頗受敬愛的祖父得知自己只剩下幾個月時間,但因為某種新的「仙丹」而「打臉醫師」;或是像克里斯潘這樣持續存活下來,對癌症說不。沒有人真的是「平均值」,而且活久一點真的很重要,但這類藥物的存活時間其實大多只比傳統療法長幾個月。此外,它們現在已經是地球上最昂貴的藥物。以重量而言,一般標靶藥物的價格是鈽的六倍,最新的CAR-T免疫療法的價格更高達每公克十億美元。但藥價與效果或延長存活時間其實沒什麼關聯。
所以我們必須問,為什麼這麼多新藥動輒每年要價數萬甚至數十萬英鎊,為製藥公司帶來數百萬英鎊獲利,但獲得的效果這麼少?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一部分在於進行臨床試驗的方式,臨床試驗的目的是蒐集資料,供管理機構決定是否核准新療法上市。許多臨床試驗以無惡化存活時間(progression-free survival)來判定藥物效果,也就是腫瘤從開始治療前的大小到繼續長大所需的時間。很少人注意整體存活時間,也就是這種昂貴又可能讓人不舒服的藥物究竟能延長多少壽命?新療法或許能比舊療法抑制癌症更久,就無惡化存活時間看來效果很好,但如果最後復發得又快又厲害,整體存活時間實際上可能不會增加。
另外一個方法是採用所謂的替代指標(surrogate endpoint),例如某種與腫瘤大小同步變化的分子在血液中的濃度。雖然這類指標可用來了解患者狀況是否朝正確方向發展,但還是無法提供確切答案,解答所有患者最想問的問題:這種藥能不能讓我活久一點?
我們或許也覺得新藥應該會和目前最好的藥物進行測試比較,實則不一定,因為很多療法的比較對象不是最佳選擇。有些試驗比較的是現在服用新藥的患者的存活時間和可能已經不正確的過往存活時間。許多藥物迅速取得許可的依據,是比較初期無惡化存活時間或針對這些「稻草人對照組」的替代指標資料,希望製藥公司以後能提供長期整體存活時間資料。讀者們可以猜猜看這個希望實現的機率有多少?
此外,參與試驗的患者通常比較年輕、體態良好、沒有重大健康問題(當然除了癌症以外)。他們通常有很高的參與意願、經常接受監測,而且比較認真接受治療。不過理想臨床試驗環境不能跟真實狀況相比:癌症患者大多數比一般試驗族群年紀更大、身體更差,此外還有各種健康問題,例如心臟病、糖尿病、失智症或腎臟衰竭等,因而對可用的療法或劑量造成限制。患者也可能因為實際或經濟理由而無法或沒有意願到醫院接受檢驗和治療,如果覺得副作用太大難以忍受,可能會停止服藥。
另一個大問題是這類藥物都大同小異。製藥公司不是提供一套包含各種小器具的工具組,讓我們用來對付癌細胞,而是給我們一個裝滿固定扳手的大袋子,裡面可能有一兩支活動扳手。目前市面上的療法大多數只針對一小部分目標,主要是激酶和類似的傳訊分子。部分原因是技術問題:找出阻斷過度活化的激酶的藥物比較容易,因為它們有微小的生物口袋,藥物很容易進入,就像鑰匙插入鑰匙孔一樣。其他許多突變癌症基因產物就很難當成目標,通常稱為「不可投藥」(undruggable)。
更糟的是,提供這麼小的存活時間效益就能取得這麼大的財務報酬,大大鼓勵了「我也做」文化 。一家公司開發出成功打擊特定目標的藥物,其他公司就會競相開發類似產品,只要稍微好一點點就能取得許可。這種方式就賺錢而言相當合理,因為開發全新藥物是未知的領域,但開發「我也做」藥物只需要已經畫好的分子地圖。此外,製藥公司彼此是競爭對手,不一定會遵守規則。跟風最新熱門藥物開發類似產品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補足自己的產品組合,不需要跟其他廠商合作。
現在許多新藥以極為微小的差距超越競爭對手,取得許可,通常只要有幾星期的效益,就能讓管理機構點頭。得舒緩(Tarceva,學名erlotinib))就以一篇指出存活時間僅增加十天的報告取得治療胰臟癌的許可,而且其中還可能有統計誤差空間。如果製藥公司測試的藥物夠多,一定會有幾種單憑運氣呈現效益,超越競爭對手。
有個方法經常用來檢驗臨床試驗結果是否真實而非碰巧或誤打誤撞,稱為「0.05 p值」。簡單說來就是如果重複做二十次相同的試驗,結果可能會有十九次相同,一次不同。這個方法對於成功或失敗的結果都適用:如果拿出二十種口味的雷根糖,分給二十組癌症患者,其中可能會有一種口味碰巧對存活時間有助益。
癌症藥物當然不是雷根糖,而且確實含有在實驗室和動物試驗中都有效果的生物活性化學物質。但以每年開發和進行試驗的藥物數量而言,可能有些產品在人類試驗中其實並未延長存活時間,只是僥倖通過統計標準。即使統計數字不算有利於藥商,或許還是可以靠行銷挽救。我看過一種最新的神奇藥物試驗結果很不起眼,但底下用小字寫著:「統計數據並不顯著但臨床上有意義」。
精準腫瘤醫學還有個問題和整個概念息息相關。拜DNA和分子分析之賜,現在我們已經能治療一小群具有特定的可採取行動突變的癌症患者,而不只是概略性的「腸癌」或「乳癌」患者。潛在市場縮小到數千人以下時,製藥公司數十億美元的經濟規模也開始縮小,所以製藥公司比較偏愛一大批相同的患者,不太喜歡一百萬個各不相同的患者。說服製藥公司針對兒童腫瘤等少見的癌症開發療法已經很不容易,它們會願意投注心力打擊同樣少見的標靶嗎?
新的昂貴藥物不停減少以及存活時間延長極少,原因是沒有誘因促成突破。患者和大眾想要新藥物,因為他們已經不想再看到自己深愛的人離開。慈善機構、企業界、學術界或政府機構投下令人瞠目結舌的巨資,進行開發嶄新療法的研究。管理機關自豪於核准了多少新藥以及通過新藥的速度多快。製藥公司有藥物成功上市時,平均至少可以獲利十億美元。我們已經淪為腫瘤基因製藥業綜合體的受害者,除非十分有錢或擁有完整保險,否則經濟上很難支撐。
大家暫且別把我當作在網路上張貼陰謀論的那類危言聳聽的神經病,我當然不相信這是因為有某些藏鏡人「隱匿靈藥」。癌症研究者和製藥業人員也是人。我們都曾經因為這種可怕的疾病失去深愛的人,有家人、朋友,也有交情極好的同事。我個人曾經收過令人難過的仇視郵件,說我是「希望大家死掉的大藥廠暗樁」,就算朋友、家人和同事接受癌症治療也一樣。
對於新藥上市所需的大規模研究和生產而言,製藥業目前仍然是最好的選擇。商業組織還必須承擔開發新療法時漫長的臨床試驗和審查過程的龐大成本。但我認為許多公司錯在他們只注意同一個地方,只想同一件事。如果製藥公司只要開發把存活時間延長幾個月的藥物,就能獲利十億美元,就沒有誘因促使他們再進步了。這就像我們答應小孩考試得到丁就可以買汽車一樣,這樣幹嘛還用功讀書?
近幾十年來,我們在癌症存活時間方面取得很大的進展,尤其是在比較富裕的國家。在英國有五成癌症患者確診後能存活十年以上,但還有五成沒辦法。這杯子可以說是半滿也可說是半空,取決於你的看法。目前已經有幾個真正的重大改變:子宮頸癌篩檢、治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基利克、治療睪丸癌的凱莫普拉(Kemoplat,學名Cisplatin)、兒童癌症領域的重大進展,以及適用於一小部分患者的免疫療法。但晚期轉移性癌症領域的真正進展仍然相當緩慢。生命短促又珍貴,太多人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癌症發展到一定大小之後,抗藥性就無法避免,所以我不認為把希望寄託在不斷增加的神奇靈丹上,就能帶來我們亟欲找尋的癌症解藥。
我們確實知道,癌症如果具有特定突變,代表在確診後可能存活久一點或短一點。如果體內有某個驅動基因促使癌細胞增殖,我們可以說它是「壞東西」或「好東西」。但現在我們其實沒有很完整的資料可以指出使用標靶藥物確實能提高存活機率,無論是幾個月或幾年。我們無法把壞癌症變成好癌症,而且如果我們不改變尋找癌症驅動基因及開發阻止這些基因的藥物的做法,結果同樣不會改變,只是出現更多小眾和昂貴的療法。當然存活率或許會慢慢提高,但不會大幅改變。
普拉薩德幾年前曾經在《自然》期刊的評論上指出:
精準腫瘤醫學很能鼓舞人心。哪個醫師或患者不想運用遺傳學,為個別患者量身打造療法?但坐時光機回到過去也很能鼓舞人心,誰不想回到過去,趁癌症還沒擴散之前好好清除它?但以二○一六年而言,這兩件事都不可行、不經濟,也不能保證未來會成功。然而這兩件事中有一件事目前說得比做得多很多,連我們自己都信以為真。
我們需要做得更多,而且必須做得更多。
打開雞尾酒櫃
如果跟腫瘤科醫師和研究人員談到標靶療法出現抗藥性,大多數人的回應可以濃縮成一個詞:雞尾酒療法。從一九五○年代開始,醫師就經常使用多種化療藥物的組合。新英格蘭地區的小兒科醫師希德尼‧法柏(Sidney Farber)率先開始在他的年幼白血病患者身上測試雞尾酒藥物,當時這種疾病被視為絕症。法柏成功地把微弱的希望轉變成實際的緩解,讓所有人都十分興奮,相信各種癌症有一天都能用適當的藥物組合治癒。
許多傳統化療包含兩種以上的藥物,分別打擊細胞內的不同機制。例如,經常用於治療何杰金氏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的聯合療法ABVD就包含艾黴素(Adriamycin)、撲類惡(Bleomycin)、敏伯斯登(Vinblastine)和達卡巴仁(Dacarbazine)四種藥物。第一種藥物負責干擾解開DNA以便複製的機制,第二種藥物負責使DNA瓦解,第三種負責癱瘓參與細胞分裂的內部細胞架構,第四種則負責把DNA鏈黏結在一起,使它無法分開。但同時使用四種藥物的副作用可能相當嚴重,不只是在治療期間,甚至可能導致心臟損傷、不孕或次發性癌症。
雞尾酒療法雖然在延長白血病、淋巴瘤和某些固態腫瘤(尤其是睪丸癌)長期存活方面相當成功,但每種癌症都有最佳治療組合的希望並未實現。有些癌症似乎具有強大的抗藥性,能直接把藥物反推出去,而且抗藥性永遠都有其他方法可以演化出來。
這個概念在精準腫瘤醫學的「美麗新世界」中捲土重來:定序腫瘤的基因、找出驅動基因,再設計出盡可能囊括最多驅動基因、不可能演化出抗藥性的雞尾酒療法。這個理論有許多源自一九九○年代中期愛滋病合併療法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又出自法柏早期的化療藥物組合研究)。
以病毒製造的分子為目標的藥物,製藥公司已經開發並測試了好幾年之久,但這些藥物個別使用時效果有限,病毒會演化出抗藥性,接著再度出現。但後來免疫學家何大一和數學家艾倫‧裴瑞森(Alan Perelson)合作提出數學方程式,指出病毒同時針對三種藥物演化出抗藥性的機率只有十萬分之一。這個見解真的改變了生命,在可使用及可負擔這種三重合併療法HAART的國家中,愛滋病患者的壽命延長到和正常人相同。
單從數學觀點看來,癌症標靶雞尾酒療法也相當合理:如果不同的藥物可分別阻斷癌細胞中的不同路徑,而且必須演化出不同的機制才會出現抗藥性,則癌症同時對兩種藥物演化出抗藥性的機率就低得多。舉例來說,如果某種能抵抗單一標靶藥物的細胞出現頻率相當低,例如十萬分之一,而且即使是很小的腫瘤,至少也有一億個細胞,那麼裡面至少會有一千個抗藥性細胞。治療或許能消滅九十九點九九九%的癌症,但這一小群抗藥性癌細胞就足以讓腫瘤復發,世界各地的醫院每天都在在證實這點。
結合兩種藥物可以把力道加強一點:如果每一種藥物以不同的方式消滅可能的腫瘤細胞,那麼一個細胞擁有兩種抗藥性突變的機率就是一百億分之一。不過這還是有可能,尤其是規模大、演化又快的癌症,而且雙重藥物組合的試驗結果也沒有達到許多研究者希望的目標。但再增加到三或四種藥物時,細胞對所有藥物都有抵抗力的機率可說微乎其微。這種療法的關鍵在於同時使用多種藥物,分別阻斷命令癌細胞增殖的不同路徑。但在製藥業的「我也做」文化影響下,現在我們最缺的就是這個。
目前腫瘤科醫師可用的成分只足以做出有限的配方。如果酒櫃裡有十種不同的伏特加、三種牌子的苦艾酒、杜松子酒和幾種果汁,我們就能調出不錯的馬丁尼、性感海灘(Sex on the Beach)或螺絲起子,但是絕對做不出古典雞尾酒(Old Fashioned)或瑪格麗塔。目前可用的癌症標靶藥物同樣相當有限。
倫敦癌症研究所教授拜森‧阿爾拉吉卡尼(Bissan Al-Lazikani)的研究團隊運用大數據和機器學習,希望充實化療雞尾酒櫃的內容。他們一開始選擇四百七十種癌症驅動基因,瞄準其中一百二十種適合當成藥物標靶的編碼蛋白。接著記錄癌細胞內不同分子的交互作用,找出哪些蛋白質彼此「交談」,以及它們是否會開啟或關閉其他基因等。
最後他們畫出整個社交網絡,這個四處延伸的網絡以幾個互相連結的重要「集中點」為中心,類似航線或網際網路連線的圖形。每個集中點代表一群含有可用藥目標的相關基因。但目前癌症藥物打擊的目標,都圍繞在整個網絡一小角的幾個集中點周圍。我們可以任意用力打擊這些目標,但網絡其餘部分仍然毫髮無傷,而且能想辦法繞道,所以癌細胞仍會發展出抗藥性,繼續生長。
阿爾拉吉卡尼團隊以更聰明的方式運用這張圖來對抗癌症,找出能打擊多個不同目標,瓦解這個網絡的藥物。後來癌症研究所使用這個方法測試將近五十種實驗室中培養的腸癌細胞。結合兩種分別打擊不同集中點的標靶藥物,可以阻止癌細胞生長一段時間,但所有細胞最後都能抵抗各種雙藥組合。不過再加入一種藥物,專門對付使細胞受損時不會死亡的「求生」分子,抗藥性就不再出現。第三個目標在網絡上位於完全不同的位置,所以細胞很難演化出對抗這個三重威脅的方法。
這個結果十分重要,但找到一種能對付生長在實驗室培養皿中的癌細胞的方法,到開發出安全有效、可用於患者身上的療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糟的是,學術界或產業界實驗室開發的藥物,大多數沒機會用在患者身上。平均說來,新療法有超過十分之九會在從實驗室到病房的漫長過程胎死腹中(而且可能曾經稱為「奇蹟」或「重大改變),其餘百分之五在臨床試驗過程中看不出效益。
研究成本高昂,所以可以想見,只要有一點點效果,製藥公司就會急著讓神奇新藥取得主管機關許可。但我十分震驚地發現有這麼多藥物一路做到進行人體測試,讓志願受試者貢獻時間和身體來參與試驗,其實卻完全沒有效果或效果微乎其微。
令人沮喪的是,從細胞到動物(通常是小鼠)的常用藥物開發途徑,其實無法讓我們開發出更好的療法。我們很擅於開發在小鼠身上對抗癌症的新藥物,但這些藥物進入人體腫瘤複雜的棲地後,很少能夠發揮預期效果。有個解決方法是使用類器官(organoid)――這是在實驗室中以患者樣本培養的「迷你腫瘤」,比培養皿裡的癌細胞或移植到小鼠體內的腫瘤更真實。研究人員目前正在製作各種癌症的類器官,用它來過濾可能克服抗藥性問題的新藥和藥物組合。
另一項令人期待的新技術是器官晶片(organs-on-a-chip)。器官晶片是小小的玻璃片,上面有細小的微流體通道,模擬實際器官內部管道,此外還有組織中的各種人類細胞或分子、幾個癌細胞和它們生存所需的所有養分。這仍然是人工合成系統,但比小鼠容易操縱和測量(也能減少研究使用動物數量),並且提供大規模高速率的新療法測試平台。此外還能以化學材料和細胞進行3D列印,在實驗室中製作組織甚至整個器官,創造更多可能用途。
阿爾拉吉卡尼期待未來有一天能製作晶片,精確重現個別患者的器官甚至整個身體,模擬血液中各種分子的濃度,同時加入患者服用的其他藥物,例如治療高膽固醇的statin類降血脂藥物等。接著只要加入癌細胞,觀察哪些藥物組合效果最好,但造成副作用的機率最低就行了。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充實腫瘤醫學雞尾酒櫃的內容。二○一九年,研究人員發表一項頗具雄心的研究初步結果。這項研究使用精確的分子剪刀(CRISPR),剪去三十種癌細胞中的每個單一基因。他們發現有六千多個病例只要除去一個基因就能消滅癌細胞,因此增加了六千多個新的治療目標。
這些基因中有許多不適合用於開發藥物,原因可能是它們對健康細胞相當重要,或是它們負責製造的蛋白質缺少分子角落和縫隙,難以形成口袋讓藥物進入。但即使排除這些難搞的目標,團隊依然找出六百個有希望的線索,其中大多數不屬於常見的「我也做」分子庫。
運用CRISPR、類器官和微流體晶片等技術,尋找新的用藥目標和針對腫瘤內分子錯誤的藥物組合,是精準醫學最大的希望。然而,依據個別癌症遺傳組成調製完美化療雞尾酒的概念儘管很吸引人,但人體能吸收的化學物質有限。
愛滋病合併療法發揮效用的原因,是病毒為複製和傳播而製造的分子和人類細胞的分子明顯不同。這表示針對特定病毒的藥物可以使用較高劑量而不造成太多附帶損傷,藥物開發人員稱為治療區間(therapeutic window)較大。但癌症出自我們自己的細胞,所以治療腫瘤中的突變分子時,連帶影響健康組織的機率大得多。把多種不同的藥物混合在一起,這個治療區間甚至可能完全消失。
最後一個大障礙在於管理而不是科學。目前新的癌症藥物,大多數必須先以臨床試驗證明它單獨使用的效果,才能取得許可。但對其中一種甚至兩種藥物的抗藥性很快就會出現,而且要為原本就應該一起使用而非分別使用的多種新藥開發雞尾酒療法更難,所以這個規定很快就顯得沒有意義。即使如此,隨著時間流逝和發生在癌細胞族群中的突變洗牌下,再加上治療造成的選擇壓力,還是可能出現幾個零星的倖存者。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跳脫打地鼠遊戲?解決方案或許不是試圖解決特定突變和不可避免的抗藥性細胞出現,而是退後一步,觀察癌症的突變全貌,尋找線索和對付它的最佳方法。
二○一五年耶誕節前,英國資訊顧問克里斯潘‧亞戈(Crispian Jago)住院接受手術,準備摘除已經擴散到肝臟的龐大腎臟腫瘤。手術看來相當成功,但第二年夏天復發――這次狀況看來不大樂觀。這類狀況一向很難精確預測,但醫師說他的壽命大概只剩下一年半左右。出乎意料,我聯絡他時他還活著,但從他最初確診已經過了將近四年。不過他多活了這麼久,不是因為現代化基因定序和分子標靶藥物,他從來沒有分析過腫瘤的DNA。相反地,他沒死是因為英國南安普敦大學醫院腫瘤科醫師馬修‧惠特(Matthew Wheater)有根據的猜測。
首先,克里斯潘嘗試服用福退癌(Votrient,學名pazopanib)。這種藥物起初似乎有效,三個月後腫瘤縮小了一成左右。但他的好運沒有維持下去,癌細胞演化出抗藥性。二○一七年夏天,腫瘤持續生長,擴散到體內各處,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
他開始服用新的免疫藥物保疾伏(Opdivo,學名nivolumab),這種藥物對某些患者有效,但不是所有患者都會見效。他剛好不屬於幸運的一群,治療開始僅兩個月,就看得出完全沒有幫助。雖然福退癌只控制癌症一年,這段時間也足以讓他等到新的療法。
惠特醫師放棄保疾伏之後,讓克里斯潘改用剛剛取得英國國民保健署許可的癌必定(Cabometyx,學名cabozantinib)。開始治療不到一星期,他就感到好轉;幾個月內,癌症就消失九十五%。讓醫師驚訝的是,這種藥物似乎控制住了癌症,不過腫瘤相關知識顯示,抗藥性到某個時候一定會出現。即使如此,克里斯潘依然樂觀地認為會有結果。他聳了聳肩說:「我覺得我就站在鬼門關前了,必須盡量活久一點,等下一種藥出現。」我不認為末期癌症患者一定會病懨懨的,而他看來很好又活力十足,很難想像他的身體已經漸漸被這些自私的細胞占據。我留意到的主要改變是他的頭髮和鬍子在一年內從深棕色變成驚人的白色。即使是在盛夏,他也穿著三件式毛呢西裝,忙著買下他找到的所有平佛洛伊德的專輯。如果我這輩子遭遇逆境時能有一點點他這幾年來的積極、堅忍和幽默感,我就很高興了。
他說:「當時他們告訴我癌症已經擴散,沒辦法動手術。我女兒英迪當時念大一,還有兩年才畢業。他們說我還有八個月,所以我想:好吧,我大概看不到了,但至少可以當成目標。」
他不只看到英迪以最高成績畢業,還很有信心能看到小兒子彼得在二○二○年取得學位。當時彼得已經二十一歲,我覺得機會很大。
除了努力活到小孩的畢業典禮,克里斯潘在這期間還有一個目標,就是活得比年老的拉布拉多犬威爾伯特更久。這隻狗的好運很遺憾地結束於二○一八年十月,現在埋在克里斯潘和太太多麗同住的可愛鄉間小屋花園裡。我撰寫這本書時,他覺得身體還算不錯,喜歡跟接替威爾伯特的黑色拉布拉多犬史丹利一起玩。
但是也有些不大好的消息。二○一九年夏天的掃描結果顯示,有個腫瘤長在他的腦部前端。雖然治療讓癌症僅限於頸部以下,但療效無法越過腦部和血液間的屏障,與偷偷摸摸行動的癌細胞不同。這顯然是個大炸彈,但他不擔心為了控制這個不受歡迎的新成員而必須接受放射線治療,反而比較煩惱不能開他心愛的保時捷。
跳脫打地鼠遊戲
一般腫瘤發展到目前技術可以診斷時,可能含有數十億到一兆個細胞,每個細胞可能都含有幾萬個基因突變和改變。它已經是個複雜的生態系,有許多不同的細胞物種在多樣化的微棲地中生活和死亡――有些物種習慣於缺氧的毒性沼澤,有些則喜歡比較舒適的環境。
每個人的癌症都是獨一無二的雪花,取決於原本的基因組成和塑造它的演化過程。它發展到開始擴散的時候,抗藥性和復發基本上已經無可避免。在某個地方,會有一些癌細胞能抵擋我們的醫學攻勢。諷刺的是,藥物目標越明確、越特殊,癌症越容易演化出對抗的方法。
克里斯潘令人驚奇的存活,是一百多年來人類專注研究的親身證言。這類成功經驗溫暖了慈善募款機構的心,也讓製藥公司賺得風生水起。但現代腫瘤醫學已經變成典型的生物領域打地鼠遊戲:先嘗試一種療法、等這種療法失效時再試另一種,如此不斷重複,直到沒有選擇為止。這個結果遲早都會到來,取決於腫瘤種類和可使用的療法而定。
精準腫瘤醫學的概念逐漸成為癌症治療的主流思想。這個概念原本的用意是以癌細胞中特定的錯誤分子為目標,例如基利克的目標是造成白血病的費城染色體,賀癌平(Herceptin,學名trastuzumab)的目標則是具有額外癌症驅動基因HER2的乳癌細胞,並且要先以診斷檢驗判定哪些患者適合採用這種療法。
這個定義有時會擴大到包含所有用於阻斷癌細胞內特定訊號的療法,也包含克里斯潘使用的福退癌和癌必定,這兩種都是酪胺酸激酶抑制劑,可阻斷癌細胞中數種不同的增殖訊號。這類藥物被視為「智慧型」藥物,與「愚笨」的傳統化療藥物不同。
腫瘤科醫師逐漸習慣依據特定的錯誤基因或分子(可行動突變)來選擇療法,而不管腫瘤發生在體內的位置。腫瘤在膀胱、腸道或乳房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這些細胞是否含有能以藥物消滅的突變。在此之前,基因檢測的費用很高,所以這種方式只適用於有限的常見目標。但DNA定序技術速度更快、費用更低之後,定序整個腫瘤基因組,尋找可行動突變將逐漸成為主流。
依據個別患者腫瘤的特定驅動突變而選擇藥物的概念,迅速從幻想化為實際。這種方式令人驚奇又有未來感,而且符合現代想法,認為應該針對每個人的腫瘤精準選擇個人化療法,而不是一體適用的標準化程序。這個精準腫瘤醫學典範已經成為癌症研究領域的信條,清楚證明三十多年來製作癌症基因清單和開發聰明(但十分昂貴的)藥物所投入的心力是值得的。
許多人非常看好這種方式改變晚期轉移性癌症患者存活時間的潛力,然而實際上的表現並不符合期待。目前為止,實際狀況是大多數人的癌症沒有接受檢測或沒有適用的基因改變可讓這些神奇子彈當成目標。
美國奧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腫瘤醫學家維內‧普拉薩德(Vinay Prasad)和同事,研究二○○六年以來美國食品藥物署(FDA)核准搭配患者腫瘤基因檢測使用的三十多種標靶藥物。十二年前在美國診斷出罹患轉移型癌症的五十多萬人中,大約有五%可以使用這類療法。到二○一八年,這個數字只提高八%左右。別忘了,這只是接受癌症檢測後可能適用的患者。有許多人從來沒有接受過腫瘤基因檢測,原因可能是費用和實用性。此外,即使基因檢測指出這些極度昂貴的療法確實有效,也沒辦法保證英國國民保健署或醫療保險會支付這些費用。
更糟的是,它的效益相當有限。普拉薩德估計,適用於基因檢測所選標靶療法的患者本來就少,真正有效益的只有略多於一半,效果平均只能持續兩年半。整體說來,適合使用基因標靶療法的人數每年僅緩步增加○.五%左右。雖然有總比沒有好,但絕對不是媒體形容的癌症療法的「量子躍遷」。
新聞標題拚命講聖杯、重大改變、奇蹟和神奇靈丹。有人說這些新療法是改變現狀的全壘打,終於帶來我們追尋已久的癌症靈藥。但就算不要說得太悲觀或忽視近年來延長存活時間的進展,實際狀況也沒有那麼美好。
在另一項研究中,普拉薩德探討使用這類誇張詞句形容新癌症藥物的新聞報導,發現這些療法有一半尚未取得FDA核准,只有七分之一曾經進行實驗室研究,用在人類患者身上還早得很。這類誇張修辭大多是過度興奮的記者的傑作,但醫師、業界專家、患者和政治人物也有散布過度誇大成功經驗之嫌。
以基因檢測決定療法越來越普遍,但本身也面臨挑戰。二○一七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一個研究團隊把九名癌症患者的腫瘤樣本寄給兩家提供最新DNA定序技術檢測突變的公司。定序結果應該會讓認為這類尖端精準腫瘤技術即將大展身手的人感到憂心。
兩家公司的結果都指出其中一名患者沒有檢測得出的基因改變。至於其餘八名患者,兩家公司從樣本檢測出的基因突變只有五分之一相同。兩家公司依據檢測結果提出建議標靶藥物時,有五名患者的建議療法組合完全不同。排除兩方檢測的技術差異或不一致後,這個結果仍然不令人意外。我們已經知道,一般腫瘤是基因各不相同的細胞株拼布,發現的突變也取決於取得及送檢的樣本。
這個精準醫學典範還有其他問題。舉例來說,在腫瘤中發現可行動的突變,不表示標靶藥物一定有效。研究人員現在發現,以出現在許多癌症中的錯誤基因為目標的藥物對某幾種腫瘤有效,但是有些腫瘤儘管具有「適合」的突變,這些藥物仍然沒有效果。
例如標靶療法招牌藥物日沛樂的目標是阻斷BRAF基因中某個突變造成的增殖訊號過度活化。對於含有這種錯誤基因的惡性黑色素瘤患者而言,這種藥物有助於延長壽命,但對含有相同突變的腸癌患者則沒有幫助。腫瘤細胞能迅速「重接」內部路徑,活化替代訊號,讓它們繼續迅速增殖。
許多人認為現代「智慧型藥物」的副作用較少,所以優於「傷身的化療」。這個觀念源自傳統靜脈注射化療,這類化療每次間隔數星期,某些患者會有幾天不舒服的副作用,接著緩和一陣子。我們或許會想,這類聰明的新療法應該能為患者帶來比較好的生活品質,但其實不一定如此。
有一項研究觀察三十八項新藥物臨床試驗結果,這些試驗涵括將近一萬四千名罹患十二種癌症的患者,但沒有發現存活時間和「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之間有明顯關聯。「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是身體、情緒和社交健康程度,以及對工作或其他事務的影響。整體而言,與接受對照治療的患者相比,新藥物使癌症復發時間平均延後一.九個月。
克里斯潘接受第一次福退癌治療時,副作用嚴重到必須住院。這種狀況不常見但不算前所未聞。此外,現在有許多標靶療法是每天服用藥錠,每天的副作用很快就會消退。比方說,醫師所謂「第三/四級腹瀉」的定義是一天上七次廁所,但臨床試驗認為這種狀況「可接受」。如果服用這種藥物真的能挽救生命,依據上廁所規畫日常生活或許是應該付出的合理代價,但許多這類藥物的存活效用最多只能算是中等。
最後還有一個最大但沒有人真心想討論的問題。新聞標題或許很吸引人,但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這些亮眼新藥並不是靈丹,而且差得很遠。人類雖然相當擅於治療早期癌症,尤其是在比較富裕的國家,但晚期轉移性癌症的存活時間通常仍然只有幾個月或十年內(當然一定有例外)。
二○一四年,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教授提托‧佛荷(Tito Fojo)觀察二○○二到二○○四年間上市的七十多種癌症新藥,這些藥物的費用每年高達數千美元。儘管聲勢驚人,但這些新藥延長的存活時間平均只有兩個月。另一個研究團隊的後續報告把時間拉長到略少於三個半月,但可能過度樂觀,原因是它只看短期臨床試驗結果,不看較長的後續時間。
偶爾也有奇蹟出現。有年輕母親或頗受敬愛的祖父得知自己只剩下幾個月時間,但因為某種新的「仙丹」而「打臉醫師」;或是像克里斯潘這樣持續存活下來,對癌症說不。沒有人真的是「平均值」,而且活久一點真的很重要,但這類藥物的存活時間其實大多只比傳統療法長幾個月。此外,它們現在已經是地球上最昂貴的藥物。以重量而言,一般標靶藥物的價格是鈽的六倍,最新的CAR-T免疫療法的價格更高達每公克十億美元。但藥價與效果或延長存活時間其實沒什麼關聯。
所以我們必須問,為什麼這麼多新藥動輒每年要價數萬甚至數十萬英鎊,為製藥公司帶來數百萬英鎊獲利,但獲得的效果這麼少?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一部分在於進行臨床試驗的方式,臨床試驗的目的是蒐集資料,供管理機構決定是否核准新療法上市。許多臨床試驗以無惡化存活時間(progression-free survival)來判定藥物效果,也就是腫瘤從開始治療前的大小到繼續長大所需的時間。很少人注意整體存活時間,也就是這種昂貴又可能讓人不舒服的藥物究竟能延長多少壽命?新療法或許能比舊療法抑制癌症更久,就無惡化存活時間看來效果很好,但如果最後復發得又快又厲害,整體存活時間實際上可能不會增加。
另外一個方法是採用所謂的替代指標(surrogate endpoint),例如某種與腫瘤大小同步變化的分子在血液中的濃度。雖然這類指標可用來了解患者狀況是否朝正確方向發展,但還是無法提供確切答案,解答所有患者最想問的問題:這種藥能不能讓我活久一點?
我們或許也覺得新藥應該會和目前最好的藥物進行測試比較,實則不一定,因為很多療法的比較對象不是最佳選擇。有些試驗比較的是現在服用新藥的患者的存活時間和可能已經不正確的過往存活時間。許多藥物迅速取得許可的依據,是比較初期無惡化存活時間或針對這些「稻草人對照組」的替代指標資料,希望製藥公司以後能提供長期整體存活時間資料。讀者們可以猜猜看這個希望實現的機率有多少?
此外,參與試驗的患者通常比較年輕、體態良好、沒有重大健康問題(當然除了癌症以外)。他們通常有很高的參與意願、經常接受監測,而且比較認真接受治療。不過理想臨床試驗環境不能跟真實狀況相比:癌症患者大多數比一般試驗族群年紀更大、身體更差,此外還有各種健康問題,例如心臟病、糖尿病、失智症或腎臟衰竭等,因而對可用的療法或劑量造成限制。患者也可能因為實際或經濟理由而無法或沒有意願到醫院接受檢驗和治療,如果覺得副作用太大難以忍受,可能會停止服藥。
另一個大問題是這類藥物都大同小異。製藥公司不是提供一套包含各種小器具的工具組,讓我們用來對付癌細胞,而是給我們一個裝滿固定扳手的大袋子,裡面可能有一兩支活動扳手。目前市面上的療法大多數只針對一小部分目標,主要是激酶和類似的傳訊分子。部分原因是技術問題:找出阻斷過度活化的激酶的藥物比較容易,因為它們有微小的生物口袋,藥物很容易進入,就像鑰匙插入鑰匙孔一樣。其他許多突變癌症基因產物就很難當成目標,通常稱為「不可投藥」(undruggable)。
更糟的是,提供這麼小的存活時間效益就能取得這麼大的財務報酬,大大鼓勵了「我也做」文化 。一家公司開發出成功打擊特定目標的藥物,其他公司就會競相開發類似產品,只要稍微好一點點就能取得許可。這種方式就賺錢而言相當合理,因為開發全新藥物是未知的領域,但開發「我也做」藥物只需要已經畫好的分子地圖。此外,製藥公司彼此是競爭對手,不一定會遵守規則。跟風最新熱門藥物開發類似產品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補足自己的產品組合,不需要跟其他廠商合作。
現在許多新藥以極為微小的差距超越競爭對手,取得許可,通常只要有幾星期的效益,就能讓管理機構點頭。得舒緩(Tarceva,學名erlotinib))就以一篇指出存活時間僅增加十天的報告取得治療胰臟癌的許可,而且其中還可能有統計誤差空間。如果製藥公司測試的藥物夠多,一定會有幾種單憑運氣呈現效益,超越競爭對手。
有個方法經常用來檢驗臨床試驗結果是否真實而非碰巧或誤打誤撞,稱為「0.05 p值」。簡單說來就是如果重複做二十次相同的試驗,結果可能會有十九次相同,一次不同。這個方法對於成功或失敗的結果都適用:如果拿出二十種口味的雷根糖,分給二十組癌症患者,其中可能會有一種口味碰巧對存活時間有助益。
癌症藥物當然不是雷根糖,而且確實含有在實驗室和動物試驗中都有效果的生物活性化學物質。但以每年開發和進行試驗的藥物數量而言,可能有些產品在人類試驗中其實並未延長存活時間,只是僥倖通過統計標準。即使統計數字不算有利於藥商,或許還是可以靠行銷挽救。我看過一種最新的神奇藥物試驗結果很不起眼,但底下用小字寫著:「統計數據並不顯著但臨床上有意義」。
精準腫瘤醫學還有個問題和整個概念息息相關。拜DNA和分子分析之賜,現在我們已經能治療一小群具有特定的可採取行動突變的癌症患者,而不只是概略性的「腸癌」或「乳癌」患者。潛在市場縮小到數千人以下時,製藥公司數十億美元的經濟規模也開始縮小,所以製藥公司比較偏愛一大批相同的患者,不太喜歡一百萬個各不相同的患者。說服製藥公司針對兒童腫瘤等少見的癌症開發療法已經很不容易,它們會願意投注心力打擊同樣少見的標靶嗎?
新的昂貴藥物不停減少以及存活時間延長極少,原因是沒有誘因促成突破。患者和大眾想要新藥物,因為他們已經不想再看到自己深愛的人離開。慈善機構、企業界、學術界或政府機構投下令人瞠目結舌的巨資,進行開發嶄新療法的研究。管理機關自豪於核准了多少新藥以及通過新藥的速度多快。製藥公司有藥物成功上市時,平均至少可以獲利十億美元。我們已經淪為腫瘤基因製藥業綜合體的受害者,除非十分有錢或擁有完整保險,否則經濟上很難支撐。
大家暫且別把我當作在網路上張貼陰謀論的那類危言聳聽的神經病,我當然不相信這是因為有某些藏鏡人「隱匿靈藥」。癌症研究者和製藥業人員也是人。我們都曾經因為這種可怕的疾病失去深愛的人,有家人、朋友,也有交情極好的同事。我個人曾經收過令人難過的仇視郵件,說我是「希望大家死掉的大藥廠暗樁」,就算朋友、家人和同事接受癌症治療也一樣。
對於新藥上市所需的大規模研究和生產而言,製藥業目前仍然是最好的選擇。商業組織還必須承擔開發新療法時漫長的臨床試驗和審查過程的龐大成本。但我認為許多公司錯在他們只注意同一個地方,只想同一件事。如果製藥公司只要開發把存活時間延長幾個月的藥物,就能獲利十億美元,就沒有誘因促使他們再進步了。這就像我們答應小孩考試得到丁就可以買汽車一樣,這樣幹嘛還用功讀書?
近幾十年來,我們在癌症存活時間方面取得很大的進展,尤其是在比較富裕的國家。在英國有五成癌症患者確診後能存活十年以上,但還有五成沒辦法。這杯子可以說是半滿也可說是半空,取決於你的看法。目前已經有幾個真正的重大改變:子宮頸癌篩檢、治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基利克、治療睪丸癌的凱莫普拉(Kemoplat,學名Cisplatin)、兒童癌症領域的重大進展,以及適用於一小部分患者的免疫療法。但晚期轉移性癌症領域的真正進展仍然相當緩慢。生命短促又珍貴,太多人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癌症發展到一定大小之後,抗藥性就無法避免,所以我不認為把希望寄託在不斷增加的神奇靈丹上,就能帶來我們亟欲找尋的癌症解藥。
我們確實知道,癌症如果具有特定突變,代表在確診後可能存活久一點或短一點。如果體內有某個驅動基因促使癌細胞增殖,我們可以說它是「壞東西」或「好東西」。但現在我們其實沒有很完整的資料可以指出使用標靶藥物確實能提高存活機率,無論是幾個月或幾年。我們無法把壞癌症變成好癌症,而且如果我們不改變尋找癌症驅動基因及開發阻止這些基因的藥物的做法,結果同樣不會改變,只是出現更多小眾和昂貴的療法。當然存活率或許會慢慢提高,但不會大幅改變。
普拉薩德幾年前曾經在《自然》期刊的評論上指出:
精準腫瘤醫學很能鼓舞人心。哪個醫師或患者不想運用遺傳學,為個別患者量身打造療法?但坐時光機回到過去也很能鼓舞人心,誰不想回到過去,趁癌症還沒擴散之前好好清除它?但以二○一六年而言,這兩件事都不可行、不經濟,也不能保證未來會成功。然而這兩件事中有一件事目前說得比做得多很多,連我們自己都信以為真。
我們需要做得更多,而且必須做得更多。
打開雞尾酒櫃
如果跟腫瘤科醫師和研究人員談到標靶療法出現抗藥性,大多數人的回應可以濃縮成一個詞:雞尾酒療法。從一九五○年代開始,醫師就經常使用多種化療藥物的組合。新英格蘭地區的小兒科醫師希德尼‧法柏(Sidney Farber)率先開始在他的年幼白血病患者身上測試雞尾酒藥物,當時這種疾病被視為絕症。法柏成功地把微弱的希望轉變成實際的緩解,讓所有人都十分興奮,相信各種癌症有一天都能用適當的藥物組合治癒。
許多傳統化療包含兩種以上的藥物,分別打擊細胞內的不同機制。例如,經常用於治療何杰金氏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的聯合療法ABVD就包含艾黴素(Adriamycin)、撲類惡(Bleomycin)、敏伯斯登(Vinblastine)和達卡巴仁(Dacarbazine)四種藥物。第一種藥物負責干擾解開DNA以便複製的機制,第二種藥物負責使DNA瓦解,第三種負責癱瘓參與細胞分裂的內部細胞架構,第四種則負責把DNA鏈黏結在一起,使它無法分開。但同時使用四種藥物的副作用可能相當嚴重,不只是在治療期間,甚至可能導致心臟損傷、不孕或次發性癌症。
雞尾酒療法雖然在延長白血病、淋巴瘤和某些固態腫瘤(尤其是睪丸癌)長期存活方面相當成功,但每種癌症都有最佳治療組合的希望並未實現。有些癌症似乎具有強大的抗藥性,能直接把藥物反推出去,而且抗藥性永遠都有其他方法可以演化出來。
這個概念在精準腫瘤醫學的「美麗新世界」中捲土重來:定序腫瘤的基因、找出驅動基因,再設計出盡可能囊括最多驅動基因、不可能演化出抗藥性的雞尾酒療法。這個理論有許多源自一九九○年代中期愛滋病合併療法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又出自法柏早期的化療藥物組合研究)。
以病毒製造的分子為目標的藥物,製藥公司已經開發並測試了好幾年之久,但這些藥物個別使用時效果有限,病毒會演化出抗藥性,接著再度出現。但後來免疫學家何大一和數學家艾倫‧裴瑞森(Alan Perelson)合作提出數學方程式,指出病毒同時針對三種藥物演化出抗藥性的機率只有十萬分之一。這個見解真的改變了生命,在可使用及可負擔這種三重合併療法HAART的國家中,愛滋病患者的壽命延長到和正常人相同。
單從數學觀點看來,癌症標靶雞尾酒療法也相當合理:如果不同的藥物可分別阻斷癌細胞中的不同路徑,而且必須演化出不同的機制才會出現抗藥性,則癌症同時對兩種藥物演化出抗藥性的機率就低得多。舉例來說,如果某種能抵抗單一標靶藥物的細胞出現頻率相當低,例如十萬分之一,而且即使是很小的腫瘤,至少也有一億個細胞,那麼裡面至少會有一千個抗藥性細胞。治療或許能消滅九十九點九九九%的癌症,但這一小群抗藥性癌細胞就足以讓腫瘤復發,世界各地的醫院每天都在在證實這點。
結合兩種藥物可以把力道加強一點:如果每一種藥物以不同的方式消滅可能的腫瘤細胞,那麼一個細胞擁有兩種抗藥性突變的機率就是一百億分之一。不過這還是有可能,尤其是規模大、演化又快的癌症,而且雙重藥物組合的試驗結果也沒有達到許多研究者希望的目標。但再增加到三或四種藥物時,細胞對所有藥物都有抵抗力的機率可說微乎其微。這種療法的關鍵在於同時使用多種藥物,分別阻斷命令癌細胞增殖的不同路徑。但在製藥業的「我也做」文化影響下,現在我們最缺的就是這個。
目前腫瘤科醫師可用的成分只足以做出有限的配方。如果酒櫃裡有十種不同的伏特加、三種牌子的苦艾酒、杜松子酒和幾種果汁,我們就能調出不錯的馬丁尼、性感海灘(Sex on the Beach)或螺絲起子,但是絕對做不出古典雞尾酒(Old Fashioned)或瑪格麗塔。目前可用的癌症標靶藥物同樣相當有限。
倫敦癌症研究所教授拜森‧阿爾拉吉卡尼(Bissan Al-Lazikani)的研究團隊運用大數據和機器學習,希望充實化療雞尾酒櫃的內容。他們一開始選擇四百七十種癌症驅動基因,瞄準其中一百二十種適合當成藥物標靶的編碼蛋白。接著記錄癌細胞內不同分子的交互作用,找出哪些蛋白質彼此「交談」,以及它們是否會開啟或關閉其他基因等。
最後他們畫出整個社交網絡,這個四處延伸的網絡以幾個互相連結的重要「集中點」為中心,類似航線或網際網路連線的圖形。每個集中點代表一群含有可用藥目標的相關基因。但目前癌症藥物打擊的目標,都圍繞在整個網絡一小角的幾個集中點周圍。我們可以任意用力打擊這些目標,但網絡其餘部分仍然毫髮無傷,而且能想辦法繞道,所以癌細胞仍會發展出抗藥性,繼續生長。
阿爾拉吉卡尼團隊以更聰明的方式運用這張圖來對抗癌症,找出能打擊多個不同目標,瓦解這個網絡的藥物。後來癌症研究所使用這個方法測試將近五十種實驗室中培養的腸癌細胞。結合兩種分別打擊不同集中點的標靶藥物,可以阻止癌細胞生長一段時間,但所有細胞最後都能抵抗各種雙藥組合。不過再加入一種藥物,專門對付使細胞受損時不會死亡的「求生」分子,抗藥性就不再出現。第三個目標在網絡上位於完全不同的位置,所以細胞很難演化出對抗這個三重威脅的方法。
這個結果十分重要,但找到一種能對付生長在實驗室培養皿中的癌細胞的方法,到開發出安全有效、可用於患者身上的療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糟的是,學術界或產業界實驗室開發的藥物,大多數沒機會用在患者身上。平均說來,新療法有超過十分之九會在從實驗室到病房的漫長過程胎死腹中(而且可能曾經稱為「奇蹟」或「重大改變),其餘百分之五在臨床試驗過程中看不出效益。
研究成本高昂,所以可以想見,只要有一點點效果,製藥公司就會急著讓神奇新藥取得主管機關許可。但我十分震驚地發現有這麼多藥物一路做到進行人體測試,讓志願受試者貢獻時間和身體來參與試驗,其實卻完全沒有效果或效果微乎其微。
令人沮喪的是,從細胞到動物(通常是小鼠)的常用藥物開發途徑,其實無法讓我們開發出更好的療法。我們很擅於開發在小鼠身上對抗癌症的新藥物,但這些藥物進入人體腫瘤複雜的棲地後,很少能夠發揮預期效果。有個解決方法是使用類器官(organoid)――這是在實驗室中以患者樣本培養的「迷你腫瘤」,比培養皿裡的癌細胞或移植到小鼠體內的腫瘤更真實。研究人員目前正在製作各種癌症的類器官,用它來過濾可能克服抗藥性問題的新藥和藥物組合。
另一項令人期待的新技術是器官晶片(organs-on-a-chip)。器官晶片是小小的玻璃片,上面有細小的微流體通道,模擬實際器官內部管道,此外還有組織中的各種人類細胞或分子、幾個癌細胞和它們生存所需的所有養分。這仍然是人工合成系統,但比小鼠容易操縱和測量(也能減少研究使用動物數量),並且提供大規模高速率的新療法測試平台。此外還能以化學材料和細胞進行3D列印,在實驗室中製作組織甚至整個器官,創造更多可能用途。
阿爾拉吉卡尼期待未來有一天能製作晶片,精確重現個別患者的器官甚至整個身體,模擬血液中各種分子的濃度,同時加入患者服用的其他藥物,例如治療高膽固醇的statin類降血脂藥物等。接著只要加入癌細胞,觀察哪些藥物組合效果最好,但造成副作用的機率最低就行了。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充實腫瘤醫學雞尾酒櫃的內容。二○一九年,研究人員發表一項頗具雄心的研究初步結果。這項研究使用精確的分子剪刀(CRISPR),剪去三十種癌細胞中的每個單一基因。他們發現有六千多個病例只要除去一個基因就能消滅癌細胞,因此增加了六千多個新的治療目標。
這些基因中有許多不適合用於開發藥物,原因可能是它們對健康細胞相當重要,或是它們負責製造的蛋白質缺少分子角落和縫隙,難以形成口袋讓藥物進入。但即使排除這些難搞的目標,團隊依然找出六百個有希望的線索,其中大多數不屬於常見的「我也做」分子庫。
運用CRISPR、類器官和微流體晶片等技術,尋找新的用藥目標和針對腫瘤內分子錯誤的藥物組合,是精準醫學最大的希望。然而,依據個別癌症遺傳組成調製完美化療雞尾酒的概念儘管很吸引人,但人體能吸收的化學物質有限。
愛滋病合併療法發揮效用的原因,是病毒為複製和傳播而製造的分子和人類細胞的分子明顯不同。這表示針對特定病毒的藥物可以使用較高劑量而不造成太多附帶損傷,藥物開發人員稱為治療區間(therapeutic window)較大。但癌症出自我們自己的細胞,所以治療腫瘤中的突變分子時,連帶影響健康組織的機率大得多。把多種不同的藥物混合在一起,這個治療區間甚至可能完全消失。
最後一個大障礙在於管理而不是科學。目前新的癌症藥物,大多數必須先以臨床試驗證明它單獨使用的效果,才能取得許可。但對其中一種甚至兩種藥物的抗藥性很快就會出現,而且要為原本就應該一起使用而非分別使用的多種新藥開發雞尾酒療法更難,所以這個規定很快就顯得沒有意義。即使如此,隨著時間流逝和發生在癌細胞族群中的突變洗牌下,再加上治療造成的選擇壓力,還是可能出現幾個零星的倖存者。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跳脫打地鼠遊戲?解決方案或許不是試圖解決特定突變和不可避免的抗藥性細胞出現,而是退後一步,觀察癌症的突變全貌,尋找線索和對付它的最佳方法。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