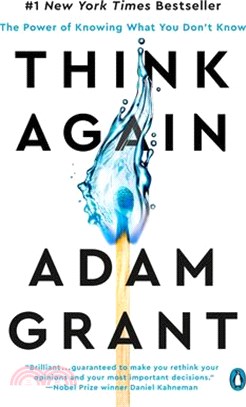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余英時經典作品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最重要的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
──余英時,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爬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影響的綿密關係。
本書收入余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余英時先生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作者簡介
安徽潛山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等。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2004年入選美國哲學會會士。曾獲日本關西大學等多所大學名譽博士,2006年獲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首屆唐獎漢學獎。著作有中英文數十種,包括《歷史與思想》、《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會友集》、《朱熹的歷史世界》、《論天人之際》、《余英時回憶錄》、《人文與民主》、《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等。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
目次
自序
第一篇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第二篇 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
第三篇 新春談心
第四篇 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
第五篇 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第六篇 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
第七篇 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第八篇 士的傳統及其斷裂
第九篇 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第十篇 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
第十一篇 接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講詞
第十二篇 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致詞
第十三篇 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書摘/試閱
自序
在這篇短序中,我想對本書的性質做一扼要的說明。首先必須解釋的是,為什麼在一部討論文化價值的論集中要特別把知識人放在與價值系統同等重要的位置呢?答案其實是很簡單的。文化的價值雖然起源於一個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之中,但必須經過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然後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規範,反過來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發生引導作用。這一整理、提煉和闡明的重大任務,就中國傳統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擔著的。本書第二篇〈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便試圖揭示:先秦各派的「士」怎樣開創出中國價值系統的原始形態。其餘各篇討論「士」(「知識人」)的文字也無不與價值問題密切相關。我將論「科舉」的新作也包括在本書之中,則旨在展示「士」如何通過制度化的途徑把各時代的主流價值傳播到整個社會。漢代的「孝廉」、「賢良」、「方正」等科目固然明白地標舉出價值取向,明、清以後以《四書》取士也充分體現了程朱一系的價值系統。
我雖然強調近代以前的中國具有一套獨特的價值系統,但同時也完全承認價值系統隨時代變動而不斷更新這一歷史事實。從先秦到清中葉,中國的價值系統已發生過幾次重要的更改,但大致仍屬於傳統內部的調整。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書沒有收入有關這一方面的論著。十九世紀末葉以下,西方文化全方位地進入中國,撼動了中國價值系統的基礎,最後則導致其全面的解體。本書第四篇〈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初步追溯了這一歷史過程。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名言在「五四」時代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念;這句名言恰恰道破了中國現代價值危機的性質。與以往局部的內在調整不同,這一次是中國價值系統的整體面臨著「重新估定」的嚴重挑戰,而「估定」的參照標準則是西方近代的價值系統。在西方的對照之下,中國人究竟對自己原有的價值系統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對於西方價值的引進又應不應該設立最低限度的防線呢?環繞這兩大問題的爭論當時便引出了種種不同的方案,從激進的、保守的到不同程度溫和的,應有盡有。到了「五四」前後,爭論的範圍已擴大到整個中西文化與歷史之間的異同上面來了。所以中西文化的爭論構成了現代中國人文研究領域中一個中心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幾乎沒有人能完全逃得出它的籠罩,我在這裡祇想強調一個論點,即所謂中西文化之爭,在剝蕉見心之後,根本上仍是中西價值系統之爭。這一爭論雖然已進行了一個世紀之久,卻依然沒有結束的跡象。在民族主義激情的鼓盪之下,爭論正在以不同的面貌展現在世人的眼前。本書所收〈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雖是一篇通俗性的短文,卻也揭開了現階段新爭論的一角。從這一角度看,本書的主題並不是已逝的歷史陳跡,而是關係著中國前途的活生生的大問題。但近二、三十年來世界人文研究也發生了新的轉向,和本書主題的探討息息相關。因此我又將近作〈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收在這裡,提供讀者參考。不用說,中西兩大價值系統之間的糾結正是中國人文研究再出發所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
最後還要指出,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士」轉化為現代的「知識人」(intellectual)大致是與二十世紀同時開始的,而以一九○五年科舉廢止為最具象徵性的年分(見第七篇〈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中國價值意識的大變動也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譚嗣同「衝決倫常之網羅」(《仁學》,撰於一八九六年)對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展開了最猛烈的批判;梁啟超的《新民說》(一九○二年)則系統地引進了西方現代的價值觀念。這兩個系列的歷史發展是一體的兩面,更進一步證實了「知識人」與「價值」之間存在著不可分離的關係。
以上的短序已旨在說明:本書雖由不同起源的論文集結而成,但全書集中在同一主題之下,各篇之間也是互相貫通的。所以這部小書自成一個獨立的單元,並不是一本雜湊的文集。
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第四篇 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全面變動的歷史階段,傳統的價值系統受到了最嚴厲的挑戰。這一百多年中,我們一方面看到傳統價值觀念的解體,另一方面也看到種種現代觀念的出現,但是價值系統所涉及的不僅是觀念世界,更重要的是日常人生。我們觀察一個社會的價值系統尤其應當著眼於該社會成員的實際行為;這主要是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不但如此,價值系統的社會實踐又往往因階層、族類、性別等而異。例如今天在西方學術界十分流行的所謂「菁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之別便和價值系統的問題密切相關,同一價值觀念在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層面中並不必然發生相同的作用。由此可知,如果我們要認真討論中國的價值系統在這一個半世紀中的變遷,似乎祇有在社會科學家和史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以後才能著手。但這個先決條件在今天還遠未具備。一九四九年以後,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幾乎完全停頓了。少數調查報告也是在最近十年中才開始的,還不能為我們提供充分的資料。
由於受到資料的嚴重限制,我們現在還不能對現代中國價值系統的流變提出比較準確的論斷。本文基本上是從思想層面進行觀察;這是出於三重考慮:第一,對於傳統價值系統的全面攻擊是從知識界、思想界開始的。第二,中國知識分子雖居於所謂「四民之首」,屬於菁英文化的層次,然而由於中國並沒有森嚴的階級制度,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從民間來的,因此他們對於傳統價值系統的批判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動向。第三,從以往的歷史看,中國知識分子雖不能說是文化價值的創造者,但他們在闡明(articulate)、維護和傳播文化價值方面,則往往起著重大的作用。現代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的變遷,追根溯源,也是從知識階層逐漸向全社會滲透的。但是這篇文字祇能就個人所知及解析略陳大概,其中一些局部的觀察和整體的結論都有待於將來經驗研究的驗證。
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是以儒家為中心而形成的,漢代以後有佛教和道教的崛起,許多民間的價值觀念往往依託在佛和道的旗幟之下。但是整體地看,儒家的中心地位始終是很穩固的。因此傳統價值系統的動搖也始於現代知識分子對儒家失去了信心。
儒家的理論從個人的修身逐步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整體。近代中國對儒教的批判最初雖是從治國、平天下(所謂「外王」)方面入手,但很快便發展到齊家的層面,最後連修身也不能幸免。於是儒家的價值系統整個都動搖了。
我們通常認為儒家的權威要到清末民初才受到正面的挑戰。就影響的廣度和深度而言,這個看法是有根據的,然而就起源而言,我們卻不能不把中國的反儒教的運動上推至十九世紀中葉。洪秀全等人信奉上帝會而到處焚毀孔廟及其他寺廟,並禁士人「讀孔子之經」,這可以代表中下層社會的邊緣分子對於儒教以至整個文化傳統的一種激烈的反抗。因此曾國藩的〈討賊檄〉才特別以「名教之大變」為號召。這一規模浩大的民變已透露出傳統價值系統的深刻危機,它絕不僅僅是一次政治、種族或經濟的抗爭。更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天國的基督教義雖極盡歪曲之能事,但畢竟代表了中國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觀念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施以猛烈的攻擊,這一象徵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西方勢力的入侵不僅在中國中下層邊緣分子的心靈中造成巨大的激盪,而且也立即使士大夫對儒家發生深刻的懷疑。太平天國時代的汪士鐸(一八○二至一八八九年)便是一個較早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汪士鐸親歷太平天國之亂,隱身江寧差不多一年,但後來曾入胡林翼和曾國藩的幕府,頗多策畫,極受胡、曾的推重。所以胡林翼說他「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八極」,又說他是「曠代醇儒,孤介不可逼視」。曾國藩也稱道他「學問淹雅,人品高潔」(均見鄧之誠〈汪悔翁乙丙日記序〉所引胡、曾書札)。
然而這位「醇儒」卻對儒家有很激烈的評論,他在《乙丙日記》中說:
由今思之,王(弼)何(晏)罪浮桀、紂一倍;釋、老罪浮十倍;周、程、朱、張罪浮百倍。彌近理彌無用,徒美談以惑世誣民。不似桀、紂,亂祇其身數十年也。
周、孔賢於堯、舜一倍;申、韓賢於十倍;韓、白賢於百倍。黃、堯、舜以德不如周、孔之立言。然失於仁柔,故申、韓以懲小奸,韓、白以定大亂,又以立功勝也。
他對孔子還保持著敬意,對孟子已多微詞,對宋代道學則深惡痛絕。所以他說:道學家其源出於孟子,以爭勝為心,以痛詆異己為衣缽,以心性理氣誠敬為支派,以無可考驗之慎獨存養為藏身之固,以內聖外王之大言相煽惑,以妄自尊大為儀注,以束書不觀為傳授,以文章事功為粗跡,以位育參贊,篤恭無言、無聲色遂致太平之虛談互相欺詐為學問。
自清初顏元以來,兩百年間從來沒出現過這樣激昂的反道學的言論。但汪士鐸排斥道學並不是出於無知。事實上,他出身於理學的家庭。據他的〈自述〉:「士鐸家極貧,然性好讀書。先君子好理學,除程、朱經注之外禁勿觀。日以無入不自得為訓。」
我們可以斷定,他中年以後思想的偏激是經歷了世變的結果。西方勢力的凌逼和太平天國的動亂使他認識到富國強兵已成當務之急,因此他才特別提倡法家與兵家。他很明白地指出:
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者多宗其言仁言禮,而略其經世之說。又以軍旅未之學而諱言兵,由是儒遂為無用之學……此皆孔子不得位,無所設施故爾。道德之不行於三代之季,猶富強之必當行於今。故敗孔子之道者,宋儒也;輔孔子之道者,申、韓、孫、吳也。
這一段話中最可注意的是他責難後代儒者—特別是「宋儒」—完全拋棄了孔子思想中注重「經世」的一面。依照汪氏的推理,祇有「經世」才能致富強,因此法家和兵家反而能夠「輔孔子之道」。這裡透露了當時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動向,十九世紀上半葉,政治、社會的危機已深,學者開始回想儒家的經世傳統,魏源強調:「自古……無不富強之王道。」他一方面諷刺宋儒說:「心性迂談可治天下乎?」
另一方面則正面提出「兼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斯始國之庖丁乎!」
這些都是汪士鐸在《乙丙日記》中所發揮的議論,不過語氣更為偏頗而已。汪氏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曾在揚州從魏源遊,深受影響,所以後來在〈感知己贊〉中論及魏源時,特別說:「魏侯經世,為世營平。」
〈感知己贊〉中又有包世臣,汪氏也推重其「經世」之學。這是他參與了經世學運動的明證。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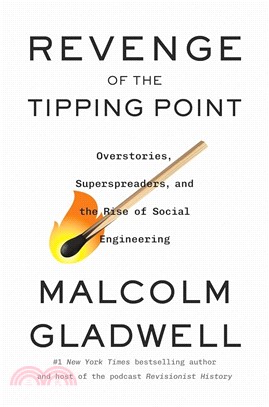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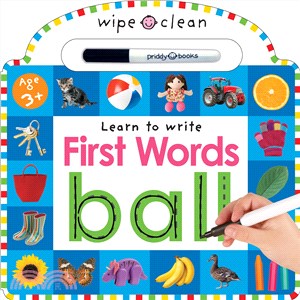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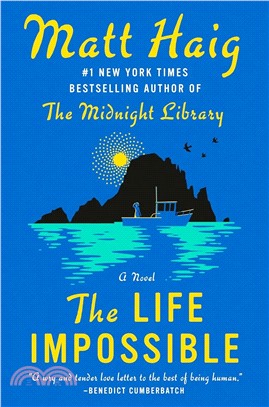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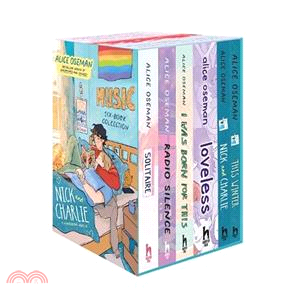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