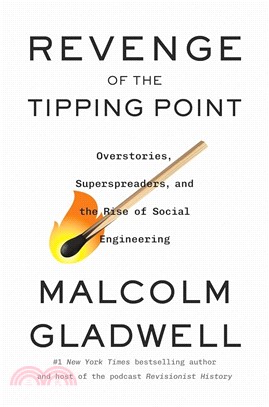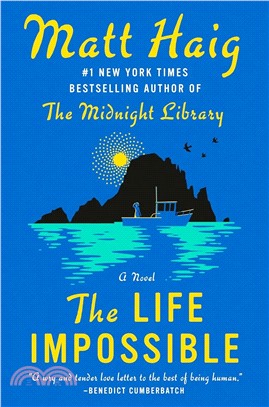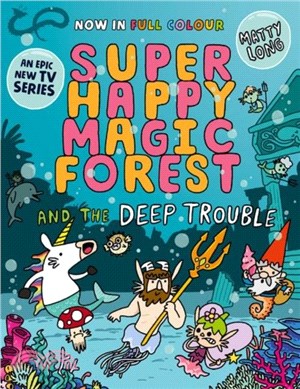神聖黑色的魔力:徹底改變人類文明、藝術、歷史的黑色故事
商品資訊
系列名:生活文化
ISBN13:9786263960855
替代書名:The Story of Black
出版社:時報文化
作者:約翰‧哈維
譯者:謝忍翾
出版日:2024/04/30
裝訂/頁數:平裝/352頁
規格:21cm*15cm*1.7cm (高/寬/厚)
重量:465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黑色作為一種沒有其他色調的「顏色」,它是沒有變化的二分法,但它象徵的東西涵蓋了所有的意義──好的和壞的。《神聖黑色的魔力》一書帶領我們追溯至聖經和古典時代,探索世界文化與這神祕顏色之間的曖昧關係,審視黑色如何以多種不可思議的方式被運用和延伸為隱喻。
作者約翰‧哈維深入研究了黑色與人類發展的深度關係:
◎他觀察到歐洲白人如何利用人們對於這種顏色的負面聯繫,以此奴役了數百萬的非洲黑人。
◎他發掘出黑色的多重象徵意義,例如希臘文中的憂鬱症(melancholia)與黑膽汁的關連,恰定義了我們消極、黑暗的情緒;又如古埃及人多使用黑色作為死亡的代表色,使其成為標準的葬禮服裝及牧師、教堂和宗教衣著的主要色調。
◎他也指出,直到黑色受到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花花公子及龐克、哥德等次文化歡迎之前,黑色本身的樸素和嚴肅,成為商人、律師和君王的長袍顏色首選。
◎最後,他探討了藝術家和設計師如何將黑色應用到作品中,從最早的洞穴壁畫到卡拉瓦喬、林布蘭和羅斯科,以及現代的建築、時尚、影視作品等。
《神聖的黑色魔力》旁徵博引了豐富精采的資料與文獻,透過作者巧手編織成引人入勝的一篇篇故事,將黑色的歷史講述得像一部貫穿古今的螢幕鉅獻,等待你來一探究竟!
★書中內含世界名畫插圖
★國際媒體一致盛讚
「豐富的知識饗宴,廣泛蒐羅奇聞妙事,並以含蓄優美的筆觸寫就……在書中作者約翰‧哈維廣灑寫作之網,遠至史前時代,旁及各類領域:藝術史、宗教(尤其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人類學、文學、時尚、紋章學、地理以及政治鎔鑄於一書,實在少見……這是一本有學問又有意思的書。」──《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約翰‧哈維的研究廣博、令人大開眼界,呈現『黑的』多種層面……本書文筆生動,寫作用心,主題迷人。強力推薦。」──《選擇》雜誌(Choice)
「對於沒有或少有色彩、時尚、教育、人類學或藝術方面先備知識的讀者而言,本書是節奏緊湊的扛鼎之作……作者的文風優美凝鍊……以本書題材之廣、之密,加之資訊豐富,卻能如此好讀,實在難能可貴……針對如此複雜的主題,《神聖黑色的魔力》是本易讀好看的入門通識佳作。」──《視覺研究》(Visual Studies)
※本書為《黑色的故事:徹底改變人類文明史的顏色》改版書
作者簡介
約翰‧哈維 John Harvey
小說家及評論家。自1974年開始在劍橋教授英文,在2000年成為文學和視覺文化領域的資深講師。劍橋Emmanuel學院的終生院士。著有《Men in Black》(Reaktion, 1997)等多部學術著作和小說。
譯者簡介
謝忍翾
師大翻譯所口譯組畢,譯有《聖堂的獻祭》、《我從死人那裡學來的把戲》、《從一杯可樂開始的帝國》、《背離親緣》。喜歡舌尖上的文字,口齒生香。懇請賜教:funnyworldeh@gmail.com
目次
第一章 最古老的顏色
第二章 古典時代的黑
第三章 神聖的黑色
第四章 阿拉伯和歐洲世界的黑色
第五章 兩位在黑暗之中的藝術家:卡拉瓦喬、林布蘭
第六章 黑色的膽汁
第七章 奴隸文化與黑人文化傳統
第八章 啟蒙時代的黑
第九章 英國人的黑色世紀
第十章 我們的顏色?
後記:棋盤、死亡、白
謝辭
書摘/試閱
前言 黑色如何成為黑色?
對於黑,達文西的立場很清楚,他說:「黑不是顏色。」話雖如此,黑仍是他調色盤上的一抹顏料,而且他還很常使用──用來畫背景。他有一幅《抱銀鼠的女子》(Lady with an Ermine,1489-90),除了女子鮮紅的袖子外,皆以朦朧帶銀光的色彩畫成,然而她身後卻是扎扎實實、不透明的黑。她還帶了一串黑項鍊。而在達文西的畫作《救世主》(Salvator Mundi)中,耶穌幽幽於我們眼前浮現,似乎是從死者的世界望了過來,一雙棕色的眼睛如蒙薄翳、彷彿目不視物,身後則是煤炭或煙灰的純黑(圖1)。這麼說來,在達文西認為,即便黑不是顏色,仍十分適合作為背景,烘托出其他色彩。
其他藝術家的反應熱烈多了。馬蒂斯曾說:「黑是種力量。」而雷諾瓦則把黑稱為「色彩之后」,並引用義大利文藝復興畫家丁托列托的話:「所有顏色中最美的就是黑。」自古以來一直有一個問題:「從顏色的角度來說,黑色究竟是什麼?」黑色不是光譜上的顏色,不可能是,因為光譜色由光所組成。另一方面,亞里斯多德則認為混合黑白二色可獲得鮮豔的色彩,後世的歌德也持同樣看法。究竟黑是濃重的有,還是空乏的無?是一種色彩,還是晦暗無光?這種模稜兩可的特性也使黑兼具許多對立的性質:是沃土還是焦炭?是時髦的衣裝或是寡婦的喪服?是夜的神祕性感,抑或代表死亡、憂鬱及哀傷?貝多芬就曾談過音樂裡的「黑和弦」。從來沒有其他顏色像黑一樣,集如此相對、如此絕對的極端於一身。
而以上這些意義,也並非亙古如常。這個顏色的歷史彷彿記錄了一段侵略史。以前黑主要代表人類生活以外各種嚇人的領域,但隨著時間過去,人類拉近了黑與自己的距離,在自己的身體甚至靈魂當中找出了黑。這個代表死亡、恐懼、否定的顏色一步步在信仰、藝術以及社會生活的基本層面占有一席之地。由此觀之,黑的歷史就是漸漸與可怕的事物和平相處的歷史。在種族的權力角力中,黑的角色也極為吃重。但在探討上述主題之前,也許該先從幾個基本的問題開始,比如黑與光的關係為何?我們怎麼看到黑?還有黑到底是不是顏色?
顏色史學家巴斯德(Michel Pastoureau)討論過黑,討論最後他不禁好奇,不知道黑是否終於變成了「一般的顏色……就像其他顏色一樣。」之所以說黑和其他顏色一樣,是因為我們有黑墨水,一如有藍墨水及紅墨水;有黑顏料,一如有赤土色的顏料。可是黑又與其他顏色不同,人沒辦法打開黑燈,卻能打開紅燈或白燈。哲學家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說,燈裡無法有灰光或棕光。但灰或棕仍是由光構成,而黑據說是沒有光的。就這點而言,黑和其他顏色都不一樣。不管光還是顏料都可說有淡紅、淺藍,卻無法說有淺黑或淡黑。黑就只有「飽和的」黑。
於是,黑既是顏色又同時不是顏色,兩種說法都時有所聞。其實,如果真要說黑是什麼顏色,應該要說是白色。因為沒有任何黑色的物品是全黑的,即便最黑的天鵝絨,壟罩在最深的陰影之中,仍會反射回少許光子。1807年英國科學家楊格(Thomas Young)就曾說過:「黑體……反射白光,唯是比例極微。」黑板上的黑漆仍然會反射近乎於零的白光到人眼之中。「近乎於零」是誇張的說法,其實不論是一塊黑板或黑布,所反射出的光約莫是一張白紙的百分之十。若反射的光不是白的,而是偏向紅光或藍光,這時我們就不會說那塊黑板是黑的,而會說是藍黑或棕黑。這是因為黑從未真正置身光譜之外,也不像紅光或綠光一樣波段較窄。黑其實是白光的小兄弟。實驗室裡有一個領域叫「超材料」(metalmateiral),這種材料由比光波更小的奈米碳管製成,所反射出來的光不到百分之0.01,應用範圍從太陽能板到隱形戰機包羅萬象,但即便是超材料也並非全黑。
不過,由黑的事物發出的白光含量太低,幾乎不能說人眼看得到。這不免令人想問:看到黑的時候,我們究竟看到了什麼?剛才我們問黑究竟是光還是沒有光?另一個類似的問題則是黑究竟是種感知,還是缺少感知?怪就怪在,我們都知道視覺仰賴光,若沒有光子撞擊視網膜,就不應有訊號傳遞,但同時我們又感覺自己「看見」了黑色的事物,而非感覺眼前所見破了一個洞。偉大的光學家亥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曾於1856年主張:「即便是因為完全無光才有黑,黑仍是千真萬確的感知。對於黑的感知,和毫無感知有清楚差異。」對於這點,他恐怕無法完全解釋,畢竟他也說過黑色的物體並沒有送出對視網膜的刺激。
近年來的研究則讓他的直覺有了根據,甚至還顛覆了原本我們以為看到的是光而非黑暗的想法,英國生理學暨生物物理學教授霍奇金爵士(Sir Alan Hodgkin)發現,視網膜細胞是因為「黑暗而非光線使光接收器的內部帶正電,並導致化學傳導物質釋放,刺激下一層的細胞。」彷彿是說,眼睛需要光,主要是因為需要看見哪裡是暗處。有位傑出的神經科學家曾經推測,在演化的遠古時代,微生物可能需要從亮處向暗處游動,後來可能也需要留心是否有黑暗的孔洞。孔洞可能代表安全,也可能有蟄伏的獵食者藏於其中。
視覺神經傳導還有其他階段。視桿細胞(rod cell)能看見明暗色調(tone),而視錐細胞(cone cell)則能看見色彩,並釋放出霍奇金所說的化學傳導物質(也就是麩胺酸)到構成第二層視網膜的雙極細胞(biploar cell)上。有一種雙極細胞會在光或顏色抵達時送出訊號,另一種則會在光(或者該說是顏色)移開時送出正訊號。視網膜送出的訊號總數大致維持穩定,並經由神經節細胞(ganglion cell)送往大腦。這些訊號顯示「這裡有光」或「這裡有顏色」,或者「暗而無光」或「這裡沒有顏色」,讓黑、暗相對於光、色有了可以比較的權重。
我們之所以會直覺認為,看到黑的時候的確是有所見,正是因為以上這番複雜的原因,而且從光學的角度來說,黑給人的存在感甚至可能要比白更強烈。要試驗這點,方法很簡單:在一張紙上交錯畫上同寬的黑白條紋,這時你看到的是黑夜中的白色欄杆?還是白色空間中醒目的黑線?雖然白條紋中充滿各種波長的光,也很可能因此看起來比黑條紋要寬,但黑條紋仍可說是較有存在感。或許正因如此,人類喜歡用木炭在淺色石頭上書寫,更勝於用粉筆在石板上寫字;喜歡用黑墨水多過白墨水;更因此在1980年代把世上的電腦從黑底亮字改成了白底黑字。
還有一個根本問題:「黑」這個字,還有其他語言裡會被翻譯為「黑」的字,到底代表什麼意思?不論就色相(hue)還是色調的而言,都不難確定法語「noir」、德語「schwarz」、義語「nero」、希臘語「mavro」的意思都和英語中的「black」一樣代表「黑」。至於譬喻用法,則可能因語言而有所不同,法語「dans le noir」和英語的「in the dark」一「黑」一「暗」,都指「被蒙在鼓裡」,但是英語「in the black」的意思卻是「有獲利」,不過「黑市」在英語是「black market」,法語則是「marché noir」,都用了「黑」字。形容顏色時,有時用詞似乎並不那麼嚴謹。英語用黑(black)來形容瘀青的眼睛;在希臘,紅酒和裸麥麵包是黑的(mavro)。不過上述用法可說是方向性用法,表示相較於一般的顏色,這裡所指的顏色更往黑的方向偏。而黑的核心意義,從字面意涵來說是碳黑、墨黑,從譬喻意涵來說則是不幸、敗壞或糟糕。
顏色詞的意思一般而言都很模糊,而且時空離現代越遠,就越難掌握其義。古代文化並沒有現在我們用的這一套曼塞爾(Munsell)表色體系,也沒有許許多多飽和的顏色。此外,時代越早,「色彩詞」就越不單純只是指色相而已。英國首相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曾好奇希臘人不知是否都是色盲,否則詩人荷馬的顏色詞怎會用得如此之少、之含糊。拉丁文形容詞「flauus」能形容蜂蜜、玉米、金髮及黃金,似乎帶有黃色的意味,但又可用於描繪羞赧的臉色、泛著波光的水,還有橄欖葉的背面。有些詞,今天我們用以指顏色,但究其詞源,還能用來形容事物外觀的其他層面。英語中綠色「green」一詞就有這一層意思。這個詞源自印歐語言中的「ghreroot」,有生長、繁茂之義,英語片語「grow green」(變得綠意盎然)當中的兩個詞都來自於此,另外「ghreroot」也演變為「grass」(草)一詞。現在「green」是顏料的一種顏色,也是光學中的「原色」,但年代更早、語義範圍更廣的意思則是青澀未熟、缺乏經驗、天真。其他的詞以前也並非單指某一色相,而是用來形容明暗。英語「black」來自印歐語言中的「bhleg」,意思是「照耀、閃耀或是燃燒」,另一個詞源則是日耳曼語「blakaz」,意思是「燒焦的」。而古英語中「blaec」一詞主要意思為「暗的」,但也有「灼燒的」之義。一直到了中世紀英語「blak」,色相才變為主要意涵,指的是煙灰、煤炭、瀝青還有烏鴉的顏色。
也不是所有與顏色有關的詞在演變的過程中都只朝單一色相前進。古英語中,「salu」指的是一種灰撲撲的暗色,更偏向棕色,但演變為現代「sallow」一詞後,形容的則是人蠟黃的膚色──要想在曼塞爾表色系中挑出這個顏色還不容易。要探討顏色詞和顏色詞的歷史很是麻煩,我下筆時已經盡量不要過度簡化。有些顏色詞的意思乍看可能和今天的用法一樣,其實並不然。從前要想把布染黑十分困難,只能用菘藍、茜草,五倍子、木藍類植物反覆染色,製成的衣料雖然用「black」、「noir」、「schwarz」或「nero」等代表黑的詞形容,但看起來可能更像是骯髒的紫色。幸好顏料和墨水多半用煙灰製成,而煙灰之黑至今未曾改變。
此外,我們也不應簡化自己使用顏色詞的方式,很多時候顏色不只是顏色,有時還帶有芬芳,這裡指的是玫瑰(rose)、晚櫻(fuchsia)、紫羅蘭(lilac)、薰衣草(lavender)等花名變成顏色詞時的情形,這些詞很少用於形容男裝,更常見於女裝,就算指的是色相,用詞也不盡然總是準確或一致,比如我們知道紅指的是倫敦公車的顏色,但仍然會把橘紅、棕紅的頭髮稱為紅髮。顯然,「黑」這個詞不只用以稱呼某個色相(瀝青的顏色)的名字。假如我們說加爾各答或外太空有個「黑洞」,心裡想的並不是塗滿瀝青的空穴,而是一片黯淡無光(取其譬喻意涵,而非光學現象),意思是窒息而死,或是星球完全崩毀。而黑依然是黑。古埃及人用木頭燃盡後的煙灰製造出黑色顏料,替擺在墓室裡的木頭偶像畫頭髮、描眼睛。他們稱這種顏色為「凱邁特」(km),也用這個詞來指稱尼羅河中肥沃的黑土,並據此稱自己的國家為「凱邁特」(Km)。凱邁特一詞有諸多意涵,可以指整個埃及,但也指「黑」,今天去博物館就可看到,他們的黑就是我們的黑。
但顏色也不需要人類起的名字。許多鳥類的視色能力都比人類要好,能夠看到紫外線光的波段。鳥類求偶時會展示飽和的羽色,當中也包括潔白和墨黑兩種顏色,這顯示要辨認、欣賞顏色並不需要言詞。鳥類身上的羽色在紫外線中可能極為繽紛,但在我們眼裡卻是毫不起眼的灰色。還有,現在有好些社會(也許以前更多)的顏色詞數量似乎十分有限,可是對於彩色寶石的欣賞卻舉世皆然。就好像有些語言用同一個詞形容綠色、藍綠色和藍色,但人人都能看見綠寶石和藍寶石的不同。從過去印加人還有阿茲特克人利用各色玻璃製造串珠,或在身上穿戴五彩繽紛的鳥羽就可看出,不論是否有言語形容,「好色之心」似乎人人有之。而且還不只是喜好而已。相反的,這種對顏色的喜好在殿堂美學不存在之處可能代表極為細膩的美感,比如村莊織造的毯子交織了各種色彩,微妙而美麗。摩洛哥的柏柏爾(Berber)地毯顏色精巧又鮮豔,當中常常包含黑色。
研究視覺中的顏色或是色彩詞用法的改變,也無法解釋人賦予顏色的價值。英國小說家喬治.艾略特的作品《米德鎮的春天》(George Eliot, Middlemarch)中,一對姊妹要共分母親的珠寶,拘謹保守的姊姊多蘿西亞感嘆道:
說來也怪,顏色竟能如香味一般沁人心脾。我想就是因為這樣,聖約翰寫〈啟示錄〉才以寶石作為精神的象徵。這些寶石看來彷彿天國的芬芳。我覺得綠寶石比其他寶石都美。
雖然黑玉、縞瑪瑙、黑電木、電氣石等寶石在十九世紀十分受人喜愛,但故事中的小匣子裡並沒有這類黑色珠寶,不過姊妹倆倒是討論了哪一件珠寶和多蘿西亞身上的一襲黑裙最為相襯。她母親早已過世多年,因此她穿黑裙並不為了哀弔,而是因為她個性一本正經,也因為那個時代覺得黑色雅致,甚可說是美麗。那次她選擇了一枚帶鑽的綠寶石戒指,還有一條搭配的項鍊。
再回來談聖經〈啟示錄21:1-27〉,聖約翰在天國的牆上看到的寶石有紅(碧玉、紅寶石、鳳信子石)、有綠(綠寶石、綠瑪瑙)、有藍(藍寶石)、有紫(紫晶),還有橘黃色(紅碧璽)。不知道聖約翰是否有一套能夠準確描繪各種寶石色相的顏色詞,不過他也不需要,他認得這些寶石,我們也看得到。無論如何,顏色詞的幫助也有限,畢竟寶石的顏色和布上的、光束中的或蝴蝶翅膀上的顏色特性很不一樣。原先他羅列牆上寶石,想呈現的是種超凡脫俗的美景,如果我們說聖約翰中的天國閃著明亮的紅、綠、黃、紫色光芒,則難以呈現,而美景之所以美,顏色居功不小。
這是因為顏色詞並不形容顏色,只賦予顏色一個名字。要以言詞描繪色彩給人的感受並不容易,也許根本不可能。就連形容黑色也是看來容易做來難。「就像什麼都看不見」或是「像暗夜」或是「像在無光的櫃中」這樣的說法,並無法形容我用來裝(黑色)手機的黑色手機袋的黑。我也許會說:「就像煙灰一樣。」或者「就像印度墨水一樣。」但是那個手機袋看起來既不像煙灰,也不像印度墨水。於是我又回頭用「黑」這個詞,這個詞指涉了黑,卻不形容黑。不這麼做,就只能比擬,也就是譬喻。
人喜歡顏色,又不確定顏色到底是什麼,於是一直以來不斷討論顏色。柏拉圖曾說,視覺是自眼中發出的火,與可視之物射出的火交互作用之後,便形成顏色。我們這個時代討論顏色,尤其近幾十年來,討論得更廣也更有系統。許多討論都源自人類學家柏林(Brent Berlin)和語言學家凱伊(Paul Kay)的書《基本色彩詞語》(Basic Colour Terms)。兩人認為即便語言中的色彩詞很少,也幾乎都會有同樣幾種顏色:首先是黑白(但這兩色也帶有明暗色調或是冷暖感覺的意味),再來是紅色,接著是黃色或綠色,然後是藍色。經光學及語言學領域多方試驗,已認定兩人的理論確有其事。他們的論點也大幅證實了神經科學研究中的觀點:一般人所能看到的顏色大致相同,人與人之間僅有少數差異,同一個人不同年紀時也有些微不同。此外,人傾向於先區分黑、白、紅、綠、黃、藍等主色,這主要是因為生物而非文化因素。
不同文化賦予顏色的意義可能天差地別,但歷史、美學以及人類學文獻也顯示,有些文化雖然差異極大,但過去數千年來賦予幾個「主色」的角色卻相去不遠:白色主要代表良善,黑色往往有負面意涵,而紅色則多帶有活力。這些特性和人類經歷的恆常事物息息相關,倒不盡然是顏色本身就帶有此種特性。許多文化中用來代表「白」的字詞可能也指母乳和精液;「紅」字可能指血液;「黑」字則可能指煙灰、煤炭、木炭、眼睛和頭髮(還有糞便)。也有許多文化一致認為黑色象徵厄運等最負面的事物,代表不孕、憎恨還有死亡。奧地利哲學家史丹納(Rudolf Steiner)覺得黑「與生命為敵……當內心有如此不堪的黑,靈魂就遺棄了我們。」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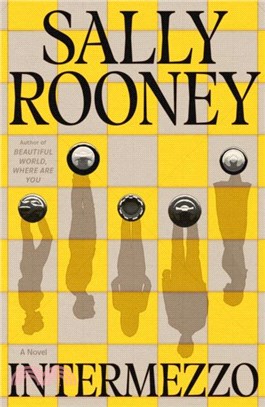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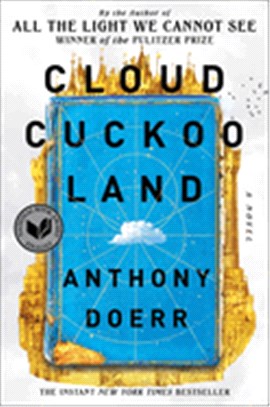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