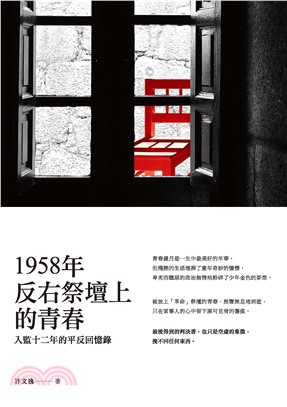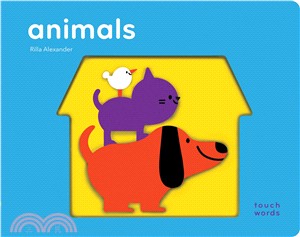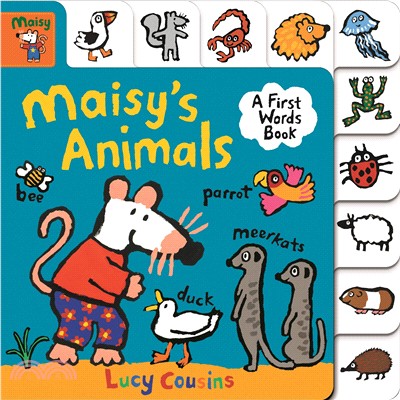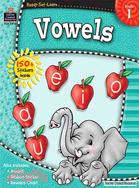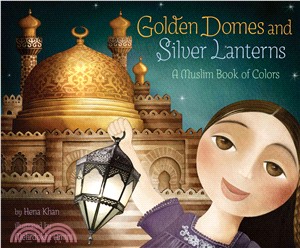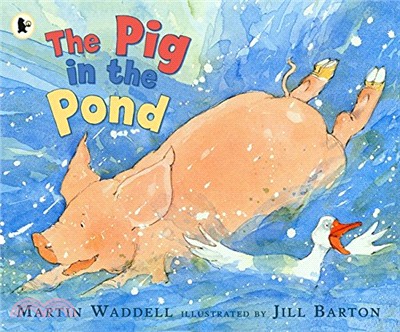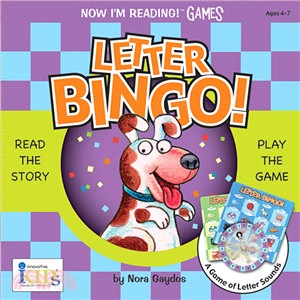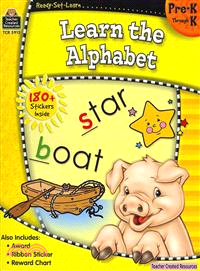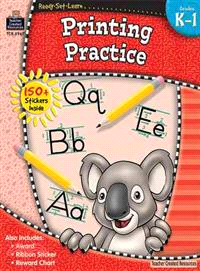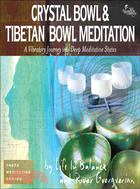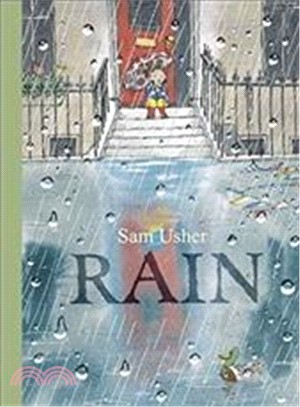1958年反右祭壇上的青春:入監十二年的平反回憶錄(電子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這是一本回憶錄。真實記錄了在一九五○年代,一個人怎樣從備考大學的單純學生,由於一場政治運動而失去學籍,又在陰錯陽差之下獲罪入獄,之後被人陷害而成為監獄就業人員,直到出獄、獲得平反的詳細歷程。
在社會這所大學裡,作者以親歷者的目光觀察到世間的萬象,從而開始用客觀和科學的態度來思考這一切,逐漸地完成了自己的蛻變。書中富有感情與真誠的文字,記錄了許多其他相似人物的命運,可以窺視到那個時代的一些脈絡,從而激起人們的反思。
作者簡介
許文逸
1940年11月出生於大陸廣西桂林市。1952年考入桂林中學讀書。1958年5月,在高中即將畢業之時,學校開展了一場反歪風邪氣的政治運動,在遭到慘烈批鬥後被開除學籍,定為政治不及格,不准考大學。離開學校後很快又被卷入一件「反革命」案,被判刑六年。滿刑後,又被強迫留在監獄作為就業人員繼續改造。1970年12月始獲釋。1979年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之路,1986年12月被廣西高級法院改判為無罪釋放。1990年10月因病提前退休。
序
前言
一九八六年一個寒冷的冬日早上,我把一張三百元的現金支票遞給銀行櫃檯裡的一個工作人員,他用驚詫的目光看了我好一會,說:「冤獄費,誰冤獄了?挨了幾年?」
我無語,心卻在滴血。
一九七九年我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之路。幾經反復,一九八○年七月桂林市中院改判為「已構成犯罪,但判刑不當,改判為免予刑事處分」。我依然不服,官司從廣西高院一直打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終於把最後的一點「尾巴」割去了。
這時,整整的二十八年已經過去了。從十八歲到四十六歲,它涵蓋了我全部的青春年華。當廣西高級人民法院向我宣佈宣告無罪,並把那張寫著冤獄費的支票遞給我的時候,我沒有一絲的激動。我只是木納的自語了:「啊啊,三百元,我一生的代價……」
人們常說,人如果老了,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昨天或者剛剛發生的事往往會忘得乾乾淨淨,而那遙遠的往事卻是異常的清晰。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我想,我確實是老了。
我這一生,歷經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盪的時代,見證了許多事件的發生與過程。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那段歷史,甚至不相信那些曾經的荒唐的事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就萌生了要把我的經歷寫出來的衝動。開始,是想寫一部小說。動筆之後,才發現難度之大已遠遠超出我的能力。
小說既沒有能力寫,就萌生了寫回憶錄的念頭。然而,按照俗成與傳統的觀念,回憶錄又豈是我這樣的布衣平民能寫的?那時,我也確實是太忙,一面要謀生,維持一家大小的生計,一面還要起早貪黑地讀書。光陰迅速,事情一擱,轉眼又是三十年過去了。於今我已是垂垂暮年,心中總不甘心讓我那段刻骨的歷史隨我一同走入墳墓。於是,我為自己羅織了一個這樣的理由:大人物(或名人)們的歷史就猶如那參天的大樹,壯美,充實,偉岸,閃耀著令人眼花撩亂的光彩。我這樣的一介草民的歷史就權當那樹下不起眼的野草,雜亂,平庸,猥瑣,絲毫沒有迷人入勝的風光。野草,根不深,葉不美,然而它也是生命。上帝既創造了它,天地又是何其的遼闊與紛繁,其間也總該有它的一片棲息之地吧。
現在我是以完全真實的筆觸來記述,既不需要煞費苦心地去構思和刻畫人物的性格,也不需要傷透腦筋去構築情節的展開與矛盾的衝突,只要把思緒整理一下,文字通順就可以了。值得慶幸的是,三十多年前我搜集和整理的許多素材,今天成了我這本回憶錄非常寶貴的資料。
透過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經歷,人們或許能窺視到一些歷史的脈絡。為了公正和不帶偏見,我必須盡力跳出個人的恩怨來客觀的描述。
我在讀初中的時候,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的信徒了。
高中即將畢業時,儘管我受到學校極其錯誤的批判和處理,我也認為這只是一個個別的事件。以後,在社會這所大學裡,無數鮮活生動的人和事,衝擊著我,我開始以一種審慎的科學的眼光來重新認識和思考這個世界。一個信念漸漸在我的心中萌生,由模糊而越來越明晰與堅定:歷史終將按人民的意志前進。「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我想,這應該是一個普遍的真理。
在洶湧的歷史長河中,我甚至連一個水泡都不是,轉眼就將消逝。下面的文字,人們如果讀後總算是多少的瞭解了一些那遠去的歷史,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我的開場白結束之時,魯迅先生《野草》中的一段話卻總也揮之不去: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目次
我的父親
童年
少年時代
畢業前夜
噩夢的開始
苦難人間
囹圄生涯
冤海拾零
我的母親
不是犯人的犯人―監獄的就業人員
文革歲月
尾聲
後記
書摘/試閱
我的父親
公元一九四○年深秋的一個晚上,我從母親的懷裡,很不情願的來到這個世界。那羸弱的哭聲和瘦小的身體,使母親懷疑我是否能養得大,並且擔心這孩子的一生恐怕是多災多難。在我以後有了一點記憶的時候,曾多次聽母親說,我生下來時簡直就只有一個量米筒那麼大。父親似乎也並不怎麼重視這樣一個小生命的到來。因為我已經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了。母親曾對我說,你父親小氣得要命,我生了你後,就只買了半斤瘦肉給她吃。這也不奇怪,因為這時,父親已經娶了第三房姨太太了。
父親名叫許繼雄,一八八六年生於湖南省零陵縣許家橋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裡。那是一個極為偏遠貧窮的小山村。當歷史往前行進了一百一十四年後的一九九○年,為整修父親的墳墓,我回到了我的故鄉。上一次是在一九四四年為躲避戰亂,我是坐在籮筐裡被挑著回來的。那時我四歲。第二年日本投降,母親帶著我們舉家又遷回桂林。
掐指算來,我在故鄉只生活了短暫的一年多,之後就再沒有回來過了。我在坐了兩個小時的火車和一小時的汽車後,登上了一輛由農用車改裝的客車。說是改裝,實際上就是在車廂的兩旁放上兩排凳子。車上擠坐著十幾個當地的農民,還有幾個沒有座位了只好站著,手扶著廂板一晃一晃的搖動。崎嶇的泥路卷起漫天的灰塵。待我半個小時後下車時,我早已是蓬頭垢面了。在泥濘的田基上走了大約兩三哩,一個破敗不堪的小小村莊出現在我的面前。同行的人告訴我,這裡就是我的故鄉,我父親出生的地方。
幾乎清一色的泥磚砌就的房屋,由於常年風雨的侵襲,有些房屋已是歪斜得很嚴重。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村子還沒有通公路,也沒有通電。在父親的年代,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村子的旁邊有一條清澈的小溪,小溪上有一座小小的石拱橋。我幼小童年的記憶中那條彎曲的、因年代久遠而磨走得鋥亮的石板小路,依然泛泛的浮著青藍的光。
一個遠房年邁的親戚接待了我們。他告訴我哪間房是我的父母住過的,哪間房我的二哥三哥住過,彷彿這一切都是昨天的事情。看著我的先人們曾經居住過的這些破敗不堪、用泥磚或已經發黑的木板圍就的幾廂低矮的房屋,那斑駁的牆壁和地上的肮髒泥土,我的腦海裡浮現出那些逝去的年華和他們艱難的生活情景。他們不屈服於這困苦的生活,勇敢地從這大山裡走了出去,依靠自己的勤勞節儉、智慧和艱苦的奮鬥,開創了家業。我的父親在一九四五年初就去世了,如果他活到一九四九年,毫無疑問,他一定將被定為大地主。然而,這裡的一切,哪裡有半點我們的電視中那地主老財奢華生活的影子?
我並不認同當年所謂的地主都是罪大惡極之人的論點。他們其實代表著當時農村的中堅力量和進步的生產力。他們頭腦比較靈活而且往往多少受了點教育,識幾個字。他們絕大部分是靠勤奮的勞動和聰明的頭腦發的家。這是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一九五○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了兩百多萬地主,搶走了他們一輩子甚至幾輩子辛苦攢積下來的財產,上演了一幕幕罄竹難書、滅絕人寰的血腥慘劇。他們都是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今天農村裡的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他們的財富和雇工的人數比之昔日的地主要多十倍、百倍。如果說那些地主該殺,那又該如何面對今日的這些先富起來的群體?
千秋功罪,我堅信,歷史自有評說。
房屋後面有一個低矮的土嶺,在我兒時的印象中,那彷彿是一座碩大無比的山峰,現在看來卻是小得就像一個土堆了。「土堆」上生長著高大茂密的樹木,童年時我時常跟我哥哥和鄰居的小夥伴們來樹蔭下玩耍,這兒就是我童年的樂園。我們在樹下找一種叫「悉卡子」的野果,用落在地上的乾枝,燃起一堆火來,把果子燒熟了吃。於今我已回憶不出這「悉卡子」的準確形狀,也說不出它的味道是甜還是香,大約總是很不錯的吧。
距村子不遠有一座連綿三四里的大山,山上長滿了樹木,鬱鬱蔥蔥。父親和奶奶的墳墓就在這山的山腰。同行的老村長對我說:「你的父親是個好人,這座山原來並不屬於我們村,多虧了你父親當年把它買下來,現在整個村子燒柴就全靠這座山。」
我說:「我的父親怎麼一下又成了好人了?過去不是說他是地主嗎?」村長說:「我們可從來沒說過你們家是地主。過去有人來調查,我總是說你們是中農的。事實上也是這樣,你父親在解放前五年就已經去世了,家產一分哪裡還算得上是地主呢?」我相信他說的是實話。一九五五年時,三哥在部隊為了入黨的事,家鄉曾寄來一個家庭成份的證明,那時我已初中畢業,我清楚的記得證明上確是寫著:「茲證明許文森同志的家庭出身中農……」我始終也搞不明白,十幾年以後,我幾個哥哥的家庭出身怎麼都成了地主?大哥的家庭出身甚至是地主兼資本家。只有我一個人填寫的還是中農成份,因為我親眼看見過那份證明,所以不管審查我的人或是來外調的怎麼說,我都是一口咬死家庭是中農。否則,我的麻煩將是更大。
父親在家排行老大,下有兩個兄弟。十三歲時,父親身背十餘斤大米,夥同村人從家鄉一路步行跋山涉水來到廣西桂林市。小小年紀,奔波數百里,途中往往食不果腹,夜無蔽所,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來到桂林,父親經人介紹進了一家印刷廠做學徒。那時的小學徒簡直就是一個傭人。搞衛生,倒痰盂,又髒又累的活都得幹。至於學手藝,那得看師傅高不高興和自己的機靈了。那時,流傳一句話:「教會徒弟打師傅。」為了自己的飯碗不被搶去,師傅們往往都留了一手。
父親是個極聰明的人,悟性很高,儘管只讀過幾年私塾,但技術學得很不錯。三年學徒,不僅精通了各種印刷技術,還刻得一手好字。學徒期滿又幫師了一年,這些日子都是只管吃飯,沒有工資的。
十七歲時,父親離開了原來的老闆,自立門戶刻字。搞了幾年,感到發展不大,就與人合作,租下一處門面,買了幾台印刷機,搞起了印刷兼刻字。由於經營得法,幾年下來,得到很大的發展。父親便自立門戶,開了間印刷廠,取名許景泰印務局。父親精通印刷技術,管理嚴格,工廠發展很快。父親甚至到上海、廣州先後採購了石印機、圓盤機、四開機、鑄字機等印刷設備,許景泰印務局成了桂林市聞名遐邇的字號。
家業大了,父親依然是異常勤儉。廠裡事無巨細,往往都躬親力行。對產品質量極為重視,信守合同。當時的印刷業競爭十分激烈,官辦的印刷廠不算,抗戰前桂林民間的有二十七家,到一九四三年,大量的文化人遷來桂林,印刷廠達到一百零九家。省、市政府等機關要印的東西都是公開招標,公私工商戶都可以投標。憑著先進的設備和高質量的管理優勢,許景泰印務局常常中標,所以生意十分興隆。有時為了趕時間按時交貨,連兒子都得上陣,也一樣發給計件工資,倘有質量問題,一樣呵斥。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發了財的人最時髦的事情是什麼呢?買田地,娶姨太太。父親也沒能走出這世俗的圈子。於是風光無限的回到老家買了幾十畝田地,又先後娶回了兩房姨太太。
正當父親事業日益興盛之時,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中華民族的又一場苦難深重的歲月開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飛機初襲桂林,市民死傷數百人。此後空襲日益頻繁。一九四一年,父親不得不把工廠遷到郊區農村,在戰亂中堅持著經營。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桂林。父親遂把所有的機器埋在菜地的地窯裡,帶上家眷,逃回湖南老家鄉下以躲避戰亂。豈料沒等到日本投降,父親便病故於鄉間,終年五十九歲。
父親病重時,知來日不多。便把家產分成了三份。按子女的多少,每個老婆一份。由於人口眾多,攤到每個人身上已沒有多少。城裡的房屋已毀於戰火,埋在地窯裡的機器,光復後幾經找尋,發現已不翼而飛,連雇來看機器的人也不見了。房子沒了,機器沒了,父親去世了,田地也賣光了,一切都完了。許景泰印務局已經徹底的衰敗,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這一切發生在解放前四到五年,哪裡還能和「資本家」、「地主」扯得上半點的干係?
父親去世時,我只有四歲多,在我的腦海裡父親的印象太朦朧了。我不記得他的音容笑貌,不記得他和我說過了什麼話,也不記得他是否親昵過我。好像他總是在忙著什麼。我讀中學的時候,曾經看見過一張父親的相片。那是一張放大了的七寸的有點泛黃的相片,相片上父親大約是五十歲的樣子,戴一頂當時有錢人時興的禮帽,稍顯削瘦的臉,緊閉的雙唇,一付嚴肅凝重的神情。然而,父親這張唯一留世的相片,後來卻是失蹤了。也許是大哥在文化大革命時燒去了。因為那時大哥的家經常有革命的小將來抄家,不燒去又能藏到何處?到處是一片紅色恐怖,一旦被抄出,那後果將是極其嚴重。
我的母親曾不止一次對我說,我太像父親了,從相貌到走路的姿態。
我卻認為,我們這些後人,沒有一個有父親的能幹與聰慧。一九九○年清明,我在闊別了四十餘年後第一次回到故鄉時,曾作七律〈一九九○年清明返湖南老家有感〉:
四十五年還故園,霪雨絲絲路維艱。
兒童喃呢音猶記,桑榆蹣跚夢難全。
溪畔柳綠聞犬豕,霧裡山青話桑田。
忽憶先人創業事,天命只作而立年。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