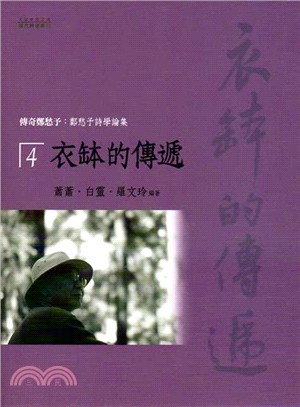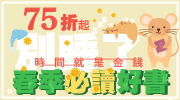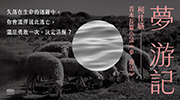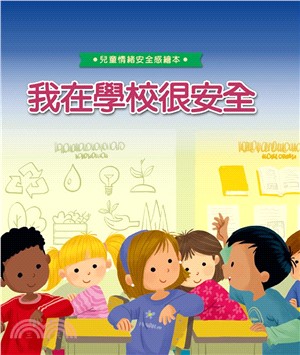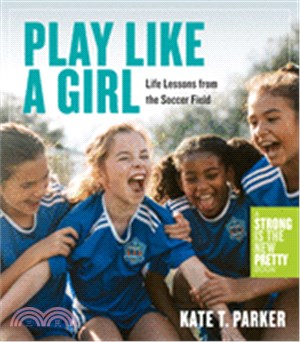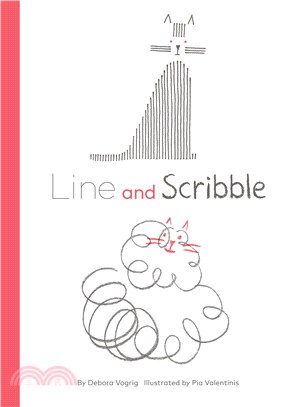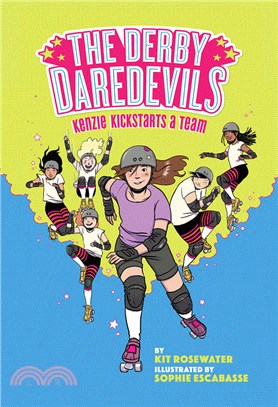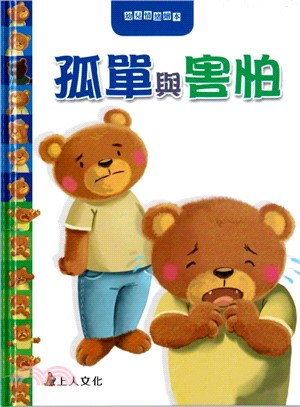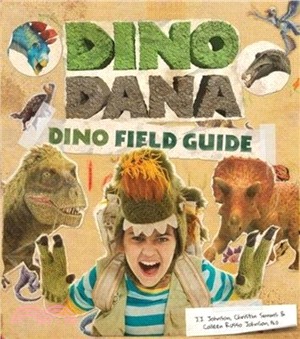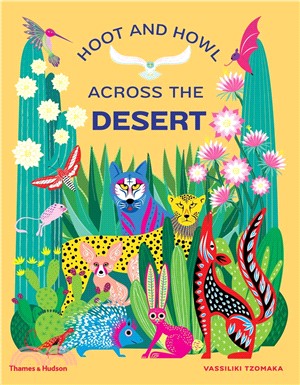被偷走的骨灰甕:楊煉文學訪談錄(電子書)
商品資訊
定價
:NT$ 360 元優惠價
:70 折 252 元
閱讀器:書紐電子書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7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這本書,談楊煉的血統――第一代可與漢族通婚的滿蒙祖母。
這本書,談楊煉的家世――吉祥戲院少東家的父親與上海電影世家的母親。
這本書,談楊煉在文革時的戀愛、階級鬥爭。
這本書,談楊煉在北京、在紐約、在紐西蘭、在德國,在世界各地的漂泊。
這本書,談楊煉與艾倫・金斯堡、蘇珊・桑塔格、阿多尼斯、高行健等當代大家的交流。
這本書,談楊煉不斷煉字煉意,不斷探察自我內在的幽暗。
這本書,談楊煉或許曾離散於中國,卻從未離散於中文的書寫、創作與生活。
歷時十天的訪談,近二十萬字,收錄詩人生活影像。
我把聽到我的詩被禁止的消息那天,作為正式開始流亡生涯的日子,詩代替詩人被殺死了。――楊煉
這本書,談楊煉的家世――吉祥戲院少東家的父親與上海電影世家的母親。
這本書,談楊煉在文革時的戀愛、階級鬥爭。
這本書,談楊煉在北京、在紐約、在紐西蘭、在德國,在世界各地的漂泊。
這本書,談楊煉與艾倫・金斯堡、蘇珊・桑塔格、阿多尼斯、高行健等當代大家的交流。
這本書,談楊煉不斷煉字煉意,不斷探察自我內在的幽暗。
這本書,談楊煉或許曾離散於中國,卻從未離散於中文的書寫、創作與生活。
歷時十天的訪談,近二十萬字,收錄詩人生活影像。
我把聽到我的詩被禁止的消息那天,作為正式開始流亡生涯的日子,詩代替詩人被殺死了。――楊煉
作者簡介
楊煉
一九五五年出生於瑞士,成長於北京。七○年代後期開始寫詩。一九八三年,以長詩〈諾日朗〉轟動中國詩壇,其後,作品被介紹到海外。迄今共出版中文詩集十四本、散文集二本與一部文論集,已譯成三十餘種外文。楊煉作品被評論為「像麥克迪爾米德遇見了里爾克,還有一把出鞘的武士刀!」也被譽為世界上當代中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聲音之一。楊煉獲得的諸多獎項,包括義大利蘇爾摩納獎(2019);雅努斯・潘諾尼烏斯國際詩歌大獎、拉奎來國際文學獎、義大利北-南文學獎等(2018);英國筆會獎暨英國詩歌書籍協會推薦翻譯詩集獎(2017);臺灣首屆太平洋國際詩歌獎之累積成就獎、李白詩歌獎提名獎在內的四項中國詩歌獎(2016);義大利卡普里國際詩歌獎(2014),義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12)等等。並於二○○八年和二○一一年最高票當選為國際筆會理事。二○一三年,獲邀成為挪威文學暨自由表達學院院士,二○一四年至今,楊煉受邀成為汕頭大學特聘教授暨駐校作家。自二○一七年起,擔任一九八八年創刊的《倖存者》詩刊雙主編之一。
朱又可
中國報紙副刊編輯。出版有《行者的迷宮》(與張煒合著)、《一個人和新疆》(與周濤合著,獲《南方都市報》二○一四年度非虛構類好書),以及人物對話選集《彆扭的聲音》等。獲第四屆「中國報人散文獎」(2015)。
一九五五年出生於瑞士,成長於北京。七○年代後期開始寫詩。一九八三年,以長詩〈諾日朗〉轟動中國詩壇,其後,作品被介紹到海外。迄今共出版中文詩集十四本、散文集二本與一部文論集,已譯成三十餘種外文。楊煉作品被評論為「像麥克迪爾米德遇見了里爾克,還有一把出鞘的武士刀!」也被譽為世界上當代中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聲音之一。楊煉獲得的諸多獎項,包括義大利蘇爾摩納獎(2019);雅努斯・潘諾尼烏斯國際詩歌大獎、拉奎來國際文學獎、義大利北-南文學獎等(2018);英國筆會獎暨英國詩歌書籍協會推薦翻譯詩集獎(2017);臺灣首屆太平洋國際詩歌獎之累積成就獎、李白詩歌獎提名獎在內的四項中國詩歌獎(2016);義大利卡普里國際詩歌獎(2014),義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12)等等。並於二○○八年和二○一一年最高票當選為國際筆會理事。二○一三年,獲邀成為挪威文學暨自由表達學院院士,二○一四年至今,楊煉受邀成為汕頭大學特聘教授暨駐校作家。自二○一七年起,擔任一九八八年創刊的《倖存者》詩刊雙主編之一。
朱又可
中國報紙副刊編輯。出版有《行者的迷宮》(與張煒合著)、《一個人和新疆》(與周濤合著,獲《南方都市報》二○一四年度非虛構類好書),以及人物對話選集《彆扭的聲音》等。獲第四屆「中國報人散文獎」(2015)。
序
「馬背上的民族,眼睛永遠盯著更遠的一條地平線」――採訪緣起
二○一八年九月七日到十七日,楊煉從柏林到匈牙利接受「雅努斯・潘諾尼烏斯國際詩歌大獎」(Janus Pannonius Grand Prize for Poetry),我應邀從廣州前往採訪。共處十天時間,我想,何不借此我們都在陌生的「他鄉」的機會,好好聊聊楊煉先生的文學人生?兩人一拍即合。
楊煉似乎永遠樂觀、不羈,溢出真誠的笑,似乎有無盡的精力。正如他說:「我每次到機場、火車站,雖然有漂泊的蒼?,同時也不乏一種興奮。因為馬背上的民族,眼睛永遠盯著更遠的一條地平線。你越向前,地平線越向遠處推移。」
楊煉有四分之一蒙古血統,祖母是第一代可以和漢族通婚的滿蒙人。奶奶的祖父從貴西道升官到貴州作臬臺,最後一任官是奉天府尹,也就是「瀋陽市長」。「奉天是清朝皇帝的龍脈,叫盛京,等於是給皇上看祖墳的。」他形容,祖母家那種蒙古性格「可以叫淳樸,也可以叫不懂事」。票號要倒閉,派人送回去兩大車銀子,被她父親以家裡放不下為由趕走,銀子也不知所終。她家後來「敗落得很慘」。
楊煉的曾祖父從清朝宮廷畫家溥雪齋手裡買來老宅,院裡的太湖石由圓明園廢墟搬來,假山、迴廊,金絲楠木雕的格柵。曾祖父後來經營了北京內城第一個現代戲園子吉祥戲院,梅蘭芳就是從吉祥唱出來的。吉祥戲院在東安市場邊,在吉祥看完戲,到對面的東來順吃涮羊肉,是一套。他本來對楊煉的父親寄予厚望,想讓他傳承家業。沒想到少東家「是一個天生的理想主義者,痛恨做買賣,後來乾脆投奔共產黨」。楊煉說現在九十八歲的父親至今對京劇往事如數家珍。
楊煉的父親在輔仁大學讀的是英文系,出身於上海電影界家族的母親(楊煉母親的舅舅是有名的《八千里路雲和月》、《新兒女英雄傳》的大導演史東山)讀的是燕京大學英文系。兩人在一九四九年後被外交部派到歐洲第一個承認紅色中國的瑞士的中國大使館工作。楊煉一九五五年出生於伯爾尼(Bärn),不到一歲就在搖籃裡被父母「拎回」北京。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母親去世,前一天,她剛剛為楊煉整理相冊並題寫說明,像是冥冥之中的遺言。後來保存在他自稱「鬼府」的家裡的母親骨灰甕竟被偷走了。若干年後,楊煉寫道:「我母親的死,丟了。」
一九七八年,楊煉結識了北島、芒克等人及《今天》雜誌,後來成為「今天文學研究會」七理事之一。一九八八年他跨出國門,沒有想到開始了三十年的環球漂泊,「詩人不知道,但詩知道。」從此他和各國詩人一樣,「詩歌是我們唯一的母語」。
「不管我人在哪兒,我的中文創作就是中國文學傳統的根。不管面對誰,只要我說中文,這就是一個中國的標誌。」楊煉說,「我心理上從不悲悲戚戚,而是充滿積極、光明正大甚至驕傲的感覺。」他肯定地說,「我或許曾離散於中國,卻從未離散於中文。」他總是從歷史轉型的視野看待中國當下現實,在他的反思中,插隊的北京黃土南店,黃土高原上的半坡遺址,一直到他漂泊的藍色大海,其實都是一個「同心圓」。在他倫敦李河谷(Lea Valley)的住所,每年都有一個「鬼魂似的」蘋果掛在後院秋天的樹枝上。那個重複出現的蘋果,讓他的「他鄉」立刻就轉化成「故鄉」。
原來,習慣了黃土地是自己內在一部分的他,在海外久了,一步步地讓大海進入了身體,恰如他在《大海停止之處》寫下的句子:終於被大海摸到了內部。「其實反過來也一樣,也是我摸進了大海的內部。」楊煉說。因為,「漂泊本身就成了故鄉」。
楊煉總能找到當下可為的「事」:他創辦北京文藝網國際華文詩歌獎,舉行鹿特丹―北京網上同步詩歌節,介紹農民工詩歌,推動中英、中德詩人互譯,編輯出版大部頭英譯當代中文詩選《玉梯》等等。
他的名字「煉」也是他詩歌及工作方式的肖像。他不斷地煉字煉意,也不斷地探察自我內在的幽暗。「埋葬你心裡唯一的黑暗,唯一的謊言。」他在詩裡寫道。有一次在德國的朗誦詩歌會後,顧彬問楊煉,你的詩這麼黑暗,光在哪裡?「我的詩也許很黑暗,但我在寫,這就是光。」當時響起掌聲一片。「貫注在創作裡的能量,絕對是最高級、最明亮的,正是這種能量照亮了黑暗的現實。」時隔多年,楊煉闡釋道。
「我的寫作像考古。」楊煉說,他選擇的那些歷史材料,其實都是自己的內心場景,主題只有一句,就是「把手伸進土摸死亡」。因為,詩有一種深度,像深埋在地層裡的那種感覺。考古是為了能發現「深現實」的詩歌。他面對詩歌就像考古工作者面對考古發掘的現場一樣,「幾千年的大時間觀念,必須落實到一個小毛刷子一點一點刷掉灰塵的動作上」,「捋掉」不少雜質,讓以前隱藏或被遮蔽的詩意凸顯出來。
這些年,楊煉活躍在世界詩壇,從二○一二年獲得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V. S. Naipaul) 任評審團主席的義大利諾尼諾(Nonino)國際詩歌獎起,他這些年幾乎算是一個國際文學獎的得獎專業戶了。二○一八年,他獲得有「詩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匈牙利「雅努斯・潘諾尼烏斯國際詩歌大獎」,躋身於菲林蓋蒂(Lawrence Ferlinghetti)、阿多尼斯(Adonis)、博納富瓦(Yves Bonnefoy)和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等當代最重要的詩人之列,是獲獎的第一位中文詩人。
「楊煉的詩歌跨越了中國大陸、臺灣和海外空間,以及古代和當代中文詩歌的時間,彰顯出『天才與激情』貫穿了這些詩歌的『超越時間的生活』。」二○一八年九月十五日,楊煉在古城佩奇(Pecs)從身兼匈牙利總理首席文化顧問、評委會主席的蘇契・蓋佐(Szocs Géza)和匈牙利文化部長彼得・費凱迪(Peter Fekete)手中接受獎座和證書。
「今天的詩歌,是個體詩學的時代。深度,同時衡量著人與詩的個性。詩歌沉潛在海底,漆黑、冷靜地審視著風波險惡的世界。」楊煉在以〈一隻海蝴蝶〉為題的受獎演說中講道。
在布達佩斯的裴多菲文學博物館(Petőfi Irodalmi Múzeum),我和楊煉第一次見面,楊煉的夫人畫家友友就驚嘆:你太像年輕時的楊煉了。
伴著這種「相像」的緣分,在匈牙利期間,我記錄下與楊煉的「多瑙河十日談」。這是珍貴的友誼之旅。
從巴拉頓湖畔(Balatonfüred),到中世紀古城佩奇,再到布達佩斯,楊煉和友友手拉手並肩走著的背影,總是在我眼前。友友說,在世界漂泊,很多朋友忍受不了回國了。他們倆相濡以沫,是他們抵抗孤獨和長久堅持下來的好方法。我想她說的准沒錯。祝福他們倆人在一起的旅行,到處都是溫柔的「故鄉」。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楊煉從汕頭大學去義大利文化古城拉奎拉(L'Aquila)領取另一項國際詩歌獎。白雲機場廣州酒家為我們晚打烊了一個小時,我們補聊了最後一章,算是為這個稍稍漫長的文學訪談錄劃上句號。
二○一八年九月七日到十七日,楊煉從柏林到匈牙利接受「雅努斯・潘諾尼烏斯國際詩歌大獎」(Janus Pannonius Grand Prize for Poetry),我應邀從廣州前往採訪。共處十天時間,我想,何不借此我們都在陌生的「他鄉」的機會,好好聊聊楊煉先生的文學人生?兩人一拍即合。
楊煉似乎永遠樂觀、不羈,溢出真誠的笑,似乎有無盡的精力。正如他說:「我每次到機場、火車站,雖然有漂泊的蒼?,同時也不乏一種興奮。因為馬背上的民族,眼睛永遠盯著更遠的一條地平線。你越向前,地平線越向遠處推移。」
楊煉有四分之一蒙古血統,祖母是第一代可以和漢族通婚的滿蒙人。奶奶的祖父從貴西道升官到貴州作臬臺,最後一任官是奉天府尹,也就是「瀋陽市長」。「奉天是清朝皇帝的龍脈,叫盛京,等於是給皇上看祖墳的。」他形容,祖母家那種蒙古性格「可以叫淳樸,也可以叫不懂事」。票號要倒閉,派人送回去兩大車銀子,被她父親以家裡放不下為由趕走,銀子也不知所終。她家後來「敗落得很慘」。
楊煉的曾祖父從清朝宮廷畫家溥雪齋手裡買來老宅,院裡的太湖石由圓明園廢墟搬來,假山、迴廊,金絲楠木雕的格柵。曾祖父後來經營了北京內城第一個現代戲園子吉祥戲院,梅蘭芳就是從吉祥唱出來的。吉祥戲院在東安市場邊,在吉祥看完戲,到對面的東來順吃涮羊肉,是一套。他本來對楊煉的父親寄予厚望,想讓他傳承家業。沒想到少東家「是一個天生的理想主義者,痛恨做買賣,後來乾脆投奔共產黨」。楊煉說現在九十八歲的父親至今對京劇往事如數家珍。
楊煉的父親在輔仁大學讀的是英文系,出身於上海電影界家族的母親(楊煉母親的舅舅是有名的《八千里路雲和月》、《新兒女英雄傳》的大導演史東山)讀的是燕京大學英文系。兩人在一九四九年後被外交部派到歐洲第一個承認紅色中國的瑞士的中國大使館工作。楊煉一九五五年出生於伯爾尼(Bärn),不到一歲就在搖籃裡被父母「拎回」北京。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母親去世,前一天,她剛剛為楊煉整理相冊並題寫說明,像是冥冥之中的遺言。後來保存在他自稱「鬼府」的家裡的母親骨灰甕竟被偷走了。若干年後,楊煉寫道:「我母親的死,丟了。」
一九七八年,楊煉結識了北島、芒克等人及《今天》雜誌,後來成為「今天文學研究會」七理事之一。一九八八年他跨出國門,沒有想到開始了三十年的環球漂泊,「詩人不知道,但詩知道。」從此他和各國詩人一樣,「詩歌是我們唯一的母語」。
「不管我人在哪兒,我的中文創作就是中國文學傳統的根。不管面對誰,只要我說中文,這就是一個中國的標誌。」楊煉說,「我心理上從不悲悲戚戚,而是充滿積極、光明正大甚至驕傲的感覺。」他肯定地說,「我或許曾離散於中國,卻從未離散於中文。」他總是從歷史轉型的視野看待中國當下現實,在他的反思中,插隊的北京黃土南店,黃土高原上的半坡遺址,一直到他漂泊的藍色大海,其實都是一個「同心圓」。在他倫敦李河谷(Lea Valley)的住所,每年都有一個「鬼魂似的」蘋果掛在後院秋天的樹枝上。那個重複出現的蘋果,讓他的「他鄉」立刻就轉化成「故鄉」。
原來,習慣了黃土地是自己內在一部分的他,在海外久了,一步步地讓大海進入了身體,恰如他在《大海停止之處》寫下的句子:終於被大海摸到了內部。「其實反過來也一樣,也是我摸進了大海的內部。」楊煉說。因為,「漂泊本身就成了故鄉」。
楊煉總能找到當下可為的「事」:他創辦北京文藝網國際華文詩歌獎,舉行鹿特丹―北京網上同步詩歌節,介紹農民工詩歌,推動中英、中德詩人互譯,編輯出版大部頭英譯當代中文詩選《玉梯》等等。
他的名字「煉」也是他詩歌及工作方式的肖像。他不斷地煉字煉意,也不斷地探察自我內在的幽暗。「埋葬你心裡唯一的黑暗,唯一的謊言。」他在詩裡寫道。有一次在德國的朗誦詩歌會後,顧彬問楊煉,你的詩這麼黑暗,光在哪裡?「我的詩也許很黑暗,但我在寫,這就是光。」當時響起掌聲一片。「貫注在創作裡的能量,絕對是最高級、最明亮的,正是這種能量照亮了黑暗的現實。」時隔多年,楊煉闡釋道。
「我的寫作像考古。」楊煉說,他選擇的那些歷史材料,其實都是自己的內心場景,主題只有一句,就是「把手伸進土摸死亡」。因為,詩有一種深度,像深埋在地層裡的那種感覺。考古是為了能發現「深現實」的詩歌。他面對詩歌就像考古工作者面對考古發掘的現場一樣,「幾千年的大時間觀念,必須落實到一個小毛刷子一點一點刷掉灰塵的動作上」,「捋掉」不少雜質,讓以前隱藏或被遮蔽的詩意凸顯出來。
這些年,楊煉活躍在世界詩壇,從二○一二年獲得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V. S. Naipaul) 任評審團主席的義大利諾尼諾(Nonino)國際詩歌獎起,他這些年幾乎算是一個國際文學獎的得獎專業戶了。二○一八年,他獲得有「詩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匈牙利「雅努斯・潘諾尼烏斯國際詩歌大獎」,躋身於菲林蓋蒂(Lawrence Ferlinghetti)、阿多尼斯(Adonis)、博納富瓦(Yves Bonnefoy)和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等當代最重要的詩人之列,是獲獎的第一位中文詩人。
「楊煉的詩歌跨越了中國大陸、臺灣和海外空間,以及古代和當代中文詩歌的時間,彰顯出『天才與激情』貫穿了這些詩歌的『超越時間的生活』。」二○一八年九月十五日,楊煉在古城佩奇(Pecs)從身兼匈牙利總理首席文化顧問、評委會主席的蘇契・蓋佐(Szocs Géza)和匈牙利文化部長彼得・費凱迪(Peter Fekete)手中接受獎座和證書。
「今天的詩歌,是個體詩學的時代。深度,同時衡量著人與詩的個性。詩歌沉潛在海底,漆黑、冷靜地審視著風波險惡的世界。」楊煉在以〈一隻海蝴蝶〉為題的受獎演說中講道。
在布達佩斯的裴多菲文學博物館(Petőfi Irodalmi Múzeum),我和楊煉第一次見面,楊煉的夫人畫家友友就驚嘆:你太像年輕時的楊煉了。
伴著這種「相像」的緣分,在匈牙利期間,我記錄下與楊煉的「多瑙河十日談」。這是珍貴的友誼之旅。
從巴拉頓湖畔(Balatonfüred),到中世紀古城佩奇,再到布達佩斯,楊煉和友友手拉手並肩走著的背影,總是在我眼前。友友說,在世界漂泊,很多朋友忍受不了回國了。他們倆相濡以沫,是他們抵抗孤獨和長久堅持下來的好方法。我想她說的准沒錯。祝福他們倆人在一起的旅行,到處都是溫柔的「故鄉」。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楊煉從汕頭大學去義大利文化古城拉奎拉(L'Aquila)領取另一項國際詩歌獎。白雲機場廣州酒家為我們晚打烊了一個小時,我們補聊了最後一章,算是為這個稍稍漫長的文學訪談錄劃上句號。
目次
「馬背上的民族,眼睛永遠盯著更遠的一條地平線」――採訪緣起
二○一八年九月八日下午,匈牙利巴拉頓湖畔翻譯之家
吉祥戲院少東家之子。出生地:瑞士伯爾尼
瑞士的和平與暴烈
整理照相冊,母親去世
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兩次背叛
二姨
叔叔的荒誕遭遇
二○一八年九月十日,布達佩斯
蒙古人奶奶
日據時代的躲與遊
「玩」自己的事
貓狗年月
二○一八年九月十一日,布達佩斯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裡的初戀
黃土店村的「階級鬥爭」和插隊女孩
初戀的分手和第一次婚姻
《今天》的活動與擺脫跟蹤
第二次婚姻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布達佩斯
嚴文井,父輩歷史縮影
跟邵燕祥、謝冕等人的交往
北京的地下文學與黃皮書
藍總是更高的
向大海報了仇
在紐約,認識艾倫・金斯堡
在美國暫停了八個月
悉尼大學的一年
第一次回中國和再去美國
蘇珊・桑塔格
阿什伯利
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布達佩斯
阿多尼斯
高行健
解構鄉愁
鬼話與鬼府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布達佩斯
汪氏小苑和揚州菜
親舅姥爺史東山之死
舅姥爺徐遲之死
二○一八年九月十六日上午,布達佩斯
但丁式的煉獄旅行與〈諾日朗〉
尋找大地本源的生命力與《豔詩》
主動和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本地」
精神的深度、思想的深度
漢語音樂和音韻的自覺
莊子的傳統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白雲機場廣州酒家
談芒克
說顧城
我的寫作像考古
寫詩需要一張熟悉的桌子
卻顧所來徑
附一:楊煉的詩
母親的手跡
二姨的肖像
奶奶的船
京劇課
蝴蝶――柏林
一粒葵花籽的否定句――致艾未未
一九八九年(死者之年)
在特朗斯特羅默墓前
附二:楊煉創作年表及中外文作品出版目錄
附三:楊煉文學小傳及評論摘要
二○一八年九月八日下午,匈牙利巴拉頓湖畔翻譯之家
吉祥戲院少東家之子。出生地:瑞士伯爾尼
瑞士的和平與暴烈
整理照相冊,母親去世
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兩次背叛
二姨
叔叔的荒誕遭遇
二○一八年九月十日,布達佩斯
蒙古人奶奶
日據時代的躲與遊
「玩」自己的事
貓狗年月
二○一八年九月十一日,布達佩斯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裡的初戀
黃土店村的「階級鬥爭」和插隊女孩
初戀的分手和第一次婚姻
《今天》的活動與擺脫跟蹤
第二次婚姻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布達佩斯
嚴文井,父輩歷史縮影
跟邵燕祥、謝冕等人的交往
北京的地下文學與黃皮書
藍總是更高的
向大海報了仇
在紐約,認識艾倫・金斯堡
在美國暫停了八個月
悉尼大學的一年
第一次回中國和再去美國
蘇珊・桑塔格
阿什伯利
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布達佩斯
阿多尼斯
高行健
解構鄉愁
鬼話與鬼府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布達佩斯
汪氏小苑和揚州菜
親舅姥爺史東山之死
舅姥爺徐遲之死
二○一八年九月十六日上午,布達佩斯
但丁式的煉獄旅行與〈諾日朗〉
尋找大地本源的生命力與《豔詩》
主動和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本地」
精神的深度、思想的深度
漢語音樂和音韻的自覺
莊子的傳統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白雲機場廣州酒家
談芒克
說顧城
我的寫作像考古
寫詩需要一張熟悉的桌子
卻顧所來徑
附一:楊煉的詩
母親的手跡
二姨的肖像
奶奶的船
京劇課
蝴蝶――柏林
一粒葵花籽的否定句――致艾未未
一九八九年(死者之年)
在特朗斯特羅默墓前
附二:楊煉創作年表及中外文作品出版目錄
附三:楊煉文學小傳及評論摘要
書摘/試閱
〈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兩次背叛〉
朱又可:你見過你的祖父嗎?
楊煉:沒見過。但見過他一張照片,我忘了他是抱著我,還是抱著我姊,可能是我,因為那時我們剛從瑞士回來,他還沒去世,而我姊姊已經五六歲了。我那個很有錢的曾祖父去世得早,他應該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一點去世的。
朱又可:開吉祥戲院的是曾祖父?
楊煉:是的,不過這裡比較複雜,我親生血緣的祖父,其實是過繼給我曾祖父的,因為曾祖父沒有孩子。我親生血緣的祖父姓黃,家鄉離莫言的老家很近,在山東諸城,也是江青、康生的故鄉,跟高密緊挨著。
我的祖父家裡是農民,很窮,闖關東時,在東北認識了我的曾祖父。曾祖父很有錢,但沒人知道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他到死也沒說。這是個很神祕的事兒。有傳聞說他曾在慈禧太后女兒的大公主府裡工作,大公主府就是現在北京寬街的中醫醫院,他跟大公主府裡的什麼女人有染,有麻煩了,最後那個女的被幹掉,他逃到了東北。
朱又可:他是做生意的嗎?
楊煉:他回北京後做很大的生意,有綢緞莊、很多房產,還要開銀行,吉祥戲院只是他財產的一小塊。
朱又可:他原來是北京的。
楊煉:北京也不是他祖籍,他真正的祖籍是揚州。所以他有錢以後,家裡永遠只用揚州廚子。
我曾祖父從東北回來以後,買了吉祥戲院。不知是不是有什麼緣由,反正吉祥戲院的創始人,恰巧是大公主府裡的大總管。
朱又可:那就是太監。
楊煉:對,他為什麼非要買大公主府裡的人創出的產業呢?很耐人尋味啊。吉祥戲院之所以最有名,是因為滿清政府禁止在北京內城有娛樂,所有的妓院、戲園子等等,都在前門外。而內城是滿人居住,都是滿人的府邸等等,不准有娛樂場所。
可大公主府這總管的勢力非常大,他能直接在東華門外建一個戲園子,而且立住了,因此吉祥戲院的名聲極大,我的曾祖父就把它買下來。
後來,我祖父過繼給了他,他們一塊回了北京。他們只差十歲,名義上我祖父是過繼給他做兒子,但合同上(相當於協議)我祖父還繼續姓黃,老根就是山東諸城城關公社的黃家莊。那村子中央是黃家祖墳。家譜上第一個名字居然寫著,樸字庭堅,黃庭堅啊!只是不知道真假,因為經常有假托名人為祖先的。
他們的協議上要求,我父親這輩出生以後,要改姓曾祖父的劉姓,所以我爸爸剛出生的名字,叫劉熾昌。我曾祖父名叫劉燮之。
朱又可:為什麼你爸姓劉,你姓楊?
楊煉:我爸跟著我曾祖父姓劉。後來投奔共產黨,改名換姓。
朱又可:姓楊是後來才改的?
楊煉:對,他的姓改了好幾次,他先改了一個于,因為和女朋友一起投奔晉察冀解放區,他們說改姓要找一個筆畫最簡單的字,就是丁,但我爸女朋友說,我要這個字,我姓丁。我爸就再加了一橫,姓于,叫于山,真夠簡單的。
再後來很戲劇性,他女朋友被解放區一個領導看上了,那人和彭真時期的北京市副市長劉仁非常近。於是他們把我爸從晉察冀調去延安,我爸離開後,給這個女友寫了很多信,但她從來沒回信。過了大概半年多,一個組織上的人來找我爸說,你不要給丁文寫信了,她結婚了,這是你給她寫的信。原來我爸給她的信都被截了,因為沒有正常的郵政,只有走黨的系統。
我的一個朋友(加親戚)叫武歆,他寫了一部小說叫《延安愛情》,在中央電視臺做了電視劇連播,屬主旋律。那個小說就是用我爸這個故事梗概發展出來的。
朱又可:組織把你爸的信給截掉。
楊煉:當然小說改變了不少,但是男主人公有我老爸的影子,還比較清楚。我問老爸,你對《延安愛情》怎麼看?我爸回答說,延安哪有愛情?
朱又可:用權力把你支走,讓你們中斷聯繫。
楊煉:但我老爸始終說,他是一個命特好的人。說實話,他命確實好,第一個好,就是他從晉察冀到延安路上走了兩個月,正好跨過了延安整風。要是讓他遭遇上,肯定倒楣,這是第一次應驗。
朱又可:如果他不去延安,可能後來的遭遇會很糟糕。
楊煉:一個是整風也會到晉察冀,你不去它那兒,它會來找你,尤其是當你直接或者間接地得罪了領導,哪裡逃得掉?
所以,在我的自傳體散文中,有寫我老爸的兩章,其中一個核心的概念,是他的兩度背叛。我也親口跟老爸這麼說過。這兩度背叛,使他成了我的精神榜樣。《敘事詩》裡邊的〈故鄉哀歌〉,就是獻給我老爸的。
這第一度背叛,是背叛他原來的富有家庭。因為他有平等社會的真夢想。我跟西方人都說,你們那左派叫什麼左派,當時中國幾百萬的富家子弟,不光是仗義疏財,而且真正反戈一擊,要把自己的家庭和階級澈底毀滅,去建立夢想中的平等中國,那才叫理想主義。而現在的西方人年輕時玩浪漫、玩反叛,年紀大一點兒就回歸主流,該怎麼掙錢怎麼掙錢,這算什麼理想?
我對老爸說:第一,如果你年輕時沒理想,我不會那麼敬佩你;第二,如果你有了一大番經歷,還不能醒過味來,再次背叛自己虛幻的夢,我也不會敬佩你。很有不少愚蠢的馬列老太太之類人物啊,他們一生就是一個愚蠢的鬧劇。但我老爸思想非常清晰,看問題很透澈。
我那本書裡寫到,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爸之所以在這一生中犯的錯誤非常少,是因為他有美感!既重視人品美,更重視作品美。就像我說過,他高中最後一年把貝多芬第九交響樂聽了一百多遍,居然忘了還有上大學那一茬。他後來喜歡中國戲曲、古典詩歌、西洋音樂,甚至對西方現代文學如數家珍。他雖然不創作,但是欣賞品位極高,甚至包括古董。
有美感的人,跟著自己內心的感受走,這是唯一可以把握的方向。所以,和其他中國知識分子相比,我老爸最大的特點,就是他一點也不在乎流行的這理論那理論。跟著時髦理論走的,今天跟這股風,明天跟那股風,無數的人掉進了坑裡。但我老爸判斷事兒,不管是對生活,對人,還是對作品,只根據「美」的感受。美感作為潛在的指引羅盤,給了他判斷方向的直覺。和這個人接觸有美感、舒服,和那個人不對頭、醜陋,就足夠判斷一切了。這看起來比較老舊而傳統,可恰恰是這樣的價值觀,經過了無數驗證,最靠得住。
朱又可:那我覺得你父親了不起。
楊煉:我曾祖父本來對我父親寄予厚望,想讓他將來傳承整個家業,沒想到我爸是一個天生的理想主義者,痛恨做買賣,後來乾脆投奔了共產黨。到一九四九年我曾祖父去世前不久,他的家產值現大洋上百萬了,那時百萬現大洋是不得了的事。
我父親投奔共產黨有家庭背景的原因,據說我曾祖父盤剝下人很厲害,而且抽大煙,抽完大煙就發火。雖然當時我老爸是小孩,也被叫到床頭猛罵。我問他,您投奔共產黨是不是為這個而逆反?他說有這個成分。
我有幾首詩寫給我父親,其中那首〈信〉,還寫到了這個。
在我看來,我父親九十七年的人生經歷,是中國歷史上變幻最劇烈的一世紀。他出生於一九二二年,滿清已經結束。但在時間傳承上,從滿清到民國、到軍閥混戰、到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共產黨時期、文革,直至文革後的經濟開放。這將近一百年,中國歷史和文化堪稱風暴迭起。我常常把他想像成一條小船,再想像這條小船居然穿過了這個世紀的狂風暴雨,不僅沒翻,而且可以說基本保持了比較正確的人生航向,這太難得了。
要知道,在這一百年裡,中國人,尤其是年輕的中國人的追求理想、追求上進,不知意味著要犯多少可怕的錯誤,如果良心尚存,不知得留下多少悔恨,不管是你迫害別人,還是你被別人迫害。而我老爸居然在將近一百年的一生,幾乎沒留下過這種悔恨。如果今天追這個理論、明天跟那個風向,最後留下的全是悔恨。
==================
〈蒙古人奶奶〉
今天聊天開始時,說了一會閒話。
楊煉說:「我現在穿的這件T恤很獨特,是艾未未設計的。前面是他那張很有名的照片,模仿死在希臘海灘上的敘利亞難民小孩趴著,他把這照片轉換成很精采的畫,印在T恤上。後面是我給他寫的那首詩〈一粒葵花籽的否定句〉的最後一行:不讓這首詩沉淪為冷漠死寂的美。
今年五月分柏林國際詩歌節,我跟詩歌節組織者講(他們跟我比較熟),艾未未在柏林住了五年,可跟詩歌一絲關係都沒有,其實他的作品很有詩意,我們應該做個活動。就這樣一來二去,我們做了一個很成功的活動,在舞臺上朗誦、對話,還設計了這件T恤衫。對話後他在T恤前面簽名,我在後面簽,人們排大隊,現場很踴躍。」
朱又可:昨天講到了你父親,不是還有你姑姑嗎?
楊煉:我兩個姑姑都是學醫的,我大姑在天津一個醫院,原來國民黨時期的大學有女生家政系,畢業後專門當高級家庭主婦,同時也要懂醫務護理。她畢業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了。我大姑上大學就在天津,畢業後就留在天津,後來她和一個搞化工的專家結婚。本來他們在天津五大道有一整棟三層的洋樓,質量非常好,一九七六年地震紋絲不動。文革中其他的樓層都被人家占了(可能是工農兵),最後剩下最底下的那一層是他們的。我去住過那兒很多次,尤其我爸爸到天津以後,我每次去都會和大姑見個面。
我大姑九十歲多一點去世,也算長壽。她丈夫更晚一些。她丈夫是某個國民黨軍閥(忘了哪一個)天津警備區司令的兒子。他們家在天津過了很多年。
四姑是我爸最小的妹妹,也是學醫的,後來在北京傳染病醫院當主治大夫。她丈夫也是學醫的。我跟他們接觸不是特別多,但是因為他們一直住在我奶奶北京的房子裡,在王府井,跟吉祥戲院隔一條胡同。那所房子是曾祖父從清朝宮廷畫家溥雪齋手裡買來的,他是溥儀那一輩,當時相當有名。那房子是溥雪齋為自己設計的畫室,院子裡的太湖石都是從圓明園廢墟搬回來的,假山非常漂亮,周圍都是迴廊,房子裡的格柵是整塊金絲楠木雕的。
我有一首詩叫〈奶奶的船〉,詩裡滲透了好多奶奶那棟房子的感覺。我叔叔從鹽場回來以後,便和四姑一直住在這個房子裡。
我奶奶的命運卻很慘,文革中,她被當做地主婆,從那個漂亮豪華的大宅子關進一個沒有窗戶、冬天沒有火的小黑屋。我最後一次去看她,是在插隊之前,大概在一九七二、七三年左右,就是到那個小黑屋裡。當時沒什麼人敢去看她,都是一個一九四九年前的老傭人夜裡偷偷給她送飯。我奶奶是蒙古人,正宗蒙古血統,坐在又黑又冷,只能圍著被子的小屋裡,心境卻特別平和。我不記得她跟我說了什麼,但語調是北京老旗人那種特別有教養、有味道、很軟的京片子。我記得她被子上放了一張報紙,語調很平靜地說了一些事兒,好像和我爸有關,還問了我弟弟的情?。她糖尿病很嚴重,但是心態特別好,所以活了七十多歲。我父親說他自己是樂者壽,其實我父親受我奶奶的影響最深。
〈奶奶的船〉這首詩就寫了這樣一個經歷。奶奶家裡原來都是當官的,尤其奶奶的蒙古祖父,在清朝末年是個比較大的官,最早是京官,後來外放到貴州的畢節,那時叫貴西道,去當道臺。
說來我還真去過畢節,那是一九八六年,我在湖南、貴州跑了一大圈。在貴州,人們有句話叫:威納赫,Kei(去)不得。威寧、納西、赫章這三個地方,都窮得不得了,去不得。這三個地方都屬畢節地區,所以我奶奶恰恰去了一個去不得的地方。但有了這一層淵源,反而讓我對畢節一帶很有感覺。
我爸爸說,我奶奶始終記得在貴州把蛇叫「老蛇」,發音像「噻」,也許是「老色」(shai),因為毒蛇都是花花的。我奶奶記得小時候一次傭人抱她上樓,剛到樓上開門,一條大粗花蛇直衝出窗戶,她嚇得要命,也從此記住了「老蛇」這個詞。
一天,靈感來了,我想起奶奶三歲時,跟著她的祖父外放貴州當道臺,他們肯定是沿著大運河從北京坐船而下,路過揚州是肯定的,畢竟揚州自古繁華之地呀,再從揚州下長江、沅江,才能慢慢到貴州。所以,〈奶奶的船〉這首詩內含的時間是交錯的,既是過去,又是現在。雖然奶奶在船上時,只有三歲,但我想像,她那小小的子宮裡,已經帶著我父親、我自己、我所有的詩,包括她自己死在小黑屋裡的命運。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都在那船上。
我也記得去看我姑姑的經歷,就是在奶奶那個房子裡。當時文革剛開始(或者還沒開始),屋子裡的雕花格柵還在。我姑姑是文革中患癌症去世的,她的丈夫姓丘,上海人,是北京友誼醫院的主治大夫,可惜健身過頭了,跑樓梯太使勁,居然栽倒死在了樓梯上。
我跟他們的關係不太密切。父親從瑞士回來以後的一年多,在北京的單位還沒有確定下來,房子也沒有定,就先在我奶奶家王府井那裡住了一段。
我的《敘事詩》裡有一首詩,就叫〈王府井――頤和園〉,因為一年多後,我父親的單位確定了,是頤和園旁邊的西苑機關,於是就搬到那邊。我對北京最早的記憶,一是我奶奶家――王府井,另一個就是頤和園,我長大的地方。
朱又可:你有蒙古血統,對吧?
楊煉:我奶奶是純粹的蒙古人,所以我按理說是四分之一蒙古血統。我奶奶家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像他們那種蒙古人,可以叫淳樸,也可以叫不懂事兒。不懂事兒到什麼程度呢,我奶奶的祖父從貴西道,升官到貴州作臬臺,他還在山西當過官,有一筆不少的銀子,存在山西的票號,也就是錢莊裡。他最後一任官是奉天府尹,也就是瀋陽市長。奉天是清朝皇帝的龍脈,叫盛京,他等於是給皇上看祖墳的,當時那重要性還是蠻大的。
票號裡的銀子一直存在山西,後來票號經營不善要破產了,當時我奶奶的祖父已經回到北京。有一天半夜,我奶奶的父親,就是她祖父的兒子,一個大少爺,突然聽到有人砸門,開門一看是山西票號的,趕著兩輛馬車把銀子送回來,說我們票號要垮臺,把錢給您送來了。誰知這位大少爺一聽,回話說,我家哪有地方擱這麼多銀子?你給我拉回去。那人說不能拉回去啊,拉回去就沒了,票號要倒了。不行。大少爺說,我們家沒地兒擱,你給我拉走。生生讓把兩大車銀子給拉走了,當然也就沒影了。
要說這家山西票號真夠誠實的,不過這位大少爺更絕。他說沒地方擱,其實可能是懶,或誰知怎麼回事。
通過這個例子,就說明滿蒙貴族們,對現實多不懂、多不在乎,也許因為吃著皇糧、鐵桿莊稼,根本就沒想到有哪天要停。
總之,我奶奶生在這樣的人家,她是第一代可以和漢族通婚的滿蒙人。她和我爺爺結婚,實際上是我那個特有錢的曾祖父的主意,他打我奶奶家的錢的主意。據說我奶奶家敗落得很慘,我奶奶的父親最後淪落到給我曾祖父看門,所謂看門,其實就是在家裡養著他,他就在門房住著。可不是一個史湘雲那樣的闊親戚,是一個窮親戚,破落的舊貴族。
我奶奶和啟功是親戚。小時候家裡人帶我爸和我大姑去親戚家玩,滿蒙人喜歡攀輩分,他們讓我大姑們叫啟功表哥或堂哥,好像是平輩,或者差一輩,關係還挺近,但都是通過這個親戚那個親戚攀起來的。
朱又可:你見過你的祖父嗎?
楊煉:沒見過。但見過他一張照片,我忘了他是抱著我,還是抱著我姊,可能是我,因為那時我們剛從瑞士回來,他還沒去世,而我姊姊已經五六歲了。我那個很有錢的曾祖父去世得早,他應該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一點去世的。
朱又可:開吉祥戲院的是曾祖父?
楊煉:是的,不過這裡比較複雜,我親生血緣的祖父,其實是過繼給我曾祖父的,因為曾祖父沒有孩子。我親生血緣的祖父姓黃,家鄉離莫言的老家很近,在山東諸城,也是江青、康生的故鄉,跟高密緊挨著。
我的祖父家裡是農民,很窮,闖關東時,在東北認識了我的曾祖父。曾祖父很有錢,但沒人知道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他到死也沒說。這是個很神祕的事兒。有傳聞說他曾在慈禧太后女兒的大公主府裡工作,大公主府就是現在北京寬街的中醫醫院,他跟大公主府裡的什麼女人有染,有麻煩了,最後那個女的被幹掉,他逃到了東北。
朱又可:他是做生意的嗎?
楊煉:他回北京後做很大的生意,有綢緞莊、很多房產,還要開銀行,吉祥戲院只是他財產的一小塊。
朱又可:他原來是北京的。
楊煉:北京也不是他祖籍,他真正的祖籍是揚州。所以他有錢以後,家裡永遠只用揚州廚子。
我曾祖父從東北回來以後,買了吉祥戲院。不知是不是有什麼緣由,反正吉祥戲院的創始人,恰巧是大公主府裡的大總管。
朱又可:那就是太監。
楊煉:對,他為什麼非要買大公主府裡的人創出的產業呢?很耐人尋味啊。吉祥戲院之所以最有名,是因為滿清政府禁止在北京內城有娛樂,所有的妓院、戲園子等等,都在前門外。而內城是滿人居住,都是滿人的府邸等等,不准有娛樂場所。
可大公主府這總管的勢力非常大,他能直接在東華門外建一個戲園子,而且立住了,因此吉祥戲院的名聲極大,我的曾祖父就把它買下來。
後來,我祖父過繼給了他,他們一塊回了北京。他們只差十歲,名義上我祖父是過繼給他做兒子,但合同上(相當於協議)我祖父還繼續姓黃,老根就是山東諸城城關公社的黃家莊。那村子中央是黃家祖墳。家譜上第一個名字居然寫著,樸字庭堅,黃庭堅啊!只是不知道真假,因為經常有假托名人為祖先的。
他們的協議上要求,我父親這輩出生以後,要改姓曾祖父的劉姓,所以我爸爸剛出生的名字,叫劉熾昌。我曾祖父名叫劉燮之。
朱又可:為什麼你爸姓劉,你姓楊?
楊煉:我爸跟著我曾祖父姓劉。後來投奔共產黨,改名換姓。
朱又可:姓楊是後來才改的?
楊煉:對,他的姓改了好幾次,他先改了一個于,因為和女朋友一起投奔晉察冀解放區,他們說改姓要找一個筆畫最簡單的字,就是丁,但我爸女朋友說,我要這個字,我姓丁。我爸就再加了一橫,姓于,叫于山,真夠簡單的。
再後來很戲劇性,他女朋友被解放區一個領導看上了,那人和彭真時期的北京市副市長劉仁非常近。於是他們把我爸從晉察冀調去延安,我爸離開後,給這個女友寫了很多信,但她從來沒回信。過了大概半年多,一個組織上的人來找我爸說,你不要給丁文寫信了,她結婚了,這是你給她寫的信。原來我爸給她的信都被截了,因為沒有正常的郵政,只有走黨的系統。
我的一個朋友(加親戚)叫武歆,他寫了一部小說叫《延安愛情》,在中央電視臺做了電視劇連播,屬主旋律。那個小說就是用我爸這個故事梗概發展出來的。
朱又可:組織把你爸的信給截掉。
楊煉:當然小說改變了不少,但是男主人公有我老爸的影子,還比較清楚。我問老爸,你對《延安愛情》怎麼看?我爸回答說,延安哪有愛情?
朱又可:用權力把你支走,讓你們中斷聯繫。
楊煉:但我老爸始終說,他是一個命特好的人。說實話,他命確實好,第一個好,就是他從晉察冀到延安路上走了兩個月,正好跨過了延安整風。要是讓他遭遇上,肯定倒楣,這是第一次應驗。
朱又可:如果他不去延安,可能後來的遭遇會很糟糕。
楊煉:一個是整風也會到晉察冀,你不去它那兒,它會來找你,尤其是當你直接或者間接地得罪了領導,哪裡逃得掉?
所以,在我的自傳體散文中,有寫我老爸的兩章,其中一個核心的概念,是他的兩度背叛。我也親口跟老爸這麼說過。這兩度背叛,使他成了我的精神榜樣。《敘事詩》裡邊的〈故鄉哀歌〉,就是獻給我老爸的。
這第一度背叛,是背叛他原來的富有家庭。因為他有平等社會的真夢想。我跟西方人都說,你們那左派叫什麼左派,當時中國幾百萬的富家子弟,不光是仗義疏財,而且真正反戈一擊,要把自己的家庭和階級澈底毀滅,去建立夢想中的平等中國,那才叫理想主義。而現在的西方人年輕時玩浪漫、玩反叛,年紀大一點兒就回歸主流,該怎麼掙錢怎麼掙錢,這算什麼理想?
我對老爸說:第一,如果你年輕時沒理想,我不會那麼敬佩你;第二,如果你有了一大番經歷,還不能醒過味來,再次背叛自己虛幻的夢,我也不會敬佩你。很有不少愚蠢的馬列老太太之類人物啊,他們一生就是一個愚蠢的鬧劇。但我老爸思想非常清晰,看問題很透澈。
我那本書裡寫到,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爸之所以在這一生中犯的錯誤非常少,是因為他有美感!既重視人品美,更重視作品美。就像我說過,他高中最後一年把貝多芬第九交響樂聽了一百多遍,居然忘了還有上大學那一茬。他後來喜歡中國戲曲、古典詩歌、西洋音樂,甚至對西方現代文學如數家珍。他雖然不創作,但是欣賞品位極高,甚至包括古董。
有美感的人,跟著自己內心的感受走,這是唯一可以把握的方向。所以,和其他中國知識分子相比,我老爸最大的特點,就是他一點也不在乎流行的這理論那理論。跟著時髦理論走的,今天跟這股風,明天跟那股風,無數的人掉進了坑裡。但我老爸判斷事兒,不管是對生活,對人,還是對作品,只根據「美」的感受。美感作為潛在的指引羅盤,給了他判斷方向的直覺。和這個人接觸有美感、舒服,和那個人不對頭、醜陋,就足夠判斷一切了。這看起來比較老舊而傳統,可恰恰是這樣的價值觀,經過了無數驗證,最靠得住。
朱又可:那我覺得你父親了不起。
楊煉:我曾祖父本來對我父親寄予厚望,想讓他將來傳承整個家業,沒想到我爸是一個天生的理想主義者,痛恨做買賣,後來乾脆投奔了共產黨。到一九四九年我曾祖父去世前不久,他的家產值現大洋上百萬了,那時百萬現大洋是不得了的事。
我父親投奔共產黨有家庭背景的原因,據說我曾祖父盤剝下人很厲害,而且抽大煙,抽完大煙就發火。雖然當時我老爸是小孩,也被叫到床頭猛罵。我問他,您投奔共產黨是不是為這個而逆反?他說有這個成分。
我有幾首詩寫給我父親,其中那首〈信〉,還寫到了這個。
在我看來,我父親九十七年的人生經歷,是中國歷史上變幻最劇烈的一世紀。他出生於一九二二年,滿清已經結束。但在時間傳承上,從滿清到民國、到軍閥混戰、到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共產黨時期、文革,直至文革後的經濟開放。這將近一百年,中國歷史和文化堪稱風暴迭起。我常常把他想像成一條小船,再想像這條小船居然穿過了這個世紀的狂風暴雨,不僅沒翻,而且可以說基本保持了比較正確的人生航向,這太難得了。
要知道,在這一百年裡,中國人,尤其是年輕的中國人的追求理想、追求上進,不知意味著要犯多少可怕的錯誤,如果良心尚存,不知得留下多少悔恨,不管是你迫害別人,還是你被別人迫害。而我老爸居然在將近一百年的一生,幾乎沒留下過這種悔恨。如果今天追這個理論、明天跟那個風向,最後留下的全是悔恨。
==================
〈蒙古人奶奶〉
今天聊天開始時,說了一會閒話。
楊煉說:「我現在穿的這件T恤很獨特,是艾未未設計的。前面是他那張很有名的照片,模仿死在希臘海灘上的敘利亞難民小孩趴著,他把這照片轉換成很精采的畫,印在T恤上。後面是我給他寫的那首詩〈一粒葵花籽的否定句〉的最後一行:不讓這首詩沉淪為冷漠死寂的美。
今年五月分柏林國際詩歌節,我跟詩歌節組織者講(他們跟我比較熟),艾未未在柏林住了五年,可跟詩歌一絲關係都沒有,其實他的作品很有詩意,我們應該做個活動。就這樣一來二去,我們做了一個很成功的活動,在舞臺上朗誦、對話,還設計了這件T恤衫。對話後他在T恤前面簽名,我在後面簽,人們排大隊,現場很踴躍。」
朱又可:昨天講到了你父親,不是還有你姑姑嗎?
楊煉:我兩個姑姑都是學醫的,我大姑在天津一個醫院,原來國民黨時期的大學有女生家政系,畢業後專門當高級家庭主婦,同時也要懂醫務護理。她畢業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了。我大姑上大學就在天津,畢業後就留在天津,後來她和一個搞化工的專家結婚。本來他們在天津五大道有一整棟三層的洋樓,質量非常好,一九七六年地震紋絲不動。文革中其他的樓層都被人家占了(可能是工農兵),最後剩下最底下的那一層是他們的。我去住過那兒很多次,尤其我爸爸到天津以後,我每次去都會和大姑見個面。
我大姑九十歲多一點去世,也算長壽。她丈夫更晚一些。她丈夫是某個國民黨軍閥(忘了哪一個)天津警備區司令的兒子。他們家在天津過了很多年。
四姑是我爸最小的妹妹,也是學醫的,後來在北京傳染病醫院當主治大夫。她丈夫也是學醫的。我跟他們接觸不是特別多,但是因為他們一直住在我奶奶北京的房子裡,在王府井,跟吉祥戲院隔一條胡同。那所房子是曾祖父從清朝宮廷畫家溥雪齋手裡買來的,他是溥儀那一輩,當時相當有名。那房子是溥雪齋為自己設計的畫室,院子裡的太湖石都是從圓明園廢墟搬回來的,假山非常漂亮,周圍都是迴廊,房子裡的格柵是整塊金絲楠木雕的。
我有一首詩叫〈奶奶的船〉,詩裡滲透了好多奶奶那棟房子的感覺。我叔叔從鹽場回來以後,便和四姑一直住在這個房子裡。
我奶奶的命運卻很慘,文革中,她被當做地主婆,從那個漂亮豪華的大宅子關進一個沒有窗戶、冬天沒有火的小黑屋。我最後一次去看她,是在插隊之前,大概在一九七二、七三年左右,就是到那個小黑屋裡。當時沒什麼人敢去看她,都是一個一九四九年前的老傭人夜裡偷偷給她送飯。我奶奶是蒙古人,正宗蒙古血統,坐在又黑又冷,只能圍著被子的小屋裡,心境卻特別平和。我不記得她跟我說了什麼,但語調是北京老旗人那種特別有教養、有味道、很軟的京片子。我記得她被子上放了一張報紙,語調很平靜地說了一些事兒,好像和我爸有關,還問了我弟弟的情?。她糖尿病很嚴重,但是心態特別好,所以活了七十多歲。我父親說他自己是樂者壽,其實我父親受我奶奶的影響最深。
〈奶奶的船〉這首詩就寫了這樣一個經歷。奶奶家裡原來都是當官的,尤其奶奶的蒙古祖父,在清朝末年是個比較大的官,最早是京官,後來外放到貴州的畢節,那時叫貴西道,去當道臺。
說來我還真去過畢節,那是一九八六年,我在湖南、貴州跑了一大圈。在貴州,人們有句話叫:威納赫,Kei(去)不得。威寧、納西、赫章這三個地方,都窮得不得了,去不得。這三個地方都屬畢節地區,所以我奶奶恰恰去了一個去不得的地方。但有了這一層淵源,反而讓我對畢節一帶很有感覺。
我爸爸說,我奶奶始終記得在貴州把蛇叫「老蛇」,發音像「噻」,也許是「老色」(shai),因為毒蛇都是花花的。我奶奶記得小時候一次傭人抱她上樓,剛到樓上開門,一條大粗花蛇直衝出窗戶,她嚇得要命,也從此記住了「老蛇」這個詞。
一天,靈感來了,我想起奶奶三歲時,跟著她的祖父外放貴州當道臺,他們肯定是沿著大運河從北京坐船而下,路過揚州是肯定的,畢竟揚州自古繁華之地呀,再從揚州下長江、沅江,才能慢慢到貴州。所以,〈奶奶的船〉這首詩內含的時間是交錯的,既是過去,又是現在。雖然奶奶在船上時,只有三歲,但我想像,她那小小的子宮裡,已經帶著我父親、我自己、我所有的詩,包括她自己死在小黑屋裡的命運。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都在那船上。
我也記得去看我姑姑的經歷,就是在奶奶那個房子裡。當時文革剛開始(或者還沒開始),屋子裡的雕花格柵還在。我姑姑是文革中患癌症去世的,她的丈夫姓丘,上海人,是北京友誼醫院的主治大夫,可惜健身過頭了,跑樓梯太使勁,居然栽倒死在了樓梯上。
我跟他們的關係不太密切。父親從瑞士回來以後的一年多,在北京的單位還沒有確定下來,房子也沒有定,就先在我奶奶家王府井那裡住了一段。
我的《敘事詩》裡有一首詩,就叫〈王府井――頤和園〉,因為一年多後,我父親的單位確定了,是頤和園旁邊的西苑機關,於是就搬到那邊。我對北京最早的記憶,一是我奶奶家――王府井,另一個就是頤和園,我長大的地方。
朱又可:你有蒙古血統,對吧?
楊煉:我奶奶是純粹的蒙古人,所以我按理說是四分之一蒙古血統。我奶奶家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像他們那種蒙古人,可以叫淳樸,也可以叫不懂事兒。不懂事兒到什麼程度呢,我奶奶的祖父從貴西道,升官到貴州作臬臺,他還在山西當過官,有一筆不少的銀子,存在山西的票號,也就是錢莊裡。他最後一任官是奉天府尹,也就是瀋陽市長。奉天是清朝皇帝的龍脈,叫盛京,他等於是給皇上看祖墳的,當時那重要性還是蠻大的。
票號裡的銀子一直存在山西,後來票號經營不善要破產了,當時我奶奶的祖父已經回到北京。有一天半夜,我奶奶的父親,就是她祖父的兒子,一個大少爺,突然聽到有人砸門,開門一看是山西票號的,趕著兩輛馬車把銀子送回來,說我們票號要垮臺,把錢給您送來了。誰知這位大少爺一聽,回話說,我家哪有地方擱這麼多銀子?你給我拉回去。那人說不能拉回去啊,拉回去就沒了,票號要倒了。不行。大少爺說,我們家沒地兒擱,你給我拉走。生生讓把兩大車銀子給拉走了,當然也就沒影了。
要說這家山西票號真夠誠實的,不過這位大少爺更絕。他說沒地方擱,其實可能是懶,或誰知怎麼回事。
通過這個例子,就說明滿蒙貴族們,對現實多不懂、多不在乎,也許因為吃著皇糧、鐵桿莊稼,根本就沒想到有哪天要停。
總之,我奶奶生在這樣的人家,她是第一代可以和漢族通婚的滿蒙人。她和我爺爺結婚,實際上是我那個特有錢的曾祖父的主意,他打我奶奶家的錢的主意。據說我奶奶家敗落得很慘,我奶奶的父親最後淪落到給我曾祖父看門,所謂看門,其實就是在家裡養著他,他就在門房住著。可不是一個史湘雲那樣的闊親戚,是一個窮親戚,破落的舊貴族。
我奶奶和啟功是親戚。小時候家裡人帶我爸和我大姑去親戚家玩,滿蒙人喜歡攀輩分,他們讓我大姑們叫啟功表哥或堂哥,好像是平輩,或者差一輩,關係還挺近,但都是通過這個親戚那個親戚攀起來的。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