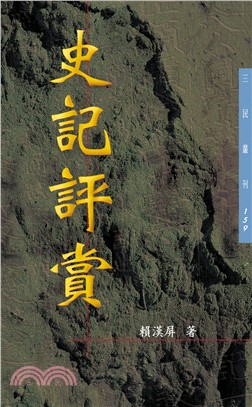相信每個東亞世界的男孩子心中,都存在著屬於自己的《三國演義》。你挺你的曹操挾天子令諸侯,我推我的劉備存仁義復漢室,他撐他的孫權納賢才據江東。不用去理會史實如何,各有各的想像,各有各的精彩。著作等身、獲獎無數的張啟疆老師,此次要將他心中的三國具現化為一部《新新三國演義》,怎能不叫人翹首企足、望眼欲穿呢?──普通人(《非普通三國》作者)
三國故事值得一讀再讀,讀正史,讀小說,讀各路翻譯、改寫、漫畫、電玩……人人心中都有一個「三國」夢。那是一個英雄狂飆,智慧、勇敢、仁愛、野心交會激盪的年代。小說家張啟疆以精鍊的文筆重繹了《三國演義》的故事,以更豐富的細節、對白(甚至人物內心的O.S.!)重現場景,文字鏗鏘,節奏明快,把我們帶回到那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宇文正(作家、聯副主編)
〈歷史,悲劇的晚點名〉 南 山
改寫的異趣
改寫,是一種藝術?還是異趣?
如何改?塗改?修改?篡改?
怎麼寫?敷寫?擴寫?重新寫?
筆者曾言:「改寫,是一項藝術,也是異數:不論你是快手、慢手、代工高手、紅油抄手或無所不能的寫手,切記:你的生花妙筆,是在雜花生樹的森林裡,栽育奇葩……文字、腔調、形式、結構都得翻新,同時要保住原著的精神與精髓。創意、『古意』並存,讓讀者在老戲碼裡看到新戲法,有所本,卻也無所泊靠……創作之妙,就在虛實交錯,相映成趣。」(〈天命所歸的悲情傳奇〉,收進新新古典《水滸傳》,二○一九年,臺北,三民)
什麼「趣」?別出心裁的妙趣。教人覷目以望的大異其趣。
或者說,類似新瓶舊酒、老屋拉皮的奇趣:對人物的詮釋、戰爭的描寫、歷史的觀照、情節的推演,以及,那個不容更動、「天下一統」的結局,自出機杼,成一家之言。
又或者,大處放眼,小處著手:「虛實交錯」的亮點在於,更動不影響大局的細節,來增添精彩度,一種無關緊要的驚天地、泣鬼神。
以《新新三國演義》為例,孔明可以「借東風」,但不能擅改赤壁之戰的結果,也不能在華容道偷偷「做掉」曹操;諸葛使出「空城計」,司馬懿明知有詐,內心不服,但為了尊重原著,也只好退兵。
貴為中國第一部長篇歷史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是根據正史《三國志》改編而來,羅貫中會乖乖「忠於史實」?清朝史學家章學誠說:「唯《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之惑亂。」
是「惑亂」?還是目眩神迷,擊節讚賞?因人而異,難有定論。若要細究《三國演義》的成色,除歷史事實外,不乏茶坊酒肆之言、巷議街談。要知道,《三國演義》成書之前,三國的故事早已在民間便廣為流傳。加油添醋有之,怪力亂神不少;將英雄將相神化的篇幅,更是不虞匱乏。
迥異於原著的開場
張啟疆的三國故事,會乖乖「忠於原著」《三國演義》?
細節不論,光是開場,這部《新新三國演義》就展現出嶄新的面貌:層層加框的文學設計,一種後現代技巧。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是讀者耳熟能詳的故事線頭;「滾滾長江東逝水」,更為世人朗朗上口,傳誦不絕。到了張啟疆筆下,顯然,這位受到現代主義薰陶的小說家對「順時敘事」的興致不高,改採「讓故事說故事」的加框手法:兩名「世外高人」(年輕書生、青衣文士)談論二位當世梟雄(曹操、劉備),談論天下英雄。
談論是「框」,談論裡有談論,故事中說故事,是謂「加框」。
或者該說,這部小說有兩個開場:「問津之一」的江邊對話,是第一開場,一番「指點迷津」、「是英雄自能識英雄」後,筆鋒一轉,帶入第二開場:正文第一章「敢問天下英雄」,也就是曹操、劉備在丞相府的「煮酒論英雄」。
乍看之下,後者是前者的曲中論,前者為後者的開場白?二位世外高人談古論今,品評人物?其實不然!讀到上部問津之八,赫然發現,外框亦為內裡,二位高人絕非置身「世外」,而是三國故事裡的關鍵角色。
細究小說時空,第一開場(江邊對話)的場景,如夢似幻,恍若夢境:
霧濛濛的江面,像是罩上厚厚一層白灰色氣牆,囚禁災澇,護衛水鄉。
神來一筆,天庭潑墨。風、雲、山、水,在一種蒸騰的快意、蛻形的丕變中,漸次消融,渾然一體。幾隻草寫天書的飛鳥,時而盤旋,忽而俯衝,點指江面,激起水花或輕漣。
(《新新三國演義‧問津之一》)
實際上,斯情斯景並非向壁虛構,而是真人實事,預埋伏筆。卷頭詞「滾滾長江東逝水」,也就從「旁注」的角色,轉進內文,成為小說實景:象徵「挾泥沙,混清濁,泯恩仇,孕魚龍」的空間設計。
時間呢?(為了避免破哏,筆者不便道破年輕書生、青衣文士的身分。)大約推估,是在「官渡之役」後,「赤壁之戰」前。換算成小說時空,第一開場的時間點,是在《新新三國演義》上部的五分之四處。
至於第二開場(煮酒論英雄)的時間切點,相當明確:西元一九九年(建安四年),約莫是百年三國史 的五分之一處。那時,黃巾賊已滅,關雲長「溫酒斬華雄」的事蹟,傳遍天下;虎牢關「三英戰呂布」的強檔,轟動上演。呂奉先乘夜襲徐郡、孫伯符大戰嚴白虎……等經典戰役,接踵而來。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局勢已經成形。八路諸侯會聚,對付兵強馬壯的袁紹。
連番好戲,就此錯過?不!滅黃巾、殺呂布、討袁紹等「前文」,在馬不停蹄的劇情行進中,交錯運用倒敘、插敘,鑲嵌圓補,前呼後應,不讓讀者錯失任何一場精彩戰役。
關鍵時刻
讀者或許要問,為什麼不話說從頭,娓娓道來,而要挑選「五分之一處」的黃道吉日?作者在玩什麼?
很簡單!孕育對決之前的對抗,對抗之前的對立,對立之前很不對盤的對弈—以江山為棋局,處處機鋒的對話來呈現。
作者張啟疆曾在自序〈老,誤讀三國〉中提及:「有人說,整個三國時代,前半段,是曹操和劉備的主場(劉備專借別人的場子,而且不還);後半齣,是諸葛亮、司馬懿的各擅勝場。」
那位「有人」,應該不是友人,是作者自己。
顯然,張啟疆認為,曹、劉之間的戰爭,早在「煮酒論英雄」那一夜,就點燃了熊熊燹火。
不然,雨停後,怎會有「兩名大漢(關羽和張飛)手提寶劍,從(丞相府)大門衝至後院,直抵亭前」—幹嘛?擔心大哥為曹賊所害,拚死來救。
附帶一提,「火攻」是中國古代戰爭的致命武器;火的意象,更是貫穿曹、劉二大梟皇運勢的徵兆。
兩人的初遇,是在討伐黃巾賊,「火焰張天,草木皆焚,旗倒營摧,哀鴻遍野」的場合:
一名細眼長髯、面白如霜的書生武將……騎著匹黑色寶馬—大宛良駒「絕影」,左眄右睞,雄霸之態,睥睨之姿,教人望而生畏。
那人的眼角餘光,從頭到腳,將劉備狠狠打量了一番,嘴角輕揚,似笑非似,隨即策馬轉身,揚長而去。
(《新新三國演義‧敢問天下英雄》)
此人是誰?教劉備心頭一緊,看倌眼睛一亮,不是白面曹操,還會是誰?
這一會,對劉備的意義是什麼?張啟疆來了一段快板:「是發現獵物的鷹眼、尋找同類的鯨唱,是煮酒論英雄的預約,是鏖戰三分國的請帖;是死敵的會前會、示現的王見王,是飛越九重顧盼自雄之際,赫見峰巒迭起、天外有天。」
還有片刻心理戲:「劉備乍見一片火海時,腦中閃過四個字:火光之災。」
這災劫,天機圖讖般的野火象徵,應驗在曹操的赤壁大敗,劉備伐吳時險些死於火燒連營……
總之,那一夜,是決定後來數十年天下大勢的「關鍵時刻」,劉備與曹操糾纏一生的「初夜」。
神話助威
如此重大的日子,難道不該「驚天地、泣鬼神」?
原著用「陰雲漠漠,驟雨將至」、「雷聲大作」,營造聲光效果。
張啟疆怎麼表現?
電光一閃,雷霆乍現,燦如白晝一瞬,又似燭龍睜眼,帶給人間詭魅的光明。
幽暗夜空狂風起,陰霾湧,暴雨將至。
一場及時雨,能澆熄神洲大陸的遍地烽火?
(《新新三國演義‧敢問天下英雄》)
堪稱金光重炮雷電交加升級版。
不只如此,為彰顯兩人的帝王命格,還請來神話助威:
龍,蟒身、蜥腿、鷹爪、蛇尾、鹿角、魚鱗、口角有鬚、額下有珠。自古以來,一直是天子圖騰、皇權象徵。傳說大禹治水,得龍之助;漢武防火,而將蚩尾置頂。有鱗者稱蛟龍,有翼者為應龍,有角者名虯龍,無角者號螭龍。能隱能顯,有真有假;春時登天,秋後潛淵。又能興雲致雨、掀波作浪……哼!總之,你曹阿瞞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假貨,我劉玄德才是「匡復漢室」的真龍。
(《新新三國演義‧敢問天下英雄》)
再加上差點嚇死劉備的那句「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像不像犯罪驚悚懸疑劇的片頭?
不過,劉備也不是被嚇大的—雖然他這一生,備受驚嚇。
之後—或者該說「之前」,張啟疆先回頭交代「桃園三結義」以來,宦官亂政、董卓專權……種種,再接回離開曹營、四處流亡、大戰赤壁、占奪荊州、稱帝川蜀……「三國鼎立」的態勢,於焉成形。
時間結構
不論怎麼岔繞、轉接,《新新三國演義》的小說舞台,上九下九共計十八章,約可粗分為四種時間:
一、群雄並起。
二、三國鼎立。
三、懿、亮之爭。
四、垃圾時間—諸葛亮、司馬懿死後到天下一統的混亂時期。
大陸版《三國》電視劇,結束在司馬懿病逝,之後的漫長數十載,一語帶過。
這部《新新三國演義》,則將「後諸葛時代」(長達四十六年)壓縮在下冊最後一章的下半段。
顯然,在史家、識者眼中,「三國」這齣豪華夜宴,在諸葛亮、司馬懿之後,只剩下比「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楊修語)更乏善可陳的殘羹剩飯。
甚至,站在「蜀漢」的敘事觀點(也可稱作「亮」點),將三國歷史濃縮為精華版,時間和空間都將縮限:時間短少了三分之二,從西元二○七年到西元二三四年,從三顧茅廬到諸葛禳星;空間呢?出臥龍崗,奪新野、戰赤壁、借荊州,進入川蜀,五月渡瀘,六出岐山,最後在五丈原劃下句點。
這是一齣局部時空秀,在儒家觀點的指揮棒下,拍成「限制級」的歷史劇,偏處一隅小王朝復國不成的故事。
超敘事觀點
但「王業偏安」是事實,以卵擊石是現實;北伐中原,是亂世忠臣實現不了的伏櫪美夢。張啟疆似乎意識到這種弔詭,而在下冊採用「超敘事觀點」:層層疊疊的「敘事」者(說書人、讀者、論者,也可以是天地萬物、日月星辰),在「茫茫大氣、濛濛江面、滔滔流水」的幻虛空間(向壁),彼此對話,交相詰問,化為「愕鳴驚叫的兩岸猿聲」。
誰在問?誰來答?
正確說,張啟疆設計了兩名幻影人物、針鋒相對的兩種聲音:吟誦聲和冷笑聲,擺盪六合,穿梭古今。
例如:
「你以為,孔明搞了一座七星壇,挑了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赤足散髮,裝模作樣……是要幹嘛?借東風?」
「難道不是?」冷笑聲故意問。
「不!時辰已至,他得仰聞天聽,夜觀乾象,恭領老天爺的諭旨:那曹賊固然可惡,但命不該絕,你得放他一馬。如果你是孔明,會怎麼做?」
(《新新三國演義‧向壁之一》)
這一段,是在旁敲「華容道捉放曹」的雙重設計,側擊天意、人事必須妥協的無奈心理。
又如,探討「直取荊、益」的得失:「得的是飛龍在天,失的是鳳落九泉。」
前者點出劉備「搶到開基立業之地」,但「蜀道通時只有(臥)龍」;後者是指龐統殞落。
「一在天上,一在地下;天地失衡,龍鳳不全,也就注定日後蜀漢的格局:難竟全功。」
那冷笑聲,一逕語不驚人死不休:「至少,在劉備率七十萬大軍東征時,有一位深諳兵法的軍師在旁,或者說,在『龐』,就不會犯下『火燒連營』的錯誤了。」
(《新新三國演義‧向壁之二》)
融入‧淡出
下冊的「向壁」,一如上冊的「問津」,具備旁敘功能的加框角色。同樣是「設計對白」,不同的是,「問津」融入情節,成為內文一部分;「向壁」卻是層層淡出,竟似退離歷史的現場。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怎麼?連杜工部的詩都拿出來搬弄?咱們身處三國時空,閣下卻用上後代詩人的觀點,想要一解『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哀痛?」
(《新新三國演義‧向壁之九》)
貌似殊途,實則同歸;作者試圖拉高層級,擴張故事的版圖。
「先生以為自己是在三國?盛唐?還是那不知伊於胡底的『後代』?」
「我以為,那滾滾長江東逝水的浪聲,依舊在為咱們的古今笑談協奏呢!」
(《新新三國演義‧向壁之九》)
兩名「時空旅人」究竟是誰?
是「蜀中多俊傑」的張溫,對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的秦宓?
是「兩朝老臣」—兩個朝代的孤臣,分據大河兩岸,傾訴「無力可回天」的萬古哀愁?
是擬人化的折戟和銷鐵,某場戰役血流漂櫓的響動?
是子虛公和烏有侯?文人筆下縱論古今的虛構角色?
是現實仇敵兼歷史朋友?被嚇壞的活司馬,夢見死諸葛?或者,臥龍崗的「大夢誰先覺」,年輕版孔明夢見自己和司馬的倥傯一生?
連(理應作古的)年輕書生、青衣文士都「復出」江湖,繼續鬥嘴。只是,前者揮扇晃腦,但見扇羽脫落,「轉瞬間變成白髮老者」;後者身半斜,背微駝,雙手交叉於後,化為「一尊斑駁石像」。
也許是「名落孫山的窮書生、投閒置散的白頭秀才,胸懷大志,抑鬱一生,一夜驚夢,以為自己可以穿時越空,更改歷史」。
也許,張啟疆欲言又止的是:你是歷史故事的撰寫者,我是掩卷嘆息的讀者。
顯然,「向壁」是「問津」的「更上一層樓」,再加多重框,框中有框,交錯疊現,擴映萬千,形成耐人尋味的「多層膜」敘事。
想像一種畫面:古往今來,成千上萬名讀者(包括史家、論者),人手一本書,聚精三國史,會神劉、關、張;時而撫案,時而掩卷,不免為世道掉淚,經常替古人擔憂……終究,殘局棄子,同聲一嘆。
如果時空可以輻湊、岔散、拼貼與重組,將諸時異空揉交在一點,便是不同時代各地讀者的「聲聚」:那一嘆,驚天巨響,勝過神龍現蹤的雷霆,是所有閱讀靈魂的觀點交混、眾聲喧嘩。
「生聚」可以得到「教訓」,靈魂、意念的交會,能譜出新曲?影響什麼?帶給世人何種殷鑑?
超越的視野
筆者以為,這位作者(同聲中的一嘆)不只是撫今追昔,還想延伸眼界,營造跨越時間,混同古今,不必為誰「掉淚」、「擔憂」的超越視野。
前述「古今笑談」、「三國?盛唐?還是那不知伊於胡底的『後代』?」即是打破歷史界線的「超越」筆法。
值得探究的是,什麼樣的視野?
曹操撚鬚輕笑,笑得雨過天青—喔不!應該說,天際的暴亂消逝無蹤,斜月破出雲層,睜一隻戲迷的眼,俯瞰人間幻劇。
(《新新三國演義‧敢問天下英雄》)
這是天上諸神的視角。
誰亡誰?誰併誰?誰歸降誰?誰殺錯誰?一代奸雄如果眼界夠遠,想像夠瘋,何妨穿越遠古之前的洪荒—那是何時?盤古開天後,火神降臨前,拜訪那橫行了千萬年,地面、水裡、空中的超級霸王:恐龍。
(《新新三國演義‧敢問天下英雄》)
有請「恐龍」嘲弄「真龍」(古中國的皇權象徵)的觀點。
顯然,作者的史觀,是隔岸觀火(遠距觀照得失功過、權力更迭),近處看花(戰爭、人性、謀略的細節敷寫),極盡栩栩如生,不想入戲太深;譏諷俯拾皆是,針砭處處可見。例如:
有情而生、為義而聚、任性而亡的悲劇三部曲。
這三人(指劉、關、張),是神的腦、心、左右手,遺落在皇權式微、神恩散軼、百姓流離的亂世,經年沉潛,各自修磨,彼此尋覓……一旦合體,天雷接通地火,風雲攪動潮浪;萬丈毫光耀暗室,一線生機救末年。是的,兵馬倥傯的東漢末年,一尊赫赫神將、無敵戰龍,殺進百孔千瘡的神州,掀開萬年曆上最沉重的板塊、最血腥的史頁。
(《新新三國演義‧敢問天下英雄》)
「任性而亡」是指:關羽因「驕矜自大,目中無人」,敗走麥城。賠了性命不說,又斷送「匡復漢室」的絕佳據點:荊州。
「『虎女焉能嫁犬子?』是滿盤皆輸的錯誤的第一步,不但阻斷孫、劉聯手,共討曹操;還招來魏、吳合謀,夾攻荊州。從一舉二得變成兩面作戰,是智也?不智也?或者,失智也?」
「也許,他打從心裡……」吟誦聲欲言又止。
「瞧不起孫權?哈!」冷笑聲變成哈哈大笑,「他若是不急著羞辱孫權,捎封信,去問問劉備和孔明的意見,我是說,就算是拒絕,也得想個漂亮說詞,局勢的發展,也許就不一樣了。」
(《新新三國演義‧向壁之五》)
災難還沒結束呢!比關羽更任性的大哥、三弟,只思報復,罔顧大局,國家大事搞成幫派火併。結果呢?張飛仇令智昏,魯莽遇害;仇上加仇,劉備傾巢而出,率軍東征,七十萬精兵,火燒連營,一夕覆滅。若非諸葛亮「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的運籌善後,蜀漢就此亡國,亦不無可能。
透過這些夾敘夾議的段落,或者說,透過評論這齣悲劇,各種聲音的激烈交鋒,不難窺知,作者對三國(尤其是蜀漢)亦譏亦憐的心理。
看他怎麼形容曹操:
從那時起,曹操胃口大開,到處姦淫擄掠,弄美眉,玩人妻,搞熟女—降將張繡的伯母,搶對手呂布部將之妻—秦宜祿的老婆杜氏,連寡婦也不放過;生平唯一敗績,竟是輸給自己兒子:他肖想袁紹次子袁熙之妻甄氏—曹植〈洛神賦〉的女主角,卻被曹丕搶先一步,插旗兼播種,生下後來的魏明帝曹叡。
(《新新三國演義‧敢問天下英雄》)
順便消遣袁紹:
可惜,家世顯赫的袁大公子,沒能在「搶新娘」鼻青臉腫的慘痛教訓中,悟出自己和曹操的差異,也是差距;否則,就不會有後來官渡之役的一敗塗地。
(《新新三國演義‧敢問天下英雄》)
亂世奸雄
關於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汝南許劭語)的評價,張啟疆另有見解:
「瞧!閣下的酸儒劣根性又冒出來了。你把曹操說得像個暴君。你們不要『暴君』,偏偏又錯信『欺君』:靠詐術上位的政治騙子(指劉備)……說到殘暴不仁、奸險狡詐,你們尊崇的『高祖皇帝』,才是箇中翹楚吧?」
(《新新三國演義‧問津之七》)
古往今來,若大旱之望雲霓的民心,養晦韜光的仁人志士,一直在殷殷期盼另一號人物:亂治世之奸雄,治亂世之能臣。
(《新新三國演義‧敢問天下英雄》)
「另一號人物」又是誰?翻遍二十五史,也許可以找到不完全吻合的零星身影。
講不完的故事,拆不盡的機關,說不清的是非功過……千百年來,何止千萬道「吟誦聲」、「冷笑聲」,圍繞這齣歷史大戲,各說各話,各自選角,各取所需,各不相讓(各懷鬼胎亦無妨);可以借古諷今,或許以古喻今,也能博古通今,當作古學今用活教材。
筆者以為,如果技術上可行,張啟疆應該會商借「黑洞視界」 ,多維度全方位超廣角八聲道,呈現切面閃爍的三國宇宙。
悲劇最深邃的本質
閱讀是喚靈術,改寫是大劈棺;言簡或可意賅,層出才能不窮。透過—力透紙背而過—書寫,作古千年的英魂、怨靈,穿透時間土壤,蜂擁而出,爭搶歷史的麥克風,大聲疾呼:「歷史的航道不容更改……」、「豈不聞,唯有浪花淘盡英雄,而英雄,從來禁不起潮浪。」
於是,「懿、亮之爭」,或許該說,「天、亮之爭」(顯然,在張啟疆眼中,「瑜、亮之爭」是假議題)便有了爭權奪利之外,更深刻、悲涼的意義:「閣下覺得,諸葛亮是在跟仲達爭?還是與天鬥?」
人與天鬥,才是悲劇最深邃的本質?
劉、關、張鬥不過自己的天性,諸葛亮摸不透老天的脾氣。
「飛越九重顧盼自雄」的曹操,反而找到應時之道:獨力不能回天,但隻手可以遮天。於是有了那句千古名言:「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其實,『天意』很簡單:民之所好而好之,民之所惡而惡之。順民心,應公理,行天道,如此而已。」年輕書生雙手抱拳,仰天一拜。
「你說的是『王道』。天吃不吃這一套,沒人知道。」
(《新新三國演義‧問津之四》)
「披鶴氅,戴綸巾,憑欄而坐,焚香操琴,而琴音不亂……好一位孔明,好一個『丞相之機,神鬼莫測』!」吟誦聲變為讚嘆聲。
「你該在意的是,神鬼之機,丞相莫測?」冷笑聲也轉成詰問聲。
「怎麼之機?如何莫測?請道其詳!」吟誦聲化出年輕書生,面露不解。
「『空城計』固然精彩,但純屬個人表演、即興之作;只能證明司馬懿『不如孔明』,卻不能改變『蜀不敵魏』的大局。」
(《新新三國演義‧向壁之八》)
想來,草船借箭、借東風,以及,在「帳內設七盞大燈、四十九盞小燈,另設一盞本命燈—七日內主燈不滅,他便可再多活十二年」的祈禳之法……再怎麼「神鬼莫測」的智者,滿腹韜略,一身皮囊,都是向天借命。
歷史的鐘擺效應?
秉燭夜讀,讀到什麼?留取丹心?留得青山?笑傲江湖?稱霸天下?
一套二十五史,月光下排排站,不過是唱歌答數,長吁短嘆,悲劇的晚點名。
耐人尋味的是,已經定讞的歷史,或許「不容更改」,但沒有規定,不可以有新的詮釋。例如:
不知為何,劉備對眼前少年(趙子龍)萌生一腔子難以言喻的「親切感」:如何親?怎麼切?他說不上來。一種比一見如故、如兄如弟更進一步的感覺。劉備只能模糊感應到「風從虎」、「雲從龍」之類的王者直覺、天命歸趨:此人必將為我所用,渾然不知:何謂「子龍」?望子如何成龍?眼前之人與他的嫡親子嗣密切相關,是護守他劉氏王朝唯一血脈的天降神兵。
心頭竄熱,咽喉凝噎,劉備突然抱住對方,又是拍肩,又是搥背……
(《新新三國演義‧常山趙子龍》)
「子龍」竟作如是解!我們當然可以將這段表演看成劉備的「識人之明」(劉備一生最成功的事,是讓自己成為「識『明』之人」),以及「收買人心」起手式。
最有趣的說法,當推卷末的「鐘擺效應」:
「昔有三家分晉,今有三家歸晉。正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一歷史鐵律,喔不!是鐘擺,顛撲不破。」
(《新新三國演義‧向壁之九》)
「三家分晉」是指春秋末年,晉國被韓、趙、魏三家瓜分的事件,也是春秋、戰國的分野。司馬光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的記載,就從這一事件開始。
兩起分合,本為巧合。但作者似乎認為,促成「歷史鐵律」的力量,來自一枚關鍵詞:司馬。
昔有漢武帝「迫害」司馬遷:施以斷子絕孫的酷刑(司馬遷因而發憤著史記,發揮文字的力量);後有司馬家斬草除根,結束以三國為名的「東漢末年」。東漢雖是亡於曹魏,但,別忘了還有蜀漢,收拾天下亂局的人,卻是司馬一族。
當然,司馬遷和司馬炎有沒有親戚關係?有待考證。百千年的開枝散葉,因果早已混亂。所以才說是「文字的力量」:以史為始,盪幅六百多年,而在歷史另一端,畫出對稱走勢圖。冥冥之中,鐘擺的起點,又落入另一位司馬家後代(司馬光)的筆下。
對照張啟疆前作新新古典《水滸傳》裡,刻意「擴大戰場」的序言:
(梁山好漢)若能結合其他在野勢力,一舉推翻貪腐無能的朝廷—個人成敗、歷史功過事小,當時的中原動盪不安,盜賊四起,蠻夷蠢蠢欲動,金兵就要南下……(這群)擁有豐富實戰經驗的「終極戰士」,應該就是保衛家國的主力軍。後來的岳飛,也許不必戰得那般孤獨與淒涼。
(《水滸傳‧自序》)
不難窺出,所謂「歷史」,不只是死去的書頁,也是活來的時空;改朝換代帶來了連鎖錯動:一頁青史不只是一個故事。斷代史的背後,是生滅消長的渾然全史,一座由複雜齒輪組成的龐然城國。
瞧瞧全書的最後一行:
結束了擾攘動亂的三國時代,也預留另一動亂時代的伏筆:五胡亂華。
(《新新三國演義‧三家歸晉》)
庚子年深秋於結廬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