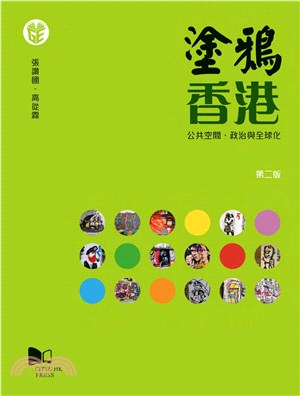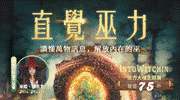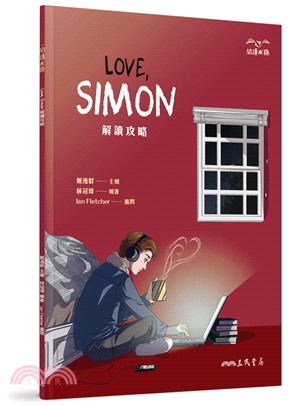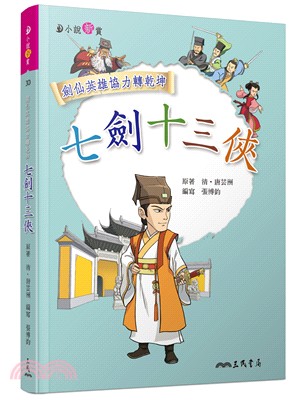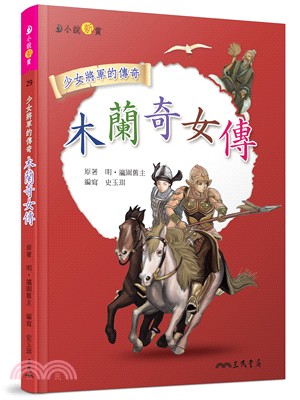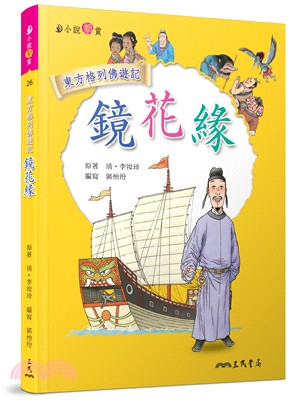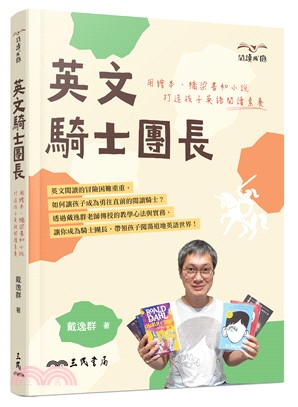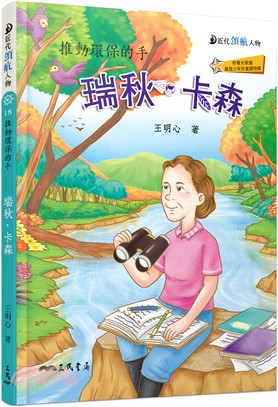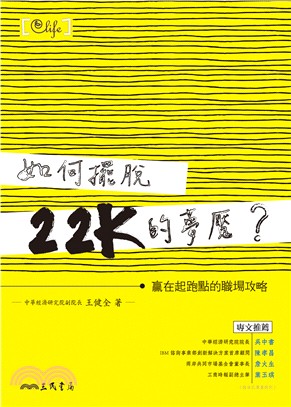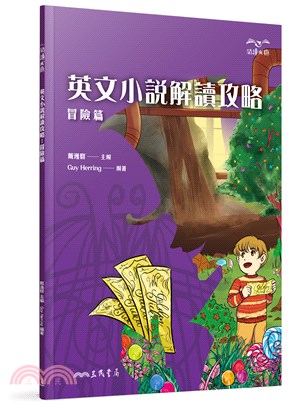塗鴉香港:公共空間、政治與全球化【第二版】(電子書)
商品資訊
定價
:NT$ 480 元優惠價
:70 折 336 元
閱讀器:書紐電子書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0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如果一粒沙可以看世界,塗鴉就足以窺探香港的面貌,《塗鴉香港:公共空間、政治與全球化》是一種實證調查、分析與批判的通識書籍。
本書於2012年出版後獲得相當反響。書有人看,便是某種認可,更是挑戰。再版,就是對讀者的回應。過去幾年,香港的發展觸及不同角落與層面,從行政長官選舉到「佔領中環」運動,經歷了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巨大演變。這期間,塗鴉世界也起了不少變化,最明顯的是,一代新人換舊人,早期的塗鴉已消失殆盡,但更多的塗鴉見證並記錄了引起紛爭的社會運動。
「佔領中環」不僅是社會運動,更是塗鴉與公共空間使用如何互動的淋漓呈現。跟世界許多都市一樣,香港在「佔中」期間的社會動盪,為塗鴉提供了一個公開登上前台的機會。不管有意或無意,所有在佔領區留下圖案、文字、符號和其他文本的人都短暫的成為塗鴉客。
塗鴉文本的存留時間通常很短暫,第一版收錄的許多圖文都已是明日黄花。過去幾年,作者持續走遍大街小巷,在公開或隱蔽的地方探索香港的最新面貌,記錄了更多本土和外來的塗鴉作品。《塗鴉香港》第二版因此更新了大量圖片,並充實內容及相關理論的探討,但保留了一些歷史切片,以檢驗情境與塗鴉的社會效應。變與不變,全可在前後對比中看出端倪。
歲月更迭,《塗鴉香港》第二版回顧的,照樣是前人在公共空間裏所留下的點滴,以及香港快速社會變遷所引起的許多公共領域的問題,多少為香港保留一份文獻。不變的是,塗鴉所展現的依然是喧嘩多樣的世界。塗鴉,其實並非「塗抹詩書如老鴨」,而是香港多元社會的縮影。
本書於2012年出版後獲得相當反響。書有人看,便是某種認可,更是挑戰。再版,就是對讀者的回應。過去幾年,香港的發展觸及不同角落與層面,從行政長官選舉到「佔領中環」運動,經歷了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巨大演變。這期間,塗鴉世界也起了不少變化,最明顯的是,一代新人換舊人,早期的塗鴉已消失殆盡,但更多的塗鴉見證並記錄了引起紛爭的社會運動。
「佔領中環」不僅是社會運動,更是塗鴉與公共空間使用如何互動的淋漓呈現。跟世界許多都市一樣,香港在「佔中」期間的社會動盪,為塗鴉提供了一個公開登上前台的機會。不管有意或無意,所有在佔領區留下圖案、文字、符號和其他文本的人都短暫的成為塗鴉客。
塗鴉文本的存留時間通常很短暫,第一版收錄的許多圖文都已是明日黄花。過去幾年,作者持續走遍大街小巷,在公開或隱蔽的地方探索香港的最新面貌,記錄了更多本土和外來的塗鴉作品。《塗鴉香港》第二版因此更新了大量圖片,並充實內容及相關理論的探討,但保留了一些歷史切片,以檢驗情境與塗鴉的社會效應。變與不變,全可在前後對比中看出端倪。
歲月更迭,《塗鴉香港》第二版回顧的,照樣是前人在公共空間裏所留下的點滴,以及香港快速社會變遷所引起的許多公共領域的問題,多少為香港保留一份文獻。不變的是,塗鴉所展現的依然是喧嘩多樣的世界。塗鴉,其實並非「塗抹詩書如老鴨」,而是香港多元社會的縮影。
作者簡介
張讚國,筆名端木少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新聞系博士(1986),曾任台灣《聯合報》記者(1976, 1978–80)、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客座教授(1993–9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客座教授(1996–97)、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教授/榮譽教授(1990–2009/2009–)、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教授(2009–2016),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客座教授(2016–2017)。
高從霖,台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州都會大學電腦資訊系學士,曾任台灣廣播公司記者和導播(1977–1981)、美國《世界日報》駐明尼蘇達記者(1998–2009)。
高從霖,台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州都會大學電腦資訊系學士,曾任台灣廣播公司記者和導播(1977–1981)、美國《世界日報》駐明尼蘇達記者(1998–2009)。
目次
第一章 「佔領中環」:社會運動的塗鴉效應
第二章 「曾灶財墨蹟」: 民粹的霸道
第三章 「皇帝萬歲」:符號的商業操作
第四章 公共空間的爭奪:法律與街頭藝術的衝突
第五章 由公共空間到公共領域:媒介的集體思維
第六章 中文塗鴉:本土與全球的融合
第七章 「低成本藝術品」:不可理喻的大眾文化
第八章 「為塗鴉而戰」:街頭藝術者的使命
第九章 結論:塗鴉的想像與想像的塗鴉
附錄:塗鴉的文本與情境
第二章 「曾灶財墨蹟」: 民粹的霸道
第三章 「皇帝萬歲」:符號的商業操作
第四章 公共空間的爭奪:法律與街頭藝術的衝突
第五章 由公共空間到公共領域:媒介的集體思維
第六章 中文塗鴉:本土與全球的融合
第七章 「低成本藝術品」:不可理喻的大眾文化
第八章 「為塗鴉而戰」:街頭藝術者的使命
第九章 結論:塗鴉的想像與想像的塗鴉
附錄:塗鴉的文本與情境
書摘/試閱
第一章
「佔領中環」:社會運動的塗鴉效應
對許多不留意的人來說,香港公共空間的塗鴉只是一種礙眼的街頭亂象,不管是文字或圖像,除了一些奇形怪狀的線條和粗俗的圖案,都難以理解,而且毫無價值可言。或許,這是塗鴉的唯一意義。
塗鴉客卻有不同的想法,他們以第三隻眼看周遭環境,面對一片開放的空間,見人所未見。塗鴉,在他們看來,「不是塗污」(DEVIL,2012 年 1 月 5 日通訊訪問)。由字眼看,這種見解並非全無道理,塗鴉兩字的確不等於塗污,儘管港人心中早有「『塗鴉等同塗污,惡意破壞』的負面印象」(《頭條日報》,2015 年 3 月 7 日,頁 28)。從內涵來說,也有點根據,塗鴉是在非法的地方書寫文字,不是塗抹污點,而是以添加的文字毀壞舊有空間的原貌,多少算得上是 Schumpeter(1942)所說的創造性破壞。
美國紐約街頭藝術家 Michael De Feo 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街頭藝術家和塗鴉藝術家都用不同的方法在街道上創造藝術(《南華早報》,2010 年 6 月 20 日,藝術版,頁10)。兩者的焦點在於文字和圖案的差別使用,塗鴉通常以文字為主。因為文字存在於特定的空間或載具,塗鴉因此是一種不連續的傳播模式;透過塗鴉,人們不必依賴面對面的互動,或者知悉作者的身份,也可以進行間接的視覺對話(Klingman & Shalev, 2001)。間接,是由於文本的製造者和接收者很少會同時出現在相同地點。
更堂皇一點,對那些兼具某種使命的塗鴉客看來,塗鴉是一種源自草根的自發性動作和聲音,發抒於內心的一種對抗國家強權或機器壓迫的自然反應,也就是意識形態的抗衡(Lachmann, 1988)。例如,針對 2011 年 3 月日本福島核能電廠受到地震和海嘯影響的災難,塗鴉客 281_Anti Nuke 於 2013 年開始在東京街頭上大肆張貼反核的圖案貼紙,決意以塗鴉引起對「巨大公共污染災難」的注意(《南華早報》,2013 年 11月 30 日,頁 A9)。個人與國家機器對抗,就像大衛與巨人的戰鬥,還有什麽比在街頭路面或牆壁上書寫抗議文字或畫上一幅敏感的圖案,更能引起行人的注目?
不過,行人注目與塗鴉客行動是兩碼事;先有塗鴉,才談得上注目與否。塗鴉出現在不被允許的地方,相當程度上破壞了香港整潔的公共設施(如橋墩、行人走道、路標或交通訊號控制箱),損毀了私人產業(如牆壁、門窗)。就算不計較財物和時間的浪費,塗鴉一方面攪亂了市容,污染視野,另一方面則無視法律規範,挑戰社會秩序。
從理論分析,塗鴉的社會後果符合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lton Friedman(1962)提出的「鄰里效應」(neighbourhood effects)。第一,除非是現行犯人贓俱獲,街頭上所看得到的塗鴉,不論是文字或圖案,官方都很難明確指定誰是罪魁禍首,因塗鴉導致的任何財物損失,便求償無門。第二,除了物業的所有權人外,塗鴉帶來的金錢支出,如粉刷公共牆壁的人力和物力,甚至短暫封閉部分道路,都可能涉及其他人的有形或無形利益(如納稅錢或交通不便和市容髒亂),這些人並不易確認,即使取得賠償或補償,也難以進行有效分配。這種「鄰里效應」是塗鴉不易根除的原因,就像空氣污染一樣,源頭飄忽不定,很難追蹤,便無法對症下藥解決。
另外,在抽象層面上,塗鴉無疑也是個人自由意志的表達,以文字或圖畫,在公共空間,堅持維護某種言論不受拘束的公民權利。在西方國家,這種執着是維繫塗鴉蓬勃不墜的主因之一,香港也有類似信仰。歸根究底,塗鴉是一種對公共空間應為公眾使用的宣稱,一旦轉化成對國家或政府不合理政治行為的抗爭,也就是對迫害的公開合理控訴。
塗鴉,可以是政治情緒宣洩的一種管道,尤其是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如 2014 年香港「佔領中環」運動,有些塗鴉客的作品的確出現在佔領區。一幅簡潔的政治圖案或幾個聳動的文字,足以勝過千言萬語,更震撼人心。塗鴉因此是反問,對任何威權建制的質疑。質疑,不光是知識的追求,也是對特定空間裏典章制度的安排和操作是否合理,進行某種試探,並尋求解決的途徑。
跟世界其他大都市一樣,如紐約、費城、巴黎、倫敦、柏林、東京或台北,香港的政治塗鴉不僅隱藏在大街小巷、溝渠水道的牆壁之中,更不時公然的出現在萬人擁擠的觀光景點或人來人往的地鐵站附近,向國家或政府宣戰。塗鴉,以一副你奈我何—in your face—的姿態攀牆附壁(ORSEK,2010 年 4 月 7 日訪問),越是法律或現實不許可的場所,塗鴉客越是躍躍欲試。
政治塗鴉因此往往與時勢有關,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由於「一國兩制」的保障,與英國殖民政府留下的一些傳統,對政治上的壓迫、排擠或獨斷,便顯得相當敏感,尤其是來自北京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肅殺之氣,即使是有關中國領導人的塗鴉也難以容忍。
「扼殺塗鴉,就是扼殺香港的未來」(李怡,《蘋果日報》,2011 年 4 月 16 日,社評,頁 A02)。話雖然說重了些,但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對民主和自由的無知或一知半解,就無異讓獨裁與奴役予取予求,甚至變本加厲,無法無天。
不論對香港或北京來說, 2014 年的「佔領中環」,很明顯的是一場追求 2017 年行政長官民主普選的社會運動,從形式和內容看,更是不折不扣的大規模塗鴉運動,整個佔領區的公共空間全成為文字、圖案、標語和符號等塗鴉展現的場所。「佔中」的政治目的,不管如何崇高,並不足以掩蓋塗鴉手段的事實。
「佔領中環」塗鴉
「佔領中環」運動從 2014 年 9 月 28 日起,到 12 月 15 日,79 天之間,在金鐘、銅鑼灣和旺角佔領區,鬧得沸沸揚揚。在整個過程中,「佔中」的符號很聳動,再加上「雨傘革命」的字眼,顯得來勢洶洶,難怪中國的黨國和香港建制派媒體口徑一致,以破壞香港經濟和法治,全面圍剿。
不管短期或長期,有關「佔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後果不易準確評估,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不少書籍無疑會圍繞它的成敗大做文章,其功過還有待歷史仲裁。本章試圖從塗鴉的視野或另類思考,詮釋「佔中」的形式和內容。
從塗鴉的定義和操作看,「佔中」的社會運動是徹頭徹尾的大型塗鴉運動,只不過它的政治色彩稀釋了塗鴉本質,換句話說,社會運動的功能或作用掩飾了塗鴉的取徑,並提供一個合理化的視野框架。新聞媒體在報導「佔中」時,因此強調的都是民主普選與官民政治對抗,忽略了塗鴉效應。
第一,「佔中」是公民不服從運動,參與者的出發點就是有意違背法律的規範,執意佔領不該擁有的公共空間—街道,在抽象理念和實際運作上,與塗鴉客強行使用公共場所,書寫或畫圖的舉動,並無區別,頂多是集體和個人的分野。
第二,在正常情況下,除了官方於路面上書寫的有關交通指示,或牆壁上張貼的告示,沒有任何人可以在香港立法會附近的街道,或其他公共場所書寫文字、畫圖或掛上各種即興和預製的視覺或形象的標語和布條。「佔中」期間,塗鴉所可能採用的工具和手法,都被派上用場,甚至發揮到極致,兩者沒有什麽不同。
第三,政治塗鴉往往以人物、議題或事件為主,「佔中」的圖文基本上也圍繞這三個方面,特別是那些簡單的口號和圖像。它們的作者通常不詳,就像塗鴉客隱去真實姓名,留在公共空間的只是他們的作品,沒人知道他們來自何方,又往何處去。他們企圖的也許是種對話,卻非一對一的連續傳播,間接溝通的對象又不夠明朗,是官方、路人或媒體,還是志同道合之輩?塗鴉亦如是。
第四,塗鴉客的死對頭,是代表公權力的警察,這種情形在世界各國皆然,除非警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警察出現在特定公共空間時,如果不是防範塗鴉於未然,便意謂公權力受到有意或無意的削弱。從頭到尾,香港警方在「佔中」地區部署重兵,甚至還使用暴力對付示威者,在在說明公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緊張衝突,一如警察與塗鴉客之間的貓鼠遊戲。
當然,「佔中」參與者不會承認他們是塗鴉客,或所作所為是十足的塗鴉,更可能辯解以塗鴉形容「佔中」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訴求,是對神聖目標的褻瀆。也難怪佔領區出現「請勿塗鴉!如要張聲請用紙代替!」的警告(圖 1.1),看起來和街道電箱上「禁止塗鴉」的貼紙,沒什麽兩樣。其實,這是對塗鴉的誤解,以工具判定塗鴉,或認為塗鴉是在牆壁上隨意書寫,忽略了縱然使用紙張寫字,再貼上牆壁,它依舊是塗鴉。
由文字到圖像,「佔中」的塗鴉數量難以計算,但是質化上可以輕易歸類。
任何社會運動都免不了使用符號(Bennett, 1980),特別是簡潔易懂的圖文。以「佔中」為例,符號有兩種,一種是指示性的,直接了當,不帶情感或價值判斷,如有關「佔中」地點或街道指示牌的文字塗鴉;另一種是濃縮性的,充滿喜怒哀樂的感受或聳動情懷,如「雨傘革命」。在北京眼中,「革命」字眼不免觸目驚心(圖 1.2)。
不論是指示性或濃縮性符號,簡約的文字或圖像往往引人注目和深思。從金鐘、銅鑼灣到旺角,最常見的是與雨傘有關的貼紙或圖案,很多是即興創作,有些是刻意設計,相當具有想像力,幾乎是街頭藝術的展示。從廣義的角度看,若非合法,街頭藝術無疑也是塗鴉,尤其是以公共空間作為畫板。自始至終,「佔中」的場地全屬非法徵用。
這些符號很多是針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各種謾駡、詛咒、譏諷、醜化和調侃的圖文,張貼在牆壁上,到處可見,尤其是「奸狼」的形象,暗示他的奸詐狡猾,甚至還蓋棺論定。它們跟平常時的塗鴉如出一轍,數目卻多出千百倍,內容更加犀利惡毒。
在金鐘政府總部附近,只要是牆壁,幾乎貼滿了五顏六色的大小紙張,就像塗鴉客以貼紙在電箱、燈柱和牆壁上留下簽名一樣。每一張都代表一個心聲,臨時被命名的連儂牆,更是密密麻麻滿佈便條紙,清一色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追求,成為觀光景點,有如塗鴉世界的「名人堂」,吸引了不少遊客。
大部分時候,逛佔領區的人可能比示威的人還多。不少人都是來看熱鬧,還在標語或海報前拍照,表示到此一遊。一些聳動標語或大型的人頭像,如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戲謔或詼諧的方式呈現,往往讓人停下腳步觀看或合照,尤其是北方南下的中國遊客。在公共空間裏,這些政治塗鴉多少表示「一國兩制」的安排還保存了一點氣息。
「佔中」運動於 2014 年 12 月 15 日被政府強行清場後正式落幕,塗鴉的社會效應卻在整個香港擴大,其中以「我愛真普選」的標語最為突出。除了街道上的黃色小貼紙四處可見,幾個主要山頭,如獅子山,從 2014 年 10 月到 2015 年 2 月,也先後四次被掛上巨大的「我愛真普選」布條,從山頂垂直而下,場面壯觀(圖 1.3)。儘管布條都很快被拆除,這些業餘塗鴉客的膽識和舉動,已驚動四方和警方,比起2011年「誰怕艾未未?」塗鴉出現在香港街頭時引起的騷動,前後相互輝映。
「誰怕艾未未?」
艾未未是中國著名的行為藝術家與異議人士,2011 年 4 月 3 日,他準備搭機前往香港,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被公安帶走。艾未未被拘留後,中國官方雖然證實,但並未正式說明他犯了什麽罪,被拘押在哪裏。一些零星的消息指出,艾未未踩到當局的紅線,涉嫌經濟犯罪。45 天後,新華社於 5 月 20 日簡短指出,北京市公安機關「已初步查明,艾未未實際控制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繳納鉅額稅款、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等犯罪行為。」
根據媒體猜測,這項指控非常嚴重,艾未未恐怕難免刑責,只是輕重而已。2011 年 6 月 22 日艾未未被釋放,官方裁定他的設計公司必須繳付 1,500 萬人民幣(港幣 1,840 萬)的欠稅和罰款。艾未未不服上訴,但官方維持原判。一般認為,以逃稅入罪是對艾未未批評政府的處罰(《南華早報》,2012 年 3 月 30 日)。
有關艾未未被捕的新聞,中國媒體不是噤若寒蟬,就是口徑一致,輕描淡寫,堅持「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北京《環球時報》,2011 年 4 月 6 日社評)。
艾未未的特立獨行所以受到關注,一方面固然和他父親是紅色著名詩人艾青(蔣正涵)有關,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藝術內涵獨樹一格,表達方式又往往「語不驚人死不休」,作品曾在歐美幾個國家展出。2008 年他與瑞士建築事務所 Herzog & de Meuron 合作,擔任北京奧運會國家體育場「鳥巢」的藝術顧問,更是名噪一時。
艾未未被逮捕的消息傳到國外,引起很大的震驚和反響。歐美主要國家的政府、新聞媒體、國際知名美術館及人權組織都公開譴責中國罔顧人權與正當法律程序,要求釋放艾未未。許多團體和個人,包括旅居外國的中國人,也發起簽名運動,強烈支持艾未未。一件本是個人與國家對抗的行為遂演變成國際間的政治角力,在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以不同形式展現。
人間有公道,歷史自有定論。艾未未的是非功過與中國政府對抗異議分子的高壓手段,不是本書討論的重點。跟「佔中」運動一樣,艾未未被捕所引發的塗鴉效應倒是值得探討:一種結合街頭藝術與社會實踐的抵抗形式,在香港悄然登上舞台,延續這個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國際都市特有的文化格局。
國際上,自發性的抗議活動相繼成為新聞報導,香港雖然是中國特別行政區,在聲援艾未未方面,卻也不落人後,除了街頭的遊行示威,各種塗鴉作品如雨後春筍,出現在主要地區的街頭巷尾,此起彼落,以游擊戰的方式,與官方周旋。
從 2011 年 4 月初起,上環、中環、尖沙咀、銅鑼灣、旺角、深水埗、荃灣等幾個人口流動頻繁的地區,在人行道、天橋、隧道牆壁等公共場所,被噴上艾未未的圖像,以及「艾未未中國良心」及「誰怕艾未未」等字句。噴漆塗鴉因為面積小,不仔細留意,很可能擦身而過;人來人往,書寫在地面上的文字則相當醒目,行人的足跡過處,恐怕很難不惹起一點塵埃。
「誰怕艾未未?」真是大哉問。提問的人是誰,對警方來說,也許很重要,難怪非調查不可。對大多數人而言,更重要的,其實是問題的答案。
剛開始時,「誰怕艾未未?」的質問只出現在特定的少數公共場所,對象有限。透過新聞轉播,尤其是電視和網絡,沒親眼看過這五個字的人多少也知道問題的存在。「誰怕艾未未?」的塗鴉遂轉化成公共空間裏的一個考題,針對所有人。這個問題隱含兩個層面:其一,到底是哪些人聞艾未未而色變?其二,艾未未這個人有什麽可怕?
第一個層面牽涉廣泛,又取決於第二個層面如何界定,兩者牽涉的是個人麻煩或社會問題的判別。艾未未是否可怕?從北京到香港,由中國到國外,基本上這是個政治或思想問題,北京當局卻尋求法律解決,即使惡法亦法,依法治理,而非因循合理的正義程序,以法治理。一旦成立,艾未未的逃稅行為就提供官方一個正當的掩護,孰是孰非,便很難理出個黑白分明的判別。
青史不會盡成灰,「誰怕艾未未」與為什麽怕的問題,遲早要理出個頭緒。不過,怕艾未未的人可能還真的不少。在香港,只是街頭上一些零星的塗鴉(圖 1.4),就弄得風吹草動,讓警方疲於奔命。香港塗鴉藝術先驅陳廣仁(MC 仁,見第八章)認為官方「真係大驚小怪咗」(《蘋果日報》,2011 年 4 月 15 日,頁 A02)。一般塗鴉或許不至於如此勞師動眾,畫上艾未未顯然非同小可了。
香港警方越是大費周章,兵分四路,到處湮滅這些帶有「犯上」的圖案或文字,以塗鴉作為政治抗議的一些社會行動家就越起勁,因為這是製造新聞的絕佳機會。原本只是在固定地區的一個特例,可以像 2006 年的科幻懸疑電影《V怪客》(V for Vendetta)裏戴着面具的獨行自由鬥士一樣,經過傳播,而引發出戴着同樣面具的無數自由鬥士,真假難分。
2011年4月間,以「塗鴉少女」為代號的塗鴉客於香港國金中心和星光大道等十多個地區留下「誰在害怕艾未未」的噴漆塗鴉後,更多的大小塗鴉,接踵出現。4月15 日 CNN 報導後,整個事件因而成為國際新聞,塗鴉或許只是引言,香港警方欲蓋彌彰,還貽笑大方。《蘋果日報》4月16 日,以〈人人都是艾未未〉為標題的新聞,就傳神的點出「V怪客」自由鬥士在香港的翻版。
「塗鴉少女」的塗鴉顯然不是出自一時魯莽或衝動,而是一番深思熟慮後良知的召喚,從她接受《塗鴉》(鄺穎萱,2011,頁 61)一書訪問的一段話可見一斑:
我認為一個良好公民的價值不在於盲目服從。我們不是被動地被法律支配,每人都是一個有理性的主體,正因為尊重法治精神,我們才如斯尋根問底,反思不同法例的出發點到底合理與否,追問公義到底是誰的公義。
短短幾句話,卻擲地有聲。「塗鴉少女」為「誰在害怕艾未未」的塗鴉提供了一個官逼民反的立足點,談的其實並非塗鴉,而是公民社會裏理性參與言論自由表達的重要。許多人,包括官方和建制派,只看到了塗鴉的表像,對她的提問充耳不聞。「塗鴉少女」其實可以不用辯解,當《蘋果日報》說「人人都是艾未未」時,民心何在,不辨自明,有關艾未未塗鴉背後的深沉問題,也就不能等閒視之。
由社會學理論和現實的角度看,名字或形象與所指涉的物體之間,有一段隔閡,沒有百分之一百的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人與事物之間的關係,也因情境不同,距離遠近,位置所在,而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巨大差異。艾未未塗鴉造成的社會效應,因此不能光從公共空間被破壞的立場切入。
在北京,艾未未是個眼中釘,不除不快。在香港,艾未未塗鴉是個礙眼的東西,不去不淨。艾未未不過是遭受國家機器相同處置的萬千中國人之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以內政為由,要外國人「閉嘴」(《南華早報》,2011 年 5 月 6 日),好歹說得理直氣壯。在特區,艾未未塗鴉頂多是個觸動政治神經的街頭圖像,官方擺出強硬姿態,顯然也要塗鴉客「封口」。
面對這些帶有政治意味的塗鴉,香港警方如臨大敵,將案件列為「刑事毀壞案」,交由重案組調查處理。《明報》譏諷為「以炮彈打蒼蠅」(2011 年 5 月 2 日社評,頁 A04),並不為過。殺雞用牛刀,總是荒唐。警方的動作倒也俐落,大部分較為引人注目的文字塗鴉都在短時間內被清洗乾淨。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關艾未未的塗鴉,以文字、噴漆或貼紙,自動在街道上到處出現,讓警方分身乏術。最特別的是,以光影將艾未未的圖形和文字,投像到主要建築物的牆面,包括駐香港解放軍總部的外牆,不留任何痕跡。塗鴉與科技結合,既達到目的,又不破壞公共空間,警方也就難以下手。
雷聲大雨點小,香港警方固然以刑事案件處理這些艾未未塗鴉,重案組倒也沒逮捕任何塗鴉客,即使抓一、兩個人殺雞儆猴,最後頂多罰款了事,甚至不了了之。塗鴉,固然礙眼,到底不至於罪無可赦,嚴重到必須如艾未未遭受牢獄之災或承擔巨額罰款。
就算官方不剷除,存留在天橋橋墩、路面或牆壁上的任何塗鴉,不論是臨時起意或蓄意而為,長年累月的任憑風吹雨打,腳步踩過,終究會隨時間消逝而逐漸褪色,慢慢被淡忘,以致消失在人們的記憶裏,尤其是集體記憶。少數得以保留較久的,大多數人將視而不見,或見怪不怪,不會引發太多情緒性或回顧的反應。「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塗鴉應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佔領中環」:社會運動的塗鴉效應
對許多不留意的人來說,香港公共空間的塗鴉只是一種礙眼的街頭亂象,不管是文字或圖像,除了一些奇形怪狀的線條和粗俗的圖案,都難以理解,而且毫無價值可言。或許,這是塗鴉的唯一意義。
塗鴉客卻有不同的想法,他們以第三隻眼看周遭環境,面對一片開放的空間,見人所未見。塗鴉,在他們看來,「不是塗污」(DEVIL,2012 年 1 月 5 日通訊訪問)。由字眼看,這種見解並非全無道理,塗鴉兩字的確不等於塗污,儘管港人心中早有「『塗鴉等同塗污,惡意破壞』的負面印象」(《頭條日報》,2015 年 3 月 7 日,頁 28)。從內涵來說,也有點根據,塗鴉是在非法的地方書寫文字,不是塗抹污點,而是以添加的文字毀壞舊有空間的原貌,多少算得上是 Schumpeter(1942)所說的創造性破壞。
美國紐約街頭藝術家 Michael De Feo 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街頭藝術家和塗鴉藝術家都用不同的方法在街道上創造藝術(《南華早報》,2010 年 6 月 20 日,藝術版,頁10)。兩者的焦點在於文字和圖案的差別使用,塗鴉通常以文字為主。因為文字存在於特定的空間或載具,塗鴉因此是一種不連續的傳播模式;透過塗鴉,人們不必依賴面對面的互動,或者知悉作者的身份,也可以進行間接的視覺對話(Klingman & Shalev, 2001)。間接,是由於文本的製造者和接收者很少會同時出現在相同地點。
更堂皇一點,對那些兼具某種使命的塗鴉客看來,塗鴉是一種源自草根的自發性動作和聲音,發抒於內心的一種對抗國家強權或機器壓迫的自然反應,也就是意識形態的抗衡(Lachmann, 1988)。例如,針對 2011 年 3 月日本福島核能電廠受到地震和海嘯影響的災難,塗鴉客 281_Anti Nuke 於 2013 年開始在東京街頭上大肆張貼反核的圖案貼紙,決意以塗鴉引起對「巨大公共污染災難」的注意(《南華早報》,2013 年 11月 30 日,頁 A9)。個人與國家機器對抗,就像大衛與巨人的戰鬥,還有什麽比在街頭路面或牆壁上書寫抗議文字或畫上一幅敏感的圖案,更能引起行人的注目?
不過,行人注目與塗鴉客行動是兩碼事;先有塗鴉,才談得上注目與否。塗鴉出現在不被允許的地方,相當程度上破壞了香港整潔的公共設施(如橋墩、行人走道、路標或交通訊號控制箱),損毀了私人產業(如牆壁、門窗)。就算不計較財物和時間的浪費,塗鴉一方面攪亂了市容,污染視野,另一方面則無視法律規範,挑戰社會秩序。
從理論分析,塗鴉的社會後果符合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lton Friedman(1962)提出的「鄰里效應」(neighbourhood effects)。第一,除非是現行犯人贓俱獲,街頭上所看得到的塗鴉,不論是文字或圖案,官方都很難明確指定誰是罪魁禍首,因塗鴉導致的任何財物損失,便求償無門。第二,除了物業的所有權人外,塗鴉帶來的金錢支出,如粉刷公共牆壁的人力和物力,甚至短暫封閉部分道路,都可能涉及其他人的有形或無形利益(如納稅錢或交通不便和市容髒亂),這些人並不易確認,即使取得賠償或補償,也難以進行有效分配。這種「鄰里效應」是塗鴉不易根除的原因,就像空氣污染一樣,源頭飄忽不定,很難追蹤,便無法對症下藥解決。
另外,在抽象層面上,塗鴉無疑也是個人自由意志的表達,以文字或圖畫,在公共空間,堅持維護某種言論不受拘束的公民權利。在西方國家,這種執着是維繫塗鴉蓬勃不墜的主因之一,香港也有類似信仰。歸根究底,塗鴉是一種對公共空間應為公眾使用的宣稱,一旦轉化成對國家或政府不合理政治行為的抗爭,也就是對迫害的公開合理控訴。
塗鴉,可以是政治情緒宣洩的一種管道,尤其是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如 2014 年香港「佔領中環」運動,有些塗鴉客的作品的確出現在佔領區。一幅簡潔的政治圖案或幾個聳動的文字,足以勝過千言萬語,更震撼人心。塗鴉因此是反問,對任何威權建制的質疑。質疑,不光是知識的追求,也是對特定空間裏典章制度的安排和操作是否合理,進行某種試探,並尋求解決的途徑。
跟世界其他大都市一樣,如紐約、費城、巴黎、倫敦、柏林、東京或台北,香港的政治塗鴉不僅隱藏在大街小巷、溝渠水道的牆壁之中,更不時公然的出現在萬人擁擠的觀光景點或人來人往的地鐵站附近,向國家或政府宣戰。塗鴉,以一副你奈我何—in your face—的姿態攀牆附壁(ORSEK,2010 年 4 月 7 日訪問),越是法律或現實不許可的場所,塗鴉客越是躍躍欲試。
政治塗鴉因此往往與時勢有關,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由於「一國兩制」的保障,與英國殖民政府留下的一些傳統,對政治上的壓迫、排擠或獨斷,便顯得相當敏感,尤其是來自北京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肅殺之氣,即使是有關中國領導人的塗鴉也難以容忍。
「扼殺塗鴉,就是扼殺香港的未來」(李怡,《蘋果日報》,2011 年 4 月 16 日,社評,頁 A02)。話雖然說重了些,但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對民主和自由的無知或一知半解,就無異讓獨裁與奴役予取予求,甚至變本加厲,無法無天。
不論對香港或北京來說, 2014 年的「佔領中環」,很明顯的是一場追求 2017 年行政長官民主普選的社會運動,從形式和內容看,更是不折不扣的大規模塗鴉運動,整個佔領區的公共空間全成為文字、圖案、標語和符號等塗鴉展現的場所。「佔中」的政治目的,不管如何崇高,並不足以掩蓋塗鴉手段的事實。
「佔領中環」塗鴉
「佔領中環」運動從 2014 年 9 月 28 日起,到 12 月 15 日,79 天之間,在金鐘、銅鑼灣和旺角佔領區,鬧得沸沸揚揚。在整個過程中,「佔中」的符號很聳動,再加上「雨傘革命」的字眼,顯得來勢洶洶,難怪中國的黨國和香港建制派媒體口徑一致,以破壞香港經濟和法治,全面圍剿。
不管短期或長期,有關「佔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後果不易準確評估,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不少書籍無疑會圍繞它的成敗大做文章,其功過還有待歷史仲裁。本章試圖從塗鴉的視野或另類思考,詮釋「佔中」的形式和內容。
從塗鴉的定義和操作看,「佔中」的社會運動是徹頭徹尾的大型塗鴉運動,只不過它的政治色彩稀釋了塗鴉本質,換句話說,社會運動的功能或作用掩飾了塗鴉的取徑,並提供一個合理化的視野框架。新聞媒體在報導「佔中」時,因此強調的都是民主普選與官民政治對抗,忽略了塗鴉效應。
第一,「佔中」是公民不服從運動,參與者的出發點就是有意違背法律的規範,執意佔領不該擁有的公共空間—街道,在抽象理念和實際運作上,與塗鴉客強行使用公共場所,書寫或畫圖的舉動,並無區別,頂多是集體和個人的分野。
第二,在正常情況下,除了官方於路面上書寫的有關交通指示,或牆壁上張貼的告示,沒有任何人可以在香港立法會附近的街道,或其他公共場所書寫文字、畫圖或掛上各種即興和預製的視覺或形象的標語和布條。「佔中」期間,塗鴉所可能採用的工具和手法,都被派上用場,甚至發揮到極致,兩者沒有什麽不同。
第三,政治塗鴉往往以人物、議題或事件為主,「佔中」的圖文基本上也圍繞這三個方面,特別是那些簡單的口號和圖像。它們的作者通常不詳,就像塗鴉客隱去真實姓名,留在公共空間的只是他們的作品,沒人知道他們來自何方,又往何處去。他們企圖的也許是種對話,卻非一對一的連續傳播,間接溝通的對象又不夠明朗,是官方、路人或媒體,還是志同道合之輩?塗鴉亦如是。
第四,塗鴉客的死對頭,是代表公權力的警察,這種情形在世界各國皆然,除非警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警察出現在特定公共空間時,如果不是防範塗鴉於未然,便意謂公權力受到有意或無意的削弱。從頭到尾,香港警方在「佔中」地區部署重兵,甚至還使用暴力對付示威者,在在說明公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緊張衝突,一如警察與塗鴉客之間的貓鼠遊戲。
當然,「佔中」參與者不會承認他們是塗鴉客,或所作所為是十足的塗鴉,更可能辯解以塗鴉形容「佔中」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訴求,是對神聖目標的褻瀆。也難怪佔領區出現「請勿塗鴉!如要張聲請用紙代替!」的警告(圖 1.1),看起來和街道電箱上「禁止塗鴉」的貼紙,沒什麽兩樣。其實,這是對塗鴉的誤解,以工具判定塗鴉,或認為塗鴉是在牆壁上隨意書寫,忽略了縱然使用紙張寫字,再貼上牆壁,它依舊是塗鴉。
由文字到圖像,「佔中」的塗鴉數量難以計算,但是質化上可以輕易歸類。
任何社會運動都免不了使用符號(Bennett, 1980),特別是簡潔易懂的圖文。以「佔中」為例,符號有兩種,一種是指示性的,直接了當,不帶情感或價值判斷,如有關「佔中」地點或街道指示牌的文字塗鴉;另一種是濃縮性的,充滿喜怒哀樂的感受或聳動情懷,如「雨傘革命」。在北京眼中,「革命」字眼不免觸目驚心(圖 1.2)。
不論是指示性或濃縮性符號,簡約的文字或圖像往往引人注目和深思。從金鐘、銅鑼灣到旺角,最常見的是與雨傘有關的貼紙或圖案,很多是即興創作,有些是刻意設計,相當具有想像力,幾乎是街頭藝術的展示。從廣義的角度看,若非合法,街頭藝術無疑也是塗鴉,尤其是以公共空間作為畫板。自始至終,「佔中」的場地全屬非法徵用。
這些符號很多是針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各種謾駡、詛咒、譏諷、醜化和調侃的圖文,張貼在牆壁上,到處可見,尤其是「奸狼」的形象,暗示他的奸詐狡猾,甚至還蓋棺論定。它們跟平常時的塗鴉如出一轍,數目卻多出千百倍,內容更加犀利惡毒。
在金鐘政府總部附近,只要是牆壁,幾乎貼滿了五顏六色的大小紙張,就像塗鴉客以貼紙在電箱、燈柱和牆壁上留下簽名一樣。每一張都代表一個心聲,臨時被命名的連儂牆,更是密密麻麻滿佈便條紙,清一色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追求,成為觀光景點,有如塗鴉世界的「名人堂」,吸引了不少遊客。
大部分時候,逛佔領區的人可能比示威的人還多。不少人都是來看熱鬧,還在標語或海報前拍照,表示到此一遊。一些聳動標語或大型的人頭像,如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戲謔或詼諧的方式呈現,往往讓人停下腳步觀看或合照,尤其是北方南下的中國遊客。在公共空間裏,這些政治塗鴉多少表示「一國兩制」的安排還保存了一點氣息。
「佔中」運動於 2014 年 12 月 15 日被政府強行清場後正式落幕,塗鴉的社會效應卻在整個香港擴大,其中以「我愛真普選」的標語最為突出。除了街道上的黃色小貼紙四處可見,幾個主要山頭,如獅子山,從 2014 年 10 月到 2015 年 2 月,也先後四次被掛上巨大的「我愛真普選」布條,從山頂垂直而下,場面壯觀(圖 1.3)。儘管布條都很快被拆除,這些業餘塗鴉客的膽識和舉動,已驚動四方和警方,比起2011年「誰怕艾未未?」塗鴉出現在香港街頭時引起的騷動,前後相互輝映。
「誰怕艾未未?」
艾未未是中國著名的行為藝術家與異議人士,2011 年 4 月 3 日,他準備搭機前往香港,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被公安帶走。艾未未被拘留後,中國官方雖然證實,但並未正式說明他犯了什麽罪,被拘押在哪裏。一些零星的消息指出,艾未未踩到當局的紅線,涉嫌經濟犯罪。45 天後,新華社於 5 月 20 日簡短指出,北京市公安機關「已初步查明,艾未未實際控制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繳納鉅額稅款、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等犯罪行為。」
根據媒體猜測,這項指控非常嚴重,艾未未恐怕難免刑責,只是輕重而已。2011 年 6 月 22 日艾未未被釋放,官方裁定他的設計公司必須繳付 1,500 萬人民幣(港幣 1,840 萬)的欠稅和罰款。艾未未不服上訴,但官方維持原判。一般認為,以逃稅入罪是對艾未未批評政府的處罰(《南華早報》,2012 年 3 月 30 日)。
有關艾未未被捕的新聞,中國媒體不是噤若寒蟬,就是口徑一致,輕描淡寫,堅持「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北京《環球時報》,2011 年 4 月 6 日社評)。
艾未未的特立獨行所以受到關注,一方面固然和他父親是紅色著名詩人艾青(蔣正涵)有關,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藝術內涵獨樹一格,表達方式又往往「語不驚人死不休」,作品曾在歐美幾個國家展出。2008 年他與瑞士建築事務所 Herzog & de Meuron 合作,擔任北京奧運會國家體育場「鳥巢」的藝術顧問,更是名噪一時。
艾未未被逮捕的消息傳到國外,引起很大的震驚和反響。歐美主要國家的政府、新聞媒體、國際知名美術館及人權組織都公開譴責中國罔顧人權與正當法律程序,要求釋放艾未未。許多團體和個人,包括旅居外國的中國人,也發起簽名運動,強烈支持艾未未。一件本是個人與國家對抗的行為遂演變成國際間的政治角力,在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以不同形式展現。
人間有公道,歷史自有定論。艾未未的是非功過與中國政府對抗異議分子的高壓手段,不是本書討論的重點。跟「佔中」運動一樣,艾未未被捕所引發的塗鴉效應倒是值得探討:一種結合街頭藝術與社會實踐的抵抗形式,在香港悄然登上舞台,延續這個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國際都市特有的文化格局。
國際上,自發性的抗議活動相繼成為新聞報導,香港雖然是中國特別行政區,在聲援艾未未方面,卻也不落人後,除了街頭的遊行示威,各種塗鴉作品如雨後春筍,出現在主要地區的街頭巷尾,此起彼落,以游擊戰的方式,與官方周旋。
從 2011 年 4 月初起,上環、中環、尖沙咀、銅鑼灣、旺角、深水埗、荃灣等幾個人口流動頻繁的地區,在人行道、天橋、隧道牆壁等公共場所,被噴上艾未未的圖像,以及「艾未未中國良心」及「誰怕艾未未」等字句。噴漆塗鴉因為面積小,不仔細留意,很可能擦身而過;人來人往,書寫在地面上的文字則相當醒目,行人的足跡過處,恐怕很難不惹起一點塵埃。
「誰怕艾未未?」真是大哉問。提問的人是誰,對警方來說,也許很重要,難怪非調查不可。對大多數人而言,更重要的,其實是問題的答案。
剛開始時,「誰怕艾未未?」的質問只出現在特定的少數公共場所,對象有限。透過新聞轉播,尤其是電視和網絡,沒親眼看過這五個字的人多少也知道問題的存在。「誰怕艾未未?」的塗鴉遂轉化成公共空間裏的一個考題,針對所有人。這個問題隱含兩個層面:其一,到底是哪些人聞艾未未而色變?其二,艾未未這個人有什麽可怕?
第一個層面牽涉廣泛,又取決於第二個層面如何界定,兩者牽涉的是個人麻煩或社會問題的判別。艾未未是否可怕?從北京到香港,由中國到國外,基本上這是個政治或思想問題,北京當局卻尋求法律解決,即使惡法亦法,依法治理,而非因循合理的正義程序,以法治理。一旦成立,艾未未的逃稅行為就提供官方一個正當的掩護,孰是孰非,便很難理出個黑白分明的判別。
青史不會盡成灰,「誰怕艾未未」與為什麽怕的問題,遲早要理出個頭緒。不過,怕艾未未的人可能還真的不少。在香港,只是街頭上一些零星的塗鴉(圖 1.4),就弄得風吹草動,讓警方疲於奔命。香港塗鴉藝術先驅陳廣仁(MC 仁,見第八章)認為官方「真係大驚小怪咗」(《蘋果日報》,2011 年 4 月 15 日,頁 A02)。一般塗鴉或許不至於如此勞師動眾,畫上艾未未顯然非同小可了。
香港警方越是大費周章,兵分四路,到處湮滅這些帶有「犯上」的圖案或文字,以塗鴉作為政治抗議的一些社會行動家就越起勁,因為這是製造新聞的絕佳機會。原本只是在固定地區的一個特例,可以像 2006 年的科幻懸疑電影《V怪客》(V for Vendetta)裏戴着面具的獨行自由鬥士一樣,經過傳播,而引發出戴着同樣面具的無數自由鬥士,真假難分。
2011年4月間,以「塗鴉少女」為代號的塗鴉客於香港國金中心和星光大道等十多個地區留下「誰在害怕艾未未」的噴漆塗鴉後,更多的大小塗鴉,接踵出現。4月15 日 CNN 報導後,整個事件因而成為國際新聞,塗鴉或許只是引言,香港警方欲蓋彌彰,還貽笑大方。《蘋果日報》4月16 日,以〈人人都是艾未未〉為標題的新聞,就傳神的點出「V怪客」自由鬥士在香港的翻版。
「塗鴉少女」的塗鴉顯然不是出自一時魯莽或衝動,而是一番深思熟慮後良知的召喚,從她接受《塗鴉》(鄺穎萱,2011,頁 61)一書訪問的一段話可見一斑:
我認為一個良好公民的價值不在於盲目服從。我們不是被動地被法律支配,每人都是一個有理性的主體,正因為尊重法治精神,我們才如斯尋根問底,反思不同法例的出發點到底合理與否,追問公義到底是誰的公義。
短短幾句話,卻擲地有聲。「塗鴉少女」為「誰在害怕艾未未」的塗鴉提供了一個官逼民反的立足點,談的其實並非塗鴉,而是公民社會裏理性參與言論自由表達的重要。許多人,包括官方和建制派,只看到了塗鴉的表像,對她的提問充耳不聞。「塗鴉少女」其實可以不用辯解,當《蘋果日報》說「人人都是艾未未」時,民心何在,不辨自明,有關艾未未塗鴉背後的深沉問題,也就不能等閒視之。
由社會學理論和現實的角度看,名字或形象與所指涉的物體之間,有一段隔閡,沒有百分之一百的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人與事物之間的關係,也因情境不同,距離遠近,位置所在,而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巨大差異。艾未未塗鴉造成的社會效應,因此不能光從公共空間被破壞的立場切入。
在北京,艾未未是個眼中釘,不除不快。在香港,艾未未塗鴉是個礙眼的東西,不去不淨。艾未未不過是遭受國家機器相同處置的萬千中國人之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以內政為由,要外國人「閉嘴」(《南華早報》,2011 年 5 月 6 日),好歹說得理直氣壯。在特區,艾未未塗鴉頂多是個觸動政治神經的街頭圖像,官方擺出強硬姿態,顯然也要塗鴉客「封口」。
面對這些帶有政治意味的塗鴉,香港警方如臨大敵,將案件列為「刑事毀壞案」,交由重案組調查處理。《明報》譏諷為「以炮彈打蒼蠅」(2011 年 5 月 2 日社評,頁 A04),並不為過。殺雞用牛刀,總是荒唐。警方的動作倒也俐落,大部分較為引人注目的文字塗鴉都在短時間內被清洗乾淨。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關艾未未的塗鴉,以文字、噴漆或貼紙,自動在街道上到處出現,讓警方分身乏術。最特別的是,以光影將艾未未的圖形和文字,投像到主要建築物的牆面,包括駐香港解放軍總部的外牆,不留任何痕跡。塗鴉與科技結合,既達到目的,又不破壞公共空間,警方也就難以下手。
雷聲大雨點小,香港警方固然以刑事案件處理這些艾未未塗鴉,重案組倒也沒逮捕任何塗鴉客,即使抓一、兩個人殺雞儆猴,最後頂多罰款了事,甚至不了了之。塗鴉,固然礙眼,到底不至於罪無可赦,嚴重到必須如艾未未遭受牢獄之災或承擔巨額罰款。
就算官方不剷除,存留在天橋橋墩、路面或牆壁上的任何塗鴉,不論是臨時起意或蓄意而為,長年累月的任憑風吹雨打,腳步踩過,終究會隨時間消逝而逐漸褪色,慢慢被淡忘,以致消失在人們的記憶裏,尤其是集體記憶。少數得以保留較久的,大多數人將視而不見,或見怪不怪,不會引發太多情緒性或回顧的反應。「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塗鴉應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