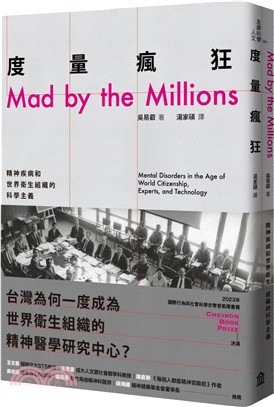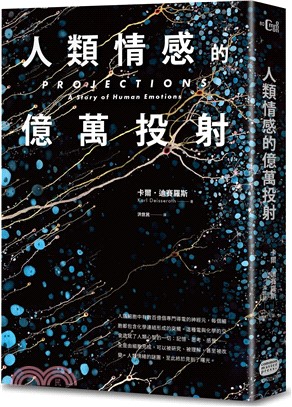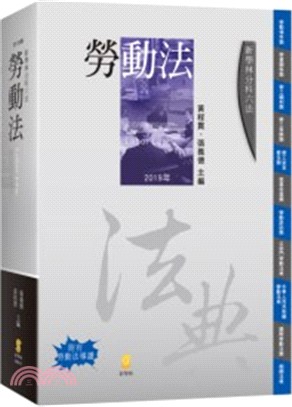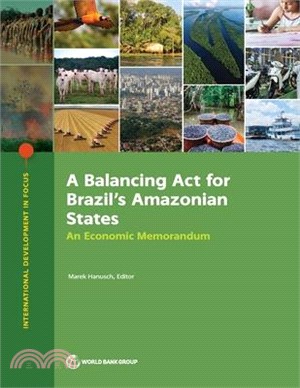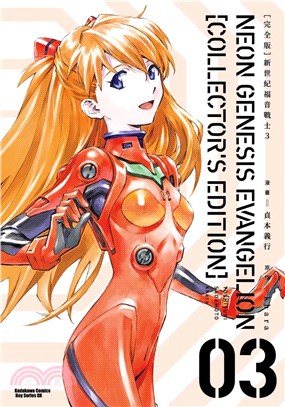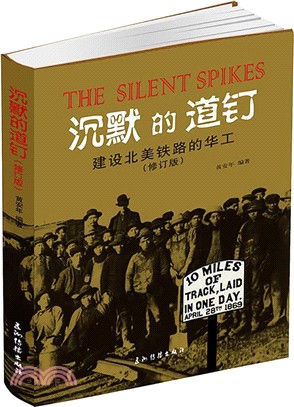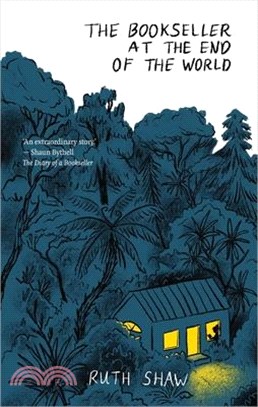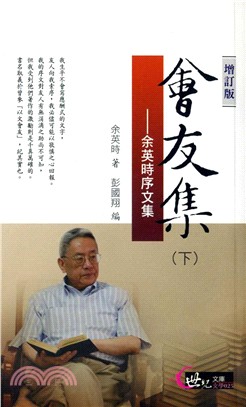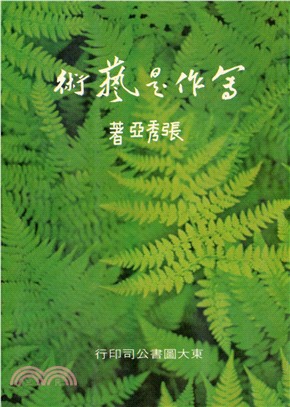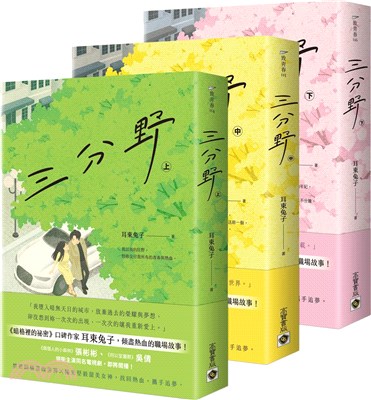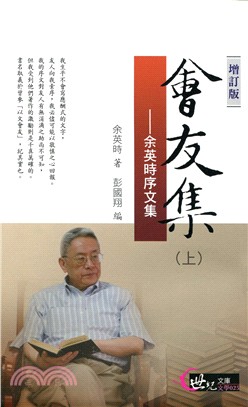度量瘋狂:精神疾病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主義
商品資訊
系列名:左岸科學人文
ISBN13:9786267462218
替代書名:Mad by the Millions: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Age of World Citizenship, Experts, and Technology
出版社:左岸文化
作者:吳易叡
譯者:湯家碩
出版日:2024/10/23
裝訂/頁數:平裝/352頁
規格:21cm*14.8cm*1.8cm (高/寬/厚)
商品簡介
◉台灣為何一度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2023年國際行為與社會科學史學會凱隆書獎(Cheiron Book Prize)決選
二次大戰後,和平降臨,隨著「世界公民」理念的興起,「如何衡量人類集體的心理健康?」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願景,伴隨科學與技術的創新、人員組織的新設計、各式資金的啟用,以及理論層次上的反省,逐漸落實成形。
在這個跨國、跨專業的全球冷戰網絡裡,台灣人林宗義醫師扮演了關鍵的重要角色。他是誰?為何有能力擔任主持精神醫學計畫的大任?冷戰的地緣政治因素如何影響此全球計畫的進展?專家(精神科醫師、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流行病學家……)如何協商出全球普世性的標準,同時又能涵納多元文化價值?什麼樣的組織設計,才能有利各國合作?成就了什麼,又失落了什麼?這段歷史又如何引領出當今精神醫學、全球公衛的樣態?
作者身體力行,進行地理大尺度的跨國檔案追尋,從檔案文獻、會議紀錄、醫學論著及口訪資料,一步步拼湊出這段歷史的軌跡。前半部從世界衛生組織出發,後半部從台灣角度重新出發,「雙向書寫」世界衛生組織運行的面貌,描繪「中心」與「地方」的互動,期許台灣成為一種方法學。
作者簡介
吳易叡
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醫學系醫學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合聘)任教,曾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香港大學任職數年。目前研究聚焦於精神醫療的跨國史與全球衛生、醫療外交史。業餘從事藝文創作,著有詩集《島嶼寄生》(春暉,2005)、散文集《赤道上的極地:新加坡微民族誌》(行人,2011),目前也致力於台灣文學的音樂轉譯。
譯者簡介
湯家碩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Amsterdam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健康、照護與身體研究群」(Health, Care and the Boday Program Group)博士候選人。主要興趣為健康、資料、數位科技與跨國治理。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人
王秀雲 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教授
王文基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特聘教授
吳佳璇 遠東聯合診所身心科主治醫師,作家
吳易澄 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
胡海國 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名譽教授、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陳嘉新《每個人都是精神官能症》作者、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精神/心理疾病是否放諸四海皆同?這個問題涉及了不同文化有關正常與異常的分野、精神疾病如何比較、測量與分類,甚至可擴及至全球性地改善精神衛生如何可能。要回答這組問題並發展出行動方案,是一大挑戰。本書《度量瘋狂》是關於戰後的世界衛生組織(WHO)中的科學家與精神科醫師在「世界公民」、「去殖民」的理念與全球化的企圖下,所進行的相關研究與行動。書中提供了豐富精彩的歷史案例,引人入勝。例如,疾病分類無疑是全球標準化的關鍵。在戰後統計技術的發展下,分類系統的修改(ICD,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是重要的工程。本書的原文版已為跨國精神醫學史及國際組織史開拓新的議題與方向,引起不少的關注與好評,中譯本的問世將能進一步擴大社群,引發討論,進而深化我們對相關議題的歷史性理解。——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教授)
迄今關於精神醫學診斷的歷史,大多從藥商利益、生物精神醫學的興起、病患經驗與身分如何重新形塑等角度切入。《度量瘋狂》相當細緻且全面地剖析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代,世界衛生組織附屬的精神疾病相關研究團體,如何在二戰之後「去殖民」及「世界公民」的理想下,在西方與非西方世界推動跨國的精神疾病研究。除了梳理當時此項研究的時代背景及地緣政治,吳易叡教授十分精闢地描繪該研究團隊的組織文化、內在的張力、特殊的知識分工型態(跨國企業加上外包制的加工出口區),以及運用的各項研究技術。在紀錄與分析精神醫學專家的研究活動時,作者特別著重「標準化」的診斷系統是如何形成。對台灣讀者而言,書中關於林宗義醫師的篇章,清楚呈現當時非西方社會的知識菁英如何在困境與機會交織的夾縫中,在國際學界找到一席之地,甚至發揮不小的影響力。此外,不同於其他論著對精神醫學發展較為單向與直白的批評,《度量瘋狂》除了凸顯相關研究人員崇高的理想,也點出該跨國研究計畫乃至一般國際團體內存的矛盾與盲點,極具洞見。《度量瘋狂》使用大量檔案文獻,醫學論著及口訪資料,視野宏大,分析縝密,為晚近醫學史、科學史及科技研究(science studies)的力作。——王文基(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特聘教授)
《度量瘋狂》爬梳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50~1970年代,從全球各地召集了一群關注心理衛生的精神科醫師、社會學家與人類學者,本著樂觀、且近乎浪漫的世界公民與國際科學主義精神,推展精神醫學診斷標準化的工作。
身為21世紀的台灣精神科醫師,或多或少都聽過前輩們積極參與WHO的事蹟,尤其是第一任心理衛生工作小組召集人林宗義教授的種種傳奇。如果沒有吳易叡的研究,再現他們的身影與學思歷程,青史幾已成灰。
雖然作者批判世界衛生組織總部的運作方式像一家公司,參與的會員國則像加工出口區,並質疑標準化診斷工具的產出過程,淡化了文化差異與忽略了冷戰脈絡,卻又從他稱這群學者「夢景」團隊,感受到作者的溫柔。——吳佳璇(遠東聯合診所身心科主治醫師,作家)
「醫學」是相當晚熟的「科學」;對比於醫學各領域的發展史中,「精神醫學」更難以科學之姿立足,如今卻也成為主流的助人工具,這個過程絕非偶然。《度量瘋狂》爬梳了精神醫學的近代發展過程;相較於專注在某些特定疾病或治療技術的演變,本書所探究的問題在於精神醫學如何在戰後人類歷經了巨大的衝擊後,在既是命定般又不失巧合的前提下,逐漸長成我們當今所熟悉的樣貌。在全球社會多元的地緣政治因素與文化脈絡下,人們的心智狀態是否是能夠相互翻譯並被理解呢?這段歷史挑戰了科學史中所謂典範之不可共量性的預設,也讓我們看見過程中不同專業領域的行動者如何並肩合作,抑或分道揚鑣的軌跡。
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從全球的視野下思索台灣。在當代全球政治氛圍中,往往被全球衛生官僚組織排除在外的台灣,曾經卻是至關重要的參與者;這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呢?唯有讓歷史說話才能明朗。如果說科學技術往往是在實驗室中誕生,《度量瘋狂》則是一本另類的實驗室史,而這個實驗室是以全球之規模尺度來運作。作者吳易叡透過豐富的史料,包括實驗檔案、書信文件、會議記錄等,企圖勾勒出這段充滿迂迴跌宕的精采敘事,值得當代精神醫學、公共衛生與全球醫療的實踐者與研究者細細品味。——吳易澄(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
吳易叡博士立足台灣,在此世界精神醫學翻轉的世代,竭盡所能地,由歷史學、社會學、與文化的觀點,審視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精神醫學在人與事的交互運作,獲得精彩而深邃的成果,這是《度量瘋狂》這本書最珍貴之處,它整理過去精神醫學的混淆,開啓對現下精神醫學的瞭解與掌握,助益台灣當代醫學精神醫學發展與大衆化。當代精神醫學以「腦與人生交相互動」的精神發展為主軸,它整合「家庭、社會、文化、心理、腦結構與基因-體質等多面向元素」,融入一個人由少而老的精神發展歷程。負向的精神發展,經由神經可塑性原理,構建了缺乏適應效率的神經廻路,形成腦結構與功能障礙,造就了精神疾病的精神病理。因此,以精神發展為本的精神醫學診斷與對應的精神醫療(含生物學治療與精神會談治療),既重「精神狀態的度量」,也強調精神內涵「主觀與直觀」的心理、家庭、社會、文化內涵。如此,開創了未來「開展性與常態性(非革命性)」的精神醫學。因此《度量瘋狂》這本書,引導大眾掌握舊時代精神醫學在理論與實務的混淆狀況,進而鋪陳了現代精神醫學發展的方向。我鄭重推薦這本書寫世界精神醫學史七十年的書,它具有顯著而重要的參考價值。——胡海國(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名譽教授、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度量瘋狂:精神疾病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主義》處理了二戰後世界精神醫學史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與其會員國當中的醫療菁英,如何建構出一套共通的精神醫療語言與相互理解架構;且以之作為基礎建設,讓相關的研究、政策、跨國網絡的國際合作得以可能。作者點出了這個龐大的國際社會精神醫學計畫如何與世界公民身分的理念相互交織,而台灣又是如何在這個跨國計畫的開展中嶄露頭角。本書章節結構井然,使用材料非常廣泛。雖然描述的對象是歷史事件、人物、組織與行動策略,但對於當前學術與實務界的關切,也非常貼合。對於醫療史、全球史、精神醫學、科技研究感興趣的人,這本著作都是絕對不可錯過的傑作。——陳嘉新(《每個人都是精神官能症》作者、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作者撰寫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跨國精神病學史。——馬修.史密斯(Matthew Smith),斯特拉思克萊德大學健康與照護社會史研究中心健康史教授
在這部力作中,作者探討了一群有抱負的專業人士如何受到平等主義和世界公民身份的烏托邦承諾驅使,因爲新成立的世界衛生組織而聚在一起,共同發展出了舉世首創、統一的精神疾病分類系統。——漢斯.波爾斯(Hans Pols),雪梨大學歷史與科學哲學學院教授,《為印尼給養》(Nurturing Indonesia)作者
這本書展現了眾人嘗試在全球層級打造統一的精神病學語言的過程,非常具有說服力。這個過程又如何與二戰後更廣泛的「重新定義世界公民身份」社會脈絡息息相關。本書提供我們所急需的歷史背景,有助理解當今全球心理健康相關討論。——安娜.安蒂克(Ana Antic),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治療法西斯主義》(Therapeutic Fascism)作者
序
迄今關於精神醫學診斷的歷史,大多從藥商利益、生物精神醫學的興起、病患經驗與身分如何重新形塑等角度切入。《度量瘋狂》相當細緻且全面地剖析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代,世界衛生組織附屬的精神疾病相關研究團體,如何在二戰之後「去殖民」及「世界公民」的理想下,在西方與非西方世界推動跨國的精神疾病研究。除了梳理當時此項研究的時代背景及地緣政治,吳易叡教授十分精闢地描繪該研究團隊的組織文化、內在的張力、特殊的知識分工型態(跨國企業加上外包制的加工出口區),以及運用的各項研究技術。在紀錄與分析精神醫學專家的研究活動時,作者特別著重「標準化」的診斷系統是如何形成。對台灣讀者而言,書中關於林宗義醫師的篇章,清楚呈現當時非西方社會的知識菁英如何在困境與機會交織的夾縫中,在國際學界找到一席之地,甚至發揮不小的影響力。此外,不同於其他論著對精神醫學發展較為單向與直白的批評,《度量瘋狂》除了凸顯相關研究人員崇高的理想,也點出該跨國研究計畫乃至一般國際團體內存的矛盾與盲點,極具洞見。《度量瘋狂》使用大量檔案文獻,醫學論著及口訪資料,視野宏大,分析縝密,為晚近醫學史、科學史及科技研究(science studies)的力作。——王文基(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特聘教授)
《度量瘋狂》爬梳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50~1970年代,從全球各地召集了一群關注心理衛生的精神科醫師、社會學家與人類學者,本著樂觀、且近乎浪漫的世界公民與國際科學主義精神,推展精神醫學診斷標準化的工作。
身為21世紀的台灣精神科醫師,或多或少都聽過前輩們積極參與WHO的事蹟,尤其是第一任心理衛生工作小組召集人林宗義教授的種種傳奇。如果沒有吳易叡的研究,再現他們的身影與學思歷程,青史幾已成灰。
雖然作者批判世界衛生組織總部的運作方式像一家公司,參與的會員國則像加工出口區,並質疑標準化診斷工具的產出過程,淡化了文化差異與忽略了冷戰脈絡,卻又從他稱這群學者「夢景」團隊,感受到作者的溫柔。——吳佳璇(遠東聯合診所身心科主治醫師,作家)
「醫學」是相當晚熟的「科學」;對比於醫學各領域的發展史中,「精神醫學」更難以科學之姿立足,如今卻也成為主流的助人工具,這個過程絕非偶然。《度量瘋狂》爬梳了精神醫學的近代發展過程;相較於專注在某些特定疾病或治療技術的演變,本書所探究的問題在於精神醫學如何在戰後人類歷經了巨大的衝擊後,在既是命定般又不失巧合的前提下,逐漸長成我們當今所熟悉的樣貌。在全球社會多元的地緣政治因素與文化脈絡下,人們的心智狀態是否是能夠相互翻譯並被理解呢?這段歷史挑戰了科學史中所謂典範之不可共量性的預設,也讓我們看見過程中不同專業領域的行動者如何並肩合作,抑或分道揚鑣的軌跡。
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從全球的視野下思索台灣。在當代全球政治氛圍中,往往被全球衛生官僚組織排除在外的台灣,曾經卻是至關重要的參與者;這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呢?唯有讓歷史說話才能明朗。如果說科學技術往往在是在實驗室中誕生,《度量瘋狂》則是一本另類的實驗室史,而這個實驗室是以全球之規模尺度來運作。作者吳易叡透過豐富的史料,包括實驗檔案、書信文件、會議記錄等,企圖勾勒出這段充滿迂迴跌宕的精采敘事,值得當代精神醫學、公共衛生與全球醫療的實踐者與研究者細細品味。——吳易澄(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
吳易叡博士立足台灣,在此世界精神醫學翻轉的世代,竭盡所能地,由歷史學、社會學、與文化的觀點,審視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精神醫學在人與事的交互運作,獲得精彩而深邃的成果,這是《度量瘋狂》這本書最珍貴之處,它整理過去精神醫學的混淆,開啓對現下精神醫學的瞭解與掌握,助益台灣當代醫學精神醫學發展與大衆化。當代精神醫學以「腦與人生交相互動」的精神發展為主軸,它整合「家庭、社會、文化、心理、腦結構與基因-體質等多面向元素」,融入一個人由少而老的精神發展歷程。負向的精神發展,經由神經可塑性原理,構建了缺乏適應效率的神經廻路,形成腦結構與功能障礙,造就了精神疾病的精神病理。因此,以精神發展為本的精神醫學診斷與對應的精神醫療(含生物學治療與精神會談治療),既重「精神狀態的度量」,也強調精神內涵「主觀與直觀」的心理、家庭、社會、文化內涵。如此,開創了未來「開展性與常態性(非革命性)」的精神醫學。因此《度量瘋狂》這本書,引導大眾掌握舊時代精神醫學在理論與實務的混淆狀況,進而鋪陳了現代精神醫學發展的方向。我鄭重推薦這本歷經七十年世界精神醫學史《度量瘋狂》的書,它具有顯著而重要參考價值。——胡海國(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名譽教授、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度量瘋狂:精神疾病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主義》處理了二戰後世界精神醫學史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與其會員國當中的醫療菁英,如何建構出一套共通的精神醫療語言與相互理解架構;且以之作為基礎建設,讓相關的研究、政策、跨國網絡的國際合作得以可能。作者點出了這個龐大的國際社會精神醫學計畫如何與世界公民身分的理念相互交織,而台灣又是如何在這個跨國計畫的開展中嶄露頭角。本書章節結構井然,使用材料非常廣泛。雖然描述的對象是歷史事件、人物、組織與行動策略,但對於當前學術與實務界的關切,也非常貼合。對於醫療史、全球史、精神醫學、科技研究感興趣的人,這本著作都是絕對不可錯過的傑作。——陳嘉新,《每個人都是精神官能症》作者、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作者撰寫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跨國精神病學史。——馬修.史密斯(Matthew Smith),斯特拉思克萊德大學健康與照護社會史研究中心健康史教授
在這部力作中,作者探討了一群有抱負的專業人士如何受到平等主義和世界公民身份的烏托邦承諾驅使,因爲新成立的世界衛生組織而聚在一起,共同發展出了舉世首創、統一的精神疾病分類系統。——漢斯.波爾斯(Hans Pols),雪梨大學歷史與科學哲學學院教授,《為印尼給養》(Nurturing Indonesia)作者
這本書展現了眾人嘗試在全球層級打造統一的精神病學語言的過程,非常具有說服力。這個過程又如何與二戰後更廣泛的「重新定義世界公民身份」社會脈絡息息相關。本書提供我們所急需的歷史背景,有助理解當今全球心理健康相關討論。——安娜.安蒂克(Ana Antic),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治療法西斯主義》(Therapeutic Fascism)作者
【小標】中文版序:在世界舞台節點重新思索全球衛生與文化
很難想像這本書的完成,從預計改寫一篇期刊文章、重新搜集資料到成為《度量瘋狂》,必須花上八年的時間,其中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到瑞士、英國、美國進行跨國的檔案研究。由於先前有幸任職於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出入境相對方便且省時的機場城市,讓我得以進行大跨度的移動。在成書之後,也才發現如此大規模的專書計畫如同這本書所關注的國際研究計畫,是多麼讓人筋疲力盡。的確,世界衛生組織在七○年代中期之後,就不曾再進行如此豪華的比較研究;歷史研究者慣於獨來獨往,也不可能複製世界衛生組織早期醫療官員團隊曾踏過的足跡。進入廿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研究贊助機構也因為環境責任之故,不再支持碳排量如此高的旅行。因此這本書不論從研究對象或是研究的執行方式來看,大概都是空前絕後。
投入學術生涯的十多年期間,所有的關切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台灣在全球衛生中的位置是什麼?這本書試圖透過一則東亞案例處理「世界主義」和「地方觀點」在各種研究和教案中的理解缺漏。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台灣代表了什麼關鍵性或從來只是位於邊陲?我用一個很「偏門」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也到了許多人跡罕至之處,先從日內瓦出發描述一個全球心理衛生計畫的開端;再從台灣出發,反向細寫曾經被視為「待開發」的「國家」如何面對世界衛生組織所想像出來的世界。我所理解的──至少針對廿世紀後半葉的醫藥衛生而言──全球化從來不是擴散,而是「全球」與「地方」在不同脈絡中互相撞擊、融合,同時又相互牴觸、拒斥的動態過程。台灣退出了聯合國之外,並未消失於世界版圖,真正消聲匿跡的,是書中所描述的,讓初代世界衛生組織放手一搏的片面理想性。
而這本書的結論或許會讓不少讀者失望。期待看到「國際衛生霸權」的讀者,可能會讀到我對於背後有著科學國際主義和人權概念撐腰的組織,在戰後的斷垣殘壁之中,卻充滿樂觀和人道情懷的讚譽;期待讀到「台灣之光」的讀者,可能會意外我用「世界標準的加工出口區」來評價這個長年被打壓,千山獨行的小國。在本書出版的前後,有許多關於世界衛生組織本身以及全球衛生的歷史書籍問世,但還沒有其他作者嘗試這種「雙向書寫」,因此我希望這個強調機構中心與地方互動的過程,成為研究國際組織的一種路徑;甚至這個案例的特殊性,也能讓「台灣」成為一種方法學。尤其在疫情期間不斷透露#TaiwanCanHelp,可以用口罩「伸出援手」的小國,似乎必須經過全面的歷史追索,才能參透其歷史意義。
而比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更重要的,是本書的科學史分析。過在科學史或是科學、技術與社會(STS)領域中,關於科學概念的形塑、科學方法的建構,都扣緊著實驗室作為理論和實作誕生的空間。但本書所探討的是精神流行病學成為精神醫學的主流研究方法,在跨國田野中,在機構之外一一探頭出來的契機。在本書中,整顆地球就是一個實驗室,六大章的主題便是構成世界衛生組織跨國研究的行動者。而台灣,就是這個變化中的世界舞台的節點。交給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時,原本的標題為《群瘋:全球公民、專家和科技時代中的精神疾病》。主標題「Mad by the Millions」,是對佛洛姆描述戰後傾圮社會狀態「folie à millions」的致敬。後來副標題則是由出版社編輯建議,順應疫情期間人們對於世界衛生組織功能不彰的關注,才成為「精神疾病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早年歲月」。很感謝左岸出版社的林巧玲編輯,為中文版找到了一個更鏗鏘有力的書名,完整捕捉了這則複雜故事的精髓。
由於深怕許多關於台灣的資料對於英文讀者不甚熟悉,因此撰寫過程中加入了不少介紹性質的段落。但在譯本之中依然將這些段落完整保存,以維持原書的完整性,同時也能讓台灣的讀者了解原著所設定與目標讀者的溝通方式。也為了更適切台灣讀者閱讀,加入了數則校注,但以不更動原書內容為原則。同時,由於這本書所處理的軸線繁瑣,想讓每一章都能夠獨立閱讀,因此會想辦法將前一章所出現過的表達,在後一章以換句話說的形式重新敘述或解釋。此外,中文譯本出現了不少在英文書中不需處理的翻譯難題,最主要是不同的專有名詞在兩岸三地不同歷史時空中呈現的詞彙。比如:譯文中的「schizophrenia」採用的是台灣衛福部在二○一四年所更換的病名「思覺失調症」,以便台灣的讀者閱讀。這個病名目前在香港和中國仍保留「精神分裂症」的稱呼。「psychosis」在本書中為「精神病症狀」,在香港則為「思覺失調」;「mental health」為「心理衛生」,「mental illness」「psychiatric disorder」則都是「精神疾病」。在台灣慣用的「憂鬱」,若出現在描寫中國的脈絡中則會置換成「抑鬱」。
值得一題的是,這本書在英文版的送印期間,一位日本的神經科學研究員捎信來表示讀了我的早期的一些論文後找到了我。他想要跟我討論「対人恐怖症(たいじんきょうふしょう)」。這是一個似乎只存在於日本文化裡的文化依存症候群。這種對於社交產生高度恐懼的症候群,似乎已經透過了新興病毒而全球化。而且他宣稱找到了中樞神經影像學的證據。後來我們甚至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由於全球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遷,甚至大規模疫病的影響,精神科的診斷分類可能會重新洗牌。於此同時,與我同時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書的公共衛生學者Eugene Richardson借用奈及利亞作家奇努阿.阿切貝(Chinua Achebe)的描述,將世界衛生組織形容為「日內瓦湖畔的原始部落」,暗示其中的科學家在塑造「全球衛生」實踐中所抱持的願景和價值觀。他開玩笑指出,世界衛生組織文化的特色是一種「gnihsup-repap(paper pushing,官僚文書作業的反向拼寫)」活動」。他們每天花許多時間在電腦前例行公事,但真正發生危機時卻無法採取果斷的行動。而位於「節點」的台灣呢?曾經身為執精神流行病學研究牛耳的先驅—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轉而強調「全球心理健康(Global Mental Health)」時,從來就沒有參與此類後續討論,但已經站上「新南向政策」高點,以先進之國的姿態輔導東南亞,現在的角色又在哪裡?能夠自外於鬆綁診斷標準、與民俗醫療攜手合作的呼籲之外嗎?會不會又複製了當年世界衛生組織南北發展的失準邏輯?這些都是這本書所關切的內容,能夠往後延伸討論的主題。
這本書在COVID-19的疫情期間付梓,出版後也由於各國的旅遊限制尚未解除,並沒有進行原先預計的宣傳。但也因為疫情,使得我得以重新思考這本書的構成,在許多線上發表會和討論會中,有幸得以和世界各地的學者交換意見,並開始往前鑽研這個故事的史前史,同時也思索這本書帶來的臨床意義。把時間點往前挪,我追索東亞精神流行病學的殖民開端,和當前存留的殖民性;另外,我也已經開始著手整理台灣的醫療外交史。除了原書的致謝名單之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在銜接兩份工作時,香港大學Vivian Lin、林佳靜、Danny Chan、前世界衛生助理總幹事福田敬二幾位教授的餐敘時光,以及回到台灣之後,國立成功大學賴明德教授、全校不分系與醫學系人社科同仁的啟發與支持、研究室助理翁伊珊、王政中的各種協助,王文基教授在校訂過程中的珍貴提醒,以及我的「鬥鬧熱走唱隊」樂團夥伴們的心靈陪伴。當然,還有翻譯的健筆湯家碩和前一段提到的巧玲,因為要處理一本涵蓋大量專有名詞,而且牽涉不同時空脈絡的語言問題,是相當耗神的。書中如還有錯誤,一概由筆者負責。最後還是要再次感謝我的家人們,尤其是不斷與我交換靈感和意見,也再度攜手在不同作品中成為共同作者的胞兄,也是醫療人類學者吳易澄。在這本書中,人類學者在世界衛生組織計劃的中途曾經悻悻然離開,卻又在廿世紀的最後十年回來。易澄讓我理解到歷史和人類學對話的重要性,和合作的可能。我們的攜手戰鬥才正要開始。
目次
中文版作者序
第一章 前言:共同的願景
曇花一現的國際願景/置疑全球衛生史/章節概覽
第二章 結構
戰爭的教訓/心理衛生成為公共衛生/心理衛生的早期實踐與「世界衛生組織模式」/一九四八年的心理衛生大會/從同床異夢到實踐合作/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新心理衛生議題/可行的計畫以及「四人小組」/從彼此妨礙到彼此合作:民族誌研究取徑/國際團隊的誕生
第三章 方法
對於共同語言的需求/美國國家心理衛生院/世界衛生組織的星探以及他們的跨國之行/一九六一:世界心理衛生聯盟與世界心理衛生年/尋求來自邊陲地帶的貢獻/「共通語言」計畫的付諸實現/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社會精神醫學計畫」的重要性
第四章 專家
非洲與拉丁美洲/台灣:一位理想的枕邊人/一段並不完整的去殖民過程/「中國」作為科學中的他者/台灣:一個用於理解「中國人」的實驗場/專家們的「夢景」/僅存在想像中的對等立場
第五章 科技
打造國際主義/分類做為一種達成標準化的手段/資訊科技/標準化診斷工具/翻譯、語言、與誤解:PSE 所存在的問題/一個具有實業性格的領導者/科技所帶來的承諾/使用錄影帶進行記錄/資料管理的科技/計算機軟體/對科技的疑惑/中立性的錯覺
第六章 不滿
因應內部爭議而提出的各種方法/分類謬誤以降/在兩個「中國」所發展的精神醫學/用於達成世界性標準的工具與其生產過程/「依存於文化」的 ICD/在全球各地移動的專家們/同一世界,多樣文化?
結語:回歸到基質
鴻溝的起源/心理衛生標準的未來:未見分曉/傾聽過去的迴響
書摘/試閱
【作者中文版序】
【第一章(節錄)】
【小標】中文版序:在世界舞台節點重新思索全球衛生與文化
很難想像這本書的完成,從預計改寫一篇期刊文章、重新搜集資料到成為《度量瘋狂》,必須花上八年的時間,其中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到瑞士、英國、美國進行跨國的檔案研究。由於先前有幸任職於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出入境相對方便且省時的機場城市,讓我得以進行大跨度的移動。在成書之後,也才發現如此大規模的專書計畫如同這本書所關注的國際研究計畫,是多麼讓人筋疲力盡。的確,世界衛生組織在七○年代中期之後,就不曾再進行如此豪華的比較研究;歷史研究者慣於獨來獨往,也不可能複製世界衛生組織早期醫療官員團隊曾踏過的足跡。進入廿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研究贊助機構也因為環境責任之故,不再支持碳排量如此高的旅行。因此這本書不論從研究對象或是研究的執行方式來看,大概都是空前絕後。
投入學術生涯的十多年期間,所有的關切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台灣在全球衛生中的位置是什麼?這本書試圖透過一則東亞案例處理「世界主義」和「地方觀點」在各種研究和教案中的理解缺漏。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台灣代表了什麼關鍵性或從來只是位於邊陲?我用一個很「偏門」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也到了許多人跡罕至之處,先從日內瓦出發描述一個全球心理衛生計畫的開端;再從台灣出發,反向細寫曾經被視為「待開發」的「國家」如何面對世界衛生組織所想像出來的世界。我所理解的──至少針對廿世紀後半葉的醫藥衛生而言──全球化從來不是擴散,而是「全球」與「地方」在不同脈絡中互相撞擊、融合,同時又相互牴觸、拒斥的動態過程。台灣退出了聯合國之外,並未消失於世界版圖,真正消聲匿跡的,是書中所描述的,讓初代世界衛生組織放手一搏的片面理想性。
而這本書的結論或許會讓不少讀者失望。期待看到「國際衛生霸權」的讀者,可能會讀到我對於背後有著科學國際主義和人權概念撐腰的組織,在戰後的斷垣殘壁之中,卻充滿樂觀和人道情懷的讚譽;期待讀到「台灣之光」的讀者,可能會意外我用「世界標準的加工出口區」來評價這個長年被打壓,千山獨行的小國。在本書出版的前後,有許多關於世界衛生組織本身以及全球衛生的歷史書籍問世,但還沒有其他作者嘗試這種「雙向書寫」,因此我希望這個強調機構中心與地方互動的過程,成為研究國際組織的一種路徑;甚至這個案例的特殊性,也能讓「台灣」成為一種方法學。尤其在疫情期間不斷透露#TaiwanCanHelp,可以用口罩「伸出援手」的小國,似乎必須經過全面的歷史追索,才能參透其歷史意義。
而比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更重要的,是本書的科學史分析。過在科學史或是科學、技術與社會(STS)領域中,關於科學概念的形塑、科學方法的建構,都扣緊著實驗室作為理論和實作誕生的空間。但本書所探討的是精神流行病學成為精神醫學的主流研究方法,在跨國田野中,在機構之外一一探頭出來的契機。在本書中,整顆地球就是一個實驗室,六大章的主題便是構成世界衛生組織跨國研究的行動者。而台灣,就是這個變化中的世界舞台的節點。交給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時,原本的標題為《群瘋:全球公民、專家和科技時代中的精神疾病》。主標題「Mad by the Millions」,是對佛洛姆描述戰後傾圮社會狀態「folie à millions」的致敬。後來副標題則是由出版社編輯建議,順應疫情期間人們對於世界衛生組織功能不彰的關注,才成為「精神疾病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早年歲月」。很感謝左岸出版社的林巧玲編輯,為中文版找到了一個更鏗鏘有力的書名,完整捕捉了這則複雜故事的精髓。
由於深怕許多關於台灣的資料對於英文讀者不甚熟悉,因此撰寫過程中加入了不少介紹性質的段落。但在譯本之中依然將這些段落完整保存,以維持原書的完整性,同時也能讓台灣的讀者了解原著所設定與目標讀者的溝通方式。也為了更適切台灣讀者閱讀,加入了數則校注,但以不更動原書內容為原則。同時,由於這本書所處理的軸線繁瑣,想讓每一章都能夠獨立閱讀,因此會想辦法將前一章所出現過的表達,在後一章以換句話說的形式重新敘述或解釋。此外,中文譯本出現了不少在英文書中不需處理的翻譯難題,最主要是不同的專有名詞在兩岸三地不同歷史時空中呈現的詞彙。比如:譯文中的「schizophrenia」採用的是台灣衛福部在二○一四年所更換的病名「思覺失調症」,以便台灣的讀者閱讀。這個病名目前在香港和中國仍保留「精神分裂症」的稱呼。「psychosis」在本書中為「精神病症狀」,在香港則為「思覺失調」;「mental health」為「心理衛生」,「mental illness」「psychiatric disorder」則都是「精神疾病」。在台灣慣用的「憂鬱」,若出現在描寫中國的脈絡中則會置換成「抑鬱」。
值得一題的是,這本書在英文版的送印期間,一位日本的神經科學研究員捎信來表示讀了我的早期的一些論文後找到了我。他想要跟我討論「対人恐怖症(たいじんきょうふしょう)」。這是一個似乎只存在於日本文化裡的文化依存症候群。這種對於社交產生高度恐懼的症候群,似乎已經透過了新興病毒而全球化。而且他宣稱找到了中樞神經影像學的證據。後來我們甚至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由於全球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遷,甚至大規模疫病的影響,精神科的診斷分類可能會重新洗牌。於此同時,與我同時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書的公共衛生學者Eugene Richardson借用奈及利亞作家奇努阿.阿切貝(Chinua Achebe)的描述,將世界衛生組織形容為「日內瓦湖畔的原始部落」,暗示其中的科學家在塑造「全球衛生」實踐中所抱持的願景和價值觀。他開玩笑指出,世界衛生組織文化的特色是一種「gnihsup-repap(paper pushing,官僚文書作業的反向拼寫)」活動」。他們每天花許多時間在電腦前例行公事,但真正發生危機時卻無法採取果斷的行動。而位於「節點」的台灣呢?曾經身為執精神流行病學研究牛耳的先驅—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轉而強調「全球心理健康(Global Mental Health)」時,從來就沒有參與此類後續討論,但已經站上「新南向政策」高點,以先進之國的姿態輔導東南亞,現在的角色又在哪裡?能夠自外於鬆綁診斷標準、與民俗醫療攜手合作的呼籲之外嗎?會不會又複製了當年世界衛生組織南北發展的失準邏輯?這些都是這本書所關切的內容,能夠往後延伸討論的主題。
這本書在COVID-19的疫情期間付梓,出版後也由於各國的旅遊限制尚未解除,並沒有進行原先預計的宣傳。但也因為疫情,使得我得以重新思考這本書的構成,在許多線上發表會和討論會中,有幸得以和世界各地的學者交換意見,並開始往前鑽研這個故事的史前史,同時也思索這本書帶來的臨床意義。把時間點往前挪,我追索東亞精神流行病學的殖民開端,和當前存留的殖民性;另外,我也已經開始著手整理台灣的醫療外交史。除了原書的致謝名單之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在銜接兩份工作時,香港大學Vivian Lin、林佳靜、Danny Chan、前世界衛生助理總幹事福田敬二幾位教授的餐敘時光,以及回到台灣之後,國立成功大學賴明德教授、全校不分系與醫學系人社科同仁的啟發與支持、研究室助理翁伊珊、王政中的各種協助,王文基教授在校訂過程中的珍貴提醒,以及我的「鬥鬧熱走唱隊」樂團夥伴們的心靈陪伴。當然,還有翻譯的健筆湯家碩和前一段提到的巧玲,因為要處理一本涵蓋大量專有名詞,而且牽涉不同時空脈絡的語言問題,是相當耗神的。書中如還有錯誤,一概由筆者負責。最後還是要再次感謝我的家人們,尤其是不斷與我交換靈感和意見,也再度攜手在不同作品中成為共同作者的胞兄,也是醫療人類學者吳易澄。在這本書中,人類學者在世界衛生組織計劃的中途曾經悻悻然離開,卻又在廿世紀的最後十年回來。易澄讓我理解到歷史和人類學對話的重要性,和合作的可能。我們的攜手戰鬥才正要開始。
【小標】第一章 前言:共同的願景
她:舉例來說,我很確定我曾經看過那間醫院,在廣島。我怎麼能對它視而不見?
他:你並沒有在廣島看過那間醫院。在廣島你什麼都沒有看到。
──瑪格麗特.莒哈絲 ,《廣島之戀》(一九五九)
(精神醫學的)普世主義的最根本假設是,精神疾病具有某種普世性,而我們進行跨文化調查的目的,即是找到此種普遍性的存在證明。有兩件事可能會掩蓋精神疾病的普世性:第一、我們在不同情境中歸類病症的方式。第二、病症如何呈現在不同的文化之中。
──朱利安.勒夫,《全球各地的精神醫學》(一九八八)
關於疾病是否具有普世性的爭論,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紀後半葉帝國主義擴張的時期。同屬各種普世性相關的思潮,西方世界對於衡量疾病的普世標準的追尋,也同樣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在帝國進行全球殖民的期間,各種健康問題因為全球遠洋貿易的發展,而首度需要祭出普世適用的標準與防治手段。標準化的命名、計算與測量系統,因此成為一套在實務上用於達成殖民統治的工具。這些系統不止可用於商業活動,也嘉惠了那些因應著標準化系統而發展出的衛生治理行動。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普遍主義可說是十分有用,因為那些信仰科學的人所追尋的往往是一套共同的基礎方法理論,用以比較、評估、以及有效治療[1]。從歷史學的觀點來看,疾病的普世性標準是為了促進公共衛生和全體人類的安適而被發展出來。然而,這樣的標準一旦被建立,,也旋即被保險公司用於獲取盈利。因此,普世性標準乃奠基於各種目的需求的一致性,而非純粹科學研究的結果。
精神疾病的普世性也經歷相似的長期辯論。要理解這個辯論的最好方式是,是將之視為兩種主要分類系統的衝突:《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與《國際疾病分類》(ICD)[2]。然而,本書的主要關切遠廣於各種與「跨越人口族群的共通性」相關的問題。放寬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的討論衍生了各種爭議,這些爭議同時也挑戰了被反對者批評為「助長全球製藥產業擴張」的分類系統[3]。舉例來說,在二○一三年五月,也就是最新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釋出前兩週,身為世界最大的心理衛生研究贊助機構,美國國家心理衛生院(NIMH)撤回了對DSM第五版的支持。NIMH當時的主任湯瑪士.R.因索,即強調NIMH不會再提供資金給任何採用新DSM標準的研究計畫,並提倡用NIMH自己的研究領域標準(RDoC)取而代之,去探索精神疾病的不同面向。NIMH並不是DSM第五版第的唯一批評者[4]。身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精神醫學教授、同時也是DSM四版(上一版DSM)指導委員會主席的艾倫.法蘭西斯(Allen Frances),也在他的暢銷著作《救救正常人》中,批評修訂新版DSM的工作小組無法針對自身採用的精神疾病分類標準提出足夠充分的支持證據[5]。除此之外,他更進一步批評DSM第五版會讓藥廠無度地提供各種治療方式給範圍廣泛的精神疾病,因此造成藥物使用的浮濫以及藥廠的暴利。
相對於DSM所受到的各種批評, ICD第五章(心理與行為失調)的重新修訂,則因為藥廠較少涉入,尚未引起各界太強烈的反應。然而,關於ICD精神疾病的分類方式,同樣也經歷了長期的辯論。 ICD的存在遠早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成立。它的前身《國際死因清單》首次出現於一八九三年,主要的編篡目的是為了監控國際貿易所導致的疾病問題,因為疾病會透過商品與跨國旅行傳播。
一九四六年,世界衛生組織接下了編寫「死因分類」的重任,並在死因清單中進一步納入疾病的成因。由世界衛生組織編篡的現代ICD樹立了一套測量與命名精神疾病的標準化系統,且該系統「可被國際接受和廣泛採納」 [6] 。伴隨各國臨床醫師與科學家所建構的完整ICD疾病分類清單,世界衛生組織臨時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四至六月於紐約舉辦的國際衛生研討會中,把精神疾病也納入討論。隨後,精神疾病也在第六次改版的ICD清單中首次現身,但其內容十分簡短,僅有數種和精神錯亂、精神官能症、以及精神障礙相關的疾病[7]。直到一九五○年間世界衛生組織的心理衛生小組發展出全面測量心裡疾病的方法系統、以及產出全球精神疾病相關人口學調查資料之後,ICD才開始發展全球通用的精神疾病診斷工具。
一九四六年的ICD第六版到二○一八年的ICD第十一版,精神疾病在分類系統中的數量快速增長, DSM也經歷了相同的過程。這樣的增長可被歸因爲新疾病類型的發現、對疾病徵狀更精緻的描述、以及對致病原因更高度的關切。就如同主導ICD第十一版精神疾病相關診斷標準、英國毛德茲里醫院出身的保加利亞籍精神科醫師阿森.賈布連斯基(Assen Jablensky)在二○一六年所言,人類對於精神疾病的理解,「主要是透過對各種疾病現象繁瑣的區分來達成,而非歸納統整[8]。」這樣的發展進程其實有違世界衛生組織的原意,希望打造一個簡明的精神疾病診斷系統。許多ICD第十版的使用者,已經認為其科學價值與全球通用性十分有限,並呼籲在推出ICD第十一版時,應該要有更完善的精神疾病病因、臨床徵狀、和治療選項等資訊,供臨床醫師與研究者依循。在二○一八年六月, ICD第十一版正式發表,當中便更新了許多科學相關內容,並降低資訊的複雜度。在聯合國會員國的臨床醫師與科學家的認可下,各種為採納ICD第十一版所進行的準備工作(例如將之翻譯成多國語言)已經開始進行,在二○二二年初正式投入使用。
一九九○年代,各種呼籲改革國際精神衛生治理體系的呼聲開始逐漸湧現,訴求將精神疾病所蘊涵的普世主義想像「去殖民化」。這樣的改革呼聲,成為精神疾病分類的知識系統演進的其中一環,當中伴隨著使用各種「非西方」標準來衡量精神疾病的嘗試。所謂「新跨文化精神醫學」所追尋的,是一種具有文化意識的精神醫學路徑,關切在特定文化或社會脈絡影響之下的體驗、解釋、和處理精神疾病的方式[9]。藉由強調科學證據和人權,全球心理衛生運動嘗試藉由志工服務(GMM)和跨領域合作,來改善心理衛生服務在「未開發」的中低收入國家的覆蓋範圍,例如當時世界衛生組織的「心理衛生鴻溝行動計畫」 [10] 。自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以來,一路延續到千禧年到來之際,這些改善心理衛生的行動越來越由下而上,強調受到精神病症所影響人士的需求(尤其是來自資源不足地區的人),並且也更具有「民主精神」,廣納來自各科學社群和領域的專家們。這些改善心理衛生的行動不僅指出時下對有精神疾病及心智障礙問題的人提供的資源不足,也讓世人看見既有方法工具並不足讓人了解世界各地的精神疾病。因此,除了對DSM或ICD提出質疑,這些行動也讓當時的人們意識到面對精神疾病時,除了給予診斷名稱之外,需要考量和發展其他實質性的介入方式。
筆者於臺灣習醫。那是一個無論公共還是私人醫療系統皆十分健全的島國。直到十九世紀末,各個殖民者仍然因為酷熱和疾病,將台灣視為不宜人居的地方。但今日,台灣有自己完整的醫療法規與訓練體系。它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被讚譽為亞洲最好的模式,並且吸引各國的衛生部門前來取經[11] 。台灣在一九七一年從世界衛生組織除名,但仍在一個被自身醫學和科學社群視為高度現代和西化的社會脈絡中[12],持續吸收各種最先進的知識並將之實踐。在我精神醫學專科訓練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前往英國學習醫學史,逐漸了解當代精神醫學和許多台灣醫學專科早期發展的軌跡,其實有別於其他亞太區域的國家。台灣發展出了一套全國性的醫療基礎建設、以及一套基於國家甄審委員會認證的訓練制度。在過去半世紀,台灣的現代醫學進展十分快速。台灣的醫學專家參與國際研究活動與研討會,並提供友邦高品質的醫療服務,這些都是以非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的身份所進行的。當我參與這些國際研討會的時候,發現自己對於這些場合所使用的語言與知識感到游刃有餘,泰半是因為台灣完善的醫學教育與先進的醫療照護體系,足讓國內的醫生與來自西方的醫生沒有太多區別。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