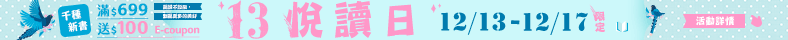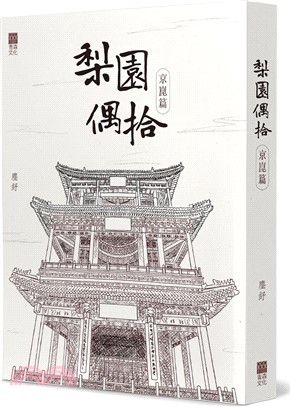梨園偶拾(京崑篇)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猶記得拙著《學林踽樂》刊行之時,序言載明:「回望三十年硯田樂,以筆名塵紓所撰的戲曲文章,少說也有兩千篇,而以其他筆名寫就的音樂文章,又何止一千?雖然歷年愛看拙作的朋友不斷催促我把已刊文章結集成書,但老是提不起勁。或許,縈繞胸臆的那種闌珊之感,就是對戲曲以至音樂現況的無奈之嘆吧。惟有把疊疊文稿束之高閣,暫且免提。」
詎料此語一出,隨即引起迴響。有些好友良言規勸,切勿打消刊行念頭;有些更進言鼓勵:既然評論文章多如浪疊,何不毅然輯錄付梓,為戲曲界稍留指爪?
三十年來肩負弘揚戲曲之責,至今雖已自決終結,再不聞問,但年來所學所觀,所感所評,多已見諸筆墨,並已累稿成疊。大體而言,年來拙文可分三大類:導賞、評論、承傳教育。前者是介紹講解;中者是微觀評隲;後者是宏觀廣論。
面對疊疊文稿,思量再三,何不稍留鴻爪,且按劇種劃分成若干篇,例如「京劇篇」、「崑曲篇」、「粵劇篇」,奉與戲迷同溯?
然而,拙文委實多如浪疊,不得不分拆上市。因此,本集先呈「京劇篇」和「崑曲篇」,期與讀者共鑑。其他篇章,容後再奉。情非得已,諸君莫怪。
詎料此語一出,隨即引起迴響。有些好友良言規勸,切勿打消刊行念頭;有些更進言鼓勵:既然評論文章多如浪疊,何不毅然輯錄付梓,為戲曲界稍留指爪?
三十年來肩負弘揚戲曲之責,至今雖已自決終結,再不聞問,但年來所學所觀,所感所評,多已見諸筆墨,並已累稿成疊。大體而言,年來拙文可分三大類:導賞、評論、承傳教育。前者是介紹講解;中者是微觀評隲;後者是宏觀廣論。
面對疊疊文稿,思量再三,何不稍留鴻爪,且按劇種劃分成若干篇,例如「京劇篇」、「崑曲篇」、「粵劇篇」,奉與戲迷同溯?
然而,拙文委實多如浪疊,不得不分拆上市。因此,本集先呈「京劇篇」和「崑曲篇」,期與讀者共鑑。其他篇章,容後再奉。情非得已,諸君莫怪。
作者簡介
塵紓
師承吳梅入室弟子汪經昌
資深戲曲評論員;藝評人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董事
文史專欄作家
著有《學林踽樂》
師承吳梅入室弟子汪經昌
資深戲曲評論員;藝評人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董事
文史專欄作家
著有《學林踽樂》
序
序
當時的戲棚設計,是前十排左右設有座位,但須另外付費。至於後面的空間,則不另收費。我就是在免費區看蹭戲。
「啟德」是粵劇恆常演出地
六十年代中開始,「啟德」名副其實是粵劇的恆常演出地,而幾乎所有粵劇演員都常在該處登台演出,直至遊樂場結業為止。當中恐怕只有芳艷芬是例外,未見在該處登台。
另一方面,日後我當了劇評人而有感於新秀演員苦無常踏台板機會,於是向政府進言開設粵劇永久場地。我的理念就是借鑑之前「啟德」戲棚長年演出的模式。隨著油麻地戲院變成戲曲表演場地,此願終於得償。由此可見,童年看戲的經驗,總有用得著的一天。
連年見識,長期浸淫,為我的戲曲路途奠下初基。這就是我劇評歷程的前話;至於日後得納汪師門牆,倒是後來的事,而因評論需要(倒不是藝術需要)先後學習京崑粵劇,更屬另一回事。
三十年 劇評路 純偶然
當年跟隨汪師習曲,只不過看作一門學問,稍予涉獵,聊自增益;怎會想過要當劇評?回想三十年前走上劇評路,確是誤打誤撞,純出偶然。
事緣九十年代初《經濟日報》「文化前線」版編輯是我八十年代任教某大專院校時的學生。記得當年某日,我閱罷「文化前線」所刊登的某篇戲曲評論,馬上向編輯投訴:「乜寫得咁差你都登嘅?」她聽後戲言道:「咁唔抵得,你嚟寫吖?」我一時氣盛,按捺不住,便馬上回答:「好,就等我寫!」如此這般,就踏上藝評的不歸路,一愰就是三十年。
藝評路上,起初幾年,只寫戲曲;隨後順乎己愛,兼寫西樂;其後更擴展至中樂,甚至偶寫戲劇,而各式評論,皆見於各大報刊。不過,為秉乎藝術原則,任何戲曲評論,絕不刊於本地粵劇雜誌,即使對方誠邀,也斷不破例。
除了硯田為樂,亦不時應邀,為文藝組織及學術機構,評論或講授戲曲及音樂,並為電台評論各式演出,以及主講或主持中西音樂暨文化節目。此外,為弘揚表演藝術,推廣藝術評論,長年擔任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董事。公職方面,則歷任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及審批員,期以一己綿力,報效藝林。
當劇評人 苦樂參半
此刻驀然回首,藝評三秩,確實苦樂參半。最苦惱的,當然是自忖發表評論時明明是良言規勸, 溫馨提示,但受者看成主觀針對,因而煽情還擊。
最大樂趣者,莫如受者聽罷評議,知所改進,或起碼誠懇交流。另一方面,透過藝評為觀眾解除各種觀賞方面的疑竇,亦是賞心樂事。
單以戲曲而言,可堪記取之事,簡直多若繁星。茲酌選數則載述,聊增談趣。
(一)自己不是演員,卻於某年聯同史濟華老師在文化中心大劇院的舞台上(請注意,是在台上;不是台下)舉行越劇導賞;另於某年應某大學舉行導賞。豈料主辦者忘記事先宣傳,結果錄得「零」上座率。這兩項記錄,敢稱前無古人。
(二)二零零八年為澳門藝術博物館所辦的「清宮戲曲文物展覽」,培訓一班對戲曲本無認識的導賞員,期以短期內把他們變成清宮戲曲文物的專才。其實,莫說是戲曲門外漢,即便是京劇老觀眾,也未必粗懂清代宮廷戲,遑論清宮戲曲文物。畢竟清宮演戲,與民間明顯有別。
要做好這樁差事,必須深諳清宮歷史,也要通曉宮廷演戲模式、規矩,以至內容。當然,極為有用的參考書,例如朱家溍與丁汝芹《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丁汝芹《清代內廷演戲史話》、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張淑賢《清宮戲曲文物》、萬依等《清代宮廷生活》,以至戴雲《勸善金科研究》,亦須稔熟。由此可見,這個課題,確實專門無比。
這個活兒,要不是藝評盟友周凡夫催請再三,我也不想接。當時我為此先後渡海三次,合共講解了差不多二十小時,才勉強訓練到那班學員權充「導賞員」。不過,整個訓練過程順暢愉快,尤其難得是賺到真摯情誼。
(三)二十一世紀初,專誠前赴杭州拜訪著名戲曲學者洛地老師;一席交談,經緯縱論,竟成莫逆。原來他年輕時追隨賀綠汀學習音樂,而賀是黃自其中一位得意門生。洛老初攻音樂,隨後轉行,由樂入曲,可謂有趣。也因此之故,他的各番見解,從不囿於戲曲框框。
二零零三年年頭,我敦請他來港演講。豈料「沙士」即將肆虐,人心虛怯;洛老竟然不憚疫情,毅然蒞港。甫見面,他高聲說到:「要不是看在老弟你面上,而是其他人邀請,我也不會來呢!」辱蒙長輩錯愛,怎不竊喜?
記得後來另有一回,我前往杭州開會,他風聞我這個老弟現身杭州,居然從上海趕車回杭,特意與我重逢敘舊。仰承眷念,既羞且喜。關於彼此每次相遇相交,我均撰文記敘,而那些拙文,亦已收入本文集。祈請翻閱。
(四)二零零二年,我在港策劃一台「麒派匯演」,以紀念京劇名角麒麟童周信芳。匯演由浙江京崑劇團京劇組承辦,負起班底之責,並由團裡麒派名家趙麟童領導其他劇團的一眾麒派演員蕭潤增、陳少雲、王全熹各演名劇;零五年,繼而策劃「崑丑匯演」,由浙江京崑劇團崑劇組擔任班底,藉此向崑曲「傳」字輩名丑王傳淞致敬;並由該團崑丑名家亦即王傳淞哲嗣王世瑤聯同早已分道揚鑣的師兄弟劉異龍、張銘榮、林繼凡、范繼信各演名劇。
這兩台戲由於選題獨特而且所選劇作頗為少演,公演時贏得業界及觀眾稱許,連著名文學家也斯學長亦向我親置好評。能夠為戲曲界敬效微勞,實感欣慰。
當時的戲棚設計,是前十排左右設有座位,但須另外付費。至於後面的空間,則不另收費。我就是在免費區看蹭戲。
「啟德」是粵劇恆常演出地
六十年代中開始,「啟德」名副其實是粵劇的恆常演出地,而幾乎所有粵劇演員都常在該處登台演出,直至遊樂場結業為止。當中恐怕只有芳艷芬是例外,未見在該處登台。
另一方面,日後我當了劇評人而有感於新秀演員苦無常踏台板機會,於是向政府進言開設粵劇永久場地。我的理念就是借鑑之前「啟德」戲棚長年演出的模式。隨著油麻地戲院變成戲曲表演場地,此願終於得償。由此可見,童年看戲的經驗,總有用得著的一天。
連年見識,長期浸淫,為我的戲曲路途奠下初基。這就是我劇評歷程的前話;至於日後得納汪師門牆,倒是後來的事,而因評論需要(倒不是藝術需要)先後學習京崑粵劇,更屬另一回事。
三十年 劇評路 純偶然
當年跟隨汪師習曲,只不過看作一門學問,稍予涉獵,聊自增益;怎會想過要當劇評?回想三十年前走上劇評路,確是誤打誤撞,純出偶然。
事緣九十年代初《經濟日報》「文化前線」版編輯是我八十年代任教某大專院校時的學生。記得當年某日,我閱罷「文化前線」所刊登的某篇戲曲評論,馬上向編輯投訴:「乜寫得咁差你都登嘅?」她聽後戲言道:「咁唔抵得,你嚟寫吖?」我一時氣盛,按捺不住,便馬上回答:「好,就等我寫!」如此這般,就踏上藝評的不歸路,一愰就是三十年。
藝評路上,起初幾年,只寫戲曲;隨後順乎己愛,兼寫西樂;其後更擴展至中樂,甚至偶寫戲劇,而各式評論,皆見於各大報刊。不過,為秉乎藝術原則,任何戲曲評論,絕不刊於本地粵劇雜誌,即使對方誠邀,也斷不破例。
除了硯田為樂,亦不時應邀,為文藝組織及學術機構,評論或講授戲曲及音樂,並為電台評論各式演出,以及主講或主持中西音樂暨文化節目。此外,為弘揚表演藝術,推廣藝術評論,長年擔任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董事。公職方面,則歷任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及審批員,期以一己綿力,報效藝林。
當劇評人 苦樂參半
此刻驀然回首,藝評三秩,確實苦樂參半。最苦惱的,當然是自忖發表評論時明明是良言規勸, 溫馨提示,但受者看成主觀針對,因而煽情還擊。
最大樂趣者,莫如受者聽罷評議,知所改進,或起碼誠懇交流。另一方面,透過藝評為觀眾解除各種觀賞方面的疑竇,亦是賞心樂事。
單以戲曲而言,可堪記取之事,簡直多若繁星。茲酌選數則載述,聊增談趣。
(一)自己不是演員,卻於某年聯同史濟華老師在文化中心大劇院的舞台上(請注意,是在台上;不是台下)舉行越劇導賞;另於某年應某大學舉行導賞。豈料主辦者忘記事先宣傳,結果錄得「零」上座率。這兩項記錄,敢稱前無古人。
(二)二零零八年為澳門藝術博物館所辦的「清宮戲曲文物展覽」,培訓一班對戲曲本無認識的導賞員,期以短期內把他們變成清宮戲曲文物的專才。其實,莫說是戲曲門外漢,即便是京劇老觀眾,也未必粗懂清代宮廷戲,遑論清宮戲曲文物。畢竟清宮演戲,與民間明顯有別。
要做好這樁差事,必須深諳清宮歷史,也要通曉宮廷演戲模式、規矩,以至內容。當然,極為有用的參考書,例如朱家溍與丁汝芹《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丁汝芹《清代內廷演戲史話》、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張淑賢《清宮戲曲文物》、萬依等《清代宮廷生活》,以至戴雲《勸善金科研究》,亦須稔熟。由此可見,這個課題,確實專門無比。
這個活兒,要不是藝評盟友周凡夫催請再三,我也不想接。當時我為此先後渡海三次,合共講解了差不多二十小時,才勉強訓練到那班學員權充「導賞員」。不過,整個訓練過程順暢愉快,尤其難得是賺到真摯情誼。
(三)二十一世紀初,專誠前赴杭州拜訪著名戲曲學者洛地老師;一席交談,經緯縱論,竟成莫逆。原來他年輕時追隨賀綠汀學習音樂,而賀是黃自其中一位得意門生。洛老初攻音樂,隨後轉行,由樂入曲,可謂有趣。也因此之故,他的各番見解,從不囿於戲曲框框。
二零零三年年頭,我敦請他來港演講。豈料「沙士」即將肆虐,人心虛怯;洛老竟然不憚疫情,毅然蒞港。甫見面,他高聲說到:「要不是看在老弟你面上,而是其他人邀請,我也不會來呢!」辱蒙長輩錯愛,怎不竊喜?
記得後來另有一回,我前往杭州開會,他風聞我這個老弟現身杭州,居然從上海趕車回杭,特意與我重逢敘舊。仰承眷念,既羞且喜。關於彼此每次相遇相交,我均撰文記敘,而那些拙文,亦已收入本文集。祈請翻閱。
(四)二零零二年,我在港策劃一台「麒派匯演」,以紀念京劇名角麒麟童周信芳。匯演由浙江京崑劇團京劇組承辦,負起班底之責,並由團裡麒派名家趙麟童領導其他劇團的一眾麒派演員蕭潤增、陳少雲、王全熹各演名劇;零五年,繼而策劃「崑丑匯演」,由浙江京崑劇團崑劇組擔任班底,藉此向崑曲「傳」字輩名丑王傳淞致敬;並由該團崑丑名家亦即王傳淞哲嗣王世瑤聯同早已分道揚鑣的師兄弟劉異龍、張銘榮、林繼凡、范繼信各演名劇。
這兩台戲由於選題獨特而且所選劇作頗為少演,公演時贏得業界及觀眾稱許,連著名文學家也斯學長亦向我親置好評。能夠為戲曲界敬效微勞,實感欣慰。
書摘/試閱
武旦表演勇猛又嫵媚
十月中旬中國京劇院青年團來港演出前,筆者在本欄簡介老旦藝術時,提到旦行自從王瑤卿、梅蘭芳致力擴大青衣領域,在青衣範疇外兼取花衫特色後,這個二合為一的新行當在旦行中獨領風騷,致使其他本該具有一定重要性的老旦和武旦黯然失色。
武旦其實是個卓然獨立而值得大力發展的行當,因為它本身有另一套與別不同的藝術要求。假如我們把旦角劇目粗分為文戲與武戲,青衣、花衫、花旦、貼旦、彩旦均專演文戲,只有刀馬旦與武旦主攻武戲。雖然同樣是演武戲,刀馬旦與武旦的藝術要求與表演特色卻有明確劃分。一般來說, 刀馬旦偏重做工、說白和功架,正因如此,一些武功條件較佳的青衣或花衫演員,可以兼演刀馬旦。
武旦則不須著意做工,而只注重武打,並且以「打出手」作為主要表演內容,而刀馬旦與武旦最顯著的分別,就是前者毋須「打出手」。所謂「打出手」,是指演員在武打時用拋、抱、踢、磕、頂、挑、耍等方法,把手上的兵器拋離及收回,從而凸顯劇中人物機警靈敏,更可藉此刺激觀眾的感官功能,增強武打的激烈效果。最常見的「打出手」,是各式各樣的踢槍動作。有些武旦演員甚至運用靠旗打出手,以旗尖繞刀、繞槍及磕槍。由此可見,武旦所需求的武功訓練,比刀馬旦嚴格得多,而武旦學員的艱苦之處,實在不言而喻。
若論近百年對武旦藝術影響最深及貢獻最大的人物,應該是清末民初的「九陣風」閻嵐秋。閻氏不但繼承了岳父朱文英迅疾勇猛但亦輕盈敏捷的武旦絕技,更兼集花衫的嫵媚及刀馬旦的豪邁於一身,達到「動時剛健、靜時婀娜」的境界。他的開打恍似流星趕月,「亮住」(停頓)時卻絲紋不動,他的「下場」動作亦經過精思——先稍作停頓,凝立片刻,再輕微晃動,然後隨著微晃之勢, 飄然下場。光是這個下場就遠勝同儕。
能夠繼承閻派武旦藝術的演員,公認有三位,其中兩位是中華戲校「德」字輩的宋德珠(亦即後來的四小名旦)及「金」字輩的李金鴻,另外一位是閻的親侄亦即「富連成」科班「世」字輩的閻世善。遼寧京劇團的李靜文,師承李金鴻和閻世善,因此繼承了不少閻派絕學,她常演的《青石山》、《扈家莊》、《取金陵》,均屬閻派戲寶。據筆者多次觀察,她的武打的確達到快、穩、準的要求,甚至蘊含幾分飄、俏、媚的韻味。
長期以來,京劇台上台下對武旦的期許,只限於武打出色,對做唸要求不高,唱功更不須講究。不過,既然青衣可以把花衫融合為一,甚至兼演刀馬旦戲,大大增加自己的表演內容,武旦何嘗不能擴大範疇,多些鑽研做唸,使所演武戲更有內涵?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十月中旬中國京劇院青年團來港演出前,筆者在本欄簡介老旦藝術時,提到旦行自從王瑤卿、梅蘭芳致力擴大青衣領域,在青衣範疇外兼取花衫特色後,這個二合為一的新行當在旦行中獨領風騷,致使其他本該具有一定重要性的老旦和武旦黯然失色。
武旦其實是個卓然獨立而值得大力發展的行當,因為它本身有另一套與別不同的藝術要求。假如我們把旦角劇目粗分為文戲與武戲,青衣、花衫、花旦、貼旦、彩旦均專演文戲,只有刀馬旦與武旦主攻武戲。雖然同樣是演武戲,刀馬旦與武旦的藝術要求與表演特色卻有明確劃分。一般來說, 刀馬旦偏重做工、說白和功架,正因如此,一些武功條件較佳的青衣或花衫演員,可以兼演刀馬旦。
武旦則不須著意做工,而只注重武打,並且以「打出手」作為主要表演內容,而刀馬旦與武旦最顯著的分別,就是前者毋須「打出手」。所謂「打出手」,是指演員在武打時用拋、抱、踢、磕、頂、挑、耍等方法,把手上的兵器拋離及收回,從而凸顯劇中人物機警靈敏,更可藉此刺激觀眾的感官功能,增強武打的激烈效果。最常見的「打出手」,是各式各樣的踢槍動作。有些武旦演員甚至運用靠旗打出手,以旗尖繞刀、繞槍及磕槍。由此可見,武旦所需求的武功訓練,比刀馬旦嚴格得多,而武旦學員的艱苦之處,實在不言而喻。
若論近百年對武旦藝術影響最深及貢獻最大的人物,應該是清末民初的「九陣風」閻嵐秋。閻氏不但繼承了岳父朱文英迅疾勇猛但亦輕盈敏捷的武旦絕技,更兼集花衫的嫵媚及刀馬旦的豪邁於一身,達到「動時剛健、靜時婀娜」的境界。他的開打恍似流星趕月,「亮住」(停頓)時卻絲紋不動,他的「下場」動作亦經過精思——先稍作停頓,凝立片刻,再輕微晃動,然後隨著微晃之勢, 飄然下場。光是這個下場就遠勝同儕。
能夠繼承閻派武旦藝術的演員,公認有三位,其中兩位是中華戲校「德」字輩的宋德珠(亦即後來的四小名旦)及「金」字輩的李金鴻,另外一位是閻的親侄亦即「富連成」科班「世」字輩的閻世善。遼寧京劇團的李靜文,師承李金鴻和閻世善,因此繼承了不少閻派絕學,她常演的《青石山》、《扈家莊》、《取金陵》,均屬閻派戲寶。據筆者多次觀察,她的武打的確達到快、穩、準的要求,甚至蘊含幾分飄、俏、媚的韻味。
長期以來,京劇台上台下對武旦的期許,只限於武打出色,對做唸要求不高,唱功更不須講究。不過,既然青衣可以把花衫融合為一,甚至兼演刀馬旦戲,大大增加自己的表演內容,武旦何嘗不能擴大範疇,多些鑽研做唸,使所演武戲更有內涵?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